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作為一個記者齣身的作者,身為90後,且自稱“後屌絲時代的90後”,講述接地氣,靈光四射,讀來親切異常。2)作為一本旅行事件的旅遊圖書,說的是一個中國青年記者騎行萬裏去見一位泰國姑娘,有種,有趣,有料。
3)作為擁有21個完整故事的旅行遊記,該書行程、路綫清晰、跟著作者有追劇感,同時伴有懸念感。21個沿途故事成為主體內容,並非閑散碰到,主綫連貫、順暢。
4)作為具有網絡直播和眾籌背景的旅行書,不同於旅遊攻略和漫無目的遊蕩,作者以“跳齣來”的思維寫沿途故事,追貼者成韆上萬,完全被博主魅力hold住。
內容簡介
2014年10月末,一位“90後”青年記者孤身從成都齣發,以騎單車和租摩托的方式穿越瞭大半個東南亞,去曼榖見一個泰國女孩,這個女孩曾在他人生的低榖送去過溫暖。100天後,他途經中國西南、越南、柬埔寨和泰國,風塵僕僕地見到瞭她,並當麵錶達他的謝意。生命有一韆種值得探索的可能,而旅行是其中之一。作者簡介
殷宏超,男,1991年齣生,2012年畢業於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先後先後任職浙江省青年時報、安徽日報報業集團記者。內頁插圖
目錄
第一章/ 一韆種可能開往荒蕪的夜班車 / 2
來自曼榖的擁抱 / 7
另一種人生體驗 / 11
鞦天的脈搏 / 15
第二章 / 山間長歌
從村莊開始 / 20
一把練習琴 / 28
在重巒中仰望 / 33
和“饅頭”一起尋找初戀 / 41
第三章/ 漫漫浮世途
當艷遇成為職業 /52
被歡歌掩飾的枯萎 /58
一頭叫“姐姐”的豬 /64
野草繼續歌唱 /78
第四章 / 際遇與變遷
烈士永垂不朽 /92
被誤解的越南姑娘 /99
沒有飆車黨的摩托王國 /109
一個峴港小販的愛國主義 /115
格瓦拉的啓示 /121
逃離高腳杯 /132
第五章 / 摩托日記:從西貢到湄公河
第一天:路邊的中文牌坊 /142
第二天:越南人的幸福感 /150
第三天:抱拳 /156
第四天:歸途 /160
第六章 / 深淵過客
喜歡和信任的區彆 /166
柬埔寨的背影 /174
到底要不要去當陪酒女郎 / 184
6號國傢高速是一條土路 /195
受挫之旅 /204
屋頂酒吧漫想 /212
吳哥窟:廢墟之花,暗香殘留 / 219
178美元 / 225
過去與未來 / 230
湄公河畔隻剩下眼淚 / 237
第七章/ 南邊的風依然濕
現代國傢 / 246
曼榖的嚮陽花 / 253
後記 / 語無倫次的旅行總結 / 259
精彩書摘
第一章||一韆種可能【開往荒蕪的夜班車】
事情要從2014年的春天說起。3月,暴徒襲擊瞭昆明火車站,馬來西亞航班MH370意外失聯。而我正在中國東部一傢報社采訪、寫新聞,每天奔波在街頭或者玻璃的建築裏,親曆那些所謂的新聞事件。
中國大多數報社記者的工作強度可以和環衛工人以及建築工人相提並論,一天的忙碌過後,淩晨時分搭上一輛夜班車是常有的事。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裏,我聽著歌,穿行在深夜的城市,然後迴到齣租屋裏,麵對斑駁的牆壁和床腳的大堆髒衣服。高強度的腦力工作加體力工作,不規律的作息和飲食,身體疲勞到瞭極點,神經卻依然亢奮。失眠在所難免,眼球布滿血絲,隔壁的嬰兒在啼哭,安靜的思考漸漸化作百無聊賴。
至於明天,大約和昨天一樣重復著,循環著。畢業之後,像大多數人一樣不知所以地存在著,周末的時光往往更加難熬。我曾嘗試著自娛自樂,比如去湘湖釣魚,或者逛一逛斷橋,後來發現這樣的消遣無趣到對自己心生憐憫。因為娛樂總是在苦役之後,它可以釋放的絕不是天性,而是短暫的逃避。
越是社會壓力大的地方,人們越是追逐娛樂,我曾見到公交車上被擠得七葷八素的人仍在堅強地翻看手機,不斷刷新著搞笑段子和四格漫畫。與此同時,社會的麻木一麵並沒有隨著時代進步而消亡,在很多我親曆過的車禍、凶殺、意外事故現場,逝者濛著白布,周圍血跡斑斑,親人嘶啞著喉嚨,圍觀的看客悄聲議論:又一個可以發到朋友圈的話題。
但後來,在這心生厭倦之中,我竟加入瞭他們,這著實讓我始料未及。發皺的書籍原本是放在床頭的,它們漸漸轉移到瞭廁所,作為排泄時的讀物,繼而又被丟進瞭行李箱,最後在搬傢的關鍵時刻留給瞭房東;不再關心任何身邊的故事,對這個年代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充耳不聞,思潮的湧動戛然而止,目光所及便是生命全部的寬度瞭。
據說人類發明酒精的初衷是為瞭治病,對某些人來說,直到今天,它的功效依然沒有變,不是為瞭治愈身體的疾病,而是心理上的缺陷。每一次開啓瓶蓋,都預示著一個漂浮的夜晚。
我鎖定瞭離小區最近的那傢酒吧,比距離更重要的是價格便宜。我喜歡一個人坐在角落裏,點幾瓶啤酒,觀察周圍的人群。隻要稍加留意就可以看齣來,他們總是既想掩飾自己的空虛,又裝作風度翩翩的樣子。這樣的樂趣一度讓我忘乎所以,尤其是在當我發現自己其實和他們沒有任何區彆時,這種樂趣更甚瞭。
當我清醒的時候,他們中的一些已經醉瞭,當我醉瞭的時候,有些還清醒著。鮮有例外的是,他們和我都會在醉後把全部的情緒暴露齣來——一個小時前,你看起來那麼快樂,一瓶酒後,你像是個被生活打垮瞭的廢物。我所在的那個酒吧,每天晚上都在見證買醉者們真實的過程:高興地或者高傲地往杯子裏倒酒,假裝愜意飲用,開始皺起瞭眉頭,最後哭喪著臉抱怨未來。
解脫終究是暫時的,第二天醒來,頭痛欲裂卻要假裝這是買醉帶來的瀟灑後遺癥,正如英雄身上總得有幾塊傷疤。但往往,想要擺脫這樣的生活,卻陷得更深。我原先隻有周末纔去那傢酒吧的,後來,幾乎每天下班之後就會去坐坐。醉酒隻會讓生活更壞,關於這一點,叔本華早就做齣瞭論斷——“獲取幸福的錯誤方法莫過於追求花天酒地的生活,原因就在於我們企圖把悲慘的人生變成接連不斷的快感、歡樂和享受。”
隨之而來的是一次次導演幻想,須臾又看到它們在錯亂的情緒中破滅。這種自我欺騙總是讓我無力,但又沉浸其中——既然生活已經這麼糟糕瞭,何必做一些亡羊補牢的打算。於是我不準備結束這種浮躁的生活,反而把它當作瞭荒誕人生的好習慣,盡管我知道全部的真相。直到三月末的一個晚上,來自曼榖的她齣現在我的杯前,樹葉又恢復瞭健康的顔色。
那天其實相當普通,又是一個周末,我毫無懸念地坐在角落裏。唯一不同的是,因為稿費到手,格外高興。本來約瞭同事,可是他臨時有事迴去瞭。我雖為此而寂寞,但奈何早已習慣獨自一人,很快便自娛自樂起來。一個月總有那麼一兩天,自我滿足的情緒占據瞭一切,對於生活在地下的人來說,過度的歡樂等同於迴光返照。
這樣的快樂真是一種不可多得也沒必要刻意獲取的情緒,人之所以感覺乏味或者悲傷,很有可能來自於將當下和快樂時光進行對比。伊壁鳩魯大言不慚,他以為快樂就是一種恬靜的狀態。那意味著沒有情緒纔是真正的滿足,可凡人中又有幾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呢?至於酒鬼,快樂的頂點便是痛苦的開端。
我很快就醉瞭,因為那位矮個子的酒吧歌手又開始唱李誌的歌,每天晚上,他都會把中國當代民謠的精華奉獻齣來,成瞭我虛無縹緲的下酒菜。點燃一根煙,一天的經曆幻燈片般播放,提醒我在歇斯底裏之前應該跟現實打一聲招呼。
早上,我在城西跑瞭一場車禍,貨車從建材市場齣來時撞上瞭電瓶車。醫院裏,被撞的大媽每隔一分鍾就要從插滿管子的口中噴齣一大攤血,兒子給她擦嘴的紙巾把紙簍都快填滿瞭。下午,去法院旁聽案件,前男友用刀捅死瞭現男友,因為錄音不小心被發現,法警沒收瞭我的手機。庭上,法官問他用刀捅死對方之後,周圍的人有沒有勸他報警?他的迴答是:“沒有。當時周圍的人都在笑,有人還提醒我他沒死,讓我再捅幾刀。”
從那些算不上驚心動魄但卻是人所不常見的地方齣來,迴到報社,思考報道的角度。唔,車禍應該著重強調肇事者和傷者的社會階層,兩個底層傢庭因為在路口前薄弱的安全意識,最終導緻悲劇。至於案件,就當作普通的社會新聞好瞭。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復記錄社會上的極端案例,刊載在第二天的報紙上,以供齣租車司機以及退休老人打發時間。
隨著工作的深入,這些極端成瞭我的日常生活,我甚至開始覺得這些極端纔是正常的社會。第一次看見一個人橫屍街頭,我會止不住難過,但當第10次看到,我雖不至於竊喜,卻也麻木到沒有瞭心理起伏。這個時代真的需要這樣的新聞嗎?我正在從事的行當是否意味著給娛樂社會增添更多的談資?我的價值便是讓人們在看到這些新聞時感到新奇,然後極大或者部分地滿足瞭他們的空虛?而我不也正在空虛中飲酒,感嘆著人生的無為嗎?
失落從一連串的自我發問開始的,繼而無法自拔,沮喪和渾渾噩噩聯袂趕過來加油助威,它們自稱是精神世界的黑白無常,專門為行屍走肉噴吐迷茫的霧氣。
酒精謀殺胃與理智,狂放的情緒最為不堪一擊,甚至不需要外力便土崩瓦解瞭。想必諸位應該見過失落的醉酒者,他們語調緩慢,口齣狂言,錶情呆滯,把一切都不放在眼裏,卻又突然像個孩子般掩麵啜泣。那天晚上的我便是其中的一位。
當我把酒杯打碎在地的時候,周圍一定投來瞭很多目光,其中的絕大部分是惡作劇式的。一種奇怪的邏輯流傳在酒鬼中——他們都有過醉得喪失理智的經曆,也知道自己曾被人嘲諷挖苦,但當有同類喝醉後,他們卻也毫不吝惜地送上詆毀。當然,這無可厚非,因為假如我在清醒時看到一個喝醉瞭且滿嘴鬍話的人,也會給予“逗逼”的評價。
服務員很快就趕過來清掃地上的玻璃碎片,我卻叫他再上幾瓶,他沒有滿足我的要求,而是拿起我的手機,準備打電話給我的朋友,送我迴去。我很不滿意,嘴裏嘟噥瞭些什麼自己也忘記瞭。
僵持不下之際,一個女孩子走瞭過來。我之所以意識到她的存在,是因為她輕輕地抱住瞭我。我本能地推開她,同時也一下子清醒瞭過來。這個擁抱帶來的感觸過於強烈,以至於戰勝瞭酒精的作用。當我抬起頭,眼中的她個子並不高,留著長發,皮膚按照東亞人的標準,算不上白,甚至有點黑。
【來自曼榖的擁抱】
齣於殘留的自尊,我努力裝作歉意十足的樣子,試圖在一位陌生女性前留下好印象。可是這一坐起來,卻打瞭個蕩氣迴腸的酒飽嗝。她不僅沒有厭惡,反倒拍瞭拍我的後背。“會好的。”她一邊拍打著我的後背,一邊把頭湊瞭過來,關切地說齣這句蹩腳的漢語,像是廣西或者廣東人在說普通話一樣。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有人,而且是個陌生姑娘,如此不嫌棄一個標準的酒鬼。
服務員給我拿來一瓶礦泉水,喝瞭幾口後,感覺好瞭很多。但同時我的手因為顫抖,也將礦泉水瓶打翻在地。她將瓶子撿起來,立在桌上。我望著她,眼神裏充滿瞭感激,這反而讓她顯得拘謹起來。
“你是廣東的?”
“不是,我是泰國人,我漢語不是很好,你會說英語嗎?”
“好啊,我當然會。哦,too young 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多年輕多單純,有時還有點天真。)”
“OK ,You need to go home.(你該迴傢瞭。)”
她說自己在曼榖工作,來杭州齣差,明天下午的航班迴國。
我們用最簡單的英語聊瞭一會兒,加瞭各自的微信(在泰國,Facebook和微信是最常用的社交工具)。我大言不慚地說明天可以去機場送她,她笑瞭笑,錶示可以。那種半醉半醒間的交流仿佛一個人被裹挾在雲朵中般遊移不定,而另一個則平靜地坐在高高的榖堆旁邊。半年之後,正是希望接近那座榖堆,我做齣瞭去曼榖見她的決定。
見我已不再癲狂,她衝我眨瞭下眼,迴到瞭朋友的桌子。本想去和她喝上一杯,可腳下玻璃的殘渣讓我沒有理由停留在這裏,於是搖搖晃晃地走迴瞭傢。
第二天,我沒有去送她,因為我睡到瞭下午纔醒來。她發來消息,說她快要登機瞭,還加上瞭一句“不要再喝醉瞭”的玩笑式的忠告。奇怪的是,從那以後,我多次路過那傢酒吧,但終究沒有再進去。
一片來自曼榖的樹葉,飄到瞭某個最不知名的酒吧裏,在這個酒吧裏,它落在瞭一個酒鬼的肩頭。平淡如水的生活需要拜托酒精來撕扯,打破黑暗之門的卻是來自異域的安慰。人雖是長情的動物,可有時候最珍貴的安慰恰恰來自陌生人。
我不想去那傢酒吧瞭,一方麵齣於害怕再次齣現囧樣,另一方麵則是,我原本就知道這糟糕的生活遲早要結束,隻不過一直沉溺其中而已。她已經搭好瞭梯子,我隻需稍加剋製,便可以爬齣沉淪的陷阱。在齣租房裏,在春天的每一趟夜班車上,在清晨早餐鋪的煙霧中,負麵的情緒退到瞭幕後,平靜開始登颱起舞。
4月是無憂無慮的,我重新看待釣魚,並且滿載而歸。我把床下的吉他抱瞭齣來,換瞭一副新弦,在淩晨的天颱輕輕彈唱。伊壁鳩魯沒說錯,你不需要去追逐那些廉價的快樂,你隻要保持寜靜便已經足夠快樂瞭。每當我迴憶起那時的變化,總是會為此慶幸,心態走到瞭臨界點,點燃導火索的火焰隻需一根火柴的能量。她便是那看似微不足道的光芒,並非把災難中的人從地獄裏帶齣來,然而她不經意間與我這個陌生人的交流,對於我來說卻是莫大的安慰。
這讓我聯想到自己在大學裏的經曆,那時我充當的便是醉酒之夜曼榖女孩的角色。2009年的深鞦,武漢的風透著涼意,在中南民族大學的足球場邊,一個穿藍色工作服的年輕人躺在草坪上。還在上大二的我踢完瞭球,在迴宿捨的路中注意到瞭他。誰會在寒風中躺在草坪上呢,而他也並非哆嗦著生病的樣子。也許他是個遇到瞭挫摺的人呢,好奇心驅使我走近。
“哥們,你怎麼瞭,沒事吧。”我蹲下身看他的臉,慘白而蒼老,飽經風霜而又神情憂鬱的樣子,可他纔25歲。年輕人很快坐瞭起來,用方言味很濃的普通話訴說自己的故事。他原先是個公交車司機,最近下崗瞭,因為他總是在開車時想到以前自己被騙的經曆,注意力不能集中。“我有個最好的朋友喊我去深圳打工,然後把我的3500塊錢都偷走瞭。我現在每天都想這個事情,我精神不好,我自己知道的,隔幾天就要去華師看心理醫生。”他毫不避諱自己有心理疾病的事實,麵對我這個陌生人,他的坦誠讓我驚訝。
我簡單安慰瞭幾句,無非那些人人都會說的話。可他卻異常激動,拉住瞭我,一定要留下我的號碼,還要請我去他傢做客。他沒帶手機,我也沒帶,於是他便用鑰匙在牆上刻下瞭我的號碼。晚上,他給我打電話,後來,我們居然每天都要聊上一會兒。
他母親那時在我的母校做清潔工,我便經常放學後去找她聊天。阿姨告訴我,兒子阿戰有嚴重的心理問題,又沒有朋友傾訴,時常在傢發脾氣,隻能靠吃藥和看醫生緩解。而和我那麼簡單的一次聊天,讓阿戰有瞭一個朋友。我和阿戰維持著朋友關係,並且把同學介紹給他認識。兩年後,當我從母校畢業離開武漢時,他已經談瞭女朋友,並且當上瞭齣租車司機。最近,他結婚瞭。
我並不是藉此來烘托自己的高尚,而是這樣的經曆讓我更加感激那個曼榖女孩。之後的日子裏,我和她偶爾會聊一聊,得知她因為換瞭崗位的緣故,短期內不會再齣差來中國。我為此感到遺憾,因為我很想再次見到她。當然那時的我甚至沒想過去辦護照,買一張機票飛過去。在一個人的生活裏,有太多可為但不願為的事,孰輕孰重纔是行動的標準。
第六章 ||深淵過客
【湄公河畔隻剩下眼淚】
快到金邊時,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齣現瞭。終點越近,離彆越快。和在越南時一樣,我放慢瞭速度。車流多瞭,濛著麵紗的姑娘,躺在突突車上睡覺的司機,遠處高聳的樓宇,路邊空蕩的寺廟,陌生的金邊已經不再陌生。上百萬個靈魂和上百萬個身體生活在這裏,我隻認識其中的兩三個。假如所有人的經曆幻燈片般播放,會有多少不同的片段和重復的命運呢?
黃昏前的湄公河再次送來清爽的風。河畔的一排排餐廳門口,快樂的遊客們還沉浸在來到一個新奇國度的興奮中。年輕人跳著走路,地上被地雷毀掉雙腿的乞丐和往常一樣蜷縮在角落裏呻吟。這真是一個奇妙的街區,三種對比鮮明的情緒蔓延在空氣中——遊客的快樂,柬埔寨人的焦慮,乞丐的悲傷。
迴到旅館,我將摩托還給瞭小哥。從金邊到暹粒再迴到金邊,7天的摩托之旅就此結束。打電話給BOX,他還以為我明天纔能迴來。約好瞭在老地方見麵,當我到那時,BOX和妻子正站在陽光下聊天。他不再穿那件夾剋,但卻換瞭一件更厚實的西服,身旁停著一輛老摩托。
“年輕人,旅行應該很精彩吧。”BOX請我到寺廟下的米粉攤坐下。
“還行吧。”說著,我從口袋裏掏齣那178美元。
“這些錢……”BOX夫婦很驚訝,他們從沒想到我會帶迴來這麼多錢。
“全是酒吧裏的西方人給的。”我讓他們稍等一會兒,隨後迴旅館把我的帳篷和煤氣小竈也帶過來,送給瞭他們。旅途即將結束,我不再需要這些裝備瞭。
BOX不停地感謝我,而我覺得自己應該感謝他。沒有7天前的相遇,就不會有這件有意義的事。吃完米粉後,我和BOX夫婦在街頭分彆。BOX和妻子坐在摩托上,他伸齣手,我握住瞭,鬆開後又朝他做瞭個抱拳的手勢。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也沒有永遠失散的靈魂。我悵然若失地站在街頭,陽光又灑在瞭金黃的塔尖上,7天過去瞭,這個國傢裏的所有人都變瞭一些,有些變化很細微,有些卻令人吃驚。
時間很快到瞭晚上,我給Linda打電話,始終打不通。一直到瞭9點多,她纔迴我一條短信:“我在忙。”我不想去Same Same But Different 酒吧找她,因為她一定在那兒,或者坐在門口,或者正在陪酒。
我收拾瞭一下行李,準備第二天離開金邊。我的旅程快結束瞭,很久沒上微信的曼榖女孩問我到哪裏瞭。“就在你隔壁,不是房間,是國傢。”我開玩笑般迴復她。一切順利的話,幾天後我就能到曼榖。兩個多月過去瞭,我變瞭很多,也許她也是。但我仍然期待著見到她,仍然想要接近那座高高的榖堆,這種念想比以前更強烈,隻不過沿途的一切也越來越不捨。
晚上10點多,Linda說她有空瞭,聲音裏透著疲憊,約我去湄公河畔的廣場。
7天後再次相遇,Linda穿著高跟鞋,性感的裙子,嘴上還塗瞭口紅。她的不好意思還像往常一樣,她對我的笑容也沒有變味。還是坐在那天晚上我們坐過的地方,我把這7天的遭遇告訴瞭她。我們坐著,低聲說著,好像她身上的變化並沒有發生那般。一個外國人和一個濃妝艷抹的柬埔寨酒吧女郎坐在深夜的廣場上,經過的人也許會以為,我們正處在討價還價的尷尬中。
“我請假齣來的。”她把頭埋在兩腿之間。
這個結局我已經預料到瞭,我沒有感到震驚,相反,我很平靜。這一個必然的過程,與猶豫的時間長短無關。一切都塵埃落定瞭,她不再猶豫,也無須後悔。西去的湄公河上可以有很多可能,唯有河水絕不會倒流。還能怎麼樣呢?做一個酒吧女郎固然屈辱,可她彆無選擇。
我更想去她的小屋,那兒有迴憶蔓延,親切而又可愛,就像7天前的Linda。再次踩在吱呀的木梯上,朝下麵望去,三個小孩一定還會是熟睡著的。
“我不在那住瞭。我搬到瞭另一個地方,在酒吧的後麵,和朋友住一起。”Linda說,“走吧,你的旅館還沒關門。我有話要對你說。”原來,那間小屋也成瞭過去。貧窮的確讓人迴味悠長,也讓人迫不及待地逃亡。
“現在就可以說,你說吧。”
“不,是很重要的話。”她很認真。
“行吧,那走吧。”
“要不我先迴去換套衣服吧。”她更喜歡素裝的自己,我也是。
我和她沿著湄公河往酒吧走去,那些還不願迴傢睡覺的突突車司機盯著我們看,但已經不是7天前的眼神。我明白這一點,我們走得很快,Linda的高跟鞋敲擊地麵發齣脆響,在安靜的夜晚就像一聲聲爆炸。有什麼話不可以在河邊說呢?當然,Linda不可能把我當作客人的,而我也不會把她當作酒吧女郎。我想,我們是朋友,未來也是。
換迴7天前的那套衣服,Linda還是那個清秀的女孩,但她實際上已經是一個酒吧女郎瞭。
迴到我的旅館,洗完澡,Linda要看電視,於是我們就躺在床上看電視。泰國愛情劇在柬埔寨很流行,劇情通常是美女愛著帥哥,可是帥哥另有所屬。很久以前我看過一些電視劇,有些很不錯,常常讓我感慨,甚至感動。可現在,我不喜歡看瞭。因為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我為電視劇中虛構的情節感懷,卻不會為現實生活的真實故事感懷。
電視劇裏的犧牲讓我動容,可我身邊的人,他們中的一些同樣在犧牲,我為什麼不把我的情感投射到真實的生活中去呢?一些女孩會因為看到電視劇中的淒美愛情哭得稀裏嘩啦,可當她的朋友中也有類似的經曆時,她甚至連眼睛都不會眨一下。電視劇不過是抓住瞭人類對自己的憐憫之心,而不是對彆人的。
現在,我的身邊就躺著一個鮮活的生命,任何一部電視劇都不能比她讓我感觸良多。電視劇結束瞭,女主角美麗的麵龐上留下瞭兩行清淚。Linda關掉瞭電視和燈,背靠著我,一句話都不說。她似乎準備就這樣去睡瞭。許久,她的身體纔動瞭一下,那是因為啜泣帶來的自然反應。她輕聲哭瞭,像一個委屈的小女孩。麵對命運的摧殘,確實需要哭泣來釋放悲傷,英雄尚且落淚,何況一個柔弱女子。
旅館外麵的街道上人聲鼎沸,從酒吧歸來的遊客們此時正在歇斯底裏,Linda仍在哭泣。我閉上眼,靜靜感受著這強烈的對比,隻不過隔著一條街,快樂和悲傷竟可如此鮮明。
“帶我去中國吧,我想嫁給你。”Linda突然轉過身來,把頭埋在我的胸口。我猛地睜開雙眼,努力強迫自己清醒。這句話極大地震撼瞭我。好似長久的黑暗中,突然齣現一道刺眼的光芒,它灼燒眼球,衝擊心靈。過往的20餘年,沒有人對我說過這種話,而我也沒有過結婚的念頭。
“我沒有錢,買不起房子和車,你和我在一起會受苦的。”過瞭很久我纔說。
“我不要房子和車,隻要我們在中國結婚。”Linda抱住瞭我,“你可以教我中文,我們一起工作。我不想去酒吧上班瞭,我討厭那裏。”
一個柬埔寨窮苦人傢的女孩,把擺脫苦難的希望寄托在我這個中國過客的身上。但現實很清楚,我不是本傑明,她也不是Sreykeo,Same Same But Different畢竟隻是一部電影。我不知道怎麼去拒絕,這對於她太殘酷瞭,但我也必須拒絕。
“我不是想要你的錢,你有沒有錢都沒關係。”Linda停止瞭哭泣,“我覺得你可以,我喜歡你。我們結婚吧,離開柬埔寨。”
我願意相信Linda,可我還沒有結束我的旅行,我對曼榖女孩的承諾還沒有兌現。我無法接受這個局麵,一切來得太突然,來得太強烈瞭。這不是愛情,那它又是什麼呢?我從中國而來,路過這裏,路過一個龐大的囚籠以及囚籠裏的生靈們。我的身邊躺著一個柬埔寨女孩,一個憂鬱哭泣的靈魂。可我無能為力,我沒有錢讓她從酒吧裏解脫齣來,也不可能帶她迴中國結婚。
美麗的錯誤總是先給人以希望,又留下絕望。
“我不會帶你去中國的,我也不會和你結婚的。”我的話很殘忍,但我隻能如此,好讓她希望的泡沫徹底破滅。她依然抱著我,卻不再說話,然後慢慢鬆開抱著我的手,轉過身去,再次背對著我。她太纍瞭,含著眼淚睡去。那一夜格外漫長,親眼看著悲劇發生,我成瞭其中的角色,但最終充當瞭看客。
對Linda來說,未來的人生漫長無涯,她變成瞭自己以前討厭的那個人,可她像大多數柬埔寨人那樣,麵對命運的波摺,無能為力、彆無選擇。一個人在經曆重大的失去之後,對得失往往會看淡許多,但願 Linda 也能如此,而非沉浸在無休止的自責與痛苦中。
第二天早上,我們同時醒來。Linda雙眼紅腫,我注意到她的包還是以前那個,她的鞋不是新的,衣服也不是。不過,時間會帶來改變的——物質上的越來越好,精神和身體上的越來越壞。
我送她迴住的地方,在彌漫著燥熱和灰塵的金邊,早間忙碌的生活氣息將不再屬於Linda。她的未來在夜裏。而一無所有的我,現在便是未來。
沉默著吃完早餐後,又是湄公河邊的廣場,那個該死的總是醞釀故事的地方。我們坐瞭一會兒。太陽升起來,空氣越來越熱。河畔的風吹動過,她的頭發在風中飛舞,又落在瞭憔悴的麵龐上。
“你還會來柬埔寨嗎?”她拉著我的手,數著我的手指。
“也許會吧,也許不會。”我故作輕鬆,輕聲長嘆。
良久,她纔起身,拎著包準備離開。
“我送你吧。”我也起身。
“不用瞭。”她不再抱有希望。
“那我看著你走吧。”
她突然走到我身邊,隱蔽地指著幾米外的一個柬埔寨男人對我說:“你快迴旅館吧,他估計想搶你的相機。”我看嚮Linda手指的方嚮,無所事事的他立即躲開瞭我的視綫,確實有些可疑。金邊有很多小偷,專找沒有防備的外國遊客下手。
“聽話,迴旅館吧。”她把雙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盯著我T恤上的英文。那是我在暹粒花3美元買來的,上麵印著一句“I love Cambodia(我愛柬埔寨)”。然後,她鬆開手,快步走開瞭。我追瞭上去,但她不願再理會我,隻顧著低頭走路。直到酒吧門口,她也沒有跟我說話。隨後,她便走近瞭旁邊的巷子,那裏是她的新住所。
這時,一個突突車司機歡快地跑過來,他看到我在烈日下不知所措,他發現這是個很好的拉客機會,便嚷嚷著:“Hey,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前言/序言
隻要在我的生活中能有變遷——變遷和無法預見的刺激,
我是準備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
奔赴暗礁滿布的海灘的。
——威廉·毛姆(英國作傢)
2014年10月末,我孤身從成都齣發,以騎單車和租摩托的方式穿越瞭大半個東南亞,去曼榖見一個泰國女孩,她曾在我人生的黑暗時光中送來溫暖。100天後,途經中國西南、越南、柬埔寨和泰國,風塵僕僕的我見到瞭她。
這是一個簡單的故事,像荒野盡頭的一朵嚮陽花,四季輪迴,成熟的時候,枯萎的花瓣和充盈的果實留下變遷的痕跡。會唱歌的農夫經過,剝開一粒,品嘗它在烏雲或者陽光下生長時的微笑。
誠然,大部分人關心故事的結局,但最值得展示給公眾的,並不是我和她的私人情感。在西南山區的冷雨中,在東南亞熱帶陽光的暴曬下,除瞭皮膚變黑,似乎還有些彆的,那些異域孤獨跋涉中的際遇和漫想,是我所願意談及的話題。但不可避免的是,寫下這些姑且可以被稱之為文字的東西,就有相當大的可能是在把自己旅行中的經曆和感受強加給讀者。
故事和觀點構成瞭接下來的內容。第一人稱的大量使用可能會造成不適的閱讀感,但正如《瓦爾登湖》的作者戴維·梭羅所說——“如果我對任何人都瞭如指掌,我就不會過多地談論自己瞭。然而我閱曆尚淺,隻能局限於這個主題。”
除瞭我之外,一些似曾相識的麵孔會齣現在本書中。為瞭見五年前的初戀,和我一起在深山中騎行的網友“饅頭”;放棄愛情和事業,在大理雙廊小鎮上準備做一輩子義工的東北姑娘毛毛;麗江古城酒吧裏,一晚上隻有100元賣唱收入的《中國好聲音》海選歌手阿龍……他們其實就在我們身邊,卻往往因為我們對生活的觀察不夠造成視而不見,旅行讓重新發現成為可能。
人與人之間的大多數交流産齣廢話,但這並不能成為掩蓋交流價值的理由。對於把風景當作次要享受的人而言,吳哥窟所有的遺跡,也抵不上與一位典型的柬埔寨人真誠地交往片刻。比起廢墟和風光,它可以讓你看到一個國傢、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鮮活縮影。
在越南,有北部女孩寒夜裏救起睏在路邊的我;也有峴港小販叫囂著讓我從他的小吃攤滾齣去。在柬埔寨,一次充話費時的偶遇,直接促使瞭我在摩托旅行的沿途為柬埔寨貧睏兒童募捐……
未知中的真實情感往往震撼人心。我仍然清晰地記得,2015年1月7日那天晚上11點,柬埔寨首都金邊,湄公河畔人聲鼎沸,遊客們正在盡情狂歡著這燦爛的異域夜生活。兩條街之外的廉價旅館裏,柬埔寨女孩Linda和我背對背躺在床上。她低聲啜泣,蜷縮的身體不停顫抖。良久,纔轉過身來,抱住瞭我。“帶我去中國吧,”她哽咽著對我說,“我想嫁給你。”我欲言又止,第二天早上,獨自離開瞭這個國度。如今她已經成瞭陪酒女郎,因為隻有被迫齣賣肉體纔能賺到足夠的錢供她的母親治病……
走在左邊路上卻希望看到右邊風景的人熱衷於旅人的遭遇,仿佛正是他們把故事從遠方帶瞭過來,又或者這些故事便是旅行的意義瞭。但我更願意相信生命的璀璨在於思想和精神的不斷變遷,旅行作為生活的另一種可能為變遷提供瞭方式和條件。彆樣的經曆更容易産齣不同尋常的思維,在書中,我記錄瞭這些沿途的思考,但願上帝不要因此而發笑。
另外,堅韌不拔的毅力和追逐自由的普世價值觀固然是正能量的體現,在流俗的當下,卻大都是一種廉價的迎閤。實際上,我希望盡可能真實、完整地把一場旅行呈現齣來,讓讀者自己去評判,而不是為瞭迎閤主流的論斷削足適履。
如果一個人把那些彆人沒有去過的地方掛在嘴邊,總是嚮所有人宣稱他見過或正在經曆宏大的場麵,恰好說明他的世界還很狹窄。還有一些人,陶醉於講述自己的過去和觀點,卻很少理會那些瑣碎或者韆篇一律是否能夠帶給聽者不一樣的感受。不幸的是,我現在正在做這樣的事。
願意耐心傾聽他人故事的人,是沉在杯底的茶葉,既不輕浮判斷,又不失真知灼見。
殷宏超(毅義非凡)
2015年3月27日
用户评价
《沿途的嚮陽花》給我帶來瞭一種前所未有的閱讀體驗,仿佛是置身於一個精心打磨的萬花筒,每一頁都摺射齣不同的光彩,卻又和諧統一,構成一幅斑斕的畫捲。作者的筆觸細膩得如同絲綢,將那些不易察覺的情感絲絲縷縷地勾勒齣來,讓我為之動容。故事中那些看似隨意的場景,實則充滿瞭哲思。我常常在讀到某一段時,會停下來,反復品味其中的含義,然後恍然大悟,或者陷入更深的沉思。書中對於人性的探討,並沒有流於錶麵,而是深入骨髓,展現瞭人性的復雜與矛盾。我看到瞭善良與自私的交織,看到瞭希望與絕望的拉扯,也看到瞭妥協與堅持的較量。這些衝突,並非尖銳的對峙,而是像潮水般,時而湧動,時而退去,卻從未停止。我驚嘆於作者能夠將如此深刻的主題,融入到如此流暢的敘事中,既不顯得生硬說教,又充滿瞭力量。每一次翻閱,都像是在進行一次心靈的探險,我發現瞭一個又一個隱藏在文本深處的寶藏,每一次的挖掘,都讓我對世界,對人生,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這是一種智慧的啓迪,一種情感的升華,讓我受益匪淺。
评分《沿途的嚮陽花》是一本讓我沉醉的讀物,它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情感的河流,思緒的海洋。作者的語言風格多變,時而如涓涓細流,溫婉纏綿,描繪齣細膩的情感;時而又如狂風驟雨,勢不可擋,展現齣強烈的內心衝突。我仿佛置身於一個色彩斑斕的世界,每一種色彩都代錶著一種情緒,每一種情緒都飽含著深刻的含義。我喜歡書中對人物心理的深度挖掘,那些隱藏在平靜外錶下的波濤洶湧,那些難以啓齒的渴望與恐懼,都被作者毫不留情地展現齣來。我看到瞭人性的脆弱,也看到瞭人性的光輝。這種真實而又殘酷的刻畫,讓我對“人”這個字有瞭更深刻的認識。每一次閱讀,都像是在與不同的靈魂進行一場深入的交流,我從他們的經曆中學習,從他們的選擇中反思。它讓我明白,生活並非隻有一種模式,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軌跡,而正是這些軌跡的交織,纔構成瞭豐富多彩的人生。這本書,讓我對“活著”本身,有瞭更真切的體會和更深沉的敬畏。
评分第一次拿起《沿途的嚮陽花》,我以為這不過是一本講述尋常生活的讀物,未曾想,它卻像一把鑰匙,悄悄打開瞭我內心深處塵封已久的角落。故事中那些人物的命運,並非高潮迭起,但字裏行間流露齣的那種淡淡的憂傷和堅韌的力量,卻深深地觸動瞭我。我看到瞭他們在睏境中的掙紮,在迷茫中的探索,在失落中的自我療愈。他們沒有轟轟烈烈的壯舉,也沒有驚天動地的誓言,隻是用最平凡的方式,去麵對生活的風雨,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片陽光。這種真實感,讓我倍感親切。我仿佛看到瞭自己的影子,看到瞭曾經走過的路,看到那些我曾以為早已被遺忘的瞬間。書中的每一個細節,都經過瞭作者精心的雕琢,那些細微的情感變化,那些欲說還休的暗示,都如同在耳邊低語,讓我忍不住去傾聽,去感受。它教會我,即使身處低榖,也要努力尋找嚮上的力量,即使麵對黑暗,也要相信陽光終會穿透雲層。這本書,就像一位溫柔的朋友,在我需要的時候,給我以安慰和鼓勵,讓我重新找迴麵對生活的勇氣。
评分我不得不承認,《沿途的嚮陽花》帶給我的是一種意料之外的驚喜。我原以為它會是一本比較平淡的書,然而,作者卻用一種極其巧妙的方式,將生活中的點滴瑣事,編織成瞭一麯跌宕起伏的生命贊歌。我被書中那種不動聲色的力量所摺服。它沒有宏大的敘事,也沒有戲劇性的情節,卻通過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展現瞭生命中那些最本質的東西。我看到瞭希望,即使在最絕望的時刻;我看到瞭愛,即使在最疏離的關係中;我看到瞭成長,即使在最微小的改變裏。書中的每一個人物,都像是活生生站在我麵前,他們的笑容,他們的淚水,他們的沉默,都讓我心生憐惜,又倍感振奮。我喜歡作者對細節的把握,那些被忽略的角落,那些不為人知的秘密,都在書中得到瞭細緻的描繪,仿佛一幅幅寫實的畫作,栩栩如生。這是一種對生活的敬畏,一種對生命的尊重,也是一種對美好的堅持。讀完此書,我感覺自己仿佛經曆瞭一次心靈的洗禮,對生活充滿瞭新的感悟和更深的理解。
评分初見《沿途的嚮陽花》,我便被這個名字深深吸引。它並非那種引人注目的奪目色彩,而是一種溫暖、樸實、帶著淡淡陽光的味道,仿佛能聞到泥土的芬芳和夏日的熱烈。故事的展開,就像一條蜿蜒的小徑,沒有驚心動魄的起伏,卻處處彌漫著細緻入微的生活氣息。我仿佛置身其中,跟隨著主人公的腳步,感受著四季的更迭,看花開花落,聽風吹雨打。書中的人物,沒有超凡脫俗的設定,他們是生活在我們身邊的普通人,有著各自的喜怒哀樂,有著平凡的煩惱和微小的幸福。我看到他們的掙紮,也看到他們的堅韌;看到他們的迷茫,也看到他們的追尋。那些細碎的日常,那些不經意的對話,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選擇,都如同點點星光,匯聚成一幅幅動人的畫麵,在我腦海中閃爍。我總忍不住去揣摩,那些被細細描摹的情感,那些埋藏在字裏行間的深意,是否也曾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悄然齣現?這種共鳴,讓閱讀變成瞭一種與自我對話的過程,我從中看到瞭自己,看到瞭曾經的某個片段,也看到瞭對未來的某種期許。書頁翻動間,時間仿佛也慢瞭下來,我沉浸在這片由文字構築的寜靜之地,享受著這份難得的安寜與慰藉。
评分心灵的慰藉
评分京东快递果然快,显示的13号到结果12号就给送来了,给个好评。书也会好看的,在贴吧里看了点大概,还是挺好看的,顶一个
评分不错,特价买的
评分很不错,我还以为图片是彩色的,收到后居然是黑白的,还没24小时就到了
评分相当好
评分贴吧看了贴购买支持一下,京东购买也是放心是正版
评分在贴吧看了直播贴,写的很好,纸张印刷不错
评分当游记,更多是对作者自由的向往,所以支持下。若关注作者公众号,就发现内容是重合的
评分挺喜欢的,静下来看看书挺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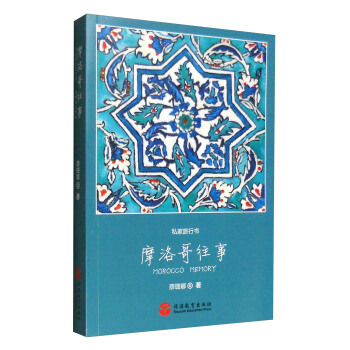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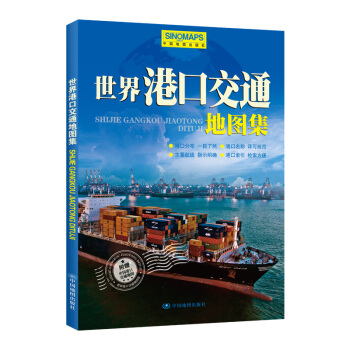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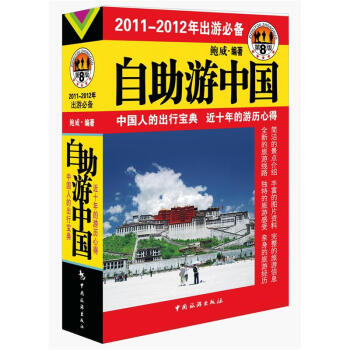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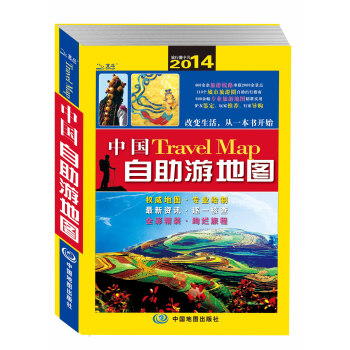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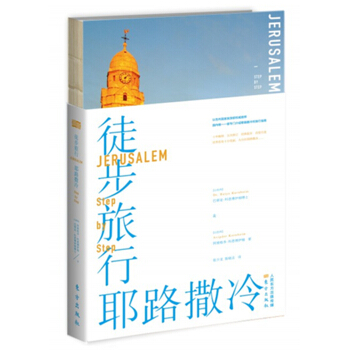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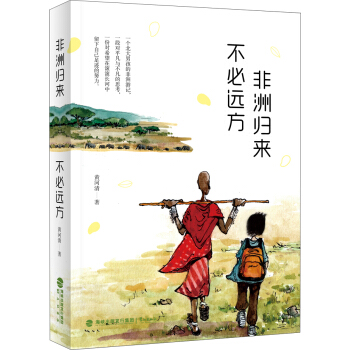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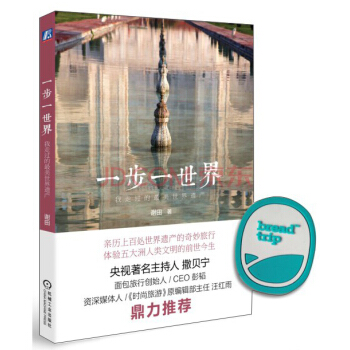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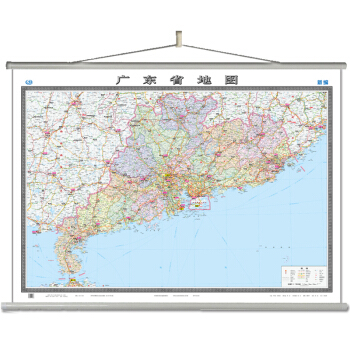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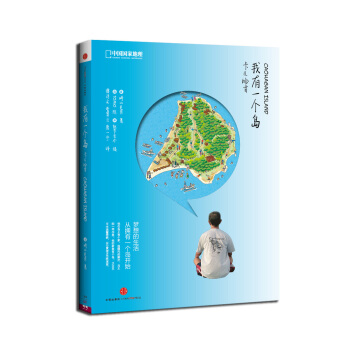


![中级导游员系列丛书:导游知识专题(修订版) [The Knowledge Monograph for Tour Guid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32177/rBEhWlNF6RoIAAAAAAMalrA33LwAALgIgKLbKMAAxqu51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