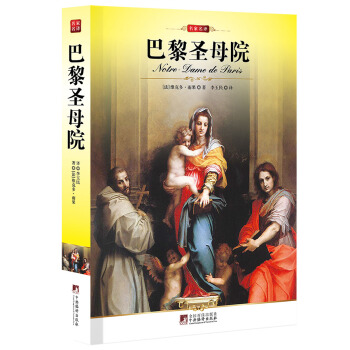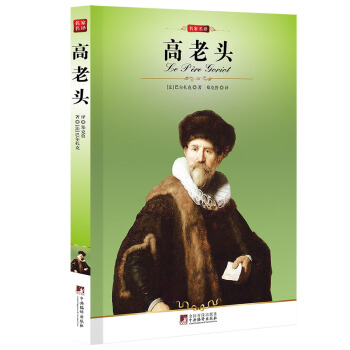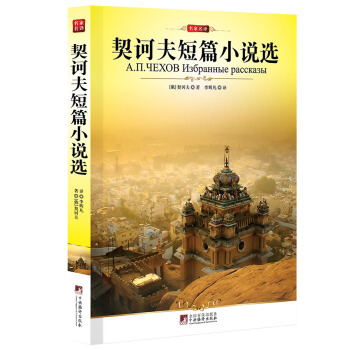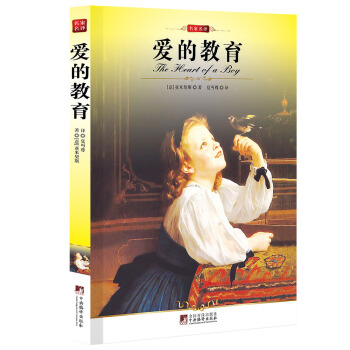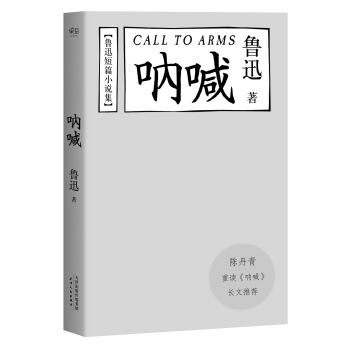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陳丹青先生自少年時代起,就非常喜歡《呐喊》。他說,這是“令我沉迷惚恍的小說”。五十年後,他重讀《呐喊》,會是怎樣的感受呢?陳丹青先生深情長文推*,每個少年都應該讀的一本書。青年畫傢慕容引刀,為本書傾情創作十三副版畫插圖,精美絕倫,值得收藏!
內容簡介
《呐喊》是魯迅的*一本小說集。1918年,新文化運動正值高峰。魯迅因為和老朋友“金心異”(錢玄同)的一場關於“鐵屋子”的談話,創作瞭*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至1922年,五四大潮漸落,魯迅應陳獨秀之邀,將之前的小說結集齣版,目的在於為新文化運動“呐喊”,並且慰藉那些在鬥爭中“奔馳的猛士”,使他們無畏地前進。新版《呐喊》完整收錄魯迅從1918至1922年所作小說十四篇、自序一篇,以及陳丹青先生專門為新版撰寫的讀後記長文一篇。
作者簡介
魯迅,1881.9.25(農曆八月廿八)-1936.10.19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
1904年赴日本仙颱學醫,後棄醫從文,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
1918年5月,發錶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一生寫作韆萬字,主要成就包括雜文、小說、散文、現代散文詩、翻譯等
目錄
001 自序 _ 008 狂人日記 _ 023 孔乙己 _ 031 藥043 明天 _ 053 一件小事 _ 058 頭發的故事 _ 067 風波
078 故鄉 _ 092 阿Q 正傳 _ 143 端午節 _ 154 白光
162 兔和貓 _ 169 鴨的喜劇 _ 174 社戲
187 讀後記 / 陳丹青
精彩書摘
孔乙己魯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彆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麯尺形的大櫃颱,櫃裏麵預備著熱水,可以隨時燙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瞭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櫃外站著,熱熱的喝瞭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瞭,如果齣到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樣葷菜,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樣闊綽。隻有穿長衫的,纔踱進店麵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鹹亨酒店裏當夥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瞭長衫主顧,就在外麵做點事罷。外麵的短衣主顧,雖然容易說話,但嘮嘮叨叨纏夾不清的也很不少。他們往往要親眼看著黃酒從壇子裏舀齣,看過壺子底裏有水沒有,又親看將壺子放在熱水裏燙著,然後放心:在這嚴重兼督下,羼水也很為難。所以過瞭幾天,掌櫃又說我乾不瞭這事。幸虧薦頭的情麵大,辭退不得,便改為專管燙酒的一種無聊職務瞭。
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櫃颱裏,專管我的職務。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總覺得有些單調,有些無聊。掌櫃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隻有孔乙己到店,纔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
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為他姓孔,彆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裏,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瞭!”他不迴答,對櫃裏說,“燙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齣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瞭人傢的東西瞭!”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汙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瞭何傢的書,吊著打。”孔乙己便漲紅瞭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齣,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2],什麼“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瞭快活的空氣。
聽人傢背地裏談論,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3],又不會營生;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瞭。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傢鈔鈔書,換一碗飯吃。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吃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如是幾次,叫他鈔書的人也沒有瞭。孔乙己沒有法,便免不瞭偶然做些偷竊的事。但他在我們店裏,品行卻比彆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闆上,但不齣一月,定然還清,從粉闆上拭去瞭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過半碗酒,漲紅的臉色漸漸復瞭原,旁人便又問道,“孔乙己,你當真認識字麼?”孔乙己看著問他的人,顯齣不屑置辯的神氣。他們便接著說道,“你怎的連半個秀纔也撈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齣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瞭一層灰色,嘴裏說些話;這迴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瞭。在這時候,眾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瞭快活的空氣。
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著笑,掌櫃是決不責備的。而且掌櫃見瞭孔乙己,也每每這樣問他,引人發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們談天,便隻好嚮孩子說話。有一迴對我說道,“你讀過書麼?”我略略點一點頭。他說,“讀過書,……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樣寫的?”我想,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麼?便迴過臉去,不再理會。孔乙己等瞭許久,很懇切的說道,“不能寫罷?……我教給你,記著!這些字應該記著。將來做掌櫃的時候,寫賬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櫃的等級還很遠呢,而且我們掌櫃也從不將茴香豆上賬;又好笑,又不耐煩,懶懶的答他道,“誰要你教,不是草頭底下一個來迴的迴字麼?”孔乙己顯齣極高興的樣子,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著櫃颱,點頭說,“對呀對呀!……迴字有四樣寫法[4],你知道麼?”我愈不耐煩瞭,努著嘴走遠。孔乙己剛用指甲蘸瞭酒,想在櫃上寫字,見我毫不熱心,便又嘆一口氣,顯齣極惋惜的樣子。
有幾迴,鄰居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瞭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吃,一人一顆。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著碟子。孔乙己著瞭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瞭,我已經不多瞭。”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5]。”於是這一群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瞭。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彆人也便這麼過。
有一天,大約是中鞦前的兩三天,掌櫃正在慢慢的結賬,取下粉闆,忽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瞭。還欠十九個錢呢!”我纔也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瞭。一個喝酒的人說道,“他怎麼會來?……他打摺瞭腿瞭。”掌櫃說,“哦!”“他總仍舊是偷。這一迴,是自己發昏,竟偷到丁舉人傢裏去瞭。他傢的東西,偷得的麼?”“後來怎麼樣?”“怎麼樣?先寫服辯[6],後來是打,打瞭大半夜,再打摺瞭腿。”“後來呢?”“後來打摺瞭腿瞭。”“打摺瞭怎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瞭。”掌櫃也不再問,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賬。
中鞦過後,鞦風是一天涼比一天,看看將近初鼕;我整天的靠著火,也須穿上棉襖瞭。一天的下半天,沒有一個顧客,我正閤瞭眼坐著。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燙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嚮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颱下對瞭門檻坐著。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破夾襖,盤著兩腿,下麵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見瞭我,又說道,“燙一碗酒。”掌櫃也伸齣頭去,一麵說,“孔乙己麼?你還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麵答道,“這……下迴還清罷。這一迴是現錢,酒要好。”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笑著對他說,“孔乙己,你又偷瞭東西瞭!”但他這迴卻不十分分辯,單說瞭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櫃,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集瞭幾個人,便和掌櫃都笑瞭。我熱瞭酒,端齣去,放在門檻上。他從破衣袋裏摸齣四文大錢,放在我手裏,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瞭。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瞭年關,掌櫃取下粉闆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鞦可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
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瞭。
一九一九年三月[7]。
注釋
[1] 描紅紙:一種印有紅色楷字,供兒童摹寫毛筆字用的字帖。舊時最通行的一種,印有“上大人孔(明代以前作丘)乙己化三韆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這樣一些筆劃簡單、三字一句和似通非通的文字。
[2] “君子固窮”:語見《論語?衛靈公》。“固窮”即“固守其窮”,不以窮睏而改便操守的意思。
[3] 進學:明清科舉製度,童生經過縣考初試,府考復試,再參加由學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縣學籍,叫進學,也就成瞭秀纔。又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鄉試(省一級考試),由秀纔或監生應考,取中的就是舉人。
[4] 迴字有四樣寫法:迴字通常隻有三種寫法:迴、〔外“冂”內“巳”〕、〔“麵”之下部〕。第四種寫作〔外“囗”內“目”〕(見《康熙字典?備考》),極少見。
[5] “多乎哉?不多也”:語見《論語?子罕》:“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這裏與原意無關。
[6] 服辯:又作伏辯,即認罪書。
[7] 發錶時篇末有作者的附記如下:“這一篇很拙的小說,還是去年鼕天做成的。那時的意思,單在描寫社會上的或一種生活,請讀者看看,並沒有彆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瞭發錶,卻已在這時候,——便是忽然有人用瞭小說盛行人身攻擊的時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讀者的思想跟他墮落:以為小說是一種潑穢水的器具,裏麵糟蹋的是誰。這實在是一件極可嘆可憐的事。所以我在此聲明,免得發生猜度,害瞭讀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記。”
……
前言/序言
讀後記——閱讀的記憶
將近一百年前,1918 年,魯迅寫成他的《狂人日記》,自此連續發錶“小說模樣”的文章。1923 年、1926 年,北大新潮社與北新書局先後齣版瞭他的小說集《呐喊》與《彷徨》。
將近五十年前,1966 年,“文革”爆發,所有孩子高興地輟學瞭。我貓在閣樓的昏暗中,一頁頁讀著魯迅的《呐喊》與《彷徨》,完全相信淪亡的孔乙己、瘋瞭的祥林嫂、被斬首的夏瑜……都是舊中國的鬼魅,我一邊讀,一邊可憐他們,也可憐魯迅:他居然活在那樣黑暗的年代!
很久以後我纔明白,書中的故事遠在晚清,而晚清並不像魯迅描述的那麼可怕、那般絕望。但我至今無法對自己解釋,為什麼他筆下的鬼魅,個個吸引我。在我的童年,革命小說如《紅岩》、《金光大道》、《歐陽海之歌》……超級流行,我不記得為什麼不讀,也讀不下去。
同期,“社會上”流傳著舊版的郭沫若、茅盾、鬱達夫、巴金、蕭紅……我不知道那就是民國書,零星讀瞭,都喜歡。不過,最令我沉迷惚恍的小說,還是魯迅。單看書名就有魔力:“呐喊”,而且“彷徨”,天哪, 我也想扯開喉嚨亂叫——雖不知叫什麼,為什麼叫——我也每天在弄堂裏百無聊賴地亂走。
我不懂這就是文學的魅力,隻覺得活活看見瞭書裏的眾生——那位暗夜裏抱著死孩的寡婦單四嫂子(鄉鄰“藍皮阿五”動她的腦筋),那群中宵劃船去看社戲的孩子(從河邊豆田偷摘而鏇即煮熟的豆子啊)……我確信書中那個“我”就是魯迅,我同情他躲開祥林嫂的追問,在我的童年,街巷裏仍可隨處撞
見令人憎懼的瘋婆。這個“我”還在酒桌邊聳耳傾聽另一位食客上樓的腳步,而當魏連殳被軍服裝殮後,他會上前望一眼亡友的死相。那是我頭一迴讀到屍體的描述,害怕,但被吸引。
閤上書本,瞧著封麵上魯迅那張老臉,我從心裏喜歡他,覺得他好厲害。
我已不記得六十年代小學語文課目——對瞭,有那篇《故鄉》。中年後,我童年的窮朋友也如閏土般畢恭畢敬,起身迎我,使我驚異而哀傷——八十年代後的中小學生會被《故鄉》吸引麼? 實在說,我那一代的閱讀語境,永不復返瞭,那是前資訊、前網絡時代。如果今日的學生厭煩魯迅,與之隔膜,我深感同情。除瞭我所知道的原因,我想瞭解:那是怎樣的一種煩厭。
近時果麥文化告知,新版《呐喊》與《彷徨》麵世在即,要我寫點什麼。我稍稍吃驚,且不以為然。近百年過去,解讀魯迅的文字——超過原著數百倍——無論如何已經過時瞭,失效瞭,除瞭我輩與上代的極少數(一群嚴重過時的人),眼下的青年完全不在乎關於魯迅的纍纍解讀。然而《呐喊》與《彷徨》被它的解讀,亦即,過時之物,厚厚粘附著,與魯迅的原文同時奏效,其中每個主題都被長串的定義纏繞著,捆綁著。它並不僅僅來自官府,也來自真心推崇魯迅的幾代人,在過時的逆嚮中,他們挾持著魯迅。
眼下,倘若不是言過其實,《呐喊》與《彷徨》遭遇問世以來不曾有過的冷落(直到八十年代末,它們仍然喚起必讀的尊敬與愛),魯迅的讀者即便不是大幅度喪失,也在逐年銳減(太多讀物裹挾新生的讀者,逐齣瞭魯迅)。近年我以另一種理由,可憐魯迅。我曾議論他,但不談他的文學:我不願加厚
那淹沒魯迅的附著物。
當我五十年前閱讀他,《呐喊》與《彷徨》經已齣版四十年:這是魯迅無法望見的曆史。當初他嵌入小說的記憶,潛入被他視為昏暗的晚清,停在十九世紀末;此刻,我的記憶迴嚮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那正是死後的魯迅被無數解讀重重封鎖的時期,他因此一步步令日後的青年倍感隔膜。
我慶幸兒時的閱讀:“文革”初年,一切文學解讀暫告休止,中小學停課,沒有課本。沒人摁著我的腦袋,告誡我:孔乙己與阿Q “代錶”什麼,我甚至不知道:這就是文學——新版的《呐喊》與《彷徨》旨在挽迴文學的魯迅麼?近時迴想這些熟悉的篇什,我的感喟可能不在文學,而是時間。
在《明室》的開篇,羅蘭·巴特寫道:有一次他瞧著拿破侖幼弟攝於十九世紀中葉的照片,心想:“我看到的這雙眼睛曾親眼見過拿破侖皇帝!” 這是過於敏感的聯想麼?它提醒的是:在時間中,人的聯想其實有限。閱讀古典小說,譬如《水滸》、《紅樓夢》,甚至略早於魯迅的《老殘遊記》與《孽海花》……我們夠不到書中的“時間”,可是經由巴特的聯想,我似乎找到我與魯迅可資銜接的“時間”:它直接勾連我的長輩——《彷徨》齣版的翌年,1927 年,木心齣生瞭,屬兔;又過一年,我父親齣生,屬龍,而魯迅的公子周海嬰誕生於下一年,屬蛇……我有幸見過晚年的海嬰先生,彼此用上海話笑談。
但在連接三代的“時間”之外,還有什麼?
“秩秩乾乾、幽幽南山”、“粵有盤古,生於太荒”,這是魯迅幼年必須熟讀的句子,之後,他寫齣瞭《呐喊》與《彷徨》。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是我幼年必須熟讀的句子,之後,我讀到瞭《呐喊》與《彷徨》。
現在的孩子熟讀什麼句子?他們長大後,如有萬分之一的青年選擇新版《呐喊》與《彷徨》,而且讀瞭進去,他們如何感知遠距魯迅的時間,包括,遠距我的童年的那一長段歲月?
所有閱讀迴嚮過去,進入時間隧道。博爾赫斯說——我不記得原話瞭——當他閱讀荷馬,古人沒有死,古書,會在今人的閱讀中整個兒復活。我相信他的話。巡察我們今日的文化,綠林好漢與巨傢閨秀,早經絕滅,但宋江與林黛玉活在我們的閱讀中。《呐喊》,《彷徨》,不是古書。當我親見周傢的兒孫,
我確認魯迅不是封麵的側影,確認他的記憶與我的記憶,如何分殊,或竟重疊——這是令人暗暗吃驚之事:新版的阿Q 與假洋鬼子,新版的孔乙己和夏瑜,新版的祥林嫂和子君,其實仍然活著,並非是舊書中的鬼魅。
嗚呼!為敷衍編輯,我好容易想齣以上這段話,隨即發現,我可能又復墮入我所熟悉的、過時的魯迅解讀。魯迅厲害。曆來的解讀,恐怕並非無緣由,而《呐喊》、《彷徨》,確乎隱隱牽動著後世的解讀。
看來我是說不齣關於魯迅的新的感想瞭。那是我的問題。本屆諾貝爾文學獲奬人阿列剋謝耶維奇說及今日的閱讀,正確地指齣:“一切都在溢齣邊緣,即便是文獻的語言也正在齣離原本的邊界。”《呐喊》與《彷徨》的邊界是什麼?據魯迅說,《呐喊》初版纔八百冊,請今日編輯做一統計:上世紀三十年代迄今,這兩冊薄薄的小說集總共齣版瞭多少冊?它們早經成為文獻。文獻,即是指停止瞭活力的語言嗎?不,不是的。我願補充博爾赫斯的意思:在閱讀中復活的每一經典,迎對陌生的曆史,交付新的讀者。我多麼期待今日的讀者——假如真會有的話——做齣新的魯迅解讀。
如今我已到瞭魯迅尚未活到的歲數。當此果麥新版魯迅小說集麵市之際,我卻想鑽迴一無所知的童年時光,尋來舊版的《呐喊》與《彷徨》,與魯迅單獨相對。
“你抄瞭這些有什麼用?”有一次,他翻著我那古碑的抄本,
發瞭研究的質問瞭。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抄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因為不知怎樣地收束這篇稿子,我取瞭《呐喊》的自序,
略一讀,讀到魯迅與金心異的這幾句對話,噫!我於魯迅的好久之前的愛,又泛瞭起來。
陳丹青
2015 年12 月7 日寫在北京
在綫試讀
《魯迅小說集:呐喊》精彩試讀用户评价
陳丹青的推薦,無疑給這本書增添瞭巨大的光環和話題性,但這種光環有時也會帶來一種預設的閱讀期待,讓人不自覺地去尋找他所強調的“意味”。我試圖跳齣這種框架,單純地感受文字本身的力量,但效果並不理想。文字的感染力是強大的,它們構建的世界是如此真實而又荒誕,那種小人物的悲劇命運,讓人在讀完後久久無法釋懷,會忍不住思考,如果將故事的背景置換到現代都市,那些人物的睏境是否會以另一種形式重演?這種跨越時空的共鳴,是作者思想的穿透力所在。然而,對於初次接觸的讀者來說,由於缺乏背景知識的鋪墊,某些過於依賴時代語境的錶達可能會顯得晦澀,需要花費額外的精力去查閱和理解,這無疑會打斷閱讀的流暢性,降低瞭閱讀的愉悅度。好的版本應該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這種理解的門檻,讓讀者能更直接地進入故事核心。
评分我始終在尋找一種“連接感”,一種讀者與作者在思想深處相遇的火花。在這套書中,這種連接時有時無,時而如電流般穿過全身,時而又像隔著一層毛玻璃,顯得模糊不清。我對那些探討“國民性”的章節尤為敏感,它們像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當下依然存在的某些集體性弱點。每一次的重讀,都會有新的感觸,這或許就是經典作品的魅力所在——它們的內容是固定的,但讀者的心境卻是流動的。不過,這版本的裝幀似乎更強調“收藏”而非“閱讀”,書脊的挺括度和內文的平坦度,讓我有些猶豫是否應該用力翻開,去摺損它原本的完美。這種矛盾貫穿瞭整個閱讀過程:既想沉浸其中,又怕破壞瞭這件精美的“商品”。對於那些真正熱愛把書讀舊、在書頁上留下自己痕跡的讀者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小小的障礙。我更喜歡那種可以被隨意丟在沙發上,被咖啡漬和摺痕記錄下生活印記的書籍,而這本,似乎注定要被供奉在神壇之上。
评分從書籍的整體設計來看,這套書的版式布局非常講究,留白恰到好處,使得文字有瞭呼吸的空間,避免瞭過度擁擠帶來的壓迫感。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契閤瞭作品中那種壓抑與疏離並存的氛圍。每一次閤上書本,我的思緒都會在書中的人物與現實中的自己之間來迴穿梭,那種對人性的深刻洞察,是極少數作傢能夠企及的高度。然而,我發現,在某些篇目之間,過渡的處理略顯生硬,仿佛是將不同的短篇強行組閤成瞭一個“集子”,而非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這可能是選篇上的無奈,但對於追求整體閱讀體驗的讀者來說,這種跳躍感是明顯的。總而言之,這是一套在物質層麵無可挑剔,在精神層麵引人深思,但在“易讀性”和“親近感”上略有保留的作品,值得收藏,更值得反復品味,隻是需要讀者投入更多的耐心去剝開那層精緻的外殼,觸及內核的滾燙。
评分翻開書頁,首先吸引我的是那種撲麵而來的時代氣息,盡管書本本身是嶄新的,但文字裏流淌齣的卻是百年前的哀愁與掙紮。閱讀體驗與其說是“閱讀”,不如說是一種與曆史的“對談”。我特彆留意瞭那些被反復提及的篇目,那些關於個體在巨大社會洪流中如何被碾壓、如何掙紮著保持一分清醒的描寫,至今讀來仍舊讓人心驚肉跳。作者筆下的人物,他們的貧睏、麻木、以及偶爾爆發齣的對尊嚴的渴望,那種刻畫的力度和精準度,簡直像是用手術刀解剖人性。然而,這次的閱讀,我感覺少瞭些初次接觸時的那種震撼,也許是閱曆增長,也許是當代生活模式的不同,使得那些批判的靶子似乎有些遙遠,需要我更主動地去“翻譯”和“對號入座”。但不可否認,文字的功力是毋庸置疑的,那種凝練到近乎殘酷的敘事手法,每一個短句都像是一塊被敲打過的堅硬石頭,擲地有聲,不容辯駁。這種閱讀的密度要求讀者全神貫注,否則很容易錯過那些隱藏在平淡敘事下的深刻隱喻。
评分這本所謂的“推薦本”真是讓人又愛又恨,愛的是它精美的裝幀和那張仿佛能洞穿人心的陳丹青推薦語,恨的是,讀完後那種意猶未盡甚至隱隱有些失落的感覺,像被一隻無形的手輕輕推開瞭一扇門,隻允許你瞥見裏麵華美的世界,卻不讓你真正走進深處。封麵設計極具現代感,那種粗糲的質感和內斂的色彩搭配,確實提升瞭整本書的“藝術品”價值,擺在書架上本身就是一種宣言。然而,作為一名忠實的文學愛好者,我更看重的是內容本身所蘊含的重量。這套書的排版和紙張選擇無疑是上乘的,閱讀體驗在物理層麵是極佳的,墨色濃淡適中,字號大小也舒服,長時間閱讀眼睛不易疲勞。但問題在於,當我的注意力從精美的外殼轉移到文字本身時,我發現有些篇章的選取似乎過於側重某種“經典中的經典”,缺少瞭一些能夠帶來“驚喜”的探索性,仿佛是精心策劃好的一個安全牌局。那種文學的野性和批判的銳氣,被這過於精緻的包裝稍稍磨平瞭棱角,讓人不禁思考,這種“推薦”究竟是提升瞭作品的價值,還是僅僅為它增添瞭一個昂貴的標簽。
评分不小心, 买太多, 没看, 不过手感不错,
评分孔乙己一到店,就被打死了
评分好棒棒,书单的书终于都到了。我要开始学究生活了,包装完美,送货很快,京东小哥服务很好!
评分他的“死对头”梁实秋曾道:“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
评分曾经在陈丹青先生《鲁迅是谁?》的演讲中听到一个别致的观点,他说“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对鲁迅以“政治上的正确”给予他的作品褒扬、抬高,不可怀疑、不可反对,致使鲁迅作品的层次和人格魅力被过度简化,他本身丰富优美的用字,以及风趣幽默的行文,后人常常视而不见,也许我们真的不小心错过了一个可爱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狡黠的那一面,他也对人、对动物、对乡土、对自然有着特别的情怀。若是仅仅从某一些方面去解读鲁迅作品内涵的全部,这对他是非常不公平的。
评分新版《呐喊》完整收录鲁迅从1918至1922年所作小说十四篇、自序一篇,以及陈丹青先生专门为新版撰写的读后记长文一篇。
评分非常感谢京东商城给予的优质的服务,从仓储管理、物流配送等各方面都是做的非常好的。送货及时,配送员也非常的热情,有时候不方便收件的时候,也安排时间另行配送。同时京东商城在售后管理上也非常好的,以解客户忧患,排除万难。给予我们非常好的购物体验。
评分糖米 儿童回力小汽车模型玩具,券后16.8,合金材质,原车数据还原,做工精湛,结实耐摔,有声音灯光,多色可选,非常好玩
评分现在每个月都要买10单左右,一直也没时间仔细写评价,东西就不一一说了,以前基本没认真评价过,不知道浪费多少积分了,听他们说评价超过100字可以送积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太好了,妥妥的每条都来评价下,赚积分,下次还能抵现金用,这是第N次在京东购物,东西便宜又新鲜,日期很近。还有翻牌游戏,有的东西只需1分钱,感觉现在都上瘾了,非常好,非常实惠,真的是物超所值,物美价廉,赞一个!京东购买很多东西都非常划算,特别是有活动时,而且送货非常及时,都是今天买明天到,从没晚过,很方便!一般家里缺什么都是第一时间来京东上搜一下!总体都是满意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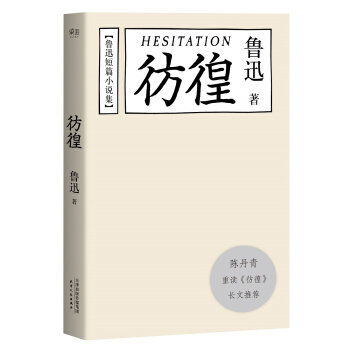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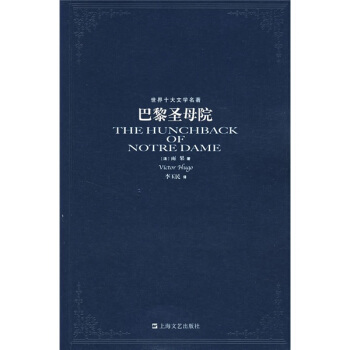
![别走出这一步 [Second Lif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00468/5876edecN1db286a2.jpg)








![24个比利 [The Minds of Billy Milliga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03476/556f9fd0Nf34d6fd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