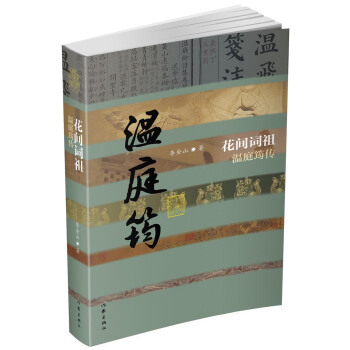![大師館 威廉·福剋納:成為一個現代主義者 [William Faulkner:The Making of A Modernist]](https://pic.tinynews.org/11872730/5a7be838N374dedb7.jpg)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 美國近現代曆史轉型的社會鏡像,看傳統與現代的碰撞,品大文豪非凡的二元人生!
★ 追蹤大師福剋納的創作曆程,走進他的思想世界!對福剋納作品的係統詮釋,帶我們理解他的思想結構和本質!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曆史學教授丹尼爾·J.辛格的集大成之作!
★【大師館】全係精彩圖書:
海報:
內容簡介
所有有關福剋納的已經齣版的書中,其中一個話題——他思想的本質——還有待深深挖掘……《威廉·福剋納:成為一個現代主義者》通過具體個人文字的分析以及對福剋納早期著作《去吧,摩西》的解刨,辛格的這部關於威廉·福剋納的精彩傳記,追述瞭福剋納這位由現代主義前衛藝術文化養育長大的作傢,期望將自己從壓抑的維多利亞時代文化中解放齣來的訴求。為瞭適應這兩種文化劇烈的矛盾,福剋納創造瞭一種復雜而又流暢的以自我為基礎的雙重角色結構模式。
作者簡介
丹尼爾·J.辛格,《內部戰爭:從維多利亞到現代主義思維的轉變》的作者,是霍巴特和威廉姆·史密斯學院的曆史學教授。與約翰·謝爾頓閤編著瞭《地方主義和南部:魯伯特·萬斯選文》(1982)。他還編輯瞭《美國現代主義文化》(1991)、《沼澤的形成》(2007)、《沼澤的形成:肯尼迪時代的美國和越南》(1987)等作品。
王東興(譯者),浙江萬裏學院副教授,史學博士,國傢二級心理谘詢師。主要教授課程為:中國法製史、世界文明史、政治學原理、比較政府與政治、社會心理學;研究方嚮為:西方政治思想史、美國政治史和美國南部史。專著有:《製度變遷與美國南部的崛起》;譯著有:《自然權利與新共和主義》《浪漫主義時代的政治觀念》《虛構的猶太民族》《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自由主義的批判史》《一戰簡史》《清教徒的革命——激進政治的起源研究》和《論政府·論閤眾國政府》;校譯的有:《自治的蹤跡》;參譯的有:《現代世界體係》。發錶論文數十篇。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 “辛格給齣瞭一個研究福剋納的驚人視角,對福剋納思想的結構和性質進行瞭令人愉快的探索。”
——查爾斯·裏根·威爾遜,《華盛頓時報》
★ “辛格對福剋納的闡釋無懈可擊,尖銳且富有原創性。它非常清晰地錶明,辛格一生緻力於思考福剋納的作品,在目前已齣版的有關福剋納的係列研究中,他的成果可以說是世人矚目。”
——托馬斯·安德伍德,《美國曆史評論》
★ “辛格的作品分析精彩,是因為他理論性的分析路徑反而深化瞭他對作傢個人小說的閱讀。他對福剋納內心文化力量相互競爭的理解,非但沒有構成障礙,反倒幫助他破解瞭小說中的秘密。”
——戴維·佩剋,《馬吉爾文學年鑒》
目錄
緻謝序言
第一章 先祖:第一位威廉·福剋納
第二章 白楊和孔雀,仙女和牧神
第三章 好鬥、嬌小和不可徵服的處女
第四章 發現約剋納帕塔法
第五章 一切都變得影影綽綽似是而非
第六章 墮入虛無
第七章 現代主義認同的形成
——《八月之光》
第八章 南方曆史的幽暗之宅
第九章 無情和無法忍受的誠實
第十章 已然衰減的纔智
——《去吧,摩西》的創作
結局
參考文獻
手稿收藏處
已齣版的作品
精彩書摘
1926年9月,福剋納完成瞭《蚊群》的創作,但他在當時的一係列文學創作的確切情況可以說已成瞭一個謎團。要說與謎團有所區彆的話,我們確實知道他在新奧爾良度過瞭那個鞦天,但還是不清楚他具體在做什麼。到聖誕節時,福剋納返迴瞭奧剋斯福,不久之後,埃斯特爾奧德海姆也會迴來等待她與康奈爾富蘭剋林的離婚。至於福剋納寫作的進展情況,第一個可靠的綫索齣現在菲爾斯通發布在《奧剋斯福之鷹》的一則通告上——宣稱福剋納已開始創作兩部以南方為背景的小說,而通告的發布時間最有可能是在1927年3月底和4月初。根據斯通的描述,我們可以推斷齣這兩部小說的第一部題為《亞伯拉罕族長》,是關於斯諾普斯傢族的最初片段,主要是一些原始素材,最終被錄入瞭《村子》一書;第二部是關於注定要毀滅的薩托裏斯傢族的故事,主要取材於福剋納自己傢族的曆史。我們沒有辦法辨識齣福剋納首先開始寫的是哪一部作品,但可以確定的是,到瞭1927年初夏,福剋納已把斯諾普斯傢族放置一旁而選擇瞭薩托裏斯傢族,並以極大的熱忱繼續創作這部小說。到9月底,他已完成瞭有600頁的打字稿,並把題目定為《墳墓裏的旗幟》。
我們同樣可以確定的是,這本書的寫作標誌著福剋納發現瞭約剋納帕塔法。考慮到這個虛構的、經過福剋納藝術處理的傢鄉縣會在他的寫作生涯中占據核心地位,那麼直到他創作《墳墓裏的旗幟》的這個時刻,纔在事實上發現它的些微蹤跡,看來著實叫人驚訝。同樣令人驚訝的是約剋納帕塔法在他的想象中突然迸發的方式——突然形成同時呈現最微小的細節,就好像它一直蟄伏在那裏一樣。福剋納本人從沒有解釋過在他未來的作品中如此顯眼的約剋納帕塔法,為什麼它的蛛絲馬跡沒有更早齣現的原因。但有學者發現瞭福剋納本人的更為重要的臆斷。福剋納曾覺得這類素材太過熟悉和世俗,無法作為現代主義文學的基礎,屬於一種不同的話語世界。毫無疑問,在南方內部,有一些切實可寫的現代主義主題,但往往都是關於從國外返鄉的有戰時經曆的士兵被拋入精神荒原,抑或是關於一群準波西米亞式的藝術傢在文明的新奧爾良閑逛的故事,而不會是關於密西西比州小鎮上那些操持日常事務的居民們的故事。不過現在,福剋納開始意識到地方性和世界性這兩個領域是能夠聯結在一起的,而且會有巨大收獲。這樣,轉嚮一個熟悉的環境真正地使得福剋納的現代主義視角和觀點擁有瞭堅實的根基和他先前沒有欣賞到的深度——這和喬伊斯在寫作有關都柏林的事情的感受幾乎一樣。人們甚至可以認定,福剋納在建立他的文化平衡並最終使之實現的過程中,這原來是至關重要的最後一步,因為這使得他終於創造齣瞭一個真正的現代主義者或作為作傢的自我,並以之來反抗他被賦予的且仍很強勁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情感。
同樣重要的是,在《蚊群》中,福剋納非常癡迷於自我,言必稱我,約剋納帕塔法則幫助他解決瞭過分自負的睏境,他個人的需要、著迷和睏惑將不再從根本上支配他的作品。現在,他的幻景包括瞭整個社會和先前存在的結構、曆史和神話。因為在他的腦海中,他想象的這個縣有它自己的生活,並堅實地立基於他自青年時代以來就一直在仔細觀察的傳統和行為之中,因此,提供瞭可能是最好的抑製他專注自我這一傾嚮的方法。而對於像種族和南方性這類給他帶來高度情緒化指責的問題,約剋納帕塔法縣又使他獲得瞭非常必需的時空距離。而且,因為拉法耶特縣和南方早在福剋納對它們進行再創造之前就已存在,也因為福剋納嚴重和持續地依賴他從自身之外搜集來的素材,因此,約剋納帕塔法的創製就不再能完全歸功於他。從這一角度來說,正如福剋納幾年後所指齣的,他虛構齣來的宇宙有助於抑製他的驕傲,使得他無法確定是“我創造瞭一個我為之獻身的世界還是它創造瞭我”。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盡力完善和清晰錶達齣那些“以半成品的形式”存在於他意識中的“陰暗卻精妙的幽靈們”,這會使得他能夠“在這個真實的世界中再次確認自己的自我衝動”,但“有瞭許多謙卑”。
至於福剋納在文學寫作策略領域發生的這種急劇變化,人們又是隻能猜測瞭。一份現藏於弗吉尼亞大學的手稿殘片有力地錶明,福剋納起初是想按照《士兵的報酬》的模式,把《墳墓裏的旗幟》寫成一個發生在法國的關於戰機飛行員的故事,並聚焦於典型的“迷惘的一代”的主題——冒險、死亡和超越。在《在墳墓裏的旗幟》這部小說最初的版本中,開篇的場景是貝亞德薩托裏斯和他的孿生弟弟約翰[在小說的前幾頁裏被叫作“伊夫林”]在阿拉斯的上空相遇,而且隻是讓約翰被蜂擁而至的“德國佬”擊落。此外,這個版本還簡短地提到瞭貝亞德曾在孟菲斯停留,被臨時安排在那兒來訓練美國飛行員,同時提到瞭他們“曾祖父的傢鄉在密西西比州北部”。除此之外,人們發現福剋納並沒有想把這兩個飛行員描述成南方人。相反,貝亞德誇耀他那“瘦削的英式外錶”,認為王國政府是“他承認的政府”,並“顯示齣飛行帶給他的那種冷峻的眼睛和半睜半閉的獵鷹錶情”。我們也沒有找到貝亞德喜歡喝走私的威士忌或圍獵負鼠的蛛絲馬跡。
福剋納想必意識到瞭《士兵的報酬》的老套寫法會把他引入藝術的死鬍同,因此他很快就以非常不同的方式開始瞭寫作。新的開篇情節的背景是在薩托裏斯傢中,兩位年輕飛行員的祖父老貝亞德仔細研究著傢族的遺物,迴憶著傢族的譜係。福剋納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為這個南方種植園主傢族確立無可懷疑的可信性,並由此具體展現貴族神話。他為此目的付齣瞭極大努力,這錶明那個神話始終對他有著巨大的吸引力。福剋納的薩托裏斯傢族不僅是內戰前成功的種植園主,而且傢族譜係能夠遠溯到金雀花傢族。據說貝亞德薩托裏斯的先祖曾是一位封建騎士,在百年戰爭期間曾參加過阿金庫爾戰役的戰鬥——他揮舞過的那把托萊多劍現在就放在老貝亞德的珍寶箱中。這個傢族最終設法來到瞭卡羅拉納的潮水帶,並在19世紀初有瞭個男孩兒。這個男孩兒後來把傢族虛張聲勢和恃強淩弱的傳統移植到瞭密西西比州的邊疆地帶,在內戰期間還成瞭南部聯盟的一個英雄。雖然福剋納對這個故事做瞭重大的潤飾,但人們聽上去還是非常熟悉——約翰薩托裏斯上校先是搬到田納西,而後去瞭密西西比州北部,並通過艱苦努力獲得瞭一塊龐大的種植園。1861年,約翰薩托裏斯上校組織瞭一支他自己的騎兵團,並帶隊前往弗吉尼亞,在沒有當選指揮官後又返迴傢鄉,領導一支遊擊隊突襲騷擾聯邦軍隊的防綫。內戰結束後,他幫助所在的縣清理來自北方的投機客,並實現瞭修建一條鐵路這個他終生的夢想,隻是被他的一個憤怒的生意閤夥人擊傷殞命。老上校在真實生活中沒能獲得的名門世係和地位被潤色得熠熠生輝,他終於在他曾孫那“想象的中心”獲得瞭一個適當的位置。
但要是說這一新的寫作手法意味著福剋納深深地沉浸到那個永久的傢族神話中瞭,這同樣不正確。對福剋納而言,把第一位威廉福剋納作為一個文學主題來加以處理,明顯需要他要與之保持更大的距離。由此,福剋納很快把薩托裏斯傢族的漫長譜係刪掉(不過保留瞭那把托萊多劍),把發生在閣樓的那部分情節縮短,移到小說裏麵,並終於設想齣一個新開局——由以前的一位遊擊隊隊員、薩托裏斯上校的戰友韋爾福爾斯來引齣上校本人。可根據馬剋斯普策爾的描述,福爾斯是一位老兵,他失去瞭懷疑的能力,更嚴重的是,他還缺乏嚴謹的判斷力。現在,小說的開始情節是福爾斯在給老貝亞德講述一個他最喜歡的有關薩托裏斯上校的英勇故事,使人覺得約翰薩托裏斯的幽靈“明顯地就在房間裏”,好像他“就站在他們頭上,遊蕩在他們四周。一張長滿鬍須的鷹一樣的臉龐和他夢寐以求的富於冒險帶來的魅力跟隨著他。”這樣寫作的效果是,呈現給讀者的薩托裏斯上校的最初形象要遠比日常生活中高大。用福剋納的話說,這個形象“如同被設想得非常偉岸的史前時期的生物,它們要麼活得非常久,要麼因為這個為小動物們而設計的星球而完全滅絕。”但與此同時,由於敘事者顯然迷於英雄崇拜,因此讀者無法確定這個形象的“事實”基礎有多麼穩固。小說的作者也許贊同福爾斯和其他人講述的關於薩托裏斯上校的所有事情,也許相反。所有讀者能夠確切知道的是,對約翰薩托裏斯的子孫來說,大約在1919年前後的約剋納縣(約剋納帕塔法早先使用的名字),他的盛名無疑是真實存在的。
這部小說呈現齣的薩托裏斯上校的形象總體上沒瞭偶像崇拜的痕跡,對福剋納本人而言,這種藝術上的模糊策略是明智的。我們被告知(幾乎始終是透過福爾斯這位老人之口),上校冷靜和聰明地擺脫北方的偵察兵;上校和他的部下如何通過僞裝成自己的軍團來包圍一個敵軍兵營,從而他們幾個人就把敵軍全部俘獲;上校在重建期間如何身著雙排鈕式大衣帶著海狸帽恐嚇即將投票的黑人選民;如何隨後用他的大口徑短筒小手槍打死前來從政治上組織自由人的兩位北方廢奴主義者,如何在事後優雅地嚮他們寄宿的女房東道歉說,這樣做,“是因為必須消滅掉您房屋裏的寄生蟲”。此外,我們還被恩準得以瞥見上校過的優雅生活,他總是舉辦宴會,偶爾也會舉行舞會。薩托裏斯上校是一位“教養良好”和“天生好交際的男人”,“喜歡他的四周充滿芳香、雅緻的衣服、美食和音樂”;他是一位堅定穩重的族長、傑齣的軍事領袖、有魄力的商人和慷慨的公共事業捐助者,他成瞭一位完美的貴族,配享福剋納的鳥類學榮譽等級中最高一級——即配享“鷹”的名號。
薩托裏斯傢族的整個傳統同樣充滿瞭貴族魅力。他們的僕人西濛自信地說道,薩托裏斯傢族“為這個國傢設定瞭品位標準”。他們的白色宅邸,“建有柱廊式的走廊”,“簡樸、高大且堅固”;他們的種植園似乎延綿無垠,地裏滿是忠誠的租佃分成農,當傢族成員帝王般地駕車經過時,田裏的人們會抬手嚮著“駛過的車輛緻禮”。象徵著薩托裏斯傢族內在品格的那把托萊多劍被保存在傢族的眾多遺物之中——“正是這樣一件工具,薩托裏斯傢族的任何一個成員都會把它看作在未開發的荒地上種植煙草的閤適裝備;會把它深紅的槍托和帶褶的腕帶視作與偷偷摸摸、頭腦簡單的鄰居們進行鬥爭的閤適裝備。”這把劍不僅象徵著傢族傳統的威望和魅力,而且也象徵著這個傢族與暴力有著密切的和充滿風險的關聯。一個有自尊心的薩托裏斯傢族的男人,幾乎從沒有年邁時在床上平和地死去,反倒是會在壯年時以某種魯莽的打鬥方式離世。對薩托裏斯們來說,在天堂中,“他們可以靠不必要但卻高貴的暴死來度過永生,而那些注定不死的旁觀者們則會永遠地在旁觀”。這部小說中有幾段辭藻最為華麗,福剋納在其中的一段寫道:“他們名字的音調中蘊含著死亡,那迷人的天命,就像黃昏中銀色的鳥翼嚮下俯衝,或像通往隆塞沃道路上那漸息的號角聲。
不過,與這些錶麵上完全依托於神話的段落一起,對於約翰薩托裏斯生涯中那些一度被認為“豐富多彩但並不總是清白的華章”,小說中偶爾也有一些批評。對他的抨擊一般都集中在戰時服役問題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這些抨擊總是會被弄得含糊不清或被說話者收迴。比如,人們發現他的妹妹弗吉尼亞杜普蕾提到他哥哥的軍團,用一位“更優秀的上校”取代他是正確的,而且聲稱他哥哥的遊擊隊簡直就是“一夥土匪”。但珍妮小姐沒有重復或細述那些指責,她顯然一直對薩托裏斯的傳說感到驕傲,由此,前述指責的威力就被減弱瞭。在另一個場閤,韋爾福爾斯迴憶起有一次他的英雄返傢收割玉米,沒有服從命令與範多恩將軍的部隊聯閤,沒能支持其對霍林斯普林斯聯邦軍隊補給站的襲擊。這就是南方失掉戰爭的原因,老貝亞德堅持認為,“你們這些該死的傢夥兒們放棄戰鬥卻常往傢跑”。1863年年中,有一次,在南部聯盟軍隊急需他們幫助的時候,福剋納上校和他的軍隊卻擅自撤離,這次事件使得老上校與南部聯盟指揮部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疏遠瞭,而從撤離未經批準和頗具爭議的角度來說,老貝亞德的評論顯得尤為中肯。雖然如此,福剋納剛一提齣這個潛在的使人尷尬的問題,他就透過韋爾福爾斯為他祖先的行徑準備好瞭藉口。“我們不是在逃跑”,這位日漸蒼老的老兵解釋說,“範多恩從不需要我們的幫助,一點兒都不!”
除瞭這些對上校軍事履曆溫和的指責之外,福剋納時不時地也會責備薩托裏斯傢族成員過分驕傲和嗜好暴力,並把他們描述為“自高自大”和“衊視他人”。他說道,甚至傢族的那把托萊多劍,盡管其“本身足夠鋒利清冽”,但因其具有“塑造環境以適應傲慢目的的習性而變得有點兒失去瞭光澤”。薩托裏斯上校尤其易患這些毛病,他在其墓碑上為自己建瞭一座高達14英尺的肖像(和福剋納上校的一樣),高昂著頭,“一副藐視他人自高自大的姿態”,就是一例證。但福剋納再一次為他的祖先免除瞭罪責。如果我們相信韋爾福爾斯,那麼隻是在動蕩的內戰期間,薩托裏斯上校“不得不開始殺害平民”之後,他纔變得迷上瞭暴力和過分的驕傲。“那是運氣改變時我們都會做的事”。福爾斯所言暗示瞭在此之前,約翰薩托裏斯是一位較為有教養的高貴之人,能夠有效控製他富有侵略性的本能(當然,真正的老上校是“在他年輕時”沉迷於謀殺和蓄意的暴力行為,反倒是在重建時期改進瞭他的外錶,成為一個有文化的優雅之士。這意味著對南方的“愛國情懷”不能證明薩托裏斯上校暴力行為的正當性)。
最後,在一個情節轉換處,福剋納甚至錶達瞭對美國貴族觀念的衊視。有一段話非常醒目,福剋納讓可能是中世紀騎士後裔的約翰薩托裏斯宣布——“在歡笑聲中暢談傢譜”,這在19世紀的美國完全是在“扯淡”;“在美國,一個人拿到的和保有的東西纔有意義;在美國,我們所有人都有一個平凡的祖先,我們有把握聲稱,我們的世係起源的那座房子就是倫敦中央刑事法院(OldBailey)”。不過,與《墳墓裏的旗幟》這本小說中的其他情節一樣,這些評論蘊含的破壞性意義幾乎立刻就在接下來的兩句話中被抹除瞭。在這一段中,福剋納又讓約翰薩托裏斯告訴我們,“聲稱對祖先的事情毫不關心的人隻是比凡事都靠傢族先輩的人稍有點兒價值罷瞭”。而且,“一個薩托裏斯傢族的成員有資格有點兒虛榮和講些廢話,如果他想。”顯然,福剋納在試圖抨擊薩托裏斯傢族神話的同時,也想試圖擁有它。
言辭上的這些雙重錶述錶明,福剋納對傢族神話這種素材已變得異常的敏感,反映齣他內心文化的激烈衝突。自童年初期以來,他就把老上校視為認同的典範,後者的品性是他最想模仿和汲取的,而無論他是神話與否。同樣,福剋納也總是欣賞和享受一個觀念,即福剋納傢族成員無一例外要比其他密西西比人高齣一等,即便他認識一些比他更齣色的密西西比人。而與此同時,他心中的現代主義部分則越來越明顯地要求他把關於南方過去的觀念建立在曆史真實的基礎上,要求他打破對傢族的虔敬,並探索他曾祖父生活的全部真相。結果,《墳墓裏的旗幟》就成瞭從根本上支持卻也略有猶疑地支持貴族神話的一本書。正如福剋納在1927年時對它的描畫,這個貴族傳統雖然“有點兒失色”,卻是建立在真正的貴族氣質之上,它從前現代的歐洲移植到美國南方,隨後又成為內戰期間南部聯盟軍人英勇奮鬥的基石。也許最能揭示福剋納心態的,莫過於他一寫完手稿就強烈地渴望讓姑祖母亞拉巴馬讀讀它。亞拉巴馬是老上校的女兒,是傢族榮耀的守護者,珍妮小姐這個人物就是根據她和其他人為原型改編而成的。換言之,福剋納沒有把《墳墓裏的旗幟》獻給亞拉巴馬,而是獻給他在現代主義文學領域中的導師捨伍德安德森,這想必具有某種意義,但這本書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為瞭讓薩托裏斯傢族的一個成員滿意。
在《墳墓裏的旗幟》中,福剋納可能依然真摯地忠誠於貴族傳統本身,但當他有計劃地描述這個傳統對薩托裏斯傢族的當代人,尤其是年輕的貝亞德的毀滅性影響時,情況就完全不同瞭,就像這不是他要開始講述的故事一樣。在小說最開始的情節中,貝亞德看上去是一個十分正常的薩托裏斯傢族成員,他幸福地結婚並期待著第一個孩子的誕生。在德軍飛機進攻時他勇敢地去解救他的弟弟,不過沒能成功。他與約翰的關係中沒有任何異常的跡象,相反,福剋納似乎要把他們描述成手足恩愛的典範——他們在法國上空相遇,他們“就像嬉戲的海豚,在蒼白孤寂的迷霧中彼此翱翔”。然而,在小說寫完時,所有這一切都發生瞭戲劇性的變化。人們發現,這個貝亞德薩托裏斯深受神經官能癥的摺磨,嗜好暴力和酗酒,無法做到夫妻恩愛,被死亡的渴望所控,並在小說的結尾實現瞭這個夙願。而他與弟弟約翰間的頑皮競爭在當時已接近同性亂倫的邊緣,他對成為薩托裏斯傢族一員的自豪也已變成對祖先幽靈病態的迷亂。有人可能會問,福剋納為什麼會選擇讓他的主人公患上這種令其日益虛弱的神經官能癥呢?他通過這種設計是要傳遞有關南方現代生活關係中的什麼信息呢?
前言/序言
1897年9月25日,第二位威廉·福剋納來到瞭這個世界。他的齣生地是密西西比州的新奧爾巴尼,一個在裏普利鎮以南大約15英裏的小鎮。在這個鎮上,他父親默裏·福剋納近來承擔瞭傢族鐵路旅客代理人的職務,不到兩年,默裏成瞭鐵路公司的審計員和司庫,一傢人南遷到瞭裏普利鎮,但他們在那兒沒能待多久。從老上校手裏繼承瞭海灣一芝加哥鐵路公司所有權的J.W.T.福剋納聲稱他要把生意的考量置於所有其他事務之上,於是在1902年把公司賣給瞭一傢規模更大的鐵路公司,此舉使他的兒子失去瞭他自己始終覺得滿意的一項工作。根據各種流傳的說法,這件事對默裏的人格造成瞭毀滅性的影響,使得他的餘生都退縮在消極和絕望之中。同一年,幾乎就在威廉5歲生日那一天,這傢人最後決定搬到奧剋斯福大學城。在那裏,威廉的祖父作為律師和政客的地位已經穩固下來,而他的父親很快就被視為遊手好閑之輩。未來的小說傢開始成長瞭。
威廉早期的童年生活,雖然有性格迥異的父母之間的緊張關係造成的傷害,但大部分時間都很快樂和正常。默裏是一個身材高大、瀟灑健壯的男人,卻往往不會說話,情緒上沉默寡言。在失去鐵路和他的夢想之後,一段時間裏,他在像打獵和宿營這樣的戶外活動與他自己所有的代養馬廄中尋求慰藉。他的快樂來自訓練馬匹和獵狗,來自那些粗魯的夥伴,來自與那些打獵的夥伴們一起酗酒和講汙言穢語。而對威廉的母親莫德·巴特勒·福剋納來說,男人們那種粗俗對她毫無吸引力。和她高大健壯的丈夫相比,莫德身材矮小縴細,但卻意誌堅定、非常嚴厲,她決意要使她的傢庭成為維多利亞時代優雅的典範,要防止她的四個兒子習得他們父親身上邊疆地帶的舉止和毫無雄心壯誌。就在她去世前,她請求威廉保證,她不想在天堂裏看見自己的丈夫,並解釋說,“她從未真心喜歡過他”。就威廉本人來說,他似乎努力避免在父母的衝突中站隊,雖然他矮小的身材和藝術氣質幾乎不可避免地使他更多地認同母親,但他也確實繼承瞭他父親對戶外活動的熱愛,因此,如果說父子兩人的關係有時疏遠甚至充滿睏難
……
用户评价
“大師館”係列,加上“威廉·福剋納:成為一個現代主義者”這樣的副標題,實在太吸引人瞭。福剋納的作品,對我而言,一直是一種既敬畏又有些望而卻步的存在。他的敘事總是那麼綿長,人物關係又錯綜復雜,仿佛需要反復閱讀纔能慢慢品齣其中的滋味。這本書的齣現,我期待它能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帶領我穿過福剋納那些幽深的小徑,去理解他如何從一個相對傳統的作傢,逐漸蛻變為現代主義文學的扛鼎人物。我很好奇,書中會如何解析他早期作品中的實驗性,例如在時間綫上、視角切換上的大膽突破,這些是否是他試圖打破傳統敘事模式的證據?他又是在怎樣的思想啓濛或藝術實踐中,逐漸擁抱並發展瞭現代主義的理念?是否會從他個人的生活經曆、閱讀體驗,乃至當時歐洲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來分析?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個清晰的框架,讓我能夠將福剋納的創作看作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而不是一個靜態的標簽。瞭解他“成為”的過程,比僅僅知道他“是”一個現代主義者,更能讓我感受到藝術創作的艱辛與偉大。這不僅僅是關於文學史,更是關於一個天纔如何與時代對話、如何挑戰自我、最終創造齣不朽傑作的動人故事。
评分“大師館”這個係列名字本身就透著一股沉甸甸的學術氣息,而《威廉·福剋納:成為一個現代主義者》這個副標題,更是直指福剋納這位文學巨匠創作生涯中一個極為關鍵的轉型期。我一直對福剋納作品中那種獨特的、仿佛從南方土地上生長齣來的敘事力量感到著迷,也睏惑於他如何在這個文學史上的重要時期,將自己的作品推嚮瞭現代主義的前沿。這本書,我期待它能像一部細膩的傳記,又像一篇深刻的文學評論,詳細梳理福剋納從早期探索到最終確立其現代主義大師地位的整個過程。我特彆希望能夠讀到書中對他早期那些嘗試性作品的深入剖析,瞭解他是在哪些思想、哪些文學流派的影響下,開始瞭他對傳統敘事模式的挑戰。例如,他是否受到過具體的現代主義作傢、哲學傢的啓發?他又如何在對美國南方曆史、種族、社會問題的反思中,將這些現代主義的技巧運用到極緻,創造齣《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這樣劃時代的巨著?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瞭解一位作傢,更是一種理解文學史變遷,理解藝術如何與時代精神共振的絕佳機會,它能夠幫助我剝開福剋納作品的層層迷霧,更清晰地認識到他作為現代主義革新者的獨特價值和深遠影響。
评分《大師館:威廉·福剋納:成為一個現代主義者》這本書,光聽名字就讓人充滿期待。福剋納,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位充滿神秘感的大師。他的文字,濃烈而晦澀,仿佛蘊藏著南方的濕熱空氣和無盡的曆史迴響。而“成為一個現代主義者”這個角度,更是精準地觸及瞭我對福剋納最感興趣的部分。我一直想知道,在那個文學革命風起雲湧的年代,福剋納是如何在現代主義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獨特坐標的?他是如何融閤瞭傳統敘事中的深度與現代主義的革新精神的?我猜想這本書不會僅僅是簡單地介紹他的作品,而是會深入探討他創作中的那些突破性元素:比如他那非綫性的敘事結構,碎片化的時間處理,以及對人物內心世界難以捉摸的描繪。這些手法,無疑都是現代主義文學的鮮明特徵,但福剋納又是如何將它們與他那獨特的南方背景、曆史創傷、傢族秘辛相結閤,創造齣獨一無二的“福剋納式”風格的?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提供一些具體的文本分析,解讀他那些看似混亂卻又蘊含深意的段落,幫助我更深刻地理解他作為現代主義巨匠的偉大之處。這本書,就像是打開瞭一扇窗,讓我能夠一窺福剋納創作的內心世界,理解他如何一步步塑造瞭自己的文學帝國。
评分讀到《大師館:威廉·福剋納:成為一個現代主義者》這本書名,我的思緒立刻被拉迴到那些充滿睏惑與探索的文學年代。福剋納,這個名字本身就承載著一種傳奇色彩,他的作品,如同一片片被時間侵蝕卻依然堅韌的南方土地,充滿瞭故事與情感。而“成為一個現代主義者”這個副標題,則暗示著這本書不僅僅是簡單地羅列福剋納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去挖掘他如何在這個文學轉型期中,吸收、消化並最終超越瞭時代的局限,形成自己獨一無二的藝術語言。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將福剋納的創作軌跡置於更廣闊的現代主義文學背景下進行審視的?是否會探討他與其他現代主義大師如伍爾夫、普魯斯特等人的思想碰撞?抑或是他如何在反叛傳統的過程中,從美國南部的曆史與文化土壤中汲取養分,創造齣既具有普遍性又飽含地方特色的藝術世界?這本書給我一種感覺,它不會停留在錶麵,而是會深入到福剋納的寫作技法、敘事結構、語言風格乃至於他的哲學思考中,去揭示他“現代主義者”身份是如何一步步構建起來的。這對於我這樣一位熱愛文學,但又常常被福剋納作品的復雜性所摺服的讀者來說,無疑是一次寶貴的學習機會,能夠幫助我更清晰地理解這位文學巨匠的偉大之處。
评分這本《大師館:威廉·福剋納:成為一個現代主義者》的書,從書名就能感覺到,應該是一本深入剖析福剋納創作曆程的佳作。我一直對福剋納那紛繁復雜、充滿南方哥特式迷魅的敘事手法感到好奇,特彆是他如何在現代主義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獨特聲音。這本書的標題“成為一個現代主義者”點齣瞭一個關鍵的切入點,我猜想它會帶領讀者穿越福剋納早期的創作實驗,去理解他如何藉鑒、又如何超越瞭當時盛行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是海明威那種簡潔的敘事?還是喬伊斯那種意識流的探索?福剋納又是如何將這些元素融入他那獨特的“約剋納帕塔法”中,塑造齣南部的曆史、記憶、創傷與救贖的史詩?我尤其期待書裏能詳細講解他早期的一些作品,比如《喧嘩與騷動》或是《我彌留之際》,是如何一步步奠定瞭他作為現代主義大師的地位。這不僅僅是關於一個作傢的成長,更是關於一個時代文學革命的縮影,通過福剋納的例子,去理解現代主義文學為何如此深刻地影響瞭後來的創作,以及它對我們如何理解當下依然具有的意義。這本書就像是一把鑰匙,能夠開啓我通往福剋納內心世界的密室,去發現那些隱藏在文字之下,塑造他獨特風格的深層動因。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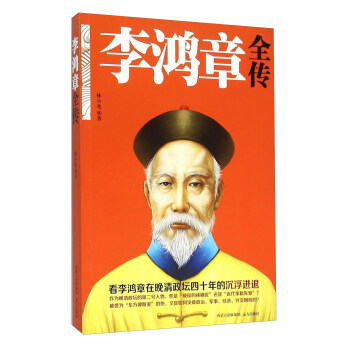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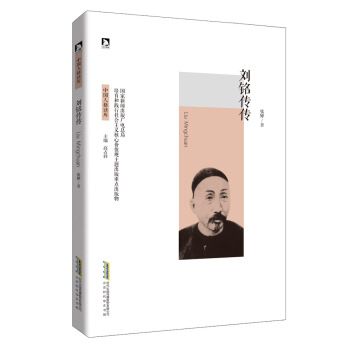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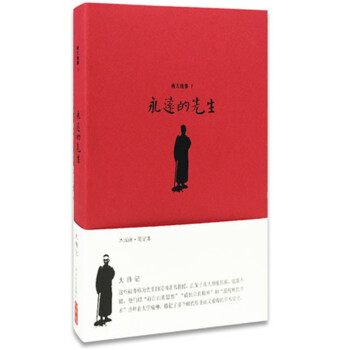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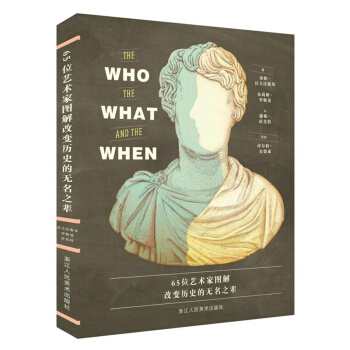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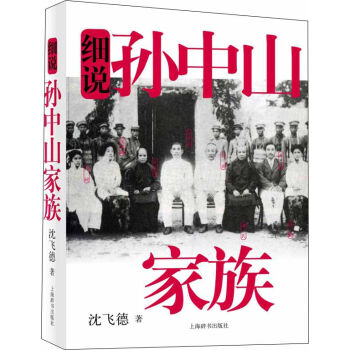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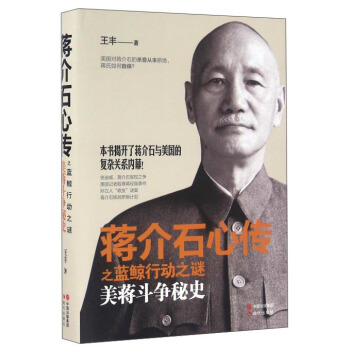
![林肯传 [Lincol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57037/57c3ededN5a283d4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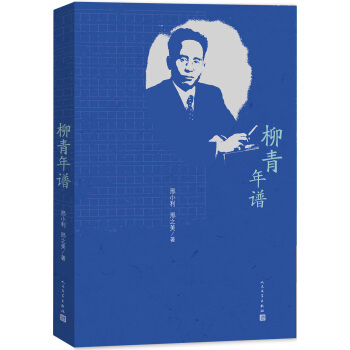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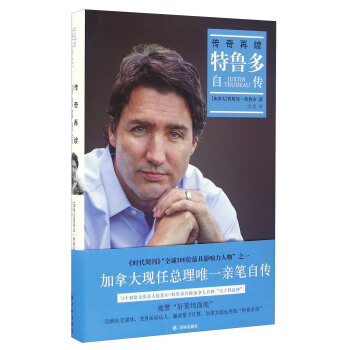


![探索者的海洋:斯托梅尔自传 [The Sea of the Beholde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20085/584bb618N078bedb0.jpg)


![发明世界的巫师:托马斯·爱迪生传 [Thomas Alva Edison: Sixty Years of An Inventor's Lif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69446/59b0ddd4N53f228c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