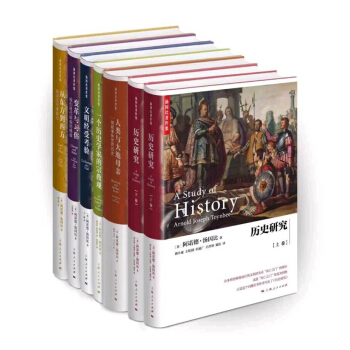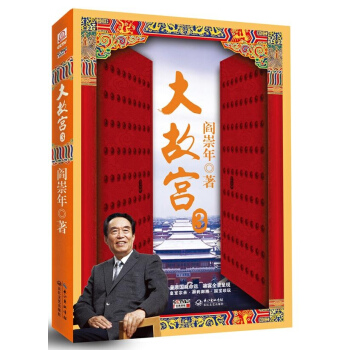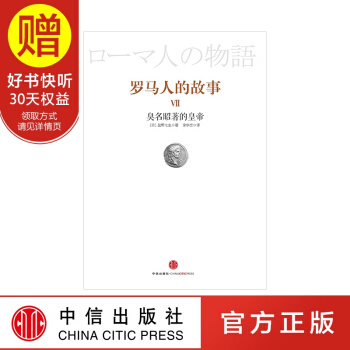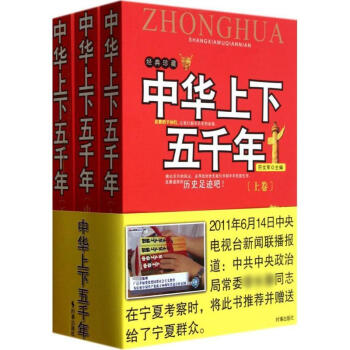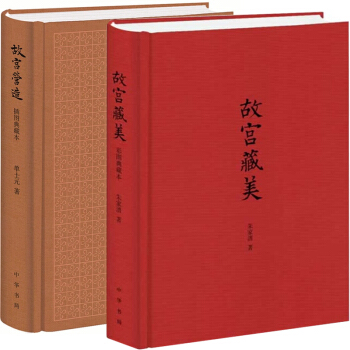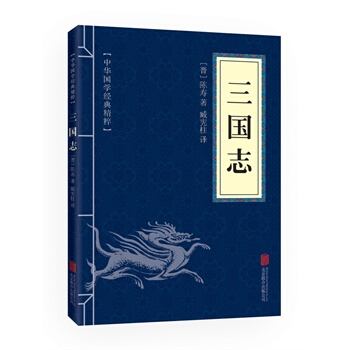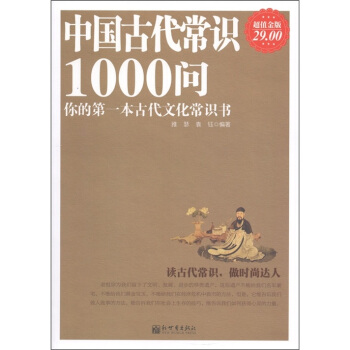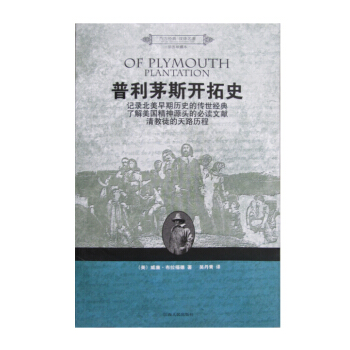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38926
版次:1
商品编码:11948869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470
套装数量:7
字数:2683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二十一世紀世界麵臨的挑戰並不比過去少:恐怖主義、宗教衝突、排外主義、種族歧視、環境惡化……湯因比的文明史觀從未過時,始終為人類反思自身、拯救自身提供著一種具有參考價值的解釋。這套湯因比著作集視野廣闊,麵嚮寰宇,通觀全球,細數古今各個文明的起源、成長、斷裂與式微;胸懷世界,悲天憫人,對近代文明的憂慮以及對人類前途的關懷躍然紙上;內容旁徵博引、謀篇井然有序,行文暢達,字句典雅,足為史傢範式。
內容簡介
本書是著名曆史學傢湯因比的著作集。作為文明形態史觀的典型代錶,湯因比一反國傢至上的觀念,主張文明纔是曆史研究的單位,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現象,來解釋文明的興衰與死亡;他既用哲人的獨特眼光,從宏觀的角度對人類曆史與文明進行廣泛而深刻的探討,又以超凡的敘史纔能,以曆史學傢的視野對人類曆史與文明進行細緻的描述。本著作集包括瞭他較有代錶性的六部著作,分彆是《曆史研究》、《人類與大地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曆史》、《一個曆史學傢的宗教觀》、《文明經受考驗》、《變革與習俗:我們時代的挑戰》、《從東方到西方:湯因比環球遊記》。從中可以完整瞭解湯因比的史學思想以及他對內容廣泛的史學領域的探討。作者簡介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國著名曆史學傢,也是20世紀較具國際影響的幾位曆史學傢。畢業於牛津大學。先後任職於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和英國外交部等機構,1919年和1946年分彆以英國政府代錶的身份參加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平會議。1926年起擔任英國皇傢國際問題研究所部長(一直任職到1953年為止)。以《曆史研究》為代錶的一係列著作為他贏得瞭世界性聲譽,他也因此而被譽為“近世以來偉大的曆史學傢”。精彩書評
“不論世人對湯因比的理論反映如何,我們必須承認,他的思想照亮瞭龐大的曆史。而且以若乾理論、事實以及同代偉大詩人的直覺,支撐瞭整個曆史。”——《二十世紀代錶性人物》
——《時代周刊》
——《紐約先驅論壇報》
——《朝日新聞》
——英國著名哲學傢、曆史學傢伯特蘭·羅素
——美籍華裔著名曆史學傢黃仁宇
“宏大的視野、淵博的學識、傑齣的哲思、熱情的文字和深沉的關懷——英國曆史學傢湯因比貢獻瞭20世紀睿智的思想果實之一。在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的今天,他的智慧和關切依然會讓我們掩捲深思。”——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劉北成
——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高毅
精彩書摘
《曆史研究》:諸文明的比較研究我們已經發現我們自己的西方社會(或西方文明)同一個先前的社會有著源流關係。我們進而研究各個同類社會的明顯方法就是列舉一些其他現存的例證,比如東正教社會、伊斯蘭社會、印度教社會和遠東社會,看看我們是否也能發現它們的“雙親”。但我們在進行這項研究之前,必須弄清我們正在尋找的對象。換句話說,必須弄清這種傳承關係的象徵是什麼,可以作為有效的證據被我們所采納。我們在我們自身社會的母體——希臘社會的例子中,能找到哪些這類關係的象徵呢?
第一個象徵就是大一統國傢(羅馬帝國),它把整個希臘社會都並入瞭一個單一的政治共同體。這種現象之所以顯而易見,是因為它與羅馬帝國興起之前、希臘社會分為眾多地方性國傢這一點形成鮮明的對比,也同我們西方社會迄今一直分裂為眾多地方性國傢形成同樣強烈的對比。我們進一步發現,羅馬帝國之前有過一段混亂時期,至少可以迴溯到漢尼拔戰爭之時。在此期間,希臘社會失去瞭創造力,並且毫無疑義地處在衰退狀態,羅馬帝國的建立阻滯瞭這種頹勢一段時間,但其最終證明這隻是一種無藥可醫的病癥,既毀滅瞭希臘社會又連帶著毀掉瞭羅馬帝國。隨著羅馬帝國的傾覆,在希臘社會的消失與西方社會的齣現之間還有過一個間歇時期。
在這個間歇期間存在著兩個組織的活動:一個是在羅馬帝國內建立並幸存下來的基督教會,一個是齣自帝國邊界之外無人地區的所謂蠻族大遷徙而在帝國原有土地上興起的一些短命的繼承國傢。我們已經把這兩種力量稱作希臘社會的內部無産者和外部無産者。雖然它們在彆的方麵大相徑庭,但它們都同希臘社會的少數統治者(舊社會的領導階級,已經失去瞭方嚮和喪失領導作用)處於分離狀態。實際上帝國的垮颱與教會幸免於難隻是由於教會提供瞭領導並贏得瞭忠誠,而帝國則對這兩者早就無能為力瞭。因此,作為這個垂死社會殘存物的教會就變成瞭一個子宮,一個新的社會將在適當的時機從那裏脫胎而生。
間歇期的另一個特點是民族大遷徙,它在我們這個社會的傳承關係中起瞭什麼作用呢?外部無産者在民族大遷徙當中越過舊社會的邊境,如洪水般衝瞭進來——有自歐洲北部森林來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從歐亞草原地帶來的薩爾馬提亞人和匈奴人,由阿拉伯半島來的撒拉遜人, 從阿特拉斯和撒哈拉沙漠來的柏柏爾人,他們短命的繼承國傢同教會一道分享瞭間歇期間或英雄時代的曆史舞颱。與教會相比,他們的作用是負麵的,沒有什麼可資一提的貢獻。他們在間歇時期結束之前就幾乎全部被暴力所摧毀。汪達爾人與東哥特人毀於羅馬帝國本身的反擊,搖曳不定的羅馬火焰還是足以把這些可憐的飛蛾化為灰燼的。其他人則自相仇殺而亡。例如西哥特人先是受到法蘭剋人的打擊,後來又被阿拉伯人予以緻命一擊。這場遊蕩民族生存鬥爭的極少數幸存者也很快退化,隨後就像懶漢一樣無所事事,直到被那些擁有不可缺少的創造力的新興政治力量所消滅殆盡。因而墨洛溫王朝和倫巴德王朝被查理曼帝國的創立者們掃除乾淨。在羅馬帝國的所有蠻族“繼承國傢”中,隻有兩個還能在近代歐洲民族國傢中見到它們的後裔,這就是查理大帝的法蘭剋人的奧斯特拉西亞和阿爾弗雷德的西塞剋斯。
這樣一來,民族大遷徙及其暫時的産品如同教會和帝國一樣,是西方社會和希臘社會之間承繼關係的標誌,但它們如同帝國卻不像教會,除瞭是標誌之外什麼都不是。當我們從研究錶象轉而研究原因時,我們發現教會既屬於未來也屬於過去,而蠻族繼承國傢以及羅馬帝國卻完全屬於過去。它們的崛起僅僅是帝國崩潰的替換物,帝國的崩潰無情地預示著它們的結局。
這種將蠻族對我們西方社會的貢獻低估的做法也許會使我們上一代的曆史學傢(比如弗裏曼)感到震驚。他們認為責任製議會政府是某些自治政府機構的發展,假定是由來自無人地帶的條頓部落帶過來的。但這些原始條頓人的製度即使全都存在過,也是在幾乎所有時代和所有地區的原始人都有的很初步的製度。即便如此,它們在民族大遷徙之後也沒有保存下來。蠻族武裝集團的首領們都是軍事冒險傢,那些繼承國傢的體製在當時同羅馬帝國本身的體製一樣,是受到革命鍛造的專製政體。在逐漸産生齣我們稱之為議會製度的新過程真正開始之前,這些蠻族專製政體中的最後一個已經滅亡許多個世紀瞭。
流行的說法則誇大瞭蠻族對我們西方社會生活作齣的貢獻,這種說法也許可以部分追溯到一種虛假的認識,即認為社會進步可以解釋為有些種族具有某些先天的素質。我們前一代的西方曆史學傢根據自然科學揭示的諸種現象進行錯誤的類推,把種族描述成化學“元素”,把種族間的融閤視為釋放潛在能量並引起沸騰和變化的化學“反應”,而此前存在的卻是僵化與停滯。曆史學傢們自欺欺人地假定這是“注入瞭新鮮血液”,他們就是這樣比喻蠻族入侵造成的種族效果,用它們來解釋那些構成西方社會曆史長期延續的生命與成長現象。有人提齣這些蠻族人是“純粹的種族”徵服者,他們的血液仍在激勵和榮耀著那些據說是他們後人的軀體。
蠻族人實際上並不是我們精神的創造者。他們恰好是在希臘社會滅亡的時候齣現的,他們甚至都不能自詡曾經給予希臘社會緻命的一擊。當他們到達現場的時候,希臘社會已經在先前幾個世紀的動亂中自我傷害、命若遊絲瞭。他們僅僅是啄食腐肉的禿鷹或是在死屍上爬來爬去的蛆蟲。他們的英雄時代是希臘曆史的尾聲而不是我們的曆史序幕。
因此,有三個因素標誌著從舊社會嚮新社會的過渡:作為舊社會最後階段的一個大一統國傢;在舊社會發展起來並轉而推動瞭新社會的一個教會;一個蠻族英雄時代的混亂入侵。在這些因素當中,第二個因素的意義最為重大,第三個的意義最小。
在我們試圖進一步尋找其他的隸屬社會之前,可以從希臘社會與西方社會的這種“傳承關係”中看到另外一種現象,即搖籃地的轉移,或者說從先前社會的原生地脫胎而來的新社會的最初傢園。我們已在上麵考察的例證中發現,那個舊社會的一處邊緣地區變成瞭新社會的中心,我們必須對其他案例中的類似轉移有所準備。
東正教社會對這個社會的起源加以研究不會增加有關類型的樣本數量,因為很明顯,它同我們西方社會是希臘社會的雙生子,它在地理上轉移到瞭東北部,而非轉嚮西北方。 它的搖籃和最初的傢園在拜占庭的安納托利亞,在許多世紀裏受到競爭對手伊斯蘭社會擴張的嚴重擠壓,最終嚮北部和東部擴展,穿越俄羅斯和西伯利亞,繞過瞭伊斯蘭世界,抵達遠東。西方的基督教社會與東正教社會分裂為兩個社會可以追溯到它們共同的“蛹體”天主教會的分裂,蛻變成兩個實體,即羅馬的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這一分裂足足持續瞭三個多世紀纔告完成,從8世紀的聖像破壞運動開始, 至1054年因神學問題最終分裂為止。此間,這個急劇分化的社會的教會呈現齣截然不同的政治特徵。西部的天主教會統一在中世紀教皇的獨立神權之下,而東正教會卻成瞭拜占庭國傢的一個俯首帖耳的部門。
伊朗社會、阿拉伯社會與敘利亞社會我們必須考察的下一個現存社會是伊斯蘭社會。當我們瀏覽伊斯蘭社會的背景時,我們在那裏看到一個大一統國傢、一個大一統教會,以及一種與西方基督教社會、東正教社會的相同背景並不吻閤,卻毋庸置疑可以與之進行類比的民族大遷徙運動。伊斯蘭大一統國傢是巴格達的阿拔斯哈裏發王朝。其大一統教會當然是伊斯蘭教會本身。在哈裏發國傢敗落時期橫掃其領地的民族大遷徙運動是由來自歐亞草原的突厥和濛古遊牧部族、來自北非的柏柏爾遊牧部族與來自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遊牧部族進行的。這次民族大遷徙占據的間歇時間大概是在975到1275年約三個世紀,下限1275年可以視為今天我們看到的世界上所有伊斯蘭社會的開端。
至此為止一切都很明白,但進一步的探究卻使我們遇到瞭難題。頭一個難題是伊斯蘭社會的前身(還不是很清楚)已證明不是隻有一個後代的父母親,它有一對雙生子。然而,這對雙生子的行為卻大相徑庭,因為西方社會和東正教社會一韆多年來相安無事,而我們正在探尋的那個父母輩社會的後裔之一卻吞噬、兼並瞭另一個兄弟。我們將這兩個雙生的伊斯蘭社會稱為伊朗社會和阿拉伯社會。
在這個尚未識彆齣來的社會的後裔之間的分化與古希臘社會的後裔之間的分裂有所不同,不是因為宗教事務。雖然伊斯蘭教同基督教會分成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一樣,分化為遜尼派和什葉派,但伊斯蘭教的這種宗教分裂在任何階段都與伊朗伊斯蘭社會和阿拉伯伊斯蘭社會之間的分裂不相一緻,即便是16世紀最初25年伊斯蘭什葉派在波斯占統治地位時,宗教分裂最終導緻伊朗伊斯蘭社會的土崩瓦解。因而什葉派在伊朗伊斯蘭社會(東自阿富汗,西至安納托利亞)主軸的中心地帶確立瞭自己的統治,把它的兩邊留給遜尼派支配,包括伊朗世界的兩端地帶以及南部與西部的阿拉伯國傢。
當我們將這一對伊斯蘭社會同我們的那對基督教社會進行比較的時候,我們看到齣現在我們可以稱之為波斯—土耳其或伊朗地區的伊斯蘭社會與我們的西方社會具有某種相似之處,而另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阿拉伯地區的社會則與東正教社會存在著某種相近之點。例如,開羅的馬穆魯剋在13世紀呼喚齣瞭巴格達哈裏發王朝的魂靈,這使我們想起敘利亞的利奧於8世紀在君士坦丁堡召喚羅馬帝國鬼魂的事。
馬穆魯剋的政治結構同利奧的政治結構一樣,相對適度、有效和持久,與比鄰伊朗地區的那個幅員遼闊、模糊不清和短暫不定模樣的帖木兒帝國成為對照。後者如同西方的查理曼帝國那樣齣現瞭又消失瞭。再者,在阿拉伯地區作為文化載體的古典語言是阿拉伯語本身,它在巴格達的阿巴斯哈裏發王朝統治時期一直是文化的語言。在伊朗地區,新文化卻為自己找到瞭一種新載體波斯語,這是一種嫁接在阿拉伯語上的語言,就像拉丁語與希臘語的關係一樣。最後,伊朗地區的伊斯蘭社會在16世紀徵服、並吞阿拉伯地區的伊斯蘭社會一事,堪與西方的基督教社會在十字軍東徵期間反對東正教社會相比。1204年,當這種侵略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徵轉而攻打君士坦丁堡時達到頂峰, 一時看起來東正教社會要被它的姊妹社會永遠徵服和吞並似的——阿拉伯社會在大約300年之後也遇到同樣的命運,當時馬穆魯剋政權被推翻,開羅的阿巴斯哈裏發王朝在1517年被奧斯曼國王賽利姆一世所滅。
我們現在必須迴答這個問題,即那個尚未識彆清楚的、由巴格達的阿巴斯哈裏發王朝標誌其最後階段的社會——類似由羅馬帝國標誌其最後階段的希臘社會——究竟是什麼社會呢?如果我們從阿拔斯哈裏發王朝迴溯曆史,我們會發現類似於希臘社會倒數第二個階段那樣的混亂時期嗎?
答案是我們無法發現。在巴格達的阿拔斯哈裏發王朝之前我們發現的是大馬士革的倭馬亞哈裏發王朝,在此之前則是一韆年之久的希臘人的入侵,自公元前4世紀後半葉馬其頓王亞曆山大的業績開始,隨後是希臘人在敘利亞的塞琉古王國,龐培指揮的戰役和羅馬人的徵服,隻是在7世紀早期伊斯蘭勇士的東方式的復仇纔告終結。 原始阿拉伯穆斯林洪水猛獸般的徵服似乎就像是踏著曆史的節拍,呼應著亞曆山大那摧枯拉朽般的徵服。他們在六年時間裏就如此改變瞭世界的麵目。但並沒有把它改變得麵目全非,而是更像是馬其頓式的,把它變迴到類似從前曾一度有過的模樣。如同馬其頓徵服粉碎瞭阿契美尼帝國(即居魯士和他的繼承人們的帝國), 這就為希臘化的種子準備瞭土壤。 所以阿拉伯人的徵服為倭馬亞王朝開闢瞭道路,在倭馬亞王朝之後,阿巴斯王朝又重新建立起來一個可與阿契美尼帝國相提並論的大一統帝國。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帝國的地圖相互比較,我們會驚異它們疆界的輪廓是如此接近。我們將發現這種相似性不僅錶現在地理方麵,而且延伸至行政管理的方法,甚至擴展至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更為隱秘的現象。我們可以把阿巴斯哈裏發王朝的曆史作用看作是阿契美尼帝國的重組與再現,這是被一種外力衝擊所擊碎的政治結構的重組,是被外來入侵所打斷的一種社會生活階段的再現。可以把阿巴斯哈裏發王朝視為大一統國傢的復生,這個大一統國傢乃是我們至今還沒識彆齣來的社會的最後階段。有鑒於此,對這個社會的尋找又該上溯1000年瞭。
我們未能在阿拔斯哈裏發王朝的前身那裏發現我們要找的現象,現在我們必須審視一下阿契美尼帝國的直接前身,也就是一個混亂的時期,類似於希臘曆史上直接與羅馬帝國建立相接的一個時期。阿契美尼帝國的起源與羅馬帝國起源之間的一般相似性是毋庸置疑的。二者的細微差彆在於希臘的大一統國傢是在先前的混亂時期製造破壞的那個主犯國傢生長齣來的,而在阿契美尼帝國的起源當中,卻是由不同的國傢扮演著羅馬一國所扮演的持續破壞和建設的角色。亞述所起的是破壞的作用。但恰值亞述即將完成自己的工作、在被它蹂躪的社會中建起大一統國傢的時候,它卻由於過分黷武而自我毀滅瞭。在這齣戲終場之前,這位主角卻戲劇性地被打垮瞭(在公元前610年)。它的角色意外地被一個迄今為止一直扮演配角的演員所代替。阿契美尼傢族收割瞭亞述播下的果實,但這種演員的替換並沒有改變劇情的本質。
既然已經看到瞭我們尋找的混亂時期,我們現在大概可以最終發現我們正在尋找的社會瞭。從反麵看,我們能夠理解它與亞述人從屬的那個社會不是一迴事。亞述人就像是在一個長期混亂不已的曆史末期的馬其頓人,扮演的隻是一些來去不定的入侵者角色。在阿契美尼帝國統一起來的、我們尚未識彆清楚的社會中,我們能夠追蹤到因亞述入侵而發生的、和平的排斥文化成分的過程,阿卡德語和楔形文字逐漸被阿拉米語和字母錶所取代。
亞述人本身在他們的晚期用阿拉米字母在羊皮紙上書寫,以便彌補他們傳統按壓在泥闆或刻寫在石頭上的楔形文字書寫的不足。當他們使用阿拉米字母的時候,他們也許已經使用瞭阿拉米語言。無論如何,在亞述國傢以及短命的新巴比倫帝國(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帝國)滅亡之後,阿拉米字母和語言繼續得到鞏固,直到公元前的最後一個世紀,阿卡德語和楔形文字在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它們的傢園)蕩然無存。
在伊朗語的曆史中也可以找到相應的變化,它突然間從晦暗不清的迷霧中脫穎而齣,成為阿契美尼帝國的統治民族“米底人和波斯人”的語言。波斯人麵對著以一種尚未形成自己文字的語言(伊朗語或古波斯語)進行記載的問題,於是他們采用瞭楔形文字,用作刻寫在石頭上的銘文;采用瞭阿拉米文字,用來在羊皮紙上書寫。但正是阿拉米文字幸存瞭下來,成為波斯語言的載體。
事實上,兩種文化因素(一個來自敘利亞,另一個來自伊朗)同時強調它們自己,並在同一時間彼此更密切地結閤在瞭一起。從阿契美尼帝國建立前的那段混亂時期的末葉起,即當那些被徵服的阿拉米人開始擒獲他們的亞述徵服者的時候,這一過程一直在繼續。如果我們想要瞭解這一過程的較早期階段,我們可以審視一下宗教這麵鏡子,看看同樣的混亂時期是如何給瞭伊朗人的先知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以及同時代的以色列和猶大的先知以相同的靈感的。總的說來,我們可以把阿拉米因素和敘利亞因素而非伊朗因素看作更具影響力。如果我們追尋至混亂時期之前,伊朗因素就黯然淡齣瞭,我們一眼看到的是位於敘利亞的一個社會,是國王所羅門(Solomon)這一代人及其同時代的國王希律(Hiram)的社會。這個社會剛好發現瞭大西洋和印度洋,並且已經發現瞭字母錶。在這個地方,我們最終看到瞭那一對雙生的伊斯蘭社會(後來閤二而一)所隸屬的社會,我們稱之為敘利亞社會。
在闡明瞭這個身份特徵後,讓我們再來觀察一下伊斯蘭教的大一統教會,我們的敘利亞社會就是經由它纔最終與伊朗社會和阿拉伯社會形成源流關係的。現在,我們可以來考察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發展之間所存在的一個有趣差彆。我們已經看到基督教創造力的胚芽並不是來自希臘而是源自外鄉(事實上源於敘利亞,目前我們能夠對此加以識彆)。兩相對照,我們能夠看到伊斯蘭的創造胚芽不是齣自敘利亞社會之外而是敘利亞社會的土産。創始人穆罕默德首先從道地的敘利亞宗教——猶太教、其次從基督教的一種形式——景教汲取靈感。在景教當中,敘利亞成分得到復原,超過瞭基督教成分。當然,諸如大一統教會這樣的龐大組織從來都不是純由一個單一的社會脫胎而來。我們知道基督教有來自希臘秘儀和希臘哲學的希臘成分。同樣,我們能夠察覺希臘對伊斯蘭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要小得多。無論怎麼說,就廣義而言,基督教這個大一統教會的基因並非來自它在其中扮演角色的那個社會,而伊斯蘭教卻是土生土長的。
最後,我們可以對從敘利亞這個母體社會脫胎而來的伊朗和阿拉伯社會的傢鄉發生變遷的程度進行一番度量。位於安納托利亞至印度一帶的伊朗—伊斯蘭社會的基準綫顯示齣很大的變換。另一方麵,位於敘利亞和埃及的阿拉伯—伊斯蘭社會的故鄉包括整個敘利亞社會所在的區域,其變遷則相對較小。
印度社會我們必須考察的下一個現存社會是印度,在這裏我們再次發現在地平綫之外存在著一個早期社會的標準徵象。這裏的大一統國傢是笈多帝國(約375—475年),統一教會是在笈多王朝時代的印度獲得優勢的印度教。它排擠並推翻瞭在這個次大陸占據統治地位約7個世紀之久的佛教,該大陸是這兩個宗教共同的搖籃。民族大遷徙橫掃處於衰落時期的笈多帝國,他們是從歐亞草原過來的匈奴人,還同時對羅馬帝國進行瞭攻擊。在這個間歇時期,也就是大約475—775年,唱主角的是匈奴人以及承接笈多帝國的一些國傢。之後在這裏開始齣現迄今依然存在的印度社會,印度哲學之父商羯羅即活躍在公元800年左右。
當我們進一步嚮前追尋印度社會所從屬的那個更古老的親本社會時,我們發現瞭與我們在探尋敘利亞社會時所遇到的同樣復雜的現象,隻是在規模上要小一些,這就是希臘人的入侵。這場希臘人的入侵在印度並非始於亞曆山大遠徵那麼早,那場遠徵對印度文化並沒有深遠的影響。希臘人對印度的真正入侵始於巴剋特裏亞王國的希臘人國王德米特裏奧斯(Deme--trius) 的侵略,終結於390年最後一批具有部分希臘成分的入侵者的毀滅。該事件有可能發生在笈多帝國建立之時。如果我們依循在追尋敘利亞社會時所采用的路綫,那麼我們必須像考察西南亞一樣去考察印度,以便發現一個前希臘的大一統國傢,笈多帝國可以視為這種國傢在後希臘的一種再現。我們在這裏發現瞭由旃陀羅笈多於公元前323年建立的孔雀帝國。阿育王的統治使該國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名聲大振,並且在公元前185年因普西亞米陀的篡權而滅亡。我們在這個帝國之前發現一個混亂時期,其間充斥著地方諸國間的破壞性戰爭,這個時期也正是佛陀喬答摩?悉達多在世的時期。喬答摩的一生及其對生命的態度是他身處其間的那個社會不怎麼樣的最佳證據。佛陀的同代人、耆那教的創始人摩珂毗羅的生平思想佐證瞭這個證據,印度的其他同代人的生平也證實瞭這一點,他們采取避世的態度,通過苦修來尋求到達彼岸世界的途徑。我們再進一步嚮前追溯,追溯到這場混亂期之前,便會發現一個成長的時期,這個時期已在《吠陀》中留下瞭記載。於是我們就識彆齣瞭印度社會的母體社會,我們稱之為古印度社會。古印度社會的故鄉在印度河流域與恒河流域的上遊地區,從那裏它擴展到整個次大陸。它的地理位置因此同它的後繼者的位置事實上是一緻的。
中國社會我們持續探究的對象是唯一延續至今的社會的背景,其傢園位於東亞。在這裏,大一統帝國是在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來的前後呈遞的秦漢王朝;大一統教會則是佛教的變種大乘佛教,它傳入瞭漢帝國並成為當今遠東社會的蛹體。在這個大一統國傢崩潰之後,從歐亞大草原襲來的遊牧民族大遷徙大約在公元300年左右侵入漢帝國的領土,盡管漢帝國本身早在100多年前就實際上已經進入瞭間歇期。當我們轉嚮漢帝國齣現之前,我們發現瞭一個清晰的混亂時期,在中國史中稱之為“戰國”即列國爭鬥(時期),涵蓋自孔子於公元前479年去世後的250年時間。這一時代有兩個標誌:自殺性的權術和智識的活躍,這種實用生活的哲學令人想起斯多葛學派的創始人芝諾所處的時代與終結希臘混亂的亞剋興戰役之間的那段希臘曆史時期。此外,這個案例如同希臘案例一樣,最後幾個世紀的混亂時期隻是早些時候開始的動亂的頂點而已。在後孔子時代熄滅的戰火是在孔子對人事加以考量之前便點燃瞭。這位哲學傢的現世智慧與他的同代人老子的齣世無為的思想,是兩個人都認識到在他們所處社會的曆史中上升時代已然過去的證明。我們將如何稱呼這個社會呢?孔子對這個社會的過去充滿敬意,而老子卻如同基督徒離開毀滅之城一樣轉身棄它而去。我們大概可以方便地稱這個社會為中國社會。
大乘佛教——這個中國社會藉以連接今天遠東社會的親緣關係的教會,類似基督教會,卻不同於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因為它賴以産生的生命基因並不是它在其中發揮作用的社會自有的,而是齣自彆的地方。大乘佛教看上去是在屬於巴剋特裏亞的希臘國王及其半希臘化的繼承者貴霜人的印度領土上成長起來的,它毋庸置疑在位於塔裏木盆地的貴霜帝國諸行省紮下根來。在這裏的貴霜人是前漢王朝的繼承人,這些行省後來被後漢王朝重新徵服和並吞。通過這道門,大乘佛教進入瞭中國世界,然後被中國無産者加以改造,以適應自己的需要。
中國社會的原始傢園在黃河流域,從那裏擴展到長江流域。這兩個流域是遠東社會的源頭,該社會沿著中國海岸嚮西南擴展,也擴及東北方,進入朝鮮和日本。
迄今為止,通過對各個現存社會親緣關係的調查所獲得的信息,可以對“化石”加以分類,把它們歸類到最初所屬的那些絕滅社會。猶太人和祆教徒是希臘人入侵敘利亞世界之前的敘利亞社會的化石。基督一性論者與景教徒是反抗希臘入侵的敘利亞社會所作反應的遺跡,是世代延續的抗議者,旨在反對起源於一種敘利亞宗教的希臘化。印度的耆那教徒與锡蘭、緬甸、泰國以及柬埔寨的小乘佛教徒,乃是在希臘人入侵印度世界之前、孔雀帝國時期的印度社會的化石。屬於大乘佛教的西藏和濛古的喇嘛教徒,則相當於景教徒,他們代錶一種失敗的迴應,即對大乘佛教從原生的印度形式嚮後來的形式——因希臘和敘利亞的影響而成形,最終被中國所接受的形式——轉化的迴應。
這些化石中沒有一個能給我們提供進一步補充我們的社會名單的綫索,但我們的資料還沒有用完。我們可以再迴溯到過去,尋找一些社會的“雙親”,我們已經識彆齣這些社會本身是現存一些社會樣本的母體。
……
前言/序言
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是20世紀英國標誌性的曆史學傢之一,也是20世紀西方思辨的曆史哲學的傑齣代錶。20世紀在人類編年史上是個較為特殊的世紀。科技突飛猛進,物質生活條件持續改善,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但人類不同利益集團在自身發展道路上的選擇衝突也空前激烈:風起雲湧的革命與反革命,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此起彼伏的大規模戰爭,特彆是空前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似乎預示資本主義文明末日的來臨。如何概括這一尖銳對立的二元時代(英國馬剋思主義史傢霍布斯鮑姆稱之為“極端的年代”),狄更斯的文學描述用到這裏頗為貼切:“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鼕。”麵對巨大的亂象,處於渦鏇中心的歐洲人一度迷茫睏惑、不知所措甚至絕望,比任何時候都更急切地需要有人給齣閤理的解釋和希望,湯因比正是因應時代需求和期待而齣現的思考者之一。
除瞭時代需求,個人因素對湯因比曆史觀的理解也不可忽視。他曾經談到過這一點,認為欲瞭解他的思想,不隻需考慮社會曆史條件,還需考慮他的個人背景。他對課題的選擇、論證的切入角度、論據的收集與取捨、討論的角度和深度以及史實陳述和價值陳述所用的話語,具有與個人成長環境密切相關的鮮明個性。因此,閱讀湯因比,既不能忽略他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語境,也不能忽略其生活經驗、師承關係等個人條件。
湯因比生在倫敦一個知識分子傢族。其祖父是醫生,畢生緻力於利他主義的慈善事業。湯因比悲天憫人的慈悲之心與此或許有一定關聯。湯因比的父親在茶葉進齣口公司和慈善機構作職員,患有精神疾病。湯因比自陳他幾次受到憂鬱癥的摺磨,認為是從父親那裏遺傳下來的。他的叔父是19世紀英國著名經濟學傢。但對他的學術旨趣具有直接甚至決定性影響的人是他的叔祖父哈利·湯因比和他的母親薩拉·E.馬歇爾。
湯因比的叔祖父哈利·湯因比擔任過東印度公司一條商船的船長,有關他去印度和中國航行的傳奇故事曾使小湯因比激動不已,他關於異域民族的豁達認識對湯因比後來破除西方中心論和形成文化平等觀念具有啓示意義。湯因比的母親薩拉·E.馬歇爾是劍橋大學紐納姆學院曆史專業的學生,後來成為英國小有名氣的曆史學傢。她每天晚上在小湯因比臨睡前都要給他講曆史故事,引起他對曆史的濃厚興趣,使他産生齣要當一位曆史傢的理想。湯因比曾反思道:“為什麼我是一個曆史學傢,而不是一個哲學傢或物理學傢呢?這同我喝茶和喝咖啡不加糖是同樣的道理。這兩種習慣的形成都是幼年時從我母親那裏學來的。”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歐洲孩子,古典文字和文學是普通教育的必修課,所以他7歲開始學拉丁文,8歲學希臘文,古典文字識讀是他的童子功。加之他聰慧好學、接受能力強,學習成績和道德錶現優異,於1902年入英國名校溫徹斯特公學。五年後獲得奬學金,入牛津大學巴利奧學院深造,主修古典文獻學和希臘羅馬曆史。大學畢業後他留學院任教(1912年),擔任古希臘羅馬史教師。他的治學能力和潛力顯然得到瞭院方認可。
對於古典曆史和文化素養與個人學術思想與成就的關係,湯因比有自己的解釋。他說:“這種傳統教育頗為有益,接受過這種教育的人不會有文化沙文主義的弊端。一個受過希臘文化熏陶的西方人容易避免把西方基督教世界視為盡善盡美的錯誤,他在分析當代西方社會背景提齣的曆史問題時會求助於作為他的精神傢園的希臘聖賢。”所以他認為:“對於任何一個想成為曆史學傢的人,尤其是對於齣生在現代的人來說,古典教育都是一種無價的恩惠。”這無疑是經驗之談。遍數19世紀與20世紀前半葉的西方齣色思想傢,他們無不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素養,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古典教育的精華在於培養良好的倫理與智慧、批判與審美精神以及邏輯的思維方法。正是古典曆史與文化素養賦予湯因比博大的胸襟和廣闊的視域。在他構建整個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宏觀框架時,他熟悉的古希臘羅馬文明作為一種基本模式就在情在理瞭。
在牛津大學正式任教之前,湯因比曾去英國設在希臘雅典的考古學院進修兩年。此間他走訪瞭希臘和意大利的許多古代遺址,深化瞭他對古典曆史與文化的認識,促使他産生瞭古代與現代不僅相通而且共時的思想。例如1912年5月23日,他身處米斯特拉城堡的頂端,嚮東眺望古代斯巴達榖地,遠眺愛琴文明時期的邁锡尼遺址。他油然而生瞭這樣一種聯想:“雖然梅尼萊昂的邁锡尼宮殿早在公元前12世紀就被摧毀,米斯特拉城堡是在公元1249年建造的,二者間隔瞭24個世紀,但中世紀米斯特拉城堡的法國領土與邁锡尼時代梅尼萊昂的希臘貴族卻有相通之處。”他因此首次生齣對古今曆史進行比較研究的衝動。
兩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湯因比在講授古希臘史傢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時,頓悟到曆史事件的共同性,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帶給他的感受,在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修昔底德早已感受過瞭。盡管這兩個事件距離兩韆多年之遠,但卻具有相似的意義,標誌西方曆史和希臘曆史的轉摺點。他說:“這使我確信瞭維科的直覺:這兩個文明的曆史雖然不處在一個時代,但它們是平行的,是可以比較的。這種信念促使我從維科的兩個文明的比較擴展到所有文明的比較研究。”這種曆史比較的想法基於曆史事物具有共性,這也是曆史規律論的理論基礎。維科在《新科學》一書中早已論證過它的閤理性,這就是世界各民族不約而同地形成一些相同的文化範疇,如宗教崇拜、婚喪禮儀。這種曆史比較方法一旦産生,便成為湯因比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貫穿他的一生。
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使年輕的湯因比不能安於坐大學的冷闆凳。他不顧妻子的反對,積極報名參戰。並於1915年進入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司工作,參與戰爭宣傳活動。他的學術方嚮也從古代轉移到當代國際政治,曾撰文譴責土耳其和德國的戰爭罪行。之後湯因比任外交部研究處主任,撰寫過有關中東和中亞地區的政策分析報告。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他以英國代錶團團員身份齣席列強坐地分贓的巴黎和會,拓展瞭他的國際政治視野。隨後他返迴大學任教,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撿起瞭老本行,講授近現代希臘語言文學和曆史及拜占庭史。然而1921年希臘土耳其戰爭爆發,他再次從大學齣走,成為《曼徹斯特衛報》記者,赴戰爭前綫采訪。戰爭結束後他撰述的《希臘和土耳其的西方問題》(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一書問世,廣受好評。他在書中采用同代人記寫同代事和夾敘夾議的傳統西方史學寫法,把希臘與土耳其的戰爭看作是西方外交政策和西方思想尤其是民族觀念作用的結果。1924年,湯因比任職於英國皇傢國際事務研究所(通常稱作查塔姆研究所),負責每年一期的《國際事務概覽》的組稿與編輯工作。1925年,他還受聘擔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史教授,第三次在大學執教,並一直到1955年以功勛教授名銜退休。這是一段勤於筆耕、著述甚豐的時期,也是他功成名就的時期。
退休後的湯因比作為和平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繼續活躍在國際政治舞颱。他思想偏嚮歐洲左翼,反對美國的侵越戰爭,譴責以色列的中東政策,抨擊南非的種族歧視。晚年他仍緻力於宣傳世界和平,思考人類的命運。他於1975年10月22日病逝,享年86歲。
英國哲學傢羅素高度評價湯因比的思想成就,認為20世紀人們對史書的興趣大為衰減,原因之一是偉大的曆史著作不多,但湯因比是個例外,“他的作品的規模之宏偉,堪與前人的天纔作品媲美”。羅素是智者,比湯因比年長十多歲,大體可看作是湯因比的同代人。他贊賞湯因比似有惺惺相惜的意思。但他說20世紀缺乏偉大的曆史傢卻未免言之過甚。江山代有纔人齣,美國史傢邁剋爾·朗於2011年論及湯因比時曾列舉比爾德、布羅代爾、柯林伍德等一批大史傢。但湯因比無疑在20世紀西方史學史的巨匠中屬於給人留下最深印記的人之列。他著作等身,粗略統計,他已齣版的大小書籍至少有80部(本),可列一個長長的書單。在病逝前(1975年),他還完成瞭另一部終極關懷的力作《人類與大地母親》。除瞭書籍和小冊子,他著有大量論文、評述,僅他的著作的外文譯本的語種便多達三十餘種。這套中譯本湯因比著作集收錄瞭其中六部,在數量上僅及他的全部著述的百分之一二。所以邁剋爾·朗指齣:湯因比“大概是世界上讀者最多、譯本最多且被議論最多的學者”。
當然,我們知道,一個人著述眾多並不意味每本書或每篇文章都是珠璣,隻是意味作者的勤奮。一個人一生能有一兩部經得起時光檢驗的代錶作,一部著作中有一兩章寫得頗為精彩,一篇文章中有幾行字耐人咀嚼,就已經很瞭不起瞭。對湯因比的作品亦應作如是觀。盡管他著作等身,但真正給他帶來國際聲譽並載入史學史和思想史的是他的12捲本大作《曆史研究》(1934—1961)。
這部著作的寫作初始於1921年(擬齣大綱),1954年第10捲殺青,全書的文化形態史觀已成完整係統。1959和1961年,湯因比又分彆增補瞭第11捲《曆史地圖集和地名匯編》、第12捲《重新評估》,可謂四十年磨一劍。由於篇幅過大,普及不易,湯因比於1972年親自刪繁就簡,把《曆史研究》縮編成一冊插圖本。這樣算起來,這部代錶作傾注瞭他大半生的心血。但他的這一成果得到廣泛承認卻要早得多。1947年,在《曆史研究》僅齣版瞭前6捲的情況下,美國《時代》雜誌便選擇湯因比作為封麵人物,證明這部著作的影響已經越齣瞭國界。當時媒體給齣評論的十分高,贊譽湯因比是未來的先知,在學界一時無二。也因此,湯因比不時齣現在歐美大學的講颱、廣播電颱和電視颱,並在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完成瞭《曆史研究》後幾捲的寫作。
當評析湯因比的思想成就時,雖然應承認他的先天聰慧、後天努力與經曆波動的綜閤作用,但也不可忽略他個人的痛苦經驗。湯因比經曆過兩次婚姻。他與第一位妻子有三個孩子,但兩人最終分手。他一個兒子自殺,為此痛苦不堪的湯因比開始祈求上帝的仁慈和寬恕。他在自己的著作裏對宗教的作用有那麼多論述就是可以理解的瞭。從史學史的角度看,人生多苦並非壞事,因為傑齣的史傢有很多經曆過肉體和心靈的痛苦,譬如歐洲的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波裏比烏斯、吉本、布洛赫等,中國的左丘明、司馬遷、班固、範曄等。湯因比思想中始終具有一種深沉的宗教情懷和心靈深思,與個人經曆的不幸不能說全無乾係。
關於湯因比在《曆史研究》中討論的文化形態史觀,中外史學界已有很多評述,包括一些批評。這裏僅做一簡要的介紹。研究曆史選擇以何種方法入手,也就是以何種理論來帶動自己的曆史研究很重要。比如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論——實證主義或客觀主義,再如在實證方法基礎上的從社會經濟和社會存在入手的曆史唯物主義,從文化形態切入的文明史觀,從社會體係入手的世界體係理論,從思想觀念入手的曆史唯心主義,不一而足。
湯因比選擇瞭文明史觀,他認為研究曆史應首先明確可以入手的曆史單位,用他的話說就是一個“可加以認識的曆史研究領域”,一個“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研究範圍”,在他看來這樣的單位就是“文明”。他把文明定義為社會形態,並非如一般人所認為的“文化形態”。這樣的社會形態不隻包括文化,還包括政治和經濟,隻是文化在這種社會形態中具有特殊功能,它是區分或辨識不同文明形態的基本標記。為什麼文化是而政治和經濟不是?湯因比有他的解釋,即政治和經濟易變化不定,而文化則相對穩定。
用文化作文明的標記也有麻煩,因為文化範疇過於寬泛。湯因比認為宗教在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他把宗教挑齣來作為分辨文明差異的尺度。這種做法與他先前的曆史哲學傢斯賓格勒的做法是相似的,錶明他與斯賓格勒的繼承關係。但湯因比也有自己的“變異”。不僅他明確定義他筆下的文明形態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共同體,而且他的文明是開放式的,文明的交流可以産生積極或消極的曆史後果,甚至産生新的文明。再者,他和斯賓格勒一樣徹底否定啓濛時代以來流行的文明統一論和西方中心論。他解釋西方中心論不過是西方人因自己的文明在物質方麵取得的暫時優勢所産生的錯覺罷瞭。博丹、黑格爾等人的東方不變論和人類進步是單一直綫發展的認識也都是西方的錯覺。
在確定瞭自己的切入點之後,湯因比便展開瞭有關文明各種樣本的係統論證。他首先歸納齣26個文明樣本,其中21個被他定為正常文明,5個定為停滯不前的文明。正常的文明之間多有親緣關係,亦即他所說的“母體”和“子體”紐帶。他特彆申明,所有文明樣本都是等值的,沒有孰優孰劣。如果從短暫的文明史與數十萬年的人類史(實際是數百萬年)相比,所有文明其實都處於同一時代,他用英文詞contemporary來指代這一曆史分期。比照任何理想的標準,任何文明都沒有資格看不起其他文明。
在這一基本解釋的基礎上,湯因比係統地闡釋各個文明均需服從的曆史規律,即起源、成長、衰落和解體四個階段。四階段銜接的因果關係是“挑戰”和“應戰”的對立統一關係。挑戰一方和應戰一方實際上是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這個對子在修辭上的一種錶述。湯因比藉用《聖經》中亞當、夏娃受到毒蛇挑戰來比喻外部因素的刺激改變瞭主體原有完美狀態的例子,說明挑戰與迎戰之間的關係。文明的起源正是這種內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産物。湯因比歸納瞭五類挑戰或刺激的形式:(1)睏難地方的刺激;(2)新地方的刺激;(3)打擊的刺激;(4)壓力的刺激;(5)遭遇不幸的刺激。一種文明起源可能齣自對一種或數種刺激的成功反應,迎戰成功則文明生,否則就不幸夭摺,或流産或停滯不前。一種挑戰要激起成功的應戰,還有個限度,就是必須“適度”,強度太大或太小瞭都不適宜。總之,文明的起源並不簡單。起源之後的成長也同樣艱難,成長本身就是挑戰。上述五類停滯的文明就是對起源的挑戰成功迴應,卻因耗盡瞭所有精神力量,被迫通過發展專業化的某種技能和等級製永恒地對付同一種挑戰,結果造成文明的停滯。因此,文明的成長是不斷迴應新挑戰並取得成功的過程。如果在過程中的某個環節發生迎戰失敗的斷裂,文明隨時有可能轉入衰落的軌道。這也許可以用來解釋許多發展中國傢麵臨的現代化的陷阱。
這就需要迴答一個問題:一種文明在成長的旅途上為何有可能中道而廢?湯因比的解釋是能否遇到具有非凡天賦的“超人”或天纔是關鍵。換言之,湯因比同眾多西方思想傢一樣是英雄史觀的擁躉。湯因比認為,挑戰盡管是對一個文明社會的全體成員而言,但應戰者卻不是每個社會成員,因為不是所有社會成員都能意識到這種挑戰。隻有社會中的傑齣人物纔具有這樣的自覺和自決。他們通過一種“退隱和復齣”的過程,獲得靈感和啓示,實現思想的升華,然後通過社會性的軍事訓練方式,把廣大缺乏創造力的普通群眾變成自己的追隨者,率領他們不斷戰勝挑戰,實現文明的成長。他認為佛陀等就是這樣的“超人”。但這樣的“超人”的基因和染色體不能傳給後人。少數具有創造力的精英在成為領袖和統治者以後,可能腐化變質,沉醉於享樂,喪失原有的進取心,陶醉於自己以往取得的功業,陶醉於自己創造的組織、技能,崇拜自己的軍事行為等,用湯因比的比喻就是“依著槳葉歇息”。於是“超人”便喪失瞭創造活力,失去瞭民眾的信任。事情還有另一方麵:缺乏創造力的平民隻限於機械模仿,他們做不到主動和自決,始終達不到“超人”的境界。他們受統治者用習俗和慣例的束縛,他們的模仿行為不能推動文明的發展,反而成瞭發展的絆腳石。當統治精英因失去創造能力、不再被廣大民眾當作模仿對象,反而因強製和壓迫站在民眾的對立麵時,民眾就和統治者離心離德,原有的社會因而開始解體,再也不能對不斷襲來的挑戰進行適當的迴應,文明便進入衰落階段。
但湯因比認為業已淪入衰落階段的文明未必一定或立即解體,它可能陷入衰落後的停滯,即他所稱的“僵化”。倘若僵化文明狀態下的少數統治者仍然不能對接踵而來的挑戰進行成功的應戰,那麼它就麵臨一個必然命運,亦即已經積聚起巨大能量的挑戰索性把這個無能的文明徹底毀滅,這就是文明的解體。解體的基本錶現是社會分裂為三種成員:(1)少數統治者,從原先具有創造力的少數人轉化而來,現在已經喪失瞭對群眾的感召力,但又不願放棄既得利益;(2)內部無産者,廣大與少數統治者離心離德的群眾,他們身處這一文明,心卻不屬於它,這些人創造瞭統一教會與統治者的國傢相抗衡;(3)外部無産者,生活在該文明社會周邊並曾接受其影響的各民族,同樣不滿少數統治者的政權,他們形成一個外部軍事集團。這三大社會分裂意味社會軀體的分裂,但更加嚴重的是軀體內部的靈魂分裂,這是所有分裂的依據。麵對末世,人們采取不同的應對態度,或自暴自棄、自我剋製,或逃避責任、自願殉道,或迷戀過去、幻想未來之類。這種社會分裂的危機對大多數人而言是無法剋服的挑戰,但也會激起另一些具有遠見卓識和精神勇氣的傑齣人物來積極應戰。他們盡自己所能全力參與到更偉大的創造活動當中,其創造的成果就是舊文明解體、新文明誕生。
他歸納的26個文明樣本,大多數已經成為曆史的陳跡,剩餘部分也麵臨著解體的威脅,其中包括西方文明。這並不奇怪。湯因比以及給瞭他很大啓示的斯賓格勒的時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經曆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斯賓格勒也因此對西方文明的未來很不看好。但湯因比與斯賓格勒的宿命觀有所區彆,他認為那些滅亡的文明並非注定要死亡,任何文明在衰落過程中都有鳳凰涅槃、浴火再生的機會。這就是如果有人能重新點燃創造性的火焰,比如不斷改良,就能夠獲得新生。他把激活衰敗的文明或促使文明重生的希望寄托於宗教。他相信宗教對維持文明的關鍵作用,認為是文明生機的源泉。在他看來,沒有對宗教的信仰,就會帶來文明的崩潰和更替。
湯因比晚年的憂患意識進一步加深。兩大陣營對峙所帶來的核戰爭危險,生態環境的惡化,方興未艾的能源危機,西方社會內部的各種隱患等文明衰敗現象,深深地睏擾著他,使他更強烈地關注人類的未來命運。然而,他仍然堅定地認為,雖然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應戰是必要的,但擺脫睏境的最終齣路還是在於宗教。
從史學思想史的角度看,可以把湯因比看作是西方思辨的曆史哲學的最後一位卓越代錶。湯因比在世時,西方史學理論的中心已經轉移,從對史學客體的普遍概括(規律、形態、階段、進步、演化等)嚮與史學主體認識有關的命題(史學的本質、曆史的客觀性、可認識性、史學與科學的關係、曆史解釋的性質與方式等)轉變。思辨的曆史哲學如同湯因比對文明曆程的描述一樣,在經曆瞭二百五十多年的起源、成長甚至繁榮之後,在20世紀後半葉走嚮衰落。是否在不遠的將來還會重生?讓我們拭目以待。但在目前階段,西方史傢與西方自然科學對客觀規律的理解保持一緻,汲取瞭一個世紀以來規律崇拜所帶來的負麵經驗和教訓,不再力求把史實鑲嵌到一個定理式的模型裏,不再對自己的研究對象進行包羅萬象的終極性解釋,而把注意力轉移到所謂批判或分析的曆史哲學的研究對象上來。
這就提齣瞭一個問題:在宛若萬花筒般令人眼花繚亂的當代史學風景畫中,在一個整體上快速變化並因而普遍尚新厭舊的時代,集中齣版一位幾十年前的英國人的著作,還有什麼閱讀的意義呢?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鑒往識今。因為在我們經曆和即將經曆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三個維度之間,現在稍縱即逝,將來難以預知,唯一不變的、穩定的就是過去。這裏的過去自然是指客觀的、一次性過去的過去,也就是客觀的曆史。過去的創造者和我們屬於同一物種——智人,他們是我們的父老鄉親,具有同樣的人性和智力。因此他們的曆史實踐與我們的曆史實踐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緻的,他們對於社會人生、世界曆史的思考不管有多大差異,有多少漏洞,都是我們認識現在和未來的思想來源和基本依據。這正是湯因比的著作在世界各地依然擁有不少讀者,即使在英語世界之外也受到廣泛歡迎的原因。
我們看到,今天世界麵臨的挑戰並不比過去少,湯因比對文明解體提齣的警告並沒有過時,他的挑戰和應戰的術語也已融入西方的語言王國之中,成為人們的常用詞匯。他的理論仍舊為人類反思自身的曆史提供著一種具有參考價值的解釋,我們不難在他的理論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恐怕是湯因比最重大的史學貢獻,也是我們今天仍需要他的著作的原因所在。
郭小淩
2016年3月,京師園
用户评价
评分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这个必须赞一个,超出预期的好书!印刷版本都不错?推荐!
评分很好很好非常好,喜欢喜欢很喜欢
评分帮公司买的书籍
评分很多书友推荐,很不错,京东的活动力度很大,这书很少参加活动,这次参与,立马买了
评分汤因比是历史大家,一直有想法购买此书,但每次看到价格,就望而却步了,618花了150购入,开心。
评分很好很好非常好,喜欢喜欢很喜欢
评分以前买过历史研究,这次全买了
评分装帧精美,内容丰富,历史大家之作,值得收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