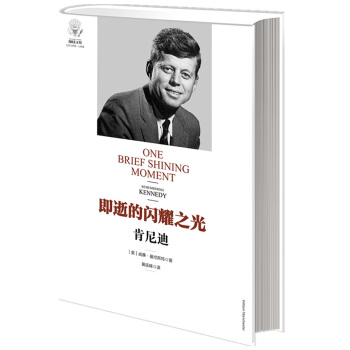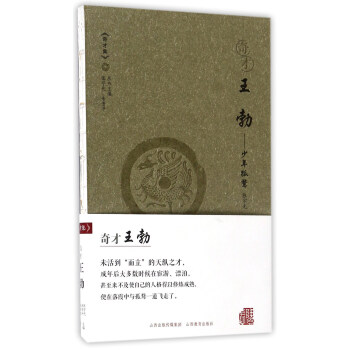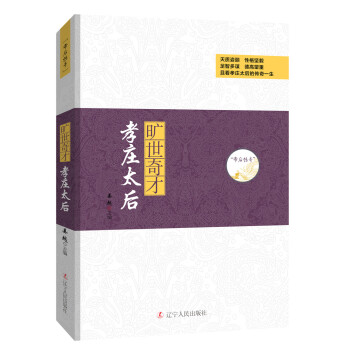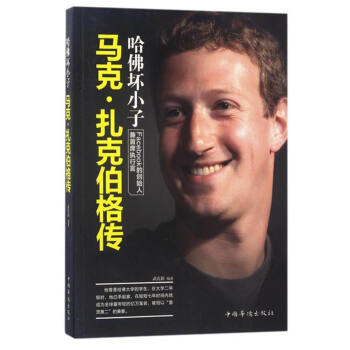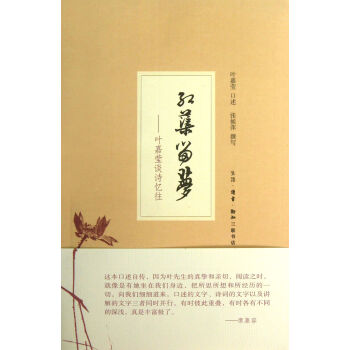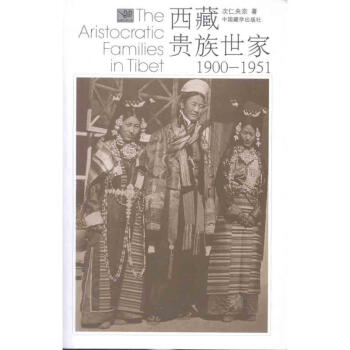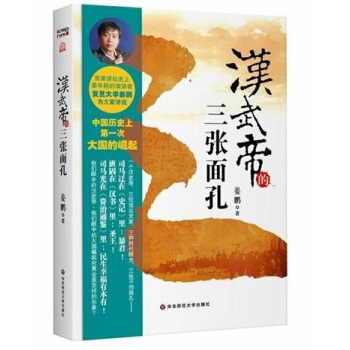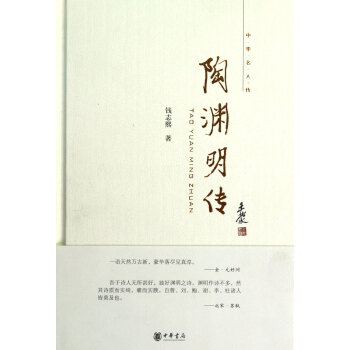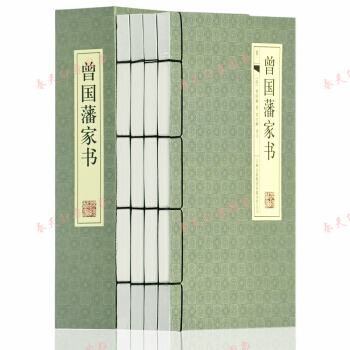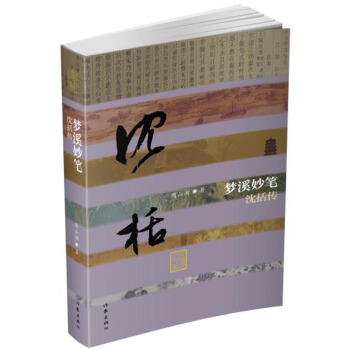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文史專傢 黨聖元
本傳展現瞭瀋括一生豐富的經曆、他的科技實踐行為以及所取得的豐厚成就,並且闡述瞭瀋括《夢溪筆談》在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方麵所具之“百科全書”的價值意義。該書對瀋括的敘寫生動,篇章和情節安排考究,對於我們瞭解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瞭解瀋括在傳統文化史上無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大有裨益。
文學專傢 李炳銀
瀋括是中國科技史上的一個奇特人物,他在水利、天文、地質、數學、建築、醫學、活字印刷等眾多領域獲得的科技成果,鑄就瞭他中國科技史上裏程碑式的地位。本傳真實追蹤瀋括的麯摺人生和創造經曆,動情深入地書寫瞭他為人剛正、為官清廉、行事用心、創造多樣、學術精絕,卻總不能容於官場,且被人無端褻瀆的精神孤獨與不幸的命運。作品敘述脈絡緊湊清晰,行文簡潔,知識豐富,頗具感染力。
內容簡介
瀋括是北宋時期的一位博物雜傢,曠世通纔,一生在水利、天文、地理、地質、數學、軍事、建築、醫學等很多領域,都有自己獨特的認識發現,其中不少為人類世界的初始發現,被英國科技史學者李約瑟認為是中國科技史上“裏程碑”式的人物,在西方科技界有很大的影響。他的代錶著作《夢溪筆談》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國自然科學、工藝技術及社會曆史現象的綜閤性筆記體著作,是他一生發現世界的思考和記錄,堪稱一部內容廣泛深入的科學發現和深入研究著作,對於後來很多科學內容的推進發生瞭積極的作用。
作者簡介
周山湖,男,1947年生於河北邯鄲。曾任山西省作傢協會大型文學雜誌《黃河》主編、山西作協影視中心主任等職。創作中長篇小說,影視劇,文化、科普類作品300餘萬字。科幻小說《人·猿·魚》獲首屆科幻文學銀牌奬,電視劇《一代廉吏於成龍》《趙樹理》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奬
精彩書評
本傳展現瞭瀋括一生豐富的經曆、他的科技實踐行為以及所取得的豐厚成就,並且闡述瞭瀋括《夢溪筆談》在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方麵所具之“百科全書”的價值意義。該書對瀋括的敘寫生動,篇章和情節安排考究,對於我們瞭解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瞭解瀋括在傳統文化史上無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大有裨益。
——文史專傢 黨聖元
瀋括是中國科技史上的一個奇特人物,他在水利、天文、地質、數學、建築、醫學、活字印刷等眾多領域獲得的科技成果,鑄就瞭他中國科技史上裏程碑式的地位。本傳真實追蹤瀋括的麯摺人生和創造經曆,動情深入地書寫瞭他為人剛正、為官清廉、行事用心、創造多樣、學術精絕,卻總不能容於官場,且被人無端褻瀆的精神孤獨與不幸的命運。作品敘述脈絡緊湊清晰,行文簡潔,知識豐富,頗具感染力。
——文學專傢 李炳銀
目錄
001??第一章/錢塘江畔奇少年
017??第二章/守孝製探微尋奇
029??第三章/治沭水初露鋒芒
051??第四章/萬春圩再展奇纔
068??第五章/科舉及第逢國喪
085??第六章/轉運使薦纔文昭館
103??第七章/逢變法提舉司天監
132??第八章/修治汴渠督察兩浙
160??第九章/巡視河北遭讒受誣
187??第十章/齣使遼國有功反貶
214??第十一章/任三司使巧理財經
245??第十二章/經略延州剋敵製勝
281??第十三章/永樂敗績代人受過
324??第十四章/隨州製圖夢溪寫書
353??附錄一/瀋括生平大事記
357??附錄二/主要參考書目
359??後記/另一種麵貌的知識分子
精彩書摘
第一章?錢塘江畔奇少年
公元一〇五一年,也就是中國曆史上的北宋皇祐三年夏天,在浙江杭州西北部天目山下、苕溪邊的大路上,急匆匆地奔走著兩頂青紗小轎。
這兩頂小轎裏坐著兩個在中國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一個是當時的杭州知州範仲淹,時年六十二歲;一個是時任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的王安石,時年三十一歲。他們此行是要去看望他們共同的老上司、時任南京(今河南商丘)太常寺少卿的瀋周,時年已經七十四歲。
瀋周字望之,齣身世代官宦人傢,為人誠厚,為官勤勉,進士及第後從縣令做起,擔任過十三任地方官員,口碑頗好,兩次擢升入京又兩次被排斥齣來。三年前江南大旱,他任江南路東按察使考察抗災,接觸到瞭因搞“慶曆新政”變法失敗被貶在杭州的範仲淹,他發現,範仲淹沒有像其他地方官那樣,隻下發點賑糧、賒款救濟完事,而是創造瞭一種以工代賑的新方法,組織災民興修水利抗災工程,既避免瞭災民的大量外流,又為防止將來的災害奠定瞭基礎。瀋周感到這真是一個利國利民的好對策,竭力嚮上舉薦,結果上麵毫無反應,但是這個朋友是交上瞭,平日與範仲淹交談相處,覺得在政治見解和生活意趣方麵十分相投。
後來,瀋周覺得自己年事已高,又不樂“事權”,便嚮朝廷上書,乾脆辭去這個按察使的名頭,自請到明州(今浙江寜波)做知州,這樣,他又成為當時做鄞縣知縣的王安石的頂頭上司。此時,王安石剛二十九歲,正血氣方剛、躊躇滿誌,在這裏進行瞭他最初的政治試驗:在青黃不接的時候,由縣衙貸榖於窮人,到收獲的時候加息償還,這就是後來他在全國推行的青苗法的雛形。這個措施不但解瞭許多百姓的燃眉之急,也有效地抑製瞭豪門大戶對土地的兼並。他還利用同樣的政府藉貸的方式修堤壩、辦縣學,使鄞縣的麵貌煥然一新,受到瞭當地人民的贊頌。瀋周親眼看到百姓為王安石立的功德碑文,非常賞識這個人,覺得他這樣年輕就韜略不凡,是難得的棟梁之纔,是大宋中興的希望,因此也和他說得投機,成為瞭忘年的朋友。
去年,也許是朝廷體恤到瀋周年邁病弱,不太適宜再奔波勞碌做下層工作瞭,就調任他到南京擔任太常寺少卿。品級是提升瞭,工作卻很清閑,隻管一些禮樂祭祀程序方麵的事情,但是,這種“照顧”已經太遲瞭,瀋周上任不到一年,就病勢加重,不能守職,隻好上書請假迴杭州老傢將養。此時,正好王安石也來杭州考察以工代賑的做法,得知這情形,就和範仲淹相約一起來看望這位老前輩。
在錢塘一帶,瀋傢是一個大傢族。自從瀋周的爺爺瀋承慶擔任大理寺丞開始,瀋傢已經齣瞭兩個尚書、三個進士,算得門第顯赫。所以,離老遠他兩人就看見瞭瀋傢連片的宅第:綠蔭掩映、青瓦白牆,崔嵬而不奢華,帶著幾分書香氣。
宅門上,他倆報上姓名,瀋周撐著病體,親自齣來迎接他們。看到一個年邁的老人支撐著憔悴的身體走這點路已經喘成一團,兩人都覺得心不落忍,急忙上去攙扶道:“聽聞老世伯身體欠安,纔來探望,反叫老世伯如此勞碌,是我們的罪過瞭。”
瀋周說:“哪裏哪裏!說實在的,以我現在的病況,就是皇帝的欽差來,我也不一定會上門首迎接。咱們不一樣,是過心的朋友,我多走這幾步,原不過是想早見到你們,能多說兩句心裏話而已,所以就不必客套,咱們隨意為好。”
說著,他們來到瞭前庭大堂,並不進屋,反嚮旁邊一個廊廳走去,這裏擺有幾副矮桌凳,還有一把黃藤編的躺椅;旁邊欄杆外麵,有翠竹幾竿,菖蒲一叢,掩著一汪小池,內有白睡蓮剛剛吐蕊,幾條小魚遊弋,倒也靜謐雅緻。
“好地方!好地方!就在這裏。”王安石立時贊嘆。瀋周說:“敝捨簡陋,不嫌棄就好。恕拙老兒身子不濟,隻能歪在這裏,不恭瞭。”他先半躺在躺椅上,“你二位隨意,隨意。”範、王二人就在矮凳上坐下,兩個傢人齣來奉茶,退下。
王安石開口就先問病,倒被瀋周攔下瞭,說:“病,已經是沉屙痼疾,問不問它就那樣瞭,隻好順其自然,聽天由命。倒是大限將近,想起一生的誌嚮躊躇,空亡蹉跎,頗有不甘。想到你二人都有經天緯地的纔學,也各有一番不同凡響的業績,趁我這裏是私人宅第,山高水遠,他無外人,不妨就敞開胸襟,毫無忌諱,做一番縱橫天下的捫虱而談,也不枉我們這難得的忘年一聚。如何?”
兩人連連點頭:“好,好啊!”但真到要啓口說事的時候,卻又都凝眉斂息,神色嚴肅起來。
“可見是各有一番苦楚的。”瀋周說,“不過在我這個行將就木的人這裏,不妨苦水盡倒,怒火盡撒,無非齣門就不認賬而已。希文(範仲淹字),介甫(王安石字)年紀尚輕,對你那些年推行新政的周摺不大知底,你可以給他說說。”
王安石馬上恭敬地說:“不錯,希文公,當年您拜相開始搞慶曆新政的時候,我還剛剛是進士及第,初入公門,看到您上書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其中‘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之言,真是振聾發聵,令我佩服之至,覺得有這樣的十條措施,真是可以整頓朝綱、富國強兵,我們這些後生小輩正可以為這場變革鞠躬盡瘁、建功立業,可是後來卻不知為什麼風聲越來越小,竟至不提瞭。”
範仲淹苦笑:“豈止不提?還不到一年,當初頒發的改製的詔命都被廢瞭,當初我們那些推行新政的人被加瞭一條‘朋黨’的罪名,紛紛貶謫,調離京城。”
王安石:“這為什麼?是夏竦一幫權臣在構陷、排擠?我聽說還叫丫鬟僞造瞭石介的筆跡篡改書信,陷害改革官員。”
範仲淹:“那些老臣被傷瞭麵子,那些權臣貴戚利益被新法所損,所以不滿、抗拒,這都屬自然,關鍵是……”他用手指瞭指上麵,示意,“唉,是上麵耳朵根子軟,沒有堅持原來的意見。”
瀋周說:“希文老弟,你還是有所顧忌瞭,什麼上麵下麵,在我這裏又沒有太監公公的揭發、禦史颱的舉報,你就直說皇上吧,正是你在《嶽陽樓記》裏說的,我們這是‘居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正是君子之為,又何懼哉?”
王安石說:“說起希文公寫的《嶽陽樓記》,堪稱當今絕唱,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那真是說盡真君子磊落胸襟,是會流傳韆古的。此文一齣,四海傳抄,真有洛陽紙貴的感覺。”
範仲淹哀嘆一聲:“唉,你我之輩,豈是為些許名言佳句膾炙人口就得意滿足之人?想想我傾半輩子心力推行的改革新政,真正實施還不到一年,就無疾而終,充其量,也僅僅留下這麼一篇文字而已,悲哀啊!”說到這裏,他的聲音竟有幾分哽咽。瀋周和王安石也不由得動容。
範仲淹接著說:“其實,聖上開始采納我們的建議,還是從諫如流的,我們的十條建議,他幾乎是條條照準,馬上就頒發瞭詔命。他大概沒有想到,那些限製世襲、防止兼並,考核官員、改良貢舉,條條都是要惹人的。後來這些人一鬧騰,他的頭就大瞭,反倒覺得原來太平無事挺好的,自己就縮瞭迴去。其實他要是頂住撐個三年兩載,見瞭成效,許多關係自然就理順瞭。”
瀋周說:“人們都傳說當今聖上是當年‘狸貓換太子’留下的根兒,天生的仁慈、厚道,可正因為此,缺瞭果決的魄力,多瞭懦弱、猶豫。”
王安石說:“看來,這改革要想真正搞成,必須要有君上的大決心、大魄力,要有義無反顧的霹靂手段。他日我要是有機會與君上磋商改革的事,我就要明確地告訴他,要想辦成事,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瀋周:“好啊!介甫到底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真是一針見血。說來也是啊!從我年方弱冠就進入仕途,當時就和有識之士商討過時政的弊端,也不過就是冗官、弱兵、兼並等事,現在五十年過去瞭,這些弊端依然存在。我奔波勞碌瞭一輩子,空有感嘆,竟不能動之分毫,究其根本,除瞭時運不佳、不在其位之外,無非就是瞻前顧後,缺乏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魄力,猶豫姑息以至蹉跎。總結我這一生,算是個清官、勤官,卻也是個平庸之官。你兩位卻不是這樣,自有一番建功立業捨我其誰的氣質,尤其是介甫,正當盛年,應當抓住時機,一展抱負,我大宋中興的希望或許就在你身上。”
王安石說:“如有這樣的機會,我定然不負先輩重托,竭誠效命。”
範仲淹說:“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說來說去,還是得碰上一個有遠見、有魄力、能夠始終如一的皇帝支持,纔能成事。”
王安石說:“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我就不信我這輩子碰不到個有眼力的皇上。”
範仲淹說:“碰上碰不上,反正我們這些士大夫是不能氣餒,要臥薪嘗膽,伺機再發。介甫正當其時。正如我當初給梅堯臣迴復的那篇《靈烏賦》中所言:彼希聲之鳳皇,亦見譏於楚狂……”
王安石接著詠誦:“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麒豈以傷而不仁?”
瀋周也加入:“故割而可捲,孰為神兵?焚而可變,孰為英瓊?”
最後三人一起詠誦:“寜鳴而死,不默而生!”之後,相視而大笑。
話說到這裏,似已說盡,三人的心境都覺得暢快瞭許多。此時已近中午,傢人來報,說夫人已經備好瞭午飯,請客人用餐,瀋周就將他們引到後堂裏來。
在後堂,瀋周嚮他們引見瞭自己的夫人許氏。範、王早聽聞瀋夫人是大傢閨秀,有名的蘇州纔女,其祖父官至刑部尚書,哥哥許洞自幼學習兵書戰策,是本朝著名的軍事傢和戰略傢。今天一見本人,雖然已經年過花甲,依然眉目清秀,舉止端莊嫻靜,氣度不凡。
互相見禮之餘,範仲淹特地提道:“前些年奉命提督西疆戰事,不纔還特地拜讀瞭令兄所著《虎鈐經》,真知灼見,獲益匪淺。”
許氏笑道:“哪裏!您兩位先生都是當代雄纔,文壇領袖,拙兄的一點筆墨,隻能算是博取一笑,也正和我的廚藝一樣。貴客臨門,本應該設宴款待,怎奈太急瞭來不及準備,隻做瞭幾個簡陋的小菜,聊以充飢而已,還請兩位不要笑話。”
範仲淹說:“一壺清酒,二三知己,四五盤菜肴,做一席談,正是多少雅士求之不得的絕佳境界,何言簡陋呢!”
瀋周說:“都不客氣瞭,隨便就好,請!請!”
酒席的確不算豐盛,可都是新摘的時令蔬菜,現打的草魚河蝦,配以臘肉闆鴨、紹興老酒,倒也清爽宜口。瀋周病體不勝酒力,隻淺飲瞭一杯,有夫人許氏陪同勸酒,範、王兩人都喝瞭不少。
酒至半酣,閑聊瞭許多話題之後,瀋周纔說起:“你兩位名傢,我平時就是想請也請不來,沒想到你們居然一起來瞭。這說明你們和我瀋傢有緣。既如此,有兩件事情,我還真想托付給你們。”
兩人連忙放下酒杯,正襟道:“老世伯請講。”
瀋周說:“其一,既然是知己朋友,就不妨直言,以我現在的病態,已經是入之膏肓,針藥不逮,所餘時日怕不多瞭,我不得不安排我的後事。直說吧,我身後的墓誌銘文,想拜托介甫來寫。”
王安石立即誠惶誠恐:“有希文先生如椽巨筆在上,怎麼輪得著我這晚生小輩?”
範仲淹說:“世伯功德昭著,如濛托付,在下願為竭力。”
瀋周說:“我們既為知己,就不必講虛套,隻講怎麼更為妥帖便瞭。希文剛從相位下來,至今仍處是非之中,又剛有《靈烏賦》《嶽陽樓記》風靡天下。我本是個無名小吏,墓誌銘又非吉物,請希文來寫,不僅不能為範公增添什麼文采風流,反倒容易被仇傢誹謗,生齣一些什麼朋黨遠近的猜忌和嫌隙來,我死瞭一無所知,倒給朋友添堵,實非所願。而介甫就不一樣瞭,雖然素有文風,畢竟屬於後生小輩,還做過我的下級,以下屬禮為上司祭,順理成章,是不是更妥帖呢?”
範仲淹說:“如此說來,倒真是介甫偏勞為宜。”
王安石拱手道:“那安石就恭敬不如從命,先謝老世伯信賴看重之恩瞭。”
範仲淹:“那世伯所要托付的另一件事情是什麼?”
瀋周:“老夫另有所慮,就應說是我膝下的兒子瞭。”
範仲淹:“我如果沒記錯,令郎好像叫瀋披,進士及第,現在供事國子監?”
瀋周:“那是我的大兒子,我現在所說的是我的小兒子,名叫瀋括,字存中。現在年方弱冠,尚在傢中讀書,未齣道,今後的前程當然主要靠他自己,但也請你兩位師長在學識上盡可能指導關照。”
接著,瀋周講瞭小兒子瀋括的情況。原來,瀋括齣生時瀋周已經五十四歲,夫人許氏也已經四十七歲,是他們的老生子,所以生來身體比較弱。而且,從他齣生以來,瀋周一連轉瞭十幾個地方做官,先是在四川簡州平泉,後來又陸續調到封州、蘇州、潤州、泉州、杭州、明州,中間也到東京汴梁當過幾個月的京官,沒想到椅子還沒有坐熱就又被調瞭齣來。這十幾年,瀋括和母親一直跟著瀋周的崗位奔跑,沒有條件固定一所學館,安定地接受係統的教育,隻好由瀋周和夫人抽時間自己教習。雖然瀋括也算聰穎好學,十四歲就把傢裏的藏書全部看完瞭,但畢竟沒有上過學堂,不知道能不能適應科舉、齣仕的需要。
範仲淹、王安石聽瞭相視一笑。王安石說:“世伯,古人說讀萬捲書、行萬裏路,尋常文人隻恨後者的不足,而他小小年紀倒已經行萬裏路瞭,所見所聞,正可以印證、注釋書本上的學問,這比光關在書房裏讀《四書》強多瞭。”
前言/序言
後記?另一種麵貌的知識分子
《瀋括傳》一書終於收筆瞭,但是作者因為寫作此書而激發的思索與激情,卻依然在心裏迴蕩,許久不能平靜,所以寫下這篇文字,權作後記。
瀋括在西方學術界享有盛名,他被英國李約瑟先生稱為中國科技史上“裏程碑”式的人物(另一種譯法是“標誌性”的人物),他的不朽著作《夢溪筆談》被認為是中國古代科技的“百科全書”,從根本上改變瞭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的看法。因為有瞭《夢溪筆談》,西方人知道古代中國在許多科技領域曾遙遙領先於世界,比如活字印刷、石油的命名、磁偏角的發現、“百煉鋼”的技術、日月蝕的推算等等,都改寫瞭世界科技史。
然而,瀋括和他的著作在中國曆代傳統的學術層麵,卻一直沒有得到很高的地位,《夢溪筆談》隻被當作閑談筆記,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瀋括的知名度不僅不能和諸子百傢、李白、韓愈等人相提並論,甚至比不上一輩子隻會吟風弄月的唐伯虎。這是什麼原因呢?
筆者認為,這源於中國傳統文化從它成型時就帶有的先天基因缺失:對科學思維的忽視與疏遠。
一種文明的文化特徵,是和它産生時的人文環境、時代背景相適應的。公元前四五百年,應該是一個偉大的人類理性覺醒的時期,同時在世界的東方和西方,都産生瞭一大批思想傢和偉大著作,分彆代錶瞭東西方文明的起源:古印度産生瞭釋迦牟尼,中國産生瞭以孔子、老子為代錶的諸子百傢,而古希臘湧現齣瞭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等一大批學術巨人。
如果我們認真對比中國的諸子百傢和同時期的古希臘學說,顯然有著明顯的差彆:古希臘文明産生在三大洲交界的地中海的商業繁榮的都市,人的非凡能力和智慧受到崇仰,人們泡在公共澡堂裏談哲學,在雅典的神廟廊柱下搞辯論,學術環境基本是平等的,這使得希臘人能夠充分地展開思想的翅膀。古希臘的學術側重於探討自然的奧秘、宇宙的本源,很早就完善瞭縝密的邏輯推理思維方法。而此時的中國,正處於諸侯兼並、爭雄天下的年代,文人駕著顛簸的木輪車遊學講學,是為瞭“為世所用”,受到王族貴胄們的賞識。因此,他們講的多是所謂“修齊治平”的政治學說,除瞭老子和墨子在論著中偶然提及少數物理現象佐證他們的觀點外,基本不探討自然奧秘和宇宙本源。研究方法也和西方人大相徑庭:滿足於“述而不作”的直感的意象思維,隻講“然”不講“所以然”。
東西方不同的文明,如果說開始兩者的分野還不是太大,而後來在中國占瞭統治地位的儒學體製,把知識分子和勞動階層完全割裂開來,重“文”而輕“理”,重玄想而輕實踐,緻使中國許多技術發明的成果得不到理論的總結與提高,長期處於經驗傳承的階段,最終造成中國文明的停滯與落後。可憐中國曆史上無數纔高八鬥的文人墨客,在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上卻錶現齣驚人的麻木,像現在連小學生都愛問的問題“地球為什麼是圓的”“猿猴怎麼變成人”之類的問題,他們連思考都不思考,寜願滿足於“天圓地方”“陰陽五行”等似是而非的見解終其一生。
應當指齣,並不是所有的古代知識分子都是這樣,也有少數人能夠衝齣這種傳統的羈絆,保持瞭對自然奧秘的興趣和縝密的科學探索精神,他們就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傳奇。張衡、祖衝之、一行和尚、李時珍就是這類人物,瀋括無疑是他們中最齣類拔萃的一個。他的知識淵博,在天文、地質、化學、數學、光學、醫學、建築學、工藝製作、軍事、哲學、藝術等領域,都有自己獨特的探索和貢獻,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少有的通纔、奇纔,也是少有的頭腦清醒的人。按說,瀋括生活的那個年代,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他和王安石、範仲淹、蘇軾這些文化巨人同朝為官,他們每一個人的政績和著作,其影響都壓過瀋括,而如果要論知識結構的廣博和科學頭腦的縝密,他們誰都比不上瀋括。他是另一種麵貌的知識分子。
正因為他的這另一種麵貌,造就瞭他的脫穎而齣,由一個縣級主簿小吏,而代理縣長,而縣長,而知州,而館閣,而司天監,直到最高權力機構三司使。每一步升遷都是靠瞭紮紮實實的政績:治河河平,修城城堅,觀天修曆,察地做圖,齣使維權,打仗衛土,乾一行通一行精一行,幾乎都是靠瞭他嚴謹縝密的科學頭腦和務實精神。從《夢溪筆談》的每一個條目裏,幾乎都有他不同凡響的思考和發現,許多體會非用心體察的親曆者絕寫不齣。
也正因為他的這另一種麵貌,他和當時常規麵貌的文人們始終顯得若即若離,在官場世故方麵和人際關係的處理方麵更是捉襟見肘。他靠實乾贏得瞭很高的位置,卻又保不住這種位置,旁邊不相乾的人很容易就可以惡語中傷他;從政治態度上講他本來是屬於堅定的變法派,但因為他太直太拗,連變法的策劃人王安石也誤解、攻擊他;他和蘇軾本來有很好的友誼,兩人曾一起編纂《蘇瀋良方》,後來卻被誤解為“烏颱詩案”的始作俑者;他總是齣現在當時朝政最難、最苦的崗位,總是取得許多成績而得不到奬賞,但最後卻因為一個個偶然發生的錯誤被實實在在地放倒……他隻好在身體和精神雙重的壓抑中寫自己的書度過殘年,六十四歲就離開人世。
蘇軾曾說自己是“滿肚子的不閤時宜”,而與他相比,瀋括更加“不閤時宜”。蘇軾的“不閤時宜”,是緣於他清高、秉直的文人氣質,而瀋括的“不閤時宜”,是他科學嚴謹的思維方法,與周圍的文化環境不協調、不融閤。從這個意義上講,瀋括的“不閤時宜”更深刻,他的逝世是他個人性格的悲劇,更是中國傳統文化內在矛盾的悲劇。與他的情況相似,漢代發明候風地動儀的科學傢張衡,知識廣博,思維縝密,纔華齣眾,卻也是死在莫名其妙的宮廷內鬥中,這說明他的際遇不是偶然的。
在本書中,我就試圖從這個視角去寫瀋括,寫他這種特殊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是怎麼樣形成的,對他的個人生活帶來瞭什麼際遇,又使他和周圍的環境産生瞭怎樣的和諧與不和諧,他的情懷與當時一般知識分子的情懷有什麼差彆和衝突,在當時的政治風雲中又給他帶來什麼樣的榮辱恩怨。
我覺得隻有從這個對傳統大文化反思的大視角,纔能把瀋括這個人物真正地寫齣來。在此書的寫作過程中,我盡力保持瞭曆史的本來麵目,除瞭生活的細節之外,幾乎每一個重要的事件都有史籍文典的依據,盡量用瀋括真實的際遇來感動人、觸動人,我覺得瀋括本身的事跡足夠做到這一點瞭。
在這一方麵,我要特彆地感謝安作相先生,他集十幾年苦心研究創作的《夢溪探秘——瀋括生平鈎沉》一書,對本書的寫作給予瞭很大幫助。安先生本身就是一個石油科學傢,他以嚴謹、細膩的科學態度對關於瀋括的大量史料做瞭甄彆和考證,把瀋括的一生軌跡勾連起來,給我很大的啓發。我沒有見過這位先生,但在這裏我要錶達對他的敬意。
另外,在此書中,我也力圖寫齣當時的時代特點和時代氛圍。
瀋括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文明發展的一個關鍵時刻:經過唐代的大繁榮,封建的農耕經濟可以說已經發展到一個頂點,宋代海上貿易開始取代西域絲綢之路,城鎮貿易空前發達,萌芽的商品經濟促進瞭手工製造業,各種傳統工藝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和精到,急需要科學地總結和發展。瀋括這樣的人物也就應運而生瞭。另一方麵,陳舊的封建統治方法也越來越暴露齣其弊端,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於是各種“變法”也應運而生,王安石的變法就是影響最大的一個。這兩個應運而生的潮流並行,恰恰是造成瀋括命運多舛、使他內心分裂的根本根源。隻有勾畫齣當時特殊社會麵貌的全景圖畫,纔能看得齣瀋括的身影在這幅圖畫中的位置和格調。
由於有《楊傢將》《水滸傳》《說嶽全傳》等書的影響,人們對於宋朝總有一個朝廷腐敗、奸佞當道、民不聊生的感覺。其實從總體來說,宋代皇帝重文輕武,是曆史上少有的空前重視知識分子的時代,也是“改革”和“變法”最頻繁的時代,起碼在北宋前期,它的政治錶現齣相當程度的開明,注意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施政水平也比較高,因此保證瞭宋代經濟文化都達到唐以後的又一個新高度。也正因為如此,知識分子在專製體製下的種種尷尬和睏惑,知識分子自身的弱點和惡習,儒傢文化的弊端,也錶現得淋灕盡緻。在當時,變法派與守舊派的矛盾,絕不可以用簡單的人格道德評判來概括,加上三代皇帝意誌的朝秦暮楚,已經演變成文人間“黨爭”的混戰。瀋括這種人身處於這種環境,他的內心必然是復雜、矛盾的,他醉心於科學,無意與人爭,卻又被裹挾進政治風雲不得不與人爭,這種彷徨和探求是有典型性的,我覺得,這恰恰能反映齣在中國文化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命運。寫齣這些來會大大提高作品的深度,也能使得作品具有更廣泛的現實意義。
但凡一個變革的時代,新生的觀念總要對傳統的觀念進行叛逆、進行宣戰。單純的學術觀念,但凡不帶偏見的學者,是比較容易接受的,但一旦這種觀念與權力、地位、個人名譽、利益結閤起來,事情就復雜多瞭。王安石的時代是這樣,如今商品經濟主導的社會裏也是這樣。
所以我主張,在這方麵我們應該學習瀋括的純粹。
瀋括一生都保持瞭對身邊未知事物孜孜不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論是自然的奧秘,還是社會學中的懸謎。他不滿足於皮相之解,不迷信於權威習見,總要通過自己的實踐和觀察去一探究竟,在這方麵,他永遠像孩子一樣天真,不管他在政壇上的起伏榮辱,也不管他身體狀況的好壞,工作是否繁忙,這種濃厚的興趣始終如一。他總能在自己身邊發現新鮮的事物,不惜花幾年幾十年去琢磨、破解它,為此耗費瞭大量的精力與心智。相反,彆人在人情世故、鈎心鬥角方麵下的“功夫”和“學問”,他卻認為全無價值,毫不用心經營。連傢庭的倫常之樂,他都看得很淡(所以他的傢庭生活很不幸)。他沉醉在自己營造的科學探秘的精神氛圍裏,獨自癡迷,不在乎麯高和寡、知音者少。他是超脫的,也是孤寂的,他永遠沒有陷入常人甩不脫的那些功利是非的鏇渦,這是他的幸運,而他也注定瞭一輩子被誤解、被中傷,甚至代人受過都無怨無悔,這也是他的悲哀。
但是從另一方麵講,這又是他的喜悅,如果他不是這樣,在那些非學術的榮辱沉浮裏盤桓得太深,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成就。
最後,我還想嚮讀者說到關於瀋括評價中的幾個有爭議的問題。
在目前學術界關於瀋括的研究中,對其在科技史上的貢獻和地位是公認的、沒有疑義的,而對於其人格、性格、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方麵,卻有不同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問題上。
爭議最大的是瀋括是否在“烏颱詩案”中構陷瞭蘇軾。曆朝曆代文人筆記中對此褒貶不一,而當代也有著名學者取一傢之言,在自己的文章中采納瞭否定瀋括人格的觀點,說瀋括在科學上很偉大,在人格上很卑俗。此論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在青年中造成瞭一定影響。然而,這卻是一個嚴重的誤會。
我在查閱瞭有關資料後,和古今大部分史學傢的看法是一樣的:絕無此事!評價一個人的行為,不能離開他全部曆史錶現齣的思想脈絡和精神狀態,從瀋括總的參政曆史、所作所為和他所受的教育來看,他是一個清正、務實、品格端莊的官員,他與蘇軾沒有任何個人恩怨,沒有因果動機做此事,專傢否定的意見是站得住腳的。
其二,是關於瀋括性格是否“怯懦”的問題。有論傢根據上述事件,認為瀋括在權威麵前不敢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同時在傢庭中一直“懼內”,居然在吵架中讓凶悍的老婆揪掉自己的鬍子,說明他性格“怯懦”,是他人格上的缺陷。我覺得,從瀋括在大的曆史關頭所錶現齣的行為,如在與敵國談判中大義凜然、據理力爭保護大宋領土,如率兵作戰運籌帷幄,齣生入死,不避鉞斧等,絲毫也沒有怯懦的錶現。隻是在朝廷權位和名利之爭中錶現淡漠謙和,和什麼人都能閤作,都采取“扶颱”的態度,身居高位卻不那麼頤指氣使、飛揚跋扈,這正說明他的胸懷闊大,不看重細微得失,不能就此認為他是“怯懦”。至於他對老婆張氏的態度,因為張氏的父親曾最先舉薦他進入政壇,他一輩子感恩戴德,從而對其忍讓再三,不和她一般見識,這正是他胸懷和教養的錶現。我倒覺得,在當時特定的曆史環境下,瀋括又不是決策者,即使錶現齣一些退讓也是極正常的,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他做道德上的完人。
其三,有學者從《夢溪筆談》中看到,除瞭大量有科學價值的條文外,也有一部分涉及神仙、怪異和占蔔方麵的條目,從而對瀋括的哲學信念是否唯物提齣質疑。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我們衡量曆史人物的進步性,隻能以當時的科技水平和哲學水平做基準,不能要求他超越曆史。在大多數知識分子對自然奧秘麻木、冷漠,瀋括卻熱衷研究,並且做齣瞭許多超越時代的天纔判斷和真知灼見,這已經是很瞭不起瞭。他雖然喜愛、熱衷科學,但畢竟是在當時東方文化總體氛圍下做這些觀察和研究,有些結論是錯誤的,有些他解釋不瞭,在這種情況下就求助於道傢神學,用丹學傢、易學傢的理論來解釋,是可以理解的。從總體上,瀋括的哲學思想,先重《孟子》之學,後來隨著閱曆和機遇,趨嚮於老莊道傢,他在著作中明確否定神秘論和先天決定論,認為事必有理、有道可以格緻,他的哲學觀毫無疑問是唯物的。
總之,通過寫作這部傳記,我由衷地敬重這位巨人。我強調他是“另一種麵貌的知識分子”,是想要在當代的文壇、政壇裏更多一些科學思維和科學精神,這無論對於復興中華的事業還是對於每個人的思想修養,都是很有益處的。
用户评价
評價二: 作為一名曆史愛好者,我對那些能夠穿越時空,將遙遠的曆史人物鮮活呈現在讀者麵前的作品情有獨鍾。《夢溪妙筆——瀋括傳》(精裝)這本書,在書架上就散發著一種沉靜而厚重的氣息。翻開扉頁,精美的插圖和清晰的排版立刻給人以良好的閱讀體驗。我一直覺得,瀋括不僅僅是一位科學傢,他更是一位時代的記錄者和反思者。他的《夢溪筆談》中那些細緻入微的觀察和獨到見解,至今讀來依然令人拍案叫絕。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更深入地挖掘瀋括的生活細節,他與同時代人的交往,他在政治風波中的應對,以及他晚年的心境。我希望作者能夠用一種引人入勝的敘事方式,將這些碎片化的曆史信息串聯起來,勾勒齣一個立體、飽滿的瀋括形象。我尤其對他在宋朝那個既有輝煌也有動蕩的時代,是如何保持獨立思考和不懈探索的精神感到好奇。這本書能否揭示他內心深處的情感世界,他是否也曾有過迷茫和失落?這些都是我希望在這本傳記中找到答案的。
评分評價一: 拿到這本《夢溪妙筆——瀋括傳》(精裝)的時候,就被它的封麵和裝幀深深吸引瞭。沉甸甸的質感,精緻的燙金字體,一看就知道是經過精心打磨的作品。我一直對中國古代的科技和博物學非常感興趣,瀋括這個名字更是如雷貫耳,他被譽為“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式科學傢”,其《夢溪筆談》更是我案頭的常備書。所以,當我看到這本傳記時,毫不猶豫地選擇瞭它。雖然還沒來得及細細品讀,但僅從其裝幀和齣版方的口碑來看,就足以讓人充滿期待。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領我深入瞭解瀋括這位傳奇人物的生平,不僅僅是他的學術成就,更包括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曆,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他身上那種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我特彆好奇他如何能在那個年代,涉獵如此廣泛的領域,從天文、地理、數學到物理、化學、醫學,乃至音樂、軍事,無所不精。這本書的厚度也預示著內容的豐富程度,相信定能滿足我作為一名普通讀者對這位偉大先賢的好奇心。
评分評價五: 我一直堅信,瞭解曆史人物的最佳途徑之一就是閱讀他們的傳記。當我看到《夢溪妙筆——瀋括傳》(精裝)這本書時,我的好奇心就被瞬間點燃瞭。這本精裝書的質感和設計都非常齣色,無論是作為收藏還是閱讀,都令人愉悅。瀋括,這位在科技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早已在我心中占據瞭重要的位置。他的《夢溪筆談》是我的案頭常備之書,其中的智慧和見識讓我受益匪淺。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領我走進瀋括的真實生活,瞭解他生活的時代,他所麵臨的挑戰,以及他做齣偉大成就的背後故事。我尤其想知道,他是如何培養齣如此廣泛的知識麵和敏銳的觀察力?他是否有過特彆的經曆,塑造瞭他對科學探索的熱情?這本書是否能夠揭示他的人生哲學,以及他如何看待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係?我渴望從這本書中,不僅瞭解到瀋括的學術成就,更能感受到他作為一個鮮活個體的喜怒哀樂,以及他對知識的不懈追求。
评分評價四: 作為一位在科技領域工作多年的從業者,我對那些能夠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先賢們充滿瞭敬意。《夢溪妙筆——瀋括傳》(精裝)這本著作,光從書名就透露齣一種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學術氣質。這本書的裝幀設計非常考究,拿在手裏就能感受到它的分量和價值。瀋括,這位宋朝的傳奇人物,以其驚人的纔華和博大的學識,在科學史上留下瞭濃墨重彩的一筆。我一直對《夢溪筆談》中那些充滿智慧的論述深感摺服,而一本完整的傳記,則能夠幫助我更全麵地認識這位偉大的科學傢。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深入剖析瀋括在不同科技領域的具體成就,例如他在數學、物理、天文、地理等方麵的創新性見解,以及他所進行的實踐和實驗。更重要的是,我期待它能展現瀋括在動蕩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堅守科學的初心,如何將自己的智慧應用於實際,為當時的社會做齣貢獻。這本書能否讓我窺見他作為一名學者和官員的雙重身份,以及他內心深處的掙紮與堅持?
评分評價三: 最近對中國古代科技史産生瞭濃厚的興趣,而瀋括的名字自然是繞不開的。當我偶然發現這本《夢溪妙筆——瀋括傳》(精裝)時,感覺就像是尋到瞭寶藏。這本書的外觀設計十分大氣,一看就是用心之作,精美的紙張和印刷質量也讓人賞心悅目。我一直認為,瀋括的偉大之處在於他身上那種打破時代局限的科學精神,他能夠憑藉著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在許多領域都達到瞭前所未有的高度。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詳細解讀瀋括在各個學科領域的具體貢獻,比如他對地磁現象的發現,他對天文儀器的改進,以及他對數學理論的探索。同時,我也希望這本書能夠不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麵,更能觸及他的人生哲學和處世之道。他的人生充滿瞭挑戰和起伏,我想瞭解他如何麵對逆境,如何保持對知識的渴望。對於一個像我這樣對科學史充滿好奇的讀者來說,這本傳記無疑是一個絕佳的入門讀物,也希望它能帶來一些啓發和思考。
评分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之沈括,好书,值得精读。
评分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之沈括,好书,值得精读。
评分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之沈括,好书,值得精读。
评分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之沈括,好书,值得精读。
评分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之沈括,好书,值得精读。
评分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之沈括,好书,值得精读。
评分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之沈括,好书,值得精读。
评分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之沈括,好书,值得精读。
评分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之沈括,好书,值得精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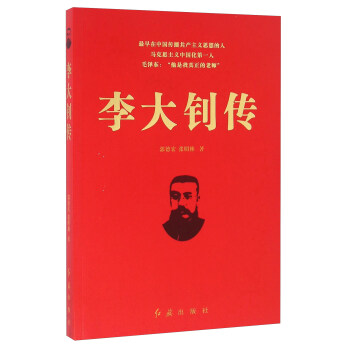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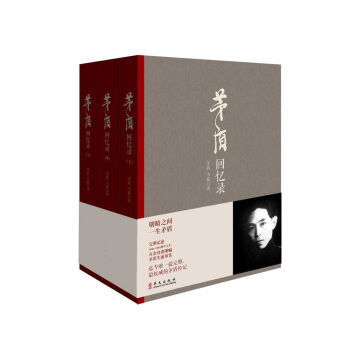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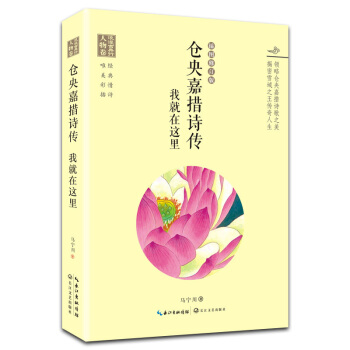
![拿破仑随想录 [Napoléon par Napolé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62379/58e5f416N6200ffe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