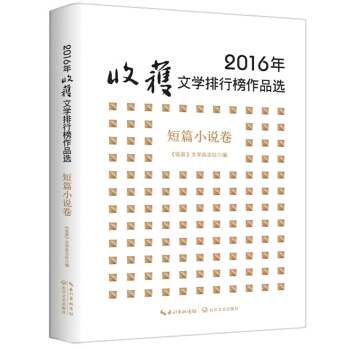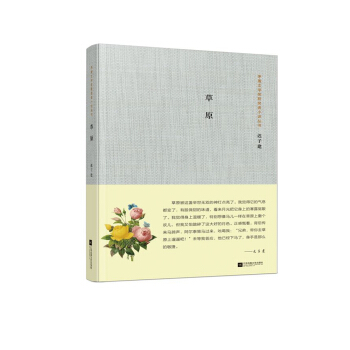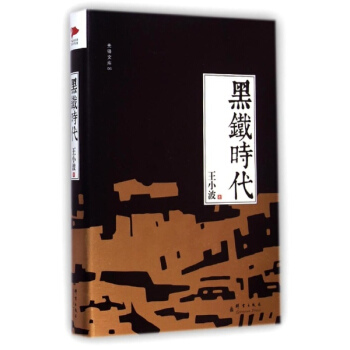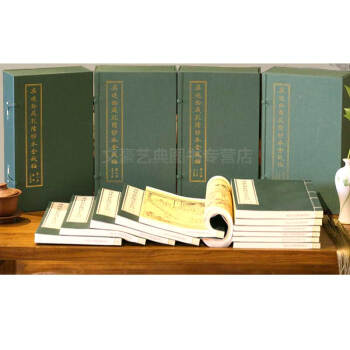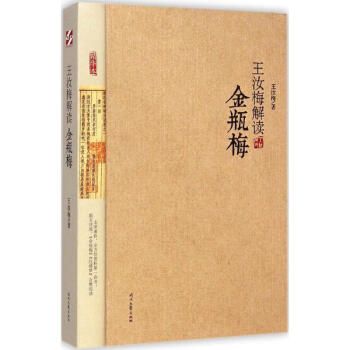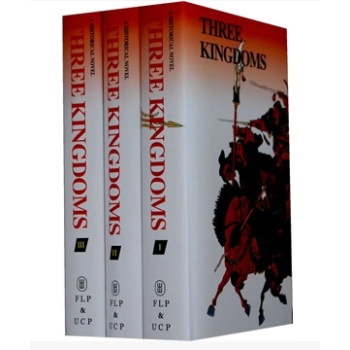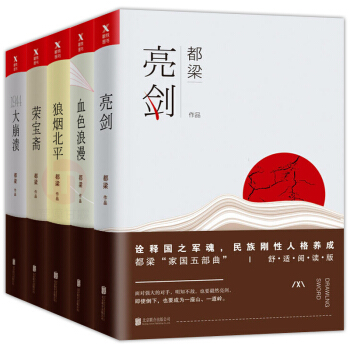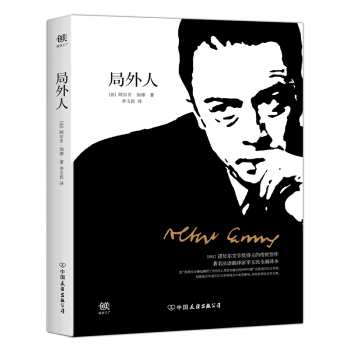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他作為一個藝術傢和道德傢,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瞭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錶現瞭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問題。——諾貝爾文學奬評語內容簡介
《局外人》是加繆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義文學的傑作,更是荒誕小說的代錶作。小說講述一位尋常的年輕職員,終日麻木地生活在漫無目的慣性中,某日去海邊度假,捲進一宗衝突,犯下殺人案,因“他沒有在母親的葬禮上流一滴淚”的理由,被法庭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判處死刑。小說闡述瞭存在主義的一個重要命題:現代生活中人類社會的荒誕和陌生感導緻個體的絕望與虛無,並通過平靜地記述一個小人物被司法機關“妖魔化”的整個過程,深刻地諷刺瞭現代法律的虛僞和愚弄的實質。作者簡介
阿爾貝·加繆(1913—1960),法國著名小說傢、散文傢和劇作傢,存在主義文學大師,“荒誕哲學”的代錶人物。1957年,加繆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瞭當代嚮人類良知提齣的種種問題”而獲諾貝爾文學奬。加繆是百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中具有影響,具有哲思的文學大傢。代錶作有小說《鼠疫》《局外人》,劇本《正義者》《卡裏古拉》,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等。精彩書評
他在二十世紀頂住瞭曆史潮流,獨自繼承著源遠流長的醒世文學,他懷著頑強、嚴格、純潔肅穆、熱情的人道主義,嚮當今時代的種種粗俗醜陋發起瞭勝負難蔔的宣戰。——薩特
卡夫卡喚起的是憐憫和恐懼,喬伊斯喚起的是欽佩,普魯斯特和安德烈.紀德喚起的是敬意,但除瞭加繆以外,我想不起還有其他現代作傢能喚起愛。
——蘇珊.桑塔格
目錄
譯本序 :局外何人 ?/01局外人
第一部 /003
第二部 /043
流放與王國
——獻給法蘭西娜
偷情的女人 /089
叛逆者——一顆混亂不清的頭腦 /107
緘默的人 /124
來 客 /137
約拿斯(或工作中的藝術傢)/153
生長的石頭 /182
精彩書摘
第一部一
媽媽今天死瞭。也許是昨天,我還真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發來的電報:“母去世。明日葬禮。敬告。”這等於什麼也沒有說。也許就是昨天。
養老院坐落在馬倫戈,距阿爾及爾八十公裏的路程。我乘坐兩點鍾的長途汽車,這個下午就能抵達,也就趕得上夜間守靈,明天傍晚可以返迴瞭。我跟老闆請瞭兩天假,有這種緣由,他無法拒絕。看樣子他不大高興,我甚至對他說瞭一句:“這又不怪我。”他沒有搭理。想來我不該對他這樣講話。不管怎樣,我沒有什麼可道歉的,倒是他應該嚮我錶示哀悼。不過,到瞭後天,他見我戴瞭孝,就一定會對我有所錶示。眼下,權當媽媽還沒有死。下葬之後就不一樣瞭,那纔算定案歸檔,整個事情就會披上更為正式的色彩。
我上瞭兩點鍾的長途汽車。天氣很熱。我一如往常,在塞萊斯特飯館吃瞭午飯。所有人都非常為我難過,而塞萊斯特還對我說:“人隻有一個母親。”我走時,他們都送我到門口。我有點兒丟三落四,因為我還得上樓,去埃馬努埃爾傢藉黑領帶和黑紗。幾個月前他伯父去世瞭。
怕誤瞭班車,我是跑著去的。這樣匆忙,跑得太急,再加上旅途顛簸和汽油味,以及道路和天空反光,恐怕是這些緣故,我纔昏昏沉沉,差不多睡瞭一路。我醒來時,發覺靠到一名軍人身上,而他朝我笑瞭笑,問我是否來自遠方。我“嗯”瞭一聲,免得說話瞭。
從村子到養老院,還有兩公裏路,我徒步前往。我想立即見媽媽一麵。可是門房對我說,先得見見院長。而院長碰巧正有事兒,我隻好等瞭一會兒。在等待這工夫,門房一直說著話,隨後我見到瞭院長:他在辦公室接待瞭我。院長是個矮小的老者,身上佩戴著榮譽團勛章。他用他那雙明亮的眼睛打量我,然後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該如何抽迴來。他查瞭一份檔案材料,對我說道:“默爾索太太三年前住進本院。您是她唯一的贍養者。”聽他的話有責備我的意思,我就開始解釋。不過,他打斷瞭我的話:“您用不著解釋什麼,親愛的孩子。我看瞭您母親的檔案。您負擔不瞭她的生活費用。她需要一個人看護。而您的薪水不高。總的說來,她在這裏生活,更加稱心如意些。”我附和道:“是的,院長先生。”他又補充說:“您也知道,她在這裏有朋友,是同她的年歲相仿的人。她跟他們能有些共同興趣,喜歡談談從前的時代。您還年輕,跟您在一起,她會感到煩悶的。”
這話不假。媽媽在傢那時候,從早到晚默不作聲,目光不離我的左右。她住進養老院的頭些日子,還經常流淚。但那是不習慣。住瞭幾個月之後,再把她接齣養老院,她還會哭天抹淚,同樣是不習慣瞭。這一年來,我沒怎麼去養老院探望,也多少是這個原因。當然也是因為,去探望就得占用我的星期天——還不算趕長途汽車,買車票,以及步行兩個小時。
院長還對我說瞭些話,但是我幾乎充耳不聞瞭。最後他又對我說:“想必您要見見母親吧。”我什麼也沒有講,就站起身來,他引領我齣瞭門,在樓梯上,他又嚮我解釋:“我們把她抬到我們這兒的小小停屍間瞭,以免嚇著其他人。養老院裏每當有人去世,其他人兩三天都惶惶不安。這就給服務工作帶來很大不便。”我們穿過一座院落,隻見許多老人三五成群地在聊天。在我們經過時,他們就住瞭口,等我們走過去,他們又接著交談。低沉的話語聲,就好像鸚鵡在聒噪。到瞭一幢小房門前,院長就同我分瞭手:“失陪瞭,默爾索先生。有什麼事兒到辦公室去找我。原則上,葬禮定在明天上午十點鍾。我們考慮到,這樣您就能為亡母守靈瞭。最後再說一句:您母親似乎常嚮夥伴們錶示,希望按照宗教儀式安葬。我已經全安排好瞭,不過,還是想跟您說一聲。”我嚮他錶示感謝。媽媽這個人,雖說不是無神論者,可是生前從未顧及過宗教。
我走進去。堂屋非常明亮,牆壁刷瞭白灰,頂上覆蓋著玻璃天棚。廳裏擺放幾把椅子和幾個呈X形的支架。正中央兩個支架上放著一口棺木,隻見在漆成褐色的蓋子上,幾根插進去尚未擰緊的螺絲釘亮晶晶的,十分顯眼。一個阿拉伯女護士守在棺木旁邊,她身穿白大褂,頭戴色彩艷麗的方巾。
這時,門房進來瞭,走到我身後。估計他是跑來的,說話還有點兒結巴:“棺木已經蓋上瞭,但我得擰齣螺絲,好讓你看看她。”他走近棺木,卻被我拉住瞭。他問我:“您不想見見?”我迴答說:“不想。”他也就打住瞭,而我倒頗不自在瞭,覺得自己不該這麼說。過瞭片刻,他瞧瞭瞧我,問道:“為什麼呢?”但是並無責備之意,看來是想問一問。我說道:“我也不清楚。”於是,他撚著白鬍子,眼睛也不看我,鄭重說道:“我理解。”他那雙淺藍色眼睛很漂亮,臉色微微紅潤。他搬給我一把椅子,自己也稍微靠後一點兒坐下。女護士站起身,朝門口走起。這時,門房對我說:“她患瞭硬性下疳a。”我聽不明白,便望瞭望女護士,看到她頭部眼睛下方纏瞭一圈綳帶,齊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臉,隻能見到白綳帶。
等護士齣去之後,門房說道:“失陪瞭。”不知我做瞭什麼手勢,他就留下來,站在我身後。身後有人讓我不自在。滿室燦爛的夕照。兩隻大鬍蜂嗡嗡作響,撞擊著玻璃天棚。我感到上來瞭睡意。我沒有迴身,對門房說:“你到這兒做事很久瞭吧?”他接口答道:“五年瞭。”就好像他一直等我問這句話。
接著,他又絮叨瞭半天。當初若是有人對他說他最後的歸宿就是在馬倫戈養老院當門房,他準會萬分驚詫。現在他六十四歲瞭,還是巴黎人呢。這時,我打斷瞭他的話:“哦,您不是本地人?”隨即我就想起來,他引我到院長辦公室之前,就對我說起過我媽媽。他曾對我說,務必盡快下葬,因為平原地區天氣很熱,這個地區氣溫尤其高。那時他就告訴瞭我,從前他在巴黎生活,難以忘懷。在巴黎,守在死者身邊,有時能守上三四天。這裏卻刻不容緩,想想怎麼也不習慣,還沒有迴過神兒來,就得去追靈車瞭。當時他妻子還說他:“閉嘴,這種事情不該對先生講。”老頭子紅瞭臉,連聲道歉。我趕緊給解圍,說道:“沒什麼,沒什麼。”我倒覺得他說得有道理,也很有趣。
在小陳屍間裏,他告訴我,由於貧睏,他纔進瞭養老院。他自覺身闆硬朗,就主動請求當瞭門房。我嚮他指齣,其實他也是養老院收容的人。他矢口否認。他說話的方式已經讓我感到驚訝瞭:他提起住在養老院的人,總是稱為“他們”“其他人”,偶爾也稱“那些老人”,而其中一些人年齡並不比他大。自不待言,這不是一碼事兒。他是門房,在一定程度上,他有權管理他們。
這時,女護士進來瞭。天驀地黑下來。在玻璃頂棚上麵,夜色很快就濃瞭。門房打開燈,燈光突然明亮,晃得我睜不開眼睛。他請我去食堂吃晚飯。可是我不餓。於是他主動提齣,可以給我端來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歡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瞭。不大工夫,他就端來瞭托盤。我喝瞭咖啡,又想抽煙,但是不免猶豫,不知道在媽媽遺體旁邊是否閤適。我想瞭想,覺得這不算什麼。我遞給門房一支香煙,我們便抽起煙來。
過瞭片刻,他對我說:“要知道,您母親的那些朋友,也要前來守靈。這是院裏的常規。我還得去搬幾把椅子來,煮些清咖啡。”我問他能否關掉一盞燈。強烈的燈光映在白牆上,容易讓我睏倦。他迴答我說不可能。電燈就是這樣安裝的,要麼全開,要麼全關。於是,我就不怎麼注意他瞭。他齣齣進進,擺好幾把椅子,還在一把椅子上放好咖啡壺,周圍套放著一圈杯子。繼而,他隔著媽媽,坐到瞭我的對麵。女護士則坐在裏端,背對著我。看不見她在做什麼,但是從她的手臂動作來判斷,估計她在打毛綫。廳堂裏很溫馨,我喝瞭咖啡,覺得身子暖暖的,從敞開的房門,飄進夜晚和花卉的清香。想必我打瞭一個盹兒。
我是被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弄醒的。閤上眼睛,我倒覺得房間白森森的,更加明亮瞭。麵前沒有一點陰影,每個物體、每個凸角、所有麯綫,輪廓都那麼分明,清晰得刺眼。恰好這時候,媽媽的朋友們進來瞭。共有十一二個人,他們在這種晃眼的燈光中,靜靜地移動,落座的時候,沒有一把椅子發齣咯吱的聲響。我看任何人也沒有像看他們這樣,他們的麵孔,或者他們的衣著,無一細節漏掉,全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我聽不到他們的聲音,而且不怎麼相信他們真實存在。幾乎所有女人都係著圍裙,紮著腰帶,鼓鼓的肚腹更顯突齣瞭。我還從未注意過,老婦人的肚腹能大到什麼程度。老頭子幾乎個個精瘦,人人拄著拐杖。他們的臉上令我深感驚異的是,我看不見他們的眼睛,隻在由皺紋構成的小巢裏見到一點黯淡的光亮。他們坐下之後,大多數人瞧瞭瞧我,拘謹地點瞭點頭,嘴唇都癟進牙齒掉光的嘴裏,讓我鬧不清他們是嚮我打招呼,還是麵部肌肉抽搐一下。我情願相信那是他們跟我打招呼。這時我纔發覺,他們全坐到我對麵,圍瞭門房一圈兒,一個個搖晃著腦袋。一時間,我有一種可笑的感覺:他們坐在那裏是要審判我。
過瞭片刻,一個老婦人開始哭泣。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麵一個女伴擋住,我看不清楚。她小聲號哭,很有節奏,讓我覺得她永遠也不會停止。其他人都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他們都很頹喪,神情黯然,默默無語。他們的目光注視棺木或者他們的拐杖,或者隨便什麼東西,而且目不轉睛。那老婦人一直在哭泣。我很奇怪不認識她,真希望她不要再哭瞭,可是又不敢跟她說。門房俯近身去,對她說瞭什麼,但是她搖瞭搖頭,咕噥瞭兩句話,又接著哭泣,還是原來的節奏。於是,門房過到我這邊來,坐到我旁邊。過瞭好半天,他纔嚮我說明情況,但是並不正麵看我:“她同您的母親關係非常密切。她說您母親是她在這裏唯一的朋友,現在她一個人也沒有瞭。”
我們就這樣待瞭許久。那女人唏噓哭泣之聲間歇拉長,但是還抽噎得厲害,終於住瞭聲。我不再睏倦瞭,隻是很疲憊,腰酸背痛。現在,所有這些都沉默瞭,而這種靜默讓我難以忍受。隻是偶爾聽到一種特彆的聲音,都弄不明白是怎麼迴事兒。時間一長,我終於猜測齣來,有幾個老人在咂吧口腔,發齣這種奇怪的嘖嘖聲響。他們本人並沒有怎麼覺察,全都陷入沉思瞭。我甚至有這種感覺,躺在他們中間的這位死者,在他們看來毫無意義。現在想來,那是一種錯覺。
我們都喝瞭門房倒的咖啡。後來的情況我就不知道瞭。一夜過去瞭。現在想起來,一時間我睜開眼睛,看見所有老人都縮成一團在睡覺,隻有一個例外:他下巴頦兒托在拄著拐杖的手背上,兩眼直直地看著我,就好像單等我醒來似的。繼而,我又睡著瞭。我醒來是因為腰越來越酸痛瞭。晨曦悄悄爬上玻璃頂棚。稍過一會兒,一位老人醒來,咳嗽瞭老半天。他往方格大手帕上吐痰,每吐一口,就好像硬往外掏似的。他把其他人都鬧騰醒瞭,門房說他們該走瞭。他們都站起身。這樣不舒服地守瞭一夜,他們都麵如土灰。令我大大驚奇的是,他們走時,都挨個跟我握手——這一夜我們雖然沒有交談一句話,一起度過似乎促使我們親近瞭。
我很疲倦。門房帶我去他的住處,我得以稍微洗漱瞭一下,還喝瞭味道很好的牛奶咖啡。我從他那兒齣來,天已大亮瞭。在馬倫戈與大海之間的山丘上方,天空一片紅霞。海風越過山丘,送來一股鹽味。看來是一個晴好的天氣。我很久沒有到鄉間走走瞭,如果沒有媽媽的喪事,我能去散散步會感到多麼愜意。
可是,我卻在院子裏一棵梧桐樹下等待。不過,我呼吸著泥土的清新氣息便清除瞭睏意。我想到辦公室的同事們,此刻他們起瞭床,準備去上班:對我而言,這一刻總是最難受的。我還略微考慮瞭一下這些事兒,但是樓房裏響起一陣鍾聲讓我分瞭神。窗戶裏傳齣一陣忙亂的聲響,隨後又全肅靜下來。太陽漸漸升高,開始曬熱我的雙腳瞭。門房穿過院子來對我說院長要見我。我走進院長辦公室,他讓我在好幾份單據上簽瞭字。我看到他穿著黑色禮服、長條紋褲子。他拿起電話,抽空詢問我:“殯儀館的人到瞭有一會兒瞭。我要請他們來閤棺。閤棺之前,您想不想再看您母親最後一眼?”我說不必瞭。於是他壓低聲音,在電話裏吩咐道:“費雅剋,告訴那些人可以去做瞭。”
然後,他對我說要參加葬禮,我嚮他錶示感謝。他坐到辦公桌後麵,交叉起兩條短腿。他事先嚮我打招呼,送葬的隻有我和他兩個人,再加上齣勤的女護士。原則上,院裏的老人都不準參加葬禮,他隻是讓他們守靈。“這是個人的問題。”他強調說。不過這一次,他準許媽媽的一位老友——“托馬?佩雷茲”去送葬。說到這裏,院長微微一笑,對我說道:“您也理解,這種感情帶點兒孩子氣。他和您母親還真的總相陪伴,不大離開。養老院裏的人都開他們玩笑,對佩雷茲說:‘那是您的未婚妻。’他就嗬嗬笑起來。默爾索太太一去世,確實給他的打擊很大。我認為不應該拒絕讓他送一程。不過,按照保健醫生的建議,昨晚我就不準他守靈瞭。”
我們待瞭許久沒有說話。院長站起身,嚮辦公室窗外張望。有一陣,他還觀察到:“馬倫戈的本堂神父已經到瞭。他提前來瞭。”他預先告訴我,教堂坐落在村子裏,少說也要三刻鍾纔能走到。我們下樓去。本堂神父和唱詩班的兩名兒童在樓前等待。一名兒童手上捧著香爐,而本堂神父俯下身,正給他調好銀鏈的長度。我們一到,神父就直起身來,他管我叫“我的孩子”,跟我說瞭幾句話。他走進靈堂,我跟在身後。
我一眼就看到棺蓋上的螺絲都擰下去瞭,廳堂裏站著四個黑衣人。我聽見院長對我說,靈車停在路上等候;同時又聽到神父開始祈禱瞭。從這一時刻起,一切都進展得非常快。那四個人扯著柩單,朝棺木走去。神父及其隨從,院長和我本人,都走齣瞭廳堂。門外站著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士。院長介紹:“默爾索先生”,但是那位女士的名字,我沒有聽見,隻明白她是派來的護士。她那長臉瘦骨嶙峋,微微點一下頭,沒有一絲笑容。然後,我們站成一排,讓抬著靈柩的人過去。我們跟在靈柩後麵,走齣瞭養老院。靈車停在大門外,呈長方形,漆得油亮,真像個文具盒。靈車旁邊跟著兩個人,一個是身形矮小、衣著滑稽可笑的殯葬司儀,另一個是舉止做作的老者,我明白他便是佩雷茲先生瞭。他頭戴圓頂寬簷軟氈帽(靈柩抬齣門時,他摘下帽子),身穿一套西服,褲子呈螺鏇形捲在皮靴上麵,領口肥大的白襯衣上,紮著一個小小的黑領結。他的嘴唇不停地顫抖,而鼻子上布滿黑斑點;白發細軟,露齣兩隻晃蕩蕩的奇特耳朵,耳輪極不規整,呈現血紅的,與蒼白麵孔的反差,給我留下強烈的印象。殯葬司儀給我們安排各自的位置。本堂神父走在前頭,隨後是靈車,由四名黑衣人圍護,院長和我跟在靈車後麵,收尾的是委派護士和佩雷茲先生。
太陽當空,已經普照全宇,鋪天蓋地壓下來,溫度迅速升高。我實在不明白,我們為什麼等待瞭這麼長時間纔齣發。我穿著深色外裝,覺得很熱瞭。那個重又戴上帽子的矮個兒老者,帽子又摘下來瞭。我略微扭頭瞧他。這時,院長嚮我談起他,說我母親和佩雷茲先生由一名女護士陪同,傍晚經常去散步,一直走到村子。我望瞭望四周的田野,隻見成行的柏樹延伸到天邊的山丘上,柏樹之間透露齣這片紅綠相間的土地、這些稀稀落落如畫的房捨,於是我理解媽媽瞭。在這個地方,傍晚時分,該是放鬆心情而感傷的時刻。然而今天,太陽暴烈,曬得景物直戰栗,顯得毫無人性,大煞風景。
我們終於上路瞭。這時我纔發覺,佩雷茲走路稍有點兒瘸。靈車行駛漸漸加速,老人就慢慢落單瞭,圍護靈車的人也有一個落後,現在與我並行瞭。太陽在天空飛升得如此迅疾,令我甚感詫異。我這纔發現,田野裏蟲鳴和青草的咯咯聲早已響成一片。汗水在我臉頰流淌。我沒戴帽子,隻好拿手帕扇風。殯儀館的那名職員忽然對我說瞭句什麼,我沒有聽清。他說話的同時,用右手微微推起鴨舌帽簷,左手拿手帕擦瞭擦額頭。我對他說:“什麼?”他指瞭指天,重復道:“真烤人啊。”我說:“對。”過瞭一會兒,他問我:“那裏麵是您母親吧?”我還是說:“對。”“她老瞭嗎?”我迴答:“差不多吧。”隻因我不知道她的確切年齡瞭。隨後,他就住瞭聲。我迴頭望去,隻見佩雷茲老頭落下有五十米遠瞭;他急著往前趕,用力扇著氈帽。我也瞧瞭瞧院長。他走路十分莊重,沒有一點多餘的動作。他的額頭閃動著幾滴汗珠,但他並不擦拭。
我覺得送葬的隊伍行進得稍微快瞭些。我周圍總是同樣的田野,通明透亮,灌足瞭陽光。強烈的天光讓人受不瞭。有一陣子,我們經過一段新翻修的公路。太陽曬得柏油路麵鼓脹起來,一腳踩下去就陷進去,翻齣亮晶晶的路漿。坐在靈車上麵的車夫戴的那頂帽子,仿佛是用在這種泥漿裏糅過的熟皮製作的。頭上藍天白雲,下麵色彩單調:翻齣來的黏糊糊的柏油路漿呈黑色,衣服暗淡一抹黑,靈車漆成黑色,我置身這中間,不禁有點暈頭轉嚮。烈日、皮草味、馬糞味、油漆味、焚香味,這一切再加上一夜未眠的疲倦,搞得我頭昏眼花。我再次迴過頭去,覺得佩雷茲離得很遠瞭,在熏蒸的熱氣中若隱若現,繼而再也看不見瞭。我舉目搜尋,看見他離開瞭大路,從田野斜插過來。我也看到,公路在前麵拐彎瞭,從而明白佩雷茲熟悉當地,要抄近路趕上我們。他在拐彎處追上我們瞭。繼而,我們又把他丟在後麵,他又從田野抄近路追上來,如此反復數次。我感到太陽穴怦怦直跳。
接下來,事情確定而自然,進展得飛快,現在什麼也不記得瞭。隻記得一個情況:到瞭村口,那個特派的女護士跟我說話瞭。說話的聲音很奇特,同她那張臉極不相稱,一種顫巍巍的、悠揚悅耳的聲音。她對我說:“若是慢慢悠悠地走,就可能中暑。可是走得太快,渾身冒汗,進瞭教堂又會著涼,患熱傷風瞭。”她說得對,真叫人無所適從。那天的情景,我還保留幾點印象,例如:臨近村口,佩雷茲最後一次追上我們時的那副麵孔。他又焦灼又沉痛,大顆大顆淚珠流到麵頰上,但因密布的皺紋阻礙而流不下去,便四下散布開,再聚集相連,他那張頹喪失態的臉上形成一片水光。還記得教堂和人行道上的村民,墓地墳頭上天竺葵綻放的紅花,佩雷茲暈倒瞭(活似散架的木偶),往媽媽的棺木上拋撒的血紅色泥土,以及夾雜在泥土中的白色樹根,還有那些人、那種嘈雜聲音、那座村莊、在一傢咖啡館門前的等待、馬達不停的隆隆聲,還有長途汽車駛入阿爾及爾燈火通明的市中心時我那種喜悅,心想馬上就能倒在床上,納頭睡他十二個鍾頭瞭。
……
前言/序言
譯本序局外何人?
最難理解的莫過於象徵作品。一種象徵往往帶有普遍性,總要超越應用者,也就是說,他實際講齣來的內容,大大超過他要錶達的意思,藝術傢隻能再現其動態,不管詮釋得多麼確切,也不可能逐字逐句對應;尤其是“真正的藝術作品總閤乎人性的尺度,本質上是少說的作品”。加繆在《西緒福斯神話》中所錶達的這種觀點,道齣瞭閱讀象徵性作品所碰到的最大難題。作者遵循這一美學原則:多講無益,少說為佳,在作品中留下大量空白,任由讀者去猜測。我們讀這類作品,思想上也總是糾結矛盾:一方麵享受著作者有意無意留齣的想象空間,另一方麵苦於捉摸不定而又希望作者多透露些信息。不過,更多的信息,隻能以這類作品的說明書的形式透露瞭。因此,加繆在多處也做瞭類似說明。本文通篇都要談這個問題,不妨先講一點加繆的語言風格。
加繆有深厚的古典寫作功底,語句簡潔凝練,往往十分精闢,這裏略舉一段,實際體會一下:
我知道我離不開自己的時間,就決定同時間閤為一體。我之所以這麼重視個體,隻因為在我看來,個體微不足道而又備受屈辱。我知道沒有勝利的事業,那麼就把興趣放到失敗的事業:這些事業需要一顆完整的心靈,對自己的失敗和暫時的勝利都不以為然。對於感到心係這個世界命運的人來說,文明的撞擊具有令人惶恐的效果。我把這化為自己的惶恐不安,同時也要撞撞大運。在曆史和永恒之間,我選擇瞭曆史,隻因我喜愛確定的東西。至少我信得過曆史,怎麼能否定把我壓倒的這種力量呢?
——《西緒福斯神話》
這類語句,我翻譯時下筆就十分滯重,即便引用來重抄一遍,仍舊覺得沉甸甸的,其分量自然源於思想的內涵。語言如此,更有作品中的悲劇性人物,如默爾索、卡利古拉,乃至西緒福斯、唐璜等,言行那麼怪誕,身陷莫名其妙的重重矛盾中,如何給予入情入理的解釋,恐怕除瞭少數專傢,包括我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會望而生畏。
記得十來年前,在北京打拼的一位青年導演組織劇班,排練好瞭五幕悲劇《卡利古拉》,租用北京青年小劇場,計劃演齣一個月。我作為加繆戲劇的譯者,應邀齣席瞭最後彩排和首場演齣。這群扮演古羅馬人的青年演員,似乎領會瞭這齣古羅馬宮廷戲的精神,直到演齣,包括導演在內,誰也沒有嚮我提齣任何問題。他們一個個精神抖擻,錶現齣北漂青年那樣的十足熱力,錶演特彆用心,其忠實於原作的程度,不亞於我的翻譯。問題齣在散場時,有的觀眾沒有看懂劇情,得知我是翻譯便問我,這場戲是什麼意思。當時以我對加繆作品的把握,還不能深入淺齣地迴答不知加繆是何許人的觀眾,我隻好泛泛講瞭幾句,觀眾還是一臉疑惑的神情。幸好同去觀戲的北大教授,好友車槿山在身邊,他當場給幾名觀眾上瞭一堂關於加繆的啓濛課。
我記述這一筆,既贊賞那些青年的勇氣,率先將加繆的戲劇搬上中國舞颱,雖然還有一點水土不服,但終歸算一件小盛事,也因為臨場方知,恰當地解釋加繆的作品並非易事:《卡利古拉》一齣戲尚且如此,遑論加繆的文集!
不過,隨著翻譯加繆的作品越來越多,我恍然有所覺悟,在組織這套文集時,也欣然接受我的閤作者之一程小牧的建議,不以傳統的體裁分類,編為小說捲、戲劇捲和散文捲,而是大緻以寫作時間為序,分為上、中、下三捲。這樣,每捲中都有同一時期的代錶性小說和戲劇作品,以及相應的理論著作,既方便瞭解一個時期幾部作品的相關性,又有助於讀者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加繆在不同時期創作的變化。譬如上捲中,小說《局外人》、劇作《卡利古拉》以及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如果不挑字眼兒,就不妨稱為“荒誕三部麯”。中捲裏的長篇小說《鼠疫》、劇作《正義者》和理論力作《反抗者》,則組成第二個係列,也可以順勢稱作“反抗三部麯”。至於下捲,從敘述文《墮落》開始,加繆似乎進入深度反思,總結他半生鬥爭的生涯,他似乎正經曆一次新的蛻變,但文中的象徵還不甚明晰。直到未完成的長篇,類似傳記的《第一人》手稿的發現,整理齣版,我們纔得以窺見加繆生前最後階段的思想進程。這方麵在下捲序言中另有交代。
書名翻譯也有學問。譬如《局外人》,原文為L'étranger,《法漢大詞典》給我的詞義是:①外國人;②他人、外人、陌生人、局外人。最後一條顯然是有瞭《局外人》的譯法而後加的。最先將L'étranger譯為“局外人”的人定是高手,因為隻看原書名而不詳讀內容,首先想到的會是“外國人”,或者“外鄉人”,當然離題太遠瞭。“局外人”含有置身局外的意思,與“局中人”“局內人”相反,倒也切閤主人公默爾索的狀態。其實,原書名在法語是個極普通的詞。而漢語“局外人”則非同一般,譯齣作者在小說中賦予這個普通詞的特殊內涵。不過,話又說迴來,中法語言文化畢竟差異極大,尤其抽象的概念,很難找到完全對應,完全對等的,就拿“局外人”來說,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指與某事無關的人”,這恐怕難以涵蓋加繆在哲理小說中使用這個詞的意義。因此不免産生一問:局外究竟何人?
加繆第一部哲理小說就用“局外人”來界定默爾索這個人物。盡管在此後的作品中,加繆並沒有把具有他的哲學血統的人物統稱為“局外人”,但是《局外人》這部小說影響太大瞭,後來的人物不管叫什麼名字,我們總不免認為,他們都屬於“局外人”這一族群。因此,如能確認這一族群是什麼人,也就等於抓住瞭加繆哲學最鮮活的成分。
加繆就斷言,“偉大的小說傢是哲理小說傢”,他還列舉齣幾位,有巴爾紮剋、薩德、麥爾維爾、司當達、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馬爾羅、卡夫卡。他們和加繆有一個共同點,都不自詡為哲學傢,卻用充滿哲理的小說創造齣自己的世界而成為偉大的小說傢。他們善於將抽象的思想化為血肉之軀,而這種“肉體和激情的小說遊戲的安排,就更加符閤一種觀看世界的需求”。他們的作品,“僅僅是從經驗上剪裁下來的一塊,僅僅是鑽石的一個切麵,閃耀著凝聚在內中無所限製的光芒”。這種作品,“既是一種終結,又是一場開端”,往往是一種“不做解釋的哲學的成果,是這種哲學的例證和圓成”。
加繆講得再清楚不過瞭:這種小說是觀看和認識現實的工具,是哲學的成果,但是也“要有這種哲學言外之意的補充,作品纔算完整”。哲理小說與哲學論著的這種相互依托的關係,我們雖然知道,而由作者齣麵這樣強調,我們就無須多慮瞭。不過,也不是一路暢通無阻,作者又特意提醒一句:“小說創作也像某些哲學作品那樣,可能呈現相同的模糊性。”而這種模糊性,恰恰又是《局外人》這部小說的一個突齣特點。也許正因為如此,這部短短的中篇小說,足以引齣數不勝數的分析評論文章和專著。因而,要弄清楚局外何人,還得透過小說中的這種模糊性,抓住加繆真正要錶達的意思,進而瞭解他所創造的“局外人”齣沒的世界。幸好,加繆又來引路瞭,他在《西緒福斯神話》中寫道:
在象徵方麵,要想掌握,最可靠的辦法就是不去撩撥,也不帶定見進入作品,更不去探究那些暗流,尤其是對卡夫卡,必須老老實實順隨他的筆勢,從錶層切入情節,從形式研讀小說。
加繆在談他如何研讀卡夫卡的荒誕作品。既然指齣瞭門道,就不要隻看熱鬧瞭。照加繆所說,最可靠的辦法有三不要:一不要隨意撩撥,這意思可就寬泛瞭,藉用時下的字眼兒,就是不要太任性,不要施展望文生義,見微知著,舉一反三的本領;二不要帶著定見進入作品,抱著定見必然心浮氣躁,匆忙質疑,自顧高談闊論,結果南轅北轍,與作品毫不相乾;三不要探究暗流,隻因暗流湧動,根本無從探測,反而捨本逐末,難說不會被暗流吞沒。要做的就是老老實實,步步緊跟作者的思路,哪怕不大理解。這樣還嫌不夠,加繆又進一步說明:
卡夫卡的秘密,就寓於這種根本性的模棱兩可之中。在自然和異常,個體和萬物,悲劇性和日常生活,荒誕和邏輯之間,這種恒久的搖擺,貫穿瞭卡夫卡的全部作品,就應該曆數這些反常現象,就應該強調這些矛盾。
是否可以說,加繆的秘密,也寓於貫穿他的作品的模糊性之中呢?雖然不能生搬硬套,但是荒誕作品之間,即使作者寫作風格迥異,也必然帶有根本性的相通之處,譬如在自然與反常之間等方麵,都同樣描述瞭大量的“反常現象”,都同樣錶現瞭重重“矛盾”。這就是為什麼加繆特彆強調,要想理解荒誕作品,就必須認真看待這些反常現象、這些矛盾,這也正是上段引文的結尾,“從錶層切入情節,從形式研讀小說”,加繆所說的意思。
現在,我們就從一處錶層,切入《局外人》的情節:一聲震耳欲聾的脆響,“一切都開始瞭”。分為兩部的小說,就好像故事從此開始,默爾索這個小職員在第一部講述的日常生活,從此全一筆勾銷,頂多能充當一件命案的證明材料瞭。“我明白自己打破瞭這一天的平衡,打破瞭海灘異乎尋常的寂靜,打破瞭我曾覺得幸福的平衡和寂靜。”隨後,他又對著那不動的軀體連開四槍,“在厄運之門上急促地敲瞭四下”。
“我明白”,這隻是默爾索的慣性思維,其實他並不明白,僅僅意識到惹上麻煩,而敲瞭四下厄運之門,是他最終纔明白過來的。第二部的情節,就在不明不白中展開瞭,起初,似乎沒人對他的案子感興趣,可是不知何故,過瞭一周,情況完全變瞭。預審法官麵帶好奇的神色打量他。這“好奇”裏麵就大有文章,默爾索被盯上瞭,隻是他還意識不到,也不可能有所警覺。因而,他迴答預審法官說,是不是非得請律師,“我認為自己的案子非常簡單”。預審法官便微微一笑,說道:“這是一種看法……”第二次審訊,預審法官問他是不是個“性格內嚮,寡言少語的人”。默爾索迴答說:“事齣有因,我從來沒有什麼重要的話要講,於是就保持沉默。”預審法官還像上次那樣微微一笑,承認這是最好的理由……
兩次預審,看上去十分簡單,波瀾不驚。然而,這正是加繆文筆的高妙之處,於無聲處聽驚雷,簡單中潛行著復雜的矛盾與衝突。且不說預審法官話裏有話,單看他兩次“微微一笑”,象徵什麼,就足夠人尋味的瞭。細品《局外人》中的這種暗筆,堪稱奇絕,筆墨之細,隱義之妙,真是妙趣橫生,令人無限遐想。我特彆欣賞我國這句古話:哭是常情,笑乃不可測。法官的笑就更加不可測瞭。
在不明不白的審案當中,還不乏滑稽可笑的場麵。預審法官說不找律師,就會給他指派一位。默爾索錶示這樣太方便瞭,司法機關連這些具體問題都負責給解決,他便同法官一緻得齣結論:法律製定得很完善。而且對法官這個人,他也覺得“非常通情達理”,“善氣迎人”,要離開審訊室時,甚至想同法官握手,幸好及時想起自己有命案在身。一次次審訊,法官和他的談話變得“更加親熱”瞭,甚至讓他産生瞭“親如一傢”的可笑印象;有時法官還把他送到門口,重又交到獄警手裏之前,拍拍他的肩膀,親熱地對他說一句:“今天就這樣吧,反基督先生。”
這種反襯手法的巧妙運用,更加突顯瞭荒誕的效果。而且怪得很,話說得越明確,意思就越模糊。經過數月審理,按預審法官的說法,默爾索的案子“進展反常”。可是確知他不信上帝之後,預審法官對他就沒有興趣瞭,“事情就再也沒有進展瞭”,已經把他的案子“以某種方式歸類瞭”,還打趣地稱他為“反基督先生”。案子進展怎麼叫“正常”,“再也沒有進展”又從何說起;而案子“歸類”似乎很清楚,“以某種方式”,又意味有多少令人猜不透的名堂。
總之,這部《局外人》感覺有點怪異,翻譯時覺得很明白,文字典雅,既簡練又明晰,可是再讀起來,似乎變得令人神經過敏瞭,仿佛隨處都話中有話,並不像錶麵文字那麼簡單。而且主人公默爾索,也越來越讓人捉摸不透瞭,他原本就是局外人,還是腳踏局內局外的人,抑或是從局內走嚮局外的人呢?本來不成問題的事,一讀再讀反成為問題瞭。下麵引齣一小段,看看我是不是有點疑神疑鬼:
(預審法官和律師)有時候談到一般性問題,也讓我參加討論。我的心情開始輕鬆瞭:在這種時刻,誰對我都沒有惡意,一切都顯得那麼自然,那麼按部就班,錶演得那麼有闆有眼,我甚至産生瞭“親如一傢”的可笑印象。
就拿這段文字來琢磨默爾索這個人物,我們還是迴到那聲震耳欲聾的槍響,“一切都開始瞭”,能說他一切都明白瞭嗎?恐怕未必。否則,他揣著明白裝糊塗,哪兒來第二部這一場場好戲呢?我們不能懷疑他的心情開始輕鬆瞭,這就錶明,他,並不完全明白,因而纔能不由自主地配閤對方演成好戲,一時還預測不齣他敲響瞭厄運之門。但是,這段話一連串的錶達方式:“顯得那麼自然”,“那麼按部就班”,“錶演得那麼有闆有眼”,還把“親如一傢”打上引號,稱為“可笑印象”,這些足以說明他有清醒的判斷。明白不明白是一迴事,但是局外人始終保持清醒。加繆在《西緒福斯神話》中談到荒誕人時,有這樣一段話:
一個富有荒誕精神的人隻是判斷……他頂多能同意利用過去的經驗確定自己未來的行為。時間將激活時間,生活支持生活。在這個既局限又充滿可能性的地盤上,他覺得除瞭清醒,他本身一切都是不可預測的。
荒誕人在有限而又充滿可能性的生命中,他本身除瞭清醒,一切都是不可預測的,這是荒誕人的一大特點。讓我們看看默爾索是否具備。在人生的兩大問題,工作和愛情婚姻上,默爾索超乎尋常的清醒態度,集中錶現在第一部第五節中。老闆打算在巴黎開設辦事處,有意把這個美差交給默爾索,這樣既能生活在巴黎,每年又有齣差旅行的機會,認為他年紀輕輕,應該喜歡那種生活。不料他隻是淡淡地附和一聲是啊,內心深處卻覺得無所謂。於是老闆就問他,是不是對改變生活不感興趣,他就明確迴答說:“人永遠也談不上改變生活。”這是默爾索對人生的一種根本認識,而這種清醒的認識貫穿全書的始終,也體現在愛情和婚姻上。女友瑪麗問他,是否願意同她結婚。默爾索迴答這對他無所謂,如果她願意,就可以結婚;瑪麗還問他是否愛她,他還是那個話:這毫無意義。
“毫無意義”和“無所謂”,幾乎成為他的口頭禪,用來對許多事情,乃至如工作前程、愛情婚姻這樣人生重大問題的錶態,顯然不近情理,毫無誠意,沒有講齣真實的想法,因而被人看成是個“怪人”。粗讀這部小說,默爾索也很容易給人留下這種印象,就覺得他說話辦事不痛快,該講的話不講,顧左右而言他。也許正是他這種寡言少語的性格,給養老院工作人員造成誤解,也正是他這種不配閤的態度,惹惱瞭辦案人員,結果開庭審判時不利的證詞和道德審判氣氛,導緻齣乎意料的重判: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將他在廣場上斬首示眾。庭長宣判完,最後問他有什麼話要說。他略一思索,隨後便迴答:“沒有。”為什麼無語,這種後果,似乎他自身也有幾分責任。帶著這樣的疑問細讀,卻發現在關鍵時刻,默爾索一反模棱兩可的態度,哪怕是對自己不利,也果斷地錶明態度,甚至斷然說“不”。下麵就節選一段律師同他的談話,具體看看在什麼情況下,他說話有些含混,而到瞭什麼火候,又有明確的態度。
“要知道,”我的律師對我說道,“問您這種情況,我實在難以啓齒,但是這又非常重要。如果我找不齣理由答辯,這就將成為指控您的一個重要證據。”他希望我能協助他。他問我,那天我是否感到難過。
律師告訴他,辦案人員調查瞭他的私生活,還去過馬倫戈的養老院,預審法官都獲悉葬禮那天,他“錶現齣瞭無動於衷的態度”。律師無疑憑經驗,認為這是個要害問題,料想檢察官會抓住他在母親葬禮時的錶現大做文章。可見,律師是從專業的角度,也從被告的利益齣發,提齣這個不近情理的問題,要求默爾索予以協助。
聽到這樣一問,我十分驚訝,如果是我不得不提齣這個問題,我都會感到非常尷尬。不過,我還是迴答說,我多少喪失瞭捫心自問的習慣,很難嚮他提供這方麵的情況,自不待言,我很愛媽媽,但是這並不能說明什麼。所有精神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過自己所愛的人死去。
默爾索十分驚訝,可是他的迴答更讓彆人驚訝。他說很愛媽媽,隻要接上一句:媽媽死瞭心裏當然難過,他非但不這麼迎閤一句,反而話頭一轉,“這並不能說明什麼”,一下子就勾銷瞭。尤其不該藉題發揮,無端將所有精神正常的人都橫掃一下,簡直就是不打自招,承認也曾盼望過自己所愛的人死去。律師的反應可想而知,他當即打斷默爾索的話,焦躁地讓他保證:“無論到法庭上,還是在預審法官那裏,都不要講這樣的話。”話說到這份兒上,但凡知趣一點兒,應對一聲也就算瞭。然而,默爾索偏不。
可是我卻嚮他解釋道,我天生如此:生理的需要往往會擾亂我的情感。安葬媽媽那天,我疲憊不堪,又非常睏倦,也就沒有留意當時發生瞭什麼情況。我所能肯定說的是,我真不願意媽媽死瞭。
律師沒法兒滿意,便思考一下,幫他齣瞭個主意,可不可以說那天,他控製住瞭心中自然的感情。默爾索斷然拒絕:“不可以,因為這是假話。”律師神情古怪,似乎有幾分反感,帶點幸災樂禍的口氣說,這可能將他置於難堪的境地。他卻提請律師注意,這段事情跟他的案子無關,律師僅僅反駁瞭一句:顯然他從未跟司法機構打過交道。接著,默爾索有這樣一段記述:
他走時麵帶慍色。我很想留下他,嚮他說明我渴望得到他的同情,但不是為瞭獲取他更好的辯護,而是……可以這麼說,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是我看齣來,我讓他很不自在。他沒有理解我的意思,對我産生瞭一點怨恨。我真想明確告訴他,我跟所有人一樣,跟所有人絕對一樣。然而,費一番口舌,其實沒有多大用處,我也懶得講,乾脆放棄瞭。
......
李玉民
2015年5月於廣西北海
用户评价
這部作品的語言風格簡直是一場文字的盛宴,充滿瞭古典的韻味與現代的銳利感,形成瞭極其獨特的張力。作者對於詞語的駕馭能力令人嘆服,他似乎能從最尋常的詞匯中提煉齣不尋常的意象。我尤其喜歡其中描繪自然景物的段落,那些句子讀起來,仿佛能讓人真切地聞到空氣中泥土和青草的味道,看到光影在物體錶麵跳躍的痕跡。這種身臨其境的代入感,在很多當代文學作品中是很難覓得的。更難能可貴的是,這種華麗的辭藻並沒有成為敘事的阻礙,反而成瞭推動情感深化的媒介。每一次情緒的轉摺,都伴隨著語言風格的微妙變化,時而如清泉般平緩,時而似驚濤般洶湧。讀到一些深刻的哲思時,常常需要停下來,反復咀嚼其中的含義,感嘆作者是如何將如此宏大的命題,凝練成如此簡潔而有力的文字組閤。這無疑是一部需要細細品味,反復翻閱的書籍,每一次重讀,都會有新的領悟。
评分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最直接感受是震撼,一種關於“存在”的根本性拷問。它探討的主題非常深刻,但並非生硬的說教,而是通過人物在極端環境下的選擇和反應,自然而然地滲透齣來。我感覺作者仿佛在挑戰我們每一個人的常識和既定的道德框架。書中的角色行動邏輯,在初看時或許會讓人感到費解甚至憤怒,但隨著情節的深入,你開始理解他們的處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感同身受。這種強烈的代入感,迫使我必須跳齣自己既有的認知舒適區,去審視那些平日裏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規範和人際關係準則。它不是提供答案的指南書,而更像是一麵棱鏡,將我們生活的世界摺射齣許多意想不到的光譜。讀完之後,我發現自己對周圍世界的看法似乎有瞭一些微妙而持久的改變,對“何為真實”、“何為公道”的思考變得更加審慎和復雜。
评分從結構上看,這部小說的構建之精巧,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建築學上的傑作。它並非那種簡單地講述一個故事,而是像一個多維度的立體結構,不同的章節、不同的人物視角,都在相互參照、彼此映照,共同構建齣一個完整而又復雜的思想體係。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敘事視角轉換上的高明之處,時而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冷眼旁觀一切;時而又切換到某個角色的內心世界,體驗那種局促和無助。這種視角的頻繁切換,極大地增強瞭故事的層次感和厚度,避免瞭任何一方敘述的片麵性。讀到高潮部分時,那些先前看似零散的綫索如同被磁力吸引的鐵屑,猛然間聚閤在一起,形成一個邏輯嚴密卻又充滿意外的結局。這種嚴謹的邏輯和意料之外的驚喜並存的狀態,讓讀者在閤上書本時,感到的是一種智力上的極大滿足感。這本書無疑是對傳統綫性敘事的一次有力挑戰和成功突破。
评分這本書的整體基調是那種略帶憂鬱和詩意的,但這種憂鬱並非矯揉造作的愁緒,而是一種源自對生命本質的深刻洞察的沉靜。它的情感錶達方式非常內斂,往往是將最強烈的情感隱藏在最平淡的描述之下。比如描寫人物之間關係的微妙變化時,作者會用大量篇幅去描繪光綫、天氣或者某個物件的細節,而真正的情感湧動,卻隻在寥寥數語中點到為止,卻威力無窮。這種“此時無聲勝有聲”的藝術處理,需要讀者極高的專注力和共情能力去捕捉那些潛藏的暗流。對我來說,閱讀它更像是一種陪伴,一種與一個深邃靈魂的長時間對話。它沒有迎閤大眾的閱讀習慣,它要求讀者付齣努力去挖掘,但正是這種要求,讓最終獲得的閱讀體驗顯得尤為珍貴。這本書,絕對是值得反復品味、細細揣摩的佳作。
评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感極其齣色,仿佛作者手裏握著一把精密的指揮棒,將故事的起承轉閤控製得恰到好處。開篇的幾章,那種壓抑而又帶著一絲疏離感的氛圍,像一塊緩慢下沉的鉛塊,沉甸甸地壓在心頭。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構建人物內心掙紮時所使用的那種剋製而又精準的筆觸,沒有過多的渲染或煽情,僅僅通過人物的言行舉止和細微的心理活動,就將那種難以言喻的睏境和迷茫展現得淋灕盡緻。閱讀過程中,我常常會陷入一種沉思的狀態,思考著文字背後那些尚未言明的動機和選擇。那種感覺就像是站在一個巨大的迷宮入口,雖然暫時找不到齣口,但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環境的復雜性與深邃。故事綫索的推進並非直綫型,而是充滿瞭巧妙的迂迴和反轉,每一次看似不經意的細節鋪墊,最終都會在關鍵時刻爆發齣驚人的力量,讓人不得不拍案叫絕。這不僅僅是一部小說的閱讀體驗,更像是一次對人性幽微之處的深度探訪,讀完後,那種迴味悠長的感受,久久不能散去。
评分一直京东买东西,积累了太多商品没有评价,就不一一写评论了,总结一下近几年的购物体验,有不满意的时候,也有满意的时候,但总体来说,比较满意。无论是快递服务和售后服务都挺不错的,重要的是商品价格和质量整体来说都还不错,促销活动时还是比较优惠的。只是,近两年的活动似乎没有前几年的活动优惠力度大了。免运费门槛年年提升。什么加重费等。还有,现在满減券也十分有限,不是那么好领取,经常看着整点也抢不到券,这一点比较郁闷。所以想买某样东西时,看着它在活动满减,但自己却老是抢不到券,只能被迫放弃了!总之,希望京东能够一直保持进步和不断改善,在京东购买东西,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母婴用品以及图书音像等,主要是冲着它的品质价格以及服务,方便快捷,东西放心,才让人选择京东。所以,希望继绠保持这些优势。现在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鱼龙混杂,大家也很头痛,才不想去看更多,因为选择,所以信赖,所以,请不要让顾客失望
评分慢慢的品,这些书够我看半年的了,特别喜欢一句话:你读的书,会融进你的血液,成为你的底气。
评分《了不起的盖茨比》被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疯狂迷恋,深受村上春树、海明威等伟大作家的喜爱!
评分我为什么喜欢在京东买东西,因为今天买明天就可以送到。我为什么每个商品的评价都一样,因为在京东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导致积累了很多未评价的订单,所以我统一用段话作为评价内容。京东购物这么久,有买到很好的产品
评分东西不错..OK!这是一个好评模版,因为本大神很懒,不想每个商品都一样一样去写好评,所以特意模仿以一位网友写下这个版本,但是这个商品不管是质量还是款式肯定是本人喜欢的,如果不喜欢的话,收到本本大神会很生气的, 然后呢,这个模版肯定会变成心里喋喋不休的抱怨,最后当然不可能忘了给这个产品好评的,这个给各位淘友一个参考, 这个产品还是值得购买的一来在一位懒惰的, 只爱购物不爱写评论的却想换积分的大神,最后祝本大神和看到这条评论的帅哥美女都变的美美哒帅帅哒 东西不错..这是一个好评模版,因为本大神很懒,不想每个商品都一样一样去写好评,所以特意模仿以一位网友写下这个版本,但是这个商品不管是质量还是款式肯定是本人喜欢的,如果不喜欢的话,收到本本大神会很生气的
评分京东618搞活动,价格优惠挺多的,买了22本书,优惠下来才用了250多块,价格真心比较便宜,而且还有几本摄影的书,这些书籍比较贵。书的质量还可以,但有些书籍没有薄膜包裹,很容易被损坏。
评分这次京东的图书节活动很给力啊,买了很多书17本书才*元。这次有的看了。下次活动继续买。
评分手残 不小心点了两下,买了两本?
评分另行配送。同时京东商城在售后管理上也非常好的,以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 [Narziβ und Goldmun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89660/590fe08aNfaa64d1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