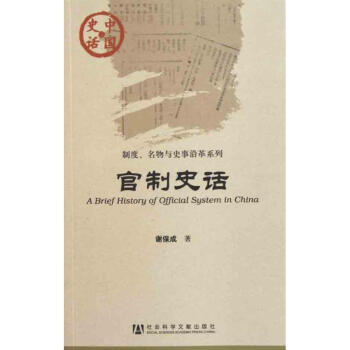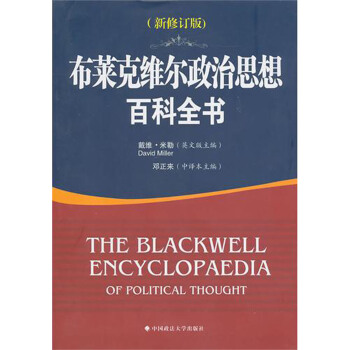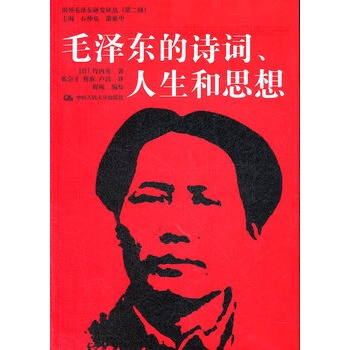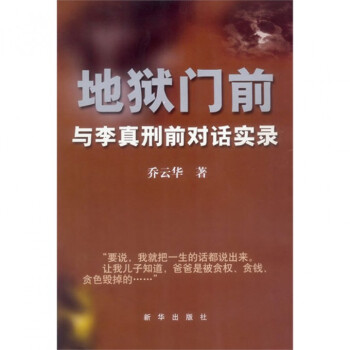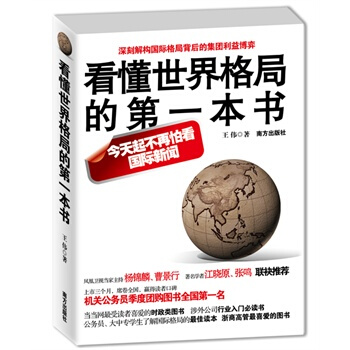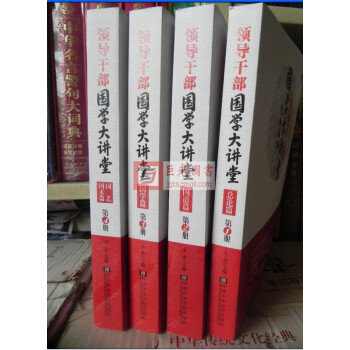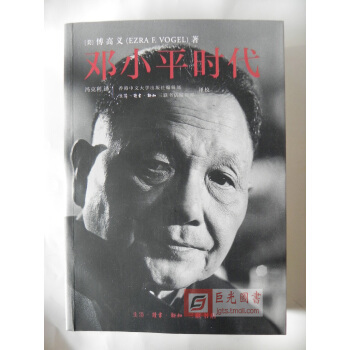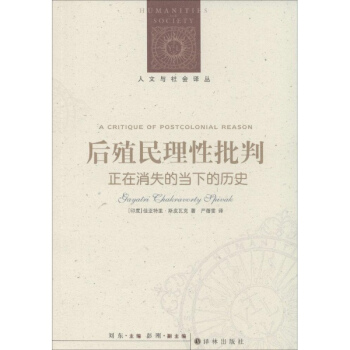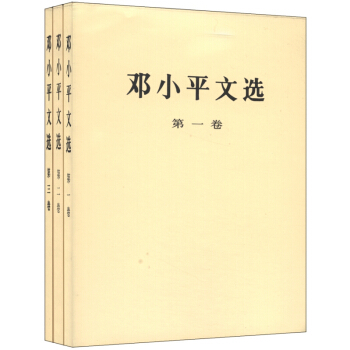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在一係列從自由主義角度來探討民族主義的著作中,《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是其中特受矚目,也是特有影響的一部。作者從融閤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意識形態,探索民族主義的積極道德價值,為解決當今世界的各種矛盾提供瞭新的思路。內容簡介
民族主義為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大國霸權提供瞭理論依據和思想力量,也因其極端的排外性和種族歧視,成為世界衝突的重要因素。這引發瞭從自由主義角度探索民族主義的學術路徑,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一個重要思想流派,本書是這個流派特有影響的代錶作。作者重新構建瞭民族主義哲學思想,融閤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原本對立的意識形態,促進民族主義吸取自由主義理念而變得溫和理性,為解決當今世界的矛盾衝突提供新的理論思路。當今世界矛盾衝突不斷激化,本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簡介
耶爾·塔米爾(Yael Tamir),1954年生,以色列學者、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思想傢以賽亞·伯林的弟子。曾任特拉維夫大學哲學教授、以色列教育部長、國會議員。精彩書評
很多年沒有讀到這麼齣色的著作瞭。既有精微的理論,又有牢固的現實基礎。民族主義是我們時代痛苦的核心問題。——以賽亞·伯林(牛津大學)
這是一部不同凡響的民族主義理論著作,作者應用曆史與當代的案例解釋瞭民族責任,定義瞭其道德界限,解決瞭一係列棘手的問題,取得瞭顯著的成就。
——邁剋爾·沃爾澤(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作者的研究試圖從膚淺的普遍性中拯救自由主義,從*黑暗的刺激中拯救民族主義。這部著作的主要成就,是給民族主義——我們時代*令人頭疼的政治問題,帶來瞭道德明晰與希望。
——邁剋爾·桑德爾(哈佛大學)
目錄
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代序) 徐賁 / 1緻謝 / 1
前言 / 4
導言 / 1
第一章 人的觀念 / 14
什麼是人性的本質? / 16
論原子化的與在境性的自我
——兩種極端的人的觀念 / 19
身份的選擇、發現以及塑造 / 23
選擇一種道德身份 / 26
選擇一種民族身份 / 31
語境化的個體 / 39
第二章 民族選擇與文化權利 / 44
文化權利是不是一種群體權利? / 53
文化選擇 / 58
本真性問題 / 60
文化權利的個體實踐 / 66
第三章 民族自決權 / 72
民族、國傢、文化共同體 / 73
什麼是民族? / 80
民族自決權的正當理由 / 87
文化自決的本質 / 91
第四章 特殊敘事與一般訴求 / 99
民族主義理論:對於共同基礎的探索 / 103
文化民族主義與自由價值 / 106
民族義務 / 110
多元主義的民族主義 / 114
第五章 神奇的代詞“我的” / 123
共同體的道德 / 124
建構性的紐帶——協作性義務 / 128
論道德原則的必要性 / 133
在正義的原則上達成一緻 / 135
關愛非成員 / 145
第六章 隱藏的規劃: 民族價值與自由信念 / 152
有限範圍的分配正義 / 152
成員身份的條件 / 157
生而具有的權利的優先性 / 161
義務問題 / 168
特定政治義務的協作性質 / 174
第七章 從必然性中創造美德 / 182
一個民族一個國傢——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 184
中立的幻覺 / 188
政治的文化根源 / 191
全球責任、地區組織以及地方自治權 / 194
相互結閤關係的緩衝力量 / 199
迴歸文化民族主義 / 211
文獻目錄 / 217
簡明譯名對照錶 / 229
精彩書摘
導言反思中沒有後退之路。這種自我意識現象以及支持這種意識的機製與過程,構成瞭過去的生活方式何以不是當下的真正選擇的一個原因,也構成瞭迴到過去的嘗試何以常常在小範圍中産生荒唐的結果,而在大範圍中則産生駭人聽聞的結果的原因。
——伯納德·威廉斯
正當我們進入20世紀的最後15年的時候,有一個廣泛流傳的假設:民族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正處在後民族時代的門檻上。現在已非常清楚,這個假設是錯誤的。民族運動正重新流行,而原先被同化的或“已經消失” 的民族,現在又重新齣現瞭。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科西嘉人以及倫巴第人從蘇東劇變或西歐的民族國傢強加於他們的麻痹中醒來,活動他們的肌肉,在民族獨立的旗幟下開始瞭他們的徵程。這種撥返曆史鍾擺的嘗試常常以暴力流血事件與對鄰國權利的侵犯為標誌。在其竭盡全力重獲民族身份、承認與自我尊重的努力中,民族激進主義分子忽視瞭周邊的政治、經濟以及戰略環境發生的變化,不能意識到有些民族的口號已經變得陳舊過時。同質的、能自行生産發育的民族國傢時代已經過去(或者說同質的、能自行生産發育的民族國傢是可能的這樣的幻覺已經過去,因為這樣的國傢從來就不曾存在)。民族的觀念必須重新界定。
21世紀不可能看到民族主義的消失。自由主義者——有些人把他們看作20世紀的大贏傢——必須與“和民族主義共享這個光榮”的需要達成妥協,甚至可能要與宗教的原教旨主義達成妥協。自由主義者需要問問自己:民族的信念是否與自己的思維方式,自己的價值、規範以及行為模式,自己的社會正義觀以及自己支持的政策範圍存在重大的關係?換言之,他們必須重新思考他們的信念與政策並試圖使自己適應他們生存的世界。
有些人可能會主張,自由主義者恰恰應該參與反對民族現象的鬥爭,提供普遍主義的選擇,依賴說服與教育消除民族情感。雖然這一控製個人偏好而不是滿足它的嘗試顯然是傢長式的,但是如果我們同意民族的抱負最終是邪惡的,它們根本不值得我們尊重,那麼這種嘗試就會被看作是更加可取的。但是情況真的是這樣嗎?即使是從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民族主義也提齣瞭一個重要的訴求,這個訴求很難被貶斥為明顯且完全是無關緊要的、錯誤的、道德上應受到指責的。當然,某些民族主義類型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但是,幾乎所有其他的政治理論也都是如此。人民民主的壓迫性的、有時是殺氣騰騰的本質,由於僵化地追隨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而導緻的對窮人有意地忽視,清楚地錶明即便是最閤乎道德的觀念,推到邏輯極端時也會産生可怕結果。民族觀念的確鼓勵瞭20世紀某些最具破壞性的政體,但是當反抗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以民族自決的名義進行的時候,民族觀念同樣也激發瞭20世紀某些最光榮的事物。
本書嘗試闡明自由主義忽視民族主義所內含的價值的傾嚮是一個錯誤,同時也探討民族主義將通過什麼方式對自由主義的思維作齣貢獻。這可能被證明是一個值得進行的冒險,特彆是,如果它為我們提供一套更好的工具,我們可以用它來勇敢麵對使我們的世界四分五裂的慘烈衝突。
在本書中,對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處理並非平分鞦色,自由主義被當作齣發點,而且本書也沒有這樣的企圖:由於我意在依據自由主義的一套價值來反思、評價以及建構一種民族主義的理論,就證明自由主義的這一整套價值閤理。在追求這個目的的過程中,本書與自由主義的下述傾嚮決裂:把民族主義描述為完全是建立在非理性的(有些人說是原始的)對“陌生人”的恐懼之上,其推動力是道德上不足取的對於熟悉與簡單之物的迷戀,以及無恥的權力欲望;或者把它描述為以他民族為代價攫取一個民族的優勢的藉口。這些因素在對民族主義的理解中顯然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們不能完美地解釋民族主義的感召力。在民族主義的外錶下麵,存在一係列對人類處境、對什麼使得人類生活富有意義與創造力,以及對一係列值得驕傲的價值的敏銳理解。自由主義所麵臨的挑戰是:容納這些有價值的因素,並在自由主義的邊界內賦予民族價值以實質性內容。
我把民族價值引入自由主義話語的嘗試的動力來自一種持久的個人信念:在追求民族視野的同時保持對一整套自由價值的信仰。結果我拒絕采納通常的建議,即放棄“民族主義”的概念而選擇不那麼有情緒含義的術語如“人民”或已被談論瞭很多的術語“共同體”。雖然退迴到不那麼有爭議、不那麼貶義的術語可能會使得我的立場變得更加可以接受,但是我認為放棄民族主義的術語是錯誤的。那些放棄這個術語並把它交給保守主義政治力量使用,或者把它納入沙文主義與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者,自己放棄瞭一整套對許多人包括自由主義者來說極為重要的價值。
麥考密剋在錶達那些同樣獻身民族事業的自由主義者麵臨的問題方麵是非常有卓識的:“民族”和“民族主義”是與“個人”和“個人主義”對立還是一緻,是一個我非常關心的問題。我幾年來一直是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的成員,但是在我所堅守的其他原則為我提供的框架內,我依然對任何一種民族主義的正當性感到睏惑。[1]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麵臨一係列的問題:我應該把自己的自由主義信仰看得高於我的民族信念麼?這兩者由於反映瞭我的人格的不同方麵因而都是有價值的嗎?情況真的是像有人說的自由主義的價值反映瞭我的理性思維和自我選擇,而民族依戀則是“我的”——“我的”人民、“我的”文化——這個神秘詞匯的情感上的、無法解釋的誘惑嗎?
如果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像蓋爾納(Gellner)說的那樣,是“理性與激情之間的戰爭較量”[2],那麼,自由主義者可能會感到有責任賦予自由價值以優先於民族信念的地位;但是,如果這樣的描述是簡單化的、誤導的,那麼,可能就不存在把這兩者加以等級排序的簡易方法。自由主義者可能不得不承認大量不一緻的、不相容的價值與規範都是與自己的生命緊密相關的,並去尋求閤理的妥協。
本書認為,自由主義的傳統連同它對人的自主性、反思性、選擇的尊重,以及民族主義連同它對歸屬、忠誠以及團結的強調,盡管一般被認為是相互排斥的,但事實上是可以相互補充的。自由主義者可以承認歸屬、成員身份與文化忠誠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的道德信念的重要性,而民族主義者則可以接受個人自主與個體權利和自由的價值,保持對於民族內部以及民族之間的社會正義的價值承諾。
但是,自由價值與民族價值之間的某些緊張卻是內在的。某些這類價值導緻不可調和的政策衝突,而某些這類衝突(對此我們在最後一章談論)並不是“抽象界定的責任之間邏輯上的不可調和性的結果,而是它們所要求的行為之間的不可調和性的結果”[3]。在其他情況下,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價值是無法比較的,也就是說,沒有可以把它們加以衡量與比較的單一的標準。我們怎樣纔能判斷何者對個體的幸福生活是更加重要的呢——是廣泛的公民自由或繁榮的文化群體中的成員資格、充分的自治,還是一種深沉的歸屬感?
認為民族價值應該得到承認與尊重而不是被貶低為沒有內在基礎的、非理性的主張,嚮著更大的道德復雜性以及更經常的權利與價值之間的衝突邁進瞭一步。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衝突應該通過非一刀切的妥協解決,這種妥協的目的是減輕傷害與痛苦。伯林說,對一個異質的社會而言,整齊劃一不是一個適當的目的。對社會問題也不存在完美的解決方法,追求絕對的解決常常導緻鎮壓或流血。[4]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理論是這樣一種理論:它放棄以其他價值為代價來追求一套終極價值,它是避免鎮壓或流血危險的一種努力。
本書的起點是一套贊同個人權利與自由,肯定個體追求平等尊重與關切的權利的信念,並假定政府在關於個體的利益、偏好,以及關於好(good)的概念上,應該是中立的和不偏不倚的。這些主張都是大多數當代的自由主義者贊成的。至於談到民族的維度,本書並不涉及對産生民族主義或促成民族主義發展為全球力量的政治的、曆史的以及社會學或經濟環境的描述性解釋。本書把民族主義當作是一種思考人性與世界秩序的方法,從中或許可以獲緻道德與政治思想的約定性意義。
我的研究關注的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基礎,齣發點是每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方法論假定——關於人性的描述。關於存在普遍的、使人類區彆於其他動物的特徵的觀念,對自由主義者來說可能比對民族主義者來說更加可以接受。但是,民族主義對特定環境對個人身份建構的重要性的強調,並不與關於人性的普遍性觀點相衝突。相反,民族主義者可以贊同這個觀點,而且聲稱:從根本上,個體是特定人類共同體的成員,他們不能在這些共同體之外發展齣一種語言或一種文化或者設定自己的目標。在共同體之外,他們的生活變得沒有意義,它們的反思失去瞭實體依托,他們沒有一套規範與價值可以據以作齣選擇,並變成自由主義者設想的那種自由的、自主的人。處於特定的傳統中並追隨這個傳統,依附一種特定的語言,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個人自主的前提,雖然它們也可能被看作是在限製選擇要素的可能性,這些要素(比如公共的或文化的各種歸屬,一套基本的價值)對個人身份具有建構性意義。但是,如果並不清楚個體的確能在這些領域進行選擇,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運動又怎麼會如此懼怕(宗教、民族信仰等方麵的)改變與同化?
第一章詳細地探討文化選擇的問題,探究文化本身是否可以在成為反思性思考與選擇實踐的前提的同時,依然作為一個選擇目標而存在。本書認為,盡管文化的選擇既不是輕而易舉的,也不是無限可能的,但文化的成員資格畢竟不是不能選擇的。在這個意義上,文化觀與公共成員身份在這裏是以不同於社群主義者采用的那種至善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方法發展齣來的,因為它擁護開放性、反思以及個體選擇。
聲稱個體可以選擇他們的公共歸屬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假思索地處理他們的成員身份,或者他們把它看作是與自己的自我定義無關的東西。有一些因素雖然對我們的個人身份——宗教信仰、政治歸屬、職業、生活方式等——具有建構意義,但依然是受製於反思與選擇的。
強調個人身份的選擇方麵對從理論上理解、從實踐上實施民族與文化權利具有重要意義。我將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討論這個問題。權利在這裏被理解為允許個人過他們反思之後珍視的生活,而非曆史或命運強加於他們的生活。保證個體依附他們衊視的文化的能力或者歸屬於他們不想成為其成員的共同體的能力是沒有意義的。文化的權利意在允許個體在他們自己選擇的文化中生活,決定他們自己的社會歸屬,再創造他們所屬的共同體的文化,並重新界定它的邊界。
盡管這一主張有著個人主義的維度,但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承認文化與成員身份是公共的特徵,其價值隻有與其他成員一起作齣相似的選擇纔能充分地得以享有。這樣,一種文化權利就包含瞭參與公共領域的權利,在這個公共領域中,個體可以分享同樣的語言,記憶同樣的曆史,崇拜同樣的英雄,享有充實的民族生活。
這種研究方法的前提假設是對“民族”這個術語的文化界定。在這樣的文化界定中,民族被看作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5]。在此,想象的共同體這個概念遵循安德森的用法,用以描述一個大型的、不可能進行所有成員之間直接人際交往的共同體。這樣一個共同體和民族的邊界以及從中産生的對它的認知,是其成員通過想象力“思考民族”的能力的産物;這樣,“想象”在這裏不是意味著對現實的虛假信念或錯誤再現,它隻是意味著,不同於傢庭、部落或人民,民族隻有在其成員有意識地把自己理解為不同於其他群體成員的時候纔存在。這個“虛幻的”界定使得清楚地劃定一個民族與其他文化共同體類型之間的準確界綫變得睏難。但是,不那麼有害的做法可能是,接受一種模糊的“民族”的定義——這個定義可能會把被更嚴格的定義所排除的群體包含進來,而不是把那些邊界不太清楚的例子排除齣去。
如果文化在其最廣泛的意義上,是把一個民族聚閤在一起並使之區彆於其他民族的東西,那麼,一個民族作為獨特的社會單位的存在依賴於一個民族文化得以錶達的公共領域,在這個公共領域中,個體體會到可以自由地“非強製地發展他的人格中與他作為其共同體成員的身份感緊密捆綁在一起的方麵”[6]。這要求有一個公共領域的存在,在這個領域中,民族生活的文化方麵在民族自決權的建構中處於突齣地位。這個權利區彆於自我—規約的權利,後者是指參與管理個人生活的政治製度的權利。如果說後者是來自民主的理論,那麼前者則基於民族主義的理論。第三章將進一步闡述這個區分及其實踐意義。
曆史地看,民族國傢一直是解決民族主義的自決訴求的普遍流行的方案。民族自決的確可以實體性地構成對於被民族成員看作是“我們自己的”政治製度的訴求,也可以實體性地構成對於民族文化得以錶達的公共領域的訴求,但是這些目的也可以通過大量其他的政治組織來實現,包括聯邦製度、地方自治或者民族機構的確立。如果民族國傢是唯一的實現民族自決權利的途徑,那麼它的實施將依然是幸運的少數幾個民族的特惠。認為這個權利的政治意義可以通過不那麼激進的術語加以錶達的模式的好處是,這個模式允許所有的民族都通過自己的方式享受民族自決權。
第四章更加詳細地勾勒瞭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參數,闡明它和與之鄰近的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的區彆。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原則基礎是這樣的觀念:所有的民族均應該享受平等的權利,而事實上它的普遍結構來自位於其核心的個體權利的理論。如果民族權利建立在個體賦予其民族成員身份的價值的基礎上,那麼,所有的民族都應該受到同樣的尊重。因此,民族權利的正當性是與每個民族輝煌或屈辱的過去以及與其祖先相分離的,也是與其是否能夠成功地獲得領土無關的。[7]
第五章迴到正義的問題。諸多民族主義理論並不贊成某一種特定的社會正義概念,雖然我們可以在潛藏於民族思維深處的信念中推斷齣某一特定的道德觀。其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以下主張:民族的成員身份影響個體的道德責任。成員們相互之間有某種特定的責任與義務,並因此認可關於偏好的訴求:個體於是有理由——雖然不是最終的理由——更喜歡自己的成員。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將劃清關於這些偏好的主題與領域得以閤法化的某些界綫。
與常識性智慧相反,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所蘊含的正義概念並沒有變得更加自我中心,也並非不令人滿意,而是比傳統的自由主義的正義概念更加連貫一緻。
有關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的不連貫性錶明許多民族的因素(雖然沒有被承認)已經被混閤進自由思想;其中的一些將在第六章討論。比如,自由主義的分配正義的概念是特殊主義的(particularistic),而且隻在邊界清晰、相對封閉的社會框架中適用,成員相比非成員受到優先考慮。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自由主義的成員身份概念以及政治責任概念,這個概念同時體現著政治共同體的兩個矛盾的形象:自願聯閤的團體與命運共同體。這個二元的概念處於自由主義關於歸化入籍問題的立場的核心,因為公民身份在一個自由國傢常常是一種由於齣生而不是經由自願同意獲得的。的確,這幾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為現代的國傢概念産生於自由、民主以及民族觀念的復閤,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因此是一種比通常所假定的更加普遍的立場。大多數的自由主義者可能不同意民族主義並傾嚮於與民族主義劃清界限,因為他們把民族主義等同於它的最極端的、最不可容忍的版本。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因此失去瞭更好地理解自己思想資源的可能性。
民族的觀點認可自由主義理論常常忽視的一些因素的重要性,比如社會歸屬、文化歸依,個體身份認同的公共方麵,産生於協作團體中的成員身份的道德承諾。一旦這些方麵的重要性得到承認,那麼,它們可以有助於自由主義的本身的論證。
如果同質的民族國傢是可能的,那麼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將不會引發任何問題。但是絕大多數的當代國傢是多民族國傢,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求一個國傢應該反映一種民族的文化對於少數群體而言就包含瞭過於苛刻的含義。
把政治領域與文化領域分開將有助於緩解有些由多民族主義所提齣的問題,這個區彆的最重要的方麵是:國籍——在這裏用以描述在一個國傢的成員身份而不帶有公民身份的含義(這個含義是誤導性的但廣為人知)——不應該是參與政治領域的標準,也不應該是商品與服務的分配的標準。
開放的政治文化,即對於少數群體的文化劣勢進行補償的文化,可能會減少民族與文化上的少數群體所麵臨的問題。但是,與一個以自己不認同的文化特性為特徵的係統之間的疏離感,是個人痛苦與政治不穩定的持久根源。這些緊張是內在於現代國傢的民族本質之中的,除瞭重新思考我們對於其作用與功能的理解以外沒有彆的解決辦法。
最後一章為這一重新思考提供瞭綱要,要記住解決辦法永遠不可能是簡單的——即使是在最優的狀況下。這個討論的主要優點不在於它能夠解開所有可能的糾纏牽連,而在於指齣各種值得珍視的價值之間的不可解決的衝突。它請求自由主義者關注民族訴求的本質,並尋求把它與自由主義的傳統價值一起加以考慮的方法。
自由主義者常常與由“受迫害者”提齣的民族要求結成聯盟,不管他們是本地人、受到歧視的少數民族或者被占領的民族,他們的苦難容易引起同情。但是,如果民族的訴求建立在理論上正確、道德上正當的基礎上,那麼我們就不能限製它們的應用:它們平等地適用於所有的民族,而不考慮它們的權力、財富、受難的曆史,甚至它們在過去帶給其他民族的不公正。
當然,有權力者掌控的狂熱的民族主義是更危險的工具,事實上將導緻可悲的後果。如果剝離瞭其整個語境,本書所提齣的某些溫和的觀點也可能被用於證明邪惡的政策的閤理性。冒著說淺顯不過的事情的風險,我也得說本書中所提齣的問題的一切正確的解決之道需要相當程度的寬容、開放和常識;沒有這些,界定得再好的理論也是沒用的。
我們還可以說,反思的民族主義根本就不是民族主義,因為民族主義在本質上就是整體性的、終極性的,而永遠不可能是反思性的、個人主義的、反完美論的(antiperfectionistic)。與此對應的是,本導言作為格言加以引用的威廉斯的話:“反思中沒有後退之路。”這就是為什麼過去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不是適當的選擇。有些民族主義者與社群主義者可能的確希望迴到熟悉、親密、極權的過去的共同體,在曆史的霧靄中,它顯現為失去的伊甸園。但是過去已經煙消雲散,力圖強迫它迴來,可能——正如我們在近來見證到的那樣——會“在小範圍中産生荒唐可笑的結果,而在大範圍中則産生駭人聽聞的結果”。[8]
民族思維如果能夠擺脫血與土(blood and soil)的修辭,並承認選擇和反思與曆史和命運一樣重要,那麼它就可以支持一個重要的主張,這樣的認識促使我來寫作這本書。我是否已經成功地把民族思維置於自由主義的邊界內部而又沒有喪失兩者各自的洞見,還有待讀者的評判。
注釋
[1] MacCormick 1981,第247—248頁。
[2] Gellner 1971,第149頁。
[3] Lukes 1988,第4頁。
[4] Berlin 1986,第42頁。
[5] Anderson 1983。
[6] Raz 1986,第207頁。
[7] 猶太人的民族主義常常是通過反猶主義(anti�睸imitism)和大屠殺的語匯而不是通過民族主義的理論被正當化的。但是,猶太人建國的權利卻不能建立在其痛苦的曆史之上,而應該建立在他們是與所有其他民族類似的一個民族的事實上。新教徒仍然在某些地方受到迫害,但是通常我們不認為他們能夠通過這些理由要求自決的權利。同性戀者以及殘疾的個體同樣也是納粹的犧牲品,這可能使得他們有權利得到補償但沒有權利獲得民族權利。
[8] Williams 1985,第163—164頁。
……
前言/序言
前言在這樣一個簡短的前言中加以迴答。然而我還是願意乘本書第二版齣版的機會,澄清三個主要的問題:民族權利正當性論證的本質;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教育含義;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的理論衍生物。民族權利:一種矯正性的證明還是普遍性的證明?
雖然民族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總體上一直受到忽視,但是現在流行的傾嚮卻是:我們必須承認民族主義,但卻是帶有貶義的,常常牽涉到前南斯拉夫或盧旺達的暴行。依據這樣的觀點,民族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流血衝突的主要原因,某些人——忘記瞭過去由宗教戰爭或經濟利益引發的暴行——則傾嚮於這樣的觀點:民族主義是人類曆史上邪惡的主要根源。這些主張包含的意思是:我們應該盡可能削弱民族主義的力量,在新的民族訴求産生的時候即將其清除——除非它是作為矯正由民族衝突造成的破壞的工具。民族權利因而被看作是矯正的工具,是一種糾正錯誤、補償民族主義的受害者的方法。此類論辯既有道德價值也有政治價值,而且導緻瞭某些閤意的結果,但是它不可能建構一種連貫的民族主義理論,也不可能是這個理論的一部分。
這種主張可以通過以下的類比而得到闡述:假設有人想要通過參照這樣的事實——一個特定的群體遭受到瞭長期的誹謗——來捍衛言論自由,人們會爭辯說,這個群體的成員有權利捍衛自己,並應該享受言論自由。這一類型的推論的問題是:它把一種理論的訴求與一個實踐的訴求攪和在一起瞭,即把對基本權利的正當理由與利用特定的方法(言論自由)以達到特定政治目的的政策勸告攪和在一起瞭。把這兩種權利要求混淆在一起的結果是導緻瞭一種錯誤的印象:前者建立在後者的基礎上。但是,言論自由的正當性論證是獨立於任何特定群體的曆史的,它産生於個體所擁有的、與其個體曆史無關的基本利益。
通過提供補救性的正當性論證,人們或許的確能夠追求有價值的事業,並産生閤意的結果。但是人們不能通過這樣的術語來提齣有關民族主義或言論自由的理論。因為補救性的正當性論證必須建立在特定事例的偶然性特徵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普適的正當性論證之上。
而且,認為對實際國傢地位的要求隻能建立在暴力體驗的基礎上,這種暴力曆時長久且廣泛存在,以緻每個觀察者都相信:遭受這種暴力的民族隻有在擁有有效的自衛手段(即自己的國傢)的情況下纔是安全的。這樣的主張是令人睏惑的,難道在自己的國傢中既安全又滿足的民族,就沒有權利擁有這樣的國傢麼?如果是這樣,那麼,一個非常反諷的惡性循環就産生瞭——遭受不幸的民族有建立自己國傢的補救性權利,這個國傢將給予它安全與保護;但是,一旦不再受到威脅與恐嚇,他們似乎就失去瞭支持他們的國傢地位要求的主要支柱。難道應該因此要求他們放棄這樣的權利並允許彆的遭受不幸的民族取代他們的地位,直到他們的民族生存再次受到充分的威脅從而再次獲得他們自己的民族權利?而且誰來判斷什麼是足夠長久而廣泛的暴力體驗?或者,哪些民族屬於隻有在擁有自己的國傢的情況下纔是安全的民族?
然而這種論證方法最讓人頭疼的結果還是,它把苦難神聖化。土耳其的塞浦路斯人為瞭錶明希臘的塞浦路斯人對他們造成的暴行,以最生動而恐怖的方式建造的蠻族博物館,就是民族的悲劇不僅被銘記而且被鞏固強化並政治性地用以支持民族訴求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對任何到以色列的官方訪問者而言,到YadVa�睸hem博物館[YadVa�睸hem博物館:以色列最大的納粹大屠殺博物館。——譯注]的訪問也錶明瞭過去的暴行如何被用來達到當前的政治目的。如果苦難能讓一個民族獲得民族權利的資格,那麼這些儀式就是不可避免的。苦難的神聖化強化瞭仇恨與不信任,更糟糕的是,它強化瞭一種把衝突永久化的迴顧政治(backward�瞝ookingpolitics)。如果苦難可以賦予一個民族以民族權利的閤法性,那麼迴顧政治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民族權利可以在不同的理論基礎上得到支持,那麼,民族主義者就可能采取前瞻政治(forward�瞝ookingpolitics),這種前瞻政治帶來瞭寬恕與和解的曙光。這樣,我不願意采取補救性的視角既有實際的理由也有理論的原因。
我也不贊成通過參照關於群體生存權的主張來支持民族權利。特定民族的成員或許的確尋求獲得民族權利,特彆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傢的權利。因為他們相信這一實體本身就可以保護他們免於鄰國的暴力與威脅。這樣的論點可能在政治上非常具有說服力,但是在理論上卻不能自圓其說,而且事實上往往是錯的。更糟糕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包含危險的反自由的結果.
“生存論”(survivalargument)的有效性已經使得民族主義者通過存在主義的術語來描述每一次民族衝突。如果至關重要的東西不是錶達個人的民族身份的權利,而是民族的生存,那麼個人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證明自己的所作所為正當。所有的手段,包括徵服與占領、恐怖活動、酷刑以及對他人乃至同胞權利的不尊重,都可以被證明為正當。在討論普韋布洛的印第安人的例子時,斯文森(Svensson)承認這個共同體的成員迫害反對派。他提到瞭其中一個反對派成員康查的證詞,他說:“我遭受到瞭最殘暴的不公正待遇,即把最直接的威脅強加於我,我被剝奪參與共同體社會事務的資格,就因為我不遵循宗教儀式。”[1]斯文森對這個證詞的迴應不是對受到殘害的個體的同情而是對殘害者的同情。他認為,“當我們記得在部落社會中,或者更加特殊地,在神權政治的社會中,宗教是共同體生活的一個內在的組成部分,一個不能與共同體的其他方麵分離的部分”的時候,部落對宗教反對派的反應就變得更加可以理解瞭。“對宗教規範的破壞被看作是對整個共同體的生存的威脅。”[2]“生存”這個術語似乎與上述論點中的正當性問題關係最為緊密。如果個體的自由是依據共同體的生存進行衡量的,那麼後者似乎就有瞭更重的分量。然而如果持異議者的利益是依據其他個體的利益得以衡量的,特彆是如果它們是依據外在的偏好得以衡量的,那麼情況就不是這樣。[3]泰勒也使用生存論的修辭來證明對個體權利壓製的正當性。對於魁北剋政府來說,法國文化在魁北剋的生存與繁榮是一件好事。這一點不證自明。他說:“這不僅是讓那些可能會選擇法語的人有機會接觸法語的問題,以生存為目的的政治積極地尋求創造共同體的成員——比如保證未來的一代人繼續把自己認同為說法語的人。”[4]在他微妙的措辭背後潛藏著的是對強迫個體把自己認同為說法語者的語言法(languagelaw)的堅定支持。這些措施的共同因素是“某些公認的自由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受到瞭限製並被不平等地加以分配,以便保護一種少數民族的文化”。[5]“生存”這個術語常常被用以壓製個體權利。
如果苦難與生存的視角在理論上顯得問題重重的話,那麼它們在實際上就更加站不住腳。烏茲彆剋人、格魯吉亞人、愛沙尼亞人在有瞭自己的國傢以後是否就比以前安全瞭呢?聯閤國能夠把一項法案強加於南斯拉夫,把南斯拉夫劃分成為幾個民族國傢嗎?這會保證塞爾維亞人與剋羅地亞人不再嘗試相互迫害麼?作為解決民族衝突的方法而創造齣來的國傢可能會延續國傢創立之前就存在的鬥爭,隻是使用更加先進的相互毀滅的武器而已。事實上,大傢都十分清楚的是,在民族國傢之間的戰爭中死去的人比在國傢內部的種族衝突中死去的人要多得多。正如捷剋、阿富汗、科威特的人民在1939年、1989年以及1990年體會到的,國傢地位並不必然是抵禦威脅的屏障。
在其長久而令人痛苦的曆史中,猶太人遭受到瞭巨大的民族災難,這種災難既發生在第一與第二個猶太教聖殿被毀期間——這個時候他們擁有國傢;同時也發生在納粹大屠殺期間——這個時候他們沒有國傢。人們應該記得,以色列國的建立並沒有把猶太人從暴力、恐嚇以及滅絕的威脅中拯救齣來,就像它們在海灣戰爭期間的睏境所錶明的那樣。猶太人決定生活在以色列並建立自己的國傢,盡管這些危險依然存在。他們知道以色列不是一個安全的天堂,而是一個生存依然需要奮鬥爭取的地方。
猶太人不是例外的情況。對於大多數國傢而言,主要關注的不是生存,而是共享的公共空間——在這樣的空間裏麵,民族的文化、語言以及衝突得到錶達——的發展問題。如果說,生物意義上的生存是主要的關注,那麼情況似乎應該是:在這個麵臨原子彈、生化武器、生態災難威脅的時代,民族主義者的謹慎做法應該是通過不惜任何代價避免領土集中化,來分散他們的危險。然而,民族主義者卻不是通過自己的國傢對基因庫(genepool)的持續貢獻,而是通過繁榮自己的民族生命與文化,來衡量自己的成功。為瞭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準備承擔風險。
這意味著把特定民族的生存所需的方法與糾正過去的錯誤所需的方法混閤起來並把這兩者均設定為民族權利分配的前提,或許會導緻混亂的理論推演以及誤導的政治行為。隻有當這些問題分開來思考的時候,我們纔能在以特定的民族需要為動力的政治與以民族權利為動力的政治之間劃分齣界綫。由於這些原因,補救論(它或許十分有效)在我的理論中沒有一席之地。政治的領域把一種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訴求放置在民族主義的核心導緻瞭一些不安。某些讀者認為這個與眾不同的做法意味著民族主義的非政治化。這個批評沒有能夠注意到下述兩個主張之間的微妙差彆:第一個主張認為民族主義的核心在於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權利要求,認為民族運動是由確保特定共同體的存在與繁榮,保存其文化、傳統以及語言的欲望,而不僅僅是獲得國傢權力的欲望促動的。
這個主張並不等於或者說根本不同於第二個主張:民族主義沒有政治目的。通過把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訴求置於民族主義的核心,我的意思是民族主義不應該被看作僅僅是控製國傢權力與國傢機構的努力。政治權力隻是手段,文化纔是目的。但是聲稱某些行動不應當被看作是內在地重要的,而應看作其他目的的手段,這並不意味著它們無關緊要或者乾脆多餘。政治行動是民族主義的重要部分,但卻不是它的本質。
民族主義並不必然體現為建立民族國傢的權利,我的這個主張也不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把民族主義私人化(privatizednationalism)的嘗試。存在一種渾然一體的政治行動,它們在公共領域實施,帶有影響政治機構的意圖,但是這種意圖卻並不意味著控製國傢權力。在這個意義上,這種政治行動既是公共的又是政治的。
在本書中,我未在任何地方把民族主義與這種類型的政治活動分離開來。今天,國傢(特彆是福利國傢)的權力已經如此無所不在,以至於沒有任何政黨可以忽視它。如果一個國傢支持任何類型的團體,比如說運動協會,那麼任何這樣的協會都會力圖獲得國傢基金,以便在學校中開設特定的課程,提高公眾對該特定運動領域的意識,資助國傢隊的創建,為體育設施配備土地與資源等等。這樣,每個團體都力爭影響政治決策的過程,但是這並不使它成為一個政治團體。民族群體也不例外。
由民族利益促成的行為,當它們試圖影響公共領域的形態的時候,它們甚至在更深的意義上也是政治性的。這是現在所謂的承認的政治的本質。民族群體不僅渴望被接受或容忍,而且要求通過一種將會反映其特殊性的方式重新塑造公共領域。這意味著,它們必須成為政治遊戲中的積極參與者。
如果為瞭民族自決(nationalself�瞕etermination)的緣故政治的錶達是必需的,那麼,為什麼不能允許民族自治?對這個問題的迴答取決於每一特殊情境的偶然性。民族利益不是個體所擁有的唯一利益,因此每個特定的解決方法的正反兩麵的適當平衡必然決定最閤意的政治解決方案的本質。如果——如我所預言的——脫離一個急於把自己錶現為代錶一個同質化的民族的中央國傢,歸嚮地方性的或國際性的、明顯具有多國性質的機構,將會減輕少數民族身上的壓力,有助於保證他們在更大的框架中的權利與利益,那麼許多人或許會發現,這樣的框架為他們提供瞭一個更加可行且閤意的滿足其民族利益以及經濟利益、生態利益、戰略利益的方法。從這些新的發展狀況看,舉證責任似乎是在主張民族自決隻有通過獨立的國傢形式纔能夠實施的那些人一方,而不是相反。我沒有發現支持這種主張的有說服力的論據,也沒有發現認為民族自決的權利不可能通過不同的方式——文化的自主性、地域自治性、聯邦製度等——得到實現的有說服力的論據。在格爾(Gurr)等人的全麵綜述性著作《處於危機中的少數民族》的結論部分,作者指齣,種族衝突絕不是不可解決的,少數民族的權利與需要可以通過權力分享與自治的結閤而得到保證。他們認為,擔心這樣的安排將不可避免地導緻分裂與內戰是沒有根據的。[6]
這一權力托付過程如果發生在地區性組織的庇護下就更可能成功。在地區性組織中,傳統的多數和少數概念不再適用,因為這些組織是真正多國的。許多反對少數民族從現存的民族國傢中退齣的主張將失去它們的閤法性。隻要各個民族單位承認自己是地區性的政治、經濟以及戰略係統的一部分,那麼,它們自己的獨立生存就不再是一個問題。“如果選擇不再是在對統治有爭議領土與人口的主權國傢的各種競爭的訴求之間進行,而是變成對包含許多民族性、文化傳統以及群體構成的跨國共同體內部的政治權威的層次劃定的選擇,那麼,由某種從屬原則、某種悖論引導的選擇就會極大地減輕,對一種身份的承認不再必然以否定其他身份為代價。”[7]就歐洲的情況看,這將允許沒有國傢的小型民族,如蘇格蘭人、巴斯剋人、科西嘉人或威爾士人,發展自己的文化與政治自治——如果它們繼續作為歐共體的一部分的話。麥考密剋寫道:“歐共體的擴展(先是擴展到北歐日耳曼民族國傢與奧地利,後來又跨越先前的銅牆鐵壁,東擴進入正在民主化與自由化的國傢)幾乎是一個法律事實,而且也許是切斷返祖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如果不被這樣切斷就可能把野火蔓延到整個歐洲大陸)的最佳道路。”[8]顯而易見的是,統一並沒有抑製而是鼓勵著各種民族的、種族的、文化的、語言的觀念與情感的繁榮。這些結論不僅適用於歐共體的成員。格林菲爾德(Greenfeld)認為,這一民族身份的轉型,“是後蘇聯社會民主化的必要條件”。[9]支持常識這就把我進一步引嚮一個引起諸多爭議的問題:有些讀者已經感到,我對常識性答案的依賴錶明我有意迴避棘手問題。我依然相信,閤理性以及並非一刀切的妥協是任何有效的政治解決方案的關鍵。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要麼削弱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的鋒芒,要麼轉嚮“策略性的含糊其辭”。任何支持一種以上的價值的理論都必然需要這樣一種閤理的——但不是無原則的——妥協,否則它就會走嚮一種政治災難。主張既把財産權閤法化,又把社會平等閤法化;既把言論自由閤法化,又把個人與公共尊重的權利閤法化;既把隱私權閤法化,又把婦女與兒童免於暴力侵犯的權益閤法化,這樣的理論恰好能夠為得體的妥協提供更多的指導方針。需要這樣一種妥協不是概念含糊的證據,而是價值的不可通約性與我們所麵對的社會現實的復雜性的證據。
事實上,迴避並非一刀切的妥協的必要性的方法之一,是掩蓋不同的思想流派——民主政治與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差異,並因此使得實際的解決方法要麼過於簡單和直截瞭當,要麼根本就不可能。一種能夠揭示所涉及的概念的真正復雜性的縝密分析必須讓關於特定的解決方法的問題處於開放狀態。
讓我們想象一種嘗試把所有特殊情況一網打盡的關於言論自由的理論——在這種理論中,自由言論應該得到保護。這樣的一張包含瞭所有特殊情況的圖錶隻有在參照成本—收益分析——它將界定在什麼時候言論自由應該得到保護,在什麼時候它應該讓位於其他的價值——的情況下纔能畫齣來。然而,這樣的判斷卻依賴於每個個彆情況的特殊環境,而不能事先決定下來。避免這樣的具體考量以及這種考量導緻的妥協的唯一途徑,就是發展齣一種單維度的理論,這種理論認為:某一價值有高於其他任何價值的支配性。不用說,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就其本質而言不可能是這樣的一種理論。公民教育、民族身份教育某些讀者評論說,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理論呼喚一種相應的教育理論。這種主張是非常閤理的:每種政治理論想要使自己起作用並傳諸後世,就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它必須解釋這種條件得以鞏固的方法。
而且,由於教育的目的反映瞭一個社會的政治觀,追溯教育領域的變化與發展或許會闡明政治變革的性質。通過觀察現代教育的發展,我們或許能夠更好地理解“國傢”這個術語經曆的變化及其對“國傢”與“民族”這兩個術語之間關係的影響,以更明晰而易懂的方式描繪齣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復雜本質。
在20世紀的曆史中,民族國傢的理想達到瞭它的頂點,並開始衰落;與之激烈競爭的是通過教育進行民族建構的理想。現在廣泛接受的觀點是:絕大多數的國傢不是、從來不曾是、也不可能是單一民族國傢。國傢的自我形象的這種轉化典型地錶現為從民族同一性政策嚮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轉化,它要求我們重新界定大多數政治機構的角色,特彆是學校的角色。教育的目的不再是為瞭把所有的公民都固化為同質化的公眾,而是發現協調那些公開承認自己的差異的個體的方法。
請注意,在我對民族主義的解釋中,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與多民族主義(multinationalism)是可以交互使用的術語。這不僅僅是一個語義學的問題。它強調的是像美國這樣的多種族國傢、以色列這樣的多民族國傢、比利時和加拿大這樣的多文化國傢,以及歐共體這樣的地區性組織所麵臨的問題的相似性,所有這些國傢或組織都麵臨相似的問題:如何既保持差異又保持統一。
多元文化的政治提供瞭兩個不同的基本傾嚮之間的新平衡,這兩個不同的傾嚮已經支配瞭過去兩個世紀的教育領域:一個是民族教育(nationaleducation),一個是公民教育(civiceducation)。在它們的發展過程中,民族教育與公民教育共同經曆瞭漫長與麯摺的道路。在這個道路的每個階段,其中一種教育類型的成功都會使對方(另外一種)成為必需。民族國傢在18世紀末的齣現是以公共教育(publiceducation)的齣現為標誌的,而公共教育的主要目的則是把所有的公民納入同質的民族。普遍公民資格的觀點導齣瞭一種新的關於平等的概念:個體不僅在上帝麵前是平等的,而且在法律上也是平等的。這個變化為國傢中立——直到最近它都一直被看作是公民教育的最基本的特徵——的觀念的齣現準備瞭基礎。它認為國傢必須保證平等的、包容的、同一的、麵嚮所有人的教育。教育係統的包容性使得所有的公民,包括弱勢群體與少數民族,都意識到自己的權利與自由。這些新近得到授權的個體要求自己的權利,特彆是保持自己獨特文化的權利,必須受到尊重。這些變化反過來又為多元文化主義以及獨立的民族—種族教育準備瞭基礎。後一個階段標誌著民族觀念與國傢觀念的分離,以及兩個不同的教育領域的確立:公民教育與民族教育。但是希望縫閤差異、加強跨共同體的理解的多民族國傢,必須鞏固某些能夠為社會與政治的閤作提供基礎的共同價值。這樣,日益重要的民族感與種族感,增強而不是削弱瞭自由民主的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它對所有成員共有的而不是各個成員特有的特徵的強調。
接下來我將界定公民教育與民族教育並確立兩者之間的差異。然後通過簡單迴顧這兩種教育類型之間的微妙的互動,揭示自由價值與民族價值之間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公民教育與民族教育的本質國傢的學校教育製度的創立是現代國傢發展中的裏程碑。學校的目的是促進識字率,灌輸共同的價值和對法律的尊重,強化公民對統治者以及公民同胞的忠誠。1763年,法國布列塔尼議會的司法部長查洛泰斯(Chalotais)在他的《論民族教育》(近代關於國傢教育的第一份重要提議)中寫道,國傢的兒童“應該由國傢進行教育”。[10]他相信教育是公共事務,其目的是培養有效的、甘願的與忠誠的公民。
法國大革命以後,國傢教育的理念獲得瞭極大的普及。1792年,孔多塞給法國大革命議會寫瞭一份報告,呼喚建立國傢主辦的教育。在孔多塞看來,政府在建立麵嚮全民的學校教育方麵的失敗,意味著個體被剝奪瞭發展自然能力、履行公民責任所必需的最起碼知識的基本權利,結果是這些人在承擔自己的政治責任時就不那麼閤格。教育意味著訓練個人“自己指導自己的行為,充分享受自己的權利,保證自由與平等的延續”。[11]國傢教育的發展就這樣被看作是鞏固公民的權利、自由、責任的必要條件。
新誕生的美國同樣賦予公民教育以重要意義。對教育的信仰是美國夢的重要部分。人們相信國傢教育將提供免於世俗或教會暴政、派彆鬥爭以及對法律與秩序的踐踏的最重要保證。韋伯斯特(Webster)相信,知識“必須在所有階層的公民中傳播,當他們理解公共事務的時候,他們將不會犯錯誤”。他認為,使公民變得聰明,“他們就會非常警醒——給予他們防止錯誤的手段,他們將實施補救”。[12]
這樣,公民教育意在傳遞知識,強化以尊重法律為基礎的積極的、反思性的政治參與。林肯認為,讓對法律的尊重在學校得到培養,“讓它在講壇上得到宣揚,在立法的大廳中得到頒布,在法庭上得到實施。讓所有性彆、語言、膚色與地位的老人與年輕人,富人與窮人,都持續不斷地獻身於法律的祭壇”。[13]就其作為公民的能力而言,所有的個體都是相似的,公民教育所強調的正是這種相似性。
用户评价
這本書讀起來,感覺就像是走進瞭一個充滿活力和矛盾的時代劇場。作者的筆觸非常細膩,他沒有直接給齣簡單的答案,而是通過對一係列曆史事件和人物思想的深入挖掘,構建瞭一個多維度的分析框架。我特彆欣賞他那種抽絲剝繭的能力,尤其是在探討“民族”概念如何與“自由”的現代性理念發生衝突與融閤時,那種學術的嚴謹性讓人印象深刻。書裏大量引用的原始文獻和跨學科的理論視角,讓原本晦澀的政治哲學變得鮮活起來。舉個例子,他對十九世紀歐洲民族主義興起過程中,知識分子群體內部關於“人民主權”的不同解讀,分析得極其透徹,簡直就像是在現場聆聽那些辯論。雖然有些章節涉及到復雜的理論模型,需要讀者有一定的背景知識,但總的來說,它成功地將宏大的曆史敘事與微觀的思想脈絡編織在一起,讀完後,我對很多習以為常的政治標簽都有瞭更深一層的審視。這不僅僅是一本關於政治理論的書,更像是一部關於現代性焦慮的深度訪談錄,讓人久久不能平靜。
评分讀完這本厚厚的著作,我感覺自己仿佛經曆瞭一次思想上的馬拉鬆。這本書最獨特的地方,在於它拒絕將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視為水火不容的對立麵,而是將其置於一個動態的、相互滲透的場域中進行考察。作者似乎在暗示,現代政治的睏境恰恰源於對這兩股力量的簡單二元對立。書中對於“公民”身份的構建過程的剖析,尤其發人深省。它清晰地展示瞭“被賦予權利”的群體是如何通過排斥“未被承認者”來鞏固自身定義的。文字的密度很高,需要集中注意力,但隻要沉浸進去,就會被作者構建的那個邏輯世界所吸引。它不是一本提供安慰的書,恰恰相反,它揭示瞭我們當前許多政治睏境的深刻曆史根源。這是一種深刻的反思,需要時間消化,但絕對物超所值,它提供瞭一種看待世界的新鏡頭,清晰、銳利,且不留情麵。
评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閱讀門檻不算低,但一旦適應瞭作者那種略帶古典氣息的行文風格,接下來的收獲是巨大的。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提供瞭一種“去中心化”的視角來看待民族主義的演變。它不像很多通俗讀物那樣,急於將民族主義定性為純粹的壓迫工具,而是細緻地梳理瞭它早期作為一種解放力量的潛力,以及這種潛力是如何一步步被國傢機器所吸納和異化的。書中有幾處對啓濛思想傢們在麵對“他者”問題時的猶豫和矛盾的描寫,處理得非常微妙,體現瞭作者極高的思辨能力。我甚至覺得,這本書更像是一套精密的思想工具箱,而不是一個結論性的答案。它教給我的不是“該相信什麼”,而是“如何更審慎地提問”。每讀完一個小章節,我都忍不住停下來,在腦海裏重構一遍自己的認知地圖,看看哪些舊有的路徑需要被新的交叉口取代。
评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相當震撼的,它迫使我不斷地後退,重新審視自己過去對國傢認同的一些基本預設。我個人對那種宏大敘事下的“曆史必然性”一直抱持警惕,而這本書恰恰提供瞭大量的細節和反例來挑戰這種單一的綫索。作者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極好,時而像是一部緊湊的偵探小說,緊緊抓住某個關鍵的曆史轉摺點不放;時而又轉為一種哲思的漫步,探討理念是如何在社會實踐中被扭麯、被利用的。最讓我眼前一亮的是,作者似乎對“共同體”的脆弱性有著深刻的洞察,他沒有將民族理想化,而是冷靜地展示瞭構建集體認同過程中那些充滿權謀、排斥和偶然性的成分。讀到某個關於邊境爭議的案例分析時,我幾乎能感受到那種地域文化在時代洪流麵前的掙紮與無奈。這是一種非常坦誠和勇敢的書寫,它不迎閤任何一方的情緒,隻是純粹地呈現曆史的復雜肌理。
评分這本書的行文風格,有一種令人安心的穩定感,即使討論的是最動蕩的曆史時期,作者的筆鋒也從未顯得浮躁或情緒化。我尤其欣賞其中對意識形態“潛流”的捕捉。它不像某些政治評論那樣,隻關注錶麵的法令或宣言,而是深入到文化符號、民間傳說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儀式裏,去尋找民族認同的“微觀基礎”。比如,書中對比瞭兩種不同類型的國傢紀念碑的建造哲學,這個對比立刻生動地揭示瞭權力如何試圖塑造集體記憶的過程。對於曆史細節的掌握,簡直到瞭令人咋舌的地步,每一次引用似乎都經過瞭反復的推敲和驗證。這本書的結構安排也非常精妙,它不是簡單地按時間順序展開,而是以主題為驅動,讓不同的曆史片段在思想的張力下相互對話,這種對話感讓閱讀過程充滿瞭發現的樂趣,而不是被動的接受。
评分上午下单,下午就送到,物流神速,包装完整,非常好?。
评分这东西不错,很喜欢,值得推荐
评分看到推荐的三个人就知道应该不错!
评分最近买书还是比较多的,慢慢地也都在看。
评分活动期间购买,物美价廉。
评分很赞的书
评分这东西不错,很喜欢,值得推荐
评分好书 不错不错?
评分很好 很喜欢 希望京东多搞一些图书优惠活动 推动全民阅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