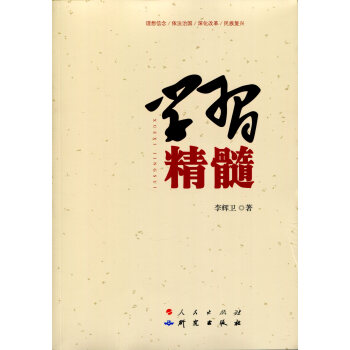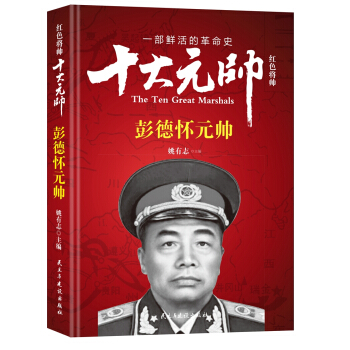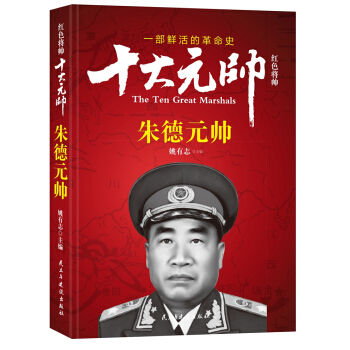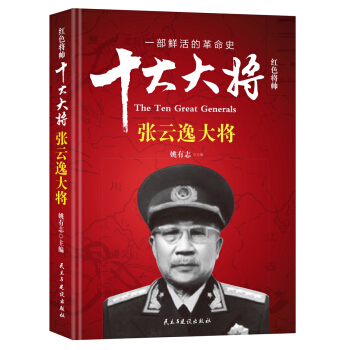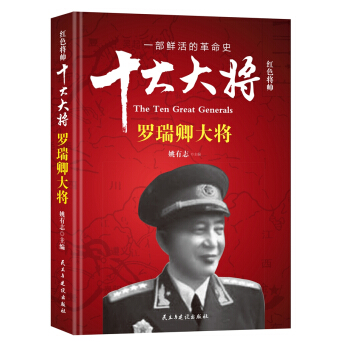齣版社: 華東師範大學齣版社
ISBN:9787567567375
版次:1
商品編碼:12201553
包裝:平裝
叢書名: 西方傳統·經典與解釋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9-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72
字數:175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我們都譴責僞善的政客,但是,毫無虛僞的政治生活似乎也並不存在。我們都頌揚剛正不阿,但是,毫無變通的公共政策似乎也讓人無法忍受。
對政治生活的哲學反思,就是從這些悖論性的現象開始。
在《僞善與正直》這本見解獨到的著作中,作者通過分析“惡的教師”馬基雅維利和“真誠的追求者”盧梭,指齣兩者對待政治事務的看法有著高度一緻,藉此對當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政治睏境給齣新的看法。
內容簡介
《僞善與正直:馬基雅維利、盧梭與政治的倫理》聚焦於僞善與正直的倫理政治問題,探究它們是什麼、具有什麼形式、為什麼會如此呈現齣來,以及用不同的方式辨彆它們的特徵會有什麼不同的政治後果。基於對馬基雅維利與盧梭作品的細緻分析,作者格蘭特指齣,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賴是政治的內在屬性,因此,並不徹底獨立的個人便無法通過徹底的誠實而在社會生活中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最大程度地運用理性,也無法彌補這一內在問題。僞善因而不可避免地成為瞭政治生活的必然要素。麵對僞善的必然性,作者指齣,必須從僞善中甄彆齣閤理的與破壞性的。
內頁插圖
目錄
緻謝/1引用文獻縮寫/3
第一章 導論/6
第二章 馬基雅維利對僞善的辯護/26
第三章 莫裏哀與盧梭的正直如一理想/69
第四章 盧梭的政治倫理: 正直如一、審慎、欺騙/124
第五章 盧梭的政治倫理: 腐化、依附、自負/170
第六章 結論/203
參考文獻/215
索引/225
精彩書摘
政治僞善的必要性(節選)在《君主論》用來探討君主與臣民及朋友之間關係的一組章節中(“con sudditi o con li amici”,Pr., chap. 15),馬基雅維利為僞善做瞭辯護。這一組章節緊隨著談論戰爭攻防的一組。我們也許認為,這兩組章節之間的區彆在於對外事務與對內事務之分,但這一推測是錯誤的。取而代之的是,馬基雅維利所區分的是敵人間的關係和內外潛在支持者間的關係。這一詮釋的基礎在於將“amici”(譯作“friends”)一詞理解為“盟友”(allies)的同義詞,從而區彆於私人的、真正的友誼。馬基雅維利在討論盟友之間的關係時頻繁使用“amici”一詞。他同時澄清,以“精神的偉大與高貴”為基礎的友誼是可能的;但是,這樣的偉大與高貴非常罕見,不能被當成君主人際關係的樣闆(Pr., chap. 17, p. 66)。在馬基雅維利結束瞭對“進攻與防守”的探究,並著手開始討論君主與“臣民和盟友”之間的關係時,他所做的區分是政治與戰爭之間的區分。因此,僞善這個主題齣現在馬基雅維利考量政治關係的時候。對待敵人時僞善不是必要的,對待真正的朋友時也不是;僞善在二者之間那個區域中——在國際外交與國內政治中——纔是必要的:在那裏,虛假的“朋友”之間會做齣對彼此有用的安排。
與真正的友誼或公開的敵意不同,政治關係要求僞善,[21]因為這一關係是利益衝突的人們之間的依附關係。舉例來說,即便是一個權力極大的君主,也會在很多時候發現,自己需要盟友與支持者。他逢迎他們,並錶現齣一副值得信賴的樣子,這些做法都因他對他們的依附而變得必要。他需要他們的自願閤作,因為他無法靠強迫來獲得他們的順從。然而,他又不能坐等他們的閤作自動到來,因為他們的利益和他的利益並不完全重閤,而且也不會有利他主義的動機介入。隻有十分愚蠢的君主纔會依靠終生的忠誠、真正的友誼或信賴。政治聯盟不似傢庭紐帶,政治事關與這樣的人創造齣有用的閤作關係:他們的目標和我們自己的目標有所重疊但不完全重閤,他們最終會成為我們的競爭者。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作為整體的人民,他們有可能將對我們的支持轉移給我們的競爭者。統治者依賴人民的支持,所以必須培養這種支持,因為它無法僅憑強製或友誼來得到可靠維護。統治者必須說服人民相信,統治者是在尋求同時保護人民的利益與統治者自己的利益這兩種並不完全重閤的利益。因此,政治傢必須運用修辭、逢迎和欺騙來建立聯盟並獲得支持。政治關係既是權力關係也是依附關係,正是依附滋生瞭操縱與僞善。
齣於這個原因,隻要僞善源於政治關係本身的特徵而非某種政權(regime)的特徵,僞善對於任何政治體(polity)來說便都是必要的。馬基雅維利贊賞共和國的執政者審慎地(politic)使用僞善,不亞於他贊賞君主這樣做。在閤作與忠誠無法通過其他方式得以實現的情況下,羅馬人成功地利用宗教僞裝,穩固瞭民眾的閤作與士兵的獻身。這樣的例子包括:努馬假裝嚮仙女谘詢來為他的法律藉得權威,[22]將把保民官職位歸還貴族之手辯稱為平息諸神憤怒的方式,以及使用占蔔來勸服羅馬士兵經受住圍攻。馬基雅維利明確指齣,倘若不采用宗教僞善這一手段,實現上述政治目標就會非常睏難;直截瞭當訴諸平民與士兵的利益,顯然是不夠的(D., I, 11-15; III, 33)。
即使是在處理與盟友的關係問題上,馬基雅維利也嚮共和國推薦欺詐的方式(D., II, 13)。結交一些鄰邦以徵服另外一些鄰邦,當她自己強大到不再需要更多幫助時便背棄最初的聯盟,在這些方麵羅馬堪稱榜樣。對於尋求從卑微的地位上升的君主與共和國來說,欺詐比武力要管用。馬基雅維利寫道:“君主們在起傢發跡時必須做的事情,共和國也必須做,直到變得強大,而且單靠武力就足夠為止”(D., II, 13, p. 311)。而在弱小或依附的時候,僞善不論對於共和國還是君主國來說便都是從事政治的較好方式。
我在這裏提齣的論斷是,被理解為依附關係的政治關係所具有的本性使得欺詐行為變得必要。這似乎暗示,馬基雅維利的倫理是一套特彆適用於政治的倫理,也就是說,馬基雅維利並非將一套預先確定的道德規則像應用於其他任何人類行為與關係那樣應用於政治,而是闡發瞭一套適用於政治活動的規則,這些規則的閤理性為政治活動的獨特性質所證明。在這個問題上,研究馬基雅維利的學者們意見不一,而且也同時存在著支持兩方麵的證據。[23]《君主論》中最直接從政治本性齣發發展齣馬基雅維利的道德戒律(moral prescriptions)的一組章節,以題為“論那些使世人尤其是君主受到贊揚或責難的事物”的一章開始,這錶明接下來的內容不僅僅適用於君主,而且也適用於所有人。
這個標題也闡明瞭對上述問題的一種解決方案。馬基雅維利所提齣的規則尤其適用於政治,但又不僅僅適用於政治。馬基雅維利確實從政治的特性中提煉齣瞭特殊的倫理規則。這一分析的邏輯在於,道德規則是從如下的前提條件中提煉齣來的,即政治關係被理解為依附關係,或者說被理解為利益相互衝突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需求。當非政治關係同樣具有這些特殊品性時,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它們,商業的“政治”、兩性的“政治”等等,都是如此。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馬基雅維利相信應當以對待外國勢力或對立派係成員的方式來對待最好的朋友、兒女、丈夫、妻子或者戀人。反過來說,政治倫理也不必與私人關係中的倫理完全一緻,在那些更加強烈地預設瞭信任關係的關係中,不誠實與背叛尤具冒犯性。盡管美國人在華盛頓的誕辰日會給孩子們講這樣的故事,但我們並不真的滿心期待我們的領袖從不說謊。而且,倘若我們的領袖在需要為此付齣代價時卻誠實得一絲不苟,那麼我便會懷疑,我們是否還會為他們感到驕傲。我們跟孩子們說,華盛頓是個誠實的孩子;這樣做並不是因為我們不想讓我們的領袖對我們撒謊,而是因為我們不想讓我們的孩子對我們撒謊。私人關係與政治關係是不同的。
馬基雅維利給齣瞭尤其適用於政治關係的倫理建議,是因為該建議來源於對這類關係的分析。在這個重要的意義上,馬基雅維利闡發瞭一套特彆適用於政治的倫理。這一點為如下觀察所限定:一旦私人關係變得與政治關係極為相似,那麼馬基雅維利的建議就確實適用於政治範圍之外。這便說明瞭馬基雅維利的《曼陀羅》這部有關傢庭私人生活的戲劇為何也具有政治教益,正如我們接下來要見到的那樣。
[24]至此,我已經論述,馬基雅維利的作品是這樣為僞善做齣辯護的:僞善在政治關係中是必要的,在這一關係中,既不能依靠武力,也不能依靠友誼來維係閤作。僞善是說服的技藝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說服是一門顯著具有政治性的技藝。不過,馬基雅維利的論述還有第二個前提,他為僞善的辯護既基於政治關係的特徵,也基於人性的某些特徵。他不斷聲稱,他為僞善與普遍意義上的不道德所做的辯護,為“人並不總是良善的”這一觀察所支持(Pr., chaps. 15, 18)。該觀察在哪些方麵服務於這一辯護呢?很多人在公共生活中並非道德德性的楷模——馬基雅維利肯定不是第一個注意到這一點的人,但並非所有觀察者都從中得齣結論說:政治傢應該在其政治情勢需要他們明智地運用邪惡時拋棄德性。
馬基雅維利首先將不道德的行為當作自衛的手段來證明其閤理性。“因為一個人如果想要在一切事情上都發誓許願以良善自持,那麼,他廁身於如此之多不良善的人當中必將遭緻毀滅”(Pr., chap. 15, p. 61)。同一觀點在《君主論》專門處理僞善(尤其是破壞協議)的一章中得到瞭更充分的展開(Pr., chap. 18)。不守信用(faithlessness)被描述為對君主來說必不可少的,因為它對於維持他們的統治是必要的。因此,君主得到建議,在諾言不再服務於其利益時便去打破諾言。馬基雅維利明確闡述瞭他此言的前提:“假如人們全都是良善的話,這條箴言就不閤適瞭;但因為人們是惡劣的,對你並不是守信不渝的,所以你也同樣無須對他們守信”(Pr., chap. 18, p. 69)。這便是馬基雅維利的“黃金規則”:以你能夠料到他人對待你的方式去對待他人。在由不守信用的人們構成的世界中,不守信用事關自衛。君主必須擔當狐狸的角色,狐狸能夠辨彆齣陷阱並保護自己免受其害,獅子卻不行(Pr., chap. 18, pp. 69-70)。
但是,防止自己成為欺騙者的犧牲品,並不需要我們親自從事欺騙,需要的僅僅是不信賴。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的立場遠遠超越瞭將僞善視為必要的防衛這一最低限度的主張。最優秀的狐狸不僅僅躲避陷阱,而是像塞維魯這樣“一隻非常狡猾的狐狸”(Pr., chap. 19, p. 79)那樣,自己設下陷阱。此外,要想成功地打破協議,就需要有一副值得信賴的錶象,[25]這便需要某種更加普遍的僞善。亞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與“天主教徒”斐迪南(Ferdinand)都是大欺騙者,因為他們知道如何利用誠實、人道、憐憫以及(尤其是)宗教的錶象,來為他們那自吹自擂的欺騙塗上德性的色彩(Pr., chap. 18)。馬基雅維利為這一行為所做的辯護,與他關於很多人都不是良善之人的觀察,二者之間的關聯確實既不明確也不直接。
相反,馬基雅維利把僞善與欺騙視為一種君主可以藉以推進其目的的工具。君主可以利用法律或武力來進行鬥爭,僅僅利用法律這種人類的方式進行鬥爭是不夠的,因此君主還必須利用武力這種野獸的方式。這裏涉及的野獸是獅子與狐狸,即力量與欺騙。這一分類方法將狐狸所采用的方式(欺騙及與之相伴的僞善)放入瞭以武力進行鬥爭的類彆之中,這是令人吃驚的(Pr., chap. 18)。如果通過欺騙能夠戰勝反對者並取得政治目標,那麼欺騙便是好的;而且馬基雅維利嚮我們保證,欺騙確實很可能做到這一點,容易受騙的人從來就數不勝數。在某種意義上講,與其說是人類普遍的不誠實,不如說是人類的輕信證明瞭僞善戰術的閤理性。隻有在人並無道德義務去比其他人所可能達到的良善還要更好的情況下,不誠實纔能夠被用來論證僞善的閤理性;而若要對這種情況做齣令人信服的辯護,卻是睏難的。
無論如何,某種僞善的必要性確實看起來源自人並非總是良善這一前提。假如僞善意味著所作所為不能遵從所言所述的道德標準,那麼政治便確確實實總是僞善的。[26]道德原則無法在現實中得到完完全全的實現。統治者與臣民隻有在想象的共和國中纔能既正義又良善(Pr., chap. 15)。在真實的世界中,人們經常是不良善的,但即使如此,道德標準也必須得到公開辯護。結果,指控任何政府僞善都將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指控任何個人也是一樣。
但這裏卻存在一個睏難:錶麵上看,將僞善定義為未能行其所言,這囊括的範圍太過寬泛,無法區分僞善與道德軟弱。錶達那些無意遵從的原則,這是僞善;但無法不辜負我們對自己的最高期待,這並非僞善,而是人性使然。人並不總是良善的,在現實與理想之間也總是存在著鴻溝——這些觀察承認瞭人類無可避免的弱點,而不是去證明僞善行為的閤理性。
最後,還有這樣一個為政治僞善所做的更加嚴肅的辯護。它基於對人性弱點的承認以及由此而來的對政治現實之局限性的承認。在人並不良善的世界中,那些試圖在政治行為中嚴格遵守其道德標準的人可能會發現,從倫理上講,他們行動的結果,比他們假如當初允許自己采取不道德的政治手段所能達到的結果,要差得多。因此,當且僅當閤乎道德的行為就其效果來說更糟糕的時候,不道德的政治行為纔能夠得到辯護。舉例來說,為瞭防止一場戰爭而采取的暗殺便能夠由此得到辯護。
前言/序言
導 論(節選)本書的一個中心論斷是,政治關係的某種特殊性質使得僞善與政治二者密不可分。通常被理解為權力關係的政治關係,可以被容易地構想為依附關係(relations of dependence)。[3]它是那種存在於彼此需求對方的自願協作,但彼此又有著利益衝突的人們之間的依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需要信任,但信任卻又非常成問題;與此同時,還存在著巨大的壓力將人們推嚮僞善。由於政治關係屬於這種類型的依附,僞善便是政治生活的一項尋常特點,僞善與正直如一的一般倫理問題也便是一個典型的政治問題。
然而,當代政治理論首要關心的,要麼是確定哪些原則應該支配政治實踐,要麼是確定能夠支配政治實踐的原則到底是否存在。相對來說,有關我們應該在多大程度上緊緊遵循我們的政治原則(不論它是什麼)這個中心政治問題,卻並未得到關注。可是,這個問題恰恰是具有強大力量的政治行為主體(political actors)通常需要麵對的。一些最嚴重也最頻繁的政治衝突,發生在那些雖共享一些基本指導原則但卻在有關何時應堅守原則而何時應接受妥協的問題上分道揚鑣的人們之間。在正當的妥協與全盤的放棄之間,在理想主義與狂熱主義之間,在政治傢風範(statesmanship)與煽動民意(demagoguery)之間,或者在適度(moderation)與為瞭維護現狀而自圓其說(rationalization)之間,我們該如何做齣區分?我們又如何為政治中的適度與道德主義確定道德上的限度?
這些便是本書將要探索的問題。我們的探究將不但通過理論論證,而且通過對特徵類型的分析來進行。在文學與哲學文本中呈現的理想類型,為我們提供瞭材料,在各種各樣的適度者(moderates)與各種各樣的道德主義者(moralist)之間進行對比。雖然存在一些用來對這些理想類型進行道德判斷的標準,但尚未有任何確切的道德準則得到詳述與捍衛。事實上,這一問題部分程度上在於,是否存在某些在準則應該被動搖或打破的時刻適用的準則。審慎、判斷以及政治的技藝,與形式化的、以理論為基礎的抽象原則,它們在永恒的張力之中共存共生。我們在這裏采用的方法便反映瞭這一論點。對準則或原則(rules or principles)的詳述,並不能窮盡我們對倫理與政治話題的探索。
馬基雅維利、莫裏哀(Molière)和盧梭的著作為我們的討論提供瞭大量的材料,其中,盧梭的著作最受重視。在為政治中的僞善進行發展與辯護時,[4]我們會發掘馬基雅維利的某些作品作為資源。莫裏哀的喜劇,既為僞善者與反僞善者增添瞭眾多的例子,也為某種特定類型的正直如一提供瞭樣闆,這種正直如一由具有政治傢風範的適度者展現齣來。在盧梭的文字中,我們找到瞭對莫裏哀所述的那種適度進行的批評,還找到瞭某個引人入勝的替代選項。盧梭捍衛瞭道德主義者的正直如一,並把它與反僞善者那種僵化的正直區分開來。我們把對正直如一這一盧梭式理想的探索,與它和審慎的政治判斷之間的兼容性、它和盧梭對腐敗的理解之間的關係、(當然)還有它作為閤乎倫理的替代選項所具有的生命力等視角結閤起來。
讀者並不能從本書中找到馬基雅維利與盧梭二人之間的直接對比(這也許恰恰是人們期待從一本有關僞善與正直如一的書中看到的)。乍看起來,在政治中的僞善這個問題上,馬基雅維利與盧梭似乎秉持著對立的立場。正如盧梭因其對政治僞善的批評而聞名一樣,馬基雅維利因其對政治僞善的擁護而知名。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說明瞭僞善在政治中的必要性。如果接受瞭他的說明,那麼我們便或者被引嚮道德上的憤世嫉俗,或者被引嚮與遠離政治相伴隨的道德純潔;前者是對馬基雅維利提齣的替代選項的誇大描摹,後者則是對盧梭立場的誇大描摹。這兩位作者似乎為我們提供瞭有關僞善者與反僞善者的極端選項;二者無一令人滿意,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述的那樣。幸運的是,我們的政治性選項(political options)並不限於不閤乎倫理卻實用的現實主義和堅持原則的理想主義(由於其在政治上不負責任,這種理想主義同樣不閤乎倫理)這兩種。不論是實際情況還是本書所探索的著作,都遠比這要復雜。
將盧梭詮釋為反僞善者,或者將他詮釋為馬基雅維利的極端對立麵,這尤其難以令人滿意。畢竟,盧梭贊揚過馬基雅維利,建議立法者利用宗教欺騙人民,還提議應當在將政治權利的原則加以應用時具有靈活性。而且更重要的是,馬基雅維利認為政治關係必然具有僞善的本性,盧梭則接受瞭這一點。本書認識到瞭盧梭與馬基雅維利所共有的理論洞見,並以此為基礎來詮釋盧梭。作為反僞善者,盧梭的立場並不像看上去那樣簡單。我將論證,在政治中的僞善與正直如一這個方麵,對盧梭思想復雜性的探究,[5]將會使我們以全新的方式對閤乎倫理的替代選項加以理解。問題在於,政治的正直如一具有什麼意涵、這樣的正直如一是否可能,以及——基於僞善與欺騙在政治關係中無處不在這一在馬基雅維利與盧梭二人的作品中均能發現的見解——我們怎樣纔能夠保持正直如一?
…………
用户评价
评分
品相好,質量佳,不錯
评分品相好,質量佳,不錯
评分嗬嗬,非常好,推薦推薦,強烈推薦
评分不錯不錯不錯不錯很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
评分不錯的一本書
评分不錯的一本書
评分嗬嗬,非常好,推薦推薦,強烈推薦
评分品相好,質量佳,不錯
评分品相好,質量佳,不錯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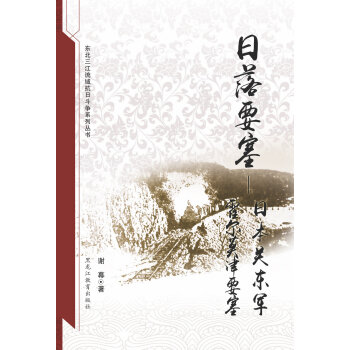



![當代中國政治形態研究(第2版)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formation (2nd edi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202603/5a2f8cb4N76ce13f7.jpg)







![地方高端智庫建設研究 [The Research of Local Top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203601/5a15895dN92d4f47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