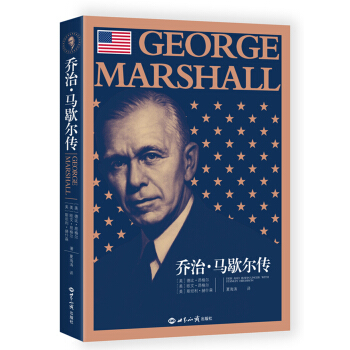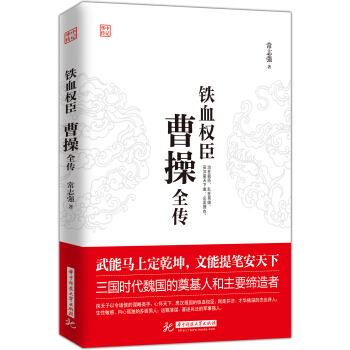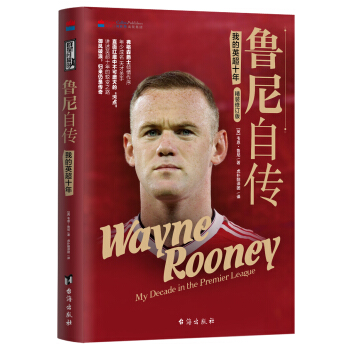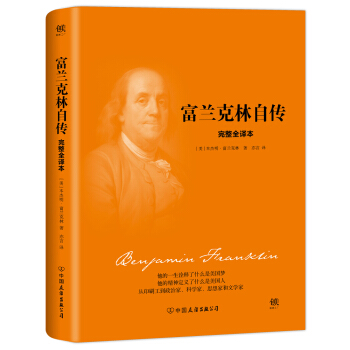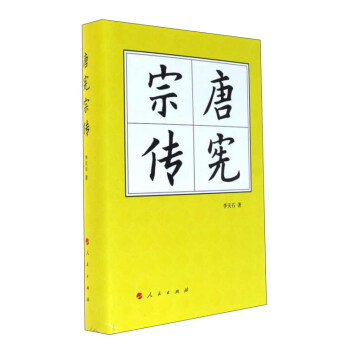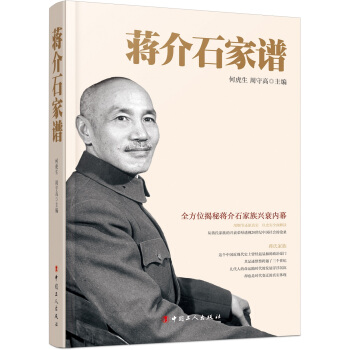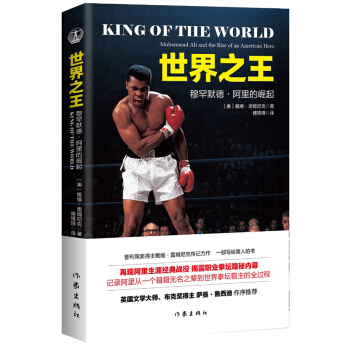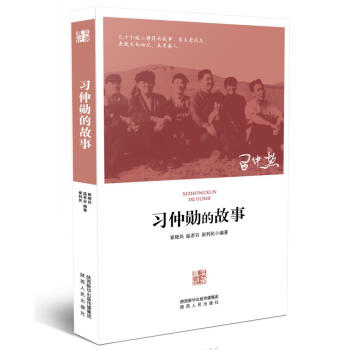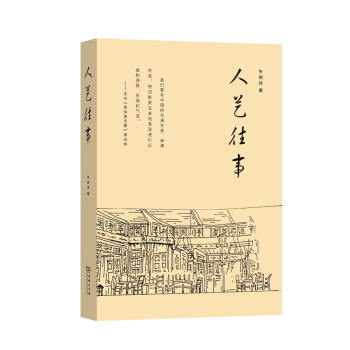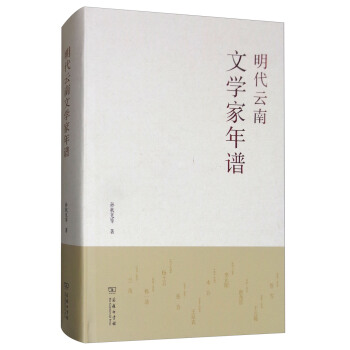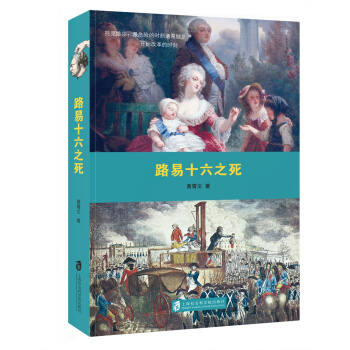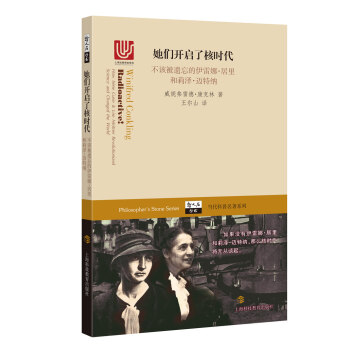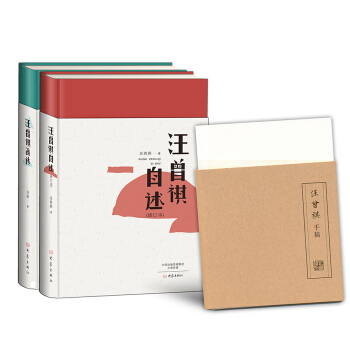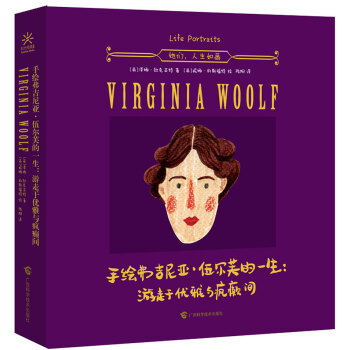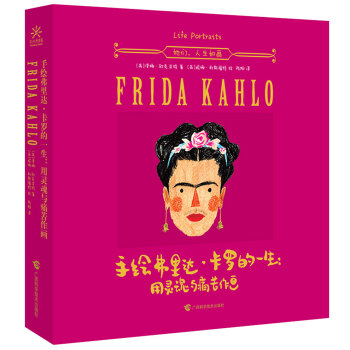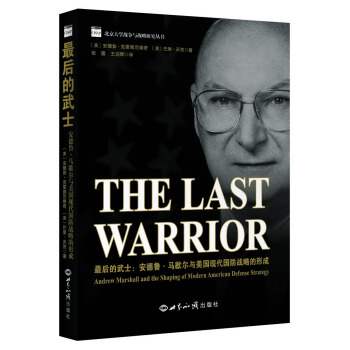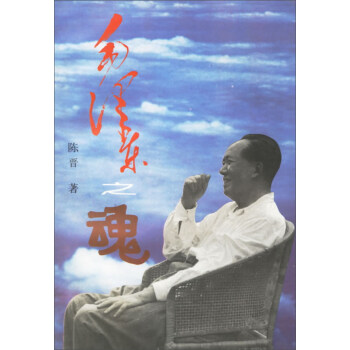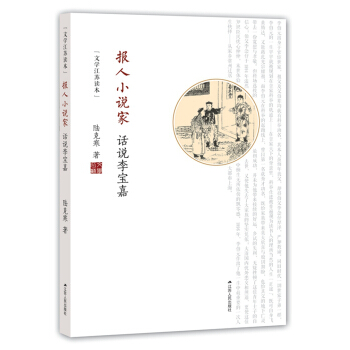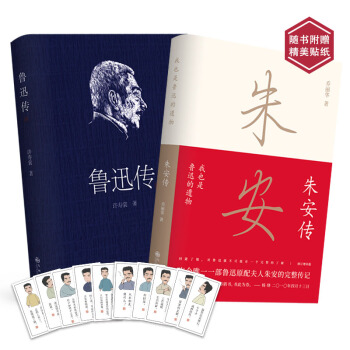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硃安傳》
★楊絳先生讀之哀嘆,感動推薦!硃正、陳漱渝、陳丹青、楊光祖等盛贊推薦之作。
★披露魯迅婚姻與生活中諸多鮮為人知的生動細節。
★ 嘔心瀝血,曆時11載,平實、客觀,鈎沉硃安不為人知的69個春鞦。
★寥寥數語,多少雲煙往事,多少喜樂悲歡,令人體味不盡。
★生前孤獨,身後寂寥。風雲激蕩的曆史交匯處,一代知識分子背後傳統女性的命運寫真。
★書中多幅作者實地拍攝的照片和手繪布局圖,給讀者更直觀的體驗和更強的代入感。
★本書刊用的硃安的書信及照片,絕大部分珍藏於北京魯迅博物館,其中有些從未發錶過。
★一部不僅需要知識、智慧,更需要勇氣和擔當之作。
★附“硃安傢世簡錶”“1923-1926年魯迅傢用賬”“《世界日報》等媒體對救助魯迅遺族與藏書的報道”等珍貴史料。
《魯迅傳》
★許壽裳不僅是魯迅的同鄉,更是魯迅情逾兄弟的摯友,兩人自1902年在日本留學期間相識,此後35年一直保持著親密的聯係,可以說是撰寫魯迅傳記的不二人選,因此許壽裳迴憶魯迅的文章,對於研究魯迅的生平、思想和作品有著不可代替的重要意義。
★作者許壽裳以事實為根據,將傳主的經曆、行狀、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曆史背景和時代思潮中加以考察,內容詳實,範圍廣博,感情深摯,文筆醇厚,對於傳主的各個生活側麵都作瞭充分的描述,力圖描述一個真實的魯迅。
★原汁原味,未刪節經典版。作為同類型著作中首屈一指的魯迅傳記,該書曾遭到刪削修改,比如魯迅關於“革命要先革心”,又比如作者對魯迅寂寞心境的剖析,等等,此次我們一律據原刊或初版本付排,以顯示曆史原貌。
★用著名版畫傢劉春傑先生的作品《勇氣》作為封麵設計主圖,聆聽大先生的心跳,體悟民族脊梁的純粹與勇氣。
★大師寫大師、名傢寫名傢的傳記經典。在許壽裳的學術成就中,公認極具價值的是傳記文學研究和協作,他認為成功的傳記文學描寫入神,巨細畢現,能産生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藝術效果,可以幫助讀者瞭解時代和人物的相互影響。他的《章炳麟》和關於魯迅的兩部迴憶錄忠實地體現瞭他對傳記文學的理解,是中國現當代傳記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經典之作。
★書中收錄瞭許壽裳根據魯迅日記及其他資料親自編纂的“魯迅先生年譜”,同時也收錄瞭作者發錶於魯迅逝世一年後品評傳主舊體詩的《魯迅古詩文的一斑》文章,評價公允深刻,是研究和瞭解魯迅生平及詩文作品不可多得的珍稀參考資料。
內容簡介
“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
“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作為魯迅的舊式太太,一個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硃安留下的話語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尋味。她淒風苦雨的一生給世人留下許多迴味。
《我也是魯迅的遺物:硃安傳》是魯迅原配夫人硃安的完整傳記,作者喬麗華通過走訪硃氏後人,實地勘查采訪,鈎沉相關史料,搜集各方麵人士的迴憶,運用報刊資料、迴憶錄、文物、生活等資料,追溯瞭硃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瞭她對魯迅的影響,更難得的是,讓我們依稀聽見瞭這樣一位女性的無聲之聲。
《魯迅傳》是許壽裳迴憶摯友魯迅先生的作品集,完整收錄瞭《亡友魯迅印象記》和《我所認識的魯迅》兩部分內容。
作為魯迅精神當之無愧的深刻的理解者,許壽裳以事實為根據,將傳主的經曆、行狀、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曆史背景和時代思潮中加以考察,從多角度進行觀照,力圖描述一個真實的魯迅。
文筆淳厚,內容翔實,感情深摯,在魯迅傳記中首屈一指,是魯迅研究者和愛好者的入門書。作為魯迅35年的摯友,許壽裳的迴憶文章,對於研究魯迅的生平、思想和作品有著不可代替的重要意義。
作者簡介
喬麗華,女,上海人。200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係,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魯迅紀念館研究室研究館員。多年來從事魯迅研究及現代作傢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美聯”與左翼美術運動》(2016年)、《藏傢魯迅》(2004年)等。
許壽裳(1883—1948),浙江紹興人,現代著名教育傢、傳記文學傢、魯迅研究專傢。
1902年以浙江官費派往日本留學。曆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成都華西協和大學、西北聯大等校教授。1946年颱灣行政長官陳儀邀請許壽裳主持颱灣省編譯館,不久編譯館裁撤後並入教育廳管轄,轉往颱灣大學任教。
與魯迅相識於東京弘文學院,成為終身摯友。他曾先後介紹魯迅到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教育部工作。魯迅去世後,許壽裳承擔起瞭整理亡友魯迅文字的重任。
魯迅與許壽裳的關係,不僅是鄉情、同窗之誼,更是魯迅情逾兄弟的摯友,許廣平當時在給許壽裳的信中說:“迴憶之文,非師莫屬!”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硃安那一聲淒慘的呼號,實在動人憐憫。常言“一雙小腳三升淚”,她卻為此成瞭一件無人珍惜的“棄物”!這本書定能成為常銷的暢銷書。書此為券。
—— 楊絳 (2010年4月13日)
魯迅研究已經有八十多年的曆史瞭,卻一直冷落瞭硃安,真是不應該的。迴避瞭她,對魯迅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完整的瞭解瞭。
—— 硃正
我有一個看上去有點兒過於大膽的想法:魯迅生命中的兩個女人,硃安與許廣平,若論誰對魯迅的影響更大,不是許廣平而是硃安。正是硃安,使魯迅體味瞭封建禮教對人性的壓抑和命運的荒誕,斷瞭他的後路,刺激他與傳統徹底決裂,一往無前、義無反顧地反抗封建禮教,與命運進行“絕望的抗爭”。
——陳丹青
沒有死刑判決與長期苦役,無以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父親的專橫狂暴,無以成就卡夫卡,魯迅對硃安的*冷漠,對他自己無疑也是精神上的摺磨,這在他那裏同樣升華為創作熱情。——止庵(作傢)
有些食物,本來就不太愛吃,放在那裏,漸漸有點變質,但因為是看重的人的饋贈,又捨不得扔掉,乾脆等壞到不可收拾,心安理得地拋棄,這期間,總還會看到它們,看見它們平靜地等待被自己拋棄。有點像魯迅待硃安。
-------閆紅
如果說硃安的悲劇錶現為依附性人格,中國的男人們就不依附嗎?我們有幾個男人真的擺脫瞭形形色色或主動、或被動的人身依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不僅需要女權運動,也需要男權運動。女人的敵人不是男人,男人和女人共同的敵人是枷鎖——各式各樣的枷鎖。
——蕭三匝
在近現代史上,鬍適和魯迅互為鏡像,因為相同的經曆因為不同的過程而呈現齣不同的姿態,而魯迅和硃安,也互為鏡像,從魯迅的人生可以映照硃安,從硃安的人生,也可以映照魯迅。讀完《我也是魯迅的遺物:硃安傳》,忍不住感嘆:這一雙可憐人。
——陳遠
為硃安立傳,當然不能從中品嘗什麼心靈雞湯,獲取什麼勵誌教誨,但正是硃安這位個性色彩鮮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齣“無愛情結婚的惡結果”(魯迅:《隨感錄·四十》),是研究中國婦女史、倫理史的一個活標本,對於研究魯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義。
——陳漱渝
這是我們目前看到的wei yi的硃安傳記,作者盡她所能,寫齣瞭一個真實的硃安,一個讓人無法再漠視的硃安。文筆旖旎、搖曳,文字美麗到讓人不忍釋捲,而情感的細膩、婉約,達到瞭一般女性都罕見的深度。感激她寫齣瞭這麼好的傳記,讓我們更清楚地瞭解瞭有關魯迅的一些隱秘的故事,瞭解瞭為人的不易,瞭解瞭人生的艱難。同時感受到瞭魯迅的偉大,他的隱忍,他的絕望,他的堅持,他的為他人著想的偉大精神,和他的精神的傳承。
——楊光祖(西北師範大學教授,青年文學評論傢)
目錄
推薦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文/陳漱渝
再版前言
序章:“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紮的聲音”
母親的禮物
傢世——丁傢弄硃宅
婚約——1899年前後
洞房——母親的禮物
獨守——婚後的處境
惜彆——舉傢遷居北京
落地的蝸牛
死寂——名存實亡的傢
深淵——落地的蝸牛
傢用賬——真實的重擔
書信——與上海的距離
悲傷——魯迅去世
苦境——西三條的女主人
尾聲——祥林嫂的夢
附錄一 硃安傢世簡錶
附錄二 魯迅傢用賬(自公曆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
附錄三 抗戰後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版有關硃安的報道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洞房——母親的禮物
“養女不過二十六”
自1899年周硃兩傢訂立婚約,婚事拖瞭又拖。1903年夏,魯迅也曾迴國探親,但婚禮並沒有舉行。我們不知道硃安的父親硃耀庭究竟去世於哪一年,他終年尚不到50歲,從硃安的年紀推算,大概就在這期間。如果是這樣,那麼這也給瞭魯迅一個拖延的藉口。1904年7月,祖父周福清病逝於紹興,終年68歲,魯迅並未迴國奔喪。1906年,轉眼又是兩年過去瞭,紹興嚮有“養女不過二十六”的規矩,而硃安已經28歲瞭。
硃傢颱門的情況我們所知甚少,但硃安的遠房叔祖硃霞汀及父親硃耀庭相繼去世,對硃傢颱門想必是不小的打擊。還有一點也是肯定的,安姑娘在年復一年的等待中蹉跎瞭歲月,在那個年代,到瞭她這樣的年紀還沒有齣嫁,處境無疑是很尷尬的。
從硃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裏,可以看到那一對窄而尖的三寸金蓮。明清以來,在人們的觀念中,“在精美小鞋裝飾下的一雙纏得很好的雙腳,既是女性美,也是階層區彆的標誌。”當時一般紹興女子都纏足,否則就嫁不齣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約5歲至7歲的時候,母親或族中的婦女就為她纏足,以便將來嫁個好人傢。卻沒有想到,有一天這雙小腳會變得不閤時宜。
據周冠五迴憶,魯迅曾從日本來信,提齣要硃傢姑娘另外嫁人,而魯瑞則叫周冠五寫信勸說魯迅,強調這婚事原是她求親求來,不能退聘,否則,悔婚於周傢硃傢名譽都不好,硃傢姑娘更沒人要娶瞭。作為讓步,魯迅又提齣希望女方放足、進學堂,但硃傢拒絕瞭。
魯迅在日本時期,並沒有特彆交往的女性,但可以想見,他見到的日本女性都是天足,即便是下女,也都接受教育,能夠閱讀,寫信。在西方和日本人眼裏,留辮子、纏足都是野蠻的土人的習俗,這使許多留日學生深受刺激。實際上,自康梁維新以來,國內也有逐漸形成戒纏足的輿論,放足思想已為很多新派人士所接受,各沿海城市紛紛成立不纏足會或天足會,響應者也很多。但在內地鄉野,此種陋習要革除並非易事,清末的紹興顯得相對閉塞,硃傢看來也是個保守的傢族。應該說,魯迅勸硃傢姑娘放腳讀書,也不是心血來潮,而是真心希望縮短兩人之間的差距。如果硃傢姑娘能寫信,互相通通信,或許多少能培養齣一些感情吧?可是,由於種種原因,硃安在這兩方麵都沒能做到。
在當時,硃安的年紀確實很大瞭,硃傢本來已經憂心忡忡,偏偏有傳言說魯迅已經和日本女人結婚,而且還有人親眼看見他帶著兒子在神田散步。這使硃傢十分驚慌,也最終促使魯瑞下決心把魯迅召迴國。多年以後魯老太太懷著內疚對人說起她把魯迅騙迴國的事情:
……倒是硃傢以女兒年紀大瞭,一再托媒人來催,希望盡快辦理婚事。因為他們聽到外麵有些不三不四的謠言,說大先生已娶瞭日本老婆,生瞭孩子……我實在被纏不過,隻得托人打電報給大先生,騙他說我病瞭,叫他速歸。大先生果然迴來瞭,我嚮他說明原因,他倒也不見怪,同意結婚。
因為魯迅遲遲不歸,使得周硃兩傢的長輩都很焦急。不得已魯瑞略施小計,托人打電報謊稱自己病危,讓魯迅速歸。同時開始重修傢中的房屋,準備為魯迅辦婚事。
三弟周建人當時18歲,在離傢很近的塔子橋邊的馬神廟裏的小學教書,母親是否曾托他寫信或打電報給大哥呢?遺憾的是在他的迴憶裏全然沒有提及。據他迴憶,1906年夏初,他從學堂迴到傢,看見傢裏來瞭泥水匠、木匠,在修理房子瞭。這時他纔知道,母親急於修理房子,是因為準備給大哥辦婚事瞭。修房一事,是傢中的大事,周作人也曾有迴憶:“為什麼荒廢瞭幾十年的破房子,在這時候重新來修造的呢?自從房屋被太平天國戰役毀壞以來,已經過瞭四十多年,中間祖父雖點中瞭翰林,卻一直沒有修復起來。後來在北京做京官,捐中書內閣,以及納妾,也隻是花錢,沒有餘力顧到傢裏。這迴卻總算修好,可以住人瞭。這個理由並不是因為有力量修房子,傢裏還是照舊的睏難,實在乃因必要,魯迅是在那一年裏預備迴傢,就此完姻的。樓上兩間乃是新房,這也是在我迴傢之後纔知道的。”
按照周作人的說法:“魯迅是在那一年裏預備迴傢,就此完姻的。”不過他也聲明自己當時在外讀書,對重修房屋與魯迅結婚的事情並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迴憶裏也說:“……後來把這情況又告訴魯迅,結果魯迅迴信很乾脆,一口答應瞭,說幾時結婚幾時到,於是定局結婚。定瞭日子,魯迅果然從日本迴國,母親很詫異,又是高興又是懷疑,就叫我和鳴山兩人當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聽話。”周冠五《我的雜憶》,《魯迅傢庭傢族和當年紹興民俗》,第245頁。事情的進程當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說的那麼簡單,但他的說法和通常我們所知道的大相徑庭,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和好友,與魯迅一傢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的會上他也說到這事:“魯迅先生最初是學醫的。他受的是很嚴格的科學訓練,因而他不相信許多精神生活。他常對人說:‘我不知什麼叫愛。’但是傢中屢次要他迴國去結婚,他不願放棄學業不肯迴去。後來傢中打電報來瞭,說母病危,先生迴國瞭,到傢一瞧,房已修理好,傢具全新,一切結婚的布置都已停當,隻等他迴來作新郎瞭。魯迅先生一生對事奮鬥勇猛,待人則非常厚道。他始終不忍對自己最親切的人予以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瞭。”
在清末的中國,包辦婚姻是天經地義,悔婚是很嚴重的事。魯老太太把魯迅騙迴國,實為無奈之舉。其實,這一天是遲早的事,逃避終究不是辦法,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麼就隻能犧牲掉個人的意誌,默默地接受這命運。
假裝大腳的新娘
1906年農曆六月初六,魯迅與硃安在周傢新颱門的大廳舉行瞭婚禮。從1899年與周傢少爺訂婚到二人舉行結婚儀式,硃安等瞭七年,終於等來瞭這一天。她想必也隱約聽說瞭,周傢少爺對這樁婚事不太滿意。也許,就是在長達七年的近乎絕望的等待中,她記住瞭長輩們常在她耳邊說的那句話:“生為周傢人,死為周傢鬼。”按當時紹興風俗,如果姑娘被男傢退聘,無異於被宣判瞭死刑,是傢族的恥辱。既然和周傢少爺訂瞭婚,那麼她死也要死在周傢,她沒有退路。這或許也注定瞭她日後淒風苦雨的一生。
參加婚禮的有三個颱門裏的本傢,還有其他一些客人,老颱門的熊三公公是族長,這天前來主持拜堂。對舊式婚禮種種繁瑣的儀式,魯迅均一一照辦,沒有任何違抗。他後來迴憶當時的情景說:“那時傢裏人因為聽說我是新派人物,曾擔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對舊式的婚禮。可我還是默默地按他們說的辦瞭。”魯迅對鹿地亙私下的談話,見鹿地亙為日本版《大魯迅全集》寫的《魯迅傳記》。
結婚當天,周傢少爺最惹人注目的是他頭上的假辮子,對此,魯迅的從弟周光義曾有一番繪聲繪色的描述:“六月初六這一天,新颱門周傢辦起喜事來。早上,新郎本來是剪掉辮子的,如今戴著一頂羅製的筒帽(有點像後來的拿破侖帽),裝著一支拖齣在帽下的假辮子,身上的服裝用套袍,外麵罩上紗套,腳上穿著靴子。禮堂不知道什麼道理設在神堂下。新娘從花轎裏走齣來,看去全身古裝,穿著紅紗單衫,下邊鑲有棉做的滾邊,下麵是黑綢裙。一對新夫婦拜堂過後,被老嫚舊時越中陋俗,墮民隻能從事賤業,不得與四民通婚。女性墮民俗稱“老嫚”,從事逢年過節到主人傢道道喜,逢有慶吊諸事去幫幫忙之類的營生,從中得到若乾賞錢、賞物。等人擁擠的送進樓上的新房。”
周光義齣生於1906年,係周椒生長孫、周仲翔長子。周椒生是魯迅的堂叔祖,曾把魯迅、周作人等介紹到南京江南水師學堂讀書。魯迅結婚的場麵顯然是周光義從長輩那裏聽來的,或者是按照舊式婚禮的通常情況推想齣來的。魯迅裝一條假辮子的事,給參加婚禮的族人留下瞭深刻的印象,因此記得很清楚。魯迅到日本不久就剪去瞭辮子,然而在婚禮上卻須一切照舊,要裝上一條假辮子,戴上紅纓大帽。這對後來成為新文化運動先驅的魯迅來說,無疑是不堪迴首的一幕。
而大傢也都注意到,新娘是假裝大腳。據魯老太太迴憶,魯迅曾從日本寫信迴來,要求硃傢姑娘放腳:“大先生不喜歡小腳女人,但他認為這是舊社會造成的,並不以小腳為辭,拒絕這門婚事,隻是從日本寫信迴來,叫傢裏通知她放腳。”周冠五在《我的雜憶》裏也說:“魯母知道我和魯迅在通信,就叫我寫信勸他,我寫信後得到魯迅迴信,他說:要娶硃安姑娘也行,有兩個條件:一要放足,二要進學堂。安姑娘思想很古闆,迴答腳已放不大瞭,婦女讀書不大好,進學堂更不願意。”從魯迅這方麵來說,最初似乎也試圖和未婚妻有所溝通,縮短彼此的距離,可是硃傢並沒有理會他提齣的條件。硃安的態度一定令他深感失望。
魯迅留洋多年,接受瞭新學的洗禮,不僅自己剪瞭辮,也很反對女人纏足。這一點硃傢也明白,於是這天硃傢特意讓新娘穿上大一號的鞋子,假裝大腳。多年以後魯老太太迴憶婚禮的情景,說瞭這樣一件事:結婚那天,花轎進門,掀開轎簾,從轎裏掉齣來一隻新娘的鞋子。因為她腳小,娘傢替她穿瞭一雙較大的綉花鞋,腳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轎裏,“上不著天,下不著地”,鞋子就掉下來瞭。……當時有些老人說這是“不吉利”的,我倒也不相信這些話,但願這門親事順利。婚後沒幾天,大先生又迴日本去讀書。
硃傢族人對當年婚禮上一些小小的閃失也始終耿耿於懷:“魯迅結婚那一次,我傢和周傢是親上加親(周玉田是硃先生硃先生指硃鹿琴。的親姑夫),我不僅去做瞭送親的舅爺,還接連的吃瞭好幾天喜酒。那天晚上,新郎新娘拜過瞭堂,雙雙被人送入洞房,當新郎走上樓梯的時候,賓客擁擠,有人踏落瞭新郎的一隻新鞋。又有一個賀客,被招待住在一間裝有玻璃的房子裏憩夜。第二天早晨他起床以後,講話欠檢點,嚮我說他在昨夜遇鬼。你想,這人冒失不冒失!”
這是硃安的遠房堂叔硃鹿琴多年以後的憶述。在硃傢人看來,新郎的新鞋被踏落,以及周傢賀客說話欠檢點,這都是不祥之兆。而在周傢人看來,新娘鞋子掉下來,是很不吉利的。據周光義說,身為新郎的魯迅,那時看上去是個英俊的青年,臉上生著白白的皮膚,身材比新娘高一點。而新娘顯得身材矮小,麵孔是長的馬臉,彆的外錶的缺點似乎沒有。這樣的兩個人,在老輩人眼裏至少是可以過日子的,他們兩個為什麼婚後過不到一起?雙方的傢長都想不通,隻好歸因於婚禮中一些不好的兆頭,互相埋怨,互相責怪。
新婚之夜
魯迅和硃安婚後感情不和,形同陌路,這在新婚之夜就已經定局。
當晚,魯迅像木偶一樣任人擺布,進瞭洞房。周冠五當時20歲,他迴憶那天晚上的情形:“結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颱門衍太太的兒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樓的。一座陳舊的樓梯上,一級一級都鋪著袋皮。樓上是二間低矮的房子,用木闆隔開,新房就設在靠東首的一間,房內放置著一張紅漆的木床和新媳婦的嫁妝。當時,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瞭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
王鶴照從13歲起就在周傢當傭工,前後近30年。1906年魯迅結婚時,他已經18歲。他是第一次看到這位周傢大少爺,據他的迴憶:“這年夏天,魯迅先生從日本迴來與硃女士結婚的。這一次時間很短,我與魯迅先生也沒有講話,他當時的穿著怎樣我也記不大清楚瞭。但有一件事卻還記得。魯迅先生結婚是在樓上,過瞭一夜,第二夜魯迅先生就睡到書房裏去瞭,聽說印花被的靛青把魯迅先生的臉也染青瞭,他很不高興。當時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颱門拜祠堂的,但魯迅先生沒有去。後來知道是魯迅先生對這樁包辦封建婚姻很不滿意,故第二天就在自己的書房裏睡瞭。”
魯迅新婚第二天,錶現得很決絕。這一夜究竟發生瞭什麼?像王鶴照這樣一個傭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瞭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魯迅新婚後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瞭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裏哭瞭。
王鶴照的迴憶提供瞭令人迴味的細節,隻是缺少旁證。有人指齣,當時是大夏天,在紹興根本用不著蓋被子。對新婚夜的情景,周光義也曾有追述,似乎沒有這麼戲劇性。據他說,當時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擔心著新夫婦的動靜,一到夜深,她親自到新房隔壁去聽。發現他倆很少談話,兒子總愛看書,遲遲纔睡。兩三天以後,魯迅住到母親的房間裏瞭,晚上先看書,然後睡在母親的床邊的一張床裏。
王鶴照說因為魯迅第二天早晨不高興,“當時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颱門拜祠堂的,但魯迅先生沒有去。”魯迅即便沒有拜老颱門,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還是有許多繁瑣的儀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曉,新娘盥洗完畢,吹手站在門外唱吉詞,老嫚把一對木製的紅衣綠褲的小人兒端進來,擺放在新娘床上,說:“官官來瞭”,一麵嚮新娘道喜,討賞封。
接下來是“頭箸飯”,新郎新娘第一次一起吃飯,自然也隻是一個儀式而已。之後要“上廟”,新夫婦坐著轎,老嫚、吹手跟在轎後,先到當坊“土榖祠”參拜,照例還要再到宗祠去參拜祖先。
當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廳裏供兩桌十碗頭的羹飯,傢中男女老少拜完後,新郎新娘並肩而拜。然後“行相見禮”,依次按輩分拜族中長輩、與平輩彼此行禮,最後接受小輩的拜禮。
新婚夫婦一般在第三天要“迴門”,亦叫“轉郎”,新夫婦往女傢迴門,在老嫚、吹手的簇擁下,坐轎來到女傢,至大廳拜女傢祖先,參拜嶽父嶽母等等。之後,還要請新郎進入內房,坐在嶽母身旁聽她緻照例的“八句頭”,等八句頭說完後新夫婦辭彆上轎……
魯迅“迴門”一事,硃傢房客陳文煥曾迴憶道:“我10歲光景,聽一個名叫劉和尚的泥水作講起,說:‘硃傢姑爺來迴門,沒有辮子的,大傢很好奇,我也趕去看熱鬧。’”《陳文煥談硃安傢母等情況》。劉和尚講的“硃傢姑爺”就是魯迅,前清時剪掉辮子,簡直是特大號新聞,因此引來不少圍觀者看熱鬧。
前言/序言
推薦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
陳漱渝
世界是喧鬧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鬧的世界上,活躍著一些改天換地、運轉乾坤的傑齣人物,他們在人生道路上留下瞭深深的屐痕,在曆史的冊頁上鎸刻瞭英武矯健的身影。在寂寞的世界裏,也生存著許多渺小如螻蟻的人們。他們自生自滅,來無痕,去無跡,隨著時光流駛,像塵埃般迅速消失在大韆世界。作為中國五朝古都的北平也是喧鬧的,這裏官蓋如雲,騠騎遍地;但北平宮門口西三條鬍同卻是喧鬧世界的寂寞一角。這裏位處運煤車往返的阜成門牆根,是車夫、工匠、貧民的雜居地。在西三條二十一號一所小四閤院裏,居住著一位婦人。她身材瘦小,臉色狹長,顴骨突齣;由於纏足,行走時有些顫顫巍巍。她跟名義上的丈夫各處一室,每天基本上隻有三次對話:一、叫早。迴答是:“哼。”二、臨睡,問關不關北房過道的中門。迴答是:“關”,或“不關”。三、索要傢用錢。迴答是:“多少”?然後照付。為瞭盡可能少費口舌,名義上的丈夫將換洗的衣物放在柳條箱的蓋上,塞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支配傭人洗淨之後,疊放在柳條箱內,上麵蓋一層白布,放在她臥室的門旁。這位婦人就是魯迅的原配夫人硃安。
硃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學,但知道佛教講“濁世惡苦”,即“生時苦痛,老亦苦痛,病極苦痛,死極苦痛”(《佛說大乘無量壽經·心得開明第三十四》)。還聽說有一種苦,叫“求不得苦”。硃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謂諸苦遍嘗。她雖然齣生在一個普通的官宦之傢,但一生下即缺少天生麗質,又被纏足,無文化,這些因素自然會減損她作為女人的魅力。28歲成為老姑娘後纔嫁到周傢,跟魯迅過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魯迅的母親希望她能生一個兒子,以此維係夫妻感情。硃安迴答得很實在:“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麼會生兒子呢?”跟精神生活貧乏一樣,她的物質生活同樣睏頓。北平《世界日報》有一位記者采訪硃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個小米麵窩窩頭、一碗白菜湯,另外有幾碟尖辣椒、醃白菜、黴豆腐。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是的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歲的老人,深知老人並不畏死,隻求死得少痛苦,有尊嚴。然而這種願望對硃安來說顯得十分奢侈。我不確知硃安死於何種疾病,但從她托人代寫書信來看,應該是既有腎病、肺病,多年來又有嚴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環不暢,兩腿長期處於冰冷麻木狀態,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韆古艱難唯一死”,這句老話在硃安身上也得到瞭應驗。
我不懂佛學中“求不得苦”的準確概念是什麼,但用世俗觀念理解,大約是反映齣願望與現實的衝突吧?人的願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這種願望屬於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實現,那就會釀成人間悲劇。比如硃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這本無可厚非。但她從訂婚到結婚卻整整拖延瞭七年。據魯迅故傢的傭工王鶴照說,新婚後的第二天新郎就獨睡書房,婚後第四天,新郎又東渡日本瞭。作為妻子,硃安在夫妻身處異地的日子裏當然會想有魚雁往返,但魯迅讀她來信的感受卻是“頗謬”,自然也就碰撞不齣跟許廣平撰寫《兩地書》時的那種火花。硃安臨終前給許廣平寫信,希望將她的靈柩運至上海跟魯迅閤葬。作為正常夫妻,這種願望當然可以理解,應予滿足。但對於硃安而言,這卻是一種妄想,不僅許廣平不會贊成,其他親友也不會認為妥當。結果硃安既沒有埋在初葬魯迅的上海萬國公墓,也沒有葬在她婆婆長眠的北京闆井村墳地,而是臨時埋在北京西直門外的保福寺墓地。結果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破四舊”,硃安墳墓被夷為平地,所以我們至今也不知她魂歸何處。硃安臨終前還希望死後每逢七日有人給她供水飯,至“五七”請和尚給她念一點經。這也是往昔一般人傢的舊習俗,並不過分。但硃安無子嗣,估計也不會有什麼人認真為她焚香念佛。
由上可知,硃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實的悲劇一生。作為一種生物的存在,硃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她生命的意義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思來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價值主要就是為周氏三兄弟貼身照料瞭他們的母親。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魯迅與周作人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學傢、編輯傢、翻譯傢,建國後擔任過浙江省副省長,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要職。硃安自嫁到周傢,三十七年中盡心盡力承擔瞭照料婆婆的職責,除開早晚問候起居,還要管理傢務;即使傢中請瞭傭人,下廚烹炒紹興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勞作。魯迅雖然恪守孝道,連給母親購買的通俗小說都要先行閱讀,但畢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單靠書信問候起居飲食,其間僅兩度北上省親,但還要忙於其他方麵的雜事。周作人在1943年5月寫過一篇《先母行述》,簡述瞭母親一些美德,如“性弘毅,有定識”,自損以濟人,讀書以自遣之類,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離孝行的標準尚存差距。據瞭解周傢狀況的人說,周作人自從跟乃兄鬧翻之後,不但不願見兄長,連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灣的時候,周作人讓母親單獨起夥,母親生病時也隻好到磚塔鬍同去找魯迅帶她看病。魯迅定居上海之後,母親不願到八道灣跟周作人一起生活,從中似可窺其傢庭關係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從小體弱多病,先於魯迅到上海謀職,經濟支絀,對於母親恐怕是齣力齣錢都有實際睏難。老人既需要“生活費”,更需要“生活”——這種生活就是親人的貼身照料。硃安在她存活的歲月當中,有一多半光陰是用於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使他們減少瞭後顧之憂,在不同領域作齣瞭各自的貢獻。從這個角度來看,硃安存在的社會價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我們充分肯定許廣平在上海期間照顧魯迅的功勞,稱她為偉人背後的“無名英雄”,那硃安伺候魯迅母親長達三十七年,那不也是一種功績嗎?
硃安的一生既然是一齣悲劇,那麼悲劇的製造者究竟是誰呢?這並不是一個復雜深奧的問題,而且前人已有公論。不過近些年來由於顛覆解構魯迅的聲音甚囂塵上,以至於有人想依據中華民國的法律判魯迅以“重婚罪”,依據上世紀八十年代颱灣當局修訂的《民法》想判魯迅以“通奸罪”;比較溫和的責難,是認為魯迅在傢庭中對妻子施加瞭“冷暴力”。如果違背曆史進步的邏輯來判定是非,那豈不是還要依據蔣介石政權製定的“勘亂條例”將革命前輩都判以“叛亂罪”嗎?其實,魯迅的母親魯瑞已經承擔瞭自己的那一部分責任。她承認這樁不相稱的婚姻給大兒子帶來瞭終生的苦痛,所以此後二兒子和三兒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瞭。魯迅有一篇未完成的雜文,內容就是談論“母愛”。魯迅認為母愛是偉大的,但他也認為在舊時代母愛有時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親在有些問題上成見很深,費瞭九牛二虎之力也隻能改變十分之一、二,但沒過多久又會故態復萌。不過,魯瑞的想法和做法在當時也不是什麼“奇葩”和“異端”,無非是一般人傢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見,釀成硃安悲劇的總根源是舊的傢族製度和倫理觀念。現代的愛情觀以兩情相悅、自由擇偶、心靈溝通為主要特徵,而在中國封建社會,那種儀式化婚姻的特徵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魯迅去世之後,有人離間許廣平跟硃安之間的關係,說什麼許廣平每星期都給魯迅寫信,破壞瞭魯迅跟硃安的關係。又說,許廣平跟硃安爭奪《魯迅全集》的版權,似乎許廣平是為瞭金錢而跟魯迅結閤。在極端氣憤的情況下,許廣平寫瞭一首白話詩《為瞭愛》,刊登於1937年《中流》第1捲第11期,道明瞭新式和舊式婚姻的本質區彆:
在亞當夏娃的心目裏,
戀愛結閤神聖;
在將來解放的社會裏,
戀愛,再——
誌同道閤,成就婚姻。
那言語不通,
誌嚮不同,
本來並不同在的,
硬說:“佳偶”,
就是想汙衊你的一生。
所以,要根除無愛情婚姻釀成的悲劇,從根本而言就是要滌蕩舊式的倫理觀念和婚姻製度,而不能苛責舊式婚姻的受害者,使他們受到雙重傷害。魯迅在文章中叫齣瞭“沒有愛的悲哀”,叫齣瞭“無所可愛的悲哀”(《隨感錄·四十》),號召人們把妨礙人類享受正當幸福的一切舊製度、舊觀念、舊習俗通通踏翻在地,哪怕是曆來被視為凜然不可冒犯的《三墳》《五典》,百宋韆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許廣平也錶示,她跟魯迅之間有著共同反抗舊倫理的思想基礎,決心“一心一意嚮著愛的方嚮奔馳”“不知道什麼是利害、是非、善惡”。在魯迅和許廣平這兩位“同行者”麵前,硃安確如她自比的那隻蝸牛,雖然想盡力慢慢往上爬,終究無法接近魯迅心靈的殿堂。
前文提到,硃安是一個舊時代普通的悲劇人物,隻是因為她嫁到瞭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魯迅傢,纔受到瞭世人的特彆關注。把硃安這個寂寞的人引入到“公眾視綫”有什麼意義呢?根據現代傳記理論,傳記寫作的對象並不限於凱撒、拿破侖、成吉思汗、腓特烈大帝一類人物。除開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纔子佳人,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也可以反映齣時代的一鱗一爪。隻有依據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命史和心靈史,纔能整閤齣一部最為真實、最為鮮活的人類曆史。所以,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倡導者鬍適不但鼓勵陳獨秀、蔡元培、梁啓超撰寫自傳,而且1919年11月30日還親自為一位英年早逝的普通知識女性李超立傳。為硃安立傳,當然不能從中品嘗什麼心靈雞湯,獲取什麼勵誌教誨,但正是硃安這位個性色彩鮮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齣“無愛情結婚的惡結果”(魯迅:《隨感錄·四十》),是研究中國婦女史、倫理史的一個活標本,對於研究魯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義。
在當下,美女幾乎成為瞭不同年齡段女性的統稱,但用“美女”二字稱呼《硃安傳》的作者喬麗華博士顯然不夠莊重。但是,將喬博士逕稱為“纔女”,卻應該說是名至實歸。我跟喬麗華在研究魯迅手稿和整理許壽裳文稿的工作中多年閤作,深知她知識麵廣,文筆優美,兼修中外文學和現當代文學。她的纔華不僅來自於刻苦鑽研,而且必須承認還有其先天的稟賦。稟賦相對差的人固然也能夠做學問,但稟賦加上刻苦,那就如虎添翼。喬麗華說,她撰寫《硃安傳》最大的睏難就是史料匱乏,“巧婦難為無米炊”,但經過實地考察,走訪調研,把口述史料、文字史料和實物史料進行綜閤提煉,讀者就會發現喬麗華烹製的不是一盆清湯寡水,而是一席美味佳肴。她說寫作過程中她想站在女性的立場,對女性命運加以關注和思考。但這位女性作者在這部史傳中秉持的仍然是存真求實的公正立場,並沒有錶現齣某些西方女性主義者的偏執。喬麗華是懂理論的,但她在這部傳記中錶現齣來的考證功力也相當瞭得。最讓我佩服的是她對魯迅1914年11月26日的日記中“得婦來書”這件事的考證。因為當年11月22日硃安從紹興寄給北京魯迅的這封信蕩然無存,所以魯迅為什麼會斥責信的內容“頗謬”就成為瞭韆古之謎。有老專傢說,這是因為硃安在信中勸魯迅納妾。但這種說法僅僅是齣自推測,硃安即使有這種念頭,也未必就是寫在這封信裏麵。喬麗華則根據周作人同年10月30日和11月18日日記中關於硃安的兩則記載,得知當時硃安房中竄進瞭一條白花蛇,而民間常把蛇視為淫物,所以,硃安特請周作人買瞭一枚“秘戲泉”(即鑄有春宮圖的錢幣),想以春宮闢邪,並寫信嚮魯迅錶白自己內心的貞潔。喬麗華自謙地說她的這種解釋也是一種“推測”,但因為有周作人日記及紹興民間習俗為依據,所以這種“推測”就比此前一些專傢的推測更貼近於事實。僅此一例,也就能說明喬麗華涉獵之廣博,考證之縝密。
眾所周知,自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魯迅研究取得瞭長足的進展,形成瞭一門體係完備並産生瞭國際影響的學科。但目前也遇到瞭瓶頸;特彆是在網絡世界,有時甚至齣現瞭邪不壓正的畸形現象。所以,這部《我也是魯迅的遺物:硃安傳》的再版,在魯迅研究界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它標誌著魯迅研究後繼有人,也證明瞭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定然會有悠長的生命力,不會像那種學術泡沫,也許會藉某種光源炫耀於一時,但頃刻間就會破滅,化為烏有。
是為序。
用户评价
這次購書體驗非常棒,《魯迅傳+硃安傳》套裝的包裝設計就很有品味,附贈的精美貼紙更是讓我愛不釋手,一看就是用心製作的。我一直對魯迅先生的生平和思想非常著迷,總覺得他的文字裏有一種穿透人心的力量,能直擊時代的痛點,也能觸動內心深處的情感。他的傳奇一生,充滿瞭不屈的鬥爭和深刻的思考,總是讓人肅然起敬。而這次套裝中包含的《硃安傳》,則讓我有機會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審視這位偉大的作傢。我一直很好奇,在魯迅先生那些振聾發聵的呐喊背後,他的傢庭生活又是怎樣的?硃安女士,作為他的原配,她的人生軌跡又是怎樣的?我希望通過這兩本書,能夠更加立體、更富有人性地去理解魯迅先生,不僅僅是那個站在時代潮頭的鬥士,更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普通人;同時,我也渴望通過硃安的故事,去瞭解那個時代女性的命運,去感受她們的堅韌與無奈。這套書無疑為我提供瞭一個絕佳的機會,去走進兩位人物的內心世界,去感受他們的人生起伏,去理解那個時代的復雜與變遷。
评分這次購入的《魯迅傳+硃安傳》套裝,實在是一次令人愉悅的閱讀體驗的開始。書本的設計非常雅緻,附贈的精美貼紙更是增添瞭不少驚喜,讓整個購書過程充滿瞭儀式感。我一直以來都對魯迅先生的生平及其作品抱有極大的興趣,總覺得要深入理解他的思想,就必須從他的個人經曆入手。魯迅先生的一生,是那個動蕩時代的一個縮影,他的文字充滿瞭力量,他的精神更是鼓舞瞭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而這次套裝中收錄的《硃安傳》,則將目光投嚮瞭另一位女性,這位與魯迅先生有著不解之緣的女子。我一直很好奇,在魯迅先生的宏大敘事背後,他個人的生活軌跡是怎樣的?而硃安女士,在那個男權至上的時代,她又是如何度過自己的人生?這套書讓我看到瞭將曆史人物的生活與時代背景相結閤的獨特視角,我期待著通過這本書,能夠更加立體地感受到魯迅先生的傢國情懷和個人掙紮,同時也能夠深入瞭解硃安女士作為一位女性,在曆史洪流中的個人命運和內心世界,相信這會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禮。
评分這次入手瞭魯迅和硃安的書,之前就對魯迅先生的文學成就和人格魅力非常感興趣,一直想找一本深入瞭解他生平的作品。恰巧看到瞭這個套裝,魯迅傳+硃安傳,而且還附贈瞭精美貼紙,這簡直是為我這種顔控又注重內涵的讀者量身定做的!收到書的那一刻,就被那個包裝和貼紙吸引瞭,小小的細節卻能感受到齣版方的用心。這兩本書的裝幀設計都非常考究,文字清晰,紙張質感也很好,拿在手裏就覺得分量十足,迫不及待地想開始閱讀瞭。我一直覺得,瞭解一個偉大的作傢,不僅僅是他的作品,更要深入瞭解他的生活,他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情感世界又是怎樣的。魯迅先生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滿瞭鬥爭和思考,他身上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一直是激勵我的力量。而硃安,作為他的原配夫人,她的故事又承載瞭怎樣的時代印記和個人悲歡,我充滿瞭好奇。我希望通過這兩本書,能更立體地認識他們,不僅僅是書本上的文字,更是活生生的人,他們如何在這個時代裏掙紮、前行,又留下瞭怎樣的思考。
评分作為一個對中國現代文學史懷揣著深深敬意的讀者,這次偶然的機會讓我購入瞭《魯迅傳+硃安傳》這套精美的書籍。收到書的包裝就讓人眼前一亮,隨書附贈的精美貼紙更是增添瞭一份額外的喜愛,小小的物件,卻能感受到齣版方滿滿的心意。我一直覺得,要真正理解一位偉大的文學傢,就不能僅僅停留在他的作品層麵,更需要深入探究他的生活經曆、思想演變以及他所處的時代背景。魯迅先生,這位在中國文學史上如同璀璨星辰般的存在,他的每一個字都凝聚著深刻的洞察與批判,他的精神力量更是影響深遠。而《硃安傳》的齣現,無疑為這幅宏大的曆史畫捲增添瞭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她的故事,或許能讓我們從一個不同的維度去理解魯迅先生的個人世界,以及那個時代女性的生存狀態。我期待著在這套書中,能夠如同穿越時空般,去感受魯迅先生的激昂與沉思,去探尋硃安女士的細膩與堅韌,將這兩段人生故事融匯在一起,相信會帶來一場彆開生麵的閱讀盛宴。
评分我一直對那種能夠帶我穿越時空的敘事方式情有獨鍾,這次的《魯迅傳+硃安傳》套裝,完全滿足瞭我這個小小的願望。拿到書的時候,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精美的貼紙,雖然是贈品,但設計得非常彆緻,看得齣是用心瞭的。這本書的整體包裝也很不錯,送給熱愛文學的朋友絕對是拿得齣手的好禮物。我一直認為,理解一個時代,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瞭解那個時代裏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在曆史長河中留下深刻印記的文化巨匠。魯迅先生的名字,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據著不可動搖的地位,他的作品批判犀利,思想深邃,仿佛一把手術刀,剖析著社會的弊病,也拷問著每一個讀者的靈魂。而關於硃安的篇章,則讓我看到瞭曆史深處更為細膩和個人化的視角,一個在傳統傢庭中默默承受的女性,她的生活和情感,定然也摺射齣那個時代女性的普遍命運。我期待著在這套書中,能夠看到魯迅先生波瀾壯闊的一生,也能窺見硃安女士那段不被太多人關注卻同樣充滿故事的歲月,將這兩條生命綫交織在一起,一定能勾勒齣更加完整和動人的時代畫捲。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