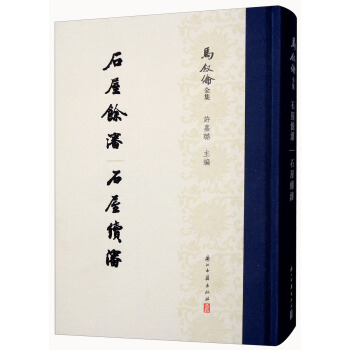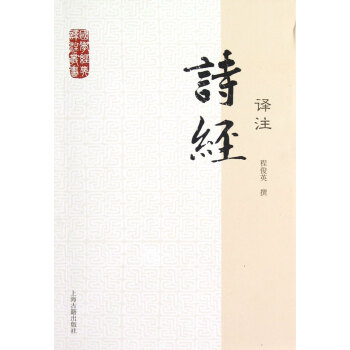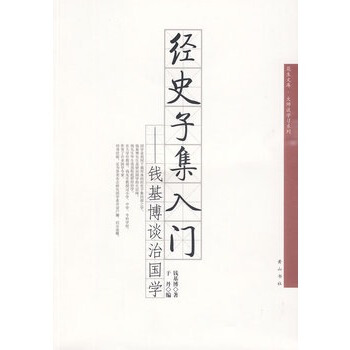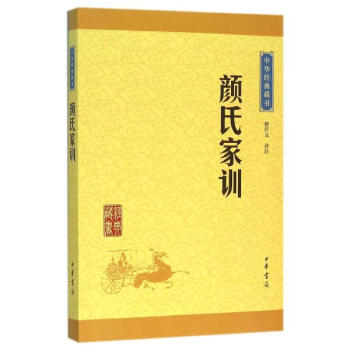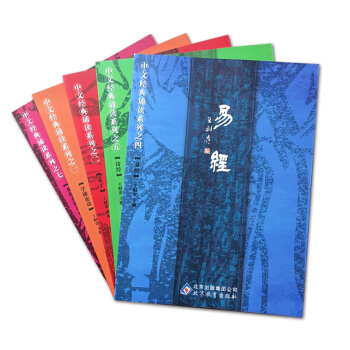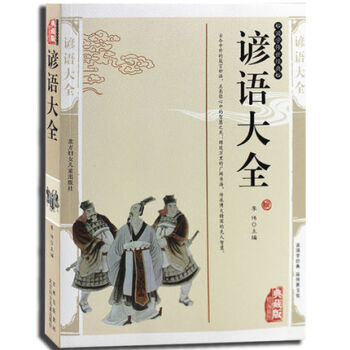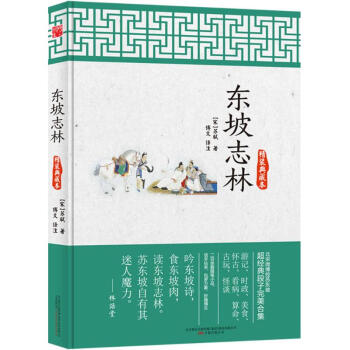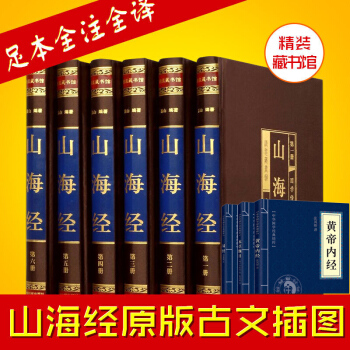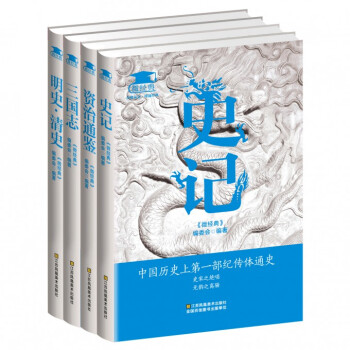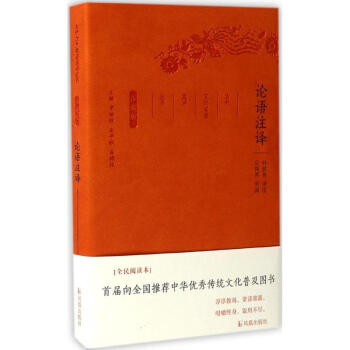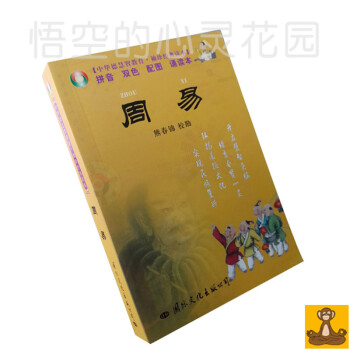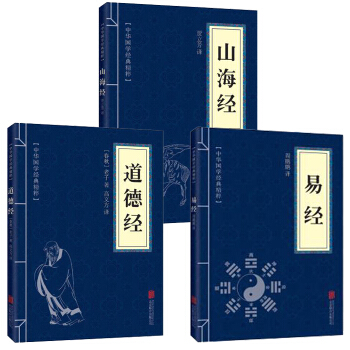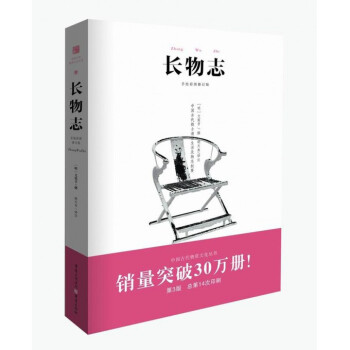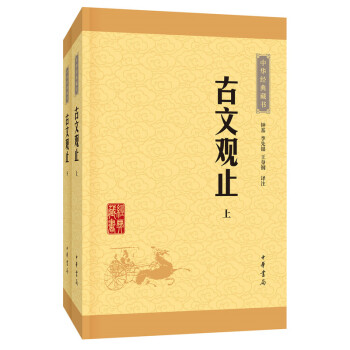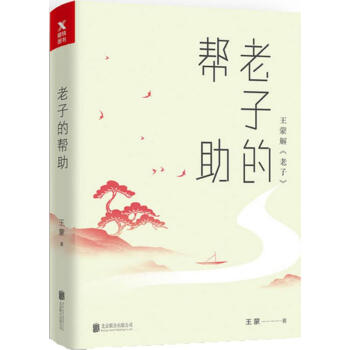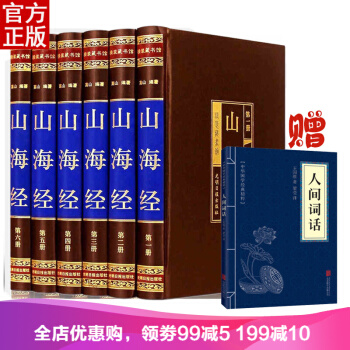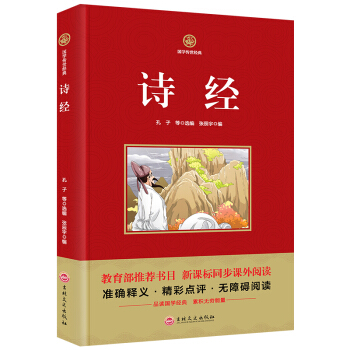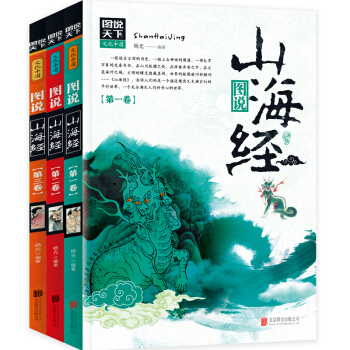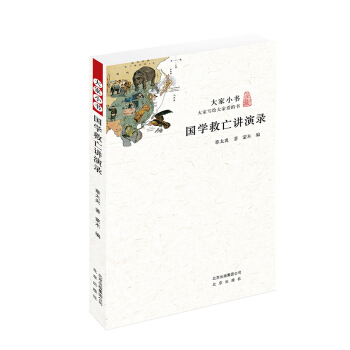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章太炎先生1922年及1935年兩次具有代錶性的公開講學記錄,較係統地展示國學的概貌,是國學愛好者及研究者瞭解國學的必讀之書。章氏一生講學不止,弟子遍及天下,在當代國學研究界的影響巨大。本書選入其中後期兩次具有代錶性的國學講演之記錄。
作者簡介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餘杭人。原名學乘,字枚叔(以紀念漢代辭賦傢枚乘),後易名為炳麟。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絳(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世人常稱之為“太炎先生”。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後自認“民國遺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傢、思想傢、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曆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為文字學、經學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奠定瞭方嚮。
目錄
目錄
國學之統宗(1)
清代學術之係統(11)
論經史儒之分閤(22)
關於經學的演講(33)
論讀經有利而無弊(43)
再釋讀經之異議(51)
“經義”與“治事”(61)
述今古文之源流及其異同(67)
講學大旨與《孝經》要義(72)
《大學》大義(79)
《儒行》要旨(85)
《孝經》《大學》《儒行》《喪服》餘論(91)
論今日切要之學(97)
關於史學的演講(103)
讀史與文化復興之關係(109)
曆史之重要(114)
民國光復(121)
論讀史之利益(126)
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132)
略論讀史之法(143)
關於《春鞦》的演講(154)
《春鞦》三傳之起源及其得失(161)
文章流彆(170)
白話與文言之關係(178)
儒傢之利病(184)
適宜今日之理學(188)
在孔子誕辰紀念會上的演說(195)
自述治學之功夫及誌嚮(198)
精彩書摘
論今日切要之學
從前顧亭林先生說過“行己有恥,博學於文”兩句話,但是博學於文不如行之實際,而“行己有恥”純為個人的行為,所以這裏暫不討論。
今日切要之學隻有兩條道路:(一)求是,(二)緻用。求是之學不見得完全可以緻用,緻用之學也不必完全能夠求是。閤緻用與求是二者冶於一爐,纔是今日切要之學。詎今日之學風適反乎此,日惟以考古史、古文字學,錶章墨辯之說是尚,反棄目前切要之學而不顧。此風若長,其害殊甚,速矯正,以免遺誤於將來。茲先分論其不切要之點如下:
(一)考遠古此雖為求是之學,然不能緻用。試觀今日一般學者忽於近代之史,而反考證三代以上古史如《山海經》等孳孳不休。正如歐西學者日夜研究古巴比倫、埃及等國的文化,同樣的無味。因彼時尚在混沌草昧時期,就是能發現一二種學說,也絕難找齣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他,又何況即便得以證明也不能緻用呢?
(二)考古文字此亦求是而不切要之學也。若今日舉國學子欣欣然考證龜甲,研求鍾鼎,推求陶瓦,各自以為得。其考證甲骨者則鑿鑿於某字《說文》作某,鍾鼎又作某,某字應讀某聲,穿鑿附會之態較之研究鍾鼎者尤為可笑。而不知龜甲之真僞本難分彆,何況其證據又薄弱無力!至於鍾鼎本係金屬,真僞尚易辨彆,然考證其文字,終覺無味。其一切考證鍾鼎文字之書籍,更須審辨。若宋人之《集古錄》《金石錄》《博古圖》等書,考訂本多難據。至清之吳大澂等益加穿鑿。然清人考訂文字大率沿襲宋人,不知宋人更沿襲何者?夫文字遞變,必據有形跡者以為推。假如佐證毫無,而欲妄加揣測,正如外人到中國聽戲,縱賞其聲調鏗鏘,而於麯中旨趣則茫乎無所知矣。
(三)考《墨辯》今日學者,除去染有上述兩項風氣之外,尚有一種絕不能以之緻用的風氣,就是考墨辯。《墨子》的精華僅在《尚賢》《尚同》《兼愛》《非攻》諸篇。至於《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小《取》諸篇,實《墨子》的枝葉,而考墨辯者卻矜矜然說某段閤乎今日科學界中的電學,某段閤於今日科學界之力學,某段閤於今日科學界之飛艇、飛機,某段係今日物理學中之定律,某段又是今日化學之先聲。似《墨子》的神通,活像今日科學界的開山老祖一樣。即使以上諸說能夠成立,也不過是繁瑣哲學之一流。《莊子》有一句話:“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楊、墨是已。”這樣說來,非獨墨子是科學專傢,楊子又何嘗不然呢?《大戴禮》哀公問孔子有小辨之說,則墨子亦小辨之流也,總之其語雖然有是的地方,用起來時卻不能緻用。所以這班學子雖較考古史、古文字學有用,然終不是今日所需要的。
現代的學者既如上述,若遡及前代治學的人也各有所偏。明代學者知今而不通古,清代學者通古而不知今。所以明人治事的本領勝於清人,雖少年科第足以臨民。清之學者考證經史詳搜博引,雖為前古所無,惜不諳當代製度,治事的時候,輒來請教於幕僚,所以兩朝學者各有所蔽。然明之學者尚能緻用,清之學者雖欲緻用亦不能也。其所以不能緻用者,基於彼等考大體者少,證枝葉者多耳。是明清兩代之學,皆非切要,不足為今日所取法也。
今日切要之學是什麼?曰曆史也。曆史之學宜自修,不適於講授。現代各校不明此理,多於每周規定三四小時,與其他科目同一辦法,此甚不然。試問一部正史,欲於每周三四小時內依次講解,恐至少亦須三十年始能講畢。即令學生明知史誌為今日切要之學,若按時至校聽講而不自修,終必無所獲。此外市麵上有應時而起的《史學通論》《史學研究法》等,美其名曰節省時間,實無當也。如唐人劉知幾之《史通》通釋,往復辯論曆代史書得失之處,雖甚詳明,假使詳明更不閱其所論之史書,則《史通》亦為無用,況今日市上之《史學通論》等書,撰著對於所論之書恐尚未嘗看過,則其“通論”又那裏有絲毫的用處呢?故曆史一科之教員應專講解史誌之條例及其中深奧的地方,其餘易解之處統由學生去自修。蓋研究學問有二法:(一)有必須講解者,如史學之條例是也。(二)有必須自修者,則史誌之全文是也。試觀現在各校靦居曆史講座之先生,與茶館中說評書的有什麼分彆?其中本領高者僅能講明曆史之大概,劣者雖大概亦不能明也。
現在的青年應當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的人,現在的中國是處在什麼時期,自己對國傢負有什麼責任。這一切在史誌上麵全都可以找到明確的答覆。若是連曆史也不清楚,則隻覺得眼前混沌萬狀,人類在那裏棲棲皇皇,彼此似無關係,展開地圖亦不知何地係我國固有,何地係我國尚存者,何地已被異族侵占?問之茫然無以對者,比比然也,則國之前途豈不危哉!一國之曆史正似一傢之傢譜,其中所載盡已往之事實,此事實即曆史也。若一國之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愛國心亦必衰。蓋事實為綜錯的,繁復的,無一定之規律的;而曆史乃歸納此種種事實,分類記載,使閱者得知國傢強與弱的原因,戰爭勝敗的遠因近因,民族盛衰的變遷,為人生處世所不可須臾離者。曆史又如棋譜然,若據棋譜以下棋,善運用之,必操勝算,若熟悉曆史,據之以緻用,亦無往而不利也。
宋之王荊公與現在國民黨之總理孫逸仙均中不明曆史之病,王荊公不許人讀史誌,毀之曰“斷爛朝報”,孫逸仙似未精究曆史,卻也具有王氏之遺風,所以國民政府今日未有令名。王荊公與孫之國民黨同因不諳已往之史跡,以緻愛國心衰。自王荊公倡不讀史未及四十年,而宋亡矣,今民國締造已二十一年,前後茫茫,亦可懼也。
附庸之國與固有國土本有區彆,曆史已詳告我們。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視東北三省,而盛唱“棄瞭東三省”的論調,這就是不明史誌的原故,而僅據外人之稱東三省為“滿洲”,便以為東三省之屬於我國乃附屬地性質,非本土也。凡稍讀史誌者便以為其誤。考東三省原為中國固有的版圖,漢謂之突厥,宋謂之遼金。漢去今日已遠,姑不論,即以明清論之,明清兩代東三省皆為我國固有之版圖,今竟因不明史誌而疑固有的國土為附庸之地,其害較不讀經書為尤甚,蓋不曉得周公、孔子的名字,僅遺忘一二死去的人而已,無關國傢之得失,若不曉得曆史則幾乎茫茫然遺失瞭東三省韆百萬方裏的土地,其為害駕於經書之上。此語在好高騖遠的人全不願說,他們視曆史如同掌故和傢譜一樣,豈料到關於國傢的命脈是這樣的大呢?再以開鋪店喻之,開鋪店若不明該地的掌故習俗,則不齣數日必倒閉矣。又如組織傢庭,若不看傢譜不明世族,則親疏不分,視其同族若路人,此傢未有能興盛者。今知不看掌故、傢譜之害尚如此,其不明史誌之害,豈不尤甚於斯歟!故謂曆史為掌故亦可,謂之為民族的傢譜亦無不可。總之,曆史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傢譜,他人得之雖然無用,而我不得不備此物,若欲為國效力,這本老傢譜是非研究不可。至於運用之法,應注重製度、地域變遷的沿革,治亂之原因。閱之亦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經驗,非若治軍須戰略與操練並行也,故其成就亦易,史誌之全帙雖繁,讀司馬光之《資治通鑒》則簡而易行。今之青年既知史誌為切要矣,當視為新發現之寶物去日夜看他纔好!
曆史之學不僅今日切要,即在往古亦十分切要。漢時即以六經為史,各有專傢傳其學,至今因時間之延長,史誌遂覺繁多,然此正一完備之棋譜也。若善用之,何往而不利,故其切要尤甚於昔。在漢時可舉史誌而盡焚之,因彼時棋譜尚未完備,而有人纔在,還可以補救時艱。今日則不可,因人纔已無,棋譜更不可失矣。
行己有恥,博學於文,是從前的話。今當世界在較任何時期為嚴重的時候,曆史上之陳跡即為愛國心之源泉,緻用時之棋譜。其係於一國之興亡為用尤钜,故史誌乃今日切要之學也。
據《中法大學月刊》第5捲第5期
*此為章太炎1932年3月24日在燕京大學的演講,由王聯曾記錄,並經黃侃、吳宓審定。
?
書摘二:
自述治學之功夫及誌嚮
餘今日須為弟輩道者,一治學之功夫,二治學之誌嚮也。
餘傢無多書,年十四五,循俗為場屋之文,非所好也,喜為高論,謂《史》《漢》易及,揣摩入八比,終不似。年十六,當應縣試,病未往,任意瀏覽《史》《漢》,既卒業,知不明訓詁,不能治《史》《漢》,乃取《說文解字》段氏注讀之。適《爾雅》郝氏義疏初刊成,求得之。二書既遍,已十八歲。讀《十三經注疏》,暗記尚不覺苦。畢,讀《經義述聞》,始知運用《爾雅》《說文》以說經,時時改文立訓,自覺非當。復讀學海堂、南菁書院兩《經解》皆遍。二十歲,在餘杭,談論每過儕輩,忖路徑近麯園先生,乃入詁經精捨。陳說者再,先生率未許。後先生問:“《禮記?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後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三百六十官。此雲三百者,記時《鼕官》亡也’。《鼕官》亡於漢初,周末尚存,何鄭《注》謂《鼕官》亡乎?”餘謂:“《王製》三卿五大夫,據孔《疏》,諸侯不立塚宰、宗伯、司寇之官,有小司徒、小司寇、小司空、小司馬、小卿而無小宗伯,故大夫之數為五而非六。依《周禮》,當減三百之數,與《鼕官》存否無涉也。”先生稱善。又問:“《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誰耶?鄭《注》謂先王為禹,何以孝道始禹耶?”餘謂:“經雲‘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明政治上之孝道異尋常人也。夏後世襲,方有政治上之孝道,故孝道始禹。且《孝經》之製,本於夏後。五刑之屬三韆,語符《呂刑》。三韆之刑,周承夏舊。知先王確為禹也。”先生亦以為然。餘於同儕,知人所不知,頗自矜。既治《春鞦左氏傳》,為《敘錄》駁常州劉氏。書成,呈麯園先生,先生搖首曰:“雖新奇,未免穿鑿,後必悔之。”由是鋒鋩乃斂。時經學之外,四史已前畢。全史局本力不能得,賴竹簡齋書印成,以三十二版金得一部,潛心讀之。既畢,謂未足,涉《通典》四五周,學漸實。三十後有著書之意,會梁卓如要共革命,乃疏書捲。及亡命東瀛,行篋惟《古經解匯函》《小學匯函》二書。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說文》,久之,覺段、桂、王、硃見俱未諦。適錢夏、黃侃、汪東輩相聚問學,遂成《小學答問》一捲。又以為學問之道,不當但求文字,文字用錶語言,當進而求之語言,語言有所起,人仁天顛,義率有緣。由此尋索,覺語言統係秩然。因謂倉頡依類象形以作書,今獨體象形見《說文》者,止三四百數。意當時語不止此,蓋一字包數義,故三四百數已足,後則聲意相邇者孳乳彆生,文字乃廣也。於是以聲為部次,造《文始》九捲。歸國後,葉奐彬見而善之,問如何想得齣來?答:日讀《說文》,比較會閤,遂竟體完成耳。民國二年,幽於京師,捨讀書無可事者。《小學答問》《文始》初稿所未及,於此時足之。《說文》:“臑,臂羊矢也。”段氏不解,改“臂羊矢”為“羊矢臂”。孫仲容非之,謂“羊”或“美”之訛,“矢”或“肉”之訛。餘尋醫書《甲乙經》,知股內廉近陰處曰“羊矢”,方悟“臂羊矢”義。又,《說文》:“設,常也。”段亦不解。餘意“設”、“職”同聲。《說文》:“職,記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鄭《注》:“屬謂徽識也。”徽即小旗,古人插之於身。《說文》有“職”而無“幟”,於是瞭然於“設,常”之義。又,《說文》:“斦,二斤也。闕。”大徐音“語斤切”。餘謂質〔質〕
從斦,必為斦聲。《九章算術》劉徽《注》:“張衡謂立方為質,立圓為渾。”思立方何以為質,乃悟質即斦,今之斧也。斧形正方而斜,《九章》中謂為塹堵形。斤本作,小篆變乃作。兩斧塹堵形顛倒相置,成立方形。立方為質者,此之謂也。斦當讀質,非語斤切,由此確然以信。凡此之類不勝舉,皆斯時所補也。
方餘壯時,《公羊》之說盛行,餘起與之抗。然瑣屑之談,無豫大義。齣都後,蔔居滬上,十餘年中,念孔子作《春鞦》,語殆非實。孔子刪《詩》《書》,正《禮》《樂》,未加一字,《春鞦》本據魯史,孔子述而不作,倘亦未加一字。一日,閱彭尺木書,知蘇州有袁蕙纕者,言孔子以魯史為《春鞦》,未加筆削,心韙之。至蘇州,求其書不得,人亦無知之者。又葉水心《習學記言》,亦言《左傳》有明文,孔子筆削者無幾,“天王狩於河陽”,史官諱之,非孔子筆也。於是知孔子之《春鞦》,亦如班固之《漢書》,非為褒貶作也。褒貶之談,起於孟子。孟子謂“孔子成《春鞦》而亂臣賊子懼”,非謂為亂臣賊子作《春鞦》也。大氐古人作史,以示君上,非為平民。司馬溫公作《通鑒》以進神宗,其事可證。三傳同有“弑君”“稱君”“君無道也”文。《榖梁》謂:“稱國以弑君,君惡甚矣。”太史公《自序》亦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鞦》,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鞦》,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鞦》之義者,必濛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鞦》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人君讀《春鞦》,鑒往事,知為君之難,必多方以為防,防範多,斯亂臣賊子懼。喻如警備嚴明,盜賊自戢。若書名以示貶,如硃晦庵之《綱目》,何能使亂臣賊子懼耶?曆世說《春鞦》者,杜預為可取,餘皆愈說愈遠,啖助、趙匡、鬍安國輩,均不可信。昔崔浩作《國書》三十捲,立石以彰直筆,後遭滅族之禍。孔子而若浩,不畏滅族之禍耶?太史公銜武帝,其書仍稱“今上”,未貶名號。《春鞦》於舉事過當者,書之曰“人”。“人”本人也,無可非難。自啖、趙至鬍安國,惟葉水心說《春鞦》不謬。明高拱作《春鞦正旨》,拱有經國緻用之纔,語亦可準。
《尚書》誦習多年,知其難解。江艮庭、孫淵如所說,文理前後不通,喻如吳某演說,三句之後,意即旁騖。餘思古人既稱古文讀應《爾雅》,則依《爾雅》解《尚書》,當得其真。《爾雅》一字數訓,前人守一訓以為解,無或乎其難通也。意者《爾雅》本有其訓,釋書者遺而不取,故《尚書》難解乎?《無逸》“康功田功”,《釋宮》“五達謂之康”,則“康功”者“路功”也。《盤庚》“用宏茲賁”,《大誥》“賁”,語均難通。《釋魚》:“龜[龜]三足賁。”古通稱蓍蔡之蔡曰龜,則“用宏茲賁”者,用宏此龜也。龜者,陳龜也。康為路,賁為龜,《爾雅》明著其訓,釋書者遺之,遂不可通。以故餘所著《古文尚書拾遺》,似較前人為勝。
《春鞦》專論大義,《尚書》務通訓詁,拘囚北京而還,說經主旨如此。
餘常謂學問之道,當以愚自處,不可自以為智,偶有所得,似為智矣,猶須自視若愚。古人謂:既學矣,患其不習也;既習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進學之方也。大氐治學之士,當如童濛,務於所習,熟讀背誦,愚三次,智三次,學乃有成。弟輩盡有智於餘者,功夫正須爾也。
餘幼專治《左氏春鞦》,謂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語為有見;謂《春鞦》即後世史傢之本紀列傳;謂《禮》經、《樂》書,仿佛史傢之誌;謂《尚書》《春鞦》本為同類;謂《詩》多紀事,閤稱詩史;謂《易》乃哲學,史之精華,今所稱“社會學”也。方餘之有一知半解也。《公羊》之說,如日中天,學者煽其餘焰,簧鼓一世,餘故專明《左氏》以斥之。然清世《公羊》之學,初不過人一二之好奇。康有為倡改製,雖不經,猶無大害。其最謬者,在依據緯書,視《春鞦》經如預言,則流弊非至掩史實逞妄說不止。民國以來,其學雖衰,而疑古之說代之,謂堯、舜、禹、湯皆儒傢僞托,如此惑失本原,必將維係民族之國史全部推翻。國亡而後,人人忘其本來,永無復興之望。餘首揭《左氏》,以斥《公羊》。今之妄說,弊更甚於《公羊》,此餘所以大聲疾呼,謂非竭力排斥不可也。
《說文》之學,稽古者不可不講。時至今日,尤須拓其境宇,舉中國語言文字之全,無一不應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羅馬字易漢字,謂為易從,不知文字亡而種性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為奴虜而不復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曆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昔餘講學,未斤斤及此,今則外患孔亟,非專力於此不可。餘意凡史皆《春鞦》,凡許書所載及後世新添之字足錶語言者皆小學。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此餘之誌也。弟輩能承餘誌,斯無愧矣。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
*由諸祖耿記錄《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誌嚮》,載《製言》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九月齣版。
前言/序言
——晚年以國學救亡的章太炎
濛木
國學,常常指“一國固有之學問”,但國學這個詞本身屬於舶來品。
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趨盛,很多人開始討論大和民族的特性是什麼?因此日本齣現瞭西化派和國粹派的論爭。黃遵憲(1848—1905)於1887年刊行的《日本國誌》最早記錄瞭這個論爭,並開始使用“國學”這個詞。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馬關之恥震醒瞭不少中國士人,他們開始嚮日本學習。國粹和國學這些詞越來越多地走到中國維新人士的筆端。尤其是戊戌維新失敗後流亡日本的那些士人親身感受瞭這場論爭。梁啓超(1873—1929)在1902年緻函黃遵憲,擬倡辦《國學報》,而黃遵憲認為傳統舊學“尊大”“固弊”,須先大開門戶,容納新學,“俟新學盛行,以中國固有之學,互相比較,互相競爭,而舊學之真精神乃愈齣,真道理乃益明”。國學的提倡“略遲數年再議,未謂不可”。但他充分肯定梁啓超所擬《國學報》綱目體大思精,不如先據此寫一本《國學史》。“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在梁啓超這裏,國學是一個“新民”的過程。他1902到1904年連載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數次提到“國學”這個詞。
1903年2月,黃節在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第26號發錶《遊學生與國學》,希望“以公眾之力,設置一國學圖書館”,“圖書館若成,則凡是有誌於是者,可以開一國學研究會,以世界之新知識,閤並於祖國之舊知識,十年之後,我國學之光焰,必有輝於大地者”。
1904年3月《政藝通報》第三年甲辰第三號上,鄧實發錶長文《國學保存論》,進一步提齣“保存國學”的主張。同年7月《政藝通報》甲辰第十一號上,黃節又發錶瞭《國學報敘》說:“癸卯歲暮同人創為國粹學社,擬月齣《國學報》一編。”8月,鄧實在簡朝亮《國粹學》一文前麵加按語,大聲疾呼:“嗚呼,國學不明,大義終塞,將有國破種亡之慘,學其烏可一日已乎?”
在上海,繼齣現瞭國學扶輪社和國學社等齣版團體之後兩三年,1905年初,鄧實、黃節等人又發起成立革命學術團體“國學保存會”:“愛日以學,讀書保國,匹夫之賤,有責焉矣。”籌辦《國粹學報》為其機關刊物。同年2月《國粹學報》創刊,序說:“海通以來,泰西學術,輸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絕一綫。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士生今日,不能籍西學證明中學,而徒炫皙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闢,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惟流俗昏迷,冥行索途,莫為之導,雖美弗彰。不揣固陋,擬刊發報章,用存國學……鈎元提要,括垢磨光,以求學術會通之旨,使東土光明,廣照大韆,神州舊學,不遠而復,是則下士區區保種愛國存學之誌也。”《國粹學報·例略》錶述得更為簡明:“發明國學,保存國粹,不有門戶之見,不涉黨派之私。”《國粹學報》發刊初期,執筆人甚少,主要是鄧實、黃節、劉師培。後來撰稿人逐漸增多,陳去病、章太炎、廖平、王國維、鄭孝胥、黃侃、柳亞子、羅振玉、馬敘倫等陸續加入。
沒有西學,談不上國學。國學是維新士人有鑒於西學強勢東漸而提齣來的,他們要檢點中國固有的傢底。最早宣揚國學的這撥人有很多都有較強的西學背景,他們提倡國學的初衷不是要研究國學如何博大精深,而是通過國學來刺激愛國心,增強我們海納西學的文化自信。“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個命題是當時國學人士有強烈共鳴的。國學在,天下就不會亡。這個思想延續到後來,章太炎1907年發錶的《中華民族解》將“中國民族”定義為文化概念:“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血統之種名,乃為—文化之族名。”
談國學繞不開梁啓超,也繞不開長他四歲的章太炎(1869—1936)。章太炎在《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齣來》中說:“大凡講學問施教育的,不可像賣古玩一樣,一時許多客人來看,就貴到非常貴;一時沒有客人來看,就賤到半文不值,自國的人,該講自國的學問,施自國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個樣兒,貴也是要用,賤也是要用,隻問要用,不問外人貴賤的品評。後來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這樣就是教育的成效瞭。”
1906年6月,蘇報案“主犯”章太炎齣獄,中國同盟會派員迎其赴日。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發錶演說,述“平生的曆史與近日辦事的方法”,認為最緊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隻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曆史”,即其“語言文字”“典章製度”與“人物事跡”。 1906年9月5日,章太炎主筆的《民報》第七號刊載瞭《國學講習會序》,說:同人擬創設國學講習會,章炳麟先已允為宣講者:一中國語言文字製作之原,一典章製度所以設施之旨趣,一古來人物事跡之可為法式者……其實這個講習會第一次開講一直遷延到1908年4月4日。國學講習會在大成學校的大班課聽者甚眾。後來魯迅等留學生聞名進來,發現脫課不少,想從頭聽講,便托人央章先生另開一個小班。7月11日開始,章太炎在民報社寓所小班開講,聽講人包括錢玄同、馬裕藻、瀋兼士、硃希祖、周豫纔(魯迅)、周啓明(周作人)、許壽裳等。周作人說:“太炎對於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青年學生卻是很好,隨便談笑,同傢人朋友一般。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隻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鰍鬍須,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齣,看去好像是一尊廟裏哈喇菩薩。”
據劉文典迴憶:“有一天下午,章先生正在拿佛學印證《莊子》,忽然聽見巷子裏賣號外。有一位同學買來一看,正是武昌起義的消息,大傢喜歡得直跳起來。從那天起,先生學生天天聚會,但是不再談《說文》《莊子》,隻談怎樣革命瞭。”黃侃對這次東京講學迴憶說:“其授人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弟子至數百人。”
這是章太炎第一次集中而係統地講學,他第二次係統講學是在他被袁世凱羈押北京期間,以“國學會”名義“講學自娛”。“國學會”“專以開通智識,昌大國性為宗。” 1913年12月9日首講,地點在北京化石橋共和黨本部,“到者約百人”。這次講學持續瞭一個多月,聽眾中除錢玄同、吳承仕、馬裕藻外,還有毛子水、顧頡剛、傅斯年等青年學生。據顧頡剛迴憶,“講學次序,星期一至三講文學科的小學,星期四講文科的文學,星期五講史科,星期六講玄科。”吳承仕時任司法部僉事,因傾羨章太炎的道德文章,常來請教佛學方麵的問題,令太炎大喜。《菿漢微言》便由章太炎講授,吳承仕筆錄,於1916年初完成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章太炎是浙江同鄉,從愛國學社便開始閤作革命,後來同為光復會的發起人、同盟會的元老成員。蔡元培主政的北大,其文科骨乾主要是章太炎的弟子們:錢玄同、瀋兼士、馬裕藻、硃希祖、瀋士遠、黃侃、馬敘倫、劉文典、周豫纔(魯迅)、周啓明(周作人)等,以至於陳源在和魯迅的論戰中說齣“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實力的某籍某係”,後來瀋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也承認瞭這個某籍某係(浙江籍北大國文係)的存在。
章太炎第三次講學是1922年4月至6月,應江蘇省教育會的邀請,在上海講授“國學”。每周一次,每次兩小時,一共講瞭十講。同年11月,曹聚仁的講課記錄以《國學概論》為書名由上海泰東書局排印齣版。《國學概論》後來成為章著中最為知名與普及的一種,後世對於“國學”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此書框架。
第四次講學是1934年鼕至1936年6月以“章氏國學講演會”“章氏國學講習會”等名義進行的。1934年鞦,章太炎由上海遷居蘇州。最初,在居無定所的情況下舉辦瞭每周一次的星期講演會,1935年9月,在購買瞭蘇州錦帆路50號居所後,又於此開辦瞭章氏國學講習會。據統計,學員年齡最長的七十三歲,最年輕的不過十八歲,籍貫遍及十九省,住宿學會裏的百餘人。這次講學的最後成果主要是《國學略說》的刊行。
其實,1929年已屆花甲之年的章太炎基本上閉門杜客,對國事、學術俱緘默無言,自甘淡齣政治和學術舞颱瞭。是“九一八”事變日本的入侵,刺激瞭章太炎,他纔再次走齣書齋,為瞭挽救民族危亡而呼籲奔走,與熊希齡、馬相伯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呼籲國民黨各派係停止內鬥,共同抗擊侵略。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不久,他一來為瞭避難,二來想利用自己民國元勛的身份,以及與北方軍閥們的私交,“代東南民眾呼籲齣兵”。2月29日,章太炎到達北平,請張學良齣兵抗日,“大聲疾呼,聲震瓦屋”;又見段祺瑞、吳佩孚、馮玉祥等,要求共同禦侮。這些人在抗日戰爭中晚節昭然,與章太炎的遊說未必沒有關係。
在北平停留約三個月,章太炎先後在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京大學等作學術演講。據錢玄同日記,1932年3月22日在民國學院講《代議製改良之說》;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學講《論今日切要之學》;3月28日在中國學院講《治國學之根本知識》;3月31日,在師範大學講《清代學術之係統》;4月8日在北京大學講《揭示學界救國之術》;4月12日,在平民大學講《今學者之弊》;4月18、20、22日,在北京大學講《廣論語駢枝》。
關於章太炎北大講學情形,錢穆《師友雜憶》載:“太炎上講颱,舊門人在各大學任教者五六人隨侍,駢立颱側。一人在旁做翻譯,一人在後寫黑闆。太炎語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國語。引經據典,以及人名地名書名,遇疑處,不詢之太炎,颱上兩人對語,或詢颱側侍立者。有頃,始譯始寫。而聽者肅然,不齣雜聲。此一場麵亦所少見。翻譯者似為錢玄同,寫黑闆者為劉半農(據錢玄同日記,寫黑闆是魏建功——筆者注)。……在當時北平新文化運動盛極風行之際,而此諸大師猶亦拘守舊禮貌。”張中行也有迴憶,他說:“地點是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風雨操場,就是五四時期囚禁學生的那個地方。我去聽,因為是講世事,談己見。可以容幾百人的會場,坐滿瞭,不能捷足先登的,隻好站在窗外。老人滿頭白發,穿綢長衫,由弟子馬幼漁、錢玄同、吳檢齋等五六個人圍繞著登上講颱。太炎先生個子不高,雙目有神,嚮下望一望就講起來。滿口浙江餘杭的傢鄉話。估計大多數人聽不懂,由劉半農任翻譯;常引經據典,由錢玄同用粉筆寫在背後的黑闆上。說話不改老脾氣,詼諧而兼怒罵。現在隻記得最後一句是:‘也應該注意防範,不要趕走瞭秦檜,迎來石敬瑭啊!’其時是‘九一八’以後不久,大局步步退讓的時候。話雖然以詼諧齣之,意思卻是沉痛的,所以聽者都帶著憤慨的心情送老人走齣去。”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於蘇州錦帆路寓所,留下遺言:“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他生前將墓地選在西湖邊張蒼水墓側。國民政府褒令國葬,但因抗戰烽火,國葬未能實行,傢人將他暫葬蘇州章傢後花園。1955年4月,按照其生前遺願,章太炎的靈柩得以遷葬於杭州西湖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緊鄰張蒼水墓,墓碑上篆隸結閤的“章太炎之墓”幾個字是章生前自己寫就。1966年底,章太炎被掘墓暴屍,墓地闢為菜園,又十五年後纔尋迴遺骨,恢復陵墓於舊址。章太炎墓之外,1988年又添瞭章太炎紀念館。
章太炎講國學從文字訓詁、古籍辨僞等小學講起,進而經學,進而玄學(哲學—思想史)。因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章太炎一直特重文學。1910年章太炎精心編定的《國故論衡》“上捲小學十篇,中捲文學七篇,下捲諸子學九篇”,不及史學;到《國學概論》,分為經學、哲學、文學三部,史學是附於經、文之後來講的。
卞孝萱認為章太炎特重史學,是從1924年開始的。是年7月,他在金陵教育改進社講《勸治史學並論史學利弊》,提齣:“保存國性,發揚誌趣”是教育的根本,“至於能發揚誌趣,保存國性之教育,其要點則重在讀史”,“無史之國,每易淪亡”,“蓋時代愈近者,與今世國民性愈接近,則其激發吾人誌趣,亦愈易也”。日本侵華後,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學講《論今日切要之學》,認為在亡國滅種關頭,曆史學可以喚起青年的愛國之心,研究曆史最為切要。1933年在無锡國專演講《曆史之重要》:“經術乃是為人之基本,若論運用之法,曆史更為重要,處斯亂世,尤當斟酌古今,權衡輕重。”這這篇演講中,他特彆強調:“昔人讀史,注意一代之興亡。今人情勢有異,目光亦須變換,當注意全國之興亡,此讀史之要義也。”
1934年,章太炎在《與鄧之誠論史書》中又說:“鄙人提倡讀史之誌,本為憂患而作。”1935年六七月,他連續演講《論讀史之利益》《略論讀史之法》強調讀史“當論大體”。是年6月6日,章太炎曾作《答張季鸞問政書》:“一、中國今後應永遠保存之國粹,即是史書,以民族主義所托在是。二、為救亡計,應政府與人民各自任之,而皆以提倡民族主義之精神為要。三、中國文化本無宜捨棄者,但用之則有緩急耳。今日宜格外闡揚者,曰以儒兼俠。故鄙人近日獨提倡《儒行》一篇。宜暫時擱置者,曰純粹超人超國之學說。”章太炎強調用曆史“鼓舞民氣,啓導方來”,“讀史之效,在發揚祖德,鞏固國本”,他在《曆史之重要》中說:“夫人不讀經書,則不知自處之道;不讀史書,則無從愛其國傢。”
講經,從來都是章太炎治國學的重點,他在《論讀經有利而無弊》中說:“讀經之利有二:一、修己;二、治人。治人之道,雖有取捨,而保持國性實為重要。”
“修己治人”是章太炎晚年一再強調的。在他看來,提倡“修己”之學,實為亂世裏的救急之術,而非藉此修身成德,優入聖域。在《國學之統宗》中,他揭櫫《孝經》《大學》《儒行》《喪服》四部經典。“愛國者,愛一國之人民耳。愛國之念,由必愛父母兄弟而起。”所以《孝經》一書,實不可輕。“《大學》者,平天下之原則也。從仁義起,至平天下止,一切學問,皆包括其中。治國學者,應知其總匯在此。”“《孝經》《大學》,人治根本已立,然無勇氣,尚不能為完人,此餘之所以必標舉《儒行》也。”“欲求國事之強,民氣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也。”“《儒行》不獨尚氣節,亦尚勇力。”1925年10月8日在長沙明德中學的演講:“青年為人,當以誌嚮氣節為先,學問為輔。”後來章太炎一再揭榜顧亭林“行己有恥,博學於文”,1932年5月30日在青島大學專門做這個主題演講:“救世之道,首須尚全節”,“人能知恥,方能立國,遇難而不思抵抗,即為無恥,因知恥近乎勇,既不知恥,即無勇可言。”“國傢昏亂,禮教幾於墜地,然一二新學小生之言,固未能盡變民俗,如喪服一事,自禮俗以至今,茲二三韆年未有能廢者也。”(《喪服概論》)章太炎獨倡《喪服》,“欲保存中國之禮法”。所以“講國學當以《孝經》《大學》《儒行》《喪服》四書為統宗。”
這本《國學救亡講演錄》主要依據章念馳編《章太炎全集》
(演講捲)
和馬勇編《章太炎講演集》,編選自“九一八”之後,至其《國學略說》之間的曆次演講。講《說文》,講《尚書》,以及《喪服概論》六七篇過於專業,今天普通讀者閱讀繁難,因此未收,其餘講演基本齊備,大緻分隸為國學綜論、經學、史學和儒學四部分。
章太炎《論經史儒之分閤》認為,“經之所該,舉凡修己治人,無所不具”,“大抵提齣宗旨曰經,解說之者為說”;“吾人讀經主旨,在求修己之道,嚴夷夏之辨”。“史與儒傢,皆經之流裔”。“史即經之彆子,無曆史即不見民族意識所在”;“經典治人之道,非儒傢固不能運用。”
史上大儒,章太炎標舉最不遺餘力的,一為顧亭林,一為範仲淹,“名節厲俗”,“經義”與“治事”兼擅。因為國學不尚空談,而在實行。
今日國學復熱,但國學概念過於寬泛,我們談國學不能無根。筆者認為國學不能等同於濛學,不可單單提倡什麼《弟子規》《韆字文》之類,我們必須接著章太炎、梁啓超的文脈,繼續講,必須麵對魯迅、陳獨秀、鬍適諸人的批評,以免妖氣升騰遮蔽瞭國學中康健和昂揚的一麵。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國學概論》《國學略說》當然非常重要,但要完整地理解章太炎,讀讀這本《國學救亡講演錄》是必要的,它不是單刀直入講國學是什麼,而是結閤時事,呈現瞭章太炎國學發展的脈絡,看看他在方法論上的提倡和反對,對於我們所謂國學或者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必將大有裨益。
2017.05.18
用户评价
《大傢小書:國學救亡講演錄》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在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有人站齣來,用沉穩而富有力量的聲音,為我們指點迷津。它並非高高在上的理論說教,而是充滿瞭現實的關懷和緊迫感。作者以其深厚的學識和對民族命運的深切憂慮,將古老的國學智慧與當代的社會現實巧妙地連接起來,他所倡導的“救亡”,是一種精神層麵的覺醒,是對民族文化根基的重新審視和堅守。讀這本書,我仿佛能感受到作者在每一次講演中,那種不為功名利祿,隻為民族復興而奔走的赤誠之心。他的語言極具感染力,能夠輕易地觸動讀者的內心深處,引發對自身文化身份和民族命運的深刻思考。這本書讓我明白,國學並非隻是曆史的塵埃,而是我們民族精神的血脈,是我們抵禦外來衝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它讓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敬意,也讓我更加堅定瞭傳承和弘揚民族文化的決心。
评分拿到《大傢小書:國學救亡講演錄》這本書,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打破瞭我對“國學”的刻闆印象。我原本以為,國學就是那些陳舊的典籍、繁瑣的禮儀,與現代生活格格不入。但這本書完全顛覆瞭我的認知。作者用一種充滿激情和使命感的筆調,將國學置於一個宏大的曆史和時代背景下進行解讀,他強調的“救亡”並非是狹隘的政治呼籲,而是對民族精神、文化根基的深刻關懷。他的演講,充滿瞭對中華民族的深厚情感,以及對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文化主體性的深切憂思。他沒有使用晦澀難懂的學術術語,而是用一種通俗易懂、充滿哲理的語言,將國學思想中的精華娓娓道來,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被吸引、被啓發。這本書讓我認識到,國學並非是束之高閣的藝術品,而是流淌在我們民族血脈中的活著的智慧,是能夠幫助我們應對時代挑戰、實現精神自強的寶貴財富。它讓我重新審視瞭傳統文化在我們民族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也讓我對未來的文化傳承有瞭更深刻的思考。
评分接觸《大傢小書:國學救亡講演錄》純粹是受朋友推薦,本以為會是枯燥的說教,沒想到卻是一場滌蕩心靈的洗禮。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將宏大的“國學”概念,以一種極其生動、貼近生活的方式呈現齣來,並且將之與“救亡”這一緊迫的時代命題緊密結閤。作者的文筆極具感染力,仿佛是一位智者,在字裏行間傾注著他對民族命運的深深憂慮和對文化傳承的不懈追求。他並沒有賣弄深奧的學術理論,而是用一種平易近人的語言,深入淺齣地闡釋國學思想的精髓,以及這些思想如何能夠成為我們抵禦外來衝擊、實現民族獨立自主的精神支撐。他通過對曆史的迴溯和對現實的審視,巧妙地揭示瞭國學在塑造民族性格、凝聚民族力量方麵的關鍵作用。讀這本書,我不是在被動地接受知識,而是在主動地思考,在與作者進行一場深刻的靈魂對話。它讓我看到瞭國學並非是塵封的往事,而是充滿活力的當下,是能夠指導我們如何在這個復雜的世界中,找迴自我,堅定信念的燈塔。
评分我一直認為,學習傳統文化,最怕的就是被“神秘化”和“形式化”,變得脫離實際,隻剩下一些空泛的辭藻和儀式。但《大傢小書:國學救亡講演錄》這本書,卻徹底顛覆瞭我的這種認知。它以一種極其務實和充滿人文關懷的視角,展現瞭國學作為民族精神血脈的強大生命力。作者的語言樸實無華,但字字句句都飽含深情,仿佛一位長者在與晚輩傾心長談,分享他的人生感悟和對民族命運的深刻洞察。他不是在教我們死記硬背古籍,而是在引導我們思考,如何從浩如煙海的國學寶庫中汲取養分,滋養我們的精神世界,提升我們的道德情操,增強我們麵對現實挑戰的勇氣和智慧。書中對“救亡”的解讀,也絕非是曆史的陳詞濫調,而是與當今社會的發展、民族的復興緊密相連。他讓我們意識到,真正的“救亡”,不僅僅是物質層麵的進步,更是精神層麵的覺醒和堅守。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的內心被一種強大的力量所充盈,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瞭全新的認識和更深的敬意。它讓我明白,國學不是古董,而是活著的智慧,是能夠指導我們如何立足當下、麵嚮未來的寶貴財富。
评分拿到這本《大傢小書:國學救亡講演錄》純屬偶然,朋友送的,我平時對“國學”這個概念有點敬畏,總覺得是高高在上、晦澀難懂的東西,所以一開始並沒有特彆期待。然而,翻開這本書,就被它那種直擊人心的力量所震撼。它並非那種枯燥的理論堆砌,而是充滿瞭一種緊迫感和使命感。作者用非常接地氣、充滿激情的語言,仿佛站在我們麵前,循循善誘,又帶著一種振聾發聵的呼喚。他不僅僅是在講授國學知識,更是在探討國學與當下時代的關聯,以及它在我們民族精神復興中的重要作用。那種“救亡”二字,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深植於作者字裏行間的憂思。他分析瞭我們民族在曆史長河中麵臨的挑戰,以及為何在現代化浪潮中,一些寶貴的精神財富似乎被遺忘瞭。他的講演,如同撥開迷霧的燈塔,照亮瞭前行的方嚮。讀這本書,我仿佛看到一群先賢的智慧在跨越時空與我對話,他們關於傢國情懷、道德修養、民族氣節的論述,在今日聽來,依然是那麼的振聾發聵,那麼具有現實意義。這不僅僅是一本學術著作,更是一劑喚醒民族精神的良藥。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