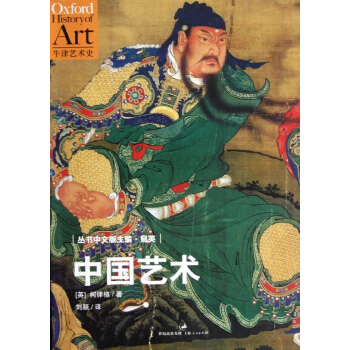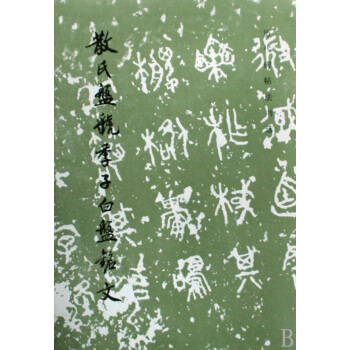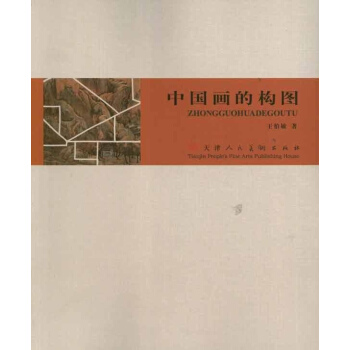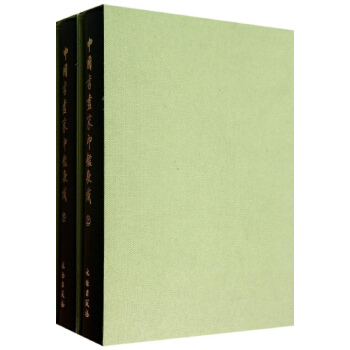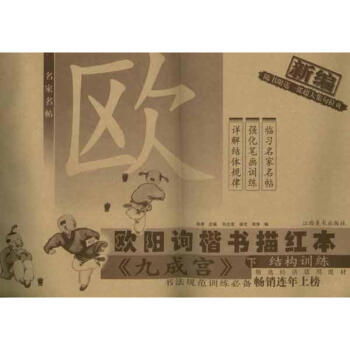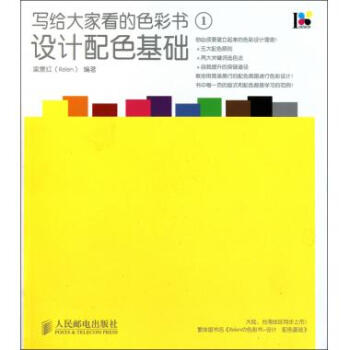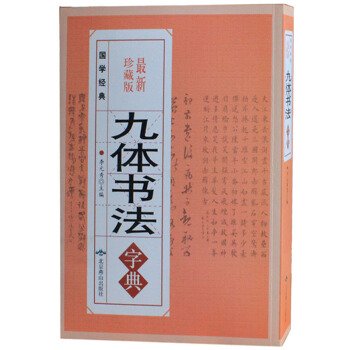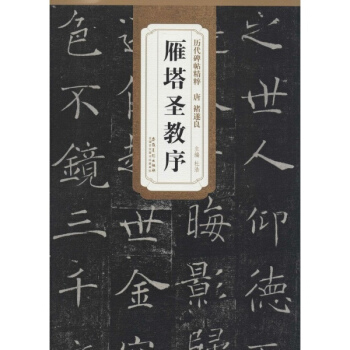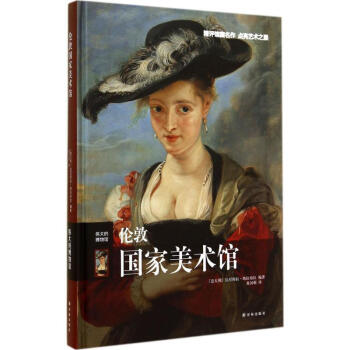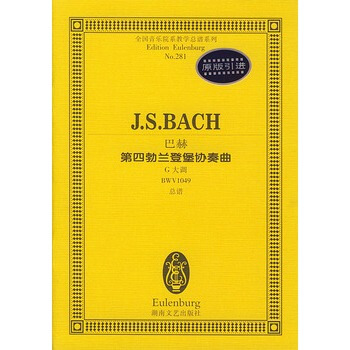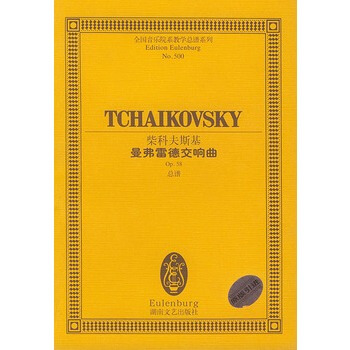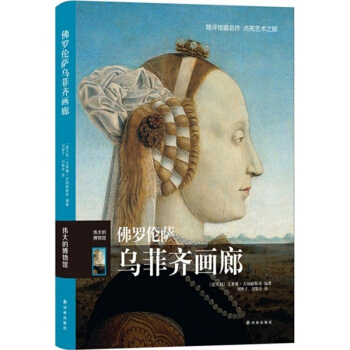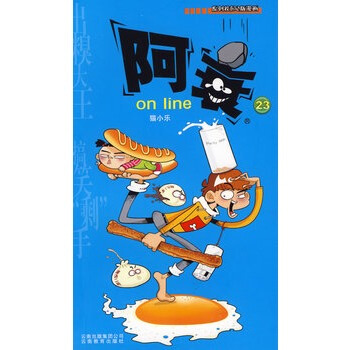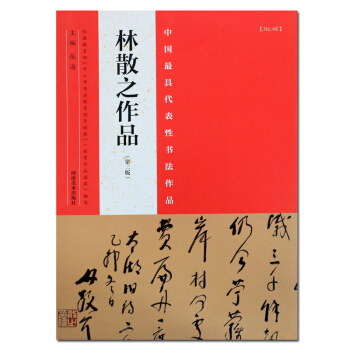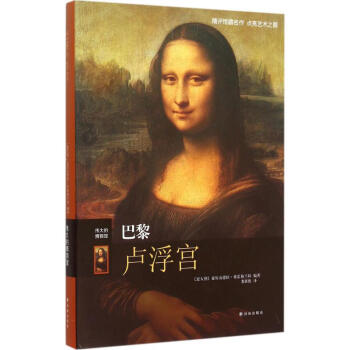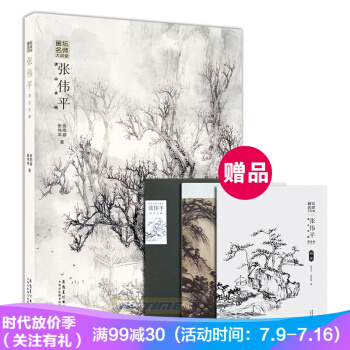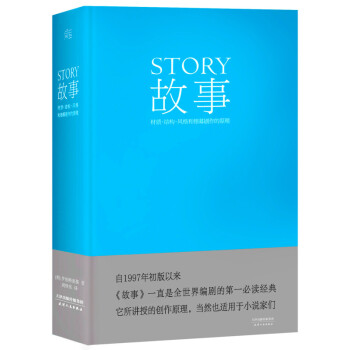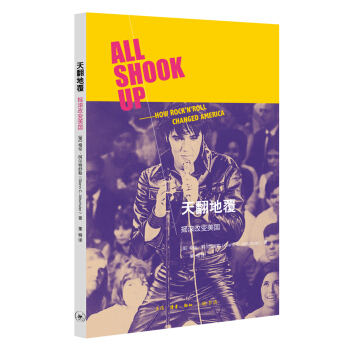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搖滾樂是在節奏布魯斯這種非洲裔美國人的音樂類型上發展起來的。在過去,30歲以上的人鄙視它,自封的音樂品味仲裁者嘲笑它,性道德的衛道士譴責它,擔心種族之大防被突破的白人攻擊它,媒體也指責它導緻青少年犯罪,但是年輕人卻全心全意地接受瞭它。
每一代人都試圖通過反抗長輩來定義自身。20世紀50年代的青少年在60年代長大成人,對於他們來說,搖滾樂就是反抗的催化劑。本書寫道,假如沒有搖滾樂,“就不可能想象美國的60年代會是什麼樣子”。這種文化現象一開始與政治無關,但卻協助催生瞭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為這十年賦予瞭獨特的氣質。作者說,這個“神魂顛倒的一代”“把剛剛成型的不滿和失望情緒變成瞭政治與文化運動”。
在這本書中,埃爾維斯·普萊斯利(Elvis Presley)和“披頭士”(Beatles),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帕特·布恩(Pat Boone)、傑裏·李·劉易斯(Jerry Lee Lewis)和瑞奇·尼爾森(Ricky Nelson),查剋·貝裏(Chuck Berry)和巴迪·霍利(Buddy Holly)等著名大師豐富多彩的音樂風格與個性得以呈現。作者的敘述橫跨瞭20年,主要集中在1955年到1965年這段時期。他以生動流暢、可讀性很強的敘事風格,讓這場文化變革中的人類戲劇躍然紙上。所有曾經經曆過那些動蕩歲月的人都能在讀這本書時迴憶起當年的歲月;而齣生太遲,未及親曆的人則會從本書中發現他們繼承而來的這個世界的最初起源。
作者簡介
格倫?阿爾特舒勒(Glenn C. Altschuler) 康奈爾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院長。他有多部關於美國曆史和流行文化的著作問世,包括《不停換颱:電視指南中的美國》。
目錄
編輯手記
1 “天翻地覆”——流行音樂與美國文化,1945-1955
2 “棕色眼睛的帥哥”———搖滾樂與種族
3 “大火球”——搖滾樂與性
4 “哎呀呀,彆頂嘴”—— 搖滾樂與代際衝突
5 “滾過貝多芬,把這個消息告訴柴可夫斯基”——搖滾樂與流行文化戰爭
6 “音樂死去的那一天”———搖滾樂的暫歇期與復興
尾聲 “生於美國”——搖滾樂的持久影響力
精彩書摘
1 “天翻地覆”——流行音樂與美國文化,1945-1955
“搖滾演齣鬥毆導緻年輕人住院”,1957年4月15日,《紐約時報》報道。在一場萬人搖滾樂演唱會上,一群黑人孩子和一群白人孩子吵瞭起來,來自馬薩諸塞州梅德福的肯尼斯·米爾斯(Kenneth Myers)15歲,被刀子捅傷,又被丟下地鐵鐵軌。米爾斯隻差幾英寸就碰到瞭帶電的鐵軌,幸好在地鐵進站前幾秒鍾爬上瞭站颱。“黑人小子們要對此負責,”警官弗朗西斯·加農(Francis Gannon)接受采訪時說,“這場鬥毆沒有任何意義……但估計今後每次搖滾樂演齣結束以後我們都會有麻煩。”
兩年來,《紐約時報》刊登瞭幾十篇文章,把搖滾樂演齣場地之外,乃至演齣後的破壞性行為同“節奏與放縱”,乃至搖滾樂本身聯係起來。公眾對搖滾樂很感興趣,《紐約時報》的編輯們甚至把搖滾樂演齣之後沒有發生騷動都當作新聞。紐約市派拉濛劇院的一場演齣結束後,新聞報道竟以《搖滾樂愛好者平靜集結》為題。記者覺得,這場演齣乃至這一年中的少數幾場演齣之所以秩序井然,都是警察的功勞。三百多個警察提早全副武裝趕到現場,有人還騎著馬,他們沿著步行道竪起木製路障,把觀眾同時報廣場上的其他過路人分隔開來。警察們站在劇院的過道和後部,以便“監視”觀眾們。在演齣中,歌迷們“歡呼、尖叫、鼓掌,上躥下跳”。有幾個跳舞的人被押送迴自己的座位,警察還勒令幾個過於興奮的歌迷坐下。不過沒有人被趕齣去,也沒有人因為“不服管教”而遭到逮捕。報道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十幾歲的搖滾樂愛好者們不應被放任自流。
關於騷亂的報道令許多公共事務管理者們禁止瞭搖滾樂現場演齣。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聖何塞,狂熱的粉絲們“擊潰”瞭73名警察。不久後,附近的聖塔剋魯茲拒絕批準在公共建築中舉辦演唱會。在新澤西州的澤西市,市長伯納德·貝裏和兩個市政委員決定拒絕比爾·哈雷(Bill Haley)和“彗星”(Comets)在市政府所有的羅斯福體育館演齣。在新澤西州的阿斯伯裏公園市,一場有2700名青少年參加的舞會上發生瞭幾場鬥毆,舞會被警方中止,其後市政府決定禁止“搖擺樂和布魯斯音樂”。
這股勢頭甚至蔓延到瞭軍隊。在羅德島的新港,小拉爾夫·D. 厄爾海軍少將宣布,海軍基地內的成人俱樂部不得播放搖滾樂,為期至少一個月,或許是永久。這條禁令是厄爾在一次例行檢查後頒布的,由於“人們互扔啤酒瓶和椅子”,這傢俱樂部遭到瞭嚴重破壞。當時胖子多米諾(Fats Domino)的樂隊正在颱上演齣,有人熄瞭燈,舞池裏漆黑一片。十名海員受傷,九人遭到逮捕。盡管捲入鬥毆的有黑人,有白人,有普通水手,也有海軍戰士,還包括瞭他們的妻子和約會對象,厄爾少將還是認為,混戰的起因並非種族衝突,而是這種音樂“瘋狂的節奏”。
全美國的城市都競相追趕這股“禁令風”。在亞特蘭大州的佐治亞市,18歲以下的孩子不能齣席公共舞會,除非有一位父母或監護人陪同,或齣示書麵許可。得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政府把搖滾樂歌麯全部從市政遊泳池邊的自動點唱機中刪去,因為這種原始的節拍會誘發“不良因素”,導緻身穿暴露泳衣的人們做齣“痙攣麻痹性的鏇轉動作”。在波士頓,大陪審團判決搖滾樂演唱會的主辦者犯有“非法損壞公共財産罪”,波士頓市長約翰·D. 西尼斯(John D. Hynes)宣布,本市不會把公共設施齣租給演齣主辦者。他說,他們舉辦的演齣總會招來“搗亂分子”。
這個國傢的大人們為搖滾樂生氣著急,試圖立法管理它,同時也在思索它對美國年輕人的誘惑力。成年人一緻同意,這種“呼呼呼、梆梆梆、叮鈴咣當、鬍言亂語的破玩意兒”是垃圾。但是關於它的影響力,他們也存在分歧。希爾達·施沃茨(Hilda Schwartz)是紐約市青少年法庭的法官,他認為搖滾樂並沒有引發騷亂或青少年犯罪。有一些“害群之馬”就是樂意到處找麻煩,不應該讓音樂對這些騷亂負責。和查爾斯頓舞(Charleston)一樣,搖滾樂能引發身體的反應,但它能讓青少年發泄過剩的精力,從本質上來說是無害的。在劇場外排隊的小孩子們發生的小衝突是惡性的、不安全的,然而大多數人都是“身心健康、追逐青春期風尚的男孩女孩,也隻有青春期的孩子纔會這麼乾”。
然而,在大眾媒體上,辯護者們的聲音被杞人憂天的聲音淹沒瞭。流行歌手們不喜歡可能到來的競爭,他們對搖滾樂的譴責尤其惡毒。弗蘭剋·辛納塔(Frank Sinatra)說,搖滾樂“有一股虛僞的、假惺惺的味道”,要知道,在40年代,青春期少女們還紛紛在他腳邊尖叫昏厥呢。“它的演唱者、演奏者和創作者大都是純粹的白癡。低能的重復,乃至調皮、淫蕩、直白的性愛歌詞讓它成瞭地球上每個留連鬢鬍子的小夥子的戰歌。”心理治療師們也參與進來。《時代》雜誌告訴讀者,精神病醫師們覺得青少年喜歡搖滾樂是因為一種深層次的變態歸屬感需求。《時代》警告說,他們對心愛的歌手是那樣忠誠,“和被希特勒接見的群眾有點像”。精神分析師弗朗西斯·布雷斯蘭德在《紐約時報》上有一個專欄,他也持類似觀點,把搖滾樂視為“音樂中的食人族和原始部落的野蠻品種”,認為它反映瞭青少年的不安全感和反叛意識,是一種“傳染病”,所以就更加危險。
有些人走得更遠,他們宣布青少年中流行的音樂是毀掉一代美國人道德感的陰謀。在這一派人的暢銷書《美國機密》(U.S. Confidential)裏,記者傑剋·萊特(Jack Lait)和李·摩蒂默(Lee Mortimer)把搖滾樂同青少年犯罪聯係起來,“有非洲叢林背景的手鼓、搖擺舞以及儀式性狂歡和性愛舞蹈、大麻、集體瘋狂。很多舞廳都提供毒品;還主辦約會活動。徵集白人女孩供黑人享用……我們知道,在很多舞廳,放唱片的DJ都是癮君子。很多人都是左翼、赤色分子,或者挑戰社會習俗的人……通過DJ,孩子們知道瞭黑人樂手和其他樂手;他們把收音機當聖殿,一天到晚開著,這一切都是精心設計的……為瞭引誘年輕人,讓新一代人屈服於黑社會的魔爪。”
搖滾樂引發瞭喧嘩與騷動。而這究竟有什麼意義呢?事實上搖滾樂的興起與傳播可以說明很多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文化與價值觀念。曆史學傢詹姆斯·吉爾伯特(James Gilbert)說,一場鬥爭貫穿在整整十年之間,是關於“流行文化的作用,由它來決定讓誰來發言,嚮什麼樣的聽眾發言,為瞭什麼目的而發言”的鬥爭。在這場鬥爭的中心,搖滾樂令這個自1945年起就生活在“焦慮時代”中的國傢感到不安。
冷戰造成瞭數不清的國外危機,其中包括柏林空運事件(Berlin Airlift)和朝鮮戰爭。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锡(Joseph McCarthy)的指控通常很靠不住,卻引發瞭人們的恐懼,令他們擔心共産黨人在全球進行顛覆活動,由此引發瞭忠誠宣誓、黑名單,以及對異見者的廣泛壓製。在1954年的全國民意調查上,超過50%的美國人認為共産黨人應該被監禁起來;58%的人認為,“就算有無辜的人受到傷害”也要找齣所有共産黨人,並懲罰他們;78%之多的人認為,如果懷疑鄰居或熟人是共産分子,最好嚮聯邦調查局舉報。當然,和冷戰一同到來的是核時代,核戰爭有可能毀滅整個人類。人們建造防核輻射庇護所,教導學校的孩子們怎樣在原子彈襲擊中自保(立刻俯臥、臂肘嚮外、頭放在胳膊上、閉上雙眼……臥倒並掩護自己)這些雖然是保險措施,但或許也顯得過於慌亂。
在50年代,傢庭似乎和國傢一樣,恐懼著來自內部的顛覆。“不僅僅是共産主義的陰謀”,美國參議員羅伯特·亨德裏剋森說,沒有什麼比麻木不仁、無動於衷、放任自流的父母“更有效果,更能讓美國意氣消沉,陷入睏惑,最終走嚮覆滅”的瞭。美國人擔心上班的母親、柔弱的父親,還擔心大群青少年恐怖分子會侵入並占據整棟房子。吉爾伯特在書中寫道,這種恐懼體現在十年來針對青少年犯罪的鬥爭之中,在幾十次議會聽證與上百份規範青年文化的立法中隨處可見。
最後,在50年代,堅守原則、堅持不懈的民權運動提齣要求——美國黑人的平等權利問題不能再拖延瞭。最高法院對布朗訟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決,亞拉巴馬州的濛哥馬利巴士抵製運動,以及聯邦軍隊護送黑人學生進入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心中學(該校之前隻收白人)等事件發生後,一場種族關係的革命已經勢在必行。北方和南方的美國人都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
搖滾樂隻是間接介入瞭冷戰中的各種爭議,但它幫助美國年輕人建立起瞭自己的社會認同,提供瞭一種討論的氛圍,讓年輕人可以檢視和駁斥成年人對傢庭、性與種族的定義。這種討論並不一定以語言來進行。搖滾樂錶演者的肢體語言與音樂的節拍能起到和歌詞一樣的作用,可以打動觀眾,有時效果更強烈。評論傢格雷爾·馬庫斯(Greil Marcus)認為,搖滾樂在試圖批評某些東西的時候,“會變得極度自以為是和愚蠢”。而當音樂非常精彩的時候,“吉他在喧囂中拼命尋找自己的一席之地,人聲尖叫哭號著,一個人唱齣另一個人的歌詞,或將它轉嚮新的方嚮——此時歌詞便成為盲目的纍贅,隻會一點一滴地浮現齣來”。當時沒有任何人對搖滾樂進行前後連貫、條理分明的評論,搖滾樂也從未能徹底擺脫50年代的傳統價值觀,但它無疑提供瞭一種新鮮的角度:那是歡快的悠閑、浪漫與性,它嘲笑延遲到來的滿足感,嘲笑那些穿著灰色法蘭絨西裝坐在辦公桌前的人們,它隻在青少年的小世界裏歡天喜地。
媒體評論傢傑夫·格林菲爾德(Jeff Greenfield)說,搖滾樂製造瞭這樣一種觀念:年輕的身體是“尋歡作樂的機器”,因此“在‘錯誤的一代’當中引發瞭第一波震蕩”,並為60年代鋪平瞭道路。格林菲爾德說:“我們在反傳統文化中所看到的一切,服裝、發型、性、毒品、對理性的抗拒、對符號與魔法的迷戀——這一切都與50年代搖滾樂的興起密切相關。搖滾樂的節奏在美國黑人的城市角落醞釀,影響瞭美國白人,引誘他們離開安迪·哈迪(Andy Hardy)電影裏鬍編的那種對乖巧女生有節製的戀慕。搖滾樂是自然之力,是野蠻的,充滿性欲;它正是父母們害怕的東西。”
用户评价
與其說這是一部嚴肅的曆史著作,不如說它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感官盛宴,作者似乎完全摒棄瞭那種循規蹈矩的編年史寫法,轉而采用瞭一種碎片化、多重曝光的敘事手法,極大地挑戰瞭傳統閱讀習慣。這種風格的運用,成功地營造齣一種極度迷離而又極度清晰的復雜氛圍,如同在舊照片上疊加瞭現代的霓虹燈光,産生瞭奇妙的化學反應。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復雜社會議題時所展現齣的那種近乎魯莽的坦誠,他毫不避諱地揭示瞭光鮮錶象之下的裂痕與矛盾,讓讀者得以窺見那些潛藏在時代錶層之下,驅動一切嚮前滾動的黑暗能量。整本書的結構如同一個結構復雜的迷宮,每當你以為找到瞭齣口時,又會被引入另一條更深邃、更令人不安的小徑。這種敘事上的大膽創新,使得即便是對該主題有所涉獵的讀者,也會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全新的、充滿未知可能性的閱讀空間。它不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拋齣更具穿透力的問題,激發讀者自身去構建屬於自己的理解坐標係,這纔是真正優秀的文本所具備的魅力。
评分這本新書的問世,著實讓人眼前一亮,它以一種近乎野蠻生長、不加修飾的姿態,闖入我們對時代變遷的理解框架。我必須承認,初翻開時,我被那種強烈的、近乎原始的敘事節奏所吸引,仿佛作者並不是在書寫曆史,而是在現場親曆一場場風暴的中心。書中的筆觸極具張力,它沒有采取那種冷靜客觀的學者腔調,而是選擇瞭用一種更為個人化、更具情感穿透力的視角,去捕捉那些轉瞬即逝的文化浪潮是如何在社會肌理中留下深刻印痕的。特彆是對某些關鍵人物的描摹,簡直是栩栩如生,那些被主流敘事邊緣化的聲音,在這裏被重新放置到瞭聚光燈下,他們的掙紮、他們的狂熱、他們的失落,都以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真實感撲麵而來。閱讀過程更像是一場漫長的、時而令人眩暈的迷幻體驗,它不斷地叩問著既有的認知邊界,迫使讀者去重新審視那些看似堅不可摧的社會結構,是如何被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化反叛所悄然侵蝕和顛覆的。這種深入骨髓的洞察力,使得全書不僅僅停留在曆史記錄的層麵,更上升到瞭一種對人類集體潛意識和時代精神病理學的深刻剖析,令人讀後久久不能平靜,腦海中迴蕩的,是那種充滿未竟之力的迴響。
评分這本書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對於“時間感”的處理,那種特有的、仿佛時間本身都在扭麯變形的敘述方式。作者似乎擅長捕捉那種“此時此刻即永恒”的瞬間,並將無數個這樣的瞬間串聯起來,形成一個無比厚重的曆史切片。它沒有采用那種綫性的、目標導嚮的敘事,而是更偏嚮於一種循環往復、螺鏇上升的結構,暗示著曆史的某些基本衝突和驅動力是恒久存在的。閱讀的過程中,我常常會産生一種強烈的代入感,仿佛能聽到背景音樂中那些被作者引用的、充滿年代感的音符在耳邊響起,這種跨越媒介的沉浸感構建得非常成功。它成功地建立起一種氛圍,讓你相信,過去從未真正消逝,它隻是潛伏起來,隨時準備以新的麵貌重新登場。這種對曆史與當下之間動態關係的深刻洞察,讓整部作品散發齣一種永不過時的魅力,無論何時翻開,都能從中汲取到新的力量和警醒。
评分閱讀此書,我體驗到一種久違的、酣暢淋灕的智力挑戰。它絕非輕鬆的消遣讀物,而是需要投入全部心神去解碼和消化的文本。作者的行文風格極其密集,信息密度高得令人喘不過氣,每一個段落都仿佛塞滿瞭多重含義的隱喻和典故,迫使你不得不時常停下來,迴味咀嚼,甚至需要查閱背景資料來理解其深層意涵。這種對讀者的“苛刻”要求,反而激發瞭閱讀的樂趣,因為它確保瞭隻有那些真正願意深入探究的人,纔能真正領略到其思想的深度和廣度。其中關於某些特定文化現象的分析,更是達到瞭令人拍案叫絕的精妙程度,它揭示瞭文化符號是如何被權力結構不斷地重新編碼和利用的完整鏈條。這種對文本細緻入微的解剖,體現瞭作者紮實的學術功底與非凡的藝術直覺的完美結閤,使得這本書的價值超越瞭單純的文化評論,而邁入瞭哲學思辨的領域。
评分這本書給我的最大震撼在於其對“邊緣”力量的聚焦和贊頌。它成功地將那些在主流敘事中被簡化、被符號化的群體,重新還原為有血有肉、充滿復雜欲望的行動者。作者的文字充滿瞭對生命力的原始贊美,他捕捉到瞭那種從壓抑中爆發齣的巨大能量是如何改變社會景觀的。我感覺自己仿佛被捲入瞭一場無休止的文化衝撞現場,那些曾經被認為是噪音、是異端的聲音,在這裏被放大、被賦予瞭宏大的史詩感。敘事節奏的把握堪稱一絕,它時而如同沉重的、緩慢移動的冰川,積纍著勢能;時而又驟然加速,爆發成一場狂亂的、不可阻擋的洪流。這種強烈的動感,使得閱讀體驗本身就成為瞭一種反抗既有秩序的姿態。更令人稱道的是,作者並未將這些變革者浪漫化到不切實際的地步,而是冷靜地指齣瞭他們行動中的局限、內部的衝突乃至最終的妥協,這種剋製的批判性,使得整部作品的論述更具重量和說服力。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