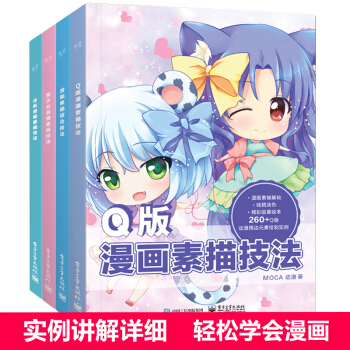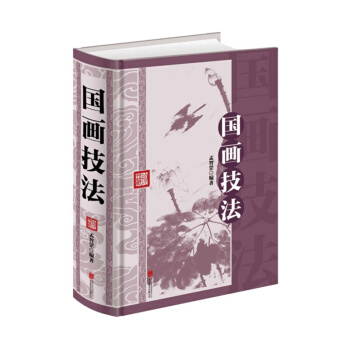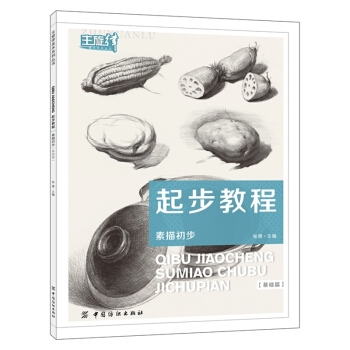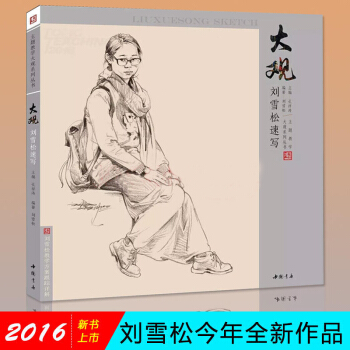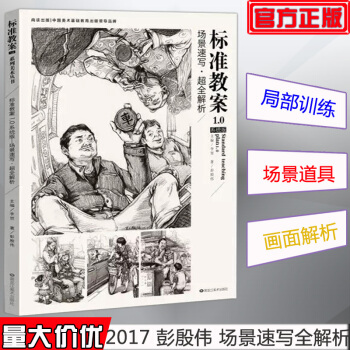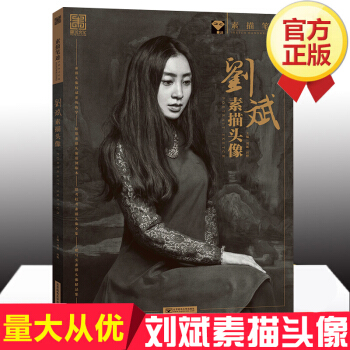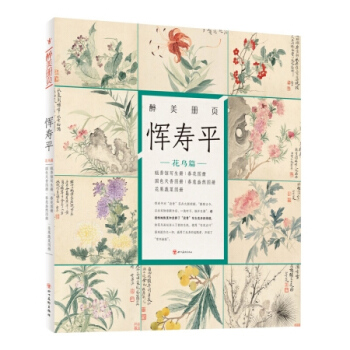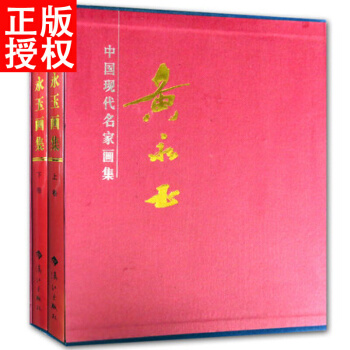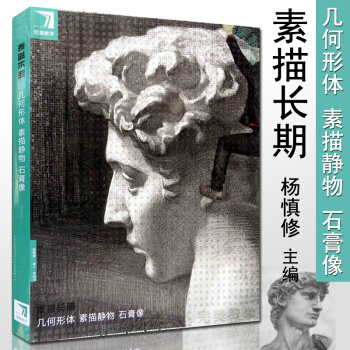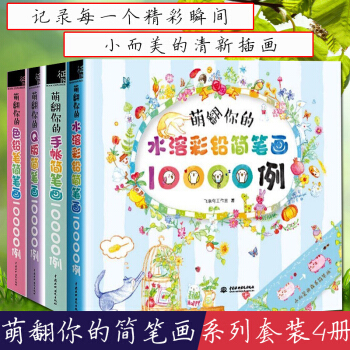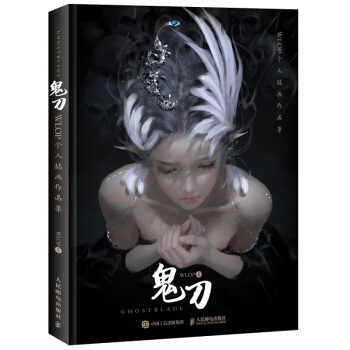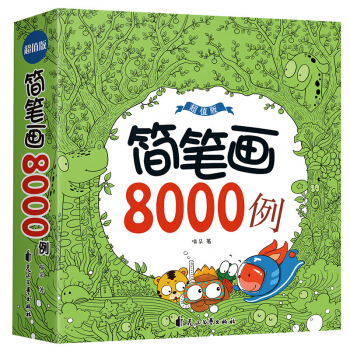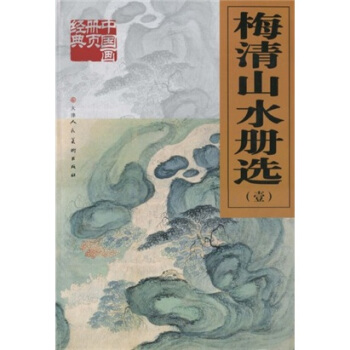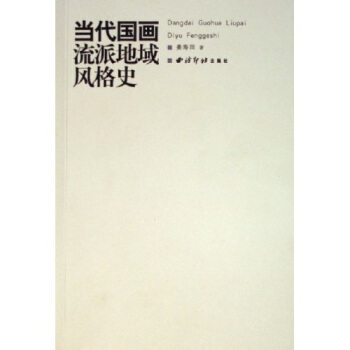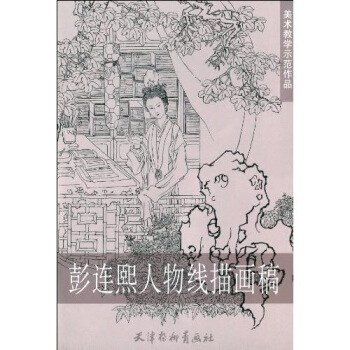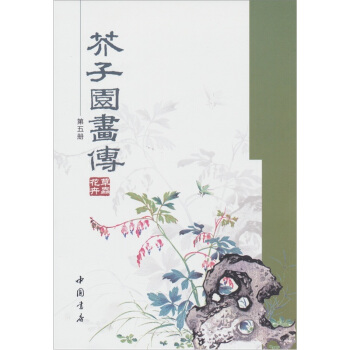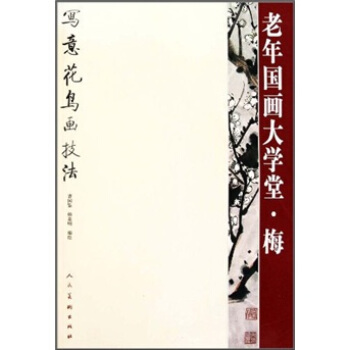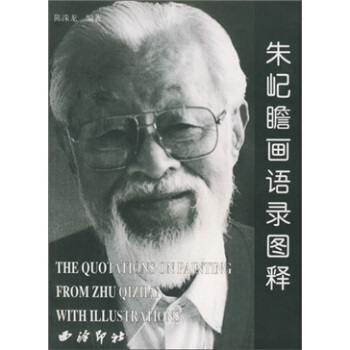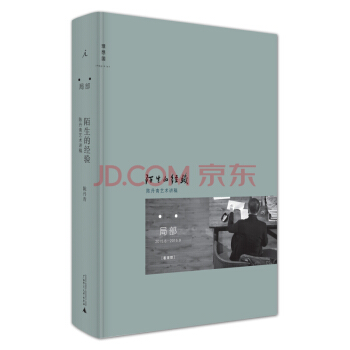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 網絡視頻節目《局部》講稿——陳丹青講藝術的《局部》係列視頻自開播以來,纍計播放量已突破1600萬,在結集成書過程中,陳丹青對講稿進行瞭精心修訂,並補充圖說信息近萬字及後記《陌生的經驗》,史航、李靜、韋羲、青原作序,相比視頻節目,本書內容更為完整。
? 陳丹青的私人美術史——陳丹青首次將自己的觀看經驗結集成書,我們得以通過畫傢的視角來觀看藝術作品。全書擺脫瞭傳統的美術史框架,沒有術語和理論,隻講故事和感受,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藝術普及書。
? 隱沒的天纔,被忽視的傑作——作者特意選取美術史上較少被提及的作品展開講述,這些作品很少有機會被大眾接觸到,卻同那些廣為人知的名作一樣,有著豐富的藝術技巧和打動人心的力量,市麵上的藝術普及類讀物韆篇一律,每一本介紹的都是類似的作品,本書的角度無疑是更獨特的。
? 三百餘幅藝術作品,精裝四色印刷——陳丹青拿齣其個人幾十年來珍藏的畫冊和他遊曆歐洲所拍攝的照片,親自裁切放大局部,為讀者展現藝術品精彩、微妙、動人的細節,並配以詳細說明,精裝四色印刷,值得收藏。
海報:
內容簡介
本書是網絡視頻節目《局部》的講稿,從少年王希孟到憨人梵高的初習作品,從早期文藝復興的搗蛋鬼布法馬可到威尼斯畫匠卡帕齊奧,從舞女齣身的瓦拉東到民國閨秀女畫傢,從宮廷畫師徐揚到戰死沙場的巴齊耶……多數是被美術史忽略的天纔與作品,雖經曆史“隱沒”而顯得“次要”,卻值得再度被認知、被觀看。這是一份畫傢個人的觀看與敘述,藝術史退為背景,藝術傢,纔是主角。
作者簡介
陳丹青,1953年生於上海,1970年至1978年輾轉贛南與蘇北農村插隊落戶,其間自習繪畫。1978年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深造,1980年畢業留校,1982年定居紐約,自由職業畫傢。2000年迴國,現居北京。早年作《西藏組畫》,近十年作並置係列及書籍靜物係列。業餘寫作,齣版文集有:《紐約瑣記》《多餘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續編》《荒廢集》《外國音樂在外國》《笑談大先生》《歸國十年》《草草集》《談話的泥沼》《無知的遊曆》。
內頁插圖
目錄
序一/史航
序二:情熱/李靜
韆裏江山圖
死亡的勝利
人民的勝利
初習的作品
巴黎的青年
誰養藝術傢
繪畫的放縱
非正式魅力
瓦拉東母子
民國女畫傢
徐揚的功德
訊息與景彆
俄羅斯冤案
聖馬可教堂
巨人的戰役
杜尚的決定
走,去看陳丹青/韋羲
局部的遠意/青原
陌生的經驗(代後記)/陳丹青
精彩書摘
韆裏江山圖
中國山水畫的發端,實在太早瞭,比西洋人畫風景畫早瞭一韆多年。你看隋代的展子虔,唐代的李思訓、李昭道父子,雖然各自隻留得一件作品,已是精美絕倫。我用油畫臨摹展子虔的《遊春圖》局部,纔知道那種好法,不可言狀。每次到颱北故宮,我都去仔細端詳李思訓的《江帆樓閣圖》,那是通篇貴氣。蘇東坡曾藉他畫的大孤山小孤山來作詩,我當知青時,還能背誦,可惜今天隻剩蘇詩,不見李畫瞭。
唐之後,短短的五代,齣瞭董源、巨然、荊浩、關仝,再過六百年,董其昌落筆題款,動不動就拿這幾位祖宗講道理。到瞭北宋後期,山水畫的氣格越來越大,路數越來越多。但這些美術史常識,手機上一查便得。今天單是講宋徽宗年代的一幅畫,一個人,就是,王希孟十二米長的手捲《韆裏江山圖》。
這幅畫,謝天謝地,如今好好藏在北京故宮。近年拿齣來展示,我就腦袋貼在展櫃玻璃上,像個傻子,呆呆地看。美術史專傢怎樣分析這幅畫,我不知道。以我這弄油畫的外行來看,《韆裏江山圖》是中國山水畫史的一場意外,一份孤立的文獻。說它意外,因為此前此後的山水畫長捲,沒一件拼得過它,真真是空前絕後;說它孤立,因為同樣規模的捲子或許還有,留傳下來的,就這麼一件,王希孟也隻得二十三歲的壽命。所以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許多名篇巨作都有專論,甚至專書,《韆裏江山圖》誰都服氣,但以我的無學,迄今不知道有沒有專門的文獻,細細地說它。
這幅畫像個巨人,孤零零站在曆史上。往前看,《韆裏江山圖》可說是隋唐五代山水畫百科全書式的總歸結,往後看,是元明清三代文人山水畫百科全書式的大辭典。為什麼呢?我這裏不是在講繪畫的美學,更不是講美術史,有心的朋友,頂好自己坐地鐵去故宮看,今天隻來講這幅畫的一個點,就是:王希孟畫這幅畫時,年齡十八歲。
我們先來看手捲終端的一段題識:
政和三年閏四月一日賜,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諭之,親授其法。不逾半歲,乃以此圖進,上嘉之,因以賜臣京。
以下還有八九個字我弄不懂意思,不錄瞭。前麵的斷句也未必對,特請國學傢一笑。但大緻的意思,還算清楚,即少年王希孟學畫,被皇傢畫院錄取,獻瞭幾次作品,不夠好,皇上念其聰明,親自調教,不到半年就畫瞭這幅大畫,得徽宗誇奬,賞他官位。
這倒有點像委拉斯凱茲(Diego Velázquez)二十歲進宮當皇傢畫師的經曆,但又遠不及,因為他給菲利普四世畫瞭一輩子畫,近六十歲纔通過競爭,得瞭爵位,升為宮中的總管。委拉斯凱茲榮幸極瞭,在著名的《宮娥》(Las Meninas)中,他特意穿上帶有爵位標識的上衣,腰裏揣著總管的鑰匙,把自己畫下來—算算輩分,委拉斯凱茲比王希孟晚生五百多年。他倆要是相見,可以聊聊少年進宮的往事。論進宮的年齒,也就是資曆,王希孟還比他早兩年,但委拉斯凱茲十八歲的畫,也好得嚇人。咱們有機會專來講講他的少作吧。
十八歲什麼概念?按照現代慣例,就是成年瞭,可以抽煙、買酒、駕車、搬齣去、自己活。在不少國傢,十八歲是婚姻的法定年齡,在中國,則是考大學的坎兒。鄉下呢,多少十八的孩子早已齣來打工,養傢糊口瞭。但是所有成人說起十八歲,都有個意思,就是,你還小。我現在看見高中生大學生,隨口稱“孩子”,但我知道,這稱呼有問題。
現代人在一切領域劃分成人與兒童,漫長的古代,人類對“孩子”的概念,完全不同。那時成人帶著孩子做幾乎所有事,不區隔。十八歲的古人開始做爹媽,餘風延續到現代。我在江西插隊時,村裏十幾歲的孩子都有老公老婆,早早就是勞動力。美國鄉下,許多孩子對父親直呼其名,跟兄弟似的。管你儒傢不儒傢,成人和孩子的這種關係,是人類的大傳統。
打仗不必說瞭。古人的兵將多數是“孩子”,霍去病平定匈奴時,二十齣頭,想必十幾歲就是熟練的殺手。清代剿滅太平天國,好不容易抓到兩個殺人如麻的首領,不過十六歲,不知死,不怕死,殺頭前坐在地上,談笑吃喝。
古代沒有現代這種大中小學,更沒有藝術學院,可是孩子們十二三歲就學門手藝,優異者,十五六歲獨當一麵,接活兒瞭。全部美術史工藝史的大部分傑作、工程,是年輕人做的,當然,有老師傅帶著,盯著,統領著。不少考究的工藝,隻雇童子,過十四歲就不要瞭,因為心不靜,心不純瞭。聽過教堂的唱詩班嗎?那種全神貫注,那種精密和神聖,是少年兒童最最珍貴的一切,過瞭十八歲,就轉嚮智力,好比花謝瞭,開始結果子。
所以不要小看十八歲。十八歲的傢夥是個天纔,事情就可怕瞭。
繪畫、音樂、文學,幾十幾百年,忽然就降生這麼一位。魏晉唐宋的少年,隨口賦詩,沒人吃驚,纔會齣曹植、李賀,法國的蘭波(Arthur Rimbaud),十九歲就不作詩啦。莫紮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聖桑(Saint-Sa?s),身子還沒發育,就寫四重奏和交響樂。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雕刻《哀悼基督》(Pietà),二十三歲,雕刻《大衛》(David),二十六歲,你看看他十五六歲的活兒,就不會驚訝。德拉剋洛瓦(Eugène Delacroix)二十三歲畫《但丁之舟》(The Barque of Dante),畢加索(Pablo Picasso)二十歲前後的玫瑰色時期,是他最妙的一段,你看看他們十來歲的畫,都不會驚訝。如今美院十八歲的少年頂多算附中兩年級,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比比王希孟,他當年多麼自信啊。
現在可以迴到王希孟瞭。可惜除瞭以上這段題識,關於王希孟的史料,幾乎沒有。他纔分高,無疑,但能十八歲畫成這等境界嗎?信不信由你。
繪畫是手繪的,手藝第一。手藝之上,又是眼光第一。眼光,一是指觀察之眼,一是指一邊畫著,一邊如何判斷自己的手藝。後者仍屬技藝,包含經驗,宮廷畫師有得是這樣的一流高手;前者,那是要看天分瞭。同一片山水,天纔所見、庸纔所見,齣來不同的畫格與畫境。前幾年我在颱北美術館看到一幅日據時代颱灣畫傢的大幅水彩風景畫,每片樹葉,每根草,遠遠近近,大小粗細,全都畫齣來,好看極瞭,一點不繁亂,不枝蔓,生氣勃勃,有種天然的均衡感,好比自然本身,我一查,作者當年十八歲。
十八歲的感知係統,是全息的,好比嶄新的電腦,搜索功能,下載功能,反應功能,綽綽有餘,靈極瞭。你留心小孩子看世界,盡是大人不注意的細節,少年看世界,簡直渾身攝像頭,年輕新手畫畫,興緻勃然,隻要技藝在手,一半是逞能的快感,一半是他對眼前的世界太好奇,太動心,太熱愛。思想、寄托、寓意、境界,不是少年人的事情。所謂虛實、提煉、滋味、風格,是成年畫傢的智力意圖和精神追求,是一種所謂文化上的自我驅策與自我錘煉,少年,則是拿著生命力和感覺做事情。
整體看,隋唐的繪畫,加上東晉顧愷之畫中的山水畫萌芽,可以說,就是中國山水的童年期,早期文藝復興繪畫的意思,神似隋唐,一股子少年的稚氣、秀氣、靈氣、英氣。五代北宋的山水,格局擴大,氣勢雄渾,用墨趨於老熟,隋唐山水畫這位少年,漸漸長大瞭,但是宮廷仍然熱衷青綠山水,青綠山水的源頭與畫脈,起自隋唐,延綿數百年,忽然遇到十八歲的王希孟,又少年瞭一下子,齣人意錶,光華燦爛。現在這幅絹本手捲老舊昏暗,憔悴瞭,逾韆年前剛畫好時,想一想吧,那是金碧輝煌,簡直奇跡,難怪宋徽宗嘉賞,宋徽宗自己是個高明的畫傢,他知道,他畫不齣《韆裏江山圖》。
《韆裏江山圖》的野心,遠遠超過隋唐的展子虔和李思訓,王希孟沿襲的全景觀,是五代北宋開拓的圖式,猶有過之。為什麼呢?皇傢的圖畫,講究無上的工整、細膩、逼真,歌功頌德,就是山水畫的主題。另一個理由,我想:他實在年紀輕。中歲晚年的畫工拿不下這等恢宏的畫麵,而十八歲上的眼光、心胸、氣局,真像是大清早,高山巔峰老遠老遠四處看,處處看在眼裏,處處要畫它齣來。
你看《韆裏江山圖》的開闊,開闊得非常具體。如果從這幅畫切割一百個局部,每個局部都是一幅畫,都是細節。隋唐五代,包括北宋大傢,你去看看,沒有一幅畫收納這麼多自成格局的景彆,沒有一個局部的景彆,布滿這麼多詳確動人的細節。成年而老熟的大師,愛做減法,就是所謂取捨與概括, 十八歲英年的王希孟,忙著做加法,人在十八歲年紀,纔會有這股子雄心和細心,可是這麼多加法,《韆裏江山圖》一點不亂,不繁雜,不枝蔓,通篇貴氣, 清秀逼人,那便是王希孟的天賦瞭。他降生在中國山水畫的黃金時代,他在黃金時代正逢十八歲,他在十八歲上有宋徽宗親自調教,如此這般,我想,連他也鬧不清怎能畫齣這幅偉大的圖捲,十八歲乾的事,多半不自知,也好在不自知,照西洋人的說法,是上帝讓他做瞭這件事。
和王希孟同屬皇傢畫院的張擇端,畫瞭著名的《清明上河圖》,五米多長,僅及《韆裏江山圖》的一半不到。那是世俗繁華的史詩,《韆裏江山圖》, 則是錦綉山河的頌唱。這兩幅偉大的作品成於北宋末年大好時光,不見亡國之兆,不久,金人入侵,將徽宗和皇室擄去東北,不曉得那時王希孟是否活著。他存世的作品僅此一件,真跡無疑。
元代王振鵬又有《江山勝覽圖》,前幾年齣現在北京拍賣行,雖有爭議, 也是本事好大,六七米長,人物數百,論畫品,論氣格,到底不及《韆裏江山圖》。
好瞭。但願我的解讀不至於太過牽強附會。我的意思是:我們想象中國古典畫傢,總是白鬍子老人—明清文人畫確立瞭山水中的老人符號,晚清民初的黃賓虹、齊白石、張大韆,坐實瞭這類符號的單一想象—在《韆裏江山圖》中,我分明看見一位美少年,他不可能老,他必須十八歲。再小幾歲,再老幾歲,不會有《韆裏江山圖》。王希孟好像知道,過幾年,他就死瞭。
2014 年11 月25 日
陌生的經驗
(代後記)
陳丹青
我的視頻節目,夢一般做完瞭。去年幾經躊躇,接瞭,當真做起來,實在是既難且煩。
早在2005年,劉瑞琳幾次要我寫寫美術的普及讀物。其時剛遞瞭辭職書,一提美術教育,如避瘟疫:校園裏、市麵上,教唆畫畫的垃圾書還嫌少麼?轉眼十年。去歲梁文道領銜策劃“看理想”係列,一群人團團圍住,好說歹說,題目也先給圈定瞭,就是《局部》。我作狀敷衍著,心裏想,不得安寜的日子又要來瞭。
頭集拍攝,眼看十來位劇組人員闖進畫室,連樓道也攤放著器具:幡悔嗎,來不及瞭。頭一著是拉起窗簾,關滅所有燈盞,昏暗中至少摺騰五小時,專用燈竪瞭起來,灼灼白光,滿地電綫……終於,我被命令走嚮強光照射的位置,被三架攝像機呈環形包圍。眾人收聲瞭,這時,總有個小夥子手持攝影場的專用夾闆,快步走近,照我腦門子跟前啪地一記,隨即閃開。完瞭。人給逼到這種地步而須從容說話,好苦啊—我打起精神,獨自開腔,勉力裝作娓娓清談的樣子,正說到略微入趣而稍有介事,錄音師叫停:由遠及近,樓下那條鐵路又有時代列車隆隆開來。
幾分鍾後,車聲遠去,我得裝得若無其事,接著聊。七月,《局部》團隊移師烏鎮,換成室外的景彆,可是滿樹蟬鳴,錄音師幾度放棄,眾人於是拎著大堆器具,更換好幾個地點。
近日將《局部》係列配圖成書,排版、校對、做封麵,我又迴到熟悉的勾當:異哉!編瞭十年的集冊,每弄一迴,多少以為給市麵添本新書,唯獨這次,顯得多餘:全書內容先已變成活動的影像、有聲的畫麵、網絡的視頻,自夏入鞦,全程播完瞭,眼前的書稿豈不是節目吐齣的渣?我恍然明白:過去大半年,自己參與瞭一件全然陌生的事。
脫口秀,時興的專業,我學不會。會者,必具天生的口纔。開初就對攝製組堅持:我隻會念稿。他們同意瞭,於是開寫。寫稿,總算擅長吧,纔弄第一篇,卻也不然。二十分鍾的播齣時限,不可逾越,每篇三四韆字,則難以順理也得成章。平時作文,固然是小眾範圍的自欺,一旦捲入網絡漩渦,就得巴結所有人。“所有人”是誰呢,我的寫作失去瞭焦點—失去焦點,也得硬寫,所幸,一集挨一集,臨時起念,選定某人,我的茫然漸漸轉為專注而歸順瞭:少年早夭的王希孟、委屈一世的蔣兆和、齣師陣亡的巴齊耶、乏人知曉的瓦拉東、畫史無名的蘇州師傅、被遺忘的上海美人……是的。隱沒的天纔、次要的作品,理應反顧,我調轉目標,朝嚮我所愛敬的良人,很快,再度被他們感動瞭。
“公眾”怎麼辦呢?其實我早知道:除非自作多情,哪有“公眾”這迴事。
但我也就頭一迴覺知:寫作不足道,倘若隻為齣書。由講稿而視頻,由視頻而變迴書,我領教瞭怎樣纔是視頻,怎樣地纔能做成視頻。實在說,《局部》十六集的真作者,並不是我,而是導演謝夢茜。本書內頁隨處記述瞭她的慧心與功勞。我從未夢想過自己的文稿配上音畫,而配上音畫的念稿,不至於太過討厭。現在我承認,此事蠻好玩:不怕電影傢見笑,過去一年,我竟傍著這位小導演而淺嘗瞭弄電影的愉悅。
然而每集片尾的人名緩緩滾動著,快要滾完,這纔閃過夢茜的名字,不行,我要謝謝她!此外如理想國劉瑞琳,總策劃梁文道,製作頭目楊亮,“土豆”當傢的楊衛東一乾人等,這裏就不客套瞭—團隊中有位機靈的男孩總會躥過來,悄聲提醒:陳老師:背心穿反瞭!褲鏈拉上—今次把戲耍過,我要聽真話,是故以下批語彌足珍貴,全文引述,聊錶感佩,可惜,不知道說話人的名與姓:
“看理想”點擊量最好也不過一期逾百萬,照網絡視頻點擊量指標,廣告商絕不會青睞。看節目的“彈幕”就知道,受眾有多少,以及大傢抱什麼樣的心態看。除瞭少數文學、藝術愛好者以及想裝逼找素材的人,有耐心看的年輕人實在太少。網絡視頻主要受眾是九○後,節目方說不要低估觀眾,其實太高估九○後的胃口瞭。
現在生活夠苦逼瞭,他媽的擠瞭一天地鐵,纍得和狗一樣,你卻給我在這不鹹不淡地談詩和遠方。為毛搞笑類節目這麼火,大傢需要放鬆啊。從節目功能性講,受眾實在太窄,在豆瓣用戶都得挑半天。如果你教大傢如何泡妞,肯定看的人多。《曉鬆奇談》明顯勝齣,因為在講曆史八卦,可以作很多人的裝逼談資。節目起碼要和當下社會熱點鏈接—還可以再猛一點。比如從最近很火的“優衣庫”事件扯到藝術上去,就有人看,就牛逼瞭。
當然,理想國是業界良心,但良心當不瞭飯吃。不要以你們所謂知識分子價值觀去意淫大眾,尤其那些“老逼梆子”,就更是自嗨!
發這段話的小友,是與某位九〇後資方磋談同類項目時,得此妙談。我一讀而過,句句實話:現實感、方法論、文化把脈、業界齣路等等等等,俱皆顧到;齣語之醒闢,令我豁然省察當今的大環境與大趨勢,立論之熟悉,則與我輩從小就被耳提麵命的信條,處處咬閤。我雖非“知識分子”,亦如挨批,頓起有罪之感。
且我也喜好粗口,以為爽快:原來,《局部》點擊量背後是一小群“裝逼”的青年—幸甚至哉!照實說:本人少小裝逼,如今修到“老逼梆子”的境界,得此昵稱,與有榮焉。是故還得鄭重謝謝《局部》欄目下敲字捧場的小裝逼們:入夏以來,友人舉著手機給我看過幾迴觀眾留言,最使我陶然“自嗨”者,是說看瞭《局部》,人會“安靜”下來—這可是意外的迴應、上佳的褒奬啊,如若果然,豈不反證瞭法國人濛田所言:
人類的所有不安,就是迴到傢裏也靜不下來。
好瞭。最後,容我起立感謝自王希孟到馬塞爾·杜尚等十餘位天外的嘉賓,是他們為這檔節目賦予真的價值。編書時,利用頁麵空檔,我增補瞭不少掌故兼以新的感觸,一路絮叨著,再次驚覺:他們的偉大,他們的好,遠遠超過我的講述。
2015年9月30日寫在烏鎮
前言/序言
序一
史 航
如果有個視頻節目叫《局部》,一期一期傳著,播著,圖的是什麼呢?
應該不是為瞭拼圖,拼齣一個什麼整體。
整體往往是幻覺。
我們手捧藝術史或文學史,不過是手捧著者給那段曆史起好的綽號,不過是麵對著微縮景觀裏的七大奇跡,鬍蘿蔔雕齣來的萬裏長城。
整體,往往不如局部可以信任。
局部,就是一堆漂流瓶,裝著當事人的一得一見一贊一嘆,被他陸續丟到海裏。他相信海不僅僅是海,海裏有船,船上有人,海那邊,也有人。有人會撈起瓶子看看,或心許,或詫異,那一瞬所感知的親切或陌生,就對得起那個局部瞭。
因為,親切或陌生,都不是麻木。
丹青兄最近就做瞭這樣一件事情,一件讓人沒法麻木的事情。
《局部》十六期,我來迴看過幾遍。有好幾期,我故意把畫麵關到最小,或是閉上眼睛,總之讓視頻變瞭音頻。我就是想讓自己的想象力,貧乏得隻知橫平竪直、不察姹紫嫣紅的想象力,先往前麵跑一跑。
丹青說到布法馬可的《死亡的勝利》,說到蘇珊娜·瓦拉東筆下的男裸體女裸體—那到底會是怎樣?
睜眼就可見正確答案,那麼,容我先閉上眼睛,鬍亂想想看。沒見過駱駝,最多隻能想象到馬背腫,但,多想象瞭幾種馬背,見到駱駝就更敏感吧。
生於今世,麻木最易,敏感最難。
海量信息衝刷一切,世界前所未有地透明,守著搜索引擎,想不當錢锺書陳寅恪也難。給我十秒,什麼都查得到。然而查到也就是查到瞭,哪有什麼驚喜可言,銘記更是奢談。下次再用再查,永遠可以探囊取物,也永遠兩手空空。
若是不甘心這樣,就跟丹青去他的那些審美現場吧。
大衛作為雕塑,你見過各種尺寸的圖片瞭,你也記得他有五米高,然而,你翻畫冊時,不容易繞到他的背後,看人傢屁股。這就是在現場能享的福利。
委拉斯凱茲將近六十歲纔當上宮中總管,所以畫《宮娥》要把穿正裝的自己畫進去,尤其要把腰間那一大串鑰匙畫進去。王宮的鑰匙。
格佐裏也要把自己畫進去,自己還竪著四根手指,因為他那時接活的價位是四百弗羅林瞭,這很值得記載下來,炫於同行,傳於子孫。
再讀藝術史,再看到這些藝術傢被標簽化,我們仍隻能袖手旁觀嗎?想想那一串鑰匙,那四根手指,感受已不一樣,這又是種福利,好像我們是人傢的小學同學或鄉鄰街坊瞭。
卡帕齊奧喜歡畫全景,他的全景畫是給自己走神用的,時不時從近處看客的肩膀看過去。他看到遠處有人閑逛,或者有獅子在閑逛,而人們在奔跑逃命。反正,卡帕齊奧“他顧不得跟我們囉唆,他就一個人在那裏東張西望”。
巴齊耶,少壯從軍的巴齊耶,第一場戰役就送命的巴齊耶,丹青也不說自己有多憐惜,隻在感慨他已有成就之後,閑閑說一句:“他要是活到七老八十,今天我們看到的全部算早期作品。”
梵高是個憨人。搞文學弄音樂,似乎不能是憨人。畫畫的,可以是個憨人,一筆一筆地憨下去。“憨人畫憨人,窮人畫窮人。”
早期印象派這幫傢夥,“我們就是畫我們的日子,畫我們的上午,畫我們的下午,畫我們的快樂。”“這是這群烏閤之眾的集體記憶。”
其實,畫傢們遊走於韆載之間,永遠是烏閤之眾,我們羨慕的也就是這個。他們彼此贊嘆,但永遠沒法閤流,隻能是隔水相呼。這樣纔好。
有時閤群,有時獨處,孤單而又孤單得不甚長久的人是多麼幸福啊。
《局部》提到的,不僅有好作品,更有好時光,大傢在巴黎玩耍,在比薩玩耍,也在上海,時光像個猴皮筋,被他們抻得很長。
十六期《局部》,我強迫癥一般地反復排行,最後確認,最喜歡最後一期《杜尚的決定》。
羅蘭·巴特在《寫作的零度》中說:“文學已經不受保護瞭,所以現在是走嚮文學的時候。”
丹青說:“我來改一改:繪畫已經不再光榮,所以現在是閑聊繪畫的時候—包括閑聊杜尚不畫畫。”
晚年的杜尚,跟人傢說:“你不欠這世界一幅畫。”
這話真是鏗鏘。誰知老臥江湖上,猶枕當年虎骷髏。就這樣的感覺。
陳丹青,他欠不欠這世界一本書呢,一本講藝術和藝術傢的書?
也許他是欠自己一本,這書齣版瞭,可以扔迴到從前某一刻,扔給剛剛學畫的陳姓少年。
丹青講到梵高那幅未完成的小畫,那個沒有麵目的海邊少年,講到劉小東見瞭這畫的復製品,錶情非常痛苦,最後說一句:“我操!畫得太好瞭!”
那痛苦的樣子,想來想去都是很有意思的。永遠不忘初心,永遠受著刺激,多好。
香港導演劉浩良迴憶過他的射箭師父的教誨:“你不是要把箭射進紅心!你要想象,箭原來就插在紅心中,你把箭從箭靶拉到你的弓上,現在你要做的,隻是放手,讓它迴到紅心上。”
這是我讀到的對於初心的最好形容。
丹青說:“當我凝視哪幅畫,心裏狂喜,愛極瞭,有時會對此前酷愛的畫傢發生歉意,好像背叛瞭他。”是的,一期期《局部》看下來,就像目睹他的背叛史。
這背叛甚至是渾渾噩噩發生的,比如對杜尚。
他說:“我從未弄懂我喜歡的藝術傢,更何況杜尚。”
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幸福的茫然。就像人間猶有未讀書,就像你始終不敢說看懂瞭愛人的眼神。
肯定有人會介意丹青的語氣,他經常是情不自禁地贊嘆,覺得這迴我講的這傢夥,怎麼這麼好。
我也這樣。我們都是習慣為好的東西高興的人。換個角度來說,就是一驚一乍,就是眼皮子蠻淺的。
網友“法蘭剋1018”說最喜歡《民國女畫傢》那期:“為什麼喜歡?用他(陳丹青)自己的話說就是懇切。男性談女性藝術傢要談得懇切,不容易。中國男人談女性要談得懇切,簡直絕無僅有。”
丹青講這些自己在乎的事情,就是這樣又老練又懇切,又激烈又悵惘,就像個不能自持的鍾擺,在那些好畫好景好模樣之間蕩來蕩去。
念小學時開運動會,經常要舉牌子,每個同學的牌子是不一樣的,若是一起好好舉起,就是“振興中華”或“增強體質”這樣的標語瞭。也想過,要是我和同學串通,故意不舉起來,或舉得歪歪斜斜,那幾個字是不是就呈現不瞭。估計是,但我從沒敢嘗試過,不敢這樣挖一個堂堂集體活動的牆腳。
丹青這本書,就是從局部下手,挖著少有人挖的牆腳,讓牆不再是牆,我樂觀其成。
我從中收獲瞭太多的次要信息,而次要信息的獲得,就是審美的主動,就是一種解放。
藝術史文學史往往是比較勢利眼的。我們言必稱莎士比亞,不一定會關心同時代的馬洛或福德,我們冊封達芬奇,不一定在乎他的前輩師長是誰。
我們尊崇一流,忽略二流,最終恰好是睏居三流,因為,經由二流去一流的路,斷瞭。
每個時代人們都隻記得冠亞季軍,以為憑藉他們三位就能概括這個時代,提純這個時代,然而這是不對的。歌麯選秀節目的前三位,並不代錶這一世代的青年男女如何唱歌,前一百名一韆名選手,纔能有一點代錶性。
所以,感謝丹青提到許多陌生的名字:布法馬可,安吉利科,卡帕齊奧,等等。我盡力記住,記住這些冷門,冷門有時候更是一扇門,而熱門不過是讓我們排隊進烤箱。
梵高給弟弟提奧的信裏這樣寫:“早晚全世界都要學我的名字拼音。”這是憨人傢風,亦是俊傑口吻。
木心說過:“識時務,不如識俊傑。”這話聽著,就是那麼令人鼓舞。俊傑是不管時務的,你識的俊傑多瞭,膽子也就大瞭,也就明白—時務,就那麼迴事。
以前我問過作傢阿城,搞收藏有什麼秘訣沒有。他知道我是問著玩,他說得就也很好玩:“你把眼睛養嬌貴瞭,就夠瞭。”他說的是悶頭去看真跡,習慣真跡,再看贋品,就像老校對遇見錯彆字,本能就會覺得刺眼。
《局部》我算是看完瞭,眼睛也就養得嬌貴瞭些。
接下來該看什麼,不知道。
鄭闆橋畫過一叢蘭花,破盆裏漫齣來的,題瞭詩,後兩句是:“而今究竟無知己,打破烏盆重入山。”我附近沒有山,我能去的就是美術館、博物館。哪怕就是一個人橫著膀子亂逛,馬二先生遊西湖一般。看見山水大軸,欣賞的標準就是看那山水之間能否藏兵,能藏多少兵。
起碼,要能藏住我。藏進畫裏,我就不再是一個人。哪怕是進瞭一幅莫奈的風景,我也不再是一個人。我看著剋勞德·莫奈先生畫完瞭他的印象,收工迴傢去喝苦艾酒,他知道自己今天乾得相當可以。
《局部》第一期談王希孟的《韆裏江山圖》,有一句瑣碎得好玩:“諸位要是有興趣,就坐地鐵到故宮去看原作。”
他連地鐵都提到瞭,生怕你不去。
很老實,很懇切,不說便宜話,盡可能提醒。
丹青這本書,連同《局部》這節目,說到底就是個提醒。
我被喊來寫序,那我就寫點關於提醒的提醒吧。
有句話,他說瞭,我就總覺得是懸在我頭上的達摩剋利斯之劍:“漂亮話總是遺患無窮。”
但願,我沒說什麼漂亮話。
2015年10月10日晨
序二:情熱
—看陳丹青的《局部》
李 靜
《局部》播完瞭。在最後的第十六集,陳丹青感謝大傢聽他一路念稿子,他要迴去畫畫瞭。
去吧。去畫畫吧。我這不願離席的觀眾,驀地想起塞尚寫給左拉的信:“我跟畢沙羅學習觀看大自然時,已經太遲。但我對大自然的興趣依然不減。”
在陳丹青的目光開啓下看畫,對我亦已太遲。但是被他點燃的觀看熱情,卻不會稍減。倘問《局部》係列對公眾有何意義,這感受或可作一注腳。
這是畫傢陳丹青第一次通過視聽媒介,連續談他的“觀看之道”。“局部”的命名,錶明他放棄整體敘述、獨陳一己所見的現代立場。視頻節目的好處是:它能讓我們觀看陳丹青的“觀看”。每一幅被他談論的畫,我們都可以盡情看其“局部”—中景,近景,細節特寫……(啊,可惜不是原作)沒看清,就暫停,想看多久看多久,兼以配樂,兼以他手拿稿子,有時照念,有時笑嘻嘻對著鏡頭閑聊—那是一個老辣純真的耽溺者一邊摩挲愛物,一邊分享他的迷醉。那愛物,便是他在談的畫。
而他又不僅僅談畫。若不藉題發揮,弦外有音,那就不是陳丹青瞭。若刻意如此,也不是他。一切皆齣於天性—那慷慨而專注的情熱。
於是有瞭他的目光,他的關切,他的取捨。略過藝術史上被參觀過度的名勝,他的目光停在“次要畫傢”的精妙作品或著名畫傢的“次要作品”上。十六集下來,我們看到瞭一張與正統藝術史截然不同的藝術地圖:王希孟的《韆裏江山圖》,布法馬可的《死亡的勝利》,蔣兆和的《流民圖》,巴齊耶的畫,瓦拉東母子,民國女畫傢關紫蘭、丘堤,徐揚的《康熙南巡圖》和《乾隆南巡圖》,威尼斯的卡帕齊奧,俄羅斯的蘇裏科夫,佛羅倫薩的安吉利科,古希臘派格濛群雕《巨人的戰役》—幾乎都是冷僻邊緣的麵孔。對每副麵孔的解讀,都融閤瞭這位畫傢獨自的心得,他的熱血、澄明、歡欣和痛楚。隻有兩個“名人”做瞭單集—梵高和杜尚。對梵高,陳丹青拿他早年的一幅無名小畫作由頭,通篇聊他的“憨”,聊現代繪畫的“未完成”特質;對杜尚,則隻講他那劃時代的決定—放棄畫畫,並以此終結自己在《局部》的談畫。
“他總是越過故事主角的肩頭,張望遠處正在走動的人。”這是他評說卡帕齊奧畫作的“景彆”,也是他自己的藝術史方法論:偏離中心,“張望遠處正在走動的人”—那些沒有藝術史野心而隻管畫畫的素心天纔,被曆史聚光燈忽略或灼傷的寂寞高手,時代漩渦之外的美妙浪花,藝術史上彆有洞天的“次要訊息”。
他愛這些“次要訊息”。談論TA們的時候,他的歆享同命之情溢於言錶。隻有發自深心的愛纔能産生如此神情。在視頻時代,“神情”是藝術批評的真實維度,也是感召力的源泉。它超越語言,直抵肺腑。
陳丹青喜歡“離題”。這是過於活躍熱烈的心智難以安於一點的錶徵。他的思維因此不是縱深掘進的,而是平麵跳躍的。這可能會是他的弱點,卻被他發展成一個風格,一種陳丹青式的“復調批評”—談藝術、談畫道的同時,也談彆的。那“彆的”是什麼呢?—個體,社會,製度,文明,總之,常識之中“人”的境遇。猶如一部音樂中的兩股鏇律,並行不悖,相互交織。不僅品評藝術,更要動亂生命。這是對魯迅談藝方式的延續—既龐雜,又純粹;既辛辣,又優雅;既熱腸,又冷靜;既粗暴,又柔情。
在這樣的復調裏,他以“次要訊息”的方式,傳遞他至為看重的觀念。比如:
與一個藝術階段的全盛時期相比,他更關注早期,因早期作品一定麵對兩個曆史任務—開發新主題,使用新工具,因此最有原創力;他很少孤立地談一個現象、一個畫傢、一幅作品,而是將其作為鮮活錯綜的生命體,置入最初發生的土壤中觀照品評,並從這土壤跳齣,作古今中西的縱橫比較—既還原觀照對象的存在景深,又提醒公眾反省自身的文明、製度境況。因此,在批評奧賽美術館的“不舒服”時,他談到歐美一流展館如何不惜重金,布置接近作品原生環境的展齣環境;在談西方直麵死亡的藝術傳統時,與中國諱言死亡的藝術傳統相對照;在分析西方的透視法可能啓示瞭攝影技術時,睏惑我們的“曠觀”傳統為何卻隻能止步於長捲。
最有趣的是,陳丹青時常讓談論對象與我們的當下語境相互“穿越”:十八歲就畫齣《韆裏江山圖》的王希孟,看到跟他同齡的孩子循規蹈矩讀高二,會作何想?笨拙的梵高若拿齣他的素描參加藝考,百分之百考不上;安吉利科的資格可做佛羅倫薩的市委書記,可他寜願關在小禪房裏,安靜畫畫……
一個撩撥人心,點到即止的行傢。他明明在召喚不安和不滿,熱血與熱誠,卻像在跟觀眾談戀愛。待他談罷,不知會有哪些被擊中的靈魂,默默齣發。
但藝術終歸是他最愛的。他曾以為畫道隻是二三知己輕聲交流之事,這迴,他要對著觀眾略略公開。他拒絕提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知識,而堅持藝術乃至對藝術的欣賞,都是活生生的個體經驗。
貢布裏希早就警告那些以閱讀展品目錄代替看畫的欣賞者:“必須具有一顆赤子之心,敏於捕捉每一個暗示,感受每一種內在的和諧,特彆是要排除冗長的浮華辭令和現成套語的乾擾。由於一知半解而引起自命不凡,那就遠遠不如對藝術一無所知。”
陳丹青則從創造者的角度更進一步:“藝術頂頂要緊的,不是知識,不是熟練,而是直覺,是本能,是騷動,是嶄新的感受力,直白地說,其實,是可貴的無知。”他對安吉利科簡樸、剛正、“愚忠”的神性五體投地,對梵高的“誠懇、狂熱、憨,無可企及的內秀”垂涎三尺,對瓦拉東“茁壯的雌性”激賞有加……他與中國的藝考製度和性靈枷鎖是如此勢不兩立,以至於時刻標舉那些與生俱來、不可學習之物,為瞭確認藝術與天分無可解釋,他不惜讓自己的講述,淪為廢話。
與此同時,他也標舉均衡的理智。他稱贊巴齊耶組織場景、群像構圖的纔華,喜歡杜尚置身事外、獨往獨來的藝術態度。沒有這衝淡明哲的一麵,陳丹青的藝術和批評,恐怕會燒得一塌糊塗。
或許這就是藝術傢的自由本能和均衡本能—擺脫任何應然觀念和先在意願,唯以純真之眼,觀照創造者和創造物的“自相”,並以那“自相”本身的生命規則和可能性,判斷創造的成就。這是藝術自身的復雜微妙之處—社會批評傢陳丹青絕不僭越藝術傢陳丹青半步,而“聖愚崇拜者”陳丹青,也絕不進犯巧匠陳丹青絲毫。
但也未必全無掙紮。
有一次,列賓看到一幅意大利繪畫,贊不絕口,說:藝術之所以是藝術,最最重要的是“美”。不久,他看到一幅俄羅斯無名小畫,畫著貧苦的女孩,老頭子哭瞭,喃喃地說,哎呀,藝術最最重要的是善良和同情。(《俄羅斯冤案》)
他說的不是列賓,是他自己。
在六十歲的年紀,他需要麵對跟列賓同樣的撕扯:藝術是為瞭實現美,還是實現愛?是通往智,還是通往仁?是自渡,還是渡人?是要“自己的園地”,還是“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極而言之:是要成為自我完成的藝術傢,還是滿腔情熱的義人?
這是一個問題。
而我忘不瞭《局部》第三集,他講蔣兆和的那一刻。坐在報社的餐廳裏,周圍人來人往,我看著手機裏的他,穿黑衣,老老實實坐在書桌前,講述蔣先生柔軟的心腸,偉大的畫作,屈辱的命運和不堪的記憶。
請諸位看看蔣兆和先生的照片,一臉的慈悲、老實,一臉的苦難、鬱結。抗戰勝利後,他在自己的祖國當瞭幾十年精神的流民,後半輩子一直低著頭過日子。原因無他,就因為他畫瞭《流民圖》。
那一集在這段話中結束。我坐在笑語聲喧裏痛哭。衝動地寫瞭一條短信:“為知道並記住瞭蔣先生,永遠感激你。”還是忍住瞭,沒有發。
2015年10月2日完稿
用户评价
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它將藝術的解讀變得不再枯燥乏味,而是充滿瞭故事性和人情味。陳丹青老師的“私人美術史”,就像是走進一位智者的心靈空間,去聆聽他對藝術的獨特見解和深刻感悟。我特彆好奇他所說的“陌生的經驗”,這是一種怎樣的探索?是發掘那些鮮為人知的藝術大師,還是對我們耳熟能詳的作品,提齣瞭意想不到的解讀?這種“陌生感”,恰恰是我最渴望從中獲得的。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打破我固有的藝術認知,讓我看到藝術的更多可能性。同時,作為《局部》節目講稿的延伸,我期待它能夠保留節目那種自然流暢的敘事風格,沒有生硬的理論說教,隻有真摯的分享。那些“三百餘幅精美彩圖”,是我對這本書的另一個重要期待。我一直認為,高質量的圖片是藝術書籍的生命綫,它們能夠直接傳遞藝術的視覺衝擊力,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解讀。我期待這些圖片能夠清晰、真實地展現原作的細節和色彩,讓我獲得如同親眼所見般的感受。“年度藝術話題讀物”的標簽,也讓我對其內容的深度和前沿性充滿瞭期待,它或許會引發關於藝術當下和未來的思考。
评分我一直對那些能夠“講述”藝術的書籍充滿瞭好感,因為我總覺得,藝術並非冰冷的物件,它們背後承載著創作者的情感、時代的印記,以及無數觀者的解讀。陳丹青老師的“私人美術史”,在我看來,就是一種極具感染力的“講述”。他不是簡單地羅列事實,而是通過自己的視角,去“活化”這些藝術作品,讓它們重新煥發光彩。我特彆好奇他所說的“陌生的經驗”,這到底是指哪些作品?是因為它們鮮為人知,還是因為他賦予瞭它們一種我們從未想過的解讀方式?這種“陌生”感,恰恰是激發我求知欲的關鍵。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打破我原有的認知壁壘,讓我看到藝術的更多可能性。同時,作為《局部》節目講稿的集結,我期待它能夠保留節目的那種自然流暢的敘事風格,沒有刻意的雕琢,隻有真摯的分享。這對於一本非學術性的藝術讀物來說,是非常寶貴的。那些“三百餘幅精美彩圖”,我相信不僅僅是插圖,更是他講述故事的重要載體,是引導我們進入他藝術世界的鑰匙。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獲得一種如同觀看《局部》時那般,既有知識的啓迪,又有情感的共鳴的閱讀體驗。
评分從書名《陌生的經驗》開始,就有一種強烈的吸引力。“陳丹青的私人美術史”則更明確瞭這本書的核心內容,我一直很欣賞陳丹青老師對藝術的獨到見解和他的坦率錶達。《局部》節目我更是期期不落,他那種娓娓道來的方式,總能讓我沉浸其中,獲得很多啓發。所以,當得知他的講稿集結成書,並配以精美的彩圖,我幾乎是毫不猶豫地想要擁有它。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將節目中那些精彩的片段,以一種更完整、更深入的方式呈現齣來。我好奇他是否會挑選一些在節目中未曾詳細闡述的作品,或者在文字中加入更多的心得體會。這本書的“年度藝術話題讀物”定位,也讓我對其內容充滿瞭期待,也許它能夠引發當下關於藝術的各種討論,或者提供一些新的視角來理解藝術在當今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三百餘幅精美彩圖”,對我來說更是至關重要,我一直認為,好的藝術書籍,必須要有高質量的圖片,這樣纔能更好地展現原作的魅力,也纔能讓讀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解讀。我期待這本書能成為我書架上一本常讀常新的藝術讀物,每次翻閱都能有所收獲。
评分從這本書的書名《陌生的經驗》來看,它就預示著一種探索和發現的旅程,而“陳丹青的私人美術史”則為這條旅程指明瞭方嚮。我一直很喜歡陳丹青老師那種不落俗套的藝術見解,以及他那種將復雜藝術問題變得通俗易懂的能力。這本書,是將他在《局部》節目中的智慧和感悟,以一種更具深度和廣度的形式呈現齣來。我特彆期待他所說的“陌生的經驗”,它們可能是藝術史上那些被忽略的珍寶,也可能是他對經典作品的顛覆性解讀。這種“陌生”,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巨大的吸引力,因為它意味著新的知識,新的視角,新的感悟。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我拓寬藝術的視野,發現那些我之前未曾注意到的美好。而“三百餘幅精美彩圖”,則是我對這本書的另一個重要期待。精美的圖片,不僅能夠讓讀者更直觀地欣賞藝術品,更能成為理解作者解讀的重要輔助。我期待這些圖片的質量能夠達到藝術畫冊的水準,能夠真實地展現原作的色彩、質感和細節。這本書的“年度藝術話題讀物”定位,也讓我對其內容的深度和影響力充滿好奇,它或許會成為引發藝術界和普通讀者熱議的話題。
评分這本書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它提供瞭一種非學院派的藝術解讀方式。陳丹青老師的“私人美術史”的定位,本身就意味著它不是一本僵硬的教科書,而是充滿個人情感和思考的分享。我一直覺得,藝術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它的情感連接,而陳丹青老師恰恰是擅長捕捉和傳達這種情感的人。他的語言風格,總是那麼真誠而坦率,不帶任何斧鑿的痕跡。我尤其好奇書中提及的“陌生的經驗”,它們可能是我從未接觸過的藝術領域,也可能是對我們熟悉的作品有著齣人意料的解讀。這種“陌生感”,是我最渴望從中獲得的新鮮感和啓示。我希望這本書能讓我跳齣固有的思維模式,用全新的視角去看待藝術。同時,“三百餘幅精美彩圖”的承諾,更是讓我對這本書的視覺呈現充滿瞭期待。精美的圖片,是藝術書籍的靈魂,它們能夠直接打動人心,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藝術的細節和魅力。我期待這些圖片能夠高保真地還原原作,讓我在閱讀時,仿佛置身於藝術品麵前。而“年度藝術話題讀物”的標簽,則暗示瞭這本書可能具有的深度和前瞻性,它或許會引發我們對藝術在當今社會中的作用和意義的思考。
评分從《局部》這個節目開始,我就被陳丹青老師獨特的藝術解讀方式深深吸引。他的視角總是那麼不落俗套,能夠從我們熟悉的作品中挖掘齣不為人知的細節,或者賦予它們全新的解讀。這本書,無疑是將這份“局部”的精彩延展到瞭紙麵,並且似乎更加深入和個人化。我最期待的是,這本書能否如同節目一樣,帶我進入一種沉浸式的體驗。那種感覺,就像是在一個安靜的午後,泡一杯茶,坐在窗邊,聽著陳丹青老師的聲音,看著他指點江山,將那些古老而充滿智慧的藝術品,鮮活地呈現在眼前。書中提及的“三百餘幅精美彩圖”,讓我對視覺的呈現充滿瞭期待。藝術,尤其是繪畫,視覺的衝擊力和細節的呈現至關重要。我希望這些圖片能夠高質量地還原原作的風貌,讓我在閱讀文字的同時,也能獲得直接的視覺享受,甚至通過圖片就能感受到原作的質感和筆觸。我一直認為,好的藝術書籍,應該是一件本身就具備藝術性的物品。從封麵到內頁的設計,再到圖片的印刷質量,都應該經得起推敲。而“年度藝術話題讀物”的標簽,則暗示瞭這本書可能觸及的深度和廣度,或許會引發很多關於藝術當下和未來的思考,這一點也讓我非常好奇。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給我一種低調而深沉的藝術氣息,一眼便知是關於藝術的。陳丹青老師的名字,本身就自帶光環,他那獨特的藝術視角和批判性思維,一直以來都吸引著我。而“陌生的經驗”這個書名,更是激發瞭我強烈的好奇心。我很好奇,陳丹青老師眼中的“陌生”,究竟是怎樣一種體驗?是他挖掘齣的那些不為人知的藝術珍品,還是他對我們熟悉的作品,提齣瞭我們從未想過的解讀?這種“陌生感”,恰恰是打破常規、激發思考的關鍵。我尤其期待這本書能夠像《局部》節目一樣,用一種輕鬆、自然、充滿人情味的方式來講述藝術。他不是在傳授枯燥的理論,而是在分享他與藝術的對話,他的每一次觀看、每一次感悟。這種“私人”的美術史,更具溫度和感染力,也更容易讓普通讀者接近藝術。“三百餘幅精美彩圖”,我相信是這本書的另一大亮點。高清、精美的圖片,是欣賞和理解藝術的必備條件。我期待這些圖片能夠真實地展現原作的細節和色彩,讓我在閱讀文字的同時,也能獲得直觀的視覺享受。這本書的“年度藝術話題讀物”定位,也讓我對其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充滿瞭期待,它或許會觸及當代藝術的某些熱點話題,或者為我們理解藝術的當下提供新的思考。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有一種獨特的吸引力,深邃的色調和簡潔的字體,讓人一眼就能感受到一種知識沉澱的厚重感。拿到手裏,紙張的質感也相當不錯,印刷清晰,色彩飽滿,這對於一本圖文並茂的書來說至關重要。我尤其喜歡它所傳達齣的那種“私人”的視角,陳丹青老師的文章,本身就帶著一種真誠和坦率,他不是在做學術研究,而是在分享他自己的觀看、思考和感悟。這種“私人美術史”的定位,一下子就拉近瞭讀者和作者的距離,仿佛是走進瞭一個熟識的朋友的書房,聽他娓娓道來那些他珍視的藝術故事。我一直覺得,藝術的魅力很大一部分在於它的情感連接,而陳丹青老師恰恰是擅長捕捉和傳達這種情感的人。他的語言,不似學院派那樣艱澀難懂,而是充滿瞭生活氣息和個人溫度,即使是對藝術不太瞭解的讀者,也能在其中找到共鳴,感受到藝術的溫度和力量。我迫不及待地想翻開這本書,去探索他眼中的那些“陌生的經驗”,去感受他如何將那些似乎遙不可及的藝術作品,化為觸手可及的溫暖。我期待這本書能為我打開一扇新的窗戶,看到一個不一樣的藝術世界,一個充滿驚喜和啓發的藝術世界。
评分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它打破瞭“藝術”這個詞常常帶來的距離感和神秘感。很多時候,我們談論藝術,總覺得是高高在上的,是少數人的專屬。但陳丹青老師的“私人美術史”,卻像一位親切的導遊,帶著我們走進他的藝術世界,分享他所看到的美好和思考。這種“私人”的視角,讓我覺得藝術變得觸手可及,也更加真實。他不是在炫耀他的學識,而是在分享他與藝術的每一次“遇見”,每一次“對話”。我尤其好奇那些“陌生的經驗”,它們可能是我們從未聽說過的藝術傢,也可能是我們熟悉的作品中被忽略的角落。正是這種未知,讓我充滿瞭探索的欲望。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讓我看到藝術的多樣性,感受到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類的創造力是如何閃耀的。而“三百餘幅精美彩圖”,我想必然是這本書的靈魂所在。高質量的圖片,能夠讓我們更直觀地感受藝術品的魅力,甚至在某些時刻,圖片本身就勝過韆言萬語。我期待這本書能成為我的“藝術啓濛讀物”,也期待它能在我心中種下一顆對藝術更加熱愛的種子。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陌生的經驗》本身就有一種強烈的吸引力,它暗示著一種探索未知、發現驚喜的過程。而“陳丹青的私人美術史”則為我們勾勒齣瞭一個清晰的輪廓:這是一次深入陳丹青老師個人藝術世界的旅行。我一直很欣賞陳丹青老師在藝術解讀上的獨到之處,他總是能夠從我們熟悉的作品中挖掘齣不為人知的細節,或者用一種全新的視角去看待藝術。我特彆好奇書中提到的“陌生的經驗”,它們會是哪些作品?是那些曆史上被埋沒的藝術瑰寶,還是陳丹青老師對經典作品的獨特解讀?這種“陌生感”,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強大的驅動力,它讓我渴望去瞭解,去學習。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打破我固有的藝術認知,為我打開一扇通往更廣闊藝術世界的大門。“三百餘幅精美彩圖”,是我對這本書的另一個重要期待。我一直相信,高質量的視覺呈現是藝術書籍的生命。我期待這些圖片能夠清晰、生動地展現原作的細節和色彩,讓我在閱讀文字的同時,也能獲得直接的視覺衝擊和美的享受。“年度藝術話題讀物”的定位,則讓我對其內容的深度和影響力充滿瞭期待,它或許會成為引發大傢對藝術進行深入討論的契機。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