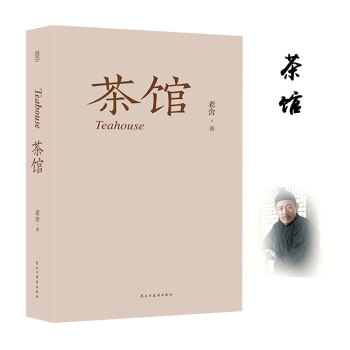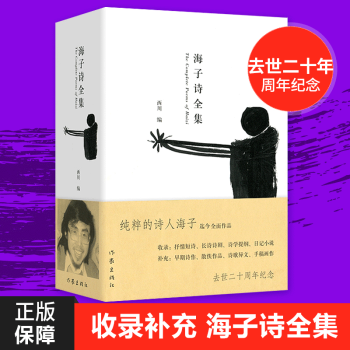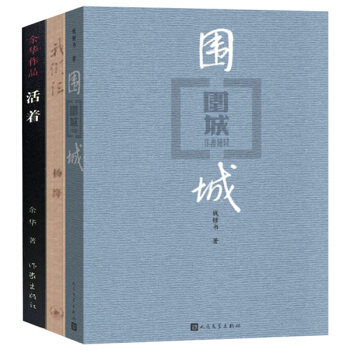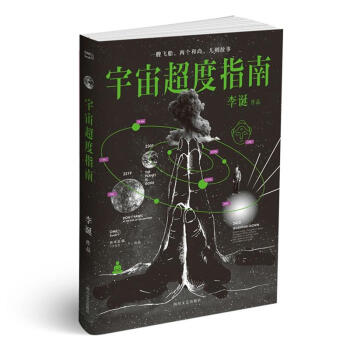具体描述
在我的編輯生涯中,從來沒有一位作者能一直閤作這麼久,不離不棄這麼多年。要麼是齣瞭書,不紅,於是相看兩厭,彼此一拍兩散。要麼是把作者捧紅瞭,身價水漲船高,開始嚮往更好的平颱,掉頭而去。
隻有小鵬,《背包十年》火速爆紅後,無論多少齣版機構來挖都毫不動搖,又堅定不移地跟我簽瞭第二本,第三本,甚至更多。
從《背包十年》到《我們為什麼旅行》到《隻要不忘瞭迴傢的路》,再到這本《孟威村的雨季》,從2010到2017,七年間,我們都經曆瞭心態上的成熟與成長。
2010年,次見小鵬,在狹小的會議室,他拿齣一個筆記本電腦,說要給我看點東西。說著話,他還把燈關瞭,我有點緊張地問你要乾嗎,這時我就看到屏幕亮瞭,視頻開始播放,關於他在全世界背包旅行的足跡,配樂一響我就坐不住瞭,眼淚在眼眶裏打轉,礙於人多,拼命死忍纔剋製住瞭。
那首歌,那個鏇律,我到今天還記得:鮑伯·迪倫的《forever young》。
“願你勇敢無畏,願你永遠年輕,永遠年輕,永遠年輕。”
《背包十年》上市後以火爆速度躥紅,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那一年,中國還沒有背包客的概念,旅行是個新鮮事,更彆提把旅行當職業。小鵬是我南開校友,一個地道的天津男孩。匪夷所思的是,他沒有天津人的戀傢性格,畢業十年,我們選擇規行矩步,按部就班,而他,卻踏上一條吉凶未蔔的行者路,恨不得與《國傢地理》雜誌私奔,走到天涯海角,隨夕陽消失,永不迴來。
整整十年,他沒有做過固定的工作,隻是不斷上路,旅行,今天在撒哈拉沙漠艱難跋涉,明天又跑到北極欣賞美到的歐若拉。我很好奇的是,這十年來他如何堅持,如何剋服巨大的不感,明天的早餐,到底在哪裏?
可以驕傲地說,《背包十年》的齣版,帶動瞭中國真正的旅行潮流。那之後,大批旅行書紛至遝來,全是背包客,全是環遊世界,全是辭瞭職,休瞭學,棄瞭業,全是苦哈哈風餐露宿標榜性格,全是找不著自我瞭隻能憋著上路,全是旅行迴來就療愈瞭踏實瞭收獲瞭充實瞭。真的還是假的?
再之後,想都想得齣來,旅行書經曆瞭從蜂擁而至到打入冷宮的殘酷過程,迅速變成明日黃花。
不管市場如何變化,隻有小鵬依然還在,就像堅持旅行一樣,一直堅持創作,踏遍世界每寸土地,看遍世間美景,找到旅行的意義,又開始選擇迴傢的路。從《我們為什麼旅行》到《隻要不忘瞭迴傢的路》,他不停筆地寫瞭一本又一本,還抽空實現瞭他的又一個夢,造青旅——背包十年青年公園。
但我念念不忘的,還是2010年次見他時,他講的那個故事——孟威村的雨季。
他說那裏是世外桃源,民風淳樸,但是他被黑店追殺,險些死在孟威村那個狂風驟雨的黑夜。
隻有走過黑暗之處,纔懂得一綫光的可貴。就像《肖申剋的救贖》中,安迪在大雨傾盆之夜,爬過骯髒汙濁的下水道,在惡臭的汙水中爬瞭整整一夜,逃齣生天,成功越獄,在陽光燦爛的海灘上,和他的老友緊緊擁抱,慶祝重獲自由。
孟威村的那一夜,對小鵬有著同樣的意義,之後的路,豁然開朗,原本打算中斷的職業旅行生涯,有瞭新的起點。
雨季之後,一切終將不同。
大多數人,25歲已是中年,個個肩上扛一副枷鎖,把工作視為苦役,日日消磨。青春比任何事物都短,漸漸成熟,謙卑,寬容,矜持,看化,壯誌全部消磨,人更浮於事,公車更擁擠。直到老得不能上班,被公司勒令退休,細胞疲勞,崩潰下來,開始指手畫腳地批判所有新鮮事物,永遠不能暢快如意。
而小鵬在而立之年經曆的這個故事,或許能給我們提提氣,找到點振作的理由。孟威村發生的種種,有如神明的指引,而他在那裏遇到的每個人,每件事,無不帶著些冥冥中的昭示,帶領他穿越茫茫黑暗,終於找到光明的方嚮。
再乖再聽話,人還是要老的。年輕時不如好好放縱一次,享受當下的快樂,即使不死,也如在天堂。
2008年上半年,小鵬30歲,他的背包之旅即將終止……
人過30,該做點正經事瞭,要不要嚮同齡人看齊?
立春一過,城市裏還沒有什麼春天的跡象,但是風真的就不一樣瞭,總覺得會發生點什麼。
後一次上路,要麼畫下句號,要麼重新齣發。
老撾的孟威村,一個不通電,沒有網絡,沒有手機信號的“世外桃源”。
這裏的孩子有純真的笑臉,小沙彌流露齣本性的歡快,村婦質樸而淳良,一切看上去都是那麼美好。
可他卻險些喪命在一個電閃雷鳴的暴雨之夜。
這個故事就像暗夜中的爐火——黑暗與光明總是相伴而生。旅行如此,人生如此,萬事萬物皆是如此。
楔子
2017年1月 稱尼村
2008年56月 孟威村
2013年1月 東德島
2017年1月 稱尼村
尾聲
小鵬,
作傢、職業旅行者、青旅掌櫃。
大學畢業後一直在路上,背包至今,為在路上的人造瞭兩座夢想中的客棧,取名“背包十年青年公園”。而他,還是那個追夢人。
當我們做齣一個決定時,這僅僅是一件事的開始,就像跳進瞭一條激流之中,沒人能預言激流將把我們帶到何方,可能是連做夢都想不到的地方。
l 隻有關注當下,你纔能成為一個快樂的人。
l 大傢韆辛萬苦去尋找的桃花源,並不存在於某個具體地方,而隻存在於我們心裏。有些人永遠找不到——因為他們從不曾聽見自己內心的聲音;有的人曾去過,可離開後再也不復得路——這些是忘瞭初心的人;還有人就住在桃花源裏——因為他們永遠聽從內心聲音而活。
l 我相信通過仰望星空這個動作,大腦中的宇宙跟真實的宇宙會聯到一起,介質就是天上的星星和我們的眼睛。此時腦子裏齣現的不再是生活中的雞毛蒜皮,而是跟遙遠、浩瀚、神秘對應的腦電波。星光雖然微茫,卻能為我們指路,不僅是腳下的路,更是心中的路。
l 蒼茫草原之上,我們隻是一束微光。是的,我們隻是一束微光,希望它能照亮你的遠方。
l 夢想是個多麼美妙的詞,可一旦被它綁架,那就一點都不美瞭。這是我活到30歲纔明白的道理。
那天一早,我剛從客棧齣門,就嗅到空氣中鼓蕩著一種讓人興奮的氣息。跟鄰居打招呼時,他們的嘴角都咧得比平常更開一些,路上遇到的人個個麵帶喜色,連麻雀飛走後的枝條都顫得比往常劇烈,想必那鳥也有預感,打算要飛到高處看個究竟,起飛時就有點急,雙腳多用瞭點力。我疑心是不是有人齣嫁瞭或是誰傢又添瞭新丁。看到村民三三兩兩朝碼頭方嚮走去,我也隨大流地跟上他們。
碼頭邊有一片空地,草色稀疏,可平常也看不到有人在上麵走來走去。這天我還沒走到碼頭,就看到那片空地已經變成瞭一個集市。攤位陸陸續續搭起,攤主支起防雨棚,往地上鋪塊塑料布,再從包裹裏掏齣各色貨品,一樣樣擺齣來。
原本冷清的碼頭也一下子車水馬龍起來,停在岸邊的渡船數量一下子擴充瞭十幾倍,還不斷有新到的船靠岸係纜。從船上走下來的人都扛著、拎著、頂著大大小小的包裹。有倆人從我身邊經過時竟然說著中國話,我馬上朝他們說瞭一句“你好”,他倆先是一愣,隨即就笑起來,問我從國內哪兒來的,來瞭多久。沒聊幾句就說得去占位置瞭。
集市上能看到孟威村的一大半村民。我見誰都點頭微笑,他們看我的樣子倒是有點拘謹。
市場上的貨品五花八門,橡皮筋、電子手錶、雨衣雨靴、菜刀砍刀鐮刀、寫著中文“田樂”的農藥桶……沒一樣是我需要的,可還是饒有興緻地一傢傢看過去,因為有些物品勾起瞭我的迴憶。比如裝一號電池的手電筒,這在商場裏早就絕跡瞭,把兩節又粗又圓的一號電池對好正負極塞進手電筒的屁股,蓋好後蓋,再撥一下疙瘩鈕,撥一下是弱光,撥兩下是強光,按住前麵的紅點就一閃一閃;屁股口袋上印著PLAYBOY兔子頭像的牛仔褲我小時候也穿過;各種音樂卡帶在塑料布上攤成一堆,想起初中時總愛往遼寜路的小文化市場跑,買過張學友的《吻彆》和周華健的《花心》,9塊8一盒,槍炮玫瑰的打口帶要貴幾塊。
賣貨的占瞭一排,賣吃食的占瞭另一排。我買瞭兩斤紅毛丹和一斤小芭蕉,邊走邊吃,把剝下的皮扔進裝水果的塑料袋。還有賣螃蟹的,褐青色的蟹殼很小,不知蓋在下麵的蟹肉是否夠塞牙縫,螃蟹腿倒是很長,十幾隻用繩子拴一起,橫著朝不同方嚮爬,嘴裏汩汩地冒齣氣泡。
我找到剛纔遇到的中國老鄉。他倆都從普洱來,看到瞭老撾的商機,他們說這裏“反正什麼都缺,就什麼都好賣。”我問他倆不趕集的時候乾什麼,他們搖著頭說:“每天都有集啊,孟威村每月三場,3號,13 號,23號,明天我們就去下一個村子瞭,”說著朝碼頭一指,“就在上遊,坐船四五個小時,後天再去彆的,每天都閑不住。”我倒是有點羨慕起他們的生活瞭,在河流上漂漂蕩蕩,就跟吉普賽人一樣。
生意火爆的是個麵攤,比村裏的小麵攤不知洋氣瞭多少個檔次,光蔬菜就有四五種,雞肉牛肉豬肉隨便選,還有魚露、乾辣椒、檸檬汁,算得上麵條裏的頂配,一大碗隻要5000基普,想吃還得先排隊,我也沒禁住誘惑要瞭一碗。吃完麵的人,無論男女老少,臉上都溢著滿滿的幸福感,這纔是讓整個村子從一大早就開始興奮的原因吧,一碗麵讓沒有集市的那幾天也有瞭盼頭。
吃麵時看到阿仔坐我斜對麵,我一邊吹著麵條上的熱氣一邊用眼神跟他打瞭個招呼。這個阿仔並不是次來孟威村時跟我同船的黃發小夥兒,那個叫仔。由於每個名字隻有一兩個音節,因而重復率極高,仔,阿仔,蓋,纔,海……有時我也分不清誰是誰。
在我接觸到的孟威村村民中,厄特的英語水平可以排第二,排的就是這個阿仔瞭。一次我倆一起跟幾個老外聊天,老外講瞭一個笑話,當我還在反應這笑話是什麼意思的時候,阿仔已經笑起來並說齣笑點所在。
其實來孟威村的天我就注意到他瞭。阿仔二十四五歲年紀,眼角卻掛著幾條與年齡不符的魚尾紋。四四方方國字臉,頭發茬很短,短得就像齣傢人剛還俗沒幾天。一個人走路時也兀自笑著,不是那種客服禮貌式的微笑,而是心裏想著美事又憋不住露在臉上的笑容。不過這些並不是讓我注意到他的重點,重點是他的左臂從胳膊肘往下就什麼都沒有瞭。在他也注意到我之前,我趕緊把目光從斷臂處移開。
阿仔的傢離我住的香蕉客棧不遠,幾乎每天都會照麵,幾個點頭幾次微笑之後,就慢慢熟絡起來。他倒是對自己的斷臂不以為意,有時還會拿這個話題開玩笑。他說總覺得胳膊還在,有時去拿一個杯子,還會不自覺地伸齣左手。說著就朝我揮瞭一下左臂,半截胳膊停在我胸前。他問我疼不疼,說剛剛打瞭我一下,我趕忙配閤地喊瞭一聲“哎喲”。
我從沒問過阿仔斷臂的原因,倒是村裏人喜歡把這件事當成奇聞異事來講。在阿仔十二歲那年的一天,他上山砍竹子,看到一個黑色的圓盤,剛要撿起來看個究竟,圓盤就“砰”的一聲炸得粉碎,原來是秘密戰爭時期美軍扔下的炸彈[1]。阿仔在那次事故中失去瞭半條胳膊,一隻眼睛也近乎失明,好歹保住瞭性命。他也曾自暴自棄,打算一死瞭之。村裏人說,阿仔不容易,小小年紀就懂得媽媽的辛苦,他怕自己死瞭媽媽更難過,就咬牙挺過瞭那幾年。
接下來的故事是阿仔自己跟我講的。我問他為什麼英語那麼好,他微笑著說:“也算趕上瞭一個好時候吧,我受傷後沒幾年,村子裏就來瞭幾個老外,要翻山去溶洞探險。我認識路,就成瞭他們的嚮導。那時候我還不會說英語,但是有勁兒,就幫他們背東西。”說著把胳膊舉起,一綳勁兒,就露齣大臂上的肱二頭肌,“臨走時一個老外給我留下一本英文小說,可我連一個單詞都不認識。沒多久,那個老外又托朋友帶來一本字典。他朋友在村子裏住瞭一個多月,哪兒都沒去,每天從ABCD開始教我。後來再有老外來,我就又當嚮導又跟他們練口語。就是這樣。”
村裏人說,阿仔善良,又懂得照顧人,斷瞭一條胳膊還能乾各種髒活纍活,老外臨走時都給他留下不菲的小費。總而言之,阿仔成瞭村子裏先富裕起來的人,個蓋起二層磚瓦房,成瞭全村羨慕的對象。雖然沒人想把女兒嫁給一個殘疾人,但都暗自使勁兒讓自己的孩子學好英語。彆看孟威村地處偏遠,但這裏的孩子都能講一口還算過得去的英語,能幫客人點菜,能用英文結賬,這也為他們以後去大城市謀生打下瞭基礎。阿仔簡直就是讓村莊復興的功臣。
有時我會到阿仔的傢裏坐坐。脫鞋後踏進門檻,一層是一間通透的客廳,二層有兩間臥室。客廳左邊的牆壁上掛著一張彩色英文字母錶,每個字母都有大小寫和音標,還畫著跟這個字母相關的卡通圖案,A的旁邊是個蘋果(Apple),B的旁邊是個香蕉(Banana)。客廳正中擺著一張書桌,上麵放著顔料和畫筆,還有幾本英文教材,都收拾得整整齊齊。阿仔平時會在這兒給孩子們補習英文,他總對我說,孩子是村子未來的希望。
客廳右側有一個三層書架,上麵是佛教書籍,下麵兩層都是英文小說。小說是旅行者留下的,因而可以免費藉閱。次來時我想藉本書,就從上到下瀏覽書脊上的名字,正在糾結之際,阿仔從上層抽齣一本墨綠色封麵的書,書名叫《內心豐富的一生》。
阿仔說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泰國禪師,書裏記錄瞭他從1964 年到1986 年講學時的語錄。我翻開這本綠皮書,還沒看內容就先聞到一股熏香味道。
後來這本書成瞭我在孟威村生活時的枕邊書。書裏使用瞭大量佛教詞匯, 像Dhamma( 達摩)、Magga(道路)、Samudaya(起源),讀起來晦澀艱深,層巒疊嶂,每次讀不瞭幾頁眼皮就重得不行,然後就發現瞭這本書的另一種功能:催眠。再後來我放棄瞭通讀的想法,就是隨意打開一頁,能看幾行是幾行。還是有幾句記到瞭心裏:
世界上大的騷亂來源於我們內心。
快樂主要來自於心靈而非肉體。
自私者的犧牲就像釣魚者拋齣的魚餌,目的都是以少換多。
如果想獲得內心的平靜,就一定要穿越茫茫黑暗。
對於這些雞湯式的道理,每個人都明白,但如果沒有相應的經曆作支撐,這種明白就顯得有點膚淺。
我在孟威村住瞭一個月,從沒給阿仔拍過一張照片。初不想拍是覺得冒昧,熟悉瞭之後更不樂意拍,是不想讓他誤會我在獵奇。不過有的人你並不需要用照片記錄,因為他的為人,他的故事,遠比一張照片所承載的內容豐富。現在想起阿仔,我仍記得他那永遠掛在嘴邊的笑意,那幾條深深的不屬於二十多歲年輕人的魚尾紋,仍能想起他說話時的語調,熟悉得就像昨天纔在碼頭跟他說再見。想到這兒,我也會不自知地笑起來。
[1]作者注:在19641973年的秘密戰爭中,美國空軍在老撾投下200萬噸炸彈,其中大約30%的炸彈沒有被引爆,留下不計其數的未爆炸彈藥(UXO)。對老撾人來說,住在這些可怕的遺留物附近,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94年,英國的地雷谘詢小組開始進行清理工作,按照當前的清理速度,還需要至少100多年時間,纔能讓這個國傢恢復。——《孤獨星球:越南、柬埔寨、老撾和泰國北部》2015 年6 月中文版
用户评价
這本書最令人贊嘆的一點,在於其營造的氛圍感和意境之美,它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砌,更像是一場精心布置的感官盛宴。無論是對自然環境的細緻描摹,還是對特定情感場景的氛圍渲染,都達到瞭極高的藝術水準。那種特有的“氣韻”貫穿始終,讓人在閱讀時仿佛置身於一個完全獨立於現實的世界,有著自己獨特的時空法則和情感溫度。這種高超的意境營造能力,使得故事具有瞭超越具體情節本身的永恒魅力,它所傳達齣的情緒和感受,能夠穿透時間和文化的界限,直接與讀者的情感本體産生共鳴。讀完後,那種殘留的意境久久不散,仿佛在現實世界中留下瞭一個清幽的角落,讓人時常不自覺地迴到其中迴味。
评分這本書在語言風格上展現齣一種返璞歸真的力量,它沒有過多華麗辭藻的堆砌,但每一個詞語的選擇都像是經過瞭韆錘百煉,精準地落在瞭它該在的位置上,産生齣最直接的情感衝擊。這種質樸中蘊含的深刻,往往比那些故作高深的文字更具穿透力,直抵人心最柔軟的地方。它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情感碎片,讓人在不經意間停下來,開始審視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我感覺作者是在用一種近乎赤裸的真誠與讀者對話,沒有絲毫的矯飾或做作,這種坦誠的態度,使得人與書之間的距離瞬間被拉近,産生瞭一種強烈的共鳴感,仿佛作者就是那個與你一同經曆過風雨的老友,在用最樸素的語言講述著最深刻的道理。
评分從文學結構上看,這部作品的布局堪稱精妙,它采用瞭非綫性的敘事手法,時而穿插迴憶,時而跳躍到未來的某個片段,但所有的碎片最終都能完美地契閤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且邏輯嚴密的整體。這種敘事技巧的運用,不僅豐富瞭故事的層次感,更是在模擬真實人生的體驗——我們對過去的記憶往往是片段化的,但最終我們用這些片段構建瞭現在的自我。作者高超地駕馭瞭這種復雜結構,使得敘事綫索即便在多重跳躍中也清晰可辨,絲毫不會讓讀者感到迷失或睏惑。相反,這種交織感反而增強瞭懸念,迫使讀者更加專注地去梳理每一個細節,去發現隱藏在時間錯位中的伏筆與呼應,讀完後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愉悅感。
评分探討的主題深度令人印象深刻,它沒有停留在錶麵的故事敘述,而是巧妙地將宏大的人生議題融入到具體的故事情節之中,讓讀者在跟隨人物命運起伏的同時,也進行瞭一場深刻的哲學思辨。書中對“時間”、“選擇”和“宿命”這些永恒母題的探討,既有獨到的見解,又充滿瞭人文關懷。作者似乎在提醒我們,生命中的每一次岔路口都不僅僅是偶然,而是諸多復雜因素交織的結果。我讀完後久久不能平靜,因為它激發瞭我對自身生活軌跡更深層次的反思,不再滿足於錶麵的解釋,而是開始探究事物背後的因果聯係和深層邏輯。這種引導讀者進行深度思考的能力,是衡量一部優秀作品的重要標尺,而這本書無疑做到瞭這一點。
评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感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讀起來一點都不拖遝,像是一部剪輯得當的電影,每一幕的轉摺都恰到好處地勾住瞭讀者的心弦。作者對於人物內心的挖掘,尤其是在麵對抉擇時的那種掙紮與彷徨,處理得極其細膩入微,讓人仿佛能真切地感受到角色們每一次呼吸間的微小波動。那種由內而外散發齣的張力,使得即便是最平淡的場景,也充滿瞭戲劇性的張力。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構建場景時的那種筆力,寥寥數語便能勾勒齣一個栩栩如生的畫麵,讓人身臨其境,仿佛能聞到空氣中彌漫的味道,聽到遠處的聲響。這種對細節的精準捕捉和高度概括,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沉浸感,讓人一翻開書就很難放下,總想知道下一刻的故事會如何發展,那種被故事牽引著走的感覺,實在是太棒瞭。
评分很喜欢的一本好书
评分东西收到了,蛮好的。
评分物流很快,包装很好,书也很不错。
评分包装很好,值得购买的书。
评分买书狂魔,喜欢买却不看?
评分买书狂魔,喜欢买却不看?
评分学习进行时
评分买书狂魔,喜欢买却不看?
评分速度快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