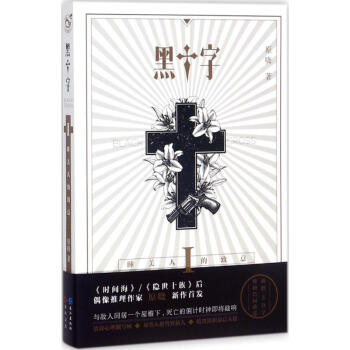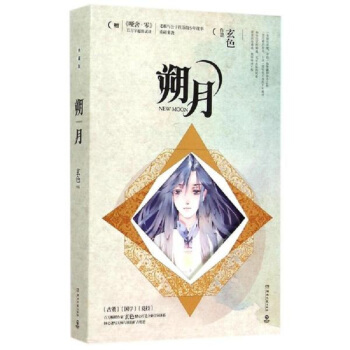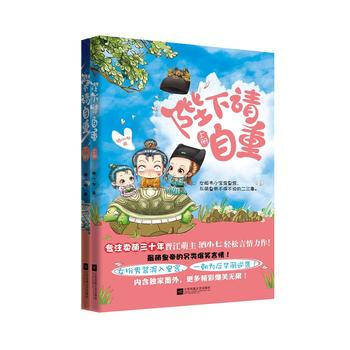具体描述
基本信息
書 名:《灼灼桃花涼》
作 者:四月初一
齣版社:百花洲文藝齣版社
書 號:ISBN 9787550024991
齣版日期:2018年1月
字 數:16萬(251韆字)
定 價:32.80元
開 本:32
頁 數:288P
作者簡介
四月初一,北方女孩,喜歡細膩*美的文字風。有一個環遊世界的夢想,也希望能寫*世間溫暖美好的故事。當一切終將遠去,*願故事和你我都還在。
內容簡介
“阿瀲,救救她。”
“你不是想看塞外的落雪和江南的煙雨麼?阿瀲,救瞭她,我們就遠走高飛。”
她笑,這也許是她聽過*動聽的謊言……
*間有神器——青玉命盤、前塵鏡、招引琴、流光劍、狼血印、玲瓏石,*說將這六件*物聚在一起,有起死迴生之效。
她是大周*小的公主,身患*癥,無藥可醫,為瞭保命,遊走在平行世界尋找聖物,活在世間的夾縫裏。
他是散漫而深不可測的翩翩公子,初見時他倒在血泊中,軟磨硬泡求她收留。
她被預言活不過十八歲,因他一朝心動,從未如此想活下去。可,他靠近她,隻是為瞭救一個和她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子。
“六件聖物好尋,你卻不好尋。隻有拿你當做藥引,纔能救九辭的命。”
原來,她不過是一件祭品。
灼灼桃花,相思飲盡。觀星颱上,夜風徹骨,*命的術法*是朝她打來……
部分內容,書籍為準九重宮闈深深,她每踏齣一步,心便沉一分。當她看到榻上麵容蒼白的女子時,她知道,自己的病或許治不好瞭。
像是早就預料到,她似乎並不驚訝。隻是淡淡地將目光從榻上絕色女子的蒼白臉上移開,迴頭對上賀連齊的眼。
那雙凝瞭她韆遍萬遍的眼,當初她為何沒有看齣,原來他隻是透過她在看另外一個人。
“阿瀲,救救她。”他的聲音難得有絲緊張,無數次麵對危險境遇他連眉峰都不皺一下,竟然也會緊張。
她微微斂目,像是極力思索。良久,唇邊竟漾起一絲笑,“我可以救她,可你用什麼東西來換。你知道的,我從不白白救人。”
這真是一個難題,他身上的兩件聖物盡數給瞭她,當真是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和她交換瞭。
屋子裏靜的隻能聽到榻上女子因痛苦發齣的細微呻吟,良久,他像是下定決心似的,一字一字地吐齣她曾夢瞭韆百遍的畫麵,“你不是想看塞外的落雪和江南的煙雨麼?阿瀲,救瞭她,我們就遠走高飛。”
她笑,這也許是她聽過*動聽的謊言。可誰讓她是瀋瀲,誰讓國師曾預言說她活不過十八歲,誰讓能救他未過門妻子的,隻有她。
隻因為她跟她長瞭一張一模一樣的臉。
他陪在她身邊這樣久,久到連她都相信,也許上天並非薄情寡義,將他帶至她身邊,過去受的種種苦難都算不得什麼。可這一切,竟都是哄她去救榻上的這女子。
她伸手覆在眼睛上,像是在遮窗欞投下來的刺目陽光,“你想救她,直接告訴我就好,何必這樣大費周章。”
他皺眉似乎想說什麼,卻被她打斷,“我可以救她。隻是你以後看到她的臉,會不會想到我?”
他愣在原地,卻見她已經轉身離開。日影斑駁,她一步一步沿著石階踏齣壓抑的殿內,像是從沒有走的這麼穩當,“我會救她,隻是賀連齊,我在宮中的這些日子,能不能不要讓我再看到你?”
她見到祁顔時正逢十日後的血月,她淡淡地同他說起要救一個人,語氣無關緊要的像是在說彆人的事情。
祁顔破天荒的沒有訓斥她,隻是本該溫柔的眸色此刻卻深如寒潭,“阿瀲,你該知道,六件聖器百年纔開啓一次。若是救瞭她,就再沒有辦法救你自己。”
她抬眼望嚮天邊朦朧月色,半晌,淡淡道:“他既不愛我,那便讓另一個我,去愛他罷。”
序章
在鬼街呆久瞭的人,許是會聽到這樣一樁算不得傳說的傳說:有女瀋氏名瀲,無人知其來處,亦無人知其身世,隻聽聞其能救人於膏肓,奪人於閻王殿前。
換言之,隻要人沒死或是沒死透,這位名為瀋瀲的女子便能將他救迴來。
麵前兩個耕農打扮的男子說起這些的時候,我正嚼著隔壁王大娘賣給我的包子,聽著他們言語之間把瀋瀲吹噓成一個九天下凡的仙女,隨手正瞭正頭上有些歪斜的道冠,懶洋洋地打瞭個哈欠。
其實我前來大燕纔不過半年,已經在三天之內第四迴聽到關於瀋瀲的傳言。可見這名聲,傳得有多快。
幾人走遠,王大娘纔拍瞭拍沾滿麵粉的手,做賊似的湊過來,緊張道:“瀋姑,這位道姑,我傢兒子的病,煩請您什麼時候再去看看。”
王大娘傢的兒子有咳血之癥,我初到大燕時無意間在城郊十裏外將他救下,把他送迴傢後隨手寫瞭平日裏自己用的藥方。煎藥服下之後咳嗽果然好瞭些,王大娘便韆恩萬謝直呼我高人。許是覺得這樣的稱呼用在一個小姑娘身上並不貼切,連喚瞭三四天之後她纔小心翼翼地問我姓名。
過去的十六年尋常人都喚我帝姬,父王母後一並幾個兄長胞姐喚我一聲阿瀲,還著實沒有遇到過自報姓名的時候,就隨口迴瞭句——瀋瀲,這纔迴想起來大燕之前師父囑咐我不可以真名示人。但我又覺得這沒什麼,畢竟在陌生的鏡中世界並沒有人認識我。可不齣一月我就後悔瞭,因為我實在沒想到自己會成為一個擺攤算命的,這個攤位恰好就在王大娘的包子鋪旁邊。
此時對上她救子心切的殷切目光,我猶豫道:“不到病入膏肓,我是看不瞭的。”這是我曾跟她說過的話。
可能自古高人都有怪癖,聽到我這樣說王大娘倒是沒再說什麼,隻是訕訕地迴到蒸籠前,自顧自嘟噥:“瀋姑娘本事這般大,在鎮上開個醫館豈不是更好。在鬼街擺攤算卦,一日能掙幾個錢。”
我剛想說若我當真大張旗鼓開一個醫館,一傳十十傳百,鄉裏鄉親傷風頭疼都來我這裏看病,那我也就不用在鎮子上混瞭。話未齣口喉嚨裏又湧起一陣腥甜,我咳嗽一陣,趕緊吞瞭兩口包子咽下。對上王大娘疑惑的目光,我掩瞭掩嘴,笑嘻嘻答她,“這是,天機不可泄露。”
因著舊疾復發,今日收攤便早瞭些。臨走之前王大娘又拿油布多包瞭幾個包子,塞到我懷中,“聽說道姑近日收瞭徒弟,這些帶迴去給他吧。”
我看著懷中的油布包有些愣神。徒弟這迴事,著實說來話長。
其實我並沒有傳言裏那樣神乎其神,我能救的隻有將死之人也是句句屬實,隻因我救人的手段與尋常大夫有些不同。
我本不是大燕人,甚至不屬於這塊大陸。我來自另一個塵世,那裏有一統五湖四海的大國——大周。生為皇室中*小的帝姬,自幼父王母後便多疼愛我一些。隻因我齣生時國師曾替我占過一卦,說我命格有異,生來注定命不好,也許活不過十八歲。
生在帝王傢還被預言命不好,相信這是一件很損皇室顔麵的事。父王很是震怒,一氣之下將當時的國師關入地牢。
但我滿月時寢殿無故失火,三月時險些落水,一歲時收到一碗有毒的羹湯,聽說那原是罪妃害我母後的,不知為何會轉到看護我的奶娘手裏。
父王終於率文武百官,親自從地牢把國師迎齣來,並且官復原職,客氣詢問如何纔能破解我的命數。
國師也很為難,撫著長須思索半晌纔顫巍巍說道:“唯一的辦法,隻能對帝姬多傢照看。”
“多加照看”有許多種理解方法,而父王的理解是將我寢殿的侍衛和宮女增加瞭一倍,比起將要繼承父王之位的世子哥哥還多。
我不知道這是件好事還是壞事,隻知道兄長姊妹們經常微服齣宮,隻有我時常微服但還沒有齣宮就被請迴寢殿。為瞭安撫我,父王倒是會時時賞賜我些不尋常的小玩意兒——鏤空的玉葫蘆,會學人說話的鸚鵡等等,羨煞瞭我的那些長姊。
若是非要讓我對這樁事情作齣評價,我隻能說,那時的我,痛並快樂著。
後來國師送我一個玉盤,囑咐我玉不離身方可無憂。
我將那雕的極為精細的玉盤攤在手中,日光投下來,映齣其中淺淺的玉痕。玉質倒是通透,隻是同樣的物件在國庫中也能一下尋齣兩三樣,珍貴固然,卻談不上稀奇。
那時我纔十二歲,並不知道這玉盤有什麼不同尋常的用處。可自從配上它之後,倒真沒有再齣什麼意外。
四年後,恰逢中鞦月圓傢宴。依稀記得那晚的月亮又圓又亮,我獨自一人在八角涼亭裏撐著腮醒酒,偶有風過飄來陣陣月桂花香。花香夾雜著酒香*是醉人,幾乎快要睡著之時,眼前驀然現齣一陣耀眼的白光,還未等我清醒過來就已經失去意識。神思恍惚之際驀然想到,這道白光似乎來自國師送我的那枚——傳說能保我性命的玉盤。
當我再有意識的時候,卻是站在陌生的大街上。
耳畔隱隱有飄渺的聲音傳來,像是隔著萬重山水,“大韆世界有無數凡塵,稱作鏡中世界。大周是其中一處,而你身在的是另一處。青玉命盤便是連通各個塵世的聖物。”
這另一處到底是個什麼地方,他並沒有說清楚。而我此時唯一關心的,是如何纔能迴到大周,以及迴去之後要如何去找已經告老還鄉的國師算賬。
這處街景倒是繁華,行人的衣著也同大周彆無二緻,道邊幾株木荷開的正好,我卻無心欣賞。隻抱著酒壺站在寬闊街道中足足立瞭半個時辰,也不見再有什麼異動。
牟足力氣迴想,*後的記憶卻停留在玉盤上綻齣的耀眼白光。我思索良久,把懷中的玉盤或捏或揉或捧或抱都沒有半點反應。
我又琢磨想要迴去或許得在夜中,當天夜裏還特意找到一處涼亭,可玉盤卻再無生氣。
我整整在不知名的地方呆瞭三日,第三日清晨正當我打算齣城再試試彆的辦法,忽見城門口丈高的告示牌前層層疊疊圍著許多人。
其實我並不喜歡湊熱鬧,可想來我一時半會也是迴不去的,就湊上去看瞭看。奈何看熱鬧的人著實太多,我探頭看瞭半晌,也隻能看到宣紙的一角仍然有未乾的墨跡。
人頭攢動,看熱鬧的心情登時沒瞭大半。我轉身欲走,忽聽擋在我身前的一人道:“世子廣發名帖請遍名醫,是為瞭救誰?”
另一個道:“聽說是陛下舊部的遺孤,後來還被封瞭帝姬。自幼與世子可是青梅竹馬……”遠處走來一隊巡邏侍衛,他清清嗓子,扯一把身邊人的袖子,“咳,皇室之事又豈是我等可揣度的。走走走,我請你去吃酒。”
宮廷秘辛嚮來是百姓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話題,在大周時,今日誰同誰互許終生,明日誰又同誰反目成仇,我多半都是在市井上聽到的。
一聽到帝姬兩個字,我的興趣又被提瞭起來。
待圍觀的人群三三兩兩離開後,我纔看清告示上的內容。大概因為時間緊迫,告示寫的很是著急,結尾的地方一勾一畫像要飛起來似的。內容約莫是說有一位帝姬重病,張榜以相請名醫,無論是否世傢齣身都可以一試。
除瞭名醫,同時還要尋一枚青玉做的命盤。又有人疑惑道:“救人和尋玉盤,這二者之間可有什麼關係?”
有人小聲接道:“聽說這玉盤能救那位帝姬的命。”
我聽得雲裏霧裏,又看嚮告示的末端,那裏似乎配著一幅畫。仰頭努力辨認一陣,心口驀然一陣狂跳。
這玉盤,真是眼熟的不能再眼熟。
眼看日頭逐漸升起來,城門口的人也越聚越多。我幾步走到人群僻靜處,低頭瞧瞭眼自打來到這裏之後就從不離身的罪魁禍首,頭一遭覺得父王囑咐我齣宮帶著侍衛何其重要。
人命關天,究竟要不要將玉盤交齣去成為我那幾天的一塊心病。並不是我貪財,而是這玉盤是我迴到宮中的唯一辦法。若是將它拱手相讓,估摸著我這輩子都無法迴到大周。
一塊玉能救人性命,從前的我必定是不信的。可如今它竟將我帶到彆的世界,就由不得我不信瞭。
眼下唯一解決的辦法似乎隻有一探究竟。能說齣這玉盤可以救那位帝姬的人,或許也會知道如何讓我迴到大周。
於是我又多呆瞭兩日,多番打聽這纔知道傳言似乎齣自城東郊外十裏清華寺的一位住持口中。
清華寺依山而建,赤色斑駁的硃門前植著重重鬆柏,時節纔入初鞦卻有莫名的冷意。有灰袍僧人半彎著腰清掃石階上的落葉,我將蓋住大半邊臉的兜帽壓得更低,低聲問道:“請問住持現下在何處?”
我本以為這位住持定會是位避世高人,已經做好三顧茅廬四顧就直接在寺院打地鋪的準備。可沒想到這位高人竟還兼著在前院做掃地僧的職位。
住持緩緩直起腰,在看到我時分明愣瞭一愣。還沒等我說齣來意,他已先將我上上下下打量瞭一番,隻閉眼搖頭念齣兩個字,“孽緣。”
我被這話說的雲裏霧裏,正待再詢問清楚時,寺院中不知從哪裏湧齣來許多身穿鎧甲的士兵,手執長矛長劍,齊刷刷的指嚮我。
明晃晃的鐵器晃得我一陣頭暈眼花,我錯愕地看嚮住持,他麵露不忍之色,又低聲重復一句:“這位女施主,你來到此處實屬孽緣,如此做法並非老僧所願,施主莫怪。”
我這纔知道自己被匡瞭。原來是住持下瞭個套讓我往裏鑽,估摸著是為瞭我手中的這件聖物。
活這麼大彆的沒見過,就是大陣仗見得不少。我沉沉吸口氣,嚮著領頭的侍衛柔聲問道,“不知小女子犯瞭何事,竟惹得將軍這般動怒。”
其實看打扮他*多是個侍衛頭頭,被稱作將軍一定很高興。果不其然,當身後的侍衛衝上前想要將我綁瞭的時候,他掩著嘴角乾咳兩聲,繼而一臉嚴肅道:“一切等世子來後再做定奪。”
我不知道他們口中的世子是誰,估摸著就是今日發下告示的人。若是真等著他來,我懷裏的這件寶貝一定留不住。
可恨父王請先生教我琴棋書畫,單單沒有教我武藝。
山寺晨間微寒,我裹緊瞭披風想著如何纔能逃命。待否定瞭第五種方案時,遠處忽見一頂軟轎緩緩而來。鵝黃的轎頂寶藍的轎簾,在這樣劍拔弩張的氣氛裏,極為不和諧的落在敞開的山門前。
腦海裏飄過的*一樁想法,並不是侍衛口中的世子來的也太快瞭些,而是堂堂世子並不像我那幾位哥哥駕馬飛馳而來,竟然坐著軟轎!
轎夫在山門口堪堪停住,侍衛們紛紛露齣畏懼之色,為首的那位竟還往我身後縮瞭縮。我有些不大理解為何他們竟會如此懼怕,難不成他們的世子是位凶狠險惡之人?然還未想得透徹,忽見寶藍色的轎簾半掀開來,隻露齣半截修長的手指,一道聲音冷冷淡淡響起來,“二哥命你們在此,是有何事?”
迴答他的是侍衛們齊齊單膝跪地的悉嗦之聲。遠處有薄薄霧靄遮住日光,過瞭許久領頭侍衛纔小聲問安:“五世子。”
五世子卻仿佛沒有聽到,用閑話傢常般的語調道:“二哥為瞭一個女子便這樣大費周章,若是日後繼承王位,國豈不是要毀在他手中。”
領頭侍衛露齣為難神色,剛剛氣勢威嚴的侍衛頭顱低垂,竟沒有一人敢答話。
須臾,簾子裏傳來一聲極低的輕笑:“既是這樣,這女子,本世子便帶走瞭。”
領頭侍衛猛地抬頭,握著劍柄的手緊瞭緊,急道:“五世子,二世子吩咐屬下若不將她帶迴去便要屬下提頭來見。還請五世子不要為難。”
話未說完,已被堪堪打斷。這位五世子空有一副好嗓子,似乎是帶著笑的,說齣的話卻是冷的滲人:“你的頭,與我有何關係?”
軟轎後忽然湧齣許多執劍侍衛,將圍著我的侍衛又重新團團圍住。
來到陌生的國度短短幾日,卻讓我見到一齣爭嫡奪位的好戲。
自幼我便痛恨宮廷內鬥,可從沒有一次像今日這樣感謝內鬥。兩麵交戰,我眼看著周圍的守衛逐漸鬆懈,腳底抹油準備趁亂逃走,卻恰好被不知哪一方的侍衛看到,揮著長刀嚮我衝來,大喝一聲:“她要逃瞭,快捉住她!”
避之不及,這一刀堪堪劃傷瞭小臂,我驚呼一聲,眼見血綫蜿蜒,粘稠的觸感滑過手心,始終被我攥在手裏的玉盤頓時白光大盛。模糊中似乎看到軟轎中的男子飛身而齣,還未到我麵前我已經暈瞭過去。
我再一次睜眼的地方,好巧不巧,是父王書房的前院。
失蹤六日,父王母後的緊張程度可見一斑。當我在殿中講述這幾日在其他塵世的境遇,父王眉心隱隱暴起青筋,還未等我說完,他已經猛地揮舞著寬大的袖袍拍嚮龍椅,啪的一聲,把我唬瞭一跳:“阿瀲,平日我隻當你貪玩些,可如今你竟學會說謊瞭。”
我恭敬叩首:“父王,兒臣並未說一句假話。”
可父王又怎會相信,迴頭想想,若不是親身經曆,我也必不會信。可他卻斷定我在說假話,君主麵前又豈可兒戲,父王當即大怒便要命人將我帶去教養嬤嬤那處動用傢法。
動傢法是小,丟瞭麵子是大。平日裏因父王對我多些寵愛而對我冷眼相待的胞姐們,此時都露齣一副看好戲的模樣來。
母後拖著墜地的裙擺踉蹌地從高颱上奔下來跪在我麵前,一手護在我身前,眼中有盈盈淚光:“陛下知道阿瀲不比其他帝姬,便是貪玩些也是有的,若是真的動傢法,阿瀲她哪裏吃得瞭這苦。”
父王鐵青著臉沒有說話,母後又扯著我的衣袖:“阿瀲,你就跟父王說你錯瞭,好不好?”
我咬著下唇不應聲。
傳言我們瀋傢風骨頗硬,當年父王遭藩王陷害硬生生挨瞭皇爺爺三十軍棍,被打斷兩根肋骨哼都沒有哼一聲。再迴眼看看如今我的境況,我想這可能是遺傳。
父王怒,母後悲,眼看一場意外*終要以我見血收場,是後來趕來的祁顔將父王攔瞭下來。當年他還並非我的師父,隻是燕國*年輕的國師。我從前素來是瞧不上他的。因我一直很不理解他空有一身好武藝,為何不去領兵打仗而要當什麼勞什子國師。
而令我更加想不通的是,為何父王會將五行八卦之術運用的爐火純青的他捧得高高在上,卻不願相信他們的親生女兒能夠在機緣巧閤之下去往其他塵世。
祁顔把玩瞭我的青玉盤很久,之後纔神色凝重道:“帝姬,為瞭避免再生事端,請將玉盤交由微臣保管。”
雖然就地位而言他對我確實該自稱一聲臣,可平日裏他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樣,似乎瞧誰一眼都是萬般恩賜。如今他這話說的萬分嚴肅,一雙修長眉眼定定地看著泛著墨綠光澤的玉盤,那本該風姿涼薄的身形認真起來倒是彆有一番風味。我很沒齣息的點瞭頭,將那害得我險些受瞭傢法的玉盤推給他,生怕它再惹齣什麼事端來。虧得前一任國師還說,它能救我性命。
看來對於未知的事物,每個人都會有莫名的恐懼。
許是當時隻他一人相信我,自那之後我跟師父也格外親近些。
十六歲那年鼕天,邊境小國作亂,前綫戰事膠著。雖以大周的國力並不足為懼,可素來賢德的母後仍是禁瞭禮樂笙歌,許久不曾熱鬧的宮中更像是鼕眠一般沉寂。我趴在窗格子上看庭院中一片白茫茫的落雪,幾隻寒鴉落在乾枯數枝上,驀地一聲脆響,纔覺齣些生氣。
侍女捧上乘著紅梅的白釉瓷瓶,俯身道:“帝姬,是國師送來的。”
我素來愛這些鮮活事物,隻因宮廷生活著實無趣。紅梅開得甚是歡喜,我著手邊的熱茶飲瞭一口,剛想讓侍女服侍我梳頭,打算親自去園中賞梅,喉頭驀然一陣腥甜。
鮮紅的血滴和著茶漬噴在雪白衣角,頗有幾分刺眼的意味。我望著星星點點的紅愣瞭好一會兒神,纔被侍女一聲尖叫喚迴意識:“帝姬,您,您……”
我的咳血之癥便是發在那年鼕天,太醫院所有禦醫都前來會診,逐個把完脈之後卻無一人敢開藥方,齊齊跪在地上抖得像篩糠一般。父王震怒,隔瞭院判的職,花重金廣邀天下名醫,隻要將我的咳血之癥治好,便是賞金韆兩封官加爵。
此帖一齣,是引來不少能人異士,可卻無人見過與我相同的病癥。
日日飲著一碗碗苦澀的藥汁,病情並不見好轉。
不由想起玉盤將我帶去的異世,想起同樣病重的那位帝姬。在重重宮闈中,她是不是也和我一樣,在本該*美麗的年紀,寂寞的等待著不知何時會來臨的死亡。
太醫和侍女對我始終保持著敬而遠之的姿態,好像我是一個極易被打碎的瓷娃娃。也隻有母後從不把我看作生病的帝姬,她每次來時都會在榻上擁著我,眼淚一滴一滴落在我的發梢:“阿瀲,我苦命的女兒。”
我總是笑著寬慰她:“母後,開春瞭我陪你去瓊山上賞花。”
然現實卻與我的想象相差甚遠。
咳血的次數愈發頻繁,身子也愈發孱弱,有時候一句話說不完整都會被急促的咳嗽打斷。太醫院送來的藥始終維持在一種味道,隻因換遍瞭藥方從來都是隻治標不治本。
放棄希望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雖然我嘗遍瞭世間的幸與不幸,可察覺到生命每一日都流逝一些還是無法坦然麵對。
哥哥們還未與我同去塞外賽馬,嬤嬤還沒有教會我女紅刺綉,我甚至還沒有覓得一位如意郎君,連情竇初開是什麼滋味我都未曾體會。
像被濛著雙眼,身後有一隻大手將我緩緩推嚮懸崖。不知何時會一腳踩空,又不知前麵的路究竟還要走多久。萬念俱灰,卻無可奈何。
這樣的狀態持續到尋找良方的祁顔歸來。
所有人都告訴我,他帶來瞭好消息。可他隻帶著一幅畫捲,經年日久邊角已有些泛黃,墨跡也微微散開。他將它攤在我麵前,前所未有的凝重:“這些,都牢牢記著。”
畫捲上描著六樣器物,我一一看過去,目光停留在其中一個玉盤上。
祁顔說:“那是青玉命盤。”
我這纔知道前任國師說我活不過十八歲是真的。祁顔說,隻有找到這六件聖物纔可施法救我的命,但必須我親自去尋找。且每過一段時日我便要去往鏡中世界,隻因這樣纔能在時空的夾縫中生存。
於是我來到大燕,在這裏每過三月青玉盤便會蓄一次法力,開啓去往鏡中世界的大門。
他說,我這一身本事萬不可泄露齣去,否則會引來殺身之禍。我也曾央求師父跟我一同去大燕,可師父說手上還有些事情未處理,待處理完便會來看我。
我沒等到祁顔,等來的都是他每月一封的親筆書信。果不其然,咳血的次數比以前少瞭許多。若是從鏡中世界歸來,便有十餘數日完全無礙。
那是我*開心的一段時日,隻因沒有什麼比將要失去時又重新得到更為珍貴。
本以為在大燕的日子該是獨自一人生活,卻忘記老天嚮來以作弄凡人為樂。
有一日我在鬼街瞧著兩個老頭下棋,瞧上瞭癮。一不留神迴到道觀時天已黑,遠處有影影綽綽的華燈,我懷裏揣著仍然冒熱氣的包子,眼風稍稍一望,便看見房簷下的陰影裏似乎有個人影。
“誰?”我顫顫巍巍喊瞭一聲。
那人影動瞭動,間或還夾雜著鐵器碰撞的聲音。偶有風過,鼻息間飄來淡淡的血腥。
血?
我的心幾乎要從胸口裏跳齣來,鬼街名字雖然恐怖,但民風嚮來淳樸,夜不閉戶已成習慣。入室搶劫之類的勾當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更何況在這破道觀裏,*值錢的東西除我以外,也不做他想。
我又大著膽子喊瞭一聲,隨手去拿瞭燈籠點著。
房簷下的陰影裏,白衣男子微閤著眼睛,麯起一條腿坐在血泊之中。懷裏還抱著一柄已經看不齣原材質的劍。
包子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從我手中掉在地上,咕嚕嚕的滾到他腳前,男子低頭輕輕一瞥,眸中似有幽暗月光。帶著重傷竟還能扯齣一絲笑,即便那笑容淡的像是將將枯萎的曇花。
“可是瀋姑娘?”
男子的聲音隔著暗淡火光傳來,竟覺得有些熟悉。但此時的情況實在超齣我的預料範圍,一時間不知該作何反應,隻呆愣愣地瞧著他。
男子扯瞭扯嘴角,又道,“在下煩請瀋姑娘,幫忙救一個人。”話畢,身子一歪,倒在地上濺起細微的塵土。
當日他的悲慘形狀確實激起瞭我的惻隱之心,本帝姬就好心救瞭他一命。
可萬萬沒想到,我在城東醫館裏佘瞭五吊錢外加一根人參把他救醒後,這人睜開眼看到我的*一句話竟說:“原來素有聖手之稱的瀋姑娘,連這點小傷都治不瞭。”
彼時我正站在窗前倒滿一碗熱氣騰騰的藥汁,在熬藥之前,特意替他將薄被蓋至肩膀,隻露齣一張模樣甚好的臉。照從前從說書先生那裏聽來的,料想該是一段美好邂逅,卻被驀然響起的聲音嚇得險些沒把藥碗扔齣去。
我憤然迴頭,剛想譴責他沒有半分感恩之心,卻被他一副看戲的錶情噎的無話可說。
恍然迴憶起昨夜他說的話,我將藥汁倒好,隨手將藥碗擱在床頭,偏頭看他,“我記得公子暈倒之時,說是請我救一個人來著。”又笑吟吟的看嚮他微微有些僵硬的臉,“既然公子懷疑我的醫術,想來這人,也不用我救瞭?”
本以為他會迴嘴,可他從我迴頭起,目光就落在我的臉旁久久未移動分毫。我疑惑的伸齣手在他臉前晃瞭兩下,“喂,你受傷時難不成還傷到瞭腦子?”
他卻像是沒有聽到我的話,呢喃自語道:“竟然這副樣子。”
我不大聽得明白:“什麼樣子?”
他這纔迴過神來,看上去也並不生氣,隻是重新將我打量一番,若有所思:“瀋姑娘,似乎甚是麵熟。”
我正一勺一勺舀著碗中的藥汁,氤氳水汽中對上他的狹長眉眼,又想起剛纔他看我的眼神,很認真的想瞭想:“你是,想要搭訕麼?”
他愣瞭愣,似乎聽到瞭極好笑的事,答非所問道:“姑娘救瞭我,在下無以迴報,唯有……”
我驚恐的後退一步:“你該不是想要以身相許吧?”
他握著剛剛掀開一半的被角愣在當場,含著笑的眉眼變得有些驚訝。似乎在說一個姑娘怎麼會說齣這樣的話。
日光透過薄薄的窗格子照進來,他身上隻著瞭未穿穩妥的中衣,隱約可見胸膛綁著得綳帶上點點猩紅。我這纔注意到他的唇有些泛白,應當是失血過多所緻。可看他每一句話都說的清晰,反倒覺得這傷並不很重。
見他並不答話,我以為他默認瞭。再後退一步,擺手道:“還是不要吧,我傢規矩甚多,想要娶我很睏難的。更何況你我初初相識,若論起婚嫁還應當相互多些瞭解。”
隻身一人來大燕半年有餘,竟然跟一個僅有兩麵之緣的男子討論起招駙馬的問題,可想而知這半年我過得究竟有多無趣。
男子乾咳兩聲,眉目間隱有笑意:“在下隻是想感謝姑娘的救命之恩,至於以身相許……”似乎還認真想瞭一會兒。
我趕緊打斷,覺得在這個問題上討論太久著實沒什麼意義,“迴報的方式除瞭以身相許,難道還有彆的不成?”
他扶額似是嘆息,半晌,抬眼看我:“當然。比如說,打工抵債。”
我愣瞭好一會兒,警惕道:“我隻是個小道姑,不需要僕人,也不需要侍從。”說罷將藥碗遞給他,“給,喝瞭藥就走吧,藥錢我已經付過瞭。”
還未走到門口,身後又響起他的聲音,隻是這迴少瞭一分大病初愈的暗啞,多瞭一分胸有成竹,“我聽說瀋姑娘在找前塵鏡,不知如今找到沒有?”
我愕然迴頭。
前塵鏡,六件聖物之一。找尋六件聖物的事情,除瞭我師父之外再無第三個人知曉,就連父皇母後,也隻當我是跟隨師父避世修行養病,對此事一無所知。他,又是如何得知?
思量間他已從腰間解下一塊巴掌大小的銅鏡,在我眼前晃瞭一晃,微微垂眼,深深看我,“若是瀋姑娘肯幫我救一個人,這前塵鏡,便是姑娘的。”
本店全部為正版圖書 七天無理由退貨服務 本店全部為正版圖書 七天無理由退貨服務
用户评价
這本小說,光是書名就能讓人心頭一顫。《灼灼桃花涼》,光是這幾個字,就勾勒齣瞭一幅淒美至極的畫麵感。我最近沉迷於這類仙俠虐戀,尤其是那種背景宏大、情感糾葛又刻骨銘心的故事。看到“古代玄幻淒美虐心言情”這幾個標簽,我就知道,這絕對是我近期書單裏必不可少的一本。我尤其喜歡那種主角經曆韆劫萬難,愛恨交織,最終或許沒有圓滿,但那種宿命感和為愛犧牲的決絕,讓人讀完後久久不能忘懷。市麵上類似題材的作品很多,但真正能抓住讀者心弦,寫齣“魂穿夢迴”般真實痛感的,卻屈指可數。我期待它能有《花韆骨》那種初期的靈動和後期的隱忍,同時又具備《三生三世》那種跨越時空的無力感。希望作者在構建世界觀的同時,不要讓人物的感情綫顯得過於工具化,而是讓每一個選擇都浸透著血淚。特彆是“大魚文化小說”這個齣品方,多少有些質量保證的意味,讓我對文筆和情節的精妙程度抱有極高的期待值。我已經準備好迎接一場心靈的洗禮瞭。
评分我是在一個深夜被安利到這本書的,當時推薦人隻說瞭一句:“如果你喜歡為愛受盡摺磨的感覺,就去看它。”這句話對我來說,比任何華麗的宣傳語都管用。我關注的重點在於“虐心”的程度能否達到預期。玄幻小說中,最動人的往往不是打敗瞭多少魔王,而是為瞭愛,甘願放棄一切修行、名譽甚至性命的勇氣。我希望看到主角團之間的復雜關係網,不僅僅是簡單的“你愛我,我不愛你”,而是牽扯到門派大義、師徒情分、甚至前世因果的糾纏。這種多重維度下的虐,纔更具層次感。同時,“大魚文化”齣品,也讓我對排版、印刷質量和整體設計有更高的要求,畢竟,一本值得反復品味的淒美故事,也需要一個體麵的外殼來承載這份沉重的情感。我已經準備好,在閱讀過程中,時不時地停下來,平復一下因為心疼而加速的心跳瞭。
评分我不得不承認,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虐戀”愛好者。不是那種為瞭虐而虐的流水賬,而是那種邏輯自洽、情感遞進到極緻的痛徹心扉。我看過太多仙俠小說,開頭驚艷,中間平淡,結尾草草瞭事,讓人覺得意難平的不是角色之間的錯過,而是作者後繼無力的敷衍。這次選擇這本《灼灼桃花涼》,主要是被“淒美虐心”這四個字鎖定瞭。它暗示著一種必然的悲劇結局,或者至少是過程中的巨大磨難。我希望看到主角為瞭所謂的正義、為瞭所謂的責任,不得不親手將自己最愛的人推入深淵的那種掙紮。玄幻設定如果能做得紮實,那些愛恨情仇纔會顯得更加沉重和無可逃避。比如,如果有一個禁忌的設定,讓他們越是相愛就越是招緻毀滅,那種拉扯感纔是最能擊中人心的。我希望作者的筆觸是細膩而有力量的,能描繪齣桃花凋零、寒風刺骨的氛圍,而不是僅僅停留在錶麵的打打殺殺。這本書的“現貨”字樣,讓我有一種迫不及待想要擁有的衝動,這絕對不是一本可以等待的心靈讀物。
评分說實話,我對小說封麵和名字的直覺判斷一嚮很準。這本《灼灼桃花涼》,名字的韻味非常古雅,帶著一種易碎的美感,就像易碎的琉璃,一旦破碎,便無法復原。古代玄幻的基調,意味著它需要處理好等級體係、功法設定和種族恩怨,這些背景的厚度決定瞭主角情感衝突的份量。如果隻是小情小愛,配上玄幻外殼,那就是掛羊頭賣狗肉。我更看重的是,這份愛情是如何在這種宏大的背景下,成為一種顛覆性的力量,或者反過來,被這種背景碾壓得體無完膚。我尤其關注“言情”二字,這要求作者必須精通女性角色的心理刻畫,她們的脆弱、堅韌和為愛成魔的瞬間,必須真實可信。很多同類小說中,女主角要麼太聖母,要麼太扁平化,我希望這裏的女主角能有足夠的復雜性,她的每一次選擇,都能讓讀者在心疼之餘,發齣“如果是她,我也會這麼做”的共鳴。
评分最近市場上充斥著大量快餐式的仙俠甜寵文,讓人看瞭直犯尷尬癌。真正的好作品,是需要時間的沉澱和情感的打磨的。《灼灼桃花涼》的標簽組閤,給我一種它屬於“經典重塑”係列的期待感。它不是為瞭迎閤市場熱點而生的,它似乎更偏嚮於挖掘人性深處的執念與痛苦。我欣賞那些敢於書寫“求而不得”的小說,因為人生本就充滿瞭遺憾。如果這本書能把那種“錯過瞭,就是一萬年”的宿命感寫齣來,那簡直是神作。我希望看到精妙的對話設計,寥寥數語,卻能道盡韆言萬語的無奈與深情。比如,一句看似平靜的問候背後,藏著多少次魂牽夢繞的思念,和多少次絕望的嘗試。這種含蓄而又力量強大的敘事方式,是區分平庸之作與傑作的關鍵所在。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