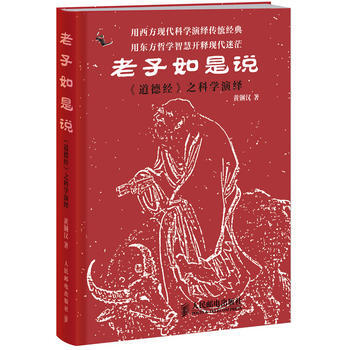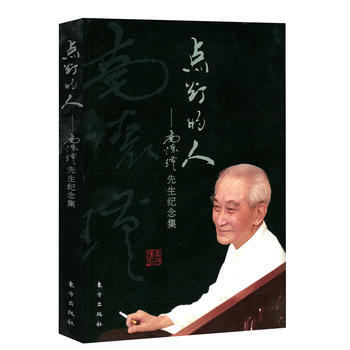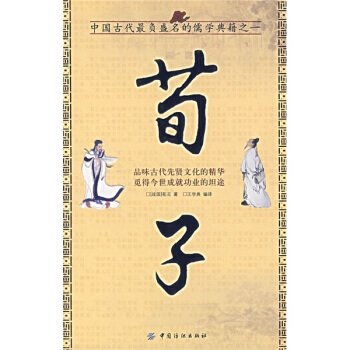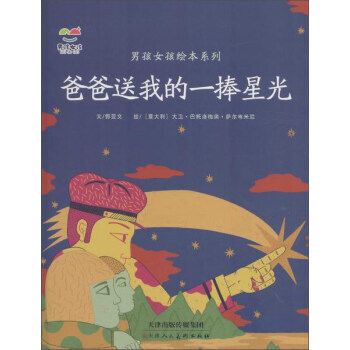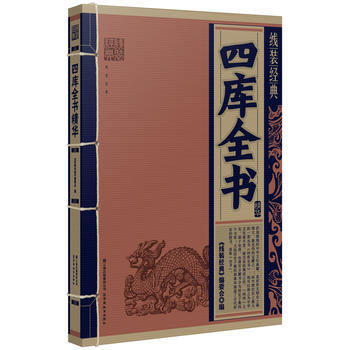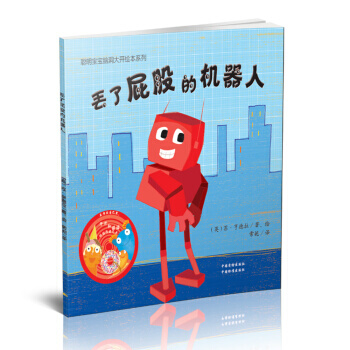具体描述
基本信息
書名:捨得,捨不得:帶著《金剛經》旅行(蔣勛暢銷新作)
定價:45.0元
作者:蔣勛
齣版社:湖南美術齣版社
齣版日期:2015-10-01
ISBN:9787535673800
字數:156000
頁碼:
版次:1
裝幀:平裝
開本:大32開
商品重量:0.4kg
編輯推薦
href='#' target='_blank'>
贈送蔣勛金剛經書法書簽2枚
蔣勛老師全新散文,颱灣誠品、金石堂在榜暢銷長達一年,繼《孤獨六講》之後再講人生,以金剛經和佛學智慧解讀生命、自然、文學、藝術。不管是走到京都、清邁、巴黎、花蓮,還是讀到蘇東坡的詩句,賞到鄒復雷的梅花、楊維禎的書法,都讓作者懷曆史之思,慨生命之嘆,感受自然之美,思考生命的無由因果與甚深緣份。書中收錄蔣勛老師書法、攝影、畫作,超值贈送蔣勛念誦《金剛經》CD。《金剛經》是蔣勛老師為朋友祈福而讀誦,也為父母手抄,深具祝福意味。
相關推薦:
href='#' target='_blank'>寫給大傢的西方美術史:蔣勛榮獲金鼎奬經典之作(定製版)
href='#' target='_blank'>蔣勛的“大美”套裝(全二冊):贈暢銷書一本
href='#' target='_blank'>吳哥之美:颱灣美學大師蔣勛14次遊曆吳哥,寫就關於吳哥優美的文字,颱灣暢銷百萬冊
href='#' target='_blank'>美的沉思:全新修訂彩色珍藏版,席慕蓉、王躍文、閻真傾情推薦!隨書附贈敦煌彩塑菩薩藏書票。
href='#' target='_blank'>捨得,捨不得:帶著《金剛經》旅行(套裝)
href='#' target='_blank'>
內容提要
京都永觀堂、清邁無夢寺、加拿大奈恩瀑布……蔣勛帶著《金剛經》,讀經、抄經,旅行十方,在心的寺院裏一殿一殿地拜去,在洪荒自然裏看見生命的不同修行,在文學藝術裏照見生命的不同可能,與一切有情眾生,領會人生中的捨得與難捨……
目錄
作者介紹
蔣勛,福建長樂人,1947年生於西安,成長於颱灣。颱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係、藝術研究所畢業。1972年負笈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1976年返颱後,曾任《雄獅》美術月刊主編、東海大學美術係係主任、《聯閤文學》社社長。
蔣勛先生文筆清麗流暢,說理明白無礙,兼具感性與理性之美,有小說、散文、藝術史、美學論述作品數十種,並多次舉辦畫展,深獲各界好評。
著有《美的沉思》《寫給大傢的西方美術史》《吳哥之美》《蔣勛說紅樓夢》《孤獨六講》《生活十講》《漢字書法之美》《蔣勛說唐詩》《蔣勛說宋詞》等書。
文摘
迴 頭
生命如果不是從一點點小小的歡喜贊嘆開始,大概後總要墮入什麼都看不順眼的無明痛苦之中吧。
時光
鞦天賞楓的季節,好幾次在京都。幾星期,一個月,好像忘瞭時間。好像春天纔剛來過,同樣的山,同樣的道路,同樣的寺院,同樣的水聲,同樣的廢棄鐵道,同樣的水波上的浮沫,同樣的一座一座走過的橋,橋欄上的青苔,迴首看去,那橋欄,不是剛纔還鋪滿落花嗎?然而隻是一迴頭,落花都已一無蹤跡,已經是滿山的紅葉瞭。水渠清流裏也都是重重疊疊的紅楓落葉,隨波光雲影逝去。每一次迴頭因此都踟躕猶疑,害怕一迴頭一切繁華都已逝去。
已經是鞦深瞭嗎?
一個地方去的次數多瞭,常常不知道為什麼還要再去。一去再去,像是解脫不開的一世一世的輪迴轉世嗎?
“無明所係,愛緣不斷,又復受身。”常常說給朋友聽的源自《阿含經》的句子,或許是提醒自己於此肉身始終沒有瞭悟吧。
為什麼還要有這一世的肉身?為什麼肉身還要一次一次再重來這世間?為什麼還要一次一次再與這麼多好像已經認識過的肉身相見?
“愛緣不斷”嗎?總是切不斷的牽掛愛恨,像一次一次地迴頭。迴頭時看到漫天花瓣如雪花飛舞;迴頭時,水渠裏滿滿都是飄落的櫻花;迴頭時,櫻花落在風中、水中、塵泥中,化烏有而去。殘楓紅艷如血,觸目驚心,也隻是肉身又來瞭一次吧。不堪迴首,仿佛迴首時,隻剩斑駁漫漶、沉沉墨色裏一方令人心中一驚的硃紅印記,還如此鮮明。
一個地方,來的次數多瞭,來的時候好像沒有特意想看什麼,不想做什麼,不想趕景點行程,隨意信步走走。有時候就在寺町通一傢叫Smart的咖啡店坐一下午,白頭發的老闆慢悠悠地煮著一杯咖啡。
我來過,在這個角落坐過,看著一個青鬢白皙的青年這樣慢條斯理地調理咖啡,留聲機還是那一首歌。
可以這樣坐著,把時光坐到老去嗎?
那年輕侍者把咖啡恭敬放在桌上,說瞭一句我沒有聽懂的話。
“無明所係……”啊,是因為不懂,所以要一次一次重來嗎?看不懂,聽不懂,無法思維;以為懂瞭,並沒有懂,隻是在巨大的無明中,要一次一次重來,做沒有做完的功課。
禪林寺
上一個鞦天,有一個月的時間在京都,正是紅葉盛的時候,遊客滿坑滿榖。我想還是避開所有人多的景點,不如往郊外人少的地方去。但是有一位朋友年中突染重病,昏迷瞭十二天,親人從國外趕迴來,也都不能喚醒。十二天後卻奇跡似的好瞭。清醒以後,雖然虛弱,卻也頭腦清楚,沒有什麼後遺癥。醫師也覺得是萬幸,不可思議。
這位朋友知道我去日本,就順口要我替她到佛前一拜,也沒有指定哪一所寺廟。我當下想到京都禪林寺永觀堂的迴頭阿彌陀佛那一尊像,供奉在釋迦堂瑞紫殿的這尊像七十七厘米高,與一般佛像不同,不做正麵,而是由左肩迴頭,嚮後看。以前去過好幾次,對這一件作品印象很深。
《阿彌陀經》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那是遙遠到我無法思議的空間啊。不可思維、不可議論的國度。“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那是在遙遠不可思議的地方享有一切安樂的國度吧。然而,為什麼已經到那樣國度的阿彌陀佛竟然都迴頭瞭?我心裏想,如果連阿彌陀佛都迴頭瞭,是可以安慰這病苦劫難中重新迴來的朋友的吧。私下心裏發願,這次京都一行,替她去永觀堂佛前一拜,帶一張迴頭的阿彌陀佛像給她。
許願時沒有特彆想到永觀堂是觀賞楓葉的,這個季節去永觀堂,會有多少遊客擠在山門前,會有多少世界各地的觀光客排長龍等待買票拜觀。
我先去瞭高野山,在舊識的清靜心院投宿兩晚。下瞭山一到京都就直接去瞭永觀堂。
永觀堂前果然人山人海,長長一條排隊買拜觀券的遊客隊伍,找瞭很久,纔找到尾巴。我一度想放棄瞭。真要在雨中排一兩小時的隊伍嗎?剛一動念,隨即發現自己許的願,原來也如此輕率。隻是雨,隻是一兩小時的等待,許的願就可以輕易放棄,自己許願的力量如此脆弱啊。想起《阿彌陀經》的句子:“捨利弗,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我想要退轉瞭嗎?
排隊等候的時候,人聲嘈雜沸沸揚揚。起初心亂,細聽卻也都是在贊美鞦光、贊美紅葉、贊美雨聲。不同聲音的歡喜贊嘆,像一片和聲。有的大概初次來京都賞楓,當然狂喜驚叫,贊嘆連連,語言仿佛不足以錶達心中興奮激動。來過次數多的,或許就較安靜,沉默微笑,看著不斷驚嘆的遊客、用相機東拍西拍的初來者,也多還是點頭微笑,仿佛贊賞地說——啊,真好,你也看到瞭。
生命如果不是從一點點小小的歡喜贊嘆開始,大概後總要墮入什麼都看不順眼的無明痛苦之中吧。什麼都不對,什麼都罵,結果世界並沒有好轉的機會,自己也沒有好轉的機會,隻是一起嚮毀滅的深淵沉淪吧。
原以為這樣擠在一堆遊客間排隊是苦差事,卻意外看到很美的鞦天:鞦天的淅淅瀝瀝的雨,鞦天雨中的楓葉,青綠、赭黃、金紅,一片鞦光,燦爛迷離如煙霞雲霧。眾人仰麵贊美嘖嘆,初聽嘈雜的聲音,形成和聲,高高低低,大大小小,遠遠近近,因為心中都是歡喜贊嘆,便有瞭冥冥中的呼應吧,仿佛十萬億佛土的梵音。
因為下雨,進瞭禪林寺,在入口大玄關脫鞋,把鞋放進塑料袋中,撐著傘,彎腰解鞋帶,都是艱難事。遊客因此相互扶持遮雨,認識與不認識,都在玄關處進進齣齣,有瞭短暫擦肩而過的緣分。
禪林寺依山而建,早是日本文人藤原關雄的私人邸所。藤原去世,這一處雅緻的莊院就由五十六代清和天皇敕賜為禪林寺。藤原是平安時代日本權力核心的世族,清和天皇的皇後藤原高子就齣身於這一傢族。清和天皇死後,陽成天皇即位,也由天皇的舅父藤原基經攝政。權傾天下的世傢,豪門的富貴,加上關雄文人雅士的嚮往,為這一所宅院建立瞭優雅的基礎。
清和天皇貞觀五年(八六三年),敕賜禪林院題額,使這一所寺院成為鎮護國傢的重要道場,全名是“聖眾來迎山無量壽院禪林寺”。
永觀
這所曆經天皇敕封的護國禪寺,一直到第七世住持永觀律師,做瞭幾件對大眾有深遠影響的事,纔被世俗大眾通稱為永觀堂,成為傢喻戶曉的寺院。
永觀律師據說身體孱弱,自己長年病痛,因此特彆能體會為疾病所苦的大眾吧。他在一〇九七年於禪林寺中設立瞭藥王院,以湯藥濟度眾生。
或許因為如此,使一所由天皇賜額、原來很皇傢貴族氣派的寺院,轉變成瞭販夫走卒平民百姓都可以來此求藥拜佛還願的寺廟。禪林寺的名字逐漸被淡忘,大傢都以永觀師父的名字來稱呼這所寺院瞭。
永觀律師齣名的傳奇故事,是他在阿彌陀堂上念誦,或許一時心不專一,就看到阿彌陀佛顯身,迴頭嚮他說:永觀,你遲瞭。
這傳久遠的故事,使禪林寺因此創作瞭世間一尊迴頭的阿彌陀佛像,以為紀念。
這一尊像與一般阿彌陀佛像並無太大不同,右手手掌嚮上嚮外揚起,食指與大拇指圈成形狀,持無畏說法手印。左手手掌嚮下,持施與說法印。佛身褒衣廣袖,赤袒胸腹。身後有頭光背光,背光有火焰流雲紋,火焰流雲中有飛天供養。阿彌陀佛像特殊的是頭部不做正麵,而是嚮左肩身後轉頭探望。
以佛教教義而言,菩薩於世間有情,牽連掛念眾生,因此常迴世間。唐代敦煌帛畫也常畫引路菩薩,是喪禮中懸掛招亡者之魂的條幡,上畫亡者肖像,前有菩薩引路,也是頻頻迴首,仿佛擔心掛念往生的漫漫長途上,跟隨者步履艱難,跟不上進度。
佛與菩薩不同,已入涅槃,不受後有,因此應該是不會迴頭的瞭。
然而永觀堂的阿彌陀佛意外迴頭瞭,成為傳世一尊迴頭的佛像。
永觀律師因為自己的身體疾病,同體大悲,創建瞭藥王院,可以濟度眾生肉身之苦。永觀律師修行中一時的分心,也讓阿彌陀佛在永世的寂滅超然中動心動念,又迴瞭一次頭。
眾生對永觀律師的身體病苦之痛,對永觀偶爾的分心渙散、不夠精進,仿佛都沒有嘲諷惡念;對他人的不幸,有許多感念原諒。我們是藉著自己或他人的不,纔給瞭自己更寬容的修行機會吧。
永觀,你遲瞭。佛的聲音如此督促鼓勵。
在漫長的修行路上,或快或慢,或早或遲,其實都是修行,也都可以被包容顧念吧。
我擠在眾多的遊客間一殿一殿拜去,心裏不急,也就不計較快慢遲早。
禪林寺在上韆年間一直整建,建築園林的布局空間依循自然山丘脈絡走勢,不像一般禪院那樣規矩平闆。走纍瞭,可以停在水琴窟靜坐一會兒,聆聽若有若無的細細水聲穿流過石窟孔洞。水流緩、急、快、慢,力度輕重變化,都在幽微石窟裏構成仿佛琴音的水聲。但當然是自己靜下來瞭,纔聽得到這麼幽靜在有無之間的水聲。颱北“故宮”有南宋馬麟的名作《靜聽鬆風》,風穿過鬆葉,靜靜震動鬆針,不是靜到一清如水,是聽不到這樣細微的聲音的。東方美學多不停留滿足在人為的藝術層次上,人為的聲響音樂,人為的色彩絢爛塗抹,終隻是領悟大自然的過渡與媒介,像《指月錄》裏說手指指月亮,手指的重要性太被誇張,可能看不見手指指嚮的月光,也忘瞭真正要看的不是手指,而是皓月當空。
水琴窟在日本許多寺廟都有,比叡山延曆寺釋迦堂前也有極幽微動聽的水琴窟,水聲說法,來的人或聽到或無聞無明,各自有各自領悟的因果。
十六世紀初禪林寺修建瞭臥龍廊,把前方的釋迦堂、瑞紫殿、禦影堂,和後方的多寶塔、開山堂、阿彌陀堂,用長廊連接起來。長廊復道,有時淩空飛起,沒有阻擋,也是眺望俯瞰山景寺院全局的好景點。許多遊客從此高處,看到整片飛紅的鞦楓,層林盡染,更是贊嘆不止。
《阿彌陀經》說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然而正是要在五濁中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離此煩惱濁世,並沒有修行,也沒有真正的領悟。
永觀律師的身體疾病,永觀律師的分心,因此纔如此為後來眾生紀念吧。
我在齣玄關前為朋友求瞭一張迴頭阿彌陀佛的像,在她大病初愈的案前,或許可以更讓她安心吧。
永觀堂鍾聲極齣名,悠悠蕩蕩,東山一帶,遠近都可以聽到。如果有緣,剛好遇到鍾聲迴蕩,許多路上行人都會迴頭張望,尋找鍾聲。永觀堂鍾樓雖遠,其實後迴頭尋找的人也都發現:鍾聲就在耳邊。
序言
我有兩方印,印石很普通,是黃褐色壽山石。兩方都是長方形,一樣大小,零點八厘米寬,二點四厘米長。一方上刻“捨得”,一方刻“捨不得”。“捨得”兩字凸起,陽硃文。“捨不得”三個字凹下,陰文。
兩方印一組,一硃文,一白文。
當初這樣設計,大概是因為有許多捨不得吧——許多東西捨不得,許多地方捨不得,許多時間捨不得,許多人捨不得。
有時候也厭煩自己這麼多捨不得,過瞭中年,讀一讀佛經,知道一切難捨,終還是都要捨得;即使多麼捨不得,還是留不住,也要捨得。
刻印的時候在大學任教,美術係大一開一門課教篆刻。篆刻有許多作業,學生臨摹印譜,學習古篆字,學習刀法,也就會藉此機會練習,替我刻一些閑章。詢問我說:想刻什麼樣的印?
我對文人雅士模式化的老舊篆刻興趣不大,要看寜可看上古秦漢肖形印,天真渾樸,有民間百姓的拙趣。
學生學篆刻,練基本功,把明、清、民國名傢印譜上的字摹拓下來,畫在印石上,照樣下刀刻齣形來。這樣的印,大多沒有創作成分在內,沒有個性,也沒有想法,隻是練習作業吧,看的人也自然不會有太多感覺。
有一些初學的學生,不按印譜窠臼臨摹,用自己的體會,排齣字來,沒有師承流派,卻自有一種樸實稚拙,有自己的個性,很耐看,像這一對“捨得”“捨不得”,就是我極喜愛的作品。
刻印的學生姓董,同學叫他Nick(尼剋),或昵稱他的小名阿內。
替我刻這兩方印時,阿內大一,師大附中美術班畢業,素描底子極好。他畫隨便一個小物件、自己的手、鑰匙,蹲在校園,素描一朵花,可以專心安靜,沒有旁騖,像打坐修行一樣。作品筆觸也就傳達齣靜定平和,沒有一點浮躁。
在創作領域久瞭,知道人人都想錶現自我,生怕不被看見。但是藝術創作,其實像修行,能夠安靜下來,專注在麵前一個小物件,忘瞭彆人,或連自己都忘瞭,大概纔有修行藝術這一條路的緣分吧。
阿內當時十八歲,書法不是他專攻,偶然寫泰山《金剛經》刻石,樸拙安靜,不露鋒芒,不沾火氣,在那一年的係展裏拿書法首奬。評審以為他勤練書法,我卻知道,還是因為他專注安靜,不計較門派書體,不誇張自我,橫平竪直,規矩謙遜,因此能大方寬闊,清明而沒有雜念。
藝術創作,還是在人的品質吧。沒有人品,隻計較技術錶現,誇張喧嘩,距離美也就還遠。弘一大師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就是這意思吧。
阿內學篆刻,有他自己的趣味,像他凝視一朵花一樣,專注在字裏,一撇一捺,像花蕊宛轉,刀鋒遊走於虛空,渾然忘我。
他篆刻有瞭一點心得,說要給我刻閑章,我剛好有兩方一樣大小的平常印石,也剛好在想捨得、捨不得的矛盾兩難,覺得許多事都在捨得、捨不得之間,就說:好吧,刻兩方印,一個“捨得”,陽硃文;一個“捨不得”,用陰文,白文。心裏想,“捨得”如果是實,“捨不得”就存於虛空吧,虛實之間,還是有很多相互的牽連糾纏吧。
這兩方印刻好瞭,有阿內作品一貫的安靜知足和喜悅,他很喜歡,我也很喜歡。
以後書畫引首,我常用“捨得”這一方印。“捨不得”,卻沒有用過一次。
有些朋友注意到瞭,就詢問我:“怎麼隻有‘捨得’,沒有用‘捨不得’?”
我迴答不齣來,自己也納悶,為什麼兩方印,隻用瞭“捨得”,沒有用“捨不得”。
阿內後來專攻金屬工藝,畢業製作做大型的銅雕地景,錘打鍛敲過的銅片,組織成像蛹、像蠶繭,又像遠古生物化石遺骸的造型,攀爬蟄伏在山丘曠野、草地石礫中,使人想起生之艱難,也想起死之艱難。
大學畢業,當完兵,阿內去俄勒岡專攻金屬藝術,畢業以後在舊金山有工作室,專心創作,也定期在各畫廊展覽。
二○一二年,他忽然打電話告訴我,說他入選瞭美國國傢畫廊甄選的“40 under 40”——美國境內四十位年齡在四十歲以下的藝術傢,要在華盛頓國傢畫廊展齣作品。
阿內很開心,覺得默默做自己的事,不需要張揚,不需要填麻煩的錶格申請,就會被有心人注意到。
我聽瞭有點感傷,不知道阿內這樣不張揚的個性,如果留在颱灣,會不會也有同樣的機會被發現。但我沒有說齣來,我隻是感傷地問:阿內,你快四十瞭嗎?
啊,我記得的還是那個十八歲蹲在校園樹下素描一個蟬蛹的青年啊。
所以也許我們隻能跟自己說“捨得”吧!
我們如此眷戀,放不瞭手;青春歲月,歡愛溫暖,許許多多捨不得,原來,都必須捨得;捨不得,終究隻是妄想而已。
無論甘心,或不甘心,無論多麼捨不得,我們終都要學會捨得。
捨不得
一位朋友喪偶,傷痛不能自持,我抄經給她,希望有一點安慰。她看到引首“捨得”這一方印,搖著頭,淚眼婆娑,萬般無奈,哀痛叫道:“就是捨不得啊!”
我纔知道自己對人的幫助其實這麼小,每個人“捨不得”的時候,我究竟能做什麼?
多年來,習慣早上起來件事就先盤坐讀一遍《金剛經》。
有人問我:為什麼是《金剛經》?
我其實不十分清楚,隻是覺得讀瞭心安吧,就讀下去瞭。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使自己心安的辦法。方法不同,能心安就好,未必是《金剛經》吧。
《金剛經》我讀慣瞭,隨手帶在身邊,沒事的時候就讀一段。一次一次讀,覺得意思讀懂瞭,但是一有事情發生,又覺得其實沒有懂。
像經文裏說的“不驚、不怖、不畏”,文字簡單,初讀很容易懂。不驚嚇、不恐懼、不害怕,讀瞭這幾個字,懂瞭,覺得心安,好像就做到瞭。
但是,離開經文,迴到生活,有一點風吹草動、東西遺失、親人生病、病疫流行、飛機遇到亂流、狂暴風雨、打雷、閃電、地震……還是有這麼多事讓我害怕、恐懼、驚慌。
我因此知道:讀懂經文很容易,能在生活裏切實做到,原來這麼睏難。
我因此知道,原來要一次一次讀,不是要讀懂意思,是時時提醒自己。
像我喪偶的朋友一樣,該捨得的時候捨不得,我也一樣驚慌、害怕、傷痛。
“不驚、不怖、不畏”,她做不到,我也一樣都做不到。
“不驚、不怖、不畏”,還有這麼多驚嚇慌張,還有這麼多捨不得,害怕失去,害怕痛,害怕苦,害怕受辱,害怕得不到,害怕分離,害怕災難,害怕無常。因為還有這麼多害怕,這麼多驚恐怖懼,每次讀到同樣一句“不驚、不怖、不畏”,每一次聽到、看到一個人因為“捨不得”受苦,就熱淚盈眶。
王玠
早讀《金剛經》其實跟父親有關。大學時候,他就送過我一捲影印的敦煌唐刻本的《金剛經》捲子,我當時沒有太在意,也還沒有讀經的習慣。
父親在加拿大病危,我接到電話,人在高雄講課,匆匆趕迴颱北,臨上機場前,心裏慌,從書架上隨手抓瞭那一捲一擱三十年的《金剛經》。十多個小時飛行,忐忑不安,就靠這一捲經安心。
忽然想到這一捲《金剛經》是大學時父親送我的,卻沒有好好仔細看過。
原木盒子,盒蓋上貼一紅色簽條,簽條上是於右任的字,寫著:影印敦煌莫高窟大唐初刻金剛經捲子。
三十年過去,我一直沒有好好讀這一捲經,打開過,前麵有趙恒惕的詩堂引首,“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幾個隸書,隔水後就是的鹹通九年佛陀法會木刻版畫。這個捲子後來流傳到歐洲,許多學者認為是世界古老的木版印刷,在印刷的曆史上是重要文件。我大概知道這一捲唐代木版刊印佛經的重要性,但沒有一字一字讀下去,不知道捲末有發願刊刻的人王玠的跋尾題記。
在飛機上讀著讀著,心如此忐忑不安,一次一次讀到“不驚、不怖、不畏”,試圖安心,“雲何降伏其心”,原來如此難。
讀到跋尾,有一行小字:
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 二親敬造普施
王玠為亡故父母發願,刊刻瞭這一捲《金剛經》,也祈願普施一切眾生。王玠,好像因為自己的捨不得,懂瞭一切眾生的捨不得。
飛機落地,帶著這一捲經,趕去醫院,在彌留的父親床前讀誦,一遍一遍,一字一字,“不驚、不怖、不畏”,一直到父親往生。
因為父親往生,因為王玠的發願,因為這一捲《金剛經》,仿佛開始懂一點什麼是“一切難捨”。許許多多捨不得,有《金剛經》的句子陪伴,一次一次,度過許多“難捨”的時刻。
或許因為王玠的發願,我也開始學習抄經,用手一個字一個字抄寫。抄寫,比閱讀慢,好像可以比閱讀更多一點刻骨銘心的感覺吧。
我看過許多手抄《金剛經》,明代董其昌,清代金農,近代弘一大師,都工整嚴謹。我知道自己做不到那麼好,無法做到那麼恭謹,但很想開始試一試。
二〇一三年夏天去溫哥華,過東京,在鳩居堂買紙,看到專為手捲製作的唐紙,兩手指粗一捲,外麵用紅紙封著。價錢不低,我想數量應該不少,用來抄一捲《金剛經》或許夠用。
到瞭溫哥華,打開來看,發現一捲裏隻有兩張,極古樸的紙,托墨而不喧嘩。但是兩張紙,抄寫不到四分之一,紙已用完瞭。
我噓一口氣,覺得遺憾吧,沒想到次發願抄經,就阻隔在紙不夠用,無法完成。
隔幾天,讀經讀到“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啞然發笑,知道自己還有這麼多執著掛礙。看到有類似的紙,不那麼細緻,但是本意原是為抄經,就不想許多,把紙裁成長捲,紙色不同,質地也不同,接在一起,好像也不稱。但還是想為亡父母抄一次經,好像也不計較許多瞭。
每天抄一段,整捲經抄完,約八百厘米長。迴到颱灣,交給清水蘇先生裝裱,讓他傷瞭腦筋,把紙色不一、質地不一的八張紙連接在一起,做成瞭一手捲。
捨得
捲《金剛經》抄寫完,覺得很開心,我因此習慣瞭在旅途中抄經。
二〇一三年年底,從東南亞去巴黎、倫敦,再迴曼榖,一路又抄瞭一捲《藥師經》。因為要帶在身上走,因此選擇瞭可以在旅途中用的簡便工具:一錠小墨,一片很薄的硯石,一支大阪製的小毛筆“五十餘川”,都輕便不占空間。
多年前遊黃山,在山腳下一青年工房看到一片歙硯,黑色,沒有雕琢。
粗粗一塊手掌心大的石片,稍經磨平,還留有石紋肌理,一端設一淺淺水盂。我喜歡這樣沒有雕飾的硯,仿佛隨時迴到溪澗,還是一塊石頭,等待溪水迴蕩。
製作的青年石工也喜歡,交給我時說:很輕,可以帶在路上用。沒有想到有一天我真的帶在路上用瞭。
通常,到一城市,進旅館房間,習慣先燒一截艾草。焚香,坐下來,在硯石上滴水,磨墨,開始抄一段經。抄完經,會覺得原來陌生的房間不陌生瞭,原來無關的地方,空間、時間都有瞭緣分。像桌上那一方石硯,原來在溪澗裏,卻也隨我去瞭天涯海角。
清邁屏河邊有一小民宿,流水湯湯,一屋子都是婆娑樹影,很寬大的露颱。麵對著河,大花紫薇和金急雨搖晃迷離,如天花亂墜,我就在花影中抄經。
無明
二〇一四年年初,因為畫展,聯絡一位許久不見的朋友。我找她幫忙,不巧接到電話時,她剛從醫院齣來,剛被醫師宣布眼疾,瀕臨失明,要動一個危險性極高的手術。電話另一端,她的聲音喘息無助,旁邊都是車子喇叭聲。我知道此時無論怎麼安慰,說多少次“不驚、不怖、不畏”,其實都無濟於事。
那幾天晨起誦經,心裏就想,或許可以順便錄音,給這位有失去視覺恐懼的朋友聽。如果失去視覺,我們還可以聽吧。
我找雲門郭遠仙,他是弄大舞颱的,替我在傢裏裝設簡便錄音器材,我可以自己操作。如此就連著幾天,錄瞭五六個清晨的讀誦,交給有鹿文化的朋友剪輯整理。
我當時擔心我的聲音不夠清明安靜,想到京都永觀堂的鍾聲,曾經遠遠傳來,讓我在吵鬧街頭匆忙間忽然停下來,仿佛心裏有聲音呼喚,可以暫時放下身邊許多“捨不得”的焦慮。也剛好悔之有日本友人熱心,就幫忙錄瞭永觀堂鍾聲來,剪輯進去。聽的時候,有一聲聲的鍾聲迴蕩,提醒我“捨得——”“捨得——”。
《金剛經》錄好,原要把原聲帶交一份給為失明恐懼的朋友,她卻說,手術意外成功,奇跡似的好瞭。我想,有這奇特因緣,心中有祈願,也就發行,普施給需要的人吧。
《金剛經》抄寫、讀誦,都有我不知道的因緣。
有鹿文化的煜幃費心幫忙很多,他去法鼓山找師父查證,我讀誦的《金剛經》是古高麗版本。
“啊,是嗎?高麗版本?”
我纔想起,是啊,那一冊黑色封麵古樸木刻刊印的《金剛經》,是多年前郝明義所贈,他與韓國是有淵源的。
我每次讀到刊刻人的名字崔瑀,有上將軍、上柱國的爵位,封晉陽侯,卻沒有細想,原來是相當中國南宋末、元初的高麗史上重要的權臣。
查瞭一下資料,崔瑀似乎無數,在政治鬥爭裏,他連手足親人也不放過。然而刊刻《金剛經》發願,他的願望是“破諸有相,共識真空”。
我讀《金剛經》,抄《金剛經》,漫漫長途,有多人護持,可知或不可知,都讓我一路走來,時時省思因果。
含笑
一路校稿,仿佛又再一次去瞭清邁無夢寺,再一次去瞭鞦天楓林迷離璀璨的永觀堂。
然而這次是草津瞭,在一大片落羽杉林間徘徊,即將白露,樹木梢頭、草叢間,都一片銀光迷濛,細看是針尖大的露珠,連成一片,讓我想到“白露為霜”的句子。但日齣之後,處暑艷陽,白露也就一一消逝瞭。
許多詩句也都是季節的不捨吧,捨得,捨不得。
從草津迴東京,隻在上野停一晚,一清早到法隆寺寶物館看思維菩薩,看金銅敲鍛鏤空的頂幡,看瞭多次,還是捨不得。
上野美術館正舉辦颱北“故宮”的國寶展,貼在大門口的海報,有汝窯溫酒的蓮花碗,有《寒食帖》。我相望一笑,想到四十年前跟莊嚴老師上課,可以一下午隻看這一件書法,隻看這一隻碗,好;但也覺得:看過瞭,也都可以捨得。
走進東洋館,展示櫃裏一捲《瀟湘臥遊圖捲》,這是近代跟《寒食帖》一起流到日本的南宋名作,當時歸菊池惺堂收藏。
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菊池在危難中從火場搶齣兩捲書畫,一是《寒食帖》,另一件就是《瀟湘臥遊圖捲》。
《寒食帖》後來迴歸颱北“故宮”,《瀟湘臥遊圖捲》留在日本,被定為國寶。
這是近代書畫史上的傳奇故事。這次《寒食帖》從颱北去東京展齣,被定為國寶的《瀟湘臥遊圖捲》也因此展齣,仿佛它們緣分未瞭,也是對惺堂先生捨命傳奇的紀念吧。
整個展場沒有太多人。我在《瀟湘臥遊圖捲》前徘徊流連,想到《金剛經》的句子:“不可思議”。山水可以如此無礙,虛實牽連不斷;墨色可以如此淡如煙嵐,若有若無;留白可以如此潔淨空明,不著痕跡。小如孑蟻的人,小如粟米的房捨,細如發絲的一綫橋梁,我一一看過,也隨看隨忘,仿佛沒有看過。還是《金剛經》說的:“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
惺堂先生當年捨命搶救的一捲畫作,就在麵前瞭。次與這件名作相見,許多老師當年的敘述講解都忘瞭,許多看過的資料考證都忘瞭,許多高畫素的精細局部復製都忘瞭。原來《瀟湘臥遊》可以好到忘瞭一切瑣碎,不可考證,不可復製,就隻有一捲,是要這樣素麵相見。
沒有捨得,沒有捨不得。
走齣美術館,寬永寺的鍾聲響起,不忍池裏夏末荷花搖曳,花瓣張開,露齣巨碩蓮蓬,一粒一粒蓮子掉落池中,下一個春末還會生根抽芽吧。
高大銀杏樹叢裏有寒蟬淒切的聲音。高亢的嘶叫,到瞭尾音,總是哀婉如泣如訴,聲音拖得長長的,那麼多不捨,那麼多捨不得。
迴颱北之後,已過中鞦,還是炎熱。
我走到知本,樂山旁有清覺寺,大殿楹聯還是源自《金剛經》的句子:
清淨即菩提,須知菩提本來淨
覺心原無住,應從無住更生心
清晨禮佛畢,在庭院散步。中庭有幾株高大含笑,都有近百年樹齡。日齣前後,含笑都還含苞,廟中老師父手持長竿,在濃密樹叢間找花。她年歲太高,眼睛不好,我就指給她看,“這裏——”“那裏——”,她把含笑一一帶枝葉鈎下,用盤盛裝,供在佛前。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蔣勛於颱東知本清覺寺
用户评价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