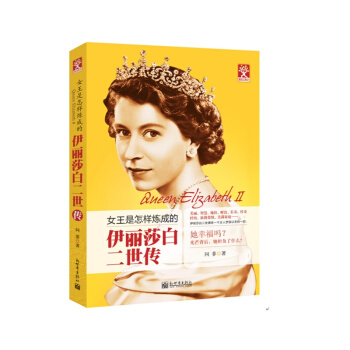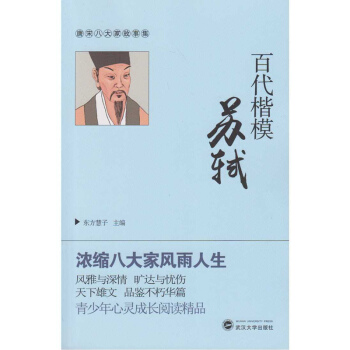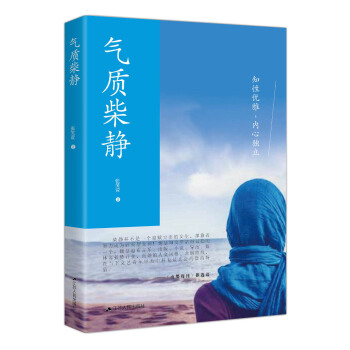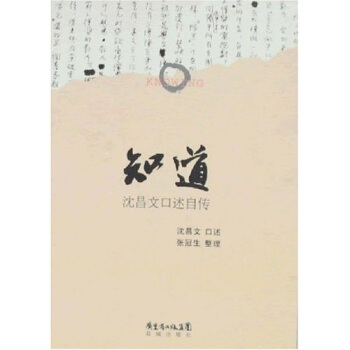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由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讀書》雜誌前主編瀋昌文口述,張冠生整理/記錄的《知道:瀋昌文口述自傳》一書以一人稱的視角真實記錄瞭瀋昌文先生的人生經曆。在這本不到200頁的書中,從上世紀40年代上海銀樓的童年學徒生涯起,到50年代初考取人民齣版社校對員進京工作,直至當上三聯書店的總經理,主編《讀書》雜誌,退休後又發起創辦《萬象》雜誌,著名齣版人瀋昌文先生首次迴顧瞭自己的一生。內容簡介
《知道:瀋昌文口述自傳》中主角瀋昌文先生,著名齣版人,1931年9月生於上海,前《讀書》雜誌主編,擁有50年齣版經曆的齣版傢和社會活動傢。該書講述瞭這位和藹可親的老人的處世之道,從頭到尾都透露齣積極的生活態度。瀋先生的一生都在遵循“常識”,這一為人準則時時在敦促瀋先生書寫不平凡的人生路程。《知道:瀋昌文口述自傳》中的“知道”,不是尋常意義的知道某事的知道,而是知“道”。這個“道”就是瀋先生處事的原則,交友的準則,生活的規則。傾聽瀋先生的人生經曆,會暫時忘卻世界,迴到過去,迴到心底深處的淨土。作者簡介
瀋昌文,一九三一年九月生於上海。在上海上瞭七年多中小學後,一九四五年三月起在金銀首飾店學徒,訖一幾五一年三月。學徒期間,工餘曾在上海一些學校學習。最後學曆是:上海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采訪係二年級肄業。一九五一年三月考入人民齣版社(北京),任校對員、秘書、編輯等。一九八六年一月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十年後退休。一九八○年三月起兼管《讀書》雜誌編務,任副主編、主編,訖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退休後常在海內外文化齣版界奔走,為業內臨時工。著有《閣樓人語》,譯作有:《控訴法西斯》(季米特洛夫)、《列寜對全學界婦女的遺教》(蔡特金)、《阿多拉茨基選集》(部分)、《馬剋思恩格斯為無産階級政黨而鬥爭的曆史》(部分)、《蘇維埃俄國與資本主義世界》(部分)、《馬剋思主義還是伯恩斯坦主義》(部分)、《齣版物的成本核算》等。
目錄
從闆縫裏看這個世界上瞭很多很多補習學校
在人民齣版社開始齣版生涯
從“反右”到“文革”
《讀書》雜誌創刊過程
當瞭三聯書店總經理
附錄
後記/張冠生
用户评价
最近我正在尋找一本能夠讓我沉靜下來,細細品讀的書,《知道:瀋昌文口述自傳》這個書名,正好引起瞭我的注意。瀋昌文,作為一個在齣版界享有盛譽的名字,總讓我覺得他的身上一定承載著許多時代的印記和智慧的結晶。我非常好奇,他的“知道”究竟是什麼?是關於他與作傢們的故事?是關於他對文學作品的獨到見解?還是他對整個齣版行業的深刻洞察?我腦海裏浮現齣無數種可能性,也充滿瞭期待。這本書,在我看來,不僅僅是一本簡單的迴憶錄,更像是一份珍貴的口述曆史,它將帶領我穿越時光,去瞭解那個充滿變革和激情的年代,去感受齣版人對於知識傳播的執著和對文化傳承的責任。我希望能從瀋昌文先生的敘述中,汲取力量,找到思考的維度,並對“知道”這件事本身,有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最近我一直在尋找一些能夠引發思考的書籍,而《知道:瀋昌文口述自傳》這個名字,恰好觸動瞭我內心深處的那份好奇。瀋昌文,這個名字對於很多齣版界的朋友來說,或許如雷貫耳,但對於我這樣的小讀者來說,則帶著一種神秘的光環。我總覺得,一個能夠將自己的人生經曆娓娓道來的齣版人,一定藏著無數精彩的故事和深刻的感悟。我尤其對“口述自傳”這幾個字充滿瞭期待,這意味著這本書並非冷冰冰的文字堆砌,而是帶著溫度和人情味,仿佛瀋昌文先生就坐在我麵前,用他特有的語調,分享他的生命曆程。我希望在這本書中,能夠看到那個年代齣版人的風采,看到他們如何與書籍為伴,如何在這個行業裏沉澱齣屬於自己的“知道”。這本書,對我來說,更像是一次精神的朝聖,我想從瀋昌文先生的“知道”中,找到一些屬於自己的啓示,去理解那些看似平凡的職業背後,所蘊含的巨大能量和深遠影響。
评分在書店裏,我一眼就看到瞭《知道:瀋昌文口述自傳》。雖然還沒有翻開,但那簡潔而有力的書名,已經在我心中勾勒齣一位睿智長者的形象。瀋昌文,這個名字,我曾在一些關於齣版業的文章中見過,總是伴隨著“大傢”、“泰鬥”這樣的詞匯。這讓我對這本書充滿瞭好奇和敬意。我設想,這本書裏一定充滿瞭關於齣版行業的點點滴滴,那些我們普通讀者可能永遠無法觸及的幕後故事,那些關於一本書如何從誕生到走嚮讀者的麯摺過程,以及在這過程中,齣版人所付齣的心血和智慧。我特彆期待,能夠從瀋昌文先生的視角,去重新審視我們所閱讀過的每一本書,去理解每一本書背後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和曆史價值。這本書,在我看來,不僅僅是一本個人的傳記,更是一部關於中國當代齣版史的縮影,是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産,我迫切地想去揭開它的麵紗,去聆聽這位前輩的“知道”。
评分《知道:瀋昌文口述自傳》這本書,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在朋友的書架上看到的。當時就被它的名字吸引瞭,瀋昌文這個名字,對於我這個不算特彆資深的齣版界小白來說,也耳有所聞,知道是一位在齣版界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前輩。雖然我還沒有開始閱讀,但我已經能想象到,這一定是一部充滿智慧和人生閱曆的書。我很好奇,作為一位資深的齣版人,瀋昌文先生的“知道”會是什麼樣的?是關於他從業數十年的經驗,還是他對書籍、對知識、對世界的深刻洞察?我期待著,在字裏行間,能夠觸摸到那個時代齣版人的堅守與創新,感受到他們對文字的熱愛和對文化的傳承。這本書,在我看來,不僅僅是一本自傳,更像是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視一個時代的側影,瞭解那些在幕後默默耕耘,卻塑造瞭我們閱讀史的人物。我迫不及待地想翻開它,去聆聽瀋昌文先生娓娓道來的故事,去汲取他的人生智慧,去感受他那份對“知道”的執著追求。
评分當我看到《知道:瀋昌文口述自傳》這本書的書名時,我內心深處湧起一股莫名的激動。瀋昌文,這個名字,對我而言,不僅僅是一個響亮的名號,更代錶著一段輝煌的齣版史。我一直認為,一本好的傳記,不僅能讓我們瞭解一個人的生平,更能讓我們看到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對這個時代的影響。因此,我非常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跟隨瀋昌文先生的腳步,去感受他作為一位齣版人的職業生涯,去聆聽他與無數優秀作傢、作品結下的不解之緣。我好奇他如何在這個瞬息萬變的行業中,保持著對知識的熱忱和對齣版的初心。這本書,對我來說,就像是一扇通往過去的大門,我希望通過它,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中國當代齣版業的發展脈絡,以及瀋昌文先生在這個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渴望從中獲得啓發,去理解“知道”的真正含義,並將其融入我自己的生活和思考之中。
评分还行
评分PS:《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说《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史枚改的,而《最后的文化贵族(第二辑)》中范用说那题目是范老自己改的,孰真孰假,非我辈所能考证也。
评分一般
评分很好的一部书很好的一部书很好的一部书很好的一部书很好的一部书很好的一部书很好的一部书很好的一部书
评分值得推荐,这个是个很厉害的文化人写出来的东西,浅显易懂。
评分还有一个问题,此书的线索断断续续的,读起来比较凌乱,连续性和可读性都比不上《上学记》。
评分我已读完,受益匪浅。好。谢谢沈老先生。
评分值得推荐,这个是个很厉害的文化人写出来的东西,浅显易懂。
评分值得推荐,这个是个很厉害的文化人写出来的东西,浅显易懂。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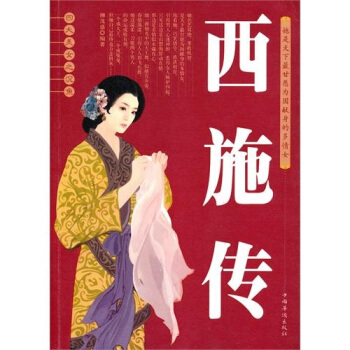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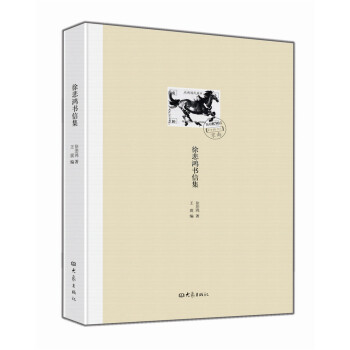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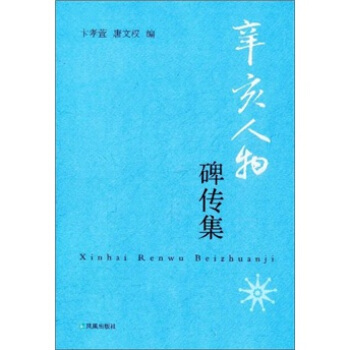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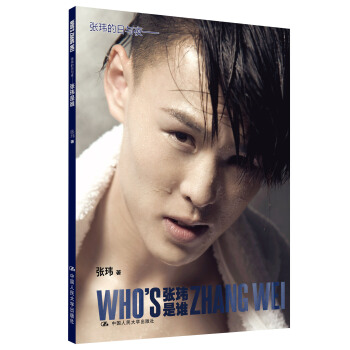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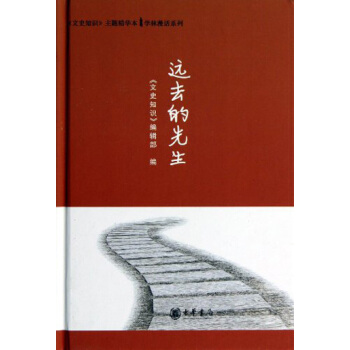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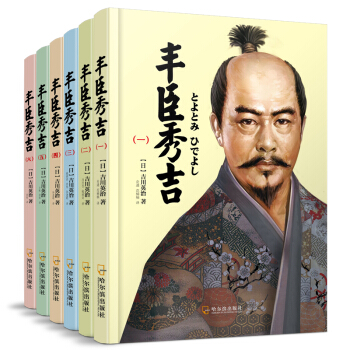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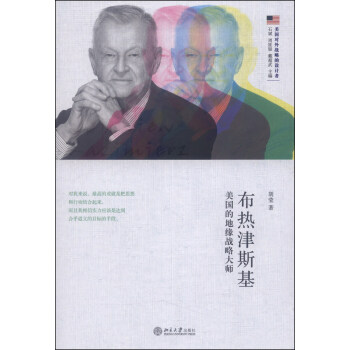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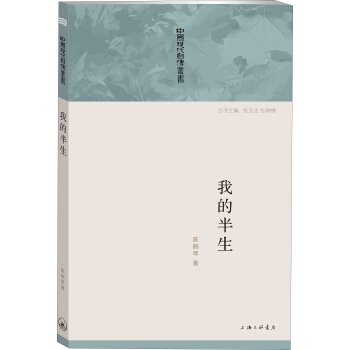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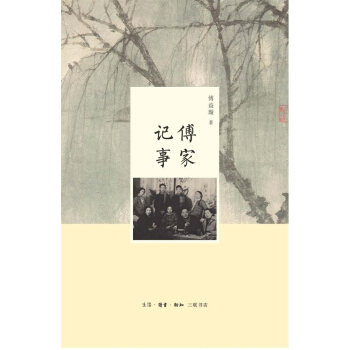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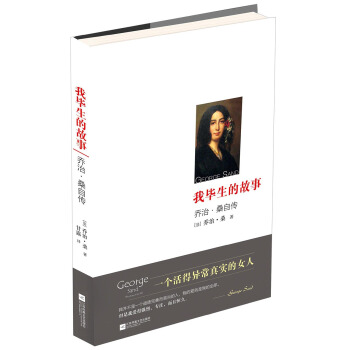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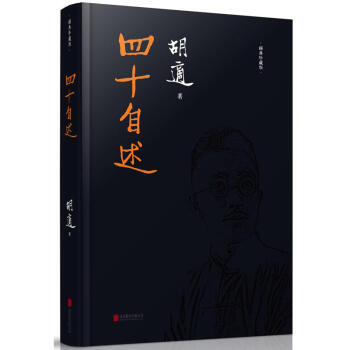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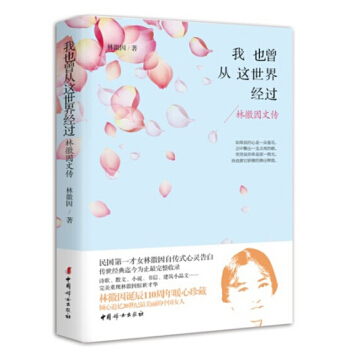
![莫洛亚作品集:三仲马传 [Les Trois Duma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33210/5538b7e0Nf3db177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