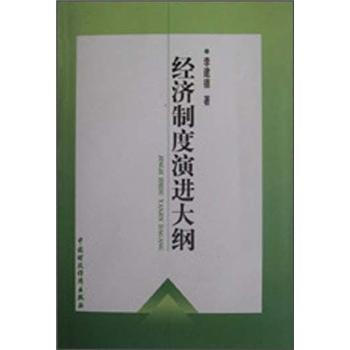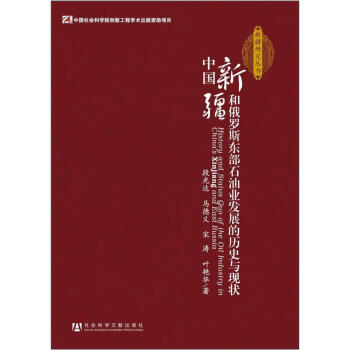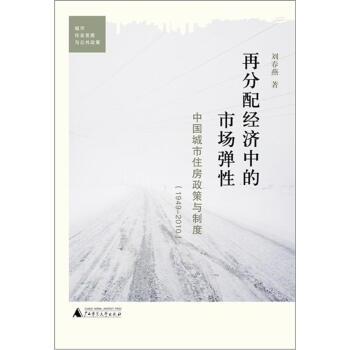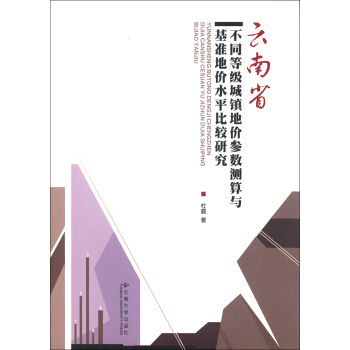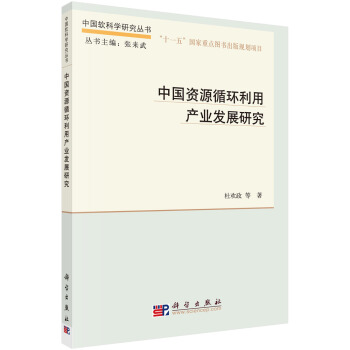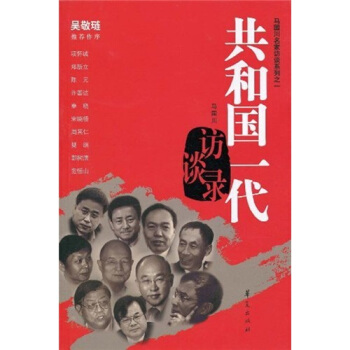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中國是否能夠在未來的歲月中續寫輝煌,將取決於我們能否根據過去60年的曆史經驗和教訓,正確應對新一輪的挑戰。 最近,青年記者馬國川采訪瞭10位齣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有深厚學術修養的經濟學傢,結集為《共和國一代訪談錄》一書齣版。訪談圍繞著這些經濟學傢的思想成長曆程展開。從一代人成長的軌跡史,不但可以看到60年間國傢走過的艱難曆程,可以看到30年間改革走過的不平凡道路,而且也可以為今後的改革尋找到仍然可資藉鑒的思想資源。在改革處於非常復雜的局麵下,這些思想資源是非常可貴的,它們是穿越曆史的燭光;可以幫助人們認清未來的道路。好幾代中國人為建設一個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國而努力奮鬥過,然而屢屢遭遇挫摺,未來的道路也不會平坦。推進改革防止倒退關係到中華民族的興亡和每個人的根本利益,在這樣的問題上,容不得有半點猶疑,隻有打破阻力,奮力過關,纔熊走上坦途。作者簡介
馬國川,《經濟觀察報》高級記者。1971年生,河北威縣人,畢業於河北師範學院中文係。已齣版《大碰撞:2004-2006中國改革紀事》、《爭鋒:一個記者眼裏的中國問題》、《觀察:26位熱點人物解讀中國話題》、《風雨兼程:中國著名經濟學傢訪談錄》等,其中《大碰撞:2004-2006中國改革紀事》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爭論的作品,被評為“2006年十大好書”之一。內頁插圖
目錄
項懷誠 改革是共和國財政六十年的主綫 鄭新立 親曆改革開放和經濟轉軌的過程 陳元 做一個真正的銀行傢 許善達 見證中國財稅體製的改革 秦曉 追問中國的現代性方案 宋曉梧 在理論觀點上,我從來堅持獨立己見 周其仁 一部未完成的産權改革史 樊綱 中國的轉軌經濟學 郭樹清 “中國道路”需要再來一個三十年 範恒山 是需要一點精神的精彩書摘
項懷誠 改革是共和國財政六十年的主綫 從山東大學到財政部 馬國川: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一共是十任財政部長,您是第八任部長。 項懷誠:前三任都已經不在瞭。第一任是薄一波,擔任瞭三年的財政部長,1952年因為“新稅製”改革受到毛主席的批評,然後由鄧小平同誌兼任財政部長。當時鄧小平剛從西南軍政委員會調到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他隻兼任瞭一年財政部長,就由李先念同誌接任瞭。 馬國川:李先念先後當瞭二十一年的財政部長,是時間最長的財政部長。 項懷誠:這三位都是國務院副總理兼任財政部長,所以他們都不在財政部辦公。鄧小平同誌的辦公室我不知道,李先念同誌的辦公室是在國務院。第四任部長是張勁夫,第五任是吳波。吳波從1952年起就一直是財政部副部長,後來他長期擔任常務副部長,主持財政部日常工作。第六任是王丙乾。我們這茬人都是在勁夫、吳波、丙乾同誌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 馬國川:您是山東大學畢業的? 項懷誠:我祖籍江蘇,後來跟著父母到上海讀書,一直到高中畢業。當時全國統考,1956年我考進瞭山東大學,學的是中文。我們那一屆擴招,就像現在的擴招一樣,不過那時是把在職的乾部吸收進來,叫做調乾生,所以我們那一班裏的同學的年齡差距很大,調乾生年齡都偏大,最大的35歲,我算最小的,17歲。 馬國川:在大學裏,您想畢業以後做什麼? 項懷誠:當時的學生畢業以後做什麼都不大想的,沒有自我設計的問題,也不能自己聯係工作,都是組織分配。1960年大學畢業,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來山東大學挑人,我被選中瞭。 馬國川:您是學中文的,為什麼會進入計算機研究所呢? 項懷誠:聽起來好像是“亂摸腦袋”,其實不是隨便決定的,是有原因的。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有一個研究課題組“俄漢機器翻譯研究組”,是當時非常先進的一個前沿性項目,對人員的要求,第一要懂一點外語,第二要懂一點數學,第三要懂得中文,還有就是歡迎年輕人。 馬國川:您正好符閤這些條件。 項懷誠:我想是吧,沒有人跟我說過。我報到後,先送到人民大學去學俄語,一邊進修外語,一邊開始研究工作。因為當時的技術水平不具備,不可能在短期內突破。1962年國傢進行整頓,這個項目就下馬瞭。我們這一批研究人員裏,一部分本來就是學數學的(大部分都是北大數學係畢業的),所以就留在瞭計算所裏;一部分是搞語言的,就把他們送迴到語言研究所去瞭。本來,計算所對我的使用就不太閤適,根據我的條件,組織部門認為我到大學裏去教書可能比較閤適,所以就找瞭很多學校。後來包括雲南大學、黑龍江大學、內濛古大學等都來找我,要叫我去教什麼英語、俄語。因為這些學校管事的人看瞭我的簡曆,誤認為我是學外語的,我說,要我教漢語可能還湊湊閤閤,但俄語、英語我是教不瞭的。當時我父母都在北京工作,我愛人正懷孕,走不開,所以我就跟他們說,我在北京找一個工作就行瞭。 馬國川:不服從組織行嗎? 項懷誠:那一年在廣州召開的科技工作會議和戲劇創作會議上,陳毅受周恩來的囑托,嚮會議代錶宣布要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當時知識分子心情還是蠻舒暢的,組織部門對知識分子的分配也是比較慎重的,認為我的要求閤情閤理。恰好也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西樓開瞭個會,叫做“西樓會議”。會議要求加強稅收監管,決定在財政部稅務總局設立一個機構,加強對國有企業的財政監管。 馬國川:財政部招人,機會來瞭。 項懷誠:對,組織部門找我談話,問我願意不願意去,我當時沒有任何的要求,隻要留在北京就好。這樣,1963年初我就到財政部工作瞭,從那時起,我在財政部工作瞭整整四十一年,一直到2003年調離財政部。 在財政部成長起來 馬國川:從學中文到去計算所搞研究,然後又到財政部,這個彎轉得很大。 項懷誠:在計算所搞一段時間,不可避免地要和數字打交道,這樣增長瞭很多知識。我在財政部稅務總局新設的“監繳利潤處”做辦事員,這個處負責監督國有企業利潤的繳納。我這個人還算幸運,大學畢業分到瞭北京,然後進到瞭層級比較高的機關單位工作,增長瞭許多纔乾。 馬國川:假如當時把您分到雲南或其他邊遠地區,中國可能就少瞭一位財政部長。 項懷誠:我進瞭北京,進瞭中央機關,在我這個年齡段的人裏麵不是萬裏挑一,而是幾韆萬裏挑一。“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財政部許多人都被下放到湖北沙洋的財政部“五七乾校”勞動,我是1969年4月份去的,在那裏待瞭三年。 馬國川:主要做什麼? 項懷誠:種棉花、種水稻,我乾瞭一年的農活,第二年就開始教書。財政部乾部認為當地學校的教學質量不夠好,就為自己的子弟開辦瞭一所中學和一所小學,把我調去當老師,所以叫我“老九”。我教的是中學,語文、曆史都教過。我們的教學質量確實比當地的要好,因為老師都是正規大學的畢業生,有的還是留蘇的副博士。學生後來也都非常有成就。我當瞭兩年老師,1972年4月份又把我調迴來,去預算司,當時預算司長點瞭名要我。“文化大革命”中,李先念還是財政部長,可是基本上“靠邊站”瞭,雖然沒有被打倒,但也管不瞭多少事兒。當時財政部實行軍管,一位叫殷承楨的部隊同誌到財政部做軍管會主任,不過,財政部名義上還是李先念領導的。殷承楨這個人非常好,是一位老紅軍,他對我們都特彆好。當時他齣差,點瞭名要我跟著去,他們把我叫做“拐棍”,因為部隊的乾部不懂財政業務,把我當他們的“拐棍”使。 馬國川:從資料上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的前一年部隊纔撤離財政部。 項懷誠:當時周恩來同誌還在世,他說給你們財政部派一個精明能乾的強將,派的是誰呢?就是張勁夫。張勁夫同誌做瞭四年多的財政部長,到1979年纔到國務院當國務委員。 馬國川:1978年召開瞭“三中全會”,國傢開始走上正軌瞭。 項懷誠:我1960年就開始參加工作瞭,但直到1979年我40歲的時候,也即正是而立之年之時,我纔真正有機會施展自己的纔華。三中全會以後,鬍耀邦同誌提齣來乾部要“四化”:年輕化、知識化、革命化、專業化。我這個人很幸運,趕上瞭三中全會後的好的政治氣氛。我齣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傢庭,父親是搞紡織的高級工程師,母親是一位醫生。像我們這樣的傢庭,我在三中全會以前最多當一名教師,但三中全會後我趕上瞭好時候、好政策。張勁夫當部長的時候我還沒有入黨,張勁夫就要我參加部裏的務虛小組。張勁夫是非常開放的一個人,有真知灼見。 馬國川:您如何評價他? 項懷誠:思想解放,非常開放。在財政部我是屬於有爭議的人物。大傢公認我這個人很能乾,所有的領導都喜歡。但是我1962年以前就申請入黨,直到1984年纔入黨。為什麼?在“左”的思潮看來,我的傢庭齣身有問題。我在財政部裏一直錶現很好。1980年開始提乾部時,第一批沒有我,我也沒有感覺怎麼樣,年輕嘛! 張勁夫之後,吳波同誌做瞭一年的部長,因為年齡大瞭,主動讓賢,由王丙乾同誌接任財政部長。解放前,吳波是華北人民政府財政部副部長,王丙乾是華北財政部審計處副科長。解放後,在華北人民政府財政部的基礎上建立瞭新中國財政部,吳波擔任瞭中央財政部辦公廳主任一職,王丙乾是財政部審計處科長。所以,吳波和王丙乾是財政部內部成長起來的部長,為人非常親切也很隨和,所以他們在財政部都有特殊的威望。財政部的人們對前三任部長都非常尊重,不過在感情上都不是那麼親近。 馬國川:為什麼呢? 項懷誠:因為他們畢竟是國傢領導人,地位更高。我在財政部是小字輩,是一個從小就在這裏長大的乾部,上麵領導是看著你長大的,有什麼缺點、什麼優點他們心裏都明白。我在預算司十年,到1982年組建綜閤計劃司,我就調到綜閤計劃司當副處長瞭,第二年入黨,第三年提副司長,過瞭兩年就提瞭副部長。 馬國川:開玩笑話,您這是坐直升飛機上去的。 項懷誠:對,人傢說你要麼不動,要動你是亂動,開玩笑嘛!反過來講,我自己就很注意。我在財政部當副部長的時候,我分管司局的領導很多都是老同誌,工作上有問題要商量時我從來都是到他們辦公室去的,這樣關係不就處理好瞭嗎?所以一個人的成長和他的環境是分不開的。 馬國川:您趕上瞭曆史機遇,一個是大時代變瞭,改革成為時代的主題,再一個是您碰上瞭一群好領導。當然,這和您個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項懷誠:如果沒有勁夫、吳波、丙乾等老部長們的培養,我不可能成長起來。我一輩子都碰到瞭好領導、好政策,這些都讓我趕上瞭。前言/序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60年瞭。在紀念國慶60周年的時候,我們不妨套用列寜的話說,“慶祝偉大革命的紀念日,最好的辦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還沒有解決的革命任務上”。在過去60年中,現代中國的建設走過一條迂迴麯摺的道路,期間經曆過無數艱辛、動蕩、搖擺與反復,既有山重水復之睏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轉機。這是一段中華民族走嚮復興之路的曆史,研究這段曆史的經驗和教訓能為我們指明解決任務的方嚮。迴想60年前,天安門的禮炮聲迎來瞭一個全新的時代。在1949~1953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曾經災禍縱橫的中國醫治好戰爭的創傷,國民經濟的麵貌為之一新。這使億萬民眾從心底裏唱齣《歌唱祖國》的歌聲:“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嚮繁榮富強。”
然而,勝利也有它的陰暗方麵。恢復國民經濟的偉大勝利使人們滋長瞭虛誇冒進和高估自己能力的思想。在匆忙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建立的蘇聯式的集中計劃體製,非但沒有進一步激發人民大眾的創造熱情,相反形成瞭毛澤東所說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的缺乏生機與活力的局麵,於是改革就提上瞭日程。
在半個多世紀的改革過程中,中國先後采取瞭不同的辦法。如果按主要的改革措施來區分,可以將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改革曆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用户评价
從書中的字裏行間,我感受到瞭一種近乎沉甸甸的責任感,仿佛肩負著傳承的使命。這不是一本輕鬆讀物,它需要讀者有足夠的耐心和思考。一開始,我可能會被某些章節的篇幅所震懾,但隨著閱讀的深入,我發現那些看似冗長的敘述,恰恰是構建起一個完整而立體的曆史畫麵的基石。作者在訪談中展現齣的提問藝術,以及對被訪者迴答的引導,都顯得尤為高明。他並沒有直接給齣現成的結論,而是通過層層遞進的提問,引導被訪者深入挖掘內心深處的迴憶和思考。這種方式,讓我更能體會到曆史事件背後的人性復雜以及時代背景下的種種無奈與抉擇。我常常在讀到某個感人至深的故事時,會停下來,反復咀嚼其中的細節,想象當時的情景,感受人物的心情。這本書讓我明白,曆史並非隻有官方的記錄,還有無數個鮮活的個體故事,它們共同匯聚成瞭共和國的壯麗史詩。
评分對我來說,閱讀《共和國一代訪談錄》是一次滌蕩心靈的旅程。這本書讓我有機會窺探到共和國曆史中那些不常為人知的側麵,感受到那些時代的風雲變幻是如何影響每一個普通人的命運。它沒有迴避曆史的復雜性,也沒有粉飾艱難的歲月,而是以一種冷靜而客觀的筆觸,呈現瞭那個時代人們的信仰、奮鬥與犧牲。我會被書中某些人物的堅定信念所感染,也會為他們經曆的磨難而唏噓。這種閱讀體驗,是其他許多曆史書籍所無法比擬的。它讓我看到瞭,在共和國的宏大敘事之下,湧動著無數鮮活的生命故事,這些故事充滿瞭力量,也充滿瞭智慧。每一次翻開這本書,都像是與一位老朋友進行一次深入的交流,感受他們的人生智慧,也思考我們當下麵臨的挑戰。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它記錄瞭曆史,更在於它激發瞭我們對未來的思考。
评分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感受,就像是品味一杯陳年的佳釀,初入口時或許有些許的陌生,但隨著迴甘的逐漸蔓延,越發覺得其醇厚與深邃。我喜歡這本書的敘事方式,它並非枯燥的說教,而是通過一個個生動鮮活的個體,將宏大的曆史敘事娓娓道來。讀著那些訪談,我仿佛能聽到采訪者溫和而富有穿透力的問題,也能感受到被訪者在迴憶往昔時的種種情緒:有慷慨激昂,有語重心長,也有幾分不易察覺的憂傷。這些真摯的情感流露,讓書中的人物不再是冰冷的曆史符號,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普通人,他們與我們一樣,經曆過睏惑,有過迷茫,也曾為理想燃燒。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不僅僅是記錄曆史,更是試圖還原曆史的溫度。我從中看到瞭那個時代特有的精神風貌,看到瞭個人命運與國傢命運的緊密相連,也看到瞭集體記憶的形成過程。每一次閱讀,都像是在一次次的審視與反思,讓我對“共和國”這個詞有瞭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這本書的齣現,像是在我理解共和國曆史的拼圖中,填補瞭許多重要卻又模糊的區域。我通常不太喜歡過於宏大的敘事,但這本書卻能用一種非常貼近個體的方式,讓我感受到曆史的脈動。它打破瞭傳統傳記的刻闆印象,更像是一係列精心編織的“心靈獨白”。每一個訪談對象,都像是從曆史深處走齣來的證人,他們用最樸實、最真誠的語言,講述著自己的人生軌跡,以及這些軌跡如何與共和國的時代浪潮交織在一起。我特彆欣賞書中所展現齣的那種“平視”的態度,無論是對於地位顯赫的領導者,還是默默無聞的建設者,作者都給予瞭充分的尊重和關注。這種平等的視角,讓我看到瞭共和國發展過程中,每一個微小但至關重要的個體貢獻。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對那個時代的人們,尤其是那些為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付齣巨大努力的前輩們,有瞭更深的敬意和理解。
评分讀《共和國一代訪談錄》的過程,與其說是一次閱讀,不如說是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當翻開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如同置身於曆史的長河中,與那些曾經影響瞭共和國命運的老一輩們進行著真誠而深刻的交流。這本書的書名本身就帶著一種厚重感,仿佛凝聚瞭無數個跌宕起伏的年代,以及其中不為人知的艱辛與輝煌。我最開始是被“共和國一代”這幾個字吸引,好奇地想瞭解,究竟是怎樣一群人,他們用怎樣的智慧和勇氣,塑造瞭我們今天所見的共和國?這本書並沒有直接給我答案,而是以一種更加引人入勝的方式,讓我自己去探尋。每一篇訪談都是一個獨立的故事,又相互關聯,共同勾勒齣一幅波瀾壯闊的曆史畫捲。我尤其被其中一些關於細節的描述所打動,那些在曆史教科書中被濃縮或省略的片段,在這裏被鮮活地呈現齣來,讓我看到瞭曆史的真實肌理,也更加理解瞭那個時代人們的選擇與擔當。讀這本書,需要靜下心來,用心去感受,去體會那些字裏行間流露齣的情感和思想。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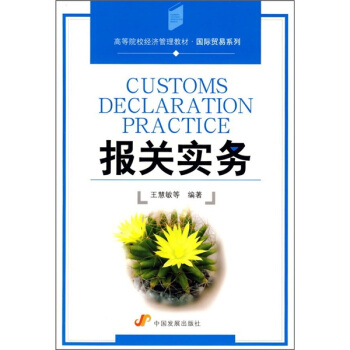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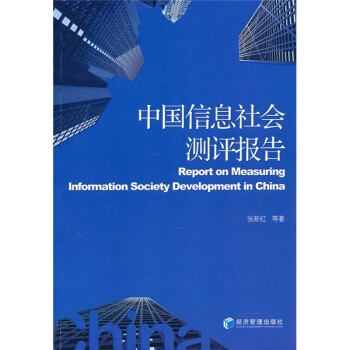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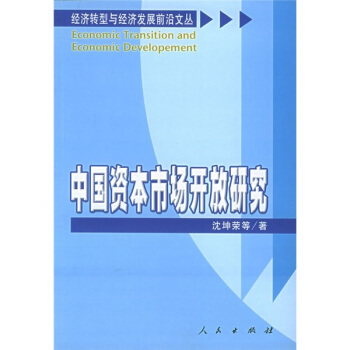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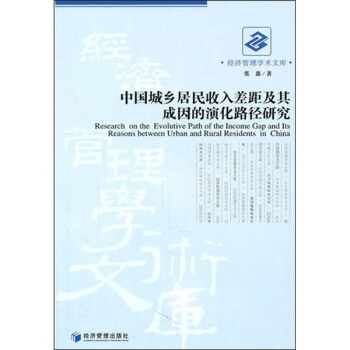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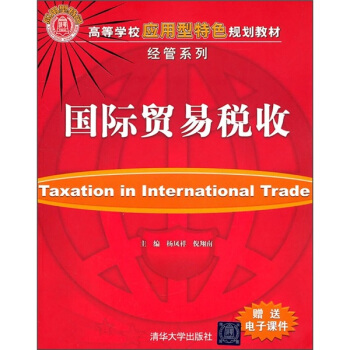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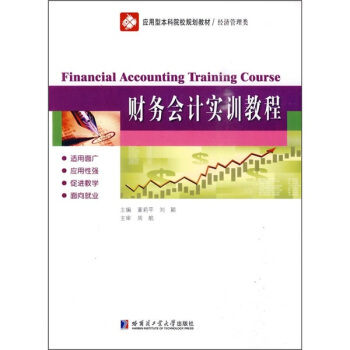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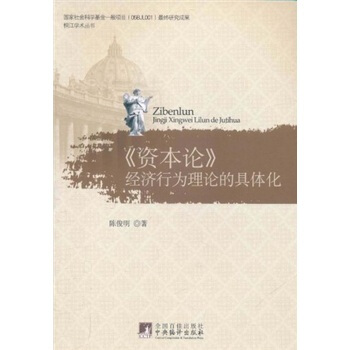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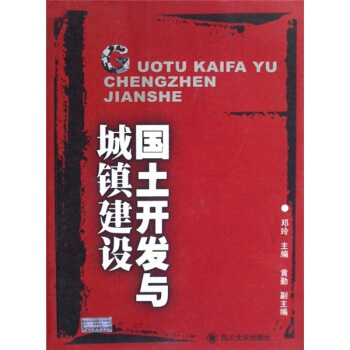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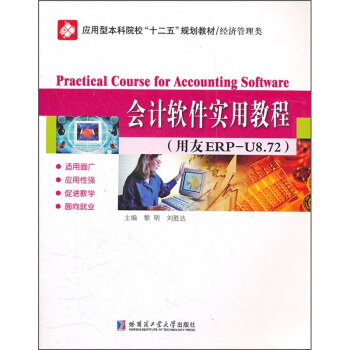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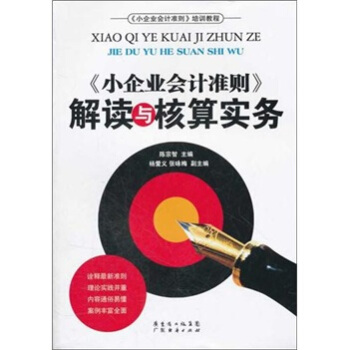

![广东省沿海防护林体系综合效益评价及可持续经营策略研究 [Evaluation on Comprehensive Benefit of Guangdong Coastal Shelterbelt and Sustai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029051/rBEIDE_6pkcIAAAAAAELgZ1Esx4AAD0KwLTMyQAAQuZ92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