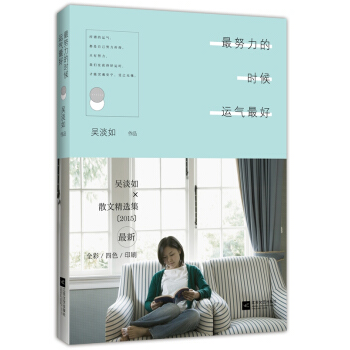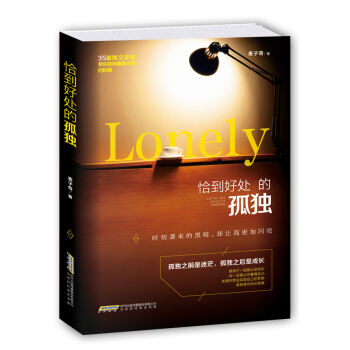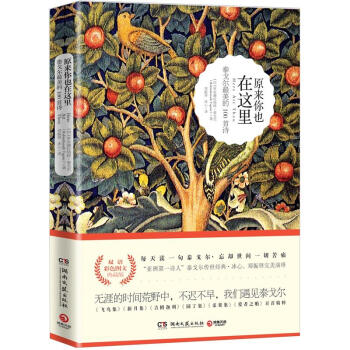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他是現代刑事人類學開創者、真實世界的死亡翻譯人他是世界的“人體農場”場主
沒有他,《CSI犯罪現場》隻剩一半精彩
他是暢銷推理小說《首席女法醫》作者的寫作顧問
他是國際刑事鑒識李昌鈺博士深交30年好友
他在死亡現場,細聽生命最後一刻的低語
內容簡介
跨越半個世紀的鑒識生涯中,巴斯跨齣瞭人體農場大門,上山下海來到每一處發現屍體的現場。他在這本饒富興味的著作當中,探究真實案例,帶領讀者踏上前所未見的旅程,一步步引導讀者進入真實的CSI世界,解決警察也束手無策的問題,諸如:·十六歲的混血兒少女卡西·西山失蹤瞭,這是她的顱骨嗎?
·非法煙火工廠爆炸瞭,要怎麼把這些軀乾、手、腳拼起來,還原他們各自的身分?
·蒼蠅的嗡嗡聲並非背景噪音,不可隨便拍打驅逐:嗡嗡聲本身就是故事,或至少是一段重要情節,指齣某人遇害的方式或時間。
·水底發現骸骨,是男是女要怎麼判斷?
·祖墳裏的那具骸骨,真的是27年前失蹤的阿嬤?
在某些案子裏,巴斯僅依賴簡單的工具和技術,例如在非法煙火工廠案裏,他可以把被爆炸射上天空的十一個人重新組閤起來。另有一些案件則需要精密復雜的技術,例如:
·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偵測刀子在傷口留下的微小元素。
·從埋葬已久的屍體采集DNA樣本中發現謀殺案的被害人可能被誤判身份。
·以21世紀的聲納係統搜索田納西東部湖泊深處,尋找35年前消失在地平綫外的飛機。
·開棺檢驗1950年流行歌星“大波普佬”,判斷他是否真是死於飛機失事。
·前往古波斯死亡現場,破解將近三韆年的疑案。
[“人體農場”簡介]
人體農場位於美國田納西州一處山腰,人類遺體曝屍曠野,沒有靈柩或陵墓阻隔,任由昆蟲、細菌和鳥類來加速腐敗分解。大自然在“人體農場”可以為所欲為,那裏的屍體或埋藏淺窪、浸泡水中、隱藏水泥地下,或鎖在汽車行李箱中。他們是凶殺死者的替身,為科學研究盡力,為正義公理獻身。
作者簡介
比爾·巴斯,法醫科學界的傳奇,曾經參與數百案件,從小鎮鎮長辦公室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他的研究,革新瞭法醫科學領域。他創建瞭世界上個也是一個專門研究屍體腐爛的實驗室:田納西州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喬恩·傑弗遜,資深記者、科學作傢和紀錄片製作人。
精彩書評
心髒強,又不怕弄髒手的讀者可以很開心的跟隨法醫人類學小組上山下海,為腐爛已久的屍體查明身份。——《齣版者周報》
書裏真實懸案的精彩度絕對不輸犯罪影集。
——《納許維爾前衛報》
本書不僅提供瞭專業的科學知識,同時也訴諸主流的犯罪迷……有些案件令人心碎,至少有一個案件是徹底神秘的。
——《書頁評論》
目錄
推薦序一 法醫鑒識科學進步的見證人/李昌鈺推薦序二 轉錄遺體故事的法醫檔案簿/石颱平
前言 法醫科學半世紀的演進與革命
第一章 金碗和燃燒的古代宮殿
第二章 水中謎案之一:在水中沉睡的顱骨
第三章 用紫外綫照亮人骨
第四章 最快的骨骼創傷鑒識
第五章 組閤屍塊的噩夢
第六章 死亡假期
第七章 尋找額竇上的“指紋”
第八章 定罪的煙蒂咬痕
第九章 聆聽蟲子的證言
第十章 人骨偵探軟件登場
第十一章 肉眼看不見的骨頭切痕
第十二章 李歐瑪·帕特森案之一:用DNA重啓舊案
第十三章 水中謎案之二:用聲納探測水底深處
第十四章 李歐瑪·帕特森案之二:替死人“做臉”
第十五章 搖滾歌手死亡的那一天
第十六章 李歐瑪·帕特森案之三:挑戰DNA鑒定極限
後記 走齣人體農場的下一步
附錄一 人類骨骼圖示
附錄二 人類學與法醫學重要詞匯錶
精彩書摘
第一章金碗和燃燒的古代宮殿
凡是看過《犯罪現場調查》的影迷都知道,死亡現場可能留存著豐富綫索,詳述生命熄滅那一剎那發生瞭什麼,而且我敢斷言,即使那一剎那發生在近3000年前。
40多年前,6000英裏路外,我遭遇瞭平生最難忘的一次經曆:運用考古學和人類學知識迴答法醫科學的問題。死亡現場在哈桑盧(Hasanlu)山頂古堡,位於伊朗西北部。一支凶猛的軍隊曾攻過這座雄偉壯觀的堡壘,攻破高大堅實的城牆,焚燒宮殿和神殿,血洗城堡。很多人死於這場戰火中,但我最關注這三具屍體,它們在一次引人注目的考古活動中被發現。
然而,計劃進行到一半,我開始擔心第四具屍體可能被捲入:我自己的屍體。我痛得直不起腰來,連續數日精神錯亂、躺在床上鬍言亂語。我的狀況或許沒有那些古戰士悲壯,但我所處的環境(生活方式,死亡腳步逼近,甚至醫術)與3000年前城寨陷落那天差不瞭多少。
1964年夏季,我35歲,是一名積極進取的助理教授,在勞倫斯市的堪薩斯大學人類學係任教。雖然我賓州大學博士文憑上的墨跡纔乾瞭三年,但我挖掘過的骸骨幾乎已超過美國任何人類學傢。1957年進賓大研究所後,我就開始在“史密森學會”打暑期工,當時該學會在整個密蘇裏河流域挖掘瞭無數個美國原住民村落的遺址。美國陸軍工兵團正沿著密蘇裏河興建一座水壩,導緻水位不斷升高;史密森學會必須跟時間賽跑,要搶在河水永遠淹沒遺址之前盡可能挖掘和保存大量的古物和遺骨。在密蘇裏河流域工作的第一個夏天,我和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尋找和挖掘數十個阿裏卡拉族印第安人的墓穴;後來我發明瞭一種方法,用推土機鏟掉墓穴頂層土壤,而不破壞埋在下麵的骨頭。到瞭1963年,每個暑期我們可以挖齣數百具骸骨。我掘墓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終於贏得一位反對開挖印第安墳墓的美國原住民激進分子所給我的封號:“頭號印第安墓盜墓賊”。
雖然1964年我還算年輕,但已積纍瞭不少獨特而廣泛的經驗,所以,當我接到在考古學界名聲漸旺的賓大考古學傢鮑勃·戴森(Bob Dyson)請我協助挖掘哈桑盧古墓的電話時,並不十分意外。很多人熟知埃及古物學傢霍華德·卡特(Howard Carter)的成就,他是發現埃及法老王圖坦卡門陵墓的英國考古學傢,但很少人聽過鮑勃·戴森的成就,這實在令人遺憾,因為鮑勃等於哈桑盧的霍華德·卡特。在鮑勃邀我去伊朗前六年,當時他31歲,卻已經在哈桑盧有瞭韆載難逢的際遇。在兩層樓高的神殿的殘骸中,在堆積如山的殘垣瓦礫和焦土灰燼下,他發現瞭三具男屍遺骨,他們是被活埋於燃燒後倒塌的屋牆之下。小心刷掉覆蓋在骨頭上的破瓦殘礫後,可以看齣三個男子顯然死在逃命之時,他們的雙臂和雙腿固定成永恒的奔跑姿勢。這幅不同凡響的圖像記錄瞭死亡的瞬間,而且保存瞭將近三韆年。
更搶眼的是跑在前麵的那個人懷裏抱的東西,這也是鮑勃邀我去哈桑盧的主要原因。那是一隻碗(也可能是花瓶或寬口酒杯),金屬製的,高約八寸,碗口直徑七寸,碗底直徑六寸。當然,倒塌的牆除瞭壓死抱碗的男人,也壓扁瞭碗。即使如此,碗上精雕細琢的裝飾圖案幾乎完好如初,保存瞭大量驚人的細節。一圈浮雕人形環繞在碗的上端,顯示三名年輕男子嚮神奉獻祭品,其中兩位神祇乘坐雙輪馬車,第三位神祇戴瞭有角的頭飾。碗的下圈是一係列較小的景象和眾多人形,包括一位裸體女神、一名男性獵人或戰士、一隻老鷹載著一個女人、另一個女人騎在獅身上。此外還有一個三人組:一個坐著的男人,加上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女人正嚮男人獻上孩子。這隻碗是如此石破天驚的發現,以緻《生活》(Life)雜誌花瞭整整11頁的篇幅報道它,按當時的衡量標準,相當於今天由當紅女主播凱蒂·蔻麗可(Katie Couric)或黛安·莎耶(Diane Sawyer)主持的一小時電視特彆報道。
碗不大,但很沉,是純金製的。今天這隻碗被戒備森嚴地保護於德黑蘭博物館,是伊朗最貴重的考古文物之一。3000年前它同樣倍受珍視,在城堡的神殿占有一席神聖之地,寶貴程度如同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或麥迪奇親王,像對待米開朗琪羅剛雕刻好或畫完的傑作一般。至少三個男人曾經為這隻碗而死,留下誓死保護它的戲劇性永恒的一幕。
到1964年初鮑勃·戴森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數百萬《生活》雜誌讀者已經驚嘆過這隻碗的繁復精緻之美瞭。但自城門攻破、神殿失火、牆壁倒塌以來,懸疑瞭幾韆年的問題至今仍然無解:這三個男人是誰,他們拿那隻碗做什麼?三人是否全部是城堡衛兵,瘋狂地保護聖物不落入異教徒之手?或者,他們是搶匪,貪婪地抱著最貴重的掠奪物逃離燃燒的神殿?抑或他們是兩種人的組閤:一個孤單的衛兵,忠誠留守到最後一刻,纔倉皇逃離神殿,後麵緊跟著兩個無情的追兵?
鮑勃問我能不能幫忙迴答這個問題。我想我能,但不容易。我必須到伊朗考察,挖齣守城和攻城的兩支古代軍隊士兵的骨頭,比較他們的骨骼尺寸與該地區當代居民的骨骼尺寸。幾十年前,科學傢還不懂得用DNA追查血統,這個做法勝算不大,而且從來沒有人試過。可是它對我有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鮑勃答應雇傭十個當地工人負責挖掘工作,並承擔一名學生的差旅費,來幫我監督工人。我決定邀請我的學生泰德·瑞斯邦(Ted Rathbun)一同前往,他沒什麼經驗但很有潛力,鞦季開學後將讀研究生。我還以為是泰德受惠於我,沒想到不久後竟是他救瞭我的命。
泰德和我於六月初搭乘環球航空公司東嚮707班機離開堪薩斯市。我們先在華盛頓特區停留過夜,看望我的母親後,再飛往紐約參觀世界博覽會(那年頭航空公司允許你在長程飛行中途停留過夜,還不加收費用)。我們從紐約飛往倫敦,在倫敦停留的時間很長,估計足夠我們繞道去看史前時期的巨石陣瞭,這群巨石在哈桑盧城堡崩塌之前已經屹立瞭一韆年或更久。在英格蘭時,我們還拜訪瞭揭穿“皮爾當人”(Piltdown Man)騙局的兩位科學傢,這齣惡名昭著的騙局是某個聰明的惡作劇者把猩猩的下顎骨(下頜)、黑猩猩的牙齒和中世紀人類的無下顎顱骨埋在一起,然後宣稱發現人類演化的“失落環節”。
如此這般在地理學及考古學兩方麵讓泰德增廣見聞後,我們終於齣發前往中東,抵達黎巴嫩首府貝魯特。那時,貝魯特是一座美麗、生機勃勃、國際化的都市,到處擠滿瞭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你可以早上在附近山上滑雪,下午在地中海遊泳、鬆弛筋骨,徜徉在蔚藍海水中觀賞乘著帆傘在空中滑翔的人。沒有炮火,沒有炸彈;那場漫長、血腥、撕裂黎巴嫩的內戰直到十年後纔爆發。貝魯特是進入伊朗的蠻荒之地前,能看到的最後一個現代文明都市。
我們原先搭環球航空班機飛往貝魯特;在貝魯特,我們改搭黎巴嫩的西達航空公司班機飛往德黑蘭,和鮑勃·戴森及其他將在哈桑盧度過暑期的美國團隊會閤。我們從德黑蘭機場直接被接送到美國大使館赴宴,大使館待我們如貴賓,而非卑微的學者和學生。
德黑蘭給我的印象遠比貝魯特軍事化。軍人四處巡邏,檢查護照和其他隨身物件。當時伊朗仍由親美的國王統治,因此相對而言,德黑蘭比較現代化和西方化,但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崛起的跡象到處可見,後來終於將伊朗變成一個好戰的迴教國傢。
我們在伊朗首府停留將近一周,等候簽證、通行證和其他文件簽發下來。計劃這趟探險的時候,鮑勃·戴森估計他可能需要派一些工作人員到附近其他遺址,所以替我和另外幾個團員申請當地的駕照,但申請被駁迴,主管官員並未說明否決理由。不過,鮑勃已在伊朗工作很久,知道裏麵的門道。他塞瞭一些美金,打點瞭一下關係,不久之後我們都拿到瞭駕照。
官員貪汙腐敗不是我在德黑蘭碰到的唯一問題。我在那裏第一次感到身體不適,開始拉肚子。問題並不嚴重,齣門在外拉肚子在所難免。我吃瞭一些止瀉藥,似乎好瞭點。
在德黑蘭辦完事,我們登上一架小型螺鏇槳飛機,朝西北飛行幾百裏,抵達東阿塞拜疆省府塔布裏茲。我們拜訪的第一站是美國領事館(大使館的分支機構),領事是一位年輕的國務院官員,叫做卡爾登·庫恩(Carlton Coon Jr.)。他的父親老卡爾登是一名人類學傢,專門研究現代人及化石人種族,1956至1960年間曾擔任我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論文審查委員。毫不奇怪,這位年輕外交官對來自他父親任教學校的探險隊産生瞭濃厚興趣。後來證明,他的興趣可能救瞭我一命。
在塔布裏茲待瞭兩晚,離開堪薩斯已兩周多,我們終於齣發上路,前往哈桑盧。哈桑盧距塔布裏茲有一整天辛苦的車程,所以我們充分利用這兩天備齊補給品。鮑勃·戴森的裝備包括一輛一噸平闆福特貨車,兩邊圍著木樁,這種貨車在堪薩斯州到處可見,載著乾草捆和傢畜在草原上馳騁。鮑勃在車後塞滿食物、工具,還有泰德和我,然後捲起滾滾沙塵上路。所經之路雖非柏油馬路,但鋪瞭碎石,還算平坦。這些道路是二戰期間美軍為瞭運送援俄物資而鋪設的,一輛接一輛的卡車、坦剋和其他重機設備曾從上麵輾過,20年後,塵土飛揚,但路況依然良好。
我們大部分時間沿著烏爾米耶湖(Lake Urmia)畔行駛,這個湖不論麵積或礦物質成分都很像猶他州的大鹽湖。兩者都是內陸湖,沒有齣海口,因此隨著水分蒸發,從該區高山衝刷到湖裏的礦物質沉澱下來,含量越來越高。我們在滾滾灰塵中沿湖而行,不時可以看到當地人在蘊含豐富礦物質的泥灘中打滾,據說這樣可以減輕風濕癥狀及其他病痛。
索爾杜茲河(Solduz)是注入烏爾米耶湖的河流之一。河水流到湖泊時,幾乎被沿途灌溉用水汲乾。夏季極少降雨,一年的水量大部分靠鼕季下雪,雪堆積在周遭高山上,有些山高達一萬多英尺,炎夏雪水融化注入河流。這一帶的山坡都是光禿禿的灰褐色,但有河水灌溉的山榖卻綠油油的,土壤肥沃,種滿小麥、水果、堅果和稻米。如果不看遠方山脈,隻看如波浪起伏的麥田,我幾乎以為我還在堪薩斯州,至少暫時還在。然後一些陌生景象進入視野,提醒我已離傢幾韆英裏(和幾個世紀),例如我看到驅趕大水牛的小牧童;堆積成山的乾草堆沿著路旁緩緩移動,完全遮住馱著乾草的驢子。
哈桑盧的現代村莊(我使用“現代”一詞非常不嚴謹)有五六韆個居民,大多數在索爾杜茲河榖的農地耕作。村莊坐落在海拔約4500英尺的高度,白天可以熱到華氏90多度(約32℃),但晚上氣溫劇降,是典型的高地沙漠氣候。我們顛簸著駛進村莊,停車時已是黃昏,太陽西垂,熱度趨減,泰德和我沾滿一身灰土,膚色黑得近乎村民。
就我看到的景緻來說,哈桑盧自公元前八百年來不曾改變多少。主要交通工具還是兩條腿,然後是驢車。建築物是用泥磚砌的,在太陽下自然曬乾;屋頂用樹苗和樹枝搭蓋,橫在牆頭上,然後鋪上幾寸厚壓緊的泥土。鼕天,掃除屋頂積雪是重要的工作,否則積雪的重量會把屋頂壓垮,不然到瞭春天融雪時泥糊的屋頂也會溶成泥漿。進到屋內,地闆也是泥地,在這些古代建築中,唯一的例外是村莊學校。校捨炫耀般地鋪著水泥地,並用窯燒的磚塊砌牆。這些房子也是用乾草鋪的屋頂,所以一棟房子失火,往往全村遭殃。
整個鎮沿著灌溉水渠連成一片,水渠叫做“圳”(jube,此字和tube同韻)。圳不隻是灌溉水源,也是傢畜飲水和女人洗衣洗碗的地方,還是村民聚集閑聊或買春的場所。這裏的娼妓綽號“圳女王”,因為她們習慣坐在圳邊,兩腳垂入水中晃蕩,等候顧客召喚。整個場景恍如迴到耶穌基督或穆罕默德的時代,但接著我瞄到一幅熟悉的現代圖像:在一大群蒼蠅底下,露天市場肉販的桌子上,擺瞭一堆壓扁的百威啤酒罐和黑牌威士忌空瓶。此景的突兀和不協調,讓我忍俊不禁。
另一個現代標誌是一颱發電機,美國考古學傢帶來的,每晚6點到10點發幾小時電。一點點科技就大大改變瞭村莊的文化。在BG(Before Generator,發電機前)世紀,村民日齣而作日落而息;在AG(After Generator,發電機後)時代,村民每晚在小電風扇吹的非自然風前麵一坐就是幾個小時,電風扇是村莊的新社會地位象徵。
我很慶幸我們在哈桑盧度過夏天,而非鼕天。鼕季酷寒,暖氣的主要燃料是動物糞便。小孩子把撿迴來的糞便和乾草攪拌在一起,做成糞磚或糞餅(餅這個字和“糞”搭在一起似乎很不對勁)。糞餅在太陽下曬乾後,疊成金字塔或圓錐形,有些大得像座房子。鼕天,這些糞餅堆被雪覆蓋;村民為瞭取用燃料,會鑽得越來越深,先從裏麵拿起。重要的是,我猜,一次不能從主要結構支點拿走太多磚塊,否則疊成巨塔的糞餅會塌在你身上。即使在夏天,糞餅仍是主要燃料;例如,燒二三十桶熱水供我的工作人員洗澡,每人一桶肥皂水和一桶清水需要兩塊半的糞餅,一塊要價25分錢。
因為放暑假,村莊學校空無一人,可以改成宿捨,供我們這些來訪的考古學傢和人類學傢藉住,總共纔10人或12人,其中有3名女性。為瞭謹守禮教,她們住在學校另一邊的廂房,和男生宿捨中間隔瞭一道牆,而且房門上鎖。泰德和我擠一間教室,教室很小,大約80平方英尺。房間隻有一扇小窗,唯一光綫來源是一盞油燈,所以室內很暗;我們早早就將牆粉刷成白色,衝散一些陰鬱黯淡的氣氛。
考古遺址在村外不遠處。城堡大緻呈圓形,規模跟田納西大學裏的伊蘭球場差不多,那是美國最大的體育館之一。堡壘建在山丘上,居高臨下俯視著河榖,因此易守難攻。二戰期間,盟軍曾在山丘上安置炮座;我不知道他們認為誰會來攻打此地——也許是鏇風似的橫掃非洲,嚮中東挺進的隆美爾坦剋部隊。不過,在隆美爾裝甲部隊齣現的2800年前,唯一的裝甲車輛是兩輪馬車。在古哈桑盧,有一條馬車道沿著山坡蜿蜒而上,從河榖通到城門口。城牆高約20英尺;衛兵可以排成一圈守在牆頭,弓箭手也可以從城牆上四座高大的方塔射箭抗敵。城牆內是龐大的宮殿建築群,牆高70來英尺。前幾個暑期,鮑勃的工作人員已修復部分圍牆以穩定結構。
要解答那三個帶碗的人是誰的問題,我必須察看、測量城堡衛兵的骸骨,而且是越多越好。鮑勃已經雇瞭100多名當地人打暑期工。他用90人挖掘古物,泰德和我分到13人,用來挖掘埋在地下的戰士。我的假設是,守護城堡的衛兵會葬在當地墓園,死於攻城行動的入侵者則不會。我在南達科他州挖掘美國原住民墓穴的過程中,已經習慣用挖土設備迅速移走成噸的錶土。在這裏,我的資源很有限;沒有推土機,隻有一頭驢子馱著兩個麻袋供我們裝泥石。我的團隊分工簡單:4個挖工,4個鏟工,4個手推車工,加上一個管水的男孩。盡管工作方法很原始,我們的工作節奏仍然相當順暢,尤其挖工齣乎意料地非常擅於分析土壤,會避免破壞古代頭顱和骨頭。很快地,我們就能一天挖齣好幾具骸骨。接下來幾個星期,我們總共挖瞭83個墓穴,比前六個暑期挖齣的墓穴總數還多瞭12個。
隨著骸骨的纍積,我們慢慢對這些古戰士的骨骼特徵有瞭大概的瞭解。他們的骨骼通常十分結實,有顯著的肌肉留下的痕跡(Muscle Markings),那是揮刀舞劍的巨大手臂和強有力的雙腿用力拉齣來的。這很閤理:戰士必須高大強壯。三個與金碗有關的男人也符閤上述大體描述,唯一引人注目的是,死時懷中抱著碗的男人雖然很高,但他隻有非常輕微的肌肉痕跡,由此判斷,他不可能非常強壯。也許他憑身高當上宮廷衛兵,但他的工作坐的時候居多,不像士兵那樣經常走動,以緻肌肉變得鬆軟。泰德甚至大膽猜測他可能是宮中太監,這是個無法證明但閤理的假設,因為太監的睪丸素分泌量很小,而睪丸素有助於運動員鍛煉肌肉(某些女性健美運動員服用閤成睪丸素的原因就在此)。我頗有信心,從他的體力不足來分析,抱碗的男人不是久經沙場、穿過層層守衛一路殺進城堡的侵略者。
但緊追在他後麵的另外兩人又是怎麼迴事?他們是陪他一起跑、守護他的呢,還是跑在他後麵追逐他?而且眼見就要抓到瞭,牆轟然一聲倒塌下來?要迴答這個問題,我必須詢問當地居民,看看能否從活人當中找到關於死人的綫索。
離開堪薩斯前,我曾搜索研究文獻,但找不到任何關於索爾杜茲河流域居民的當代研究。有位叫做亨利·費爾德(Herry Fields)的人類學傢曾經測量過幾個中東地區居民,包括住在此地南邊七八十英裏的族群,但沒有一個來自阿塞拜疆,更彆說索爾杜茲河流域的瞭。我問鮑勃·戴森能不能利用午休或其他空檔時間測量工作人員,他說當然可以。於是我拿著一把尺四處走動,見到工作人員就量,量他們的身高、臂長、頭顱的長度和寬度,還有鼻子的高度和寬度(他們通常有個大鷹鈎鼻)。過瞭幾天,我發現很多人排隊等候測量,不光是工人,連女人和小孩都來瞭。他們從村莊徒步過來,來迴要走三十分鍾。我大惑不解,於是請翻譯員去打聽,為什麼我的測量計劃人氣這麼旺。他問瞭好些人都不得要領,但最後終於真相大白:原來街頭謠傳我在替人量鼕天的大衣尺寸,凡是我量過的人都會得到一件免費大衣。
這時候我已經量瞭80人,心裏很過意不去,雖然錯不在我,但這些人的希望被點燃,然後鼕天一到,便會破滅。他們從來沒被量過,我試圖澄清,請翻譯員跟他們解釋測量純粹是為瞭科學,我沒有能力送他們大衣雲雲。但不管怎麼說村民都不相信,他們繼續來找我,最後我隻好停止我的測量計劃。
另一個停止測量的原因是我生病瞭,還病得不輕。我在德黑蘭感染的腸病菌死灰復燃,而且來勢洶洶,腹痛如絞導緻我全身蜷麯,痛得直不起腰來。我的消化係統被不明細菌攻擊,一陣陣幾乎止不住的腹瀉和一波波痛苦不堪的便秘輪流發作。加上我經常嘔吐,飢餓和脫水使我虛弱無力。我忽冷忽熱,上一秒冷得發抖,下一秒又發燒流汗。連續數日,我陷入精神錯亂、鬍言亂語的狀態。
那幾天,當泰德外齣察看挖掘工作時,探險隊記錄員卡露琳·達絲剋便照顧我,給我喝開水和酸奶(伊朗人治百病的萬靈丹),如果我咽得下去,還給我一點米飯。到瞭晚上,辛苦瞭一天的泰德接著照顧我。神智清醒的時刻,我想到我的妻子安,那時她已懷孕8個月;想到我的兒子查理和比利,還有我可能永遠見不到的嬰兒。我發誓我不能死在伊朗。
但是我需要幫助。病情開始惡化時,我寫信迴傢,問我的醫生能不能寄一些需要處方的抗生素給我,因為我們帶來的非處方藥劑毫無效用。不幸的是,正常管道不能郵寄處方藥劑。多虧美國領事卡爾登·庫恩,他給我們想瞭辦法。就在我開始懷疑我是否活得下去時,一整包強效抗生素的外交快遞包裹從美國運抵塔布裏茲,再由領事館派人送到哈桑盧給我。這些藥並沒有讓我立刻藥到病除,但接下來幾天,我逐漸振作起來,體力恢復大半,人也重迴工作現場。我後來又花瞭6個月時間纔完全康復,但藥到的頭幾天,我已篤定自己不會死在離傢和親人幾韆裏外的索爾杜茲河流域原始村莊。
在我康復後,我們率領工作人員花瞭好幾天開挖庫德族遺址,那是一座山頂要塞,兩韆年前毀於地震。開車去的那天十分炎熱,一路上塵土飛揚,所以我們停在一條小溪邊乘涼休息,順便清洗一番。我們剝得隻剩內褲,跳進溪裏洗澡;當我抬頭一望,發現附近山丘上聚集瞭一群庫德婦女,睜大眼睛瞧著我們。我們揮手緻意,她們興奮地嘰嘰喳喳說個不停,但我不知道她們在說什麼。
庫德要塞遺址沿著山坡而建,成階梯狀,距離山榖約一韆英尺。午休時間,我們使勁推一塊大石滾下山,然後歡呼著看它摔得粉身碎骨。從它滾落之處堆積的碎石可知,我們不是第一個有這種孩子氣衝動的人。
返迴哈桑盧,暑期也快結束瞭,我們開始做收尾工作。我們從一開始就一邊挖掘,一邊將齣土的骨頭裝箱。泰德和我在探險隊完全結束暑期工作前先行離去。我們大概比鮑勃早走一兩個星期,因為學校即將開學,而且我們兩個都有傢人在翹首以盼。安剛生下我的第三個兒子吉姆,她望眼欲穿盼我迴傢,我也一樣。鮑勃必須留下來關閉現場,並整理歸類整個暑期纍積的齣土文物。我們隨便挑瞭一天宣告工作結束。
在夏季結束、現場關閉、工作人員全部離去時,美國大使及德黑蘭博物館館長會一起檢查齣土文物,這些文物已分成兩批,價值大抵相同,分彆標示為“A”和“B”。然後製作小紙簽,放進帽子裏,由美國人和伊朗人以抽簽方式決定哪一國得到A批,哪一國得到B批。我們將全部骨骼分成數目大緻相等的十六個單元,一個裝滿骨頭的大木箱為一單元,擺在博物館走廊上。但也許沒有人在意骨頭,也許他們始終沒時間抽簽分骨頭,最後這些骨頭跟著我到瞭堪薩斯州,後來又跟著我從堪薩斯搬到田納西。
這是後話瞭。
1964年8月中旬,我的伊朗汽車駕照終於派上用場。我開著一輛路虎旅行車,載著泰德和另外兩位人類學傢,離開哈桑盧前往德黑蘭。我從德黑蘭搭機飛往貝魯特,轉機到倫敦、紐約和堪薩斯市,安、查理、比利和嬰兒吉姆在機場接我。
離傢時我身體強壯,信心滿滿;迴傢時我身體孱弱,也不再那麼自信。除瞭染上重病,我還碰到兩個難題,使我難以迴答鮑勃·戴森那三個攜碗的男人是誰。我們知道攻擊者曾燒毀宮殿,但不知道他們是否占領村莊並定居下來,或者僅僅摧毀城堡然後揚長而去,這是一個難題。另一個難題是該地區的遷徙模式近年來發生劇烈變化。幾韆年來,索爾杜茲河流域人口一直十分穩定,而且與世隔絕,不像歐洲,很久以前種族之間已經混閤和雜居。該地區位置偏遠,環境惡劣,所以能保持地理上和基因上的孤立。烏爾米耶湖構成天然屏障,阻擋來自東北方的移民;幾韆英尺高的紮格羅斯山脈擋在西邊,限製與伊拉剋的接觸;北邊的山脈甚至更高(包括18000英尺高的亞拉拉特山),擋住土耳其移民。但在20世紀90年代,公路和機動車輛肯定能衝破這些藩籬,跟哈桑盧的古代入侵者攻破城堡一樣確鑿無疑。索爾杜茲河流域的現代居民很多是上個世紀從土耳其移入的,當我測量一些貌似“洋人”的頭或鼻子時,我不知道我記錄的是某個古代入侵者的後代,還是20世紀移民的子孫。如今人類學傢已經學會用DNA追蹤現代居民的古代祖先,也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信息來迴答三個攜碗男人的身份問題,但代價昂貴。
我也相信答案將會和1964年,我在時光凝固瞭3000年的村莊想象死亡現場的直覺一樣。我相信身體柔軟、右臂抱碗的守衛,和兩名更健壯、更強悍的宮廷衛兵是一夥的,後者因身材和體力而被挑選為戰士。最不可能作戰的那一個被賦予攜帶金碗的任務,當他倉促地從大火和侵略者手中救齣金碗時,另外兩人守在他後麵保護著他。
自那次以後,我又見過許多死亡現場。每一個現場都告訴我一個故事,有時候故事完整,有時候殘缺不全。很多死亡現場比哈桑盧古堡還陰森恐怖,但沒有一個比之更令人難忘,更可望而不可即。
第二章
水中謎案之一:在水中沉睡的顱骨
法醫人類學傢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確認無名屍的姓名和身份。不知姓名的死者通常是凶殺案的被害人;有的時候,死者是重大災難的受害人,如卡翠納颶風或世貿大樓恐怖攻擊;偶爾是天災或意外事故罹難者,發現時沒有任何身份證件。
“身份”是個有趣的概念。是什麼讓我們成為一個獨特的個體?思想和感覺的總和?我們在族譜上的位置,特定男女結閤的産物?或我們買車子和房子、兌現薪水支票、報稅時留下的文件記錄?或指尖上的渦紋和流紋?DNA的化學結構?
當然,答案為“以上皆是”,但不止於此。就法醫學而言,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方法可以確認一個人的身份。近年來,黃金標準已經變成測定DNA類型,因為我們每個人體內的每一個細胞核都帶著一張基因藍圖,用生化密碼寫成,這個加密訊息長達三十億行,而且人人不同。但DNA鑒定絕非確認身份的唯一技術,往往還不是最快或最高效的技術。不管你從電視節目例如《犯罪現場調查》得到什麼印象,DNA分析可能需要幾周甚至幾個月的時間,還要花費數韆美元。基因鑒定雖然越來越快也越便宜,但在速度和經費上,較之拿骸骨上的牙齒、補牙及其他特徵,和失蹤者生前牙科病曆、X光片及其他醫療數據比對的方法,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1974年3月,我搬到諾剋斯維爾接管田納西大學人類學係還不滿三年,有天下午,我辦公室來瞭四個人:布朗特郡(就在諾剋斯郡南邊)警長、布朗特郡驗屍官、東田納西飛行員協會會長和一名《梅利維爾日報》的記者。
事實上,到我辦公室的是四個人和一個顱骨。顱骨是一個男孩發現的,他沿著布朗特郡綿延裸露的河岸散步時,發現這個顱骨半埋在沙裏。這就解釋瞭為什麼會有報社記者跟來——梅利維爾是布朗特郡政府所在地,但它是個小鎮,因此有人在新近露齣的河岸邊發現人類頭顱,馬上就變成大新聞。
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在田納西河及其支流開挖瞭一連串湖泊,每年鼕天管理局會降低湖泊水位,作為洪水管製措施,當春雨來臨時,水庫便能容納增加的水量。有些田納西河支流的湖泊,例如諾瑞斯湖和方塔納湖,每年鼕天水位降低十五至二十英尺之多;但勞登堡湖必須維持平底船可以航行的深度,因此管理局隻把水位降低幾英尺。雖然纔降幾英尺,已經足夠露齣大片水岸,成為古箭頭搜尋者的主要活動範圍。管理局到來之前,他們在此尋找田納西河流域原住民的遺留物當紀念品。
我不知道這個布朗特郡男孩是不是在找印第安遺物;不管想找什麼,反正他找到一個人類的顱骨。他把顱骨留在河邊,但那天晚上,他告訴瞭父親這件事。“我們最好迴去把它拿來。”男孩的父親說。他們一取迴顱骨,就與布朗特郡警察局聯係,可以想見警方多麼急著要確定這是古人還是今人的顱骨,或者是一起凶殺案中被害人的顱骨。
從眼睛上方厚實隆起的眉棱來看,這顯然是男性頭顱。狹窄的鼻孔,還有牙齒與嘴部的垂直構造,都在說明這是高加索人種,不是尼格羅人種(黑人或非裔美國人的牙齒和嘴部通常嚮前突齣,這種區彆特徵叫做“突頜”)。門牙背麵基本上平坦而非鏟形,這便排除瞭美國原住民的可能性。此外,除瞭缺少下顎骨(下頜),頭顱的情況好得齣奇——太過於完整如新,因此不可能埋在泥裏幾十年或幾百年。汞齊補牙(從手藝判斷,應該是一位好牙醫的傑作)證實這個頭顱的年代不久。顱骨沒有破損,如果死者是凶殺案的被害人,緻命原因一定不是頭部受擊或中槍。從牙齒磨損及顱縫(頭蓋骨各個骨頭之間的接縫)明顯的情況,我估計年齡在30歲到34歲之間。
這個顱骨隻有兩樣東西似乎不尋常。一是眼窩後麵齣現屍蠟(adipocere)——一種像蠟或肥皂般的物質。adipocere是拉丁文術語,照字麵翻譯是墓穴之蠟,當身體脂肪組織在非常潮濕的環境中腐化,譬如地下室或河岸,就會形成屍蠟。大多數人不知道,除瞭極度營養不良的人以外,每個人的眼球背後都有成袋的脂肪。如果你曾見過集中營幸存者的照片,一定會注意到他們的眼睛凹下去,好像深陷在頭顱裏麵;那是因為他們耗盡身體儲備的所有脂肪,包括眼睛後方的小護墊。所以知道頭顱發現地點後,我並不驚訝看到成團屍蠟藏在眼窩裏麵。
另一個不尋常的特徵是頭顱形狀——頭蓋骨明顯高聳狹窄。加上傾斜的額頭和斜長的眼睛開口(眼眶),讓頭顱看起來幾乎是東方人的模樣。當我看到那個又高又尖的頭蓋骨時,腦中馬上閃過一種罕見疾病,被稱作“舟形頭”(scafoscephalae)的畸形頭顱;造成舟形頭的原因是矢狀縫提早愈閤。矢狀縫是額骨(前額)與頂骨(顱骨兩側)之間的接縫,以緻童年時期頭顱無法再橫嚮生長,隻好往上長,愈長愈高以容納大腦發育。如果某人有舟形頭,你拿到此人的顱頂,把它倒過來,就會看到頭蓋骨內部呈V字形,像船殼內層或船的龍骨。今天,如果孩子天生有此缺陷,有辦法矯正——外科醫生可以用骨鋸重新打開矢狀縫,讓頭顱正常生長;鋸開的骨頭最後會再接閤,但那是在頭顱長到正常寬度以後的事。
眼前這個特彆的頭顱還不夠高不夠尖,還不算典型的舟形頭病癥。如果此人今天還是個孩子,可能不需要動外科手術,但他的頭顱比例已經比大多數人更接近舟形頭瞭。
帶頭顱來的四個人當中,最讓人想不到的是東田納西飛行員協會會長吉姆·剋林。剋林告訴我,有一名叫埃墨·雷諾茲的諾剋斯維爾男子兩年前駕小飛機失蹤,事實上,他是駕著剋林的飛機,載著一名16歲少女欣賞風景,預定隻做短途飛行。女孩名叫琳達·漢德瑞剋,從密歇根州來諾剋斯維爾拜訪姑媽。她的姑媽和姑夫住在考剋斯天空牧場的管理員拖車屋裏,考剋斯天空牧場是一個利用河岸草地當跑道的小型簡陋機場,在顱骨發現地點上遊約四英裏處。飛機於1972年1月某日下午近黃昏時起飛,當時雷諾茲說,他要帶琳達去看諾剋斯維爾的燈火。應該是一趟短途飛行,因為飛機上隻有約半小時的燃油。當兩人沒有迴來時,民間空中巡邏隊曾展開空中搜尋,但在樹木繁茂的陸地或河流淺灘都未看到飛機墜毀跡象;當地救難隊在河裏打撈瞭一陣子,同樣徒勞無功。有一種說法在部分執法人員之間流傳,臆測雷諾茲可能帶著這位十多歲的少女私奔瞭;他當年32歲,已經娶妻,生瞭五個孩子。但查問附近他可能前往加油的機場,也查不到任何關於飛機降落或飛行路綫的綫索。
頭顱的年齡和種族正好與雷諾茲相符。從顱骨牙齒的良好情況來看,這名男子顯然定期看牙醫。而且,有一顆臼齒形狀特彆,補牙方式也特彆。
大多數人的臼齒有所謂的“Y5”形狀,也就是咬閤麵有五個尖端,尖端之間的溝槽連成一個Y字形,所以稱作“Y5”。而這個顱骨的其中一顆臼齒有比較少見的“4+”形狀,也就是隻有四個尖端,其間溝槽連起來的形狀像個加號。在人類演化史上,臼齒形狀的差異可以追溯至幾百萬年前我們的祖先——中新世(大概2700萬年前)的猿類身上。中新世與20世紀之間,牙科醫學的發展比靈長類的演化迅速得多。到瞭20世紀70年代,與時俱進的牙醫已經知道,如果病人臼齒的中央溝蛀掉,單把蛀洞補起來還不夠,耐久的補法是沿著溝槽鑽齣通道,做比較大範圍的填補,以確定補牙材料固定在牢靠的基礎上。這名男子的“4+”形臼齒上有一道獨特的長形填補,顯然齣自非常高明的牙醫之手。“我相信埃默·雷諾茲的牙醫能告訴我們這是不是他。”我對辦公室裏這一小群人說。其中一人(我忘瞭是誰)打電話給埃墨的妻子,她指引我們去找一位名叫羅伯·格雷爾的牙醫。
我打電話給格雷爾醫生,他的診所在木蘭大道一棟老房子裏。“我可能有你一位病人的顱骨,”我告訴他,“我能不能帶到你那裏請你看看,比對一下病曆?”他同意瞭,請我次日一早把顱骨帶去他的診所。
我把顱骨放在裝食品雜貨的牛皮紙袋裏,上午九點帶著它來到診所。“這可能是埃墨·雷諾茲。”我說。格雷爾醫生把手伸進紙袋,拿齣顱骨,一看就說:“是啊,就是埃墨。”他沒有參考雷諾茲的病曆就這麼說;事實上,他甚至還沒有檢查牙齒。他和我一樣,一眼認齣那個高聳狹窄的顱穹——牙醫四年來每隔六個月就要彎腰俯視一次的頭蓋骨。如果格雷爾曾疑惑為什麼埃墨沒有按時來洗牙,他的疑問現在得到解答瞭。
原來格雷爾醫生曾在空軍擔任牙醫,恢復平民身份後纔開設私人診所。服役期間他曾數度奉命做牙齒鑒定,辨認死於飛機失事和燒焦的飛行員屍體,因此他對法醫牙科或齒科學既有興趣也有經驗。牙齒鑒定(比對死者的牙齒與生前X光片或診療紀錄)用作呈堂證據已經有一個多世紀,但軍隊是國傢主要的齒科專傢人纔庫,因為軍人死於爆炸、飛機墜毀及其他無法做尋常視覺辨識情況的風險更大。
認齣頭顱的特殊形狀後,格雷爾醫生抽齣一張圖錶,確定顱骨上的牙齒與埃墨的診療記錄吻閤。牙醫和我聊瞭一下彼此鑒識飛機失事罹難者的經驗,然後我謝謝他的幫忙,把顱骨放迴紙袋,走齣診所。
我步下門前颱階走嚮車子,與兩名站在人行道上的男子擦身而過時,相互打瞭個招呼,其中一人接著說:“請問你是不是在鑒定我們兄弟身份的那個人?”顯然他們聽說有個頭顱被送到我那裏鑒定,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秘書告訴他們,我去請教格雷爾醫生瞭。
我告訴兩名男子我是誰,承認我正設法鑒定一個水庫邊上發現的頭顱。他們隨即自我介紹說他們姓雷諾茲,我想他們大概真的是埃墨的兄弟,有權知道實情。“我很遺憾告訴你們這件事,”我說,“我們已經確認這是埃墨·雷諾茲。”我和他們談瞭幾分鍾,之後我發現兩人在瞄我手中的紙袋。我一時不知怎麼應對。思索片刻後,我問他們:“想不想看你們的兄弟?”他們討論瞭幾分鍾,最後決定要看。我把頭顱拿齣來——就在木蘭大道,諾剋斯維爾一條繁忙大街的人行道上——兩人異口同聲說:“是啊,是埃墨沒錯。”我覺得很有趣,即使沒有軟組織,認識他的人還是能認齣他。
我從來沒有和雷諾茲的遺孀聯係過,但我聽說,確認他的身份後,她如釋重負,終於可以申報死亡,領取他的壽險賠償金瞭。她要撫養五個孩子,過去兩年來,手頭一定相當拮據。雖然一具屍體或骸骨(或顱骨)的身份確認總是難免令人傷心,但也意味著事情告一段落,有機會——或許不無痛苦地——擺脫不確定和睏惑的狀態,開始療傷止痛,迴到常軌繼續過日子。
我在周一接到這個頭顱。周五那天,我交齣報告給布朗特郡警局,詳述我檢查顱骨與確認身份的經過,確認的根據是:顱骨上一顆臼齒的特殊填補完全符閤埃墨·雷諾茲的牙科病曆(另一顆有奇特牙根的牙齒也符閤)。
接下來那周,我爬進布朗特郡救難隊的一艘平底鋁閤金小艇。他們把船拖上一處小水灣的沙灘,水灣掩藏在那段河流沿岸的巉岩下,到處是廢棄物,男孩就是在這裏發現顱骨的。當救難隊的潛水員在深水處搜尋時,誌願者也用鋁竿刺探淺水區,希望能從金屬互撞的當啷聲音中找到飛機殘骸的位置。我則淘篩沙子和被水衝到岸上的層層枯枝及垃圾,希望找到埃墨的顱下骨骼(頭顱以下的部分),以及他的乘客琳達·漢德瑞剋的任何遺物。
救難隊後來擴大搜索範圍,加入六個其他地區的救難隊,搜索範圍也往上遊延伸瞭好幾英裏。但我在頭顱衝上岸的地點沒有再發現任何東西。經過幾百個小時的搜尋,潛水員和長竿隊隻找到一個工具袋,吉姆·剋林說那是飛機上的東西。但僅此而已,沒有找到飛機,也沒有發現其他骨頭。河流不肯讓齣它懷抱的死者,至少目前還不肯。
事情好像已經蓋棺定論瞭,直到31年後,重新開始搜尋遺骸時。
但那是另一個科技更上一層樓的故事……
……
前言/序言
法醫科學半世紀的演進與革命51年前一個4月的早晨,我在堪薩斯大學骨頭實驗室裏正彎腰看著一盤骨頭,突然,我的人類學教授查理·斯諾(Charlie Snow)走瞭進來, 問我願不願意陪他去處理一樁人身鑒識案。就在那一刻,我的人生方嚮改變瞭,我的事業生涯也從此轉摺。
當時一位律師問斯諾博士,通過火燒過的遺骸能否判定死者身份。遺骸是在列剋星敦城外一輛卡車上發現的,燒焦的駕駛室中同時還找到瞭司機的屍體。這輛卡車被越過公路中綫的全國連鎖超市A&P;的貨車撞上,車毀人亡,包括卡車司機和乘客(據說兩人同居)在內共3人喪生。斯諾博士告訴律師,隻要能找到跟司機同居者的牙科病曆,他就一定能辨彆燒過的遺骸到底是不是她。這可不是信口雌黃,身為美國陸軍中央鑒識實驗室主任,斯諾博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的許多年裏,一直在鑒定腐敗的、破碎的及燒成灰的美國士兵遺體。他是這個專門學科的先驅,這門學科數十年後被稱為“法醫人類學”(Forensic Anthropology):利用傳統上注重古老人骨研究的體質人類學知識和技術,協助破解刑事案件,尤其用來辨認凶殺案中無名被害人的身份,並還原他們遇害的經過。即使不能指認被害人姓名(我就有一架子無法指認姓名的骸骨),法醫人類學傢仍能協助警方提供種種細節,包括被害人的種族、性彆、身高、習慣使用左手還是右手(理所當然,慣用右手的人右臂肌肉附著點往往比較粗大),以及遇害方式——被害人是被刺殺、槍擊、勒死、棍棒打死或被其他方式奪命?從留在骨頭上的痕跡都可看齣端倪。
斯諾博士邀我陪他去處理這樁改變我一生的鑒識案,是因為我有車,而他沒有,雖然我寜可相信這不是主要因素,而是他看中瞭我在骨頭辨識上逐漸展露的纔華。不管怎麼說,我開車載著我倆前往埋葬死者的鄉村教堂墓園。裝遺骸的棺材浸滿水,濕嗒嗒的,發齣惡臭,與我前一天在實驗室研究的那個象牙色光澤的骨頭天差地彆。事實上,當棺蓋掀開時,入目的景象和氣味太過刺激,以緻我當場吐瞭起來。
那是51年前的往事,此後我處理過數百樁鑒識案。很高興告訴大傢,從那次嘔吐至今,我不曾在鑒識過程中再吐過;而且在這段歲月裏,法醫科學——用來破解刑案的人類學、昆蟲學、齒科學(牙科)、遺傳學和其他協助逮捕凶手並證明其犯罪的科學——已經突飛猛進。當年我在肯塔基州的泥濘墓地,站在斯諾博士身邊彎腰嘔吐時,根本想不到會有像今天這樣的發展。
我並不是說20世紀50年代的法醫科學和法醫科學傢是原始落後的。在肯塔基州受教於斯諾博士之後,我進入賓州大學,拜到國際知名的“骨頭偵探”威爾頓·剋魯格曼博士(Dr. Wilton Krogman)門下,攻讀博士學位。沒有人稱剋魯格曼為法醫人類學傢,這個名稱當時尚未被創造齣來,不過我這輩子,無論在認識剋魯格曼之前或之後,從未見過任何人比他更擅長在人骨上找綫索,更會聆聽死者悄悄訴說的秘密,透露他們生前是什麼人,以及如何遇害。剋魯格曼最擅長的領域是兒童骨骼生長與發育,尤其是他們的牙齒。因此,不管什麼時候,都有數十位齒科學專傢在他門下學習。我在賓大那幾年,是他實際教過的唯一一個法醫人類學學生,雖然我沒有接受牙醫或齒科學的正規訓練,但我學到瞭有關人類牙齒的豐富知識,尤其是如何由牙齒辨彆被害人的年齡和身份。
我在事業生涯中學到的最重要課題之一是,伸張正義要靠團隊努力。任何凶殺案破案過程中,團隊成員可能包括製服警察、便衣刑警、犯罪現場和實驗室技術員、指紋專傢、法醫、槍械和彈道鑒定專傢、毒物分析學傢、法醫牙科醫師及DNA專傢。
不過,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法醫的團隊工作不隻是跨越學科專業,也包含數十年的研究和創新。我站在剋魯格曼博士高大的肩膀上,而剋魯格曼自己又站在托馬斯·溫格特·托德(Thomas Wingate Todd)的肩膀上,後者是剋利夫蘭的凱斯西儲大學傳奇解剖學傢,這位科學傢最先注意到恥骨會隨年齡增長穩定持續地變化,從恥骨變化可以推斷無名骸骨的年齡。其他在早年應用考古學和人類學技術提供現代凶殺案偵查綫索的巨人,包括史密森學會的體質人類學傢艾曆斯·赫爾德利奇卡(Ale· Hrdli·ka)和達爾·史都華(T. Dale Stewart)。19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聯邦調查局先後嚮赫爾德利奇卡和史都華請教的案件多達數百件,該局距史密森學會僅一箭之遙。兩人在協助聯邦調查局辦案過程中,像剋魯格曼一樣,幫助界定瞭法醫人類學的工具、技術和能力。
1972年,美國法醫學會體質人類學組召開首次會議;五年後,我們一小撮人創立瞭美國法醫人類學傢協會。在我的事業生涯中,曾有一度,約3分之2的經協會認證的法醫人類學傢是我訓練齣來的;現在這個比例比以前低,因為我已經退休瞭,由其他教師接棒培養博士。不過,如果仔細看法醫人類學傢的“族譜”,我的名字下掛著令人欣慰的粗大枝椏,並再分支成許多受人敬重的名字,這些科學傢分布在不同機構,如史密森學會、中央鑒識實驗室、聯邦調查局、喬治亞州調查局、肯塔基州法醫署,以及為數眾多的大學,其中也包括田納西大學,該校開設瞭世界數一數二的法醫人類學課程。
田納西大學法醫人類學課程的重點(也是它最有名的部分)當屬人類學研究場,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是“人體農場”(有些年輕同事聽瞭就皺眉)。經常有人問我為什麼創立人體農場,但願我能迴答說,因為我那個齣色的學術腦袋突然靈光一閃而迸齣完全成熟的構想,但真相是,人體農場和許多學科進程一樣,一次跨齣一兩步。從1960年到1971年,我在勞倫斯的堪薩斯大學教授人類學,在那11年中,我有時替堪薩斯執法人員鑒定骨骼殘骸,協助的對象從地方警局到堪薩斯州調查局。最後我和哈洛·奈依(Harold Nye)成瞭朋友。奈依在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經典小說《冷血》(Cold Blood) 描述的真實刑案裏,扮演緝拿殺人凶手的關鍵角色,他後來升為堪薩斯州調查局局長。
1971年我搬到諾剋斯維爾,接管田納西大學人類學係。我上任時,對我略有耳聞的田納西州法醫問我,願不願意擔任該州的法醫人類學傢,協助執法機構辨認屍體。我答應瞭,當時我並未料到田納西州的凶殺案被害人與堪薩斯州的截然不同。在堪薩斯州,警方請我鑒定某人身份時,通常帶來一盒乾燥的骨頭;堪薩斯州地廣人稀,氣候乾燥,偶爾骨頭上會附著殘存的一點點木乃伊化的組織,但多半時候我鑒定的案子隻剩下骨骼遺骸。反之,田納西州麵積隻有堪薩斯州一半大,人口卻是它的兩倍,雨量則是好幾倍,被害人的屍體往往比較新鮮、比較臭,也比較多蟲,多得數不清,爬滿瞭蛆。當田納西警員或地區檢察官問我這些屍體已經放瞭多久時,我沒有紮實可靠的科學根據能作答。所以,我決定補充自己不足的知識。田納西大學醫學中心後方有一片幾畝大的荒廢地,林木雜生,中間有一塊焦黑空地,醫院在此焚燒垃圾多年。1980年,我在這片荒地中鋪瞭一塊16平方英尺的水泥地,四周和上麵用鐵絲網圍起來,我打算在掠食性動物進不去(除非它小得能夠鑽過鐵絲網孔)的圍欄裏麵擺放屍體,供我和我的研究生密切觀察,記錄在長期死後間隔期間(extended postmortem interval)人體腐敗的順序和時間。
1981年5月,我們收到第一具供研究用的捐贈遺體。為瞭不讓捐贈者的身份曝光,我製定瞭一套編號係統,研究報告上隻提人體號碼,不寫姓名。第一具人體在1981年取得,因此編號是1-81;不久2-81、3-81和4-81接踵而來。1982年,編號順序由1-82開始,然後是2-82,以此類推。
起初遺體捐贈很少,我們隻有從州內各地法醫提供的、無人認領的屍體中挑選。最初幾年,編號甚至隻有個位數;不過,現在很多人知道我們在研究,願意給予支持,因此每年的編號也邁入三位數——超過一百具屍體,捐贈的遺體數量遠遠超過無名屍。公眾之所以對我們的研究日益好奇,一個早期和影響深遠的因素是帕特麗夏·康薇爾的小說《人體農場》,這本書於1994年鞦天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事實上“人體農場”的綽號並非康薇爾所創(據我們瞭解,這個不知算不算榮耀的命名歸功於一位名叫伊凡·傅特瑞爾的聯邦調查局指紋專傢),但她確實打響瞭我們的知名度。她的書讓我們聲名大噪,這些年人體農場已被拍成許多電視紀錄片,常有文章登在報紙和雜誌上,也被廣播電颱采訪過,過去兩年還成為暢銷犯罪小說“巴斯犯罪鑒識小說係列”的主題,那是我用筆名傑弗遜·巴斯和喬恩·傑弗遜閤著的。小說情節和許多角色純屬虛構,但科學部分有根有據,是基於二十幾年來人類學研究場的豐富實驗。隨著人體農場的名聲越來越響亮,它的規模也越來越大,現在它有兩三英畝林地,用高大的木籬笆圍起來,但近年捐贈的遺體大幅增加,這塊地已不夠用瞭。幸好田納西大學錶示願意擴大研究場,再增加11英畝地。不過,如果業務繼續以當前速度增長的話,幾年內新增的麵積又會不夠用。這些日子,人們真的是死也要進人體農場……
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我們展開研究計劃時,實驗目的隻是想迴答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手臂多久纔會脫落?顱骨什麼時候開始外露?在什麼時間點人體會腐敗至隻剩枯骨?一般人也知道,腐敗過程在夏天比鼕天快得多。然而過不瞭多久,研究計劃就變得高深復雜瞭,我們研究齣死後腐敗的時間錶和數學公式,一旦取得屍體發現前數日或數周的氣溫記錄,就可以據此估算死者死亡時間,而且準得齣奇。我們從實驗得知,關鍵在於“日均溫纍積值”(Accumulated-Degree-Days),簡稱積溫值(ADD),也就是每天平均氣溫的總和。例如,一具屍體在最炎熱的夏天放進人體農場,平均氣溫達到華氏80度,經過十天,這具屍體的日均溫纍積值將是華氏800度,早已進入化成骨骼的階段。在酷寒的鼕天,連續十天每天溫度都是冷得刺骨的華氏30度,屍體的日均溫纍積值隻有華氏300度,幾乎纔剛開始因內部腐爛産生氣體而膨脹。利用積溫值標齣分解進程最妙的地方是,數據可以用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不管哪裏的屍體,在大約1250到1300積溫值之間,都會分解得隻剩光禿禿的骨頭,或是骨頭上覆蓋著木乃伊化的乾縮組織。
此外還有昆蟲研究。那是我們最早期的研究計劃之一,1981年由我的研究生比爾·羅德裏格茲(Bill Rodriguez)負責,記錄眾多來屍體進食的昆蟲種類:來瞭哪種昆蟲,何時齣現,停留多久。比爾蹲在屍體旁,一坐就是幾個鍾頭,還要忙著驅趕企圖在他鼻孔和嘴巴邊産卵的蒼蠅,他替一門新的專業領域奠定瞭基礎,這個領域迅速成為法醫昆蟲學。如今,得益於比爾在人體農場開疆闢土的昆蟲研究,世界各地的犯罪現場技術員都知道要搜集被害人身上的昆蟲標本,交給昆蟲學傢分析這些蟲子已在屍身進食多久。自從比爾首開昆蟲研究的先河,已有無數昆蟲學傢來過人體農場,因為這裏有舉世無雙的研究設施,任何時候都擺著數十具人類屍體,處於不同的腐化階段,有新近死亡的,有完全骨骼化的,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各種情形,供觀察研究之用,對科學傢和對昆蟲一樣,來者不拒。
昆蟲學傢並不是唯一依賴人體農場提供獨特研究機會的科學傢。我以前的一個研究生阿帕德·瓦斯博士(Dr. Arpad Vass),目前是橡樹嶺國傢實驗室研究員,花瞭幾年時間采集屍體腐化時釋放齣的氣體,並進行化學分析。到目前為止,阿帕德已經辨認齣450多種不同的氣體成分;根據這個,阿帕德研發齣一款“機械鼻”,用程序操控它來嗅齣秘密藏屍點,就像訓練搜尋犬找屍體一樣。阿帕德也利用“死後法醫化學”(姑且用這個彆扭的名詞)來判斷死後的間隔時間:通過分析死亡的化學作用及腐爛産生的化學物質,並研究屍體腐爛過程中各種化學物質的比例變化(就像昆蟲學傢研究昆蟲來來去去的換班行列),阿帕德能夠找齣化學作用與時間的關聯,像看時鍾一般,由腐物讀齣屍體已死亡多少個鍾頭,或多少天、多少周。他也研究屍體為什麼會釋放能量場(Energy Field)——他的假設是,分解時的化學反應實際上將屍體變成一個巨大的生化電池;如果這個假設成真,則意味著代言“金霸王”電池的活力兔 ()①即使已經死瞭,但屍體可能還保有一些電壓。
關於田納西大學的法醫課程,大多數人不瞭解的是,當一具屍體在人體農場完全變成骨骼之日,纔是它的科學生命開始之時。事實上當事人填錶同意捐贈遺體給人體農場——現在已有超過1000人填瞭錶——他們同意捐贈的其實是骸骨;肌肉隻是包裝骸骨、可被生物分解的材料。在內伊蘭球場下方上鎖的房間裏,一層層迅速擴充的架子上,田納西大學建立瞭美國規模最大的骸骨收藏室(屍體身份、年齡、性彆、身高和種族都已知的骸骨),可能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到瞭2007年,威廉·巴斯捐贈收藏的標本近七百個,而且平均每三天增加一具骸骨。這些標本是訓練人類學傢和法醫科學傢的可觀資源(除瞭本係學生外,通過全國法醫學會,人類學係每年還協助訓練數百名犯罪現場與刑事犯罪實驗室技術員);也是提供數據給法醫人類學數據庫(Forensic Anthropology Data Bank)的金礦,該數據庫儲存瞭世界各地人種的詳細骨骼尺寸,這讓法醫科學傢碰到無名骸骨時,也能輕鬆判斷骨頭所屬的種族,知道是歐洲人、美國原住民、非裔美國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太平洋島民、澳洲原住民,還是中國人,或數據庫裏包含的數十種任何其他族群。依靠捐贈的骸骨還開發齣鑒彆函數分析程序(ForDisc),這個功能強大的計算機程序是我的同事、也是我過去的學生理查·簡茲博士(Dr. Richard Jantz)在田納西大學開發的,隻要根據幾個簡單的骨骼測量尺寸,就可以判斷無名骸骨的性彆、身高和種族(這個程序在第十章《人骨偵探軟件登場》詳述的案件中扮演瞭關鍵角色)。2006到2007年,每具捐贈收藏的骸骨都做瞭斷層掃描。我期盼在未來幾年,這些掃描數據能用在各種各樣有趣的研究與應用法醫科學上,例如聯邦調查局實驗中的顔麵重建軟件ReFace(詳情見第十四章《李歐瑪·帕特森案之二:替死人“做臉”》)。
法醫科學近幾十年最戲劇化也最具革命性的進展之一是DNA鑒定問世。雖然DNA鑒定不是魔杖——如李歐瑪·帕特森案痛苦地顯示——但它仍是石破天驚的突破。DNA研究不再局限於遺傳學範疇;人類學領域目前興起一門新學科,叫做“分子人類學”(Molecular Anthropology)。田納西大學人類學係師資陣容現有一位纔華洋溢的年輕分子人類學傢格雷茜拉·卡芭納博士(Dr. Graciela Cabana)加入,毫無疑問,通過在人體農場的研究,她一定會找到迷人的領域發揮她的專長。
有一項研究人體農場大概永遠不會去做,那就是寫書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至少是我的身體健康。2002年,我開始寫迴憶錄《大法醫:死亡翻譯人》之初,有天我的心髒停止跳動,幾乎死亡。而後,就在這本書快完成之際,我的心髒科醫生通知我,2002年與死神擦身而過時植入的心律調節器即將壽終正寢,必須馬上更換。我周三早晨進入手術室,當天中午就迴傢瞭。第二天,我感覺很好,好到可以帶愛犬小崔去做每天下午例行的散步,開刀剛過兩個星期,我已經能開車去納什維爾,對一群醫療專業人員發錶兩小時演講瞭。錶麵上我已退休多年,事實上有時我仍然每周工作四五十個小時,不過是齣於自願,而非為瞭生計。偶爾也會忙到想推掉工作,但多數時候我還是欣然接受,因為我愛演講,也喜歡接受有趣的法醫案件谘詢。例如,再過不久,我會去協助一組法醫科學傢開棺檢驗赫赫有名的魔術師哈利·鬍迪尼(Harry Houdini)的屍骸,他死於1926年萬聖節,據說死於盲腸破裂,但80年來謠言不斷,有說他曾被人威脅,也有說他被下毒,疑雲重重,像魔術師變的戲法一樣,遮蔽瞭真相。
鬍迪尼可以說是世界最偉大的脫逃藝術傢,但到頭來,他還是逃不過死神的魔掌。我們沒人逃得過,但在科技和醫療的魔法下,有些人能夠大大延長在人生舞颱錶演的時間。我很幸運,心髒科學像法醫科學一樣,在我成年後突飛猛進。
然而,人類心髒一如人類心智,依舊神秘莫測,有時還帶著緻命的缺陷,像永遠戒不掉的嗜殺傾嚮,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注意。能夠幫助解決一些凶殺案,同時提供科學工具協助其他法醫科學傢破案,是我的天職,也是我的殊榮。我從未想過藉由人體農場得到什麼名號,我隻是比其他人先跨齣科學研究的一步,希望能解答凶殺案調查過程或課堂討論中引發的問題。但這些研究逐漸引導我和我的同仁及學生步上奇妙的旅程。
接下來的章節裏,你將讀到我們在人體農場學到的一切是如何協助我們辨認死者、還原他們的遭遇,在許多案件中(可惜不是所有案件)將凶手繩之以法。但真正的突破,如同我在弗吉尼亞理工學院的槍擊慘案之後領悟的,仍然難以企及。當我們不隻學會破解更多凶殺案,而且學會防止更多凶殺案時,真正的突破纔會到來。
直到那一天來臨,我們在深鎖的大門和木頭圍籬後麵不怎麼美妙的研究,將繼續給調查人員提供更多和更好的工具,破解真實世界(人體農場之外的世界)發生的犯罪案件。
比爾·巴斯博士
諾剋斯維爾,田納西州
2007年6月
用户评价
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就像是在經曆一場跌宕起伏的過山車。故事的節奏把握得非常好,總能在你以為一切都塵埃落定時,拋齣一個意想不到的轉摺,讓你措手不及。這種強烈的反差感,讓我始終保持著高度的緊張感,生怕錯過任何一個重要的綫索。作者在製造懸念方麵簡直是大師級的,他善於運用各種手法,一點點地剝開真相的層層外衣,吊足瞭讀者的胃口。有時候,即使我自認為已經猜到瞭結局,但最終的真相卻往往比我想象的還要復雜和齣乎意料。這種驚喜與震撼並存的感覺,是我追求的閱讀體驗。而且,書中對社會現象的探討也相當深刻,它不僅僅是講述一個故事,更是在藉故事來反思現實,引發讀者對人性、道德、法律等問題的思考。這種寓教於樂的寫作方式,讓我覺得這本書的價值遠不止於故事本身。
评分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智力挑戰。我常常在閱讀過程中,試圖去梳理脈絡,找齣其中的邏輯漏洞,但每一次的推理,似乎都隻能觸及到冰山一角。作者巧妙地設置瞭重重迷霧,讓真相變得撲朔迷離,既考驗著讀者的觀察力,也考驗著讀者的邏輯思維能力。我感覺自己就像是在和作者玩一場高智商的遊戲,他步步為營,而我則竭力地想要跟上他的步伐。每一次的猜想被推翻,都讓我更加興奮,也更加渴望去揭開謎底。而且,書中對細節的嚴謹程度令人驚嘆,哪怕是看似無關緊要的小物件,也可能隱藏著至關重要的綫索。這讓我不得不全神貫注,仔細審視每一個字,每一個段落。這種燒腦的閱讀體驗,對於我這樣的讀者來說,簡直是莫大的享受。
评分剛翻開這本書,就被那種撲麵而來的懸疑氛圍給吸引住瞭。書中的開篇就營造瞭一種緊張而又充滿未知的情境,讓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作者在細節的刻畫上非常到位,無論是人物的微錶情,還是場景的描繪,都栩栩如生,仿佛身臨其境。我尤其喜歡作者對案件發生地那種細緻入微的描寫,讓每一個場景都充滿瞭故事感,也為案件的偵破增添瞭更多可能性。讀著讀著,我感覺自己也變成瞭一個局外人,但又忍不住想要深入其中,去探究那些隱藏在錶象之下的真相。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真的非常難得。而且,書中對一些專業知識的穿插,並沒有顯得枯燥乏味,反而通過生動的敘述,讓我對一些原本陌生的領域産生瞭濃厚的興趣,甚至會主動去查閱相關資料,這在以往的閱讀體驗中是很少見的。整體來說,這本書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它成功地勾起瞭我的好奇心,讓我對後續的劇情充滿瞭期待,也對作者的敘事能力和知識儲備感到由衷的贊嘆。
评分從這本書中,我不僅僅收獲瞭一個精彩的故事,更學到瞭許多我從未接觸過的知識。作者在敘事中,將一些專業領域的知識巧妙地融入其中,但並沒有讓人感到生硬或晦澀。相反,通過生動的例子和深入淺齣的講解,我仿佛上瞭一堂生動的科普課。我對某些過去覺得遙不可及的領域,現在有瞭一個全新的認識,甚至産生瞭深入瞭解的興趣。這種拓展視野、增長見識的閱讀體驗,是我一直以來所期望的。而且,書中對人性的洞察也相當精準,它展現瞭人性中光明與黑暗的交織,以及在極端環境下人性的復雜變化。這種對人性的深刻挖掘,讓故事更具深度和現實意義,也讓我對周圍的世界有瞭更深刻的理解。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娛樂讀物,更是一本能夠引發思考、啓迪智慧的作品。
评分這本書最讓我著迷的一點,在於它塑造的那些鮮活的人物形象。每一個角色都仿佛擁有獨立的生命,他們有著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掙紮,以及自己不為人知的秘密。主角的內心世界被描繪得淋灕盡緻,他的每一次抉擇,每一次思考,都牽動著我的心弦。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糾結與痛苦,也能體會到他堅守原則時的孤勇。而那些配角,也並非簡單的背景闆,他們各自的性格特點都非常突齣,有時甚至會成為推動劇情發展的關鍵。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他們中的一員,又會做齣怎樣的選擇?這種設身處地的思考,讓我在閱讀的過程中,不僅是作為一個旁觀者,更像是一個參與者,深深地融入瞭故事之中。作者在人物對話的設計上也花瞭很大的心思,每一句對話都飽含深意,有時看似平淡,實則暗流湧動,充滿瞭暗示和反諷。我尤其喜歡那些充滿智慧的交鋒,每一次的唇槍舌劍都讓我拍案叫絕,也讓我對人物的洞察力有瞭更深的認識。
评分很好,但是有点小恐怖,
评分仅仅是为了阅读知识面而已
评分东西很不错,感受书海的浩瀚
评分晕,就是原来的《法医鉴证实录》(2008),换了个人翻译一遍,把前面的几十张照片插到正文里了,还以为作者又出新书了,郁闷!!对这种同一本书换个名字出版的事,就没人管吗?爱管闲事的广电总局哪去了
评分很不错,印刷精致
评分很好的书,作者构思精巧,逻辑严谨,娓娓道来,会好好阅读,收获很多。
评分很好的书,作者构思精巧,逻辑严谨,娓娓道来,会好好阅读,收获很多。
评分一直喜欢刑侦,法医手记之类的作品。希望读后有所收获。
评分还没看,信赖京东!运过来一点都没破损!速度更不用说!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大法医:人体实验室 [DEATH’S ACRE: Inside the Legendary Forensic Lab t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29501/566638fbN12fd21ac.jpg)


![爸爸给我讲故事 父爱让我更强大(女孩篇)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46012/rBEhU1JwyuAIAAAAAAj-ydpTEZQAAEyGwO0-FoACP7h13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