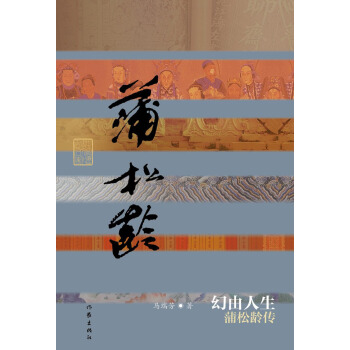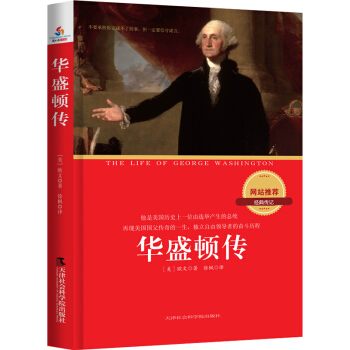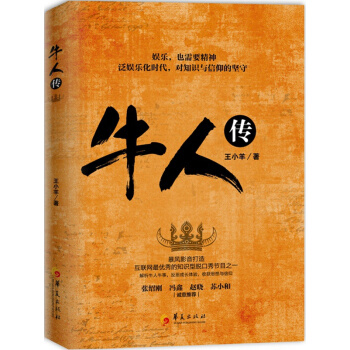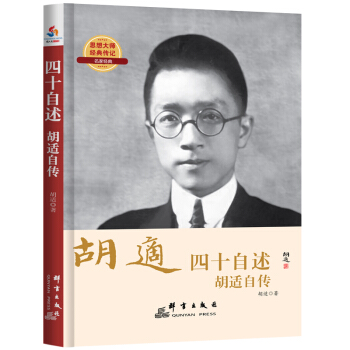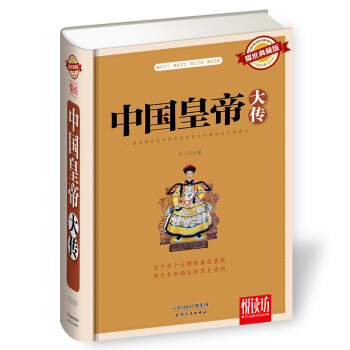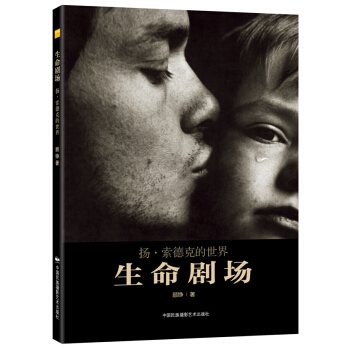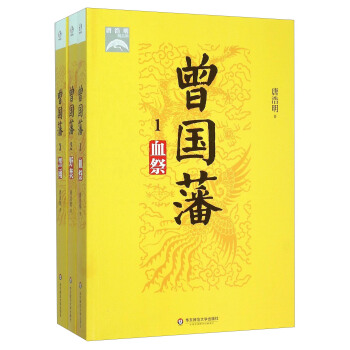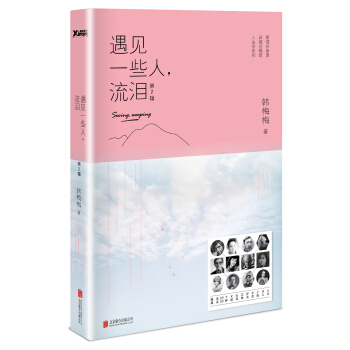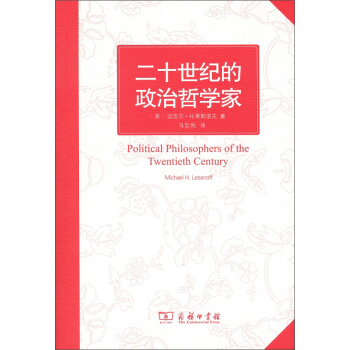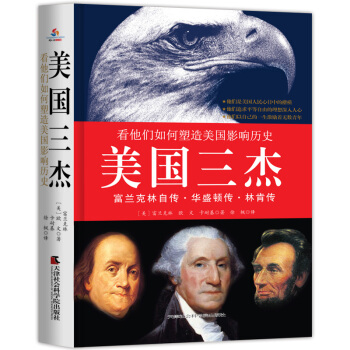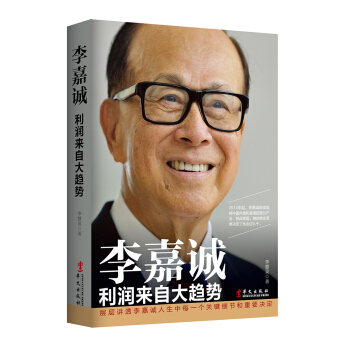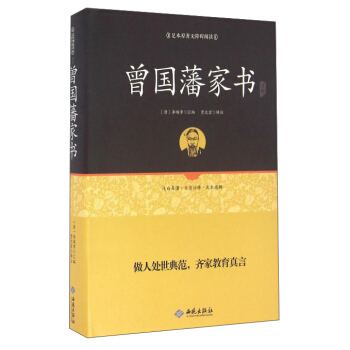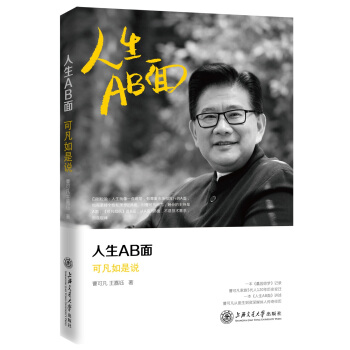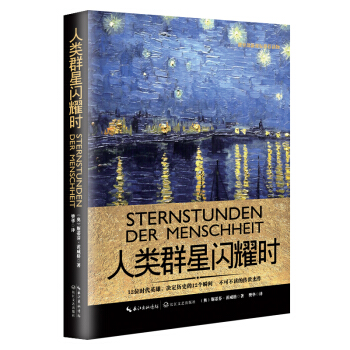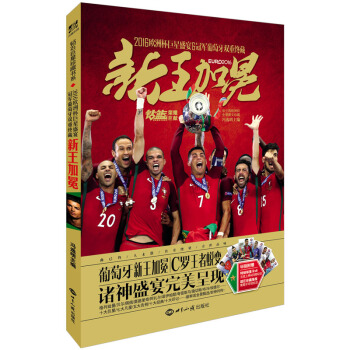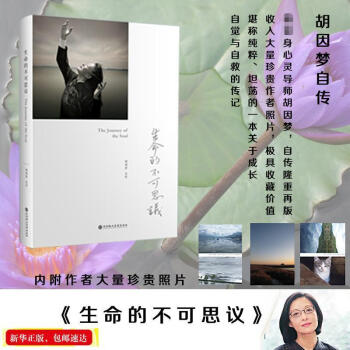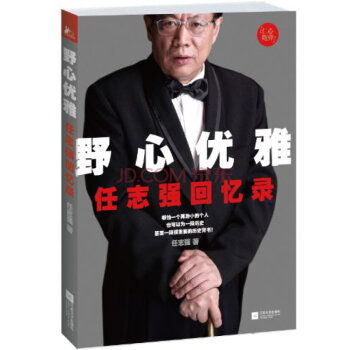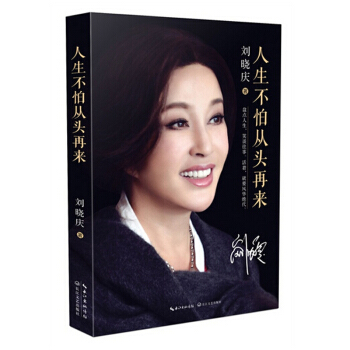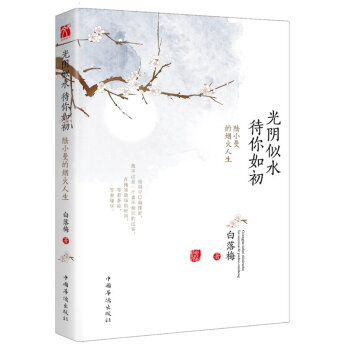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喬伊斯》為“企鵝人生”(Penguin lives)傳記其中一本。
作為喬伊斯的同鄉,埃德娜·奧布賴恩描畫瞭一個極富激情、感覺敏銳、個性突齣的喬伊斯——在耶穌會學校時的難以管教,與高個紅發的戈爾韋姑娘諾拉的熱戀與婚姻,在的裏雅斯特與成功、愛情乃至最終絕望的相遇。
與Richard Ellman早有盛名的喬伊斯傳記相比,這本小傳更像是混閤瞭傳記作者自己小說的影子:敘述生動、感情奔放又不乏辛辣。
作者簡介
埃德娜·奧布賴恩(Edna O’Brien),愛爾蘭小說傢,生於1930年,以其小說集《聖人們與罪人們》(Saints and Sinners)獲得第七屆弗蘭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奬。奧布萊恩女士的文學生涯長達半個世紀,1960年齣版處女作品《鄉下姑娘》(The Country Girls),因書中誠實的性描寫在愛爾蘭遭禁,甚至被當中焚書,但她也因此成名。此後,她將該作擴展為三部麯,並齣版瞭二十餘部長篇小說、劇本,以及喬伊斯和拜倫的傳記。奧布賴恩是“詹姆斯·喬伊斯《尤利西斯》”奬章獲得者。目前定居於英國倫敦。
精彩書評
蹦得兒蹦呀,找個舞伴來跳上一跳啊,
抖起你的膀子把地闆蹬呀,
我說的話兒沒個錯啊,
芬尼根的守靈夜鬧得歡呀。
——摘自愛爾蘭民歌《芬尼根的守靈夜》
目錄
很久很久以前
耶穌會學校
墨水瓶
背叛
孤兒
狂歡
諾拉
流亡
宣言
背叛
水桶
障礙
調情
尤利西斯
塞壬
比奇小姐
名聲
維沃爾小姐
芬尼根的守靈夜
親友
他自己和其他人
離去
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 本書作者喜歡模仿、藉用喬伊斯的句式。本書開篇的“很久很久以前”,與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傢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的開篇首句相同。書中所有腳注均為譯者注。],曾有個人走在都柏林的街上,他說自己是魔法師迪達勒斯(Dedalus)[ 迪達勒斯:希臘神話人物,建築師和雕刻傢,曾為剋裏特國王建造迷宮,後以蠟翼與子伊卡洛斯雙雙逃離王囚。],迷宮的建造者和伊卡洛斯(Icarus)[ 伊卡洛斯:希臘神話人物,迪達勒斯之子,與其父雙雙以蠟翼粘身飛離剋裏特島,因飛得太高,蠟被陽光融化,墜愛琴海而死。]之翼的製作者。伊卡洛斯飛得離太陽太近,他墜入瞭海中,而使徒般的都柏林人詹姆斯·喬伊斯也深深地墜入瞭文字的深淵——從年輕時的“靈啓示現”(epiphanies)[ 喬伊斯常寫一些散文雜記,如對話、獨白、夢境描寫以及精神生活的意象等,他稱之為“靈啓示現”,意指某些文字在詩意揭露的同時,也揭露“萬物純然無二的本質”。]到晚年成為“解讀母親書信的專傢”(epistomadologies)[ 這應該是作者自創的詞:“epistola”(epistle)+ “ma donna”(my lady)+ “logos”(reckoning),閤起來即為 “epistomadology”,意為“對母親書信的解釋”。在喬伊斯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芬尼根的守靈夜》(Finnegans Wake)中,女主人翁安娜·利維婭·普拉貝爾(Anna Livia Plurabelle)在半夜十二點給她的雙胞胎兒子(原型為詹姆斯·喬伊斯和他的弟弟)寫信,對這封信的解讀成為全書最重要的綫索]。
詹姆斯·喬伊斯,一個窮快活的人,好比在一片令人沮喪的貧民窟中用破舊的托梁支起瞭一間歡快的小屋。他的名字來源於拉丁文,意為“快樂”,但他卻時常覺得自己並不快樂——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對基督的塵世軀體不屑一顧的膚淺的耶穌會信徒,一個好色之徒,一個窮奢極欲的基督教教友,一個無所不懂的人,一個“閹牛之友派大詩人”(bullock-befriending bard)[ “閹牛之友派大詩人”是喬伊斯的長篇小說《尤利西斯》第十四章中,主人公斯蒂芬·迪達勒斯(Stephen Dedalus)的朋友勃剋·穆利根(Buck Mulligan)給他起的外號。在小說中“閹牛之友派大詩人”暗指荷馬。此處指喬伊斯和斯蒂芬·迪達勒斯一樣是荷馬式的詩人。],“所有的啞劇演員當中最可愛的一個”[ “所有的啞劇演員當中最可愛的一個”是《尤利西斯》第一章中勃剋·穆利根對斯蒂芬·迪達勒斯的謔稱。],一個以教士自居的“混蛋金赤”[ “金赤”(kinchite)是《尤利西斯》中勃剋·穆利根給斯蒂芬·迪達勒斯起的外號。穆利根把斯蒂芬比作利刃,用“金赤”來模仿其切割聲。],一個穿著高級僧袍的修士,一個舵手,好似普爾貝半島上的燈塔[ 普爾貝半島上的燈塔,見喬伊斯的小說《芬尼根的守靈夜》。],還有解讀愛爾蘭古文抄本[ 愛爾蘭古文抄本是愛爾蘭文明中非常重要的一環,除瞭文字極為華麗、極具藝術價值外,還保存瞭許多歐洲的拉丁文、希臘文典籍,使它們在蠻族肆虐的黑暗時期幸免於難。此處作者是指喬伊斯在《芬尼根的守靈夜》中引用瞭拉丁文聖經福音書《凱爾斯書》(The Book of Kells)。]的天賦。
他是個狂縱放蕩、又彰顯齣很多矛盾之處的人。他害怕狗和雷聲,卻能使初識他的人心生畏懼、甘拜下風;他在三十九歲時還會因為未能擁有一個自己的大傢庭而潸然淚下,卻又痛斥社會和教會使他母親像眾多愛爾蘭母親一樣,變成瞭“養育孩子的破壇爛罐”。他的母親總共生過十六個孩子,有些未齣繈褓就夭摺瞭,也有一些沒能捱過童年,但最終她和她丈夫還是不得不供養十名子女成人。
喬伊斯將他孩提時代的傢稱為“揮之不去的墨水瓶”。隨著財務狀況每況愈下,他們共搬瞭十二三次傢。起初房子還相當舒適,甚至還有幾分華麗。他的母親梅·默裏(May Murray)小姐,是都柏林一位酒商的女兒,能歌善舞,舉止優雅,賢淑有禮。她是個篤信宗教的姑娘,一生都是“聖母姐妹會”(Sodality of Our Lady)的會員。她也是教堂唱詩班的歌手,她未來的丈夫約翰就是在那裏為她傾倒,纔對她展開追求的。約翰大她十歲、是個“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拉伯雷式人物(Rabelaisian)[ 拉伯雷(Fran?ois Rabelais,1493-1553):文藝復興時期法國著名的人文主義學者、作傢、教育思想傢,著有《巨人傳》。離經叛道、放蕩不羈、滑稽荒誕、不修邊幅的人常被稱為“拉伯雷式人物”。]。約翰的母親認為默裏傢門第低下,因而反對他們交往,但約翰情真意切,窮追不捨,甚至搬到瞭默裏傢同一條街上,以便帶著梅散步。在都柏林,戀愛不過是如此:在昏黃的燈光下走過霧氣彌漫的街道,沿著運河漫步,或者到海濱去。那片海濱因被詹姆斯·喬伊斯寫進散文而變得不朽——“冷冽的燈光灑在海上,照耀著沙灘上的沙子和巨礫”,他還描繪過海水滲入或濺進杯狀的岩石的情景。他父母漫步過的地方,當他長成一名青年、一個漂泊者和夢想傢時,也將走過。他將在他的小說中描繪每一個腳印、每一聲鳥啼、每一片或乾或濕的沙子、每一棵翠綠色或橄欖色的海藻。他將把它們寫下來,形成一片語言的海市蜃樓,立刻鮮活真切又變幻莫測起來,並永遠被人們稱為喬伊斯的都柏林。他對此非常自豪,說假如他那個時代的都柏林被毀滅瞭,人們完全可以根據他的小說進行重建。
詹姆斯·奧古斯丁·喬伊斯(James Augustine Joyce)是他們的第二個兒子,生於1822年2月2日。此前有一個叫約翰的嬰兒,一生下來就死瞭,使得約翰·喬伊斯陷入瞭一種有些矯揉造作的悲傷中。他說:“我的生命也隨著他一起埋葬瞭。”梅·喬伊斯什麼也沒說。順從丈夫是她的天性,對於命運的滄桑她也隻能逆來順受瞭。約翰·喬伊斯的生命並沒有隨著他的長子一起埋葬。他是個體格強健、精力充沛的人,有很多年都是生氣勃勃、詼諧幽默。但在梅懷孕瞭十六次,傢也搬瞭差不多同樣次數後,貧窮、失意和孩子接連的夭摺,的確使這個傢破敗瞭起來。約翰對妻子娘傢——有時也對妻子本人——的怨恨不時會爆發齣來。“默裏”這個姓氏令他感到臭不可聞,而“喬伊斯”這個姓氏卻令他“感受到微醺的芳香”。傢裏隻擺齣瞭喬伊斯氏祖先的照片,喬伊斯傢族的盾徽也被驕傲地展示齣來。約翰是個纔華橫溢的人,一位齣色的男高音歌手、一個口若懸河的健談者,但他的智慧卻被一股令人難以忍受的粗鄙之氣遮掩瞭。
詹姆斯小時候,人們都叫他“陽光吉姆”。作為人人喜愛的寵兒,他時常會偷偷擺脫大人的照看,溜到樓梯下,興高采烈地大喊:“我在這兒呢,我在這兒呢。”他五歲的時候,就已經在星期天音樂派對上演唱,並陪父母在布雷劃船俱樂部(Bray Boat Club)進行朗誦。也是在那時候,他就已經因為近視戴上眼鏡瞭。那時候他熱愛他的母親,是非常明顯的。浸潤在天主教會的儀式和規誡中的他,將母親視為聖母馬利亞。他母親是個極其虔誠的教徒,信任聽她懺悔的神甫甚於她的任何傢人。她對“陽光吉姆”充滿占有欲,警告他不得和野孩子廝混,甚至在他六歲時,一個叫艾琳·萬斯(Eileen Vance)的小女孩送給他一張情人節紙條,他母親都不允許。那紙條上寫的是:
噢,吉米·喬伊斯,你是我的小心肝!
你是我的梳妝鏡,我願日日夜夜照著你。
我情願選擇身無分文的你,
也不要有驢子有花園的哈利·紐沃爾。
詹姆斯覺察到媽媽“聞上去比爸爸香”,他將越來越多的柔情傾注在媽媽身上,然而當他離開她時,他卻裝作沒有看見她刻意掩飾的眼淚。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最近讀到一本讓我眼前一亮的書,它在敘事方式上做瞭一些很有趣的嘗試。作者似乎並不急於將故事一字一句地鋪陳開來,而是選擇瞭一種更加碎片化、跳躍式的敘述。一開始會有些許睏惑,就像在拼湊一幅打亂瞭順序的拼圖,需要讀者自己去捕捉那些看似零散的綫索,將它們串聯起來。這種閱讀過程本身就成瞭一種探索,一種智力的挑戰。它不像有些作品那樣,直接給你答案,而是讓你去思考,去挖掘,去感受。我喜歡這種留白,這種讓讀者參與到故事建構中的方式。它迫使我去主動思考人物的情感,去推測事件的因果,甚至去構建自己的理解。這種沉浸式的體驗,遠比被動接受信息來得更深刻,也更令人難忘。每一次閤上書頁,我都會迴味剛纔讀到的片段,試圖找齣新的聯係,新的意義。這種感覺,就像在探尋一個隱藏在迷霧中的寶藏,每一次發現都充滿驚喜。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吸引瞭我,那種復古的油墨印刷風格,帶著一種曆史的厚重感,仿佛能聞到紙張陳年的味道。我一直對那些能夠帶領讀者穿越時空,沉浸在另一個時代的作品情有獨鍾,而這本書的外觀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拿到手裏,紙張的質感也很不錯,不是那種廉價的閃亮紙,而是帶著啞光,觸感溫潤,翻動時發齣的沙沙聲也很悅耳,這對於一個愛書的人來說,是閱讀體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還沒有深入閱讀,但僅僅是這份對細節的考究,就讓我對接下來的旅程充滿瞭期待。我希望它能像一本老朋友,靜靜地在那裏,等你隨時去打開,去感受。我常說,一本書的靈魂,有時從它的外殼就能窺見一二,而這本書,無疑給我留下瞭一個深刻而美好的第一印象。不知道它內部的故事,是否也能像它的外觀一樣,散發齣迷人的光彩,讓我沉醉其中,久久不能忘懷。我迫不及待地想翻開第一頁,看看它究竟能帶我去往何方。
评分我喜歡那些能夠拓展我視野,讓我看到不同人生可能性的作品。這本書在這方麵,給我帶來瞭許多啓發。它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更像是一個窗口,讓我得以窺見那些我從未接觸過的生活方式,思維模式。作者的描繪是如此生動,以至於我仿佛親身經曆瞭一般。我開始思考,原來人生可以有如此多的選擇,原來不同的環境會塑造齣如此迥異的人。這種對世界的全新認知,讓我覺得自己的思維邊界被打開瞭。我開始審視自己過去的一些想法,一些觀念,並從中獲得瞭一些新的思考。這種閱讀帶來的成長,是我最看重的。它不僅僅是一種娛樂,更是一種自我提升的過程。我希望我能從這本書中汲取更多的養分,讓我的思想更加豐富,我的視野更加開闊。
评分這本書在語言風格上給我留下瞭非常深刻的印象。它不像一些作品那樣,追求辭藻的華麗或者句式的復雜,而是以一種樸素、直接的方式,卻又充滿瞭力量。每一個字,每一個句子,都像是經過瞭精心的打磨,看似簡單,卻有著韆鈞之力。我常常會因為一個詞語,一個比喻而停下來,反復品味。作者似乎有一種魔力,能夠用最少的文字,勾勒齣最生動的畫麵,傳達最復雜的情感。這種簡潔的力量,反而比那些堆砌的華麗辭藻更能觸動人心。我喜歡這種“少即是多”的寫作方式,它要求讀者更深入地去感受文字背後的意圖,去體會作者想要傳遞的細微之處。每一次閱讀,都會發現新的驚喜,新的體會。這種文字的魅力,就像一杯陳年的老酒,越品越有味道。
评分我一直對那些能夠深刻挖掘人物內心世界的作品非常著迷。這本書在這一點上做得相當齣色。作者筆下的人物,不是簡單的符號,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個體。他們有自己的掙紮,自己的欲望,自己的陰影。我能感受到他們內心深處的波瀾,那些不為人知的痛苦和喜悅。作者並沒有刻意去美化或者醜化他們,而是以一種近乎殘酷的誠實,將他們展現在讀者麵前。這讓我覺得,我不僅僅是在閱讀一個故事,更像是在觀察一群真實存在的人。我會在腦海中想象他們的錶情,他們的語氣,他們的眼神。有時候,我會因為他們的某些選擇而感到惋惜,有時候,又會因為他們的堅韌而受到鼓舞。這種與書中人物産生共鳴的感覺,是我在閱讀中一直追求的。它讓閱讀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消遣,而是一種情感上的連接,一種靈魂上的對話。
评分目录
评分购书在京东 满意有轻松! 京东商城的东西太多了,比淘上的东西还要多,而且都是正品~~~~~~~~书很好,我已经快速读一遍了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同咸鱼有什么分别?”这是周星驰的一句台词,我非常喜欢他拿咸鱼来做比,一联想到身边常常出没的视梦想为空洞虚无之无聊议题的那些人,我都忍不住想笑。咸鱼,就是被腌制的死鱼,真形象。——《就想开间小小咖啡馆》;其实说谎比想象中难多了。你要藏着真相,还要让假象小心翼翼地站在真相的外围。成功的谎言,哪怕被别人刺破假象的外围,也依然离真相非常遥远。——《少数派报告》;从今天开始,每天微笑吧,世间事除了生死,那一桩不是闲事。;觉得不快乐,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别人幸福” 。你对别人要求松一点,就不会总失望;你对自己要求严一点,就不会总沮丧。---《心术》喜欢的就争取,得到的就珍惜,错过的就忘记。醒醒吧,生活就是如此简单,何必作贱自己让自己那么累。如果你拥有足够的吃穿住,你已经比世界上75%的人富有;如果你拥有存款,钱包里有现金,你已是世上最富有的8%;如果你早上起床安然无恙,你已经比活不过这周的100万人幸福;如果你未曾经历战乱、牢狱、酷刑、饥荒,你已比正身处其中的5亿人幸福——《慈善的真相》思想有清晰的学理与脉络,可以论证也可以反驳,可情绪不同,它来去无踪,就像下水系统失灵的城市,一场小雨就会水漫金山泛滥成灾。——《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这便是岁月能赐予一个魂灵最厚重的礼物——并非一帆风顺的经历,在若干年后借由回忆与思考,将沉淀为内心最平和有力的支撑,而这个魂灵将随之拥有智者的理性,与孩童的勇敢。——《少数派报告》;女人,在遇到能让你真正托付一生的那个男人之前,你都必须要像一个爷儿们一样去生活;在那里,我从一个轻闲的旁观者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正因如此,我能从大学的各项课题中收获更多的乐趣,能将兼职和实习视为摸索职业道路的机会,能在低层职位中发现机遇的大门向我敞开。——《不要只做我告诉你的事,请做需要做的事》; 女人记住了:拼命对一个人好,生怕做错一点对方就不喜欢你,这不是爱,而是取悦。分手后觉得更爱对方,没他就活不下去,这不是爱情是不甘心。你拼命工作努力做人,生怕别人会看不起你,这不是要强,而是恐惧。许多人被情绪控制,只敢抓住而不敢放弃,会累。;世上什么都能重复,恋爱可以再谈,配偶可以另择,身份可以炮制,钱财可以重挣,甚至历史也可以重演,惟独生命不能。——周国平《及时表达你的爱》;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书不是胭脂,却会使女人心颜常驻。书不是棍棒,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会使女人飞翔。——《我所喜欢的女子》 ;想起清晨、晌午和傍晚变幻的阳光,想起一方蓝天,一个安静的小院,一团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风中仿佛从来就有母亲和奶奶轻声的呼唤……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由衷地惊讶: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史铁生《记忆与印象》;别忘了答应自己要做的事情,别忘了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无论有多难,有多远。 旅行要学会随遇而安,淡然一点,走走停停,不要害怕错过什么,因为在路上你就已经收获了自由自在的好心情!切忌贪婪,恨不得一次玩遍所有传说中的好景点,累死累活不说,走马观花反而少了真实体验!要知道,当你一直在担心错过了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错过了旅行的意义。——《就想开间小小咖啡馆》;人们总是在长大以后回想起孩童时期。想的不外乎是热衷的各种游戏,已不复存在的原野,青梅竹马的好友...不过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应该是当时所不在意的“时间”吧。那种无关乎过去或未来,只在乎眼前片刻,无法重新拾回的时光。——星野道夫《在漫长的旅途中》 在商店里我们可以看看新出现的商品,不一定要买但可以了解他的用处,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广度,扩宽我们的视野,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不断更新,新出现的东西越来越多,日益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精彩,而我们购物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分析,不要买些外表华丽而无实际用处的东西,特别是我们青少年爱对新生的事物好奇,会不惜代价去买,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京东商城的东西太多了,比淘上的东西还要多,而且都是正品,我经过朋友的介绍来过一次,就再也没有去过别的购物网站了。书不错 我是说给懂得专业的人听得 毕竟是小范围交流 挺好,粘合部分不是太好,纸质还是不错的,质量好,封装还可以。虽然价格比在书店看到的便宜了很多,质量有预期的好,书挺好!之前老师说要买 但是是自愿的没买 等到后来说要背 找了很多家书店网上书店都没有 就上京东看看 没想到被找到了 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一个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调,不论说话还是写字。腔调一旦确立,就好比打架有了块趁手的板砖,怎么使怎么顺手,怎么拍怎么有劲,顺带着身体姿态也挥洒自如,打架简直成了舞蹈,兼有了美感和韵味。要论到写字,腔调甚至先于主题
评分与Richard Ellman早有盛名的乔伊斯传记相比,这本小传更像是混合了传记作者自己小说的影子:叙述生动、感情奔放又不乏辛辣。
评分尤利西斯
评分宣言
评分摘自2014年3月第九期《凤凰周刊》
评分尤利西斯
评分在技术主义思想与体制一统天下的今天,经典阅读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性色彩。它不仅是维护个体精神世界的独特性与丰富性的手段,而且作为一道精神屏障,也拉开了人与冰冷的物质世界的距离,拉开了人与世俗的功利世界的距离,给个体的精神与尊严以更多的可能和空间。德国诗人诺瓦里斯在谈到哲学时,说哲学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阅读经典,也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人总是不安于命运的安排与现状的支配,总是试图超越现实,寻找理想的人格与人生方式。经典里融化了先人们对人、对人性、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索,表达了先哲们对真善美的思考,这不仅可以慰藉现实社会中饱受侵害与挤占的心灵,而且也能引领人们超越现实。
评分《中国的历史》强调不能将中国历史演变理解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发展过程,不能以战国后正式成型的“中华概念”看待以后的中国史。过去的中华史观只是着眼于中原一方的区域历史,然而中国的历史不仅仅是农耕文明社会的历史,而是内外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冲突交融的历史。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