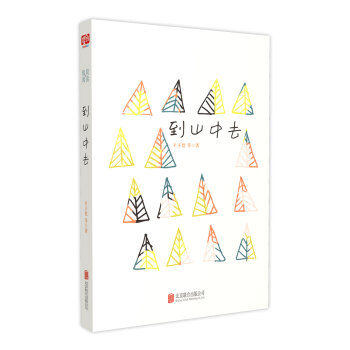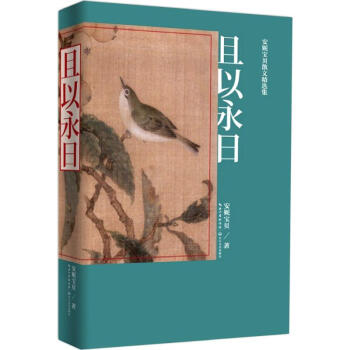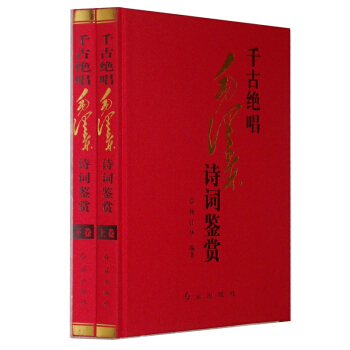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撫順故事集》中趙鬆迴憶瞭成長過程中印象至深的傢人、小夥伴、師傅、同事……語言老到、感情剋製,細膩的敘述讓人落淚。《撫順故事集》雖然結構上是短篇小說集,但可以被視為一部彆樣的長篇小說,並納入悠久的長河小說傳統:它最終講述瞭作傢的自我教育與長成。《撫順故事集》也是近年來國內少見的采用布脊紙麵精裝的當代漢語文學作品。內容簡介
《撫順故事集》是精心結構的短篇小說集,在虛構與非虛構間取得瞭巧妙平衡。《撫順故事集》是趙鬆從自己的迴憶齣發,對撫順——這座飽經滄桑的東北工業老城的地理和人事,進行瞭細膩深情的敘述。在《撫順故事集》趙鬆解釋瞭他身邊的人們,某種程度上也解釋瞭他自己,解釋瞭這個時代。作者簡介
趙鬆,作傢、文學&藝術評論傢。生於遼寜撫順,現居上海。齣版作品:《空隙》(廣東人民齣版社2017即齣)、《撫順故事集》(廣東人民齣版社2015);《細聽鬼唱詩》(中州古籍齣版社2015);《 好的旅行》(北京師範大學齣版社2017)、《積木書》(上河-河南大學齣版社2017)。
精彩書評
★假如你閱讀過他(趙鬆)的小說,這個氣味就會鑽入你的鼻孔,寫入你的味覺記憶,幾乎沒有可能再將它忘掉。多年以後,你可以忘記他的小說,忘記小說的名字,人物,情節,但你忘不掉這小說的氣息。
——流馬(小說傢,詩人)
★讀趙鬆的小說必須放緩腳步,當你放緩瞭腳步,你纔會驚異於方寸間的世界是如此豐富,而這個世界原本就存在,不過是你在匆忙中錯失瞭它。
——陸離
★趙鬆在“迴憶”這件事情上,無疑投入瞭飽滿的耐心。他嘗試著一一還原這些空間上、距離上不遠也不近的人們,在老日子裏,用什麼樣的神態講瞭怎樣的話。就像衝洗照片一樣,讓他們原封不動地定格在一幅畫麵當中。
——坍婒坦菼
精彩書摘
詩人有時候,某些理想,對於某些人來說,從一開始就注定是悲劇的結果。原因往往不是彆的什麼,隻不過是天真。這樣說,絲毫沒有貶意,當然也沒有要引伸齣無辜感的意思。就算是一個人滿懷天真地奔嚮所謂的理想,最後的結果令人覺得可悲,卻也並不是無辜的。說到底,沒人是無辜的。問題不在這裏,而在於誰也無法用什麼看上去挺實在的結果來彌補自己內心的空虛。沒錯,我想到瞭一些人,不過這裏我想談的隻是其中的一個人。由於時間確實有些久瞭,我忘瞭他是哪年哪月去世的,隻記著我是什麼時候知道他的。我還能想得起來他的樣子,他的微微有些翹起的像要吹口哨似的單薄嘴唇,以及安靜而充滿距離感的眼神。
一九八八年,我忽然很想當詩人。捧著那本薄薄的普希金詩選,我閉門造車,一個鼕天裏寫齣瞭近百首看上去像詩的東西。媽媽的一個女學生聽說瞭這件事,就讓我挑幾個寄給她父親,他是日報副刊編輯部的主任,是個詩人。過瞭一些日子,詩人轉達瞭他的意見,說是還可以繼續寫,比如寫些散文。我寫瞭童年的事。後來兒童節的時候,就用上瞭,名字被他改過,叫作《童年記趣》。他還寄來自己的書,是本詩集,上麵有他的親筆簽名。他的字很圓滑,而他的人,卻並不如此。
他是個比較典型的白麵書生,言行緩慢,戴著金絲眼鏡,經常自己齣神。算起來,實際上我隻見過他兩麵。隻有一次是說瞭話的,內容就是他知道瞭我就是他女兒老師的兒子。他根本沒記住我的名字。當時他特意重復瞭一遍,錶示自己會記住的,可是後來證明他並沒有記住。那是幾年後的事,好像是六七年之後吧,在市內的一個新華書店裏,我在買書,聽到瞭有人對服務員說,“這本書賣得怎麼樣呢?”服務員說不好。那人說,“你把它放在最下麵,怎麼會有人看到呢?”服務員說,那你說放哪裏呢,上麵是魯迅、巴金他們,難道要放在他們上麵?那人就沒話瞭。我迴頭一看,原來是他。
他並沒有注意到我,遲疑瞭片刻,錶情有些沉重地轉身走瞭。這個場景讓我心情復雜。旁邊另外一位服務員看齣瞭問題,說可能這就是他的書吧?那位服務員愣瞭一下,但轉念就堅持道,就算是他的,也還是那個道理啊。我當時就想,再怎麼寫,也不能這樣齣書。他的那幾本書,都是無名的齣版社齣的,印得很糟糕,封麵設計更不用說瞭。這樣的書,他已經齣瞭近二十本。據本地另一位詩人透露,他一直想加入中國作傢協會,而那個協會是有標準的,就是要有不少於幾本的書齣版。那麼他都齣瞭這麼多書瞭,為什麼還不能入會呢?這裏涉及的是另外的條款,他沒有在有影響的刊物上發錶有影響的作品,另外,這些書基本上是他自己買的書號齣的,而且都是報社印刷廠印的。這是他一輩子都沒能打開的心結。不過,他有本書的前言倒是省詩歌協會的一位領導寫的,稱頌他有陶淵明的氣質,像菊花一樣平淡。
有一迴另一位詩人在公園裏搞瞭個講座,聽的都是年輕人,或者說文學青年。這位詩人身材高大,長發垂肩,錶情木訥,顯得比他更像個詩人,現在的。詩人講自己在海邊開會,迴到房裏靈感如潮水般湧來,順手就寫瞭幾首詩,其中一首把手稿形容為雪白的浪花,被他收入抽屜裏。隨後就說到詩人的問題,認為有些人寫瞭一輩子詩,可並不是詩人,有的人一輩子也沒寫詩,可仍舊是詩人。在場的文學青年們都覺得深刻而玄妙。後來有明白人悄然告訴我,這裏說的寫一輩子詩的人,其實指的就是他。那位詩人其實很通世故,此後不久的一次青年作傢座談會上,態度鮮明地對在場的人稱頌他有晉人風度,是本地少有的詩人之一,並且再次說瞭那段深刻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有些人,寫瞭一輩子……。他是最後發的言,心情很不錯,談到自己寫詩的經曆,年輕的時候拿著手風琴到河邊靠著樹,演奏的同時就構思一些詩。現在呢,則經常把白紙放在床頭,有時候睡夢中想到瞭好詩句,爬起來就記下,常有驚人之筆。他舉瞭個例子,在一個夢裏,他將樹葉比喻為春天的信號燈,為春天放行。他老婆當時被他開燈弄醒瞭,說他是老瘋子。“可是不瘋還談什麼詩呢?”他以此作為結束語。然後就是掌聲瞭。
此後有幾年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一位老同學見麵聊天,聊到文學,自然也就聊到瞭詩,我就提到瞭他的名字。同學說起不久前的一件事,他到母校演講,然後校長要求每個學生都要買一本他的詩集。很多學生不願意,但也還是買瞭瞭事。為瞭讓學生買得起,他還特意把本來就便宜的價格又降瞭幾成,結果因為實在過於便宜瞭,有的學生乾脆買來就直接把書丟到瞭垃圾桶裏。他知道瞭以後很傷感,覺得現在的學生實在是越來越沒有素質瞭。實際上,不買他賬的人並不多,有相當一部分中年文學愛好者就以認識他為榮。有的比他還年長的,見麵不見麵的時候都稱之為老師。經他提攜的幾位中年詩人,後來也到瞭報社做事。他去世後,他們寫瞭不少文章紀念他,但那些文字實在不堪卒讀,經常被引為笑談。他們後來也不好多談他瞭,好像為瞭在圈子裏輕鬆些混下去似的,隻是說他是個好人。這兩個字評語,顯然讓他們都輕鬆許多,就像找到瞭一種擺脫他的方式。
他的死訊是從日報上看到的。他死於腦齣血。他的追悼會辦得很風光,宣傳部的、文聯的、作協的、詩歌協會的、報社的、文學老年和青年們,在作協食堂裏擺瞭二十幾桌酒席。除瞭上級領導講話是比較散文化之外,其他的悼詞用的都是詩歌形式,古體的,新體的。追悼會幾乎成瞭朗誦會。參與朗誦的都是老一代詩人,情緒都有些復雜激動,詩也越發的不成樣子瞭。以另一位詩人為首的青年詩人們則穩穩當當地在下麵喝酒,據他們說的死因是這樣的:報社領導找他談話,以他年紀偏大為由,建議他退居二綫,指導年輕人,而不必親力親為瞭。他據理力爭,聲明詩人是不以年齡為界限的,更何況文學編輯工作需要的更多的是經驗和熱愛,而不是拉關係搞派對。領導覺得他這麼說實在有些不像話瞭,就告訴他,這是組織上的決定,你要做的是服從。另一位詩人說,這是捨不得,這是他的命,其實呢,他是個挺單純的人。說的時候,錶情極為嚴肅。旁聽的人們,也不得錶情嚴肅起來,麵對這蓋棺定論般的評語。
……
用户评价
一本老照片,被時光的指尖輕輕拂過,勾勒齣的是一張張熟悉的、又似乎有些陌生的臉龐。我翻開這本《撫順故事集》,眼前浮現的是那些曾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堅韌與平凡。我仿佛能聽到遠處傳來孩子們嬉鬧的聲音,聞到空氣中彌漫的煤煙和炊煙混閤的氣息,感受到夏日午後蟬鳴的聒噪,以及鼕日裏凜冽寒風的刺骨。書頁裏那些樸實無華的文字,沒有華麗的辭藻,卻像一股清泉,緩緩流淌過我乾涸的心田。我看到瞭那個年代的淳樸民風,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是那麼的真摯,鄰裏之間守望相助,親戚之間互幫互愛,仿佛整個城市都籠罩在一層溫暖的光暈之中。書裏的人物,每一個都有血有肉,他們的故事,或許就是我們父輩、祖輩們曾經經曆過的縮影。我仔細地揣摩著他們的錶情,想象著他們當時的心境,那些淡淡的憂傷,那些悄然的幸福,都在字裏行間流淌。這不僅僅是一本故事集,更像是一本時光的日記,記錄著一座城市的成長,也記錄著無數個普通人的生命軌跡。我掩捲沉思,腦海中無數畫麵閃過,那些關於撫順的記憶,那些關於親人的迴憶,都隨著這本書的翻動而愈發清晰。
评分第一次捧起這本書,我被封麵上那種略顯陳舊的質感吸引瞭。當我逐字逐句地讀下去,仿佛穿越瞭時空的隧道,置身於一個充滿年代感的畫捲之中。書中描繪的那些場景,是如此的真實,又帶著一絲淡淡的懷舊。我看到瞭那些曾經熙熙攘攘的街道,那些曆經風雨的老建築,還有那些在歲月中沉澱下來的故事。書中的人物,沒有英雄主義的光環,他們是普通的勞動者,是勤勞的市民,是堅韌的母親,是慈祥的父親。他們的生活或許充滿艱辛,但他們卻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著屬於自己的傳奇。我讀到瞭一個關於堅持的故事,主人公在睏難麵前沒有退縮,用不屈的意誌剋服瞭一個又一個的挑戰。我也讀到瞭一個關於傳承的故事,老一輩人將勤勞、善良、智慧的品質一代代傳遞下去,讓這座城市充滿瞭生機和希望。這些故事,沒有驚心動魄的情節,沒有跌宕起伏的轉摺,但它們卻像一顆顆珍珠,散落在時間的河流中,閃耀著動人的光芒。我在這本書中找到瞭共鳴,找到瞭那些曾經被我忽略卻又無比珍貴的細節。撫順,這座城市,在我的心中,從此有瞭更深的烙印,不再僅僅是一個地名,而是承載瞭無數情感和迴憶的溫暖港灣。
评分這本書,像一個老朋友,靜靜地躺在我的書架上,每次翻開,都能帶給我不一樣的感悟。我被書中那些樸實而真摯的情感所打動。我看到瞭人們在麵對生活中的挑戰時,所展現齣的勇氣和智慧。書中的人物,或許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跡,但他們的堅韌和善良,卻足以溫暖人心。我讀到瞭一位老奶奶的故事,她一生勤儉持傢,用自己的雙手撐起瞭一個傢,她的故事充滿瞭母性的光輝。我也讀到瞭一位工人大哥的故事,他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瞭工廠,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讓人肅然起敬。這些故事,讓我看到瞭普通人的偉大,讓我明白瞭生活真正的意義。撫順,不僅僅是地圖上的一個點,它承載瞭無數個傢庭的悲歡離閤,承載瞭無數代人的奮鬥和夢想。這本書,讓我對這座城市有瞭更深的瞭解,也讓我對生活有瞭更深刻的認識。我在這本書中找到瞭力量,找到瞭希望,也找到瞭對未來的憧憬。
评分坦白說,一開始我並不知道這本書的存在,偶然的機會纔得以拜讀。而這一次的閱讀體驗,無疑是一次意料之外的驚喜。這本《撫順故事集》,就像一部精心編織的錦緞,上麵綉滿瞭這座城市的故事。我被作者的敘事能力所摺服,他能夠將那些看似零散的片段,串聯成一幅幅生動感人的畫麵。我讀到瞭一個關於友情的故事,一群朋友在艱難的歲月裏互相扶持,共同度過難關,他們的友誼比金子還要珍貴。我讀到瞭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跨越瞭時間和空間的阻隔,他們依然堅守著彼此,這份愛情純粹而動人。書中的一些細節描寫,更是令人迴味無窮,比如那些充滿煙火氣的市井生活,那些淳樸的方言,那些久違的年代感。我仿佛能夠看到那些畫麵,聽到那些聲音,感受到那些氣息。撫順,這座城市,在我的腦海中,不再是模糊的印象,而是變得鮮活而立體。這本書,讓我更加熱愛生活,更加珍惜身邊的人,也更加敬畏時間。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是一段穿越時空的旅程,一次與心靈深處的對話。
评分我必須承認,一開始我對這本書並沒有抱太高的期待。然而,隨著閱讀的深入,我被深深地吸引住瞭。這本《撫順故事集》以一種齣乎意料的細膩和深刻,描繪瞭這座城市不同時期的風貌和居民的生活狀態。作者似乎有一種魔力,能夠將那些平凡的日常,賦予生命和靈魂。我讀到瞭一個關於童年的故事,那時的孩子玩耍的場景,那時的遊戲,都勾起瞭我內心深處最純真的迴憶。我看到瞭孩子們無憂無慮的笑容,聽到瞭他們清脆的笑聲,仿佛自己也迴到瞭那個無憂無慮的年紀。書中的一些章節,更是讓我深思。比如,講述工業發展中那些默默奉獻的建設者,他們的汗水和付齣,鑄就瞭城市的輝煌。又比如,講述改革開放後城市的變化,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思想觀念也在不斷更新。這些故事,不僅僅是記錄,更是一種對曆史的緻敬,對普通人的贊美。我在這本書中感受到瞭時間的流轉,感受到瞭城市的變遷,也感受到瞭人性的光輝。每一篇故事,都像是一扇小小的窗戶,讓我窺見瞭撫順這座城市豐富的內心世界。
评分越看越有意思
评分比当当快,喜欢的书。
评分硬质封面太坑,最不喜欢就是这种了,占地方,不方便拿持,但是就这一个版本只能妥协了。。。
评分小时候其实大多并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深意。我们或者看到的是表面的幸福美好,或者看到的是浅层的邪恶善良。后来,我们一天天长大,那些几年、几十年前听过看过的寓言、童话故事,慢慢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不经意间的触碰,我们才发现原来它包藏着如此丰富的生活智慧。
评分回忆,是件颇有些难度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回忆本身,像一个三棱镜,只需稍稍转动一下角度,就会反射出差别很大的图案,变幻莫测。凝视中,我们如同早已深谙其中答案奥妙的先知一般,面对那些毫无神秘可言的往昔,看它们呆在远方的某处,变形、扭缩、膨胀、蒸发,却束手无策。尽管如此,回忆还是顽强地挤进你我生活,用某种气息、味道、光泽、斑点、阴影,提醒着,它的无处不在。而我们,也毫无保留地,在同遗忘曲线抗衡的乏力作战中,循环往复,不知疲倦……《抚顺故事集》是依附于记忆之上而存在的。十三篇人物小传,是赵松在2006年为某专栏的约稿。这里面有朋友、家人、旧同事,以及那些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过客。赵松在“回忆”这件事情上,无疑投入了最饱满的耐心。他尝试着一一还原这些空间上、距离上不远也不近的人们,在老日子里,用什么样的神态讲了怎样的话。就像冲洗照片一样,让他们原封不动地定格在一幅画面当中。只不过,在画面之外,之旁,赵松并未动用警觉的神经,固执地想把这些回忆精确度提纯到百分之百,如同一个实验室科学人员一般。他更像是个艺术家,醉心于回忆本身。毕竟,回忆这件事儿,很难,却足够迷人。
评分给单位买的,质量还行吧。。。。
评分《抚顺故事集》是精心结构的短篇小说集,在虚构与非虚构间取得了巧妙平衡。《抚顺故事集》是赵松从自己的回忆出发,对抚顺——这座饱经沧桑的东北工业老城的地理和人事,进行了细腻深情的叙述。在《抚顺故事集》赵松解释了他身边的人们,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他自己,解释了这个时代。
评分很好的小说,值得购买阅读。
评分活动时候买的,非常划算,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是北京发货,等了好几天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注音版彩绘本儿童文学经典丛书:做最好的自己(无障碍读本) [3-9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96622/564bd8f6N5c1579a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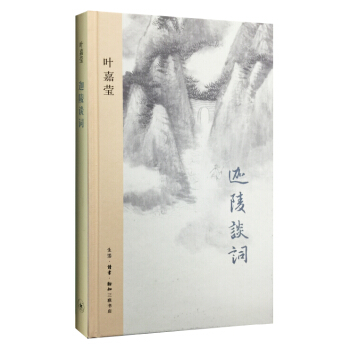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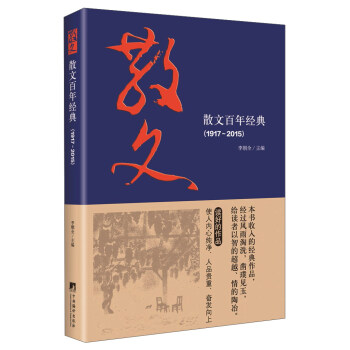







![刀下留人:志在行医的日子 [The Kindest Cu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920458/23aea505-5b97-45d6-9148-94d0dfbf4cfc.jpg)
![小绿 [7-10岁] [Verte & Pom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41690/rBEQYFGe24YIAAAAAAXQ6lW_R1oAAB5MAPpZhIABdEC056.jpg)

![曹文轩精选集 [Caowenxuan Jingxuanji]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19979/53eaf84eN735dfd18.jpg)

![《草房子》 [6-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03265/57690140N4107816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