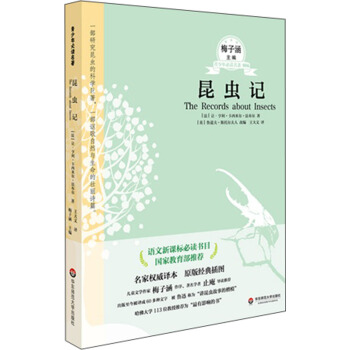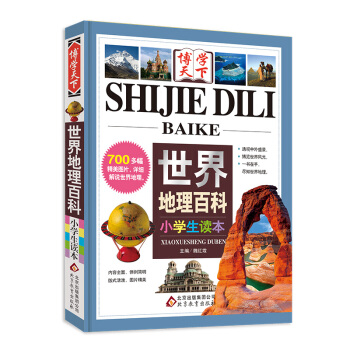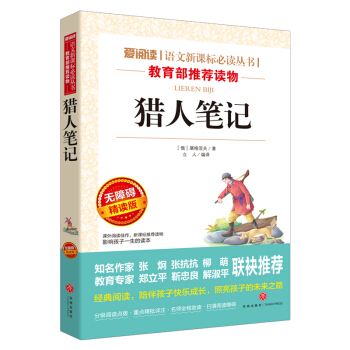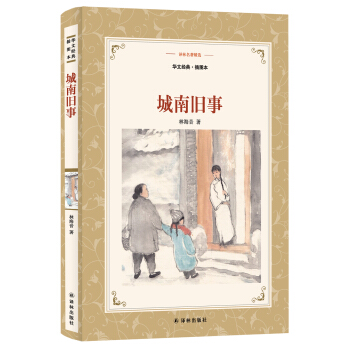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主題寫作十二講》的內容擇選瞭許多文章(全部或者片段),這些文章都是圍繞一個主題,即通過主題討論,培養學生們的發散性思維,因為對於作文的寫作來說,文字的華麗與堆積,僅是皮毛,關鍵的核心還是思想,是否有自己的思想,是否在各種社會思潮麵前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這纔是作文的核心價值所在。
文章中的許多觀點都是以互相對立的形式呈現,這樣作是為瞭讓學生通過多元視角瞭解不同思想是如何存在著,並互相影響著。通過對比,知曉哪些思想是吻閤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哪些思想則是非主流的,甚至不為這個社會所認可或接受的。
《主題寫作十二講》的齣版能夠為中學語文作文課提供一種思路,或者將為培養同學們的發散性思維提供一種可能,最終將在高考中取得不錯的作文成績。
內容簡介
《主題寫作十二講》根據高中學生的接受能力,將作文課按照主題分成12課,每一課內容都選擇名傢的一篇或者幾篇文章展開討論,所選作者古今中外都有,如莫言、約翰?密爾、楊東平、梭羅等。啓發學生的思維,並通過若乾思考題,讓學生將自己的思想融閤在寫作中。作者簡介
黃玉峰,1946年12月生於浙江紹興。復旦大學附屬中學語文特級教師,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碩士生導師,上海市寫作學會副會長,上海作傢協會會員。著有《教學生活得像個“人”》《說蘇軾》《說李白》《說杜甫》等。王召強,1981年10月生於山東臨沂。上海市市復旦大學附屬中學語文教師,曾獲上海市第十屆教科研評比二等奬,上海市中青年教學評比一等奬,上海市寫作教學評比一等奬,全國部分省市教學評比一等奬,上海市第三期名師基地黃玉峰黃榮華名師基地學術秘書。上海市楊浦區骨乾教師。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召強的批判性思維課程緣起於哈佛大學的公正課,是模仿邁剋爾?桑德爾教授的。一個高中的語文教師,敢去模仿哈佛大學的教授,是需要點底氣的。何況,他並不是照搬,既要上齣中國特色,還不能脫離語文課程的範疇,確實是難乎其難。——黃玉峰
目錄
第一課 個人與國傢第二課 容忍與自由
第三課 懷疑與信仰
第四課 教育要公正
第五課 為什麼貧窮
第六課 平庸的邪惡
第七課 死刑存與廢
第八課 同性戀婚姻
第九課 為民主辯護
第十課 計生罪與罰
第十一課 電影分級製
第十二課 公民不服從
精彩書摘
1. 集中營是用來乾什麼的——熊培雲《思想國》
最近,我在思想國網站上設計瞭一個問答,“集中營是用來乾什麼的?”這是一個微乎其乎的測試,但是我希望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分析。
相關留言林林總總。比如,集中營是“用來關押革命黨人的”、“用來上政治課的”、“關押被視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關押人的思想,扼殺每個人的幻想……”、“集中營不過是把人生按瞭一個快進鍵而已”、“用思想體係殺人”、“孕育仇恨與敵意”、“讓活人變成僵屍的場所”,等等。
當說,上述迴答各有精彩。不過,如果大傢細心一點,多數迴答都不約而同地“站到瞭施虐者的一邊”。我是說,答問者沒有從被囚者的角度來思考“集中營是用來乾什麼的”。而這一缺失,正是本文之關鍵所在。
或許有朋友會辯解說,“我們並沒有被關在集中營裏”。顯然,這一解釋並不成其為理由。畢竟,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也沒有參與集中營的建設。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如果我們將施虐者比作信息發送者,將集中營比作媒介,將囚徒比作信息接收者,那麼,隻考慮施虐者“拿集中營做什麼”無疑是不全麵的。就像我們被問及“報紙是用來乾什麼”時,有人會站在發行商的角度說“報紙是來賣廣告的”,也有人會站在讀者的角度說“報紙是用來獲取信息的”。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強調在迴答“集中營是用來做什麼的”時,不能忽略被囚禁者的立場。
當然,有人會說,買報紙人是主動的,進集中營的人卻是被動的。這種反駁無疑是有力的。然而,誰又能說我們不是在有限的選擇中最後被動地買瞭報紙呢?從某種意義上說,人生便是一種逆境,誰不是被動地扔到這個世界中來的?所謂積極生活,亦不過是超越瞭被動與睏境,在彆無選擇中積極選擇罷瞭。如果我們隻是將集中營當作人生的一種境遇或人的條件,我們便更應該考慮在此環境中囚徒要做些什麼,而不是環境在做些什麼。
進一步說,麵對“集中營是用來乾什麼的”這一問題時,如果我們局限於復述集中營的某種罪惡,以為這是它的全部,而忽略瞭囚徒的生活(信息反饋),那麼這種迴答就是一種消極迴答,至少它是不全麵的迴答。而這種被人們不經意間忽略瞭的“信息反饋”,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我把它理解為“在逆境中(積極)生活或抵抗”。眾所周知,沒有反饋的傳播是不完整的,反饋使信息接收者變成瞭信息發送者,使受動者變成施動者。當這種反饋是積極的時候,我們可以將此解釋為人在接到源於逆境的改造信息後,開始以自己為信息源,試圖改造逆境。換句話說,在集中營裏,囚徒變成瞭信息發送者,納粹軍警變成瞭信息接受者,此時,集中營變成瞭一種為囚徒所用的媒介。對於囚徒來說,從解碼到反饋,他至少有兩次積極生活的機會。
如前所述,從自由或人生的角度來說,無論生活在怎樣一個國傢或時代,人的一生都像是在“集中營”裏度過,集中營是人的境遇或條件。法國人說,“生命是一次沒有人能夠活著逃齣去的冒險”,似乎也給我們的生活罩上瞭某種末日情緒——逃齣去瞭也是死。然而,當我們試著樂觀地看待這一切,不難發現許多人仍然活著逃瞭齣來。否則,為什麼每當我徜徉在巴黎的奧塞博物館裏,總能在《吃土豆的人們》裏麵聞到文森特?凡高先生的鼻息呢?當然,如你所知,這裏逃齣來的不是肉體的凡高,而是凡高的積極生活。積極生活是凡高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我關於這個世界的思考與寫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樣。
人,應該在希望中棲居。但是,為什麼我們總是習慣站到施惡者一邊去想集中營能做些什麼呢?相反,我認為人應該思考的是人要做什麼,而不是逆境要做什麼。或許,這纔是《肖申剋的救贖》賜予觀眾的最大收獲。如主人公安迪所說,“有一種鳥是關不住的,因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著自由的光輝”。一個熱愛自由與幸福的人,一個把自己的一生當作遠大前程的人,應該始終如一地保有一種“關不住”的精神,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紅杏齣牆。關心自我實現,追逐自己的命運。勇敢的人,應當對罪惡視而不見。
在索爾仁尼琴筆下,有一種齣牆者是“堅定的逃跑者”:
“堅定不移的逃跑者!”索爾仁尼琴寫道,“這是指那些堅信人不能住在籠子裏的人,而且對這個信念一分鍾也未曾動搖過的人。這種人,不管讓他去當個有吃有喝的監獄雜役,把他放在會計科或文教科,還是安排在麵包房乾活,他都始終想著逃跑。這是那些從被關起來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夢寐以求逃跑的人。這是鐵瞭心決不妥協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動都服從於逃跑計劃的人。這樣的人在集中營裏沒有一天是隨隨便便度過的,不管哪一天,他要麼是在準備逃跑,要麼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瞭,被打得半死躺在勞改營監獄裏。”
真正的逃跑者永遠在路上,而且永不絕望。
在以上材料中,熊培雲認為,“人,應該在希望中棲居”,“人應該思考的是人要做什麼,而不是逆境要做什麼”,“真正的逃跑者永遠在路上,而且永不絕望”。針對這種觀點,請你能夠提供至少三個比較有說服力的論據。
2.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惡
——梁文道《常識》
說到反罪,說到日本的戰爭責任,很多人會直覺地以德國在二戰之後的錶現來做比較,追問日本人為何不像德國人那般深切懺悔。得齣的答案往往歸結到日本文化的本質或者各式各樣的“日本人論”,例如人類學傢本尼迪特(Ruth Benedict)經典著作《菊花與刀》裏的著名判斷:日本的“恥感文化”不同於西方的“罪感文化”。這種化約的文化解釋不隻大而化之擺脫瞭曆史細節,而且過度強調瞭日本的特殊性,反過來正好證明瞭日本人無論如何不會認錯,因為他們的文化就是如此。因此這類很知識分子的論述方式,竟然與大陸網站上激進的平民言論不謀而閤。那些被認為很民粹很粗暴的憤青同樣覺得日本是“死不認錯”的,因為“日本人骨子裏就是這麼賤”,隻不過知識分子懂得使用一些學術詞匯罷瞭。
我們的確可以也的確應該把日本拿來與德國比較,隻是我們不隻要問“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那般痛切自悔”,而且還得自問身為戰爭受害者的自己:為什麼我們不像納粹受害者那樣去追究加害國的責任呢?納粹德國在波蘭、捷剋、俄羅斯等多國犯下的罪行,不是互不相乾的“德波曆史問題”、“德捷曆史問題”與“德俄曆史問題”,而是被視作一組跨越國境的“反人類罪惡問題”。當一個波蘭猶太人在戰後痛斥當年納粹暴行的時候,他會很清楚這不隻是兩國之間的曆史仇恨,而且是發生在波蘭的一件重大罪惡,這個罪惡也曾降臨在其他國傢之中。反過來說,有多少中國人意識到在抗日戰爭以外,曾經有過萬菲律賓戰俘受虐至死?有多少中國人知道日本在整個中南半島殺瞭多少人?又有多少中國人有興趣去瞭解日本帝國在韓國怎樣推行皇民化運動?中國人總是習慣性地把日本當年犯下的罪行狹隘地理解成兩個民族之間的仇恨,而非禍及整片東亞的反人類罪行。
同樣地,包括《經濟學人》在內的許多西方知名媒體也傾嚮淡化日本的戰爭罪行,將其描述成“日本與亞洲多國的曆史矛盾”,並且詳列戰後日本官方曾經作齣的道歉次數,證明日本業已清除罪責。日本國內也有許多意見認為他們道歉道得夠多瞭,不懂中國乾嗎還老叫他們認錯,覺得這是一種利用曆史的勒索手段。問題是,如果今天認錯認得實在很徹底的德國齣瞭一個政客去希特勒靈前緻意,或者有一本教科書將種族滅絕說成是人類純化,大傢又會怎麼樣呢?恐怕不隻各國傳媒將嚴辭聲討,德國政府和一般百姓也會義憤填膺,暴跳如雷吧。所以關鍵並不在於日本作過多少次官式道歉,也不在於那是普通的道歉還是深有悔意的謝罪;而在於盡管有今天,居然仍有人敢於公開聲稱侵略亞洲其實是解放亞洲,卻不用擔心任何後果。
在描述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裏麵,我們常常看到對比起粗野不文的美軍,德國軍官總是一派儒雅,喜歡誦讀歌德甚至能夠彈一首貝多芬的奏鳴麯。為什麼這樣的人會參與如此駭人聽聞的冷酷殘殺呢?這大概也是德裔美籍哲學傢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去耶路撒冷旁聽納粹黨徒艾剋曼(Adolf Eichmann)受審時,心裏帶的疑問。她驚訝地發現“艾剋曼既不陰險,也不凶橫”,完全不像一個惡貫滿盈的罪犯,就那麼彬彬有禮地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稱“他的一生都是依據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動都來自康德對於責任的界定”。艾剋曼所做的一切都來自遵從命令,頂多就是特彆熱心軍階晉升罷瞭,所以艾剋曼形容自己隻不過是“一座機器裏的螺絲釘”。
這就是後來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惡”(evil of banality)。人類不需要是個什麼大奸大惡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隻需要閤作,一個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難以想象難以言傳的邪惡。“真正睏擾我們的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朋友的行為。持續一生的友誼可以在一夜之間被摧毀,就因為害怕錯失瞭加入曆史的潮流。他們隻是在納粹的威勢麵前失去瞭自己下判斷的能力。”(Hannah Arendt《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很多學者形容納粹的罪行是史無前例的“極端之惡”(radical evil),其規模其內涵超齣瞭人類想象力的邊界。而漢娜?阿倫特獨到之處,就是指齣即使邪惡如納粹,到底也是個在地上行走的機器,是個人類零件組成的組織和機構。而人之所以會附和它甚至加入它,隻是因為受到誘惑,隻是不想與他人不同,隻是想做個乖乖聽話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惡”。正是因為這個“平凡之惡”的觀點,我們可以討論在獨裁專製的政權底下,個人的道德責任問題。去逼問當年的德國人何以不反抗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在反省巨大的邪惡是如何由每一個人不經意的每一步逐漸積纍而成。納粹黨衛軍不都是痛下決心要做凶手的,他們可能平凡如你我,他們甚至可以是個熟讀康德知書達禮的“好人”,他們隻是漸漸地交齣瞭判斷的能力。
因此我們可以拿日本與德國相提並論,因為在二戰期間,它們的社會都是極權主義盛行,“平凡之惡”浸淫瞭整個國度。所謂“日本軍國主義”其實是建立在天皇製上的一種社會製度,以神格人身的天皇為中心,由上而下一層層地構成瞭整個國傢的秩序。在這個秩序裏麵,個人沒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動完全是上級替他規定的。因此日本思想傢丸山真男稱之為“不負責任的體係”。可是得注意這套秩序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什麼日本民族性,而是明治維新之後纔透過各種文宣教育手段建立起來的新事物。如果要日本人徹底接受戰爭責任,就得揭穿天皇製的神話,使得大傢重新認識到那部大機器裏的小零件,到底是個有自省能力可以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對於推說“我也是個被國傢欺騙的受害者”或者“我隻是奉命行事”的人,必須像對著錯愕的艾剋曼一樣,指齣他埋沒理性終於與邪惡閤作的曆程。
針對以上材料中梁文道主張的:“隻是我們不隻要問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那般痛切自悔,而且還得自問身為戰爭受害者的自己:為什麼我們不像納粹受害者那樣去追究加害國的責任呢?”請發錶你的看法。
……
前言/序言
一個非典型語文教師的教育夢 復旦附中 王召強 五年前,一個很偶然的機緣,我在網上觀看瞭哈佛大學教授邁剋爾·桑德爾開設的公開課《公正課》,深為嘆服。桑德爾上課的地點設在哈佛大學最大的講堂——桑德斯劇院,每周一節,每節都有一韆多名學生來聽課,連樓上的座位都擠滿瞭人。桑德爾的《公正課》,涉及自由、民主、權利、義務、公正、平等、幸福等重大政治哲學論題,討論的熱點有墮胎、代孕、種族歧視、同性婚姻等等。課堂上既有唇槍舌劍的火藥味,又不乏風趣與幽默,引人入勝,令人迴味。於是我就萌發瞭把“公正課”引入中學課堂的想法。當時最大的睏惑在於,桑德爾上的是大學通識政治哲學課,而我帶的是高三語文課,如何纔能找到兩者的契閤點,讓我可以在語文課上名正言順地上公正課呢?我把目光轉嚮瞭令語文老師頗為頭疼的作文課和口語交際課。何不仿效桑德爾,以社會熱點為話題,引導學生在課堂上討論,在討論中生成批判性思維的核心知識,培養學生的公民素養呢?這不正是一舉多得的創舉嗎? 接下來就是抓住教育契機,精心選擇議題的時候瞭。當時在我的班上剛好有兩個文藝男青年,整天齣雙入對,引起班級女生的側目而視,以至強烈不滿。她們私下裏嚮我反映:我們文科班的男生本來就少,在去掉一對帥哥,簡直就太“浪費資源”瞭。我馬上就意識到,這是一個關於同性戀教育的絕佳機會。我先推薦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觀看瞭李安導演的經典同性戀影片《斷背山》,然後讓學生就李銀河《關於同性戀婚姻閤法化的提案》展開討論。在討論之前我先在班級中做瞭一個小調查,結果令我大為震驚。全班45位同學,隻有5人反對同性戀婚姻閤法化。我完全沒有想到現在的學生思想會如此開放。雖然隻有5位同學對議題持反對意見,但是這次討論卻空前激烈。辯難雙方各不相讓,就同性婚姻這一敏感議題展開激烈交鋒。整整討論瞭兩節語文課以後,還意猶未盡,直接“霸占”瞭接下來的班會課繼續討論。 班會課結束以後,學生本來可以放學迴傢瞭,但是還賴著不走,要求繼續討論,又延長瞭半個小時方纔罷休。這是我執教以來,學生第一次主動要求加時上課。初次嘗試,就讓我嘗到瞭“公正課”的甜頭。雖然辯難雙方最終誰也無法說服對方,但是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學生對班級裏的兩位文藝青年指指點點。通過這次討論,至少讓學生認識到:不應該歧視同性戀;同性不但可以戀愛,在有些國傢,甚至可以結婚;民主不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真正的民主應該對於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加以人權上的尊重和保護。 從此以後,我就走上瞭一條校本課程開發的“不歸路”。在參考桑德爾的《公正課》和內爾?諾丁斯的《批判性思維課程:學校應該教授哪些知識》的基礎上,我迅速總結經驗,深入瞭解學生學情,廣泛閱讀教育專著,密切關心時事,逐步摸索打磨齣十二個“有中國特色”的批判性思維課程,比較成熟的議題分列如下:教育要公正、死刑存與廢、同性戀婚姻、個人與國傢、容忍與自由、為什麼貧窮、平庸的邪惡、電影分級製、懷疑與信仰、計生罪與罰、為民主辯護、公民不服從。這些議題乍看屬於“宏大敘事”,但是一經結閤熱點時事,隻要選準角度,提齣一個比較具有爭議性的核心問題,都會變得非常真實有趣,將學生帶入桑德爾所說的“道德睏境”,而麵對這些道德睏境,正確的態度不是迴避,而是“理性地省察”。“理性地省察”的過程,就是批判性思維養成的過程。我們的目的,絕對不是灌輸什麼絕對真理,而是“喚醒理性的不安”,看看理性能把我們引嚮何方。我把這門課程命名為“批判性寫作課程”,把課程的總目標定位為塑造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獨立人格。這句話齣自陳寅恪先生寫給王國維先生的碑銘,工作伊始,我就把這句話作為班訓,專門請書法傢題詞,張貼在班級裏。當時還有人說我是“資産階級自由化”,這要是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就會被當作“精神汙染”給清除瞭。 後來我搬齣溫傢寶總理2011年10月25日在南開中學看望師生時的講話,他也引用瞭這句話,再也沒有人對我指指點點瞭。所謂的批判性思維,其實源於杜威的“反省性思維”,哈貝馬斯則稱之為“解放性學習”,美國批判教育學傢亨利?吉魯認為,批判性思維的核心問題是“這個社會在我身上已經塑造齣來的而我不再願意按照這種狀態生存下去的(東西)到底是什麼”,並嚴峻地指齣,“我們首先應該關注的是這樣的教育問題,即教學生批判地思考,教學生學習如何肯定他們自己的經驗,並且教他們理解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必須為瞭一個更公正的社會而奮鬥。” 基於批判性思維的寫作教學,即引導學生善於從身邊發生的社會現象齣發發現問題,運用邏輯思維分析問題,並結閤社會實踐解決問題。它更側重於寫作的過程化指導,而非寫作的結果;它更側重於寫作者的思維技能訓練,而非語法修辭訓練;它更側重於寫作者的思維質量的提升和健全人格的養成,而非僅僅停留在寫作能力的提高。美國教育傢馬莎?努斯鮑姆在《告彆功利——人文教育憂思錄》一書中針對要在學校培養現代公民的具體舉措問題,即認為學校要“大力培養批判性思維,大力培養發齣異議之聲所需的技能和勇氣。”因為她認為:“教育並不隻是被動地吸收事實和文化傳統,它還嚮思維挑戰,使思維具備積極的、勝任的、徹底的批判力,去麵對復雜的世界。”在開發批判性寫作課程的過程中,我曾經三次選用“民主”為話題,讓學生針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是否適宜開展以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為典範的政治改革”這一頗具爭議性的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進而想讓學生從正反雙方的討論中歸納總結齣論證過程中常見的謬誤和值得注意的問題。但是前兩次討論的結果都很不理想。 後來,我逐漸認識到,對於民主教育這個話題,我過於耽溺其中而不能自拔,我急於把“德先生”灌輸到學生的頭腦中,而沒有認識到,這種強力灌輸的過程,本身就不符閤“德先生”的風範,犯瞭教育領域中急功近利的“極左”錯誤。雖然我在學生討論的過程中,極力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無禁區”等民主理念,但是學生在我的課上僅僅獲得瞭形式上的言論自由,學生的確可以毫無忌憚地發錶自己的見解瞭,但是我卻不能夠藉助這個話題引導學生走嚮思維的深處。可以說我解放瞭學生的嘴巴,卻束縛瞭學生的思維。有鑒於此,筆者開始留心學生比較關心的熱門話題。當時筆者執教的是高三年級,在我的班級中有兩個學生戶籍屬於外地,雖然他們從小就在上海長大,通過藉讀上海中小學校,一路讀到瞭高中,但是卻因戶籍限製無法參加高考。班級學生對這兩位同學的遭遇都頗為同情,深感教育之不公,私下裏經常討論高考招生政策,而社會上也在熱議異地高考、教育公平的話題。我頓覺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契機,教育公平的話題隸屬於政治學上分配正義的範疇,正符閤我孜孜以求的“民主的基礎”的教育目標。在備課的過程中,我發現旅美學者薛湧發錶瞭一篇題為《大學要按城鄉人口比例招生》的博文,主張大學招生應重視城鄉比例,以示教育公平。我把這篇文章印發學生討論,以教育公平為話題,以是否贊同薛湧的觀點為問題,分頭查找資料,搜集論據,歸納論點,再在課堂上展開針鋒相對的辯難。可以說,這次關於教育公平的大討論是空前成功的,至少是三次討論以來最成功的一次。 於是,我教育生涯中的第一次公開演講,就這樣獻給瞭北一女中。在兩岸三地語文教學研討會上的演講結束之後,颱灣的老師私下裏問瞭我很多關於公民教育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王老師,您是齣於怎樣的個人機緣,開始關注公民教育的?”換句話說,我搞公民教育,有哪些個人因素。說來話長。先從我個人成長經曆中遭受的一次“不公正”待遇說起。 1992年的夏天,懵懵懂懂的我,參加瞭一場毫無概念的考試——小學升初中選拔考,從此決定瞭我一生的道路。考試結果齣來瞭,毫無懸念,我又是全班第一名,全村隻有一個班,也就是全村第一名。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每次期末考試,我就是第一名。分數自然達到瞭鎮中心中學的錄取分數,而且是全村唯一達綫的一個。 整個暑假,我都沉浸在無憂無慮的歡快生活中,直到收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天。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落榜瞭,而分數沒有達綫的三位同學卻考進瞭鎮中心中學,其中有一個同學的分數被我甩瞭70多分,我則被鄰村的一所鄉村中學錄取的。收到通知書的那一天,我流淚瞭。不多,但是很傷心。我搞不清楚,到底發生瞭什麼事。為什麼上天,對我如此不公?我跑去問我的母親,她也說不清楚。後來鄰居提醒我母親:“是不是因為你們傢沒有去送禮?”“送什麼禮?送給誰?”我母親怯生生地問。“送給在鎮中心中學上班的王某某啊,他是教導主任,聽說其他三個學生的傢長都送禮瞭。”鄰居齣於好意提醒說。“也用不著送太多,兩條煙,一箱酒就行瞭。”鄰居補充說明道。兩條煙、一箱酒,就這樣抵消瞭我小學五年的勤奮努力。當天晚上繼父下班以後,帶我一起“拜訪”瞭教導主任,看看還有沒有轉圜的餘地。臨行前母親徵詢我的意見:“要不要帶點禮品?”“不要。我的分數又不是沒到。”我倔強地說。這注定是一場異常尷尬的會麵。教導主任一傢人顯得異常冷漠。對我們這對如此不識相的父子無言以對。繼父反復替我申訴:“可是他的分數明明達綫瞭啊,而且還比人傢高那麼多。”我則在一旁默默流淚,以示抗議。教導主任支吾瞭半天,沒有給齣任何解釋。在迴傢的路上,我暗暗下定決心,將來一定要考上大學,做一名好老師。至於“好老師”的標準,我到現在都沒有想清楚,不過有一點倒是肯定的。那就是公正。 很多年以後,我大學畢業,選擇瞭留在上海工作。總有人問我,為什麼不迴山東,替傢鄉做貢獻。我是這樣迴答他們的:“迴老傢,沒有關係,不送禮,連工作都找不到。還怎麼做貢獻。”套用一句托馬斯?曼的名言,那就是,哪裏有公正,哪裏就是我的傢鄉。他的原話是,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我的祖國。講得比我狠多瞭。這麼麯摺復雜的故事,我當然沒有講給颱灣的老師聽。我隻是告訴她,我齣生在大陸最窮苦的鄉村,在農村整整生活瞭18年,切身地體會到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在我上大學之前,連肯德基、麥當勞都沒有聽說過,在我來上海之前,隻在高中地理課本上看到過一張南京東路的照片。對上海所有的想象,還停留在許文強的上海灘時代。臨行之前,我的母親反復叮囑我:“韆萬不要到長江裏遊泳!”到瞭上海以後,我真的要說一句:“我的娘呀,您真的想多瞭。華師大倒是有一條麗娃河的,隻是從沒見過有人在裏麵裸泳,何況您的兒子連一條泳褲都捨不得買。” 後來我在上海看到的一切,都不禁讓我思考,是什麼原因造就瞭這麼嚴重的社會撕裂。以教育為例,為什麼上海的學生如此輕而易舉地就考進瞭大學,而我的山東同胞們,連讀完小學、初中的幾率都很低。在我的小學同學中,五年級畢業的時候,還剩下22人,9人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在我的初中同學中,初三畢業的時候,原來兩個班級的120人,一共還剩下22人,後來乾脆閤並成一個班級。考上重點高中的,隻有我一個;通過復讀最終考上高中的,也就3個人;最終考上大學的,當然就隻剩下我這個孤傢寡人瞭。在華師大偌大的校園裏,我曾經苦苦尋覓著我的老鄉,在我們這一屆的同學中,我隻找到瞭三個人。種種“不公平”、“不公正”的社會現象,急劇超越瞭我個人遭遇的“童年創傷”,我不禁要進一步反思:發生在我這一代人身上的悲劇,到底是怎樣産生的?郭於華在《傾聽底層》一書中指齣:“個人的苦難往往是社會世界深層的結構性矛盾的産物。 ”正是齣於探究社會世界深層的結構性矛盾的動機,我纔開始瞭我的批判性思考之旅。 從颱灣訪學歸來之後,我越發認識到通過開設批判性思維課程推動公民教育的重要性,2015年2月開始,我想把這門課程作為選修課先在我們學校開設起來,慢慢地推廣齣去。開設選修課當然少不瞭編寫校本教材,我利用工作之餘和寒假期間把我之前的講義認真修訂瞭一番,變成瞭這本《喚醒理性的不安——公民寫作十二課》,承濛時代科技文獻齣版社不棄,願意齣版此書,敬謝不敏!在編寫的過程中,得到黃玉峰老師悉心的指導和語文教學界同仁的熱忱鼓勵,在此一並緻謝! 王召強 乙未年正月初一草識於鬆江孤寒堂用户评价
《主題寫作十二課》,這個名字勾起瞭我內心深處對寫作的渴望。我一直認為,寫作是錶達思想、傳遞情感最直接的方式。但遺憾的是,我的寫作之路走得磕磕絆絆,常常陷入思維的泥沼,找不到前進的方嚮。我希望這本書能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帶領我走齣迷霧。 我理解的“主題寫作”,是一種更加專注、更加深入的寫作方式。它不是漫無目的地抒發,而是有明確的中心思想,並且能夠圍繞這個中心,展開層層遞進的論述。我總是羨慕那些能夠將一個簡單的概念,剖析得淋灕盡緻,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不僅獲得信息,更能獲得啓發。 “十二課”這個結構,讓我覺得這本書的設計非常用心。它暗示著一個係統性的學習過程,每一課都有其獨立的價值,但又相互關聯,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知識體係。我猜想,這本書會從寫作的基礎開始,逐步深入到更復雜的技巧,讓讀者能夠紮實地掌握寫作的要領。 我特彆期待書中能夠提供一些實際的寫作練習。光有理論是不夠的,隻有通過親身的實踐,纔能真正地將知識內化。我希望能夠通過這些練習,學會如何構思一個引人入勝的開篇,如何組織一篇邏輯嚴密的文章,以及如何用精準的語言,傳達我內心深處的想法。 總而言之,我期待《主題寫作十二課》能夠成為我寫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摺點。我希望它能夠幫助我剋服寫作中的種種睏難,提升我的寫作水平,並且最終能夠寫齣那些能夠觸動人心、啓迪思想的作品。這不僅僅是對寫作技巧的追求,更是對自己思想深度和錶達能力的不斷探索。
评分《主題寫作十二課》,單看書名,就有一種“乾貨滿滿”的感覺。我常常覺得,市麵上的寫作書籍,很多都停留在“怎麼寫”的層麵,卻很少去深入探討“寫什麼”和“為什麼要這樣寫”。我對於那種能夠引導讀者找到寫作的“根本”的書籍,有著天然的興趣。 寫作對我來說,常常是一場與內心的對話,也是一場與讀者的溝通。但很多時候,我感覺自己的聲音不夠清晰,或者我的觀點不夠鮮明。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我學會如何提煉齣文章的核心思想,如何用最簡潔、最有力的方式錶達齣來。就像在一堆雜亂的綫頭中,找到那根最關鍵的主綫。 “主題寫作”這個概念,在我看來,是一種更加有策略性的寫作。它不僅僅是把想法寫齣來,更是要圍繞著一個明確的“主題”,進行有針對性的創作。我猜想,這本書會從如何確定主題,如何挖掘主題的深度,到如何圍繞主題展開論述,都有詳細的講解。我特彆想知道,這本書是否會提供一些創新的方法,來幫助我們發現那些隱藏在日常中的寫作主題。 “十二課”這個說法,給我一種循序漸進的學習體驗。我感覺它不像是一次性的信息轟炸,而是有節奏、有層次地展開。我很好奇,這十二課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學習路徑?是先從構思入手,還是先從語言訓練開始?我非常期待能夠跟隨這本書的指引,完成一個完整的寫作訓練過程。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我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寫作體係。不是那種萬能的公式,而是能夠根據不同的寫作需求,靈活運用其中的方法。我希望讀完這本書,我能夠更加自信地麵對寫作的挑戰,也能夠寫齣更加有影響力、更有價值的作品。這不僅僅是為瞭提升寫作技巧,更是為瞭更好地錶達自己,與世界進行更深入的連接。
评分《主題寫作十二課》,這個書名本身就充滿瞭吸引力。我總覺得,寫作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技術。而“十二課”這個設定,仿佛是在嚮我傳遞一種“學有所成”的保證,一種清晰的學習路徑。我是一個喜歡係統性學習的人,所以這個名字對我來說,有著天然的吸引力。 我一直覺得,寫作的本質是思想的錶達。而“主題寫作”這個概念,恰恰抓住瞭這個核心。它意味著,我們寫的每一篇文章,都應該有一個鮮明的主題,這個主題就像是文章的靈魂,貫穿始終。我渴望能夠掌握一種方法,讓我的文章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砌,而是能夠清晰地傳達我的思想,並且能夠引發讀者的思考。 “十二課”的結構,讓我覺得這本書的編排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它不像那種零散的寫作技巧的羅列,而是形成瞭一個完整的課程體係。我猜想,每一課可能都有其獨特的側重點,比如如何構思,如何選材,如何布局,如何潤色等等。我非常好奇,這十二課到底包含瞭哪些精彩的內容,又會以怎樣的方式來教授。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些切實可行的方法和工具,來幫助我提升寫作能力。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講解,更重要的是能夠提供一些具體的練習和案例,讓我能夠通過實踐來鞏固所學。我希望讀完這本書,我能夠對寫作更有信心,也能夠寫齣更具吸引力、更深入人心的作品。 總而言之,我對《主題寫作十二課》充滿期待。我希望它能夠成為我寫作道路上的一個重要啓濛,讓我能夠更好地理解寫作的本質,掌握寫作的技巧,並且最終能夠寫齣那些能夠錶達真我、影響他人的優秀作品。
评分《主題寫作十二課》這個名字,聽起來就有一種治愈的效果。我常常覺得自己的寫作就像是一團亂麻,想到什麼寫什麼,缺乏方嚮,也缺乏內在的邏輯聯係。每次寫完,都覺得不滿意,總覺得哪裏不對勁,卻又說不清楚。我一直渴望能有一本這樣的書,能夠幫我理清思路,就像把那些零散的想法一點點串聯起來,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我覺得寫作最難的部分,往往不是遣詞造句,而是如何把一個抽象的概念,或者一個模糊的感受,轉化成清晰、有力量的文字。特彆是當你想錶達一些更深層的東西時,就更加睏難瞭。很多時候,我們腦子裏明明有一個清晰的想法,可是一落到紙上,就變得麵目全非。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些有效的工具和方法,來幫助我跨越這個鴻溝。 “十二課”這個數字,讓我覺得它是一個精心設計的課程體係。不像那種一本通式的寫作指南,它更像是一個有溫度的老師,一步一步地引導你。我猜想,每一課可能都有其獨特的主題和側重點,比如如何構思,如何組織結構,如何打磨語言,甚至是如何尋找寫作的靈感。我非常好奇,這十二課究竟會涵蓋哪些方麵,又會以怎樣的方式展開。 我一直對那些能夠將復雜問題簡單化,並將抽象概念具象化的寫作方式非常感興趣。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些具體的案例和練習,讓我能夠通過實踐來學習。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講解,更重要的是能夠讓我動手去嘗試,去感受,去體會。我相信,隻有通過不斷的實踐,纔能真正地掌握寫作的精髓。 我最期待的,是這本書能夠幫助我建立一種更自信的寫作心態。很多時候,因為覺得自己寫得不夠好,就會産生畏難情緒,甚至放棄。如果這本書能夠讓我看到寫作的樂趣,能夠讓我相信自己能夠寫齣有價值的內容,那將是最大的收獲。我希望它能成為我寫作路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叫做《主題寫作十二課》,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字的時候,就立刻被吸引住瞭。感覺它不像市麵上那些泛泛而談的寫作指導,而是有著非常明確的針對性和係統性。我一直覺得寫作這件事情,如果能有一個清晰的框架,有明確的“課”來指導,會比自己摸索要有效得多。 我曾嘗試過很多次的寫作,無論是寫日記、寫博客,還是工作中的報告,總感覺自己總是在一個比較淺的層麵打轉。有時候靈感來瞭,寫得也挺順暢,但一旦要深入挖掘主題,或者要邏輯嚴密地組織論點,就顯得力不從心。我渴望能掌握一種方法,能夠讓我的文章更有深度,更有說服力,而不是僅僅停留在錶麵描述。 “主題寫作”這個詞對我來說,意味著一種更具目的性的寫作。它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思想的錶達和觀點的傳遞。而“十二課”則給人一種踏實的感覺,仿佛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學習過程,每一個環節都設計得恰到好處,能夠帶領讀者一步一步地掌握核心技巧。我特彆期待能夠通過這本書,學會如何找到自己真正想要錶達的主題,並且能夠圍繞這個主題,構建齣有吸引力的內容。 我相信這本書不僅僅是麵嚮那些已經有一定寫作基礎的人,更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入門指南。對於那些和我一樣,對寫作有熱情,但又覺得無從下手的人來說,一本像《主題寫作十二課》這樣的書,就像是一盞指路明燈。它或許能幫助我們理清思路,找到屬於自己的寫作節奏,並且能夠自信地拿起筆,開始錶達。 我對這本書的期望很高,我希望它能夠教會我如何進行深度思考,如何提煉齣文章的“靈魂”,如何在眾多的信息中找到那個最能打動人心的“主題”。同時,我也希望這本書的練習能夠幫助我將理論付諸實踐,真正地提升我的寫作能力。這不僅僅是關於寫作技巧,更是關於如何更有效地思考和溝通。
评分给高中的孩子拓展下写作思维有帮助
评分“召强的批判性思维课程缘起于哈佛大学的公正课,是模仿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的。一个高中的语文教师,敢去模仿哈佛大学的教授,是需要点底气的。何况,他并不是照搬,既要上出中国特色,还不能脱离语文课程的范畴,确实是难乎其难。”-------黄玉峰
评分帮小侄女买的书,没什么毛病
评分内容很好,很有启发性,值得一读。
评分我一直很信任京东京东的东西是最好的主要是服务好很多东西一直都坏了,也有人管
评分谈谈读这本书的几点心得:(一)为什么购买这本书?作者之一是黄玉峰,--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是我非常敬佩的名师,于是购买了这本书。(二)初读印象:体例严谨,按主题编次。(三)主题深刻,思辨性强,利于高中生的思维训练与发展。(四)推荐阅读人群:本书适合高中生阅读。
评分谈谈读这本书的几点心得:(一)为什么购买这本书?作者之一是黄玉峰,--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是我非常敬佩的名师,于是购买了这本书。(二)初读印象:体例严谨,按主题编次。(三)主题深刻,思辨性强,利于高中生的思维训练与发展。(四)推荐阅读人群:本书适合高中生阅读。
评分京东买书,非常划算,快递小哥也很给力!
评分很好的书,不但孩子看了很受益,我觉得对于我们成年人也很受益!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