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一本70年前的畢業紀念冊,重新認識一個“18歲的外婆”。★溫暖一整季的催淚之作,值得每個人一讀再讀的“中國故事”!
★饒平如、金宇澄、梁鴻、嚴彬閱後感動推薦!
1945年,山河破碎,勝利來之不易。年輕的她和同學們在求學之路上輾轉流亡,曆盡艱辛,譜寫瞭難忘的青春鏇律。
2015年,世事變幻,舊人一一凋零。已經走過93年人生之路的她,是否還能重拾舊日的同窗之誼?和80後外孫之間又會有怎樣感人的親情故事?
剋羅齊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或許我們也可以說,一切曆史都是個人史——所有舞颱宏大、布景繁復的大曆史,都是一個個平凡人細微的個人生活史。當“抗日戰爭”這段70年前的大曆史逐漸淡齣所有人的真實記憶、紀念成為國傢意誌下的慶典儀式時,曆史是空洞的、屬於過去的、與己無關的。但是曆史本應是鮮活的,它與一個個麵目清晰、情感躍動的人密切相關。外婆(劉梅香)和她的同學們,70多年前就是這樣的曆史親曆者。
讀《梅子青時》,波瀾壯闊的時代大背景在青春少年的求學生活後麵時隱時現,其中人物的生活經曆、脾氣性情、命運跌宕,都在大曆史中一一展開,令人聯想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巨流河》中個人命運與傢國曆史的糾纏。然而最感人的還是,那份從個人齣發對一個時代的真實記錄,是我們在曆史教材中看不到的,堪稱另一部《平如美棠》《窮時候,亂時候》。
內容簡介
1937年日本全麵侵華後,浙江杭州淪陷,原處蕭山的湘湖師範學校被迫南遷流亡辦學,師生一路輾轉至義烏、鬆陽、慶元、景寜等地。外婆(劉梅香)在1941年入學湘湖師範,四年青春時光轉瞬即逝,而在此結識的同學師長、奠定的世界觀價值觀,卻深刻地影響瞭外婆的一生。70年後的今天,在一次偶然整理外婆的舊物時,外孫(張哲)發現瞭一本70年前的畢業留言冊。這次偶然的相遇,連接起瞭外婆的現在與過往,也讓外孫重新認識瞭外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彌足珍貴,70年前外婆在抗戰與求學中的少時故事,穿越戰火和動蕩的久遠年代,仍深深地吸引著像他這一代年輕人……這既是93歲外婆的一部抗戰求學迴憶錄,也是祖孫兩代間一麯令人感喟的心靈對話。作者簡介
劉梅香(1923—),浙江鬆陽人,1941—1945年入學南遷後的浙江省立湘湖鄉村師範學校(簡稱“湘湖師範”),因抗戰形勢需要,先後流亡至鬆陽、慶元、景寜等地學習。1945年畢業後在浙江任小學教師,直至退休。張哲,浙江杭州人,曾從事互聯網和媒體工作。
精彩書評
★花朵如曆史中的人生細節,疏忽這特殊性,它們將隨時消失。感謝作者,讓遙遠的色彩在這本書裏展開,遠方的氣息、時間縫隙裏難忘的畫麵,都被保存下來,這是作者、讀者的幸運。——金宇澄(作傢、茅盾文學奬得主)
★一個普通老人的生命史,卻摺射齣那個大時代最細微的神經和肌理,充滿質感和活生生的美。該書以人物口述的迴憶和作者親曆的現實相互印證,為我們呈現齣曆史的變遷、滄桑和生命頑強的“在”。
——梁鴻(作傢、教授)
★沿著書中外婆的青春紀念冊,在湘湖師範之外我看到炮火中的西南聯大,看到張充和的“麯人鴻爪”,看到中國式傳統傢庭幾代人血脈中的故事。小時代固然怡人,那端莊壯麗的人生卻是學不來的。
——嚴彬(詩人、鳳凰網讀書頻道主編)
★這不僅僅是一本介紹外婆個人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生活曆程的傳記,而且也是一本描述人間師友精誠團結、互助友愛的真情,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美德,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好書。
——饒平如(《平如美棠》作者)
目錄
初章 時空奇遇次章 流動的學堂
續章 星星月亮太陽
尾章 彆亦難
精彩書摘
13寫字颱理得相當整齊,但裏麵的大多數東西在我看來都沒有什麼必要保留。
木尺,剪刀,旅遊紀念章,手帕,剪報本,賬本,相冊。
相冊當然是需要保留的,隻是除瞭傢人和她自己的老照片,還有太多我不認識的麵孔,大概是她的同學、同事、學生和遠親。
在一疊本子的最底下,有一個相對較小的冊子,封麵和封底用深藍色的布包裹著,可能是因為年代太久遠,錶麵有一些接近黑色的汙漬,但整體上仍是整潔和挺括的。冊子的一端用褐色的繩子穿過,顯示它原本隻是一張張單獨的白紙,後來被人為地做成瞭現在的樣子。
也許是好奇心的驅使,也許隻是下意識的一個動作,我翻開瞭這個小冊子。
次章流動的學堂
十四
從前的識字班裏,湘湖師範的學生給我們教課,讓我對教師這個身份産生瞭一種尊敬。但是小學班主任的做法又讓我有瞭新的思考。我想,假如我是教師,一定不會對學生厚此薄彼,要麼不做,要做就做個好教師。
我終於決定去考湘湖師範。我感覺到,這個學校無論師生都平等、樸素、熱情、上進。我想,自己應該加入到他們當中去。
這一次爸爸照樣反對,但不像上次那麼固執瞭。我哪裏管得瞭那麼多,自說自話,和堂姑媽美盡、堂阿叔劉城一道,先參加湘師辦的補習班,再去報名考試。
盡管我這個人平時膽子算大的,但考試那天還是有點擔心。湘湖師範過去每年隻招一個鞦季班,遷到古市以後,春鞦兩季各招一班。我參加的是鞦季考試,一個班五十個名額,參加考試的卻有兩韆多個人。
考完以後,我緊張瞭幾天,後來漸漸平復下來,每天該做啥還做啥。有一天我在鎮上的二阿姨傢裏,突然有人在門外喊我,我心裏一激動,曉得有戲瞭。
來的人是毛培芬。她跟我一道參加補習班,兩個人很談得來,但她小得多,當時還隻是個小姑娘。她的爸爸和阿哥都是湘湖師範的老師,那天錄取名單定下來瞭,她爸爸在辦公室裏抄榜,她就偷偷躲在後麵看底稿,看到第三名就是自己名字,高興得叫瞭齣來。再看下去,看到劉梅香三個字,立刻二話不說,跑到上安村我們傢裏,見到我爸爸,就朝他大叫:
“考取瞭,梅香考取瞭!”
但是我爸爸不相信。毛培芬聽他說我在鎮上,三步並瞭兩步又跑過來。姆媽和二阿姨聽到喜訊,高興得呆掉瞭,不曉得說啥個好。我還是有點不太敢相信,我說:“培芬,走,我同你看榜去。”
我們走到小上安附近的廣因寺,當時湘湖師範就設在寺裏。我一眼就看到瞭自己的名字,大概在四十名左右,我曉得,錄取是篤定的瞭。但是美盡和劉城呢?還沒有尋到他們的名字,我就被毛培芬拉走瞭。
迴到傢裏,我告訴爸爸:“我要讀湘湖師範瞭。你不要不相信,是真的,我親眼看到榜瞭。”
爸爸啥都沒有錶示。但是那天晚飯,他的飯量特彆大,講話特彆多。我想,他心裏麵一定是開心的。
劉城聽說我考上瞭,也跑去廣因寺看榜。本來他感覺考得不錯,一定能夠錄取,結果名字是看到瞭,不過是在備取生裏。所謂備取生,要比正取生低一個級彆,一共十個人,正取生最後不去讀的話,就從備取生裏按分數高低依次補上。美盡沒有考好,她連備取生也不是,徹底沒有上榜。
分數不好,運氣來補。那時正是抗戰前期,浙江北部的杭州等地淪陷,省政府臨時南遷到永康,教育廳遷到麗水。那一次因為報考的人多,校長金海觀也想推行鄉村的普及教育,所以特地坐車去麗水,嚮教育廳申請擴招。當天下午他就迴到學校,帶來廳裏的答復:
“允許擴招!”
這樣一來,五十個就變成瞭一百個,我們正取生編成甲班,十個備取生和分數再靠後的四十個人編成乙班。美盡剛好在那四十個人裏,等於她和劉城一道過關。我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抓住美盡的手說:
“太好瞭,我們三個又變成同學瞭。以後等我們畢業,最好也到一個學校當老師。人傢同事一問,三個都是上安劉傢的,多少光榮!”
那時我不可能料到,美盡和劉城後來都沒能迎來畢業的那天。
15
鞦妹推門進來,把保溫杯裏的茶倒進杯蓋,遞給床上的外婆:“喝掉再講,一邊喝一邊講要嗆的。”
外婆點點頭接過,抿一小口,愣瞭一愣,小心地再抿一口。鞦妹知道是茶太燙,要去奪那杯蓋,被外婆伸齣一隻手掌製止:“不要緊的。”
我補上一句:“我在這裏沒關係,你去隔壁看電視吧。”
“她蠻好的。”鞦妹齣去之後,外婆指著門對我說,“經常給我講笑話。哄我開心嘍!最主要一點,看我看得很牢,哪裏像原先的剛妹,一天到晚擺臉色給我。”
“不要再去想剛妹瞭,最好把這整個人都忘掉。”我想起伍醫生說過,以後要盡量讓外婆避免情緒激動,絕對不能再動怒。
“是嘍,忘記掉,都忘記掉。鞦妹問我在醫院裏的事情,我隻記得後麵,前麵全都不記得瞭,隻曉得摜瞭一跤,然後大阿舅迴來,再就慢慢齣院瞭。至於啥個毛病,你們不告訴我,我也沒地方去查,隻看到是住在神經科。你不要笑,神經科又不是精神病,你當我不懂啊?我想我大概也老年癡呆瞭。人傢不是說嗎,老年癡呆剛開始的時候,近的事情沒印象,老早的事情倒記得蠻靈清,我就是這樣。”
從愛說話這一點來看,她已經恢復得和原先差不多瞭。
外婆齣院前,媽媽、姨媽和大舅舅私下一商量,把當月工資結給剛妹,直接辭退瞭她,專門從傢政公司再新找瞭個保姆,名叫鞦妹。鞦妹六十一歲,杭州蕭山人,據傢政公司老闆說,她是他們的金牌阿姨。開始大傢隻當是噱頭,接迴傢一段時間後,發現鞦妹不但做事認真,性格也算憨厚,不會耍滑頭,和外婆相處融洽,因此大傢漸漸放心。
房間裏隻剩下我和外婆。我坐在床邊的方凳上,她靠坐在床頭,背倚著兩個靠枕,“咦?”一笑,缺瞭門牙的黑洞又露齣來,但現在已經明顯不同於上個月瞭,看起來精神不錯,“要我講啥啦?”
深藍色的布皮小冊子擺在我和外婆中間。
我小心地翻開第一頁,上麵是這樣寫的:
認清目的——寫作原是為瞭歌唱人生,發現人生的真理,而嚮大眾作極細微的體驗!
繼續翻下去,每一頁都是不同人題寫的畢業留言,少的幾個字,多的連寫兩頁,字體各不相同,卻竟然各有各的風格韻緻。留言最後都有署名和印章,題寫者的名字大多可以辨認齣來。
這一件舊物,隔瞭七十年的歲月風塵,此刻重見天日,竟然萌齣新生。文字背後的人那時都還是十幾二十歲的青春少年,求學於亂世之中,目睹山河破碎,身曆生離死彆,是否都曾經為傢國的命運而焦慮不堪?胸懷的一角,又是否也有過蠢動的小情小愛?
冊子背後,隱形的主角正是我的外婆。如果不是這確鑿的物證,我根本不知道要怎樣去想象,眼前這個老婦人也有過意氣風發的年代。的確,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外婆曾經有許多次試圖給我講她的往事,關於村坊、祠堂、老傢的親戚,還有——湘湖師範的人和事。可是這些對我來說都太遠太遠瞭。我從沒有去過她的老傢,也無從去想象那些陌生的建築、風景和人。
至於湘湖師範,對我來說也隻是一個模糊而過時的名詞。也許它有過一些故事,可是,在當下的時態裏,這四個字所指嚮的實體早已經不復存在。那麼我還能怎樣去認識它呢?
仔細想想,也許我纔是錯過瞭太多的那個人。世界無常,生命是流動的,從認識這個被我稱作外婆的人那天起,她一直都是個老太太。如果說歲月為她帶去過什麼改變,那也隻不過是老、更老、都這麼老瞭。
但是,在那之前呢?沒有人生下來就是老人,外婆也一樣。她年輕過,這大概沒錯,隻是我從沒有仔細去想這迴事。就算去想,也沒法眼見為實。所幸此刻眼前物證人證俱在,所以,我想趁現在找迴外婆的青春年少,找迴她的一生。
“你就按照這個冊子的順序,一頁一頁翻,翻到哪裏,就給我講講這個同學的故事。這樣明白吧?”我盡可能啓發她。她點點頭。
“嚴時豪,遂昌人。潘思彩,鬆陽人,男的。楊天锡,他也是鬆陽人。周天青,地下黨……”
她翻頁的速度比我想的還要快,一兩句話就帶過一個人。一個人的一生怎麼可能這麼單薄呢?我嘗試用提問來引導她迴想更多的細節:“你怎麼曉得他是地下黨?”
“我就是曉得,怎麼曉得的老早忘記掉瞭。那個時候是國民黨政府,共産黨還在地下活動,說是說國共閤作,一同抗戰打日本人,實際上呢,兩邊矛盾也蠻多的啦。這個你曉不曉得?這種曆史的東西你看得蠻多,恐怕曉得的。”
不是太簡略就是扯太遠,這樣的講述沒法讓人滿意。“算瞭,繼續說周天青吧,他後來呢?”
“後來?後來麼畢業,畢業瞭麼讀大學,讀瞭大學麼教書。再後來不曉得,不曉得有沒有死,這兩年沒聯係過。”
我嘆瞭一口氣,把小冊子閤上,小心地放到一邊,對外婆說:“這樣吧,還是不要一頁一頁講瞭,我們換個辦法,你今天就講講湘湖師範。剛進這個學校,有什麼事情印象特彆深刻?”
外婆遲疑瞭一下。看得齣來,她在仔細思索和斟酌。片刻之後,她緩緩地開口:“抗戰八年,湘湖師範七遷校址……”
十六
抗戰八年,湘湖師範七遷校址。我進湘師的時候,已經是學校南遷到廣因寺的第三年。
廣因寺是古市鎮對岸的一座大寺,從我傢裏都看得到。它的曆史很久遠,有一韆多年瞭。學校遷到這裏,寺裏的和尚幫瞭大忙。他們曉得學校遷來是為避日本人,又看到老師學生都在積極宣傳抗戰救國,因此十分感動。他們把不同殿堂的菩薩都搬到同一間,這樣騰齣很多房間給我們當教室,當宿捨。當然,他們也不收租金,完全是義務齣藉地方。他們尊重我們,我們也懂得要尊重他們,盡量互不打擾。那時候因為抗戰,大傢身份地位雖不同,但心都是齊的。
廣因寺時期,湘湖師範的處境相對平穩,所以壯大得很快,班級數目不斷擴展,到後來寺裏容納不下,就在附近的一些城隍廟裏麵設瞭分部。一年級的時候,我睏覺的宿捨在廣因寺,但吃飯、上課都在七八裏路之外的梧桐口、葉川頭兩個村。這裏是第四分部,藉用瞭翁傢、葉傢兩個祠堂,還有一個土地廟,重新改造一番,變成教室和食堂。
湘湖師範的學生大多數是窮人傢的伢兒,學校是不收取學費的。雜費倒是要交,食堂裏糧食緊張,所以用米來交。我們當時的米是連糠都在的,總共一百斤榖子,糠去掉的話其實隻有九十二斤,所以大傢叫它九二米。開學那天,爸爸陪我一道去學校,我拎箱子,他幫我挑米。
學校裏一切都是新鮮的,頂頂新鮮的是集體生活,我還是第一次過。女生宿捨是大通間,上下鋪,不同班級都睏在一道,每個人隻有五十公分寬的鋪位。我睏在下鋪,美盡就睏在我邊上。
夜裏燈一熄,大傢睏覺,哪怕明天考試,你想背書也沒有地方好去背,因為沒有燈。那個時候的燈,盤兒裏倒一點桐油,點起來能點多少時間呢?有的時候不小心桐油倒翻,熄燈時間都還沒到,就沒燈可點瞭。
一天夜裏,我同美盡講悄悄話,講講就睏著瞭。不曉得怎麼迴事,忽然被美盡推醒,她把我手拉瞭去,搭在她棉被上。
是水。
“落雨瞭?”
手一摸,不但她棉被濕光,水還沿著床闆流到我這邊。美盡說,啥個雨,當然不是。她跳起來,敲敲上鋪。我們正上麵是金泳芳同汪重華兩個人,美盡問起來,金泳芳不響,汪重華曉得意思瞭,連忙道歉,大傢一道把被單拉起來去烘乾,然後洗手揩身。
原來金泳芳從小身體多病,一直有尿床的問題。我同她說,這不是你存心的,所以我不怪你,隻是既然你自己曉得,應該提前要申請調到下鋪纔對,睏在上鋪不但自己不方便,還要殃及人傢。金泳芳很不好意思,汪重華同她要好,很幫著她,兩個人連連說:
“劉梅香,謝謝你。”
於是我同美盡換到上鋪,金泳芳同汪重華換到下鋪,隻不過這一夜我們沒得睏瞭,因為被單沒有乾。後來,金泳芳在下鋪還是經常尿床,汪重華天天睏覺前給她烘被單。
每天早上五點鍾,天還沒有亮,我們就要爬起來瞭。衣裳穿好,第一件事是疊棉被,因為等我們去梧桐口上課後,宿捨裏會有老師來檢查內務。大傢棉被疊整齊,杯子帶上,毛巾冰得硬邦邦瞭也拿去,走七八裏路,走到梧桐口的食堂。
食堂是祠堂改的,外麵有條溝。天氣冷的時候,溝底下還有水在流,上麵冰已經凍牢瞭。我們把冰敲掉,底下的水兜起來送到嘴巴裏,先含著漱口,含到水焐熱瞭再開始刷牙,然後洗臉。
全部弄好,纔可以吃飯。剛開學的時候還好,後來糧食不夠,有時隻有粥喝,老師想盡辦法去收購糧食,纔保證大傢有飯吃。吃飯的時候老師學生都一樣吃大竈,一張小方桌,沒有凳子,大傢圍起來站著吃。一桌一桶飯,男男女女都是一樣的大碗,碗口十五公分,碗底七公分,這是學校發的,你胃口再大也大不起,一個人就一隻碗,除非碗裏吃完瞭纔可以再去盛。
有的人一次性一碗盛滿,再去盛的時候桶裏已經沒有飯瞭,這樣的人比較老實。有的人呢,故意盛少一點,盡快吃光,好去盛第二碗,這就滑頭瞭。也有女同學用這個方法,第二碗盛來都撥給要好的男同學,因為男同學確實身體很好,愛運動,打籃球,飯量也就比彆人大很多。
如果這一桌女同學多,男同學就運氣,因為女同學吃得少。陶愛鳳很調皮,她自己其實飯量不大,有一次故意隻盛瞭半碗,迴到位子上說瞭一句:
“啊呀,沒瞭沒瞭。”
告訴彆人桶裏麵已經沒有飯瞭,被她盛光瞭。我正在吃飯,忽然看到她眼睛啪啪啪朝我眨。我心裏奇怪,這是做啥?結果是她在惡作劇。幾個男同學正在發牢騷說不夠吃,她又走過去,拿起飯瓢兒沿著桶裏畫圈圈,飯兜起來給他們看。男生先是一愣,然後一擁而上,都去搶飯瞭,陶愛鳳就在我旁邊哈哈哈拍桌子笑,得意得很。
我倒是寜願多盛點,一大碗吃下去,肚皮撐瞭也不管。有一次飯吃好,我去溝裏兜水洗碗,人一蹲落去,肚皮受到壓迫,哇!全都吐齣來瞭。不隻是我,好多人都這樣吐過,說明大傢都怕餓肚皮。
菜呢,恐怕現在的人很難想象。據說抗戰以前,湘師在蕭山時的夥食其實還算不錯,肉骨頭煮黃豆之類的營養菜經常可以吃到。可是南遷到古市以後,夥食就變成一個大難題瞭。好的時候青菜蘿蔔,差一點是鹹菜、毛豆配,最艱苦的日子裏,一桌十個人,隻有一個菜鉢頭,裏麵是鹽湯。
啥是鹽湯?無非就是拿鹽泡泡湯,俗稱鹽開水。
說個插麯好瞭。每桌十個人,大傢是輪流值日洗鉢頭的。有一次,我這桌輪到陳曼青值日,她不曉得為瞭啥事情遲到瞭,等她終於趕到,我們已經吃到一半。她看見桌上擺著鉢頭,朝裏一張,先是一愣,然後闆起臉孔,拿瞭鉢頭去泔水桶邊上,啪一下把裏麵倒光。轉身走迴來,嘴巴裏還嘟嘟囔囔:
“哪個這樣下作?菜吃光瞭一口都不留給我,洗碗水倒擺在桌上,還要我來收。”
開始她走齣去大傢還在發愣,到她說齣這番話來,一桌人哈哈大笑。我笑得仰天撲地,肚子都痛死瞭。陳曼青更加氣惱,大聲說:“遲到瞭是我不好,但你們為啥要笑我?”
我告訴她:“你倒掉的哪裏是洗碗水,是我們今天的鹽湯!”
她呆掉瞭,轉頭看看這桌,看看那桌,果然鉢頭裏都是鹽湯,她真是難為情死瞭。
……
用户评价
這本書,我想我會反復地閱讀,因為它帶來的不僅僅是一次閱讀體驗,更是一種精神的洗禮。《梅子青時:外婆的青春紀念冊》最讓我著迷的地方,在於它對人物內心世界的細膩刻畫。外婆年輕時的那些敏感、彷徨、勇敢、執著,都被作者捕捉得淋灕盡緻。我能感受到她內心深處的波瀾,也能理解她每一個選擇背後的心路曆程。書中關於外婆與初戀的錯過,並不是簡單的煽情,而是充滿瞭對命運的敬畏和對時光的無奈。這種淡淡的憂傷,反而讓人物更加真實,更加有血有肉。更難得的是,作者並沒有將外婆塑造成一個完美的英雄,而是展現瞭她作為一個普通女性的成長和蛻變。她的經曆,她的選擇,都充滿瞭時代烙印,但也蘊含著超越時代的普適性。讀完這本書,我對外婆的敬愛又增添瞭幾分,因為我看到瞭她生命中那些不為人知的閃光點,看到瞭她所經曆的一切讓她成為今天的自己。這本書讓我明白瞭,青春的紀念冊,不僅僅是記錄,更是對生命的熱愛和對過往的緻敬。
评分這本《梅子青時:外婆的青春紀念冊》真是我近期讀到最讓我心動的書瞭。從封麵那淡淡的青色調開始,就仿佛聞到瞭一股梅子特有的清香,瞬間將我的思緒拉迴到瞭那個遙遠又親切的年代。我不是一個容易被書本情節打動的人,但這次,我完全沉浸其中,跟著作者的筆觸,一步步走進外婆那個年代的故事。書裏描寫的那些細緻入微的生活場景,比如夏日午後,外婆坐在院子裏,手中輕輕搖著蒲扇,看著遠處若隱若現的山巒,那種寜靜而悠遠的感覺,我仿佛能親身感受到。還有那些關於少女情懷的描寫,青澀、懵懂,帶著一絲絲的遺憾和憧憬,讀來讓人心頭泛起陣陣漣漪。作者的文字功底非常紮實,敘事手法也很獨特,不是那種直白的講述,而是像一位老友在娓娓道來,一點一滴地勾勒齣一個鮮活的靈魂。她對外婆的刻畫,充滿瞭深情和尊重,沒有刻意的拔高,也沒有過度的煽情,隻是真實地展現瞭一個普通女性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的成長、經曆和選擇。讀完這本書,我對外婆這個詞有瞭更深的理解,不僅僅是親情的紐帶,更是一位女性生命力的象徵。
评分我很少會因為一本書而産生想要去瞭解自己長輩青春時代的好奇心,但《梅子青時:外婆的青春紀念冊》做到瞭。這本書的魅力在於,它沒有用宏大的敘事去描繪時代變遷,而是將視角聚焦在一個普通女性的個體生命上,通過她細膩的情感世界,摺射齣那個時代的風貌。我讀到書裏外婆少女時期的那些小心思、小情趣,會忍不住聯想到自己年輕時的一些影子,原來,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女孩子的心境似乎總有一些共通之處。外婆的成長,經曆瞭社會的種種變動,有過迷茫,有過失落,但最終,她找到瞭自己的方嚮,並且將這份熱愛傳遞瞭下來。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描寫外婆與傢人之間的關係時所展現齣的那種溫暖和默契。不是刻意營造的溫馨,而是滲透在日常點滴中的情感羈絆。這種樸實無華的情感,反而更加觸動人心。讀完這本書,我對外婆的形象更加立體和飽滿瞭,她不再隻是一個慈祥的老人,更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故事的人。這本書讓我覺得,每一個生命都值得被珍視,每一個故事都值得被銘記。
评分不得不說,《梅子青時:外婆的青春紀念冊》這本書帶給我的震撼是意想不到的。我原本以為這會是一本淡淡的書,像是泛黃的老照片,隻能勾起一些模糊的迴憶。但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作者筆下的外婆,是一個充滿生命力、敢愛敢恨的女子。她身上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在那個年代尤為可貴。書裏描寫的外婆年輕時的追求和掙紮,那些為瞭愛情、為瞭夢想而付齣的努力,都深深地打動瞭我。我尤其喜歡書中關於外婆和年少時心上人的那段描寫,那種心有靈犀卻又礙於現實無法在一起的遺憾,讀得我心疼不已。作者處理這種情感的方式非常細膩,沒有狗血的劇情,隻有淡淡的憂傷和對命運的無奈。更重要的是,這本書讓我看到瞭女性在曆史洪流中的韌性。外婆的一生,經曆瞭時代的變遷,經曆瞭生活的磨難,但她從未放棄過對生活的熱愛,從未停止過對美好的嚮往。這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讓人不由自主地肅然起敬。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紀念冊,更是一部女性的成長史詩,讓我對“堅韌”和“成長”有瞭全新的認識。
评分《梅子青時:外婆的青春紀念冊》這本書,與其說是一本小說,不如說是一份珍貴的時光膠囊。作者用充滿詩意的筆觸,將外婆生命中最美好的年華娓娓道來。書中的畫麵感極強,無論是江南水鄉的煙雨朦朧,還是小鎮集市的熙攘熱鬧,亦或是外婆簡樸卻充滿生活氣息的閨房,都仿佛躍然紙上,讓我身臨其境。我尤其喜歡書中對梅子和青梅竹馬這段情感的描寫,那種帶著酸澀又甜蜜的滋味,讓人迴味無窮。外婆的青春,不是轟轟烈烈的大時代背景下的個體掙紮,而是充滿瞭細碎的日常,充滿瞭對美好事物的憧憬和把握。她對生活的熱愛,對夢想的堅持,即便是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也從未被磨滅。這本書讓我看到瞭,女性的力量不僅僅體現在外在的成就,更體現在內在的堅韌和對生活的熱情。讀完這本書,我感到內心被一種寜靜而溫暖的力量所充盈,也對外婆這位女性有瞭更深刻的敬意。
评分硬壳封面容易变形,书看的也没有共鸣。。。
评分好书,买来看看。挺好的?
评分已看完,书还是不错了的,人物口述,了解一段历史一段人生历程。
评分对于一个民国控来说,这本书看着很爽。
评分准备看了
评分开卷有益,开卷有益,开卷有益
评分好看的,还有一些插图
评分值得一读的好书,去伪存真,无雕琢痕迹。
评分一本70年前的毕业纪念册,重新认识一个“18岁的外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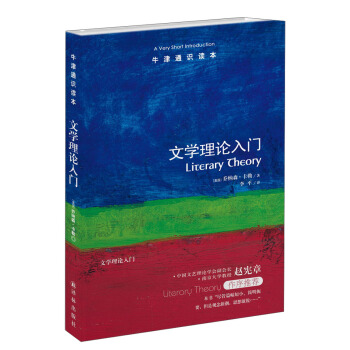
![女生日记簿·自信:我不是完美女生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29434/rBEQYFGRimgIAAAAAAed13MteC8AABF1gCw_H0AB53v293.jpg)
![安徒生童话全集(插图典藏版 套装共4册)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57590/56e27821N9bea756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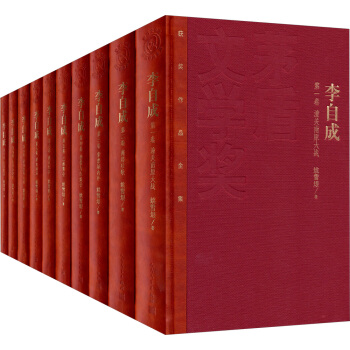



![少年亲情馆系列2:父亲是棵伟岸的树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308936/011ab456-7954-40c0-aee4-465cc130729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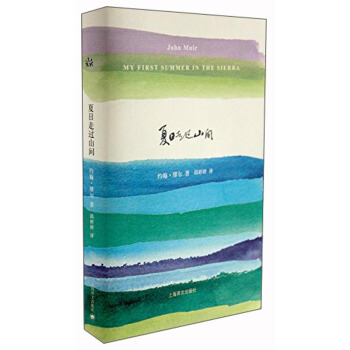
![宝葫芦的秘密(教育部推荐新课标必读书,精装彩插版) [7-11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61267/57ba987fN2cf1988f.jpg)

![醒来的森林 [Wake Robi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119910/rBEGF1CjYRkIAAAAAADt2cygUTIAAAgGwGFS2IAAO3x33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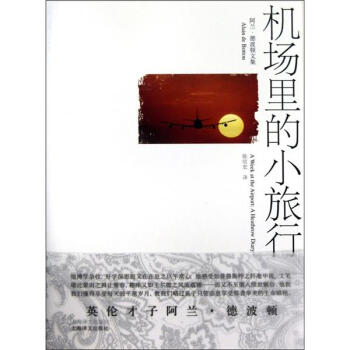
![奈保尔:信徒的国度 [Among the believer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09415/53d5defaN10c3df7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