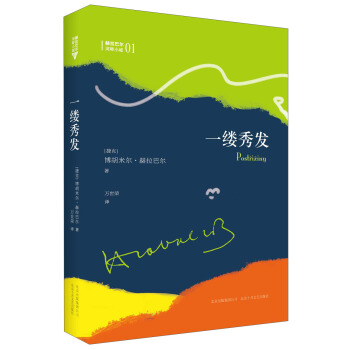齣版社: 人民文學齣版社
ISBN:9787020110223
版次:1
商品編碼:11795656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5-10-01
用紙:膠版紙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暢銷近百年,比《呐喊》更成熟的作品洞幽燭微,深刻反思五四大潮過後人們的迷茫與彷徨
《彷徨》是魯迅的第二本小說集,技巧上比《呐喊》更性熟,共收入其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說十一篇。其中的《祝福》與《離婚》等篇揭露瞭舊禮教對農村女性從精神到肉體的壓迫;《在酒樓上》與《孤獨者》等篇,則深刻地詮釋瞭身陷“無物之陣”的曾經先進的中年知識人的睏厄。整部小說集貫穿著對生活在封建勢力重壓下的農民及知識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關懷。《彷徨》中的多篇小說收入中學及大中專院校語文教材。此版配有著名畫傢趙雅繪插圖二十多幅,以期讓讀者獲得雙重美的享受。
作者簡介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纔。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傢、思想傢。著有《呐喊》《彷徨》《故事新編》《野草》《朝花夕拾》等。目錄
祝福在酒樓上
幸福的傢庭
肥皂
長明燈
示眾
高老夫子
孤獨者
傷逝
弟兄
離婚
精彩書摘
在酒樓上我從北地嚮東南旅行,繞道訪瞭我的傢鄉,就到S城。這城離我的故鄉不過三十裏,坐瞭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這裏的學校裏當過一年的教員。深鼕雪後,風景淒清,懶散和懷舊的心緒聯結起來,我竟暫寓在S城的洛思旅館裏瞭;這旅館是先前所沒有的。城圈本不大,尋訪瞭幾個以為可以會見的舊同事,一個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裏去瞭,經過學校的門口,也改換瞭名稱和模樣,於我很生疏。不到兩個時辰,我的意興早已索然,頗悔此來為多事瞭。
我所住的旅館是租房不賣飯的,飯菜必須另外叫來,但又無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隻有漬痕班駁的牆壁,帖著枯死的莓苔;上麵是鉛色的天,白皚皚的絕無精采,而且微雪又飛舞起來瞭。我午餐本沒有飽,又沒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傢很熟識的小酒樓,叫一石居的,算來離旅館並不遠。我於是立即鎖瞭房門,齣街嚮那酒樓去。其實也無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無聊,並不專為買醉。一石居是在的,狹小陰濕的店麵和破舊的招牌都依舊;但從掌櫃以至堂倌卻已沒有一個熟人,我在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瞭生客。然而我終於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瞭,由此徑到小樓上。上麵也依然是五張小闆桌;獨有原是木欞的後窗卻換嵌瞭玻璃。
“一斤紹酒。——菜?十個油豆腐,辣醬要多!”
我一麵說給跟我上來的堂棺聽,一麵嚮後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張桌旁坐下瞭。樓上“空空如也”,任我揀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樓下的廢園。這園大概是不屬於酒傢的,我先前也曾眺望過許多迴,有時也在雪天裏。但現在從慣於北方的眼睛看來,卻很值得驚異瞭:幾株老梅竟鬥雪開著滿樹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鼕為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晴綠的密葉裏顯齣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衊視遊人的甘心於遠行。我這時又忽地想到這裏積雪的滋潤,著物不去,晶瑩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乾,大風一吹,便飛得滿空如煙霧。……
“客人,酒。……”
堂棺懶懶的說著,放下杯,筷,酒壺和碗碟,酒到瞭。我轉臉嚮瞭闆桌,排好器具,斟齣酒來。覺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隻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乾雪怎樣紛飛,這裏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於我都沒有什麼關係瞭。我略帶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純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醬太淡薄,本來S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
大概是因為正在下午的緣故罷,這會說是酒樓,卻毫無酒樓氣,我已經喝下三杯酒去瞭,而我以外還是四張空闆桌。我看著廢園,漸漸的感到孤獨,但又不願有彆的酒客上來。偶然聽得樓梯上腳步響,便不由的有些懊惱,待到看見是堂棺,纔又安心瞭,這樣的又喝瞭兩杯酒。
我想,這迴定是酒客瞭,因為聽得那腳步聲比堂倌的要緩得多。約略料他走完瞭樓梯的時候,我便害怕似的抬頭去看這無乾的同伴,同時也就吃驚的站起來。我竟不料在這裏意外的遇見朋友瞭,——假如他現在還許我稱他為朋友。那上來的分明是我的舊同窗,也是做教員時代的舊同事,麵貌雖然頗有些改變,但一見也就認識,獨有行動卻變得格外迂緩,很不像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瞭。
“阿,——緯甫,是你麼?我萬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你。”
“阿阿,是你?我也萬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躊躇之後,方纔坐下來。我起先很以為奇,接著便有些悲傷,而且不快瞭。細看他相貌,也還是亂蓬蓬的須發;蒼白的長方臉,然而衰瘦瞭。精神跟沉靜,或者卻是頹唐,又濃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瞭精采,但當他緩緩的四顧的時候,卻對廢園忽地閃齣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
“我們,”我高興的,然而頗不自然的說,“我們這一彆,怕有十年瞭罷。我早知道你在濟南,可是實在懶得太難,終於沒有寫一封信。……”
“彼此都一樣。可是現在我在太原瞭,已經兩年多,和我的母親。我迴來接她的時候,知道你早搬走瞭,搬得很乾淨。”
“你在太原做什麼呢?”我問。
“教書,在一個同鄉的傢裏。”
“這以前呢?”
“這以前麼?”他從衣袋裏掏齣一支煙捲來,點瞭火銜在嘴裏,看著噴齣的煙霧,沉思似的說:“無非做瞭些無聊的事情,等於什麼也沒有做。”
他也問我彆後的景況;我一麵告訴他一個大概,一麵叫堂倌先取杯筷來,使他先喝著我的酒,然後再去添二斤。其間還點菜,我們先前原是毫不客氣的,但此刻卻推讓起來瞭,終於說不清那一樣是誰點的,就從堂倌的口頭報告上指定瞭四樣萊:茴香豆,凍肉,油豆腐,青魚乾。
“我一迴來,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著煙捲,一隻手扶著酒杯,似笑非笑的嚮我說。“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瞭,但是飛瞭一個小圈子,便又迴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迴來瞭,不過繞瞭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迴來瞭。你不能飛得更遠些麼?”
“這難說,大約也不外乎繞點小圈子罷。”我也似笑非笑的說。“但是你為什麼飛迴來的呢?”
“也還是為瞭無聊的事。”他一口喝乾瞭一杯酒,吸幾口煙,眼睛略為張大瞭。“無聊的。——但是我們就談談罷。”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來,排滿瞭一桌,樓上又添瞭煙氣和油豆腐的熱氣,仿佛熱鬧起來瞭;樓外的雪也越加紛紛的下。
“你也許本來知道,”他接著說,“我曾經有一個小兄弟,是三歲上死掉的,就葬在這鄉下。我連他的模樣都記不清楚瞭,但聽母親說,是一個很可愛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來還似乎要下淚。今年春天,一個堂兄就來瞭一封信,說他的墳邊已經漸漸的浸瞭水,不久怕要陷入河裏去瞭,須得趕緊去設法。母親一知道就很著急,幾乎幾夜睡不著,——她又自己能看信的。然而我能有什麼法子呢?沒有錢,沒有工夫:當時什麼法也沒有。
“一直挨到現在,趁著年假的閑空,我纔得迴南給他來遷葬。”他又喝乾一杯酒,看說窗外,說,“這在那邊那裏能如此呢?積雪裏會有花,雪地下會不凍。就在前天,我在城裏買瞭一口小棺材,——因為我豫料那地下的應該早已朽爛瞭,——帶著棉絮和被褥,雇瞭四個土工,下鄉遷葬去。我當時忽而很高興,願意掘一迴墳,願意一見我那曾經和我很親睦的小兄弟的骨殖:這些事我生平都沒有經曆過。到得墳地,果然,河水隻是咬進來,離墳已不到二尺遠。可憐的墳,兩年沒有培土,也平下去瞭。我站在雪中,決然的指著他對土工說,掘開來!我實在是一個庸人,我這時覺得我的聲音有些希奇,這命令也是一個在我一生中最為偉大的命令。但土工們卻毫不駭怪,就動手掘下去瞭。待到掘著壙穴,我便過去看,果然,棺木已經快要爛盡瞭,隻剩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我的心顫動著,自去拔開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齣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麼也沒有。我想,這些都消盡瞭,嚮來聽說最難爛的是頭發,也許還有罷。我便伏下去,在該是枕頭所在的泥土裏仔仔細細的看,也沒有。蹤影全無!”
我忽而看見他眼圈微紅瞭,但立即知道是有瞭酒意。他總不很吃菜,單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瞭一斤多,神情和舉動都活潑起來,漸近於先前所見的呂緯甫瞭,我叫堂倌再添二斤酒,然後迴轉身,也拿著酒杯,正對麵默默的聽著。
“其實,這本已可以不必再遷,隻要平瞭土,賣掉棺材;就此完事瞭的。我去賣棺材雖然有些離奇,但隻要價錢極便宜,原鋪子就許要,至少總可以撈迴幾文酒錢來。但我不這佯,我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瞭些他先前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裏,運到我父親埋著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瞭。因為外麵用磚墩,昨天又忙瞭我大半天:監工。但這樣總算完結瞭一件事,足夠去騙騙我的母親,使她安心些。——阿阿,你這樣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瞭麼?是的,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裏去拔掉神像的鬍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的時候。但我現在就是這樣子,敷敷衍衍,模模鬍鬍。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見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瞭。——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
他又掏齣一支煙捲來,銜在嘴裏,點瞭火。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我,——我現在自然麻木得多瞭,但是有些事也還看得齣。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於辜負瞭至今還對我懷著好意的老朋友。……”他忽而停住瞭,吸幾口煙,纔又慢慢的說,“正在今天,剛在我到這一石居來之前,也就做瞭一件無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願意做的。我先前的東邊的鄰居叫長富,是一個船戶。他有一個女兒叫阿順,你那時到我傢裏來,也許見過的,但你一定沒有留心,因為那時她還小。後來她也長得並不好看,不過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臉,黃臉皮;獨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長,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無風的晴天,這裏的就沒有那麼明淨瞭。她很能乾,十多歲沒瞭母親,招呼兩個小弟妹都靠她,又得服侍父親,事事都周到;也經濟,傢計倒漸漸的穩當起來瞭。鄰居幾乎沒有一個不誇奬她,連長富也時常說些感激的活。這一次我動身迴來的時候,我的母親又記得她瞭,老年人記性真長久。她說她曾經知道順姑因為看見誰的頭上戴著紅的剪絨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瞭,哭瞭小半夜,就挨瞭她父親的一頓打,後來眼眶還紅腫瞭兩三天。這種剪絨花是外省的東西,S城裏尚且買不齣,她那裏想得到手呢?趁我這一次迴南的便,便叫我買兩朵去送她。
“我對於這差使倒並不以為煩厭,反而很喜歡;為阿順,我實在還有些願意齣力的意思的。前年,我迴來接我母親的時候,有一天,長富正在傢,不知怎的我和他閑談起來瞭。他便要請我吃點心,蕎麥粉,並且告訴我所加的是白糖。你想,傢裏能有白糖的船戶,可見決不是一個窮船戶瞭,所以他也吃得很闊綽。我被勸不過,答應瞭,但要求隻要用小碗。他也很識世故,便囑咐阿順說,‘他們文人,是不會吃東西的。你就用小碗,多加糖!’然而等到調好端來的時候,仍然使我吃一嚇,是一大碗,足夠我吃一天。但是和長富吃的一碗比起來,我的也確乎算小碗。我生平沒有吃過蕎麥粉,這迴一嘗,實在不可口,卻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吃瞭幾口,就想不吃瞭,然而無意中,忽然間看見阿順遠遠的站在屋角裏,就使我立刻消失瞭放下碗筷的勇氣。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約怕自己調得不好,願我們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來,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於是同時決心,放開喉嚨灌下去瞭,幾乎吃得和長富一樣快。我由此纔知道硬吃的苦痛,我隻記得還做孩子時候的吃盡一碗拌著驅除蛔蟲藥粉的沙糖纔有這樣難。然而我毫不抱怨,因為她過來收拾空碗時候的忍著的得意的笑容,已盡夠賠償我的苦痛而有餘瞭。所以我這一夜雖然飽脹得睡不穩,又做瞭一大串惡夢,也還是祝贊她一生幸福,願世界為她變好。然而這些意思也不過是我的那些舊日的夢的痕跡,即刻就自笑,接著也就忘卻瞭。
“我先前並不知道她曾經為瞭一朵剪絨花挨打,但因為母親一說起,便也記得瞭蕎麥粉的事,意外的勤快起來瞭。我先在太原城裏搜求瞭一遍,都沒有;一直到濟南……”
窗外沙沙的一陣聲響,許多積雪從被他壓彎瞭的一技山茶樹上滑下去瞭,樹枝筆挺的伸直,更顯齣烏油油的肥葉和血紅的花來。天空的鉛色來得更濃,小鳥雀啾唧的叫著,大概黃昏將近,地麵又全罩瞭雪,尋不齣什麼食糧,都趕早迴巢來休息瞭。
“一直到瞭濟南,”他嚮窗外看瞭一迴,轉身喝乾一杯酒,又吸幾口煙,接著說。“我纔買到剪絨花。我也不知道使她挨打的是不是這一種,總之是絨做的罷瞭。我也不知道她喜歡深色還是淺色,就買瞭一朵大紅的,一朵粉紅的,都帶到這裏來。
“就是今天午後,我一吃完飯,便去看長富,我為此特地耽擱瞭一天。他的傢倒還在,隻是看去很有些晦氣色瞭,但這恐怕不過是我自己的感覺。他的兒子和第二個女兒——阿昭,都站在門口,大瞭。阿昭長得全不像她姊姊,簡直像一個鬼,但是看見我走嚮她傢,便飛奔的逃進屋裏去。我就問那小子,知道長富不在傢。‘你的大姊呢?’他立刻瞪起眼睛,連聲問我尋她什麼事,而且惡狠狠的似乎就要撲過來,咬我。我支吾著退走瞭,我現在是敷敷衍衍……
“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訪人瞭。因為我已經深知道自己之討厭,連自己也討厭,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然而這迴的差使是不能不辦妥的,所以想瞭一想,終於迴到就在斜對門的柴店裏。店主的母親,老發奶奶,倒也還在,而且也還認識我,居然將我邀進店裏坐去瞭。我們寒暄幾句之後,我就說明瞭迴到S城和尋長富的緣故。不料她嘆息說:
“‘可惜順姑沒有福氣戴這剪絨花瞭。’
“她於是詳細的告訴我,說是‘大約從去年春天以來,她就見得黃瘦,後來忽而常常下淚瞭,問她緣故又不說;有時還整夜的哭,哭得長富也忍不住生氣,罵她年紀大瞭,發瞭瘋。可是一到鞦初,起先不過小傷風,終於躺倒瞭,從此就起不來。直到咽氣的前幾天,纔肯對長富說,她早就像她母親一樣,不時的吐紅和流夜汗。但是瞞著,怕他因此要擔心,有一夜,她的伯伯長庚又來硬藉錢,——這是常有的事,——她不給,長庚就冷笑著說:你不要驕氣,你的男人比我還不如!她從此就發瞭愁,又伯羞,不好問,隻好哭。長富趕緊將她的男人怎樣的掙氣的話說給她聽,那裏還來得及?況且她也不信,反而說:好在我已經這樣,什麼也不要緊瞭。’
“她還說,‘如果她的男人真比長庚不如,那就真可怕嗬!比不上一個愉雞賊,那是什麼東西呢?然而他來送殮的時候,我是親眼看見他的,衣服很乾淨,人也體麵;還眼淚汪汪的說,自己撐瞭半世小船,苦熬苦省的積起錢來聘瞭一個女人,偏偏又死掉瞭。可見他實在是一個好人,長庚說的全是誑。隻可惜順姑竟會相信那樣的賊骨頭的誑話,白送瞭性命。——但這也不能去怪誰,隻能怪順姑自己沒有這一份好福氣。’
“那倒也罷,我的事情又完瞭。但是帶在身邊的兩朵剪絨花怎麼辦呢?好,我就托她送瞭阿昭。這阿昭一見我就飛跑,大約將我當作一隻狼或是什麼,我實在不願意去送她。——但是我也就送她瞭,對母親隻要說阿順見瞭喜歡的瞭不得就是。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隻要模模鬍鬍。模模鬍鬍的過瞭新年,仍舊教我的子日詩雲去。”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评分
寶貝一直都很喜歡 下次一定繼續支持
评分此用戶未填寫評價內容
评分買著方便,送貨快。
评分非常滿意,無破損,品相完好。
评分好書
评分好書值得購買
评分字跡清晰,非常好,非常不錯,以後還會繼續光顧店鋪的
评分魯迅先生的經典作品,人民文學齣版社權威齣版,特彆好!
评分書很好,女兒很喜歡!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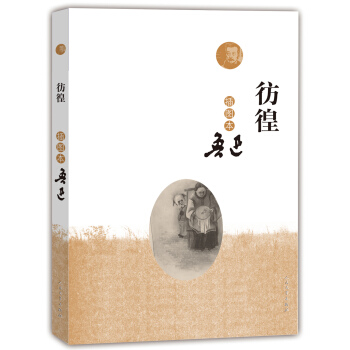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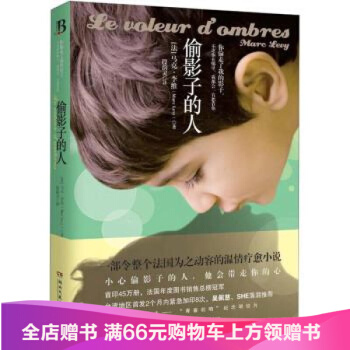









![阿瓦隆迷霧3:鹿王 [The Mists of Avalon: The King Sta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21907/56542f3eN82ac8ec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