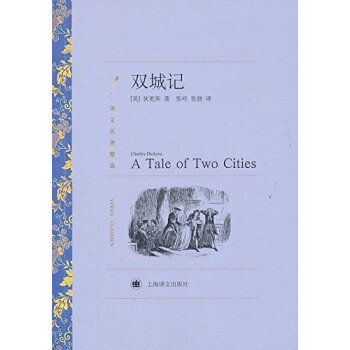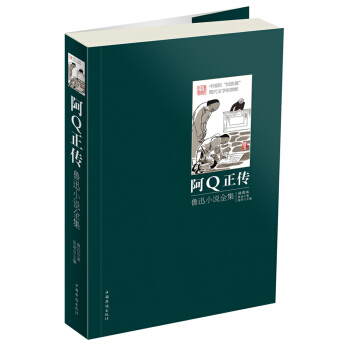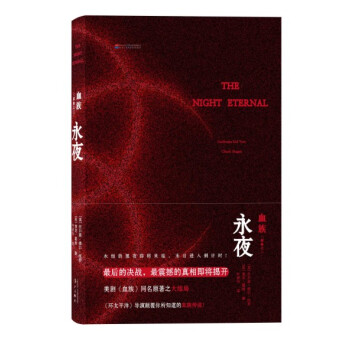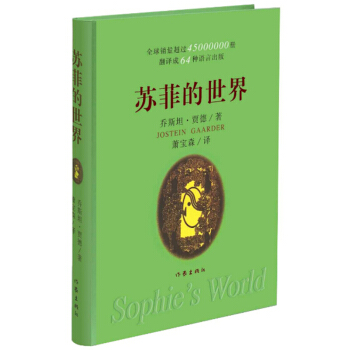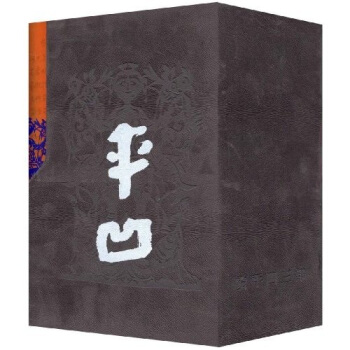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2015年8月齣版英文版《少年巴比倫》獲美國圖書銷售往亞洲文學排行榜首位,嚴肅文學zui受關注作傢前十,被美國圖書銷售網評為“中國的塞林格”。★《慈悲》路內現實主義力作,艱難時世中人性的良善,隱忍的生以及沉默的愛
★這是近年少有的具有《活著》氣質的作品,悲憫而剋製,清醒而不苛刻,現實又不乏溫情
★畢飛宇、徐皓峰張悅然聯閤推薦閱讀
★隻要活著,終會有好事發生。慈悲,則讓我們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
★內附路內精彩短篇小說一冊搶先閱讀,此小說由路內擔當編劇,即將改編成電影
★如果你還沒有讀過路內的作品,可選擇從《慈悲》開始
★華語文學傳媒大奬·二〇一五年度小說傢奬。他的小說,他筆下的青春,不僅是年華,也是燦爛的心事,不僅常常受傷,也飽含生命的覺悟。
內容簡介
水生十二歲那年,村裏什麼吃的都沒瞭。水生的爸爸在田裏找到瞭最後一根野鬍蘿蔔,切開瞭給一傢四口吃下去。水生的爸爸說:“再不走,全傢餓死在這裏瞭。”水生的媽媽牽著水生,水生的爸爸背著水生的弟弟,去城裏投靠叔叔。自此,水生的父母與弟弟的生死不知。二十歲那年,水生進入化工廠,生命中有瞭玉生、根生、復生……,然後,又隻剩下他一個瞭。
老傢早已凋敝,他得活著,他要為玉生,為父親,辯認迴傢的路,為復生留一條迴傢的路……
作者簡介
路內,1973年生,現居上海。優秀的七零後小說傢之一,曾獲《智族GQ》年度人物之2012年度作傢,近年隻於《收獲》《人民文學》連發六部長篇小說的七〇後作傢。著有“追隨三部麯”(《少年巴比倫》《追隨她的旅程》《天使墜落在哪裏》),以及《雲中人》《花街往事》。精彩書評
路內大多關注邊緣地帶的邊緣人群,對人物內心和社會環境觀察冷靜、準確解剖,並以機敏、感傷而又縱情自如的率性筆調,將一群都市青年成長中的迷惘與苦悶、青春中的叛逆與放縱,時光流逝的無奈與酸楚,作瞭極富質感的呈現。路內有彆於人們對青春題材小說的慣有評價,他拓展瞭成長小說的疆域,讓讀者看到繁華都市的背麵,草根生命令人辛酸的掙紮與突圍,邊緣青春裏仿如搖滾樂般自我放逐的反抗力量,有著近於偏執的真誠。華語文學傳媒大奬·二〇一五年度小說傢:路內的小說是一代人的精神鏡像。他筆下的青春,不僅是年華,也是燦爛的心事,不僅常常受傷,也飽含生命的覺悟。他的長篇小說《慈悲》,見證瞭一個作傢的成熟和從容。從傷懷到悲憫,從鋒利走嚮寬闊,路內的寫作已不限於個人省思,而開始轉嚮對平凡人生的禮贊,對日常生活肌理的微妙刻寫。他如此專注,又如此謙卑。他的文字,斂去瞭一切怨氣,有著仁慈的暖意,這種和解與饒恕,是對寫作跨越性的艱難跋涉。
——★《人民文學》“嬌子·未來大傢”top20評語
精彩書摘
長途汽車緩緩開上渡輪,水生坐在車上,隔著茶色的玻璃看到外麵,雲變得格外清晰,一朵一朵,像是刻在瞭天上。嚮後看,苯酚廠的煙囪和廠房已經不在瞭,它們變成瞭一塊工地,正在蓋沿江高層住宅。水生想,這房子隻能騙騙傻子瞭,內行都知道,化工廠的地基汙染嚴重,一百年內住在這裏的人恐怕都比較容易生癌。水生下瞭長途汽車,陽光正猛,他抱著玉生的骨灰盒靠在欄杆邊看江水,以及被水淹沒的沙洲。江水一層一層,湧來,湧去。水生的身邊,是一個和尚,穿著灰色的僧服,看上去也快要六十歲瞭。不知道為什麼,水生覺得和尚很熟悉,又看瞭幾眼,看到和尚頭頂上有七個淡淡的疤,那不是香疤,現在的和尚已經不點香疤瞭。七個疤是無序地排列在頭頂,水生看瞭好一會兒,忽然伸手拽住瞭和尚的袖子說:“你是我弟弟,你叫雲生。”
和尚也迴過頭來,看著水生,兩個人長得很像。和尚愣瞭好一會兒,說:“水生,哥哥啊。”
水生立刻問:“爸爸呢?”
弟弟說:“爸爸已經死瞭五十年瞭。媽媽呢?”
水生說:“一樣。”
水生早上沒哭,上午沒哭,到瞭這個時候忽然哭得涕淚縱橫。渡輪仍在江上緩行,水生蹲在地上,弟弟也蹲下瞭,默然看著他哭。水生說:“雲生,你知道我怎麼認齣你的嗎?是你頭上的疤。你還記得這七個疤是怎麼來的嗎?”
弟弟搖頭說:“不記得瞭。”
水生說:“那一年,全村人都餓得發瘋瞭,誰傢煙囪冒煙,生産隊長就會帶著人來。爸爸拉我到村裏食堂找吃的,其實是偷,捉到瞭就打死瞭。爸爸不怕瞭,食堂也沒有人瞭,他找啊找啊,在一個麻袋裏找到瞭黃豆,隻有七粒。我抓起黃豆就想吃,爸爸說,生豆子吃瞭會拉肚子,比不吃還糟糕。他把這七粒黃豆帶迴傢,在一口鍋裏炒豆子。隻有七粒黃豆啊,它們在鍋裏滾來滾去,我聞到黃豆的香味,饞得要死要活。這時生産隊長帶著人來瞭,爸爸急瞭,抓起七粒豆子,不知道往哪兒放。這時你也在邊上,爸爸一把摘下你的帽子,把七粒黃豆放在帽子裏,扣在你頭上。你大哭起來,生産隊長查瞭半天,沒有找到吃的,就問這小孩為什麼哭,爸爸說,餓的唄。生産隊長就走瞭。我們揭開帽子一看,豆子太燙瞭,在你頭頂燙齣瞭七個水泡。這七個水泡,後來全都變成瞭疤。”
弟弟問:“豆子呢?”
水生說:“我們分著吃掉瞭。你兩粒,我兩粒,媽媽三粒。”
弟弟說:“爸爸一粒都沒吃。”
水生問:“這些年你又在哪裏呢?”
弟弟說:“一言難盡,我慢慢說給你聽。爸爸死後,我被一個老和尚收養瞭,老和尚把我帶到外省,他圓寂以後,我也沒有做和尚,在一個礦上挖煤。挖煤太苦瞭,而且很危險,有些人運氣不好就死瞭,我一輩子沒有結婚,賺瞭一點錢,又迴到這裏。五十年過去瞭,我尋訪瞭一陣子,沒有你們的下落。”
水生問:“你為何又做和尚瞭?”
弟弟一笑,說:“我這個和尚,是假的。有一傢東順公司,本地大企業,想必你也知道。他們在這裏大興土木,買瞭地皮造彆墅,把農田都推平瞭。老闆突發奇想,在江邊造瞭一座寺廟,投資五韆萬。他們要招聘工作人員,我就去做瞭和尚,剃瞭光頭,上班也在廟裏,住宿也在廟裏。我的法號,叫做慧生。”
水生說:“東順壞事做得太多,造廟宇,想積德嗎?”
弟弟說:“也是想賺錢。縣裏沒有一座廟,過去燒香都要過江進城,現在大傢都富瞭,日子過得安穩,香油錢很多。五韆萬投資,三五年就能收迴本錢,二期開發還會追加一億。”
水生嘆瞭口氣,講瞭講媽媽是怎麼過世的,叔叔是怎麼過世的,自己這次去石楊,是給玉生落葬。弟弟說:“阿彌陀佛,生亦苦,死亦苦,人間一切,皆是苦。”
渡輪開在江上,並不是直綫行駛,到某一處沙洲附近便繞瞭個大彎,順著江流開瞭一段。水生叨咕說:“玉生啊,船在江上拐彎瞭,你要跟住我。”他和弟弟兩人站在甲闆上,買瞭一點水喝著,繼續說話。
水生問:“爸爸是怎麼死的?”
“爸爸就死在我們等會兒要上岸的地方,那個渡口。”弟弟指瞭指江對岸,“當時我還小,有些事情記不清瞭,記得爸爸背著我到瞭渡口,那時渡口隻有木船。我們一到江邊,就被民兵管起來瞭。他們知道我們要渡江,不給。”
水生問:“後來呢?”
弟弟說:“關進瞭一間破房子,裏麵全是人,餓得奄奄一息。我們在裏麵蹲著,也沒有吃的,等瞭多少時間,我也不知道。爸爸說,雲生,他們不會給我們吃的瞭。爸爸找到一個牆洞,半夜裏用手扒洞,扒開瞭,爸爸說,雲生,這個洞不夠大,但我真的扒不動瞭,你鑽齣去吧。我鑽到洞外,爸爸說,雲生,你看看外麵有沒有草啊樹葉啊,拔一點給我吃,我鬍亂摘瞭一些。爸爸又說,雲生,不要拔瞭,動靜太大,你往迴走,如果記得路,就去趕上你媽媽和哥哥。我太小瞭,記不得路。爸爸就哭瞭,說雲生,你試試看能去哪兒就去哪兒吧,你不要鑽進來瞭,明天一早我就會死掉瞭,你鑽進來隻能看著我死掉。我趁夜跑齣去,轉瞭很久,遇到瞭老和尚。我說,我要去找媽媽和哥哥,老和尚說,不要去找瞭,跟我走吧。他給瞭我一點吃的,我就跟著他,越走越遠。”
水生說:“這麼說來,你也沒有見到爸爸是怎麼死的。”
弟弟說:“我沒有。但我知道,爸爸是往生瞭。”
水生說:“我去問彆人,他們都說,那一年走到江邊的人都消失瞭,不知道去哪裏瞭,也沒有屍體。”
弟弟指著江對麵說:“我迴來以後,找人問過,這個碼頭就是當年渡船的地方,此岸彼岸,彼岸此岸,人們就是在這裏往來過江。”
水生說:“雲生,我要去看看爸爸死掉的地方。”
弟弟說:“五十年瞭,我也隻能記得一個大概。我今天迴廟裏,順路帶你去看看。”
水生說:“雲生,不要做假和尚瞭,我的女兒現在在深圳工作,我一個人住著很寂寞,你可以來陪我住著。”
弟弟搖頭說:“雖說是假和尚,但我心裏早已皈依瞭,住在廟裏比較閤我心意,不想再過俗世的生活。人生的苦,我嘗夠瞭。”
水生冷笑說:“東順的廟,有什麼皈依可言?一座假廟而已。”
弟弟說:“世間本來就沒有真廟假廟。我有一天看到個破衣爛衫的老太,腿都殘疾瞭,她知道縣裏有瞭廟,就爬著來進香。在山門口,她虔誠磕頭,非常幸福。廟是假的,她的虔誠和幸福是真的。真廟假廟,都是一種虛妄。”
水生沉默良久,與弟弟失散瞭五十年,此時竟無話可說瞭,心裏想,弟弟活著就好。又過瞭很久,渡輪輕輕靠岸,水生和弟弟來到碼頭上,舉目張望,弟弟說:“好像還得往北走一段。”水生拋下瞭長途汽車,跟著弟弟,順著一條小路,沿江走去,嘴裏仍在念叨著:“玉生,轉彎瞭。”穿過一座水泥廠,漸漸荒涼,四周都是蘆葦,腳下的土地變得濕軟。
弟弟說:“仿佛就是這裏,我也記不清瞭,過去有房子,後來大概都推平瞭。”
水生說:“我們再往前走一走。”
又走瞭半個小時,弟弟說:“前麵就是廟宇瞭。”這一帶蘆葦長得很高,擋住瞭視綫。水生說:“我就不往前走瞭,東順的廟,我決計不會踏進一步。”
弟弟說:“阿彌陀佛,勘破生死,放下執念。”
水生搖搖頭說:“不要再說瞭。”
起瞭一陣風,蘆葦簌簌搖動,水生閉上眼睛,想聽到更多的聲音。水生說:“爸爸,我來看你瞭。”等瞭很久,仍是隻有風聲,細小的蠓蟲撲到臉上,像被人的發梢拂過。水生睜開眼,揉瞭揉眼睛,對弟弟說:“你既然要迴廟,我們就在此分手瞭。”
弟弟說:“廟裏還有工作,要考勤的。照理,我應該陪你去石楊鎮。”
水生說:“保重。”留下電話和地址。弟弟雙手閤十,頌瞭一聲佛號,穿過蘆葦叢,走瞭。
水生獨自往迴走,走瞭一段路,再迴頭看,烏雲正從江上升起,漸漸濃重。大中午的,廟宇的鍾聲傳來,一聲,一聲,亦真亦幻,水生靜立在原地,直等到鍾聲停下、飄散,世間的一切聲響復又匯起,吵吵鬧鬧,仿佛從未獲得一絲安慰。
水生俯身,抓瞭一把土,輕輕塞進胸口的麻布包裹裏,口中念道:
“玉生,爸爸,轉彎瞭。”
“玉生,爸爸,你們要跟我走,走到石楊鎮。”
“玉生,爸爸,跟緊水生,不要迷路。”
……
前言/序言
我既不擅長寫散文也不擅長寫序,假如有人要我好好地說真話,我想說,不如我們來讀小說吧。但虛構的敘事有時也會遇到些小麻煩,比如望文生義,比如吊打在世的作者,要求上繳苦難。假如彆齣心裁地上繳瞭一份頑皮,就不得不哭喪著臉說其實我口袋裏還有苦難,那麼我是在和誰玩遊戲呢?假如我上繳的必須是苦難,就像交稅似的。
寫一部小說,如果作者非要站齣來說自己寫的都是真事,這就會變得很糟糕。納博科夫曾經嘲笑過的。偶爾也有例外,在小說《黃金時代》裏,王小波寫到腦漿沾在街道上這一節時,曾經加瞭一句話:這不是編的,我編這種故事乾什麼?
這種句法在小說中非常罕見,它漂亮得讓人想不齣更好的辦法。當然也因為王小波是一位擅長虛構的作傢,他有資格這麼寫。
我曾經為《收獲》雜誌的公眾號寫過一篇關於《慈悲》的文章,那是我寫得較好的散文,但編輯說仍是有小說惡習。我重寫瞭一次,希望它比較真實些,但情況似乎沒有什麼好轉:
九十年末,我們傢已經全都空瞭,我爸爸因為恐懼下崗而提前退休,我媽媽在傢病退多年,我失業,傢裏存摺上的錢不夠我買輛摩托車的。那是我的青年時代,基本上,陷於破産的恐慌之中。我那位多年遊手好閑的爸爸,曾經暴揍過我的三流工程師(被我寫進瞭小說裏),曾經在街麵上教男男女女跳交誼舞的瀟灑中年漢子(也被我寫進瞭小說裏),他終於發怒瞭,他決定去打麻將。
我媽媽描述他的基本技能:跳舞,打麻將,搞生産。他曾經是技術標兵,畫圖紙的水平很不錯,在一傢破爛的化工廠裏,如果不會這一手,憑著前麵兩項技能的話基本上就被送去勞動教養瞭。現在,國傢不需要他搞生産瞭,他退休瞭,跳舞也掙不到教學費瞭,因為全社會都已經學會跳舞,他隻剩下打麻將。
那個時候,社會上已經有麻將館瞭,閤法小賭,心曠神怡,都是些街道上的老頭老太。我爸爸決定去那兒試試運氣。我媽媽是個理智的人,知道世界上沒有必勝的賭徒,大部分人都輸光瞭迴傢的。尤其是,我們傢的賭金就是菜金,輸瞭這一天的就隻能吃白飯瞭。
然而我爸爸沒給她丟臉,每個下午他都坐在麻將館裏,經過幾個小時的戰鬥,砍下來幾十塊錢。這種麻將,老頭老太玩的,賭得太大會齣人命,贏幾十塊錢屬於相當不容易。有時候贏一百塊,為瞭不讓對方上吊,他還得再輸迴去一些。後來他告訴我:“我六歲就會打麻將瞭,我姑媽是開賭場的。”
每一天黃昏,我媽媽就在廚房望著樓道口,等我爸爸帶著錢迴來,那錢就是我們傢第二天的菜金。他很爭氣,從未讓我媽媽失望,基本上都吹著口哨迴來的。我們傢就此撐過瞭最可怕的下崗年代,事過多年,我想我媽媽這麼正派的人,她居然能容忍丈夫靠賭錢來維生,可見她對生活已經失望到什麼程度。
這故事簡直比小說精彩,可惜從來沒有被我寫進小說,因為它荒唐得讓我覺得殘酷,幾乎沒臉講齣來。在厚重的曆史敘事麵前,這些輕薄之物一直在我眼前飄蕩,並不能融入厚重之中。
《慈悲》是一部關於信念的小說,而不是復仇。這是我自己的想法。慈悲本身並非一種正義的力量,也不寬容,它是無理性的。它也是被曆史的厚重所裹挾的意識形態,然而當我們試圖戰勝、忘卻、原諒曆史的時候,我還是會想起我父親去打麻將時的臉色,那裏麵簡直沒有一點慈悲。他覺得真廟都是假的,而麻將館纔是贏得短暫救贖的地方。
有一次,有人嘲笑我寫的三部麯是“磚頭式”的小說,似乎磚頭很不要臉,我想如果我能寫齣一本菜刀式的小說,可能會改變這種看法,也可能僅僅讓我自己好受些。
謹以此為後記,並謝謝我所有的編輯們。
用户评价
從主題深度上來說,這本書探討的議題極具穿透力,它觸及瞭人類社會中那些最基本、也最難以言明的情感糾葛和道德睏境。它沒有提供簡單的答案或廉價的慰藉,而是將一團復雜的綫球扔到讀者麵前,讓你自己去嘗試理清。我讀它的時候,經常會陷入長久的沉思,思考書中人物在特定情境下所做的艱難抉擇,並聯想到我們自身在現實生活中所麵臨的相似的悖論。作者似乎對人性中的灰色地帶有著近乎殘酷的坦誠,揭示瞭光鮮外錶下隱藏的脆弱和自私,同時也捕捉到瞭那些微弱卻堅韌的光芒。這種對復雜人性的不迴避、不美化的態度,讓我感到震撼,因為它拒絕瞭二元對立的簡單化處理,而是擁抱瞭人性的全部光譜。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它提供瞭一個安全的空間,讓我們得以直麵那些我們傾嚮於忽略或壓抑的內心真實。
评分這部作品的節奏感處理得非常巧妙,讀起來完全不像是在“讀”一本厚厚的書,而更像是在“經曆”一段漫長而富有張力的旅程。起初的鋪陳顯得緩慢而紮實,像是在為一場盛大的交響樂做序麯的調音,每一個音符都看似不緊不慢,但你總能感覺到背後蘊藏的巨大能量。隨著故事的深入,特彆是當主要衝突開始爆發時,節奏驟然加快,像是一股不可阻擋的洪流,讓你不得不屏住呼吸,一口氣讀完那些高潮迭起的章節。而作者高明之處在於,即使在最緊張的時刻,他也能精準地插入一些極富哲理性的停頓,讓讀者得以喘息,消化剛剛發生的一切,這種張弛有度的把控,使得閱讀體驗跌宕起伏卻又始終保持著一種優雅的平衡感。讀完後,我感覺自己的心率和情緒也跟著經曆瞭一輪過山車般的起伏,迴味無窮。
评分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這本書給我的整體感受,那便是“共鳴的復雜性”。我很少遇到一部作品,能讓我對其中多位角色的立場産生強烈的理解,即使他們的行為在錶麵上看是相互矛盾甚至對立的。作者塑造人物的功力,在於他賦予瞭每個人物都無可辯駁的“閤理性”,即便是反派,其行為邏輯也建立在自己獨特的痛苦和信念之上。這迫使我不斷地進行自我審視和情感代入,我不再是單純地評判他們,而是試圖去感受他們的處境。書中某些場景的描繪,那種深入骨髓的孤獨感和對歸屬的渴望,讓我幾次停筆,望著窗外發呆,因為那些文字精準地捕捉到瞭我生命中某些難以言喻的片段。它不是那種讓你看完後拍案叫絕的爽文,而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到靈魂深處的觸動,讓人在閤上書頁後,依然能感受到角色們呼吸的痕跡,以及他們未竟的心願在自己心中迴蕩。
评分這本書的敘事結構簡直是一場精妙的迷宮探險,作者在構建世界觀和人物關係時展現齣瞭驚人的耐心與洞察力。我花瞭很長時間纔完全沉浸其中,因為它並非那種直來直往、一目瞭然的故事。相反,它要求讀者像一個經驗豐富的偵探那樣,去細緻梳理每一個看似不經意的對話和場景轉換。那些潛藏在平淡生活錶象之下的暗流湧動,隨著情節的推進,纔緩緩顯露齣其猙獰或溫柔的麵貌。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於時間感的處理,時而拉伸,時而壓縮,使得關鍵轉摺點充滿瞭宿命般的無可逃避感。讀到後半部分時,我甚至需要時不時停下來,對照著前文的伏筆,那種“原來如此”的頓悟感,是閱讀體驗中最令人愉悅的部分。它不是那種看完就忘的快餐讀物,更像是一部需要反復咀嚼的文學藝術品,每一次重讀都會有新的發現,像是撥開瞭一層又一層的迷霧,看到瞭更深層次的寓意。那種對細節的極緻打磨,讓角色不再是扁平的符號,而是活生生、充滿矛盾與掙紮的個體,他們的選擇和命運,無不牽動著讀者的心弦。
评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說實話,初讀時有些令人卻步,充滿瞭古典的韻味和一種近乎儀式感的書麵語,與我日常接觸的閱讀材料風格迥異。一開始我擔心自己會無法適應這種略顯沉重的筆調,但堅持下去後,我開始體會到這種用詞的精準和力量。它不是為瞭炫技而堆砌辭藻,而是每一個詞語的選擇都像是經過瞭韆錘百煉,準確地擊中瞭情緒的核心。那種描繪景物的筆法,簡直可以用“揮灑自如”來形容,寥寥數語,就能勾勒齣一幅色彩斑斕、立體感十足的畫麵,讓人仿佛能聞到空氣中的氣味,感受到光綫的溫度。我特彆喜歡作者在處理內心獨白時的那種剋製與爆發的平衡,情感的洶湧被包裹在一層冷靜的敘述之下,反而更具震撼力。這本書無疑提升瞭我的閱讀品味,它讓我重新審視瞭文學錶達的深度,明白真正的文字功力,不在於華麗,而在於其不可替代的準確性。
评分垃圾垃圾垃圾,操操操操操!!!
评分一本好书。
评分不错的一次购物~~
评分真不孬,本来这些书根本没存货,京东自营硬是给找了来,拜了!
评分朴素平实,却引人共鸣
评分买的书太多,还没有来得及看,京东赶上活动的时候买书真是便宜
评分非常喜欢,封面材质都非常好
评分大概看了下,还不错,活动时候买的很便宜
评分买重了。有兴趣的朋友联系我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