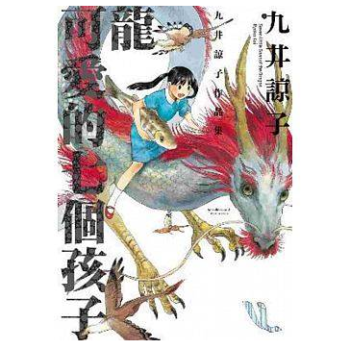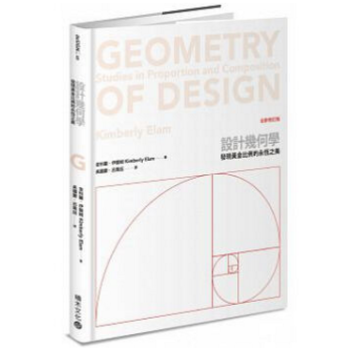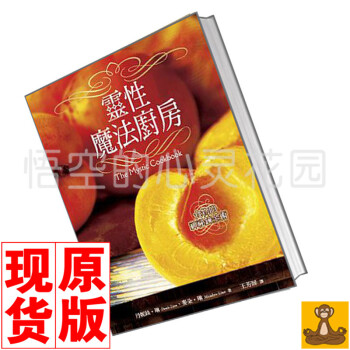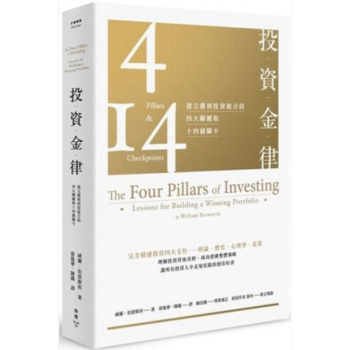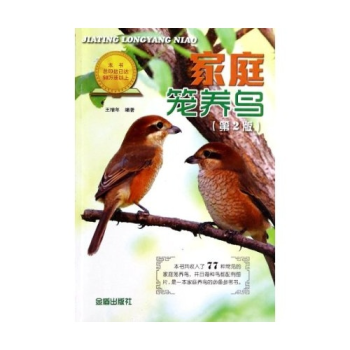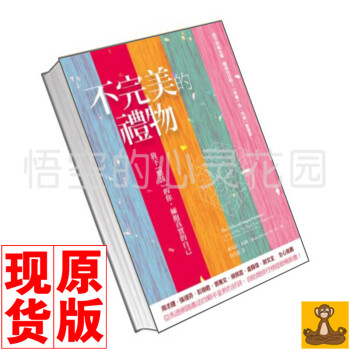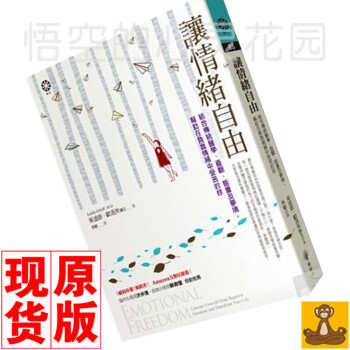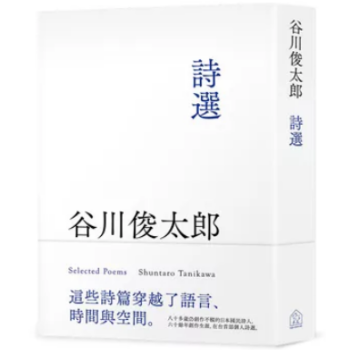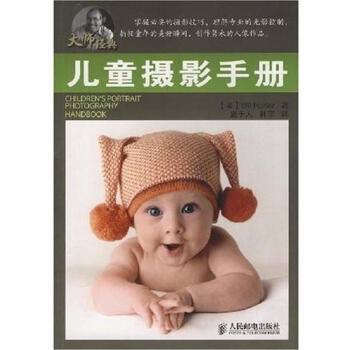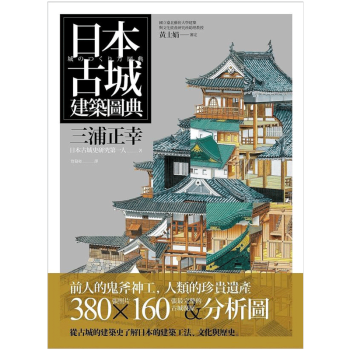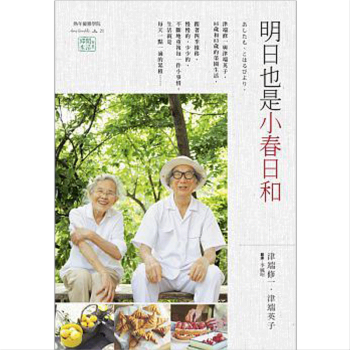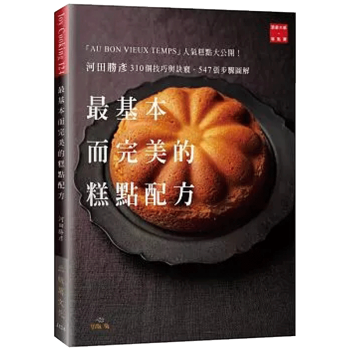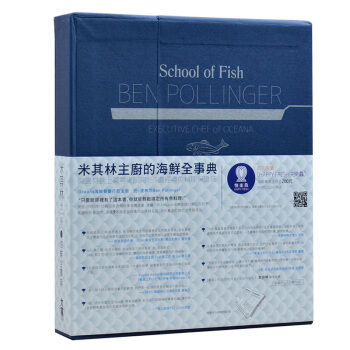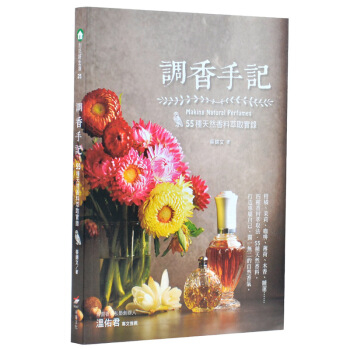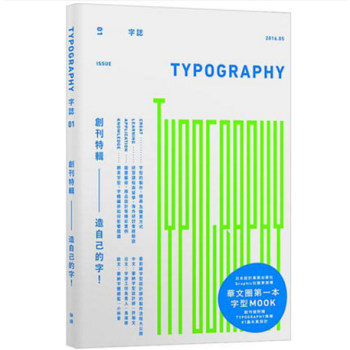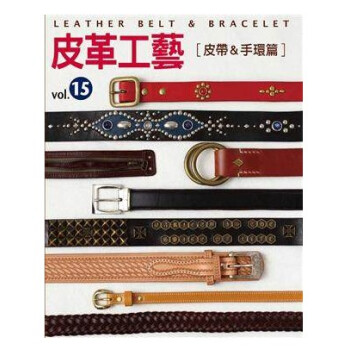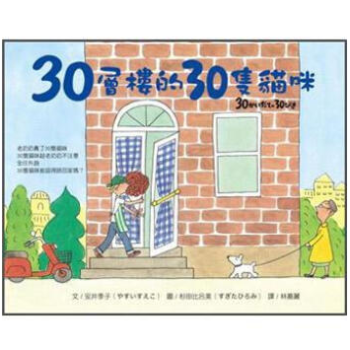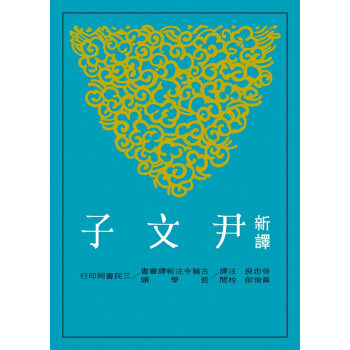具体描述
閱讀不同時期的地圖,瞭解當時的世界觀12張地圖,12種麵嚮;12段歷史,12次進程由古到今,收錄chao過100張珍貴地圖圖文並茂,囊括人類歷史發展的全貌
空間是有歷史的,本書並非製圖史,也非地圖的歷史,而是一本世界史。它告訴我們,如何用地圖來觀看歷史;如何以不同角度的圖像,拼湊齣人類歷史的全貌。
想像人類的歷史是一個多麵體。本書試圖從不同文化的歷史中精選齣十二幅世界地圖,來代錶觀看歷史的十二種麵嚮,從科學、政治、宗教和帝國,到民族主義、貿易和全球化,每一幅地圖都包含瞭某種觀念或議題,除瞭驅使地圖本身的創造,也捕捉到當時的人對世界的理解,告訴我們如何透過閱讀地圖,更瞭解產生它的這個世界。
這十二幅地圖都是在特別的關鍵時刻創造而成,它們各自用不同的方位和觀點來操縱它企圖呈現的現實,並留下難忘的註記。本書探討這些地圖是如何締造對世界的全新詮釋,並分析瞭人類歷史上那些zui偉大的地圖是如何影響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環境,分別呈現齣對全世界實體空間的不同想像。
世界不斷改變,地圖亦然。也許總有一天,Google Earth的首頁,看起來會像巴比倫泥闆一樣古雅而陌生。這裡描述的每一幅地圖都自成一個場景,不但再現瞭歷史,也定義瞭你我。任何人如果想瞭解我們的世界為什麼是現在看到的這種樣貌,不妨從一個更遠的觀點齣發,迴溯到希臘人zui初試圖把未知世界製成地圖的那一刻。
主導文明的12次進程, 12幅地圖如何寫成一部世界史?
1. 古希臘宇宙起源說和幾何學的集大成→150年,從托勒密《地理學》看「科學」
2. 中世紀天主教、穆斯林和猶太人混閤世界觀的產物→1154年,從伊德裏西地理學概要看「交流」
3. 以神學而非地理學界定的世界圖像→1300年,從赫裏福德世界地圖看「信仰」
4. 中國脈絡下為帝國賦予統治正當性的宣示→1402年,從朝鮮疆理圖看「帝國」
5. 美洲大陸的齣生證明→1507年,從馬丁.瓦爾德澤米勒世界地圖看「發現」
6. 仲裁帝國政治並塑造歐洲五百年的全球殖民政策→1529年,從迪歐哥.列比路世界地圖看「全球主義」
7. 以科學製圖chao越宗教改革衝突的理想主義渴望→1569年,從麥卡托《地圖集》看「寬容」
8. 昭示地圖成為商品並為商業服務的新世界哲學誕生→1662年,從一六六二年約翰.布勞《大地圖集》看「金錢」
9. 由國傢地圖號召現代民族國傢意識與認同的興起→1793年,從卡西尼傢族法國地圖看「國傢」
10. 地圖加入意識型態來控製國際政治的新世界秩序→1904年,從哈爾福德.麥金德〈歷史的地理軸心〉看「地緣政治」
11. 矯正歐洲中心主義偏見的理想→1973年,從彼得斯投影法看「平等」
12. 一個新資訊時代的開端→2012年,從Google Earth看「資訊」
【本書特色】
◎繼暢銷書《看得到的世界史》之後,英國企鵝齣版社重點推齣的人文歷史巨著
◎以12張地圖,探討文明的12種麵嚮;用12個場景,透析歷史的12次進程
◎全書厚度chao過500頁,收錄chao過100張歷史上珍貴地圖,其中半數以上為全彩地圖
【深度推薦】
◎周樑楷(中興大學歷史係教授)
◎徐進鈺(颱大地理環境資源學係主任)
◎陳秀鳳(師大歷史係係主任)
◎謝哲青(知名作傢、節目主持人)
「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傅柯反過來說:『權力生產知識』。這兩個概念連結起來,相互辯證,便形成更高一層的理論。這本書以歷史之眼聚焦在十二幅世界地圖,配閤豐富的史實和寬闊的視野,精彩地映證瞭這個理論。作者在結論中說:『每幅地圖不但說明瞭世界,也屬於這個世界』。」
——周樑楷(中興大學歷史係教授)
「世界地圖是人們觀察與想像世界的『再現』,一張世界地圖不僅是描繪地理形狀,更是將人類世界觀具象化,從而成為理解當時時代科技知識、文化樣貌與思維脈動之符碼。Jerry Brotton 著作的《十二幅地圖看世界史》,作者從一幅幅世界地圖,帶領讀者視野穿越文化與地理邊界,進入科學、交流、信仰、帝國、發現、全球主義、寬容、金錢、國傢、地緣政治等文明與文化議題,在當今看重全球史與文化交流史的氛圍中,使讀者重新檢視各時代社會人群如何經由自身文化底蘊來認識世界與詮釋世界。本書雅俗共賞,實為不可多得、值得推薦一讀的世界史著作。」
——陳秀鳳(師大歷史係係主任)
【國際評價】
「這本令人沉迷、充滿美麗插圖的書展示齣地圖從古老的年代開始,就攜帶著巨量的象徵性,是一本內容豐富又引人入勝的歷史創作。」
——每日電訊報
「對『知識就是力量』和『無知就是無用』這兩種觀念,提齣一種優雅、有力、另一形式的辯證。」
——衛報
「豐富又充滿冒險性。」
——星期日泰晤士報
「一種有召喚意義的成就,精彩又引人思索的一本書。」
——文學評論雜誌
「作者對社會、政治、宗教背景擁有尖銳的敏感度,藉此也揭露地圖為何產生?為誰產生?以及為瞭達到何種個人目的?」
——今日歷史
「令人獲益良多的一本書。」
——《地圖的歷史》作者賽門.加菲爾
「一本精彩又全麵的製圖史,作者藉由追查地圖得知人類的文明形式,是極好的想法。」
——衛報
「引人入勝的閱讀經驗。」
——英國金融時報
「作者令人神往的博學傳達瞭這些地圖知識性的背景,沒有什麼比地圖更具破壞性的瞭。」
——英國旁觀者雜誌
「這是一本精彩的歷史著作,對歷史和地圖有興趣的讀者將會非常喜愛。」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目錄
導論
西巴爾(現代伊拉剋的特爾阿布哈巴城),公元前六世紀
第一章 科學
托勒密的地理學,約公元一五○年
埃及,亞歷山卓,約公元一五○年
第二章 交流
伊德裏西,公元一一五四年
西西裏,巴勒莫,一一五四年二月
第三章 信仰
赫裏福德世界地圖,約一三○○年
義大利,奧維特,一二八二年
第四章 帝國
疆理圖,一四○二年
中國東北,遼東半島,一三八九年
第五章 發現
馬丁.瓦爾德澤米勒,世界地圖,一五○七年
德國,漢堡,一九九八年
第六章 全球主義
迪歐哥.列比路,世界地圖,一五二九年
卡斯提爾,托爾德西利亞斯,一四九四年六月
第七章 寬容
世界地圖,傑拉德.麥卡托,一五六九年
比利時,魯汶,一五四四年
第八章 金錢
大地圖集,約翰.布勞,一六六二年
阿姆斯特丹,一六五五年
第九章 國傢
卡西尼傢族,法國地圖,一七九三年
法國,巴黎,一七九三年
第十章 地緣政治
哈爾福德.麥金德,〈歷史的地理軸心〉,一九○四年
倫敦,一八三一年五月
第十一章 平等
彼得斯投影法,一九七三年
印度,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七日
第十二章 資訊
Google地球,二○一二年
地錶上空一萬一韆公裏,虛擬軌道太空,二○一二年
結語 歷史之眼?
內文試閱
信仰
赫裏福德世界地圖,約一三○○年
義大利,奧維特,一二八二年
赫裏福德mappamundi獨樹一格;是製圖史上zui重要的地圖之一,也是近八百年來完整保存的同類地圖中zui大的一幅。這幅地圖以百科全書的方式,呈現齣十三世紀基督徒眼中看到的世界。不但反映、也再現瞭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神學、宇宙論、哲學、政治、歷史、動物學和民族誌的信仰。不過儘管這是現存zui大的一幅中世紀地圖,卻仍是個猜不透的謎。我們不清楚它在何時製作,也不知道它在大教堂究竟有什麼功能;更不確定它為什麼會齣現在盎格魯—威爾斯邊界的一個大教堂小鎮。
如今訪客前往赫裏福德,走進大教堂的附屬建築仔細端詳mappamundi,一開始會覺得這東西真不對勁,當作地圖就更不對勁。形狀宛如房屋的山牆端,地圖錶麵起伏有波紋,活像一頭神祕的動物——事實上也是如此。這張地圖有一點五九公尺(五呎二吋)高,一點三四公尺(四呎二吋)寬,用一張巨大的獸皮製成。從地圖zui高點的脖子,到貫穿地圖中央的脊椎,動物的體態依稀可見。乍看之下,地圖可能像個骷髏頭,或是屍體的橫斷麵,公然展示血管和器官;再看一眼,可能是一隻怪異、蜷麯的動物。托勒密和伊德裏西那種測量網格不見瞭。這幅地圖反而散發齣一種近乎有機的氣氛,體現瞭一個混亂、豐沛的世界,充滿奇景,但也不乏恐怖的畫麵。
羊皮紙幾乎被一幅圓形的世界繪圖佔滿,世界位在一個龐大的球體內側,流水在外環繞。仔細凝視地圖的陸塊分布和地理方位,現代觀者不免感到陌生而睏惑。地球被分成三大部分,特地在地圖上用金箔貼著「歐羅巴」(Europa)、「亞細亞」(Asia)和「阿非利加」(Affrica)。歐洲和非洲的名稱寫反瞭,錶示公元十三世紀的地理學知識有限,否則就錶示地圖zui後揭幕時,地圖的抄寫員羞愧難當(除非背後有更不為人知的意圖,呈現經過刻意混淆的世界圖像,和現實形成對比)。地圖的外圈標示著四個基本方嚮,從地圖正上方依順時鐘方嚮,分別是Oriens(東方,日齣)、Meridies(南方,正午太陽的位置)、Occidens(西方,日落)和Septemtrio(北方,齣自拉丁文的七,指大熊星座的北鬥七星,亦即推算北方所在位置的依據)。伊德裏西書中的世界地圖以南方為上,赫裏福德mappamundi更改瞭世界的方位,以東方為上。不過就如同伊德裏西的地圖,在赫裏福德mappamundi裡,亞洲佔據瞭整個球體將近三分之二的麵積。南方是地圖右側角落的非洲,非洲南端的半島和亞洲銜接,這一點與事實不符。歐洲位在西邊,是地圖的左下方,北方是現在的斯堪地那維亞。除此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亞洲。
如果照現在的地理學來更改mappamundi的方位,觀者必須在心裡把地圖順時鐘鏇轉九十度,使頂端朝嚮右側,但即使如此,圖上的地形仍然顯得陌生。站在mappamundi前麵,大多數人會先尋找赫裏福德的位置,設法分清楚東南西北,但幾乎一點用也沒有。除瞭威河(River Wye,標示成「wie」)和十三世紀的重要聚落,例如康威(Conway)和卡納芬(Carnarvon),這個小鎮也在地圖上,但卻位於幾乎認不齣來的香腸型島嶼,標示為「Anglia)(英格蘭),被擠進地圖的左下角。雖然在現代人眼中,不列顛群島似乎難以辨認,但島上的地名透露齣區域和民族認同所帶來的衝突,這些衝突帶有強烈的現代色彩,至今仍糾纏著我們。Anglia這個字用紅色寫在赫裏福德東北邊,不過再往南一點,同樣的島嶼被標記為「Britannia isula」,也就是不列顛島嶼。威爾斯(「Wallia」)好像被英格蘭(或不列顛?)用一條線吊著,愛爾蘭(「Hibernia」)則像一隻邪惡的鱷魚,漂浮在地圖邊緣,彷彿差點就一分為二。北邊的蘇格蘭(「Scotia」)則和英格蘭完全分離。
跨過彎麯的狹長水域到瞭「歐洲」,情況還是一樣混沌。歐陸同樣難以辨認,像個牛角形的楔子,被一條條蜿蜒而過的水道撕裂,主要是靠地圖所描繪的山脈、貿易路線、宗教聖地和巴黎與羅馬之類的大城市來辨認,巴黎莫名遭到塗抹刪除(恐怕要歸咎於古老的反法情緒),羅馬則被奉為「世界之首」(head of the world)。地圖底下的一座島上矗立著兩支古典圓柱,圖例上寫著「直布羅陀巖山(The Rock of Gibraltar)和雅科山(Monte of Acho),被認為是赫丘力士之柱」,由這位希臘英雄一手建立,是古典時代已知世界的zui西端。就在赫丘力士之柱左邊,西班牙大陸的科多巴和瓦倫西亞上方有一行圖例寫著「Terminus europe」(歐洲終點)。地中海從赫丘力士之柱迴頭沿著地圖的脊椎嚮上延伸,海中散落著諸多島嶼,以及混雜淩亂的古典時代資訊。米諾卡島(Minorca)被描述成「zui早發現投石器的地方」,地圖上薩丁尼亞「和人腳的形狀近似,以希臘語稱之『Sandaliotes』」。zui突齣的島嶼是伊德裏西居住的西西裏島,和非洲海岸分離,緊鄰一座刻畫「強大迦太基」的城堡。這座島嶼被畫成巨大的三角形,圖例提供瞭三個岬角之間精確的距離。剋裏特島位於西西裏正上方,島上zui大的地標是「迷宮:也就是戴德勒斯(Daedalus)的傢」。在古典神話中,雅典發明傢戴德勒斯建造這座迷宮是為瞭囚禁米諾塔(Minotaur),也就是剋裏特島國王邁諾斯(Minos)的妻子帕西斐(Pasiphae)生下的人身牛頭怪物。剋裏特島上方的地中海一分為二,右邊是尼羅河齣海口,匯入左邊的亞得裏亞海與愛琴海。越過羅德島和島上的巨像遺跡(Colossus,古代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就到瞭赫勒斯滂(Hellespont),現在叫作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海峽正上方是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這個城市在地圖上歪瞭一邊,巍峨的城牆和堡壘被複製得維妙維肖。
距離中心點越遠,地圖和現代的地理實況差異越大。越往地圖上方看,聚落的分布越稀疏、圖例越詳細,開始齣現長相奇特的怪物和模擬圖像。一隻山貓昂首跨過小亞細亞,圖例寫著:「牠可以透視牆壁,撒齣的尿液化為黑石。」挪亞方舟位於更上方的亞美尼亞,再上去是兩隻麵目猙獰的動物,在印度來迴踱步。左邊是老虎,右邊是「蠍尾獅」(manticore),長瞭「三排牙齒、人臉、黃眼、血紅膚色,獅身、蠍尾、發齣嘶嘶聲。」繼續深入亞洲,會看到金羊毛、神話中的獅鷲、人吃人的恐怖場景,還有一段圖例描寫恐怖的塞西亞人(Scythians),說他們住在山洞裡,「把敵人的頭顱製成杯子」。zui後,在地圖的左上方,也就是已知世界的盡頭,有一段圖例總結說:
「這裡有各種chao乎想像的恐怖:難耐的寒冷,強風不斷從山上吹來,當地人稱為「比索」(「bizo」)。這裡有極度野蠻的民族,吃人肉、吸人血,是該隱被詛咒的子孫。上主用亞歷山大大帝把他們關起來,因為在看得到國王的地方,發生瞭一場地震,高山倒塌在周遭的山嶽上。在高山消失的地方,亞歷山大築起一道不滅的高牆,把他們封在裡麵。」
*
這段圖例融閤瞭聖經和古典時代的「野蠻民族」的起源,也就是歌革與瑪各的部族。他們是挪亞之子雅弗的後裔,模樣醜怪,散居在已知世界zui北端。啟示錄預言當末日到來時,撒旦將從「地上四方」集結歌革與瑪各的部族攻擊耶路撒冷,然後敗下陣來(啟示錄20: 8-9)。早期基督教和古蘭經記錄亞歷山大大帝輝煌戰績的版本指齣,國王抵達高加索山脈時,用黃銅和鐵鍛造大門,阻擋歌革和瑪各號稱是伊德裏西繪製的圓形界地圖也複製瞭這道屏障。上述所有的經外傳說都認為歌革和瑪各是zui大的蠻族,在事實和隱喻上都是基督教的邊緣人,對任何一種文明都是yongjiu的威脅。
來到地圖上的亞洲右側,地圖想像齣一個同樣令人詫異而驚恐的世界。棲息在東南區域的有鱷魚、犀牛、人麵獅身獸、獨角獸、風茄怪獸(mandrakes)、半人半羊獸和一個非常不幸的人種,「一片外凸的嘴唇大到足以為臉孔遮陽」。在地圖的右上角,紅海和波斯灣以紅色的爪形切入陸地,斯裏蘭卡(被標示為「Taphana」,或是照古典資料來源標示為Taprobana)位於紅海和波斯灣的齣口,而非印度東南海岸外海。迴頭往下看,一條蝌蚪狀的河川代錶尼羅河上遊,貫穿非洲南方海岸(當時誤以為尼羅河流上遊先流經地底,然後重新銜接到尼羅河下遊,因此在地圖上的位置比較偏嚮內陸)。
尼羅河右側是拉得極長的非洲,除瞭西北岸的赫斯珀勒斯山(Mount Hesperus)以外,沿途沒有任何聚落,直到右上角(埃及南部)纔齣現幾間聖安東尼修道院。地圖上描繪的非洲完全不符閤地理實況:它weiyi的功能是說明尼羅河的源頭,並刻畫齣另一種「怪物」民族的世界;不是歌革和瑪各,而是位於地圖zui南端,和他們遙遙相對的醜怪民族。在赫斯珀勒斯山以南,地圖上齣現各種稀奇古怪的人,長相和行為都異乎尋常,首先是「乾金斯衣索比亞人」(Gangines Ethiopians),全身赤裸,拄著柺杖,互相推擠。圖例上寫著「他們沒有友誼可言」。說不上是怪物,比較像反社會分子。但再往南會看到長瞭四隻眼睛的「馬米尼衣索比亞人」(Marmini Ethiopians);一個「嘴巴和眼睛長在肩膀上」的無名種族;「嘴巴和眼睛長在胸口」的「布雷米斯人」(Blemmyes);菲利人(Phillis)會「把新生兒拿到蛇麵前,來測試妻子的貞潔」(換句話說,是殺害私生子);還有蹺腿人(Himantopods),可憐隻能「用爬的,不能用走的」。
來到現代地圖上的赤道南方,這裡的人種更加醜怪而奇特。一個紮瞭頭巾、留著大鬍子的人,身上長瞭一個女人的乳房,還有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被標示為「兼具兩性的民族,在許多方麵都違反自然」,下麵是一個無名人士,「嘴巴被封死」,隻能用麥管進食;再往下是「影腳人(Sciapodes),雖然隻有一條腿,但跑起來飛快,還可以用腳掌遮蔭;這個人種也叫作獨眼人(Monoculi)」。地圖上畫的影腳人不但隻有一條腿(腳上多瞭三根腳趾),眼睛也隻有一隻。這份怪物人種名單上的zui後一個人種在非洲東岸,「是一個沒有耳朵的人種,叫作無耳人(Ambari),兩隻腳掌互相排斥」。
這不是我們現代人所理解的地圖。這是一個由神學而非由地理學界定的世界圖像,圖上的地點是透過信仰而非位置來理解,依照聖經事件的時間行進,比地球空間的刻畫更重要。矗立在地圖正中央的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耶路撒冷,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點,生動的耶穌受難圖位於耶路撒冷正上方,聖城以圓形的城牆錶示,很像一個巨大的神學嵌齒。耶路撒冷位於地圖中心,是因為上帝在舊約聖經的以西結書說過:「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將它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國都在它的四圍。」(以西結書5: 5)伊德裏西對這個城市的描述展現瞭多層次的神話地理學,如今隻剩下純屬基督教的想像。
以神學而非地理學的角度從耶路撒冷往外探索地圖呈現的地形,我們開始看齣地圖形狀本身一個比較清楚的邏輯。亞洲布滿瞭舊約聖經的地點和場景。耶路撒冷被法蓮山(Mount Ephraim)、橄欖山和約沙法榖(Valley of Jehoshaphat)環繞;再往北是巴別塔,以及巴比倫、所多瑪和蛾摩拉等城市。右邊是約瑟的「穀倉」——中世紀對埃及金字塔的說法——和西奈山,摩西在山上領取上帝交給他的十誡。這幅地圖也編排瞭齣埃及記錯綜複雜的行路歷程,穿越死海和約旦河,然後抵達耶利哥(Jericho),沿途經過一係列的著名景點,包括變成鹽柱的羅得(Lot)之妻。
在多采多姿的地理、聖經、神話和古典學細節中,觀者不斷仰頭凝望地圖zui頂端,及其背後的神學思維。在地圖頂端,圓形邊界下麵就是伊甸園,人間樂園,是一座固若金湯的圓形島嶼,以四條河流灌溉,是亞當和夏娃的傢園,地圖上畫的是他們被逐齣伊甸園的當下。伊甸園南邊是被逐齣的這一對男女,上帝詛咒他們要在下麵的地球世界行走。在這一幕場景的正上方,脫離瞭人文時空的俗世框架,復活的基督坐在那裡主持審判日。他周邊的圖例寫著「看哪,我的見證者」,意謂被釘十字架的疤痕(他的釘痕和右胸矛刺齣的傷口)證明他就是上帝應許的彌賽亞。基督的右邊(觀者的左邊)是使靈魂從墳墓裡復活的天使,高喊「起來吧!你將得到永恆的喜樂」。基督的左邊是被詛咒的人,一個天使揮舞著燃燒的劍,喊著「起來!你們要到地獄燃起的火裡」,把他們帶到地獄之門。
在這兩幕對比強烈的場景之間,坦胸的馬利亞抬頭凝望著她的兒子。「看哪,親愛的兒,我的胸口,你從這裡得到瞭肉身,」她對他說:「你也在我的胸口尋覓聖母的乳汁。」「發發慈悲,」她苦苦哀求:「遵照你自己許的諾言——垂憐所有服侍過我的人,既然你使我成為救贖的道路。」馬利亞這番懇求恐怕是一種刻意的提醒。要我們想起路加福音裡那段對話,「眾人中間有一個女人」大聲對耶穌說:「懷你胎的和乳養你的有福瞭。」看這幅地圖的人應該很清楚耶穌的迴答:「是,卻還不如聽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路加福音11: 27-28)他們會知道,zui後的審判是根據你是否有嚴格遵守上帝之言。
聖經整個復活和審判的場景就位在mappamundizui頂端,現代讀者可能會在這裡尋找世界地圖或地圖集的注釋或說明。但赫裏福德mappamundi提供的不是文字名稱,而是基督教創世和救贖故事的視覺圖像。它描繪世界如何在上帝手中創造,又如何隨著審判日來臨而走嚮末日,以及「新天新地」的創造(啟示錄21: 1)。這是一幅宗教信仰的地圖,中心具有象徵意義,邊緣充滿瞭怪物,迥異於托勒密將近一韆年前在亞歷山卓創造的幾何學地球規劃圖,或短短一百年前在巴勒莫創造的伊德裏西世界地圖。從托勒密到赫裏福德mappamundi齣現的這段時間,基督教成為全球性宗教,也根據本身的神學形象,創造鏗鏘有力的新世界觀。赫裏福德mappamundi是這個野心勃勃的世界新圖像永恆的典範,形塑這個新圖像的不是科學,而是以信仰為主。從這幅地圖陌生的地理構造,以及在現代人眼中顯得古怪的民族誌和異乎尋常的地形,或許可以看齣古典希臘羅馬文明以後的發展,以及基督教的興起,但儘管這個宗教隻是勉強接受地理學,卻仍採用齣自公元八世紀的mappaemundi,作為未來六百年世界zui重要的圖像。
第四章 帝國
疆理圖,一四○二年
中國東北,遼東半島,一三八九年
從高麗到朝鮮王朝的過渡期間,被視為韓國歷史上的關鍵時刻,透過政治、法律、公民和官僚結構的改革,使朝鮮的文化與社會脫胎換骨。權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打造新的軍事基礎設施來統一管理領土。官僚的權力集中,並依照新儒學的信念,引進文官考試製度;土地國有化;提齣更公平的新賦稅製度;佛教幾乎全麵廢除。同時朝鮮的興起,也屬於帝國與文化地理學比較廣泛的一次重組。明朝在一三六八年建國,錶示濛古在東亞的影響力逐漸消失。在東邊,東亞另一個強權,日本,正開始統一南北朝,建立瞭一段和明朝及朝鮮的關係相對和平與繁榮的時期。
為瞭把自己謀朝篡位的舉動正當化,太宗和他的新儒學輔臣運用古代中國的「天命」(Mandate of Heaven)觀來解釋王朝興衰。隻有上天能給予統治的道德權利。對太宗而言,為瞭不負這個新天命,除瞭更換新的統治者,還要遷移到新首都。朝鮮把都城從鬆都(Songdo,現在北韓的開城〔Kaes?ng〕)遷至漢陽(Hanyang,現在南韓的首爾〔Seoul〕),建立景福宮(Ky?ngbok Palace)作為新居。新政府同時委託製作兩幅新地圖,一幅畫的是地球,一幅畫的是天空。後者被稱為「天象列次分野地圖」(Positions of the Heavenly Bodies in their Natural Order and their Allocated Celestial Fields),刻在一塊逾兩公尺高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展示於景福宮。這幅天文圖是以中國的星象圖為依據,難得的是複製瞭希臘黃道十二宮的中文名稱(中國從公元九世紀開始與穆斯林世界往來,黃道十二宮因而傳到瞭中國)。雖然有許多地方齣錯(許多星星排列錯誤),卻顯示瞭一三九○年代初期,太宗和他的天文學傢所看到的天象位置。這張地圖代錶瞭新王朝對天空的新想像,藉此對朝鮮王國賦予天定的正當性。
到瞭一三九五年,太宗手下的天文學傢完成瞭這幅星象圖,而率領這班天文學傢的權近(Kw?n K?n,1352-1409)是一位新儒學的改革者,官拜議政府贊成事,是朝鮮新政權zui高品階職務。權近當時已經著手製作另一幅地圖,這一次囊括整個世界,於公元一四○二年繪製完成。原版的地圖沒有流傳下來,但有三份摹繪本,目前都收藏在日本。京都龍榖大學圖書館(Ryūkoku University Library)收藏的摹繪本zui近被鑑定是一四七○年代末期或一四八○年代的產物,是公認zui早、也保存得zui好的版本,其中還包括權近所寫的跋。名稱叫《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Honil kangni y?ktae kukto chi to),多半被簡稱為疆理圖(Kangnido map)。是東亞現存zui早的世界地圖,比中國和日本的世界地圖更早,是李氏朝鮮zui早的製圖學呈現,也是zui早把歐洲畫齣來的亞洲地圖。
疆理圖以鮮豔彩墨繪於絲絹而成,做工精巧,富麗堂皇。大海是橄欖綠色,河水是藍色。山脈標示成鋸齒狀的黑線,比較小的島嶼畫成圓圈。大地豐潤的土黃色把這些地物襯托得更加鮮明。地圖來來迴迴寫滿瞭黑色的中文字,明確指齣各個城市、山嶽、河川和重要的行政中心,長寬各為一百六十四與一百七十一公分,原本用一根棍棒繫著,可以從上往下展開,大概和星象圖一樣,是為瞭掛在屏風或牆壁上而設計,展示在像景福宮這種備受矚目的地點。就像星象圖使朝鮮王朝座落在新的天空下,疆理圖也讓李氏朝鮮在地球的新繪圖上有瞭位置。
我們在第三章談過,基督教的地圖以東方為上,許多伊斯蘭地圖以南方為尊,疆理圖則是以北為上。世界是一片綿延不絕的大陸,沒有一塊塊分離的陸地或環繞周邊的海洋。地圖是長方形,加上正上方以陸地為主,似乎呈現齣一個扁平的地球。位於正中央的不是韓國,而是中國,一片鐘擺形的遼闊大陸,從印度西岸延伸到中國東海。事實上,中國在地圖上非常搶眼,印度次大陸彷彿被吞噬瞭,看不齣西岸在哪裡,而印尼群島和菲律賓群島縮小成一連串圓形的小島,沿著地圖zui下方顛簸前進。中國無遠弗屆的政治和知識影響力,也可以從地圖頂端的題字看齣來,題字下方羅列齣中國歷代都城,緊接著描述當時中國的省、縣,以及往來各省縣的路線。
中國的東邊是地圖上麵積僅次於中國的大陸,韓國,周邊彷彿被一大串小島包圍;這些其實是海軍基地。乍看之下,製圖者對其祖國的描繪,跟韓國現在的輪廓大同小異,尤其是和伊德裏西所描繪的西西裏,或甚至哈丁漢的理查所畫的英格蘭一比,更顯得極為相似。雖然北邊的疆界平扁無奇,地圖卻把韓國畫得格外詳細。標示齣四百二十五個地點,包括二百九十七個縣、三十八個海軍基地、二十四座山、六個省會,朝鮮的新都漢陽以鋸齒狀的紅色圓圈標示,十分醒目。
漂浮在地圖右下角的是東亞另一個主要強權,日本,畫在實際位置的遠西南方。叉狀的尖端指嚮中國與韓國,頗具威脅意味。為瞭抵銷這種明顯的威脅感,故意把日本相對於韓國的麵積縮小,地圖上的韓國是實際麵積的三倍,而且日本又比實際上的麵積少瞭一半。日本zui西端的島嶼九州(Kyushu),在地圖上指嚮北方,把群島實際的位置順時針轉瞭九十度。
更讓現代人跌破眼鏡的,是地圖如何描繪中國以西的世界。偌大的斯裏蘭卡位於中國西岸(而非印度東南岸)外海,但楔形的阿拉伯半島很容易認齣來,紅海及非洲西岸也很鮮明。在葡萄牙航海探險首度發現可以環航非洲之前八十幾年,疆理圖就畫齣瞭非洲,包含現在世人很熟悉的非洲南端,儘管整體的麵積被嚴重低估(非洲大陸比現代的中國大瞭三倍以上)。另一個古怪的地方是非洲大陸正中央好像有一片大湖,雖然這也可能代錶撒哈拉沙漠。地圖在非洲、歐洲和中東標示的許多地點,是把阿拉伯語地名翻譯成中文,顯示在這個相對早期的階段,伊斯蘭製圖涵蓋的範圍已經非常廣泛(伊德裏西的地理學知識所及zui遠的地方是韓國)。
刻畫在非洲上方的歐洲同樣令人好奇。地中海(雖然不像地圖上其他的海洋畫成綠色,令人有些混淆)的形狀畫得簡單卻容易辨認,伊比利半島也一樣。亞歷山卓畫得像一座寶塔。有一個首都被標示成紅色,可能是君士坦丁堡,歐洲的輪廓包含大約一百個地名,多半仍舊沒有可信的翻譯。連德國都齣現在地圖上,根據語音拼成A-lei-man-i-a。地圖zui邊緣有一個很小的長方形,好像是不列顛群島,不過更像是亞速爾群島,也就是《地理學》裡的世界zui西端,可能是因為托勒密的觀念有一部分傳到瞭中國,纔會被複製在疆理圖上。
疆理圖對非洲和歐洲地名與形狀的知識,很可能傳承自托勒密,不過他的影響力僅及於此。疆理圖上看不齣明顯的經緯網格、比例尺或明確的方位;可想而知,疆理圖對南亞地區提供瞭較為詳細的視角,而托勒密的座標在這裡漸漸淪為臆測性的地理學,同時也看不到他的地名。像赫裏福德或西西裏製作的那些中世紀基督教和伊斯蘭地圖,都繼承瞭希臘的文化傳統,相形之下,疆理圖秉承的是截然不同的製圖學傳統,根植於韓國和作為基礎的中國,對於地球在更浩瀚的宇宙中的地位有怎樣的識覺。
希臘羅馬世界的社會與文化傳承各不相同,產生瞭各種互相衝突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世界,前現代的東亞則不然,廣義地說,這個區域是由一個大帝國塑造而成:中國。韆百年來,中國自視為是正當帝國quanwei的中心,無庸置疑,作為中國的統治者,皇帝自視為文明世界(也就是天下,「普天之下」)的領袖。像韓國這樣的衛星王國隻是中國大局勢中的一個小角色;不在中國勢力範圍內的民族被當作無關緊要的蠻族,根本不值一提。治理一個廣大而相對疆界分明的帝國,必須由歷史上zui先進的前現代官僚體係來創造和管理。維繫遼闊(而且不斷變化)的帝國邊界耗資甚巨,加上知識界堅信中國天生在政治上至高無上,在地理上居於中心,因此,不同於中世紀末期的歐洲,中國對世界其他地方興趣缺缺。中國人的信仰以佛教和儒傢傳統為基礎,迥異於西方在希臘羅馬世界衰亡後發展齣來的基督教和穆斯林的經書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作為普世的宗教,相信自己肩負神聖的責任,要把他們的宗教宣揚到世界各地,佛教和儒傢則完全沒有這種觀念。這樣形成的製圖傳統著重於確立邊界和維繫帝國的實務作業,官僚菁英研究這些問題,要比西方的宗教社會早得多。中國的製圖傳統不曾試圖以某個宗教或意識型態之名,把想像齣來的地理學投射到中國邊界以外的地方,也無意鼓勵或促成遠至印度洋以外的長途旅行和海權擴張(明朝在一四三○年代就把船隊召迴,從此不再到海外探險)。中國怎麼做,韓國就怎麼跟。韓國早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年,在這段期間,韓國往往是帝製中國的附庸國,韓國的製圖者差不多都想為王國的統治菁英提供實用的地圖,以達成政治統治的行政管理。疆理圖的目的也一樣,但背後有一個非常獨特的觀點。地圖的製作務必要符閤朝鮮半島鮮明的自然地理,以及符閤韓國與疆域更大、勢力高高在上的鄰國之間的關係。
*
地圖大多會呈現圖像與文字的交互作用,疆理圖也不例外,地圖下方有洋洋灑灑的四十八行圖例,齣自權近筆下:
天下至廣也,內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幾韆萬裏也。約而圖之於數尺之幅,其緻詳難矣。故為圖者皆率略。惟吳門李澤民《聲教廣被圖》,頗為詳備;而歷代帝王國都沿革,則天颱僧清濬《混一疆理圖》備載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右政丞丹陽李公燮理之暇,參究是圖,命檢校李薈,更加詳校,閤為一圖。其遼水以東,及本國之圖,澤民之圖,亦多缺略。今特增廣本國地圖,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圖。井然可觀,誠可不齣戶而知天下也。夫觀圖籍而知地域之邇遐﹐亦為治之一助也。二公所以拳拳於此圖者,其規模局量之大可知矣。
權近的跋文似乎和伊德裏西處理《娛樂》的手法有些相似:基本上不確定已知世界的大小和形狀;為瞭製作比較全麵性的地圖,必須藉用既有的地理學傳統(伊德裏西藉用瞭希臘和伊斯蘭傳統,權近則採用中國的傳統);關鍵在於對一批專傢提供政治和行政贊助;zui後產生令人驚奇和喜悅的成果。
跋文裡提齣的兩個彼此相關的元素,提供瞭理解這幅地圖的一個方法:首先是當時地圖創作的政治背景,其次是中國製圖術的影響。金士衡(Kim Sahyong, 1341-1407)和李茂(Yi Mu,卒於1409年)屬於朝鮮王朝新儒學輔臣的核心成員。一四○二年,就在疆理圖製作前幾個月,兩人雙雙參與韓國北疆的土地測量,然後聯袂齣使中國;金士衡一三九九年前往中國時,取得瞭權近提過的中國地圖。權近記載疆理圖在一四○二年成圖,但寫的不是朝鮮王朝的年號,而是鄰國中國的年號建文。建文帝硃允炆(統治期一三九八-一四○二年)是明朝第二任皇帝,也是明太祖洪武帝硃元璋(統治期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的孫子。佛教高僧兼製圖師清濬被洪武皇帝召為左覺義,負責監督一三七二年在南京舉行的法會,為新政權取得正當性。清濬《混一疆理圖》一份十五世紀的摹繪本顯示,上麵描述瞭中國早期各朝代的地理與歷史,據權近指齣,李薈(Yi Hoe)東邊「增廣」瞭韓國,西邊增繪瞭阿拉伯半島、非洲和歐洲。李薈(1354-1409)是高麗政權的高官。後為朝鮮太宗流放,一四○二年返迴都城,繪製朝鮮王朝的地圖,到瞭著手籌畫疆理圖時,他已在李氏朝鮮擔任檢詳官(k?msang)(可能是看中他繪製地圖的長纔)。
繼洪武皇帝登基的硃允炆被叔父燕王硃棣推翻,經過兩年的血腥內戰,硃棣自立為永樂皇帝。 待疆理圖完成時,硃允炆已死。儘管明白使用明朝而非朝鮮的年號,當權近指齣必須校正中國製圖師李澤民「遼水以東」的韓國地圖的缺略時,他點齣瞭兩國近代爭議中zui具軍事敏感性的地區。除此之外,他weiyi的地理觀察是疆理圖上增加瞭日本,另一個在歷史上不斷為韓國帶來麻煩的強大鄰國。這幅地圖顯然企圖在十五世紀初變動不定的東亞政治世界中,為新成立的朝鮮王國取得一席之地。
無論權近的跋文喚起瞭中國與韓國之間多少區域朝代政治的變遷,既然明白錶示這幅地圖的繪製是以中國製圖術為基礎,他對中國地圖製作的仰慕是無庸置疑的。李澤民和清濬的地圖都是在十四世紀上半葉繪製,但中國對韓國政治和地理學的影響力可以迴溯到更早之前。自從公元前四世紀初,韓國成為獨立王國以來,麵對在疆域與國力上更勝一籌的鄰國的文明,歷朝君主與學者都想從中尋找治國之道、科學與文化上的啟發。這絕對不是一種全然被動的關係。一方麵,韓國不斷主張在政治上脫離中國而獨立,另一方麵,隻要情勢有利,就大膽挪用中國的文化成就。
作者資料
傑瑞.波頓(Jerry Brotton)
歷史學傢,倫敦瑪莉皇後大學文藝復興研究教授,也是研究地圖歷史和文藝復興製圖領域的重要專傢學者,他的著作《The Sale of the Late King’s Goods》是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和西塞爾提爾曼獎(Hessell-Tiltman History Prize)的決選之作。在2010年,更被英國BBC第四頻道邀請主持係列節目《地圖:權力、掠奪與占有》(Maps: Power, Plunder and Possession)。
基本資料
作者:傑瑞.波頓(Jerry Brotton)
譯者:楊惠君
齣版社:馬可孛羅
齣版日期:2015-01-06
ISBN:9789865722364
規格:平裝 / 部分彩色 / 480頁 / 16.8cm×23cm
用户评价
這本書簡直是一場思想的馬拉鬆,帶領讀者穿越瞭人類文明的漫長圖景,那種宏大的敘事結構和細膩的局部描摹結閤得天衣無縫。作者並沒有局限於傳統的編年史敘述,而是巧妙地利用瞭“地圖”這一獨特的媒介,將空間、權力和思想的演變緊密地編織在一起。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不同文明間互動模式的解析,尤其是那些在教科書上常常被輕描淡寫但實際上卻深刻影響瞭世界走嚮的關鍵節點。比如,書中對中世紀伊斯蘭黃金時代在知識傳播中所扮演角色的論述,就顛覆瞭我過去那種僅將目光聚焦於西歐的狹隘視角。讀完後,感覺自己像是站在一個高聳的瞭望塔上,俯瞰著曆史的河流如何蜿蜒麯摺,匯入今日的海洋。那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不僅僅是對知識的獲取,更是一種看待世界復雜性的新框架的建立。它迫使你跳齣既有的文化偏見,去理解為何某些地理位置會成為權力的中心,而另一些則逐漸沉寂。這種跨學科的融閤,讓曆史不再是枯燥的年代堆砌,而是一幅活生生的、不斷變動的權力、信仰與地理相互作用的動態畫捲。
评分這本書在敘事節奏和信息密度上達到瞭一個極高的平衡點。雖然主題宏大,涉及數韆年曆史和數個大洲,但作者總能找到那個精確的角度切入,讓讀者不至於迷失在信息的洪流中。對我個人而言,它在解釋“權力轉移”的機製方麵,提供瞭極具啓發性的框架。權力不是憑空齣現的,它依附於特定的地理優勢、技術壟斷,以及最關鍵的——對知識和敘事的控製。書中對宗教地圖和政治地圖的疊加分析尤其引人入勝,它展示瞭信仰的疆界是如何與帝國的邊界相互滲透、相互定義的。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仿佛獲得瞭一套新的“導航係統”,不再滿足於錶麵的曆史事件,而是開始探究事件背後的地理製約、資源博弈和思想的底層邏輯。這絕對是一本值得反復翻閱,每次都能帶來新發現的深度曆史著作。
评分這本書最令人稱奇的地方,在於它對於“視角”的操控藝術。它不像一般的通史那樣企圖麵麵俱到,而是聚焦於那些能夠清晰勾勒齣世界格局變遷的關鍵“圖景”。每一次切換地圖,都像是一次視角焦距的調整,從宏觀的帝國擴張疆域,迅速拉近到貿易路綫上某個關鍵港口的社會生態。特彆是關於“氣候變化”與“文明興衰”之間隱秘關聯的探討,極其發人深省。作者沒有采取宿命論的解釋,而是展示瞭環境壓力如何巧妙地被政治決策和技術創新所放大或緩解。閱讀過程中,我數次停下來反復揣摩那些關於資源分配和地緣政治的章節,它們提供的分析工具遠超齣瞭曆史學的範疇,更像是現代地緣戰略學的精妙注解。對於我這種一直好奇“為什麼是這裏而非彆處”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瞭一個極其令人信服且邏輯嚴密的解釋體係,它將曆史的偶然性與結構性力量平衡得恰到好處,讓人在閤上書本後,仍能感受到曆史的呼吸和脈動。
评分坦白說,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充滿挑戰性的,但這種挑戰恰恰是它價值所在。它要求讀者具備一定的曆史和地理基礎,因為它毫不避諱地深入探討瞭復雜的條約、宗教教義的細微差彆,以及技術革新背後的社會動員能力。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民族主義”這一現代性核心議題時的剋製與深刻。他沒有將民族主義簡單地描繪成一種壓倒一切的意識形態,而是將其置於特定的曆史地理環境中,剖析它是如何被印刷術、鐵路網絡和新的教育體係所塑造和傳播的。這種細膩的解構,讓我對許多自認為早已理解透徹的概念産生瞭新的認識。可以說,這本書不是那種可以輕鬆消遣的讀物,它更像是一次嚴謹的智力探險,需要讀者全身心地投入,去梳理那些交織在一起的綫索——科學的突破如何催生瞭帝國的野心,而帝國的傾覆又如何為新的貿易路綫和思想傳播打開瞭空間。
评分如果說有什麼書能夠真正地改變一個人觀察世界的方式,那麼這本絕對榜上有名。它最大的貢獻在於揭示瞭“互聯性”的深度。我們常常習慣於將曆史割裂成歐洲史、亞洲史或美洲史,但這本書的核心論點似乎是通過“地圖”這個媒介,不斷地提醒我們:沒有哪個文明是孤立存在的。無論是絲綢之路上的貨物交換,還是大航海時代瘟疫的傳播,都清晰地錶明,人類曆史的每一次重大轉摺,都是一次全球性的、即便當時的人們尚未完全意識到的係統性重組。作者對於“全球化”的溯源尤其精彩,他沒有將全球化僅僅視為近現代的産物,而是追溯到早期航海技術和跨區域信仰體係建立的階段。這種遠古的視角,極大地拓寬瞭我對“現代性”起源的理解,也讓我對當前世界麵臨的挑戰,如供應鏈中斷或文化衝突,有瞭更深層次的同理心和洞察力。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