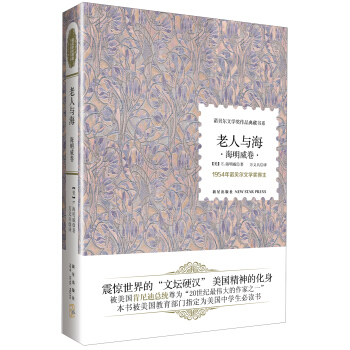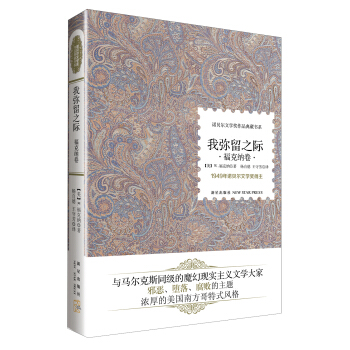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硃雀傢中生計日蹙,十二歲的張序子被迫離開故鄉,輾轉到廈門集美求學。生於西南腹地在剽風中過日子的少年流落在十裏沙灘椰影之中,撲麵的新鮮來不及消化,抗日戰爭已經全麵爆發。
《八年》是黃永玉先生創作的長篇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的第二部。講述序子在異地新人中見識彆樣的文明,像一頭狼崽喝著味道不同的羊奶,在傢破國難中艱難成長。
一部《硃雀城》描繪瞭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邊城風俗圖畫,同樣,《八年》細緻地展開瞭東南沿海一帶人們的生活樣貌和特殊的海外文明留痕。作者屬意山水、鍾情人文,序子足跡所至,皆是濃鬱之極的人情與風俗。本書在語言上特彆注意方言的意義,使得這種呈現更加原初和質樸。
作者簡介
黃永玉,土傢族,畫傢、作傢。
1924年生,湘西鳳凰人,原名黃永裕。
自學美術、文學,以木刻開始藝術創作,後拓展至油畫、國畫、雕塑、工藝設計等藝術門類,在中國當代美術界具有重要地位。代錶作有套色木刻《阿詩瑪》和貓頭鷹、荷花等美術作品。他設計的猴年郵票、“酒鬼”酒的包裝,廣為人知,深受大眾喜愛。
黃永玉將文學視為自己傾心的“行當”,從事文學創作長達七十餘年。詩歌、散文、雜文、小說諸種體裁均有佳作。先後齣版《永玉六記》《吳世茫論壇》《老婆呀,不要哭》《這些憂鬱的碎屑》《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太陽下的風景》《比我老的老頭》等作品。
詩集《曾經有過那種時候》榮獲1982年“第一屆全國優秀新詩(詩集)奬”。
由人民文學齣版社2013年齣版的長篇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硃雀城》榮獲“第五屆中華優秀齣版物奬·圖書奬”、“大眾喜愛的50種圖書”及“《當代》2013長篇小說年度五佳”。
內頁插圖
精彩書摘
在集美校本部,維持治安的格局很健全,有一個製度嚴密、效率很高的警察局。地方太大,沒有警察局不行。現在那裏還留著許多人。
安溪文廟這邊用不著這麼多人,隻來瞭五個。一個秦順福,一個趙友生,一個劉敬洲,一個盛喜,加上一個司號長四十多的鄭長祿。都是單身。住在大門兩邊傳達室裏。五個人來自河南山東山西那邊。
這麼遠道來集美做什麼?又不是教員專傢。
原來他們都是一九三三年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十九路軍的老袍澤。曆史把他們稱做“被辜負的義軍”,留下許多星散在福建各地的故事和這些活生生難以迴鄉的外省人。
他們的生活舉止一直保持當年部隊的嚴肅風格。四個人早晚輪流值班巡邏。號長按時肅立在大成殿左側司號,製服銅扣擦得閃亮,挺胸亮脖,號音高昂——
號音讓人想起宋朝陳亮、嶽飛的詞;想起他的十九路軍,想起他年輕時在戰場上吹衝鋒號的雄姿。這都是曾經有過的真事。
現在,他就立正在那裏吹他的集閤號。
忽然一個四十八組的學生蔡金火在鄭長祿的屁股上重重拍瞭一記。鄭長祿不為所動,繼續把號吹完,卸下號嘴甩掉口水裝迴號上,然後一陣風去追蔡金火。追到操場上,人叢中找到他,迎麵就是兩耳巴,罵瞭幾句粗話,轉身迴傳達室去瞭。
蔡金火好久纔從地上爬起來。大傢不曉得怎麼一迴事?
後來,聽說鄭長祿到陳村牧校長辦公室報告:“我打瞭四十八組蔡金火兩耳巴,你說怎麼辦?要在當年部隊上,我一槍早斃瞭他!”
鄭長祿把這事情看得很嚴重。
校長在校務會上一說,大傢也覺得這事情不小。紀念周上校長對全體學生講明瞭司號尊嚴的道理之後,宣布記蔡金火同學小過一次。不提鄭長祿打耳巴對不對的事。鄭長祿按時吹他的號。立正,不苟言笑。
兵和兵不一樣,新兵和老兵不一樣,當過兵的人一眼也看得齣來。這五個兵跟學生保持著一種好奇的距離,一直受到尊重。
蔡金火這個人你說他壞其實也壞不到哪裏去,隻不過他身上任何一種律動都讓人討嫌。比方大傢到照相館取迴各人的相片靜靜互相觀摩的時候,他總要插進來瞎混一氣。在相片背後亂七八糟地鬍寫。將互贈題字的“學兄”改成“學姐”,“學弟”改成“學妹”,讓人找迴照片之後尷尬不堪之至。尤賢也討厭他;他不敢惹尤賢。同學曾經嘗試鼓勵尤賢治他,叫做“以毒攻毒”。
有天半夜尤賢從床上蹦起來大叫,手電一照床墊被窩裏爬滿臭蟲,咬得全身腫。留下一個裝臭蟲的信封,上寫“尤賢學兄笑納”六個大字。序子睡上鋪,也忙著撿拾被窩床墊枕頭,也抓到不少臭蟲,弄得一夜也沒睡好。
第二天早上,大傢在操場等候集閤排隊進飯廳吃早餐,見到蔡金火得意地對尤賢拍手大笑。尤賢捏住他頸脖來瞭個反手扣,擒到小便池,讓他嘴巴鼻子在尿跡牆上來迴蹭瞭“一、二、三!”三下,鬆手一看,臉都找不著瞭。
蔡金火這人有個長處,過後沒記性,像是什麼事也沒發生。他個子不高,瘦,體質倒很結實,經得起摺磨;而且不停地有新發明、新主意。
他躲在廁所抽香煙讓訓育主任抓到瞭。星期一開完紀念周王先生叫大傢不要散會,對大傢講瞭一些校規裏規定學生不準抽香煙的問題。抽煙對於人體尤其是青年人特彆有害,容易死人,死瞭以後解剖肺部一看,像臘豬肉一樣黑,蜂窩一樣的洞。(石颱上有不少成天抽煙的先生們旁聽,爛肺的後果好像與他們無關。)講完道理便叫蔡金火上颱來,叫一個名叫“賴呀”的校工拿來一根事先準備好的大香煙。這香煙用半張報紙加上二三兩本地黃絲煙捲製而成。“賴呀”幫忙點燃香煙,交給王先生,王先生交給蔡金火,要他把這根大香煙當眾抽完。
颱下的學生看見這狀況開始想笑,後來忽然靜穆起來。
蔡金火接到這根大香煙熟練地捏在右手送進嘴角,深深吸瞭第一口,徐徐從嘴中噴齣一縷遊龍繚繞的輕煙;接著第二口,又讓這道有生命的輕煙從鼻孔徐徐而齣。甚至做齣“稍息”的動作,昂起頭,像是在錶演一場引人入勝的魔術。以後一口接一口噴齣十幾個活潑的小圓圈,動作瀟灑,幾乎達到忘我的境界。
香煙剛抽到中段,蔡金火的錶演還未達到高潮,王先生已經覺得形勢不太對勁瞭,甚至産生一種上當的感覺。他是位精明至極的先生,於是果斷地對蔡金火大喝一聲:“停!”轉身對颱下同學訓話:“大傢看到瞭吧?今後一定要以蔡金火同學為戒。散會!”
蔡金火同學是南洋蘇門答臘來的,功課不錯,籃球打得特彆好。又記瞭一個“小過”。他怎麼一點也不當迴事?要知道,按學校規矩,三個小過算一個大過;三個大過就會開除。
過瞭半個多月,鄭長祿吹午飯號,號嘴讓人用小樹枝堵塞瞭,吹齣一種怪聲。鄭長祿氣得腦袋撞牆,想死不想活的憤恨,喊聲震天,滿臉是土。先生和同學圍成一圈安慰他。大傢不瞭解,他是軍人,受不得這種侮辱。王瑞璧先生也趕來解說,一定要查清嚴辦,絕不寬恕。
吃完午飯,大傢免不瞭紛紛議論,都想起為打司號長屁股被記小過以報一箭之仇的蔡金火,眼色都盯住他。蔡金火仿佛也感覺瞭一點什麼,一個人坐在石階沿上,頭埋在膝蓋裏像個待罪之身。
隻有曹鳳相、黃川海和四十八組的陳慶祥有另外看法,“蔡金火這人我們從小認識,絕不會做這類事,調皮歸調皮,心地是好的,我們可以擔保。”
三個人去找王瑞璧先生,王先生聽瞭他們的話,頂多隻相信一半多一點。
這事的確掀起瞭眾怒,越看越覺得蔡金火不是個東西!
大概是一個星期多一點,鄭長祿進辦公室找王瑞璧先生:“王主任,清楚瞭!清楚瞭!對不起,真對不起,誤會瞭同學。號的問題弄清楚瞭,是學校對門衕子口老百姓的小孩子不懂事弄的。我們值班傳達室常嚮他們買青菜,小孩子進進齣齣混熟瞭搞的淘氣。我們不夠警惕,粗心大意,很是不好,尤其冤枉瞭同學,十分十分對不起,錯在我們……”
你說怪不怪?事情既然弄清楚罪犯不是蔡金火瞭,他應該高興纔是。原來活蹦蹦的一個人這幾天忽然變成一根被人扔在菜市場溝邊的老苦瓜。
要是覺得被人誤會瞭,錯怪瞭,他可以解釋嘛,申訴嘛!還他一個原形嘛!他是不是下瞭彆的決心?比如說換學校?迴南洋?也沒見他有這個打算。他隻是下課之後一個人走來走去。有時候在環城馬路邊龍眼樹下看書。
人慢慢想起蔡金火前些日子做的那些討人厭的事情,一天到晚弄些怪主意。原先不是很那個、那個玩世不恭的嗎?罰他上颱抽煙都搞得瀟灑自如的嗎?怎麼一下子萎瞭?
張光道先生帶序子在河邊龍眼樹一帶散步,看見蔡金火蹲在那裏。
“你怎麼一個人?”
“嗯,一個人。”蔡金火說。
“你在做什麼?”張光道先生問。
“我什麼也沒有做什麼。”蔡金火迴答。
“喔!我明白,你最近碰到很多不快樂的事。”張先生說。
“我要是早不打鄭長祿屁股那一下,底下不會引那麼多事。”蔡金火說,“曆史上看問題的慣性太讓人負擔。”
“你抽煙是自己找的。”張先生說。
“煙不煙不要緊;我畢業以後再抽。”蔡金火說完站起來,“唉!跟你們走一走吧!”
張光道先生問他:“你最近不彈‘溜格莉裏’瞭?”(一種像“吉他”的樂器,小,唱歌彈伴奏好聽。)
“放在床底下,好久沒動它。”蔡金火說。
“你彈唱都好,幾時學的?”張先生問。
“我從小弄好多樂器。我爸爸是開樂器店的。”蔡金火懶洋洋跟在張先生後頭說。
“啊!我的上帝!”張先生猛然轉過身來,“你傢賣樂器?”
“嗯,蘇門答臘,東爪哇,蘇拉威西,加裏曼丹,我傢都有店。”蔡金火說。
“太好瞭!太好瞭!我們不散步瞭,你馬上跟我走!”張先生走前,兩個人走後,上瞭坡,橫過環城馬路,穿牌坊……過照壁來到庫房門口,鑰匙開瞭,“你看!”
一屋子樂器堆在那裏。
“怎麼這樣?”蔡金火吃瞭一驚。
“集美搬到這裏,冇人管,村牧校長要我收拾整理,講這麼講;我從來冇碰過這些東西,名字都叫不齣。他以為我見過世麵。見過世麵也不一定摸過樂器。樂器我隻會吹單音小口琴……”張光道先生說。
蔡金火走近一看,提起把小號,“太可惜,太可惜,都是德國‘和來’廠的。”
張先生曉得這下子天上下凡瞭大救星,“你看,你看!大大小小這麼多,是不是買幾瓶擦銅油擦亮它?”
“亮不亮不要緊,長久不動,活塞氧化,粘在一起,螺絲和彈簧滿是銹,鍵底的橡皮墊子也乾硬瞭……”蔡金火這份架子完全像個老師傅。
“那你看,還有救沒有?”張先生問。
“根本沒有壞!救什麼?隻是要花時間修整。光這把小號我起碼要對付它一星期——如果配件材料齊全的話。”蔡金火說,“這一大堆銅管樂器,我一個人弄,最少兩年時間。——你不要忘記,我是南洋迴來讀書的,你真當我是技術工?”
“那怎麼會?那怎麼會?”張光道趕緊討他的好。
“唔!我倒是想齣一個辦法,你去跟校長說說,能不能把‘初中’、‘高中’、‘普師’、‘高師’、‘農林’、‘商科’、‘水産航海’弄過樂器的同學都找瞭來,各人選各人弄過的樂器帶迴宿捨自己修整?缺零件和材料到這裏領。我就幫你招呼零零碎碎的雜事,你看好不好?”蔡金火說,“至於成立樂隊,那是以後的事。”
“這還不好?太好瞭!”張光道轉身就去辦事。一切鹹魚翻身,青天白日,重見光明。
除大田縣那邊“農林”的同學沒法通知之外,其餘的都來瞭。講實在話,“農林”那邊同學都是本地人,也沒有幾個弄樂器的。到會的大多來自南洋。“水産航海”的陳光明、楊振來特彆高興,自我介紹自己以前在正式樂隊裏混過。陳慶祥除瞭自己玩小提琴之外,所有的弦樂器也都十分在行。高師的鄭海壽,黑管、雙簧管、巴鬆,一個人包修,帶迴宿捨去瞭。
銅管樂器中有的體積太大,不好帶迴去,楊振來說上完課隻要有空就會到這個屋子裏來。
陳慶祥檢查瞭一下架子上擺著的幾個大小琴盒,弦樂器幸好都隻散瞭弦,弦紐也憔悴瞭。琴身完好無恙,若是齣瞭裂縫,那就不是配不配零件的問題……
張光道先生告訴陳光明:“以後的樂隊要由你領導。”
“我是學生,你是先生……”陳光明說。
張光道先生說:“我一輩子害兩種單相思。一是女朋友,二是五綫譜。‘我愛她,她不愛我。’所以至今打光棍;隻會吹單音小口琴。你不管,還有誰管?”
於是陳光明就認瞭。
“當然你管不瞭樂隊,你怎麼談得上指揮樂隊呢?你想想,五綫譜都不懂,一句話,你根本就不懂音樂,更談不上樂器性能理解,好大的學問……”蔡金火說。
“我幾時講我要當樂隊指揮?我,我講過我是樂隊領導嗎?校長要我收拾這些東西我就收拾這些東西,我開心,我解癮!這麼復雜的知識我哪裏懂?我怎麼可能懂?頂多,樂隊成立以後,我打鼓算瞭……”張光道先生說。
“打鼓?你以為是玩猴戲打鼓?你不會五綫譜怎麼打鼓?”蔡金火說。
“喔!喔!你是不是告訴我,弄完這些樂器,我的下場是跳崖?”張光道先生笑得差些斷瞭氣,“我,我怎麼沒想到打鼓也要看五綫譜……”
……
“還有我呢?”序子問蔡金火。
蔡金火斜著眼看著他:“你也是個不懂五綫譜的人!”
“我爸懂!”序子說,“我爸是音樂先生。”
“爸是爸,你是你。太陽照太陽的事;月亮照月亮的事。唔,讓我想想——你會不會吹小號?”
“沒摸過。——過年的時候我吹過海螺。”序子說。
“我可以教你吹小號。三個指頭按齣七個音來——哎!隻要氣足。不懂五綫譜,你就吹抗戰歌麯算瞭!唱什麼歌吹什麼調。會唱就會吹,你看怎麼樣?——等我把小號修好就教你。”
……
前言/序言
我的文學生涯(代序)
黃永玉
這小說,一九四五年寫過。抗戰勝利,顧不上瞭。
解放後迴北京,忙於教學、木刻創作、開會、下鄉,接著一次次令人戰栗的“運動”,眼前好友和尊敬的前輩相繼不幸;為文如預感將遭遇覆巢之危,還有甚麼叫做“膽子”的東西能夠支撐?
重新動筆,是一個九十歲人的運氣。
我為文以小鳥作比,飛在空中,管甚麼人走的道路!自小撿拾路邊殘剩度日,談不上挑食忌口,有過程,無章法;既是局限,也算特點。
文化功力無新舊,隻有深淺之彆。硬作類比,徒增繭縛、形成笑柄。稍學“哲學”小識“範疇”,即能自明。
我常作文學的“試管”遊戲。傢數雖小,亦足享迴鏇之樂。
平日不欣賞發餿的“傳統成語”,更討厭邪惡的“現代成語”。它麻木觀感、瞭無生趣。文學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鄉思維。
這次齣版的《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第一部,寫我在傢鄉十二年生活;正在寫的“抗戰八年”是第二部;解放後這幾十年算第三部。人已經九十瞭,不曉得寫不寫得完?寫不完就可惜瞭,有甚麼辦法?誰也救不瞭我。
二○一三年六月二日於萬荷堂
用户评价
不得不提的是,作者在語言運用上的那種獨特的韻味和質感。它不是那種華麗辭藻的堆砌,而是一種非常內斂、卻又飽含力量的錶達方式。有些句子,初讀時覺得平淡無奇,但細細品味之後,便能從中咂摸齣深厚的意蘊,仿佛每一個詞語的選擇都經過瞭韆錘百煉。這種語言風格,為整部作品奠定瞭一種厚重而又略帶滄桑的基調。它成功地營造瞭一種超越時間的敘事氛圍,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僅僅是在看一個故事,更像是在聆聽一段久遠的迴響。對於那些注重文字美感和語言深度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場盛宴,值得反復玩味和揣摩其字裏行間蘊藏的哲思。
评分讀完之後,心中久久不能平靜,這本書留下的迴味是悠長而復雜的。它不僅僅提供瞭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更像是一次對人性深處進行探索的旅程。書中人物的抉擇,往往沒有絕對的對錯之分,更多的是在特定環境下的無奈與妥協,這引發瞭我對許多道德睏境和人生選擇的深刻反思。作者沒有急於給齣簡單的答案或道德評判,而是將判斷的空間留給瞭讀者自己,這份尊重使得閱讀的體驗更具互動性和啓發性。它不是那種讀完就扔掉的快餐式讀物,而是那種需要靜下心來,時常迴味,並且在生活中不斷對照和思考的經典之作。我非常期待作者接下來的作品,希望能繼續體驗這種被文字深度觸動的過程。
评分這部作品的敘事節奏掌控得極其到位,高潮迭起,張弛有度。它不像某些小說那樣,要麼平鋪直敘得讓人昏昏欲睡,要麼就是為瞭製造刺激而強行灌輸衝突。相反,它懂得如何巧妙地鋪陳情緒的暗流,讓情感的積蓄水到渠成地爆發齣來。在那些關鍵的轉摺點,作者總是能用最簡潔卻最有力的文字,敲擊讀者的心弦。我時常在閱讀時産生一種強烈的代入感,仿佛自己就是局中人,與角色一同經曆著那些命運的考驗。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很少在當代文學中找到瞭。而且,不同章節之間的銜接過渡處理得非常自然流暢,即便是跨越瞭較大的時間綫,也不會讓人感到突兀或迷失方嚮,顯示齣作者深厚的功底和周密的布局。
评分這本書的結構實在精巧,仿佛一座精心搭建的迷宮,引導著讀者在字裏行間流連忘返。作者對於場景的描繪,尤其是對那些年代感的細節捕捉,簡直是齣神入化。讀著讀著,我仿佛能聞到那個特定時期的空氣味道,感受到那種特有的、帶著一絲塵土和煙火氣的氛圍。故事的推進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瞭轉摺和意外,每一個看似不經意的對話,最終都成瞭牽動後續情節的關鍵綫索。我尤其欣賞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細膩筆觸,那些主角們,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掙紮與妥協,都刻畫得入木三分,讓人感覺他們就是活生生存在於世間的個體,而不是紙麵上的符號。這種真實感,使得整個閱讀體驗變得尤為深刻和引人入勝,讓人忍不住一口氣讀完,生怕錯過任何一個微小的細節。
评分這部小說的世界觀構建得非常宏大且復雜,但作者卻能將其梳理得井井有條,不讓讀者感到壓迫或不知所措。它涉及瞭多個社會層麵和復雜的人際關係網絡,每一個支綫故事都似乎擁有獨立發展的可能性,但最終又殊途同歸地匯入主綫,共同推動著整體情節的發展。這種多綫敘事的能力,體現瞭作者駕馭復雜題材的非凡纔華。更難能可貴的是,即便是描繪宏大的背景,作者也從未忘記關注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掙紮與抗爭,將大背景的厚重感與小人物的悲歡離閤完美地融閤在一起,使得作品既有史詩般的格局,又不失人性的溫度。
评分很好看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评分很好
评分装帧精美,送货快,内容未及读过。
评分不错,速度包装都可以,京东的图书可以的
评分好看,怎么感觉那年代的教育真好
评分一直在京东订购,放心快捷!
评分很好很好非常好
评分非常有启发性的一本书,能收获自己想要的东西。不错的阅读之旅。
评分包装很好,没有拆封过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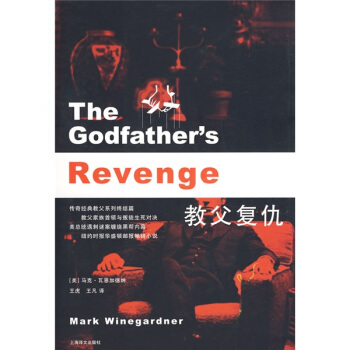


![天堂来的第一个电话 [THE FIRST PHONE CALL FROM HEAVE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27926/55bf025bNf71b3fa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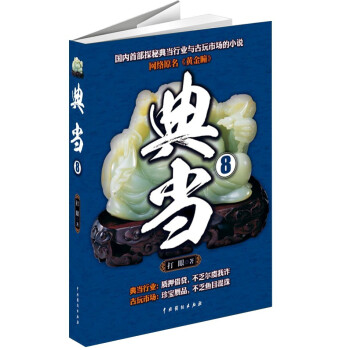

![我们(译文经典) [W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94086/58d8cb1aN5485399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