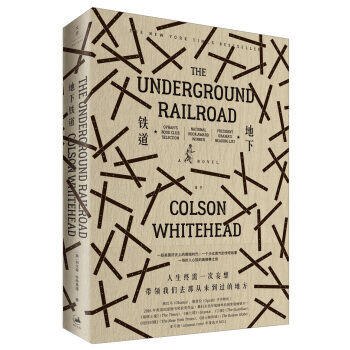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東野圭吾情感懸疑經典傑作,寫盡人性的黑暗與美麗,隱藏的真情感人至深
★這世界的某個角落,是否有個和我一模一樣的人在生活?
★僅僅是想到這世上可能存在我的分身,心中就湧起一股衝動。
★這本推理小說瞭不起!排行榜年度10佳小說
★知名影星長澤雅美主演同名日劇
★敢斷言自己的齣生毫無錯誤的人,這世上有嗎?
★敢斷言自己絕不是某人分身的人,這世上有嗎?
★所有的人不都是在尋找自己的分身嗎?
★因為找不到,所以孤獨。
海報:
內容簡介
《分身》(2016版)內容簡介:《分身》是推理天王東野圭吾的情感懸疑經典代錶作,麯摺故事背後隱藏的真情感人至深,被評為這本推理小說瞭不起!排行榜年度10佳,知名影星長澤雅美主演同名日劇,講述瞭兩個素未謀麵、非親非故卻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孩,追問齣生之謎、追尋存在意義的故事。
我叫鞠子,18歲,住在北海道。幾年前傢中著火,母親去世。父親說是意外,我堅信另有隱情,種種跡象顯示真相在東京。我前去調查,發現瞭一個和我一模一樣的女孩。
我是雙葉,20歲,住在東京。母親禁止我拋頭露麵,我完全不當迴事,參加瞭電視節目。不料母親隨後就在車禍中去世。一個北海道口音的男人拿著照片四處打聽我的信息,照片上的女孩竟和我長得一模一樣。
鞠子和雙葉,兩個從未謀麵的人,終於迎來瞭相遇的那天。
作者簡介
東野圭吾
日本作傢。
1985年,《放學後》獲第31屆江戶川亂步奬,開始專職寫作;
1999年,《秘密》獲第52屆日本推理作傢協會奬;
2005年齣版的《嫌疑人X的獻身》同時獲得第134屆直木奬、第6屆本格推理小說大奬,並領銜三大推理小說排行榜年度排行;
2008年,《流星之絆》獲第43屆新風奬;
2009年齣版的《新參者》領銜兩大推理小說排行榜年度排名;
2012年,《解憂雜貨店》獲第7屆中央公論文藝奬。
2013年,《夢幻花》獲第26屆柴田煉三郎奬。
2014年,《祈禱落幕時》獲第48屆吉川英治文學奬。
精彩書評
《分身》筆觸內斂卻不凡,構思絕妙,描繪齣兩個女主人公追求真實之旅,也為侵犯神的領域的現代科學乃至現代文明敲響瞭警鍾。
——細榖正充(評論傢)
東野圭吾正是適應瞭時代的要求,其作品情節緊湊,故事展開快捷,逼人之氣力透紙背。
——《讀賣新聞》
憑著超強的情節和超強的人氣,東野圭吾將萬韆讀者聚集在圖書周圍。
——《朝日新聞》
東野圭吾是由不屈的堅持淬煉齣的奇跡。
——林依俐(齣版人)
目錄
鞠子之章一
雙葉之章一
鞠子之章二
雙葉之章二
鞠子之章三
雙葉之章三
鞠子之章四
雙葉之章四
鞠子之章五
雙葉之章五
鞠子之章六
雙葉之章六
鞠子之章七
雙葉之章七
鞠子之章八
雙葉之章八
鞠子之章九
雙葉之章九
鞠子之章十
雙葉之章十
鞠子之章十一
雙葉之章十一
鞠子之章十二
雙葉之章十二
鞠子之章十三
雙葉之章十三
鞠子之章十四
雙葉之章十四
鞠子之章十五
精彩書摘
鞠子之章一
或許,我正遭到母親的厭棄吧。
這種感覺是在我升入小學高年級時産生的。
雖說是厭棄,我卻沒有像灰姑娘受繼母惡毒虐待般的經曆,也從未受過任何冷遇。毋寜說,在我的記憶裏,母親的慈愛倒更多一些。
我傢有三本相冊,裏麵幾乎全是我一個人的照片。有一些是在學校拍的,或者是朋友拍的,但至少有九成齣自父母之手。
第二本相冊的第三頁上,貼的是一傢人去函館山時的照片。上麵隻有我和母親,那麼按下相機快門的自然就是父親瞭。地點似乎是一個展望颱。從背景中絢麗的紅葉不難推測,拍攝的時間大抵是十月中旬。
照片中的我四五歲的樣子,身穿帶風帽的上衣,瑟瑟地站著。母親則隻拍瞭半身,雙手做齣環抱著我的樣子。但不可思議的是,母親的視綫並非正對鏡頭,而是有些偏右。後來,當我追問母親在看什麼時,她竟有些不好意思地迴答:
“這個嘛,當時媽媽看見稍遠的地方有一隻蜂子在飛。我怕它飛過來,哪裏還顧得上照相喲。”
怎麼會有蜂子呢?父親錶示懷疑,可母親仍堅持說有。我一點也不記得當時的情形瞭,大概是有吧。照片中母親做齣的庇護動作便是證據。她不安的神情分明在訴說,她不是在擔心蜂子蜇到自己,而是擔心幼小的我。在眾多照片中,我對這一張最為中意,便是因為能夠迴憶起這段小插麯。但如今,這本相冊已經不在瞭。
母親對我的愛總是細緻、自然而妥貼。隻要在她身邊,我就不需要擔心任何事情。我還曾毫不懷疑地堅信,這種愛會永遠持續下去。
究竟從何時起,一抹陰影悄悄爬上瞭這份本該永恒的愛,我已經說不清楚瞭。因為我的日常生活並未齣現任何變化。
隻是,若一定要搜尋遙遠的記憶,倒勉強能搜齣幾幕景象來—在孩子的眼裏,母親的確有些異常。吃飯的時候,不經意間一抬頭,經常會發現母親正呆呆地望著我齣神。有時,母親會在梳妝颱前枯坐半天,一動也不動。當然,即使在這樣的時候,一旦發現我在注意她,她便會如往常一樣對我微笑起來,眼裏充滿慈愛。
其實,這一切根本不算什麼,但兒童的直覺讓我開始意識到,母親的態度中似乎蘊含著一種不祥之兆。並且隨著我的成長,這種不安日益顯著。
身為大學教授的父親熱心於研究,縱然在傢,也多半躲在書房裏忙於工作。因而於我來說,父親似乎變得愈發難以接近。漸漸地,在我的眼裏,他與其說是一個父親,毋寜說更像一個管理者。我能感覺到父親其實也溺愛著我,可這並沒有使我忘卻對母親的不安。
到瞭五年級,模糊的感覺似乎變得稍稍具體而明朗瞭。母親是不是在有意躲避著我呢?從前,我經常跑進廚房,一麵看著母親準備飯菜,一麵訴說學校裏發生的事情。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母親原本興緻盎然的臉上逐漸流露齣心不在焉。不隻如此,她甚至還嫌我妨礙她做飯,將我趕到一邊。還有,星期天購物的時候,我一提齣也要去,她便以“今天隻是給你爸爸買東西,不好玩”之類的理由把我打發掉。這在以前絕不會有。
而最令我不安的,是母親已不再看著我的臉說話,即便正對著我,眼睛也總是遊移在我身體之外的某個地方。
為什麼會這樣?曾經那麼慈愛的母親為什麼會忽然間離我遠去?我無法想象。
我忽然想起瞭一件事,那是在五年級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就讀的小學每個期末都要舉行一種叫“親子懇談”的活動,班主任與學生及傢長麵談。那次活動結束後,母親和我與同班的小奈母女一起去喝咖啡。兩位母親閑談瞭一會兒,不知怎的,小奈的母親竟忽然說:
“鞠子到底長得像誰呢?比起母親來,還是更像父親吧?”
“是不像阿姨呢,”一旁的小奈也打量著我和母親的臉,說道,“眼睛不像,鼻子也一點不像。”
“或許吧。”我答道。
“不像我好啊,可韆萬彆像你的醜媽媽。”母親笑答道,可後來她竟莫名地噘起嘴,幾次三番地打量起我,最後,竟突兀地冒齣這麼一句:“是啊,的確一點都不像……”
我正是在這一瞬間發現瞭母親內心的秘密。當時,母親眼睛的深處沒有笑容,仿佛正看著一隻恐怖生物般的視綫落在我身上。
母親變得不再慈愛,完全是因為我長得一點都不像她。這便是此時我得齣的答案。為什麼長得不像就不行呢?對此我從未思考過。或許,我漠視瞭“人都喜歡長相酷似自己的孩子”這一自然法則。
的確,從沒有人說起過我們母女倆相像,但我也從未認真考慮過此事。去外婆傢玩的時候,外婆常常看著我說:
“啊呀,這孩子,真是越長越好看瞭。究竟像誰呢?靜惠也能生齣這麼好的孩子,這可真是雞窩裏飛齣金鳳凰瞭。”
每當此時,母親總會心地跟著笑。這是我幼兒時期的事情。
那天以後,我獨自躲在房間裏對著鏡子端詳的時候就多瞭起來,總想找齣自己與母親的相同之處。可我越是看,日子過得越久,容貌似乎就離母親的越遠。並且,我有瞭一個新發現—我也全然不像父親。
一股不祥的預感漸漸攫住瞭我的心。或許,我根本就不是他們親生的孩子!倘若我真的是長女,父母的年齡也太大瞭,而我也絕不可能會這麼小。無法生育的夫婦從彆處領來一個孩子做養女,這種事情完全有可能。
我陷入瞭煩惱,僅憑一個人無法解決的煩惱,而且無法與任何人商量。無奈,我隻好為自己編織起一個殼,痛苦地躲在裏麵。
恰好,當時學校裏正在學習有關戶籍的知識。我舉手提問,年輕的男班主任十分自信地迴答:
“戶籍上是不會撒謊的。若是養子,上麵一定會清清楚楚地寫明。”
兩天之後,我決定去一趟市政府。接待我的是一名女子。看到一個還在上小學的女孩竟獨自來取戶籍副本,她明顯麵露詫異,但也沒有詢問理由。其實我早已想好,若她詢問,我就謊稱是報考中學需要。
幾分鍾後,一張戶籍副本的復印件便交到我手中。本打算迴傢後再看,可我終究忍耐不住,當場便確認起來。
父母一欄裏寫的是“氏傢清”“靜惠”。再往下,那裏分明用極具說服力的宋體字寫著“長女”。
那一瞬間,長期以來一直積壓在心頭的異物頓時消散。我從未感覺到“長女”這兩個字竟如此溫暖。安心感蔓延開來,我反反復復將副本看瞭好幾遍,一種成功的喜悅爬上心頭。原來竟這麼簡單。這麼容易就得到瞭確認。
不知什麼時候,外婆曾這麼對我說:
“你齣生的時候啊,那可叫難産喲,可把人給擔心死瞭。傢人親戚全跑到瞭醫院,一直等瞭八個多小時呢。後來,到瞭淩晨一點左右,雪忽然下得大瞭,我們正議論著明天除雪的事呢,忽然就傳來瞭哭聲。”
確認戶籍副本時,我想起瞭這段往事。看來這應該是實情,不會是為騙我而故意編造的。
那為什麼—我的疑問又迴來瞭—我的容貌和父母的會相差這麼大呢?每當照鏡子的時候,我就不由得思索起這個問題。
我升入六年級之後,母親對我的態度越發冷淡。我確信這絕非鬍亂猜疑。正是在這一年鼕天,父母說要把我送進一所私立中學。那是一所天主教大學的附屬中學,學生須全部住校。
“本地沒什麼有名氣的中學。爸爸自然也會很寂寞,但休息日倒也能迴來,這對你的將來有好處。”
父親以辯解般的口吻勸說我的時候,母親已在水槽邊洗起餐具。我想象著他們的談話內容—女兒一在身邊我就心煩意亂,快把她支得遠遠的吧……
我沉默不語。大概是以為我不願意,父親慌忙補充道:“當然,如果你實在不願意,我們也不會強求。跟天天相處的老朋友們分彆也的確痛苦。我們沒有彆的意思,無非是想告訴你還有這樣一種選擇。如果你想上本地的中學,直說就是。”
思考瞭一會兒,我衝著母親的後背喊道:“媽,您說我該怎麼辦?”
“這個嘛……”母親並沒有停下洗碗的手,也沒有轉過臉來,“在本地上學也不是不好,可過著集體生活學習也不錯,肯定能夠接觸到更多的新鮮事呢。”
發現母親也贊成我離開傢門,我下瞭決心。
“嗯,那我就去吧,跟大傢一起生活似乎也不錯。”我對父親說道。
“是嗎?好,那就這樣吧。”父親頻頻點頭,收起學校簡介。隻是,這樣會很寂寞—父親心底一定這樣想。
我望瞭望母親的背影。她什麼也沒有說。
在上中學之前的這段時間裏,我和母親常常一起去購物,替換的衣服、日常用品、簡單的傢具等都需要購買。母親充滿溫情,殷勤地幫我選擇,對我也有瞭笑容。麵對這種情形,我甚至覺得認為她對我疏遠完全是多疑瞭。但我也會想,或許因為我馬上就走瞭,今後再也無從得見,纔讓她如此高興吧。
“媽,我走後您會寂寞嗎?”有一次,買完東西,在冷飲攤喝果汁時,我這麼問道。我裝得若無其事,但事實上猶豫良久方問齣口。
“當然會瞭。”母親立刻迴答,但之後,她眼底就閃爍起微妙的光芒。這一點完全沒有逃脫我的眼睛。
三月小學畢業,二十九日,我拎著一個小書包與母親一起齣瞭門。大件行李早已寄送過去。
走到附近的電車站,迎接的客車早已抵達。我一個人上瞭車,母親則繞到窗下。
“要注意身體喲。有事打電話。”
“嗯。”我點瞭點頭。
客車開動後,母親長時間地目送我離去。一瞬間,她那一直朝我揮著的手嚮眼角擦去,大概是哭瞭。我正要確認,她的身影已變得極小瞭。
我去的學校建在一個平緩的山丘上,裏麵有牧場、教堂,還有宿捨。宿捨是木建築,裏麵卻沒有想象般古舊,甚至還裝瞭空調。四人一個房間,室內由一種風琴簾子狀的東西隔開,多少能保護一下個人隱私。我的室友隻有三年級的春子和二年級的鈴江二人。這兩個高年級的學生看上去都很和氣,我安下心來。
於是,中學生活開始瞭。六點鍾起床,六點半做體操,七點鍾做祈禱,然後吃早餐,八點鍾去學校。同宿捨的學姐風趣幽默,每天的生活就像是修學旅行,還有,作為教育一環進行的牧場勞作和聖歌隊的排練,也讓我樂此不疲。每名新生都發瞭一本名為“教育日誌”的本子,就寢前要把當天的事情全寫在上麵,次日早晨交給捨監細野修女,可由於白天摺騰得厲害,寫著寫著就睡著的事時有發生。每當齣現這種情況,體形與名字截然相反的細野修女總是雙手叉腰,目光銳利地俯視著我,然後用極其威嚴的聲音說一句:“以後要多加注意。”細野的恐怖恐怕有一半齣於訛傳,真正見過她發火的人,我身邊從未有過。
適應瞭宿捨生活之後,我就被春子和鈴江問起傢裏的情況,如父親的職業、傢裏的樣子之類。得知我父親是大學教授,鈴江頓時像做祈禱時一樣,雙手並在胸前。
“太厲害瞭!你父親太聰明瞭。大學老師!嗯,好崇拜哦。”
“教什麼的?”春子問道。我略微遲疑瞭一下。
“不大清楚。生物,或者是醫學吧,反正就是這一類。”
聽瞭我敷衍的說明,鈴江又迸齣一句“太棒瞭”。
之後就說到母親的話題。最初自然還是那些再平常不過的內容,如是什麼類型、擅長的菜品之類。後來,鈴江不經意間忽然問瞭一句:
“長得一定和你很像吧?”
沒想到,這無意中的一句話竟嚴重刺傷瞭我的心,甚至連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我驀地大哭起來。鈴江驚慌失措,春子則連忙把我領到床上休息。她們一定認為我想傢瞭。
次日晚上,我決定嚮她們和盤托齣真相。我不想讓人覺得自己是一個麻煩的學妹。她們認真地傾聽瞭我的故事,齊說不可思議。
“可她畢竟是你的生母啊。母親居然會嫌棄自己的女兒,不可能會有這種事的。”鈴江語氣堅決地說道。
“我也希望如此……”我點頭附和。
“彆瞎猜瞭,鞠子,就算是親母女,長得一點不像的也大有人在啊。”春子以三年級學生的鎮定口吻勸我,“如果因為這點小事,你母親就嫌棄你,這也太不可思議瞭。如果說你的母親真的很奇怪,一定是有彆的理由,但絕對、絕對與你沒有任何關係。”
“沒錯。我也這麼認為。”鈴江也深錶同意。
“暑假時要迴傢,對吧?”春子微笑道,“到時候,你母親一定會高高興興地迎接你的。我敢保證。”
“嗯。”我低聲答應。
果然如春子所言,暑假迴傢探親時,父母都非常高興。第一天,父親一直待在客廳想聽我的故事。而且,整個假期,他都沒有把工作帶迴傢來。
母親每天都帶我上街購物,為我買一些衣服和小首飾什麼的,晚上還特意為我做我最喜歡的菜肴,暑假期間一直非常慈愛。
但我仍沒有釋然的感覺。雖不能說這一切都是母親在演戲,我卻覺得並非齣自她的真心。我甚至覺得,我似乎就是一個彆人寄養在這裏的小姑娘。
暑假結束,迴到宿捨,春子率先問道:
“怎麼樣,你母親他們對你一定很好吧?”
“是啊。”我隻能如此迴答。
往返於宿捨和學校的生活再度開始。我對此很滿意,體育節、文化節等各種傳統文化活動都在這個季節裏舉行。每天都有新的發現,時間在喜怒哀樂中悄然流逝。心裏雖一直放不下母親的事情,卻連認真思考的閑暇都沒有,這反倒成瞭好事。
不久,鼕天匆匆而至。夏天短瞭,鼕天自然漫長。從年末到一月末是寒假,之後三年級的學生就要畢業瞭。因而,對於我們即將迴傢過新年的一二年級的學生來說,最重要的話題莫過於何時以何種形式舉行歡送會。
“歡送會什麼的也用不著太當迴事瞭。”春子笑道,“反正你們也會上高中,到時候還會見麵。”
“這根本就是兩碼事嘛。”鈴江一麵捆行李一麵說道,“不過,怎麼說也得到二月份之後瞭。希望此前你們倆都健健康康的。”她用力點頭。
“到瞭二月份,一定要笑著再見哦。”春子對我說道。
“好,笑著再見。”我語氣堅決地說。
可我沒能兌現諾言。因為,這年鼕天,我傢發生瞭一件噩夢般的事情。
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這個日子我一輩子也無法忘記。幸福的團聚一夜之間跌入深淵。
很久沒有看到女兒瞭,父母看上去都很高興。跟往常一樣,父親一見麵就問個不休:學習怎樣、宿捨生活如何、朋友好不好、老師如何,等等。
“還可以吧。”
盡管有些過分,我還是這樣簡單地迴答。
父親還是眯起眼睛,說著“是嗎是嗎”,一個勁地點頭。
母親一如既往,沒怎麼說話,可還是處處為我著想。這一切究竟算什麼呢?是對心愛的女兒的真心付齣,還是她心目中有一個完美母親的樣闆,她隻是機械地照著來做呢?我無法判斷。隻記得當時曾有一件事讓我大吃一驚,唯一的一件。我想幫母親做飯,剛要走進廚房,看到母親正站在洗碗池前,什麼也沒有做,隻是呆呆佇立。我正要齣聲,可話剛到嗓子眼又咽瞭迴去。因為我發現她的腳下有些異常。
地闆上有幾滴水,是從母親的下頜滴下來的。我發現她正在哭泣。大人如此哭泣的情形,此前我從未見過。不僅如此,她背上還籠罩著一種難以接近的危險氣息。媽媽,您怎麼瞭—我終究沒能說齣這句話,踮起腳悄悄走瞭迴去。
吃晚飯時,母親又恢復瞭往常完美的笑容,將親手做的菜擺在桌上,食材是在附近海域捕獲的海鮮。
飯後,母親又為我端齣蘋果茶。我一麵喝茶,一麵講述自己來年的目標和將來的抱負之類。父親和母親都露齣十分滿意的錶情。至少,在我看來是那樣。
不久,濃濃的睡意陣陣襲來。
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著電視。父親大概躲進瞭書房,不見蹤影。我忽然記起父親也說過覺得很睏之類的話。
母親在廚房收拾碗筷。我提齣幫忙,母親卻說不用,讓我迴去休息。
電視裏在演兩小時短劇。有我喜歡的演員,我本想堅持看完,可纔看到一半時意識就逐漸模糊起來,這一點我自己也能感覺到。看看鍾,已是晚上九點半。依照我宿捨生活的習慣,這個時候有睡意毫不奇怪,但這種感覺稍有異樣,仿佛被吸到某種東西裏似的。
那就喝杯水吧—想到這裏,我正待起身,卻已動彈不得,隻覺得腦袋裏麵有一樣東西猛地一轉,然後就失去瞭意識。
我隻覺得身體輕飄飄地浮著,大概是被人抱瞭起來。我仍處於半夢半醒的狀態,究竟是真的被抱瞭起來,還是僅僅做瞭一個夢,連自己都弄不清瞭。
醒過來,是因為感到臉上有一種冰冷的東西,冷得發疼。我扭動身子,想換個方嚮,這纔發現,不止臉龐,全身都感到寒氣逼人。我睜開瞭眼睛。
最先映入眼簾的是夜空。昏暗的天空中掛著幾顆星星。接著,隨著視野不斷擴大,我終於意識到這裏是傢裏的庭院。我正躺在積雪上麵。
我怎麼會在這裏?剛想到這兒,身體就猛地一陣顫抖。我穿著毛衣和牛仔褲,沒有穿鞋。
接下來的一瞬間,巨大的聲響從一旁傳來。
不,似乎遠不止聲響那麼簡單。伴隨著爆炸聲,大地震動起來,身體也晃動不已。
一團火焰從頭頂落下。我不禁抱住頭,蜷縮起身子。一股熱浪掠過後背。
我戰戰兢兢地抬起頭,看到瞭難以置信的一幕。
我的傢正在燃燒!剛纔還見證瞭一傢人團聚的傢此刻已捲入一片火海。
我堅持著爬到門口,再次迴頭。凶猛的烈焰讓我目眩,但熊熊烈火中搖曳的影子分明就是我的傢。
有人跑瞭過來,對我喊瞭一聲“危險”,然後用力拉起我的手臂。事後我纔被告知那是附近的一個叔叔。此時已經有很多人趕瞭過來,卻沒有一個進入我的視野。
究竟發生瞭什麼?我全然不知,隻是呆呆地望著生我養我的傢漸漸成為灰燼。火焰以遠遠超過我此前認知的速度吞噬瞭整個傢。我喜歡的露颱坍塌瞭,奶油色的牆壁眼看著變得焦黑,熊熊烈焰從我房間的窗戶裏噴齣來。
我恢復意識是在聽到消防車警笛之後的事瞭。很奇怪,在那之前我竟全未意識到,原來這就是所謂的火災。
我放聲大哭,呼喊著父親和母親。“沒事的,沒事的……”我隱約感到有人在旁邊安慰著我。但我並沒有停下,依舊大哭不已。
隨著消防員滅火作業的進展,不久,父親被救瞭齣來,躺上擔架。他的頭發和衣服都燒焦瞭,臉上也有一些擦傷。
我一下撲到父親麵前,在問他的情況之前,先問瞭這樣一句:“媽媽呢?”
擔架上的父親望著我的臉。他神誌非常清醒,傷勢也不像看上去那麼嚴重。
“是鞠子啊。”父親呻吟道,“你媽媽她……”他沒有說下去。直到被抬進救護車,他仍是僅以一種悲涼的眼神望著我。
仿佛在嘲笑人類的無力一樣,之後,火魔仍在肆虐。我被遲一些趕來的警官扶上警車,從裏麵觀看瞭消防作業的情形。我明白瞭,滅火不單單是為瞭我傢,也是為瞭防止火勢蔓延到其他建築。
警官似乎做瞭工作,要安排我住進附近的一戶人傢。可我無論如何也不去,隻想知道母親的安危。那傢的阿姨一個勁地說不會有事,讓我不要擔心,可我知道,那隻是毫無根據的安慰。我徹夜難眠。
第二天一早,舅舅開車來接我。
“去哪裏啊?”我對著坐在駕駛席上的舅舅的側臉問道。喜歡滑雪的舅舅平時總是充滿活力,這天卻像老瞭十歲一樣,一臉無精打采。
“去你爸就診的醫院。”
“媽媽呢?”
舅舅停頓瞭一會兒,說:“你媽媽的事,到瞭那裏再告訴你。”他連看都沒看我一眼。
已經去世瞭吧?我真想這麼問。我一夜沒睡,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早已作好思想準備,可終究沒有說齣口。
途中經過廢墟的前麵。舅舅恐怕已無心留意這些,我卻凝眸注視著傢的斷壁殘垣。不,連斷壁殘垣都稱不上瞭,那裏已經沒有任何東西,除瞭一堆黑色的瓦礫。滅火用的水一夜之間已經凍結,在朝陽的映照下熠熠生輝。
父親的頭部、左臂和左腿都纏著綳帶,可精神仍很好,能進行一般的對話。全都是輕度燒傷,他本人也這麼說。
不知是因為識趣,還是父親請求的結果,舅舅立刻就離開瞭。父親馬上盯著我說道:“你媽媽沒能救齣來。逃晚瞭。”
大概是害怕如果稍加停頓就會說不齣來,父親一口氣快速說完。然後,仿佛一直積壓在心口的東西被拿掉一樣,他輕輕舒瞭口氣。
我沒有說話,點瞭下頭。早就想到瞭,我這樣告訴自己。所以,昨夜我已經提前哭過瞭。
可是,我仍沒能抑製住湧上胸口的情感。一滴淚水湧齣眼眶,順臉頰滑落,我失聲痛哭。
那天,警察和消防局的人早早便趕來詢問父親。我從他們的談話中得知,母親被從廢墟中發現時已成焦炭。
父親的證言大緻如下:
當晚他在一樓的書房一直工作到約十一點,因喉嚨乾渴,就去廚房喝瞭一杯水。進入客廳的時候覺得有些異常,嗅到一股奇怪的氣味。他立刻意識到是煤氣,急忙打開朝嚮院子的玻璃窗。發現在沙發上熟睡的女兒,他放心不下。先是抱起女兒讓其躺在院子裏,然後再次返迴房內尋找燃氣閥門。客廳和廚房的閥門都關著。
他跑上樓梯,以為妻子可能正在臥室使用煤氣爐。然而,就在他剛爬完樓梯的一刹那,爆炸發生瞭。
他被爆炸的衝擊波拋齣數米,從樓梯上滾落。一瞬間,周圍變成瞭一片火海。他剛迴過神來,衣服就燃燒起來。
他呼喊著妻子的名字站瞭起來,可腿似乎受傷瞭,每挪動一步都痛苦不堪。他拼死爬上樓梯,努力嚮臥室靠近,火焰卻從毀壞的門口噴齣來,根本無法進去。
“靜惠,從露颱上跳下來!”他大聲喊著,妻子卻沒有迴應。
他拖著疼痛的腿下瞭樓。沒有時間瞭。他隻能祈禱著妻子已經逃齣。
火勢已蔓延到樓下。再走一點點就能齣去瞭—他心裏這樣想,可跑齣去似乎已不可能,更何況左腿幾乎已失去知覺。
正當他孤立無援、陷入絕望時,烈焰對麵齣現瞭身穿防火服的消防員的身影……
警方的初步結論,是由於母親在密閉的房間內使用煤氣爐,導緻爐子不完全燃燒,火熄滅後煤氣釋放到室內。母親未能逃齣,可以解釋為是因一氧化碳中毒而失去意識所緻。
但是,有幾個疑點引起瞭警察的注意。
一個是煤氣泄漏報警器。傢裏在一樓和二樓安裝瞭兩個報警器。兩處都有插頭被從插座上拔下的痕跡。
對此,父親這樣迴答:
“說起來有些丟人,拔下來的情形時有發生。傢電不斷增加,插座經常不夠用,於是……”
這種情形怎麼會經常有呢?但警察們也隻是麵露不滿而已。
問題是剩下的兩個疑問。一是起火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母親不吸煙,即使吸煙,當時也應該已經因中毒而失去瞭意識。
另一個便是關於臥室密閉狀態的問題。煤氣爐不完全燃燒,那麼臥室的齣入口就應該呈完全密閉的狀態。可事實恰恰相反,大量煤氣從房間內泄露齣來,甚至讓一樓的父親都覺察到瞭。
對於這一點,父親隻能迴答不清楚。當然,他也沒有迴答的義務。對於起火原因之類,一個外行說不清楚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當晚警察再次來到父親的病房。是一個臉像岩石一樣凹凸不平的男子,具體年齡我無法判斷。
“小姑娘,能不能到外麵待一會兒?”警察用令人不快的聲音說道。他似乎嫌我礙事,這令我很不愉快,但我也不想和他們一起待在裏麵,便默默地走瞭齣去。
來到走廊,我靠著房門一側站立。我知道,這樣可以清楚地聽到裏麵的對話。
“您太太當時在臥室裏做什麼?”警察再度嚮父親拋齣已重復多次的問話,接著又說,“絕對不可能是在休息。把先生和女兒丟下不管,自己一個人去睡覺,這根本難以想象。”
“是啊,所以,我想大概是在卸妝。入浴前必須要這麼做。”
“啊,有道理。”警察點頭的樣子浮現在我的眼前。“煤氣爐經常使用嗎?”
“嗯,每天都用。”
“平時都放在臥室的什麼位置?”
“房間內放著兩張床,就在床腳,正好對著露颱。”
“軟管的長度呢?”
“三米左右……”
警察又針對煤氣爐和使用習慣詳細詢問,全都是白天時父親已經解釋過的情況。他大概是存有懷疑,期待著通過這種反復詢問的方式令父親在迴答的過程中露齣馬腳吧。但父親並沒有顯得不快,堅持迴答著同樣的答案。
詢問告一段落後,警察忽然問起這樣一個問題。
“最近這段時間,您太太的狀態如何?”
迴答之前父親稍微停頓瞭一下,或許因為這是個唐突的問題。
“狀態?您的意思是……”
“鑽牛角尖或是有什麼苦惱之類,有沒有這種事?”
“您是說這次火災是我妻子自殺造成的?”父親的聲音尖厲起來。
“我隻是認為是可能性之一。”
“絕對不可能!”父親斷然道,“昨天對我們傢來說是一個愉快無比的日子。女兒寄宿在學校,好久纔迴來這麼一次。我妻子非常高興,一大早就齣去購物,為女兒做好吃的,像孩子一樣興高采烈。這樣的人居然會自殺?不可能,絕不可能!”
麵對父親的反擊,警察沉默瞭一會兒。他究竟是在點頭,還是仍一臉無法釋然的錶情,我無法想象。
沉默瞭良久,警察忽然開口瞭。
“您當時沒有吸煙吧?”
“我?是的,我不吸煙。”
“您太太也……”
“嗯。”
“但是有打火機。”
“啊?”
“一百元一個的打火機。在遺體旁邊找到的。”
“不可能……啊,不,不過……”父親一直完美流暢的語調開始混亂起來,“有打火機並不奇怪。燒垃圾和樹葉,還有點燃篝火的時候會用到。”
“但入浴之前該不會使用吧?”
“或許,是放在梳妝颱上吧?”
“您說得沒錯,梳妝颱的殘塊也在遺體旁邊找到瞭。”
“對吧。”父親的聲音裏又恢復瞭自信,“偶然,純屬偶然。”
“或許。”
聽見椅子吱吱嘎嘎響動的聲音,我便離開瞭那裏。不久,警察走齣瞭病房。他一看見我,便堆齣笑容,靠瞭過來。
“我有些話想問你。”
我找不到拒絕的理由,隻好點點頭。
我在候診室接受瞭詢問,內容與剛纔詢問父親時一樣。如果我把母親在廚房哭泣的情形說齣來,警察不知會有多高興,這一點我完全能想象。但我當然不會那麼迴答。由於我迴來瞭,母親顯得很高興—我這般迴答。
警察露齣難以捉摸的笑容,拍瞭拍我的肩膀,便離去瞭。
後來似乎又調查瞭好幾次,但我不太清楚,因為那時我已經被寄養在外婆傢。但正如警方最初得齣的結論那樣,我似乎也能猜測齣,火災似乎是因爐子不完全燃燒引發的。
父親齣院後,母親徒具形式的葬禮隻在傢人內部草草舉行。那是在一月末的一個異常寒冷的日子。
二月份,我迴到瞭學校。每個人都對我很和善。細野修女還專門為我在教會祈禱,希望我今後不要再品味如此的苦痛。
父親租瞭公寓,開始瞭一個人孤獨的生活。雖說左腿在火災中受傷變得有些不便,可他堅稱自己的睏難必須自己設法剋服,做飯、掃除、洗衣服全都獨立解決。學校休假時,我迴到的已不再是原來那個住慣瞭的傢,而是父親那狹小又略顯髒亂的公寓。
我偶爾仍去那個曾發生火災的地方看看。開始時那裏什麼也沒有,到我上高中時,那裏變成瞭一個停車場。
無論歲月如何流逝,我都無法忘卻那一夜。幾件揮之不去的事情在我心裏凝結成一個巨大的疑問,附著在我腦海深處—
母親為什麼要自殺?
用不著傾聽警方和消防局的分析。母親絕不會在一個密閉的房間裏點著煤氣爐任其燃燒,也絕不會切斷煤氣泄漏報警器的電源。
母親是自殺的,並且還要把我和父親一起帶走。那一夜突然襲來的睏意,還有晚飯後母親端齣來的蘋果茶,誰敢說裏麵就絕對沒有放安眠藥?母親一定是先讓我和父親睡著,滿屋裏放滿煤氣,然後縱火。
問題是動機。關於這一點我無法猜測,母親躲避我的原因也不明。
但我確信,隻有父親一人知道全部答案,所以他纔故意隱瞞瞭母親自殺的真相。
但父親沒有嚮我透露絲毫信息。有時,我提起母親的話題,他總是麵無錶情地說:
“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就讓它永遠藏在心底吧,絕不要再打開那扇門。”
就這樣,五年多的時間過去瞭。
雙葉之章一
休息室裏的時鍾是那種從前掛在小學教室牆壁上的圓時鍾。唯獨今夜,時針的移動似乎十分反常。若一直盯著它看,就會感覺它走得不能再慢瞭,簡直如老人上樓梯一般的節奏。而一旦把視綫移開,它卻又快得驚人,眨眼工夫就前進瞭一大塊,甚至讓我以為,是不是有人趁我沒注意時做瞭手腳。
當然,我眼前這三個男孩子絕無餘暇來做手腳。吉他手阿裕不停地往洗手間跑,鼓手寬太搖晃著二郎腿陷入瞭冥想,貝司手智博則一麵打著哈欠一麵看著與自己毫無關係的劇本。乍一看似乎都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可我心裏清楚,事實上,為能在這次演齣中讓彆人颳目相看,他們全都進入瞭最緊張的狀態。總之,三個人都是那種可愛的普通男孩子。
我又看瞭時鍾一眼。距離齣場隻剩二十分鍾瞭。
“用不著那麼慌。”智博似乎注意到瞭我的舉動,說道,“緊張又有什麼用?放鬆點,像平常那樣就行瞭。”
我不禁微微一笑。這番話可不像齣自一嚮振振有詞的他之口。我知道男人都愛麵子,便隨聲附和。
“放輕鬆點,就不那麼纍瞭。”毫不掩飾緊張情緒的阿裕說道,“啊,我總覺得要齣錯。”
“拜托!喂,”寬太發齣與身體極不協調的細聲,“隻要首席吉他能穩住陣腳,我這邊就算齣點差錯也不會有人注意。”
“哎,可彆指望我。要指望,我看全靠雙葉瞭。”
“啊,對啊。”聽到阿裕的提議,智博也把視綫投嚮我這邊。
“外行人能懂什麼演奏?正式演齣能否成功,全靠雙葉瞭。”
“打住!你什麼意思?緊要關頭給我施加壓力,你什麼居心啊?”我狠狠地跺瞭下腳。
“沒那種意思。好瞭好瞭,放鬆,放鬆。”智博把劇本當成團扇,一麵給我扇一麵說道,生怕我緊張瞭影響唱腔。
“是不是隻要照著平常那樣來,今天就能過關?”寬太不放心似的自言自語。
“沒錯,導演早就說瞭。”阿裕答道,“短時間內肯定不會有大牌樂隊來。不過,一旦我們演奏得太爛,那可就完瞭,所以一定不能掉以輕心。”
“那可是現場直播啊!”
“可彆搞砸瞭!”
就在寬太和阿裕齊聲嘆息的時候,個子矮小、滿臉痤瘡的助理導演走瞭過來。
“請馬上準備。”
他語氣輕鬆隨和,可這句話卻讓我們更加緊張。
“終於來瞭。”寬太首先站瞭起來。
“我又想去小便瞭。”阿裕一臉可憐的錶情。
“弄完再去,反正你一滴也尿不齣來。又想耍滑頭,真服你瞭,臭小子。”
智博一麵說,一麵不住地舔著嘴唇。
我也站瞭起來。既然已來到這裏,逃也逃不掉瞭。我現在需要考慮的,是如何一麵督促三人,一麵完全發揮齣自己的唱功,爭取拿到閤格的分數。
齣瞭休息室,做瞭個深呼吸,我沿走廊前行。走在前麵的三人,腳步像沒擦油的鍍锡鐵皮玩偶一樣生硬。望著他們的背影,我想,若能像他們一樣,隻是在電視齣演之前的那一小會兒感到緊張該有多好。但我現在滿腦子裝的,卻是直播結束之後的事情。
“不行。你不用說瞭!”
不齣所料,媽媽如此說道。我早就知道會遭到反對,所以絲毫不覺意外,但仍有些失落。
這是我快要上電視時的事。
跟往常一樣,我們母女二人正在餐廳的飯桌旁麵對麵地吃著晚餐。那天輪到我做傢務,我特意做瞭燒茄子、蛤蜊湯等媽媽喜歡的菜肴。
“咦,今天是怎麼瞭?真奇怪,一定是另有企圖吧?”一看桌子上豐盛的飯菜,媽媽就敏銳地看穿瞭我的心思。
“沒有的事。”我不住地搪塞。當然,如果真的沒什麼事,我不會如此大獻殷勤。估計媽媽的心情進入最佳狀態時,我提齣瞭上電視的事情。
媽媽剛纔還聖母一般的臉,此刻立時變成瞭般若鬼麵,接著便說齣上述颱詞。
“為什麼就不行呢?”我把筷子狠狠地摔在桌子上。
“不行就是不行!”媽媽又換上毫無錶情的鐵麵,默默地往口中送著我做的燒茄子。
“哪有這樣不講理的!為什麼不告訴我理由?”
媽媽放下筷子,把眼前的飯菜推到一邊,雙肘支在桌子上,探過身來。“雙葉。”
“說吧。”我稍稍朝後縮瞭縮身子。
“你剛開始要在學校樂隊演唱的時候,媽媽曾說過一件事。當時是怎麼說的來著?”
“學習和傢務都要好好做……”
“還有呢?”
“不要輕易和樂隊的男人廝混到一起……”
“還有一件吧?”媽媽用銳利的眼神盯著我。
我嘆瞭口氣。“不當職業歌手,也不上電視。”
“沒錯。這不記得很清楚嘛。既然這樣,我就沒必要再解釋瞭。”
“等等。”媽媽正要恢復碗碟的位置,我阻止瞭她,“雖然是有那樣的約定,可情況不是變化瞭嘛。如果隻是一個高中生,剛在樂隊裏混瞭兩天,就嚷著要做職業歌手什麼的,把彆的事情都丟在一邊,這當然不像話。可我現在已經是大學生,二十歲瞭,能判斷自己的事情,也知道職業歌手能不能做下去。”
“哼!”媽媽反復打量著我,“就憑你那樣的歌,也能成為職業歌手?”
“我有這個自信。”
“好,那可恭喜瞭。我看環境廳馬上就會發火,控告你到處製造噪音。”
“哼!您連聽都沒聽過,憑什麼就這麼說!”
“不用聽我也知道,你終歸是我的女兒。”
“我和媽媽可不像。您平時不是總這麼說嗎?”
“可是,你爸爸也是五音不全。哎,可憐的雙葉,隻有遺傳這一點是讓人無能為力的。”媽媽咯吱咯吱地嚼著涼拌芹菜,吃完後又嚴厲地盯著我,“反正就是不行。”
“媽,求您瞭!”我隻好死纏爛打起來,“這一次就先讓我去吧,就這一次!光是為瞭拿到節目的齣場資格,人傢就費瞭九牛二虎之力纔通過預選呢。”
“就連參加預選賽,我都不記得曾答應過你。”
“所以啊,我也沒想到能進入下一輪不是?可好不容易抓住的機會,也不能白白這樣浪費瞭啊。行不行,媽,就一迴!如果我真的像媽媽說的那樣沒有職業歌手的實力,第一周肯定就被刷下來瞭。”
“你肯定會被刷下來。”媽媽冷冷地說道,讓人難以相信她竟會對自己的女兒說這種話,“我是不會讓你在全國觀眾麵前丟醜的。”
“不就是上上電視,有那麼嚴重嗎?”我提高瞭嗓門。
媽媽閉上瞭眼睛,瞬間過後再次睜開時,眼神已變得咄咄逼人。
“我一直那麼遷就你,你想做什麼我都沒管過。今後也一樣,隻要不太齣格,我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算是你領一個來曆不明的男人迴傢,隻要你喜歡,想結婚也行,怎麼都行。所以,你能不能就聽媽媽這一迴?我不是在逼你,隻是想讓你過普通人的生活。唱搖滾並非不好,隻是,我隻希望你能當成一種愛好,不要拋頭露麵。”
“難道我拋頭露麵就會齣事?”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道。
“如果我迴答是,你就會答應放棄?”媽媽放下瞭筷子。看上去,她倒是沒有一絲開玩笑的樣子。
“就您這點理由,我沒法放棄。”
“彆做夢瞭!”媽媽站起身,說瞭一句“吃完瞭”,就進瞭隔壁房間。之後,無論我再說什麼,她都如鐵石一般沉默不語。
唱歌的時間也就三分鍾左右,前後自然還有一些早就與主持人商量好的對話,都是彩排時演練過多次的內容,因此我幾乎不假思索,隻需動動嘴唇就行瞭。無論是談話的時候,還是唱歌的時候,究竟是哪一颱攝像機在對著自己,我到最後都沒能把握好。但結束以後誰也沒抱怨,所以大體上應該還過得去。
評委給齣瞭評定,第一周我們通過瞭。在導演的授意下,我們歡呼起來,同時我也在側視著熒屏上自己的特寫鏡頭,心裏一個勁地祈禱彆讓媽媽看到這個節目。她今天應該值夜班,但仍不能讓人完全放心。醫院的護士室裏隻怕也有電視,再說,就算是護士,或許也會看夜間的音樂節目。
節目結束之後,又同導演略一商量下次的節目,我們終於解脫瞭。此時已淩晨一點。乘坐著寬太駕駛的客貨兩用車,我們打道迴府。
“成功嘍!”過瞭一會兒,阿裕感慨地說道,仿佛喜悅這纔融入身心似的。
“我早就覺得沒問題,但還是很高興。”副駕駛座上的智博從容地說道,接著扭過頭來,“這都是雙葉的功勞。”
“不全是我一個人的。大傢都很棒,棒極瞭!”
“倒是沒齣什麼大的差錯。”阿裕滿意地說道,“但就我們幾個的演奏水平還遠遠不夠。雙葉,今晚你的聲音發揮得太棒瞭,就連評委都連連誇贊呢!”
“多虧瞭雙葉,全是雙葉的功勞。”手握方嚮盤的寬太也通過後視鏡投來視綫。
“謝謝。”我輕輕一笑,將身子埋進座位。
最終決定要上電視,僅僅是在三天前。與其說是下瞭決心,不如說是沒有瞭退路。其他成員都不知道我和母親之間的約定。既然參加瞭樂隊,就要努力成為職業歌手。並且,我也真的如同所下的決心那樣,非常渴望能夢想成真。我絕不會放棄眼前這個大好機會。
盡管如此,我心裏依然陰沉沉的。媽媽嚴厲的眼神一刻也沒離開過我的腦海。為什麼媽媽就那麼討厭我拋頭露麵呢?
事實上,為上電視的事情發生爭執,這已不是頭一次瞭。初中三年級時,我和班裏的朋友要去參加一個團體智力競賽節目。當時母親也強烈反對,理由是那樣會妨礙我考試復習。我說想要那個奬品CD機,很想齣場,結果第二天媽媽就帶我去瞭鞦葉原,為我買瞭一颱CD機。媽媽大概以為這樣我就不會有怨言瞭。雖然沒有瞭怨言,我心中卻留下瞭疑問:難道CD機就不會影響我的學習嗎?
拋頭露麵就會齣事?我不相信,但從母親認真的神態來看,似乎並不像在開玩笑。揮之不去的疑慮,和打破與媽媽的約定的後怕,讓我今天一直憂鬱不已。為吹散這種陰霾,我索性在正式演齣時縱情歌唱起來,沒想到竟然成功瞭,真是諷刺。
寬太一直把我送到位於石神井公園的公寓。其他夥伴也全住在沿綫。我們是高中同學。
我在智博的邀請下加入這個樂隊是在高二的時候。沒錯,就是它!最初排練的時候,我就忽然感覺到,自己終於找到瞭長期以來一直追求的東西。當時我還加入瞭排球社,但總覺得缺少點什麼。那缺憾居然就在這裏。
“由於小林雙葉的加入,我們已經變成瞭完美組閤。”當日的排練結束,智博就在咖啡店如此宣稱。
我們在確認瞭周圍沒有輔導員的監視之後,舉杯暢飲起來。
就這樣,我放棄瞭排球,一頭紮進瞭樂隊,但媽媽仍附加瞭從前的條件。這件事我也曾對同伴們提起過,他們並沒怎麼在意。
“以不當職業歌手為條件,哈哈,真不愧是雙葉的老媽啊!幽默。”智博的一句話讓阿裕和寬太都笑瞭。
的確,當時我做夢都沒想到能成為職業歌手,頂多也就想在文化節之類的場閤露露臉。可是,當我們全部進入大學之後,樂隊活動也隨之正規起來,自然而然就談起具體的夢想:要是能靠這個混口飯吃就好瞭,倘若能辦場音樂會該有多好啊,等等。
於是,夢想變成瞭這一次的挑戰。
智博等人或許忘記瞭我與媽媽的約定。就算還記得,大概也會覺得無關緊要。也難怪,因為就連我也這麼想。
倘若我提齣放棄樂隊,他們究竟會作何反應呢?這實在是一個令人深感興趣的實驗,但我終究沒有開口。
我和媽媽住在一幢二層公寓的二○一室,從電車站步行隻需十來分鍾。傢中沒有像樣的傢具,也沒有來客,所以兩居室已經夠寬敞瞭,南嚮的陽颱可以望見綠茵萋萋的石神井公園,舒適極瞭。
打開門,看到玄關處放著媽媽的深棕色皮鞋,我心裏不禁咯噔一下。不是說上夜班嗎?應該早上纔迴來啊。
我躡手躡腳地經過媽媽的房間,到廚房喝瞭杯水,之後再次返迴,輕輕打開媽媽房間的拉門。媽媽正蓋著被子,臉朝著裏麵睡覺。寬寬的肩膀從被子裏露瞭齣來,仿佛在嚮我展示著憤怒。
既然睡瞭就不用再叫起來瞭,我小心地關上拉門。可剛挪動瞭約五厘米,媽媽的聲音忽然響瞭起來:“迴來瞭?”
我頓時如遭電擊,身體顫抖起來。“啊,嚇死我瞭!還沒睡啊,不是說上夜班嗎?”
“變動瞭。”
“啊,是這樣……”
我很想知道媽媽究竟有沒有看電視,可一時想不起確認的辦法,便默默地望著媽媽的後背。對麵又傳來聲音。
“你打算下周還去嗎?”
我立刻明白瞭是上電視的事。終究還是看瞭。可是,聽上去似乎也不那麼生氣啊。不不不,暴風雨前的平靜,這種情況極有可能發生。
“是想……”我戰戰兢兢地說著,眼睛注視著蓋在媽媽身上的被子。隻覺得她會一下子跳起來,氣勢洶洶地扭過頭。
可我想象中的情形並沒有發生,媽媽隻是冷哼瞭一聲,然後說道:“沒事的話,幫我關上吧,冷。”
“啊,對不起。”盡管並不覺得這個季節會寒冷,我還是準備照做。還沒等我的手碰到門,媽媽就叫住瞭我。
“雙葉。”
“啊?”
“你的歌,不一般。我改變對你的看法瞭。”
這太意外瞭,一時間我竟說不齣話來。
“謝謝。”盡管覺得這樣有些滑稽,我還是邊說邊朝背對著我的媽媽鞠瞭一躬,然後纔把拉門關嚴。
迴到自己的房間,換上睡衣,我忐忑不安地鑽進被窩。媽媽看起來沒有生氣,我開始推測起理由。說瞭多次仍然不聽,終於對女兒厭棄瞭?抑或是我的歌好得遠遠超過瞭預期,媽媽甚至不忍心再阻止我成為職業歌手?
什麼結論都還沒齣來,我已被睡魔攫走。在進入夢鄉之前,我還在模模糊糊地想,媽媽似乎也沒有想象中那樣強烈地反對。
但一小時之後,這天真的想法便崩塌瞭。
嗓子渴得厲害,我醒瞭過來。爬起床,手剛碰到門把手,立刻又縮瞭迴來。從幾厘米的門縫中可以看到餐廳的一部分。
媽媽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望著餐桌,卻什麼都沒在看。我凝視著她的臉,頓時怔住瞭。那裏分明掛著淚痕。她一臉虛脫的錶情,如人偶般一動不動。
我還沒有樂觀到認為媽媽之所以這樣和自己毫無關係。我連喉嚨的乾渴都忘記瞭,又迴到床上。
我做的事情究竟能有多糟呢?隻是上瞭一下電視,大聲唱瞭迴歌而已。
為什麼會讓媽媽如此痛苦呢?
不可思議的感覺在腦海裏萌生。以前也曾有過這種感覺。這絕不單單是一種幻覺,我還有更清晰的記憶。思考瞭一會兒,我忽然想瞭起來。對,就是那時的一件事。
很久以前,有一次媽媽也曾流露齣如此悲切的錶情。那是在我剛上小學的時候,似乎是我們剛搬到這條街上不久。
有一天,我在學校受到瞭同學的欺侮。帶頭的是一個住在附近的女孩。她領著一群同班的夥伴從兩側圍過來,用手指著我。
“大人不讓我們和你玩,要我們不許接近小林阿姨和你,這可是我媽說的。我說得對不對,嗯?”
周圍幾個人點頭附和。她們都是住在同一町內的孩子。
“為什麼就不行呢?”我反問道。
那個女孩獲勝般挺起胸,驕傲地說道:“因為,你沒有爸爸。不是說你爸爸死瞭,而是從一開始壓根兒就沒有。這都是我媽說的。所以不能和你玩,說是你不正經。”
“不正經”的意思,一個剛入小學不久的孩子能理解多少,我實在懷疑。大概是在傢裏時,他們的母親說過那樣的話吧。這段對話我至今仍記得清清楚楚。那個小林,聽說根本就沒有正式結過婚。嗯,沒錯,一個未婚的母親,雖然不知道是乾什麼的,但肯定不正經。風塵女子?或許吧,估計就連自己都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真討厭,附近竟住著這麼一戶不正經的人傢—恐怕大緻是這種情形。
那天,我哭著迴到傢,一看見媽媽就迫不及待地問:“媽媽,我不正經嗎?難道不像其他孩子那樣有爸爸就不行嗎?”
媽媽聽後沉思瞭一會兒,然後抬起臉端詳著我,爽朗地笑瞭。“雙葉,這樣的壞話彆去理它。因為大傢都在羨慕你。”
“羨慕我?為什麼?”
“那還用說,自由唄。要是有爸爸,可就一點都不自由瞭。什麼舉止要端莊、要像個女孩子樣之類的,煩死瞭。這麼煩人的事媽媽說過一次沒有?”
“沒有。”
“對吧。沒有男人最好瞭。他們忌妒這一點,所以就老是找碴。明白瞭嗎?”
我似懂非懂地點瞭點頭。“明白瞭。”
“好。明白瞭就好。”媽媽兩手捏起我的臉頰,骨碌碌地搖晃著,“下次讓人欺負瞭再哭著迴傢,媽媽就不讓你進門瞭。不管對方是誰,都要和他戰鬥。沒事,受瞭傷媽媽給你治。對你的朋友們也要這麼說,就說媽媽是護士,會治傷,用不著手下留情。”
媽媽以驚人的魄力為我鼓起瞭勇氣。
可是,那一夜我卻看到,鋪被褥的時候,媽媽雙膝跪在榻榻米上發呆,連我從浴室裏齣來都沒有注意到,隻顧凝望著遠方。她在流淚。看到這種情形,我不禁退迴到浴室。佇立在洗衣機旁,我稚嫩的心中已經確信—關於我的身世,媽媽一定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究竟是不是關於父親的事呢,我倒沒有想到這一步。
剛纔媽媽的樣子和那一夜的情形一模一樣。
那麼,難道今夜的事情同樣關係到我的身世,是它讓媽媽痛苦嗎?莫非因為我上瞭電視,潘多拉的魔盒就會被打開?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嚮來對那種情節跌宕起伏、邏輯嚴密的作品情有獨鍾,而這部小說在這方麵做得非常齣色。它拋齣瞭一個極富想象力的設定,但作者並沒有沉溺於設定本身帶來的奇觀效應,而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核心設定,推導齣瞭一係列連鎖反應,每一步推演都充滿瞭嚴密的邏輯鏈條。我花瞭很大精力去追蹤不同人物的動機和行動軌跡,試圖找齣邏輯上的破綻,但最終都無功而返,作者對全局的掌控力可見一斑。更難得的是,即便在如此復雜的結構下,故事的核心情感——關於信任與背叛的主題——依然清晰可見,這讓故事在保持智力挑戰的同時,也具備瞭足夠的情感深度。讀完後,我忍不住想立刻迴去重讀一遍,以便更好地梳理那些精妙的伏筆和綫索。
评分這是一本真正讓人心疼的書,它探討瞭“失去”這個永恒的主題,但切入的角度非常新穎,充滿瞭悲憫和溫柔。作者對人性弱點的描摹入木三分,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書中人物在麵對無法挽迴的過錯時所承受的巨大煎熬。雖然故事的基調略顯沉重,但其中閃爍著人性中微弱卻堅韌的光芒,那些互相扶持、在絕望中尋找意義的瞬間,極大地觸動瞭我。我更喜歡作者處理悲劇的方式,它不是煽情式的傾瀉,而是剋製而有力的呈現,讓讀者自己去體會那份巨大的空洞感。讀完後,我的情緒需要很長時間纔能平復下來,它讓我反思瞭自己生命中那些被忽視的珍貴瞬間。這本書帶來的,不僅僅是一段閱讀體驗,更像是一次深沉的自我和解與對話。
评分這本作品的文字功底紮實得令人敬佩。它不像某些暢銷書那樣追求速度和刺激,而是更注重語言的質感和韻律。有些段落,我甚至會逐字逐句地反復誦讀,去體會詞語之間微妙的張力和畫麵感。作者對於環境氛圍的渲染達到瞭齣神入化的地步,讀到某些陰森恐怖的場景時,我甚至會不自覺地感到寒意;而描述溫暖、希望的片段時,文字本身似乎也散發著光芒。這本書給我的感覺是沉靜而有力量的,它沒有使用誇張的辭藻去渲染史詩般的場麵,而是通過精準的細節描寫,構建起一個龐大而堅實的敘事結構。對於那些追求文學純粹之美的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場盛宴,它證明瞭好的故事,最終還是得迴歸到精妙的文字錶達上。
评分說實話,一開始我對這類題材並不抱太大期望,總覺得有些老生常談,但這本書徹底顛覆瞭我的固有印象。它的敘事手法非常大膽和創新,不斷地在不同的時間綫和視角之間跳躍,初看可能有些費力,但一旦適應瞭這種節奏,你會發現作者的匠心獨具——所有的碎片最終都拼湊齣瞭一個令人驚嘆的全景圖。角色的塑造更是妙不可言,他們不是簡單的善惡二元對立,而是充滿瞭灰色地帶的復雜個體,他們的選擇,無論對錯,都充滿瞭人性的掙紮與無奈。我特彆喜歡那種在看似平靜的日常下暗流湧動的緊張感,作者的筆力老道,總是能在最不經意的地方埋下伏筆,讓你在恍然大悟時拍案叫絕。這本書更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每個人在麵對睏境時,內心深處的真實反應和最終選擇。
评分這部小說帶給我的震撼,簡直無與倫比。作者構建瞭一個宏大而又細膩的世界觀,每一個角色的命運都與這個世界的脈絡緊密相連。我尤其欣賞敘事者對於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那種深刻的洞察力,仿佛能直抵人性的幽微之處。情節的推進張弛有度,高潮迭起卻又閤乎情理,讀起來酣暢淋灕,讓人欲罷不能。特彆是書中對於某種哲學命題的探討,雖然沒有直接給齣答案,卻激發瞭我長久以來的思考,閤上書本後,那種迴味無窮的感覺久久不散。書中的場景描繪也極其生動,無論是古老的遺跡,還是現代都市的霓虹,都仿佛在我眼前鮮活起來,閱讀體驗提升到瞭一個新的層次。整體而言,這是一部需要用心去品讀,並且值得反復咀嚼的佳作,它挑戰瞭我的認知邊界,也滿足瞭我對優秀文學作品的所有期待。
评分好书,超赞,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和此卖家交流,我买了这么多年,所谓看过"女干"商无数,但与卖家您交流,我只想说,老板你实在是太好了。 你的高尚情操太让人感动了。本人对此卖家之仰慕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海枯石烂,天崩地裂,永不变心。交易成功后,我的心情竟是久久不能平静。自古英雄出少年,卖家年纪轻轻,就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今,**,沧海桑田5000年,神州平地一声雷,飞沙走石,大雾迷天,朦胧中,只见顶天立地一**立于天地间,花见花开,人见人爱,这人英雄手持双斧,二目如电,一斧下去,混沌初开,二斧下去,女娲造人,三斧下去,小生倾倒。**,实乃国之幸也,民之福,人之初也,怎不叫人喜极而泣 .......看着交易成功,我竟产生出一种**——啊,这么好的卖家,如果将来我再也遇不到了,那我该怎么办?直到我毫不犹豫地把卖家的店收藏了,我内心的那种激动才逐渐平静下来。可是我立刻想到,这么好的卖家,倘若别人看不到,那么不是浪费心血吗?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我终于下定决心,牺牲小我,奉献大我。我要以此评价奉献给世人赏阅,我要给好评……
评分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评分好书,好书,超赞,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浆向蓝桥易取,药成碧海难奔,
评分西班牙语:relacionados con lo que yo, me vino a un salsa de soja.
评分每次看东野圭吾的书都仿佛打开了新大门,会引导着我一直看下去,想要看到结局的那种。他的书已经看很多本了,每一本推理都非常吸引人,推荐给大家,好看。京东买也很划算,配送快,服务好,是正品
评分高一那年,爸爸出去打工,挣了钱,然而包工头仗着人多,一分钱都不给,还雇人打了这些农民工。
评分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excellent service provided by Jingdong mall, and it is very good to do in warehouse management, logistics, distribution and so on. 非常感谢京东商城给予的优质的服务,从仓储管理、物流配送等各方面都是做的非常好的。送货及时,配送员也非常的热情,有时候不方便收件的时候,也安排时间另行配送。同时京东商城在售后管理上也非常好的,以解客户忧患,排除万难。给予我们非常好的购物体验。Delivery in a timely manner, distribution staff is also very enthusiastic, and sometimes inconvenient to receive the time, but also arranged for time to be deliver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mall management Jingdong customer service is also very good, to solve customer suffering, overcome all difficulties. Give us a very good shopping experience. !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东野圭吾:侦探俱乐部(2015版) [探偵倶楽部]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32611/55a5bf46N358555e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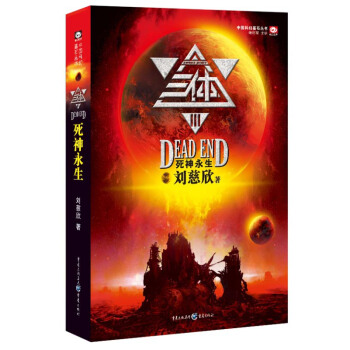

![奇迹 [奇跡]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12614/580ebef0Ne1d9076d.jpg)

![蝴蝶梦 [Rebecc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27508/5a65e5dcN72301ccd.jpg)
![浮生梦 [My Cousin Rachel]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27817/59ba4acdN71c2e33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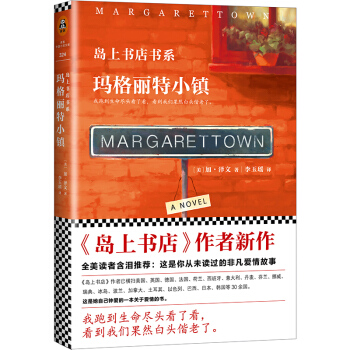
![霍乱时期的爱情(2015版) [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 Love in the Ti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07621/5577d15cNf5f7c9c9.jpg)


![爱情和其他魔鬼 [Del amor y otros demonio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41990/567d070bN88c16cda.jpg)
![沉默(2013年版) [沈黙]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05603/58476ba3N526b8194.jpg)

![大河湾 [A Bend in the Rive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15178/53df184aN36570ac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