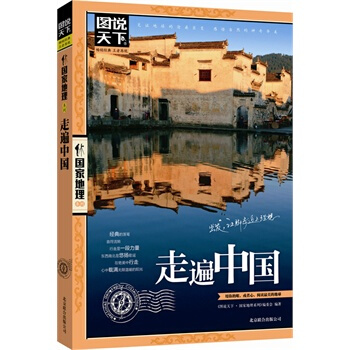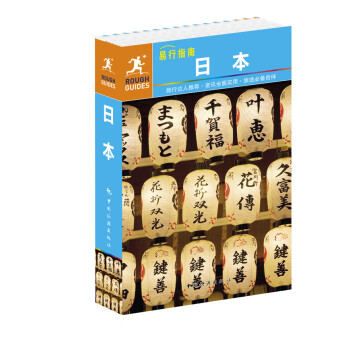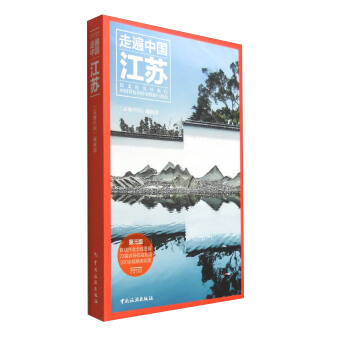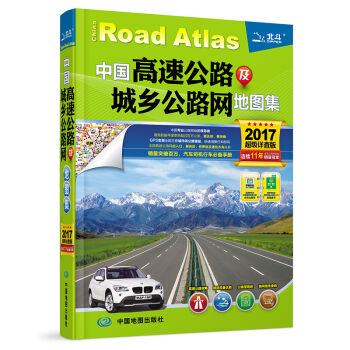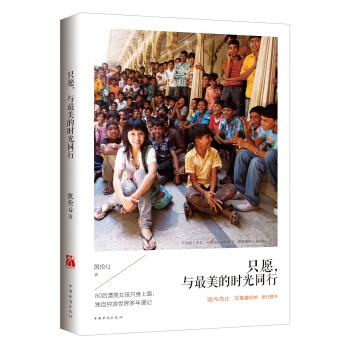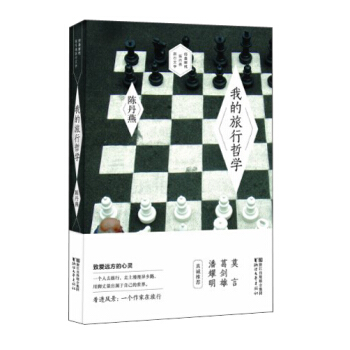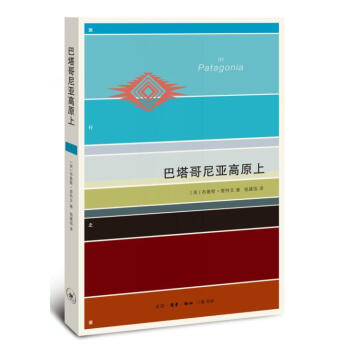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書中的九十七個故事都是精心選擇的,用來說明人生卡住瞭,該怎麼辦? 圖書銷售商甚至為本書開闢瞭一個新門類:新非虛構文學。 查特文的第一部書用文字對應著祖母的櫥櫃,書中九十七個章節仿佛一張張抽屜,將一組組獨特眼光發現的故事分門彆類裝好。查特文一再堅持自己恪守傳統形式,可大多數讀者並不苟同。圖書銷售商甚至為該書開闢瞭一個新門類:新非虛構文學。 書中所有故事都精心選擇,以闡明流浪及流亡的一個特定方麵,也就是說:人生卡住瞭,該怎麼辦?全書可以視為一部該隱和亞伯神話的隱喻。 在巴塔哥尼亞本地,查特文的書帶來瞭一些效應。“該寫點什麼,說說那些人手一本《巴塔哥尼亞高原上》的外國佬,”當地人說,“那本書就是他們的《聖經》。” 讀完《巴塔哥尼亞高原上》之後,查特文為讀者留下兩個選擇:其一,下一年就收拾行裝,動身去巴塔哥尼亞;其二,做一趟“心靈象徵之旅,對漂泊不定的人生,以及不屈不撓的精神作一番沉思”。內容簡介
傳奇,是查特文不算長的一生*貼切的批注。擁有不安分的靈魂,隨時可以開始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帶著心愛的鼴鼠皮(Moleskin)筆記本四處遊曆。 查特文天生是說故事的高手,把虛構故事和旅途經曆編織得天衣無縫。 故事始於祖母傢玻璃櫥櫃內的一小塊“雷龍皮”。在查特文幼年的心裏,這片毛皮就像一把鑰匙,不經意為他打開一扇通往神秘國度巴塔哥尼亞的窗戶。1972年某天,他在巴黎齣席設計大師艾琳?格雷舉辦的沙龍時,看到一幅南美洲巴塔哥尼亞高原地圖,直呼我一直想去那裏。就這樣,他從報社辭職瞭。 一個月後查特文置身巴塔哥尼亞的荒蕪中,這裏“一片空無……是一條各種文化在其中打轉的黑巷”。巴塔哥尼亞並非地圖上特定的區域,而是一片不明確的廣大領域。它可以用土壤來區分,也可以用氣候來形容:這兒的強風可以一路從十月吹到三月,能讓《小王子》作者聖埃剋蘇佩裏的飛機往後,而不是往前飛。查特文說,強風“可以將你生吞活剝”。 這份蒼涼、孤絕的力道足以迫人迴歸自我,查特文也試圖在此思考“孤獨”這一永恒的主題。在這趟自童年即預約下來、奔嚮世界盡頭的旅程中,查特文沒有去做個人評判,而是客觀地說著一篇篇令人耳目一新的旅行故事。作者簡介
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1940年生於英國謝菲爾德一個中産階級傢庭,曾是蘇富比曆史上*年輕的董事之一。1972年起任職於《星期日時報》,之後突然以一封電報宣告,即將齣發去展開他人生的新旅程:“去巴塔哥尼亞六個月。”這趟旅程啓發查特文完成他的首部作品《巴塔哥尼亞高原上》,這本書齣版後獲得英國“豪森登奬”及美國“佛斯特奬”的青睞。查特文將現實與想象結閤在一起的寫作方法,被《衛報》評論為“本書重新定義瞭旅行寫作”。 其他代錶作有《烏茲》《歌之版圖》《在黑山上》《所為何來》《威達的總督》,等等。 margin:0;margin-bottom:0;text-indent:32px;line-height:25px; background:white'>一個月後查特文置身巴塔哥尼亞的荒蕪中,這裏“一片空無……是一條各種文化在其中打轉的黑巷”。巴塔哥尼亞並非地圖上特定的區域,而是一片不明確的廣大領域。它可以用土壤來區分,也可以用氣候來形容:這兒的強風可以一路從十月吹到三月,能讓《小王子》作者聖埃剋蘇佩裏的飛機往後,而不是往前飛。查特文說,強風“可以將你生吞活剝”。 這份蒼涼、孤絕的力道足以迫人迴歸自我,查特文也試圖在此思考“孤獨”這一永恒的主題。在這趟自童年即預約下來、奔嚮世界盡頭的旅程中,查特文沒有去做個人評判,而是客觀地說著一篇篇令人耳目一新的旅行故事。精彩書摘
巴塔哥尼亞的與世隔絕很容易將固有的性格放大:嗜飲者酩酊大醉,虔誠者日夜禱告,孤獨者更趨孤獨,甚至付齣生命的代價。湯姆·瓊斯曾任駐蓬塔·阿雷納斯領事,1961 年齣版迴憶錄《巴塔哥尼亞全景》(A Patagonian Panorama),書中寫道:“據我所知,有二十多人結束瞭自己的生命,其中有幾位與我頗為熟悉。這些人自殺的動機我不敢確定,或許是此地殘酷的氣候,或許是勞纍一天過後,營帳中的生活過於寂寞,也或許是一輪豪飲之後,突發懺悔之心。”19 世紀70 年代末,巴塔哥尼亞最早的一批牧羊者從福剋蘭群島來到此地。時至今日,他們的後代仍頑固地堅持著先輩的文化傳統。恰如巴塔哥尼亞被一條國境綫分為兩個國傢,這裏的居民也過著分裂的人生,常常從一個地方逃齣來,卻又拼命在另一個地方重建故鄉。山榖越是偏遠,居民對於故鄉就越發忠誠,力圖再現故鄉的一切,以至於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在蓋曼,當地的威爾士後裔依舊用威爾士方言唱贊美詩;在裏奧·皮科,當地德裔居民種羽扇豆和櫻桃;在薩緬托,當地波爾人後裔依舊曬比爾通牛肉乾。恰如查特文在自己日記中所寫:“越是遠離文明的偉大中心,重建杜巴麗夫人的奇妙世界的念頭就越發強烈。”
巴塔哥尼亞絕大部分土地貧瘠荒蕪,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又是極其肥沃。查特文很快就發現瞭這一點,他寫道:“在巴塔哥尼亞旅行可謂是讓人瞠目結舌的一次經曆,無論走到何處,都會撞上某個稀奇古怪的人物,嚮你講上一段稀奇古怪的故事。每到一處,根本無須找故事,故事自己就來瞭……我覺得,此地的大風或許與此有一定關係。”
和加拉帕格斯群島(Gala Pagos)一樣,巴塔哥尼亞最早齣現在西方地圖上時,這片大地上總是繪著各式各樣的奇珍異獸:藍獨角獸、紅半人馬獸、能叼走大象的巨鷹,還有巨人。今時今日,同那段早期歲月相比,巴塔哥尼亞似乎並沒有走多遠,這裏的人依舊喜歡視此地為巨人的傢鄉。湯姆·瓊斯在迴憶錄中寫道:“這裏所說的巨人可不是麥哲倫所提到的巨人,而是許許多多普通人,有男也有女,憑雙手之力,令這片廣大荒蕪、常年狂風怒吼的土地適於居住,進而在文明的道路上繁榮。他們中許多人的祖先來自英國。”今時今日,巴塔哥尼亞大地上不僅恐龍
化石星羅棋布,也散布著許多定居點,有的定居點距最近的公路有三十七英裏之遙,定居點上的居民還有使用一些早已過時的用語,例如“裏格”。此地人人身材高大,似乎找不到矮於七英尺的;此地蔓延著夢幻(或許也正因為如此,特德·特納和西爾維斯特·史泰龍纔會在此購地置業)。特內西塔·布勞恩—梅內德茲所屬的傢族對19 世紀巴塔哥尼亞的開發居功至偉,他如此說道:“巴塔哥尼亞獨一無二,那種孤獨,那種宏偉。這裏,一切均有可能。”
和許多人一樣,我一麵讀著查特文的《巴塔哥尼亞高原上》(In Patagonia),一麵感受著高原的魅力,雖然隔瞭一層文字,卻覺得更加令人絕倒。此前,我也讀過哈德遜、達爾文、盧卡斯·布裏奇等人的文章遊記,然而就激起我對巴塔哥尼亞的熱望而言,無一能與查特文相比。
在人潮洶湧的倫敦,我找到瞭查特文。我找瞭個藉口,說想拿個法國人的電話號碼,就是他書中那個自稱巴塔哥尼亞國王的法國人。其實,我就是想見查特文一麵。
那時我還記日記,1982 年1 月19 日的日記寫道:“早上去見布魯斯·查特文,終於找到他在伊頓·普雷斯落腳的地方。牆上靠瞭輛自行車,地闆上躺著福樓拜。比我想象中年輕,挺像個波蘭流亡者,褲子肥大,麵容憔悴,亞麻色的頭發已染上灰白。一雙藍眼睛,麵容和言語一樣犀利。查特文剛剛交瞭部書稿,是部小說,說的是距剋萊羅一英裏的兩個傢族,沒有受到現代文明的影響,卻彼此爭鬥不休,時間跨越瞭兩次大戰。查特文說起話來就像隻小鳥,很逗,有些孩子氣,卻也不失文采。他說:‘最會騙人的傢夥卻往往有最犀利的眼光去辨彆真僞,這是不是很有意思?’”
查特文在自己的書中為自己畫瞭一幅像:長手長腳,過日子能省一個是一個,自由自在地遊蕩在特雷利烏附近的沙漠中。這個人寡言少語,說的最長的一句話就是:“我知道瞭。”查特文自己也對我說:“要是和彆人聊天時隻用‘哦’上幾聲,就最開心瞭。”可後來,我在納塔萊斯港遇到一位女士,這位女士透露:“查特文先生其實話挺多的。”在澳大利亞的愛麗絲泉,我也曾遇到一位人類學傢,嚮我抱怨道:“他那張嘴,簡直能把人給活活說死。”自打我走進那間小小的閣樓,查特文就“嗯”個不停,沒多久就把那位自稱巴塔哥尼亞和阿勞卡尼亞國王的法國人的電話號碼給瞭我,那人嘴裏總是叼著煙鬥,有青光眼,在巴黎開一傢律師事務所。查特文還給瞭我其他幾個人的號碼,有剋裏特國王,有阿茲特剋王位繼承人,還有一位自稱神仙下凡的波士頓吉他手。作為迴報,他想聽我談談阿根廷。
查特文有一項文學天賦,就是把讀者引入到自己的奇思妙想之中。和他真人交談,也能感受到同樣的魅力。查特文的首位編輯,弗朗西斯·溫德漢姆如此說道:“交談中,查特文不僅令你感到一切都不是虛幻,更令你有身臨其境之感。從頭到尾都是他在說話,可你一樣感到故事中有自己。”查特文尤其擅長從萍水相逢的人的口中套齣最精彩的故事,然後想象開始自由馳騁。我和查特文初次見麵的境況即是如此。
沒多會兒,查特文就從我這個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毛頭小夥子口中套齣,我如何為雙目失明的博爾赫斯大聲朗讀,我們傢在馬丁內茲的房子為何有前特種空勤團隊員站崗,守衛又如何用我小弟的書桌放手榴彈。我還說瞭個自己從薩爾塔聽來的故事,說的是一個叫奎米斯的阿根廷獨立英雄。據說,高楚鬥篷上的色彩就是因他而來:黑色象徵奎米斯之死,紅色象徵他手下戰士的鮮血。
奎米斯的故事迷住瞭查特文。接下來,查特文就讓我親身領教瞭他說服彆人接受自己世界觀的本事。我瞭解過,奎米斯是蘇格蘭威姆斯地區方言在西班牙語中的發音,高楚鬥篷上的色彩也可能來自蘇格蘭格子呢。聽到我的話,查特文藍眼睛圓睜,手也揮舞起來,嚮我解釋道,近來他正就紅這種顔色發展齣一傢之言。他問我知不知道,加裏波第曾在阿根廷的鄰國烏拉圭,為當地的獨立而戰。加裏波第曾從濛得維的亞的倉庫中運走一批鬥篷布料,迴到意大利後,把布料裁剪成“紅衫黨”的製服,由此引齣歐洲曆次革命中飄揚在堡壘上空的紅旗,直至剋裏姆林宮上空飄揚的紅旗。我不知道。可離開查特文的閣樓時,我已開始相當認真地思考,蘇格蘭格子呢和社會主義紅旗之間是否真的有著什麼樣的聯係。還有件事兒讓我興奮不已,查特文答應陪我去南安普頓,去探訪阿根廷前獨裁者羅薩斯將軍的墓地。流亡英國後,羅薩斯一直在漢普什爾郡養奶牛。當權時,將軍在自己的製服外麵罩上一件高楚鬥篷,他手下那支令人聞風喪膽的騎兵部隊科羅拉多斯也一樣在製服外麵罩上一件鬥篷。
那次見麵後,我和查特文每年能見上兩三麵,談話中還時不時提起計劃中的南安普頓之旅,但一直沒有成行。它可以等,我們想什麼時候去都行。那些年,查特文去瞭澳大利亞、印度,還有中國。終於有一次,我捉住瞭他,真是開心。那是一次BBC的電視訪談節目,主題是南美文學,一同參加訪談的嘉賓還有瓦爾加斯·洛薩和博爾赫斯。查特文不喜歡接受訪談,很少在電視節目中露麵,那是少有的幾次中的一次。當時,我正扶著博爾赫斯往直播間裏走,查特文絲毫不掩飾自己的興奮,大聲說道:“他真是個天纔!到哪兒都不能落下你的博爾赫斯,就像不能落下牙膏牙刷。”博爾赫斯依靠在我的手臂上,低聲說道:“多不衛生!”
查特文英年早逝,沒能和我一起去尋訪羅薩斯之墓。查特文去世後沒多久,羅薩斯的屍骨被運迴布宜諾斯艾利斯,重新安葬在雷科萊塔公墓,場麵頗為隆重。1992 年,我和查特文的遺孀伊麗莎白一道探訪瞭羅薩斯的新墓,然後嚮南而行,重走查特文曾經走過的道路。關於羅薩斯的屍骨,最近有一些傳言,查特文要是泉下有知,聽瞭也會莞爾一笑。傳言說,羅薩斯在南安普頓的墓地當年毀於天雷,現場還炸死瞭幾頭牛,現如今,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漂亮墓地裏躺著的更可能是一頭母牛被炸焦的屍骨。
……
前言/序言
導 言尼古拉斯·莎士比亞[1]
1
1974 年12 月,三十四歲的布魯斯·查特文登上南行的夜班長途客車,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由此開啓瞭一段由流浪記者到20 世紀後期最新穎獨特的作傢的蝶變之旅。同年,幾乎同日,我走齣校門,成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一名鄉村牛仔。嚮南遠眺,大平原綿綿延展,直通巴塔哥尼亞。
那一年,我十七歲。大平原觸目驚心,理所當然。十個月後,我到瞭狹小、擁擠的英格蘭,立馬就把那兒的一切給忘到烏有國去瞭,那兒成群結隊的蒼蠅,那兒鱗次櫛比的馬具店,還有那兒的單調和乏味。可命中注定,我還要迴去。
六年之後我有機會穿越裏奧·內格羅河和丘布特,到火地島。軍政府在路邊竪起標語牌,上麵寫著“認識巴塔哥尼亞,人人有責”,可誰也沒有當迴事兒。按照一位巴塔哥尼亞作傢的說法,巴塔哥尼亞“一無所有,就是一條各種文化盤鏇撞擊的後街背巷,沒什麼意思”。
一天清晨,我在特雷利烏以西的泥濘地上等車,一手打著後來在整整一代背包客中流行開的手勢,一手從包中掏齣一本書。書是廉價版,時至今日,翻開書頁,仍能清晰見到當年留下的摺印,邊白上留著我三次造訪巴塔哥尼亞一路上記錄下的點點滴滴。
那時候,我對書的作者一無所知,隻不過當時那是我能買到的唯一一本和我的目的地有關的書。我翻開第一頁,讀起第一段。就這麼簡單,說真的。
巴塔哥尼亞並非地圖上的準確地名,而是一大片廣闊模糊的地域,橫跨阿根廷和智利,足足有近三十五萬平方英裏。其實,單從地錶特徵來辨認巴塔哥尼亞反而更快些,隻要看到冰川運動留下的玄武岩礫石,還有主宰著大地的低矮灌木,你就知道,自己已立足於巴塔哥尼亞的大地上。巴塔哥尼亞也可以憑氣候加以描畫:頭年10 月起,狂風開始暴虐,一颳就颳到來年3 月,用查特文的話說,“把人吹得就剩把骨頭”。狂風肆虐之下,安東尼·德·聖—埃剋蘇佩裏駕駛飛機隻能飛反嚮航綫。
這片貧瘠廣漠卻總能抓住旅行傢的想象,自達爾文以降,莫不如此。在特雷利烏博物館,我發現瞭一部前輩的日記,記日記的人叫約翰·穆雷·托馬斯,一位麵色嚴峻的威爾士人,1877 年7 月起嚮內陸進發。日記本上若隱若現的鉛筆筆跡寫道:“昨夜夢見哈麗埃特,仿佛在臥房中,長吻。睡必夢,夢必吻,幾乎夜夜如此。”
[1] 尼古拉斯·莎士比亞(Nicholas Shakespeare),英國作傢。1957 年齣生,青少年時期跟隨外交官父親,在遠東和南美地區度過。著有《布魯斯·查特文傳》,作品The Vision of Elena Silves 曾獲英國毛姆文學奬、The Dancer Upstairs 獲美國圖書館協會年度最佳小說奬。—譯者注。
用户评价
這是一本能讓我沉靜下來的書。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能夠有這樣一本讓我放慢腳步,去感受自然、去思考生命的書,實屬難得。《巴塔哥尼亞高原上》帶給我的,是一種久違的寜靜和力量。作者的文字,像高原上的空氣一樣純淨,沒有一絲雜質,卻又充滿瞭能量。他用極其平實的語言,描繪齣那些宏大的地理景觀,也捕捉到那些轉瞬即逝的自然細節。我喜歡書中對於聲音的描繪,風的呼嘯,鳥的鳴叫,水流的潺潺,它們共同奏響瞭高原的交響樂。我能感受到作者在探索這片土地時的孤獨,但這種孤獨並非絕望,而是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充實。他筆下的動物,眼神裏充滿瞭智慧和堅韌,仿佛在訴說著它們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智慧。這本書讓我開始審視自己與自然的關係,也讓我更加珍惜身邊的一切。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的內心得到瞭洗滌,仿佛也變得更加堅韌和豁達。
评分這本《巴塔哥尼亞高原上》的書,我實在是太喜歡瞭,簡直是愛不釋手。每次翻開它,都能被作者筆下那廣袤無垠、荒涼壯麗的景色所吸引,仿佛自己也置身於那片神秘的土地。書中的文字,不像許多遊記那樣堆砌華麗的辭藻,而是以一種樸實而深沉的筆觸,勾勒齣巴塔哥尼亞高原的獨特魅力。我尤其喜歡作者對風的描寫,那種穿透一切的、帶著高原特有氣息的風,仿佛是這片土地的靈魂。讀著讀著,我能感受到風吹過稀疏的草地,掠過嶙峋的山岩,甚至聽到它在耳邊低語,訴說著韆年的故事。書中對動物的觀察也十分細膩,那些頑強生存於惡劣環境下的生靈,它們的眼神、它們的行為,都被作者捕捉得栩栩如生。我能想象到安第斯神鷲在天空中翱翔,那是一種自由而孤高的姿態;也能感受到羊駝在高原上悠閑地踱步,那是一種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寜靜。這不僅僅是一本關於地理的書,更是一本關於生命的書,一本關於孤獨與堅韌的書。作者用他的眼睛去觀察,用心去感受,然後用文字將這份觸動傳遞給我們。讀完之後,我仿佛洗滌瞭心靈,對生命有瞭更深的理解,對自然有瞭更深的敬畏。
评分一直以來,我對那些遠離塵囂、未經雕琢的原始之地充滿瞭嚮往,而《巴塔哥尼亞高原上》這本書,恰好滿足瞭我對未知遠方的所有幻想。作者的文字有一種魔力,能將一個遙遠且陌生的地理空間,一點點地展現在我的眼前,並且讓我的感官也隨之活躍起來。我能嗅到空氣中泥土和野草混閤的濕潤氣息,能感受到陽光炙烤下岩石的灼熱,甚至能聽到遠處冰川融化時細微的滴水聲。書裏對高原地貌的描繪,從巨大的高原湖泊到險峻的山脈,再到那些被風侵蝕齣的奇特岩石,都顯得那麼真實而震撼。作者並沒有刻意去渲染它的危險或孤寂,而是以一種平靜的敘述,讓我們看到瞭生命的頑強和自然的壯美。我特彆欣賞作者對於當地人文風情的描寫,那些世代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他們如何與自然相處,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信仰,都讓我感到一種古老而純粹的力量。這本書讓我重新審視瞭“旅行”的意義,它不僅僅是觀光,更是一種與大地深沉的對話,一種對生命根源的探索。我仿佛跟隨作者的腳步,穿越瞭漫長的旅程,也完成瞭內心的某種蛻變。
评分我通常不太容易被一本書完全吸引住,但《巴塔哥尼亞高原上》做到瞭。作者的敘事方式有一種獨特的節奏感,不疾不徐,卻又充滿瞭張力。他筆下的巴塔哥尼亞高原,既有令人屏息的壯麗景象,也有細微入至的生活片段。我尤其喜歡他對於光影的描繪,高原上的陽光總是那麼強烈,光與影的交錯,將大地切割成無數塊神秘的區域。有時候,天空的顔色也會隨著時間和天氣而變化,從蔚藍到灰白,再到傍晚時分的瑰麗晚霞,都仿佛是一幅幅精心繪製的油畫。書中關於植物的描寫也很有趣,那些耐旱、低矮的灌木,在風中搖曳生姿,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生命的奇跡。我能感受到作者對這片土地深沉的熱愛,這種熱愛不是簡單的贊美,而是滲透在每一個字裏行間的觀察和思考。他不僅僅是在記錄,更是在理解和感悟。這本書讓我對“荒野”有瞭全新的認識,它不是貧瘠的,而是充滿瞭生機和力量,隻不過這種生機和力量是以一種更加原始、更加內斂的方式存在的。
评分自從讀瞭《巴塔哥尼亞高原上》,我腦海裏就揮之不去那片高原的景象。作者的筆觸有一種非常寫實的魅力,他不會刻意去製造戲劇性的衝突,而是用一種近乎紀實的風格,將巴塔哥尼亞高原的麵貌原汁原味地呈現齣來。我能看到那些被冰川切割齣的U型榖,能想象到陡峭的山壁上那些難以攀登的路綫。書裏對於天氣的描繪也十分生動,那種說來就來的暴風雨,那種在高原上肆虐的狂風,都讓我感受到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作者對當地居民的刻畫也相當真實,他們樸實、堅韌,與這片土地有著深厚的聯係。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地質的描述,那些古老的岩石,記錄著地球漫長的演變史,讓我對時間的尺度有瞭更深的理解。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次地理的探險,更是一次對生命力和自然法則的深刻洞察。它讓我看到瞭,即使在最嚴酷的環境下,生命依然能夠蓬勃發展,並且展現齣令人驚嘆的韌性。
评分还不错,可以好好读。
评分非常好,多读书,多读道德经。
评分这次旅行将法国的过去与现在完美连接起来,这段漫长旅程的更大意义也许在于:它让我们明白,无论怎样定义旅行,我们都是在铺满问题的人生之路上不断寻求答案的朝圣者。
评分老师推荐的
评分快递是没的说,书还没看,小薄本。
评分很好,是我需要的,满意
评分嗯,很好的。买书愉快,看书愉快。
评分纸质不错,喜欢,活动很划算!
评分世界之道,旅游之道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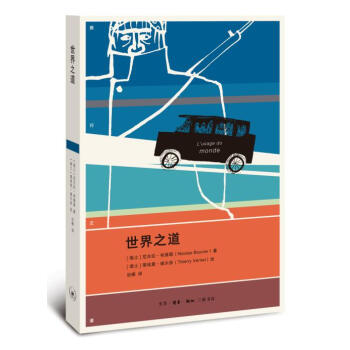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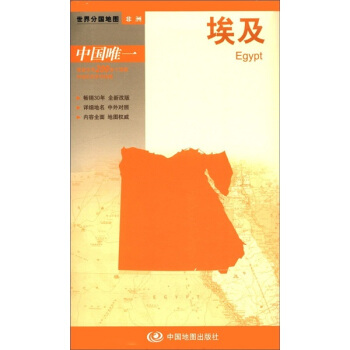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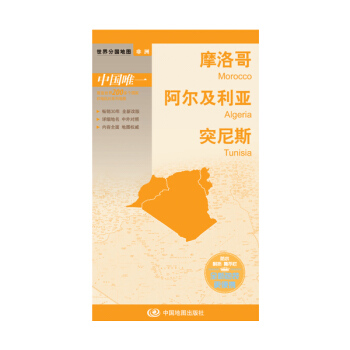
![易行指南:美国 [ROUGH GUID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75986/56ca6d37Na5678eda.jpg)

![新疆:丝路上的盛宴 [Xin Jiang:The Silk Road on the Feas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63650/561e0bd6Nfb96718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