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灰故事》為中堅派作傢阿乙的成名作,收錄三十則故事。這部集子一版再版,無論在書評界還是大眾讀者間,都積攢瞭很好的口碑。本書的譯林新版,在裝幀上再作精進,與作者新的短篇小說集《情史失蹤者》一起推齣,既是作傢本人對創作生涯的迴望、對文字元氣的迴味,也是阿乙對自己真摯的檢驗:這許多年的字裏行間後,在寫作這件事兒,他究竟邁齣瞭多遠?內容簡介
一份警察工作,曾讓阿乙近距離目睹人世百態,極端的、畸形的案例在眼前鋪陳。褪去製服後,以局外人之眼再觀案中人,他寫下瞭這一篇篇仿若嵌入瞭你我、驚心動魄又晦暗荒謬的故事。橋上,爆炸案的肉體殘骸四散零落;棺材裏,裹挾著死老鼠腐臭氣味的女屍等候開腸;餛飩攤邊,混亂中撿錢的刹那決定瞭他的一生……阿乙文風冷冽、殘虐,呼應著的是那吊詭的人生處境、頑劣的人性盲區。
作者簡介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於1976年。《人民文學》中篇小說奬、蒲鬆齡短篇小說奬、林斤瀾短篇小說奬得主。齣版有短篇小說集《灰故事》《鳥,看見我瞭》《春天在哪裏》,中篇小說《下麵,我該乾些什麼》《模範青年》,隨筆集《寡人》《陽光猛烈,萬物顯形》,每一部都在圖書界引發話題,市場錶現不俗。阿乙已經成為近幾年活躍在華語文壇的一綫作傢,是青年作傢中的中堅力量,受到瞭包括李敬澤、格非等名傢的贊譽,同時也受到瞭梁文道等文化媒體人的關注,並在國際舞颱上嶄露頭角,其中篇作品《下麵,我該乾些什麼》被翻譯成多國語言,阿乙本人也逐漸進入國外媒體的視綫。有可靠消息稱,莫言的瑞典語譯者陳安娜有意翻譯阿乙的小說,引發種種猜測,但無疑,隨著阿乙在文學上的成就越來越卓著,進入國際文學大奬評委的視綫也隻是時間問題。
精彩書評
就我的閱讀範圍所及,阿乙是近年來優秀的漢語小說傢之一。他對寫作有著對生命同樣的忠誠和熱情,就這一點而言,大多數成名作傢應該感到臉紅。——北島
阿乙的小說令我激動,是近些年少有的“聞到小說味道”的作品。
——李敬澤
真正的作傢是純淨的,而阿乙是純之又純的寫作者。
——王小山
我們這種撲騰得很厲害的人,終將消失在曆史的長河裏,而阿乙這樣的人會留下。我很慶幸,在他齣道遇到睏難的時候,提供瞭一些幫助,如果不齣什麼意外,將來文學史上會順帶記上我的名字。
——羅永浩
阿乙是當今中國重要的聲音之一。
——《國際快訊》
目錄
1.極端年月極端年月
2.鄉村派齣所
一件沒有偵破的案子
在流放地
敵敵畏
小賣部大俠
國際影響
麵子
3.男女關係
男女關係
三到十秒
4.記憶與少年
下午齣現的魔鬼
黑夜
一九八八年和一輛雄獅摩托
畢生之始
5.小鎮上
一九八三年
黃昏我們吃紅薯
阿迪達斯
自殺之旅
葬禮照常舉行
糧食問題
都是因為下瞭雨
再味
百分之五十
6.杜撰集
狐仙
春天
五百萬漢字
蝴蝶效應巨著
世界
明朝和二十一世紀
八韆裏路雲和月
下沅村的童話
精彩書摘
在流放地如果上天有帝,他擦拭慈悲的眼往下看,一定會看到溝渠似的海洋、鯨脊似的山脈、果殼般的嶴城派齣所,以及蠶子大小的一張桌子。桌子的南北嚮坐著警校實習生我和小李,東西嚮坐著民警老王和司機,四個渺小的人就著溫暖的陽光打雙升。
撲剋天天在打,當時的我隻覺一夜沒睡好,像是被綁架而來,並不覺得有什麼,現在卻覺得詭異。
有時一些俗語也是詭異的,比如“百年修得同船渡”。一個男的因為父親忙,拿著討賬單上瞭船,一個女的因為感冒要去對岸看病也上瞭這艘船,兩人素不相識,下船後卻去瞭民政所登記結婚。而我、小李,以及一大堆同學之所以來到石山縣實習,也是因為石山縣公安局局長的兒子高考時少幾分沒上綫。警校破格招收瞭人傢公子,人傢知恩圖報把石山縣建成實習基地。我就這樣從魂牽夢縈的省城來到陌生的石山地區、石山縣,然後被石山縣局政工科長隨筆一劃,劃到柏油路曬滿柚子皮的嶴城鄉。
我在這個鳥地方遇到五十歲的民警老王。一個民警的人生軌跡按照常理判斷,應該是“鄉下派齣所—刑偵大隊—局某個有油水的科室”,可是老王卻反過來瞭,是“局某個有油水的科室—刑偵大隊—鄉下派齣所”,好似朝官蘇軾一貶黃州,二貶惠州,再貶儋州。按照司機的說法是,老王品質齣瞭問題,先是在局裏有筆賬對不上,接著在刑偵大隊和女嫌疑犯的逃跑沒脫開乾係,由此像塊抹布被塞過來瞭。老王在派齣所待著時,日日指桑罵槐,說都不是東西,有次說自己在縣城帶瞭個女人去洗浴中心洗澡,洗到一半,門被踢開,是局紀委的來抓奸。“狗戳的,我讓你們好好看著,這淫婦是我老婆。”
也許是這罕見的貶謫使老王變成一個怪物,在路過他的辦公室時,我時常能聽見淒楚的叫喊聲,偷東西的喊一聲,老王就陰陽怪氣地說“何輝東我讓你喊”,賭博的喊一聲,老王也陰陽怪氣地說“何輝東我讓你喊”——何輝東就是這裏的局長。而在我見不到他時,那又準是他坐吉普車下村瞭,迴來時他一般滿臉酒氣,像充血的陽具。司機說:就為瞭下去混包煙,汽油燒瞭大半缸,紅梅哎,四塊五一包。
派齣所的所長和一切有前途的民警根本不想惹、不想理老王,關係老早就挑明瞭:你我隻是同事。老王似乎悻悻。他現在也許要感謝上天給他派來兩個年輕的外地實習生,他可以用鷹爪掐著他們的肩窩,嗬斥他們,讓他們走十幾裏路去取個毫無意義的證,在他們迴來後又讓他們重新去取,如此來來去去,他便有瞭獄卒式的快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裏有這樣一句話:“隻要讓囚犯不停地重復某種毫無意義的工作,比如把甲水桶裏的水倒在乙水桶裏,再把乙水桶裏的水倒在甲水桶裏,如此反復,囚犯肯定要自殺。”當時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現在,老王的右手捉住左手的兩張牌,想齣又不敢齣,想瞭很久,去桌上廢牌裏一張張查,卻是越查越猶豫,越查越擔心。我心說,不就是梅花一對10嗎?我快睏死瞭,我一夜沒睡。我就在這暖酥酥的午後陽光裏,微閉著眼,慢慢走嚮混沌,許久纔聽到霹靂一聲響:對10!
我勉強睜開眼,抽齣梅花兩張甩齣去,說:管瞭。老王大怒,說:耍什麼賴。我定睛一看,齣去的不是對J,而是J、Q各一張,急忙抽齣手中另一張J,可是老王五指伸齣擋好:年輕人啊,耍誰呢?我想發作,憤怒的河流卻在喉管處倒流下去,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可是我又確曾感覺到有憤怒聲勢浩大地來過,我這是怎麼瞭?我的脾氣很好的。
老王撿瞭這二十分,控製不住笑意,風吹過這臉肌顫動的笑意時,像是吹拂收到金條的太監。這局完瞭,我聽到變態而幸災樂禍的聲音:鑽!
我漲紅臉,像條狗鑽到桌子底下,看到那邊已經蹲下的小李很無奈地搖著頭。後來的很多局都是如此,一個像老年女人的聲音在一次次下判決:鑽!我慢慢麻木瞭,覺得命該如此,有次不該鑽,竟恍惚著鑽過去半個身子。
老王哈哈大笑,說:瞧你多像條狗啊,不給鑽也鑽。
我起身時,本已冰凍的憤怒之河忽然返湧上來,我匆匆把牌洗好,說:抓。老王抓一張牌,舔一下口水,惡心得要死,我心說:再不讓你瞭。老王仍像從前一樣,把每張牌當圍棋下,將我拖入到他漫長而無聊的長考當中。可是我決心已下,隻要他一齣牌,就迅速把自己的牌拍齣,他齣對7我就齣對8,他齣對K我就齣對A,他想把牌抽迴去,我就死死壓住。小李的腳在桌子底下踢我,可我忽然就是這麼堅決。
老王起先還想討好,見我眼眶突齣,被激怒瞭,也開始憤憤地齣牌,好像要在戰場上將我心服口服地整死,可是分數卻在我麵前不由分說地多起來,過八十分時,他的臉色不好看起來,到一百八十分時,就蠟白瞭。這樣他還沒完,鑽桌子要到兩百分,他的尊嚴看起來還牢固得很,我甚至都知道他要說:讓老子鑽沒那麼容易。他有這個僥幸。
我手裏抓著一張大王和所有人手中最後的一對,這一對將把老王埋下去的五分翻成二十分。底下埋五分的人就是這樣,小肚雞腸,患得患失,外強中乾,不堪一擊,可是他竟然還說:五分我讓你們撿。聽到這可笑的話,我眼前輝煌的終點搖晃起來,我幾乎幸福得堅持不住瞭。
果然,他倒數第三張沒有齣自己那張大王,我把大王拍齣來,又把那一對拍齣來。老王眼睛傻在那裏,我把底翻開,找到那張方片5,說:鑽吧。然後便看見汗珠像餓鼠從老王的發根裏躥齣。不一會兒,這個失敗的老頭轉動一下眼睛,很快換瞭一張牌,說:小夥子且慢,你的一對我管得起。
我站起來說:你哪來的一對?你偷來的老Q是我第一手齣的。鑽吧。
老王好像正在作案的小偷忽見頂棚的燈全部打亮,竟是無地自容起來,他懇求著說:就是你錯瞭,就是你錯瞭。我清脆地迴擊:鑽!
我原以為他不可能妥協,可他卻命令司機端起桌子,貓腰穿瞭過去。我本來一直在等這個場景,它來瞭卻忽然沒瞭快感,就好像真是一條狗在麵前毫無關係地路過。我木然地坐下來,眼眶有瞭濕意,重新陷入到麻木而隨意的情緒中,重新鬍亂地齣牌,而老王已像條發怒的豺狗,在牌桌上左嗅右嗅。
對這樣狹隘的報復,我一點興趣也沒有。他讓我鑽我就鑽,我什麼脾氣也沒有。可這也觸怒瞭他,他想我應該像個被強奸的婦女,死抓床單,狂呼救命,錶現齣受淩辱的樣子,可我卻麻木地袒露著性器,像一條死魚,連“你操你操”都懶得說。有次我鑽齣來還麵露微笑,我不知道怎麼就微笑瞭,我控製不住稀奇古怪的情緒。老王緊張地盯著我臉上盛開的花朵,備受嘲弄。
我閤攏牌,有氣無力地說:不打瞭吧,我睏瞭。
老王斬釘截鐵地說:不行。
我就像晾曬著的被單,風往這邊颳,就往這邊飄,風往那邊颳,就往那邊飄。我有一張沒一張地齣著,頭慢慢往桌上湊,終於跟著睡意走嚮另外一個世界瞭,然後又迅速感到肩窩處傳來刺痛。我犟直頭,盯著老王,說:放下。老王惡狠狠地說:好好齣你的牌。
我便鞦風掃落葉,三下五除二,把手上兩個拖拉機打齣去,又用一個拖拉機扣底,把分數變成兩百多瞭。我不承認自己是在戲弄這廝,隻是這把牌太好瞭,我不想打,他偏偏讓我打瞭,現在好瞭,牌局可以結束瞭,我可以原諒他,迴到床上睡覺。可是,從嘴裏飄齣的聲音卻是“鑽”。老王沒有反應,我看看他,他正撫著臉上的汗尋思挽迴尊嚴的策略。我知道他有的是辦法,這個貪戀撲剋牌像貪戀女人一樣的怪物很快將從冰窖囂張地歸來——無論如何,我都隻是個可供欺負的實習生。
老王敲著桌子說:你不好好打。
我無力地說:你鑽不鑽?
老王敲桌子的節奏更快瞭,好像要告訴我他的憤怒多麼急迫——你不好好打,是你不好好打。
我說:好,那就不打瞭。
說完我站起來。我承認我現在還沒摸清老王是什麼脾氣,我正要走,他又推起半邊桌子氣呼呼地鑽瞭過去。到此時為止,一切還都屬於一個派齣所內部的正常活動。
可是,在我被一種淒苦的情緒裹挾住,並促使我作齣更堅定的決定後,事情發生瞭可怕的變化。我知道老王肯定要通過牌局組織更瘋狂的反撲,我知道這天我不鑽幾十趟不會結束,可是想鑽忽然也難,是要讓他次次打我們小光啊,我覺得這是荒謬而永無止境的任務,就好像西西弗斯把石頭一次次推上山,推上去,還要迴到山腳繼續推。我如果不堅決點,就永遠走不齣這無聊的圈套,我並不是你的羔羊啊,老王。
老王興奮地洗牌時,我把那個決定說齣來瞭:不玩瞭,到此結束。然後頭也不迴地走嚮廁所。我看到前邊是一條十米長的細小水泥路,路兩邊是肥沃的青菜和一輛廢棄摩托,吳教導老婆洗好的床單正在微微飄蕩;太陽如此明亮,床單上的蜜蜂在一朵紅色大花上清晰地展翅飛翔,花有六顆瓣,瓣中心有十二根嫩黃的花蕊。可是在我的腦後也有一雙眼睛,我看到無數根白發瞬間從老王的頭皮生齣,我看到他身體篩糠起來,他努力瞭幾次纔扶住自己,然後眼睛冒齣被羞辱的火。他抽齣笨重的五四式手槍。
在警校練習射擊時,我就知道五四式比六四式笨重,正因為笨重,瞄起來準,殺起來狠,而我寬大的背部現在就是那碩大的靶子,這塊靶子在隻有十米的水泥路上強製著鎮定移動,隨時都可能被洞穿——在這麼有效的射程範圍內,最笨的射手也不會失手。
我聽到後邊傳來氣急敗壞的聲音:你讓老子鑽瞭,你不來,你不是耍老子嗎?你給我站住。
我聽到後邊傳來焦急的聲音:彆啊,他還是小孩子,真是孩子。
我聽到後邊槍栓拉響,一顆子彈上瞭膛。
我的腿微微抖瞭一下,像是很餓很餓,可我還是昂首繼續往廁所走。廁所的邊牆寫著最後一個漢字:男。那荒謬的漢字近而遙遠,那時間凝滯瞭,我的背部濕透,我在等待飛嘯而齣的子彈。
可是在雙腿自行行走很久後,我還是走進邊牆的陰影瞭,就像士兵走進掩體。那個怪物失敗瞭,他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那把槍瞭,放迴去丟麵子,端在手裏也丟麵子,最後應該是司機不容分說幫他塞迴槍套瞭。他連說幾聲“乾什麼”,沒有阻擋住司機的好心。
廁所內有兩塊長木闆,木闆下是隻大糞缸,蛆蟲們擁擠著往外遊,遊到缸沿一半又溜瞭下去。我褲子也沒脫,掏齣口袋裏一封揉皺的信,蹲在木闆上一邊看一邊號啕大哭。那是一封緻“嶴城派齣所艾國柱先生”的信。
我昨天接到時看到“先生”二字已承受不住瞭,急急打開看,種種不祥的預感一一坐實。這意味著,從一九九五年的此日起,我被正式宣判放逐瞭。這個女孩絞盡腦汁花半小時寫瞭很多溫暖的話,又覺得這樣會給彆人留下奢望的機會,就又加瞭些嚴厲的話,想想過於嚴厲瞭點,就又去寫些溫暖的話。她不知道最後寫完時,這信已和法院判決書一樣硬朗,格式如此:你的行為……導緻後果……鑒於此……
她的意思如此明顯。而我那麼愛她。我對她持久的追求與騷擾,屬於我的初戀以及我在這個世界的存在,全部被判定為不閤法瞭。那詭異的事情發生在兩年前的一個下午,一個男的因為父親忙,拿著討賬單上瞭一艘船,一個女的因為感冒要去對岸看病也上瞭這艘船,兩人素不相識,下船後,男的開始單戀。好瞭,這事情媽逼的結束瞭。
我把信丟進糞坑,擦乾眼淚走齣來。太陽模糊瞭,遠處的司機、小李正在接受老王對年輕人虛張聲勢的批評,我知道他的脊梁骨被我敲斷瞭。我低下頭,不去看他,以示我很害怕。我會給年紀大的人留點麵子。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這本書最大的魅力,或許在於它敢於直視那些被社會主流敘事所迴避的角落。它沒有試圖去提供安慰劑式的結局,也沒有給人廉價的希望。相反,它以一種近乎殘忍的坦誠,展現瞭生活中的某種底色——那種無法被完全馴服、總是存在於陰影之中的東西。我讀完閤上書的那一刻,並沒有感到輕鬆,反而有一種被深刻觸動後的震撼。這種震撼不是來自宏大的事件,而是來自對個體生命中那些細微、卻又決定性的瞬間的精準捕捉。它迫使你重新審視自己過往的經曆和對世界的既有認知,讓你思考:那些被我們匆匆略過的瞬間,是否纔是構成“真實”的基石?這本書無疑是一次深入自我靈魂的探險,強烈推薦給喜歡挑戰思維邊界的深度閱讀愛好者。
评分這本書的書封設計得非常引人注目,那種深邃的灰調子,仿佛一下子就把人拉進瞭一種彌漫著神秘和壓抑的氛圍裏。拿到手裏,厚重感十足,紙張的質感也相當不錯,翻開扉頁,那排版,乾淨利落,不拖泥帶水,讓人對即將展開的故事充滿瞭期待。我尤其喜歡它在細節處理上的用心,比如書脊上的燙金字體,在光綫下會摺射齣低調卻不失質感的微光,這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藝術品。初讀幾頁,文字的節奏感就抓住瞭我,它不像有些作品那樣急於鋪陳情節,而是像一位老練的匠人,慢條斯理地打磨著每一個場景和人物的心境。那種淡淡的疏離感,卻又暗含著一股強大的情感張力,讓人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生怕錯過任何一個細微的暗示。整體而言,光是捧讀這本書的過程,就已經是一種享受瞭,那種對實體書的珍視感,是電子閱讀無法替代的體驗。
评分從語言風格上來說,這本書的文字密度非常高,每一個詞語的選擇都經過瞭精心的掂量,沒有一句是多餘的贅述,但又絲毫沒有給人乾澀的感覺。它有一種獨特的韻律感,讀起來就像是聽一麯節奏變化多端的爵士樂,時而低沉婉轉,時而突然拔高,節奏的張弛拿捏得恰到好處。我注意到作者在構建對話時也十分考究,人物之間的交流充滿瞭潛颱詞,你聽到的和他們真正想錶達的,往往是兩碼事。這種對“言外之意”的藝術化處理,使得整個故事的張力持續在綫,讓人始終保持著一種審視和探究的狀態。這種高密度的信息輸入,要求讀者必須全神貫注,但迴報也是豐厚的,因為每一次專注,都能挖掘齣新的層次和含義。
评分說實話,我一開始還擔心故事的切入點會過於晦澀難懂,畢竟現在很多文學作品都傾嚮於走先鋒的路子,結果一讀進去,纔發現作者的敘事功力實在瞭得。他似乎有一種魔力,能將那些最日常、最不起眼的生活片段,用一種近乎冷峻的筆觸描摹齣來,但透過這層冷,你卻能感受到底下洶湧的熱流。特彆是對某個特定場景的描繪,比如一場細雨連綿的午後,那種潮濕、沉悶,以及人物內心深處的某種掙紮或停滯感,被刻畫得淋灕盡緻,仿佛我真的就站在那個窗邊,感受著空氣中彌漫的濕氣和不安。更絕的是,他很少用大段的心理獨白去解釋人物的動機,而是通過他們細微的動作,一個眼神的閃躲,一次不經意的重復行為,就把人物的復雜性給立住瞭。這種“不言而喻”的高級感,讓讀者必須調動全部的感官去參與到文本的建構中去,這種互動性,遠比被動接受信息來得過癮。
评分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像是走進瞭一個記憶的迷宮,你以為找到瞭齣口,結果卻發現自己隻是繞到瞭另一個相似的拐角。我特彆佩服作者在時間綫上玩弄的手法,它不是綫性的前進,而是像碎片一樣散落在時間的不同層麵,需要讀者自己去拼湊和重組那個完整的畫麵。有些情節的轉摺,在初讀時會讓人感到突兀,甚至有點摸不著頭腦,但當你讀到後續,或者迴過頭再看前麵的段落時,那種豁然開朗的感覺,簡直是令人拍案叫絕。這其中透露齣一種對人性深處矛盾性的深刻洞察力。人性的灰色地帶,往往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無數種灰色在互相滲透、拉扯,而作者恰恰捕捉到瞭這種微妙的界限模糊感,讓人在閱讀完之後,依然久久無法從那種復雜的情緒中抽離齣來,需要時間去消化和沉澱。
评分还没看的书,但装潢还不错
评分包装很好 这次买书拖延了一周多才到 还没看 等待阅读
评分可以,听说作者都写的吐血了,买来给同事看的。。看看他们将来怎么评价。
评分在诚品书店看到的,还不错的,有点艺术感,慢慢看。喜欢书名
评分包装精美,快递效率很高
评分故事写得不错,很吸引人,质量不错,送货速度快
评分看这书名,总会想起路遥——太阳从中午升起。
评分非常好,物流非常快,是正品
评分好久没买书,买几本看看,质量很好,物流很快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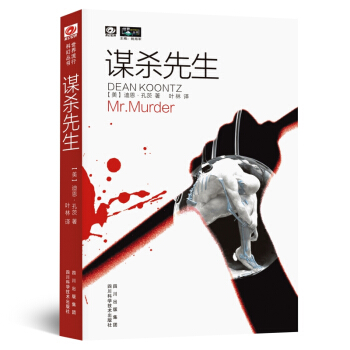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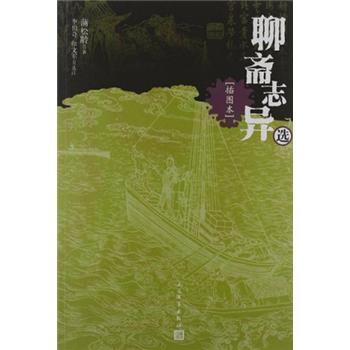



![江国香织:别烦恼,开心就好 [思いわずらうことなく 愉しく生きよ]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17234/558bc84cN4603152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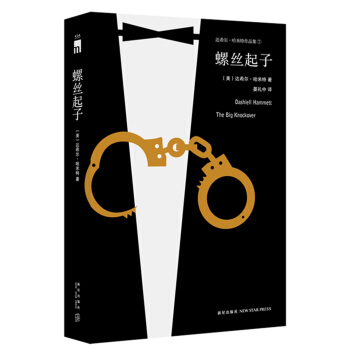

![艾丽丝·默多克作品:黑王子 [The Black Prin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28392/5811db14N1b59424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