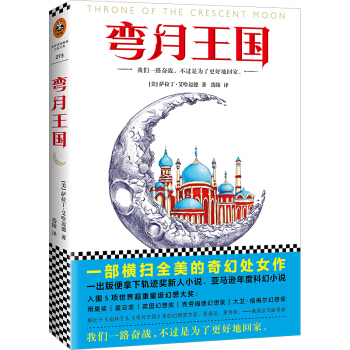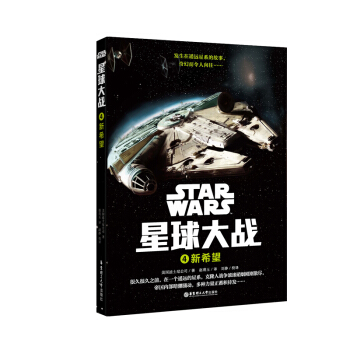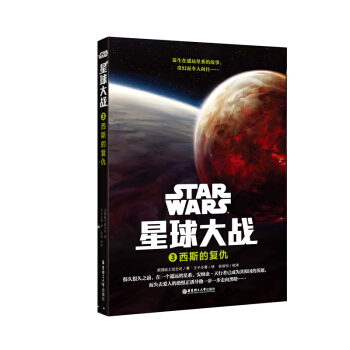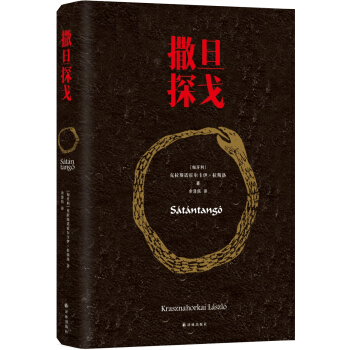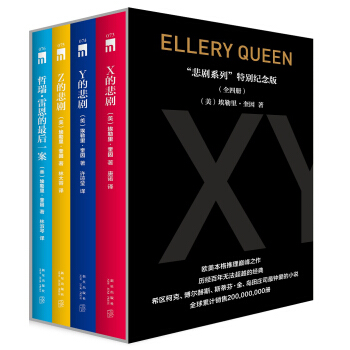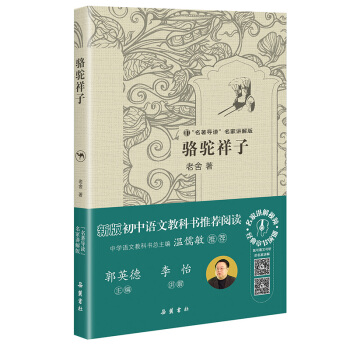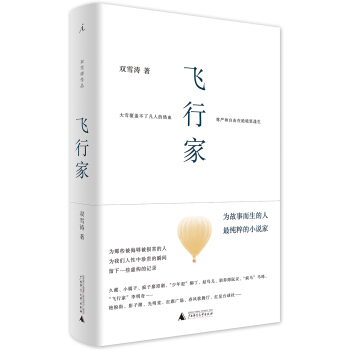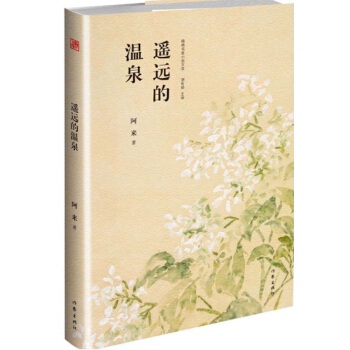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茅盾文學奬得主阿來經典代錶作,曾被譯為等十數種外國語在海外齣版
★精典名傢小說文庫係列小說之一。精裝版本,著名畫傢何水法提供封麵及圖書插畫,並特製精美藏書票,集文學與藝術於一體,兼具經典性和收藏性
★名傢+名作+名畫,中國人提升文學修養的必選必讀書。
內容簡介
“我”從小就聽牧馬人貢波斯甲老人說,在參差雪峰的後麵,有個叫措娜的溫泉,那裏美如仙境。這溫泉成瞭“我”少年時代自由與浪漫的圖騰,一個美麗而遙遠的憧憬。若乾年後,已是攝影師的“我”終於來到瞭嚮往已久的措娜溫泉,拍下瞭美麗的藏女祼浴照。而這一切遭到瞭“我”兒時的夥伴賢巴的嘲弄。賢巴參軍迴來後當瞭縣長,把這神秘的溫泉開發成瞭一個不倫不類、汙濁不堪的廢泉。我童年美好的夢幻也隨之破滅。那被毀壞的溫泉,見證瞭人類的貪婪與野蠻。
作者簡介
阿來:1959年生人。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早期寫作詩歌,後轉嚮小說創作。傢鄉河流的名字是di一本書的名字:《梭磨河》。後陸續齣版有中短篇小說集《舊年血跡》《月光裏的銀匠》《格拉長大》《遙遠的溫泉》,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隨筆集《就這樣日益豐盈》《看見》《草木的理想國》,以及非虛構作品《大地的階梯》《瞻對: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等。
曾獲茅盾文學奬,華語文學傳媒大奬等文學奬項。
有《塵埃落定》《格薩爾王》和《遙遠的溫泉》等多部譯為英、法、意、德、俄、日和西班牙等十數種外國語在海外齣版。
以齣生成長於邊疆地帶而關注邊疆,錶達邊疆,研究邊疆。
精彩書評
阿來是邊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護者。他的寫作,旨在辨識一種少數族裔的聲音,以及這種聲音在當代的迴響。阿來持續為一個地區的靈魂和照亮這些靈魂所需要的儀式寫作,就是希望那些在時代大潮麵前孤立無援的個體不緻失語。
——謝有順 中山大學中文係教授
精彩書摘
上 篇
我們寨子附近沒有溫泉,隻有熱泉。
熱泉的熱,春夏時節看不齣來。隻有到瞭鼕天,在寨子北麵那條十多公裏縱深的山溝裏,當你踏雪走到瞭足夠近的距離,纔會看見在常綠的冷杉和杜鵑與落葉的野櫻桃和樺樹混生林間升起一片氤氳的霧氣。霧氣離開泉眼不久,便被迅速凍結,失去瞭繼續升騰的力量,變成枯黃草木上細細的冰晶。那便是不凍的熱泉在散發著熱力。試試水溫,冰冷的手會感到一點點的溫暖,在手指間微微有些粘滑,水不能飲用,因為太重的鹽分與濃重的硫黃味。鹽、硫黃,或者還有其他一些來自地心深處的礦物,在泉眼四周的泥沼上沉澱齣大片鐵銹般紅黃相間的沉積物。
鼕天,除瞭獵人偶爾在那裏歇腳,不會有人專門去看那眼叫卓尼的熱泉。
夏天,牛群上瞭高山草場。小學校放瞭暑假,我們這些孩子便上山,整天跟在牛群後麵,怕它們走失在草場周圍茂盛的叢林裏。嗜鹽的牛特彆喜歡喝卓尼泉中含鹽的水,啃飽瞭青草便奔嚮那些熱泉。大人不反對牛多少喝一點這種鹽水。但大人又告誡說,如果喝得太多,牛就會腹脹如鼓,吃不下其他東西,飢餓而死。所以,整個夏天,我們隨時要奔到熱泉邊把那些對鹽泉水缺乏自控能力的牛從泉眼邊趕開。如今,我的聲帶已經發不齣當年那種帶著威脅性的長聲吆喝瞭,就像再也唱不齣牧歌中那些逶迤的顫音一樣。當年,沉默的我經常獨自歌唱,當唱到牧歌那長長的顫動的尾音時,我的聲帶在喉嚨深處像蜂鳥翅膀一樣顫動著,聲音越過高山草場上那些小葉杜鵑與伏地柏構成的點點灌叢,目光也隨著這聲音無限延展,越過寬闊的牧場,高聳的山崖,最後終止在目光被晶瑩奪目的雪峰阻斷的地方。
是的,那是我在渴望遠方。
遠方沒有具體的目標,而隻是兩個大緻的方嚮。梭磨河在群山之間閃閃發光奔流而去,漸漸浩大,那是東南的遠方。西北方嚮,那些參差雪峰的背後,是寬廣的鬆潘草原。
夏天,樹蔭自上而下地籠罩,苔蘚從屁股下的岩石一直蔓生到杉樹粗大的軀乾,布榖鳥在什麼地方悠長鳴叫。情形就是這樣,我獨坐在那裏,把雙腳浸進水裏,這時的熱泉水反而帶著一絲絲的涼意。泉水湧齣時,一串串氣泡迸散,使一切顯得異樣的硫黃味便彌漫在四周。有時,溫順的鹿和氣勢逼人的野牛也會來飲用鹽泉。鹿很警惕,竪著耳朵一驚一乍。橫蠻的野牛卻目中無人,它們喝飽瞭水,便躺臥在銹紅色的泥沼中打滾,給全身塗上一層斑駁的泥漿。那些癩瞭皮的難看的病牛,幾天過後,身上的泥漿風乾脫落後,便通體煥然一新,皮上長齣柔順的新毛,陽光落在上麵,又是水般漾動的光芒瞭。
牧馬人貢波斯甲說:“泥漿能殺死牛馬身上的小蟲子。”
貢波斯甲還說:“那泥漿有治病的功效。”
貢波斯甲獨自牧著村裏的一小群馬。他的馬也會來飲鹽泉。通常,我們要在這個時候纔能在鹽泉邊上碰見他。
他老說這句話,接著,孩子們就哄笑起來,問:“那你為什麼不來治治你的病?”
貢波斯甲臉上有一大塊一大塊的皮膚泛著慘白的顔色,隨時都有一些碎屑像死去的樺樹皮從活著的軀乾上飄落一樣,從他臉上飄落下來。大人們告誡說,與他一起時,要永遠處在上風的方位,不然,那些碎屑落到身上,你的臉也會變成那個樣子。一個人的臉變成那種樣子是十分可怕的。那樣的話,你就必須永遠一個人住在山上的牧場,不能迴到寨子裏,迴到人群中來。也沒有女人相伴。
而我恰恰認為,這是最好的兩件事情:沒有女人和一個人住在山上。
住進寨子的工作組把人分成瞭不同的等級,讓他們加深對彼此的仇恨。女人和男人住在一起,生齣一個又一個的孩子,這些孩子便會來過這半飢半飽的日子。我就是那樣齣生長大的孩子中的一個。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特彆想和貢波斯甲一樣,沒有女人並一個人住在山上。
我的舅母患很厲害的哮喘,六十多歲瞭,她的侄女格桑麯珍,我好些錶姐中的一個,是寨子裏歌聲最美的姑娘,工作組說要推薦她到自治州文工團當歌唱演員,不知怎麼她卻當上瞭村裏的民兵排長。她經常用她好聽的嗓子對著舅母的房子喊話。她喊話之後,那座本已失去活力的房子就像死去瞭兩次一樣。喊話往往是人們集體勞動從地裏歸來的時候,淡淡的炊煙從一傢傢石頭寨子裏冒齣來,這一天,舅母傢的房頂便不會冒齣加深山間暮色的溫暖炊煙。舅母從石頭房子裏走齣來,臉也像一塊僵死的石頭。她從自傢的柴垛上抽齣一些木柴,背到寨子中央的小廣場上,這時,天空由藍變灰,一顆顆星星漸漸閃亮,夜色降臨遠離世界的深山,舅母用背去的木柴生起一大堆火。人們聚集在寨子中央的小廣場上,熊熊火光給眾人的臉塗抹上那個時代崇尚的緋紅顔色。舅母退到火光暗淡的一隅。火把最靠近火堆的人的影子放大瞭投射齣去,遮蔽瞭彆人應得的光綫與溫暖。我們族人中一些曾經很謙和很隱忍的人,突然嗓音洪亮,把舅母聚集傢庭財富時的慳吝放大成不可饒恕的罪惡,把她偶爾的施捨變成蓄意的陰謀。
最近的陰謀之一是給過獨自住在山上的花臉貢波斯甲一小袋鹽,和一點熬過又曬乾的茶葉。
這個傳遞任務是由我和賢巴完成的。後來,貢波斯甲的錶弟的兒子賢巴又將這個消息泄露給瞭工作組。總把一件軍大衣披在身上的工作組長重重一掌拍在中農兒子賢巴的瘦肩膀上說:“你將來能當上解放軍!”被那一掌拍坐在地上的賢巴趕緊站起來,激動得滿臉通紅不知所措。結果,當天晚上,寨子裏又響起來瞭錶姐的好嗓門,舅母又在廣場上升起一堆火,大傢又聚集起來。又是那些被火光放大瞭身影的人,奇怪地提高瞭他們的聲音。那些年頭,大傢都不是吃得很飽,卻又聲音洪亮,這讓人很費猜量。
我看著天空猜想,雲飄過來,遮住瞭月亮。天上有很大的風,鑲著亮邊的烏雲疾速流動,嗖嗖作響。
第二天,賢巴的半邊臉便高高腫脹起來,有人說是他父親打的,有人說是花臉貢波斯甲打的,甚至有人說,那一巴掌是我那一年就花白瞭頭發的舅母打的。從此,我與賢巴就不再是朋友瞭。有人在我們之間種下仇恨瞭,這仇恨直到他穿上瞭軍裝迴到寨子給男人們散發香煙,給女人們分發糖果時也沒有消散。我是說,那時,他已經不恨我瞭,但我仍然恨他。
從此以後,我纔在放牛的時候和貢波斯甲說話。他坐在泉水一邊,低一點的地方,讓我坐在泉水另一邊,高一點的地方,他告訴我一些寨子裏以前的事情。經他嘴講齣來的故事,沒有鬥爭會上揭發齣來的那麼罪惡。他好像也沒有仇恨,連講起自己得病後跟人私奔瞭的妻子時,他那花臉甚至淺淺地浮現齣一些笑意。
但他一看到侄兒賢巴,臉上新掉瞭皮的部分便顯得特彆鮮紅,但他從來不說什麼,隻是不看他,而彆過臉去望那些終年積雪的山峰。
他也問我一些寨子裏的事情。這時,牛們使勁甩動尾巴,抽打叮在身上的牛虻。我告訴他,我想像他一樣,一個人住在山上。他臉上露齣痛苦而憐惜的錶情,伸手做齣一個愛撫的動作,雖然他的手伸嚮虛空,但是隔著泉眼,我還是感到一種從頭頂灌注到腳底的熱量。
我不敢抬起頭來,卻聽見他說:“但是,你不想有跟我一樣的花臉。”
我更不敢抬頭應聲瞭。
突然,他說:“其實,隻要讓我去一次溫泉,在那裏洗一洗身子,洗一洗臉,迴來時,就光光鮮鮮地不用一個人住在山上瞭。”
這是我第一次聽人說起溫泉。
他告訴我,溫泉就是比這更燙的泉水,跟這水一樣的味道,但裏麵沒有鹽。他說,溫泉能治很多的病癥,最厲害的一手就是把不光鮮的皮膚弄得光鮮。雙泉眼的溫泉能治好眼病與偏頭痛,更大的泉眼療效就更加廣泛瞭,從風濕癥到結核,甚至能使“不乾淨的女人乾淨”。
我不知道女人不乾淨的確切含意,但我開始神往溫泉。於是,那眼叫做措娜的溫泉成瞭我有關遠方的第一個確切的目標。我想去看一眼真正的溫泉,遙遠的溫泉,神妙的溫泉。我不愛也不想說話,父母又希望我在人群中間能夠隨意說話,大聲說話。我想,溫泉也是能治好這種毛病的吧。
我問花臉溫泉在什麼地方。他指指西邊那一列參差著的雪峰,雪峰間錯落齣一個個埡口。公路從寨子邊經過,在山腰上來來迴迴地盤鏇,一輛解放牌卡車要嗡嗡地響上兩三個鍾頭,纔能穿過埡口。汽車從東邊新建中的縣城來,到西邊寬廣的草原上去。村裏的孩子既沒有去過東邊,也沒有去過西邊。除瞭寨子裏幾個乾部,大人們也什麼地方都不去。以至於我們認為,人是不需要去什麼太遠的地方的。但是,貢波斯甲告訴我,過去,人們是常常四處漫遊的。去拜聖山,去朝佛,去做生意,去尋找好馬快槍,去奔赴愛情或瞭結仇恨。還有,翻過雪山,騎上好馬,帶上美食,去洗那差不多包治百病的溫泉。
“但是,如今人像莊稼一樣給栽在地裏瞭。”花臉貢波斯甲嘆瞭一口氣,無奈地說。
迴到山下,我去看種在地裏的莊稼。
豌豆正在開花,蜜蜂在花間嗡嗡歌唱。大片麥子正在抽穗,在陽光下散發著沉悶的芬芳。看來,地裏的莊稼真是不想什麼遠方,隻是一個勁地成長。一陣輕風吹來,麥子發齣絮絮的細語。我卻不能像莊稼一樣,站在一個地方,什麼都不想。
有一天我受好奇心驅使,爬到瞭雪山埡口,往東張望,能看到幾十裏外,一條河流閃閃發光,公路順著河榖忽高忽低地蜿蜒。影影綽綽地,我看到瞭縣城,一個由一大群房子構成的像夢境一樣模糊的巨大輪廓。轉身嚮西,看到寬廣的草原,草原上鼓湧著很多姑娘胸脯一樣渾圓的小丘。那就是很切近的遙遠。用一個少年的雙腳去丈量這些目力所及的距離,不能用一個白晝的時間抵達的地點,就是我那時的遙遠。而且,有一眼叫做措娜的溫泉就在草原深處的某個地方。
我從雪山下來,貢波斯甲問我:“看到瞭嗎?”
我說看到瞭草原。比我們山脊上的草場更寬更大罷瞭,上麵有閃閃發光的河流與湖泊罷瞭。
貢波斯甲這個自卑的人,第一次對我露齣瞭不屑的錶情:“我是說你看到溫泉瞭嗎?”
我搖頭。
貢波斯甲說:“嘖,嘖嘖,就在那座岩石鐵紅的小山下麵嘛。”
我沒有看見那座小山。那一天,我覺得他臉上一直隱現齣一種驕傲的神情。但我安坐在熱泉邊上,突然覺得自己永遠也去不瞭那樣的地方,永遠也想象不齣一座鐵紅色的山峰是個什麼樣子。三隻野黃羊從熱泉裏飲瞭水走開瞭,我覺得自己就像這些什麼都不知道的野羊一樣。
貢波斯甲說:“那個時候去溫泉嘛,糟老頭子是去醫病,年輕娃娃是去看世界,去懂得女人。”
晚上,山風呼呼地吹過牧場的帳篷頂,我想,女人,是好嗓門的錶姐那樣的女人,還是舅母那樣苦命的女人?我睡不著,披著當被子的羊毛毯子走齣帳房,坐在滿天的星星下,坐在雪山的剪影前。看見遠遠的山榖那邊,一團燈火,那就是貢波斯甲孤獨的傢。打從他花瞭臉,走瞭女人,他就成瞭寨子裏的牧馬人。其實,那個時候馬已經沒有什麼用處瞭。老人們說,打從一個又一個工作組來瞭又走,走瞭又來,人就像上瞭腳絆的馬,給永遠限製在一個地方瞭。他們隻能常常在老歌裏暢遊四方。歌裏唱的那些人,有的暢遊之後迴來瞭,有的就永遠消失在遙遠的地方。從我懂事起,人們就老說著從來不見人去的溫泉。溫泉就在雪山那邊的草原上,那是過去的概念。現在的說法是,雪山這邊是一個縣的某某公社某某大隊某某生産隊。草原上的溫泉又是另一個縣的某某公社某某大隊某某生産隊。牧場也劃齣瞭邊界。我們的牛群永遠不能去到埡口那邊的草原。而在過去的夏天,人們可以趕著牛群,越過埡口,一天挪移一次帳房,十多天時間便到瞭溫泉的邊上。溫泉就是上百裏大地上人群的一個匯集,一個龐大的集市,一次盛大的舞會,和滿池子裸浴的男女。
一個特彆醉心於過去男人們浪遊故事的年輕人酒醉後說瞭一句話。結果,隻好自己在寨子裏的小廣場上生起熊熊大火,然後,垂著頭退後,把臉藏在火光開始暗淡的地方。情形就是這樣。生起火堆的人不該照到灼人的火光。
前言/序言
我隻感到世界撲麵而來(代後記)
這次受《當代作傢評論》雜誌林建法先生的邀請,來渤海大學參加交流活動,他預先布置任務,一個是要與何言宏先生做一個對話,一個是要我準備一個單獨的講演,無論是何言宏預先傳給我的對話要點,還是林建法的意思,都是要我側重談談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或者說是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關係這樣一個話題。這是文學藝術界經常談及的話題,同時也是一個越談越歧見百齣、難以定論的話題。
去年十月到十一月間,有機會去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做瞭一次不太長的旅行。我要說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旅行,一方麵是與過去隻在文字中神會過的地理與人文遭逢,一方麵,也是對自己初上文學之路時最初旅程的一次迴顧。在這次旅行中,我攜帶的機上讀物,都是八十年代閱讀過的拉美作傢的作品。同行的人,除瞭作傢,還有導演、演員、造型藝術傢,長途飛行中,大傢也傳看這幾本書,並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地理環境中交換對於這些書的看法,至少都認為,這樣的書,對於直接體會拉丁美洲的文化特質與精神氣韻,是最便捷、最有力的入門書。我說的是同行者的印象,而對我來說,意義顯然遠不止於此。我是在鬍安·魯爾弗的高原上行走,我是在若熱·亞馬多的叢林中行走,我是在博爾赫斯的復雜街巷中行走!穿行在如此廣闊的大地之上,我所穿越的現實是雙重的,一個實際的情形在眼前展開,一個由那些作傢的文字所塑造。我沒有機會去尋訪印加文化的舊址,但在瑪雅文化的那些輝煌的廢墟之上,我想,會不會在拐過某一座金字塔和仙人掌交織的陰影下與巴勃羅·聶魯達猝然相逢。其實也就是與自己文學的青春時代猝然相逢。
所以提起一段本該自己不斷深味的旅行,是因為在那樣的旅途上自己確實想瞭很多。而所思所想,大多與林建法給我指定的有關民族與世界的題目有著相當關係。在我來說,在拉美大地上重溫拉美文學,就是重溫自己的八十年代。那時,一直被禁閉的精神之門訇然開啓,不是我們走嚮世界,而是世界嚮著我們撲麵而來。外部世界精神領域中那些偉大而又新奇的成果像洶湧的浪頭,像洶湧的光嚮著我們迎麵撲來,使我們熱情激蕩,又使我們頭暈目眩。
林建法的命題作業正好與上述感觸重閤糾纏在一起,所以我索性就從拉美文學說起,其間想必會有一些與民族性與世界性這個話題相關的地方。
所謂民族性與世界性,在我看來,在中國文學界,是一個頗讓人感到睏擾,卻又長談不已的話題。從我剛剛踏上文壇開始,就有很多人圍繞著這個話題發錶瞭很多的看法,直到今天,如果我們願意平心靜氣地把這些議論做一個冷靜客觀的估量,結果可能令人失望:那就是說,迄今為止,與二十多年前剛開始討論這些問題時相比,在認知的廣度與深度上並未有多大的進展。而且,與那時相比較,今天,我們的很多議論可能是為瞭議論而議論,是思維與言說的慣性使然,而缺乏當年討論這些話題時的緊迫與真誠。一些基本原理已經被強調瞭一遍又一遍,可是具體到小說領域,民族化與世界性這樣的決定性因素在每一個作傢身上,在每一部成功抑或失敗的作品中究竟起到怎樣的作用,尤其是如何起到作用,還是缺少有說服力的探討。
這個題目很大,如果正麵突破,我思辨能力的貧弱馬上就會暴露無遺。那麼,作為一個有些寫作經驗的寫作者,結閤自己的創作實踐,結閤自己的作品,來談一談自己在創作道路上如何遭逢到這些巨大的命題,它們怎麼樣在給我啓示的同時,也給我更多的睏擾,同時,在排除瞭部分睏擾的過程中,又得到怎樣的經驗,把這個過程貢獻齣來,也許真會是個值得探求一番的個案。
談到這裏,我就想起瞭薩義德的一段話:“所有文化都能延伸齣關於自己和他人的辯證關係,主語‘我’是本土的,真實的,熟悉的,而賓語‘它’或‘你’則是外來的或許危險的,不同的,陌生的。”
以我的理解,薩義德這段話,正好關涉到瞭所謂民族與世界這樣一個看似尋常,但其中卻暗含瞭許多陷阱的話題。“我”是民族的,內部的,“它”或“你”是外部的,也就是世界的。如果“它”和“你”,不是全部的外部世界,那也是外部世界的一個部分,“我”通過“它”和“你”,揣度“它”和“你”,最後的目的是要達到整個世界。這是一個作傢的野心,也是任何一個文化在當今世界的生存、發展,甚至是消亡之道。
就我自己來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寫作,那時正是漢語小說的寫作掀起瞭文化尋根熱潮的時期。作為一個初試啼聲的文學青年,行步未穩之時,很容易就被裹挾到這樣一個潮流中去瞭。尤其是考慮到我的藏族身份,考慮到我依存著那樣一種到目前為止還被大多數人看得相當神秘奇特的西藏文化背景,很容易為自己加入這樣的文化大閤唱找到閤乎情理的依據。首先是正在學習的曆史幫助瞭我。有些時候,曆史的教訓往往比文學的告訴更為有力而直接。曆史告訴瞭我什麼呢?曆史告訴我說,如果我們剛剛走齣瞭意識形態決定論的陰影,又立即相信文化是一種無往不勝的利器,相信咒語一樣相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樣的斬釘截鐵的話,那我們可能還是沒有擺脫把文學看成一種工具的舊思維。曆史還告訴我們,文學,從其産生的第一天起,就作用於我們的靈魂與情感,無論古今中外,都自有其獨立的價值。它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可以豐富一種文化,但絕對不是用於展示某種文化的一個工具。
文學所起的功用不是闡釋一種文化,而是幫助建設與豐富一種文化。
正因為如此,我剛開始寫作就有些裹足不前,看到瞭可能不該怎麼做,但又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剛剛上路,就在岔路口徘徊,選不到一個讓人感到信心的前行方嚮。你從理性上有一個基本判斷,再到把這些認識融入到具體的寫作實踐中還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具體說來就是,這樣的認識隻是否定瞭什麼,那麼你又相信什麼?又如何把你所相信的觀念形態的東西融入具體的文本?從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應該說,我就這樣左右彷徨徘徊瞭差不多十年時間。最後,是大量的閱讀幫助我解決瞭問題。
先說我的睏境是什麼。我的睏境就是用漢語來寫漢語尚未獲得經驗來錶達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漢語寫過異域生活,比如唐詩裏的邊塞詩,“西齣陽關無故人”,以為就是離開漢語覆蓋的文化區,進入異族地帶瞭。但是,在高適、王昌齡們的筆下,另外那個陌生的文化並沒有齣現,那個疆域隻是供他們抒發帶著蒼涼意味的英雄情懷,還是徵服者的立場,原住民沒有齣現。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過:“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我依此指引,讀過很多納蘭容若,卻感覺並不解決問題,因為所謂“未染漢人風氣”,也是從局部的審美而言,大的思想文化背景,納蘭容若還是很徹底地被當時的漢語和漢語背後的文化“化”過來瞭的。
差不多相同意味的,我可以舉元代薩都剌的一首詩:“祭天馬酒灑平野,沙際風來草亦香。白馬如雲嚮西北,紫駝銀甕賜諸王。”
“白馬如雲嚮西北”“沙際風來草亦香”,與邊塞詩相比,這北地荒漠中的歌唱,除瞭一樣的雄渾壯闊,自有非漢文化觀察感受同一自然界的灑脫與歡快。這自然是非漢語作傢對於豐富漢語審美經驗的貢獻。但也隻是限於一種個人經驗的抒發,並未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而且,這樣的作品在整個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學中並不多見。
更明確地說,這樣零星的經驗並不足以讓我這樣的非漢語作傢在漢語寫作中建立起足以支持漫長寫作生涯的充分自信。
好在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與納蘭容若和薩都剌們完全不同的時代,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有條件通過漢語溝通整個世界。這其中自然包括瞭遙遠的美洲大陸—講拉丁語的美洲大陸,也包括講英語的美洲大陸。
在這個時期,美洲大陸兩個偉大的詩人成為我文學上的導師:西班牙語的聶魯達和英語的惠特曼。
不是因為我們握有民族文化的資源就自動地走嚮瞭世界,而是我們打開國門,打開心門,讓世界嚮我們走來。
當世界撲麵而來,纔發現外麵的世界不是一個簡單的闆塊,而是很絢麗復雜的拼盤。我的發現就是這個文學的版圖中,好些不同的世界也曾像我的世界一樣喑啞無聲,但是,他們終於嚮著整個世界發齣瞭自己洪亮的聲音。聶魯達們操著西班牙語,而這種語言是幾百年前他們的祖先從另一個大陸帶過來的。但是,他們在美洲已經很多很多年瞭,即便是從血統上講,他們也不再全部來自歐洲。拉美還有大量的土著印第安人以及來自非洲的黑人。在幾百年的時間裏,不同膚色的血統與文化都在彼此交融,從而産生齣新的人群與新的文化。但在文學上,他們還模仿著歐洲老傢的方式與腔調,從而造成瞭文學錶達與現實、與心靈的嚴重脫節。拉丁美洲越來越急切地要用自己的方式錶達自己,並嚮世界發言。告訴世界,自己也是這個世界中一個莊嚴的成員。如今我們所知道的那些造成瞭拉美文學“爆炸”的作傢群中的好些人,比如卡彭鐵爾,親身參與瞭彼時風靡歐洲大陸的超現實主義文學運動,還能夠身在巴黎直接用法語像艾呂雅們一樣嫻熟地寫作。但就是這個卡彭鐵爾,在很多年後迴顧這個過程時,這樣錶達為什麼他們重新迴到拉美,並從此開始重新齣發:拉丁美洲作傢,“他本人隻能在本大陸印第安編年史傢這個位置上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為本大陸的現在和過去而工作,同時展示與全世界的關係”。他們大多不是印第安人,但認同拉丁美洲的曆史有歐洲文化之外的另一個源頭。
這句話還有一個意思,我本人也是非常認同的,那就是認為作傢錶達一種文化,不是為瞭嚮世界展覽某種文化元素,不是急於嚮世界呈現某種人無我有的獨特性,而是探究這個文化“與全世界的關係”,以使世界的文化圖像更臻完整。用聶魯達的詩句來說,世界失去這樣的錶達,“就是熄滅大地上的一盞燈”。
的確,卡彭鐵爾不是一個孤證,聶魯達就在他的偉大詩歌《亞美利加的愛》裏直接宣稱,他要歌唱的是“我的沒有名字不叫亞美利加的大地”。如果我的理解沒有太大的偏差,那麼他要說的就是要直接呈現那個沒有被歐洲語言完全覆蓋的美洲。在這首長詩的一開始,他就直接宣稱:
我來到這裏,是為瞭歌唱曆史
從野牛的寜靜,直到
大地盡頭被衝擊的沙灘
在南極光下聚集的泡沫裏
從委內瑞拉陰涼安詳的峭壁洞窟
我尋找你,我的父親
混沌的青銅的年輕武士
接下來,他乾脆直接宣稱:“我,泥土的印加的後裔!”而他尋找的那個“混沌的青銅的年輕武士”,不是堂吉訶德那樣的騎士,而是一個相貌堂堂的古代印加勇士。
我很為自己慶幸,剛剛走上文學道路不久,並沒有迷茫徘徊多久,就遭逢瞭這樣偉大的詩人,我更慶幸自己沒有麯解他們的意思,更沒有隻從他們的偉大的作品中取來一些炫技性的技法來障人眼目。我找到他們,是知道瞭自己將從什麼樣的地方,以什麼樣的方式重新上路齣發,破除瞭搜羅奇風異俗就是發揮民族性、把獨特性直接等同於世界性的沉重迷思。
從此我知道,一個作傢應該盡量用整個世界已經結晶齣來的文化思想成果盡量地裝備自己。哲學、曆史學、地理學、人類學……不是把這些二手知識匆忙地塞入作品,而是用由此獲得的全新眼光,來觀察在自己身邊因為失語而日漸沉淪的曆史與人生。很多的人生,沒有被錶現不是沒有錶現的價值,而是沒有找到錶現的方法。很多現實沒有得到觀察,是因為缺乏思想資源而無從觀察。
也許無論是地理還是文化都豐富多彩的拉丁美洲就具有這樣的魅力,連寫齣瞭宏大嚴謹的理論巨著《文化人類學》的人類學傢列維-斯特勞斯,當他把考察筆觸伸嚮這片大陸的時候,也采用瞭非常文學化的結構與筆觸,寫下瞭《憂鬱的熱帶》這樣感性而不乏深邃考察的筆記。
所以,我準備寫作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的時候,就從馬爾剋斯、阿斯圖裏亞斯們學到瞭一個非常寶貴的東西。不是模仿《百年孤獨》和《總統先生》那些喧鬧奇異的文體,而是研究他們為什麼會寫齣這樣的作品。我自己得齣的感受就是一方麵不拒絕世界上最新文學思潮的洗禮,另一方麵卻深深地潛入民間,把藏族民間依然生動、依然流傳不已的口傳文學的因素融入小說世界的構建與營造。在我的故鄉,人們要傳承需要傳承的記憶,大多時候不是通過書寫,而是通過講述。在高大堅固的傢屋裏,在火塘旁,老一代人嚮這個傢族的新一代傳遞著這些故事。每一個人都在傳遞,更重要的是,口頭傳說一個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每一個人在傳遞這個文本的時候,都會進行一些有意無意的加工。增加一個細節,修改一句對話,特彆是其中一些近乎奇跡的東西,被不斷地放大。最後,現實的麵目一點點模糊,奇跡的成分一點點增多,故事本身一天比一天具有瞭更多的浪漫、更強的美感,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於是,曆史變成瞭傳奇。
是的,民間傳說總是更多訴諸情感而不是理性。有瞭這些傳說作為依托,我來講述末世土司故事的時候,就不再刻意去區分哪些是曾經真實的曆史,哪些地方留下瞭超越現實的傳奇飄逸的影子。在我的小說中,隻有不可能的情感,而沒有不可能的事情。於是,我在寫作這個故事的時候,便獲得瞭空前的自由。我知道,很多作傢同行會因為所謂的“真實”這個文學命題的不斷睏擾,而在寫作過程中感到舉足維艱,感到想象力的束縛。我也曾經受到過同樣的睏擾,是民間傳說那種在現實世界與幻想世界之間自由穿越的方式,給瞭我啓發,給瞭我自由,給瞭我無限的錶達空間。
這就是拉美文學給我最深刻的啓發。不是對某一部作品的簡單的模仿,而是對他們創作之路深刻體會後找到瞭自己的道路。
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常常背著聶魯達的詩集,在我故鄉四周數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四處漫遊。走過那些高山大川、村莊、城鎮、人群、果園,包括那些已經被叢林吞噬的人類生存過的遺跡。各種感受綿密而結實,更在草原與群山間的村落中,聆聽到很多本土的口傳文學,那村莊史、部落史、民族史,也有很多英雄人物的曆史。而拉美的爆炸文學中一些代錶性的作傢,比如阿斯圖裏亞斯、馬爾剋斯、卡彭鐵爾等作傢的成功最重要的一個實踐,就是把風行世界的超現實主義文學的東西與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土著的口傳神話傳統嫁接到瞭一起,從而創造齣一種全新的隻能屬於西班牙語美洲的文學語言係統。卡彭鐵爾給這種語言係統一個命名是“巴羅剋語言”。他說:“這是拉丁美洲人的敏感之所在。”是不是為瞭標新立異纔需要這樣一種語言?不是,他說,“為瞭認識和錶現這個新世界,人們需要新的詞匯,而一種新的詞匯將意味著一種新的觀念。”
這句話有一個重點,首先是認識,然後纔是錶見,然後纔談得上是錶現,但我們今天,常常在未有認識之前,就急於錶現。為瞭錶現而錶見,為瞭獨特而錶現。為什麼要獨特?因為需要另外世界的承認與發現。
在我看來,一個小說傢在寫作過程中,感受更多的還是形式的問題:語言、節奏、結構。任何一個環節處理不好,都會讓你失掉一部真正的小說。一個好的小說傢,就是在碰到可能寫齣一部好小說的素材的時候,沒有錯過這樣的機會。要想不錯過這樣的機會,光有寫好小說的雄心壯誌是不夠的,光有某些方麵的天賦也是不夠的。這時,就有新的問題産生齣來瞭:什麼樣的形式是好的形式?好的形式除瞭很好錶達內容之外,會不會對內容産生提升的作用?好的形式從哪裏來?這些都是小說傢應該花大量的時間—在寫作中,在閱讀中—去嘗試,去思考的問題。
我從二〇〇五年開始寫作六捲本的長篇《空山》,直到今年春節前,纔終於完成瞭第六捲的寫作。這是一次非常費力的遠徵。這是一次自我設置瞭相當難度的寫作。我所要寫這個機村的故事,是有一定獨特性的,那就是它描述瞭一種文化在半個世紀中的衰落,同時,我也希望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因為這個村莊首先是一個中國的農耕的村莊,然後纔是一個藏族人的村莊,和中國很多很多的農耕的村莊一模一樣。這些本來自給自足的村莊從五十年代起就經受瞭各種政治運動的激蕩,一種生産組織方式、一種社會剛剛建立,人們甚至還來不及適應這種方式,一種新的方式又在強行推行瞭。經過這些不間斷的運動,舊有秩序、倫理、生産組織方式都受到瞭毀滅性的打擊。維係社會的舊道德被摧毀,而新的道德並未像新製度的推行者想象的那樣建立起來。我正在寫作《空山》第三捲的時候,曾得到一個機會去美國做一個較長時期的考察,我和翻譯開著車在美國中西部的農業區走過瞭好些地方。那裏的鄉村的確安詳而又富足,就是在那樣的地方,我常常想起司坦貝剋的巨著《憤怒的葡萄》。那些美國鄉鎮給人的感覺絕不隻是物質的富足,那些鄉鎮裏的人們看上去,比在紐約和芝加哥街頭那些匆匆奔忙的人更顯得自尊與安閑。但在司坦貝剋描述的那個時期,這些地區確實也曾被人禍與天災所摧殘,但無論世事如何艱難,命運如何悲慘,他們最後的道德防綫沒有失守,當製度的錯誤得到糾正,當上天不再頻仍地降下災難,大地很快就恢復瞭生機,纔以這樣一種平和富足的麵貌呈現在一個旅人眼前。
但這不是我的國度、我的傢園。
八十年代,我們的鄉村似乎恢復瞭一些生氣,生産秩序暫時恢復到過去的狀態,但人心卻迴不去瞭。而且,因為製度安排的缺陷,剛剛恢復生機的鄉村又被由城市主導的現代經濟衝擊得七零八落。鄉村已經不可能迴到自給自足的時代瞭,但在參與到更大的經濟循環中去的時候,鄉村的利益卻完全被忘記。於是,鄉村在整整半個世紀中失去瞭機會。而這五十年恰恰是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五十年,也是經濟發展令數以億計的人們物質與文化生活都得到最快提升的五十年。所以,我寫的是一個村莊,但不止是一個村莊。寫的是一個藏族的村莊,但絕不隻是為瞭某種獨特性,為瞭可以挖掘也可以生造的文化符號使小說顯得光怪陸離而來寫這個異族的村莊。再說一次,我所寫的是一個中國的村莊。在故事裏,這個村莊最終已然消亡。它會有機會再生嗎?也許。我不忍心抹殺瞭最後希望的亮光。
那麼,這個故事是民族的還是世界的?這本書的內容,是獨特的還是普遍的?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最大的努力就是不讓這樣的問題來睏擾我。
那時,我就想起年輕時就給我和聶魯達一樣巨大影響的惠特曼。他用舊大陸的英語,首先全麵地錶現瞭新大陸生機勃勃的氣象。在某些時候,他比聶魯達更舒展,更寬廣。那時我時常溫習他的詩句:“大地和人的粗糙所包含的意義和大地和人的精微所包含的一樣多/除瞭個人品質什麼都不能持久!”
他還常常發齣歡呼:“形象齣現瞭!/任何使用斧頭的形象,使用者的形象,和一切鄰近於他們的人的形象。/形象齣現瞭!/齣入頻繁的門戶的形象。/好消息與壞消息進進齣齣的門戶的形象!”
這也是我對文藝之神的最多的企求:讓我腦海中齣現形象,人的形象,命運事先就在他們臉龐與腰身上打下瞭烙印的鄉村同胞的形象;生命剛剛展開,就顯得異常艱難的形象;曾經抗爭過命運,最後卻不得不逆來順受者的形象。與惠特曼不同的是,我無從發齣那樣的歡呼,我隻是為瞭不要輕易遺忘而默默書寫,也是為瞭對未來抱有不滅的希望。
正是從惠特曼開始,我開始進入英語北美的文學世界,相比南方的拉美作傢,應該說,更大群、更多樣化的美國作傢的作品,特彆是美國猶太作傢和黑人作傢給瞭我更持久的影響與啓發。
寫作《塵埃落定》的時候,我吃驚小說怎麼這麼快速地完成瞭。而在寫作《空山》這部小說的時候,我卻一直盼望著它早一點結束。現在,它終於完成瞭,我終於把過於沉重的擔子從肩上卸下來,心中卻不免有些茫然。很久,我都不讓這部小說齣現在我的腦海中。直到要來參加這次活動,覺得該談一談它,纔讓它重新進入我的意識中間。如果需要迴應一下開始時的話題,也就是說,這部小說是民族的還是世界的?或者因為它是民族的,因此自動就是世界的?我想,有些小說非常適閤作這樣的文本分析。但我會更高興地看到,《空山》不會那麼容易地被人裝入這樣的理論筐子裏邊,不是被撿入山藥的筐子,就是被裝到西紅柿的筐子,我想有些驕傲地說,可能不大容易。直到現在,我還是隻感到人物命運的起伏—那也是小說敘事的內在節律,我感到人物的形象逐一呈現—這也關乎小說的結構,然後,是那個村莊的形象最初的顯現與最後的消失。民族、世界這些概念,我在寫作時已經全然忘記,現在也不想用這些彼此相斥又相吸,像把玩著一對電磁體正負極不同接觸方式一樣把玩著這樣的概念,我隻想讓自己被命運之感所充滿。
需要申明一點,小說名叫《空山》與王維那兩句閑適的著名詩句沒有任何關聯,如果說,這本書與拉美文學還有什麼聯係,那就是寫作過程中,我常常想起一本拉美人寫的政論性著作《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因為我們的報章上還開始披露,這本書所寫的那個五十年,中國的鄉村如何嚮城市,中國的農業如何嚮工業—輸血。是的,就是這個醫學詞匯,同樣由外國人擁有發明權。
最後,我想照應一下演講的題目,那是半句話。全句話是:我隻是打開瞭心門,我沒有走嚮世界,而是整個世界嚮我撲麵而來!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語言風格非常獨特,帶著一種古典文學的韻味,但又不失現代的銳利感。許多句子讀起來朗朗上口,像是經過反復打磨的詩歌,每一個詞語的選擇都顯得那麼精準和必要,幾乎找不到可以刪減的贅餘之處。作者對於意象的運用達到瞭爐火純青的地步,比如反復齣現的某種天氣、某種顔色,都不僅僅是環境的烘托,更像是某種情緒的投射或者命運的預兆。閱讀過程中,我常常停下來,對著某個段落反復揣摩,試圖理解其中更深層的象徵意義。它不像快餐讀物那樣直白易懂,而是更傾嚮於提供一種美學的享受。如果你是那種對文字本身的美感有極高要求的人,這本書絕對能讓你大呼過癮,它在文字層麵提供的滿足感,是很多當代小說難以企及的。
评分給我最大的震撼是書中對“選擇”與“後果”這一主題的探討。作者似乎並不熱衷於評判角色的好壞,而是冷靜地展示瞭他們人生道路上的每一個岔路口,以及每一個選擇所帶來的不可逆轉的連鎖反應。看著主角們在巨大的時代洪流或個人的命運漩渦中掙紮,做齣那些既無奈又堅定的決定,我感到一種深刻的共鳴和無力感。這不是那種簡單的善惡二元論故事,而是充滿瞭灰色地帶的成人世界。書中那些配角的命運綫也同樣精彩,他們像是無數麵鏡子,摺射齣主角的不同側麵,也展示瞭生活復雜的多樣性。讀完之後,我花瞭很長時間來整理自己的思緒,思考如果我站在他們的位置,我會如何抉擇,這無疑是一次深刻的自我審視。
评分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這本書的氛圍,我會選擇“沉鬱的史詩感”。它講述的似乎是一個很私人的故事,但字裏行間卻透露齣對更宏大曆史變遷的關注。時間跨度很大,背景設定也相當復雜,涉及到一些我原本不太瞭解的地域文化和曆史背景,但作者的處理非常巧妙,沒有使用晦澀難懂的術語,而是通過人物的日常遭遇,自然而然地將讀者帶入那個世界觀中。我感覺自己仿佛在閱讀一份被時間塵封的傢族編年史,充滿瞭宿命的味道,但又不失人性的微光。那種在宏大敘事下,個體生命所能展現齣的韌性和對美的堅守,是支撐我一口氣讀完的核心動力。它成功地將個人悲歡融入瞭時代的背景闆中,讓故事既有微觀的溫度,也有宏觀的厚重。
评分坦白說,這本書的敘事結構對我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它跳躍性很大,時間綫經常被打亂,像一個被打碎的鏡子,需要讀者自己去努力拼湊齣完整的圖像。起初我有些跟不上節奏,甚至覺得有些混亂,但當堅持讀到三分之一處時,那種“豁然開朗”的感覺纔真正齣現。你會發現那些看似不連貫的片段,其實是作者精心設計的綫索,它們在不同的時間點交匯,最終形成一個宏大而精密的結構。這種敘事手法很考驗作者的功力,稍有不慎就會變成故弄玄虛,但幸運的是,作者精準地把握住瞭那個度——既保持瞭足夠的神秘感,又保證瞭最終的邏輯自洽。我尤其喜歡作者在描述那些重大事件時所采取的疏離感,不直接灌輸情感,而是讓事件本身去說話,讓讀者自行去體會那種巨大的悲慟或狂喜。
评分這本小說讀下來,感覺就像是跟著主角在迷霧中穿行,每一個轉摺都齣乎意料,卻又在迴味之後覺得閤乎情理。作者對人物內心的刻畫極其細膩,那種掙紮、猶豫,甚至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執念,都被描摹得入木三分。我特彆欣賞那種潛藏在日常對話之下的暗流湧動,錶麵上風平浪靜,底下卻可能醞釀著一場巨大的情感風暴。情節的推進不是那種一蹴而就的爆發力,而是像抽絲剝繭一樣,層層遞進,每揭開一小部分真相,都會讓人對之前所有的人物關係和動機産生新的理解。書中的場景描寫也很有畫麵感,無論是喧囂的都市場景還是寜靜的鄉野小路,都仿佛觸手可及,讓人不禁沉浸其中,忘記瞭自己身處何方。整體而言,這是一部需要細細品味的佳作,它不提供廉價的娛樂,而是提供瞭一種深入人性的體驗,讀完之後,心裏會留下一些久久不散的思考和餘韻。
评分书的质量不错,就是开本小点。只是一个中篇,精装有点浪费,如果能再加点作者作品简介的内容就好了。
评分很小很薄的一本。
评分还没看,先收着,慢慢看,这次是真赚到了。
评分书好!好!好!好!
评分不错的书,不错的价格不错的服务。
评分阿来的《遥远的温泉》写得很好,这是我时隔五年后再次购买这本书,反复阅读,获益匪浅。网购本书,物流速度快,服务态度好,而图书的质量也是杠杠的。
评分读书日活动总会买很多书,京东向来都是先提价再搞活动,所以没有抢到券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价格优势,好在纸张还行,送货也非常快。
评分满减活动,一下子买了很多本,物流较快,然后书的质量可以
评分是正版到货很快,非常满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肯·福莱特:圣殿春秋(套装全三册) [The Pillars of the Eart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64055/59a8b8f1Nd2aed7c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