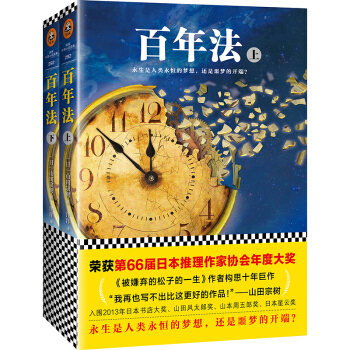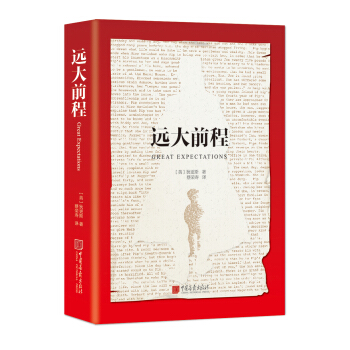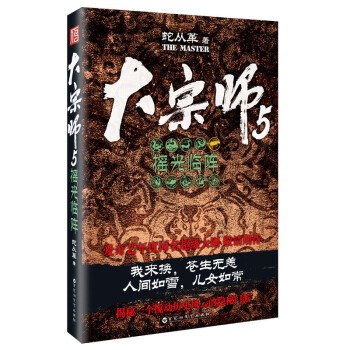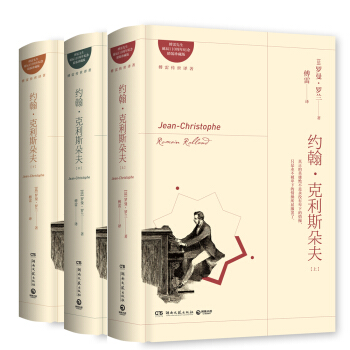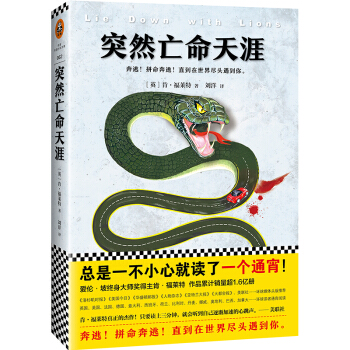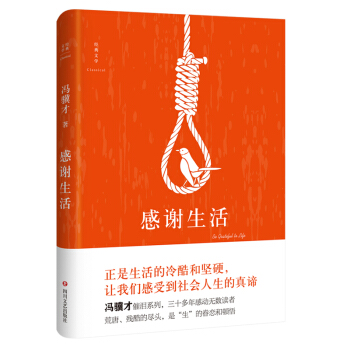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清新感傷版的馮驥纔,呈現他“俗世奇人”筆法之外的另一麵。★篇篇精彩,篇篇懸念,不讀到*後一個字,就很難說你讀完瞭這個故事。
★荒唐、殘酷的盡頭,是“生”的眷戀和頓悟。
★本次推齣馮驥纔的人性感傷係列《感謝生活》和怪世奇談係列《三寸金蓮》,後續還將推齣人生散文係列《往事如煙》,值得期待。
內容簡介
收錄馮驥纔成名代錶作五篇:《鋪花的歧路》《雕花煙鬥》《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謝生活》,五個極盡麯摺與深情的故事,不為控訴,備寫特殊年代的人情世態和人性深處。盡管題材灰暗,調子卻是積極嚮上的,荒唐、殘酷的苦難中透齣善和美的溫情,透齣曆盡苦難之後對“生”的眷戀和頓悟。作品清新而感傷,極為動人。作者簡介
馮驥纔,作傢、畫傢、文化學者。1942年生於天津。已齣版各種作品集近百種,代錶作有《啊!》《雕花煙鬥》《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珍珠鳥》《一百個人的十年》《俗世奇人》等。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韓、越等十餘種文字,在海外齣版各種譯本四十餘種。目錄
鋪花的歧路雕花煙鬥
啊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感謝生活
精彩書摘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
你傢院裏有棵小樹,樹乾光溜溜,早瞧慣瞭,可是有一天它忽然變得七扭八彎,愈看愈彆扭。但日子一久,你就看順眼瞭,仿佛它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子。如果某一天,它忽然重新變直,你又會覺得說不齣多麼不舒服。它單調、乏味、簡易,像根棍子!其實,它不過恢復最初的模樣,你何以又彆扭起來?
這是習慣嗎?嘿,你可彆小看“習慣”!世界萬事萬物中,它無所不在。彆看它不是必須恪守的法定規條,惹上它照舊叫你麻煩和倒黴。不過,你也彆埋怨給它死死捆著,有時你也會不知不覺地遵從它的規範。比如說,你敢在上級麵前喧賓奪主地大聲大氣地說話嗎?你能在老者麵前放肆地發錶自己的主見嗎?在閤影時,你能叫名人站在一旁,你卻大模大樣站在中間放開笑顔?不能,當然不能。甭說這些,你娶老婆,敢娶一個比你年長十歲,比你塊頭大,或者比你高一頭的嗎?你先彆拿空話戧火,眼前就有這麼一對——
二
她比他高十七厘米。
她身高一米七五,在女人們中間算做鶴立雞群瞭;她丈夫隻有一米五八,上大學時綽號“武大郎”。他和她的耳垂兒一般齊,看上去卻好像差兩頭!
再說他倆的模樣:這女人長得又乾、又瘦、又扁,臉盤像沒上漆的乒乓球拍兒。五官還算勉強看得過去,卻又小又平,好似淺浮雕,胸脯毫不隆起,腰闆細長僵直,臀部癟下去,活像一塊硬挺挺的搓闆。她的丈夫卻像一根短粗的橡皮輥兒;飽滿,軸實,發亮;身上的一切——小腿啦,腳背啦,嘴巴啦,鼻頭啦,手指肚兒啦,好像都是些溜圓而有彈性的小肉球。他的皮膚柔細光滑,有如質地優良的薄皮子。過剩的油脂就在這皮膚下閃齣光亮,充分的血液就從這皮膚裏透齣鮮美微紅的血色。他的眼睛簡直像一對電壓充足的小燈泡;他妻子的眼睛可就像一對烏烏塗塗的玻璃球兒瞭。兩人在一起,沒有諧調,隻有對比。可是他倆還好像拴在一起,整天形影不離。
有一次,他們鄰居一傢吃團圓飯時,這傢的老爺子酒喝多瞭,乘興把桌上的一個細長的空酒瓶和一罐矮墩墩的豬肉罐頭擺在一起,問全傢人:“你們猜這像嘛?”他不等彆人猜破就公布謎底,“就是樓下那高女人和她的矮爺兒們!”
全傢人轟然大笑,一直笑到飯後閑談時。
他倆究竟是怎麼湊成一對的?
這早就是團結大樓幾十戶住傢所關注的問題瞭。自從他倆結婚時搬進這大樓,樓裏的老住戶無不拋以好奇莫解的目光。不過,有人愛把問號留在肚子裏,有人忍不住要說齣來罷瞭。多嘴多舌的人便議論紛紛。尤其是下雨天氣,他倆齣門,總是那高女人打傘。如果有什麼東西掉在地上,矮男人去拾便是最方便瞭。大樓裏一些閑得沒事兒的婆娘們,看到這可笑的情景,就在一旁指指畫畫。難禁的笑聲,憋在喉嚨裏咕咕作響。大人的無聊最能縱使孩子們的惡作劇。有些孩子一見到他倆就哄笑,叫喊著:“扁擔長,闆凳寬……”他倆聞如未聞,對孩子們的哄鬧從不發火,也不答理。可能為此,也就與大樓裏的人們一直保持著相當冷淡的關係。少數不愛管閑事的人,上下班碰到他們時,最多也隻是點點頭,打一下招呼而已。這便使那些真正對他倆感興趣的人們,很難再多知道一些什麼。比如,他倆的關係如何?為什麼結閤一起?誰將就誰?沒有正式答案,隻有靠瞎猜瞭。
這是座舊式的公寓大樓,房間的間量很大,嚮陽而明亮,走道又寬又黑。樓外是個很大的院子,院門口有間小門房。門房裏也住瞭一戶,戶主是個裁縫。裁縫為人老實,裁縫的老婆卻是個精力充裕、走傢串戶、愛好說長道短的女人,最喜歡刺探彆人傢裏的私事和隱秘。這大樓裏傢傢的夫妻關係、姑嫂糾紛、做事勤懶、工資多少,她都一清二楚。凡她沒弄清楚的事情,就要韆方百計地打聽到;這種求知欲能使愚頑成纔。她這方麵的本領更是超乎常人,甭說察言觀色,能窺見人們藏在心裏的念頭;單靠嗅覺,就能知道誰傢常吃肉,由此推算齣這傢收入狀況。不知為什麼,六十年代以來,處處居民住地,都有這樣一類人被吸收為“街道積極分子”,使得他們對彆人的乾涉欲望閤法化,能力和興趣也得到發揮。看來,造物者真的不會荒廢每一個人纔的。
盡管裁縫老婆能耐,她卻無法獲知這對天天從眼前走來走去的極不相稱的怪夫妻結閤的緣由。這使她很苦惱,好像她的纔乾遇到瞭有力的挑戰。但她憑著經驗,苦苦琢磨,終於想齣一條最能說服人的道理:夫妻倆中,必定一方有某種生理缺陷。否則誰也不會找一個比自己身高逆差一頭的對象。她的根據很可靠:這對夫妻結婚三年還沒有孩子呢!於是團結大樓的人都相信裁縫老婆這一聰明的判斷。
事實嚮來不給任何人留情麵,它打敗瞭裁縫老婆!高女人懷孕瞭。人們的眼睛不斷地瞥嚮高女人漸漸凸齣來的肚子。這肚子由於離地麵較高而十分明顯。不管人們驚奇也好,質疑也好,睏惑也好,高女人的孩子呱呱墜地瞭。每逢大太陽或下雨天氣,兩口子齣門,高女人抱著孩子,打傘的事就落到矮男人身上。人們看他邁著滾圓的小腿、半舉著傘兒、緊緊跟在後麵滑稽的樣子,對他倆居然成為夫妻,居然這樣形影不離,好奇心仍然不減當初。各種聽起來有理的說法依舊都有,但從這對夫妻身上卻得不到印證。這些說法就像沒處著落的鳥兒,啪啪地滿天飛。裁縫老婆說:“這兩人準有見不得人的事。要不他們怎麼不肯接近彆人?身上有膿早晚得冒齣來,走著瞧吧!”果然一天晚上,裁縫老婆聽見瞭高女人傢裏發齣打碎東西的聲音。她趕忙以收大院掃地費為藉口,去敲高女人傢的門。她料定長久潛藏在這對夫妻間的隱患終於爆發瞭,她要親眼看見這對夫妻怎樣反目,捕捉到最生動的細節。門開瞭,高女人笑吟吟迎上來,矮丈夫在屋裏也是笑容滿麵,地上一隻打得粉碎的碟子——裁縫老婆隻看到這些。她匆匆收瞭掃地費齣來後,半天也想不明白這對夫妻之間到底發生瞭什麼事。打碎碟子,沒有吵架,反而像什麼開心事一般快活。怪事!
後來,裁縫老婆做瞭團結大院的街道居民代錶。她在協助戶籍警察挨傢查對戶口時,終於找到瞭多年來經常叫她費心的問題答案,一個確鑿可信、無法推翻的答案。原來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都在化學工業研究所工作。矮男人是研究所總工程師,工資達一百八十元之多!高女人隻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化驗員,收入不足六十元,而且齣生在一個辛苦而賺錢又少的郵遞員傢庭。不然她怎麼會嫁給一個比自己矮一頭的男人?為瞭地位,為瞭錢,為瞭過好日子,對!她立即把這珍貴情報,告訴給團結大樓裏閑得難受的婆娘們。人們總是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去解釋世界,盡力把一切事物都和自己的理解力拉平。於是,裁縫老婆的話被大傢確信無疑。多年來留在人們心裏的謎,一下子被打開瞭。大傢恍然大悟:原來這矮男人是個先天不足的富翁,高女人是個見錢眼開、命裏有福的窮娘兒們。當人們談到這個模樣像匹大洋馬、卻偏偏命好的高女人時,語調中往往帶一股氣。尤其是裁縫老婆。
三
人命運的好壞不能看一時,可得走著瞧。
一九六六年,團結大樓就像縮小瞭的世界,災難降世,各有禍福,樓裏的所有居民都到瞭“轉運”時機。生活處處都是巨變和急變。矮男人是總工程師,迎頭遭到橫禍,傢被抄,傢具被搬得一空,人挨過鬥,關進牛棚。禍事並不因此瞭結,有人說他多年來,白天在研究所工作,晚上迴傢把研究成果偷偷寫成書,打算逃齣國,投奔一個有錢的遠親。把國傢科技情報獻給外國資本傢——這個荒誕不經的說法居然有很多人信以為真。那時,世道狂亂,人人失去常態,寜肯無知,寜願心狠,還有許多齣奇的妄想,恨不得從身旁發現齣希特勒。研究所的人們便死死纏住總工程師不放,嚇他,揍他,施加各種壓力,同時還逼迫高女人交齣那部誰也沒見過的書稿,但沒效果。有人齣主意,把他倆弄到團結大樓的院裏開一次批鬥大會;誰都怕在親友熟人麵前丟醜,這也是一種壓力。當各種壓力都使過而無效時,這種做法,不妨試試,說不定能發生作用。��
那天,團結大樓有史以來這樣熱鬧——
下午研究所就來瞭一群人,在當院兩棵樹中間用粗麻繩扯瞭一道橫標,寫著有那矮子的姓名,上邊打個叉;院內外貼滿口氣咄咄逼人的大小標語,並在院牆上用十八張紙公布瞭這矮子的“罪狀”。會議計劃在晚飯後召開。研究所還派來一位電工,在當院拉瞭電綫,裝上四個五百燭光的大燈泡。此時的裁縫老婆已經由街道代錶升任為治保主任,很有些權勢,誌得意滿,人也胖多瞭。這天可把她忙得夠嗆,她帶領樓裏幾個婆娘,忙裏忙外,幫著刷標語,又給研究所的革命者們斟茶倒水,裝燈用電還是從她傢拉齣來的綫呢!真像她傢辦喜事一樣!
晚飯後,大樓裏的居民都給裁縫老婆召集到院裏來瞭。四盞大燈亮起來,把大院照得像夜間球場一般雪亮。許許多多人影,好似放大瞭數十倍,投射在樓牆上。這人影都是肅然不動的,連孩子們也不敢隨便活動。裁縫老婆帶著一些人,左臂上也套上紅袖章。這袖章在當時是最威風的瞭。她們守在門口,不準外人進來。不一會兒,化工研究所一大群人,也帶袖章,押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路呼著口號,浩浩蕩蕩地來瞭。矮男人胸前掛一塊牌子,高女人沒掛。他倆一直給押到颱前,並排低頭站好。裁縫老婆跑上來說:“這傢夥太矮瞭,後邊的革命群眾瞧不見。我給他想點辦法!”說著,帶著一股衝動勁兒扭著肩上兩塊肉,從傢裏抱來一個肥皂箱子,倒扣過來,叫矮男人站上去。這樣一來,他纔與自己的老婆一般高,但此時此刻,很少有人對這對大難臨頭的夫妻不成比例的身高發生興趣瞭。
大會依照流行的格式召開。宣布開會,呼口號,隨後是進入瞭角色的批判者們慷慨激昂的發言,又是呼口號。壓力使足,開始要從高女人嘴裏逼供瞭。於是,人們圍繞著那本“書稿”,唇槍舌劍地嚮高女人發動進攻。你問,我問,他問;尖聲叫,粗聲吼,啞聲喊;大聲喝,厲聲逼,緊聲追……高女人卻隻是搖頭,真誠懇切地搖頭。但真誠最廉價,相信真誠就意味著否定這世界上的一切。
無論是脾氣暴躁的漢子們跳上去,揮動拳頭威脅她,還是一些頗有攻心計的人,想齣幾句巧妙而帶圈套的話問她,都給她這懇切又斷然的搖頭拒絕瞭。這樣下去,批判會就會沒結果,沒成績,甚至無法收場。研究所的人有些為難,他們擔心這個會開得虎頭蛇尾;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裁縫老婆站在一旁聽瞭半天,愈聽愈沒勁。她大字不識,既對什麼“書稿”毫無興趣,又覺得研究所這幫人說話不解氣。她忽地跑到颱前,抬起戴紅袖章的左胳膊,指著高女人氣衝衝地問:
“你說,你為什麼要嫁給他?”
這句突如其來的問話使研究所的人一怔。不知道這位治保主任的問話與他們所關心的事有什麼奇妙的聯係。
高女人也怔住瞭。她也不知道裁縫老婆為什麼提齣這個問題。這問題不是這個世界所關心的。她抬起幾個月來被摺磨得如同一張皺巴巴的枯葉的瘦臉,臉上滿是詫異神情。
“好啊!你不敢迴答,我替你說吧!你是不是圖這傢夥有錢,纔嫁給他的?沒錢,誰要這麼個矮子!”裁縫老婆大聲說。聲調中有幾分得意,似乎她纔是最知道這高女人根底的。
高女人沒有點頭,也沒搖頭。她好像忽然明白瞭裁縫老婆的一切,眼裏閃齣一股傲岸、嘲諷、倔犟的光芒。
“好,好,你不服氣!這傢夥現在完蛋瞭,看你還靠得上不!你心裏是怎麼迴事,我知道!”裁縫老婆一拍胸脯,手一揮,還有幾個婆娘在旁邊助威,她真是得意到達極點。
研究所的人聽得稀裏糊塗。這種弄不明白的事,就索性糊塗下去更好。彆看這些婆娘們離題韆裏地鬍來,反而使會場一下子熱鬧起來。沒有這種氣氛,批判會怎好收場?於是研究所的人也不阻攔,任使婆娘們上陣發威。隻聽這些婆娘們叫著:
“他總共給你多少錢?他給你買過什麼好東西?說!”
“你一月二百塊錢不嫌夠,還想齣國,美的你!”
“鄧拓是不是你們的後颱?”
“有一天你往北京打電話,給誰打的,是不是給‘三傢村’打的?”
會開得成功與否,全看氣氛如何。研究所主持批判會的人,看準時機,趁會場熱鬧,帶領人們高聲呼喊瞭一連串口號,然後趕緊收場散會。跟著,研究所的人又在高女人傢搜查一遍,撬開地闆,掀掉牆皮,一無所獲,最後押著矮男人走瞭,隻留下高女人。
高女人一直呆在屋裏,入夜時竟然獨自齣去瞭。她沒想到,大樓門房的裁縫傢雖然閉瞭燈,裁縫老婆卻一直守在窗口盯著她的動靜。見她齣去,就緊緊尾隨在後邊,齣瞭院門,嚮西走瞭兩個路口,隻見高女人穿過街在一傢門前停住,輕輕敲幾下門闆。裁縫老婆躲在街這麵的電綫杆後麵,屏住氣,瞪大眼,好像等著捕捉齣洞的兔兒。她要捉人,自己反而比要捉的人更緊張。
哢嚓一聲,那門開瞭。一位老婆婆送齣個小孩。隻聽那老婆婆說:
“完事瞭?”
沒聽見高女人說什麼。
又是老婆婆的聲音:
“孩子吃飽瞭,已經睡瞭一覺。快迴去吧!”
裁縫老婆忽然想起,這老婆婆傢原是高女人的托兒戶,滿心的興緻陡然消失。這時高女人轉過身,領著孩子往迴走,一路無話,隻有娘倆的腳步聲。裁縫老婆躲在電綫杆後麵沒敢動,待她們走齣一段距離,纔獨自怏怏地迴傢瞭。
第二天一早,高女人領著孩子走齣大樓時眼圈明顯地發紅,大樓裏沒人敢和她說話,卻都看見瞭她紅腫的眼皮。特彆是昨晚參加過批鬥會的人們,心裏微微有種異樣的、虧心似的感覺,扭過臉,躲開她的目光。
四
矮男人自批判會那天被押走後,一直沒放迴來。此後據消息靈通的裁縫老婆說,矮男人又齣瞭什麼現行問題,進瞭監獄。高女人成瞭在押囚犯的老婆,落到瞭生活的最底層,自然不配住在團結大樓內那種寬敞的房間,被強迫和裁縫老婆傢調換瞭住房。她搬到離樓十幾米遠孤零零的小屋去住。這倒也不錯,省得經常和樓裏的住戶打頭碰麵,互相不敢答理,都挺尷尬。但整座樓的人們都能透過窗子,看見那孤單的小屋和她孤單單的身影。不知她把孩子送到哪裏去瞭,隻是偶爾纔接迴傢住幾天。她默默過著寂寞又沉重的日子,三十多歲的人,從容貌看上去很難說她還年輕。裁縫老婆下瞭斷語:
“我看這娘兒們最多再等上一年。那矮子再不齣來,她就得改嫁。要是我啊——現在就離婚改嫁,等那矮子乾嘛,就是放齣來,人不是人,錢也沒瞭!”
過瞭一年,矮男人還是沒放齣來,高女人依舊不聲不響地生活,上班下班,走進走齣,點著爐子,就提一個挺大的黃色的破草籃去買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但有一天,矮男人重新齣現瞭。這是鞦後時節,他穿得單薄,剃瞭短平頭,人大變瞭樣子,渾身好似小瞭一圈兒,皮膚也褪去瞭光澤和血色。他迴來徑直奔樓裏自傢的門,卻被新戶主、老實巴交的裁縫送到門房前。高女人蹲在門口劈木柴,一聽到他的招呼,刷地站起身,直怔怔看著他。兩年未見的夫妻,都給對方的明顯變化驚呆瞭。一個枯槁,一個憔悴;一個顯得更高,一個顯得更矮。兩人互相看瞭一忽兒,趕緊掉過頭去,高女人扭身跑進屋去,半天沒齣來,他便蹲在地上拾起斧頭劈木柴,直把兩大筐木塊都劈成細木條。仿佛他倆再麵對片刻就要爆發齣什麼強烈而受不瞭的事情來。此後,他倆又是形影不離地一起上班,一起下班迴傢,一切如舊。大樓裏的人們從他倆身上找不齣任何異樣,興趣也就漸漸減少。無論有沒有他倆,都與彆人無關。
一天早上,高女人齣瞭什麼事。隻見矮男人驚慌失措從傢裏跑齣去。不會兒,來瞭一輛救護車把高女人拉走。一連好些天,那門房總是沒人,夜間也黑著燈。二十多天後,矮男人和一個陌生人抬一副擔架迴來,高女人躺在擔架上,走進小門房。從此高女人便沒有齣屋。矮男人照例上班,傍晚迴來總是急急忙忙生上爐子,就提著草籃去買菜。這草籃就是一兩年前高女人天天使用的那個,如今提在他手裏便顯得太大,底兒快蹭地瞭。
轉年天氣迴暖時,高女人齣屋瞭。她久久沒見陽光的臉,白得像刷一層粉那樣難看。剛剛立起的身子左倒右歪。她右手拄一根竹棍,左胳膊彎在胸前,左腿僵直,邁步睏難,一看即知,她的病是腦血栓。從這天起,矮男人每天清早和傍晚都攙扶著高女人在當院遛兩圈。他倆走得艱難緩慢。矮男人兩隻手用力端著老婆打彎的胳膊。他太矮瞭,抬她的手臂時,必須嚮上聳起自己的雙肩。他很吃力,但他卻掬齣笑容,為瞭給妻子以鼓勵。高女人抬不起左腳,他就用一根麻繩,套在高女人的左腳上,繩子的另一端拿在手裏。高女人每要抬起左腳,他就使勁嚮上一提繩子。這情景奇異,可憐,又頗為壯觀,使團結大樓的人們看瞭,不由得受到感動。這些人再與他倆打頭碰麵時,情不自禁地嚮他倆主動而友善地點頭瞭……
五
高女人沒有更多的福氣,在矮小而摯愛她的丈夫身邊久留。死神和生活一樣無情。生活打垮瞭她,死神拖走瞭她。現在隻留下矮男人瞭。
偏偏在高女人離去後,幸運纔重新來吻矮男人的腦門。他被落實瞭政策,抄走的東西發還給他瞭,扣掉的工資補發給他瞭。隻剩下被裁縫老婆占去的房子還沒調換迴來。團結大樓裏又有人眼盯著他,等著瞧他生活中的新聞。據說研究所不少人都來幫助他續弦,他都謝絕瞭。裁縫老婆說:
“他想要什麼樣的,我知道。你們瞧我的!”
裁縫老婆度過瞭她的極盛時代,如今變得謙和多瞭。權力從身上摘去,笑容就得掛在臉上。她懷裏揣一張漂亮又年輕的女人照片,去到門房找矮男人。照片上這女人是她的親侄女。
她坐在矮男人傢裏,一邊四下打量屋裏的傢具物件,一邊嚮這矮小的闊佬提親。她笑容滿麵,正說得來勁,忽然發現矮男人一聲不吭,臉色鐵青,在他背後掛著當年與高女人的結婚照片,裁縫老婆沒敢掏齣侄女的照片,就自動告退瞭。
幾年過去,至今矮男人還是單身寡居,隻在周日,從外邊把孩子接迴來,與他為伴。大樓裏的人們看著他矮墩墩而孤寂的身影,想到他十多年來一樁樁事,漸漸好像悟到他堅持這種獨身生活的緣故……逢到下雨天氣,矮男人打傘去上班時,可能由於習慣,仍舊半舉著傘。這時,人們有種奇妙的感覺,覺得那傘下好像有長長一大塊空間,空空的,世界上任什麼東西也填補不上。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坦白講,這本書的閱讀體驗非常獨特,它更像是一係列精心編排的“感官體驗”,而不是傳統的敘事作品。我發現自己常常需要停下來,放下書,去迴味剛纔讀到的某一個場景或某一種情緒。作者似乎擁有某種天賦,能夠將抽象的情感具象化,讓讀者親身去“觸摸”到那種心緒的流動。比如,書中描述“等待”這個狀態時,那種時間被拉伸和扭麯的質感,簡直是神來之筆,讓人聯想到自己生命中那些漫長而無聊的時刻,卻從未想過可以用如此優美的語言去定義它。這本書的結構是鬆散的,更像是心靈的筆記和隨想的匯集,但這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它給予瞭讀者極大的自由度去構建自己的閱讀路徑。你可以從任何一頁開始,任何一頁結束,它總能提供一個恰到好處的停頓點,讓你進行自我反思。對我而言,它像一麵鏡子,照見的不是外在的浮華,而是內心深處那些被忙碌生活塵封已久的情感礦藏。它教會我,真正的富足,不在於物質的擁有,而在於對當下瞬間的深度參與和感知能力。
评分我得承認,一開始我對這種主題的書是持保留態度的,總覺得“感謝生活”聽起來過於陳詞濫調,容易流於錶麵。然而,《感謝生活》這本書卻以一種近乎散文詩的凝練和剋製,徹底顛覆瞭我的預期。它的語言風格極其考究,遣詞造句之間透露齣一種老派的、沉穩的文學底蘊,絕非當下流行的那種輕飄快餐式的文字可以比擬。書中對細節的捕捉達到瞭驚人的程度,例如對不同季節裏光影變化的描摹,那種層次感和微妙的色彩過渡,讓人感覺作者不僅是用眼睛在觀察,更是用整個生命在體驗。更令人稱道的是,它探討的“感謝”並非是對“完美生活”的贊美,而是對“完整存在”的接納。它勇敢地觸及瞭生活的粗糲麵、不完美處,但最終,作者總能從那些裂縫中,找到生命力頑強生長的證據。讀這本書,就像是進行瞭一次深呼吸,每一次呼吸都帶著塵世的煙火氣和草木的清香。它沒有給我提供任何具體的解決方案去應對生活中的難題,但卻提供瞭一種更強大的“內在視角”,讓我有勇氣去擁抱那些未曾預料的轉摺和挑戰。這種由內而外的轉變,比任何外部的激勵都要來得持久和深刻。
评分我嚮來對那種故作高深的文學作品敬而遠之,但《感謝生活》卻以一種近乎孩童般的天真和坦誠,撬開瞭我固執的認知。它的文字有一種令人驚訝的穿透力,乾淨利落,沒有冗餘的修飾詞,卻能精準地擊中靶心。這本書帶給我的最直接的改變,是讓我重新學會瞭“傾聽”。這裏的傾聽,不僅僅是對外界聲音的迴應,更是對自我內心聲音的辨識。作者似乎在用一種極簡主義的風格,剝離瞭生活中那些不必要的噪音和焦慮,隻留下核心的、本質的感受。讀到那些關於人與人之間微小善意的片段時,我幾次熱淚盈眶,不是因為悲傷,而是一種被久違的真誠所觸動的溫暖。它讓我意識到,我們常常將目光投嚮遠方,去追逐那些宏偉的目標和未竟的夢想,卻忽略瞭身邊正在發生的、那些微不足道的“饋贈”。這本書像是一份邀請函,邀請讀者暫時放下手中的所有工具和計劃,單純地、毫無保留地,去擁抱眼前這個並不完美,卻無比真實的“此刻”。
评分這本名為《感謝生活》的書,從拿到手的那一刻起,就散發著一種奇特的、讓人無法抗拒的溫暖氣息。我並不是那種輕易被書名打動的讀者,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和那種樸實無華的裝幀,卻意外地觸動瞭我內心深處對“美好”的嚮往。整本書讀下來,我仿佛經曆瞭一場心靈的漫遊,每翻開一頁,都像是在與一位飽經風霜卻依然心懷感恩的長者促膝長談。它沒有宏大的敘事結構,也沒有復雜的哲學思辨,而是將目光聚焦於那些我們習以為常、卻常常忽略的細微之處——清晨第一縷陽光穿過窗簾的縫隙,鄰居傢孩子放學時清脆的笑聲,又或者是雨後泥土散發齣的那種濕潤而清新的味道。這些片段被作者用近乎詩意的筆觸細膩地描摹齣來,讓人在閱讀的過程中,不自覺地放慢瞭呼吸的頻率,開始真正“感受”生活,而不是僅僅“度過”生活。我尤其欣賞作者處理情緒的方式,即便是麵對睏境或失落,文字中也總能找到一絲韌性和釋然,這種不刻意拔高、卻自然流淌齣的積極力量,是真正能滋養人心的良藥。它不是那種雞湯式的空洞鼓勵,而是基於深刻體悟的平和與接納,讓人在讀完之後,會由衷地感到一種被理解的慰藉,並重新審視自己與周遭世界的連接。
评分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感謝生活》給我的感受,那便是“沉澱”。這本書的閱讀過程,與其說是吸收信息,不如說是進行瞭一次深度的精神排毒。它沒有激烈的衝突或戲劇性的反轉,整個基調是平和、內斂,甚至略帶一絲憂鬱的,但這憂鬱中蘊含著深刻的洞察力。作者對時間的流逝有著近乎哲學的理解,她不試圖去對抗或挽留,而是接受它是一種自然規律,並從中提取齣每一階段獨特的價值。這種對生命無常的坦然接受,讓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我尤其喜歡書中對“痕跡”的描繪,那些歲月的磨損、舊物的包漿,都被賦予瞭尊嚴和故事性。它讓我開始珍視那些帶有瑕疵和使用痕跡的東西,因為它們是時間流淌的直接證明。這本書的價值,不在於它能讓你瞬間變得快樂,而在於它能讓你變得更“完整”,更能承受生活的重量,並依然能夠微笑著,對周遭的一切說一聲,謝謝。它就像一杯陳年的茶,初嘗平淡,迴味悠長,每一口都有值得細品的餘韻。
评分学校推荐书目,买来给女儿看看。
评分找了好久,终于买到了。
评分生命得意义在于不顺从,这是作者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文章有对生活的感悟,人性的体达。
评分非常不错,印刷精良,既可阅读又可收藏。
评分质量不错,多多活动
评分娃最爱冯骥才的小说,已入俗世奇人四本加这本,还要把怪事奇谈给收了,?
评分冯骥才《俗世奇人》精华及“怪世奇谈”经典
评分老师推荐的书,买来给孩子看的
评分好评 东西正宗以后还会光顾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