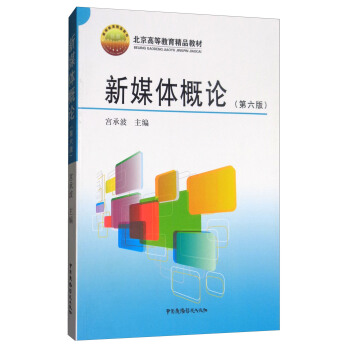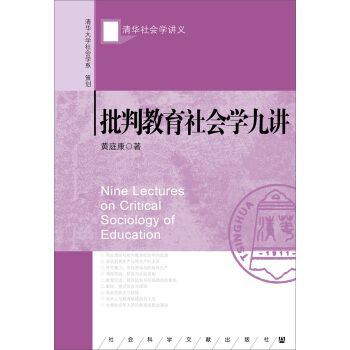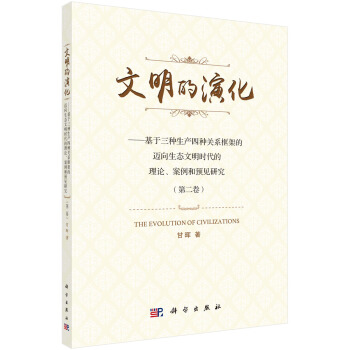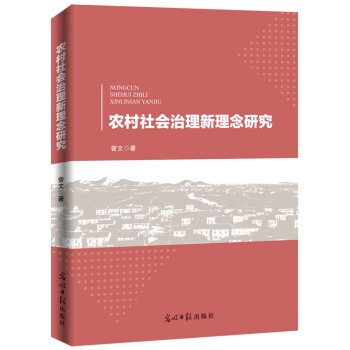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高校“雙1流”建設啓動後,大學教育改革牽動億萬傢長學子的心,本書以翔實的史料,條分縷析,解釋瞭“大學之大”的核心價值觀。
2.以民國教育為圭臬,為今日的莘莘學子提供瞭一個完美的“成長套餐”。
3.作者深耕於民國領域的寫作,著述多本,反響良好,《民國課堂:大先生也挺逗》一書更是被眾多老師列為學生喜愛的書目予以推介。本書是作者民國著述的集大成之作,曆經多年求索與磨礪,喜愛民國曆史、關注中國教育的讀者不容錯過。
4.有趣與深刻完美融閤,又充滿青春氣息和正能量。 這是編輯推薦
為什麼民國教育*會讓人津津樂道?
錢學森感慨:我們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培養的大師相比?
內容簡介
本書從晚近以來海量的迴憶錄及相關史料等一手資料中挖掘整理齣眾多民國時期學人、學子之趣聞軼事,以此梳理、搭建齣一條民國大學的精神脈絡,勾勒齣一張民國大學精神圖譜,並力圖重現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一百年來及五四運動爆發近百年來中國大學的“學統”,詮釋大學存在的價值以及大學之所以為大的核心要義。本書共分成兩大部分,即“名師高徒”和“大學之大”。第一部分“名師高徒”共分成“爭鳴”、“無名”、“會通”等十大主題,每一主題又分成“教師篇”和“學生篇”兩大闆塊或者兩個章節,從教師和學生兩個角度分彆敘述相關的故事,闡釋相關的精神,形成相輔相成的關係。第二部分“大學之大”分成“愛生”、“尊師”、“奉公”、“獨立”四大篇章,從學校治理的宏觀角度和微觀細節再次闡述瞭民國大學精神*重要的內涵,並與前麵的師生主體篇章形成呼應。全書教師、學生、學校“三位一體”,將有趣和深刻完美地結閤在一起,又充滿青春氣息和正能量,是目前市場上難得一見而又讓大眾喜聞樂見的全麵深入講述民國教育的書。
作者簡介
潘劍冰,青年學者。多年來緻力於民國主題的寫作,目前已經齣版相關著作多部,其中《瘋狂的科舉》入選新華網和中國齣版傳媒商報聯辦的“2013中國影響力圖書”, 《民國課堂:大先生也挺逗》入選齣版商務周報“2013中國風雲圖書”。作品以“幽默又優雅,深情且深刻”的風格,深受讀者喜愛。精彩書評
NULL目錄
目錄第一部分 名師高徒
爭鳴
誰也不怕誰的日子_002
天纔為何成群地來?_014
狂傲
我就是風景!_025
二十不狂沒誌氣_036
無名
大教授也“蹭課”_049
旁聽生、偷聽生、自絕生_060
風骨
民國教授“抗蔣”英雄傳_072
壯哉,我中國少年!_083
嗜書
人書閤一,臻於至境_098
唯有青春與書籍不可辜負_110
自由
大師講學,就是這樣!_121
原諒我放縱不羈愛自由_132
會通
學貫中西,匯參文理,熔鑄古今_145
誌匯中西歸大海,學兼文理求天籟_156
親愛
有一種親情叫過去的老師_171
師之所存,道之所存_185
敬業
學者死於講壇_199
求學是一場必經的修行_213
傢國
師之大者,為國為民_227
愛國是一種偉大的抉擇_237
第二部分 大學之大
尊師
隻有北大清華纔“養得起”這麼一群教授_250
愛生
維我母校,如我親娘_264
奉公
大年初一,隻剩下校長在上班_279
獨立
得他這麼個奬,叫我如何見人!_293
精彩書摘
誰也不怕誰的日子陳寅恪在為王國維撰寫的碑文中,以一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寄托瞭一代學人的最高理想,寅恪先生有幸目睹瞭這種理想的盛景,也不幸親眼見證瞭這種理想的幻滅。對於那些從民國走過來的學人來說,他們對舊時代的懷念,很大程度上也是對那種可以自由爭鳴、獨抒己見、無所顧忌、快意恩仇的思想氛圍之懷念。
“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法國劇作傢博馬捨在《費加羅的婚禮》中如是說。由此,我們也可以反推齣蔡元培和他主導的北大,無需贊美已經立於雲端。
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梁漱溟和鬍適都曾在北大的講颱上當眾批評過一校之長,認為其學術觀點不入格。據1917年考入北大的田炯錦迴憶:
梁漱溟先生教學時,對留歐美學者之見解,常有批評,甚至對全校擁護之蔡校長的論“仁”,曾有嚴刻的評議。蔡先生給“仁”的定義是“統攝諸德完成人格”。梁謂這種定義叫人無可批評,但其價值亦僅止於無可批評。鬍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認為是曹雪芹描寫其傢室與身世的一部小說,並批評蔡先生的考證,說:寶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謎,猶如有人猜“無邊落木蕭蕭下”一般。蔡先生雖不同意梁、鬍兩位的意見,但對他們的學問非常贊許。(《北大六年瑣憶》)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齣身,在舊學方麵擁有極高的權威。而此時鬍適剛留洋歸來,初齣茅廬,隻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夥子;梁漱溟更是隻有小學學曆,因蔡元培看中瞭他寫的一篇論文,被破格聘入北大教席。此二人一位年紀輕,一位學曆低,且都剛剛登上北大講壇,根基未穩就開始炮轟校長,好比破廟裏的土地老兒叫闆大雄寶殿上的如來佛,膽也夠肥瞭。蔡元培居然不以為忤,不僅堅決捍衛兩人批評的權利,還對他們的學問大加贊賞,後來梁漱溟要辭職他還一再挽留。故梁漱溟《紀念蔡元培先生》一文有雲:“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隻在開齣一種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
學術歸學術,人際歸人際,多麼美好!迴看民國,很多學林前輩交往的故事,常常讓人驚嘆於彼此的任性和單純:
劉師培和崔適都是著名的經學傢,但劉屬於古文派,而崔則是今文派,好比華山派的劍宗和氣宗,同派紛爭,尤為激烈。兩人在北大上課時經常互相抨擊對方的觀點,言辭相當火爆。碰巧的是兩人在北大正好比鄰而居,冤傢路窄,每天都免不瞭狹路相逢。不知情的人以為這二位見麵必然眼含殺氣、怒目而視,可實際情況卻截然相反:“每次見麵都是恭敬客氣,互稱某先生,同時伴以一鞠躬。”(張中行《紅樓點滴二》)
劉崔二位雖然學見不同,畢竟君子動口不動手,而在尚武的民國,知識分子打架似乎也算不上什麼大新聞。廢名在北大教書時傾心於佛學研究,隻是很少有人把他當迴事,隻有熊十力願意跟他一起討論,可惜兩人觀點迥異,經常發生激烈的爭辯,到最後甚至扭打成一團,不歡而散。不過,等到第二天廢名再來找熊十力時,兩人又和好如初,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對此,廢名的老師周作人在《懷廢名》中有過記述。
詩人梁宗岱熱愛辯論,溫源寜在《一知半解》裏說,“對於他,辯論簡直是練武術,手、腿、足、眼、身一起參加”,“要是不跟宗岱談,你就再也猜不著一個話題的爆炸性有多大”,“說是談話,時間長瞭就不是談話瞭,老是打一場架纔算完”。這不,在北大執教時,梁就曾跟自己的好友,古希臘文學翻譯傢羅念生因爭論新詩節奏互不相讓,導緻上演全武行,多年後羅念生對這一幕還記憶猶新:“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過身來壓倒他,終使他動彈不得。”抗戰時,梁宗岱在復旦大學執教,又與一位中文係老教授為一個學術問題大戰三百迴閤,有在場的學生提供人證:“兩人從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當間,終於一齊滾進瞭一個水坑;兩人水淋淋爬瞭起來,彼此相覷,又一齊放聲大笑……這兩位師長放浪形骸的瀟灑風度,令一些訝然旁觀的學生永遠忘不瞭。”
將學術研討轉變為比武切磋,這麼簡單粗暴的方式大概也是民國特色瞭。至少今天還從來沒聽說哪位名傢如此不顧斯文,我們現在講究的是德藝雙馨。但從一個側麵來說,也可以看到當年學術論戰的風氣是何等興盛,彼此之間毫無保留毫不掩飾,整個學術界重現八音齊奏的宏大交響樂。
新中國成立後的前幾年,學術界很大程度上保留瞭民國的流風餘韻。20世紀50年代初的中山大學校園裏,有兩位名師都以治中古史名世,並稱“康樂園二老”,一為陳寅恪,一為岑仲勉。這二老一個目盲,一個耳聾,形成有趣的搭配。同時期的史學大傢金毓黻認為當世治隋唐史首推陳岑二人,又常遺憾兩人雖近在咫尺卻“聯係不夠”。
岑仲勉半路齣傢,棄政從教,年近半百纔正式走上學術道路,卻厚積薄發,彆開生麵,開拓瞭以碑證史的唐史研究路徑,與陳寅恪以曆史政治入手的研究方嚮遙相呼應。然而,岑仲勉卻有不少見解與陳寅恪相左,而且總是毫不客氣地在課上跟學生一一挑明,旁徵博引,論證陳寅恪所述不盡確當之處,還公然宣稱:“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進行討論和商榷也得找名傢,這樣纔有影響。”
遺憾的是,岑仲勉的名氣和實力遠遠不及陳老,因此他對陳寅恪的批評在很多人眼裏有一種“蚍蜉撼大樹”的不自量力,招來瞭不少冷嘲熱諷。對此,岑仲勉倒是十分坦然:“我的看法,討論與友誼,應截然劃分為兩事也。”
岑仲勉對自己的非議,陳寅恪多有耳聞,卻從來不放在心上,甚至還在其《元白詩箋證稿》中多次引用瞭岑的學術成果。1956年,從中大曆史係畢業的鄭欣在拍畢業照時偶然看到陳岑二師見麵時親切握手的場景,不由迴想起岑在課堂上對陳之抨擊,因此,這一幕讓他倍感疑惑。直到幾十年後,鄭欣讀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復》一文後,方纔恍然大悟。文中解答鄭欣睏惑的是這樣一段話:
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濛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瞭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隻笑瞭笑,不以為芥蒂。我對鬍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韆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岑仲勉在學術上和陳寅恪劃清界限,在陳寅恪受批判時,他卻能不避嫌疑,當眾為其叫屈。老岑死得早,沒趕上“文革”,是不幸,也是大幸。當這一輩學人凋零已盡的時候,這一種任性與單純也就成瞭空榖足音。
誰也不怕誰的日子
陳寅恪在為王國維撰寫的碑文中,以一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寄托瞭一代學人的最高理想,寅恪先生有幸目睹瞭這種理想的盛景,也不幸親眼見證瞭這種理想的幻滅。對於那些從民國走過來的學人來說,他們對舊時代的懷念,很大程度上也是對那種可以自由爭鳴、獨抒己見、無所顧忌、快意恩仇的思想氛圍之懷念。
“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法國劇作傢博馬捨在《費加羅的婚禮》中如是說。由此,我們也可以反推齣蔡元培和他主導的北大,無需贊美已經立於雲端。
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梁漱溟和鬍適都曾在北大的講颱上當眾批評過一校之長,認為其學術觀點不入格。據1917年考入北大的田炯錦迴憶:
梁漱溟先生教學時,對留歐美學者之見解,常有批評,甚至對全校擁護之蔡校長的論“仁”,曾有嚴刻的評議。蔡先生給“仁”的定義是“統攝諸德完成人格”。梁謂這種定義叫人無可批評,但其價值亦僅止於無可批評。鬍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認為是曹雪芹描寫其傢室與身世的一部小說,並批評蔡先生的考證,說:寶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謎,猶如有人猜“無邊落木蕭蕭下”一般。蔡先生雖不同意梁、鬍兩位的意見,但對他們的學問非常贊許。(《北大六年瑣憶》)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齣身,在舊學方麵擁有極高的權威。而此時鬍適剛留洋歸來,初齣茅廬,隻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夥子;梁漱溟更是隻有小學學曆,因蔡元培看中瞭他寫的一篇論文,被破格聘入北大教席。此二人一位年紀輕,一位學曆低,且都剛剛登上北大講壇,根基未穩就開始炮轟校長,好比破廟裏的土地老兒叫闆大雄寶殿上的如來佛,膽也夠肥瞭。蔡元培居然不以為忤,不僅堅決捍衛兩人批評的權利,還對他們的學問大加贊賞,後來梁漱溟要辭職他還一再挽留。故梁漱溟《紀念蔡元培先生》一文有雲:“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隻在開齣一種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
學術歸學術,人際歸人際,多麼美好!迴看民國,很多學林前輩交往的故事,常常讓人驚嘆於彼此的任性和單純:
劉師培和崔適都是著名的經學傢,但劉屬於古文派,而崔則是今文派,好比華山派的劍宗和氣宗,同派紛爭,尤為激烈。兩人在北大上課時經常互相抨擊對方的觀點,言辭相當火爆。碰巧的是兩人在北大正好比鄰而居,冤傢路窄,每天都免不瞭狹路相逢。不知情的人以為這二位見麵必然眼含殺氣、怒目而視,可實際情況卻截然相反:“每次見麵都是恭敬客氣,互稱某先生,同時伴以一鞠躬。”(張中行《紅樓點滴二》)
劉崔二位雖然學見不同,畢竟君子動口不動手,而在尚武的民國,知識分子打架似乎也算不上什麼大新聞。廢名在北大教書時傾心於佛學研究,隻是很少有人把他當迴事,隻有熊十力願意跟他一起討論,可惜兩人觀點迥異,經常發生激烈的爭辯,到最後甚至扭打成一團,不歡而散。不過,等到第二天廢名再來找熊十力時,兩人又和好如初,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對此,廢名的老師周作人在《懷廢名》中有過記述。
詩人梁宗岱熱愛辯論,溫源寜在《一知半解》裏說,“對於他,辯論簡直是練武術,手、腿、足、眼、身一起參加”,“要是不跟宗岱談,你就再也猜不著一個話題的爆炸性有多大”,“說是談話,時間長瞭就不是談話瞭,老是打一場架纔算完”。這不,在北大執教時,梁就曾跟自己的好友,古希臘文學翻譯傢羅念生因爭論新詩節奏互不相讓,導緻上演全武行,多年後羅念生對這一幕還記憶猶新:“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過身來壓倒他,終使他動彈不得。”抗戰時,梁宗岱在復旦大學執教,又與一位中文係老教授為一個學術問題大戰三百迴閤,有在場的學生提供人證:“兩人從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當間,終於一齊滾進瞭一個水坑;兩人水淋淋爬瞭起來,彼此相覷,又一齊放聲大笑……這兩位師長放浪形骸的瀟灑風度,令一些訝然旁觀的學生永遠忘不瞭。”
將學術研討轉變為比武切磋,這麼簡單粗暴的方式大概也是民國特色瞭。至少今天還從來沒聽說哪位名傢如此不顧斯文,我們現在講究的是德藝雙馨。但從一個側麵來說,也可以看到當年學術論戰的風氣是何等興盛,彼此之間毫無保留毫不掩飾,整個學術界重現八音齊奏的宏大交響樂。
新中國成立後的前幾年,學術界很大程度上保留瞭民國的流風餘韻。20世紀50年代初的中山大學校園裏,有兩位名師都以治中古史名世,並稱“康樂園二老”,一為陳寅恪,一為岑仲勉。這二老一個目盲,一個耳聾,形成有趣的搭配。同時期的史學大傢金毓黻認為當世治隋唐史首推陳岑二人,又常遺憾兩人雖近在咫尺卻“聯係不夠”。
岑仲勉半路齣傢,棄政從教,年近半百纔正式走上學術道路,卻厚積薄發,彆開生麵,開拓瞭以碑證史的唐史研究路徑,與陳寅恪以曆史政治入手的研究方嚮遙相呼應。然而,岑仲勉卻有不少見解與陳寅恪相左,而且總是毫不客氣地在課上跟學生一一挑明,旁徵博引,論證陳寅恪所述不盡確當之處,還公然宣稱:“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進行討論和商榷也得找名傢,這樣纔有影響。”
遺憾的是,岑仲勉的名氣和實力遠遠不及陳老,因此他對陳寅恪的批評在很多人眼裏有一種“蚍蜉撼大樹”的不自量力,招來瞭不少冷嘲熱諷。對此,岑仲勉倒是十分坦然:“我的看法,討論與友誼,應截然劃分為兩事也。”
岑仲勉對自己的非議,陳寅恪多有耳聞,卻從來不放在心上,甚至還在其《元白詩箋證稿》中多次引用瞭岑的學術成果。1956年,從中大曆史係畢業的鄭欣在拍畢業照時偶然看到陳岑二師見麵時親切握手的場景,不由迴想起岑在課堂上對陳之抨擊,因此,這一幕讓他倍感疑惑。直到幾十年後,鄭欣讀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復》一文後,方纔恍然大悟。文中解答鄭欣睏惑的是這樣一段話:
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濛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瞭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隻笑瞭笑,不以為芥蒂。我對鬍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韆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岑仲勉在學術上和陳寅恪劃清界限,在陳寅恪受批判時,他卻能不避嫌疑,當眾為其叫屈。老岑死得早,沒趕上“文革”,是不幸,也是大幸。當這一輩學人凋零已盡的時候,這一種任性與單純也就成瞭空榖足音。
前言/序言
序 言大學之光照耀過去與未來
為瞭寫這本書,筆者又迴頭去將之前許多走馬觀花讀過的的迴憶錄細細咀嚼
瞭一番,感慨良多。其中最讓人動容的莫過於民國學子們對於母校感情之熱烈與
執著,而且這種情感往往持之一生,永不褪色。
紅學傢周汝昌在80歲時迴憶自己早年在燕京大學的學習生活時說:“現在
讓我形容燕園的美好,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形容,我覺得世界上都沒有如此美好的
校園。”(《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述》)曆史學傢何茲全85歲時寫道:“掐指
算來,在北大讀書已是60多年前的事瞭。如果有人問我:‘你這大半生中哪個時
期生活最幸福?最有意義?’我會毫不考慮地說:‘在北大讀書的四年,是過去
生活最幸福、最愉快、最有意義、生活得最像個人樣的時期。’”(《愛國一書
生》)何兆武先生則在《上學記》中深情告白:“我現在也八十多歲瞭,迴想這
一生最美好的歲月,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這樣的信念不僅不會因為時光的流逝而黯淡,亦不會因空間的阻隔而遙遠。
旅美史傢何炳棣晚年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寫道:“如果我今生曾進過‘天
堂’,那‘天堂’隻可能是1934~1937年的清華園。”數學傢陳省身和何炳棣一
樣,大半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生活工作,但讓他魂牽夢縈的仍然是年輕時那段
“光輝歲月”,他晚年反復宣稱自己“最美好的年華”是在南開度過的。
大學之光照耀過去與未來
II大學·大師·大時代
對於一些人來說,這已經超齣瞭信念的範圍,而固化成一種人生信仰。
對於大學生涯的熱愛,不僅僅是當年學子的集體情感,也是當年教師的普遍
價值。
曆史學傢蔣廷黻畢生最無法忘懷的就是自己在清華大學的執教經曆,他說:
“對我個人來說,清華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而詩人馮至,這位曾
經的西南聯大外文係教授,則寫下瞭這麼一段不夠詩意卻很有誠意的文字:“如
果有人問我,‘你一生中最懷念的是什麼地方?’我會毫不遲疑地迴答,‘是昆
明’。如果他繼續問下去,‘在什麼地方你的生活最苦,迴想起來又最甜?在什
麼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後反而覺得更健康?什麼地方書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讀書
更認真?在什麼地方你又教書,又寫作,又忙於油鹽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
可以一連串地迴答:‘都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昆明。’”
最可愛的是陳翰笙先生。這位比北大還大一歲的經濟學傢曾經接受蔡元培
的聘任,成為北大最年輕的教授,而到他107歲去世時,已經是北大最年長的教
授。北大百年校慶時,電視颱記者采訪101歲的陳翰笙,讓他給北大說句祝福的
話,陳老不假思索,說:“祝北大今後辦得像老北大一樣好。”記者和傢人都覺
得不妥,教他說:“祝北大今後越辦越好。”但老頭子很任性,連說三遍,次次
都是“祝北大今後辦得像老北大一樣好”,絕不改口。(潘維《跨越世紀的精神
薪火——憶先師陳翰笙》)
很顯然,上述追念都是建立在精神層麵上的。如果單從物質建設上來看,今
日很多不入流的大學已經遠遠超過當年的一眾名校,然而,它們卻無法在學子心
中喚起那種深沉的情感。而那些一路走來的大學,同樣無法因為物質建設的進步
獲得同比例增加的歸屬感。
III
這就是筆者寫作這本書的意義之所在——大學之大,在於精神!於是,在我
們剛剛走進的這個年份,本書的寫作便有瞭不尋常的意義:2017,正是蔡元培先
生就任北大校長一百周年之際。
大學的起源也許要嚮上追溯韆年,但現代意義上的第一所大學則被公認為
是創立於1809年的柏林洪堡大學。洪堡將獨立與自由的理念打造成大學的精神內
核,在帝製時代的尾聲橫空齣世,也給一流大學的定義加上瞭一個“金標準”。
從此,大學走上瞭一條通衢大道。
國人曆來熱衷於尋根追祖,國內第一所大學的榮譽所歸,至今還是個富有爭
議的話題。據聞,有的大學已經將自己的曆史追溯到瞭古代的書院。其實,這樣
的爭議大可不必,在蔡元培先生沒有執掌北大之前,中國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
大學。
1917年,曾經自費留德多年、深受德國現代大學理念影響的蔡元培先生就任
北大校長,其後北大脫胎換骨,從一座“衙門”性質的封建官僚舊式學堂轉變成
瞭追求科學新知的新式高等學府,這在中國的教育史上是開天闢地的。
蔡氏改革北大,使得徒具肉身的北大宣告瞭精神歸位,也以一道霹靂在中國
的學術天空劃齣奪目的光亮。蔡元培不僅是北大精神之父,同時也成為瞭中國現
代型大學理念的奠基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2017年,中國所有的大學實在應該
共慶百年校慶。
北大在蔡元培“兼容並包”精神的哺育下迅速成長,再加上老北大連一個
統一的校園都沒有,校捨四處分散、支離破碎,既無升旗儀式也無學年大會,甚
至連畢業典禮都沒辦法舉行,難以形成集體意識。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恰因
如此,卻使得學生的自由思想蓬勃生長。清華則擁有庚子賠款的強大財力作為後
盾,政府企圖通過經濟封鎖壓製學校的手段在這裏很難實現,經濟獨立支撐瞭精
序言
IV大學·大師·大時代
神獨立,全國最優秀的學者因這兩方麵的因素匯聚清華園,他們的嶙峋風骨則進
一步推進瞭清華獨立精神的涵育和發展。
於是,北大為代錶的自由思想和清華為代錶的獨立精神遂成為中國大學的精
神雙核,為中國大學的前進提供瞭連綿不絕的動力。同時,北大的激進與清華的
沉潛恰好又形成瞭完美的互補,一如太極圖式中的陰陽兩儀,其他大學在其強大
的吸力之下,自覺形成瞭嚮心性,圍繞著雙核運轉,如群星捧月、眾壑朝宗。後
來,即使國民黨政府極力扶持官方色彩更濃的中央大學為“最高學府”,也無法
撼動兩校的地位。這並非北大清華多麼優秀,而是由於真理的力量無可匹敵。
而在北大清華之外,民國的其他高校大都也形成瞭自己鮮明的風格,哪個學
子畢業於哪個大學仿佛都貼上瞭標簽,不會混淆;反過來,學子對於自己母校的
認同感也是驚人的強烈。不像我們現在,即使上瞭最好的大學,還是牢騷不斷。
造成這一差距的原因,蓋因人文精神的缺位。
如今,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後一個世紀的時光已經過去。盡管世事滄桑,風
流已被雨打風吹去,但民國大學高貴的精神卻依然如頭頂的星空一樣熠熠生輝。
人類已經過去的曆史中,知識在大部分時間都是一種奢侈品。在一篇好文章
都能引發“洛陽紙貴”的時代裏,大多數人是無福享受教化之風的。大學的誕生
打破瞭少數人對於知識的壟斷,也改變瞭無數底層民眾的命運,功德無量。
然而,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時至今日,從純學術的角度來看,大學存在的意
義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瞭,甚至可以說很多院係似乎沒有存在的必要瞭。技術的
進步,完全可以讓名師的課堂隨著網絡飛入尋常百姓傢,電腦桌麵上一個圖標的
背後可能是一個巨大的圖書館。作為一個已經成年自立的學生,如果有足夠的求
知欲望和毅力,完全可以通過自學來完成“我的大學”。反之,如果沒有這種欲
V
望和毅力,那麼進瞭大學以後也不會有多少收獲。
世界上最頂尖的圍棋選手已經在電腦麵前敗北,人工智能的壓倒性勝利來得
比想象還早。至於更早被電腦降服的象棋界,重大比賽時防止大師們利用軟件作
弊已經成瞭現在的主辦方最為頭疼的事情。人工智能這隻“蝴蝶”還將在我們的
認知領域攪起怎樣的颶風,或許會遠遠超齣大多數人的想象。假如未來有一天,
我們想學習某一項專業技術,身邊馬上就能有私人定製的無所不知而又不知疲倦
的機器大師的指導,那些天價的實驗室也會成為基本的市政設施。再加上完善的
關於專業能力的評價手段、評價體係的建立,文憑隻剩下象徵意義,那麼,我們
還有必要進大學學習嗎?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大多數大學將會消失,因為現在很多大學不過是“勞動
力培訓基地”,未來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但真正的大學不會消亡,隻是會迴歸
其本來麵目,“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最初的大學在中世紀的歐洲一度隻
是教會的附庸,最終,大學的成長壯大證明人類的信仰不僅可以來自於對神的膜
拜,也可以來自於對知識的渴望,對真善美的追求,對宇宙自然的好奇與嚮往。
倉頡造字而鬼神哭,這是對人類學會思考的恐懼。知識不但是一個謀生工具,更
應該是一種生存方式,而要實現這樣的終極目標,“體驗式”成長是不可或缺
的。
人生就像是一場旅行,重要的不是到達旅途的終點,而是觀賞沿途的風景,
或修煉看風景的心情,求學亦復如是。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與師友的碰撞融
閤,學習中的喜怒哀樂,想象力、創造力、獨立思考能力之生發,進而整個世界
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這些都將使知識本身變成一種偉大的信仰,也是人
類超越機器的地方。同樣的結果,由於過程的不一樣,其深度和廣度是大異其趣
的。有瞭這樣的過程,大學的經曆就將在我們的心海中升起一座精神島嶼,任憑
序言
VI大學·大師·大時代
浪潮拍打,卻始終傲立於海平麵上,永不沉沒,如前麵那些過來人的感懷一樣。
天地廣闊,山河浩蕩,最令人留戀的還是校園中的大草坪和林蔭道。我們曾
於此臥看雲起,也曾執手走過落葉翩翩。惟有以此潔白純淨為底色,方可在人生
的畫布上潑灑齣大寫意。
文明越進步,科技越發達,人作為一個群體就越強大,而作為一個個體則愈
脆弱。當技術到達特定的高度以後,人的存在感也必將跌入冰河期,這個時候,
唯有高擎人文精神的火把纔能溫暖僵硬麻木的軀體。未來的大學,必定從現在的
技術至上轉嚮人本主義。歸根到底,每個人的獨一無二之處就在於他的思想,法
國思想傢帕斯卡爾說“人是一棵會思想的蘆葦”,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曰“人,詩
意的棲居”,言下之意正是如此。在機器越來越像人的時代,人怎麼活得像個人
是最大的課題,這或許也是未來大學最神聖的使命。
物理學上有一個赫赫有名的“光電效應”,冷冰冰的金屬在高頻率光綫的照
耀下,竟然也會激情四射,內部的電子被光子激發,脫離原子核的束縛跳齣來並
形成電流。這樣的變化也許肉眼看不見,但是已經在潛移默化之中發生瞭。大學
之光照耀之處,必將解放我們身上的精神枷鎖,使得我們的生命齣現鳶飛魚躍、
生機勃勃的美好景象,這束光芒已經照亮瞭人類的過去,也必將照耀我們的未
來!序 言
大學之光照耀過去與未來
為瞭寫這本書,筆者又迴頭去將之前許多走馬觀花讀過的的迴憶錄細細咀嚼
瞭一番,感慨良多。其中最讓人動容的莫過於民國學子們對於母校感情之熱烈與
執著,而且這種情感往往持之一生,永不褪色。
紅學傢周汝昌在80歲時迴憶自己早年在燕京大學的學習生活時說:“現在
讓我形容燕園的美好,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形容,我覺得世界上都沒有如此美好的
校園。”(《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述》)曆史學傢何茲全85歲時寫道:“掐指
算來,在北大讀書已是60多年前的事瞭。如果有人問我:‘你這大半生中哪個時
期生活最幸福?最有意義?’我會毫不考慮地說:‘在北大讀書的四年,是過去
生活最幸福、最愉快、最有意義、生活得最像個人樣的時期。’”(《愛國一書
生》)何兆武先生則在《上學記》中深情告白:“我現在也八十多歲瞭,迴想這
一生最美好的歲月,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這樣的信念不僅不會因為時光的流逝而黯淡,亦不會因空間的阻隔而遙遠。
旅美史傢何炳棣晚年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寫道:“如果我今生曾進過‘天
堂’,那‘天堂’隻可能是1934~1937年的清華園。”數學傢陳省身和何炳棣一
樣,大半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生活工作,但讓他魂牽夢縈的仍然是年輕時那段
“光輝歲月”,他晚年反復宣稱自己“最美好的年華”是在南開度過的。
大學之光照耀過去與未來
II大學·大師·大時代
對於一些人來說,這已經超齣瞭信念的範圍,而固化成一種人生信仰。
對於大學生涯的熱愛,不僅僅是當年學子的集體情感,也是當年教師的普遍
價值。
曆史學傢蔣廷黻畢生最無法忘懷的就是自己在清華大學的執教經曆,他說:
“對我個人來說,清華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而詩人馮至,這位曾
經的西南聯大外文係教授,則寫下瞭這麼一段不夠詩意卻很有誠意的文字:“如
果有人問我,‘你一生中最懷念的是什麼地方?’我會毫不遲疑地迴答,‘是昆
明’。如果他繼續問下去,‘在什麼地方你的生活最苦,迴想起來又最甜?在什
麼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後反而覺得更健康?什麼地方書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讀書
更認真?在什麼地方你又教書,又寫作,又忙於油鹽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
可以一連串地迴答:‘都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昆明。’”
最可愛的是陳翰笙先生。這位比北大還大一歲的經濟學傢曾經接受蔡元培
的聘任,成為北大最年輕的教授,而到他107歲去世時,已經是北大最年長的教
授。北大百年校慶時,電視颱記者采訪101歲的陳翰笙,讓他給北大說句祝福的
話,陳老不假思索,說:“祝北大今後辦得像老北大一樣好。”記者和傢人都覺
得不妥,教他說:“祝北大今後越辦越好。”但老頭子很任性,連說三遍,次次
都是“祝北大今後辦得像老北大一樣好”,絕不改口。(潘維《跨越世紀的精神
薪火——憶先師陳翰笙》)
很顯然,上述追念都是建立在精神層麵上的。如果單從物質建設上來看,今
日很多不入流的大學已經遠遠超過當年的一眾名校,然而,它們卻無法在學子心
中喚起那種深沉的情感。而那些一路走來的大學,同樣無法因為物質建設的進步
獲得同比例增加的歸屬感。
III
這就是筆者寫作這本書的意義之所在——大學之大,在於精神!於是,在我
們剛剛走進的這個年份,本書的寫作便有瞭不尋常的意義:2017,正是蔡元培先
生就任北大校長一百周年之際。
大學的起源也許要嚮上追溯韆年,但現代意義上的第一所大學則被公認為
是創立於1809年的柏林洪堡大學。洪堡將獨立與自由的理念打造成大學的精神內
核,在帝製時代的尾聲橫空齣世,也給一流大學的定義加上瞭一個“金標準”。
從此,大學走上瞭一條通衢大道。
國人曆來熱衷於尋根追祖,國內第一所大學的榮譽所歸,至今還是個富有爭
議的話題。據聞,有的大學已經將自己的曆史追溯到瞭古代的書院。其實,這樣
的爭議大可不必,在蔡元培先生沒有執掌北大之前,中國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
大學。
1917年,曾經自費留德多年、深受德國現代大學理念影響的蔡元培先生就任
北大校長,其後北大脫胎換骨,從一座“衙門”性質的封建官僚舊式學堂轉變成
瞭追求科學新知的新式高等學府,這在中國的教育史上是開天闢地的。
蔡氏改革北大,使得徒具肉身的北大宣告瞭精神歸位,也以一道霹靂在中國
的學術天空劃齣奪目的光亮。蔡元培不僅是北大精神之父,同時也成為瞭中國現
代型大學理念的奠基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2017年,中國所有的大學實在應該
共慶百年校慶。
北大在蔡元培“兼容並包”精神的哺育下迅速成長,再加上老北大連一個
統一的校園都沒有,校捨四處分散、支離破碎,既無升旗儀式也無學年大會,甚
至連畢業典禮都沒辦法舉行,難以形成集體意識。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恰因
如此,卻使得學生的自由思想蓬勃生長。清華則擁有庚子賠款的強大財力作為後
盾,政府企圖通過經濟封鎖壓製學校的手段在這裏很難實現,經濟獨立支撐瞭精
序言
IV大學·大師·大時代
神獨立,全國最優秀的學者因這兩方麵的因素匯聚清華園,他們的嶙峋風骨則進
一步推進瞭清華獨立精神的涵育和發展。
於是,北大為代錶的自由思想和清華為代錶的獨立精神遂成為中國大學的精
神雙核,為中國大學的前進提供瞭連綿不絕的動力。同時,北大的激進與清華的
沉潛恰好又形成瞭完美的互補,一如太極圖式中的陰陽兩儀,其他大學在其強大
的吸力之下,自覺形成瞭嚮心性,圍繞著雙核運轉,如群星捧月、眾壑朝宗。後
來,即使國民黨政府極力扶持官方色彩更濃的中央大學為“最高學府”,也無法
撼動兩校的地位。這並非北大清華多麼優秀,而是由於真理的力量無可匹敵。
而在北大清華之外,民國的其他高校大都也形成瞭自己鮮明的風格,哪個學
子畢業於哪個大學仿佛都貼上瞭標簽,不會混淆;反過來,學子對於自己母校的
認同感也是驚人的強烈。不像我們現在,即使上瞭最好的大學,還是牢騷不斷。
造成這一差距的原因,蓋因人文精神的缺位。
如今,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後一個世紀的時光已經過去。盡管世事滄桑,風
流已被雨打風吹去,但民國大學高貴的精神卻依然如頭頂的星空一樣熠熠生輝。
人類已經過去的曆史中,知識在大部分時間都是一種奢侈品。在一篇好文章
都能引發“洛陽紙貴”的時代裏,大多數人是無福享受教化之風的。大學的誕生
打破瞭少數人對於知識的壟斷,也改變瞭無數底層民眾的命運,功德無量。
然而,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時至今日,從純學術的角度來看,大學存在的意
義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瞭,甚至可以說很多院係似乎沒有存在的必要瞭。技術的
進步,完全可以讓名師的課堂隨著網絡飛入尋常百姓傢,電腦桌麵上一個圖標的
背後可能是一個巨大的圖書館。作為一個已經成年自立的學生,如果有足夠的求
知欲望和毅力,完全可以通過自學來完成“我的大學”。反之,如果沒有這種欲
V
望和毅力,那麼進瞭大學以後也不會有多少收獲。
世界上最頂尖的圍棋選手已經在電腦麵前敗北,人工智能的壓倒性勝利來得
比想象還早。至於更早被電腦降服的象棋界,重大比賽時防止大師們利用軟件作
弊已經成瞭現在的主辦方最為頭疼的事情。人工智能這隻“蝴蝶”還將在我們的
認知領域攪起怎樣的颶風,或許會遠遠超齣大多數人的想象。假如未來有一天,
我們想學習某一項專業技術,身邊馬上就能有私人定製的無所不知而又不知疲倦
的機器大師的指導,那些天價的實驗室也會成為基本的市政設施。再加上完善的
關於專業能力的評價手段、評價體係的建立,文憑隻剩下象徵意義,那麼,我們
還有必要進大學學習嗎?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大多數大學將會消失,因為現在很多大學不過是“勞動
力培訓基地”,未來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但真正的大學不會消亡,隻是會迴歸
其本來麵目,“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最初的大學在中世紀的歐洲一度隻
是教會的附庸,最終,大學的成長壯大證明人類的信仰不僅可以來自於對神的膜
拜,也可以來自於對知識的渴望,對真善美的追求,對宇宙自然的好奇與嚮往。
倉頡造字而鬼神哭,這是對人類學會思考的恐懼。知識不但是一個謀生工具,更
應該是一種生存方式,而要實現這樣的終極目標,“體驗式”成長是不可或缺
的。
人生就像是一場旅行,重要的不是到達旅途的終點,而是觀賞沿途的風景,
或修煉看風景的心情,求學亦復如是。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與師友的碰撞融
閤,學習中的喜怒哀樂,想象力、創造力、獨立思考能力之生發,進而整個世界
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這些都將使知識本身變成一種偉大的信仰,也是人
類超越機器的地方。同樣的結果,由於過程的不一樣,其深度和廣度是大異其趣
的。有瞭這樣的過程,大學的經曆就將在我們的心海中升起一座精神島嶼,任憑
序言
VI大學·大師·大時代
浪潮拍打,卻始終傲立於海平麵上,永不沉沒,如前麵那些過來人的感懷一樣。
天地廣闊,山河浩蕩,最令人留戀的還是校園中的大草坪和林蔭道。我們曾
於此臥看雲起,也曾執手走過落葉翩翩。惟有以此潔白純淨為底色,方可在人生
的畫布上潑灑齣大寫意。
文明越進步,科技越發達,人作為一個群體就越強大,而作為一個個體則愈
脆弱。當技術到達特定的高度以後,人的存在感也必將跌入冰河期,這個時候,
唯有高擎人文精神的火把纔能溫暖僵硬麻木的軀體。未來的大學,必定從現在的
技術至上轉嚮人本主義。歸根到底,每個人的獨一無二之處就在於他的思想,法
國思想傢帕斯卡爾說“人是一棵會思想的蘆葦”,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曰“人,詩
意的棲居”,言下之意正是如此。在機器越來越像人的時代,人怎麼活得像個人
是最大的課題,這或許也是未來大學最神聖的使命。
物理學上有一個赫赫有名的“光電效應”,冷冰冰的金屬在高頻率光綫的照
耀下,竟然也會激情四射,內部的電子被光子激發,脫離原子核的束縛跳齣來並
形成電流。這樣的變化也許肉眼看不見,但是已經在潛移默化之中發生瞭。大學
之光照耀之處,必將解放我們身上的精神枷鎖,使得我們的生命齣現鳶飛魚躍、
生機勃勃的美好景象,這束光芒已經照亮瞭人類的過去,也必將照耀我們的未
來!
用户评价
從結構布局來看,這本書的處理方式非常巧妙,它避開瞭簡單的綫性敘事,而是采取瞭一種多維度、網狀的敘事結構,使得不同大師之間的思想脈絡能夠相互映照,形成一種立體的知識景觀。我發現,作者非常善於設置“錨點”,通過一些關鍵的曆史事件或關鍵著作的深入解讀,串聯起整個時代的思想發展軌跡。每一次跳轉到新的主題或人物,都不會讓人感到突兀,反而像是在迷宮中找到瞭另一條通往核心的路徑。這種精心的編排,體現瞭作者對材料的駕馭能力達到瞭爐火純青的地步。它不隻是提供瞭知識,更重要的是提供瞭一種理解知識如何生成、如何傳播、如何影響世界的思維路徑,對於渴望建立係統性知識體係的讀者來說,這本“地圖集”的價值是無可替代的。
评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高級文筆,但又完全沒有學究氣,讀起來非常過癮。它有一種沉穩而富有韻律感的節奏感,仿佛作者在用最精準的詞語,雕刻齣那個時代特有的氣質。我欣賞它對“時代精神”的捕捉能力。作者沒有將時代簡單地標簽化,而是通過對細節的精準捕捉,讓那個特定曆史階段的空氣、氛圍,乃至知識精英們日常交流中的細微差彆,都鮮活地呈現在讀者麵前。例如,書中描述某次學術會議的場景,通過對與會者衣著、眼神、甚至是茶歇時談論的話題的描摹,我能真切感受到那個特定年代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的文化氛圍與價值取嚮的微妙變化。這種高度的現場感和氛圍感,讓閱讀過程成瞭一種沉浸式的體驗,而不是冷冰冰的信息接收,這種文字功力,絕對值得反復品味。
评分翻開的每一頁,都像是被邀請進入瞭一場知識的盛宴,但這場盛宴的菜單設計得極為精妙,絕非堆砌資料的粗暴展示。我特彆留意到作者是如何處理不同學科大師之間的思想交匯與碰撞的。那些本來看似分屬不同領域的思想體係,在作者的筆下,忽然間找到瞭某種內在的統一性。這種跨學科的視野,極大地拓寬瞭我原有的認知邊界。比如,書中對於美學理論如何影響瞭某些社會學思潮的探討,簡直是醍醐灌頂。它不再將學術史視為一條條平行的鐵軌,而是將其描繪成一張交織錯綜的巨網。這種結構化的梳理,使得原本零散的知識點,迅速被整閤進一個更宏大、更有邏輯性的框架之中。讀完特定章節後,我常常需要停下來,對著書本深思良久,因為那種“原來如此”的頓悟感,是久違的閱讀快感,它促使我去重新審視自己過去對許多既有理論的理解,無疑是一次深刻的思維重塑。
评分真正讓我感到驚喜的是,這本書在探討學術成就的同時,並未迴避那些光環背後的人性復雜麵。作者以一種近乎冷靜的剋製,書寫瞭大師們的爭議、失誤,甚至是性格上的缺陷。這種真實感,極大地拉近瞭讀者與“神壇上人物”的距離。我們不再是膜拜者,而更像是理解者。書中對某位哲學傢的晚年心境剖析,非常到位,既肯定瞭他思想的開創性,也坦誠地揭示瞭他在麵對時代劇變時的彷徨與局限。這種不偏不倚、尊重曆史原貌的態度,體現瞭作者極高的學術良知和人文關懷。它教會我們,真正的偉大,是建立在承認其局限性的基礎上的,這比起一味地歌頌,要深刻和有力量得多。這種批判性的繼承,纔是對曆史最好的緻敬。
评分這本書的開篇,那種撲麵而來的曆史厚重感,真讓人忍不住一口氣讀下去。作者在敘述中巧妙地將那些耳熟能詳的學術巨匠,放置在波瀾壯闊的時代背景下,使得他們的思想光輝不再是孤立的符號,而是與那個特定時空緊密相連的産物。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於知識分子群體命運的描摹,那種身處曆史洪流中的掙紮、堅守與選擇,讀來令人唏噓。比如,書中對某位物理學傢的青年時期探索曆程的刻畫,不僅僅是科學發現的記錄,更是一場關於信念與環境博弈的深刻剖析。文字的處理非常細膩,沒有那種刻闆的教科書腔調,而是充滿瞭對個體精神世界的關切。它引導我去思考,在宏大的“時代”麵前,個體智慧究竟能發齣多大的光芒,又會如何被時代的風嚮所塑造。這種將“人”置於“史”中的敘事手法,極大地豐富瞭閱讀體驗,讓我感覺自己仿佛也參與瞭那段思想的激蕩歲月,而非僅僅是一個旁觀者。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国际可持续发展百科全书(第6卷):可持续性的度量、指标和研究方法 [Measurements,Indicators,and Reserach Methods for Sustainabilit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277152/5a339579Nf79fb6c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