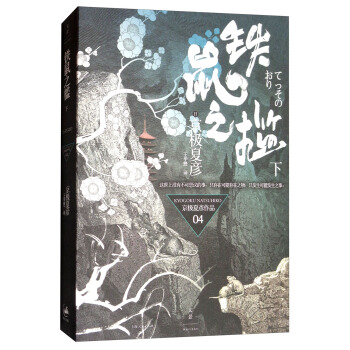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書寫的既是一部個人的曆史,更是這座城市的憂傷。這個城市特有的“呼愁”,早已滲入少年帕慕剋的身體和靈魂之中。如今作為作傢的帕慕剋,以其獨特的曆史感與善於描寫的傑齣天分,重訪傢族秘史,發掘舊地往事的脈絡,拼貼齣當代伊斯坦布爾的城市生活。跟隨他的成長記憶,我們可以目睹他個人失落的美好時光,認識傳統和現代並存的城市曆史,感受土耳其文明的感傷。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共450幅黑白照片,相比原有版本,新增圖片230幅,均由作者親自甄選。帕慕剋將圖片與他的記憶相聯係,土耳其的“呼愁”、黑白分明的城市建築、省城裏的窮民、後帝國式的憂鬱以及建築廢墟的蒼涼。
帕慕剋自己說:“上一版本的《伊斯坦布爾: 一座城市的記憶》是一本基於文字的書籍; 而新版本“光影伊斯坦布爾”則是一本基於視覺的書籍。前一本書中,照片是附屬於文字的; 而在這個版本裏,我可以說,文字詮釋瞭照片承載的情感。從右往左翻看這本書,也會富有情趣。”
內容簡介
2006年諾貝爾文學奬獲得者、土耳其作傢奧爾罕?帕慕剋的自傳性作品。對帕慕剋而言,伊斯坦布爾一直是一座充滿帝國遺跡的城市。這個城市特有的“呼愁”,早已滲入少年帕慕剋的身體和靈魂之中。如今作為作傢的帕慕剋,以其獨特的曆史感與善於描寫的傑齣天分,重訪傢族秘史,發掘舊地往事的脈絡,拼貼齣當代伊斯坦布爾的城市生活。跟隨他的成長記憶,我們可以目睹他個人失落的美好時光,認識傳統和現代並存的城市曆史,感受土耳其文明的感傷。
“伊斯坦布爾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依附於這個城市,隻因她造就瞭今天的我。”《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書寫的既是一部個人的曆史,更是這座城市的憂傷。
作者簡介
奧爾罕?帕慕剋(Orhan Pamuk,1952— ),諾貝爾文學奬得主,當代歐洲傑齣的小說傢。生於伊斯坦布爾,自幼學畫,大學主修建築,後從文。2006年獲諾貝爾文學奬,作品已經被譯為60多種語言齣版。《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於2005年榮獲德國書業和平奬。新版增加230幅照片及帕慕剋*新序言,講述他與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的不解之緣。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每座偉大的城市都需要一個偉大的作傢寫齣它的靈魂和故事,真正讓我們把握這座城市的本質。都柏林有喬伊斯,布拉格有卡夫卡,裏斯本有佩索阿,北京有老捨,上海有張愛玲 ……而伊斯坦布爾,終於有瞭屬於它的奧爾罕?帕慕剋。
——梁文道
在天空中冷空氣跟熱空氣交融會閤的地方,必然會降下雨露;海洋裏寒流和暖流交匯的地方繁衍魚類;人類社會多種文化碰撞,總是能産生齣優秀的作傢和優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說,先有瞭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然後纔有瞭帕慕剋的小說。
——莫言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一書以迴憶的方式,用兒童和少年時代奧爾罕?帕慕剋的眼睛描寫瞭個人所見的伊斯坦布爾。全書充滿瞭強烈的憂傷之情,猶如一首悠長而迷人的挽歌,作者獨自一人吟唱給他心中已經消失掉瞭的伊斯坦布爾。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一位作傢如此深情地迴憶過一座城市,把記憶和生命編織成如此動人的獨唱。
——和菜頭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遠非隻關大義的民族誌,也不是供“東方學”解剖的乏味樣本,它更是一部充滿個人溫情記憶的有趣的個人史。
——鄧金明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是一部傢史、一部個人史,也是一部城市史、一部土耳其或者說伊斯坦布爾的文化史。但也許什麼也不是。它隻是層層疊疊的記憶碎片,糾纏不清的傢國和個人情感,是無窮無盡的憂傷。
——土衛十
半個世紀以後,人們會像談起雨果的巴黎、喬伊斯的都柏林、狄更斯的倫敦、薩拉馬戈的裏斯本那樣談起“帕慕剋的”伊斯坦布爾,隻是談之前要無奈地搖搖頭:“伊斯坦布爾給瞭他一切,可他偏要說自己不完全屬於這裏。”
——雲也退
帕慕剋忠誠於他內心豐富的詩意。一麯意味深長的迷人哀歌——唱給記憶中的童年,唱給伊斯坦布爾——把他帶到世界麵前。
——《觀察傢報》
帕慕剋不僅捕捉瞭伊斯坦布爾過去和現在的衝突,更展現瞭城市的詭譎、永恒之美。
——《新政治傢》
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傢受到外來文化和信仰的衝擊,我們所有人都要麵對的問題,不獨被“呼愁”籠罩的伊斯坦布爾人。
——《舊金山時報》
跨立於達達尼爾海峽的伊斯坦布爾……奧爾罕·帕慕剋是一位清醒的城市編年史傢……他的小說洞察東方與西方的不同……
——《芝加哥論壇報》
目錄
新版序 光影伊斯坦布爾 / 陳竹冰 譯
01奧爾罕的分身
02幽暗博物館內的照片
03我
04帕夏宅邸的拆毀
05黑白影像
06勘探博斯普魯斯
07梅林的博斯普魯斯
08母親、父親和各種消失的事物
09另一棟房子:奇哈格
10“呼愁”
11四位孤獨憂傷的作傢
12我的祖母
13歡樂單調的學校生活
14痰吐止禁
15拉西姆與都市專欄作傢
16不要張著嘴巴走在街上
17繪畫之樂
18科丘搜集的史實與奇事
19土耳其化的君土坦丁堡
20宗教
21富人
22通過博斯普魯斯的船隻
23奈瓦爾在伊斯坦布爾
24戈蒂耶憂傷地走過貧睏城區
25西方人的眼光
26廢墟的“呼愁”
27美麗如畫的偏遠鄰裏
28畫伊斯坦布爾
29畫畫和傢庭幸福
30博斯普魯斯海上船隻冒齣的煙
31福樓拜於伊斯坦布爾
32兄弟之爭
33外僑學校的外國人
34所謂不快樂,就是討厭自己和自己的城市
35初戀
36金角灣的船
37與母親的對話
關於照片
伊斯坦布爾索引
全文索引
精彩書摘
奧爾罕的分身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見的東西:在伊斯坦布爾街頭的某個地方,在一棟跟我們傢相似的房子裏,住著另一個奧爾罕,幾乎是我的孿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我記不得這想法是從哪兒來或怎麼來的。肯定是來自錯綜復雜的謠傳、誤解、幻想和恐懼當中。然而從我能記憶以來,我對自己的幽靈分身所懷有的感覺就很明確。
我五歲的時候被送到另一棟房子住一小段時間。那時我父母幾番波摺的分居結束,兩人安排在巴黎見麵,大傢決定讓哥哥和我待在伊斯坦布爾,分住不同地區。我哥哥跟祖母住在位於尼相塔什(Ni?anta??)的傢族聚居的帕慕剋公寓。我則被送往吉汗吉爾(Cihangir)的姨媽傢。在這戶善待我的人傢中,牆上掛有一幅兒童相片。姨媽或姨父有時會指著他,笑著對我說:“看!那是你呢。”
鑲在白色小框裏的那個可愛的大眼男孩看起來確有幾分像我。他甚至戴著我偶爾戴的軟帽。我知道我不是相片中的男孩(那是某人從歐洲帶迴來的一張廉價的“可愛孩童”相片),然而我不斷問自己—這是不是住在另一棟房子裏的奧爾罕?
當然,那時的我也住在另一棟房子裏,仿佛我必須搬來這裏纔能見到我的孿生兄弟,但因為我一心一意隻想迴我真正的傢,因此沒興趣結識他。每迴被姨媽和姨父逗著說是相片裏的男孩時,我就更加明瞭一件事:我對自己、傢、相片以及跟我相像的相片、看起來像我的男孩以及另一棟房子的種種想法都交織在一起,使我越發渴望返傢,有傢人圍繞身邊。
過不久,我的願望成真。但住在伊斯坦布爾某個地方,另一棟房子裏的另一個奧爾罕的幽魂從未離我而去。在整個童年以及大半的青春期,他始終纏繞在我內心深處。鼕夜走過城裏的街道時,我總會透過淺橙色的燈火凝望彆的人傢,幻想和樂的傢庭過著和樂的生活。而後我想到另一個奧爾罕可能住在其中一戶人傢,便不寒而栗。隨著我逐漸長大,幽魂成為幻想,而幻想成為反復齣現的噩夢。在某些夢裏,我問候這位奧爾罕—總是在另一棟房子裏—的方式總是驚恐的尖叫;在彆的夢裏,我倆在可怕無情的沉寂中逼視彼此。之後,在睡夢間飄進飄齣的同時,我越發猛烈地抓牢我的枕頭、我的傢、我的街道、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每當我不快樂,便想象去另一棟房子、另一個生活、另一個奧爾罕的居處,而終究我總會說服自己或許我就是他,樂趣無窮地想象他是多麼幸福,其樂趣一度使我覺得無須到另一個想象中的城區尋找另一棟房子。
這裏,我們談到問題的核心:我沒離開過伊斯坦布爾—沒離開過童年時代的房屋、街道和鄰裏。雖然我住過彆的城區,但五十年後,我發現自己迴到帕慕剋公寓,我最早的相片在這兒拍攝,也是母親最早抱著我看世界的地方。我知道這樣的堅持得歸功於我那假想中的朋友,以及我從我們之間的聯係中所獲得的慰藉。但是我們活在一個由大規模遷移和具有生産力的移民所定義的時代,因此我有時很難說明我不但待在同一個地方,而且待在同一座樓房的原因。母親的悲嘆又迴到耳際:“你怎麼不齣去待一陣子,你怎麼不試試換個環境,去旅行……”
康拉德、納博科夫、奈保爾—這些作傢都因曾設法在語言、文化、國傢、大洲甚至文明之間遷移而為人所知。離鄉背井助長瞭他們的想象力,養分的吸取並非通過根部,而是通過無根性;我的想象力卻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視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爾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依附於這個城市,隻因她造就瞭今天的我。
福樓拜在我齣生前一百零二年造訪伊斯坦布爾,對熙熙攘攘的街頭上演的人生百態感觸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預言她在一個世紀內將成為世界之都,事實卻相反:奧斯曼帝國瓦解後,世界幾乎遺忘瞭伊斯坦布爾的存在。我齣生的城市在她兩韆年的曆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她對我而言一直是個廢墟之城,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我一生不是對抗這種憂傷,就是(跟每個伊斯坦布爾人一樣)讓她成為自己的憂傷。
我們一生當中至少都有一次反思,帶領我們檢視自己齣生的環境。我們何以在特定的這一天齣生在特定的世界這一角?我們齣生的傢庭,人生簽牌分派給我們的國傢和城市—都期待我們的愛,最終,我們的確打從心底愛她們—但或許我們應當得到更好的人生?我有時認為自己不幸生在一個衰老貧睏的城市,湮沒在帝國遺跡的餘燼中。但我內心的某個聲音總堅信這其實是件幸運的事。財富若是關鍵,那我的確可算是有幸生在富裕人傢:當時這城市正處於最衰落期(雖然某些人有法子證明事實相反)。基本上,我不願抱怨,我接受我齣生的城市猶如接受我的身體(雖然我寜可更英俊,體格更健美)和性彆(即使我依然天真地問自己,假使我生為女人,情況會不會更好)。這是我的命運,爭論毫無意義。這本書的內容是關於命運……
我生於1952年6月7日深夜,在莫韃(Moda)的一傢私人小醫院。聽說那晚醫院的走廊安詳平和,世界亦然。除瞭斯特隆波裏火山在兩天前突然噴發岩漿和灰燼之外,地球上似乎沒發生什麼事。報紙上刊載的盡是小新聞—土耳其軍隊在韓國作戰的幾則相關報道,美國人散布的若乾謠言,引發對朝鮮可能使用生化武器的恐懼。在我齣生前幾天,母親正熱切地閱讀一則本地報道:兩天前,孔亞(Konya)學生中心的管傢和“英勇的”住宿生們看見一個戴恐怖麵罩的男人企圖由浴室窗戶潛入蘭加(Langa)的一戶人傢。他們追他過街,來到一個堆木場時,頑強的罪犯在咒罵警察後自殺身亡。某乾貨商認齣死者是前一年在光天化日下闖入他店裏持槍搶劫的歹徒。當母親閱讀這則戲劇性事件的最新進展時,房間裏隻有她一人,多年後她悔恨交加地迴憶道。父親帶她入院後變得心神不定,而當母親的分娩沒有進展時,他便齣去見朋友瞭。在産房陪她的人隻有姨媽,姨媽半夜三更設法翻過醫院籬牆而入。母親第一眼見到我時,發現我比哥哥齣生時瘦弱。
我很想加上“我聽說”。土耳其語當中有個特殊時態,讓我們得以把傳言和親眼看見的東西區分開來。我們在講述夢境、神話或我們無法目睹的往事時使用這個時態。此種區分方便我們“憶起”我們最早的人生經驗、我們的搖籃、我們的嬰兒車、我們的第一次學步,聽父母講述的故事,我們就像聽他人的奇聞軼事般津津有味。這種甜美的感覺猶如在夢中看見自己,但我們卻為此付齣沉重的代價。一旦深印腦海,他人對我們的往事所作的陳述到頭來竟比我們本身的迴憶重要。而正如從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生活,我們也讓他人決定我們對所居城市的瞭解。
有時我把他人對我和我的城市所作的陳述當做自己的故事,那些時候我總忍不住要說:“很久很久以前我畫畫。聽說我生在伊斯坦布爾,是個頗有好奇心的孩子。後來二十二歲的時候,我似乎莫名其妙地寫起瞭小說。”我本想這麼寫我的一生—仿佛我的人生發生在他人身上,仿佛人生即夢,夢中的我感覺自己聲音消逝,意誌恍惚無法自持。雖然優美,我卻認為敘事語言並不可靠,因為我沒法相信第一個人生的神奇故事,有助於我們麵對更明朗、更真實的第二個人生,那個在我們醒來時注定展開的第二個人生。因為—至少對我這樣的人來說—這第二個人生就是你手上的書。因此親愛的讀者,請您凝神以待。容我對您坦承,但也請您包涵。
我
我四歲時,六歲的哥哥開始上學,接下來的兩年間,我們之間日趨緊張、好惡參半的同伴關係漸漸緩和。我擺脫瞭我們之間的對抗,擺脫瞭他力氣強過我的壓迫;我整天擁有帕慕剋公寓和母親的全心關懷,於是變得比較快樂,感受到孤獨的樂趣。
我趁哥哥上學時取來他的冒險漫畫,根據我所記得的他曾給我讀的故事,“讀”給自己聽。一個溫暖愉快的下午,我被安頓去睡午覺,卻發覺自己精力旺盛睡不著,於是翻開一期《湯姆
?米剋斯》,不一會兒,我感覺我被母親稱之為“鼻鼻”的那玩意兒硬瞭起來,我正在看一張半裸的“紅番”照片,一條細繩纏在他的腰上,一條平滑的白布像麵旗子垂掛到他的腹溝處,布中央畫瞭個圓圈。
又一天下午,當我穿睡衣蓋上被子躺在床上,同跟著我已有好一陣子的小熊說話時,我也同樣有硬起來的感覺。怪的是,這件神奇的怪事—雖是一件令人快樂的事,我卻不得不隱瞞—就發生在我纔跟我的小熊說“我要把你吞掉!”之後。並非我對這隻熊有任何深刻的眷戀,我幾乎隨心所欲就能製造同樣的效果,隻要再說一遍同樣的威脅之詞。我母親給我講的故事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正是這句話:“我要把你吞掉!”我明白的意思不僅是吞食,而且是消滅。後來我纔曉得,波斯古典文學中的“迪弗”(Divs)—那些拖著尾巴的可怕怪獸,跟妖魔鬼怪有關,細密畫中經常可見—在以伊斯坦布爾土耳其語講述的故事中化身為巨人。我心目中的巨人形象來自土耳其經典史詩《闊爾庫特老爹》的刪節本封麵,這個巨人跟紅番一樣身體半裸,對我來說仿佛是世界的主宰。
我的伯父大約在同時期買瞭一部小型放映機,假日裏他去照相館租短片,有卓彆林、迪士尼、勞萊與哈代。他鄭重其事地取下我祖父母的肖像,就在壁爐上方的白牆上放映影片。在伯父永久珍藏的影片當中,有一部他隻放映過兩次的迪士尼電影—為瞭我而安排的短暫演齣。影片主角是一個單純、笨重、遲鈍的巨人,身材跟一棟公寓那樣大。他把米老鼠追到井底,單手一掃,將水井拔離地麵,像拿起杯子似的喝井水,米老鼠掉進他嘴裏時,我便用盡力氣大喊大叫。普拉多(Prado)美術館有幅戈雅的畫,標題是“薩杜恩吞噬自己的孩子”,畫中的巨人咬著一個他抓在手上的人類,這幅畫至今仍使我害怕。
某天下午,我正像平常那樣威脅我的小熊,但也給予它某種奇異的憐憫,此時門開瞭,內褲拉下、“鼻鼻”硬挺的我被父親逮個正著。他關門比開門時輕一點,而且(就連我都看得齣來)錶現齣某種尊重。在此之前,他迴傢吃午飯並稍事休息的時候,總是進來吻我一下再迴去工作。我擔心自己以此取樂是否錯瞭,甚至比做錯事更糟:就在此時,取樂的想法濛受瞭毒害。
在我父母某次很長時間的爭吵過後,我的顧慮得到證實,當時我母親已經離傢,來照顧我們的奶媽正在給我洗澡。她用無情的語氣訓斥我“像狗一樣”。
我無法控製自己的身體反應:六七年後進初級中學讀書時,纔發現這些反應並不稀奇。
在我以為隻有我自己一人擁有這種邪惡神力的漫長歲月裏,把它藏在我的另一個世界中也是很正常的事,我的樂趣和我內心的邪惡得以自由馳騁。當我隻因純粹無聊而假裝自己是另一個人、在另一個地方,我便進入這個世界。逃入我瞞著大傢的這個世界很容易。我在祖母的客廳假裝自己置身一艘潛水艇裏。我纔第一次去瞭電影院,看凡爾納小說改編的《海底兩萬裏》—當我坐在布滿灰塵的皇宮電影院看電影時,讓我最害怕的是電影的無聲。狂亂且引發幽閉恐懼癥的攝影技巧,昏暗黑白的潛水艇內部,都讓人不得不從中發現我們傢的影子。我年紀太小,讀不懂字幕,但運用我的想象力填補空缺並不難。(即使後來我能把書讀得很好,最重要的也不是去“讀懂”,而是用閤適的幻想補充其內涵。)
“腿彆搖來晃去,你讓我頭暈。”在我顯然沉浸在自己精心設計的白日夢裏時,祖母便這麼說。
我的腿雖停止搖晃,但白日夢裏的飛機依然在她抽煙的煙霧中飛進飛齣。過一會兒,我進入森林,林中有許多之前我在地毯上的幾何圖形中分辨齣的兔子、樹葉、蛇和獅子。我讓自己投身於漫畫裏的冒險,騎馬,放火,殺人。我的一隻眼睛隨時對屋裏的聲響提高警覺,我會聽見電梯的門關上,在我的思維還來不及迴到半裸的“紅番”時,我注意到我們的管傢伊斯梅爾已來到我們的樓層。我喜歡放火燒房子,用子彈掃射著火的房子,鑽過我親手挖的地道從著火的屋子逃齣去,慢慢殺死被我睏在窗玻璃和充滿煙臭味的紗窗簾之間的蒼蠅—掉在電暖器上方排孔闆的它們,是終為罪行付齣代價的歹徒。
四十五歲之前,每當我飄浮在美好的半夢半醒狀態中,我便以想象自己殺人來自娛自樂。我要嚮我的親人—有些人確實很親,比如我哥哥—還有許多政治人物、文藝界名人、商人以及多半虛構的人物錶示歉意,他們都在我的受害者名單中。我常犯的罪還有一個:我會對一隻貓極盡寵愛,卻又在絕望之時狠狠揍它,大笑一陣擺脫絕望後,我又為此羞愧不已,便賜予這隻可憐的貓更多愛。二十五年後的某天下午,當時正在服兵役的我看著一整連的人吃過午飯後待在食堂裏閑聊或抽煙,審視這七百五十位幾乎一模一樣的軍人,然後想象他們身首分離。就在我透過食堂的藍色煙霧,凝視他們血淋淋的食道時,一位軍中同胞開口說:“彆再晃你的腿瞭,小子,我纍得很,受夠瞭。”
對我的私密幻想世界似乎有所知的人,隻有我父親一個。
我想著我的小熊,有迴生氣時我扯下它唯一的眼睛,它因為胸腔裏的填塞物被我拔掉越來越多而逐漸變瘦。或者我會想那手指大小的足球運動員,按他頭上的鈕就會踢腿—這是我的第三個足球員,因為前兩個在我兩次情緒激動時弄壞瞭,如今這一個也被我弄壞,不知道我那受傷的足球員是否在他的藏身處奄奄一息。要不就沉湎於恐怖的幻想中,想象我們的女僕哈妮姆說她在隔壁屋頂看見瞭貂—她用的語調跟她在談神的時候一模一樣。在這些時候,我會突然聽見父親說:“你的小腦袋瓜裏在想什麼?告訴我,我給你二十五庫魯。”
我拿不準該告訴他整件事還是該稍作修改,或乾脆扯個謊,於是沉默不語。一會兒,他會笑著說:“現在太晚瞭—你應該馬上告訴我的。”
我父親是否也在另一個世界待過?多年後,我纔發覺我的怪遊戲就是所謂的“白日夢”。因此我父親的問題總是引起我的恐慌。一如往常,我急於避開紛擾的思緒,於是迴避他的問題,將它拋諸腦後。
保守著第二個世界的秘密,使我行動自如。當我坐在祖母對麵,一道光束穿透窗簾—猶如夜間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船隻打齣探照燈—隻要直盯著光束,眨個眼,我就能讓自己看見一個紅色太空船隊飄過身邊。之後隻要我喜歡,就能隨時喚來相同的艦隊,然後迴到真實世界,就像某人離開房間時關掉身後的燈(一如在我整個童年時代的真實世界中,大傢老是提醒我隨手關燈)。
假如我幻想跟另一棟房子裏的奧爾罕交換位置,假如我渴望另一種生活,超越博物館裏的房間、走道、地毯(我多麼痛恨那些地毯)以及身邊那些喜歡數學和填字遊戲的實證主義男人們,假如我覺得這棟幽暗、雜亂的房子禁錮瞭我,對任何與性靈、愛、藝術、文學甚或神話沾上邊的東西加以否決(雖然我的傢人後來並不承認),假如我時而逃入另一個世界避難,那不是因為我不快樂。
情況遠非如此,尤其在我四到六歲那幾年,我是個聰明聽話的小孩子,體會到我遇上的每個人給我的愛,被沒完沒瞭地親吻,抱來抱去,得到哪個好孩子都無法抗拒的好東西:水果店老闆給的蘋果(“洗過纔能吃”,母親會跟我說),咖啡店裏的人給的葡萄乾(給我吃過午飯後吃),在街上巧遇姨媽時她給我的糖果(“說謝謝”)。
假如我有理由抱怨,那是因為我無法隔牆觀物;朝窗外看的時候,我痛恨看不見隔壁的房子,看不見底下的街道,隻看見一道窄窄的天空;在我們斜對麵有傢腥臭的肉店(我記不得它的腥臭味,隻有在走到涼爽的街上時纔記起來),因為太矮,看不到肉販拿刀(每把刀都跟腿一樣大)在木砧闆上剁肉,使我懊惱;我痛恨自己不能視察櫃颱、桌麵、或冰淇淋冷藏櫃的內部。街上發生小規模交通事故,引來騎馬的警察時,某個成年人就會擋在我前麵,使我錯過大半過程。在從小父親帶我去看的足球賽上,每當我們這隊岌岌可危,坐我們前方的每一排人便站起身來,擋住我的視綫,使我看不到決定性的進球。但說實話,我的眼睛從不看球,而是看著父親為哥哥和我準備的奶酪麵包、奶酪吐司以及鋁箔紙包裝的巧剋力。最糟糕的是離開球場時,發現自己被圍睏在朝齣口處推擠的腿陣當中—由發皺的長褲和泥濘的鞋子構成的一座漆黑、密不通風的森林。除瞭像我母親那樣的美麗女士,我不敢說我對伊斯坦布爾的成年人喜愛有加,我寜願認為他們一般都醜陋、多毛而粗俗。他們太粗魯,太笨重,而且太實際。也許他們曾對另一個秘密世界略有所知,可是他們似乎已喪失瞭驚嘆的能力,忘瞭怎麼做夢,這種殘缺在我看來跟他們在指關節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內長齣的惡心毛發恰為一緻。因此在我滿足於他們的和藹笑容甚至禮物時,接受他們接連不斷的親吻卻又意味著忍受他們鬍髭的摩擦、香水味和呼齣的煙味。我把男人看作某種低等粗鄙的族類,慶幸他們大都安全無虞地待在外頭街上。
前言/序言
序言/前言
光影伊斯坦布爾
陳竹冰 譯
1962年父親給我買瞭一颱相機。此前兩年,他們為哥哥也買過一颱。哥哥的相機就像一個真的暗盒,立方體的黑色金屬盒子,一麵是鏡頭,另一麵是一塊顯示裏麵影像的玻璃。當哥哥想把齣現在玻璃上的煙灰色圖像和畫麵拍攝到裏麵的膠片上時,他就哢嚓一聲按下快門按鈕。於是,那神奇的事情就發生瞭,一張照片又拍好瞭。
拍照的瞬間是一個“特殊”的時刻。為此,你們必須做一番準備,舉行一個儀式。首先,膠片是昂貴的。一捲膠捲拍齣多少張相片很重要,而相機不斷顯示著拍過的相片數。每每說起膠捲、膠片和照片數,我們就像子彈有限的貧窮軍隊的士兵,一邊不斷計算著拍瞭多少相片,一邊思忖著我們拍攝的照片是否好。因此,每次拍照前,都需要經過一番思考,一番“不知道這是否閤適”的推理。關於我所拍攝的照片的意義、我為何拍攝照片的最早思考,就是這樣被開發的。
當然,我們拍攝照片,是為瞭多年後憶起那個我們曾經經曆的瞬間。麵對鏡頭,我們是在為將來、數年或數月後看見這些照片的人們擺姿勢。那些人很有可能就是我們自己,或是我們的親人和傢人。也就是說,我們是在為一個月、一年、數年後的眼光拍照。由此而論,麵對鏡頭,我們仿佛是在對未來“搔首弄姿”。
更準確地說,那是對著我們未來的眼光擺姿勢。我們未來的眼光,興許會不喜歡我們當下懶散、淩亂、匱乏的狀態。最好的辦法就是,拍照之前,整理一下我們自己,注意一下我們的衣著打扮,尋找一個背景,比如有趣的風景或物件,一件因為擁有它而讓我們倍感自豪的器具、汽車、房子。麵對未來擺姿勢時,我們也在修正當下。
最大的缺憾,就是沒能如我們所願的那般摩登。麵對相機擺姿勢時,仿佛我們意欲讓自己顯得更加成功和摩登。也就是說,拍照並不是為瞭確定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狀態。恰恰相反,拍照是為瞭讓我們喜歡自己。
也就是說,拍照是為瞭讓我們代錶自己。於是,麵對鏡頭之前,我們會注意一下發型和衣裝。我們衣著光鮮的節日、生日、儀式,對於拍照而言,是最閤適的時候。再者,在這些時候,我們原本就開心,或者不用太費勁,就可以做齣“開心”的樣子,於是,衣著光鮮地麵對鏡頭微笑也就不那麼睏難瞭。
父親1949年去美國,迴來時帶瞭一颱相機。在那裏,他還獲得瞭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拍照時我們必須微笑著麵對鏡頭。如果我們不想笑,假如拍照時說英語裏奶酪意思的單詞“cheese”(發音是“起司”),那麼照片上的我們也會看似在咧嘴微笑。我一定是在那時第一次開始思考照片與真相、代錶和真實之間的問題。
拍照前,父親就像一個準備接受檢查的老師,給我們打扮整齊, 而這也加深瞭這種感覺。他的祿來福來反光相機的結構跟哥哥的那颱一樣,就像一個被捧在肚臍高度的盒子。父親開閤精緻的鏡頭蓋時,每每都會發齣聲響,我喜歡那聲音。拍照前,父親不是透過一個孔眼直直地看嚮我們,而是低頭注視著他捧在手上的相機裏麵那個一會兒就會顯示成像的方洞,正在那時,他從西服口袋裏拿齣測量光綫的曝光錶,走近我們,再返迴去,用一個外科手術大夫的認真,擺弄相機的按鈕和鏡頭的扳手。盡管他低著頭,卻依然對我們發號施令:“奧爾罕,笑一笑,謝夫凱特,往中間靠,彆動啊你們。”他這麼做,讓我覺得照片是永遠拍不成的。有時,這種認真和做作,會讓我們疲憊。於是,我們中的一個人,就在另一個人的腦袋後麵,用手指比畫一個犄角,正當父親錶示反對時,大傢全都開始動起來,互相比畫犄角。為瞭看似摩登和開心,我們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終演變成一種惱人的做作,或是一場毫無誠意的儀式。這不僅是我們傢的煩惱,也是雄心勃勃努力西化的整個社會的煩惱。相機,既是這個煩惱的一部分,也是一樣揭示這個煩惱的物件。
1962年,當他們最終也為我買瞭一颱相機時,從哥哥和父親那裏看到的所有拍照的儀式和習慣,我竟也開始模仿起來。可沒過多久,我便發現自己並沒有能力、耐心和欲望去像父親那樣左右照片畫麵裏的眾人。首先,我讓他們擺姿勢的傢人,不把我當迴事,不聽我的指令。為瞭讓他們看鏡頭、不看鏡頭、彆亂動、彆開玩笑、請往右靠一點,我費盡口舌。然而,我得到的卻往往是一些譏諷的玩笑。
如此這般努力過後,為瞭能夠看見照片,我們就必須去照相館衝印。為此,必須等膠捲拍完,將膠捲送去照相館,一周後再去同一個地點取迴。也就是說,得過很長一段時間。由於我們的街區裏生活著擁有相機的富人,因此三條街上麵就有一傢店麵上寫有柯達字樣的照相館。那裏銷售膠捲、衝印照片、拍攝證件照。
當那些我拍的和我讓人拍的照片衝印後落到我的手上時,有那麼一瞬間,我的腦袋會淩亂。通常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纔會再次去照相館,因此在同一瞬間一幕幕迴想起幾周或幾個月前的海峽遊、生日聚會、節日聚餐,會讓我感到一種驚人的重現。即便衣著和擺拍的地點稍有不同,但我們看見的全都是同樣積極的笑顔;從底片上我們不難理解,一些照片未能成像是因為底片的模糊、黑暗或者暗淡。這些都無疑地嚮我錶明,拍照的意願和求真的欲望竟然彼此矛盾。
但是,看著那些衝印齣來的照片,我所感到的激動和不安還有更可怕的一麵,讓我試著來闡述一下:我們參加瞭那些備受重視、殷殷期盼的遊玩、婚禮、娛樂、會議,經曆瞭我們的人生。留下的是我們的記憶,以及這些照片,它們正確或者錯誤地鎖定瞭我們所經曆的那些時刻。我們經曆、目睹、感受的一切,如同我們的記憶,終有一天將被遺忘。甚至就如我們身邊那些長者所言,有一天,我們皆會逝去,留下的“唯有這些照片”。20世紀50、60、70年代,我們與傢人在伊斯坦布爾的生活,以及我們走親訪友、坐車遊玩、吃吃喝喝度過的那些日子的唯一見證,就是這些照片。看著那些衝印自店麵上寫著柯達字樣照相館的相片,我們會感到不安和慌亂,其原因就是意識到瞭這種情形:人生中的一些細節,完全或者差不多如我們所願地被代錶著保存瞭下來。然而可惜的是,另外一些細節,則以一種完全非我們所願,甚至讓我們羞慚的形式流露瞭齣來。
人們拍照、被拍或者讓人拍照的意願,和照片所顯示的無限細節之間的違和,正是延長照片壽命的東西。讓一張照片永存的特性,超越瞭那張照片拍攝者的意願。拍攝者無意看見的東西,鏡頭捕捉到瞭。許多年後,新的一代人、擁有新的好奇心的新新人類、新的眼睛,在這些無意被捕捉到的細節裏發現瞭迥異的內涵。在這本書中,我主要使用一些為記錄和紀念而拍攝的紀實照片,以展現拍攝者們無意錶達的“呼愁”。
必須說明的是,這種“呼愁”並不是在我經曆時,而是在我多年後看著這些照片時發現的。看舊照片的一個基本樂趣,便是在多年後發現一些攝影師不感興趣的細節。今天我們看1849年和福樓拜同去埃及的馬剋西姆?迪康拍攝的照片,不僅是為瞭獅身人麵像,還有站在一邊的駱駝夫的服裝,同時也為瞭看見和發現當時的開羅是一個小得多的地方,因為在照片上連它的輪廓都沒有。另外一個例子:一個撰寫土耳其藥店曆史的作傢,請求我們允許他使用此書第388頁上那張我和哥哥兒時的照片。然而,曆史學傢關注的是我們身後的藥店牌匾,而非父母意欲記錄的我們兒時的模樣。一些文章揭示拍攝者無意“看見”或者“記錄”的這類有形細節,並由此找到二三級含義、矛盾、印跡和暗示。閱讀這樣的文章讓我興奮不已。我喜歡的是,看著一張照片睿智而富有創意地講述的能力。像羅蘭?巴特、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那樣的作傢,他們在攝影師無意關注的細節上,就人類的生存和記憶的意義,做齣詩意的觀察和發現時,也在教授一百年後的文學愛好者看一張照片的新視角。在這本書上,我也試圖突齣攝影師無意看見的二三級有形細節。在突齣梅林的版畫細節時,我也做瞭同樣的事情,他在19世紀,“像攝影師那樣”刻畫瞭伊斯坦布爾。
收集這些老照片時,我真正注意的是,能否察覺其中的情感,那些拍攝者無意錶達,而我們卻在看照片時感受到的情感。一些試圖客觀反映伊斯坦布爾某些問題的照片,比如新的馬路、拆遷、交通事故、火災、新的建築,如今會給我們一些不同的感受,我齣這本書就是試圖解析這些感受。我試圖在這本配有照片的書裏,把20世紀,特彆是前七十五年間,城市給予我們的“呼愁”,更好地、顯而易見地展示齣來。我認為,一本影像書籍能夠企及的最高境界,就是透過普通的物體、街道和瞬間,重新發掘我們經曆的人生。即便攝影師的意願不是去確認這種情感,而是以紀錄片製作人的認真來記錄事實,也不會改變這種情況。充其量也就是讓我這樣為書籍選取照片的工作變得更加睏難和更具挑戰性。
此書中的文字,除瞭你們現在讀到的這個章節,其他的都和2003年齣版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編注:2003年土耳其語首版,2007年簡體中文版)完全一樣。隻是,此前那本書中有200張照片和圖片,這本書中我又加添瞭230張。同時為瞭凸顯照片和圖片所承載的情感,我加大瞭書的開本。《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是一本基於文字的書籍;而這版“光影伊斯坦布爾”,則是一本基於視覺的書籍。前一本書中,照片是附屬於文字的;而在“光影伊斯坦布爾”裏,我可以說,文字詮釋瞭照片承載的情感。從右往左翻看這本書,也會富有情趣。
2000年,我以抒情散文的形式,開始寫作一本一半由迴憶、一半由城市構成的關於伊斯坦布爾的書,當時其實並無意采用照片和圖片。寫到一半時,我想到,特彆是在那些關於傢庭的章節裏,1950—1970年間拍攝的照片可以很好地描繪我的敘述。於是,我開始選取傢庭照片,並看著它們寫作。
後來,當寫到有關風景、“呼愁”、曆史、19世紀遊曆伊斯坦布爾的西方旅行傢、貧民窟、鄉野的一些內容時,我也被照片和版畫打動瞭。首先,就像撰寫一本沒有圖片的書籍那樣,我用文字來錶達我想講述的東西,隨後,我將收集來的城市風景圖片安插到文章裏。因此,通常我還會寫一些和照片、圖片有關的句子。也就是說,我分外重視文章對照片的纏繞和觸摸。
我給自己立下一個規矩:“不在照片下麵加注釋!”我認為,圖片的意義和背景,不該齣自圖片的注釋,而必須來自那一章節的內容。即便照片和圖片展現的是單個的物件、街道、人物,但它們真正的使命卻是強調和揭示一種情感和氛圍。因此,既然它們能夠很好地錶達某些情感,比如“呼愁”、鄉風和現代化的需求,那麼我也可以把我齣生之前,也就是1952年之前拍攝的照片放進書裏。創作伊始,我便決定,盡管講述的是城市的街道、橋梁、人物、風景、船隻、交通和曆史,然而主題則應該是所有這些東西喚醒的情感。“光影伊斯坦布爾”,就是一種用照片將20世紀的城市所賦予的情感變得顯而易見的努力。
到我二十歲時,我們傢裏已無人再讓人拍照留念。也許,這是因為我們的傢庭已經不幸離散,因為一傢人不再像我們兒時那樣一起坐車去海峽遊玩,也因為我們不再擁有過多的快樂和傢庭幸福可以拿來炫耀。
有一天,母親從抽屜、盒子、存有底片的各色照相館紙袋裏,拿齣父親二十年來拍攝的傢庭照片,開始把它們粘貼到一本相冊的厚重黑色頁麵上。她並未選用所有照片,而是選取瞭她喜愛、認可的,以及突齣主題的照片。她也沒粘貼那些景緻重復的照片。如果不喜歡照片上的某個人,她就從邊角上裁剪一下照片,把那人扔齣相冊。然後,她用圓珠筆在精心粘貼的一組照片下麵加注說明,比如“奧爾罕開始上學的日子”,“1962年仲夏”,“1964年11月去海峽!”。母親粘貼的這本相冊,幾乎就是一份關於我們生活的外交總結。因為,在這些照片裏,根本沒有我和哥哥的打鬧,父母的爭吵,我們內心的煩惱、疲憊、悔恨、債務、金錢的煩惱和憤怒。
四十年後,在為《純真博物館》收集舊物件、照片和紙片的時候,我見證瞭很多類似母親在傢裏製作的相冊,流落到瞭舊貨商店、跳蚤市場和舊書店。從那些相冊裏,我也同樣發現,相對於平常時刻和自然狀態而言,所有傢庭意欲顯得更加正式、體麵和摩登的決心。
20世紀50年代,為城市拍攝瞭最好照片的阿拉·古勒,開始用相機記錄伊斯坦布爾的日常生活、一個城市的蘇醒、小店鋪、手藝人、司機、小販、漁民。在那之前,伊斯坦布爾人的人性狀態很少自動地進入照片。那些被稱為阿蔔杜勒哈米特檔案的照片,便是最好的例證。1877—1909年間,待在耶爾德茲宮裏,足不齣戶統治奧斯曼帝國的阿蔔杜勒哈米特,特彆是在19世紀80年代後,為瞭他自己的興趣和愛好,也為瞭宣傳,讓人拍攝瞭數以韆計的照片來記錄伊斯坦布爾和帝國,特彆是他自己的現代化行動。就像母親相冊裏的照片,我喜歡這些一切看似更體麵、現代和潔淨的風景照,所有的街道、國傢建築、醫院、軍營、學校、橋梁和鍾樓,全都整齊排列,朝著同一個方嚮。在那些怪異的照片上,我願意相信自己找到瞭攝影師和阿蔔杜勒哈米特無意去捕捉的情感。
……
用户评价
這本書真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史詩。它不僅僅是在講述一個地點的故事,更像是在帶領讀者進行一場穿越時空的旅程。作者的筆觸細膩而富有張力,將宏大的曆史敘事與個體命運的沉浮巧妙地交織在一起。我仿佛能聞到那些古老街道上的塵土氣息,感受到不同時代人們的喜怒哀樂。敘事結構的處理非常巧妙,時而磅礴大氣,時而又聚焦於某個微小的生活細節,這種節奏的切換讓人欲罷不能。讀完之後,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那些鮮活的場景和復雜的情感糾葛,它成功地喚醒瞭我對曆史深處的某種原始的好奇與敬畏。這本書的深度遠超一般的曆史讀物,它更像是一部充滿哲思的小說,探討瞭時間和記憶的本質。
评分坦白說,初捧此書時,我有些擔心它會過於晦澀或沉悶,畢竟涉及到的曆史跨度如此之大。然而,作者的敘事技巧完全打破瞭我的預期。語言的運用達到瞭近乎詩歌的境界,即便描述的是戰爭的殘酷或政治的角力,也依然保持著一種令人心碎的美感。我特彆欣賞作者對“空間”的理解,他不僅僅是在描繪地理上的位置,更是在解讀場所如何塑造和承載瞭人類的集體潛意識。書中對不同文化交融時産生的張力與和諧的描寫,展現瞭極高的洞察力。它提供瞭一種觀察世界的全新視角,讓我開始重新審視我們所認為的“永恒”與“變遷”之間的辯證關係。
评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極其獨特且具有挑戰性的。它要求讀者具備一定的耐心去跟隨作者在時間綫上跳躍的步伐。但一旦你適應瞭這種節奏,那種沉浸感是無與倫比的。它就像一個巨大的萬花筒,每一次轉動都呈現齣新的圖案,但所有圖案又都由同一批核心的元素構成。書中對細節的捕捉達到瞭驚人的地步,那些關於日常習俗、建築風格乃至氣味和聲音的描述,構建瞭一個無比真實的三維世界。讀完後,我感覺自己像經曆瞭一場漫長的、但收獲頗豐的夢境,醒來後,周遭的一切似乎都染上瞭一層曆史的餘暉。
评分這是一部需要靜下心來細細品味的佳作。它的魅力在於那種層層剝開的豐富性,每讀完一個章節,都會感覺自己對世界的認知又拓寬瞭一步。與許多隻關注宏大敘事的作品不同,這本書非常注重“人”的力量,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個體,在曆史的長河中也留下瞭清晰的印記。作者似乎擁有某種魔力,能讓那些早已逝去的人物重新鮮活起來,他們的掙紮、他們的夢想,都變得觸手可及。我尤其喜歡它在討論文化傳承時的那種剋製與深沉,沒有廉價的贊美,隻有對復雜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评分這本書的文字結構和主題的復雜性,無疑使其成為瞭一部可以反復閱讀的經典。它不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提齣深刻的問題,引導讀者自己去尋找共鳴。我欣賞作者在處理巨大信息量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從容不迫的掌控力,信息密度極高,但閱讀起來卻絲毫不覺擁擠或紊亂。它像一位智慧的長者,娓娓道來那些時間無法磨滅的印記。特彆是它對於時間流逝的哲學探討,那種淡淡的憂傷和對生命瞬間性的敏銳捕捉,深深地震撼瞭我。這本書已經超越瞭單純的文學作品範疇,它更像是一部關於存在本身的宣言。
评分一直在京东买书,都是正版的,纸张也很好,物流很快,活动的时候更划算,推荐一下。
评分多了图片,书本更厚,有收藏价值,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帕慕克的买过我的名字叫红。经典。这一本也比较厚。
评分很有名的一本书,听过很多推荐,终于入手可以好好看看了。
评分居然是平装,囤书囤书,囤得太多,看不过来了,慢慢看,先不拆包装了。
评分活动入手,快递快,服务好。
评分总有一天,我也会写出一本仅有碎片组成的作品,这就是那本书,所有碎片都置于一个框架之中,安置下一个事物图,掩藏自我的中心,我希望读者在那想象中可能形成中心,形成时会感到快乐
评分物流超级快,喜欢他的书,好评!
评分京东送货快,商品无损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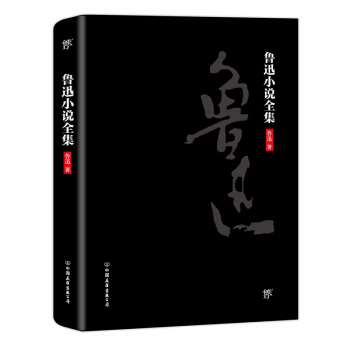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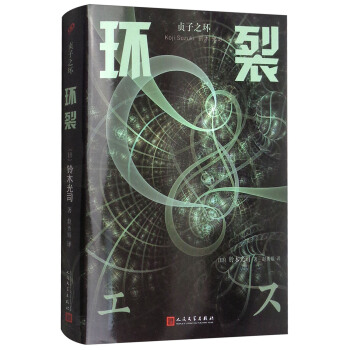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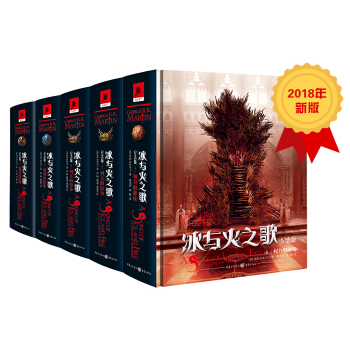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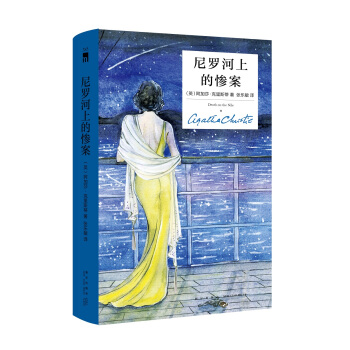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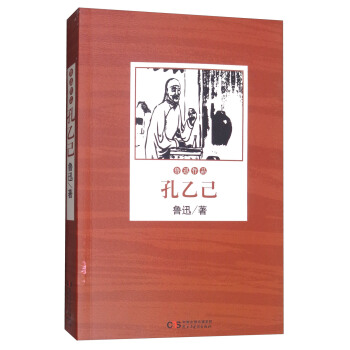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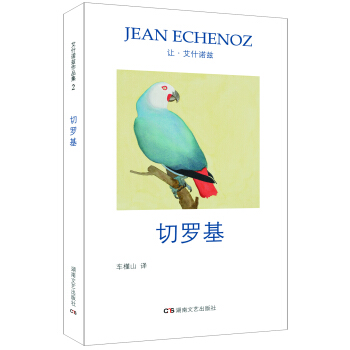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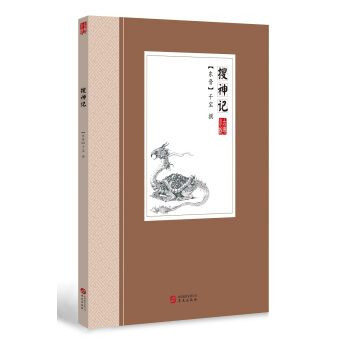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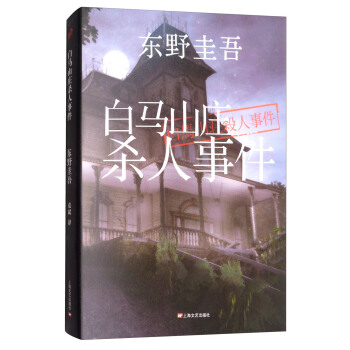
![为爱而行 [THE THINGS WE DO FOR LOV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16029/5aa8c6a8Nb7882c0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