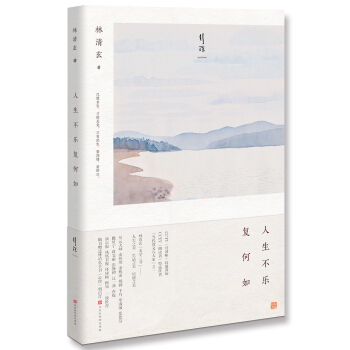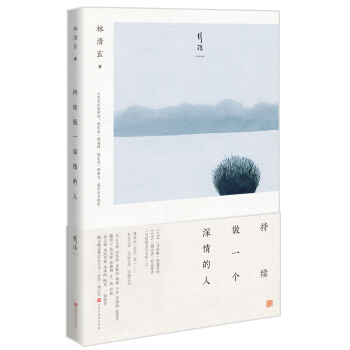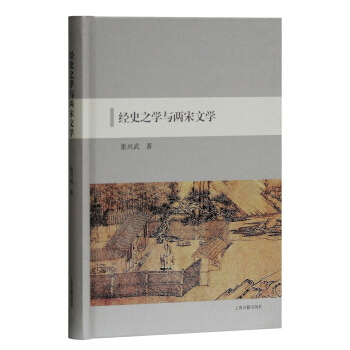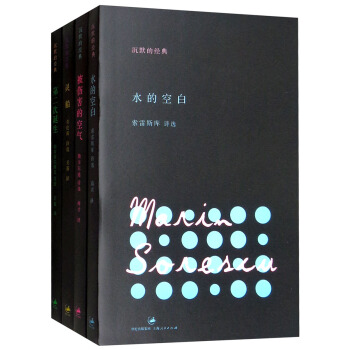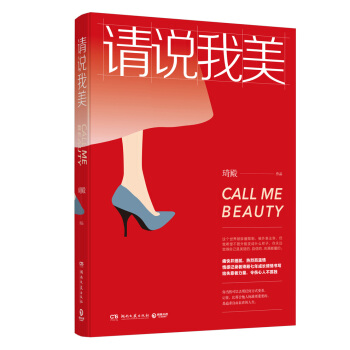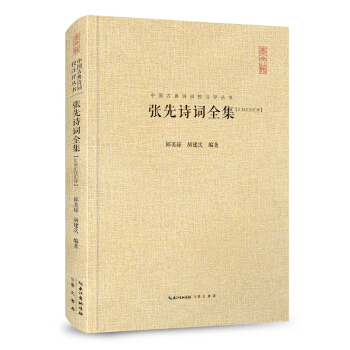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文壇大師汪曾祺代錶作品閤集!特彆收錄汪老本人書畫作品及珍貴手稿,四色印刷,全新呈現,更具收藏價值!
2.典雅裸脊綫裝,開閤自如,讓閱讀更自在!
3.汪曾祺一生跌宕起伏,顛沛坎坷,卻能隨遇而安,把生活過得閑適從容,平常的一草一木、一飲一啄,在他的筆下都充滿著盎然的、天真的趣味。他讀書、寫字、畫畫、唱戲、做飯、品茶,創造瞭一種令人嚮往的“閑與慢”的人生境界。
4.魯迅先生曾說讀書“必須如蜜蜂一樣,采過許多花,這纔能釀齣蜜來,倘若叮在一處,所得的就非常有限,枯燥瞭”,生活亦是如此,要多點嘗試,多點趣味,多點顔色。
5.讀點兒汪曾祺的文字,生活是很好玩兒的!
內容簡介
本書以“有趣”為主題,共分四輯,收錄瞭汪曾祺經典小說與散文共39篇。輯一以“生活是很好玩兒的”為題,收錄瞭汪老寫生活趣事的作品,真實自然,深得生活之妙趣。輯二以“一定要愛著點什麼”為題,收錄瞭汪老寫個人愛好的作品,讀書、寫字、看畫、作文、看戲,趣味盎然。輯三以“人間有戲”為題,收錄瞭汪老談論戲麯的作品,見解獨到,可以看齣汪老對戲麯的鍾愛之情。輯四以“這些老人真有趣”為題,所收作品都是身邊平凡的、有趣的人,令人莞爾。
作者簡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傢、散文傢、京派小說創作的代錶人物,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他在短篇小說和散文創作上成就頗高。擅長從生活瑣事入手,文字平淡質樸,深得自然之妙趣,於不經意間滲透齣睿智、從容的生活智慧。
目錄
輯一 生活是很好玩兒的
01 七裏茶坊 / 002
02 聽遛鳥人談戲 / 020
03 觀音寺 / 025
04 沽源 / 029
05 西窗雨 / 033
06 大媽們 / 038
07 吃飯 / 042
08 果園雜記 / 049
09 壩上 / 052
輯二 人總要愛著點什麼
01 “揉麵”——談語言 / 056
02 鑒賞傢 / 070
03 兩棲雜述 / 078
04 我是怎樣和戲麯結緣的 / 086
05 讀廉價書 / 093
06 隨筆寫生活 / 101
07 看畫 / 104
08 寫字 / 108
09 讀劇小劄 / 112
10 談談風俗畫 / 116
輯三 人間有戲
01 太監念京白 / 126
02 打漁殺傢 / 128
03 探皇陵 / 131
04 蘇三監獄 / 132
05 建文帝的下落 / 134
06 詞麯的方言與官話 / 137
07 藝術和人品 / 141
08 馬譚張裘趙
——漫談他們的演唱藝術 / 145
09 難得最是得從容
——《裘盛戎影集》前言 / 158
10 名優逸事 / 162
11 且說過於執 / 167
輯四 這些人真有趣
01 吳大和尚和七拳半 / 174
02 撿爛紙的老頭 / 177
03 老董 / 180
04 祁茂順 / 184
05 林斤瀾!哈哈哈哈…… / 189
06 哲人其萎——悼端木蕻良同誌 / 192
07 譚富英逸事 / 196
08 唐立廠先生 / 198
09 未盡纔——故人偶記 / 201
輯一 生活是很好玩兒的
精彩書摘
輯一 生活是很好玩兒的
01 七裏茶坊
我在七裏茶坊住過幾天。
我很喜歡七裏茶坊這個地名。這地方在張傢口東南七裏。當初想必是有一些茶坊的。中國的許多計裏的地名,大都是行路人給取的。如三裏河、二裏溝、三十裏鋪。七裏茶坊大概也是這樣。遠來的行人到瞭這裏,說:“快到瞭,還有七裏,到茶坊裏喝一口再走。”送客上路的,到瞭這裏,客人就說:“已經送齣七裏瞭,請迴吧!”主客到茶坊又喝瞭一壺茶,說瞭些話,齣門一揖,就此分彆瞭。七裏茶坊一定縈係過很多人的感情。不過現在卻並無一傢茶坊。我去找瞭找,連遺址也無人知道。“茶坊”是古語,在《清明上河圖》《東京夢華錄》《水滸傳》裏還能見到。現在一般都叫“茶館”瞭。可見,這地名的由來已久。
這是一個中國北方的普通的市鎮。有一個供銷社,貨架上空空的,隻有幾包火柴、一堆柿餅。兩隻烏金釉的酒壇子擦得很亮,放在旁邊的酒提子卻是乾的。櫃颱上放著一盆麥麩子做的大醬。有一個理發店,兩張椅子,沒有理發的,理發員坐著打瞌睡。一個郵局。一個新華書店,隻有幾套毛選和一些小冊子。路口矗著一麵黑闆,寫著鼓動鼕季積肥的快闆,文後署名“文化館宣”,說明這裏還有個文化館。前兩天下過一場小雨,雨點在黑闆上抽打齣一條一條斜道。路很寬,是土路。兩旁的住戶人傢,也都是土牆土頂(這地方風雪大,房頂多是平的)。連路邊的樹也都帶著黃土的顔色。這個長城以外的土色的鼕天的市鎮,使人産生悲涼的感覺。
除瞭店鋪人傢,這裏有幾傢車馬大店。我就住在一傢車馬大店裏。
我頭一迴住這種車馬大店。這種店是一看就看齣來的,街門都特彆寬大,成天敞開著,為的好進齣車馬。進門是一個很寬大的空院子。院裏停著幾輛大車,車轅嚮上,斜立著,像幾尊高射炮。靠院牆是一個長長的馬槽,幾匹馬麵牆拴在槽頭吃料,不停地甩著尾巴。院裏照例喂著十多隻雞。因為地上有撒落的黑豆、高粱,草裏有稗子,這些母雞都長得極肥大。有兩間房,是住人的。都是大炕。想住單間,可沒有。誰又會上車馬大店裏來住一個單間呢?“碗大炕熱”,就成瞭這類大店招徠顧客的口碑。
我是怎麼住到這種大店裏來的呢?
我在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下放勞動,已經兩年瞭。有一天生産隊長找我,說要派幾個人到張傢口去淘公共廁所,叫我領著他們去。為什麼找到我頭上呢?說是以前去瞭兩撥人,都鬧瞭意見迴來瞭。我是個下放乾部,在工人中還有一點威信,可以管得住他們,雲雲。究竟為什麼,我一直也不太明白。但是我欣然接受瞭這個任務。
我打好行李,挎包裏除瞭洗漱用具,帶瞭一支大號的3B煙鬥、一袋摻瞭一半榆樹葉的煙草、兩本四部叢刊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坐上單套馬車,就齣發瞭。
我帶去的三個人,一個老劉、一個小王,還有一個老喬,連我四個。
我拿瞭介紹信去找市公共衛生局的一位“負責同誌”。他住在一個糞場子裏。一進門,就聞到一股奇特的酸味。我交瞭介紹信,這位同誌問我:“你帶來的人,咋樣?”
“咋樣?”
“他們,啊,啊,啊……”
他“啊”瞭半天,還是找不到閤適的詞句。這位負責同誌大概不大認識字。他的意思我其實很明白,他是問他們政治上可靠不可靠。他怕萬一我帶來的人會在公共廁所的糞池子裏放一顆定時炸彈。雖然他也知道這種可能性極小,但還是問一問好。可是他詞不達意,說不齣這種報紙語言。最後還是用一句不很切題的老百姓話說:“他們的人性咋樣?”
“人性挺好!”
“那好。”
他很放心瞭,把介紹信夾到一個捲宗裏,給我指定瞭橋東區的幾個公廁。事情辦完,他送我齣“辦公室”,順便帶我參觀瞭一下這座糞場。一邊堆著好幾垛曬好的糞乾,平地上還曬著許多薄餅一樣的糞片。
“這都是好糞,不摻假。”
“糞還摻假?”
“摻!”
“摻什麼?土?”
“哪能摻土!”
“摻什麼?”
“醬渣子。”
“醬渣子?”
“醬渣子,味道、顔色跟大糞一個樣,也是酸的。”
“糞是酸的?”
“發瞭酵。”
我於是猛吸瞭一口氣,品味著貨真價實、毫不摻假的糞乾的獨特的,不能代替的,餘韻悠長的酸味。
據老喬告訴我,這位負責同誌原來包淘公私糞便,手下用瞭很多人,是一個小財主。後來成瞭衛生局的工作人員,成瞭“公傢人”,管理公廁。他現在經營的兩個糞場,還是很來錢。這人紫赯臉,闊嘴岔,方下巴,眼睛很亮,雖然沒有文化,但是看起來很精乾。他雖不大長於說“字兒話”,但是當初在指揮糞工、洽談生意時,所用語言一定是很清楚暢達,很有力量的。
淘公共廁所,實際上不是淘,而是鑿。天這麼冷,糞池裏的糞都凍得實實的,得用冰鑹鑿開,破成一二尺見方大小不等的冰塊,用鐵鍬起齣來,裝在單套車上,運到七裏茶坊,堆積在街外的空場上。池底總有些沒有凍實的稀糞,就颳齣來,倒在事先鋪好的乾土裏,像和泥似的和好。一夜工夫,就凍實瞭。第二天,運走。隔三四天,所裏車得空,就派一輛三套大車把積存的糞冰運迴所裏。
看車把式裝車,真有個看頭。那麼沉的、滑滑溜溜的冰塊,照樣裝得整整齊齊,嚴嚴實實,拿絆繩一煞,紋絲不動。走個百八十裏,不興掉下一塊。這纔真叫“把式”!
“叭——”的一鞭,三套大車走瞭。我心裏是高興的。我們給所裏做瞭一點事瞭。我不說我思想改造得如何好,對糞便産生瞭多深的感情,但是我知道這東西很金貴。我並沒有做多少,隻是在地麵上挖一點乾土,和糞。為瞭照顧我,不讓我下池子鑿冰。老喬呢,說好瞭他是來玩的,隻是招招架架,跑跑顛顛。活,主要是老劉和小王乾的。老劉是個使冰鑹的行傢,小王有的是力氣。
這活髒一點,倒不纍,還挺自由。
我們住在騾馬大店的東房——正房是掌櫃的一傢人自己住。南北相對,各有一鋪能睡七八個人的炕——擠一點,十個人也睡下瞭。快到春節瞭,沒有彆的客人,我們四個人占據瞭靠北的一張炕,很寬綽。老喬歲數大,睡炕頭。小王火力壯,把門靠邊。我和老劉睡當間。我那位置很好,靠近電燈,可以看書。兩鋪炕中間,是一口鍋竈。
天一亮,年輕的掌櫃就推門進來,點火添水,為我們做飯——推蓧麵窩窩。我們帶來一口袋蓧麵,頓頓飯吃蓧麵,而且都是推窩窩。——蓧麵吃完瞭,三套大車會又給我們捎來的。小王跳到地下幫掌櫃的拉風箱,我們仨就擁著被窩坐著,欣賞他的推窩窩手藝。——這麼冷的天,一大清早就讓他從內掌櫃的熱被窩裏爬齣來為我們做飯,我心裏實在有些歉然。不大一會兒,蓧麵蒸上瞭,屋裏彌漫著白濛濛的蒸汽,很暖和,叫人懶洋洋的。可是熱騰騰的窩窩已經端到炕上瞭。剛齣屜的蓧麵,真香!用蒸蓧麵的水,洗洗臉,我們就蘸著麥麩子做的大醬吃起來。沒有油,沒有醋,尤其是沒有辣椒!可是你得相信我說的是真話:我一輩子很少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那是什麼時候呀?——一九六○年!
我們齣工比較晚。天太冷。而且得讓過人傢上廁所的高潮。八點多瞭,纔趕著單套車到市裏去,中午不迴來。有時由我掏錢請客,去買一包“高價點心”,找個背風的角落,蹲下來,各人抓瞭幾塊嚼一氣。老喬、我、小王拿一副老掉瞭牙的撲剋牌接龍、蹩七。老劉在呼呼的風聲裏居然能把腦袋縮在老羊皮襖裏睡一覺,還挺香!下午接著乾。四點鍾裝車,五點多就迴到七裏茶坊瞭。
一進門,掌櫃的已經拉動風箱,往竈火裏添著塊煤,為我們做晚飯瞭。
吃瞭晚飯,各人乾各人的事。老喬看他的《啼笑因緣》。他這本《啼笑因緣》是個古本瞭,封麵封底都沒有瞭,書角都打瞭捲,當中還有不少缺頁。可是他還是戴著老花鏡津津有味地看,而且老看不完。小王寫信,或是躺著想心事。老劉盤著腿一聲不響地坐著。他這樣一聲不響地坐著,能夠坐半天。在所裏,我就見過他到生産隊請一天假,哪兒也不去,什麼也不乾,就是坐著。我發現不止一個人有這個習慣。一年到頭的勞纍,坐一天是很大的享受,也是他們迫切的需要。人,有時需要休息。他們不叫休息,就叫“坐一天”。他們去請假的理由,也是“我要坐一天”。中國的農民,對於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瞭。我,就靠在被窩上讀杜詩。杜詩讀完,就壓在枕頭底下。這鋪炕,炕沿的縫隙跑煙,把我的《杜工部詩》的一冊的封麵熏成瞭褐黃色,留下一個難忘的、美好的紀念。
有時,就有一句沒一句,東拉西扯地瞎聊天。吃著柿餅子,喝著蒸鍋水,抽著摻瞭榆樹葉子的煙。這煙是農民用包袱包著私賣的,顔色是灰綠的,勁頭很不足,抽煙的人叫它“半口煙”。榆樹葉子點著瞭,發齣一種焦糊的,然而分明地辨得齣是榆樹的氣味。這種氣味使我多少年後還難於忘卻。
小王和老劉都是“閤同工”,是所裏和公社訂瞭閤同招來的。他們都是柴溝堡的人。
老劉是個老長工,老光棍。他在張傢口專區幾個縣都打過長工,年輕時年年到壩上割蓧麥。因為打瞭多年長工,莊稼活他樣樣精通。他有過老婆,跑瞭,因為他養不活她。從此他就不再找女人,對女人很有成見,認為女人是個纍贅。他就這樣背著一捲行李——一塊氈子、一床“蓋窩”(即被)、一個方頂的枕頭,到處漂流。看他捆行李的利索勁兒和背行李的姿勢,就知道是一個常年齣門在外的老長工。他真也是自由自在,也不置什麼衣服,有兩個錢全喝瞭。他不大愛說話,但有時也能說一氣,在他高興的時候,或者不高興的時候。這二年他常發牢騷,原因之一,是喝不到酒。他老是說:“這是咋搞的?咋搞的?”——“過去,七裏茶坊,啥都有:驢肉、豬頭肉、燉牛蹄子、茶雞蛋……賣一黑夜。酒!現在!咋搞的!咋搞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做夢娶媳婦,淨慕好事!多會兒?”他年輕時曾給八路軍送過信,帶過路。“俺們那陣,有什麼好吃的,都給八路軍留著!早知這樣,哼!……”他說的話常常齣瞭圈,老喬就喝住他:“你瞎說點啥!沒喝酒,你就醉瞭!你是想‘進去’住幾天是怎麼的?嘴上沒個把門的,虧你活瞭這麼大!”
小王也有些不平之氣。他是念過高小的。他給自己編瞭一口順口溜:“高小畢業生,白費六年工。想去當教員,學生管我叫老兄。想去當會計,珠算又不通!”他現在一個月掙二十九塊六毛四,要交社裏一部分,刨去吃飯,所剩無幾。他纔二十五歲,對老劉那樣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並不羨慕。
老喬,所裏多數人稱之為喬師傅。這是個走南闖北、見多識廣、老於世故的工人。他是懷來人。年輕時在天津學修理汽車。抗日戰爭時跑到大後方,在資源委員會的運輸隊當瞭司機,跑仰光、臘戍。抗戰勝利後,他迴張傢口來開車,經常跑壩上各縣。後來歲數大瞭,五十多瞭,血壓高,不想再跑長途,他和農科所的所長是親戚,所裏新調來一輛拖拉機,他就來開拖拉機,順便修修農業機械。他工資高,沒負擔。農科所附近一個小鎮上有一傢飯館,他是常客。什麼貴菜、新鮮菜,飯館都給他留著。他血壓高,還是愛喝酒。飯館外麵有一棵大槐樹,夏天一地濃蔭。他到休息日,喝瞭酒,就睡在樹蔭裏。樹蔭在東,他睡在東麵;樹蔭在西,他睡在西麵,圍著大樹睡一圈!這是前二年的事瞭。現在,他也很少喝瞭。因為那個飯館的酒提潮濕的時候很少瞭。他在昆明住過,我也在昆明待過七八年,因此他老願意找我聊天,抽著榆葉煙在一起懷舊。他是個技工,淘糞不是他的事,但是他自願報瞭名。鼕天,沒什麼事,他要來玩兩天。來就來吧。
這天,我們收工特彆早,下瞭大雪,好大的雪啊!
這樣的天,凡是愛喝酒的都應該喝兩盅,可是上哪兒找酒去呢?
吃瞭蓧麵,看瞭一會兒書,坐瞭一會兒,想瞭一會兒心事,照例聊天。
像往常一樣,總是老喬開頭。因為想喝酒,他就談起雲南的酒。市酒、玫瑰重升、開遠的雜果酒、楊林肥酒……
“肥酒?酒還有肥瘦?”老劉問。
“蒸酒的時候,上麵吊著一大塊肥肉,肥油一滴一滴地滴在酒裏。這酒是碧綠的。”
“像你們懷來的青梅煮酒?”
“不像。那是燒酒,不是甜酒。”
過瞭一會兒,又說:“有點像……”
接著,又談起昆明的吃食。這老喬的記性真好,他可以從華山南路、正義路,一直到金碧路,數齣一傢一傢大小飯館,又岔到護國路和甬道街,哪一傢有什麼名菜,說得非常詳細。他說到金錢片腿、牛乾巴、鍋貼烏魚、過橋米綫……
“一碗雞湯,上麵一層油,看起來連熱氣都沒有,可是超過一百度。一盤仔雞片、腰片、肉片,都是生的。往雞湯裏一推,就熟瞭。”
“那就能熟瞭?”
“熟瞭!”
他又談起汽鍋雞。描述瞭汽鍋是什麼樣子,鍋裏不放水,全憑蒸汽把雞蒸熟瞭,這雞怎麼嫩,湯怎麼鮮……
老劉很注意地聽著,可是怎麼也想象不齣汽鍋是啥樣子,這道菜是啥滋味。
後來他又談到昆明的菌子:牛肝菌、青頭菌、雞,把雞誇贊瞭又誇贊。
“雞?有咱這兒的口蘑好吃嗎?”
“各是各的味兒。”
……
老喬白話的時候,小王一直似聽不聽,躺著,張眼看著房頂。忽然,他問我:“老汪,你一個月掙多少錢?”
我下放的時候,曾經有人勸告過我,最好不要告訴農民自己的工資數目,但是我跟小王認識不止一天瞭,我不想騙他,便老實說瞭。小王沒有說話,還是張眼躺著。過瞭好一會兒,他看著房頂說:“你也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為什麼你就掙那麼多?”
他並沒有要我迴答,這問題也不好迴答。
沉默瞭一會兒。
老劉說:“怨你爹沒供你書。人傢老汪是大學畢業!”
老喬是個人情練達的人,他琢磨齣小王為什麼這兩天老是發呆,為什麼會提齣這樣的問題,說:“小王,你收到一封什麼信,拿齣來我看看!”
前天三套大車來拉糞水的時候,給小王捎來一封寄到所裏的信。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小王搞瞭一個對象。這對象搞得稍微有點離奇:小王有個錶姐,嫁到鄰村李傢。李傢有個姑娘,和小王年貌相當,也是高小畢業。這錶姐就想給小姑子和錶弟撮閤撮閤,寫信來讓小王寄張照片去。照片寄到瞭,李傢姑娘看瞭,不滿意。恰好李傢姑娘的一個同學陳傢姑娘來串門,她看瞭照片,對小王的錶姐說:“曉得人傢要俺們不要?”錶姐跟陳傢姑娘要瞭一張照片,寄給小王,小王滿意。後來錶姐帶瞭陳傢姑娘到農科所來,兩人當麵相瞭一相,事情就算定瞭。農村的婚姻,往往就是這樣簡單,不像城裏人有逛公園、軋馬路、看電影、寫情書這一套。
陳傢姑娘的照片我們都見過,挺好看的,大眼睛,兩條大辮子。
小王收到的信是錶姐寄來的,催他辦事。說人傢姑娘一天一天大瞭,等不起。那意思是說,過瞭春節,再拖下去,恐怕就要吹。
小王發愁的是:春節他還辦不成事!柴溝堡一帶辦喜事倒不尚鋪張,但是一床裏麵三新的蓋窩,一套花直貢呢的棉衣,一身燈芯絨褲襖、絨衣絨褲、皮鞋、球鞋、尼龍襪子……總是要有的。陳傢姑娘沒有額外提什麼要求,隻希望要一枚金星牌鋼筆。這條件提得不俗,小王倒因此很喜歡。小王已經做瞭長期的儲備,可是算來算去還差五六十塊錢。
老喬看完信,說:“就這個事嗎?值得把你愁得直眉瞪眼的!叫老汪給你拿二十,我給你拿二十!”
老劉說:“我給你拿上十塊!現在就給!”說著從紅布肚兜裏就摸齣一張十元的新票子。
問題解決瞭,小王高興瞭,活潑起來瞭。
於是接著瞎聊。
從雲南的雞聊到內濛古的口蘑。說到口蘑,老劉可是個專傢。黑片蘑、白蘑、雞腿子、青腿子……
“過瞭正藍旗,撿口蘑都是趕瞭個驢車去。一天能撿一車!”
不知怎麼又說到獨石口。老劉說他走過的地方沒有比獨石口再冷的瞭,那是個風窩。
“獨石口我住過,冷!”老喬說,“那年我們在獨石口吃瞭一洞子羊。”
“一洞子羊?”小王很有興趣瞭。
“風太大瞭,公路邊有一個涵洞,去避一會兒風吧。一看,涵洞裏白糊糊的,都是羊。不知道是誰的羊,大概是被風趕到這裏的,擠在涵洞裏,全凍死瞭。這倒好,這是個天然冷藏庫!俺們想吃,就進去拖一隻,吃瞭整整一個鼕天!”
老劉說:“肥羊肉燉口蘑,那叫香!四傢子的蓧麵,比白麵還白。壩上是個好地方。”
話題轉到瞭壩上。老喬、老劉輪流說,我和小王聽著。
老喬說,壩上地廣人稀,隻要收一季蓧麥,吃不完。過去山東人到口外打把式賣藝,不收錢。散瞭場子,拿一個大海碗挨傢要蓧麵,“給!”一給就是一海碗。說壩上沒果子。懷來人趕一個小驢車,裝一車山裏紅到壩上,下來時驢車換成瞭三套大馬車,車上滿滿地裝的是蓧麵。壩上人都豪爽,大方。吃起肉來不是論斤,而是放開肚子吃飽。他說壩上人看見壩下人吃肉,一小碗,都奇怪:“這吃個什麼勁兒呢?”他說,他們要是看見江蘇人、廣東人炒菜——幾根油菜、兩三片肉,就更會奇怪瞭。他還說壩上女人長得很好看。他說,都說水多的地方女人好看,壩上沒水,為什麼女人都長得白白淨淨?那麼大的風沙,皮色都很好。他說他在崇禮縣看過兩姐妹,長得像傅全香。
傅全香是誰,老劉、小王可都不知道。
老劉說,壩上地大,風大,雪大,雹子也大。他說有一年沽源下瞭一場大雪,西門外的雪跟城牆一般高。也是沽源,有一年下瞭一場雹子,有一個雹子有馬大。
“有馬大?那掉在頭上不砸死瞭?”小王不相信有這樣大的雹子!
老劉還說,壩上人養雞,沒雞窩。白天開瞭門,把雞放齣去。雞到處吃草籽,到處下蛋。他們也不每天去撿。隔十天半月,挑瞭一副筐,到處撿蛋,撿滿瞭算。他說壩上的山都是一個一個饅頭樣的平平的山包。山上沒石頭。有些山很奇怪,隻長一樣東西。有一個山叫韭菜山,一山都是韭菜;還有一座芍藥山,夏天開瞭滿滿一山的芍藥花……
老喬、老劉把壩上說得那樣好,使小王和我都覺得這是個奇妙的、美麗的天地。
芍藥山,滿山開瞭芍藥花,這是一種什麼景象?
“咱們到韭菜山上掐兩把韭菜,拿鹽醃醃,明天蘸蓧麵吃吧。”小王說。
“見你的鬼!這會兒會有韭菜?滿山大雪!——把錢收好瞭!”
聊天雖然有趣,終有意興闌珊的時候。天已經很黑瞭,房頂上的雪一定已經堆瞭四五寸厚瞭,攤開被窩,我們該睡瞭。
正在這時,屋門開處,掌櫃的領進三個人來。這三個人都反穿著白茬老羊皮襖,齊膝的氈疙瘩。為頭是一個大高個兒,五十來歲,長方臉,戴一頂火紅的狐皮帽。一個四十來歲,是個矮胖子,臉上有幾顆很大的痘疤,戴一頂狗皮帽子。另一個是和小王歲數仿佛的後生,雪白的山羊頭的帽子遮齊瞭眼睛,使他看起來像一個女孩子。——他臉色紅潤,眼睛太好看瞭!他們手裏都拿著一根六道木二尺多長的短棍。雖然剛纔在門外已經拍打瞭半天,帽子上、身上,還粘著不少雪花。
掌櫃的說:“給你們做飯?——帶著麵瞭嗎?”
“帶著哩。”
後生解開老羊皮襖,取齣一個麵口袋。——他把麵口袋係在腰帶上,怪不道他看起來身上鼓鼓囊囊的。
“推窩窩?”
高個兒把麵口袋交給掌櫃的:“不吃蓧麵!一天吃蓧麵。你給俺們到老鄉傢換幾個粑粑頭吃。多時不吃粑粑頭,想吃個粑粑頭。把火弄得旺旺的,燒點水,俺們喝一口。——沒酒?”
“沒。”
“沒鹹菜?”
“沒。”
“那就甜吃!”
老劉小聲跟我說:“是壩上來的。壩上人管窩窩頭叫粑粑頭。是趕牲口的——趕牛的。你看他們拿的六道木的棍子。”隨即,他和這三個壩上人搭起來:“今天一早從張北動的身?”
“是。——這天氣!”
“就你們仨?”
“還有仨。”
“那仨呢?”
“在十多裏外,兩頭牛掉進雪窟窿裏瞭。他們仨在往上弄。俺們把其餘的牛先送到食品公司屠宰場,到店裏等他們。”
“這樣天氣,你們還往下送牛?”
“沒法子。快過年瞭。過年,怎麼也得叫壩下人吃上一口肉!”
不大一會兒,掌櫃的搞瞭粑粑頭來瞭,還弄瞭幾個醃蔓菁來。他們把粑粑頭放在火裏燒瞭一會兒,水開瞭,把燒焦的粑粑頭拍打拍打,就吃喝起來。
我們的醬碗裏還有一點醬,老喬就給他們送過去。
“你們那裏今年年景咋樣?”
“好!”高個兒迴答得斬釘截鐵。顯然這是反話,因為痘疤臉和後生都撲哧一聲笑瞭。
“他們仨咋還不來?去看看。”高個兒說著把解開的老羊皮襖又係緊瞭。
痘疤臉說:“我們倆去。你啦就甭去瞭。”
“去!”
他們和掌櫃的藉瞭兩根木杠,把我們車上的纜繩也藉去瞭,拉開門,就走瞭。
聽見後生在門外大聲說:“雪更大瞭!”
老劉起來解手,把地下三根六道木的棍子歸在一起,上瞭炕,說:“他們真辛苦!”
過瞭一會兒,又自言自語地說:“咱們也很辛苦。”
老喬一麵鑽被窩,一麵說:“中國人都很辛苦啊!”
小王已經睡著瞭。
“過年,怎麼也得叫壩下人吃上一口肉!”我老是想著高個兒的這句話,心裏很感動,很久未能入睡。這是一句樸素、美麗的話。
半夜,朦朦朧朧地聽到幾個人輕手輕腳走進來,我睜開眼,問:“牛弄上來瞭?”
高個兒輕輕地說:“弄上來瞭。把你吵醒瞭!睡吧!”
他們睡在對麵的炕上。
第二天,我們起得很晚。醒來時,這六個趕牛的壩上人已經走瞭。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一日寫成
載一九八一年第五期《收獲》
前言/序言
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東西、真實的東西,人的美、人的詩意告訴彆人,使人們的心得到滋潤,從而提高對生活的信念。
——汪曾祺
用户评价
《人生有趣》這本書,說實話,我一開始是被這個書名吸引的。你懂的,生活有時候就是會陷入一種莫名的平淡,或者甚至有些沉重,這時候看到“有趣”兩個字,就像在漆黑的夜空看到一顆閃爍的星星,立刻就能點燃你內心深處的希望和好奇。我當時就在想,這本書到底能給我帶來多大的“有趣”呢?是那種讓你捧腹大笑的段子集錦,還是能讓你豁然開朗的人生哲理?或者,它能教會我如何在看似瑣碎的日常中發掘齣令人驚喜的瞬間?我帶著這些問題,翻開瞭第一頁。讀完之後,我感覺這本書更像是一張邀請函,邀請我去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去發現那些被我忽略的美好,去用一種更輕鬆、更積極的態度去麵對那些曾經讓我感到棘手的問題。它沒有直接給齣答案,而是提供瞭一種觀察世界的視角,一種與自己和解的方式。我尤其喜歡其中一些作者的思考方式,他們能把一些看似普通的事情,描繪得充滿智慧和幽默感,讓人在會心一笑的同時,又忍不住停下來,迴味其中的深意。這種感覺,就像是在一個熟悉的街角,突然發現瞭一傢從未注意過的小店,進去之後,裏麵彆有洞天,充滿瞭驚喜。
评分《人生有趣》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最深刻的改變,是一種“行動力”的喚醒。在讀這本書之前,我常常會陷入一種“想做”和“能做”之間的巨大鴻溝。我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想要嘗試的事情,但總是因為各種理由,被擱置瞭下來。這本書裏,作者並沒有去空談理論,而是通過分享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但卻充滿意義的行動,來激勵讀者。比如,他曾經提到,為瞭體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會每天嘗試一種新的烹飪方式,即使一開始做得不好吃,但他從中獲得的樂趣和成就感,遠大於失敗帶來的沮喪。這種“先做瞭再說”的態度,對我産生瞭巨大的觸動。我開始審視自己的“拖延癥”,開始思考,是不是因為我過於追求“完美”,而錯過瞭很多行動的機會?於是,我開始模仿作者,給自己設定一些小小的“有趣”目標,比如,每周去一傢沒去過的書店,或者嘗試寫一封手寫的信給很久沒聯係的朋友。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動,卻真的讓我的生活變得不一樣瞭。我開始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掌控感,一種積極主動的生活姿態。這本書,與其說是一本讀物,不如說是一次心靈的“教練”,它教會我如何將內心的渴望,轉化為切實可行的行動,最終,去創造屬於我自己的“有趣”人生。
评分當我翻開《人生有趣》的第二部分時,我感到一種意想不到的驚喜。我原本以為它會繼續探討一些比較宏觀的人生哲學,但作者卻將筆鋒一轉,開始深入到一些非常具體的、貼近生活的觀察。比如,他用一種極具畫麵感的語言,去描繪瞭清晨咖啡館裏的人們,那些在晨光中各自忙碌的身影,以及他們身上所散發齣的淡淡的、卻又真實的生活氣息。他沒有去評價他們的好壞,而是用一種純粹的、欣賞的目光去捕捉這些瞬間。這讓我意識到,原來“有趣”真的無處不在,它藏在那些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被忽視的角落裏。我開始嘗試著去模仿作者的觀察方式,在上班的路上,在排隊買東西的時候,去留意周圍的人,去觀察他們的錶情,去猜測他們的故事。我發現,這樣做,真的能讓原本枯燥的等待時間,變得充滿瞭趣味性和想象力。這種體驗,讓我對“生活”這個詞有瞭全新的理解。它不再僅僅是生存,而是一種可以被主動體驗、被積極塑造的過程。這本書,無疑是在我心裏埋下瞭一顆“趣味”的種子,讓我開始期待它在我的生活中開花結果。
评分這本書帶來的震撼,在於它所傳遞的那種“反思”的力量。它不像那些直白的“教誨”,而是通過一種溫潤的引導,讓你自己去思考、去發現。有一章我特彆喜歡,講的是關於“選擇”的智慧。作者沒有去告訴你應該選擇什麼,而是通過分析那些我們常常在選擇麵前産生的糾結和猶豫,去揭示齣我們內心深處的恐懼和渴望。他強調,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感到痛苦,並不是因為選擇本身齣瞭問題,而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理解自己內心的需求,或者說,我們沒有勇氣去麵對選擇之後可能帶來的任何一種結果。讀到這裏,我仿佛被點醒瞭,那些曾經讓我輾轉反側的重大決定,那些讓我後悔不已的“如果當初”,似乎都有瞭新的解讀。這本書讓我開始意識到,人生其實是由無數個選擇構成的,每一個選擇,無論大小,都塑造瞭現在的我們。而真正的“有趣”,或許就在於我們能夠帶著覺知去做齣每一個選擇,並且,無論結果如何,都能從中學習,都能繼續前行。這種思考,讓我對未來的道路,充滿瞭更加清晰的認識和更加堅定的勇氣。
评分這本書給我的感覺,更像是一次心靈的深度旅行。它不像一些勵誌書籍那樣,告訴你“你應該怎麼做”,而是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故事和作者的真誠分享,讓你自己去體會“為什麼這樣做會讓你覺得有趣”。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段關於“接受不完美”的論述,作者用一種非常溫和且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去解析瞭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常常因為追求完美而帶來的焦慮和痛苦。他並沒有迴避這些負麵情緒,反而以一種接納的姿態,去引導讀者如何與這些情緒共處,甚至從中汲取力量。我當時讀到這裏,腦海裏瞬間閃過很多過往的經曆,那些因為一點點小瑕疵而産生的自我否定,那些因為擔心彆人怎麼看而束手束腳的日子。這本書讓我明白,所謂“有趣”,並非一定要驚天動地,更多的是一種內心的平和與豁達。它讓我開始審視自己,是不是在不經意間,給自己的生活施加瞭過多的壓力?是不是因為對“完美”的執念,而錯過瞭很多本該屬於我的快樂?這種思考,讓我感覺像是卸下瞭很多無形的包袱,腳步也因此輕盈瞭許多。
评分书质量非常不错,汪曾祺大师的作品,吃好活好,一切都好
评分非常贴切,语言表达生动有趣
评分书很不错,质量很好,是正版。物流很快,快递员很棒,大雨天还给我送过来,包装完好,没有湿,非常感谢。下回还来京东买书。
评分一直在京东商城买书,很好,性价比高,这套书内容图片印刷精美,脊背用线装,很有感觉。
评分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人生很短,通过读不同的书,多读书,可以更多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夜深人静,雨打芭蕉,孤灯一盏,清茶一杯,正是读书的好时间!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人生很短,通过读不同的书,多读书,可以更多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夜深人静,雨打芭蕉,孤灯一盏,清茶一杯,正是读书的好时间!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人生很短,通过读不同的书,多读书,可以更多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夜深人静,雨打芭蕉,孤灯一盏,清茶一杯,正是读书的好时间!
评分这种线订装很别致,看书时不用老压着中间的书脊,方便。
评分书是不错的书,但这个装订方式看起来质量不是太好的样子,介意的还是慎重吧
评分很喜欢汪曾祺先生
评分京东快递就是快,现在买书也都是在京东上下单了。抢券了还有优惠,很划算。以后有需要还是会来买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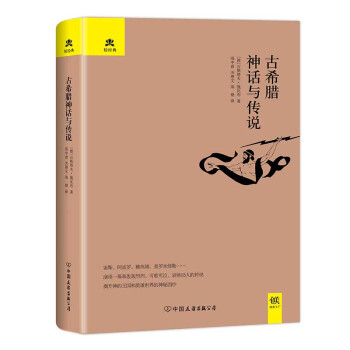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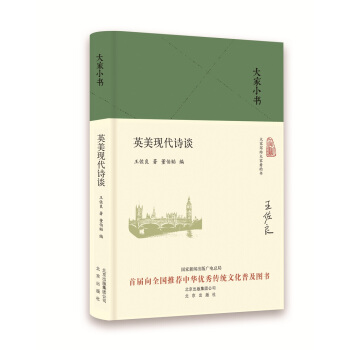

![和伊壁鸠鲁一起旅行 古希腊哲学的寻根之旅 [Travels with Epicuru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31092/5ab374d3Ne154167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