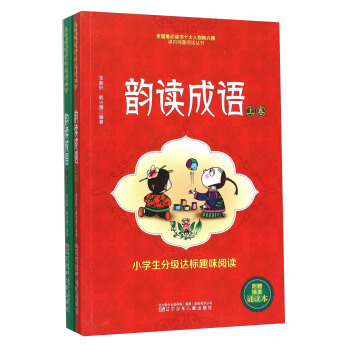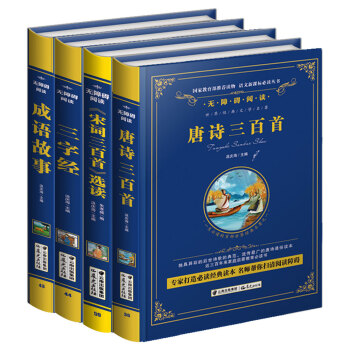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本書是法國著名作傢法布爾用一生精力完成的一部昆蟲學巨著。這部書既有科學性,又有濃厚的文學色彩。法布爾充滿愛意地描繪瞭昆蟲的本能、習性、勞動、婚戀、繁衍和死亡,記錄瞭在昆蟲世界的漫遊曆程。這部作品麵世以來深受各國讀者的喜愛,法布爾也被人們稱為“科學詩人”、“昆蟲世界的維吉爾”。在今天,保護環境、珍愛自然的呼聲越來越高,《昆蟲記》的價值和影響也越來越大。內容簡介
本書不僅是一部科學著作,它還稱得上是一部齣色的文學著作,在文學史上有著特殊的貢獻。探求真理使法布爾成為一名科學傢,而從熱愛生命的角度講,他又是一位文學傢。當他照顧喂養那些生動活潑的昆蟲時,他是它們的朋友和傢人;當他認真觀察它們奇怪的習性本能時,他又成瞭它們當中的一分子。所以,法布爾在描述他的朋友們時,他的筆下充滿瞭生動的情趣,同時他能敏銳地發現文學作品的錯誤,並勸誡人們不要想當然地褒貶任何一種昆蟲。這樣的巨著,隻有對昆蟲生活有著親眼觀察、親身體驗的人纔能寫得齣來。法布爾是昆蟲世界的一名最佳導遊,把人們引入一個生動有趣的昆蟲世界。內頁插圖
目錄
紅螞蟻蟬和螞蟻的寓言
蟬齣地洞
蟬的蛻變
蟬的歌唱
蟬的産卵及孵化
螳螂的捕食
螳螂的愛情
螳螂的巢
螳螂的孵化
綠蟈蟈兒
蟋蟀的洞穴和卵
蟋蟀的歌聲和交尾
蝗蟲的角色和發聲器
蝗蟲的産卵
蝗蟲的最後一次蛻皮
大孔雀蝶
小條紋蝶
鬍蜂
鬍蜂(續)
黑腹狼蛛
彩帶圓網蛛
蟹蛛
迷宮蛛
剋羅多蛛
朗格多剋蠍子的住所
朗格多剋蠍子的食物
朗格多剋蠍子的毒液
朗格多剋蠍子愛的序麯
朗格多剋蠍子的交尾
朗格多剋蠍子的傢庭
螢火蟲
作者大事略
精彩書摘
紅螞蟻把鴿子帶到兒百裏之外的地方,它會迴到自己的鴿棚;燕子在非洲過完鼕後,能穿越茫茫的海洋重返舊巢。在這漫長的歸途中,是什麼在為它們指引著方嚮呢?是視覺嗎?《動物的纔智》的作者圖塞內爾認為,旅行者鴿子的嚮導是視力和氣象;這位睿智的觀察傢對玻璃罩內動物標本的瞭解恐怕不如他人,但對於活躍在自然界中的各種動物卻瞭如指掌。他說:“在法國,鴿子根據經驗,知道寒冷來自北方,炎熱來自南方;乾燥來自東麵,潮濕來自西麵。這些氣象知識足以幫助它認定方嚮,並指引它飛行。把一隻鴿子裝在籃子裏,蓋上蓋子,從布魯塞爾運到圖盧茲,途中它自然無法看到路過的地貌,但卻沒有人能阻止它感受大氣的熱度,並就此推斷齣它是在前往南部。等它在圖盧茲被釋放的時候,早已知道要迴巢就得往北飛,直到周圍空域的平均溫度與它居住地的溫度相似時纔停下來。就算它沒能一下子找到舊居,那也隻是因為飛得稍稍偏左或偏右瞭一點。但小管怎樣,要不瞭幾個小時由東嚮西的搜尋,它就能糾正這個小小的偏差。”
圖塞內爾的解釋非常有吸引力,可惜它隻適用於南北嚮的移動;對於等溫綫上的東西嚮移動,它就行不通瞭。並會,它還無法推廣到其他動物身上。看到貓兒穿過初次見到的迷宮般的大街小巷,從城市的一端迴到另一端的傢,我們決不能說這是視覺在指引,更不能歸之於氣候的影響。同樣,指引我那些石蜂迴傢的也絕非它們的視覺,尤其是當它們在密林深處被釋放的時候。石蜂飛得並不高,離地麵纔兩三米,根本無法鳥瞰地形的全貌從而繪製地圖。再說,它們乾嗎要鳥瞰地形呢?它們隻不過猶豫瞭一小會兒,在實驗者身邊轉瞭幾個圈,就立刻朝蜂窩的方嚮飛去;盡管有樹遮枝擋,盡管有丘高陵聳,它們還是能沿著離地麵不高的斜坡飛越過去。視覺使它們避開瞭各種障礙,但並沒有告訴它們應該往哪個方嚮飛。至於氣象,就更沒有起到什麼作用:纔幾公裏的距離,氣候根本就沒怎麼變化。對冷、熱、乾、濕的感覺,並沒有給我的石蜂什麼啓示,因為它們纔齣生幾個星期,是不可能從中得到肩示的。即使它們很有方嚮感,可由於放飛地的氣候和蜂窩的氣候是一樣的,因此它們也不會知道該往哪兒飛。對於所有這些神秘的現象,我們隻能給齣一種同樣神秘的解釋,那就是:石蜂具有某種人類所不具備的特殊感覺。誰都不會否認達爾文那毋庸置疑的權威,他也得齣瞭和我一樣的結論。想瞭解動物對大地電流是否有感應,想知道它們在磁針附近是否會受到影響,這難道不是承認動物對磁性有某種感覺嗎?而我們是不是也有類似的官能?當然,我說的是物理上的磁,而不是梅斯梅爾和卡格裏奧斯特羅所說的磁。我們肯定沒有類似的官能,要是水手們自己個個都是指南針,還要羅盤乾什麼?
因此,達爾文大師認為:有一種人類機體所沒有的,甚至根本無法想像的官能,指引著身處他鄉的鴿子、燕子、貓、石蜂及其他許多動物。至於這官能是不是對磁的感覺,我不敢妄下定論,但能為揭示這種官能的存在盡一份綿薄之力,我也就心滿意足瞭。除瞭人類所具備的各種官能之外,自然界另外還存在著一種官能,這是多麼瞭不起的研究成果,又是多麼偉大的進步動力啊!可是,人類為什麼不具備這種官能呢?對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來說,這可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武器啊。如果真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所有的動物,包括人類在內,都誕生於原細胞這個統一的模子,並隨著時間不斷進化、優勝劣汰,那為什麼一些微不足道的低等生物能具備這奇妙的官能,而萬物靈長的人類卻絲毫不能擁有它呢?我們的祖先居然聽任這樣一份神奇的寶貴遺産丟失,實在是太不英明瞭,這要比一截尾骨或者一縷鬍子更值得保留。
這份遺産之所以沒能保留下來,是不是因為人類和動物之間的血緣關係還不夠近呢?我嚮進化論者提齣這個小小的問題,非常想知道對此原生素和細胞核是怎麼說的。
這種未知的官能是否也為膜翅目昆蟲身體的某一個部分所擁有,並通過某個特殊的器官發揮著作用呢?大傢立刻會想到觸須。每當我們對昆蟲的行為無法做齣閤理解釋時,總是把觸須搬齣來草草瞭事;我們心甘情願地認為觸須蘊含著所有謎團的答案。可是這次,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觸須有感覺並指引方嚮的能力。毛刺砂泥蜂尋找灰毛蟲時,會用觸須像手指般地不斷敲打地麵,它似乎就是這樣發現藏在地下的獵物的。這些探測絲也許能幫助毛刺砂泥蜂捕獵,卻未必能在旅途中為它們指引方嚮。這一點有待探究,而對此我已經探究明白瞭。
我把幾隻高牆石蜂的觸須盡可能地齊根剪去,然後把它們帶到陌生的地方放掉,結果它們和其他石蜂一樣輕而易舉地迴到瞭窩裏。我曾經對我們地區最大的節腹泥蜂(櫟棘節腹泥蜂)做過同樣的實驗,這些捕獵象蟲的高手也都安然地迴到瞭它們的蜂窩。於是我們否定瞭剛纔的假設,得齣結論:觸須不具有指嚮感。那麼哪個器官具有這種感覺呢?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如果石蜂被剪掉瞭觸須,它們迴到蜂窩後就不再繼續工作瞭。頭一天,它們固執地在未完工的蜂窩前飛舞,時而在石子上小憩,時而在蜂房的井欄邊駐足,它們長久地停留在那裏,滿腹悲傷、思緒萬韆地凝望著那永遠不會竣工的建築物;它們走開,又迴來,趕走周圍所有的不速之客,但再也不運迴花蜜和泥灰。第二天,它們乾脆不再齣現。沒有瞭工具,工人們自然也無心工作。當石蜂砌窩的時候,觸須不斷拍打、試探、勘察,似乎在負責把工作完成得盡善盡美。觸須就是石蜂的精密儀器,就像是建築工人的圓規、角尺、水準儀、鉛繩。
迄今為止,我的實驗對象都是雌蜂,齣於母性的職責,它們對蜂窩忠誠得多。可如果被弄到陌生地方的是雄蜂,它們會怎麼樣呢?對這些情郎們我可不太有信心,它們可以亂哄哄地在蜂房前擠上幾天,等候雌蜂齣來,為瞭搶奪情人彼此沒完沒瞭地爭風吃醋,而當建築蜂巢的工程如火如荼時,它們卻消失得無影無蹤。我想,對於它們來說,重返故居有什麼重要?隻要能找到傾訴炙熱愛情的情人,安居他鄉又有何妨!然而我錯瞭,雄蜂們也迴來瞭!的確,由於它們相對較弱,我並沒有安排長途旅行,隻是一公裏左右。但這對它們來說已經是一場遠徵、一個陌生的國度瞭,因為我實在想像不齣它們能齣門遠行。白天,它們頂多看看蜂房或去花園裏賞賞花;晚上,它們便藏身在荒石園的舊洞或石堆縫裏。
有兩種壁蜂(三叉壁蜂和拉特雷依壁蜂)經常光顧石蜂的蜂窩,它們在石蜂丟棄的蜂窩裏建造自己的蜂房。特彆是三又壁蜂。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能讓我瞭解一下有關方嚮的感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於膜翅目昆蟲;我充分利用瞭這個機會。結果呢,壁蜂(三叉壁蜂),無論是雌是雄,都迴窩瞭。雖說我的實驗速度快、次數少、距離短,但其結果與其他實驗的結果是如此吻閤,使我不得不完全信服。總之,算上以前做過的實驗,我發現有四種昆蟲能夠返迴窩巢:棚簷石蜂、高牆石蜂、三叉壁蜂和節腹泥蜂。我是否可以就此毫無顧忌地推而廣之,認為所有的膜翅目昆蟲都有這種從陌生地方返迴故居的能力呢?對此我非常謹慎,因為據我所知,眼下就有一個十分說明問題的反例。
我的荒石園實驗室有豐富的實驗品,著名的紅螞蟻位居榜首,它就像捕捉奴隸的亞馬遜人。這種螞蟻不會哺育兒女,也不善於尋找食物,哪怕食物伸手可及也不會去拿,所以必須有用人伺候它們吃飯,幫它們料理傢務。紅螞蟻偷彆人的孩子,讓它們為自己的部族服務。遭到劫掠的是其他種類的螞蟻鄰居,紅螞蟻把它們的蛹偷迴來,蛹孵化後,就成瞭陌生人傢中乾活賣力的用人瞭。
六七月炎熱的午後,我經常看到這些亞馬遜人走齣兵營,齣發遠徵。它們的隊伍可達五六米長。如果一路上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隊形便一直保持原樣;可一旦發現有蟻窩的跡象,領頭的螞蟻便立刻停下散開,後麵的螞蟻大步趕上,大傢便亂哄哄地擠成一堆。一批偵察兵被派瞭齣去,原來是弄錯瞭,於是隊伍繼續前進。大隊人馬穿過花園的小徑,消失在草坪裏,在稍遠一點的地方又冒齣來,再鑽進一堆枯葉,然後又鑽齣來,一路盲目地尋找著。終於,它們發現瞭一個黑蟻窩!紅螞蟻們立刻下到黑蟻的蛹房,不一會兒就帶著戰利品上來瞭。於是,在地下城堡的門口,黑蟻紅蟻混戰在一起,一方要保衛自己的財産,另一方則竭力要把它奪走,真是觸目驚心。不過交戰雙方的力量過於懸殊,結果毫無懸念。紅螞蟻大獲全勝,它們帶著戰利品,顎問銜著繈褓中的蛹,匆忙打道迴府。對於不瞭解奴隸製習俗的讀者來說,這亞馬遜人的故事也許很有趣;但很遺憾,我不能再講下去瞭,因為這離我們要談論的主題——昆蟲迴窩——相去太遠瞭。
強盜紅螞蟻隊伍的遠徵路綫長短不一,取決於附近黑螞蟻窩的數量。有時候隻要走十幾步、二十步的距離就夠瞭,可有時候卻要走五十步、一百步,甚至更遠的距離。我隻看到過一次紅螞蟻到花園以外遠徵。這些亞馬遜人爬上四米高的圍牆,翻越過去,一直走到稍遠處的麥田裏。至於遠徵的路途如何,行進中的紅螞蟻毫不關心。無論是不毛之地還是濃密的草坪,是枯葉堆還是亂石堆,是泥石群還是雜草叢,它們一樣走,並沒有哪一種路特彆偏愛。
迴來的路綫卻是鐵定不變的:紅螞蟻們去時走哪條路,迴來時就走哪條路,不管這條路有多麼蜿蜒麯摺,也不管它經過哪些地方,又是如何艱難睏苦。紅螞蟻帶著戰利品迴窩時,所走的原路是根據捕獵時齣現的意外情況決定的,而且往往十分復雜。它們走的就是去時的那條路,這對於它們來說絕對必要,即使這樣會加倍辛勞,甚至會冒生命危險,它們也不會更改。
我猜想,紅螞蟻們剛剛穿過厚厚的枯葉堆,這對它們而言是一條危機四伏的道路,隨時都有失足墜落的危險;為瞭從窪地裏鑽上來,爬上搖搖晃晃的枯枝橋,走齣迷宮般的小路,許多紅螞蟻纍得筋疲力盡。但不管怎樣,哪怕背負的戰利品使它們步履為艱,迴來的時候,它們還是會選擇穿越那個睏難重重的迷宮。要想減輕疲勞的話該怎麼辦呢?隻需稍稍偏離先前的路綫就可以瞭,在不到一步開外的地方,就有一條平坦的好路。可紅螞蟻們對這條近在咫尺的歸途卻視而不見。
有一天,我發現它們又齣去搶劫瞭,它們排著隊,沿著池塘砌磚的內側行進。池塘裏的兩棲動物前一天已被我換成瞭金魚。呼嘯的北風從側麵橫掃隊伍,把整排整排的螞蟻都颳到瞭水裏。金魚們蜂擁而至,張開大口,吞噬著落水者。雄關漫道,天塹還沒越過,隊伍就慘遭塗炭。我以為它們迴來時一定會改走另一條路,繞過這緻命的危險。可根本沒有。銜著蟻蛹的隊伍依然沿原來的險途返迴,於是金魚們吃到瞭從天上掉下的雙份餡餅:不僅是紅螞蟻,還有它們的獵物。紅螞蟻寜願再一次被屠殺,也不願換一條路綫。
如果這些亞馬遜人在遠徵途中隨意兜圈,經常走不同的路,那麼它們迴傢識途的睏難就會陡增;一定是因為這個原因,它們養成瞭原路返迴的習慣。如果不想迷路,紅螞蟻就彆無選擇:它們必須走自己認得、並且剛剛走過的那條路。爬行毛蟲從窩裏齣來,到另一棵樹或另一根樹枝上去尋找可口的樹葉時,會沿途織一條絲綫,迴傢時它就循著這條絲綫走。這是遠行時可能迷路的昆蟲所使用的最基本的方法。相對於爬行毛蟲和它們幼稚的絲路,石蜂和其他昆蟲的方法大不一樣,後者依靠某種特殊的感覺來指引方嚮。
雖然紅螞蟻和石蜂一樣,也屬於膜翅目昆蟲,但它迴傢的辦法卻沒那麼高明,這一點可以通過它隻能順著原路返迴的事實得到證明。那麼,它會不會在某種程度上效仿爬行毛蟲的辦法呢?也就是說,它不一定在途中留下指路的絲綫,因為它不具備這樣的工具;但它可以留下某種氣味,比如某種甲酸味,然後靠嗅覺來給自己指路。很多人就是這樣認為的。
那些人說:螞蟻是靠嗅覺來指路的,而嗅覺器官似乎就是那動個不停的觸須。對這個看法我不敢苟同。首先,我不相信嗅覺器官會是觸須,理由前麵已經說過瞭;其次,我希望通過實驗,證明紅螞蟻不是靠嗅覺來指引方嚮的。
花整整幾個下午等候我的亞馬遜人齣窩,而且常常無功而返,這實在太浪費時間瞭。於是我找瞭一個幫手,她可沒有我那麼忙。她就是我的孫女露絲,這個小調皮鬼對於我跟她講的有關螞蟻的故事很感興趣。她曾經目睹瞭紅螞蟻和黑螞蟻的大戰,對於搶奪繈褓中孩子的事情一直若有所思。她腦子裏充滿著崇高的職責,對自己小小年紀就能為科學這位貴婦效力感到萬分自豪;天氣好的時候,她便滿花園地跑,監視紅螞蟻,她的任務是仔細辨認紅螞蟻所走的路綫,一直跟蹤到被它們洗劫的蟻窩。她的熱情已經經受過瞭考驗,所以我很放心。那天,我正在書房寫每天例行的筆記,她突然來敲門瞭:
“砰!砰!是我,露絲。快來,紅螞蟻進黑螞蟻的窩瞭,快來!”
“你看清它們走的路瞭嗎?”
“是的,我做瞭記號。”
“什麼?做瞭記號?怎麼做的?”
“就像小拇指那樣,把白色的小石子撒在路上。”
我趕緊跑過去。情況就像我六歲的閤作者露絲剛纔所說的那樣。她事先準備瞭小石子,一看到紅螞蟻的隊伍齣動,就一直跟著,每隔一段距離,便在它們走過的路上撒下幾顆石子。現在,亞馬遜人已經搶劫完畢,開始沿著用石子標齣的路綫迴傢瞭。這段距離大約有一百米,我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我事先策劃好的實驗。
我用一把大掃帚,在馬蟻經過的路上掃齣一米左右的寬度,把路麵上的粉末物質全部掃掉,代之以彆的東西。盡管路上還留有這些粉末物質的氣味,但螞蟻不見瞭這些粉末,就會暈頭轉嚮。就這樣,我在這條路的四個不同地方用掃帚掃過,每個地方相隔幾步遠的距離。
前言/序言
1823年12月22日,讓-亨利·卡西米爾·法布爾齣生於法國普羅旺斯的聖雷恩村。此後的幾年間,法布爾是在離該村不遠的馬拉瓦爾祖父母傢中度過的,當時年幼的他已被鄉間的蝴蝶與蟈蟈兒這些可愛的昆蟲所吸引。七歲那年,法布爾迴到聖雷恩開始上學,但那一段兒時歲月一直深深地銘刻在他的心中。1833年,法布爾一傢來到瞭羅德茲,其父靠經營一傢咖啡館維持生計。四年後,一傢人又移居到圖盧茲。法布爾進瞭圖盧茲的神學院,但中途退學,齣外謀生,曾在鐵路上做過工,也在市集上賣過檸檬。後來,他通過瞭阿維尼翁師範學校的選拔考試,獲得奬學金,並在三年的學習後獲得瞭高等學校文憑。
畢業後,時年十九歲的法布爾在卡本特拉開始瞭他的教師生涯,所教授的課程就是自然科學史。
1849年,他被任命為科西嘉島阿雅剋肖的物理教師。島上旖旎的自然風光和豐富的物種,燃起瞭他研究植物和動物的熱情。阿維尼翁的植物學傢勒基安嚮他傳授瞭自己的學識。此後,他又跟隨著莫坎一唐通四處采集花草標本,這位博學多纔的良師為法布爾後來成為博物學傢、走上科學研究的道路奠定瞭堅實的基礎。
1853年,法布爾重返法國大陸,受聘於阿維尼翁的一所學校,並舉傢遷進瞭聖一多米尼剋街區的染匠街一所簡樸的住宅裏。1857年,他發錶瞭《節腹泥蜂習性觀察記》,這篇論文修正瞭當時昆蟲學祖師萊昂·杜福爾的錯誤觀點,由此贏得瞭法蘭西研究院的贊譽,被授予實驗生理學奬。這期間,法布爾還將精力投入到對天然染色劑茜草或茜素的研究中去,當時法國士兵軍褲上的紅色,便來自於茜草粉末。1860年,法布爾獲得瞭此類研究的三項專利。
後來,法布爾應公共教育部長維剋多·杜盧伊的邀請,負責一個成人夜校的組織與教學工作,但其自由的授課方式引起瞭某些人的不滿。於是,他辭去瞭工作,攜全傢在奧朗日定居下來,並一住就是十餘年。
在這十餘年裏,法布爾完成瞭後來長達十捲的《昆蟲記》中的第一捲。期間,他多次與好友一同到萬度山采集植物標本。此外,他還結識瞭英國哲學傢米爾,但米爾英年早逝,兩人醞釀的計劃“沃剋呂茲植被大觀”因此夭摺。同時,一大不幸降臨到法布爾身上:他共有六個孩子,其中惟一與父親興趣相投、熱愛觀察大自然的兒子儒勒年僅十六歲便離開瞭人世。此後,法布爾將發現的幾種植物獻給早逝的儒勒,以錶達對他的懷念。
對真菌的研究一直是法布爾的愛好之一。1878年,他曾以沃剋呂茲的真菌為主題寫下許多精彩的學術文章。他對塊菰的研究也十分詳盡,並細緻入微地描述瞭它的香味,美食傢們聲稱能從真正的塊菰中品齣他筆下所描述的所有滋味。
1879年,法布爾買下瞭塞利尼昂的荒石園,並一直居住到逝世。這是一塊荒蕪的不毛之地,但卻是昆蟲鍾愛的土地,除瞭可供傢人居住外,那兒還有他的書房、工作室和試驗場,能讓他安靜地集中精力思考,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種觀察與實驗中去;可以說這是他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天地。就是在這兒,法布爾一邊進行觀察和實驗,一邊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蟲的觀察筆記、實驗記錄和科學劄記,完成瞭《昆蟲記》的後九捲。如今,這所故居已經成為博物館,靜靜地坐落在有著濃鬱普羅旺斯風情的植物園中。
法布爾一生堅持自學,先後取得瞭業士學位、數學學士學位、自然科學學士學位和自然科學博士學位,精通拉丁語和希臘語,喜愛古羅馬作傢賀拉斯和詩人維吉爾的作品。他在繪畫、水彩方麵也幾乎是自學成纔,留下的許多精緻的菌類圖鑒曾讓諾貝爾文學奬獲得者、法國詩人弗雷德裏剋·米斯特拉爾贊不絕口。
法布爾晚年時,《昆蟲記》的成功為他贏得瞭“昆蟲界的荷馬”以及“科學界詩人”的美名,他的成就得到瞭社會的廣泛承認。法布爾雖然獲得瞭許多科學頭銜,但他仍然樸實如初,為人靦腆謙遜,過著清貧的生活。他的纔華受到當時文人學者的仰慕,其中包括英國生物學傢達爾文、1911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比利時劇作傢梅特林剋、德國作傢榮格爾、法國哲學傢柏格森、詩人馬拉美、普羅旺斯文學傢魯瑪尼耶等。由於《昆蟲記》中精確地記錄瞭法布爾進行的試驗,揭開瞭昆蟲生命與生活習慣中的許多秘密,達爾文稱法布爾為“無法效仿的觀察傢”。當他居住在塞利尼昂時,不少學者、文學傢們紛紛前去拜訪他。法布爾在自己的居所曾接待瞭巴斯德、英國哲學傢米爾等學者,但與他們的通信並不頻繁。公共教育部長維剋多·杜盧伊將法布爾舉薦給拿破侖三世,後者授予他榮譽勛位勛章。法國政治傢雷濛·普恩加萊①途經塞利尼昂,特意繞道荒石園嚮他緻意。
擁有多重身份的法布爾的作品種類繁多:作為博物學傢,他留下瞭許多動植物學術論著,其中包括《茜草:專利與論文》、《阿維尼翁的動物》、《塊菰》、《橄欖樹上的傘菌》、《葡萄根瘤蚜》等;作為教師,他曾編寫過多冊化學物理課本;作為詩人,他用法國南部的普羅旺斯語寫下瞭許多詩歌,被當地人親切地稱為“牛虻詩人”,此外,他還將某些普羅旺斯詩人的作品翻譯成法語;閑暇之餘,他還曾用自己的小口琴譜下一些小麯。
然而,法布爾作品中篇幅最長、地位最重要、最為世人所知的仍是《昆蟲記》。這部作品不但展現瞭他科學觀察研究方麵的纔能和文學纔華,還嚮讀者傳達瞭他的人文精神以及對生命的無比熱愛。
1915年,將一生奉獻給昆蟲研究的學者法布爾逝世瞭,享年九十二歲,他在鍾愛的昆蟲的陪伴下,靜靜地長眠於荒石園,然而他僅有的幾張照片,以及他所留下的樸實優美的文字,仍能讓讀者們瞥見這位學者的身影:一位和藹老者,鶴發童顔,目光敏銳而純真,一副法國南部鄉間的樸素打扮,頭戴寬邊遮陽帽,脖係方巾,手裏握著他的寶貝捕蟲網;不用開口,他嘴邊常掛著的舒心微笑,就仿佛已經在邀請您進入他的昆蟲世界。
《昆蟲記》原著書名可直譯為《昆蟲學的迴憶》,副標題為“對昆蟲本能及其習俗的研究”。共十捲,每捲由若乾章節組成,絕大部分完成於荒石園。1878年第一捲發行,此後大約每三年發行一捲。
原著內容如其名,首先最直觀的就是對昆蟲的研究記錄。作者數十年間,不局限於傳統的解剖和分類方法,直接在野地裏實地對法國南部普羅旺斯種類繁多的昆蟲進行觀察,或者將昆蟲帶迴自己傢中培養,生動詳盡地記錄下這些小生命的體貌特徵、食性、喜好、生存技巧、蛻變、繁衍和死亡,然後將觀察記錄結閤思考所得,寫成詳細確切的筆記。
但《昆蟲記》不同於一般科學小品或百科全書,它散發著濃鬱的文學氣息。
首先,它並不以全麵係統地提供有關昆蟲的知識為惟一目的。除瞭介紹自然科學知識以外,作者利用自身的學識,通過生動的描寫以及擬人的修辭手法,將昆蟲的生活與人類社會巧妙地聯係起來,把人類社會的道德和認識體係搬到瞭筆下的昆蟲世界裏。他透過被賦予瞭人性的昆蟲反觀社會,傳達觀察中的個人體驗與思考得齣的對人類社會的見解,無形中指引著讀者在昆蟲的“倫理”和“社會生活”中重新認識人類思想、道德與認知的準則。這是一般學術文章中所沒有的,但卻是文學創作中常見的。不同於許多文學作品的是,《昆蟲記》不是作傢筆下創造齣來的世界,所敘述的事件都來自於他對昆蟲生活的直接觀察,有時甚至是某種昆蟲習性的細枝末節。
其次,雖然全文用大量筆墨著重介紹瞭昆蟲的生活習性,但並不像學術論著一般枯燥乏味,本書行文優美,堪稱一部齣色的文學作品。作者的語言樸實清新,生動活潑,語調輕鬆詼諧,充滿瞭盎然的情趣和詩意。作者對自然界動植物聲、色、形、氣息多方麵恰到好處的描繪,令讀者融入瞭19世紀法國南部普羅旺斯迷人的田園風光中。作者在描寫中使用大量栩栩如生的比喻,此外,他憑藉自己拉丁文和希臘文的基礎,在文中引用希臘神話、曆史事件以及《聖經》中的典故,字裏行間還時而穿插著普羅旺斯語或拉丁文的詩歌。法布爾之所以被譽為“昆蟲界的荷馬”,並曾獲得諾貝爾奬文學奬的提名,除瞭《昆蟲記》那浩大的篇幅和包羅萬象的內容之外,優美且富有詩意的語言想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昆蟲記》融閤瞭科學與文學,這也意味著它既有科學的理性,又有文學的感性。書中不時語露機鋒,提齣對生命價值的深度思考,試圖在科學中融入更深層的含義。
作品中的理性成分體現作者的研究與思考中。法布爾在對昆蟲的觀察研究中,反復試驗,並考證多方資料,對主流學術觀點敢於質疑,探求真相,追求真理,竭盡自己之所能對知識結構不斷探索和補充,對自己的觀察結果不輕易下定論,同時錶明自己的懷疑願您在輕翻本書書頁時,能再度喚起孩童時代撥開草葉、尋見昆蟲的愉悅心情。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書脊上閃爍著“譯林名著精選”幾個字,瞬間勾起瞭我對經典文學的嚮往。我一直認為,名著之所以能流傳百世,必然有著超越時代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魅力,而“精選”二字則預示著我即將接觸到的,將是經過時間淘洗、匯聚精華的瑰寶。當我翻開這本書,撲麵而來的紙張的溫潤觸感和油墨的淡淡清香,都讓我感受到一種儀式感,仿佛即將開啓一段神聖的閱讀之旅。這本書的外觀設計也相當雅緻,封麵上的插畫風格獨特,色彩柔和,卻又蘊含著某種神秘的氣息,讓人不禁想要一探究竟。我期待著,在這本“譯林名著精選”中,能夠邂逅那些曾經令無數讀者為之動容、為之沉思的偉大故事,體驗文字的力量,感受語言的韻律,並在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思考和啓迪。
评分我一直堅信,經典之所以能夠經久不衰,是因為它們所探討的主題是永恒的,是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這本“譯林名著精選”,單憑其名號就足以吸引我。我尤其對那些能夠引起共鳴、能夠觸動我內心深處的作品充滿瞭好奇。從這本書的裝幀來看,它似乎是經過精心打磨的,無論是紙張的質感,還是排版的疏朗,都傳遞齣一種對閱讀本身的尊重。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帶我進入一個全新的思想世界,讓我接觸到那些曾經影響過無數人的觀念和思想。我希望能夠從中汲取力量,獲得啓發,並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地拓展自己的視野,深化自己的思考,讓自己的內心世界變得更加豐盈和成熟。
评分我一直對那些能夠深入剖析人性的作品情有獨鍾,它們如同鏡子般,映照齣我們內心深處的復雜情感和種種矛盾。這本書的裝幀設計,尤其是封麵那幅充滿故事感的插畫,就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它沒有選擇過於鮮艷奪目的色彩,而是以一種沉靜而富有張力的構圖,暗示著其中蘊含著某種深刻的意義,一種需要細細品味纔能體會到的韻味。我好奇作者是如何將人性的種種側麵,那些光明與黑暗,那些美好與醜陋,巧妙地編織進故事情節中的。我期待著在閱讀過程中,能夠感受到角色們內心世界的起伏跌宕,理解他們行為背後的動機,並從中反思自身,獲得對人性和社會的更深刻認識。一本好的名著,不應僅僅是消遣,更應該是一次與自我心靈的對話,一次對人生真諦的探索。
评分我一直對那些能夠展現齣作者獨特視角和深刻洞察力的作品充滿好奇。這本書的“昆蟲記(插圖本)”這樣的組閤,本身就讓我感到一種特彆的吸引力。“昆蟲記”似乎暗示著一種對微觀世界的關注,而“插圖本”則意味著視覺上的享受和補充。我好奇作者是以怎樣的視角來觀察和描繪昆蟲的?他是否能夠發現那些我們平日裏容易忽略的細節,並從中提煉齣深刻的道理?我期待著,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昆蟲的知識科普,更能夠通過對昆蟲世界的描繪,摺射齣更廣闊的社會現象和人生哲理。我希望能夠從這本書中,獲得一種全新的觀察世界的角度,一種對生命本身的敬畏,以及一種對自然規律的理解。
评分初次看到這本書,它的名字就牢牢抓住瞭我的眼球。“昆蟲記”這個詞語,本身就帶著一種自然界獨有的神秘與秩序感。我一直認為,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師,其中蘊含著無數的智慧和啓示。而這本“插圖本”,更是讓我充滿瞭期待。我設想著,那些精美的插圖,是否能夠生動地展現齣昆蟲世界的奇妙景象,是否能夠將文字的描述轉化為可視化的畫麵,讓我仿佛置身於那微小的生命之中,親眼見證它們的生存之道。我想象著,作者是如何用細膩的筆觸,描繪齣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靈,它們復雜的社會結構,它們驚人的生存技巧,它們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方式。我期待著,在這本書中,能夠打破我對昆蟲的刻闆印象,發現一個全新的、充滿魅力的昆蟲世界。
评分再便宜点就好了,稍微贵了一点点,书不错
评分good service 回头查了一下,我是从2010年3月开始网络购书的,算起来快5年了。师傅是我的女友“好梦”,她是个样样时尚都能搞懂的70后女子,若干年前我看她拿了一摞书在付款,才知道还有这等方便之事:网上选书,书到付款。于是赶紧回家登录京东书城,挑选,下单。果然,很快书就送到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不知在京东下了多少订单,四五十次应该有了吧,因为我早已是VIP钻石用户啦。好了,废话不多说。
评分的质量很好,孩子特别喜欢,值得信赖,可以入手!
评分质量还行,
评分挺好的呀,呵呵。挺实用的。挺不错。
评分以前买过其他版本,还是这个好!
评分终于买回来了。一直想看的一本书!
评分给儿子买的,看了,不错
评分没什么不好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