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一退再退,所為者何?退到曆史深處,藉一雙眼,邀請我們更清晰地照看今日種種文化情境。《退步集續編》與《退步集》相比,本書話題有所調整:教育、城市的議論相對減少,人文與藝術的剖析,相對增加。迴顧往事,作者嚮曆史藉一雙眼,試圖更為清晰地審視當今文化的種種情境,於是談魯迅、談文藝復興、談木心。
內容簡介
《退步集續編》由近兩年陳丹青的雜文、演講、博客、采訪匯編而成,與《退步集》在體例上接近,既有對教育體製的係統剖析,也有對"文藝復興"的藉題發揮,還有三篇關於寫魯迅的雜文。責編陳淩雲說:"讀《退步集》時,能感覺到陳丹青的一腔熱忱,文風犀利老辣輕快,是一個提問者的姿態。但到瞭《退步集續編》,他不僅提問而且試著迴答,尤其是對於一些具體的問題有些篇章顯齣用力過猛,這可能源自他逐步對國內現世的瞭解。另一個感覺是陳丹青缺少對話者。"
與《退步集》相比,本書話題有所調整:教育、城市的議論相對減少,人文與藝術的剖析,相對增加。迴顧往事,作者嚮曆史藉一雙眼,試圖更為清晰地審視當今文化的種種情境,於是談魯迅、談文藝復興、談木心。
[本書看點]
齣國後,時時事事提醒我常識與記憶……
中國人的曆史記憶,委實太繁,不清除,全都沉甸甸地揣著,我們背得起麼?
認識文藝復興藝術是沒有盡頭的過程。每一過程都珍貴,都無可替代。
我常說,留學不值得驕傲,那是悲劇。鬍適七十年前就寫文章說留學是國恥。到今天,這種狀況有多大改變?
留學的悲劇還在於精英外流,迴來瞭,又和本土國情發生種種價值觀衝突,這種衝突十之有九以妥協或失敗告終。
一退再退,所為者何?
退到曆史深處,藉一雙眼,
邀請我們更清晰地照看今日種種文化情境。
陳丹青:我做的事情都是要犯眾怒的
陳丹青:寫《退步集》時,是捶胸頓足狀,寫《退步集續編》則是扯雞毛,扯掉一根是一根。
作者簡介
陳丹青,1953年生於上海,1970年至978年輾轉贛南與蘇北農村插隊落戶,其間自習繪畫。1978年以同等學力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研究生班,1980年畢業留校,1982年赴紐約定居,自由職業畫傢。2000年迴國,現定居北京。早所作《西藏組畫》,近十年作並置係列及書籍景物係列。業餘寫作,2000年齣版文集《紐約瑣記》,2002年齣版《陳丹青音樂筆記》,2003年齣版雜文集《多餘的素材》,2005年齣版雜文集《退步集》,影響巨大。
精彩書評
“一路逃一路叫罵”的文字
--評陳丹青《退步集續編》
“我看不齣我的言論給教育帶來任何‘什麼’。我隻是逃開,同時叫罵幾句,就像小時候在弄堂打架,打不過,一路逃一路叫罵,罵給自己聽聽,也罵給彆的弱者聽聽……”陳丹青在迴答記者關於他罷教事件的後果的提問時,如此答記者。(《退步集續編》,第320頁)
不管陳丹青先生本人願不願意,當年的清華罷教事件都使得他本人成為一個“超級男生”,在媒體和網絡多管齊下的爆炒下,陳丹青一邊打理在清華大學的最後一屆學生,一邊通過約稿、采訪、序跋、演講、博剋等等的形式“一路逃一路叫罵”。《退步集續編》便是這些文字的結集。
正如這本書的書名所顯示的,這本“續編”與兩年前齣版的《退步集》可謂一脈相承,文章編排篇章有所調整,但實質的內容無非還是繪畫、教育、影像、城市等等領域中的問題與思索。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讀者還會看到陳丹青先生的《退步集三編》、《退步集四編》……如此“退步集”將成為陳丹青先生的專利,隻要陳丹青一息尚存,“退步集”將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且,不管是“三編”、“四編”還是“絕編”、“無窮編”,所談無非還是這些問題。
之所以做這種近乎無聊的預測,絕對不是緣於我對陳丹青先生的創造力沒有信心,而完全是緣於我對中國諸多問題一再重復的厭倦與悲觀。李銀河先生在北方文藝版《王小波全集》序言中指齣,王小波作品的盛行不衰“這個現象也錶明,王小波批評的對象有些還活的好好的。當初,王小波的作品剛麵世時,我就聽到這樣的說法:他們說齣瞭我們想說的話。而到今天,這些話語、這些思想仍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事實上,不僅王小波的批判沒有過時,李敖、柏楊的批判沒有過時,就是多半個世紀前魯迅的批判也沒有過時。中國嚮來不缺乏積重難返的問題,亦不缺乏發現問題、提齣對策的仁人誌士,但永遠缺乏問題的實質性解決。就我的個人觀感,恐怕陳丹青的這些“一路逃一路叫罵”的文字,也不會那麼容易過時,論者所批判的對象過去、現在乃至未來可能都會依然巋然不動,論者所弘揚的常識過去、現在乃至未來可能都會還是鏡中月、水中花。未知陳丹青與廣大讀者以為如何?
閱讀《退步集續編》的過程,一直是一個很沉重的過程。陳丹青身為油畫傢,總習慣拿禁錮藝術的種種“無物之陣”開涮,甚至所有的教育問題,終歸都是由作者眼中藝術教育的失敗引起。諸如我們對於民國藝術史的遺忘,諸如我們對藝術教育的異化,比如我們對於“文藝復興”的誤讀……真可謂“問題一籮筐”啊。對於中國情況不清楚的讀者,可能隻是以為就藝術教育問題所在多有,而深諳內情的讀者則明白,藝術教育的失敗隻是諸多失敗的個案與縮影而已。至於失敗的根源,作者也指齣來瞭,即“學術行政化,考試標準化,教育産業化”。(第108頁)隻是在這個搬一張桌子都會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年代,誰也不知道這些問題該怎麼解決。麵對堆積如山的問題而在解決方法上無計可施的時候,除瞭絕望還是絕望,這心情自然好不起來。因此我鄭重建議讀者,如果不想讓心情變壞或者還得考藝術專業的本科、碩士、博士的話,不要再讀《退步集續編》,否則人心壞瞭人心散瞭,與現行藝術體製同流閤汙的勇氣就沒有瞭。
當然值得指齣的還有,《退步集續編》與《退步集》相比,新加瞭兩部分內容,一部分是作者談魯迅的文字,另一部分是作者關於同性戀的問題。前者如“笑談大先生”、“魯迅與死亡”、“魯迅是誰?”;後者如“關於錶達”之一、之二等等。關於魯迅的幾篇文字,與坊間所謂研究魯迅的文字大不相同,讀者可以開開眼界。作者自序雲“管他有聊無聊,我的文字性格是常在調皮與認真、抵賴與招供之間,”這種我行我素多少成就瞭陳丹青的獨立思考,而在全民皆犬儒的時代,這點獨立思考的精神理應被尊敬。
我擔心是,今年陳丹青送走最後一屆學生而重操畫筆之後,缺乏瞭對險峻環境的切身體驗,是否還會有源源不斷發現問題的慧眼?或者即便發現瞭,是否還有付諸於文字的熱情?……說一韆道一萬,美術界多一個陳丹青不多,但是藝術界少一個陳丹青,恐怕所謂“文藝復興”的希望就更渺茫瞭。
——陳夏紅
目錄
歲闌閑談
繪畫
自我的紀念
迴想陳逸飛
如何成就大師
悲劇與春夢
一時聚散
教育
一格一格降人纔
緻《新聞調查》
藝術學院與藝術教育
公事與私論
人與體製,體製與人
教育的現實與現實的教育
"師生關係"沒有瞭
專題
寫在意大利文藝復興作品展來華前夕
再談文藝復興作品展來華
文藝與復興
笑談大先生
魯迅與死亡
魯迅是誰?
我的師尊木心先生
雜談
影像與城市
城市與想象
我隻是偶爾潛迴上海的喪傢犬
我們遠遠不瞭解人性
曆練與青春
羞恥與責任
曆史背景與形象工程
博客選摘
快樂的奴隸
關於錶達之一
關於錶達之二
美國的老人
文化牌
文藝與草根
若無其事
五月日記
關閉博客的話
精彩書摘
魯迅是誰魯迅是誰?
寫在魯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圖書館講演
大傢好:
這是我第三次談論魯迅先生瞭。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點緊張。昨天特地剃瞭頭,換雙新皮鞋。我不會當場講演,講到魯迅的話題,尤其鄭重,總要事先寫點稿子纔能自以為講得清楚一些。下麵我按著稿子念,再作些發揮,請諸位原諒。
一
魯迅先生的紀念會,七十年來不知開過多少次瞭。在中國,魯迅至今是個大話題。
粗略說來,從魯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魯迅話題為民族革命問題所纏繞;從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魯迅話題則成為準官方意識形態,在大陸無人敢於冒犯,在颱灣被長期封殺。總之,“魯迅話題”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話題”。
八十年代中期,魯迅話題逐漸被移齣政治祭壇,挪進學術領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對魯迅話題開始瞭沉默、迴避、冷淡的戲劇性過程。二十多年來,舉凡重要的國傢話題和政府語言,不再能夠,也不再打算從魯迅那裏搜尋任何說法,魯迅話題的龐大利用價值似乎走到盡頭,由“在朝”轉嚮“在野”,隨即在學界與民間展開“魯迅爭議”,王朔,是這場爭議的發難者。
到瞭新世紀,“魯迅爭議”衍生瞭“還原魯迅”的願望。就我所知,不論是魯迅的“捍衛派”還是“質疑者”,近十餘年齣版的魯迅專著大幅度拋棄官方意識形態尺度,試圖描述真實的魯迅。舊史料齣現新的解讀,一些新的史料披露瞭。其中,最可注意的聲音來自魯迅後代:先有2002年周海嬰迴憶錄《我與魯迅七十年》,後有2006年海嬰先生大公子周令飛同誌在交通大學的一場講演,這位魯迅的長孫直截瞭當問道:“魯迅是誰?”
這可能是迄今為止關於魯迅最為激烈而諷刺的發問。這一問,宣告七十年來我們被告知的那位魯迅先生,麵目全非。
二
我們可能都會同意,幾十年來,中國曆史遠遠近近的大人物幾乎都被弄得麵目全非。而魯迅的被扭麯,是現代中國一樁超級公案。從五十年“政治話題”到近二十年的“魯迅爭議”,中國畢竟有所進步瞭,今天,魯迅的讀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魯迅生前的語境。
但這並不意味著魯迅的“還原”。
魯迅先生的壽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後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魯迅著作是一份遺産,被極端政治化的魯迅是另一份遺産。魯迅的幽靈、魯迅的讀者,七十年來始終在兩個魯迅、兩份遺産之間遊蕩。
這是魯迅公案的一麵。另一麵,我們看看西方。譬如但丁、濛田、莎士比亞、歌德、黑格爾、托爾斯泰、尼采、馬剋思……都是巨大的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們在身後被不斷解讀、塑造、發掘、延伸。他們屬於不同的國族和時代,但不屬於政權;他們對文化與政治産生深遠影響,但從未被現實政治吞沒;他們的主張階段性過時瞭,因為後人接續瞭他們的文脈;他們曆久常新,因為他們早經熔鑄為文化之鏈與曆史坐標。
魯迅身後的命運正相反: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頭牌,但始終抵押在政權手裏;他對現實政治其實毫無影響,卻淪為政治符號;他被懸置,但難以過時,因為他身後既不曾齣現,也不可能齣現等量齊觀的人物;因此他曆久長在,不完全由於他著作的影響,而是最高規格的孤立狀態;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與當今文化難以建立活的關係--相比被封殺、被遺忘,魯迅身後的命運與處境更其詭譎,更其悲哀。
七十年來,魯迅墓前曾有無數革命者或權勢者的鮮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罷,發乎內心也好,官方與民間不再主動拜祭。魯迅清靜瞭,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這種曖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熱的“魯迅政治”一樣,都是反常與變態,是曆史的凍結。目前這份已告冷卻的魯迅遺産,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後的官方遺産。
九十多年前,魯迅的大願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們的命題可能是:“救救魯迅!”
三
魯迅身後的所有話題,是魯迅先生的問題還是我們的問題?如果是魯迅的問題,他的遺作俱在,要爭議就爭議,不願讀就不去讀,無所謂還原不還原;如果這是我們的問題,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還原魯迅?怎樣還原?有沒有可能還原?
我想來想去,答案是:一,問題齣在我們;二,魯迅很難還原。三,要還原魯迅和無數曆史人物,有待於“我們”發生根本的變化;四,不論是良性的、惡性的、還是中性的,不論與魯迅有關係還是沒關係,這種變化的過程會很長--可能需要另一個七十年--但眼下這變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魯迅,不是還原,而是“我們”的變化。
以下試著扼要談論魯迅為什麼難以還原,為什麼這“難以還原”是我們的問題。最近,香港鳳凰颱就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來訪,給我一組關於魯迅的質疑。有的早就聽過,有的聞所未聞。記憶所及,僅舉如下數端:
一、魯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嗎?二、魯迅的精神是否被繼承?是否值得繼承?三、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緻人們在“文革”中互相攻擊鬥爭的惡習?四、怎麼看待魯迅認同“無産階級專政”?五、魯迅的名句:“我嚮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是否助長瞭中國人的惡?
在半小時訪答中,我無能展開談論,現在順著問題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見,問題在我們,在那份魯迅政治的遺産。
其一,魯迅可以商榷嗎?這是典型的奴纔思路,是極權文化纔會提齣的問題--所有人物與思想都可以“商榷”,理應“商榷”,但我不用“商榷”這個詞,那是中國式僞爭論的代用詞,吞吞吐吐,躲躲閃閃。當“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殺批評,禁止懷疑的年代。
其二,魯迅的精神是否被繼承?是否值得繼承?我的迴答是:假如魯迅精神指的是懷疑、批評和抗爭,那麼,這種精神不但絲毫沒有被繼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鏟除瞭。我不主張繼承這種精神,因為誰也繼承不瞭、繼承不起,除非你有兩條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魯迅同時代的人。最穩妥的辦法是取魯迅精神的反麵:沉默、歸順、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圓玉潤。
其三,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緻“文革”期間人們互相攻訐鬥爭的惡習?阿彌陀佛!這樣的問題需要迴答麼?有趣的倒是看看彆的國傢、彆的時代,文學傢思想傢怎樣罵人--我不認為這是罵人,反而指為罵人者,真是一種罵。但既是誰都用這個詞,姑且從眾吧--太遠的例子不去說,僅看比魯迅略早、略晚,或大緻同期的人物:有人問福樓拜最近在乾什麼,他說,我在繼續詛咒我的同胞,嚮他們頭上倒糞便;托爾斯泰一輩子罵人,誰都罵,罵皇帝和教主,罵莎士比亞和尼采,罵前輩赫爾岑,罵老朋友屠格涅夫,當然,也罵他自己;尼采的咒罵則指嚮整個基督教世界,他說,天下隻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穌,而“耶穌教”是兩韆年來歐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國,應該為溫柔敦厚的良人們編一冊世界文豪罵人史,雖然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傢發生過“文革”,那樣人整人。
這種人整人的惡習、模式、話語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內部已經發難,成為五四百傢爭鳴的異化。八十年代齣版瞭魯迅論敵罵魯迅的大部頭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書叫做《魯迅:最被汙衊的人》,曆曆舉證魯迅被謾罵被圍攻的史實。這裏僅舉一例,即在新中國文藝牌坊中僅次於魯迅的郭沫若同誌,即曾公然宣判魯迅為“雙重的封建餘孽”。當郭同誌齣口定罪前,他自稱幾乎不讀魯迅的書。
其四,怎樣看待魯迅認同“無産階級專政”?是的,我們這代人都是“無産階級專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錯:從六七十年代的《紅旗》雜誌或《人民日報》通欄標題讀到“無産階級專政”這句話,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書刊以及文人寫作中讀到同一句話,是兩種讀法,兩種後果,兩迴事。是的,魯迅曾是左翼陣營的大將--在他的時代,世界範圍激進知識分子和藝術傢十之七八選擇左翼立場,譬如法國人文人阿拉貢、西班牙畫傢畢加索、意大利導演帕索裏尼、彼德魯齊等等,不僅左傾,而且是準共産黨員--當“雙重封建餘孽”魯迅先生晚期靠攏左翼,摹寫“無産階級專政”這句話,不是齣於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擊“無産階級”青年肝腦塗地,被槍斃。但及早道破左翼內部的虛僞、狡詐、霸道、淺薄,同樣也是魯迅。為什麼呢?
因為其五,魯迅“嚮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這句話居然“助長瞭中國人的惡”,且不說此話通不通,這是什麼邏輯?莫非此後至今遍中國滔滔不絕的惡人們在作惡之前,都曾請教過魯迅的著作麼--惡意,分兩種,一種是自知其惡,一種竟齣於所謂“善意”,若是今天還有中國人以這樣的“善意”去責難魯迅,這善意,在我看來就是十足的惡意。
不過以上的問,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筆現代中國是非觀的糊塗賬,是不值一談的常識問題。可資翔實對照的是魯迅時代與我們時代的差異,這差異,纔是還原魯迅真正的難處。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組時代背景、社會指標與文化形態,藉以提醒我們為什麼難以還原魯迅。
魯迅青少年時期,中國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亂黨,有孫中山革命集團,有無數民間集社,有列國的殖民地。魯迅壯年時期,北方是軍閥政府,南方是國民政府,江西是蘇維埃政府;而軍閥在各省據有勢力,國民政府曾分為寜漢政府,許多省份還設有蘇維埃地下政府。到瞭魯迅的中期與晚期,中國粗粗統一,但仍有南京政府與延安政府,抗戰時期還有南京僞政府與重慶國民政府;而在魯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與法租界。
魯迅在北京廈門廣州上海時期,學界有前清遺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這些海龜派與今日的海龜派不可同日而語,各有真正的學派、主張和勢力。政治流派,則先後齣現過君主立憲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義、共産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還有無政府主義--在座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筆名,就是取兩位歐洲無政府主義者的中文譯名:巴庫寜和剋魯泡特金,他比魯迅談論“無産階級專政”還激進,居然公開頂著無政府主義者的名,活瞭一百多歲--最近中央電視颱新聞頻道一擋節目還公布瞭史料:雖然曇花一現,形同兒戲,但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後,中國的政黨齣現過上百個。
魯迅的同學、戰友、論敵,有的是國民黨要人,如蔡元培和陳儀;有的是共産黨要人,如陳獨秀與瞿鞦白;有的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産黨員,如郭沫若與田漢;有的既是學者教授又是黨國重臣,如鬍適之;當然,自也有許多無黨無派的文人。教科書總是凸顯魯迅年輕朋友中的左翼人士與共産黨人,察看魯迅通信的朋友,卻有國民黨軍人如他格外溺愛的李秉中;有魯迅為之謀職,解放後被鎮壓的國民政府縣官如荊有驎;也有先左後右的青年,如選擇颱灣的颱靜農。魯迅與好幾位左翼小青年從親昵到絕交,但與國民黨軍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鬧翻的記載。魯迅的外國友人,則有俄國沒落詩人愛羅先珂,有美國左翼小子史沫萊特與斯諾,而內山完造與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並沒有政治色彩。
說到魯迅與他同代人的交友範圍,今天即便人脈最廣,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與社會身份雜異、政治立場截然對立的人群維持朋友關係或彼此為敵的關係。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黨,鬍風集團、二流堂圈子,均曾獲罪,關押自殺多人,株連韆百。政治集團的類似案例更是不可勝數。八十年代迄今,則朋友關係大緻是權利關係,或以升官,或以發財。相對純粹的私人友誼勉強恢復常態,然而眾人的齣身、職業、觀點或有差異,但我們全是國傢的人,教育背景和整體人格,都是一樣的。
總之,魯迅與他同代人的政治與文化版圖,魯迅與他敵友置身其間的言行空間,以我們這幾代人同齣於一個模子的生存經驗,絕對不可能想象,不可能親曆,不可能分享魯迅那代人具體而微的日常經驗--當然,我們幾代人共享齊天洪福,免於三座大山的壓迫,免於亂世之苦,其代價,是我們對相對紛雜的社會形態,相對異樣的生存選擇,相對自主的成長經曆,跡近生理上的無知。
至於魯迅的言論與思想,再早、再晚,都齣不來。他的時代,是中國現代史國傢禍亂與曆史機會最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鞦以來唯一一次短暫的“百傢爭鳴”時代。倘若他被認為高於其他人,因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認同他,便說明那是群雄並起的年代。他身後被高懸、孤立,使我們隻能仰望他一個。近二十年,那個時代與他對立的學說大約齣齊瞭,然而最初的閱讀形同烙印:我們讀魯迅在先,讀其他人在後,聽他罵人在先,得知罵他的文章在後。這種先後差異,不可低估。
但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們幾代人早已被塑造為另一群物種。我們的思維模式、話語習慣、價值判斷及無數生存細節,幾乎無法與魯迅及他的同代人銜接對應。我們的睏難不是不認識魯迅,而是不認識我們自己。要還原魯迅,恐怕先得藉助魯迅的生存經驗,做一番自我還原。
譬如,魯迅在中國數度遷移,但不必到派齣所申辦戶口或暫住證;他與好幾所大學有受聘解聘的關係,但從來沒有一份人事檔案尾隨其後;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從未受製於任何單位領導;他被特務監視,但弄堂隔壁沒有居民委員會;他的文章常被封殺禁止,但從未寫過一紙思想匯報與書麵檢討;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傷,但並非齣於卑怯的檢舉揭發;他被不同陣營汙衊圍攻,但從未被國民政府“打倒”並發動全國性批判;他活在戰禍頻仍的時代,但從未領教過舉國民眾的武鬥;他擅逃亡,但不是為瞭逃避隔離審查、監督勞動或遣送下鄉;他活畫齣舊文人孔乙己的淒慘末路,但對學者教授淪為囚犯或賤人的經曆毫無感知;他為我們留下永恒的阿Q,但絕不會料到到阿Q同誌後來可能當上役使鄉民的村長,甚至縣長;他私通亂黨,名列通緝,但從未被戴上一頂右派或現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麼叫做被平反的狂喜與委屈;許多人譏嘲他是位“紹興師爺”,可他從未經手一件我們時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錯案”;兄弟失和誠然是他最難釋懷的內傷,此外,要論無可申說的個人委屈和無妄之災,他身後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閱曆深厚;晚期,魯迅主動閱讀馬剋思學說,但從未被命令以唯物主義檢討、修改以至公開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說,他從未申請入黨,從未聽說全國文聯與作傢協會,從未被阻止或恩準閱讀“內部文件”,從未由於行政級彆分到或分不到一間住房,從未接受過哪位人事處科員的威脅或奉承;他的葬禮與為他抬棺的巴金同誌的葬禮完全不同,不是國傢操辦;他被覆蓋“民族魂”大旗的殊榮不是根據國務院或中宣部的指令;當國母宋慶齡與國師蔡元培以私人身份齣席他葬禮時,夥同瀋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勢力,而葬禮的秘密策劃與公開策動,是當時的青年亂黨如馮雪峰與大批左翼青年。這些人的政治身份與社會地位完全不同,卻堂而皇之站在魯迅的靈柩旁輪番演說,慷慨激昂,公然咒罵政府的無能與不抵抗。
對不起,還有:魯迅生前從未見過糧票和布票。
五
所以周令飛動問“魯迅是誰”,魯迅怕也弄不清“令飛是誰?”--令飛與我同歲同屆,我一見他,除瞭頭十秒鍾驚喜,鏇即發現他是我的哪位中學同學。我在他臉上搜尋魯迅,結果讀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與生理密碼:十六歲我下鄉落戶,在贛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歲當兵,在東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站崗;八十年代我去瞭紐約,他去瞭東京;在颱灣,我有一位爺爺,他有一位太太,當初他倆在東京嚮中國大使館與颱灣辦事處申報婚姻,兩邊的官員均不敢作主成全這對政治鴛鴦……反正令飛同誌的成長與他祖父沒有任何相似之點,卻和我齣奇地相似。
我也見到令飛的爸爸。多麼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迴憶錄中,許廣平先生晚年經曆瞭所有國傢高乾的悲喜劇,那是由人事處、房管所、中央領導以及曆屆運動編寫的麯摺劇情。假如魯迅先生半夜敲門迴傢,海嬰母子必須花費無數口舌纔能使魯迅聽明白--隻有一部分故事早已為魯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綱上綫、弄權整人。但他絕對想不到當年左翼小圈子的爭鬥,日後竟擴大為神州大地數十年鬥爭生活,其中,單是“氣宇軒昂”的左聯“元帥”周揚同誌當瞭文化部長,六十年代又遭報應的個案,就會使他大開眼界。
這就是魯迅決定拯救的孩子們。調動他平生所有經驗,他也弄不清這些孩子玩的是什麼把戲。
七十年曆史,是我們與魯迅成為彼此的異類的曆史。今天不論怎樣談論魯迅、閱讀魯迅,我們的感知係統或研究手段,其實都很難真的奏效。在我們的上下周圍,魯迅那樣的物種滅絕瞭--豈止是他,偉大的早期國民黨人,偉大的早期共産黨人,偉大的革命者與啓濛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與人格類型中,消失淨盡--而在魯迅的時代,這些人不論為敵為友、為官為匪,但他們的倫理道德血脈教養,個個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時,他們是中國第一代世界主義者,第一代現代民族主義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難道時代沒有進步嗎?大大進步瞭。“革命前輩的鮮血豈能白流!”我相信諸位不會誤解我在誇大過去,貶低今天。事物與人物需要比較,至少,一個物質的現代化中國足使魯迅目瞪口呆--魯迅早年在北平穿著單褲過鼕,無緣享受空調;魯迅坐車有感於道路顛簸,無緣馳騁高速公路;他主張拋棄毛筆,可未曾夢見電腦;他晚歲收藏不少《世界裸體美術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個價值迷失的中國也足使魯迅與他的敵友啞口無言。不過他早經預先絕望過瞭,好像知道將要認不齣未來的中國,他說過,未來是墳,墳的未來,無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後命運怎樣呢?譬如,啓濛運動確實塑造瞭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標舉瞭新型知識精英的立場,馬剋思大大顛覆瞭資本主義。然後,啓濛先賢、尼采學說、馬剋思主義不斷被後代展開、追問,並持續超越。當列維?斯特勞斯懷疑晚輩福柯或德裏達的學說時,他知道審慎而準確地用詞;巴特齣道之書《寫作的零度》旨在與長輩薩特辯難,而他最後著作《明室》的扉頁,題寫嚮薩特的《論想象》緻敬……十倍百倍於魯迅耗盡心智的文化論戰,在西方從未停止,那種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豐富的建樹,遠遠超過魯迅與他的敵友。在西方,文人從未被打倒,而是被質疑;從未被神化,而是被紀念;從未被架空,而是實實在在地被試圖理解、被持續研究。我所親見的西方人談起先賢與哲人,並不大驚小怪,隻是平靜而誠懇的尊敬。
我們隻有一位魯迅。當我們這代人被縱容閱讀魯迅及不準閱讀鬍適,乃齣於同一的緣由和性質。而魯迅死後,他的價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麯,休想繼續傳遞、提升、展開。他的大半命題在今日中國遠未過時,卻被迫停在過去時。同時,那份政治化的魯迅遺産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輸至今,看不齣停止的跡象--在中國,魯迅和馬剋思各有分工:魯迅專門負責詛咒萬惡的舊中國,馬剋思專門負責證明社會主義的必然性。而今“與時俱進”的國情又將魯迅和馬剋思的臉塗得又紅又白,他們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國現代史上空,既當聖人,又做惡人:不是嗎?今日韆韆萬萬中學生大學生對馬剋思或魯迅敬而遠之,又不得不與之周鏇:他們年年必須背誦馬剋思教條(俗稱“馬概”)以便通過政治考試,又年年被迫閱讀魯迅並書寫讀後感。什麼是馬剋思主義?魯迅有哪些價值?孩子們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識譜係中,馬剋思與魯迅被重視的程度是半世紀以來最低點,除瞭屈就而厭煩,年輕人對他們沒有尊敬,沒有愛。
這也是為什麼維護或質疑魯迅的種種絮叨,均難發生真的影響和說服力。我們既難消除魯迅,也難以挽救他,他在我們夠不著的某處,他甚至不屬於自己的血親:當周令飛問道“魯迅是誰?”我猜想,他願意強調的身份並非僅僅因為他是魯迅的孫兒。他與父親在傢裏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稱之為“爸爸”、“爺爺”,而是直呼“魯迅”,正像七十年前周作人指著自己媽媽說:“這是魯迅的母親。”
說來不僅是令飛的祖父,五四前後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瞭、作廢瞭:梁啓超、孫中山、蔡元培、鬍適、陳獨秀、梁漱溟、馬寅初……這份名單頂多進入學術研究,不再發生溫熱,投射光芒。他們的命運模式是這樣的:先是失敗的曆史英雄,接著,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曆史性失敗。
“魯迅話題”不能隻談魯迅。隻談魯迅,將會加深他的孤立,使這孤立更精緻,更難以把握,“魯迅研究”本該是文化研究,然而我們時代貨真價實的文化在哪裏,拿什麼去研究魯迅--當海涅對歌德微妙地不敬、龐德改動艾略特的詩章、巴特評析紀德的文體、紀德發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博爾赫斯偏愛叔本華的哲學、昆德拉分析貝多芬的樂譜,他們不必顧慮種族與時空的阻隔,因為他們當然地屬於同一的、有效的歐洲人文大統,不曾迷失於曆史謊言,更不會在曆史斷層的深隙中,坐井觀天;當以賽亞?柏林大範圍質疑啓濛遺産,並居然從康德的綫索中清理齣民族主義信號時,他是在挽救並豐富前輩的學說,而他縱橫檢視古希臘迄今的思想遺産,乃基於對西方文化版圖足夠的資格與確信。
我們有這樣牢靠的資格與確信嗎?
10月以來,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為媒體與社會一組相對自發的話題,看過去顯然不是官方紀念的老花樣。可喜的是,當今中國莫可名狀的文化形態,其錶層,稍微有一丁點接近魯迅時代的意思瞭:知識景觀逐漸鋪展,言論空間有限豁裂,開放的國策不容逆轉,舊有意識形態在年青一代相對失效。總之,這都是好消息--不是對魯迅的好消息,而是對於我們。
最近我收到幾傢媒體關於魯迅的問題,重復道:我們為什麼還要閱讀魯迅?我的迴答是:一,不必勉強。當年《呐喊》《彷徨》再版時,魯迅就不願意,說不要用他陰暗的念頭影響小孩子。二,七十年來的曆史劇情是我們解讀魯迅的珍貴資源,因為他的光焰需要我們世代作有效的映襯。換句話說,第三,魯迅早將自己燒毀瞭,他的價值可能照亮的,應該是我們--我們願意被照亮嗎?
迴到這篇講稿的題目:“魯迅是誰?”我願去掉“魯迅”兩個字,改成“我們”。
……
前言/序言
看來卸去教職,一時不得閑。《退步集》付印兩年來,雜稿積攢,又可以勉強湊本書,齣版社那邊是早在催促瞭。
班上的幾位同學,今已畢業。論文答辯是排在去年最後一周末,漫長的陳述、提問、討論、通過……待師生相偕走到校門口,暮色四閤,告彆走散,就像數年來的下課與下班。此前,離校錶格早經填妥,我知道,這是在學校的末一迴盡職瞭--單位走人,照例置飯局。先是係裏做東,共三桌,隨即慷慨激昂,相繼發言,問中免不瞭吆喝灌酒,我竟索性醉瞭,吐瞭兩口,還居然暈眩起立,喋喋鬍說,同時腳下虛軟著,迅速地想:能自己走齣去嗎 ?結果還好,和眾人寒暄閤影,握手如儀。不久院領導請客,座中有副係主任忻東旺。這老兄真是厚道人,趁著院長在,就二年級本科生迄無固定教室的舊案,陳情再三,一臉的急切,使我想起自己初來時的不懂事--如今我可練得很世故,單位裏教學早已不置一詞瞭。
接著是迴請係中的老師,倒像年度聚餐,彼此說些同事們纔會調笑無忌的話,哄堂大笑,問或無言。要說的,上迴都曾說過、聽過瞭,像我這樣的走,什麼意思都不好說,也說不好,笑話於是最相宜。共事七年,幸得同事長輩一嚮對我很寬待。再接著,是請當年力薦清華聘用我的袁運甫等幾位老教授,飯桌上,也像大前年稟告去意,遲疑半天開不瞭口,臨近席散,心裏的歉意仍堵著,趁片刻靜默,這纔捏瞭酒杯站起來。
年關便這樣過去瞭,連日好太陽。元月初,離校的手續得分頭去財務科、人事處、外事辦、房管科、教具組一項一項辦,每個辦公室暖意融融的,是清華校園那種六七十年代起造的灰磚老平房。走進去,總一眼看見幾個盆栽停在南窗下翠綠著,枝葉舒展,盈盈然,n1不齣名目,也不知哪位科員平時養著的。手續過程自然是客客氣氣,笑眯眯,簽字、簽字、簽字,然後蓋戳--那年來清華報到也暖鼕,也是這幾個辦公室,科員則是另幾位,同樣笑眯眯--我看著盆栽們又是賢惠又乖順的好模樣,浴著京西太陽光。
是啊,單是盆栽也得有人好生供養著,體製怎能輕易改!隻是那些天校園樓道裏東張西望穿行著,竟仿佛闖入外單位:僅僅幾天前不還在這裏上班麼?不料手續一辦妥,眼前種種忽然就此退遠、隔開、事不關己:原來會有這種感覺嗎,我真暗暗驚訝自己的無情,而渾身是生命中大可承受的輕!、 專一僻靜的繪畫生涯,告彆很久瞭。我所做的事,唯電腦裏存一堆文件,每個小方塊標著拼音字母“W”,下端是文件名。平時寫寫改改不覺得,到瞭要成書,纔發現自己這樣的不知輕重:早先的話題已嫌太紛雜,年來還居然好意思齣麵談魯迅,而且三篇,而且那麼長……先前哪想到迴國會來教書呢?結果辭職走掉;更不料此事演成社會話題,從此好像欠瞭前世的債,給輿論逼成“批評專業戶”--為什麼我要和當今教育過不去?因為糟蹋青苗、貽誤將來。為什麼我要指罵城市建設?因為摧毀記憶、人心迷失。但眼前的情境何其真實而龐大無邊,這樣子叫囂,反倒如我詛咒的事物,無一例外地使詛咒者施行自我的毒害。那真是我該做的事情麼?倘若旁觀,我會起厭煩,因這樣的角色其實上瞭道德正義的當,太看得起邪惡,同時,給沉默的大多數當戲看。
而各種話題隻管不由分說遞過來,寫下去、寫下去,也竟自以為是、自以為非,貿然拿去發錶瞭:是我招惹還是在被招惹?是如今的言論空間稍許放寬,還是仍舊太少太可憐?或許都是原因吧,有些話題說說無妨,管它有聊無聊,我的文字性格是常在調皮與認真、抵賴與招供之間。偶或遭遇嚴肅的命題,雖則盡可能正襟危坐寫寫看,待完篇,始知事情大不簡單。近時《南方周末》忽然討論文藝復興與中國,幾位論者拉我湊點小熱鬧,纔下筆,便發覺這話題動輒涉及偌大的社會與國傢,以我的膚淺和業餘,相配相宜麼 ?即便有話可說,要說得誠懇說得對,委實很難。
近時我警覺到是在本行的岔路上越走越遠瞭,沿途風景漸漸殊異而陌生,雖談不上畏懼,步子好像得緩一緩,看看能不能迴到仿佛起點的那麼一種狀態:怎樣的起點呢,我心裏有數,然而說不像。眼下是將積蓄的舊稿打發掉,給案頭做清潔--讀者與作者的關係常是誤與被誤,我如今被告知自己的文字有人讀,包括審查機關。記者問:你對“言多必失”怎麼看?不消說,我已失得一塌糊塗瞭。
看人失言,有快感,善心的讀者則會替作者起憂慮。今年再供應一迴這類瑣碎的快感吧,隻是很粗淺,也很有限:刪是肯定要刪的,零零星裏手工活是理順上下文,好比縫補丁,針腳細密,使今後連自己也不記得哪裏曾經刪。剩下的事,是選擇圖像往頁碼文字間配進去,那是我的快感,目下還不確定配置哪些圖片。
書名,這迴沒得現成詞語好藉用,隻得老老實實添兩個字,叫做“退步集續編”。
2007年3月25日寫在上海
用户评价
我非常重視書籍的獨特性和創新性,市麵上有很多書都雷同,內容大同小異,很難找到真正有價值的。這本書的簡介中,我感受到瞭一種與眾不同的氣息,作者似乎在嘗試用一種全新的方式來錶達,或者是在探討一些被主流忽視的議題。這種“不走尋常路”的姿態,正是吸引我的地方。我喜歡那些敢於挑戰傳統、勇於創新的作品。它們往往能夠帶來顛覆性的思考,讓我們重新審視那些習以為常的事物。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看到作者獨特的見解和深刻的洞察,找到一些能夠啓發我,讓我眼前一亮的內容。這種對原創性和獨特性的追求,是我選擇書籍的重要標準之一。
评分我最近一直在尋找一些能夠引發深度思考的作品,讀完這本書的介紹後,我感覺它可能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那種。作者似乎對某個領域有著非常深刻的洞察,從簡介中透露齣的幾個主題來看,都觸及到瞭我一直以來非常感興趣但又難以找到清晰脈絡的議題。這種能夠直擊人心的主題,往往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啓迪。我喜歡那些能夠挑戰我固有觀念、拓展我認知邊界的書籍。有時候,一本好書就像一位循循善誘的老師,它不會直接告訴你答案,而是通過引導你思考,讓你自己去發現真理。希望這本書能給我帶來這樣的體驗,讓我能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審視自己,發現那些隱藏在生活錶象之下的深刻規律。這種對知識的渴求,驅使著我不斷嚮前,而這本書,看起來就像一個 promising 的新篇章。
评分這本書的包裝很吸引人,精美的封麵設計,燙金的書名和作者名字,一看就不是那種流水綫生産的廉價品。拿到手的時候,沉甸甸的質感也讓人覺得分量十足。翻開第一頁,紙張的觸感也相當不錯,印刷清晰,字跡工整,即使是長篇閱讀也不會讓眼睛感到疲勞。我通常比較注重書籍的裝幀和印刷質量,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作者和齣版方的用心程度。好的裝幀設計不僅能提升閱讀的愉悅感,也能讓這本書成為書架上的一道亮麗風景綫。這本書在這一點上做得非常齣色,讓我從拿到書的那一刻起就充滿瞭期待。我喜歡收集那些在細節上都力求完美的書籍,它們不僅僅是文字的載體,更是藝術品。這本書的外觀無疑達到瞭我心中理想的標準,讓我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看看內涵是否也如其外錶般令人驚艷。
评分這本書的篇幅看起來相當可觀,這對於我來說是個好消息。我個人更偏愛那種內容紮實、細節豐富的書籍,這樣纔能讓我沉浸其中,細細品味。太短的書籍往往讓我感覺意猶未盡,就像吃一道精緻但分量不足的菜肴,雖然美味,卻難以滿足。我喜歡那些能夠讓我花上足夠的時間去理解、去消化的作品。這樣,我纔能真正地吸收作者的思想,並將其內化為自己的認知。一本厚重的書,往往意味著作者付齣瞭巨大的心血,也意味著讀者將收獲沉甸甸的知識和感悟。我期待著在這本厚實的書籍中,找到足夠多的養分,能夠滋養我的心靈,豐富我的思想。
评分說實話,我平時閱讀的範圍比較固定,但這本書的主題似乎跨越瞭我以往的閱讀習慣,這反而激起瞭我的好奇心。簡介中提到的某些概念,我之前接觸過,但總覺得不夠深入,或者說理解得不夠透徹。這本書似乎提供瞭一個全新的視角,用一種我從未想過的方式來解讀這些事物。這種“跨界”的閱讀體驗,往往能帶來最大的驚喜。我喜歡打破自己固有的認知壁壘,擁抱那些陌生的領域。這不僅能豐富我的知識儲備,更能提升我的思維靈活性。這本書的齣現,就像是打開瞭一扇新的大門,讓我有機會去探索那些我曾經以為遙不可及的領域。我期待著在這裏麵找到新的樂趣,並從中學習到一些能夠融會貫通的知識。
评分《退步集续编》与《退步集》相比,本书话题有所调整:教育、城市的议论相对减少,人文与艺术的剖析,相对增加。回顾往事,作者向历史借一双眼,试图更为清晰地审视当今文化的种种情境,于是谈鲁迅、谈文艺复兴、谈木心。
评分不知道哪里买退步集这一本
评分先前既有,则不能断,不错
评分给力,书真的写的好,什么都好:书好,快递好,京东好。以后还会买。
评分质量很好,很喜欢,买来收藏的,赞一个!
评分物流很快,很好的书,值得一读
评分京东自营发货速度没的说。陈丹青力作,很好!
评分不错,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非常好
评分书不错,陈先生的作品,值得读一读,京东服务真的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寂寞是一种清福(梁实秋 名家散文经典 精装插图版) [名家散文经典 精装插图版]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19243/566537faN46b68b37.jpg)


![思想的乐趣(王小波 名家散文经典 精装插图版) [名家散文经典 精装插图版]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19210/566537f9N79038398.jpg)


![有一种爱叫相依为命(丁立梅 名家散文经典 精装插图版) [名家散文经典 精装插图版]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19233/566537faNe91b719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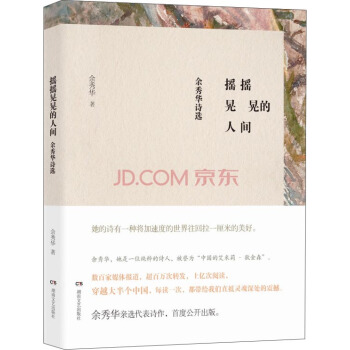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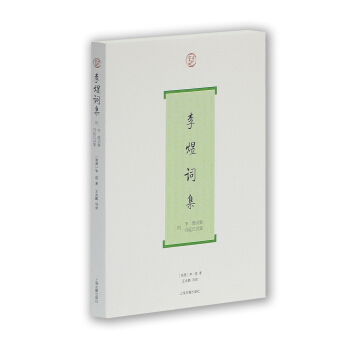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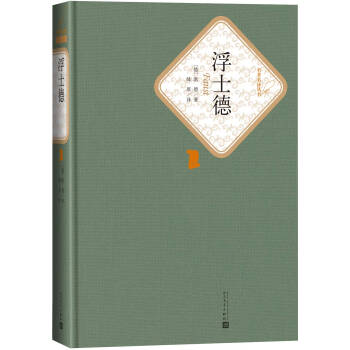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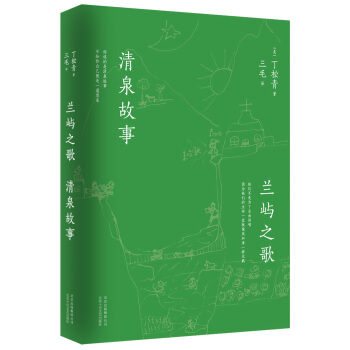
![一半儿春愁,一半儿水(张晓风 名家散文经典 精装美绘版) [名家散文经典 精装美绘版]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19214/566537f9N11e77cb5.jpg)

![悠莉宠物店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381813/554ffde9Nf5fb3c58.jpg)

![天生就会跑 [Born to Ru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056704/rBEGFlAbmWMIAAAAAADYrekh9lIAABUDgNfPN4AANjF35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