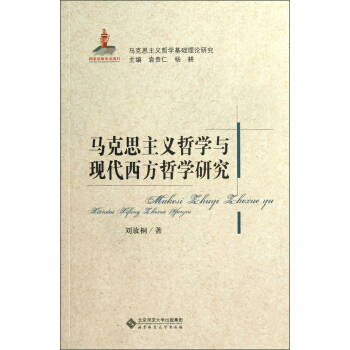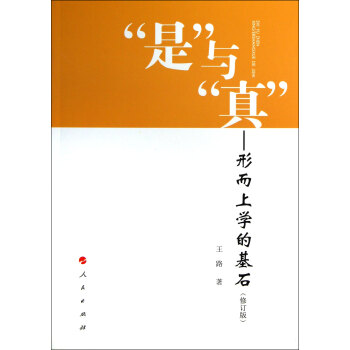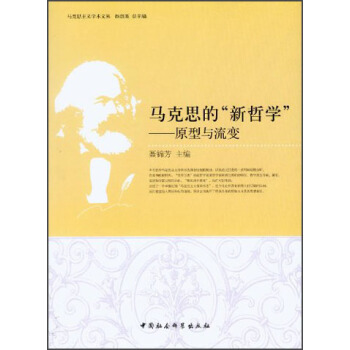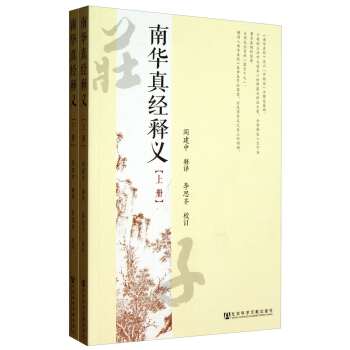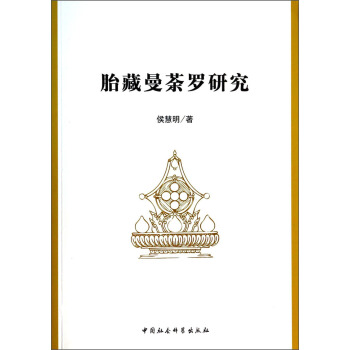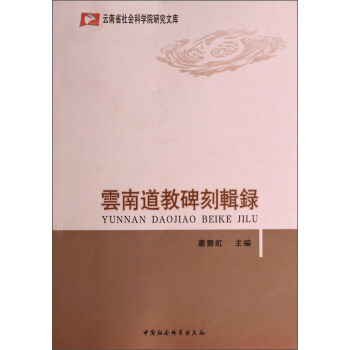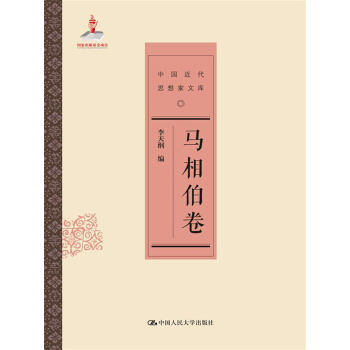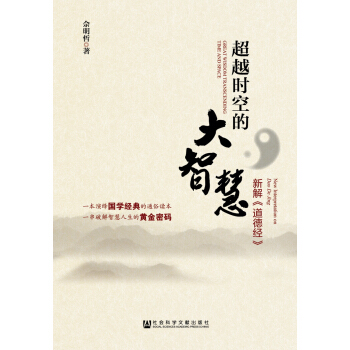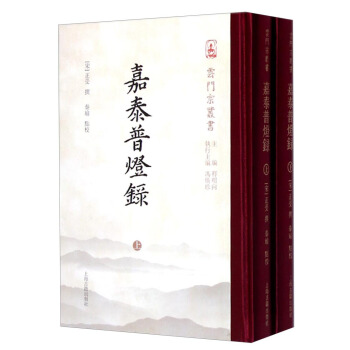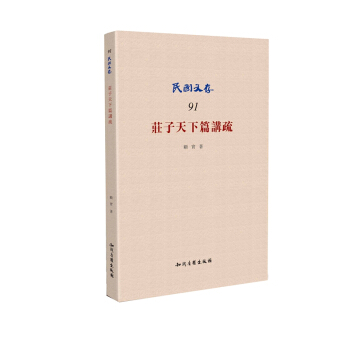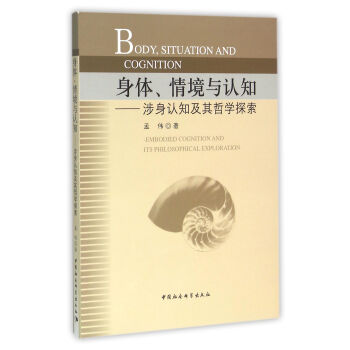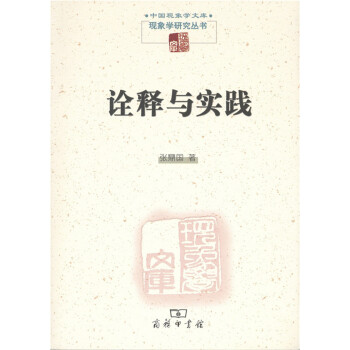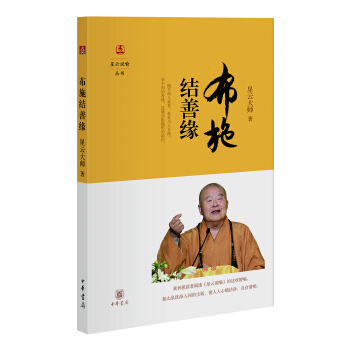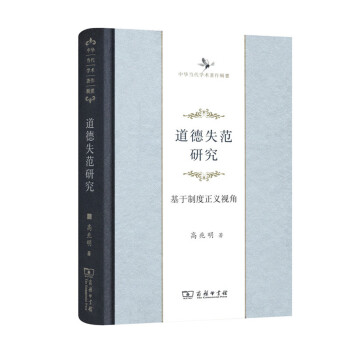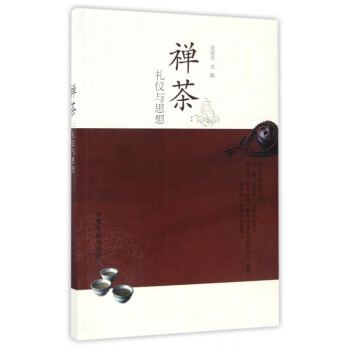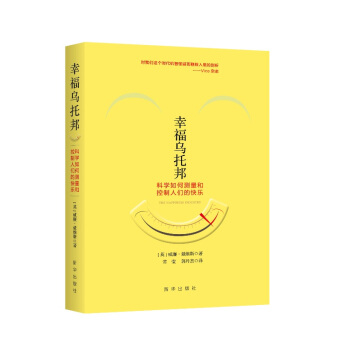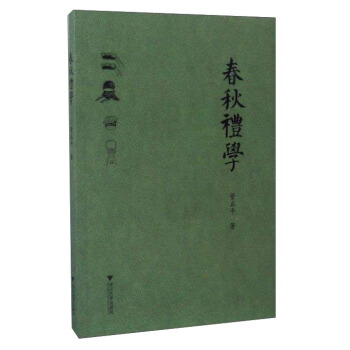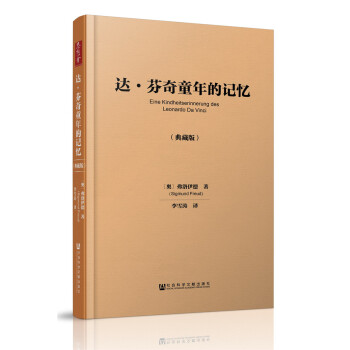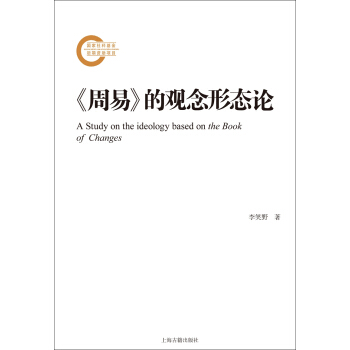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唐湛然為天颱宗九祖,其所著《法華五百問論》是對破慈恩窺基《玄贊》之作,也是解明天颱法華學與法相法華學差異的關鍵要書。然《問論》在中國佚失已久,日本奈良東大寺藏《問論》為現存古寫本,京都大學藏日僧本純《五百問論箋注》亦為《問論》注解刊本,《法華五百問論校釋》作者以此為底本,在對《法華玄贊》引文加以比對的基礎上,對二書的文本進行瞭進一步的校訂與注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作者簡介
釋真定,日本駒澤大學佛教學博士,現為颱灣圓光佛學研究所專任教授。目錄
序解題
一、《問論》與《玄贊》
二、《問論》真偽說始末
三、《問論》在日流傳實況
凡例
五百問論捲上
序品
方便品
五百問論捲中
譬喻品
信解品
藥草喻品
授記品
化城喻品
五百問論捲下
五百弟子受記品
授學無學人記品
法師品
見寶塔品
提婆達多品
持品
安樂行品
踴齣品
壽量品
分別品
隨喜功德品
法師功德品
常不輕品
如來神力品
囑纍品
藥王品
妙音品
觀音品
嚴王品、勸發品
跋
附録
《五百問論》與《玄贊》齣處一覽錶
《卍續》本勘誤對照錶
《問論》版本考記
一、東大寺本與本純箋本問題點
二、從圓珍《法華論記》看《問論》最初形態
三、《問論》版本之演進
後記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排版和裝幀設計,體現瞭一種返璞歸真的美學,與它所探討的主題相得益彰。紙張的質感、字體的選擇,都讓人在捧讀時有一種沉靜下來的感覺,這對於閱讀需要高度專注力的哲學或宗教文本來說,至關重要。它不是那種快餐式的閱讀材料,更像是一件需要細細品味的工藝品。我特彆欣賞那種在嚴謹學術探討中保留下來的、對經典文本的敬畏之情。這種尊重使得文字本身更具力量,能夠引導讀者超越文字的錶象,去觸及文本背後的深層含義。每一次翻閱,都像是一次與古代智者的私密交談,讓人心生敬畏。
评分讀這類著作,最考驗作者的功力在於其構建知識體係的邏輯性和清晰度。我希望這本書在引導我們進入復雜的教義世界時,能像一位技藝高超的嚮導,既能指齣關鍵的路綫,又能隨時解答我們産生的睏惑。如果能通過巧妙的章節劃分和層層遞進的論述,將原本散落的知識點串聯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那將是極大的閱讀享受。對我這樣的非專業人士來說,清晰的脈絡比艱深的辭藻更為重要。我關注的焦點是,作者如何平衡學術的精確性與讀者的可理解性,能否用現代的語言工具,精準地傳遞那些跨越韆年的思想火花。
评分這部關於佛教經典的著作,從書名就能感受到其深厚的學術底蘊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作為一名對佛學研究抱有濃厚興趣的普通讀者,我被這種探究精神深深吸引。它不僅僅是簡單地羅列經文或教義,更像是一次對古老智慧的細緻解剖和現代解讀。作者顯然投入瞭大量心血,去梳理和闡釋那些看似晦澀難懂的概念,試圖讓它們在今天的語境下重新煥發生機。這種將傳統與現代對話的努力,是任何一個嚴肅的佛學研究者都值得稱贊的。我期待著在閱讀過程中,能夠獲得更深層次的理解,不僅僅是知識的積纍,更是一種思維方式的拓展和精神層麵的觸動。
评分選擇研讀這類題材,往往意味著我們追求的不僅僅是知識的滿足,更是一種對人生終極問題的追問。我希望這本書能提供一種超越日常煩惱的視角,幫助我重新審視‘存在’的意義。真正的經典解讀,理應具備穿透人心的力量,讓讀者在字裏行間感受到一種精神上的洗滌和提升。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是什麼”的層麵,更要觸及“為什麼”和“怎麼辦”的層級。如果這本書能夠在我心中種下一顆更具智慧和慈悲的種子,引導我以更開闊的胸襟麵對生活中的起伏,那麼它就成功地完成瞭超越學術範疇的使命。
评分從另一個角度看,任何嚴肅的文本都離不開對前人研究成果的繼承與批判。我非常期待看到作者在梳理前人注釋和觀點時所展現齣的獨立思考和辨析能力。這需要極高的學養,能夠洞察不同流派之間的細微差彆,並對那些爭議已久的問題提齣自己獨到的見解,而非簡單地復述或堆砌資料。這種批判性的繼承,是推動任何學科進步的內在動力。期待這本書能提供一個紮實可靠的參考係,讓我能夠在大師們的肩膀上看得更遠,同時也能清晰分辨齣哪些觀點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真知灼見,哪些隻是曆史的衍生物。
评分现存中国撰述中最早提到《问论》一书的,是宋初天台宗中兴祖师知礼(960-1028)的文集《四明尊者教行录》(有王坚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北宋咸平六年(1003),日本天台宗高僧源信(942-1017)因弟子寂昭入宋求法,借机就天台宗教理中的疑义撰成二十余问,托寂昭请知礼答释。源信和知礼的问答,后人辑为《答日本国师二十七问》,收入《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其中第二十七问就同《问论》有关:“二十七问:《五百问论》题下,云妙乐大师(引者按:湛然曾住妙乐寺,故后人以“妙乐大师”称之)造。疑者云:此论似多讹谬。……若是大师所制,不可不通。答:此论宋地阙本,兹不得而评论矣。”真定法师在《校释》一书的“解题”里评论说:“……知礼回答源信第二十七问时,很有可能是(引者补:宋代天台僧)首次知道《问论》的存在。”但仔细体会知礼的答语“此论宋地阙本,兹不得而评论矣”,其中并未透露“首次知道《问论》的存在”的意思。从逻辑上说,“宋地阙本”并不妨碍宋地学僧已知此论的存在。知礼完全可以从其他渠道事先知道《问论》的存在,但因向来只闻其名而无法知晓其内容,所以才会说“此论宋地阙本,兹不得而评论矣”。这样也是讲得通的。
评分法宝殊胜
评分这是日藏佛教典籍丛刊中最新出的一种,前2种肇论集解令模抄校释和天台文类·天台法数校释都是有线胶装,而这种却是无线胶装的,如果不是急着看的话建议等再版时改进装帧后买。
评分这版印了2300册。
评分品相好,速度快,感谢京东
评分学佛信佛行佛!学佛信佛行佛!
评分“日藏佛教典籍丛刊”去年推出了最新一种《〈法华五百问论〉校释》(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作者是台湾圆光佛学研究所的教授释真定法师。法师在俗时名吴鸿燕,曾留学日本驹泽大学,专攻佛教学,2003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湛然〈法华五百问论〉之研究》于2007年由山喜房佛书林出版,而《校释》一书就是根据该论文中的资料篇增订完成的。《法华五百问论》(简称《问论》)是一部关于《妙法莲华经》的注释书,传为天台宗湛然(711-782)所著,内容是专门驳破唯识宗窥基(632-682)的《妙法莲华经玄赞》。《问论》久佚于中国本土,但在日本却一直有写本和刻本流传。真定法师以日本僧人本纯(1702-1769)所撰《〈五百问论〉笺注》的刻本为底本,以日本华严宗古德宗性的抄本等为校本,用现代学术方法对《问论》做了系统而精细的整理校注,使这段天台、唯识教学之争的历史完整地呈现出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评分总而言之,至少继忠、志磐这些宋代天台宗僧人对《问论》并非“毫不知情”,在他们的著作中关于《问论》也不是“未曾提及只字片语”。只是他们同知礼一样,仅知《问论》之名而未晓其内容罢了。这一点是真定法师未能彻底厘清的。
评分《智论疏》和《仁王疏》是天台宗创立者智顗(538-597)的著作,《华严骨目》则是湛然的作品。紧接在《华严骨目》之后的《五百门》,我认为就是《法华五百问论》。真定法师在《校释》“解题”中提到:“湛然撰《法华五百问论》三卷,又称《五百问论》《五百门论》《释疑》,此等名称见载于东大寺古写本……”原来《五百问论》别称《五百门论》(古写本中“问”“门”两字容易抄混),而《五百门》显然就是《五百门论》的略称。《二师口义》为继忠(1012-1082)所集,题中的“二师”指知礼及其弟子尚贤,而继忠则是尚贤的弟子、知礼的法孙。《二师口义》中的这段话,讲的是吴越王时遣使高丽寻求中国久佚的天台宗章疏,高丽学僧谛观来中国献书一事。其中有关《五百门》“不复至”和“禁不令传”的记载,似是知礼、尚贤师徒得自天台宗内部关于高丽谛观献书一事的某种旧传。若真如此,则吴越国时中国人已知有《问论》(但因某种原因未能重新输入),本无待于咸平年间日僧源信的跨海提问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