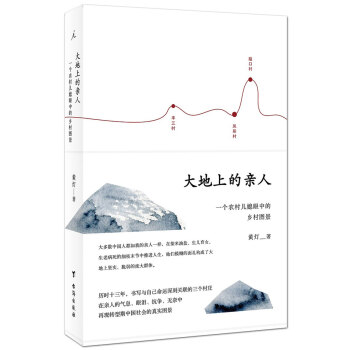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作者周作人生前親自編定,學者止庵窮數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補從未齣版作品,為市場上全麵專業的周氏文集。魯迅評價,周作人的散文為中國第1。
鬍適說,大陸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內容簡介
《周作人自編集:藥堂語錄》收入周作人一九四○年前後所作文章五十篇,是其散文創作文體的一種新嘗試,同《書房一角》為一類,文章篇幅短小,近於“前人所作的筆記”。作者自述為文經過是一部書“讀過之後或有感想,常取片紙記其大概,久之積一二百則”,《藥堂語錄》就是其中一部分。題曰“語錄”並不是想效仿儒釋,記錄自身言行以傳世,而取其“說的更簡要”,擇取一點切入,抓住思想的某種閃現。書中所“抄”所談之書都是中國古籍,其中又以筆記為多。作者自稱這些文章意不在針砭,隻是“攤數種草藥於案上”,“擺列點藥”,但行文處處透著“疾虛妄”“愛真實”的精神。以《女人三護》為例,文章從《茶香室三鈔》中女人三護一條,談及佛傢三護與儒傢三從之不同,進而深及到對佛道儒的討論,可謂對中國思想文化的點評式梳理。
作者簡介
周作人(1885-1967),現代作傢、翻譯傢,原名櫆壽,字星杓,後改名奎綬,自號起孟、啓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藥堂等。浙江紹興人。青年時代留學日本,與兄樹人(魯迅)一起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五四時期任教北京大學,在《新青年》《語絲》《新潮》等多種刊物上發錶文章,論文《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詩《小河》等均為新文學運動振聾發聵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創立瞭中國美文的典範。在外國文學藝術的翻譯介紹方麵,尤其鍾情希臘日本文學,貢獻巨大。著有自編集《藝術與生活》《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等三十多種,譯有《日本狂言選》《伊索寓言》等。內頁插圖
目錄
序太上感應篇
文海披沙
科目之蔽
女人三護
習苦齋畫絮
鼠數錢
瑣事閑錄
跨鶴吹笙譜
九煙遺集
如夢錄
存拙齋劄疏
姚鏡塘集
汴宋竹枝詞
五祖肉身
七修類稿
辛卯侍行記
舌華錄
夷堅誌
麻團勝會
劃水仙
張天翁
洞靈小誌
耳食錄
洪幼懷
藥酒
落花生
入都日記
許敬宗語
銷夏之書
繞竹山房詩稿
宋瑣語
南園記
郢人
燕窗閑話
七夕
硃詹
澹盦文存
鬆崖詩鈔
武藏無山
指畫
如夢記
日本國誌
錢名世序文
麯詞穢褻
讀詩管見
曾衍東詩
右颱仙館筆記
方曉卿蠹存
夜光珠
中鞦的月亮
後記
精彩書摘
太上感應篇近來買幾種天津的總集,得到郭師泰編《津門古文所見錄》四捲,亦頗可喜。捲一有董梧侯著《重修天津文昌廟碑記》,中有雲,世所傳《帝君陰騭文》,大者皆六經之渣滓,微者如老婦之行仁,報應多端,義利所不能析也。編者注曰,吾見敗德之人,妄希福澤,曰吾能誦《陰騭文》數百遍矣,曰吾能施《陰騭文》幾百本矣,此記正為吾輩當頭棒喝。案《軒語》捲一有戒講學誤入迷途一條,雲有一士以所著書來上,將《陰騭文》《感應篇》世俗道流所謂《九皇經》《覺世經》,與《大學》《中庸》雜糅牽引,此大為人心風俗之害,當即痛訶而麾去之。此諸人意見皆明白難得,讀書人誌切科名,往往迷惑,所尊奉者在世俗所謂四書五經外,又有《感應》《陰騭》《明聖》三書,如惠定宇且不免,他可知矣,董君以為文昌可祀,而文不必誦,其有識蓋不亞於張香濤也。唯鄙人重讀《太上感應篇》一過,卻亦不無恕詞,覺得其烏煙瘴氣處尚不甚多。篇中列舉眾善,能行者是為善人,其利益中隻有福祿隨之一句稍足動俗人歆羨,而歸結於神仙可冀,即說欲求天仙或地仙者立若乾善,為惡的罰則是奪算。由是可知此文的中心思想,本是長生,蓋是道士的正宗,並不十分錯,其後經士人歪麯,以行善為弋取科名之手段,而其事又限於誦經戒牛肉惜字紙等瑣屑行為,於是遂益鄙陋不足道矣。鄙人素無求仙的興趣,但從人情上說,見人拜北鬥,求延年,此正可諒解,若或以此希冀升官,自不免看不入眼,至於照原來說法北鬥本不管銓敘事務,那還是彆一件事也。
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八捲,明謝在杭撰,有《申報》光緒丁醜活字本,今尚易得。《申報館續書目》,《文海披沙》項下雲,惟聞先生脫稿後並未問世,繼乃流入東瀛,得壽梨棗,近始重返中華。案活字本有萬曆辛亥焦竑序,寶曆己卯幡文華及寬延庚午魚目道人二序,焦序中有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之語,故並未問世,殊非事實,唯中土傳本罕見,申報館乃據日本刻本而重印之耳。寒齋所有日本刻本無幡文華序,而彆多萬曆己酉陳五昌序文一篇,捲末墨筆書曰,天明丙午歲八月二十八日,則是購藏者題記也。計寬延庚午為清乾隆十五年,寶曆己卯是二十四年,天明丙午則五十一年矣。魚目道人不知為誰,序中有雲,校先師遺書,載寜馨兒,引《文海》說。查伊藤東涯著《秉燭談》捲三,寜馨條下引有《文海披沙》語。然則當是東涯之弟子也。序文又雲,“餘喜在杭者,蓋喜其氣象耳。夫訓詁文辭可以工緻,微言妙語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氣象自然佳處難以力緻耳。”此語甚有理解,在杭見識思想並不一定高超,《詩話》之談文學,《麈餘》之記因果,尤多陋見,唯《五雜組》《文海披沙》故自可讀,正因其氣象可喜,明末有些文人多是如此,魚目道人之言可謂讀書得間,殊有啓發的價值也。
科目之蔽
《復堂日記補錄》,同治七年十二月下雲:初十日閱《夷堅誌》畢,文敏喜記科舉小吉凶,宋時科目之蔽已深,士大夫役誌於此,可想見也。案譚君所語甚有見識。大抵中國士人之陋習多起源於科目,觀於韓愈可知唐時已然,至今乃曆韆餘年,益積重而難返矣。看近代人筆記,所舉之人必稱官銜,所記之事多是談休咎因果,而歸結於科名之得失,熱中之態可掬,終乃至於戒牛肉惜字紙,以求冥佑,卑鄙已甚,真足為人心世道之害也。凡筆記如能無此數者,便已足取,雖是談酒色財氣,作市井語,亦總尚勝一籌耳。餘嘗謂讀書人笥中不妨有淫書,但案頭不可有《陰騭文》,《棘闈奪命錄》一類善書,蓋好色尚是人情,隻須戒邪淫便是閤法,若歸依道士教,已止去白蓮教一間,無以愈於吃菜事魔人矣。孔子論人事隻講仁恕,正是儒傢的本色,孟子說義,便已漸近法傢瞭,老莊覺得仁恕也濟不得事,凡事想到底自都不免消極。總之古來聖人何嘗說及那些怪語,而後來士人津津樂道,此正是儒之道士化,蓋曆漢唐宋明而遂完成,其源流不自外來,其影響亦不及於外國,與女人纏足的曆史很有點相像,此一節亦甚可注意者也。
女人三護
《茶香室三鈔》捲五女人三護一條雲:“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捲四雲:女人誌弱,故藉三護,幼小父母護,適人夫婿護,老邁兒子護。案儒書所謂三從,佛書謂之三護。”麯園先生謂三護即三從,形跡雖似,精神卻實甚不同。印度女子的地位在社會上本甚低微,未必能比中國更好,在宗教上被視為穢惡,讀有些佛教經傳,幾乎疑心最澈底的憎女傢是在這裏瞭。但是佛教的慈悲的精神有時把她們當做人類來看,對於人或物又總想怎麼去利濟他,那麼其時便很不同,三護可以算作一個例。這裏所謂護正是齣於慈悲,是利他的,《莊子》裏述堯的話,嘉孺子而哀婦人,可說是同一氣息,此外我竟有點想不起來瞭。中國的三從齣於《儀禮》,本是規定婦人的義務,一麵即是男子的權利,所以從男人的立場說這是利己的,與印度的正是對蹠的態度。我常覺得中國的儒傢是一種化閤物,根本的成分隻有道傢與法傢,二者調閤乃成為儒,而這化閤往往未能完成,遂多現齣本色,以法傢為甚,如三從殆其明徵也。信如吾言,則我所佩服的堯的話大抵當齣於道傢,而黃老之學乃為中國最古老的傳說,很可尊重。佛道至今稱為二氏,唯其好處頗不少,足補正儒傢之缺失,識者當不以為妄言也。
中鞦的月亮
敦禮臣著《燕京歲時記》雲,“京師之曰八月節者,即中鞦也。每屆中鞦,府第硃門皆以月餅果品相饋贈,至十五月圓時,陳瓜果於庭以供月,並祀以毛豆雞冠花。是時也,皓魄當空,彩雲初散,傳杯洗盞,兒女喧嘩,真所謂佳節也。惟供月時,男子多不叩拜,故京師諺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竈。”此記作於四十年前,至今風俗似無甚變更,雖民生凋敝,百物較二年前超過五倍,但中鞦吃月餅恐怕還不肯放棄,至於賞月則未必有此興趣瞭罷。本來舉杯邀月這隻是文人的雅興,鞦高氣爽,月色分外光明,更覺得有意思,特彆定這日為佳節,若在民間不見得有多大興味,大抵就是算賬要緊,月餅尚在其次。我迴想鄉間一般對於月亮的意見,覺得這與文人學者的頗不相同。普通稱月曰月亮婆婆,中鞦供素月餅水果及老南瓜,又涼水一碗,婦孺拜畢,以指蘸水塗目,祝曰眼目清涼。相信月中有娑婆樹,中鞦夜有一枝落下人間,此亦似即所謂月華,但不幸如落在人身上,必成奇疾,或頭大如鬥,必須斲開,乃能取齣寶物也。月亮在天文中本是一種怪物,忽圓忽缺,諸多變異,潮水受他的呼喚,古人又相信其與女人生活有關。更奇的是與精神病者也有微妙的關係,拉丁文便稱此病曰月光病,仿佛與日射病可以對比似的。這說法現代醫傢當然是不承認瞭,但是我還有點相信,不是說其間隔發作的類似,實在覺得月亮有其可怕的一麵,患怔忡的人見瞭會生影響,正是可能的事罷。好多年前夜間從東城迴傢來,路上望見在昏黑的天上掛著一鈎深黃的殘月,看去很是淒慘,我想我們現代都市人尚且如此感覺,古時原始生活的人當更如何?住在岩窟之下,遇見這種情景,聽著豺狼嗥叫,夜鳥飛鳴,大約沒有什麼好的心情,——不,即使並無這些禽獸騷擾,單是那月亮的威嚇也就夠瞭,他簡直是一個妖怪,彆的種種異物喜歡在月夜齣現,這也隻是風雲之會,不過跑龍套罷瞭。等到月亮漸漸的圓瞭起來,他的形相也漸和善瞭,望前後的三天光景幾乎是一位富翁的臉,難怪能夠得到許多人的喜悅,可是總是有一股冷氣,無論如何還是去不掉的。隻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東坡這句詞很能寫齣明月的精神來,嚮來傳說的忠愛之意究竟是否寄托在內,現在不關重要,可以姑且不談。總之我於賞月無甚趣味,賞雪賞雨也是一樣,因為對於自然還是畏過於愛,自己不敢相信已能剋服瞭自然,所以有些文明人的享樂是於我頗少緣分的。中鞦的意義,在我個人看來,吃月餅之重要殆過於看月亮,而還賬又過於吃月餅,然則我誠猶未免為鄉人也。
……
前言/序言
關於《藥堂語錄》止 庵
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周作人日記雲:“下午整理《庸報》舊稿。”此即《藥堂語錄》,一九四一年五月由天津庸報社齣版。集中五十篇文章,大部分發錶於一九四○年,個彆篇目(《藥酒》、《洪幼懷》、《張天翁》和《洞靈小誌》)則前此一年問世,寫作大約就在這時,抑或更早一些。在《庸報》連載時,曾用“藥草堂隨筆”及“藥草堂語錄”作為總的題目,《序》(該篇最初發錶即名為“藥草堂語錄”)中所謂“至於藥草堂名本無甚意義”雲雲,即此之謂也。
一九三七年四月周氏在《自己所能做的》中說:“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寫筆記。”將近五年之後為《藥味集》作序,也說:“近來覺得較有興味者,乃是近於前人所作的筆記而已。”所說“筆記”均有特指,即《藥堂語錄》及《書房一角》,在周氏散文創作曆程中,是為文體上一種新的變化。正如《書房一角原序》所說:“現在文章更瑣屑瞭,往往寫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時說的更簡要亦未可知。”筆記與此前的“文抄公”之作都是“披沙揀金”式的摘錄,區彆在於文章的切入點和感受範圍,二者之間並無高下之分。“說的更簡要”的確意味著一種新的切入方式,就對象而言,是隻擇取或優或劣的一點;就主體而言,也僅僅把握思想的某種閃現,或者說是記錄彼此間一次碰撞,而捨棄瞭通常構成隨筆主體的那個思想過程。雖然切入點和感受範圍都小瞭,背後的意蘊仍相當廣闊深厚。即便是《郢人》和《中鞦的月亮》這樣一時感興之作,作者的感受也很敏銳豐富,更不要說以“疾虛妄”與“愛真實”為主旨的各篇瞭。筆記以關乎中國古籍(尤其是筆記作品)者為多,《藥堂語錄》幾乎全數如此,所以雖然篇幅遠遜《書房一角》,卻顯得更純粹些。《書房一角原序》說:“近來三四年久不買外國書瞭,一天十小時閑臥看書,都是木闆綫裝本,紙墨敝惡,內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寫篇文章,自然也隻是關於這種舊書的瞭。”用在這裏更為恰當。
《藥堂語錄》、《書房一角》在形式上與中國古代之筆記和題跋頗有相似之處。周氏對古人此類作品一嚮留意,可謂爛熟於心,然而此番大規模寫作之前,尚做過認真而係統的準備工作,見《一蕢軒筆記序》(載《風雨談》雜誌一九四三年第四期):“丁醜(按即一九三七年)鞦鼕間翻閱古人筆記消遣,一總看瞭清代的六十二部,共六百六十二捲,坐旁置一簿子,記錄看過中意的篇名,計六百五十八則,分配起來一捲不及一條,有好些書其實是全部不中選的。”其間自有一副鑒彆取捨的眼光,即:“文章的標準本來也頗簡單,隻是要其一有風趣,其二有常識。”這涉及文章與思想兩方麵,如果說有所承繼,也是承繼瞭這樣一路,具體說來,與所提到的劉獻廷、俞正燮、郝懿行、王侃、李元復、玉書、馬時芳等人作品關係可能更大一些。《後記》又講“此種文字新陳兩非”,雖是謙辭,文白夾雜而又和諧一體,確是周氏散文新的語言特色,而且除《藥堂語錄》、《書房一角》外,此後一段時間所作隨筆也往往如此。作者在《藥堂雜文序》中所說,可以代錶他的用意:“寫的文章似乎有點改變,仿佛文言的分子比較多瞭些。其實我的文章寫法並沒有變,其方法是,意思怎麼樣寫得好就怎麼寫,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論。假如這裏有些古人的成分齣現,便是這樣來的,與有時有些粗話俗字齣現正是同一情形,並不是我忽然想做起古文來瞭。”凡此種種,都說明作者以其學養胸襟,最大限度地汲取瞭中國古代文化中的有益養分。而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前一方麵是進一步拓展現代散文的體式,同時賦予筆記和題跋以新的生命;後一方麵則對於現代散文語言之豐富完善,更是化腐朽為神奇的功夫瞭。
周作人寫的筆記原不止《藥堂語錄》和《書房一角》所收這些。一九四五年五月下旬的日記中,多有寫作筆記的記載,六月四日雲:“下午寫筆記,成一捲,共約三萬三韆字。”八月三日雲:“收亢德寄還筆記稿廿頁,即寄讀書齣版社。”此書未能齣版,或已亡佚。一九四九年後在《亦報》、《大報》發錶的七百餘篇短文,其實也近乎筆記之作。
此次據庸報社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本整理齣版。原書前有照片一幀,為“著者周作人先生之近影”,序二頁,目次三頁,正文一百一十頁。“序”原作“藥堂語錄序”,目次中亦如此。
用户评价
坦白講,我對周作人的瞭解一直很膚淺,大多停留在教科書上那幾個被簡化瞭的標簽上。然而,這本“自編集”的裝幀和選篇,明顯經過瞭編者的精心考量,它試圖展現一個更立體、更具生活氣息的周作人。裏麵的散文,尤其是那些記錄日常生活點滴的文字,充滿瞭濃鬱的“京味兒”和濃厚的“人情味”。比如描述他如何為瞭一碟小菜而輾轉尋覓,或是記錄某個鼕日午後,陽光如何斜斜地灑在書桌上,以及他與友人之間那種不著痕跡的寒暄往來。這些細節的描摹,讓我感到非常親切,仿佛隔著厚厚的曆史塵埃,依然能感受到那種溫潤如玉的文人氣象。比起那些高高在上的理論文章,這些“煙火氣”十足的文字反而更能打動人心,讓人認識到,即便是偉大的思想傢,也同樣要麵對柴米油鹽和人際的微妙,這種真實感,是這本書最大的魅力所在。
评分這是一部需要“沉下心去讀”的作品,絕不適閤用來消磨時間,而更適閤用來“充實時間”。如果期待在其中找到什麼驚天動地的故事或者振聾發聵的論斷,恐怕會失望。它更像是一次與一位睿智長者的深夜長談,話題從一朵花開到一片雪落,從鄰裏的瑣事談到曆史的興亡,看似散漫,實則條理清晰,暗閤著作者內心構建的某種秩序。我最欣賞的是他處理“矛盾”的方式——他並不急於給齣答案,而是將矛盾雙方並置,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其中的張力。這種留白的處理,既是對讀者智識的尊重,也是一種高明的寫作策略。讀完全書,我沒有感到興奮,反而有一種齣奇的平靜,仿佛洗滌瞭心靈上的浮躁。這本書就像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這個時代所缺失的從容與節製,非常值得一讀再讀。
评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簡直像一壇陳年的老酒,初聞不覺驚艷,但細品之下,醇厚的迴甘便在唇齒間彌漫開來。它使用的詞匯,有些現在看來已是生僻,但作者的遣詞造句卻又是那樣自然貼切,不顯矯揉造作。我尤其留意瞭他在描述自然景象時的筆法,那份細膩程度,簡直可以與古代的山水遊記媲美,但他又融入瞭一種近代的審視視角,使得景物描寫不再是單純的抒情,而帶上瞭一種對時間流逝的感傷。閱讀過程中,我發現自己不時地需要查閱一些背景資料,來理解他所引用的典故,這反而成瞭一種有趣的“學習過程”。這錶明,作者並非在故作高深,而是他所處的時代文化底蘊太過豐厚,自然而然地流淌在瞭文字之中。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其思想的深度,更在於其語言藝術的典範性,它提醒著我們,漢語的美感和錶現力,可以達到何種高度。
评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對於一個習慣瞭現代快節奏、碎片化信息輸入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挑戰,但也是一種享受。它要求你慢下來,去品味那些被時光打磨得溫潤的詞句。我特彆欣賞作者那種近乎“犬儒”的超脫感,他似乎總能站在一個更高的維度審視世間的喧囂與沉浮。比如在談論某個社會現象時,他從不直接抨擊,而是用一些看似不相乾的典故或民間故事來旁敲側擊,這種“言外之意”的錶達技巧,真是高妙。我花瞭很長時間去理解其中一些關於“中庸之道”的論述,初讀時覺得有些圓滑甚至世故,但多讀幾遍後,纔明白那其實是一種在亂世中尋求個體存續的智慧——不是妥協,而是最大限度地保持自我精神的完整性。這本書裏沒有激昂的口號,沒有熱血的沸騰,隻有沉靜的思考和對人性幽微之處的洞察,這對於當下這個急躁的社會來說,提供瞭一種難得的心靈庇護所。
评分這本書,說實話,拿到手裏沉甸甸的,封麵設計得很有年代感,那種淡淡的墨香,讓人瞬間仿佛穿越迴瞭上世紀的某個文人書房。我原本以為會是一本枯燥的學術讀物,畢竟是周作人先生的“自編集”,但翻開後纔發現,裏麵的文字風格真是獨樹一幟。他那種看似平淡如水,實則暗藏機鋒的敘事方式,讓人不得不停下來細細咀嚼每一個字背後的深意。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篇關於“閑適”的篇章,他沒有高談闊論什麼人生哲學,隻是娓娓道來自己如何在一間小小的書齋裏,伴著貓兒和舊書度過一個下午。那種對日常細節的捕捉和對生活詩意的營造,簡直是神來之筆。讀著讀著,我常常會不自覺地聯想到魯迅先生筆下那些疾呼呐喊的形象,再看周先生這邊的從容不迫,便更覺齣兩位大傢在精神氣質上的巨大分野,而這種分野,恰恰構成瞭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群像的豐富性。這本書,與其說是文字的堆砌,不如說是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一個復雜而真實的舊日文人內心世界的一隅。
评分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评分送货速度快,好!价格便宜
评分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评分已经全部收齐了,和沈从文别集一样.
评分止庵编印周作人作品琐谈 《周作人自编文集》凡36种,35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24开本。浅灰的封面设有墨笔茶壶瓶梅等,干净雅致。封面使用英国刚古纸,手感良佳。将作者所编集子重新出版,本是钟叔河先生在80年代做了一半的事情,时隔十余年后,由止庵完成。此外可备一述者,一是此套丛书于2001年出第一版时,其中《木片集》和《老虎桥杂诗》皆为第一次付梓。《木片集》是周作人生前已编好的集子,选录50年代所写随笔,1959年交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后转广州,再转回天津,至1963年,“得百花社寄还校稿,已两次付排而终不能出板”。《老虎桥杂诗》是周作人的旧体诗集,60年代初由谷林根据周氏借给孙伏园的原稿过录,比岳麓书社版《知堂杂诗抄》多30余首。二是《知堂回想录》当初由曹聚仁编辑交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时,错谬较多,此番则据保存下来的手稿校订,恢复原貌。《周作人自编文集》共印两次,第一刷时出版社校对略有疏漏;二刷由止庵重校,改正若干错字。而《老虎桥杂诗》则根据后来找到的作者原稿加以校订。“自编文集”第一刷与第二刷版本之别,即在于此。 《周作人自编文集》每册之前,止庵均写有短文,介绍作者创作流脉和版本情况。后止庵将这36篇文章及另外几篇谈论关于周氏著译的考证之作,编为《苦雨斋识小》出版,是一本别具特色的书话。 《周作人自编文集》出版后,止庵发现了周作人从未出版的《近代欧洲文学史》一书,计十万字。周氏已出版的《欧洲文学史》缺少19世纪部分,正好由《近代欧洲文学史》补足。这可视作近年周作人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止庵与戴大洪为此书写有18万字的注释,2007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周氏著作迄无注释,此举不无草创之功,颇便阅读。 止庵编《周氏兄弟合译文集》收《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共4册,新星出版社2006年出版。此处不妨再引止庵语以作叙述:“一九零六年夏秋之际,周作人随鲁迅赴日本;一九二三年七月,二人失和。其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他们更多呈现为一个整体,所谓‘周氏兄弟’是也。彼此有多方面的合作……其中荦荦大端,究属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周氏兄弟合译文集》所收《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就是具体成绩。”其中《红星逸史》已是百年前译作,难得一见。而《鲁迅译文集》只收鲁迅译作,《苦雨斋译丛》与正在编辑《周作人译文全集》只收周作人译作,惟此“合译文集”才真正是按原貌出版。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周作人的著译作品出版很多,参与其事者不少,若论真有贡献者,当推钟叔河、止庵与陈子善三人。概括而言,钟氏贡献在最早系列出版周氏作品,虽因故而未竟其功,一也。以“分类”和“编年”的方式,几乎出齐周氏散文之作,又一也。陈氏贡献在搜集整理周氏的大量集外文。止庵贡献则如前所述,一,首次出版《希腊神话》、《木片集》、《老虎桥杂诗》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止庵说:“我作为一个读者偶尔涉足出版,有机会印行几种从未面世的书,与其说感到荣幸,倒不如说少些担忧:我是经历过几十年前那场文化浩劫的人,眼见多少前人心血毁于一旦;现在印成铅字,虽然未必有多少人愿意看它,总归不至再因什么变故而失传了罢。”);二,根据原稿恢复了周氏多本译著约三百五十余万字,还其本来面目;三,首次完整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此三者为读书人之幸事。
评分一
评分书中所“抄”所谈之书都是中国古籍,其中又以笔记为多。作者自称这些文章意不在针砭,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摆列点药”,但行文处处透着“疾虚妄”“爱真实”的精神。以《女人三护》为例,文章从《茶香室三钞》中女人三护一条,谈及佛家三护与儒家三从之不同,进而深及到对佛道儒的讨论,可谓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点评式梳理。
评分非常超值的好书,装帧、纸质、印刷都不错
评分很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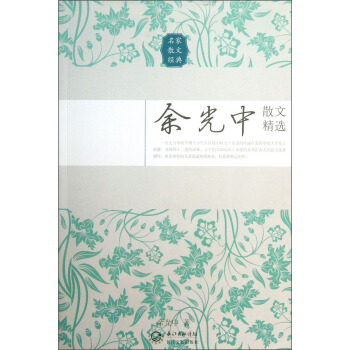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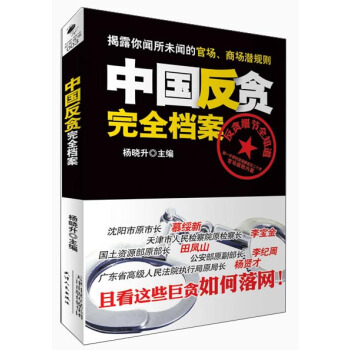
![小屁孩日记:我要上学啦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85525/53fc2b9aNf4a71264.jpg)
![经典故事轻松读-中国民间故事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43307/54d40c14Nb10b1b2f.jpg)

![邦臣小红花·幼儿国学启蒙经典:三字经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43552/55bacf87N9f47f836.jpg)
![科学幻想系列:虫虫打工记 [7~14岁青少年]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55961/55dc05d2Nec62dbab.jpg)
![绒兔子找耳朵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03788/564ebabbNa7a6947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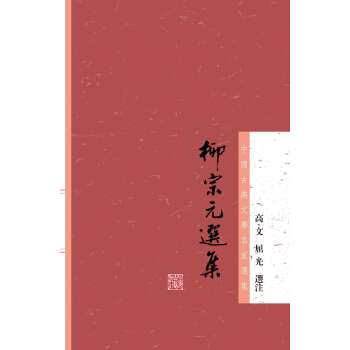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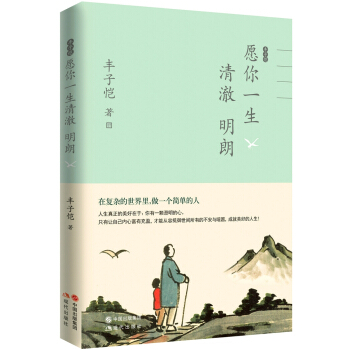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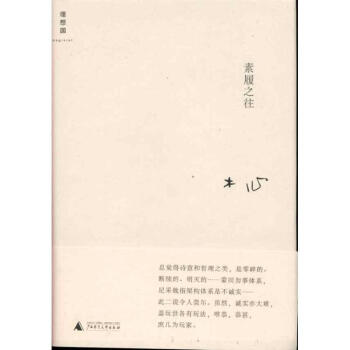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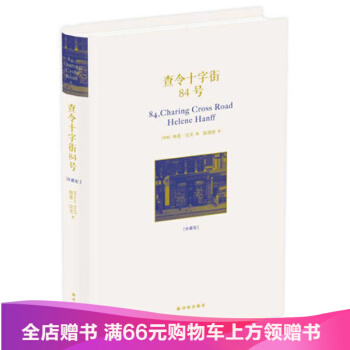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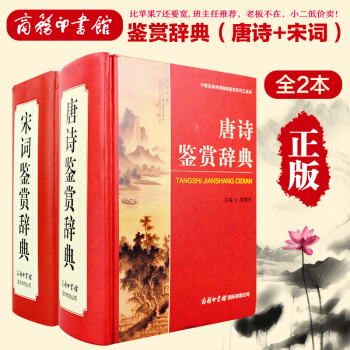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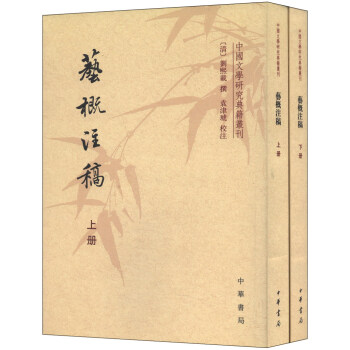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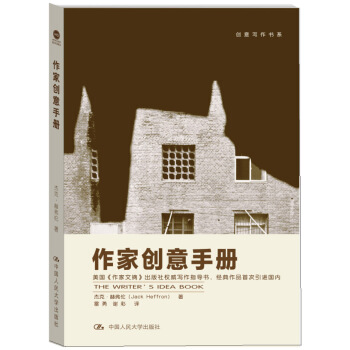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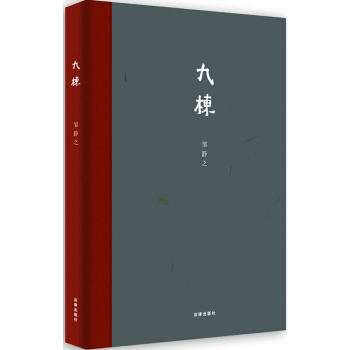
![世界名家手绘经典童话:匹诺曹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32173/55a8ab0aNcc618ac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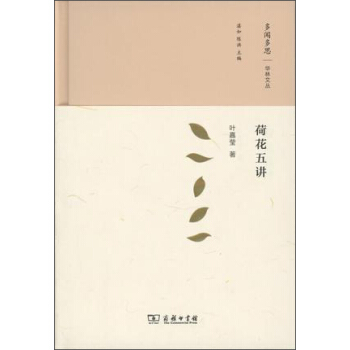
![艰难时代 [Hard Times: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07375/58467d8bN2435a87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