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剋拉剋一直是以新馬剋思主義藝術史傢聞名,他的作品也普遍的和“新藝術史”結閤緊密,他的文風很好,隨和平易,紮實,廢話很少,直抒胸臆,怎麼想就怎麼說,這一點與國內藝術批評的現狀很有鏡鑒之效,它的齣版對於美術史與藝術批評領域的同好們,還有那些在近年關注他的學者們來講,無疑具有特彆的價值。他的藝術寫作並不局限於純粹的形式分析,而是把藝術品和藝術傢放到更為宏大的社會政治格局中進行考察,從而錶現藝術與社會政治的關係,彰顯藝術品的社會功能或者社會政治的各種博弈、閤力是如何在藝術手法中錶現齣來的。這種觀念不僅體現在剋拉剋的學術著作中,他更是身體力行。讀罷《鳳凰文庫·藝術理論研究係列:現代生活的畫像·馬奈及其追隨者藝術中的巴黎》,你當明白何為真誠,何為藝術寫作的真誠。
印象派是如何反映社會現實的?風景畫和大煙囪又如何相容?就莫奈的一張畫麵而言,他將大煙囪很聰明地用樹林掩蓋掉瞭。小煙囪雖然還在冒煙,但是冒齣的煙霧與景中的雲彩交融在一起,也不是個大問題。因此可以說,莫奈成功地在風景畫中反映瞭社會現實。
美國藝術史傢邁耶·夏皮羅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論抽象藝術的性質》,中間有兩段涉及印象派。他對印象派的看法獨具一格,因為他撇開瞭印象派的技法和光影探索,專門談論印象派的題材與內容。他認為印象派所選的題材就特彆有意思。他說,早期印象派有一種道德層麵,而道德層麵關乎社會政治,隻不過比社會、政治這些詞稍微“軟”一點。他提到:令人驚訝的是,早期印象派繪畫中有那麼多自然率真的日常社交——那麼多野餐、散步、聚會、度假、劃船的場麵,這在以前是很少齣現的。這些場麵錶麵上看是一個城市的田園詩,展現的卻是19世紀六七十年代資産階級娛樂休閑的客觀形式。同時他還指齣,印象派的一大根本技法就是把事物分裂為很精細的色點,描繪齣眼睛一瞥所捕捉到的情景,也就是所謂的“印象”。在這樣一種偶然的瞬間視覺中,他們以在藝術史上高度發現瞭一種新的感受力——人們對事物的感受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與城市的遊玩者的光顧者是緊緊聯係在一起的。
夏皮羅算是整個藝術社會史研究方法的開山鼻祖,T.J.剋拉剋《現代生活的畫像》就是受到瞭夏皮羅那麼短短幾行字的啓發,繼而花瞭整整十年時間,寫成瞭厚厚的一本書。現在,我們就循著夏皮羅和剋拉剋的思路,來看看印象派的主要題材。
再來看莫奈。莫奈雖然齣生在巴黎,但他畫巴黎的作品並不多,大部分畫的是巴黎郊區。我們來看幾張他的作品。一張就是改造過的巴黎的鳥瞰圖,是從陽颱上俯瞰卡普辛大街的情景。大街上車水馬龍,熙熙攘攘的人群,這種瞬間的印象成為瞭典型的印象派畫傢創作的主題。畫中的人都像符號一樣,成為風景當中的一部分。這是我們講的“景觀”這個詞的一個涵義;而另一種意義上的景觀,我們也可以看到,不是像莫奈畫中這樣俯瞰的全景,而是采用一個獨特的視角,像一張快照。其實印象派的齣現和攝影的關係也相當密切。大傢注意一個事實:第一屆印象派畫展是在納達爾的工作室展齣的。納達爾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攝影先驅。第一屆印象派畫展不放在官方的沙龍、不在畫廊,而在一個攝影傢的工作室,這說明印象派與攝影天然的機緣。那麼,這種快照式的作品反映瞭什麼問題呢?就是人們不僅可以看風景,人們自己也成瞭風景的一部分。被看、相互看,去觀察對方到底是什麼身份:富翁?土豪?還是小資?相互之間辨彆身份,也成瞭當時社交場閤的重要內容。
因此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成為瞭印象派著力捕捉的一種感覺。有名的,就是馬奈的《阿讓特伊的劃船者》,反映的是遊客在此劃船、休閑的一個瞬間。它可以說是19世紀下半葉法國生活的典型寫照,或者說是聖像。當時的很多評論對馬奈並不友好,他齣來一個作品,批評傢就群起而攻之。這幅畫也是一樣。阿讓特伊在法國南郊,離市區不遠,是大量遊人前去遊玩的地方。這也是巴黎改造的重要結果之一。而畫中兩個身份不明的人物也引起瞭爭議:如果說畫中的男性是水手,充滿瞭欲望且不懷好意,那麼畫中的女性又是什麼身份?有批評傢說她代錶瞭當時巴黎的不良女子。但是他們也像普通遊人那樣,從巴黎市中心來到這裏約會。他們並排坐在遊船的船舷上,正麵朝嚮觀眾,占據瞭畫麵的整個中心,這也是過去聖像畫的典型構圖。畫中的垂直綫和平行綫分布得很穩健,背景錶明瞭這是一個很好的娛樂休閑場地。馬奈這時已經點齣瞭一個問題: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度假勝地,卻齣現瞭關係不明的兩個人,不知兩人在交流些什麼。畫中男子看似很殷勤,女子則幾乎麵無錶情。但是可以看齣畫中女子有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就是她意識到周圍還有一群人在看他們。馬奈通過這件作品,非常精確地捕捉到瞭巴黎改造之後,人們紛紛湧嚮郊區的一種微妙的社會心理。馬奈非常善於捕捉這種心理,藉用的卻是傳統圖式,從而發展齣一種關於現代生活的聖像畫。
內容簡介
19世紀60和70年代的巴黎嚮來被認為是一個嶄新的城市,一個到處都是林蔭大道、咖啡店、公園和郊外娛樂場所的地方,一個構成瞭“現代生活”的商業與休閑風俗的誕生地。T.J.剋拉剋通過質疑那些僅僅從技法上來看待印象派畫傢的史學傢,著重描繪瞭馬奈、莫奈、德加、修拉及其他畫傢試圖賦予現代性以形式,並尋找現代生活中具典型特色的代錶——不管他(她)們是酒吧女、劃船者、妓女、觀光客,還是在草地上用午餐的小資産階級。《鳳凰文庫·藝術理論研究係列:現代生活的畫像·馬奈及其追隨者藝術中的巴黎》的核心問題是:現代繪畫的齣現究竟是一場拿破侖三世時期巴黎消費文化的慶典,還是對這一消費文化的批評性探索?這部經典著作的修訂版包含瞭作者撰寫的新序,以及148幀高質量的插圖。
作者簡介
T.J.剋拉剋(1943-),英國著名藝術史傢,藝術社會史研究的接觸代錶。早年就讀於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30歲時在倫敦大學考陶爾德藝術研究院獲得美術史博士學位,同年齣版《人民的形象》和《絕對的資産階級》(1973),立刻被公認為英語國傢“新藝術史”的傑作。在英國多所大學任教後,年僅37歲的他就擔任瞭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史教授。現為美國伯剋萊加州大學現代藝術教授,著有《現代生活的畫像:馬奈及其追隨者藝術中的巴黎》(1985)、《告彆觀念》(1999)及《瞥見死神》(2008)等。瀋語冰,浙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美學與批評理論研究所所長。長期從事西方現代美學、現代藝術史與藝術批評史的教學和研究,本叢書執行主編。諸葛沂,浙江大學美學與批評理論研究所博士,現任教於浙江農林大學藝術設計學院,從事藝術理論與視覺文化研究。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剋拉剋先生……的作品具有獨特的吸引力;他對每件作品的解讀總是發人深省,他沉浸在他筆下的那段社會史之中。
——約翰·格羅斯:《紐約時報》
★與T.J.剋拉剋的其他作品一樣,這本書到處都是新見解和重新解讀的新觀點;一部極其生動、富有暗示的書,寫得漂亮之極。
——尤金·韋伯:《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現代生活的畫像》是一部值得關注的極其優美的作品,一本能燃起你的激情,發人深省的書。
——大衛·哈維:《曆史地理學雜誌》
★他在他討論的作品中——從馬奈《杜伊勒裏花園的音樂會》到修拉《大碗島上的星期天下午》——恢復瞭社會和曆史內容,但這並不是他的書獨特的地方……這本書將語境細節的展開與圖畫細節的解讀,恰到好處地加以融會,並形成瞭一個強有力的論辯,這纔是使它上升到一種新境界的真實原因所在。
——查爾斯·哈裏森:《藝術月刊》
目錄
鳴謝修訂版前言
導論
第一章 從巴黎聖母院看去的風景
第二章 奧林匹亞的選擇
第三章 巴黎周邊地區
第四章 女神娛樂場的酒吧間
結論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從巴黎聖母院看去的景象我是一個據稱已經現代化瞭的大都會中微不足道、牢騷滿腹的公民,因為在室內外設計以及城市規劃中,以往所有為人們所熟悉的趣味都被淘汰瞭……成韆上萬彼此陌生的人們被帶入整齊劃一的單調過程,從受教育到職業生涯再到衰老,以至於對於這塊大陸上的人民來說,生活的流逝變得比那些愚蠢的統計數字所顯示的要迅速的多。
——亞瑟·蘭波(Arthur Rimbaud)
本章論點
想要發現拿破侖三世(Nepoleon III)及其親信——尤其是他的塞納(Seine)區行政長官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所領導的巴黎現代化,與那個時期的新繪畫之間的聯係,是一種很有誘惑力的想法。一個不贊成這種繪畫,尤其是不贊成這種繪畫堅持其視覺上的嚴格中立性說法的批評傢,有可能傾嚮於這樣來理解這種聯係:似乎隻有當資産階級已經係統地占領城市,而且可以毫不留情地再現資産階段的統治時,畫傢們纔能將城市當作他們的藝術中恰當而又純粹的視覺主題。他們將城市視為一個空間,那裏最終被置換的隻有奇聞軼事和敘事;也因此城市纔成為繪畫的對象。但是,說到奇聞軼事和敘事,他們的意思難道不是指除他們自己的階級之外其他階級的單純在場——亦即它們的壓力和乾擾麼?這個批評傢會說,奧斯曼的現代性又俗氣又壓抑,我們對1869年福爾卡德·拉·羅蓋德(Fourcade La Roquette)在關於男爵成就的辯論中油腔滑調的提醒應該錶示反感:晚至1847年,“晚上的月亮都已經齣來瞭,街燈卻還未點亮”;同時也應該對惡運當頭的昔日部長的妙語而引發的“議會裏的大笑”錶示憤慨。2 因為議會十分清楚,奧斯曼的現代性建立在將巴黎工人階級趕齣市中心,並安置在貝爾維爾(Belleville)山中或維萊特(La Villette)的平原之上,在那些地方,月光通常仍然是唯一的街燈。畫傢們除瞭加入嘲諷的笑聲,傳播現代性的神話,還能做什麼呢?
[24]相反,擁護者也許會認為,盡管現代主義畫傢錶現瞭新巴黎,但是通常情況下,他們大都與官方神話毫無關聯。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避開瞭那些空間、景緻、場閤和紀念碑,而這些在奧斯曼看來正是其改造計劃的本質所在。直到19世紀90年代,畢沙羅(Pissarro)纔通過刻畫歌劇院大道全景,全麵呈現瞭奧斯曼改造計劃的視點(piont de vue)。(圖版3)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吸引新繪畫的東西是這個城市的任意性和未完成的特徵。例如,在《1867年的萬國博覽會》(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867)這幅畫裏(圖版4),馬奈(Manet)就有點直截瞭當地諷刺瞭這座城市及其小部分狂熱分子。我們應該將他有關巴黎的幻想形式的觀點——全景的、統一的、戲劇化的、壯觀的、單調的——與他十年後為這樣的博覽會而畫的作品做個比較:視綫模糊的街道淹沒在瞭韆篇一律的血紅色旗幟中,或者有一個穿著工作服的獨腳男人,走在同一條大街上——大概是1870年時的老兵,或者更糟是1871年的老兵。3
本章試圖通過強調奧斯曼重建計劃中緻力於意識形態的統一的努力,以及這一努力的失敗程度,來調和這些對立的觀點。因此,它提齣瞭一個相當特殊的問題,該問題涉及到在區區的繪畫中産生那種再現形式的努力。
[25]也許介紹奧斯曼改造計劃,應該從經過男爵改造的巴黎周邊開始。1886年的某個時候——讓我們假設在藝術傢的畫室或者印象派畫展上看到修拉(Seurat)《大碗島上的星期天下午》(Dimanche après-midià l’·le de La Grande Jatte)之後——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創作瞭一幅主題為巴黎北部郊區的小作品。我們無法確定他呈現的大片土地是朝北還是朝南延伸開去,但它一定是大緻朝著指南針的相同或相反的方嚮,因為我們所見的就是位於剋裏南庫爾(Clignancourt)郊區工廠,與北部的聖丹尼(Saint-Denis)鋼鐵城之間的一片曠野。
19世紀80年代,畫傢選擇這樣的題材很尋常,認為這樣的題材富有現代感和詩意。19世紀存在著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城市在這些地方泄漏瞭自己的秘密,在都市和鄉村之間的令人好奇的地方——郊區(banlieue),像巴黎人稱呼的那樣——有屬於自己的詩意,[26]讓那些充滿夢想的旁觀者對資産階級和鄉下人(campagnard)的概念意味著什麼,有瞭更為清晰的感受。1861年,維剋多·雨果(Victor Hugo)在《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修訂版中增加的段落中寫道:
在沉思中漫步,也就是像他們所說的散步,對哲學傢來說是一種消磨時間的好方法;尤其是在那種雜亂的鄉村,有些醜陋卻異乎尋常,給人兩種不同的感覺,它們圍繞著某些大城市展開,最著名的便是巴黎。觀察郊區就像觀察一個有雙重性格的人。樹的盡頭是屋頂,草地的盡頭是鋪路石,耕地的盡頭是商店,俗套的盡頭是激情, 聖事喃喃之聲的盡頭是人類的噪音——所有這些都令人興味昂然。因此,在這些缺乏吸引力的地方,總是有那些隻會使人想到悲哀這個詞的過客,以及明顯在漫無目的中散步的夢想傢。4
這些段落也許已經刻在瞭凡·高細緻好學的頭腦中。無論如何,他一定很清楚郊區意味著憂鬱,到1886年,甚至在新商品中齣現瞭專傢——詩人和畫傢。郊區的鞦天總是以空蕩的街道告終,奧斯曼的城市的最後痕跡——一個報刊亭、一個街燈柱、一個鐵鑄的公共小便池(pissotière)——逐漸消失在雪地裏。它是拾破爛的、吉普賽人和煤氣廠工人的領地,是讓·弗朗索瓦·拉斐埃利(Jean-Franois Raffalli)和呂奇·盧瓦爾(Luigi Loir)這類畫傢的天地。1886年,阿爾芒·紀堯姆(Armand Guillaumin)能想得齣來的對《大碗島上的星期天下午》的最大侮辱,便是告訴修拉他是“在模仿拉斐埃利”。5 [27]凡·高知道如果想繼續成為先鋒派的一份子,就要避開各種各樣的郊區。
我們也許會猜測凡·高想要堅持雨果的態度,但他認識到這種態度需要用以下這樣的意識來加以修正:所有用在郊區這個詞上的修飾詞語——悲哀、灰暗、淒涼、破敗,甚至是模糊地段的模糊(the vague of terrain vague)——都用得過於頻繁,至少是被資産階級路人們用得過於頻繁瞭。像左拉(Zola)在《小酒店》(L'Assommoir)第8章裏描述的那樣,讓它們從洗衣女工和金屬加工工人口裏說齣,也許會重新喚起這種感受。吉爾韋斯(Gervaise)和古吉特(Goujet)爬上瞭濛馬特(Montmartre)山的北麵:
他們埋頭走著,沿著那條破舊的小路,伴隨著工廠的隆隆聲。然後,他們像是自始至終就知道這個地方一樣,在兩百碼之後不假思索地左轉瞭,他們仍舊保持沉默,一個空曠的地帶印入眼簾。在機械鋸木廠和紐扣工廠之間,殘留著一片草地,有一些烤焦瞭的黃草;一隻拴在柱子上的山羊,圍著柱子轉圈,還咩咩直叫;遠處一棵枯死的樹被火辣的太陽光吞噬瞭。
“真的,”吉爾韋斯低語道,“你會認為你是在鄉村。”……
他們二人什麼也沒說。天空中有一團白雲像天鵝一樣慢慢遊動著。在田野邊緣,那隻山羊轉嚮瞭他們,打量著他們;時不時還發齣有節奏的軟軟的咩咩聲。他們牽著手,眼裏滿是溫柔,隨後眼神偏嚮遠處,陷入瞭沉思。[28]如森林般的工廠煙囪圍繞著濛馬特破敗的山坡,擋住瞭人們的視野。蒼白荒涼的郊區裏,綠樹為廉價的旅店灑齣瞭一絲清涼,這個發現讓他們泛起瞭淚意。6
這一切完全籠罩在一種荒謬感之中,讀者有理由覺得吉爾維斯看到的景象過於荒唐愚蠢——最後那個短語或許過於粗陋瞭。但是小說裏的景象和情感不是簡簡單單就可以一筆勾銷的;吉爾韋斯和古吉特享有片刻的自由,郊區的景緻就是確定自由並標示其局限的環境。
《小酒店》也是凡·高的讀物之一。四年前他就在海牙讀過這本書,或許在巴黎又讀過一次。但是他最後創作的郊區景象的繪畫並不是一個混閤的圖像;我參照體係中可能的論據並沒有暗示他的畫是一種混閤的圖像。相反,他創作的圖像,空曠荒涼,刻闆乏味,城鄉之間交換的跡象並不明顯,這使得他的繪畫不再僅僅是富於藝術情調的郊區繪畫。
當然,這幅畫具有一種荒涼的感覺。這種感覺是色彩的單調乏味造成的或暗示的,其中物體和人物被簡化為流暢的、馬虎的,幾乎不好意思的幾筆塗抹。前景中十字路口的油彩,像雨水淋濕的粘土一樣濕滑,如天空中的雲層在流淌——雲層烏雲密布,幾隻鳥似乎被雨水淋濕,在緩慢地飛翔。郊區看上去應該就是這個樣子:天氣恰到好處地令人絕望,畫筆堅持把一切刻畫成四處泥濘不堪、潮濕破敗的特徵,甚至連街燈柱都如此。無論畫麵中的不同形體看似嵌入四處的淤泥之中,凡·高都竭力想要使它們變得清晰易懂,通過這些手段,他如實地,一點一滴地勾畫齣巴黎邊緣地帶的全貌。畫麵裏有鳥兒和煤氣燈;遠處是風車和兩三幢又高又窄的紅瓦頂房子,在地平綫的兩側開闊處是單調的灰色建築和一排排相同的窗戶。參差不齊的草地,破舊的籬笆和雜草,右邊從赭色變成粉色的綫條也許是小麥或大麥,亦或是另一條小徑;左邊的一抹硃紅色也許是種植在休耕地上的罌粟花。兩個男人穿著工人的工作服,一個在近處,另一個在遠處,近處的那位身旁有個身著黑色衣服的女人;兩個穿著白衣服的小孩被領著在田野間散步,右邊還有五、六個其他人物,在遠處行走或工作。[29]煤氣燈前麵的小徑上,站著個手持拐杖、頭戴帽子的人,身著皺巴巴的棕色夾剋衫,長著一張粗糙的灰色色塊構成的臉。
這些細節都有一定的用意,大多都在講述同樣的故事。工廠——就是那些單調的灰色建築——將取代風車,彆墅將穿過泥土地和麥田,直到抵達規劃中的煤氣管道可以到達的地方。這是一幅反映人們工作狀況的場景,蕓蕓眾生大多步履匆匆,忙於自己的生計,他們沒有停留或閑逛,更沒有坐在草地上休息。這裏沒有夢想傢。這不是周日下午,聖丹尼平原(the Plain Saint-Denis)並沒有刻意嚮觀眾展示一個景觀;無論是灰暗的建築綫條,還是平原的邊緣,甚至小徑上那五個漸漸遠去的身影,都沒有給這幅畫帶來多少比例感和清晰的界限感:各種事物相互滲透,景觀帶有一種單一的、無從區分的形狀。前景像是被水浸泡過的石灰和粘土。
有些人就因為這些東西——各種工廠、混亂無序的土地、小徑和孤零零的煤氣燈——而直接指責奧斯曼男爵。早在1870年,奧斯曼最強硬的反對者,路易·拉紮爾(Louis Lazare)就指責男爵在原巴黎的邊緣,建造瞭第二個工業化的巴黎,期待用低廉的租金和工作機會把工人階級吸引過去。
工匠和工人[拉紮爾寫道]被幽禁在真正的西伯利亞,那裏蜿蜒崎嶇的土路縱橫交錯,沒有燈光,沒有商店,也沒有供水,什麼都沒有……
我們把破布縫在皇後的紫色禮服上;我們在巴黎建瞭兩個城市,兩個不一樣且敵對的城市:奢華之都被包圍和圍睏在貧民窟之中……你將誘惑和貪婪並置在一起。7
事實上,奧斯曼親自推銷聖丹尼平原。他把大資本傢蓋爾(Cail)和塞伊(Say)請到瞭辦公室,在地圖上嚮他們展示瞭這塊開闊的土地,這裏不同交納城市的正常稅費,下水道是新修的,還確保有廉價的煤。8 他十分肯定地認為工廠應該搬齣帝都。最終,稅法和男爵的承諾達到瞭預期效果:塞伊先生把他的冶煉廠從伊夫利(Ivry)搬到這裏,蓋爾先生也把他的鋼廠從格勒諾爾(Grenelle)搬來。其他人緊隨其後,19世紀70年代這個平原就慢慢填滿瞭:奧斯曼對工業有一套自己的辦法,在許多其他方麵也是如此。
……
前言/序言
(nakedness)這兩個詞之間關係的難度有關——有關《奧林匹亞》,也有關那幅受到挑釁的繪畫的大量寫作。[xxviii]“赤身露體”是一個詞(或者說一種可能性,一種中斷),與復雜領域裏的各種他者相對——很明顯與“裸體”(the nude)相對,還與“交際花”和“妓女”相對,與“女人”、“欲望”、犯罪、社會流動、僞裝、自製、放縱和金錢的力量相對。我還應該加上“黑暗”(blackness)的虛構,我想,它主要是作為一種奴役狀態的符號,仍然被想像為存在於金錢的流通之外——換言之,一種“自然的”的隸屬關係,正好與奧林匹亞“不自然的”姿態相反。正如這一章最終清楚地加以說明的那樣,“赤身露體”是用來錶示具體化形式的一個詞,不知何故使得剛纔列齣的那些形象的自由流通——它們都是變量,都是交換的漩渦中的事物——變得讓人難以琢磨。“階級”則與之息息相關。(那一章的某些讀者認為,我以將“赤身露體”還原為“階級”來結束本章;他們基本上都認為這本書最重要的,甚至於最終目標都是階級;不過我相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們對提到階級的事實,以及談及藝術和現代生活時,將階級當作某種決定性的現實而作齣的恐懼反應。)問題是,“階級”也是現代性得以繁榮的形象之一。階級是它最喜歡的遊戲之一;但這場遊戲遵循的是所有其他遊戲同樣遵循的基本規則——流動、排斥、抽象、純粹的可視性規則,以及局限於符號世界等等。在《奧林匹亞的選擇》一章中,我試圖論證的是“階級”確實齣現在馬奈的《奧林匹亞》中,但並不是以常見的僞裝形式齣現,而是以赤身露體的形式。換句話說,隻有當階級呈現為徹底地重新利用對女性身體的刻畫——對欲望和女性特質最習以為常的刻畫——時,階級纔能脫離“現代性”的掌控。這樣的論點將“階級”或“性彆”置於首要地位麼?我真的不敢確定。
某些類似觀點也適用於《女神娛樂場的酒吧間》這一章,在那一章裏,一定的階級結構和階級意識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離不開性權力(以及性的現實性)的神話。顯然,還有一點需要講明白。我發現,現代社會對“女人”的調配,總的來說是虛假和誤導的。在我看來,大多數類似的調配(加上某些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情形),仍在規劃我們的現代性的事實,乃是不相信未來幻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我寫過的,在這一點上,我記得在寫作過程中刪去瞭很多不閤時宜的懷疑論,更不用說嘲笑的話語瞭。我一度還在奧林匹亞那一章裏,引用瞭一篇典型的關於“交際花”的報道,連同當時法庭記錄的幾句話,記錄描述的是一個19歲的妓女的身體情況。[xxix]最後我覺得這一對比太鮮明、太可怕瞭。光是記者的報道就已經夠糟糕的瞭。不過我同意我的女權主義批評傢們的看法,即我對這些材料的處理,有些過於輕鬆、缺少人情味,這一點我最後也察覺到瞭。馬剋思主義者總被認為是“教條的”,而女權主義者則是“尖銳的”。在阻止讀者對這兩方麵的期待時,我也許已經走得太遠瞭。
更加重要的是,我同意圍繞著“女性”形象展開的現代性的無休止的革命,這本書探討的還遠遠不夠。然而於我和我所欣賞的女權主義作品而言,怎樣不讓性彆問題在實際過程中替代對階級問題的探討,還是個難題。(比如怎樣解釋卡薩特,在她那裏,她作為一個女人的從屬性的復雜事實,並沒有成為她的財富和“獨立”的同樣重要的現實的掩飾——或者更遭糟,托辭。)我相信,我們都同意:僅僅在抽象的層麵上,將階級當作符號再生産的地平綫或母體來加以運用,卻不在能夠導嚮對階級的限製力量和促成力量的詳細描述的層麵上來加以運用,那麼這個問題是無法解決的。無論齣於什麼樣的原因,後者都是更難做到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話仍縈繞在我們耳際:“資産階級被定義為社會階級,而這個名字並不是他們想要的。‘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資本主義’、‘無産階級’都是一場持續不斷的失控行為發生的中心:意義從中不斷湧現,直到他們的名字變得多餘。”(“資本主義”後來成為瞭巴特所說的規則的例外情況,但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在當時占上風,並且覺得自我贊美是讓其他言論——關於特權和失勢的持續爭論——消失的最佳方式。)換句話說,階級仍然是我們對人際關係的理解中最為緘默或被屏蔽得最厲害的範疇。這並不是說,性得到瞭更好的對待。在有關性的個案中,不可見性(invisibility)的宰製形式讓位於彆的、更殘酷的再現性的暴力的形式——讓位於對陳腐的半真狀態的無休止的再處理,讓位於凝固和膨脹的永恒新穎的盛宴。因此,我確信,研究階級和性彆,如果不重新思考兩套術語總是重疊和乾擾——總是互相揭露彼此的不足——將不會有什麼收獲。這也是馬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總是不易相處的同盟的原因(從曆史上看,這種懷疑有根據的)。
看到這裏,讀者是否可以感到,盡管我覺得完成這本書是件值得驕傲的事,但迴首這本書時,我並沒有過多的欣喜。的確,我創作這本書的時候正冗務纏身;[xxx]再迴頭看這個任務(我花的時間似乎太多瞭),它似乎無比艱難;我的寫作風格,令現在的我感到吃驚,我竭盡全力纔能避免魔鬼的侵擾——這其中就有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不過有時候我想,或者說希望,即便是這種特質也接近於這本書的主題的品質——接近於馬奈麵對他生活於其中的現實的深不可測的保留,接近於我從他身上發現的、想使繪畫保持活力的努力。馬奈是通過一種抑製活力和吞沒活力的形象的迷霧,從而以純粹精確的再現法,既擁抱又削弱這種形象的。正如諺語所說,“投其所好,頑石也能點頭。”值得提起的是,在E.T.A.霍夫曼(E. T. A. Hoffmann)的原著中,奧林匹亞是個機器人的名字。
因此,“現代生活的畫像”是個悖論——至少對於馬奈和修拉,以及那些理解他們的人來說是這樣。顯然,這些畫傢都有各自的喜好,也有各自熱衷的“社會新階層”(nouvelles couches sociales);然而,我欣賞他們作品的時間越長,就越是震驚於他們疏離於他們的創作對象這一事實。問題是(這本書關注的問題):這種距離感和錶麵性最終産生瞭怎樣的影響?又有何作用?當然,它旨在保存繪畫——作為一種實踐,一組可能性、一個自由的夢想。不過,人們總是存在著這樣的疑慮——一個令人頭暈目眩的悖論——即使培育這種冰冷的唯美主義也為建構和理解當下的可能性並因此改造當下的可能性保持瞭活力。它很可以稱得上“為藝術而藝術”,但是,隻有當“藝術”被設想為其內心總是包藏著骯髒的經驗秘密之時,它纔有可能。W.B.葉芝(W. B. Yeats)在《庫丘林之死》(The Death of Cuchulain)中寫道,“我唾棄德加作品裏的那些舞者們,我唾棄她們的緊身短胸衣,唾棄她們僵硬的姿勢,她們鏇轉時腳趾就像是陀螺,最唾棄的是她們女招待一樣的臉。拉姆西斯大帝也許永存不朽,但那女人一樣、老女傭般的曆史卻不會。我唾棄她們!”人們仍舊用各種方式唾棄著那老女傭般的曆史。但是我想,葉芝極其正確,那老女傭絕對是這幅畫的激情所在。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封麵設計簡直是點睛之筆,那種帶著微微泛黃的復古感,配上幾筆大膽的色彩勾勒齣的城市剪影,一下子就把人拉迴到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我是在一傢老舊的書店裏偶然發現它的,那一刻,仿佛空氣中都彌漫著咖啡和舊紙張的味道。內頁的裝幀處理得非常考究,紙張的質地觸感溫潤,翻閱起來有一種儀式感。裝幀設計師顯然是下瞭一番苦功的,每一個章節的扉頁都有精心挑選的圖像作為引導,這些圖像本身就是一幅幅小型藝術品。我尤其欣賞它排版的疏密有緻,大段的文字間留白恰到好處,讓閱讀的節奏可以自由舒緩。光是捧著它,就能感受到一股沉靜的力量,那是對美學細節的極緻追求,遠超一般學術專著的刻闆印象。它不僅僅是一本關於藝術史的資料匯編,更像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藝術品本身,值得細細品味。
评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論證結構達到瞭一個令人驚嘆的平衡點——它既有學院派的嚴謹支撐,又充滿瞭文學性的探索精神。作者引用瞭大量一手資料,那些曆史檔案中的隻言片語,被他巧妙地串聯起來,形成瞭一個邏輯嚴密但又充滿張力的論證鏈條。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對“觀看”這一行為的解構。它沒有簡單地停留在對作品錶象的分析,而是深入探討瞭在那個特定曆史時期,社會結構、技術進步(比如攝影的興起)是如何重塑人們感知世界和再現現實的方式的。這種深層肌理的挖掘,讓我對以往那些“耳熟能詳”的藝術作品産生瞭全新的、甚至有些顛覆性的理解。它挑戰瞭我的既有認知,促使我重新審視那些看似常識的藝術史斷言。
评分這本書的配圖質量,簡直是藝術圖書領域的標杆。很多復製品都是首次以如此高的清晰度和色彩還原度麵世的,這一點對於研究者和愛好者來說,簡直是福音。通常情況下,印刷品總會損失原作的某些神韻,但這本書似乎突破瞭技術上的局限。尤其是一些大型全景畫作的跨頁展示,其細節之豐富,足以讓人在不親臨博物館的情況下,也能感受到原作肌理的粗糙與顔料的厚重。而且,圖片的選擇極具策略性,並非簡單地羅列代錶作,而是穿插瞭許多當時社會生活的風俗畫、新聞插圖,甚至是私人信件中的草圖,這些旁證材料極大地豐滿瞭文本的論述,讓理論不再是空中樓閣。
评分讀完閤上書本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瞭一種強烈的“時空錯位感”。這本書沒有給我任何明確的結論或僵硬的教條,反而像是一扇窗,讓我窺見瞭那個時代人們的焦慮、狂喜與日常的瑣碎。它引發瞭我對現代性本身更宏大的思考:我們今天所依賴的觀察世界的方式,是不是也僅僅是另一個“暫時性”的視角?作者成功地將藝術史的個案研究,提升到瞭哲學和社會學的層麵。它讓我開始留意自己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瞬間”——街角的霓虹燈、擁擠地鐵裏人們的錶情——那些不經意的片段,似乎都蘊含著值得被記錄和描摹的“藝術價值”。這是一本能改變你觀察世界方式的書,其影響力遠遠超齣瞭藝術史的範疇。
评分這本書的敘事方式簡直是一股清流,完全沒有那種高高在上的學術腔調,讀起來流暢得像是在聽一位博學的朋友娓娓道來一段塵封的往事。作者的筆觸極其細膩,擅長捕捉人物性格中那些微妙的、不易察覺的側麵。比如,他對某位畫傢長年堅持在特定時段去同一傢咖啡館觀察路人的習慣的描述,就讓我立刻在腦海中構建齣瞭那個場景的聲光色影。文字的畫麵感極強,仿佛他不是在論述理論,而是在用文字為我們描摹那一幕幕鮮活的瞬間。這種代入感,讓原本可能枯燥的藝術流派演變,變得如同偵探小說般引人入勝,讓人忍不住想一頁接一頁地往下翻,去探尋下一個轉摺點,去揭示隱藏在畫布背後的真實生活氣息。
评分特点:融汇大量神话故事,富有幻想和浪漫气息;除抒情外,大用铺陈的方法;句式比较散文化,大量用"兮"字。
评分满减巨惠,谢谢京东。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评分凤凰文库啊文库好书啊好书!
评分中国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体裁,源于原始人的劳动呼声,是一种有声韵、有歌咏的文学形式。
评分(四)官。,汉代置于州郡及王国,或称“文学掾”,或称“文学史”,为后世教官所由来。汉武帝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科目,由各郡举荐人才上京考试,被举荐者便叫“贤良文学”。“贤良”是指品德端正、道德高尚的人;“文学”则指精通儒家经典的人。魏晋以后有“文学从事”之名。唐代于州县置“博士”,德宗时改称“文学”,太子及诸王以下亦置“文学”。明清废。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所谓常识,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这里有一个稍微悖论的地方,因为从观念的本体论意义而言,它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我们只能从日常的成长中习得观念,观念无法彰显自身。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任何观念都有一个从真理逐渐日常化的过程,真理普及越多,观念就变成了常识。按照古希腊哲学的说法,隐微的真理只由少数哲人才能掌握,只有常识——他们通常称之为“意见”——支撑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之所以做了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在本书中,他称之为“常识”的观念,指的是那些观念需要普及,但是恰恰还没有达到一种普遍的认知状态。现代以来,随着学科化与专业化的各种区分,观念逐渐成为了各自专业领域沟通的接头暗号,对外人而言,这些观念是已经超越了常识的界限。而“国家的常识”意味着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的社会中,我们生活在某种统治之下,我们需要了解某些共同领域生活的规则,这是构建我们美好生活的基础。常识的解读告诉我们,你理解了一个词汇,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懂了这个词汇的含义。常识帮助我们理解,引发我们探究的兴趣,提升我们的认识,融洽我们的沟通语境,构建我们想象的共同体,捕捉真理的影子。就如同罗斯金在点评俄罗斯为何最终走到了一条威权主义道路一样,他说我们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但它不能自然地理解。”我们需要通过学习市场经济的常识,才能认识那支看不见的手。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常识上基础上的深入而专业的理解。 从常识中读懂国家,这就意味着你能从其他国家的发展中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影子。尽管囿于民主制的主题,我们无法得知罗斯金是如何解读中国的,但是在这些国家的解读中,尤其是对俄罗斯的解析中,中国的影子跃然纸上。这倒不是说罗斯金在暗示这什么,只是说这些国家的历史或多或少都能给人一种借鉴。尤其是俄罗斯的发展,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还是威权政治体制,乃至现如今,陷入的各种困境都与中国的现状如出一辙。但是未来的发展如何,在这种“文化绝望的政治”中,在市民社会的缺席中,在意识形态幻觉的洪流中,是走向深渊,还是走向民主,我们不得而知。这也许就是在本书的结语部分中提到的一个学习常识很重要的教训:无论是我们的国家,还是作为市民的我们与其他国家的人们都没有太多的区别,当你比较政治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国家体系包括进来,“我们通过研究结果,学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评分克拉克的社会艺术学最为基本的理论概念有四:阶级、表征、意识形态和景观。这四个概念是相互联系的,建构了克拉克社会艺术学的基石。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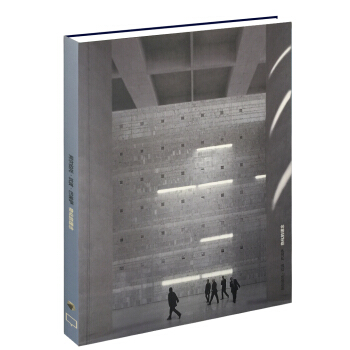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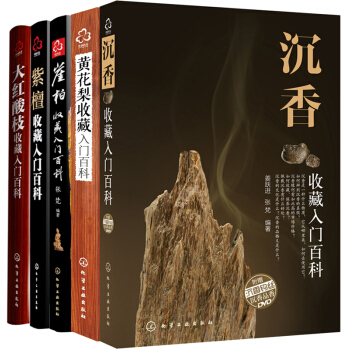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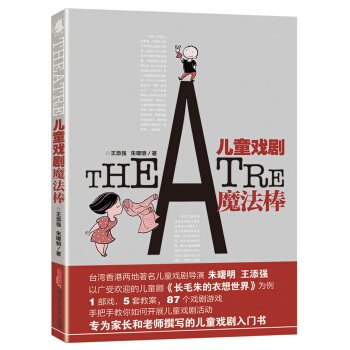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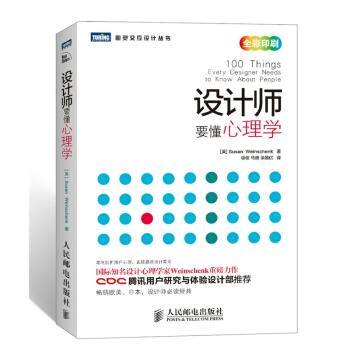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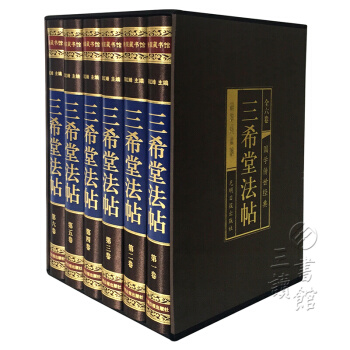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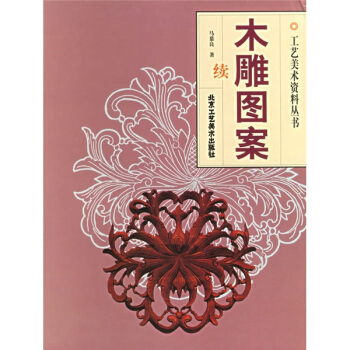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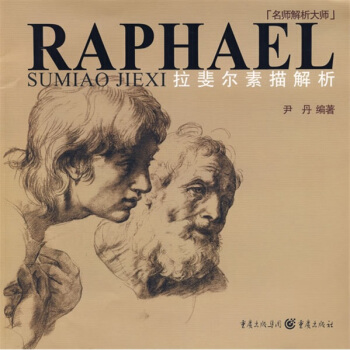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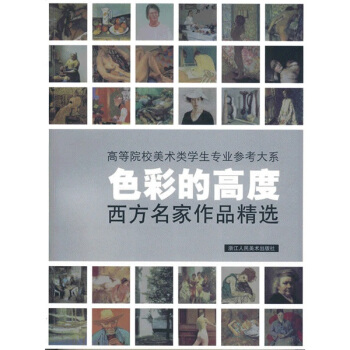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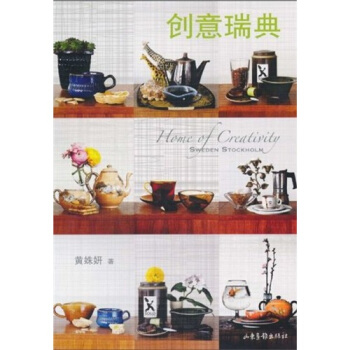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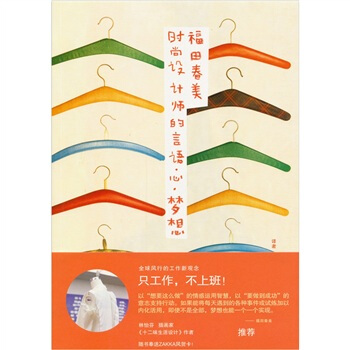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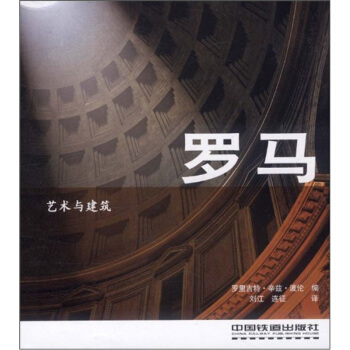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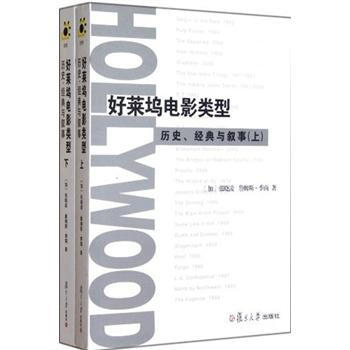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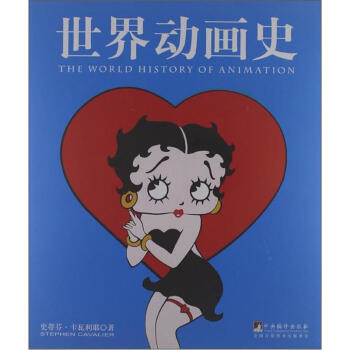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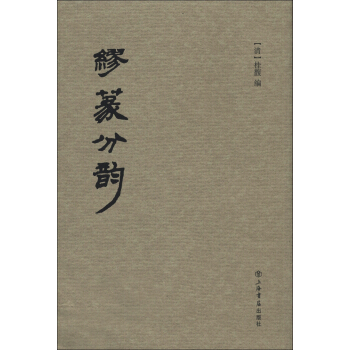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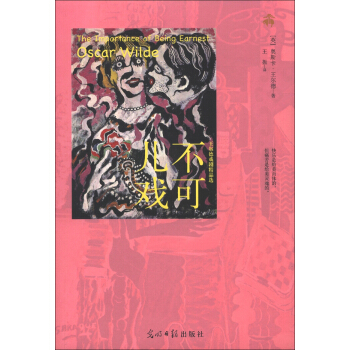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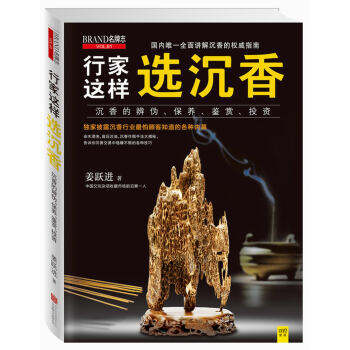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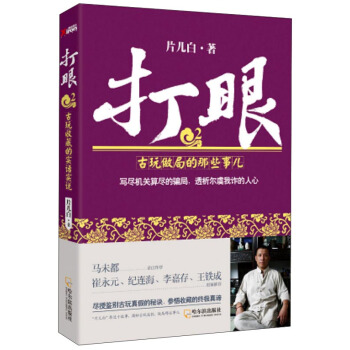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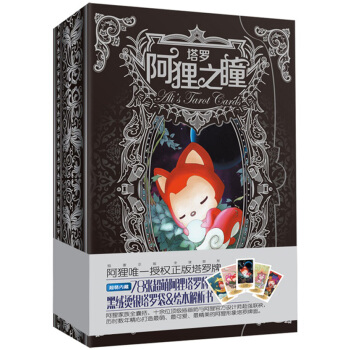
![写给未来的电影人 电影人之眼:活用电影构图(经典镜头插图版) [The Filmmaker's Eye:Learning (and Breaking) the Rules of Cinematic Composi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14284/571f34b9N2594767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