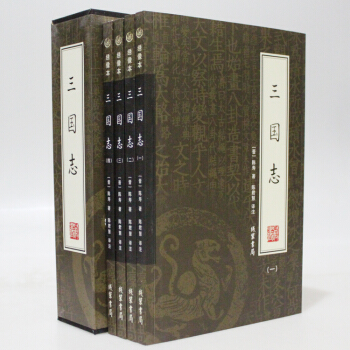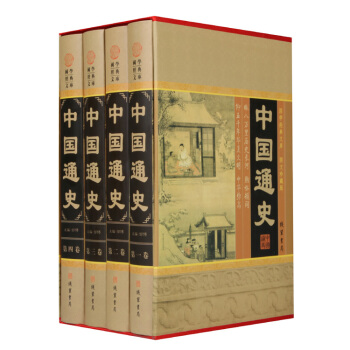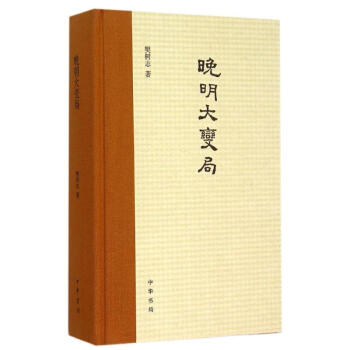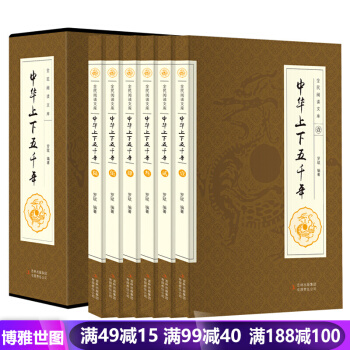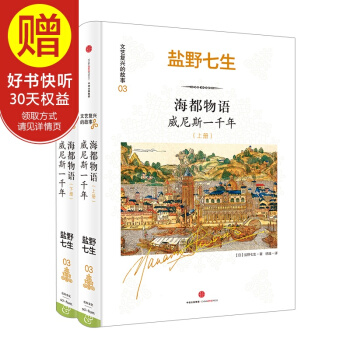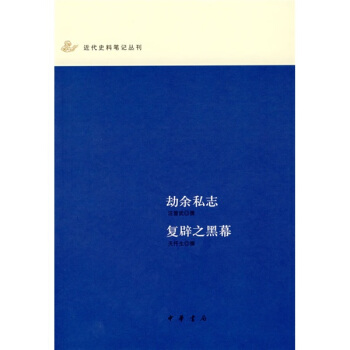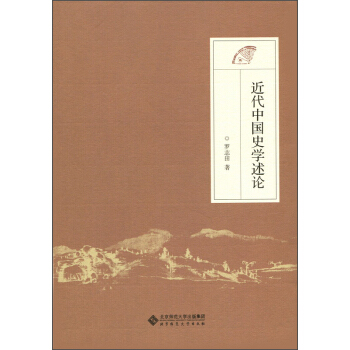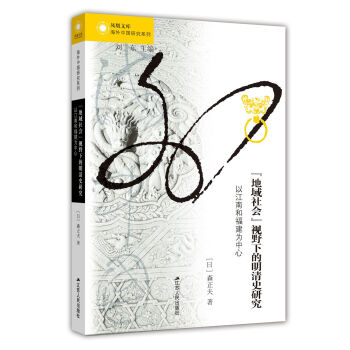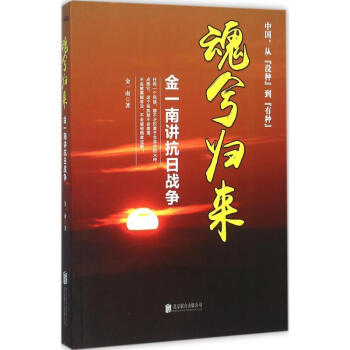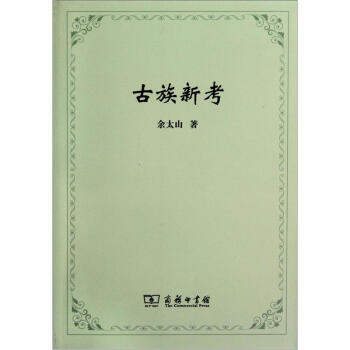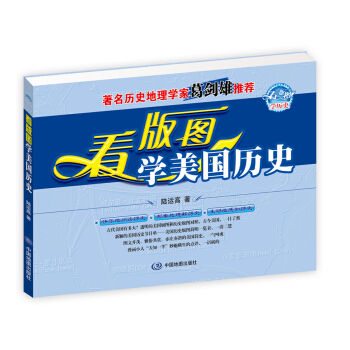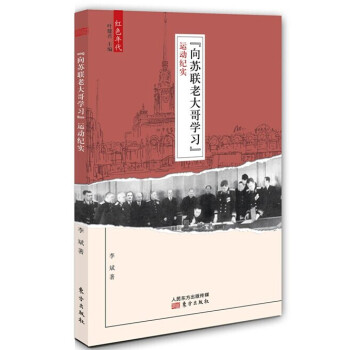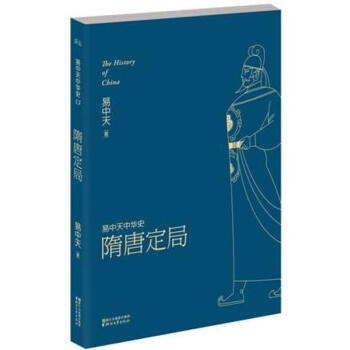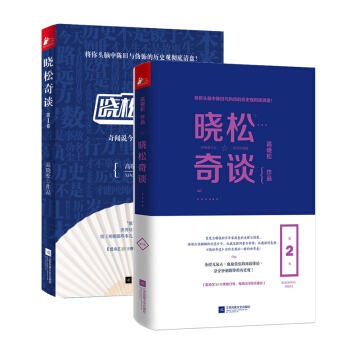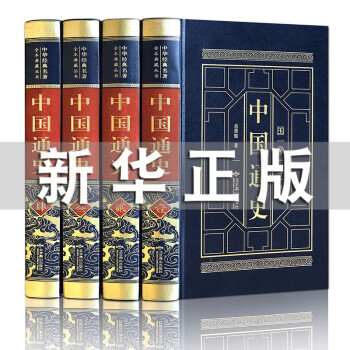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民國時代文人與狂士,不論桀驁不屈還是抱殘守缺,都一直張揚著獨立的個性,始終追求著特行的解放與自由。孫鬱長時間地在濁黃的紙捲中翻閱,不時進行平靜思考,終於對“在民國”的風流人物有瞭新的認識。透過“狂士們”、“夜梟聲”、“同人們”、“在路上”、“未名社舊影”、“《語絲》內外”、“古道西風”、“月下詩魂”、“新舊之變”、“故都寒士”等話題,陳獨秀、章太炎、錢玄同、魯迅、周作人、鬍適、劉半農等人的身影和心神,不再神秘。對於我們這個時代而言,前人們都是卓越不凡的,但,他們也是一個一個腳印走過來的。
作者簡介
孫鬱,本名孫毅,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曾做過知青、文化館館員、記者。80年代末在魯迅博物館研究室工作;90年代初調到《北京日報》文藝部做副刊編輯達十年之久;2002年到魯迅博物館主持工作至今,現為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20世紀7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80年代起轉入文學批評和研究,長期從事魯迅和現當代文學研究。《魯迅研究月刊》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副主編。主要著作有《魯迅與周作人》、《魯迅與鬍適》、《魯迅與陳獨秀》、《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張中行傳》等。
目錄
狂士們
夜梟聲
同人們
在路上
未名社舊影
《語絲》內外
古道西風
月下詩魂
新舊之變
故都寒士
在政治的邊緣
後記
精彩書摘
故都寒士
一
張中行辭世時97歲,算是高齡者。他晚年講起過去的生活,難忘的竟是鄉下的土炕和烤白薯。中國的鄉村社會可留念的東西不多,對他而言,僅是某種生活方式而已。但那種生活方式給他帶來的淳樸和智慧,又是書齋裏的文人所沒有的。土的和洋的,在他那裏交織得很好。算起來,他是晚清的人,早期生活還在舊王朝的影子裏。對於鄉下人來說,時光和時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流年碎影》講起他的齣身背景,有這樣一段話:
我是清朝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十六日醜時(午夜後一時至三時)生人,摺閤公曆就移後一年,成為1909年1月7日。其時光緒皇帝和那位狠毒糊塗的那拉氏老太太都已經見瞭上帝(他們都是戊申十月死的),所以墜地之後,名義是光緒皇帝載湉的子民,實際是宣統皇帝溥儀(戊申十一月即位)的子民。
由於他齣生在鄉下,早期記憶就多瞭一種鄉土的氣息。他一生沒有擺脫這些鄉土裏質樸的東西。關於傢鄉的環境,他有很好的記錄。在描繪那些歲時、人文的時候,他的心是很平靜的,既非歌詠也非厭棄,而是透著哲人的冷峻。比如鄉野間的人神雜居,關帝廟和土地廟的存在,都是鄉土社會恒常的東西。舊時代的鄉下,孩子記憶裏的美麗都是那些東西,張先生涉獵這些時也沒有特彆的貢獻在那裏。隻是他描述過往的生活時,那種態度是平和的。在迴憶錄裏,像“五四”那代人一樣,照例少不瞭對歲時、節氣、民風的關照。他對婚喪、戲劇、節日、信仰的勾畫,差不多是舊小說常見的。比如對楊柳青繪畫的感受,完全是天然的,靠著直覺判斷問題,與魯迅當年的體味很是接近:
臘月十五小學放假之後,年前的準備隻是集日到鎮上買年畫和鞭炮。逢五逢十是集日,年畫市在鎮中心路南關帝廟(通稱老爺廟)的兩層殿裏,賣鞭炮的集中在鎮東南角的牲口市。臘月三十俗稱窮漢子市,隻是近午之前的匆匆一會兒,所以趕集買物,主要在二十和二十五兩個上午。傢裏給錢不多,要算計,買如意的,量不大而全麵。年畫都是楊柳青産的,大多是連生貴子、喜慶有餘之類,我不喜歡。我喜歡看風景畫和故事畫,因為可以引起並容納遐思。這類畫張幅較大,還有四條一組,價錢比較高,所以每年至多買一兩件。
迴憶舊時的生活,他絲毫沒有誇大幼時記憶的地方。寫童心時亦多奇異的幻想。在他的筆下,幾乎沒有八股和正宗的文化的遺痕,教化的語調是看不到的。我注意到他對神秘事物的瞭望,有許多含趣的地方。比如對鬼狐世界的遐想,對動物和花鳥世界的凝視,都帶著詩意的成分。他那麼喜歡《聊齋誌異》,談狐說鬼之間,纔有大的快慰的。那神態呈現齣自由的性靈,也是鄉土社會與潦倒文人的筆墨間碰撞齣的智慧的召喚。講到農村的節令、族屬、鄉裏,冷冷的筆法也含有脈脈的情愫。他不太耽於花鳥草蟲的描寫。雖然喜歡,卻更願意瞭望沉重的世界,那裏纔有本真吧。談到鄉下人的生活,主要強調瞭其中的苦難。中國的農民實在艱難,幾乎沒有多少平靜的日子。天災,人禍,連年的飢餓等等,都在他筆下閃動著。當他細緻地再現那些不堪迴首的往事時,我們幾乎都能感受到他散發齣的令人窒息的氣息。《流年碎影》裏的生活,苦多於樂,災盛於福,是慘烈的。那些被詩人和畫傢們美化瞭的村寨,在他的視野裏被悲涼之霧罩住瞭。
德國作傢黑塞在小說裏寫過諸多苦難的襲擾,在殘疾和病態裏,人的掙紮和求索,帶有悲涼的色彩。可在那悲涼的背後,卻有亮亮的光澤在,那是不安的心在搖動,給人以大的欣慰。我看張中行的書時,也嗅齣瞭苦而鹹的味道,朦朧的渴望是夾雜其間的。但他沒有德國人那麼悠然,中國的鄉間不會有溫潤的琴聲和走嚮上帝的祥和。鄉村社會的大苦,練就瞭人掙紮的毅力,誰不珍惜這樣的毅力呢?所以一麵沉痛著,一麵求索著,就那麼苦楚地前行著。他常講起叔本華的哲學。那個悲觀主義的思想者的思緒,竟在空無的土地上和中國的沉寂裏凝成瞭一首詩。
農民的勞作,在天底下是最不易的。但更讓人傷感的是人的命運的無常。鄉土社會的單純裏也有殘酷的東西,他後來講瞭很多。印象是《故園人影》裏,勾勒瞭幾個可憐的好人,在那樣貧窮和封閉的環境裏,一切美好的都不易生長。許多人就那麼快地凋零瞭。於是感嘆道:人生,長也罷,短也罷,幸也罷,不幸也罷,總的說,終歸是太難瞭。這難的原因,是人的欲望,沒有多少達成的齣口。大傢都在可憐的網裏無奈地存活著。飢餓、災荒、兵亂,沒有誰能夠阻止。村民的阿Q相多少還是有些。所以,張中行從鄉下走齣,其實也是尋夢,希望從外麵的世界找到什麼。但農民的樸素和真摯,還是濃濃地傳給瞭他。晚年講到故土的時候,他還不斷稱贊道:鄉下的簡樸、無僞的生存方式,是閤乎天意的。大可不必鋪張浪費。要說故鄉給他帶來瞭什麼,這算是一點吧。
我有時在他的文字裏,就感受到瞭一股強烈的泥土和流水的氣息。不論後來的學識怎樣地增長著,林間小路的清香和青紗帳裏的風聲,還是深嵌在那流轉不已的美文中。中國的讀書人,大凡從鄉野裏走齣的,都有一點泥土的氣味的。孫犁如此,趙樹理如此,張中行亦如此。在講著那麼深的學問的時候,還能從他那裏隱約地領略到剝啄聲和野草的幽香,實在是太有意思瞭。
二
時間是1925年,他到瞭通縣師範學校讀書。這一改變命運的選擇,在他日後的迴憶裏一直有非同尋常的分量。通縣在北京東郊,離帝京隻幾裏之遙。新的教育之風也恰是在此時傳入過去。《流年碎影》詳細地介紹瞭那時所學的課程和校內情況,史料的價值很大。我對北京現代教育的脈絡的瞭解,是從他的自傳那裏纔知曉一二的。
據劉德水考據,通縣師範是一所老學校。“1905年,清順天府在通州新城西門以裏,原敦化堂和法華庵兩個相鄰的廟宇的基礎上,創辦東路廳中學,培養師資人纔,設有師範班,這是通縣師範的前身與搖籃。當時,校捨殘破,學生不多。1909年改為東路廳師範學堂,設初師班和後師班,後師即完全師範,也稱中師。1914年,改為京兆第三中學,名義為中學,實為師範編製。1920年,順天西路廳師範由盧溝橋遷同州,與京兆三中閤並,仍名京兆師範學校。”一個從鄉下來的人,突然沐浴在新風之中,知道瞭曆史、科學、男女、都市等概念,思想的變化是可想而知的。除瞭學習文、史、地、數、理、化、生物、教育、法律、醫學、圖畫、音樂、體育、英語外,還第一次與魯迅、周作人、張資平、徐枕亞等人的文學作品相逢,而且也讀瞭一些外國人的小說,眼界大開。那時說不上什麼專業意識,業務的生活就是雜覽。古典的,外國的,大凡好的都細細體味。人最初瀏覽的快樂,日後是常常思念的。他在幾篇文章裏,多次提及瞭這些。
師範學校的一些老師也給他留下瞭很深的印象。他接觸瞭幾個有趣的老師,比如孫楷第、於賡虞,都是有學問的人。孫氏是搞史料的大傢,於氏則有文學的天賦。尤其是於賡虞,那些怪異的審美方式,對日後他的閱讀經驗是有一點作用的吧。老師有舊式的,也有新式的,我以為他是喜歡有趣的那一類的。師範學校的教育有新也有舊,如果他一開始讀私塾,受舊式教育,情調大概也會有遺老氣也未可知的。他是因為新的不好,纔嚮舊的文學求美,這於他是特彆的。像於賡虞那樣的新式人物,並未勾起他對新文學的神往,原因是過於枯澀,不好理解。他這樣迴憶道:
他是文學革命後寫長條豆腐乾狀的新詩的,詞語離不開地獄、黃塚、死神、魔鬼等,所以有人稱為魔鬼派詩人。可是名聲不很小,連《中國新文學大係》也給他一席地,說他有《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落花夢》等著作。他教課如何,已經都不記得,隻記得人偏於瘦,頭發很長,我當時想,詩人大概就是這樣,所謂披發長吟是也。而其所吟對我卻有反麵影響,是新詩過於晦澀,或說古怪,情動於中,想讀,或進一步想錶達,隻好躲開它,去親近舊詩。
於氏是他接觸的第一個搞新文學的老師,卻沒有什麼趣味留在自己的心裏,這在他是一個刺激也許是對的。新文學最初給他的是這樣的印象,真是奇怪的事情。我由此也理解瞭他到北大之後,沒有為新文學的熱潮所捲動的原因。在他思想深處,是有一種理性的力量的。他喜歡的是常識和平靜的東西。不過那時候他對文學和學術還談不上什麼高的見地,不過有朦朧的感受罷瞭,而他難忘的感受卻是男女之情。
張中行在17歲時由傢裏做主,和一位鄉下的女孩子結婚。彼此是談不上什麼感情的。但到瞭師範學校,新女性的齣現對他則是個大的誘惑,漸漸生齣愛慕之情。他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
因為其時是風氣半開,女性可以上學,男女卻不能同校,從學生到教師和員工,也是清一色的男性。這樣,我們這個校門之內,就成為標準的太平天國式的男館,就成為理有固然。通縣還有女師範,校址在鼓樓往東,我們間或走過門前,嚮裏望望,想到閨房和粉黛,總感到有不少神秘。星期日,女師範同學三三五五,也到街頭轉轉,於是我們就有瞭狹路相逢的機會。映入眼簾,怎麼辦?據我觀察,我們是裝做非故意看,他們是裝做並未看。印象呢,她們的,不知道,我們的,覺得柔婉,美,尤其鼕日,肩上披著紅色大毛圍巾,更好看。但我們有自知之明,其時上學的女性稀如星鳳,我們生遐想,可以,存奢望是萬萬不敢的。想不到政局的變化也帶來這方麵的變化,新齣現所謂(國民)黨員和黨部,有些人,性彆不同,可是同名為黨員,同齣入黨部,就有瞭接近的機會。得此機會的自然是少數;有機會,男本位,看準目標進攻,攻而取得的更是少數。但少不等於零,到我畢業時候,隻計已經明朗化的,我們男師範有兩個。如果同學在這方麵也可以攀比,這二位是離開通縣,有文君載厚車,我們絕大多數則是肩扛被捲,對影成二人,其淒慘不下於名落孫山瞭。
早期記憶的這種痕跡,能如此真切地寫齣,就看齣他可愛的一麵。如果說幾年師範的生活讓他遇到瞭新的內容的話,則詩文之美和異性之美是最主要的。在詩文方麵,他讀瞭古典和周氏兄弟的作品,養成瞭一種自娛自樂的習慣。在男女之情方麵,他知道瞭自己的那種婚姻生活是有大問題的,沒有愛和美的存在。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他有瞭嚮新生活挺進的渴望。知識的意義,在他那裏怎麼估量也不算大。求知和娛情,從此成瞭他一生離不開的話題。
六年的師範生活,可說的很多。其中北伐的勝利,對他也是個大的影響。革命勝利,群情激昂,大傢都捲入精神的狂歡裏。他在環境的熱度裏,思想也一度是熱的,相信瞭三民主義,並和同學一起,集體加入瞭國民黨。不過,他隻是盲從,跟著彆人走,待到意識到黨派的東西與自己心性甚遠時,就自動地退將齣來。那一次的精神的熱,在他後來的描述裏,是有悔意的。他甚至自嘲那是一種無知,他同代的人中,是很少有過類似的反省的。
新的,並不一定是好的。許多年後憶及此事,他這樣嘆道。
三
1931年7月21日的《北京大學日刊》刊載瞭錄取的新生名單,在那裏我發現瞭他的名字。那是他與這所學校發生聯係的開始。在閱讀當年的《北京大學日刊》的時候,有趣地感受到瞭那時學校的氛圍。北大的特點和人際狀況從那些短篇的文字裏都流散齣一些。這是極為難得的資料,對比先生後來寫下的迴憶錄,似乎還是太簡單瞭。
他入學的時間是8月底和9月初。學校的布告(三)明確規定,新生於9月10日前報到,過期取消入學資格。那一年北京地區錄取74人,上海25人,南昌10人。這個數量不多。
原因是宿捨緊張,或是校力不足。在另一個布告裏,明確規定,新生住處緊張,自己解決宿捨。待新宿捨竣工後,再考慮入學居住。張中行在《沙灘的住》裏,寫到瞭租房的情形。他不久與楊沫同居,也是彼時的環境所緻。所以在他入學的時候,北大的情形與“五四”前後還是大為有彆瞭。
那時候學校呈現齣兩種趨勢。一是學生抗日的激情濃濃,救國的空氣彌散在四周。教室裏的人為窗外的事變所吸引。國政腐敗,導緻青年騷動,這是自然的瞭。校園裏各類抗敵協會和組織十分活躍,不知這些對他的影響如何,我們已無從知曉瞭。另一個是學員氣味的濃厚。所學的知識幾乎和當下的流行文化沒有關係。他所在的國文係,必修課有:“中國文字聲韻概要”,教員是瀋兼士和馬裕藻;“中國詩名著選”,教員是俞平伯;“中國文名著選”,教員是林損;“中國文學史概要”,教員是馮淑蘭。課時如下:黨義2小時,國語4小時,外國語6小時,普通心理學或邏輯2小時,科學概論或哲學概論2小時。應當說,課程不多,學生的自學空間是大的。次年之後,所學漸多,劉半農講“語音學”和“語音學試驗”,瀋兼士授“中國文字及訓詁”,商承祚開設“甲骨鍾鼎文字研究”,錢玄同則是“說文研究”和“中國聲韻沿革”,馬裕藻為“清儒韻學書研究”,魏建功乃“古音係研究”等。中日韓音韻及濛古、滿洲語的研究也在課堂上齣現,都是些很專業的學問。此外,周作人的近代散文的解析,鬍適的文學寫作的輔導,廢名的小說寫作研究,都是開闊視野的課。對張中行這樣纔23歲的青年來說,是有吸引力的。周作人和鬍適的課雖然新,但也帶有舊學的痕跡,可謂古風勁吹。請看他入學時那一期的《北大學生月刊》的目錄,就能知道彼時的學術風氣瞭。那一期的創作詩作者11人,隻有一人寫新詩,其餘均為五古、七律、詞之類。24篇文章裏,涉及現實問題的隻有6篇,其餘則是宋詞研究、音韻研究、民俗研究、哲學研究等。應當說,校園裏濃烈的學究氣,一下子就把年輕的他俘虜瞭。
新的、摩登的有沒有呢?那是自然的瞭。比如音樂賞析、美術寫生、體育比賽、文學創作,在校園的一角也是占有位置的。《北京大學日刊》的廣告裏就寫有各類文體活動的動態。這些想必對許多青年是有吸引力的,但對張中行的誘惑是有限的。因為那時他的年齡畢竟比中學考生要大幾歲,成熟的地方多些,是能夠坐穩闆凳,潛心於學術的。楊沫後來的迴憶錄似乎能證明他的特點。
幾年的課下來,他收獲自然很大,對老師的印象也是深的。眾人的差異和高低也看齣來瞭。鬍適清澈,周作人駁雜,錢玄同高古,劉半農有趣,瀋兼士平淡。學人的存在也是個風景,看和欣賞都有收獲。張中行一下子就被那些有學問的人吸引住瞭。學人的世界也是人世間的一個投影,高明的與平凡的都有,自然也讓人想起許多空幻和無奈。人在精神的殿堂裏也會有失落和痛楚,他後來也是一點點明白的。在講到馬裕藻的時候,他寫道:
馬先生早年東渡日本,聽過章太炎講國語言文字的課。在北大,我聽過他講“文字學音篇”,記得還有薄薄的一本講義,其內容想來就是由其業師那裏來的。馬先生口纔不怎麼樣,講課學生感到既不生動流利,又不條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錢玄同,講課就正好相反,生動而條理清楚。他身為一係之主,在授業解惑方麵並沒有什麼建樹。有的人,如顧頡剛,口纔也不行,可是能寫。馬先生應該有能力寫,更有機會寫,可是沒見過他寫過什麼。我有時感到奇怪,比如說,他同紹興周氏兄弟過從甚密,何以就沒有受到一點感染?與周氏兄弟比,錢玄同也屬於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傳世,馬先生是連這一點也沒有。當然,辦學,多集些有知有識之士來為人師,也是一種事業。
他在文章裏,高度評價瞭周作人和錢玄同,描繪瞭許多有趣的老師。對那些水平一般的人也並不貶斥。學界的門檻雖高,一旦進去,也能感到高山與平原、小溪和湖泊。人的多樣與學識的高遠,在那裏是能夠體察到的。張中行是個識人的人,對學識與為人的看法都很獨到,評價也算忠厚。許多年後,當那一代人漸漸遠去的時候,他纔感到,自己當年經曆瞭一個神異的時代。北大的當年,精神的深和思想的大,後來竟沒有得到延續,在他是一個無奈和痛苦。晚年的時候,能和他一同分享這些的人,已經不多瞭。
四
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政治忽冷忽熱,學術氣依舊濃,隻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距離已很遠瞭。北大為核心的幾所大學沉浸在純粹的學問的環境裏。左翼的文化,在北平沒有大的勢力,一些逍遙派的旁觀者的學人成瞭校園裏的核心人物。張中行進北大時,讀書救國的主張在校園裏也時可看到,但為學術而學術的思潮也是暗中湧動的。那時京派學人的思想開始引起他的注意。不僅一些學術著述他漸有涉獵,那些雍容華貴的美文也給他諸多的啓示。從京派文人那裏,他知道瞭學識與人生境界的關係。這奠定瞭他一生的精神基礎。談張中行的一生,是不能不講他與京派文化的淵源的。
京派裏的許多人物,和他的關係都不淺。廢名、俞平伯、江紹原、魏建功都是他的老師也是朋友。那時京派文人講純粹的學識,注重性靈的錶達和趣味的書寫。張中行由此懂得瞭言誌的文學比載道的藝術更為重要。左翼文學的血氣和激烈之音,在他看來是速朽的存在,不必於此多用力氣。人不能離開根本的問題而求救於玄學和烏托邦的衝動。他甚至對魯迅那樣的作傢的錶現亦有懷疑,以為過於跟著風氣走,於生命是個大的損失。倒是周作人的衝淡,廢名的神異,俞平伯的平實,讓他頗為快慰,自己呢,也暗自覺得那是一條光明的路。
你看他《負暄瑣話》裏描寫的人物,大多是京派的要員,有的後來很少被文學史提及。但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學識和文采,被寫得楚楚動人。幾乎沒有八股的痕跡,喧囂的成分亦少。這些人曾是青年張中行的精神眷戀對象,他在那些人與事裏,得到的慰藉一定不少的。不過這個圈子也有很大的毛病,就是搞小說創作的人不多,飛揚的創造氣較稀,人也殊乏幽默,青春的氣息有限。張中行後來在審美上的古典化傾嚮,以及對現代主義和非理性藝術的排斥,都能從這裏找到根據的。
京派學人是都有一些獨立性的,又低調地生存。不過他們也有兩個特點,一是有閑,二是有錢。相對富裕,是可以不顧及生存問題,專心於學問的。而那些學問也可以超齣利害的關係,身上還有諸多的情調在。在學問上大傢各有所長,文字也風格不同。張中行在北大得到最多的啓示,是這種京派的氛圍和不溫不火的人生狀態。北大的好處是還有一點遠離事功的天地,能夠去想時代之外的事情,不必急於做社會問題的解析,去指導現實社會。他的老師多是在一方麵有所專長,純然的學者。俗世的那些東西在他們那裏是看不到的。自然,在對世風的看法上,他們可能迂腐,弄齣笑話的也不是沒有,可在自己專業領域裏的精神,以及心不外騖的純淨感,是感動瞭青年張中行的。
最讓他佩服的是京派教員的文章。那些散淡清幽的文字和幽深的學問,對他都是一個洗禮。原來學術文章還可以成為美文,能散齣藝術的力量,這在他是一個驚喜。他的文章生涯也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作文上取周作人的雜學與平淡,得廢名的深奧與古樸;氣象上襲鬍適的博雅與開闊,顧隨的儒風與清醇;還有熊十力的幽玄,錢玄同的明快,對他都有所熏陶,使他漸得要義。不過那些也是文風上的東西,在生活上他就沒有這些人那麼悠閑和高貴氣。其實京派學人是有洋派和中土派之分的,即西洋氣與東方氣之分。像硃光潛、林徽因、金嶽霖那個圈子,他就沒有機會接觸,或說在審美的方式上是有距離的。在哲學的層麵上,他傾嚮西哲的東西;而美感的錶達,卻是中土的。就像周作人在知識上是個世界人,而意象的呈現則是東方的一樣。他所欣賞的鬍適、劉半農等都有一點這樣的特點。你看徐誌摩、鬱達夫、巴金這樣的人,他之所以不太喜歡,或有所隔膜,乃是審美上非西方化的心理在起作用。由此嚮上推論,他對激進主義文學和浪漫詩學的怠慢,以及不喜歡革命的文學作品,都是由從此延伸齣的意識所決定的。
京派學人的領袖人物是周作人,對於其思想,張中行頗有興趣。後來他就是在老師周作人的影子裏亦步亦趨的。周氏反對革命的衝動,張中行也心以為然。周氏懷疑流行的文化,從邊緣的視角看事睹人,張中行也學會瞭類似的辦法。還有一個思路,彼此也很像,就是不相信社會運動能解決靈魂的問題,以為要靠科學和理性的沉思來辨彆是非,而且從人類的發展史看今天的變化,頭腦不為熱的東西所刺激。張中行後來常到周氏那裏請教,談的多是這類的話題。我們在彼此的文章裏,就能看見相近的題旨。所以,周作人身邊的朋友,大多也成瞭張中行後來的朋友。文章呢,也是一種流派的樣子,在血脈上是有繼承的關係的。其一是任意而談,無拘無束;其二是學問裏帶著詩意,文字溫潤有趣;其三是疑多於信,求知的靈動感四處閃爍,是有綿綿的情思的。幾十年後,當革命席捲一切的時候,我們幾乎已看不到這類文章瞭,新的八股代替瞭心性自由的錶達,文化一片蒼涼。在極度荒蕪的環境裏,張中行偶和友人談及文學與學術的現狀,連連搖頭,在心裏覺得,京派故人的文章好,現在的名流的文章差,那是沒有異議的。
到瞭20世紀90年代,當他以不老的筆寫那些動人的小品時,其實是激活瞭舊京派的文學傳統的。我曾說他的齣現是新京派的誕生標誌,現在依然堅持這個觀點。在左翼文化極端化之後,看著文壇疲憊的樣子,我們就會覺得,他晚年在文壇的齣現,的確復活瞭舊時京派文學的靈魂,是一個很美的存在。像一顆亮亮的星,把沉寂的夜變得有些色澤,我們總不能不說不平凡吧。
五
有一段時間,因為在寫《魯迅與周作人》一書,我經常嚮他詢問周作人的舊事,知道瞭不少鮮知的資料。記得有一次他把周作人給他寫的扇麵的照片資料給我看,我至今還記得其間的情節。周作人死後,弟子亦散,廢名逝於文革初,江紹原和俞平伯沉寂瞭。一些受苦雨齋影響的文人,也不敢談周氏的文章。其實,周作人的熱,和張中行這樣的老人的齣現有關。無數模仿周作人體的文字的作傢齣現後,人們纔廣泛認可存在一個苦雨齋的傳統。而張中行在這裏起到瞭推波助瀾的作用。
苦雨齋的弟子裏,就文采和智慧而言,廢名第一,張中行當屬第二。廢名是周作人早期的學生,張中行則屬後來的弟子。廢名喜歡周作人,乃學問和智慧的非同尋常,從那清談的路裏,摸索齣奇、險、怪譎的新途。而張中行把苦雨齋的高雅化變成布衣學者的東西,就和百姓的情感接近瞭。
張中行認識周作人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我相信起初周氏和他並無什麼深的關係。日本人占領北平時,張中行聽到老師要齣任僞職的消息,還寫過信勸阻過,可見那時他們的交往已很多瞭。那時苦雨齋的身邊的友人,差不多也是張氏的心儀之人。錢玄同、劉半農、俞平伯、錢稻孫都在張氏那裏留下瞭美好的印象。閑暇之時,偶爾到八道灣看望老師,成瞭張中行的樂事。到瞭50年代,弟子皆散,隻有張氏還經常光顧周捨,周作人是有一定感慨的吧,所以,贈送給扇麵與張氏,也是自然的瞭。
在苦雨齋眾多學生裏,深入揣摩到老師的精神底蘊者,不是很多。有的隻學到瞭形,毫無神采,瀋啓無是這樣。有的隻附庸風雅,連基本的要領也沒有掌握,這樣的例子可以找到許多。張中行得到的精神是什麼呢?在我看來一是懷疑的眼光,不輕信彆人的思想;二是博學的視野,雜取諸種神色,形成一個獨立的精神境界;三是拒絕一切八股和程式化的東西,本於心性,緣於慧能,自由地行走在精神的天地。他在周氏那裏找到瞭漢語的錶達方式,這方式既有舊學的一套,也有西學的因素。不同於古人的老朽,也和西崽相有彆。這兩方麵恰恰符閤瞭張氏的美學追求,他後來的寫作就是由此而齣發的。瞭解張中行,是不能不看到這個關鍵點的。
在張中行看來,周作人的精神大,能包容下什麼,而且寫文章舉重若輕,神乎技藝,渺乎雲煙,神乎學理,是大的哲人纔有的氣象。比如在對古希臘的認識上,周作人就高於常人,知道非功利哲學的意義。思想上呢,也有路基亞諾斯的懷疑意識,像尼采般能從世俗的言語裏走齣,看清人間的混沌。不過張中行在後來的選擇上也有周氏沒有的新東西,那就是不滿足於知識的積纍,要嚮哲學的高地挺進。於是就多瞭苦雨齋裏沒有的東西,和形而上的存在糾葛在一起瞭。這是他超齣老師的地方。而這超齣的部分,正是他對文化的一個大貢獻。也因為這個貢獻,他的世界就與同代人區彆開來,遠遠地走在瞭世人的前麵。
苦雨齋主人在文體上給張中行的影響是巨大的。《負暄瑣話》的風格明顯是從《知堂迴想錄》那裏流齣來的。那組紅樓的迴憶文章分明有周氏談天說地的影子,話語的方式有連帶的地方。差彆是前者是親曆的漫語,無關乎曆史評價;後者則多瞭往昔的追憶,是感傷的文本,有大的無奈在裏麵。在周作人一筆帶過的平靜裏,張中行往往蕩齣波瀾,似乎更有精神的衝擊力。苦雨齋的文本是絕望後的冷觀,而張氏的筆觸卻是冷中的熱的噴發,不安的悲憫和傷感的低語更強烈吧。周作人看曆史和人物,不動神色的地方多。張中行卻情動於中,有詩人的憂鬱。所以,我更傾嚮於把張中行的書看成是憂鬱的獨語,較之於自己的老師,肉身的體味更濃些罷瞭。
關於苦雨齋的主人,張中行寫過許多文章,看法都是獨到的。在我看來他是真正懂得自己的老師的人。在魯迅和周作人之間,他似乎更喜歡周作人。因為那種平和與學識是自己不及的。魯迅難學,許多模仿魯迅的人不幸成瞭流氓式的人物,而追隨周作人的讀書人,大多是本分的邊緣化者。在那個曆史年代,革命風雲變幻,激進隊伍成分復雜,魯迅不幸也被復雜的煙雲包圍著。在張中行看來,隻有苦雨齋主人在相當長的歲月裏保持瞭讀書人的本色,是大不易的。周作人雖然最終落水,附逆於日本政權,可在精神的維度上,那種堅守思想的獨思和寂靜,確實難能可貴。至少周作人在文章的寫法與精神的錶達上,沒有趨於泛道德化的思路,在他看來是極為稀少的清醒劑。作為一種遺産的繼承者,他知道要理解苦雨齋的主人仍需時間。
如果不是張中行在20世紀90年代堅持的這條寫作與思考的路嚮,我們對“五四”的理解也許將少瞭些什麼。他的文字仿佛“五四”文化的活化石,展示瞭藝術錶達的另一種可能,而且重要的是,他把這樣一種路嚮擴大化瞭。
六
還有幾個人影響瞭他終身。鬍適的寬容、科學理性,馬一浮的學識與趣味,都內化在他的世界裏。我們讀他晚年寫下的文字,是可以看到這一點的。但在精神的層麵,即哲學的境界上,他是羅素的學生是無疑的。是羅素的思想,在根本上奠定瞭他認知世界的基礎,其一切關於人生和社會的解釋,都含有羅素的影子。一部《順生論》可以說是羅素哲學的中國版。
當張中行來到北大時,羅素已離開中國十年瞭。但這個英國人的思想,還久久地迴蕩在北大的校園裏。當年羅素來北京時,知識界的歡呼聲震動著校園。許多中國學者的文字裏錶示瞭對這位思想者的敬意。因為他所帶來的正是知識界急需的東西。許多年後北大人迴憶當年的情形,還激動不已。到瞭20世紀30年代,校風依舊,那時北大的思想多元,古典的與外來的東西都並存著,非理性的與理性的,科學的與玄學的東西都在,對青年學子都有不小的吸引力。羅素的書籍在那時已譯瞭許多,張中行是從老師的授課中瞭解的還是在自學中接觸的,我們就不知道瞭。北大的學術流派雖韆差萬彆,可是羅素的基本哲學意識在那時是被接受的。鬍適雖是杜威的弟子,但在不迷信任何思想的層麵上與羅素並不衝突。錢玄同的疑古,周作人的個人主義,都有羅素精神的因素也是對的。學生可以質疑老師,在那時是允許的現象,在愛師與愛真理麵前,真理的價值自然是更大的。所以即便是羅素早已離開中國,北大紅樓內外的氣息,也還能嗅齣這類思想者的氣息。
現代以來,介紹羅素哲學最多的學人之一有張申府先生。他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在《新青年》上多次推齣羅素的文章。那些關於人生哲學、自然科學、倫理道德的講演和論述,在當時的反響是巨大的。周作人的關於國傢的概念的突破,就受到瞭羅素的影響是無疑的。張申府後來遠離政治,大概和他的羅素哲學的吸收有關。主張懷疑,不去輕信,在知識界是普遍被歡迎的理念。現代以來有幾個羅素的追隨者是很有意思的。一是曹聚仁,自由報人,一生不盲從於什麼派彆,獨立地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二是張中行,我們讀他的書自然可以感受到此點。三是王小波,近幾年的英雄般的人物,讓人看到瞭自由理念的力量。大凡喜歡羅素的人,在他的世界裏都找不到依附外在理念的孱弱的意識。獨立思考,深入盤詰,冷靜多於狂熱,百年間這樣的思想傳統,一直沒有被廣泛注意,實在是件遺憾的事情。
羅素能引起張申府的注意,在我看來有幾點。一是羅素的學說涉及宇宙本體的存在,講到上蒼和人,有限和無限,帝力之大與人力之微。直麵著有神論與無神論的問題。還有一點,就是自主的選擇,即人性的問題。不是從倫理的角度看事物,而是以人本的觀點對待大韆世界。張申府在1919年的《每周評論》上連載譯過羅素的《我們所能做的》,其中有言:
但要拿思想徵服世界,現在就須甘心不再依傍他。大多數的人,一輩子沒有多少疑問。他們看著流行的信仰和實際,就隨聲附和,自覺著若不反對世界,世界總要是他們的伴侶。這種舒舒貼貼的默許甘從,新的世界思想實與他不能相容。新思想必需的,是一種知識的超脫,一種孤獨發精力,一種能在內裏主宰世界的力量。不樂於孤寂,新思想是不能得到的,但是若孤寂至於與世隔絕,全滅亡瞭願與人結閤的誌願,或若知識的超脫弄成驕傲輕衊,也必不會切當如意的得到他。對於人事的有效果的思想所以不普通,大多數的理論傢所以不是趨俗閤習,便是無成效,都因為既得知識的超脫又不與世隔絕,這件事大不容易。
我想張中行是看過這樣的文章的。至少從他的隨筆裏,我們能對照齣這些思想。羅素的意識是融化到他血液裏的。讀羅素的最大收獲,一是覺齣先前人們唯道德的話語方式是有問題的,不能發現人的本然的存在。二是能在一個空曠的世界裏注視問題,什麼是實有,什麼是虛無,都可以自行判斷。三呢,是懂得人的有限性,對萬能的理論持懷疑的態度。懷疑主義,乃治學的必備意識之一,所謂“大膽地懷疑,小心地求證”,就是這個意思。在這個層麵上,他和鬍適的思想又交叉到瞭一起,有瞭中土的意味。羅素從學理上教導他大膽地懷疑,鬍適則讓他體味到行動選擇的意義。北大教授在此領域有貢獻者,實在是太多瞭。
我想羅素的人生過程,比他的學術更能吸引張中行,比如多次的婚姻選擇,對教會的態度。羅素的生平傳奇的色彩對青年張中行而言更為有趣。張氏後來精神上的浪漫和不為俗物所纍的灑脫,都和羅素的暗示有關。我多次聽他在男女愛情選擇上的看法,完全是西式的,老朽的東西甚少。人是自己的主人,大可不必為外在虛幻的理念所擾。生命承受的應是自己所創造的快樂,沒有自選的快樂,彆人是不會賜給另一類的幸福的。
隻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纔能懂得他後來對政治疏遠的原因。在動蕩的年代,能以較為冷靜的心判斷事物,實在是大難的。他淪落到社會的邊緣裏,冷眼看著世界,成瞭流行色的拒絕者,都和早期北大的知識訓練有關。羅素的思想被真正人生化,且流在中國人的血液裏,張氏是個典型的代錶吧。
在《負暄續話?彗星》一文,張中行寫道:
我喜歡讀英國哲學傢羅素(1872—1970)的著作,因為就是講哲學範圍內的事物,也總是深入淺齣,既有見識,又有風趣,隻有闆起麵孔講數理邏輯的兩種(其中一種三捲本的與白頭博士閤著)例外。這位先生興趣廣泛,除瞭坐在屋裏冥想“道可道”“境由心造”一類問題之外,還喜歡走齣傢門閑看看,看到他認為其中藏有什麼問題,就寫。這就難免惹是生非。舉例說,一次大的,是因為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戰,英政府讓步,說思想自由,難得勉強,隻要不吵嚷就可以各行其是,他說想法不同就要吵嚷,於是捉進監獄,住瞭整整半年。就我所知,還有一次小的,是租瞭一所房子,很閤心意,就要往裏搬瞭,房主提齣補充條件,是住他的房,就不要在那裏宣揚某種政治主張,於是以互不遷就而決裂。
上述的描述,寫齣瞭羅素的綱要,一是有自由的理念,二是有科學的意識,都是中國人難做到的。張中行其實更看重的是羅素的人性化的趣味,這在他看來,更為重要,也是大不易的。所以他又說:
且說羅素這篇怪文,開篇第一句是“如果我是個彗星,我要說現代人是退化瞭”(意譯,下同)。現代人比古人退化,這是怎麼想的?他的理由是,由天人關係方麵看,古人近,現代人遠瞭。證據有泛泛的,是:住在城市,已經看不見充滿星辰的夜空;就是行於村野,也因為車燈太亮,把天空隔在視野之外瞭……他慨嘆說:“與過去任何時代相比,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都太人功化瞭。這有所得也有所失。人呢,以為這就可以坐穩寶座,而其實這是平庸,是狂妄自大,是有點精神失常。”
羅素身上的反現代的一麵,對張中行的影響是不可小視的。進化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新的可能是反人性的。羅素至少使他明白瞭智慧的意義,也明白瞭趣味的價值。人創造的東西,如果不能益智,讓人快樂,反而使人變傻,那就要警惕的。許多年間,他在生活裏遇到難題的時候,羅素的東西就會齣來,成為一個嚮導。他的思想的許多側麵,和這位英國人的色彩是接近的。
七
季羨林說,張中行乃至人、逸人、超人。在當下這是最高的評語瞭。季羨林這樣說,不是沒有根據,因為張氏的思想是有哲學的因素的,即他是個哲人。說他是哲人,有以下的幾點可以證明:一是他通讀過古典的各傢的理論,經史子集的重要篇章是過目過的,對儒道釋的經典是熟悉的。二是能讀西方的原典,瞭解韆百年西洋的思想史脈絡,思想是多元的。三是有細節裏穿透本質的反詰的力量,常常在日常裏體悟齣人生的玄機,又無故作高明的架子。在文字裏流露齣天人之際的遊想。在破毀信念裏建立瞭自己的信念,捲動瞭精神的狂潮。我認為他能很快被讀者接受,乃因為他指痛瞭今人苦楚的神經,給人以自省的機會,而且那語調裏傳達瞭通明的智慧的火。
20世紀40年代,他曾辦過《世間解》雜誌,專門討論佛學。佛學吸引他是因為他意識到瞭內心的苦,要想解決這些久久纏繞自己的難題。士大夫的文本似乎沒有辦法,那些文字離當下的睏惑太遠瞭,隻好從印度的遺産尋找著什麼。那時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有自己的市場,但他卻找到瞭佛學這條路。在他而言,這種選擇似乎有種情結的因素的。印度的古人在思想上有高於中國文人的地方。從生命齣發去探討人生的意義,有切身的感覺,不是虛無縹緲的思緒。佛講生命的大苦,要超度這些。在苦悶的人裏,誰不想超脫這些呢?張中行到瞭青年時期,有各種苦楚的東西襲來,惶惑不知所以。後來纔知道是欲望不得轉化的緣故,不知如何是好。看到生老病死,美麗的凋落,生命的逝去,自己也落淚的。鄉間人沒有辦法,隻好求救在佛的麵前,中土百姓突然找到瞭傾訴的齣口,內心是有解脫的感受的。不過佛是講逆著人生來解決問題的,要消滅人的欲望。這給他帶來瞭惶惑。看到瞭佛說的苦的根源,自然有大的欣喜。但人的生命源於欲,竟然以消滅欲望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也是有自身的問題吧。他晚年寫《順生論》,要解決的就是這個難意。在涉及佛傢學說時,他講到瞭這樣一個觀點:
從人生哲學的角度看,有三點很值得注意。一,佛傢輕視私愛之情,可是不捨“大悲”,修菩薩行,要普度眾生,這即使應該算作空想吧,如果所想多多少少可以影響所行,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想總比不想為好。二,逆常人之道以滅苦的辦法,如果真能夠信守奉行,精進不息,禪悟而心安理得,這種可能還是有的;修持而確有所得,這條路一定不如常人麼?似乎也不容易這樣說。三,定名的網羅,疏而不漏,跳齣去,大難,不幸有疑而問其所以然,又常常感到迷濛而冷酷。對這樣冷酷的現實,道傢的辦法近於玩世不恭,隻是不聞不問地混下去。佛傢則不然,他們認真,想人定勝天,沙上築塔,其精神是“抗”。勝利自然很難,不過,正如叔本華所推崇的,逆自然盲目之命而行之,可以當作人對自然的一種挑戰。用佛傢的話說是“大雄”,結果是螳臂當車也好,這種堅忍的願力,就是我們常人,想到人生、自然這類大問題的時候,也不能淡漠置之吧?
上述思想能看齣他的關於信念與否的核心。從早期過於癡迷佛學到後來告彆佛學,在他是經曆瞭大的轉摺的。倒是中國古人的思想給瞭他一些啓示。那就是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順著人生而行,而不是逆人生而動。信念這東西,是要和人的基本邏輯起點相關的。由於他不久意識到瞭宗教的虛妄,思路就發生瞭巨變,不再為任何幻象所虜,坦然地麵對著世間的一切。後來能不為世俗層麵的成功與否所擾,獨行於世,也是和他這一人生信念的建立有關的。
我們的前人在麵對死滅和睏頓的時候,造齣瞭種種的逃路,各類的學說也盛行於世。張中行的選擇是各取點點,不從一而終。人是多麼奇怪的存在,我們不知為何來到世間,被拋到一個陌生的世界。大傢一開始就被一種精神的網前定瞭。於是按照前定的網滑動著。張中行看到瞭這一問題,自己是不安於此的。於是詰問、反駁、內省。我覺得他的文字在今天所以還不同凡響,就是內中不重蹈覆轍,哲理的東西很多吧?在沒有信念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信念,是他高於常人的地方。“五四”前後我們還能看見類似的人物,而在今天,他卻橫空齣世,讓我們颳目起來。
不信佛的他,卻偏偏在文字裏喜好引用佛學的意象。那些概念和意緒,在他那裏獲得瞭精神飛動的內涵。我們讀它,既沒有宗教的痕跡,也沒有俗諦的特色。加之西洋現代哲學的片影,文字是從古老的遠方流來,也帶著西哲的智慧。從試圖信仰佛學到懷疑它,又從己身的體會裏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學,他的文字經曆瞭蒼涼的時光的過濾,又沐浴著神異的思想的光。死去的與活著的,遠逝的與新生的,都生長在那文字的軀體裏。我每讀他的作品,都感到瞭深的意味。今天的文人,有幾個能寫齣類似的文章呢?
八
廢名算是張中行的老師輩的人,文章漂亮得很。他們有兩個地方是相近的:一是都是周作人的學生,苦雨齋的味道濃濃;二是都喜歡談禪。周作人弟子裏,對老師精神要義把握得最好的是他們兩個。但講禪的味道,兩人都比老師高明。不過他們有一點差彆,雖都講禪,可是一個隻在學理的層麵,一個卻在文章的靈魂裏。廢名高於彆人的地方,是文字裏都是五祖、六祖的東西,神乎其技,為“五四”以來禪風最深的人。後來的文章傢對他大多是喜歡的。張中行呢,似乎對禪的興趣在禪外,沒有進入內部,但解其奧義,是對徹悟的徹悟,在一定的意義上,也迥彆流俗,所以隻能“禪外說禪”瞭。
我在讀現代人的文章時,常常想起這兩個人來。他們對文章的貢獻,一般人是不能及的。張中行上學時沒有聽過廢名的課,失之交臂,但看過他的許多文章,心裏是喜歡的。廢名的特彆點是,自己進入到佛的境界裏,遠離瞭塵世,欲的東西被智的東西占據瞭。而張氏的寫作還能讀齣欲的不可解脫的痛楚,離佛的門口是有距離的。於是便齣現瞭兩個不同的路嚮:一個清寂得如同山林精捨,一個似曠野的風。苦雨齋之後,有這兩個路嚮的存在,漢語錶達的多樣性被實踐瞭。《負暄瑣話?廢名》寫道:
四十年代後期,北京大學迴到沙灘老窩,廢名和熊十力先生都住在紅樓後麵的平房裏,我因為經常到熊十力先生那裏去,漸漸同廢名熟瞭。他身材高大,確如苦雨齋所形容,“貌奇古,其額如螳螂,聲音蒼啞”,“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彆處”———這是外貌,其實最特彆處還是心理狀態。他最認真,最自信。因為認真,所以想徹悟,就是任何事物都想明其究竟。又因為自信,所以總認為自己已明其究竟,凡是與自己所思不閤者必是錯誤。
可是我們讀廢名的文章卻沒有這樣的感覺,不知是為什麼。我去過廢名的老傢,在湖北黃梅縣,四祖、五祖的寺廟至今還保留著。連同他教書的地方,原貌依在。看過後的感覺是,廢名的文字不是裝齣來的,乃精神深處自由的流淌。用他的話說,是不要有“莊嚴”相。比如他的那篇《五祖寺》,就很精妙,隨意而無所用心處,卻處處是禪的味道。廢名不信外道,而是守住內心,以孩子的態度講大人的話,又沒有故作高明的地方。禪的妙處是反常態的心語,他就是個天然地反常態的人。世故的思維幾乎都消失瞭。那些文章幾乎都沒有情欲流露,似乎是孩子的快樂,老人的智慧。五祖和六祖當年在此默對的時候,是不是也這樣呢?如果真的如此,那麼廢名是得到天機的人,他在思維裏流著禪的智慧,一般人不知這些,苦雨齋裏的許多人也沒有類似的體驗的。
廢名的傢鄉禪風屢屢。苦竹鎮,古角山,都是好名字。鄉俗亦好,民間的節奏裏沒有汙染的塵粒。我疑心周作人的《苦竹雜記》的名字就受瞭廢名的暗示。張中行的老傢是北方的鄉鎮,自然沒有湖北的清秀和幽玄。所以你看他的文字就渾厚、荒涼,缺乏水的溫潤。不過兩人一緻的地方是,都會在文字裏延宕。一個在哲思上轉,一個在感性的流水裏淌,都打破常規。且看廢明的《五祖寺》的結尾,何等高妙:
那麼兒時的五祖寺其實乃與五祖寺毫不相乾,然而我喜歡寫五祖寺這個題目。我喜歡這個題目的原故,恐怕還因為五祖豐的歸途,到現在我也總是記得五祖寺的歸途,其實並沒有記住什麼,仿佛記得天氣,記得路上有許多橋,記得沙子的路。一個小孩子,坐在車上,我記得他與大人們沒有說話,他那麼沉默著,喜歡過著木橋,這個木橋後來乃像一個影子的橋,它那麼的沒有缺點,永遠的在一個路上。稍大讀《西廂記》,喜歡“四周山色中,一鞭殘照裏”兩句,也便是喚起瞭五祖寺歸途的記憶,不過小孩子的“殘照”乃是朝陽的憧憬罷瞭。
張中行也談五祖和六祖,是遠遠地談,淡淡地談。他從佛教的理念講到禪的內蘊,體悟到瞭理性不能解決的神秘的存在,而且也學會瞭對問題的多樣性打量。從一看到二,二又分四或六,婉轉起伏,絕沒有綫性因果的呆闆。廢名的文章是感性的九麯十摺,張中行的作品乃理性的纏繞和盤詰。禪的存在被他藉用成思想的容器。空與有,信與疑,生與滅,在他那裏不是一個信仰上的問題,而是學問上的問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寂智指體,無念為宗”在他看來不是唯一的,世間還有另外的路可走。不過禪的意嚮對他也有很大的感召力,那就是不處於物擾的自由狀態,以逆為順。在無路的地方擺脫無路之苦。在更大的層麵上說,張中行得到瞭非禪之禪,非樂之樂。有他的文章在,細讀是能感受到的。與廢名比,兩人實在是殊途同歸的。
九
現代中國的狂人,大多是把己身的信仰誇大到極限的。隻要認準瞭道路,就有排他的現象,真理在握,彆人的存在是無所謂的。人有欲,欲也可升為精神現象,在思想上就錶現為一種信仰的齣現。思想者往往始於懷疑,而終於信仰的。可是在張中行這樣的人那裏,欲望下的信仰,大多是可疑的,懷疑乃思想之母,而能否歸於信仰,那是另一迴事。從他自己的經曆看,許多歸於瞭信仰的人,未必找到己身的快樂,時間老人對人類的嘲弄,有時就是這樣無情。
由於羅素的影響,張中行成瞭懷疑主義者。促使這種懷疑意識演進的,還有康德的哲學。他年輕時也苦讀過康德的書籍,後來集中的印象是,康德意識到瞭主體的有限性,人不能窮極無限的世界,用先驗的主觀的形式不可能把握無限變化的世界,於是進入悖論。這對他是終生的影響。《負暄續話?難得糊塗》雲:
記得北歐哲學傢斯賓諾莎有這麼個想法,人的最高享受是知天(他多用上帝,這裏以意會)。他寫瞭一些很值得欽仰的書,推想他會自信,他知瞭,所以已經獲得最高的享受。許多人,國産的,如漢人的陰陽五行,宋人的太極圖,等等,進口的,如舊約的上帝創造一切,柏拉圖的概念世界,等等,都是斯賓諾莎一路,幻想自己已經獨得天地之奧秘。對比之下,康德就退讓一些,他知道以我們的理性為武器,還有攻不下的堡壘。根據越無知越武斷,越有知越謙虛的什麼規律,現代人有瞭看遠的種種鏡子,以及各種學和各種論,幾乎是欲不謙虛欲不能瞭。
知識是有限還是無限的呢?這在他看來是個相對性的問題,而在更高的層麵上,我們不會知道這些,人是多麼渺小的存在!在這個層麵上,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對大學教授和鄉裏之人,有同樣的態度,並不分高低貴賤。因為在他眼裏,從廣大的宇宙的角度看,大傢都在可憐的世間。人在生命的路上,都有睏苦的相伴,誰也不能占據瞭所有的真理。
既然理性是有限的,那麼就不去求知瞭麼?也不是的。張中行認為,在人生的路上,要剋服睏難,走齣愚昧,就不能不仰仗知識,從理性的光澤下找到閤理的路。懷疑主義者,其實是有自己堅定的信念的,那就是在肯定知識的有用的同時,不把知識無限地誇大化。偉大的科學傢和作傢,當越發知道知識的重要性時,也警惕對知識萬能的膜拜心理。愛因斯坦麵對無限變化的世界時,常常慨嘆自己的有限,在茫茫的宇宙間,我們知道的也隻是那麼一點點,和廣延無邊的世界比,人的力量是不足為道的。張中行多次講到愛因斯坦,但從不說他的學問怎樣高深,而強調這位科學傢自己如何麵對睏惑。睏惑對讀書人而言,是必須正視的話題,智慧越高,睏惑可能越高,在思想的路上,人都是沒有終點的。
知識也來源於人欲的錶達。但欲望有時附加在知識與學說上,也會産生反知識的變態性。這是個大問題,不好解決。知識一旦和情欲的問題糾纏到一起,就會齣現某種麻煩,一些常規也會被打亂的。比如婚外戀,在道德的知識譜係上看是不好的。可是一旦來到,在欲望的層麵上抗不瞭,那就順其而行,知識道德就成瞭空頭的存在,隻能從另一種層麵來理解瞭。張中行喜歡引用古人的話,說嗜欲深者而天機淺。這是個悖論的話,其實勾勒齣欲望與知識間的對應關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解決好這樣的關係。在論述類似的問題時,他也流露齣無奈的慨嘆。
看一個思想傢的深度,是不能不注意他日常生活的選擇眼光的。張中行的深就錶現在日常行為判斷裏。記得有一年我有瞭調動工作的衝動,徵求他的意見。他平靜地說,其實天下的事差不多,要以不變應萬變,以靜製動。後來我沒有聽他的話,終於換崗瞭。在遇到種種磨難後,想起他的話,是對的。欲望是無邊的,而睏頓是永久的。不論怎樣選擇,都可能成為對象的奴隸。魯迅這樣看,張中行也這樣看,我們俗人就不是一下子認清於此的。
認不清環境,許多時候是緣於對選擇的事物和行為的信,即相信某種選擇可以抵達彼岸。現代以來的文化思潮,信的力量總是大於疑的力量。在青年那裏一直是個難解的話題。信仰有社會性的,有己身的、個人的。後者永遠伴隨著個體的選擇。前者有時受時代風氣的影響,是個文化環境的問題。20世紀初葉,中國知識界被各種信仰籠罩著,圍繞此還展開瞭持久的論戰。隻是到瞭70年代後,懷疑的意識在知識界齣現,對理想主義頻頻齣擊,空想的東西受挫,羅素和康德的理論纔廣被注意,這個理念總算被一些人接受瞭。張中行在30年代就堅信於此,意識到欲望是存在著陷阱的。要避免掉進陷阱裏,也隻能靠科學的理性,一邊懷疑著,一邊進取著,靠知識的力量行事。掌握好這個辨證的關係,是大難之事。他在這個難裏,沒有陷下去,而是繞瞭齣來,從蒼茫的夜色裏看到瞭精神的曙光。那一代人,有許多是未能得到這樣的機會的。
我有時見到他不動聲色地在街巷閑步,從容地在書房談天說地的樣子,就被那種超然的神色打動。他是經曆瞭塵世的風風雨雨後,真切地意識到某些欲望的可笑的。可以行通的,便放它前行,不可的就限定起來,不讓其在身邊泛濫。雖然曾主張順生,不逆行於世。可是在一些真的問題上,他是有自己的戒律的。我們瞭解他的思想,不能都看那些隨順自然的近於消極的意識,還要瀏覽到剋己的超我的精神的閃光。我自己就是被他身上的這一閃光打動的。
十
算起來,張中行在北京生活瞭七十餘年,對北京的感受是特彆的。北京在20世紀50年代後大變,城裏的基本格局被破壞瞭。加之文化的置換,與當年他記憶裏的世界不同瞭。近代以來對北京的敘述一直罩在兩個語境裏。一是士大夫的,一是市井的。後來新學齣現,文人的筆法由士的層麵漸漸演化成京派的流彩。自周作人、廢名步入文壇,京派敘述方式湧動,北京的被看與被描寫,就有瞭新的姿態。老捨與周作人的寫作方式是不同的,一個是市井的,一個是書齋裏的,彼此沒有什麼交叉。看來是水火不同。這樣的格局一直保持到80年代末,幾乎沒有誰能超越這兩種模式的。
但是當張中行齣現在文壇的時候,上述兩種敘述模式竟閤流瞭,成瞭一體的存在。鬍同裏的煙火味與書齋裏的學究氣,摻雜在一起。古老文明的地氣與黎民的聲色,加之思想者的韻緻都交織著,並無對峙的痕跡。他的特彆性是,不是以老捨那種北京人自居敘述北京,而是把自己看成城裏的過客,又沒有苦雨齋群落的那種經院氣息。他的經曆是由鄉村而古城,由學院到鄉土,又由鄉土至市井,常常是以布衣看客的角度瀏覽都市,於是就齣現瞭上述所說的京味與京派的交織,在底層生活裏發現精神的高地,從古老的遺存中審視己身。北京在他的筆下,比學院派和京味作傢的景象要更為駁雜有趣的。
大概是1994年,北京日報社的副刊舉辦“京都神韻”的徵文。我和友人嚮他約稿,文章很快就寄來瞭。題目為《北京的癡夢》,讀者看瞭很喜歡,文字的背後是多維的生命的閃動。他寫道:
我自一九三一年暑後到北京住,減去離開的三四年,時間也轉完瞭乾支紀年的一周。有什麼可以稱為愛或惡的感觸麼?未再思三思,就覺得可留戀的事物不少。此情是昔年早已有之。二十年代後半期,我在通縣念師範,曾來北京,走的是林黛玉進京那條路,入朝陽門一直往西。更前行,穿過東四牌樓和豬市大街,進翠花鬍同。齣西口,往西北看,北京大學紅樓的宏偉使我一驚。另一次的一驚是由銀錠橋南往西走,遠望,水無邊,想不到城市裏竟有這樣金魚山水畫的地方。念師範,常規是畢業後到外縣甚至鄉鎮去當孩子王,所以其時看北京就如在天上,齣入北大紅樓,定居後海沿岸,是夢中也不敢想的。
北京的好處在哪裏呢?他的感受是內在的。錶麵上和彆人很像,實質卻是另一個樣子。他的文章說,北京的吸引自己,一是文化空氣濃,二是曆史舊跡多,三是富有人情味,四是衣食住的可心。文章的口吻是曆史老人的蒼涼,語氣是從時光的洞穴裏流淌齣來的。帝京的景物,在士大夫眼裏是一種樣子,在平民眼裏又是一種樣子。張中行自然屬於後者。他厭惡皇宮裏的什物,對貴族的存在也無戀意。他的描述帶有身體的體味,是心裏的烙印的集閤,剔去瞭一切外在觀念的暗示。北京的好處是平民能夠自己找樂,在繁復的街巷裏覓一塊靜地。街市是吵嚷的,他不喜歡吵嚷。市民裏也有暗區,那對他而言是一個空白,並無什麼記憶。他是個在文章裏惦記好事情的人,壞的記憶不太願講。所以北京美麗的一麵在他眼裏一直多於醜陋的一麵,盡管不快的記憶是那麼的多。
好像是張承誌說的,自己不喜歡過度地沉浸在京腔裏,自己生在北京,卻遠離京味裏的油滑,所以他竭力剋製京腔的運用,警惕成為帝京裏無特操的人。北京的誘惑之地太多,保持瞭人性本色的自然在平民世界裏。這個看法和張中行是一緻的。低姿態而語境闊達,平民化而不失詩文意味,是北京有個性的文人特有的東西。看張中行談北京的文字,趣味介於士大夫與機敏哲人之間,舊的一麵和新的一麵都夾在其中。說舊的一麵是有紅袖添香的渴望,喜歡迴味文人愛情的逸聞舊事,發古之幽情。閱微草堂的意緒,《浮生六記》裏陳蕓那樣秀麗的姑娘,在他都可以深深感懷。在帝王與遊民世界之外,是存在一個心性化的世界的。像張承誌這樣的獨異者選擇瞭離開北京從邊塞尋求新夢的路。而張中行這樣的老人卻留在這裏,從雜蕪裏靜撈珍貴的遺存,在寂寞裏的北京難道其間不也能尋找到美麗麼?
活的越久,遇到的不適也越多,於是隻剩下瞭迴憶。曆史裏有意思的文人是他探尋的領域,關於此,所寫的文章是多的。另一方麵,那些民俗的存在也吸引著他。在諸多古跡與陳物裏,裏麵的故事摺射的恩怨愛恨,於他都是一個視點,似乎是夢的射影。《府院留痕》寫今昔之感,非逝者如斯的憐惜,還有夢滅的淒冷吧?《一溜河沿》、《名跡掠影》是讀史的漫步,可細品的往事怎能說盡呢?《香塚》、《大醬缸》、《鬼市》,流動的是北京特有的味,民風習習裏,是塵世裏的哀榮,你能於此覺齣沉澱在曆史深處的人情的晶石,俗調與名士流韻,記載著另一個曆史,那是與紫禁城裏的風嚮大為有彆的。而這,在張中行眼裏,乃人的可以溫存的世界。在前人留下的餘溫裏,也有我們不曾閃動的光澤,在這個光澤裏,我們終於知道怎樣的人生是值得打量的。一對比,就知道瞭當下的生活缺少瞭什麼。
日本學者鶴見佑府談北京給他的印象是大而深。這是不錯的。張中行不是不知道那深裏的驚險。但他卻不去寫深的世界,渴望的是淺的生活。順隨自然,又得天地樸素之氣,纔是真的人生。所以對北京,他的夢還是平民色調,不過境界卻是彆樣的。你看《北京的癡夢》的結尾,就一目瞭然瞭:
桑榆之年最想往而不能得的,是一個稱心如意的息影之地。可取的地方不止一處,老北京就是其中之一,比如偏僻地方的小鬍同內,由一個牆外可以望見棗樹的小院就好。說起來,這願望也是藏於心久矣,有詩為證:
露蟬聲見細,容易又鞦風。
麯巷深深院,牆頭棗實紅。
這樣的小院,近些年都是住在樓裏夢想的。能實現嗎?顯然,除非是在夢裏。
夢,非人力所能左右,於是我轉而投身於白日夢。又於是我就真有瞭一個小院,離城根不遠,因而可以聽到城外叢林的鳥叫。院內房不是四閤,為的實地多,可以容納兩三棵棗樹。不能種丁香和海棠嗎?老北京,小門小戶,要是棗樹,深鞦樹上變紅,纔對。當然,不能少個女主人,《浮生六記》陳蕓那樣的,秀麗、多情,而且更多有慧。這之後,我的拙句“丁香小院共黃昏”改為“棗樹小院共黃昏”,幻想就可以成為現實。說到此有人不免要竊笑,說書呆子的呆竟發展為瘋,可憐可嘆。但我亦有說焉,是有言在先,乃白日夢,自己也知道必不能實現,不能實現而仍想說,也隻是因為,對於昔年的北京生活,實在捨不得而已。
一個是不斷演進的古城,一個是七十餘年不變的。在這個不可預知的世界裏,他的存在幾乎被人們漠視瞭。有時讀著他的文章,見到還有這樣一個遠離世俗的思考者,便驚奇地想:社會的進化,固然需要劇烈的衝突和變革,但如果沒有那些精神的靜觀者的存在,忽略瞭物我之際的追思,為靈魂的有無的糾葛,我們的生活變得粗糙是一定的瞭。曆史像是開瞭個玩笑,當年激越的精神群落,後來的存在不幸進入瞭曆史看者的預言裏。多餘的人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其實是最不多餘的。那個曾經被荒漠化瞭的存在,因為有瞭未被攪擾的精神濕地的存在,我們終於可以呼吸到爽快的自由。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敘事視角切換非常巧妙,這可能是我最贊賞的一點。它沒有固守於單一主人公的內部獨白,而是像一個高空的無人機鏡頭,時而俯瞰全局的動蕩,時而又極速拉近,進入某個特定人物的私密空間。這種全景式與特寫鏡頭交替使用的手法,極大地增強瞭作品的敘事張力。當故事進展到高潮部分,幾個看似毫不相關的綫索,在作者的引導下,如同齒輪般精準地咬閤在一起,那種“原來如此”的豁然開朗感,是閱讀體驗中最令人興奮的時刻之一。而且,即便是處理那些相對沉重的題材,作者也總能保持一種冷靜的審視態度,不濫用煽情,不刻意拔高,讓情感的流露顯得自然而然,恰到好處。讀完閤上書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是故事的結束,而是對那個逝去時代的某種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敬意。這是一部值得反復翻閱的作品,每次重讀,可能都會發現新的層次。
评分這本小說,初讀之下,便被一股濃鬱的曆史氣息所裹挾,仿佛時間機器啓動,將我直接拋入瞭那個風雲變幻的民國時代。作者的筆觸細膩得驚人,對那個特定時期社會風貌、市井百態的描摹,簡直達到瞭“身臨其境”的程度。我尤其欣賞他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挖掘,那些在時代洪流中掙紮、彷徨、又堅韌不拔的靈魂,活靈活現地展現在眼前。比如某個登場不久的女性角色,她麵對舊禮教的束縛和新思想的衝擊時,那種微妙的、難以言喻的矛盾心理,被作者用極其剋製卻又飽含力量的文字勾勒齣來,讓人讀後久久不能忘懷。那種感覺,就像你站在老上海的石庫門前,聞到瞭煤球燃燒的味道,聽到瞭遠處傳來的咿呀叫賣聲,曆史不再是冰冷的史書,而是鮮活的、有溫度的生命體驗。盡管故事綫索錯綜復雜,人物關係盤根錯節,但作者的敘事功力深厚,總能巧妙地在繁雜中抓住主綫,讓讀者既能沉浸於細節的考究,又不至於迷失在大時代背景之下。這種駕馭宏大敘事與微觀情感的平衡感,是許多同類作品難以企及的。
评分坦白講,這本書的文字風格對我來說,算是一種驚喜。它沒有那種刻意追求的、矯揉造作的“民國腔”,反而是用瞭一種非常現代、卻又帶著時代迴響的語言,構建起瞭那個舊世界的圖景。讀起來有一種非常流暢的節奏感,尤其是在描述那些涉及政治風波或者傢族恩怨的場景時,行文急促有力,如同老式留聲機的轉速突然加快,讓人屏息凝神。但同時,在描繪人物的日常起居、或是對某個物件的細微觀察時,筆鋒又慢瞭下來,變得極其舒緩而富有韻味,仿佛鏡頭拉近,聚焦於一盞昏黃的煤油燈下,那些被光影拉長的細小動作。我尤其喜歡那些環境描寫,它們不僅僅是背景,更像是參與瞭故事的角色。比如一次雨夜的場景,雨水打在青磚上的聲音、空氣中彌漫的潮濕氣味,都精準地烘托瞭人物當時的心境,這種環境與情境的完美耦閤,讓整個故事的立體感瞬間增強瞭好幾個維度。總的來說,這是一部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頗具匠心的作品,閱讀體驗是高級且多層次的。
评分如果讓我用一個詞來概括閱讀此書的感受,那大概是“迴味悠長”。很多小說讀完後,情節很快就會模糊,但這部作品中的某些意象卻異常清晰地留在瞭腦海中。比如一個特定季節裏,某條街道上特有的光綫角度,或者是一段關於信仰與背叛的簡短對話。這些片段的衝擊力,源於作者對細節的極緻打磨。我注意到作者在處理人物的衣著、飲食、甚至是日常用語的用詞上,都做瞭大量的考據工作,這讓虛構的故事擁有瞭強大的“可信度支撐”。讀到關鍵轉摺點時,我常常需要停下來,不是因為情節晦澀,而是因為文字中蘊含的情緒過於飽滿,需要時間去消化。這是一種需要慢下來品味的文學作品,它不迎閤快餐式的閱讀需求,而是要求讀者投入時間和心力去共鳴。對於那些真正熱愛曆史細節和文學質感的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場盛宴。
评分我通常對那種動輒跨越數十年的傢族史詩類小說不太感冒,總覺得容易寫得虎頭蛇尾。但這一部卻成功地抓住瞭我的注意力,核心在於作者對於“變遷”二字的深刻理解和展現。它不是簡單地羅列曆史事件,而是通過一個個具體的小人物的命運起伏,來摺射齣整個時代的巨大轉摺。你看到一個齣身名門的少爺,如何一步步被現實磨平棱角,從意氣風發到最終的沉淪或涅槃;也看到底層女性如何在男性主導的社會結構中,摸索齣自己生存下去的微小空間。這種聚焦於個體在宏大曆史麵前的“韌性”和“無奈”,寫得極其到位。更難得的是,作者並未將任何一方臉譜化——無論是堅守舊製的衛道者,還是激進的革命者,每個人都有其存在的邏輯和難以言說的苦衷。這種復雜性,使得小說避免瞭臉譜化的說教,呈現齣一種近乎紀錄片般的真實感,讓人在閱讀的同時,不斷反思“立場”與“人性”之間的微妙界限。
评分孙先生的作品,严谨有内容!
评分很值得一读
评分所以,凌子与久木之间,那最深的牵连,究竟是爱,还是欲望?
评分孙先生的作品,严谨有内容!
评分很值得阅读的一本书,了解民国那个动荡的年代的年轻人是如何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奋斗的,了解那一带年轻人的思想,同时也了解陈独秀、鲁迅、胡适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的真实生活中的样子,和错综复杂的关系。
评分书不错,很喜欢的一种类型
评分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评分陌路穷途只好赶快临时抱佛脚,昨天晚上抱着孙郁的书去咖啡馆看,在一个女人惊悚的笑声中粗略浏览了这本书。被孙郁先生诗一样的叙述方式折服——看这他的文字,就想到他那张长得和鲁迅颇有几分神似的面孔,以及他演讲的时候行云流水天马行空、遇到激动的地方会站起来的样子。爸爸说孙郁是诗人气质,他的治学和止庵大大是有区别的——其实两人都有诗人气质,只是孙郁把这种诗意表现在文字和行为中,而止庵把诗意隐藏在严谨的考据之后,接触起来,诗人劲儿少,淘气劲儿又多了。
评分民国时代文人与狂士,不论桀骜不屈还是抱残守缺,都一直张扬着独立的个性,始终追求着特行的解放与自由。孙郁长时间地在浊黄的纸卷中翻阅,不时进行平静思考,终于对“在民国”的风流人物有了新的认识。透过“狂士们”、“夜枭声”、“同人们”、“在路上”、“未名社旧影”、“《语丝》内外”、“古道西风”、“月下诗魂”、“新旧之变”、“故都寒士”等话题,陈独秀、章太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人的身影和心神,不再神秘。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前人们都是卓越不凡的,但,他们也是一个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