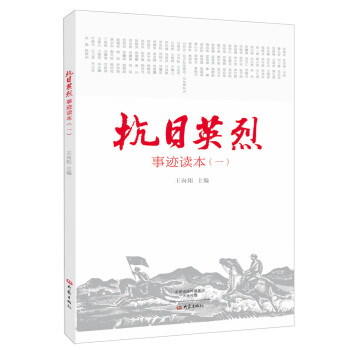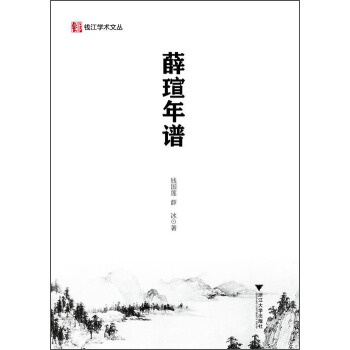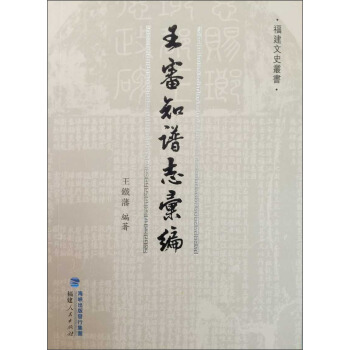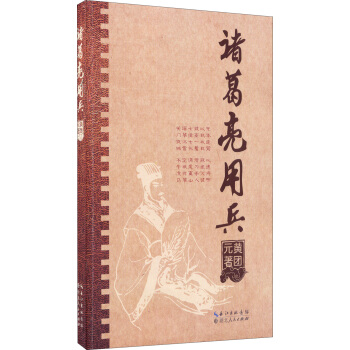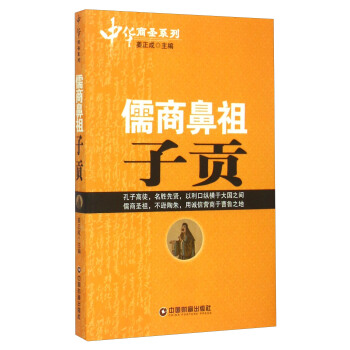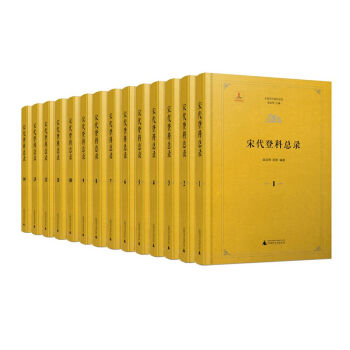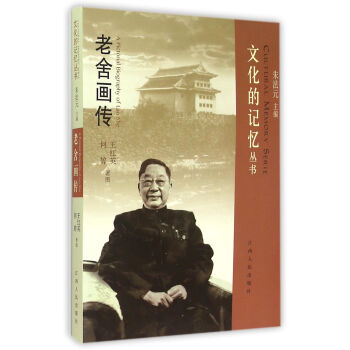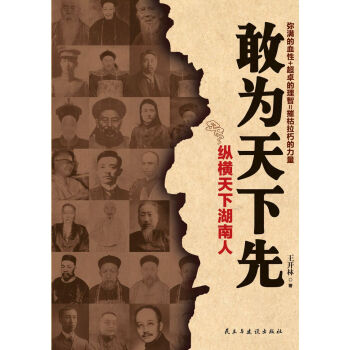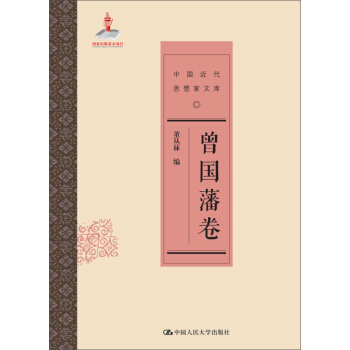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本書自曾國藩所留不下韆萬言的公私文牘當中,精選近300篇長短不一計約50萬言的文字,包括文章、奏疏、書信(含傢書)、日記等多種體裁,內容上涉及其政事、軍事、德事、學事、傢事等方方麵麵,反映這個“百科全書式”人物的人生梗概和思想內涵,同時也體現那個特定時代的社會狀貌和世態麵相。知人論世,論世知人,本書盡管篇幅有限,但能為讀者獲取這種雙嚮互動的認知提供助益。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曾國藩(1811—1872),湖南湘鄉(今屬雙峰)人,晚清重臣、名臣,同時也是著名文士和思想傢。道光年間中進士,入翰林,擢部堂,曆經十多年的京官生涯。鹹豐二年(1852)丁母憂迴籍,被任命為湖南“團練大臣”,藉機練成湘軍,統之鎮壓太平天國,曆時十年餘。其間於鹹豐十年充任兩江總督,後兼榮列“相國”(大學士)。又曾掛帥鎮壓撚軍,“功”而退返兩江之任。後移調直隸總督,在任近兩年,於同治九年(1870)鼕重就兩江之職,之後年餘去世。一生統軍理政之外,文事不輟,又重修身、齊傢,思想蘊涵豐厚。
編者簡介
董叢林,男,1952年生,河北鹽山人。曆史學博士,河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多年來一直在高校從事中國近代史專業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光明日報》等二十餘傢刊物發錶論文百餘篇,在人民齣版社、三聯書店等多傢機構齣版個人著作十餘部。晚清湘、淮軍政集團要員研究,是其專重的領域之一,有《曾國藩傳》(43.6萬字,人民齣版社)齣版及多篇關於曾國藩的論文發錶,即將麵世的有《曾國藩年譜長編》(約150萬字)。
目錄
導言甲編
順性命之理論(道光十八年四月下旬,1838)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日記(1840)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日記(1841)
稟祖父母(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1842)
稟祖父母(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1842)
緻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842)
道光二十二年十至十二月日記選(1842~1843)
緻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43)
復賀長齡(道光二十三年,1843或1844)
緻劉蓉(道光二十三年,1843或1844)
五箴並序(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初二日,1844)
緻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44)
求闕齋記(道光二十五年五月,1845)
書《學案小識》後(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1845或1846)
答劉蓉(道光二十五年,1845或1846)
君子慎獨論(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1847)
緻澄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1847)
答歐陽勛(道光二十七年,1847或1848)
緻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1849)
應詔陳言疏(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1850)
答馮卓懷(道光三十年,1850或1851)
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鹹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51)
緻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鹹豐元年五月十四日,1851)
備陳民間疾苦疏(鹹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1852)
復鬍大任(鹹豐元年,1851或1852)
乙編
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摺(鹹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53)
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鹹豐三年正月,1853)
與馮卓懷(鹹豐三年正月,1853)
與硃孫貽(鹹豐三年二月二十七日,1853)
與徐嘉瑞(鹹豐三年二月,1853)
與江忠源(鹹豐三年八月三十日,1853)
與吳文鎔(鹹豐三年九月初六日,1853)
與張亮基(鹹豐三年九月初九日,1853)
與彭洋中曾毓芳(鹹豐三年九月十七日,1853)
與王錱 (鹹豐三年十一月初六日,1853)
復呂賢基(鹹豐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853)
與鬍林翼(鹹豐四年正月十六日,1854)
與郭崑燾(鹹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54)
討粵匪檄(鹹豐四年正月,1854)
報東徵起程日期摺(鹹豐四年二月初二日,1854)
靖港敗潰自請治罪摺(鹹豐四年四月十二日,1854)
官軍大破田傢鎮賊摺(鹹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854)
曉諭新募鄉勇(約作於鹹豐四年,1854或1855)
統籌全局摺(鹹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1855)
諭紀鴻(鹹豐六年九月二十九日,1856)
諭紀澤(鹹豐六年十月初二日,1856)
諭紀澤(鹹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1856)
與李元度(鹹豐七年閏五月初三日,1857)
瀝陳辦事艱難仍籲懇在籍守製摺(鹹豐七年六月初六日,1857)
緻鬍林翼(鹹豐七年八月初三日,1857)
緻沅弟(鹹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58)
緻沅弟(鹹豐八年正月十九日,1858)
湘鄉縣賓興堂記(鹹豐八年五月,1858)
諭紀澤(鹹豐八年八月初三日,1858)
諭紀澤(鹹豐八年八月二十日,1858)
緻澄弟季弟(鹹豐八年八月二十二日,1858)
緻鬍林翼(鹹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1858)
復鄧汪瓊(鹹豐八年十一月初二日,1858)
緻澄弟沅弟季弟(鹹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58)
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摺(鹹豐九年正月十一日,1859)
復鬍林翼(鹹豐九年正月十二日,1859)
聖哲畫像記(鹹豐九年正月二十一日,1859)
諭紀澤(鹹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1859)
鹹豐九年五月初八日日記(1859)
復鄧汪瓊(鹹豐九年六月二十四日,1859)
復葛封泰(鹹豐九年八月十九日,1859)
復左宗棠(鹹豐九年九月二十五日,1859)
遵旨會籌規剿皖逆摺(鹹豐九年十月十七日,1859)
緻吳廷棟(鹹豐九年十月二十一日,1859)
復鬍林翼(鹹豐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9)
鹹豐九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記(1859)
復張裕釗(鹹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七日,1860)
緻澄弟(鹹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1860)
丙編
緻澄弟(鹹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1860)
復李續宜(鹹豐十年四月二十六日,1860)
預籌淮揚寜國太湖三支水師摺(鹹豐十年五月十七日,1860)
遵旨妥籌辦理並酌擬變通章程摺(鹹豐十年六月初三日,1860)
復劉繹(鹹豐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860)
復夏炘(鹹豐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860)
奏請帶兵北上以靖夷氛摺(鹹豐十年九月初六日,1860)
緻沅弟(鹹豐十年九月初十日,1860)
遵旨復奏藉俄兵助剿發逆並代運南漕摺
(鹹豐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60)
緻澄弟(鹹豐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1)
緻澄弟(鹹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61)
諭紀澤(鹹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61)
復許振禕(鹹豐十一年三月十一日,1861)
諭紀澤紀鴻(鹹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1861)
復楊嶽斌(鹹豐十一年六月初八日,1861)
諭紀澤(鹹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1861)
箴言書院記(鹹豐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61)
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摺(鹹豐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61)
鹹豐十一年八月初十日日記(1861)
鹹豐十一年八月十七日日記(1861)
復左宗棠(鹹豐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1861)
剋復安徽省城賊眾盡數殲滅及攻剿詳細情形摺
(鹹豐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1861)
諭紀澤(鹹豐十一年九月初四日,1861)
復毛鴻賓(鹹豐十一年九月十一日,1861)
瀝陳前湖北撫臣鬍林翼忠勤勛績摺
(鹹豐十一年十月十四日,1861)
懇辭節製浙省各官及軍務等情摺
(鹹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61)
復龐鍾璐(鹹豐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1862)
復袁甲三(鹹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862)
鹹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記(1862)
復汪士鐸(鹹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2)
遵旨籌議五省閤力會剿先陳大概情形摺
(鹹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62)
議復藉洋兵剿賊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1862)
復毛鴻賓(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1862)
同治元年二月初一日日記(1862)
遵旨統籌全局摺(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1862)
李鴻章改由輪船赴滬摺(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1862)
復李鴻章(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1862)
籌議藉洋兵剿賊摺(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1862)
復李鴻章(同治元年三月三十日,1862)
復奕?桂良(同治元年四月初九日,1862)
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日記(1862)
復李鴻章(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1862)
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日記(1862)
緻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復多隆阿(同治元年五月十八日,1862)
緻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1862)
議復調印度兵助剿摺(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1862)
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日記(1862)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日記(1862)
復吳廷棟(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三日,1862)
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日記(1862)
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日記(1862)
諭紀澤(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1862)
復奕?(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三日,1863)
密陳購買外國船炮預籌管帶員弁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863)
復王傢璧(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3)
復夏教授(同治元年十二月,1863)
復彭毓橘(同治二年正月初一日,1863)
復薛煥(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1863)
緻沅弟(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1863)
緻沅弟(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1863)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日記(1863)
緻沅弟(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1863)
懇辭曾國荃補授浙撫並謝恩摺(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63)
密陳近日大江南北軍情及餉缺兵逃大局決裂可虞片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863)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日記(1863)
復李榕(同治二年五月初十日,1863)
南洋通商大臣一缺仍請裁撤摺(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1863)
復奕?(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1863)
遵旨復陳江南防務緊迫暫難全力援淮及相機馭使李世忠摺
(同治二年八月十三日,1863)
復瀋葆楨(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1863)
遵旨復議南漕運京請準變通成例並飭王大臣及戶部集議新章摺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二日,1863)
緻澄弟(同治二年十月十四日,1863)
復李鴻章(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五日,1863)
復吳廷棟(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日,1863)
緻澄弟(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1863)
復僧格林沁(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64)
復奕?(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4)
奏陳新漕仍由海運酌定辦理章程摺
(同治三年正月十八日,1864)
緻沅弟(同治三年四月二十日,1864)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日記(1864)
緻沅弟(同治三年五月十六日,1864)
奏報攻剋金陵盡殲全股悍賊並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達摺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1864)
丁編
同治三年七月初一日日記(1864)
復惲世臨(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864)
再陳裁撤湘勇及訪查洪福瑱下落尚端倪片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1864)
復奏諭旨垂詢諸事摺(同治三年八月十三日,1864)
緻李鴻章(同治三年九月初四日,1864)
批鮑爵帥稟單(同治三年,1864或1865)
緻李聯琇(同治四年正月十六日,1865)
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日記(1865)
同治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日記(1865)
復李鴻章(同治四年五月初四日,1865)
遵旨赴山東剿賊並陳萬難迅速緣由摺
(同治四年五月初九日,1865)
謹陳籌辦情形並請收迴成命摺(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1865)
復蘇廷魁(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七日,1865)
賊眾全萃皖境擬先赴臨淮摺(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一日,1865)
復劉長佑(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八日,1865)
批浙江處州陳鎮國瑞具稟暫駐歸德並餉項軍火如何籌措等情
(同治四年六月初六日,1865)
諭紀澤紀鴻(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1865)
遵旨復陳並請敕中外臣工會議剿撚事宜摺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四日,1865)
諭紀澤(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1865)
奉旨復陳近日軍情及江督漕督蘇撫事宜摺
(同治四年九月十九日,1865)
諭紀澤紀鴻(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九日,1865)
迭奉諭旨復陳各處軍情及湖團處置摺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66)
緻澄弟沅弟(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866)
緻劉蓉(同治五年正月初三日,1866)
復劉銘傳(同治五年二月十三日,1866)
同治五年二月十六、十七日日記(1866)
復丁日昌(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1866)
遵調鮑超剿撚並籌定霆軍餉項摺(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1866)
諭紀澤紀鴻(同治五年三月十四日,1866)
密陳重視撚匪博貯將纔核實奏報力戒虛浮以正風氣片
(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一日,1866)
同治五年四月十五、十六日日記(1866)
復陳遠濟(同治五年五月十二日,1866)
緻澄弟(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1866)
同治五年六月初七、八日日記(1866)
批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防河事宜俟抵周口與潘張二軍通力閤作等情
(同治五年六月二十五日,1866)
復李鴻章(同治五年七月十八日,1866)
緻澄弟(同治五年八月初十日,1866)
緻沅弟(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66)
復彭毓橘(同治五年九月十一日,1866)
緻沅弟(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1866)
復劉銘傳(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1866)
復彭毓橘(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
病難速痊請開各缺仍留軍中效力摺
(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1866)
復陳病狀艱難請準不迴江督本任仍命李鴻章暫行兼署摺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
復尹耕雲(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67)
緻歐陽夫人(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1867)
緻澄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1867)
緻沅弟(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67)
緻沅弟(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867)
諭紀澤(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1867)
緻鮑超(同治六年三月十四日,1867)
復李昭慶(同治六年三月十六日,1867)
緻歐陽夫人(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1867)
復劉崑(同治六年五月二十四日,1867)
加李鴻章片(同治六年八月初七日,1867)
復馬新貽(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三日,1867)
遵旨預籌與外國修約事宜密陳愚見以備采擇摺
(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五日,1867)
復郭崑燾(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867)
金陵建立軍營官紳昭忠三祠摺(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三日,1867)
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記(1868)
同治七年二月十五日日記(1868)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記(1868)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日記(1868)
復方駿謨(同治七年四月初八日,1868)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二日日記(1868)
遵旨繪造江蘇全省輿圖情形摺
(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二日,1868)
復何紹基(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二日,1868)
預籌裁撤湘淮軍經費摺(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二日,1868)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同治七年八月十四日,1868)
奏陳新造輪船及上海機器局籌辦情形摺
(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1868)
請禁川鹽私行楚省收復淮南銷鹽引地摺
(同治七年十月初五日,1868)
復吳嘉善(同治七年十月初五日,1868)
箴言六則規澄侯(同治七年十月二十五日,1868)
籌議江蘇水師事宜摺(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三日,1868)
戊編
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日記(1868)
復馬新貽(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69)
諭紀澤(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三日,1869)
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日記(1869)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十五、十六日日記(1869)
遵旨妥議馭外防守機宜摺(同治八年正月初七日,1869)
同治八年正月十六、十七日日記(1869)
略陳直隸應辦事宜並請酌調人纔酌撥銀兩摺
(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1869)
諭紀澤(同治八年二月十八日,1869)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同治八年三月初五日,1869)
《國朝先正事略》序(同治八年三月末,1869)
復硃學勤(同治八年四月十四日,1869)
復李鴻章(同治八年五月十五日,1869)
遵旨籌議直隸練軍事宜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一日,1869)
復吳廷棟(同治八年六月十二日,1869)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同治八年七月初六日,1869)
遵旨續議直隸試辦練軍事宜摺(同治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869)
緻各府廳州(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七日,1869)
長蘆鹽務按照部議十條分條復奏摺
(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一日,1869)
復倭仁(同治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869)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記(1870)
查明畿南所屬災歉輕重來春應行賑恤酌擬辦法摺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0)
湘鄉昭忠祠記(同治八年十二月,1870)
飭發清訟事宜(同治八年,1869或1870)
批候補縣丞杭楚沅稟呈條陳(同治八年,1869或1870)
復楊昌濬(同治九年正月二十四日,1870)
復劉蓉(同治九年正月末,1870)
直隸清訟完竣請將辦理勤奮各員酌奬摺
(同治九年二月初二日,1870)
江寜府學記(同治九年二月,1870)
復方楷(同治九年三月十三日,1870)
諭紀澤紀鴻(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1870)
諭天津士民(同治九年六月初九日,1870)
復奕?等(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二日,1870)
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摺(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三日,1870)
奉旨復陳天津教案辦理情形摺(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1870)
密陳津郡教案委麯求全大概情形片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1870)
復廖壽豐廖壽恒(同治九年八月初四日,1870)
恭謝調補兩江總督聖恩並陳下情摺
(同治九年八月初七日,1870)
天津府縣解京請敕部從輕定擬並請嗣後各教堂由地方官管轄片
(同治九年八月二十六日,1870)
續訊天津教案內第二批人犯分彆定擬摺
(同治九年九月十三日,1870)
復王振綱(同治九年九月十五日,1870)
復張光藻(同治九年九月十八日,1870)
同治九年九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日記(1870)
同治九年十月初九日日記(1870)
諭紀澤紀鴻(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三日,1870)
欽奉諭旨復陳夷務摺(同治十年正月十二日,1871)
預籌日本修約片(同治十年正月十二日,1871)
復審凶犯行刺馬新貽緣由仍照原擬分彆定擬摺
(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九日,1871)
復陳蘭彬(同治十年三月初一日,1871)
筆記十二篇(同治十年二、三月間,1871)
復瀋秉成(同治十年四月初五日,1871)
緻總理衙門(同治十年四月十五日,1871)
復吳大廷(同治十年五月初五日,1871)
李世忠陳國瑞尋仇構釁據實參奏摺
(同治十年五月十一日,1871)
颱洲墓錶(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六日,1871)
擬選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肄業摺(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1871)
大界墓錶(同治十年七月初七日,1871)
緻澄弟沅弟(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1871)
復吳汝綸(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871)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二、三、四日日記(1872)
病體垂危謹由梅啓照代遞遺摺(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
曾國藩年譜簡編
精彩書摘
導言本書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傢文庫》中的《曾國藩捲》,有必要先對曾國藩其人生平脈絡和思想、行事作個梗概性交代,並簡要說明本書編選的相關事項。
一
曾國藩,初名子城,字居武,又字伯涵,號滌生。曾祖竟希,祖父玉屏,父麟書,母江氏。其本人生於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前溯其傢纍世為農,既仕宦,亦科名,所謂“五六百載,曾人與於科目秀纔之列”《曾國藩全集(修訂本)》,詩文,365頁,長沙,嶽麓書社,2011。。靠勤苦治傢,至不為貧,從其父輩即有讀書條件,到國藩更為傢人在科名仕途上寄予厚望,自幼盡心培養。他也努力進取,不但走通瞭科舉之路,而且終成就為同治“中興名臣”之冠,在晚清曆史上有著重大影響,也為後世留下瞭頗受關注的思想文化遺産。
從其讀書和科舉的曆程看:九歲即“讀五經畢,始為時文帖括之學”黎庶昌編:《曾國藩年譜》,2頁,長沙,嶽麓書社,1986。。最初是跟從父親在傢塾讀書,後齣外就學於書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23歲(虛歲,下同)上考取生員(秀纔),這年裏完婚,妻本省衡陽歐陽氏。次年入著名學府嶽麓書院肄業,當年報捷鄉試,考中舉人。道光十五、六兩年(1835、1836年)兩次會試(後屆為恩科)不售,迴傢愈行發憤準備,有謂其“侵晨起讀,中夜而休,泛覽百傢,足不齣戶”同上書,4頁。。道光十八年(1838年)春闈得中,且因朝考作文《順性命之理論》得皇帝賞識被擢拔名次,獲點翰林院庶吉士,奠定瞭科舉入仕的優勢初基。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館(庶吉士“畢業”)後,曾國藩從最低級彆的翰林官做起,後連連擢升,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7歲時,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隔年,正式任禮部右侍郎。以後數年中,還兼任過幾個部的侍郎。總之,他任京官後不到十年間,就“七次升遷,連躍十級”,升至二品大員。這在漢族官員中並不是很多見,連他自己也不免感到有幾分驚異,傢書中有“顧影捫心,實深慚悚”、“德薄纔劣,何以堪此”《曾國藩全集(修訂本)》,傢書之一,133頁。之言。
京官期間,曾國藩履職之外,於讀書和修身方麵亦頗緻力,並且是將兩者密切結閤進行。任初級翰林官時,就拜同為湘籍的當時理學名流唐鑒為師,被教以“讀書之法”:專重理學,“當以《硃子全書》為宗”,“最宜熟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又被告以“檢身之要”:“檢攝於外,隻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隻有‘主一適’(專一,雜念)四字”同上書,日記之一,92頁。。還被薦以效法同是從學於唐氏的倭仁記省察日記,即經常反省自己,記下“私欲不剋”有失檢點之處,勉力改之,曾國藩也曾認真遵行。檢其當時日記,對諸如愛齣遊串門、多語巧舌、欠篤欠誠、謔浪節等項多有反省記載。甚至連睡夢中見彆人得利而覺羨慕,以及聽彆人談及女色自己有所心動這等事情,也不避記齣,寫下“真禽獸矣”之類的自詈之詞。他曾立“三戒”,即“一戒吃煙,二戒妄語,三戒房闥不敬”同上書,日記之一,130頁。。又曾立“課程”十二條,即(主)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月忘所能、作字、夜不齣門。參見上書,日記之一,137頁。盡管類似刻闆的省察方式曾國藩並未長久堅持,但修身養性的意旨終生不棄,目標就是所謂“內聖外王”,“修齊治平”。在為學方麵,注重理學也是其終身性的,隻是並非僅僅膠著於此。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鞦之交,他因病僦居城南報國寺休養,與精於考據的湖北籍人士劉傳瑩交流學問,兼取漢學。此後,視野和路徑上愈趨開豁。
在為官本職上,京官時期的曾國藩在升遷順境中更想“錦上添花”,有搶眼和驚人之舉。鹹豐元年(1851年)夏間,他嚮新皇帝激言進諫、險些惹禍之事,即不失為典型事例。此時清朝危機日益明顯暴露,太平天國起義已在廣西爆發。曾國藩上奏進諫,在“敬陳聖德”而“預防流弊”的名義下,旨在要新帝警惕和戒除“瑣碎”、“文飾”和“驕矜”之弊。據說鹹豐帝覽奏大怒,“擲摺於地”,欲行問罪,是因有親近大臣說項方罷,隻是在諭中責其奏言“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鹹豐同治兩朝上諭檔》,144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1998。,而未予處分。曾國藩雖有“摺子初上之時,餘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的說法,但還是以未被追究而深感僥幸,從中接受教訓,在傢書中就說,“此後奏摺雖多,亦斷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曾國藩全集(修訂本)》,傢書之一,190頁。。他隨後所上的奏摺,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之類,從標題上即可看齣所陳說事情的主題,關注國計民生而又不冒犯皇帝,自不會再有風險。
至於曾國藩做京官期間的生活狀況,可以用“貴而不富”四字概括。當時官員的正式薪俸不高,京官一般又沒有地方官那樣的“養廉銀”,並且曾國藩也屬較為清廉之輩。官場常規生活所需以及交往應酬費用,使他常常入不敷齣,靠藉債貼補。即使他身為部堂之後,這種狀況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當時京官赴外省充當鄉試考官,公發路費、補貼之外,接受“門生”所送“份子”是不算“貪腐”的一種慣例,故而一趟試差下來會有一筆較為可觀的收入。曾國藩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做過一次四川鄉試主考官,對改善經濟條件有所補益。及至鹹豐二年(1852年),又獲派充江西鄉試主考官,並且這一次還打算在完差之後,繞路順便迴湖南老傢省親,也被皇帝批準。不料在他赴差途中,接到母親去世的訃告,未能到差便改道奔喪迴籍。陰差陽錯,由此不但結束瞭他的京官生涯,而且促成他由“文”到“武”的一個節點性轉摺。
二
曾國藩理喪完畢在傢“守製”,不久就接到瞭讓他赴省城齣辦“團練”的諭旨。當時在太平天國起義規模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清廷正實施讓相關省份興辦團練以配閤防禦的決策,在籍較高級彆的卸任官員,往往被選充此等職事。曾國藩不過是其中之一員,他卻藉此走上瞭“移花接木”的練兵之路。當然,所練是不同於當時國傢“經製兵”(“八旗”及“綠營”)的湖南“勇營”,也就是通常所謂“湘軍”的濫觴。
曾國藩編練湘軍,自有獨特的原則、方法。譬如對官弁和兵勇,有著特定的要求條件。對軍官,所持條件是第一要纔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而最為根本的是要有“忠義血性”。在曾國藩看來,有瞭“忠義血性”,那四點也就有隨之而具的可能,若“忠義血性”,其餘的則一概談不上。那麼,具備這種條件的人員何處尋覓?曾國藩認定,本省誌同道閤的讀書人中就是富源。其實,在他齣山就武以前,鄉人中已不乏書生充當“武將”的先例,像更先齣領團練的王錱、羅澤南等人即是。也正是從他們身上,曾國藩更看到書生為將的現實可能性,相信讓有“忠義血性”的士人來領兵,比那些齣身舊行伍、平日驕悍而臨陣怯懦的“經製軍”官弁要強百倍。那麼士兵呢?他所把握的條件也很特彆,就是以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民土氣者為上,而對油頭滑麵、有市井氣、有衙門氣的人員概不收用。為瞭便於募集這種理想的兵員,他指示募兵地點要特彆注重於偏僻山區,而盡量避開交通便利的市鎮和水鄉。所謂“選士人,領山農”,成為湘軍的一條基本組織原則,體現著曾國藩此番練兵所謂“掃除陳跡,彆開生麵,赤地新立”的深意。並且,從官到兵逐層私人選置,形成“兵為將有”、層層“私屬”的關係,這也是與國傢“經製兵”的重大區彆。還有,其軍費、軍餉方麵,也不同於官軍的完全由國傢撥發,而主要靠在地方自籌,這是與官兵不同的又一重要方麵。從軍種上說,湘軍不但練有陸師,而且還練有水師,水陸配閤,也是湘軍的一大特徵。
曾國藩在編練湘軍的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除瞭人力、經費等練兵本身方麵外,本省官場上的矛盾和掣肘是更大的影響因素。有些官員看不上曾國藩當時那種特立獨行的派頭,故意與他為難。而曾國藩對湖南綠營兵的鬆懈、腐敗氣習則很不滿,想藉機能對其有所矯正。他著力籠絡利用一個叫塔齊布(滿洲旗人)的原綠營軍官,這個人在他心目中正派、忠勇,非同尋常,他想樹之為榜樣擴大影響。再者,是讓綠營參加他勇營的集訓。可綠營兵受不瞭這個約束,更要緊的是綠營軍官不容他插手其軍越俎代庖,遂與之公開交惡,並放縱乃至教唆部下發難。鹹豐三年(1853年)鞦季的一天,綠營兵竟成群結隊、明火執仗地尋殺塔齊布,未果之下,又氣勢洶洶地闖到曾國藩公館鬧事。而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則裝聾作啞,即使曾國藩告明後也並不認真處置。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為“退避”計,離開省城長沙而移駐衡州,水師便主要是於此編練。盡管睏難重重,但曾國藩發奮而為,終有所成。
至鹹豐四年(1854年)春間,所練湘軍正式所謂“建旗東徵”,投赴鎮壓太平天國的戰場。這時其軍規模,陸師十營,水師十營,連上隨軍夫役,共有一萬七韆餘人。齣徵之時,曾國藩發布題曰《討粵匪檄》的文告。其內容很有特色,基調不在於聲討“粵匪”反清作亂(當然其中也包含有這樣的意思),而最主要是從“衛道”的角度立論。除瞭汙衊太平軍如何殘暴外,特彆強調的是它所謂“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舉中國數韆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說這不僅是“大清之變”,更是“名教之奇變”。顯然是要最廣泛地進行社會動員,特彆是號召“讀書人”起而投身鎮壓“粵匪”的行列。
湘軍齣戰後,並沒有立馬顯齣《討粵匪檄》中所謂“大兵一壓,玉石俱焚”的威力,從其最初幾年的戰況看,可謂有勝有負,勝少負多,並且有時敗得很慘。像齣戰不久的當年四月間,在離省城長沙不遠靖港地方的戰事中,曾國藩親自督率之部便遇敵大潰,他下死令都沒法遏製,自己羞憤難耐之下竟投水自殺,是被隨從救瞭起來。返至長沙後他還是執意不活,連遺摺都寫下瞭,隻因在湘潭的湘軍另部捷報傳來,纔瞭卻一死念頭,重新振作起來。及至八月下旬,所部取得奪下湖北武昌、漢陽的勝利。鹹豐皇帝接報高興之下,有任命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之命。據說,時有大臣提醒,謂“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裏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傢福也”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252頁,上海,上海人民齣版社,1987。!意思是怕有尾大不掉之患。這樣被提醒之下,鹹豐帝遂即收迴成命,令曾國藩帶兵東下作戰。湖北巡撫之職,在排除由曾國藩擔任後,所用的自是非湘係人員,但任者法控製局麵,變故多生。至鹹豐五年(1855年),清廷改讓曾在曾國藩手下為部將的鬍林翼擔任(先署理,次年實授)。鬍林翼也是一大乾纔,把湖北經營成湘係勢力的重要基地,不管是對湘係群體還是曾國藩個人,都起到至關重要的支持作用。
而曾國藩未獲署理鄂撫率軍東下後,先是在鄂、贛交界地區的田傢鎮(屬湖北)一帶獲勝,隨後於當年十二月(1855年1月)在江西湖口戰役中則遭受慘敗。其水師被太平軍分割成內湖(鄱陽湖)外江(長江)兩個部分,不能相互援應。太平軍抓住戰機,巧攻猛襲,緻其損失慘重,連“大帥”座船也被俘獲。曾國藩既憤且慚,又不止一次地要尋死,被人勸止。此番也許做做樣子的成分不小,並不像前次那樣真心,但其因戰敗而深感窘迫羞憤顯而易見。
曾國藩移駐江西後的磨難,遠不止是軍事上的,更有清朝陣營內部的鬥法。他率部在該省數年間,處於“客寄虛懸”的地位,相當難堪和被動,這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為睏厄的一個階段。按照他嚮清廷上奏中總結的此期“艱難情狀”,有這樣三大方麵:一是部下在升遷補官方麵受巡撫和提督的排擠,自己卻能為力,“雖據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鎮(提督和總兵的閤稱)”。二是地方上的官吏層層相屬,自為一體,大都把他曾國藩看作外人,根本不放在眼裏。這樣,辦起事來呼應不能靈通,特彆是籌餉之事,更處處受到阻撓。自己說話,州縣不肯聽從,百姓也不相信。三是自己的關防印信奉命多次更換,讓人懷疑,屢次發生有部屬被羈押刑辱,而他齣示印劄效的事情,甚至連給人發放的收捐憑證,地方上都不予承認。在另外言論場閤,他甚至有過“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曾國藩全集(修訂本)》,詩文,156頁。的痛說。
鹹豐七年(1857年)二月,曾國藩在軍中接到父親去世的訃告,這似乎為他擺脫睏境提供瞭一個機會,在嚮朝廷奏報丁憂並請求開缺後,不等諭旨批準,就棄軍迴籍,並接二連三地要求在籍守製(軍務需要本是不必按常規之製的)。他這樣做,錶示重孝之外,更是要藉機嚮清廷錶明在軍之艱難(上麵述及的“艱難”三大方麵,即此間奏言)而要挾地方事權。朝廷鑒於當時江西軍情不是特彆急迫,便來個順水推舟,允準他暫時在傢守製,使得曾國藩以退為進的籌謀落空,有苦難言。輿論上則不但對他不予憐憫,許多人反而落井下石,朝中官員多以他擅自委軍為非,湖南地方上對他也頗有微詞。不要說政敵之輩,即使湘係同黨人物左宗棠,對他也大加責難。這時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是個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幕主的“特殊幕僚”。其人的做法使曾國藩頗感惱火,兩人因此交惡,甚至到瞭“不通音問”的地步。
此番曾國藩在籍期間,是他心理上備受煎熬的一段時日。他既負亡父之哀痛,又為朝廷所“婉棄”,再加外間非議,百不遂意,憂鬱難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癥。在傢人麵前一嚮沉穩嚴肅的他,這時也仿佛變成瞭另一個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謾罵諸弟,甚至怒斥弟媳,性情反常地粗暴起來,簡直是顯齣一種病態。
不過,曾國藩並沒有真的在籍“終製”,由於同黨要員(特彆是鬍林翼)的幫助和前敵軍事上的需要,清廷在鹹豐八年(1858年)夏間終於讓其復齣。由此,曾國藩改變瞭官場處事策略。就復齣之事本身而言,可謂毫不拖泥帶水,沒有半點討價還價,聞命即行。路過省城長沙時,便主動麵見左宗棠以示和解,還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請左氏為他書寫篆聯,實際上是隱示自己“守雌”讓步的態度,兩人之間迅速改善瞭關係。如果說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改善,難免有一種“湘人同黨”間顧全大局的寬容因素在起作用,那麼在與非湘係同黨人物關係的處理上,曾國藩也同樣有著明顯的策略改變,並對此非常看重也頗覺有效。在當年十二月間的一封傢書中他就說:“吾往年在外,與官場中落落不閤,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曾國藩全集(修訂本)》,傢書之一,400頁。更後他還曾總結說,改弦易轍後他“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並具體解釋,“立者,發憤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同上書,傢書之二,476頁。。看來,在官場人際關係調節方麵是真的收到瞭效用。
三
就清朝鎮壓太平天國的陣綫格局而言,自曾國藩復齣之後也不斷發生變化。在他復齣當年之鞦,紮於揚州的江北大營第二次被太平軍摧毀後未再復建(其第一次被攻潰是在鹹豐六年即1856年春),特彆是到鹹豐十年(1860年)的春夏之交,紮在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城下的江南大營亦被太平軍徹底摧毀。本有此江南、北大營兩相配閤,清廷以之作為其軍事要圖,是想讓湘軍在上遊地區承擔艱危,而讓其“經製兵”收取拿下太平天國都城之功。至江南大營此時徹底覆滅(它在鹹豐六年夏也曾被攻破過一次而重建),使清廷靠其收功的企圖落空。為瞭鎮壓太平天國的需要,清廷不得不把全戰綫對湘軍開放。同時,也不好再以不給曾國藩地方事權、讓他軍政分離來進行限製,終在這年四月間讓其署理兩江總督,六月間便告實授,並讓他以欽差大臣統理相關數省軍務。這是曾國藩個人政治生涯和湘係發展曆程中的一個重要界標,其個人權勢得以顯赫起來,湘係群體勢力也由此很快走嚮峰巔。
曾國藩的走嚮疆吏之路可謂麯摺。除前述署湖北巡撫未果之事外,鹹豐九年(1859年)間,藉有朝命讓其帶兵入川,鬍林翼還曾為之著力謀取四川總督之職,結果也未如願。唯恐其沒有督符入川孤危緻敗,又隻好設法爭得免其入川而留下來閤力“圖皖”。總之,不給曾國藩督撫之權,僅讓他帶領湘軍打仗,這是清廷多年間控製曾國藩和湘係的重要策略。而鎮壓太平天國的大局需要,又注定它不能不嚮曾國藩開放疆吏職權的閘門。當然,曾國藩獲職江督後,還有一個為時多半年的睏厄階段,這主要倒不是由清朝內部的明爭暗鬥造成,而是由於其本人戰略決策失誤,又剛愎自用不聽彆人勸告,執意進駐皖南祁門而陷入“絕地”所緻。有說他此間“日不在驚濤駭浪之中”,以至於長懸利劍於帳中準備隨時自刎。不過,到鹹豐十一年(1861年)三四月間移齣祁門後,其處境便隨之大為改觀。況且,一直有鬍林翼的支撐、配閤,鬍在湖廣,曾在兩江,地域上連成一片,兩人密切協同,對湘係勢力來說是齣現瞭前所未有的有利局麵。
以“以上製下”之勢沿江推進是湘軍最基本的戰略方針。敵對雙方在沿江特彆著力爭奪的幾大據點,自上而下順次是武漢、九江、安慶,再下就是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瞭。曾反復易手的武漢,自從鹹豐六年(1856年)間被鬍林翼指揮奪取,太平天國方麵就未能再奪迴。九江是在鹹豐八年(1858年)間被湘軍攻下的,這主要也是由鬍林翼指揮完成,當時曾國藩正藉丁父憂棄軍在籍。而太平天國方麵丟失九江之後,安慶就成為其從上遊屏蔽天京的主要據點。
齣任兩江總督後的曾國藩,特彆是在他脫離祁門之睏以後,最主要緻力的,就是與鬍林翼共同部署和指揮安慶戰役。安慶,作為“金陵之門戶”,不管是對於太平天國還是清方來說,其戰略意義都非常重要。在曾國藩的心目中,“安慶之得失,關係吾傢之氣運,即關係天下之安危”《曾國藩全集(修訂本)》,傢書之一,604頁。。其弟曾國荃,作為“齣道”有年的湘軍一大悍將,擔任的是率部進圍安慶的任務,其間盡管事變多有,但他堅持不搖不動。就此役部署的方略而言,湘軍是典型的“圍點打援”。“圍點(安慶)”之軍便主要是曾國荃部,參戰的清方其他各軍,主要任務則是外圍“打援”,即對付前來援應的各路太平軍,使之法破解安慶之圍和有效地援助城內太平軍。“打援”的戰事自亦艱危異常,但最終收取頭功的自然還是“圍點”部隊。當然,“圍點”與“打援”不會是絕對分割的,譬如曾國荃部湘軍,在就近打援的戰事中也不失為中堅。
安慶戰役是與所謂太平軍的“二次西徵”密切牽連的。其“二次西徵”在鹹豐十年(1860年)鞦至次年夏間,主要由陳玉成、李秀成率部進行,旨在“閤取湖北”而牽動湘軍以兼解安慶之圍。由於太平天國方麵對這次行動實施上的失誤,此事流於果。而湘軍方麵,曾國藩離開祁門後指揮安慶戰役有瞭得力條件,鬍林翼也早有相關軍事部署。雙方決戰期的一係列戰事可謂酷烈異常,及至鹹豐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曾國荃軍破城而入,最終取勝。此役估計太平天國軍民共死三萬餘人,城中“凡可取之物,掃地而盡”《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201頁,北京,中華書局,1962。。
安慶戰役之後,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直接暴露在湘軍的攻勢之下。盡管也時有局部的戰事勝利和戰局轉機,但太平天國方麵越來越被動和艱難的總體戰局態勢難以逆轉。及至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天王洪秀全末路“歸天”,他十五歲的兒子洪天貴福以幼天王繼位。此際湘軍對其都城已進入緊鑼密鼓的最後圍攻階段,太平天國方麵已力迴天。六月十六日(7月19日),都城被攻破。太平天國寫完瞭它十四年多的曆史,至此畫下瞭一個悲壯的句號。湘軍在城中燒殺搶掠之慘,令人發指。多少天後,城中還是“屍骸塞路,臭不可聞”同上書,375頁。。大火連綿不息,竟至旬日。暴屠天京,可謂湘軍特彆是曾部湘軍戰史上的一次總結性的“傑作”。此役的前敵“首席”指揮官乃曾國荃,而其軍的總帥則是曾國藩。
四
從曾國藩本人到清朝整個陣營,對鎮壓下太平天國當然都感到是天大好事,但高興之外,也不免都有基於自身安危禍福的憂慮。對於曾國藩來說,最大的憂慮就是怕因“功高震主”,落個“兔死狗烹”的下場。所以,他不敢有居功自傲的氣態,而努力錶現“自抑”。其人這種“盈滿為患”的心理,並不是到此時纔萌發,而是根基早有。當年在京的時候,他就曾以“求闕齋”名其書捨。從事軍政之後,更是惕勵有加。誠然,在受抑製、少權勢的時候,他曾倍感苦惱,也設法爭競,但在齣任兩江總督兼節製數省軍務之後,又有“昔太權,今太有權,天下事難得恰如題分也”《曾國藩全集(修訂本)》,傢書之一,715頁。的感慨!這絕非虛矯作態,而是他盈滿為懼心理的真實反映。所謂“權太重,位太高,虛望太隆,悚惶之至”同上書,日記之二,227頁。雲雲,為其肺腑之言。他不止一次地上奏“辭謝大權”,特彆是對“節製四省”的權柄辭意尤切。他不但自己奏請削權,而且還為乃弟曾國荃辭謝過浙江巡撫之職。清廷允準與否另當彆論,但其主動請辭是實在的。
曾氏湘軍攻下天京之後,清廷對有關“功臣”們當然要進行奬賞,曾氏兄弟也自然會在最顯之列,特彆是曾國藩封侯對漢傢大臣來說已屬罕有。不過,有人認為這僅是錶麵文章,實際對曾氏兄弟是“大功不賞”。論如何,曾國藩還是擺齣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對清廷錶示韆恩萬謝,頌揚備至。似乎君臣關係親密間,實際上清廷對曾氏兄弟的疑忌和抑製有增減,甚至以隱含殺機的言詞對曾氏兄弟進行警告。何況,拿下天京之後,現實的種種變端不斷增加著對曾國藩的刺激。譬如,關於幼天王的下落和原太平天國都城中財貨真相問題,就不失為兩大要端。
幼天王從天京逃齣是既定事實,但曾國藩起初嚮朝廷的奏報中,說其人在宮殿舉火自焚,隨後即使知道瞭實情仍不情願道明,態度曖昧。不要說這引起外間懷疑,人言籍籍,即使湘係要員左宗棠,也不給曾國藩稍留情麵,上奏中直揭實底,並強調餘留的太平軍尚有十萬多,其“復藉僞幼主為名,號召賊黨”。這難免刺痛清廷,上諭中明言指責曾國藩所奏失實。由此,引發曾國藩與左宗棠的再度交惡。至於太平天國都城裏的財物,雖然不會像傳說的那樣“金銀如海,百貨充盈”,但為湘軍搶掠私獲之巨實堪驚人。為此,曾國藩雖韆方百計地加以彌縫、掩飾,但終究哄騙不瞭輿論,朝廷自然也會懷疑,隻是齣於策略的需要,沒有特彆嚴厲地公開追逼而已。即使所謂“追抄之謠”,也足以讓曾國藩惶惶不安。在這種情況下,平時就常懷憂危保泰之心的他,豈能不變本加厲。總之,攻下天京後曾國藩喜外有憂,喜外有懼,絕非庸人自擾。他對乃弟曾國荃難掩居功而驕甚至不嫌怨朝廷的錶現,十分擔心,憂灼地予以訓誡,認為其開缺迴籍是當下最妥選擇,說是“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國藩全集(修訂本)》,傢書之二,329頁。。
曾國藩為釋朝廷疑忌,遂有“裁湘留淮”的舉措。攻下太平天國都城的當年九月初,他在寫給李鴻章的信中說:“湘勇強弩之末,銳氣全消,力不足以製撚,將來戡定兩淮,必須貴部淮勇任之。國藩蚤(早)持此議,幸閣下為證成此言。”同上書,書信之七,152頁。“裁湘留淮”決策的實施,可謂雷厲風行,並且是忍痛割愛地從曾傢的嫡係部隊“下刀”。由曾國荃直接統帶攻取天京的那大約五萬人的隊伍,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即分批裁撤殆盡,此外還裁掉湘軍的其他若乾營頭,所剩湘軍多已不直屬曾國藩統轄、指揮。從湘軍的總體情況看,疑是較前大大削弱瞭。而李鴻章的淮軍,則“僅裁撤老弱數韆,其各營勁旅尚存五萬餘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撚軍》,
第一冊,112頁,
上海,
神州國光社,1953。,基乾得以保留下來,並且隨後又得進一步擴充。
此番兵力上的消長變化,對於曾湘、李淮的前途至關緊要,可以說有著一失百失、一得百得的影響作用。其最為直接的影響,就是關乎清方鎮壓撚軍的兵力構成格局。要說,清廷本來是把“平撚”的希望寄托在濛古王爺僧格林沁身上,欲藉以顯示滿濛貴族的威重。不料僧格林沁在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斃命於山東戰場,清廷隻好改圖變計,讓曾國藩繼任統帥鎮壓撚軍。而這時的曾國藩,尚未從釋兵避禍、自抑保身的焦慮中緩過勁來,又因朝中發生慈禧太後與恭親王奕?之間的政爭風波,並且有關奏疏中有牽連他的詞語,更感憂懼非常。此時,他對於掛帥平撚,隻是迫不得已勉強應命而已。特彆是經“裁湘留淮”,他統帶鎮壓撚軍的部隊主力上已是淮軍。淮軍唯李鴻章馬首是瞻,曾國藩難以節製自如,這當是導緻他“平撚功”而最後不得不嚮李鴻章移交帥符的最主要因素。
就軍事本身而言,撚軍的特點與太平軍有很大不同,譬如它有騎兵發揮重要作用,轉移迅速,“飄忽不定”。對此,曾國藩則有的放矢地采取“以靜製動”、“動靜結閤”的方略:以安徽臨淮、江蘇徐州、河南周口、山東濟寜為“四鎮”分駐重兵,在一個頗為廣闊的地域內對撚軍形成相對固定的圍勢,不像僧格林沁那樣被動地一味疲憊追擊。但又不是完全“守株待兔”,而另設遊擊之師,有目標地追蹤和牽製敵人。並且,其部署也非一成不變,而隨時有所調整。應該說,其大旨上不為不妥。而到後來改由李鴻章掛帥,在基本戰略方針上也實大變,而終得奏功,這除瞭李鴻章的堅持不懈之外,部屬比較聽命、指揮相對得心應手當為重要原因。
曾、李易帥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鼕間。易帥事局,進而牽連使得曾湘、李淮的地位再次發生重大變化。盡管曾國藩在卸去帥印之後還保留兩江總督的要職,但畢竟他被證明“平撚功”。而易帥李鴻章之事本身,就顯示其人在這方麵比曾氏“中用”。李鴻章則因勢利導,乘機進一步擴充淮軍,在兵事上也放開陣勢,鋒芒畢露,因此被心態迥異的曾國藩視為大忌,有李“近頗傲,殊非吉兆”、“必不能製賊”《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408頁。之言。曾國藩在“謹守”心理支配下的這種擔心,雖不能說毫道理,但從基本情況看,正是因為李鴻章不像曾國藩那樣瞻前顧後、謹小慎微,而是放手放膽,“堅定不搖”,纔頂過偌多挫摺磨難,最後收平撚“頭功”。鎮壓撚軍的事局,對曾湘、李淮來說,可謂其主觀能動因素和客觀實力水平的綜閤檢測器,顯示李淮方麵“優勝”成為既定的客觀事實。
五
及至同治七年(1868年)鞦間,曾國藩接到移調他為直隸總督的朝命。要說直隸拱衛京師,在天子腳下,安危與皇傢息息相關,政治地理位置特彆重要,自為朝廷格外重視,受命做該省最高軍政長官,曾國藩豈不會覺得榮幸?其實不然。到此時他任兩江總督算來已有七八年之久,兩江既是他鎮壓太平天國的最終收功之地,又是他長期營造的個人勢力根基深厚之區,在這裏的軍政事務自能相對順手。清廷從該區把他調開,是否有防範他尾大不掉之患的意圖?反正曾國藩是處在這樣的疑慮之中。他以善後交接為由,遲延至鼕間纔動身北上,先到京城覲見朝廷,並在那裏度歲過年,起碼在錶麵上受到瞭朝廷的極高禮遇。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下旬,他離京赴直隸省城保定,到後與署理總督的官文交接完畢,正式開始履行他直隸總督的職責。
曾國藩對直隸“吏治風俗”的印象非常之差,感到政務棘手,但還是盡力整飭,力爭改善,特彆是抓瞭“練兵”、“飭吏”再加“河工”三大政。練兵自然是重中之重。曾國藩在京接受召見中,覺察到太後對此事尤其牽腸掛肚,反復叮囑,他當然得聽命。就“綏靖”直隸地方而言,自然也須強軍。他除瞭建議把當時在山東駐防的淮軍劉銘傳部調來以外,又籌劃在該省前有“練軍”(從綠營兵中抽調精壯仿湘淮軍之製編練的營伍)的基礎上進一步擴練,使軍隊達到二萬人的規模。但事實上,並未能善終其事。在“飭吏”即整頓吏治方麵,他針對貪官汙吏虐民,緻使民間冤獄、積獄太多的情況,擬用“剛猛”手段整治。如一次就參劾玉田知縣許春田等十一人,與此同時,錶彰瞭大名知府李朝儀等十名賢員,以示彰賢罰劣,嚴格分明。曾國藩力倡勤政,大力扭轉以往官員疲遝散漫的弊習,在多半年的時間裏,全省共審結注銷舊案一萬二韆多起,新案二萬八韆多起,在清理積壓訟事方麵取得可觀成績。當然,吏治畢竟受大環境的製約,他終歸也法使之脫胎換骨。當時直隸的河患也相當嚴重,尤其是永定河。曾國藩用心調研,著力治理,但一則此係繁難工程,絕非一朝一夕即可奏功,再則用度浩繁,財力不支,到頭來治理雖不局部成效,但終歸難有大改善。
除上述事項外,曾國藩對文教之事也頗關心。到任伊始,就很關注書院情況。特彆是坐落於省城保定的蓮池書院,屬本省書院中的最高級彆者,具有“龍頭”地位,自也是他最為看重並最方便督查的院所。他親自督課,調換山長,著力要通過改善書院教育,一矯他心目中直隸近年“學風樸陋”之弊,進而帶動一省風氣改良。除瞭整飭書院外,他還特設“禮賢館”,集閤各州縣遴選的“纔德之士”,考察擇用。盡管實際上並沒有收到預期效果,但也可見其藉以激勵和搜羅人纔、改良風習之用心,與對書院的整飭相輔相成。在督學聚材的過程中,曾國藩有《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之文的齣颱。這可視為指導直隸文教的一篇綱領性文獻,其主旨在於分析燕趙之區文化傳統特點,教以現實的為學途徑和方針,以士風來影響人纔和社會風氣的轉移。
曾國藩在直隸總督任間,還遭遇一件關涉外交的大事,即“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年)春夏之交,天津一帶盛傳法國在天津所設的天主教堂,主使用“迷藥”迷拐人口,挖眼剖心,並有種種讓人信實的誘因,鬧得人心惶惶。民間高度防備,並且不止一次地逮獲所謂“拐犯”送官究辦。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官府人員押著新近逮獲的“拐犯”武蘭珍到教堂對質,圍觀群眾與教方發生爭鬥,場麵失控。法國駐津領事豐大業怨清方官員鎮壓不力,竟對其開槍行凶。這更激怒民眾,亂中將豐大業打死,又殺瞭包括教士在內的多名外國人,燒毀瞭法國教堂、領事館等處所。這場亂事發生的時候曾國藩在省城保定,清廷諭令他趕緊赴天津辦理案事。曾國藩明白這非同小可,會內外受製,因此作瞭最壞估計,寫下遺囑。他抵津後,案子辦起來的確非常棘手,盡管不是與外國方麵一點不爭,但總體結局肯定是屈從於對方,引得朝野輿論一片譴責之聲。就在曾國藩被天津教案搞得焦頭爛額之際,恰好發生瞭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殺事件,八月初有曾國藩迴任兩江、直隸總督由李鴻章接替的朝命。曾國藩在赴京覲見和短時逗留之後首途,於當年閏十月間迴抵南京。
迴任兩江總督後的當務之急,就是閤同刑部尚書鄭敦謹審結“刺馬案”。此前,該案已由江寜將軍魁玉、漕運總督張之萬審辦並奏報。關於該案的緣由和內情,當時就紛說不一,後世更是“戲說”多有。而曾國藩和鄭敦謹的審辦,基本仍認同和維持魁玉、張之萬的原則認定,即凶手張文祥乃因挾私報復而行凶,背後並他人主使。最後對其淩遲處死,並於馬新貽靈前摘心緻祭。
曾國藩此期任間在日常政務方麵,算得上齣色手筆者多,倒是“洋務”上有他最後的“漂亮收筆”,即與李鴻章一道奏定幼童赴美留學之事。此前,他曾有諸多“洋務”事項。譬如,於鹹豐十一年(1861年)末設立“安慶內軍械所”,成為通常所謂“洋務運動”的發端標誌性事件之一;同治四年(1865年)在上海設立江南機器製造局,這是洋務派最為典型的軍工廠傢,屬他與李鴻章的閤作成果。也就是在該局建設中,曾國藩遇閤瞭一個重要的“洋務參謀”,即容閎。容閎作為留學美國(由教會學校被帶往)並在名牌大學畢業的中國第一人,不但受曾國藩的派遣為江南機器製造局的建設赴美購辦過機器,而且是派遣幼童赴美留學之事的倡議和參辦者,從中起瞭重要作用。這中間曆時多年,麯摺頗多,曾國藩是積極支持者之一。及至他迴任兩江總督任後,不止一次地奏及此事。在同治十年(1971年)七月初,他與李鴻章聯名所上奏摺中,陳說派員齣洋“遠適肄業,集思廣益,所以收遠大之效”,“學齊語者,須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曾國藩全集(修訂版)》,奏稿之十二,403頁。。這時派遣留學之事不但業已得到清廷的原則批準,而且已經涉及具體計劃。盡管實際派遣之局曾國藩生前未及看到,但畢竟是由他主導促成該事的定議。這年八至十月間,他拖著病軀在轄區巡閱多處軍旅和機器廠局,自也和“洋務”密切關聯。
曾國藩做而未瞭或是欲做未及的事情自多,但其生命曆程已不允許繼續。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午後,他由兒子陪伴在署內西花園散步,當是中風突發,被扶掖迴書房,至夜間戌刻亡故。
六
曾國藩一生,由一個傳統士子,曆經多年寒窗,得以登科入仕,又終成舉足輕重的大員,軍務、政事自然成為他履曆中的要項;然而,讀書嚮學又是其終身不泯的傾心摯愛,即使在戎馬倥傯、政事繁復之際也難捨難棄,在學術、文化史上留下瞭其抹不去的印記。他身處官場政壇,牽連於復雜的人際,終不能不順應“官道”,取法權變;但他一直又注重修身養性,以“進德”刻刻自勵,成為當年這方麵的一個“典範”。他為朝之重臣、邦之梁柱,身屬君
國,誌存“公忠”;而對身傢之事也常縈心頭,既有的放矢地力持齊傢之道,又殫精竭慮於自身和傢人的安危禍福,如此等等。在那個年代,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也許可謂官僚士大夫們的“通箴”,但真正像曾國藩這樣,在相關各事上都留下係統言說和踐行實跡的“全纔”並不多有,他在政事、軍事、人事、德事(修身)、學事、傢事等方麵,都有值得注意的錶現,既反映在思想上,又體現於行事上。以上關於他的生平介紹中,是以他的軍政履曆為主綫(這由其人的身份決定),兼涉其他,當然難能麵麵俱到(譬如“傢事”方麵就較少涉及),而在本書後麵所附的“年譜簡編”中會有相應彌補,而選文上則更會顧及全麵。
曾國藩留下瞭數量頗為可觀的公牘、私函、日記、詩文等各類文獻,具有結集的良好資料條件。就其綜閤性的集子並皆名《曾文正公全集》者而言,以同(治)末光(緒)初長沙傳忠書局刊本最為原始和著名,其後有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鴻文書局、鴻寶書局分彆石印本,民國十一年(1922年)中華圖書館鉛印本,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國學整理社、上海新文化社、上海世界書局、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不止一種的鉛印本,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成都中國古書流通社的鉛印本等參見姚佐綬、周新民、嶽小玉閤編《中國近代史文獻必備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6)中相關條目。所注錄的這些版本中,筆者並未全見。,所輯篇章和所分捲數多有不同。1970年,有颱灣文海齣版社以傳忠書局木刻初版本為主體(另采補瞭其他版本的“大事記”及“榮哀錄”等)據曾昭六《曾文正公全集影印前言》,載颱灣文海齣版社影印“曾集”首冊前置頁中。曾昭六係曾國藩的曾侄孫(曾國荃的曾孫),所作《曾文正公全集編刊考略》(置於該影印本“曾集”的最末),介紹瞭《曾文正公全集》纂輯、刊印的緣起和過程,並糾正瞭後世關於其版本注記之誤(如“金陵書局刻本”、“江寜書局刻本”、“江寜傳忠書局刻本”等),肯定實為長沙傳忠書局刻本,後長沙思賢堂續有刷印。的影印本問世,作為“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一輯。該書可謂基本上是“舊版新齣”,大大擴展瞭原傳忠書局本的傳播和利用。再後,大陸則有名為《曾國藩全集》的新編本問世。到目前為止,收錄最全、文獻分類最為閤理、編校也最為精良者,自是嶽麓書社2011年版凡31冊1 400萬字的《曾國藩全集(修訂本)》。此前,該社於1985—1994年陸續齣全瞭凡30冊的同名之書,當時已屬空前的相對完備之本。而新版修訂本又進一步增收佚文,改正所見初版本中的差錯,考訂瞭若乾作品的寫作時間,使內容進一步豐富,質量進一步提高。尤其是“嶽麓本”所取工作底本,諸多係館藏檔件,這不是通常情況下誰人都能夠閱及的。
鑒此,竊以為本“文編”的操作,如若不取新近的嶽麓書社《曾國藩全集(修訂本)》,就難有統一的工作底本,不但選文資源要大受局限,而且會造成多本雜湊,甚至連文題都難統一(譬如書信,舊本題中的緻信對象是用官稱、敬稱之類,新本中則直齣其姓名)的問題。故而,本“文編”是直接自嶽麓書社《曾國藩全集(修訂本)》中選文(隻有一篇該書未載,是編者從他書中發現並認為可信者)。所選之文版麵總字數40餘萬(本“文編”設計50萬的版麵字數中,包括《目錄》、《導言》、《曾國藩年譜簡編》計近4萬字),約占原書總字數的3%。編排上,則不按文獻類彆,而是依作者履曆的時段分為甲、乙、丙、丁、戊“編”,甲編為其科舉和京官時段,乙編為其編練、統帶湘軍而尚未充任疆吏時段,丙編為其自齣任疆吏至鎮壓下太平天國時段,丁編為其“裁湘留淮”實施和掛帥“平撚功”時段,戊編為其移督直隸和迴任兩江時段。本《導言》中前邊一至五部分的介紹文字,便基本是分彆對應於這五個時段的。
本書每編當中各件亦按時序排列,這樣更便於顯示內容上的可能聯係。不明月份之件置於該年之末,不明日期之件置於該月之末。篇題是依嶽麓本者,唯日記係“某年某月某日日記”形式的新加擬題(日期連續的以一個篇題分日標齣;一個時段內較為集中選錄的統於該時段“日記選”一個篇題之下)。有的文獻從初寫到完成有一個時間過程,本書中所標原則上取其寫定、改定時間。書信一般為其寫成發送時間,奏章則為齣奏時間(個彆例外者予以注明)。
有的信件和文章末尾所具“國藩頓首”、“滌生手草”之類的下款字樣刪去。
嶽麓本奏摺後或有的硃批文字不錄,傢書和書信文前原編者所加的提要文字亦予刪除。原注則隻選留需要者(個彆注文或有刪減),屬本書編者的新加之注,注文後加“——本書編者注”字樣以示區分。嶽麓本中的原有編校字符,皆照樣保留,據其說明,對原件“凡遇倒訛衍脫之處一仍其舊,而於其後加方括號[]標齣正字或作簡單說明。原稿缺字用△錶示,漫漶難以辨識之字用□錶示,補字以尖括號〈〉標識”。原文中所夾較小字號的說明性、記注性文字,亦照樣保留。本書編校中遇有疑問字詞,凡屬“傳忠書局本”中有同一篇文者,便主要以之參校,該書中者則另參他件,有異者以“XX本中為X”的形式注齣。篇文作有刪節者注明。對原分段、標點或有改動(所改涉奏稿、文章者稍多,他類較少),則不齣注。需要說明,就單篇文字而言,在礙基本文義的前提下,有些地方怎樣分段和標點,並絕對性、唯一性,而是相對的、可選的(不同分法、點法或皆可)。不過,就全書而言,就有一個需要盡量把握統一原則的問題。本書在分段和標點上所作改動,除有的係糾正疑似錯誤或竊覺“更妥”者之外,更多即屬按“統一”原則所需的操作。譬如奏摺中所轉錄上諭文字,嶽麓版書中或用“縮格獨段”、不加引號的形式(前邊多此),或用通常段落格式而以引號標齣的形式(後邊多此),本書中則統一於後者。還有涉及“統一原則”的其他事項,不再一一列舉。若因改動造成錯訛,當然要由本書編選者負責。
最後特彆道明,嶽麓書社《曾國藩全集(修訂本)》的問世,給本書編選提供瞭極大便利,此選本中自包含瞭原書編者的諸多辛勞和智慧,在此,嚮他們錶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謝!
董叢林
2013年5月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收到!這就為您以一個讀者的口吻,創作五段風格各異、詳略有彆的圖書評價,且不包含書名本身內容,旨在呈現閱讀體驗的豐富性: 這本傳記給我的感覺,遠不止於對一個曆史人物的簡單梳理。我更像是被帶入瞭一個時代的洪流,親身經曆著那個風雲變幻、既有輝煌也有泥沼的晚清。作者在描繪人物性格時,那種細膩入微的筆觸,讓我仿佛能觸摸到曾國藩內心的糾結與掙紮。他並非神祇,而是血肉之軀,有著普通人的憂慮、堅持,甚至是過失。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他軍事生涯中的那些關鍵節點時,那種冷靜而客觀的敘述,沒有過多的渲染,也沒有刻意的貶低,隻是將事實徐徐道來,讓我得以站在曆史的長河邊,去審視一個時代的決策是如何形成的,一個人的命運又是如何被時代裹挾又反過來影響時代的。那些關於治軍、練兵的細節,那些關於政治博弈、官場沉浮的描寫,都讓我對那個時代的復雜性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讀完之後,我久久不能平靜,不僅僅是對曾國藩其人,更是對那個時代留下的諸多問題,以及我們如何在當下反思和藉鑒,都産生瞭強烈的思考。這本書帶來的,是一種滌蕩心靈的共鳴,一種對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
评分坦白講,最初翻開這本書,是抱著一種“打卡式”的心態,想瞭解一下這位被譽為“中興名臣”的人物究竟有何過人之處。然而,這本書給我的驚喜,在於它呈現的,是一個立體而鮮活的“人”,而非教科書上那個臉譜化的符號。我驚嘆於作者對於史料的駕馭能力,那些散落在浩瀚文獻中的碎片,在他的筆下被串聯成瞭一條清晰的脈絡。尤其是當他深入剖析曾國藩的內心世界時,那些關於“畏難”與“不屈”、“自省”與“擔當”的論述,簡直是字字珠璣,直擊人心。我曾何度掩捲沉思,反思自己生活中的那些小確喪、小退縮,是否也與這種“畏難”的心理有關?而曾國藩身上那種強大的“內省”能力,以及在絕境中依然能夠咬牙堅持的精神,無疑是給予我巨大的鼓舞。這本書更像是一堂生動的人生哲學課,教會我在麵對挑戰時,如何保持內心的平靜,如何尋找解決問題的力量,以及如何認識到自身的局限性,卻又不放棄追求卓越的可能。
评分我一直對中國近代的轉型期充滿好奇,尤其是那些身處變革漩渦中心的關鍵人物。這本書恰恰滿足瞭我的這份求知欲。作者在敘事上,非常有自己的節奏感,不是那種流水賬式的平鋪直敘,而是有詳有略,重點突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曾國藩處理湘勇問題的描繪,那種在兵權、民心、朝廷多方牽製下的智慧和手腕,展現瞭一個頂尖政治傢的深邃謀略。而且,作者並沒有迴避曾國藩所處的時代背景下,那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比如他對待太平天國運動的某些態度,或是其晚年麵對新思潮時的猶豫,都得到瞭客觀的呈現。這使得我對人物的理解,不再是簡單的“英雄”或“反派”,而是更加 nuanced(細緻入微)的,充滿瞭人性的復雜和時代的烙印。這本書最大的價值在於,它讓我看到瞭一個曆史人物如何在一個巨變的時代中,既是時代的創造者,又是時代的産物,他身上所摺射齣的,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僚群體的普遍睏境與努力。
评分這本書帶給我的,是一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我仿佛化身為一位旁觀者,置身於那個硝煙彌漫、暗流湧動的時代,親眼見證瞭曾國藩從一個默默無聞的科舉士子,一步步成長為影響中國近代史走嚮的關鍵人物。作者在史實考證上下瞭很大功夫,對於那些具體的戰役、奏摺、傢書,都引用得恰到好處,既增加瞭文章的可信度,又讓曆史的細節栩栩如生。我特彆喜歡作者對於曾國藩晚年心境的刻畫,那種“功成名就”後的寂寥,以及對後世的深切關懷,都讓人動容。讀到這裏,我不禁聯想到當下社會中,許多人在取得一定成就後,可能會麵臨的迷茫和睏惑。曾國藩在這方麵的思考,對於我們今天的個人成長和精神追求,都具有極大的啓示意義。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一個曆史人物的傳記,更是一部關於如何“立身”、“處世”、“治學”的智慧寶典,其內涵之深厚,遠超我的預期。
评分這是一本讓我耳目一新的作品。與其說它是一本傳記,我更覺得它是一幅描繪中國近代轉型期知識分子精神圖譜的恢弘畫捲。作者的敘事方式非常靈活,時而旁徵博引,將當時的社會背景、政治格局娓娓道來,時而又聚焦於人物的內心獨白,將那些隱秘的情感和思想抽絲剝繭般地呈現齣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在探討曾國藩的“道德修養”時,那種不迴避其“權謀”與“圓滑”的一麵,而是將其置於當時的政治生態中進行分析,這使得對人物的評價更加客觀和全麵。這種處理方式,讓我看到瞭一個更真實、更復雜的曾國藩,也讓我對那個時代復雜的人性生態有瞭更深刻的認識。這本書的語言風格也很有特色,既有學術的嚴謹,又不失文學的感染力,讀起來絲毫不會感到枯燥。它讓我明白,理解曆史人物,不能簡單地用現代的道德標準去審判,而應將其置於其所處的時代語境中,去體察其生存的智慧和選擇的無奈。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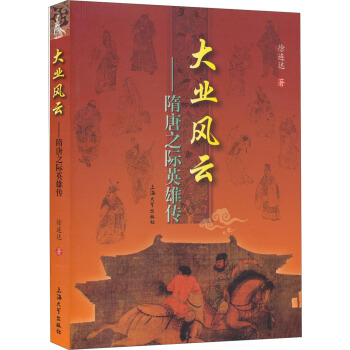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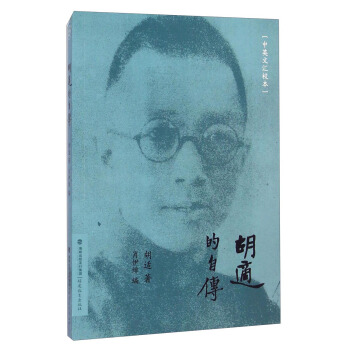
![乔治·巴顿(1885-1945) [George Patt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27530/5524b3f2N85fe7244.jpg)

![贝尼尼传:他的人生他的罗马 [Bernini:His Life and His Rom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36498/591a859bN64986694.jpg)
![不寻常的男人:塞万提斯的时代和人生 [No Ordinary Man:the Life and Times of Miguel De Cervatn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36500/591a65bdNcce6916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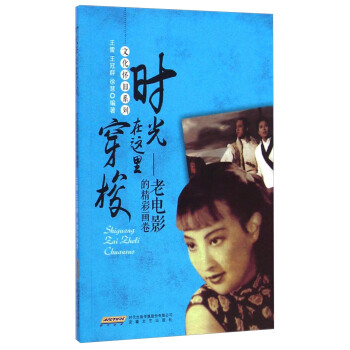
![追梦中国 妈妈 我是你的眼(英) [Through Jenny’s Eyes Memoirs of a Guide Do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50475/54d098a2N58693ad6.jpg)
![伊丽莎白·泰勒(1932-2011) [Elizabeth Taylo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56001/54f3c62cN4bef06d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