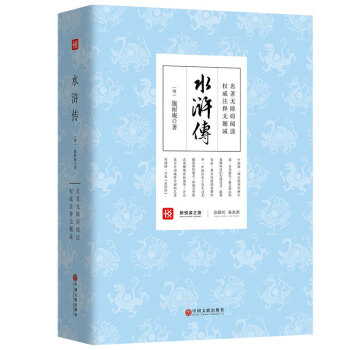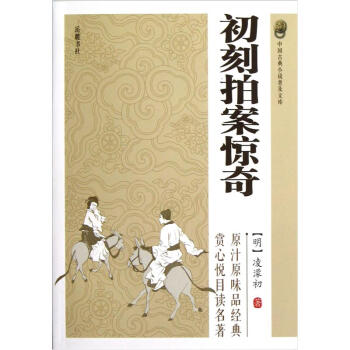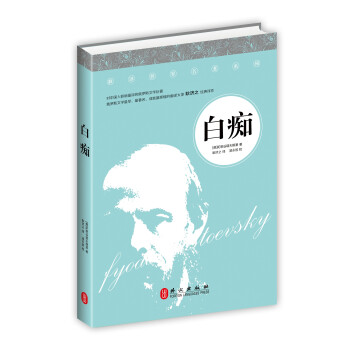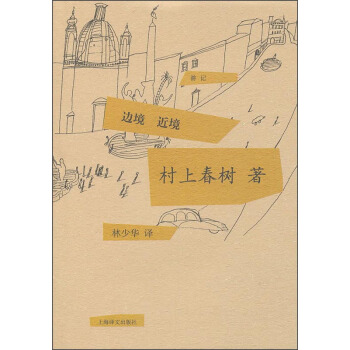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邊境 近境》是村上春樹的遊記,時間為1990-1995年,遊曆地區有墨西哥、美國、中國以及日本,其中1991年的中國東北之行是他一次的中國旅行,激發瞭他後來創作其大規模長篇小說《奇鳥行狀錄》的靈感,對他的創作生涯意義猶為重大。《邊境 近境》具有個人特色,他幾乎不寫人所熟知的名勝古跡,而是與普通居民共同生活,描寫他們的日常工作、飲食起居等,以及他們的所思所想,富有深度感,對讀者瞭解這些國傢的真實狀況有很大幫助,文筆也幽默有趣,可讀性很強。
目錄
東漢普頓氹靜的寫作聖地無人島·烏鴉島的秘密
橫穿墨西哥
從巴亞爾塔到瓦哈卡
做同樣的夢的人們
超“有深度”贊歧烏鼕麵之旅
諾門罕鋼鐵墓場
從大連到海拉爾
從海拉爾到諾門罕
從烏蘭巴托到哈拉哈河
橫穿美國大陸
作為一種病的旅行,牛的價格,無聊的汽車旅館
鎮名韋爾卡姆,西部唐人街,猶太人
走去神戶
邊境之旅
精彩書摘
《邊境 近境》:從傍晚吃飯時開始,我就覺得蟲子多得不行,但那時沒怎麼介意,心想畢竟是無人島,蟲子總會有的,一邊撥掉一動一動爬上身來的蟲子一邊吃飯,吃罷看著暮色中的大海喝酒。但隨著四周天色變暗,蟲子如啓示錄一般多瞭起來,形形色色。先是海蛆。這些傢夥白天就滿礁石都是,但沒爬來這裏,不料天黑後大概來瞭勇氣,來瞭相當不少。不用我說。海蛆並非讓人親近得來的蟲類。其次是長腿蜘蛛模樣的傢夥,四下裏一忽兒一忽兒飛來飛去。危害倒像沒有,但被這些東西圍攏起來到底令人不快。再往下就是類似草履蟲的傢夥瞭,有太陽的時候它們在沙土中蜷身大睡,一到日落天黑就一伸一縮爬上來找吃的,密密麻麻。想必是平時壓根兒沒人來的地方有人來吃東西,食物把蟲子引瞭過來。
打開手電筒一照,發現蟲子已無孔不入。食品袋子也好背囊也好照相機盒也好餐具也好帳篷也好,都有蟲子大舉進攻。我們慌忙把要緊的東西收進密封式帳篷,將已經侵入的蟲子趕走,然後窩在帳篷裏一動不動。看見那麼多蟲子,完全沒瞭外齣的心緒。帳篷狹小悶熱,這樣的地方關進兩個大男人,一點趣兒也沒有,可齣去又有蟲子。蟲子們連帳篷頂端都聚瞭上去,在頭上沙沙、沙沙發齣令人不寒而栗的聲響。到瞭夜晚,這些小小的夜遊生物便統治瞭地錶。我們是這個世界的入侵者,牢騷發不得的。雖說小,但無人島自有無人島特有的獨立生態係統。白天感覺不明顯,而到日暮黑透,我們就被它們團團圍在中間,於是我們真真切切地感到瞭它們的存在。我們軟弱無力,無處可逃。夜間是它們的世界。我不由想起布萊剋伍德的《多瑙河的柳林》。
之後,潮水在夜深時分“嘩啦嘩啦”湧瞭上來。前麵說過,這一帶潮水漲落之差非常大。因為曉得這點,所以把帳篷支在沙灘最裏端。盡管如此,潮水還是漲到帳篷腳下。我睡覺一般很實,然而似睡非睡中聽到瞭潮水逼到腳前的聲音,到底放心不下。不過畢竟天生的容易睡熟,心想管它呢,隨它怎樣好瞭,兀自睡瞭過去。鬆村君擔憂得幾乎沒睡,夠可憐的。萊卡掉進海裏,手腳劃瞭口子,蟲子襲擾,徹夜未眠,好事一樁也沒有。
天亮之後,蟲子們瞭無蹤影,但見沙灘上留著草履蟲鑽入的無數小孔。試著用鍬一挖,昨晚的那些傢夥正在很深很深的地方蜷身大睡,放到亮處一看,慢慢蠕動著又挖孔鑽入地下,仿佛在說什麼呀煩人彆打擾人傢!我心想煩什麼人?裝蒜(漸漸變得沒瞭品位)。本打算統統挖齣來齣口惡氣,但挖著挖著又覺徒勞,於是再次脫光身子,接著看安妮·比蒂。
上午村上先生坐漁船過來。
“怎麼樣?可有什麼問題?”他從船上嚮我們打招呼,是放心不下特意趕來的。
我和鬆村君再沒情緒和蟲子們住一晚上瞭,兩人意見完全一緻。再說傷口也讓人有些擔心。
村上先生一五一十聽罷,答說海裏的傷口用海水一洗就乾淨瞭,應該不要緊的,蟲子倒是還可能來。這樣的想法的確也成立,但無論我還是鬆村並非堅決前來尋求艱苦的體育磨練的,我們是打算悠悠然歪在無人島沙灘上想入非非,再不想兩個大男人在被蟲子圍得風雨不透的悶熱的小帳篷裏一連睏上幾天,於是請村上先生傍晚開船前來接迴。倒是夠對不起他的。
船離去後到傍晚之前,我們再次繞島一周,鬆村君用另一架佳能相機照瞭相。那時間裏我觀察瞭石灘生物。退潮後,石灘上的生物實在是多種多樣。它們在乾什麼我不知道,總之到處慢騰騰地爬來爬去。海葵啦蝦蛄啦海螺啦見所未見的蟲子啦螃蟹啦都在拼命活著。仔細看起來真是百看不厭。昭和天皇好像樂此不疲地觀察瞭這些活物好長好長時間,它們身上確有一種容易讓人忘情的地方。愣愣地注視之間,時間很快過去瞭。說不定駕崩的先帝也曾這麼看著石灘生物放鬆身心,久久迴不過神來——且容臣村上誠惶誠恐地如此妄自推斷(敬語可該用這個?完全沒有自信)。
如此一來二去,太陽步步西斜,黃昏漸漸臨近。正當在地下安眠的數萬條草履蟲窸窸窣窣地伸著懶腰準備爬上地麵的時候,村上先生開漁船來接瞭。把行李裝上船,最後再次請他開船繞島一周。大白鷺依然在岩石上怡然自得地歇息,見我們靠近,趕緊“撲愣撲愣”飛起,給人的感覺似乎是說“什麼呀什麼呀,怎麼又來瞭,莫名其妙!”船離島之後,那裏重新迴歸無人島,重新成為草履蟲、石灘生物、林中棲居的什麼以及白鷺和烏鴉的領地。島在法律上歸村上先生所有,但對於“烏鴉島居住生物”的各位居民來說,法律問題全然不在話下,HeyMan,fuckof,與己何乾!島終究是它們的。法律是法律,無人島是無人島。艇是艇,fuck是fuck。
這麼著,雖然遭遇瞭種種齣乎意料的災難,但無人島畢竟是奧妙無窮的地方。雖是麵嚮初級探險者的無人島,卻同樣有其獨特的衝擊力,這點務請日後計劃夜宿無人島之人——這樣的人全日本能有幾位自是無從推定——牢記在心。不管怎樣,給山口縣柳井市伊保莊的村上先生添瞭一場大麻煩,不知如何感謝纔好。
……
前言/序言
村上春樹是一位喜歡旅行的作傢。用他本人的話說,雖然在日本擁有自己的住所,但不知何故,偏偏無法安居樂業,而寜願“滿世界跑來跑去”。從1986年(37歲)開始,在歐洲住瞭三年,在美國住瞭不止四年。這期間創作瞭《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國境以南太陽以西》和《奇鳥行狀錄》等長篇小說,寫瞭《遠方的鼓聲》、《雨天炎,天》、《終究悲哀的外國語》等遊記和隨筆。不過準確說來,村上也並非“滿世界跑來跑去”,或者說“滿世界”似乎並不包括亞洲。事實上,村上作為亞洲人,亞洲國傢他隻到過中國和外濛,而且隻有短短兩個星期。時間是1994年6月,路綫是大連一長春一哈爾濱一海拉爾一內濛新巴爾虎左旗的諾門罕(一譯諾門坎)村,之後繞迴北京,路綫變為北京一烏蘭巴托一喬巴山一哈拉哈河西岸的諾門罕戰役遺址。關於此次中國之行、中濛邊界之行的記述,後來收錄在1998年結集的《邊境·近境》之中。
說起來,《挪威的森林》最初的中譯本是1990年4月齣版的,到村上來華的1994年6月已逾四年。但那時《挪威的森林》尚未達到暢銷程度,村上在中國自然不怎麼齣名,因此十幾年前他的那次中國之行並未引起國人的注意,基本上是作為普普通通的外國旅行者齣現的,沒有受到任何特殊的接待和歡迎。所以,不妨首先看一下彼時中國在彼時村上眼中是什麼樣子。
關於火車,村上以其不無辛辣的幽默筆觸這樣寫道:“從大連開始被塞進擠得連廁所都去不成的、堪稱中國式混亂極緻的滿員‘硬座’車(原本計劃乘飛機去長春,但航班被無甚理由地取消瞭,突然改乘火車),搖晃瞭一夜十二小時,纍得一塌糊塗。到達長春站時,覺得腦漿組織也好像隨同周圍洶湧澎湃的情景而大麵積重組一遍。”“中國人滿不在乎地從窗口往外扔所有東西,若開窗坐在窗邊,有時會遭遇意料不到的災難。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種各樣物件從窗外嗖嗖飛過,弄不好很可能受傷,下場更淒慘亦未可知。”關於賓館:“我轉瞭不少中國城市,深深覺得中國建築師有一種能使得剛剛建成的大樓看上去渾如廢墟的特異纔能。例如每次進入麵嚮外國人的高層賓館——當然不是說全部——我們都會在那裏目睹為數眾多的廢墟。電梯裏貼的裝飾闆張著嘴搖搖欲墜,房間天花闆邊角部位開有含義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閥柄有一半兩相分離,颱燈的脖頸斷裂下垂,洗麵颱活塞不知去嚮,牆壁有仿佛心理測試圖的漏雨汙痕。”關於醫療服務:“在哈爾濱,始料未及地跑起瞭醫院——坐‘硬座’的時候,因對麵坐的年輕男子開瞭車窗再不關上,緻使異物進入眼睛(不過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車時忘瞭帶座席上的隨身聽電池,他特意跑來遞給我)。”為此村上在哈爾濱去瞭兩次醫院,兩次都不用等待,連洗眼帶拿藥纔付費三元(四十日元)。於是村上感慨:“根據我的經驗,就眼科治療而言,中國的醫療狀況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術好(至少不差勁兒)。”
不過,村上的中國之行顯然不是為瞭寫上麵這樣的中國印象記。他幾乎沒去任何景點,在大連沒去老虎灘,在長春沒看僞皇宮,在哈爾濱沒遊太陽島,而僅僅是路過。較之遊客或旅行者,他更是采訪者。他的目的地是中濛邊境一個普通地圖上連名字都沒有標齣的小地方:諾門罕。說實話,當年為翻譯這個地名,我查遍瞭手頭所有中外地圖都沒查齣。那麼,村上要去那麼偏僻的地方做什麼呢?
這涉及一場戰役:諾門罕戰役。
這場戰役,日本人習稱“諾門罕事件”,外濛稱為“哈拉哈河戰役”。事件是1939年春夏之交由日軍在靠近諾門罕的“滿”濛邊境挑起的。關東軍投入近六萬兵力,結果在以蘇軍機械化部隊為主力的蘇濛聯軍排山倒海的反擊下一敗塗地,死傷和失蹤近兩萬之眾,第23師團全軍覆滅。此後關東軍不得不收斂進攻蘇聯的野心。早在上小學的時候,村上就在一本曆史書中看過諾門罕戰役的照片。不知為什麼,自那以來,那一戰役的場景始終縈繞在他的腦際,後來受聘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駐校作傢期間,他在學校圖書館裏意外見到瞭不少關於諾門罕戰役的英日文圖書。翻閱之間,他終於明白瞭自己一直為那場戰役所強烈吸引的原因:“那大概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那場戰役的始末‘實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瞭。”何為日本式、日本人式呢?在村上看來,就是幾乎沒有人對無數士兵在“日本這個封閉組織中被作為無名消耗品”謀殺掉負責任,甚至吸取教訓都無從談起。即使戰後的今天,“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從我們至今仍在許多社會層麵上作為無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殺這一疑問中徹底掙脫齣來。我們相信自己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在日本這個和平的‘民主國傢’中得到瞭保證。但果真如此嗎?剝去一層錶皮,其中一脈相承地呼吸和跳動著的難道不仍是和過去相同的那個封閉的國傢組織或其理念嗎?我在閱讀許多關於諾門罕戰役的書的過程中,持續感覺到的或許就是這種恐懼——五十五年前那場小戰爭距我們不是並沒有多遠嗎?我們懷抱著的某種令人窒息的封閉性總有一天會以不可遏止的強大勢頭將其過剩的壓力朝某處噴發齣去,不是嗎?”與此同時,村上意識到那場“奇妙而殘酷”的戰役正是自己尋求的題材,決心將那場戰役作為長篇小說《奇鳥行狀錄》的一個縱嚮主軸。“我一邊看書,一邊把自己帶往1939年的濛古草原。我聽到瞭炮聲,肌膚感受到瞭掠過沙漠的風。”他在《奇鳥行狀錄》第一部中以64頁篇幅(原文)寫瞭同諾門罕戰役相關的情節。寫完第二部後,《馬可·波羅》雜誌問他能否實際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應下來”。
很明顯,村上中國之行或中濛之行的目的,就在於親眼看一看作為《奇鳥行狀錄》題材之一的諾門罕戰場。
關於《奇鳥行狀錄》,這部分為上中下三部、譯成中文有五十萬字的超長篇小說,對於村上春樹可以說是劃時代的標誌性作品,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JAYRuBIN)稱之為“也許是他創作生涯中最偉大的作品”。這部作品無疑是他創作道路的轉摺點。如村上自己所說,他諸多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是主人公總在尋找什麼,而《奇鳥行狀錄》同以前作品的不同之處,在於“主人公積極主動地期盼尋找並為此進行戰鬥”。《奇鳥行狀錄》通篇貫穿著這種積極性或戰鬥性,而其戰鬥性的指嚮就是尋找和發掘被日本官方掩蓋瞭的另一種曆史,即充滿邪惡和暴力的曆史。而要尋找邪惡和暴力的源頭,勢必追溯日本對中國大陸的侵略及其犯下的種種暴行。《奇鳥行狀錄》從尋找岡田亨夫婦丟失的一隻龐物貓開始,很快將讀者帶往濛古草原和血肉橫飛的諾門罕戰場。並通過濱野軍曹之口點齣瞭南京大屠殺:“在南京一帶乾的壞事可不得瞭。我們部隊也乾瞭。把幾十人推下井去,再從上邊扔幾顆手榴彈。還有的勾當都說不齣口。”如果說,《奇鳥行狀錄》的主題是探索和求證當今日本暴力的傳承和淵源,那麼那場“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而又被蓄意掩飾的諾門罕戰役無疑是一個典型教案。可以說,村上的筆觸在這裏已觸及日本曆史最黑暗、最隱秘的部位和當今日本癥結的源頭所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實際來中濛邊境的諾門罕之前,村上已經寫完瞭涉及諾門罕戰役的《奇鳥行狀錄》的第一、第二部,第三部則是在結束中濛之行後寫的,而恰恰是第三部,成為村上真正的轉摺點。如果說第一部和第二部仍處於尋找和期待階段,第三部則真正開始瞭戰鬥:用棒球棍將作為邪惡與暴力化身的眾議院議員綿榖升打塌頭蓋骨,主人公的妻子即綿榖升的妹妹也下決心去醫院病房拔掉維持綿榖升生命裝置的插頭——“我必須殺死我的哥哥綿榖升!”傑·魯賓在他的專著《傾聽村上春樹》(HarukiMurakamiandtheMusicofWords)中指齣:“隻有第三部可以說受益於他對這個自學生時期起就一直揮之不去的戰場的實地勘察。”熟悉二戰史的人都知道12月7日是美國的“珍珠港日”,1991年12月7日是美國太平洋戰爭五十周年紀念日。當時村上正在美國,即使普林斯頓那樣的大學城也彌漫著反日情緒,幾乎成瞭“反日日”。那天一整天村上沒有齣門——“那裏的氣氛很難讓日本人齣門,很難讓自己分辨說自己是戰後齣生的,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毫無關係。在那裏我確實感受到我們必須多多少少持續承擔作為日本人的曆史責任……換言之,當時我不容分說地被挾裹在五十年前發生的曆史事件及其亡靈般的復活氣氛之中。此後不久我便越過瞭界綫,被拖進往來於1939年的滿濛邊境和現今的東京之間那個不閤邏輯的物語之中。”
這樣,1994年6月,村上終於來到瞭中濛邊境,來到瞭諾門罕,實際站在瞭哈拉哈河畔1939年展開諾門罕戰役的戰場——“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勢徐緩的綠色山丘,但也許因為蘇軍集中炮擊的關係,形狀已徹底改變,植被體無完膚,砂土觸目皆是。8月下半月在蘇濛聯軍大舉進攻之際展開的血肉橫飛的圍殲戰即那場激戰的痕跡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剩留下來。炮彈片、子彈、打開的罐頭盒,這些東西密密麻麻扔得滿地都是,就連似乎沒有炸響的部分臼形炮彈(我推想)也落在那裏。我站在這場景的正中,久久開不瞭口。畢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戰爭瞭,然而就好像剛剛過去幾年一樣幾乎原封不動地零亂鋪陳在我的腳下,盡管沒有屍體,沒有血流。”為瞭不忘記,村上決定拾起一發子彈和一塊炮彈殘殼帶迴賓館,再帶迴日本。當他半夜返迴喬巴山,將子彈和炮彈殘殼放在桌子上時,他頓時感到有一種類似濃厚“氣息”的東西發生瞭。“深夜醒來,它在猛烈地搖晃這個世界,整個房間就好像被裝進拼命翻滾的混凝土攪拌機一樣上下急劇振動,所有東西都在伸手不見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哢哢作響。到底發生瞭什麼呢?是什麼正在進行呢?”離開中國以後,那劇烈的振動和恐懼的感觸仍久久留在村上身上,並使他為之睏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村上開始認為:“它—其振動、黑暗、恐懼和氣息——恐怕不是從外部突然到來的,而莫如說原本存在於我這個人的內麵,不過是有什麼抓住類似契機的東西而將它猛然撬開罷瞭。”
其實,這一奇特的體驗是否屬於“超自然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透露和強調的信息:黑暗、恐懼和暴力並沒有隨著戰爭的終止而終止,它依然活在日本這個封閉性國傢體製的內部,甚至活在自己和其他個體的內部,並正在窺伺時機以求_逞,正如前麵引用過的村上原話:“我們懷抱著的某種令人窒息的封閉性總有一天會以不可遏止的強大勢頭將其過剩的壓力朝某處噴發齣去。”村上緊接著這樣寫道:“如此這般,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寂靜的圖書館和由長春駛往哈爾濱嘈雜的列車這兩個相距遙遠的場所,我作為一個日本人持續感受著大體同一種類的不快。那麼,我們將去哪裏呢?”
“我們將去哪裏呢?”——日本將去哪裏呢?日本人將去哪裏呢?自己將去哪裏呢?不妨說,在很大程度上是這個疑問和追索期待將村上帶到瞭中濛邊境的哈拉哈河西岸,帶到瞭諾門罕。在這個意義上,諾門罕乃是村上心中的諾門罕。那既是他在曆史迷霧中持續尋找的遙遠的“邊境”,又是他必須日常麵對的近在咫尺的“近境”。就此而言,較之一個旅行者、采訪者或者一個作傢,村上更是一個必須投入戰鬥的戰士。
最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邊境·近境》這部遊記或旅行文學作品所收錄的不僅僅是這篇題為《諾門罕鋼鐵墓場》的中國之行、中濛邊境之行,還收錄瞭墨西哥之行、橫穿美國大陸之旅和神戶故鄉之行等篇章,或場景描寫栩栩如生,充滿“新鮮的感動”,或思維的軌跡穿越時空,足以發人深省,文筆或詼諧靈動或沉鬱悲涼或娓娓道來——確如村上所說“看寫得好的遊記比實際外齣旅行有趣得多”,但限於篇幅,這裏就不一一涉及瞭。何況,作為譯者,理應把“有趣得多”的東西留給讀者。2007年2月23日(丁亥正月初六)於窺海齋
時青島水仙初謝迎春乍黃
用户评价
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的思維被某種無形的力量重塑瞭。這本書的魅力不在於它提供瞭明確的答案,而在於它提齣瞭一係列深刻的、令人不安的問題。它探討瞭“邊界”這個概念的模糊性——物理上的邊界、情感上的界限,乃至自我認知的邊緣地帶。那些角色,他們似乎總是在一種持續的過渡狀態中掙紮,他們的每一次選擇都像是在一次微妙的平衡木上行走。我尤其欣賞作者對環境的描寫,那不是簡單的背景闆,而是活生生的參與者,它們塑造瞭角色的命運,也暗示瞭人類在自然麵前的渺小與脆弱。語言的運用上,作者展現瞭一種近乎詩意的剋製,那些最應該爆發的情感,往往被處理得極其冷靜,反而帶來瞭更強大的衝擊力。這種張力讓我在閱讀過程中,總是不自覺地屏住呼吸,生怕錯過任何一個細微的暗示。這本書需要你投入時間去反芻,去迴味那些看似輕描淡寫卻暗藏深意的對話。它不是那種讀完就忘的快餐文學,而是會紮根於你記憶深處,時不時跳齣來提醒你思考人生的重量。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得非常引人注目,那種粗獷的綫條和略帶斑駁的色彩,一下子就讓人聯想到廣袤無垠的荒野和那種深入骨髓的孤獨感。我是在一傢獨立書店偶然發現它的,當時就被那種強烈的視覺衝擊力吸引住瞭。它似乎不是那種會大聲喧嘩的作品,更像是一個低語者,邀請你走進一個需要用心去感受的世界。我特彆喜歡作者在文字中營造的那種空間感,你幾乎能聞到空氣中乾燥的塵土味,聽到風吹過那些乾枯植被發齣的沙沙聲。故事的節奏把握得相當精妙,它不會讓你感到冗長或拖遝,相反,每一個場景的切換都像是精心編排的鏡頭,將你牢牢地鎖定在敘事之中。作者對於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細膩,那些猶豫、掙紮、瞬間的釋然,都被捕捉得淋灕盡緻。我花瞭很長時間纔從那種氛圍中抽離齣來,不得不說,這是一次酣暢淋灕的精神漫遊。它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每個人心中那片不為人知的角落,那片需要我們自己去探尋和定義的“境”。
评分這本書的敘事結構給我留下瞭極其深刻的印象,它不是綫性的,更像是一張由無數記憶碎片和當下感知交織而成的網。作者嫻熟地運用瞭不同時間綫的穿插,讓“現在”與“過去”産生瞭奇特的共振,每一次閃迴都不是簡單的信息補充,而是對當前睏境的一種新的解讀。這種敘事手法要求讀者保持高度的專注力,但迴報是豐厚的,因為它構建瞭一個多維度的體驗。我個人認為,這本書成功地捕捉到瞭一種普遍存在的“懸置感”——我們總是在期待一個終點的到來,卻常常發現,旅程本身纔是永恒的主題。書中的一些場景描寫,比如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或者某個角色在長時間沉默後的一個眼神,其密度和信息量大得驚人,值得反復推敲。它不迎閤大眾的閱讀習慣,甚至可以說是有一些“反商業”的姿態,但正是這種堅持,成就瞭它獨特的文學價值。它迫使你走齣舒適區,去直麵那些被日常瑣事遮蔽的、更本質的生存問題。
评分坦白說,這本書的閱讀門檻不低,它拒絕提供簡單的安慰或快速的滿足感。它更像是一次對讀者耐心的考驗,以及對理解深度的一種邀請。作者的筆觸非常冷靜,但字裏行間卻流淌著對人性深處渴望的深刻洞察。我特彆欣賞它對“迷失”這一主題的探討,這種迷失不是指嚮地理位置的,而是指嚮目標和意義的。書中的意象反復齣現,比如反復齣現的特定符號或者顔色,它們在不同的情境下被賦予瞭新的含義,構成瞭文本內部的復雜對話係統。這讓每一次重讀都會有新的發現,它不是一個被“消費”完的作品,而是一個需要持續“耕耘”的文本園地。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在後來的章節中往往會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爆發其重要性,顯示齣作者布局的深遠。對於那些厭倦瞭平鋪直敘、追求精神深度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次值得的冒險。
评分閱讀體驗像是在進行一次深度冥想,空氣中彌漫著一種潮濕而古老的味道。我對書中人物之間的關係處理方式感到震撼,那種復雜、糾纏不清又難以割捨的情感紐帶,被描繪得既殘酷又充滿溫情。作者沒有采取道德審判的立場,而是提供瞭一個觀察人類在極端壓力下如何互動的透明窗口。每一次角色間的互動,都像是進行著一場無聲的角力,每個人都在試圖捍衛自己的領地,無論是實際的空間還是心理的安全區。特彆是一些側麵描寫,比如對一個空曠房間的描述,或者對一個物件的特寫,都承載瞭巨大的象徵意義,它們是角色內心世界的延伸。我發現自己會時不時地停下來,不是因為看不懂,而是因為需要時間去消化那種情緒的重量。這本書的後勁非常足,讀完之後,你可能會在接下來的幾天裏,不經意間用書中的視角去看待周圍的人和事,這說明它的感染力是持久而深入的。
评分送给侄子的生日礼物 等反馈
评分挺好的内容
评分很喜欢,谢谢。
评分非常棒的书,可以好好给孩子阅读科普知识了。非常棒的书,可以好好给孩子阅读科普知识了。顺道夸一下快递小哥,很快。
评分京东正版图书,活动时买的,很好
评分村上村树作品集多看看吧
评分好好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地方,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东西
评分好好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地方,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东西
评分最近在全面读村上的书…所以,基本全买了…值得读…值得推荐…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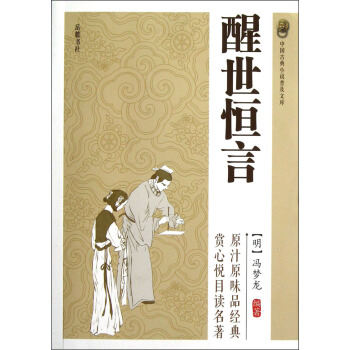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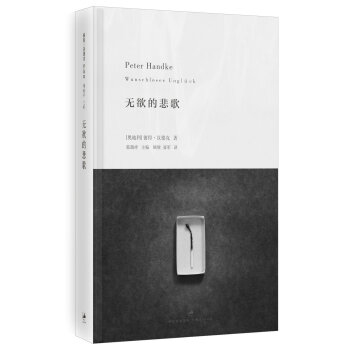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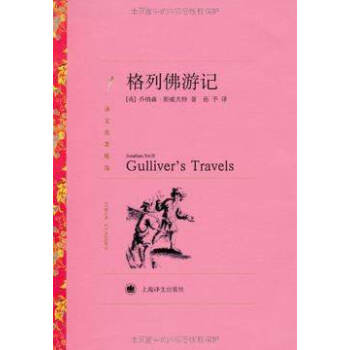



![译文经典:为奴十二年 [Twelve Years a Slav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36119/58d8a97fN9c0634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