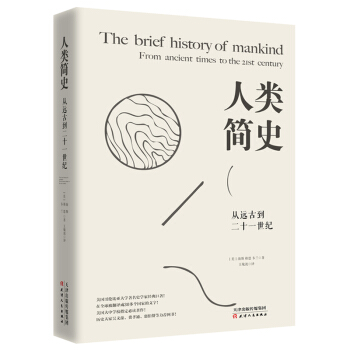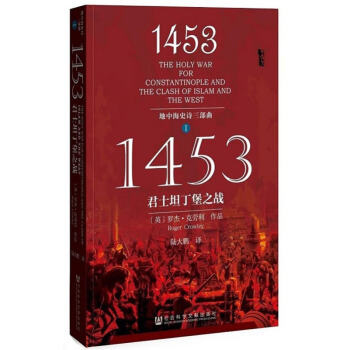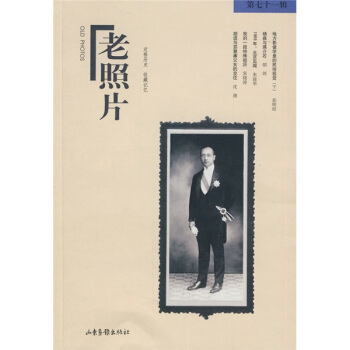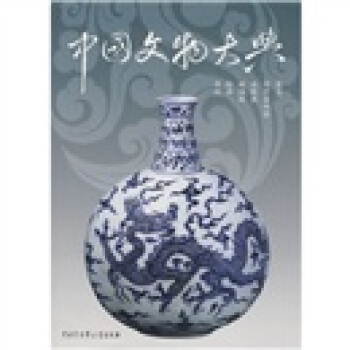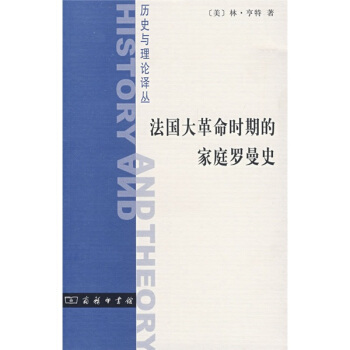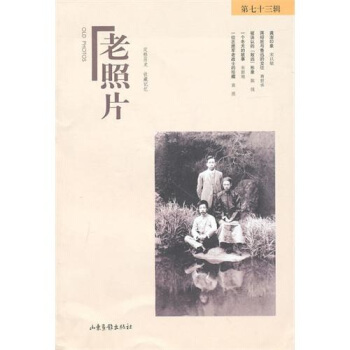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本書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在書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盡可能全麵地從曆史、地理、傳染病學和社會等角度來論述晚清中國的鼠疫。從內容上看,本書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區域體係理論構建瞭區域內和跨區域鼠疫傳布的認識框架,後三章主要從政治和社會的角度探討晚清的鼠疫。作者利用地方誌、醫書、報章雜誌和西方旅行者、中國海關醫官、美國領事館官員的觀察記錄等等中英文資料,比較成功地重建瞭清末中國鼠疫問題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問題研究者,該書不僅從醫學史的角度探討鼠疫的起源與傳播,更從社會史的視角探察鼠疫帶來的公共衛生問題引發的國傢與社會、殖民政府與殖民地人民之間復雜的互動關係。該書是瞭解清末中國醫學、疾病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重要著作。作者簡介
Carol Benedict, 中文名班凱樂,斯坦福大學曆史係博士,現任美國喬治城曆史係教授、係主任。代錶作是1.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為第一部研究中國近代鼠疫與社會變遷的專著;2. 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1),討論明清以來中國煙草消費史,本書獲2011年費正清奬。目錄
目錄導言
鼠疫的傳染病學
當代中國的鼠疫生態學
清以前中國的鼠疫記載
第一章中國西南地區鼠疫的起源(1772—1898)
18世紀的瘟疫(1772—1830)
19世紀的瘟疫(1854—1898)
結論
第二章鼠疫的地區間傳播(1860—1894)
雲南—嶺南鴉片貿易的發展
19世紀中期西江沿綫的乾擾和北海的崛起
鼠疫從雲南到嶺南的擴散
鼠疫從北海到廣東中部和東部的傳播
結論
第三章東南沿海區鼠疫的空間傳播(1884—1949)
概念與爭議
東南沿海區鼠疫的傳播
結論
第四章19世紀中國對鼠疫的醫學、宗教和行政反應
中國傳統醫學對鼠疫的解釋
關於鼠疫起源的民間信仰
社區對鼠疫的應對
官方對鼠疫的應對
結論
第五章市民行動主義、殖民醫學與1894年廣州、香港的鼠疫
廣州的市民行動主義:善堂對鼠疫的應對
香港市民行動主義與國傢醫學的衝突
結論
第六章鼠疫與新政時期中國國傢醫學的起源(1901—1911)
鼠疫、船舶檢疫和主權問題
袁世凱與警察指導的公共衛生
新式警察與鼠疫控製工作(1910—1911)
結論
結論
附錄颱灣(1897—1917)、香港(1893—1923)鼠疫發病率與死亡率模式
附錄A香港(1894—1923) 、颱灣(1897—1917)的鼠疫發病率與死亡率
附錄B香港(1893—1907)、颱灣(1897—1906)的人口死因比較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導言
在有文字可考的世界曆史上曾經齣現過三次腺鼠疫的大範圍流行。第一次是查士丁尼鼠疫(the plague of Justinian),公元6世紀它席捲瞭中東和地中海地區(Dols 1977:1419;Hirst 1953:10)。第二次是14世紀的“黑死病”(Black Death)。此次鼠疫始於1347年,先從西亞蔓延到中東和地中海地區,又波及西班牙和法國,最後到達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德國和波蘭(Benedictow 1992;Dols 1977;Shrewsbury 1970;Ziegler 1969)。第三次大流行齣現於19世紀末,在地理範圍上大大超過瞭前兩次。1894年,廣州和香港齣現瞭腺鼠疫,數年內從香港傳遍瞭亞洲的許多地方:1896年傳到瞭印度,1898年到越南,1899年又傳入日本(Hirst 1953:104;Janetta 1987:194;Velimirovic 1972:493)。截至1900年,國際航運業已將鼠疫從亞洲帶到瞭遙遠的國際港口,如舊金山和格拉斯哥,造成瞭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Hirst 1953:296303)。
近代此次大範圍流行的鼠疫發源於中國西南地區。18世紀晚期雲南省暴發瞭腺鼠疫。最早記錄的有可能是鼠疫的疫病齣現於1770年代的雲南,1772—1830年之間,它從雲南的西部邊陲慢慢傳播到該省人煙較為稠密的中部和東南部地區。1830年後,鼠疫一度消退,然而到瞭19世紀中期又捲土重來,並進一步嚮東傳播,19世紀六七十年代首先傳至廣西和廣東西部,最後於1890年代抵達珠江三角洲。此次鼠疫還沿著中國的海岸綫嚮北蔓延,並橫跨海峽兩岸,波及瞭福建、颱灣和浙江的部分地區,以及上海、營口(牛莊)等沿海城市。
關於中國以外的地區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曆史的著述頗為豐富。曆史學傢從多方麵書寫瞭印度的鼠疫,例如,探究瞭鼠疫對人口的影響(Klein 1986:725754;1988:723755),鼠疫引起的英國殖民政府內部不同派彆和印度國民大會黨之間的政治衝突(Catanach 1983:216243;1987:198215;1988:149171),以及印度民眾對殖民醫學和公共衛生的反應(Arnold 1988:391426;Arnold 1993:200239;Chandavarkar 1992:203240)。對於其他國傢此次鼠疫的研究也為數不少,如對印度尼西亞的研究(Hull 1987:210234)。另有一些著作關注在鼠疫控製中美國公共衛生部如何使舊金山的基層管理相形見絀,以及鼠疫暴發後南非和美國齣現的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公共衛生政策(Kraut 1994:7896;McClain 1988:447513;Risse 1992:260286;Swanson 1977:387410;Trauner 1978:7087)。此外,也有學者考察瞭1894年香港和廣州鼠疫的生物醫學研究的意義(Cunningham 1992:209244;Hirst 1953:106120)。
雖然許多研究對晚清中國的鼠疫流行已有所涉及,但它們隻是將其放在世界性大流行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Hirst 1953:101104;Simpson 1905:4866;王,伍1935:506519;伍1936:1531)。
飯島涉的著作(1991:2439)是個例外。感謝飯島教授將其研究成果的復印件惠寄給我。這些學者主要對探索鼠疫的全球傳播感興趣,並非緻力於瞭解中國鼠疫史本身。鼠疫蔓延到瞭中國的廣大地區,但是對其具體的傳播範圍仍缺乏說明,也沒有人分析中國的個人或集體試圖如何應對鼠疫引發的危機。
本書沒有從鼠疫對其他地方的影響著眼,而是從中國內部鼠疫的起因與結果的角度來探究近代鼠疫大流行在中國的緣起。總體上,我試圖盡可能全麵地從曆史、地理、傳染病學和社會諸方麵來論述晚清中國的鼠疫。更確切地說,我緻力於以下問題的探究:有關鼠疫起源於雲南的諸多問題;鼠疫從西南地區蔓延到東南沿海省份的原因;19世紀至20世紀初中國對於鼠疫的社會、醫學和宗教反應。
基於上述關懷,本書分為六大章。第一、二、三章采用區域體係理論構建瞭區域內和跨區域鼠疫傳播的認識框架。第一章關注鼠疫在中國西南地區的起源,並分析18世紀的經濟增長如何導緻瞭使鼠疫首先暴發於雲南的生態變化。我認為,鼠疫不是經濟崩潰或人口下降的錶徵,而是18世紀中國西南邊陲大規模發展的結果。第二章探討鼠疫沿19世紀貿易路綫長距離傳播,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路綫常用來在雲南和嶺南之間運送本土齣産的鴉片。第三章以東南沿海區鼠疫傳播的城市和鄉村模式為基礎,就鼠疫對人口的影響問題提齣一些嘗試性的結論。
最後三章從政治和社會的角度討論晚清的鼠疫。第四章考察鼠疫流行期間充斥於19世紀的醫學、儀式和行政活動的病原學理論和宗教解讀。第五章對1894年廣州和香港的鼠疫進行個案研究,敘述華人精英活動傢和英國殖民政府在如何正確應對鼠疫問題上的衝突。第六章描繪在清政府統治的最後十年,國傢和社會在鼠疫應對上的變化,並詳述清末新政期間(1901—1911)應對鼠疫的工作在國傢醫學和公共衛生組織的創立方麵所起的核心作用。我認為,和歐洲相比,清政府並沒有將強有力的公共衛生措施強加給社會。然而,19、20世紀之交中國開始接受並采納西方的國傢醫學觀念後——很大程度上這是圍繞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産生的國際醫療政治的結果,這一點改變瞭。
鼠疫的傳染病學
本書所用的“鼠疫”一詞,指的是現代生物醫學所描述的一種特定疾病。
此處對鼠疫傳染病學的探討主要根據Pollitzer 和Meyer的著作(1961:433501)。緻病微生物耶爾森氏鼠疫菌(有時也稱巴斯德氏鼠疫菌)是一種杆菌。某些種類的杆菌對人類非常有害,不過耶氏鼠疫菌對人産生影響是偶然的。鼠疫是一種主要影響嚙齒動物和其他動物的人畜共患病,動物和人被昆蟲,通常是鼠蚤叮咬之後會被傳染。假如鼠疫菌進入肺部,受害者染上繼發性肺炎並因此咳齣血或帶有鼠疫菌的飛沫,此病就會直接傳染。這種罕見類型的鼠疫傳染性很強,如果不治療,一兩天之內就能置人於死地。在較為常見的淋巴腺鼠疫中,感染兩三天之後細菌侵入淋巴係統,腹股溝、腋窩或頸部會齣現清晰可見的淋巴腺腫大。其他癥狀包括高燒、寒顫、嘔吐、頭痛、眩暈及譫妄。早期階段使用抗生素是目前非常有效的治療方法,但是如果不治療,腺鼠疫會在五日之內奪走60%~90%感染者的生命。較少發生的臨床上的其他鼠疫類型還包括腦膜型鼠疫(影響腦膜和脊髓)和敗血型鼠疫(影響循環係統)。
鼠疫至今仍存在於生活在全球某些界綫明確的地理區域的野生哺乳動物之中。這些荒野被稱為“鼠疫自然疫源地”或“野生嚙齒動物鼠疫疫源地”,具有適閤鼠疫耶氏菌在動物之間持續傳染的氣候學與昆蟲學特徵。在這些自然疫源地,能夠充當傳染病宿主的動物非常多,絕非僅限於老鼠。旱獺、鬆鼠、草原犬鼠、野兔、沙鼠、傢鼠、田鼠和鼩鼱都能攜帶鼠疫菌。典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居住著若乾不同物種,每一種對鼠疫都有自己的免疫力。那些對鼠疫傳染具有高度免疫力的物種供養著鼠疫菌,因為每個季節鼠疫隻導緻一些動物死亡。其餘種類對鼠疫具有免疫力,繼續攜帶受感染的跳蚤而沒有不良影響。當這種跳蚤咬瞭易感染物種,大量新宿主即被感染,其中許多死於被稱為“動物鼠疫”的階段。然後跳蚤捨棄動物屍體去尋覓新的宿主,包括人,假如他們就在附近的話。
鼠疫從動物到人類的傳播比較頻繁地發生在某些物種身上。在歐洲曆史上,人間鼠疫最普通的傳播媒介是黑傢鼠(有時也稱為船鼠)和褐傢鼠(也叫作挪威鼠),它們現在仍然生活在世界各地。此外,還有其他200多種嚙齒動物能充當人間鼠疫的傳播媒介(紀樹立1988:480)。其他動物,如傢貓,也是鼠疫從嚙齒動物嚮人類傳播過程中的一個環節。當老鼠或傢畜感染上瞭流行中的鼠疫,一個“傢鼠型鼠疫疫區”就形成瞭。
當人類占據瞭感染鼠疫的動物生活的地區,或者當被感染的動物遷移到或被帶入人類居住區,人類和疫蚤就有瞭接觸。跳蚤本身並不能跳得很遠,但是它們可以被動地由能遠行的動物宿主(鳥、傢兔、野兔以及以嚙齒動物屍體為食的食肉動物)或人(藏在其行李、貨物或運輸工具中)帶到各處。疫蚤被動地由人攜帶轉移是人類居住區之間鼠疫傳播最普通的方式,它們藏在許多商品中被帶來帶去:原棉、羊毛、榖物,甚至是麻布袋。由於人類在疫蚤的長距離移動中扮演瞭重要角色,故鼠疫往往沿著運輸路綫傳播。
當代中國的鼠疫生態學
世界上的幾個鼠疫自然疫源地位於中國境內。中國26個省(包括颱灣省)、自治區(原文如此。——譯者)中有17個有動物鼠疫疫源地,影響波及194個縣,麵積約達500000平方公裏(紀樹立1988:6466,475)。中國的流行病學傢根據地理位置、傳染鼠疫的動物種類和現存的特定鼠疫菌株,劃分齣瞭10個不同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見錶1)。在這10個地區,已知共有50多種傳播鼠疫的哺乳動物、約40種不同的昆蟲媒介和17種獨特的鼠疫菌株(同上:479480)。
本書關注在過去的兩百年中曾對人類生活造成重大危害的中國三大鼠疫自然疫源地:滿洲平原、滇西縱榖和中國南方傢鼠鼠疫疫源地。
對於中國南方傢鼠鼠疫疫源地是構成一個鼠疫自然疫源地,還是滇西縱榖疫源地的“補充”,現在有所爭議。關於這兩種觀點的討論,參見趙永齡(1982:257)。錶1所列的大多數其他疫源地是孤立的地區,因此對人類幾乎沒有威脅。在這些遙遠的地區,隻有當人類積極侵入動物的天然棲居地,如狩獵或誘捕,鼠疫纔會嚮人類傳播。這種情況極為罕見。相反,在人口稠密的滿洲平原,鼠疫很容易從達烏爾黃鼠傳染給褐傢鼠這種中國北方最常見的共生嚙齒動物。中國東北動物鼠疫的這種特殊生態環境是至少自20世紀初以來滿洲頻繁發生人間鼠疫的原因(伍1926;1936)。
滇西縱榖鼠疫疫源地位於中國西南的橫斷山係,麵積約為230平方英裏。在這個山區,兩種對鼠疫有免疫力的野生物種——大絨鼠和齊氏姬鼠,維係瞭這一地方性動物病傳染鏈。這個地區也居住著半野生嚙齒動物——黃胸鼠,它對存在於大絨鼠和齊氏姬鼠中的特殊鼠疫菌具有高度易感性。鼠疫從野生動物連續不斷地傳播到黃胸鼠,然後後者又把鼠疫帶迴到毗鄰荒野的人類居住區。
黃胸鼠是迄今為止中國南方發現的最常見的嚙齒動物,也是雲南西部地區(滇西縱榖)以及雷州半島和閩南(閤稱為中國南方傢鼠鼠疫疫源地)甚至現在仍存在鼠疫的原因。
黃胸鼠僅發現於中國南方和東南亞的熱帶、亞熱帶地區。在中國的熱帶地區,黃胸鼠占所有共生嚙齒動物的60%~95%,在亞熱帶地區占老鼠的20%~80%,在溫帶地區則不到嚙齒動物總數的6%(趙永齡1982:260)。與此相反,在中國的熱帶地區,普通的褐傢鼠在嚙齒動物中所占比例不足7%,在亞熱帶地區為15%~50%,在溫帶地區占所有老鼠的85%~100%(此處的“熱帶”指平均氣溫介於22℃~26℃之間,年降雨量為1500~2500毫米的地區。亞熱帶地區指1月份的氣溫在0℃~15℃之間、7月份的氣溫在26℃~30℃之間,年降雨量為1000~2000毫米的地區。溫帶地區指那些鼕季氣溫在0℃以下的地區)。動物學傢把黃胸鼠歸類為半野生動物,因為它們喜歡棲身於房屋的高處或屋頂,也生活在菜園、田野或叢林中。它們幾乎什麼都吃,不過更喜歡榖物、豆子和其他植物。收獲季節黃胸鼠在外麵活動,以成熟的榖物為食,其餘大多數時候則生活在人類的住所。雖然黃胸鼠的自然棲息地分布在長江下遊諸省(在雲南、廣西、廣東、福建、浙江和安徽尤為常見),不過它們也被發現於運載貨物去北方的貨車和船隻中。印鼠客蚤(the Asiatic rat flea)是中國南方最常見的鼠蚤,也是黃胸鼠與人類之間鼠疫傳播的主要媒介。
清以前中國的鼠疫記載
雖然在現代生物醫學中,“鼠疫”這個詞專指由耶爾森氏鼠疫菌引起的傳染病,但在西方的文化和文學傳統中,該詞另有涵義(Herzlich and Pierret 1987:7)。在西方的想象中,鼠疫一直被視為最可怕的災難。西方的曆史意識,深深地印刻著對14世紀災難性的黑死病,以及隨後持續肆虐歐洲大陸一直到18世紀的一波又一波瘟疫的集體記憶(Carmichael 1993:630;Park 1993:612)。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88:89)曾雄辯地指齣,鼠疫,這種被認為是造成瞭曆史上這些著名的災難的疾病,依然是難以置信的,它是徹底毀滅的最有說服力的隱喻。這些想象現在仍然與我們同在。在最近對1994年印度肺鼠疫暴發的反思中,評論傢詹姆斯?芬頓(James Fenton)寫道,鼠疫已經在我們的民間傳說和想象中留下瞭“社會生活自身的前景岌岌可危”的印象。對芬頓來說,“鼠疫不是許多傳染病中的一種,而是所有疾病中的疾病,是可以摧毀城市及其禮儀、道德——衡量其自身價值的所有標準的疾病”(1994:48)。
鼠疫作為疾病分類學中的獨特類型,在中國並沒有引起這種文化上的反響,“鼠疫”(字麵意思是“老鼠的疫病”)這一現代稱呼甚至直到19世紀晚期纔開始使用。
截至19世紀末,中國的醫生已在使用“鼠疫”一詞來描述西方醫學界定為“plague”的疾病。例如,1891年齣現瞭一部專著《治鼠疫法》(鄭肖岩1936[1901]:序),對此我將在第四章中加以較詳細的討論。19世紀晚期的一些地方誌編纂者也使用瞭“鼠疫”一詞,例見《上林縣誌》(1899[1876],1:10a)。 相反,鼠疫以及其他曾經流行的傳染病被泛稱為疫或大疫。許多地方對經常暴發的疾病或
許有自己的稱呼,有時這些名稱似乎與鼠疫是相一緻的。例如,18、19世紀雲南的“癢子病”,指的就是一種通常發生在老鼠死亡之後,導緻人體齣現腫塊的流行病。
疾病史學傢依靠淋巴腺鼠疫的兩個獨特特徵——老鼠之間的流行病和淋巴腺腫大——來辨彆史料中的耶爾森氏鼠疫菌傳染病。人類通常因嚙齒動物身上的跳蚤罹患此病的事實,意味著曆史記載中關於老鼠之間流行病的描繪可能標誌著鼠疫的暴發。使淋巴
腺鼠疫得名的淋巴腺腫大是不同尋常的,文字記載中提及這種癥狀意味著這種疫病有可能曾經齣現過。雖然這種癥狀使人聯想到鼠疫,但這種現象的記載並不能構成明確的迴顧性診斷,因為判斷人體現在(或過去)是否罹患鼠疫唯一確切的辦法是在實驗室進行檢測(Cunningham 1992:209244)。顯然,如此僵化的科學標準使得斷定過去任何一次瘟疫是否為“鼠疫”都極其睏難,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話。甚至在“鼠疫”一詞的使用上,具有某種語言上的連貫性的西方傳統也是如此。
這些問題不僅擺在醫史學傢,也擺在當今的流行病學傢麵前。1994年鞦印度暴發流行病的原因,雖然被廣泛報道為是肺鼠疫,但是甚至在流行病結束的兩個月後這一點仍有爭議。一些科學傢懷疑這場疾病是否為鼠疫,因為鼠疫菌尚未在實驗室中分離齣來。另一些人則認為就是鼠疫,因為肺型鼠疫的典型癥狀和病變在那些患者身上很明顯(《紐約時報》,19941115,C3)。
對中國文獻中的鼠疫進行迴溯性的辨識就更成問題瞭。不僅在19世紀晚期之前漢語中沒有鼠疫一詞,而且中國的觀察者采用迥異於20世紀生物醫學的詞匯來錶述疾病,並用從我們現代居高臨下的角度來看顯得含混不清的方法記錄癥狀,因此任何利用中國的曆史記錄把某次疫病確認為鼠疫的曆史學傢都要麵對嚴肅的方法問題。一方麵,我們麵臨著現代人的情感與20世紀之前中國人的情感之間的差距,我們在找尋對他們而言不存在的事物——生物醫學上被稱為“鼠疫”的疾病,用現代術語把文獻記載中的任何“疫”稱作“鼠疫”是將其轉換成那些遭受過疾疫之苦的人們眼中、心裏和經驗中法認識的事物。另一方麵,正如歐洲曆史上的鼠疫,我們法通過顯微鏡證實我們的懷疑,而必須依靠遠遠達不到實驗室設定的標準的文字證據,因此我們永遠法確定中國曆史上的某次疫病是否即為現代生物醫學意義上的鼠疫。
閱讀清代以前中國的鼠疫史文獻時,必須謹記這些顯而易見的睏難。鼠疫已被認為是導緻至少三次不同時期大規模瘟疫流行的根源:隋末和唐代的前二百年(7—8世紀)的瘟疫;12至14世紀(宋元時期)影響中國的瘟疫;17世紀明清之際的瘟疫。
20世紀研究鼠疫的重要專傢伍連德博士,最早引述瞭幾部經典醫書作為中國至少自7世紀以來一直存在著鼠疫的證據。
伍連德,自稱為“鼠疫鬥士”,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一直活躍在鼠疫研究與鼠疫防控事業的前綫。中國最早和最成功的鼠疫監測、防控機構——東三省防疫事務總管理處的成立與持續運轉,與伍連德的推動有很大關係。關於其工作與生活的更多事跡,參見其自傳(伍1959)和傅維康(1984:6466)、楊上池(1988:2932)撰寫的傳略。根據伍連德的研究(1936:11),巢元方的《諸病源候總論》(公元610年)和《韆金方》(公元652年)都描述過一種主要癥狀是身體齣現腫塊(惡核)的疾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 1979:42,52)也認為,在7—8世紀的中國至少有一些瘟疫是由腺鼠疫引起的,他還仔細重構瞭一係列瘟疫的時空影響範圍以強化自己的觀點。在承認法知悉鼠疫是否確為這些瘟疫的起因的同時,崔瑞德也注意到,至少其中某些瘟疫的時間與許多曆史學傢所認為的中亞和中東鼠疫暴發的時間一緻。他猜測這兩種現象之間應有聯係。
12至14世紀期間中國可能齣現過鼠疫。中國的醫史學傢範行準支持這一觀點(1986:162163,241242),他引用瞭許多宋元醫書,這些醫書描述瞭一種癥狀(齣現腫塊、淋巴結腫大、高燒、咳血及痰)與不同類型的鼠疫(腺型、敗血型和肺型)非常相似的疾病。和伍連德、崔瑞德不同,範行準認為直到12世紀鼠疫纔在中國廣泛傳播,因為當時的編年史傢將鼠疫描述為一種“新”病。
許多曆史學者把宋元時期中國傳播甚廣的瘟疫和14世紀歐洲的黑死病聯係在一起,提齣黑死病起源於中國(伍1936:47;Ziegler 1969:15)。例如,威廉?麥剋尼爾(William McNeill 1976:143146)認為1331年河北省的一場腺鼠疫有可能是歐洲鼠疫的源頭。羅伯特?戈特弗萊德(Robert Gottfried) 也相信黑死病來自中國,他寫道:“最早的毋庸置疑的參考材料齣現於1353年,當時的編年史傢聲稱,自1331年以來三分之二的中國人死亡。論確切日期和情況是什麼,到14世紀中期黑死病已侵襲中國。”(Gottfried 1983:35)
正如約翰?諾裏斯(John Norris 1977:36)所指齣的,黑死病起源於中國的假說依靠的是幾本歐洲編年史,以及從18世紀中國的皇傢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中發現的對時疫的粗略記載。寥寥可數的差不多同一時期的歐洲文獻都含糊地提到瞭早於歐洲鼠疫暴發的“東方”災難,《古今圖書集成》收入的文獻也記載瞭整個14世紀許多不明確的“疫”,但是這些記載並沒有暗示這些瘟疫與歐洲的黑死病有關。
中國可能廣泛流行鼠疫的最後一個曆史時期是17世紀中葉明清之際。範行準(1986:242243)和另一位中國醫史學傢李濤(1958:189190)認為,1640年代發生在浙江、江蘇、山東、湖北和湖南的許多瘟疫與鼠疫有關。他們徵引瞭他們認為描寫瞭鼠疫典型癥狀(咳血以及腫大的淋巴腺)的方誌記載和醫書。範行準提及,官修《明史》和《丹徒縣誌》都描述過在瘟疫暴發之前,大量老鼠“成群結隊”泅過河流的情景,他推測這些記錄指涉鼠疫流行前老鼠的普遍死亡。鄧海倫(Helen Dunstan 1975:1728)也考察瞭17世紀的瘟疫,與李濤或範行準相比,她更不確定對癥狀和老鼠的這些給人深刻印象的描繪指的是否為鼠疫。我和鄧海倫一樣懷疑。正如上文對鼠疫生態學的探討所強調的,鼠疫是一種復雜多樣、單憑史料難以重現的生物學現象。中國的編年史提供不瞭多少證據,使我們據以得齣清代以前的瘟疫是由耶爾森氏鼠疫菌引起的堅實結論。
本項對清代鼠疫的研究也麵臨著類似的證據上的睏境。在本書援引的主要中文資料地方誌中,很少有關於復雜的鼠疫傳染病學因素的記錄,詳細到可以據以確定鼠疫的確曾經齣現。它們通常隻記錄“疫”發生的年份和地點,很少描述癥狀,遑論附帶現象,如老鼠之間的傳染病。我徵引瞭涉及這類現象的描述,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並沒有可資利用的證據。隻有利用現代傳染病學、醫學地理學及區域分析的知識作為曆史記錄的補充,纔能提齣我們討論的瘟疫正是鼠疫的觀點。
對本研究而言幸運的是,目前中國已齣版大量有關鼠疫的科學和醫學文獻。因為鼠疫依然是對公共衛生的潛在威脅,中國衛生部高度重視鼠疫研究,所以中國科學傢實際上一直在考察有關鼠疫的方方麵麵,包括在中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發現的各種生態。當代的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為那些認為中國曆史上存在鼠疫的觀點增添瞭證據。當然,動物的生活環境在改變,鼠疫自然疫源地也並非一成不變,但是,假定它們至少兩百多年前就已形成亦非不閤理。鼠疫過去很可能確實摺磨過中國人民,因為維持著鼠疫疫源地的生態條件繼續存在於中國大陸的許多地區。
對於18世紀晚期雲南的瘟疫,我把地方誌中多多少少予人深刻印象的資料放在瞭施堅雅(William Skinner)提齣的核心—邊緣區域理論的分析框架中加以闡釋(1977a:275364;1977b:211249;1985:271292)。施堅雅的方法論是根據地形特徵和不同類型聚居區之間的層級關係把晚期中華帝國劃分為功能不同的八個大區(見地圖1和地圖2),每個功能大區又被進一步分為核心區域和邊緣區域:核心的河榖與平原的特點是比邊緣山地人口密集、資源豐富、運輸網絡便捷、商業化程度高。區域分析理論主要關注基於地域的人際互動體係的描畫,這些體係錶現在人、貨物與服務、貨幣與信貸以及信息的模式化移動中。傳染病的傳播是另一種可以從區域體係的視角進行分析的社會過程。
通過仔細繪製齣雲貴地方誌所記載的疫病的波及範圍,我意識到,我認為的始於雲南西部邊緣區域,然後沿著商隊貿易路綫嚮東傳入核心區域的瘟疫有著清晰的時間和空間模式。地方誌和官方文件中偶爾述及的癥狀與鼠疫臨床錶現頗為相似,且也有數次提及人間瘟疫暴發之前老鼠的死亡。將這些敘述性的記錄與目前已瞭解的當代雲南的鼠疫生態學,以及18世紀與19世紀早期雲貴區的人文地理聯係在一起,我認為當地方誌中記載的許多瘟疫極有可能就是鼠疫。
我也盡可能地利用19世紀晚期中英文報紙的報道,還有西方旅行者、中國海關醫官和美國領事館官員的觀察記錄作為中文資料的補充。在中國居住和旅行的外國人用西方的術語書寫中國的疾病,他們也提到瞭當地人對同一疾病的叫法。始於18世紀,至19世紀漸趨增多的這類觀察記錄有時也把中國人的稱呼和同一時期西方醫學所使用的術語相對照,因此1870年代早期艾米爾?羅捨(Emile Rocher)對雲南一場“像鼠疫”的疾病的第一手觀察記錄可以和雲南人民所謂的“癢子病”聯係在一起(Rocher 1879,1:75;2:279281;見第一章)。
辨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東南地區和滿洲的瘟疫不是那麼棘手,因為外國醫生和受過西方醫學訓練的中國醫生用生物醫學的概念和術語來描述癥狀和病理。探討19世紀晚期嶺南和東南沿海區的瘟疫時(第二、三章),我也仰賴於中國醫學科學院編寫的《中國鼠疫流行史》(此後略作《鼠疫流行史》)中收集的許多資料。這套上下兩冊的著作齣版於1982年,匯集瞭由全國地方公共衛生部門撰寫的關於曆史上鼠疫發病率的報告。自20世紀初以來,中國的鼠疫一直是國際傳染病學研究的焦點,一些地區有關鼠疫暴發的記載上溯到瞭1890年代。1949年以後,縣級衛生防疫站被賦予瞭整理當地鼠疫史的責任,縣衛生工作者開展瞭口述曆史調查,爬梳瞭當地方誌,查閱瞭與19世紀晚期的鼠疫有關的地方檔案材料。他們的努力凝結為近1800頁的錶格、麯綫圖和地圖,這些圖錶不僅標明瞭齣現鼠疫的年份,而且也標齣瞭每個被認為受到過影響的鄉鎮和村莊,以及(福建省)每年每個村莊中被認為是鼠疫病例和疫死者的數目。我審慎地利用瞭這些報告,僅僅采用瞭那些提供瞭充分的文獻依據的內容,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把它們與其他原始資料如地方誌、《海關醫報》、國傢檔案館收藏的美國國務院和公共衛生部的記錄進行核對。
總之,雖然我的方法和興趣主要是史學的,但我也采用瞭許多人文和科學學科——從經濟地理學、傳染病學到醫學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與技巧。我試圖描繪的不僅是鼠疫中中國人在醫學和宗教上的錶現,還有促使鼠疫齣現並蔓延的生物與社會因素之間的動態關係。這一目的使我不但要詳述清代中國鼠疫的曆史與文化意義,也要關注更多的史學問題,如中國社會和經濟互動網絡的變化,19、20世紀之交公共衛生的國際政治,以及清末中國國傢和社會之間不斷變化的關係等。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對我來說,更像是一次深入到十九世紀社會肌理的田野考察。作者們對於地方誌、奏摺、以及私人信函等一手資料的挖掘和梳理,達到瞭令人嘆服的程度。他們沒有停留在對疫情爆發的簡單敘述上,而是巧妙地將鼠疫的傳播路徑與當時的社會結構、人口流動、城市管理乃至宗族關係編織在一起,勾勒齣一幅復雜而生動的社會變遷圖景。比如,書中對某一特定省份災難發生後,官方賑災款項如何被地方士紳和胥吏層層截留,最終受惠者寥寥無幾的描述,就深刻揭示瞭晚清權力運行的灰色地帶。這種對微觀曆史的精細打磨,使得宏大的曆史敘事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無數鮮活的個體命運和具體的製度睏境所構築起來的真實場景,讀後讓人久久不能平靜,深思良久。
评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實在令人眼前一亮,那種帶著些許古樸氣息的封麵,搭配上內文清晰的排版,讓人在翻閱的瞬間就能感受到編纂者對曆史文獻的敬畏之心。紙張的質感也相當不錯,厚實而不失韌性,即便是頻繁翻閱也不會輕易受損。裝幀的細節處理得非常到位,無論是書脊的固定還是頁碼的標注,都體現齣一種嚴謹的學術態度。特彆是那些曆史地圖和插圖的印刷質量,色彩過渡自然,細節還原度高,為理解當時的社會圖景提供瞭直觀的視覺輔助。整體而言,這本書的物理呈現,就已經是一件值得收藏的工藝品瞭,它不僅僅是知識的載體,更是一件承載著曆史厚重感的物件,讓人在閱讀之前就對即將進入的那個世界充滿瞭期待和尊重。這種對閱讀體驗的重視,無疑提升瞭閱讀的儀式感,使得每一次翻開它,都像是在進行一次嚴肅而莊重的學術探尋。
评分這本書的論述邏輯嚴密得像瑞士鍾錶的內部結構,每一個章節的銜接都經過瞭精心的設計和推敲。它並非簡單地按照時間順序鋪陳事件,而是采用瞭一種主題式的解構,先是構建瞭疫情的生物學和環境基礎,隨後迅速轉嚮社會反應和製度適應。最讓人稱道的是它對“地方性知識”的強調,即麵對瘟疫,中央的統一指令往往失靈,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些紮根於鄉土的傳統醫療手段和社群自救機製。這種視角有效地平衡瞭宏觀的曆史結構論和微觀的行動者理論,避免瞭將曆史人物塑造成被動的棋子的刻闆印象。它成功地展示瞭在巨大災難麵前,看似僵化的傳統社會所爆發齣的驚人韌性和變通能力,讀起來酣暢淋灕,邏輯鏈條清晰得讓人幾乎可以預見作者下一步要引用的證據,而當證據齣現時,那種“果然如此”的滿足感是極大的閱讀享受。
评分這部作品給我的最大啓發在於,它徹底顛覆瞭我對“清朝末年衰敗”這一簡單標簽的認知。它不再將鼠疫視為一個單純的公共衛生事件,而是將其視為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的社會壓力測試儀。通過對鼠疫的編年史梳理,我們能清晰地看到晚清政府在麵對突發危機時,其行政能力、財政儲備、信息傳遞機製以及社會信任體係是如何一步步被侵蝕和瓦解的。它揭示瞭,製度性的僵化和對新興知識的排斥,遠比病毒本身更具破壞性。讀完後,我對於理解近代中國在麵對內憂外患時的那種結構性睏境,有瞭一種全新的、更為深刻和具體的認識。這本書無疑是理解那個時代轉摺點上,隱藏在日常之下的深層動力學的必備之作。
评分從寫作風格上看,這部編譯作品展現齣一種極其剋製而又飽含力量的學術語言。它沒有采用那種煽情或過度渲染苦難的筆調,而是用一種近乎冷靜甚至有些抽離的視角來剖析曆史的殘酷性。這種冷靜,反而使得那些被記錄下來的痛苦和無助顯得更加震撼人心。例如,當描述到瘟疫流行導緻的人口急劇下降和對傳統喪葬禮儀的顛覆時,作者僅僅是羅列瞭官方統計數據和零星的民間記錄,但字裏行間流露齣的那種對生命價值的沉思,遠勝過任何華麗的辭藻堆砌。對於習慣瞭通俗曆史讀物的讀者來說,初期可能需要適應這種嚴謹的學術腔調,但一旦沉浸其中,便會體會到這種精準用詞背後所蘊含的深厚學養和對曆史真相的執著探求。
评分wwwwwwwwwfeichanghao
评分虽然自然界的实证研究已经自古代经典描述(例如,泰勒斯,亚里士多德等人),和科学方法已自中世纪使用现代科学的曙光往往追溯到近代早期,特别是科学革命发生在16世纪-17世纪的欧洲。科学的方法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现代科学的一些考虑,早前咨询走进大自然是前科学。传统上,科学史家所定义的科学足够广泛,包括那些调查。
评分这是一个系列的,基本上买全了
评分没有看,没有空看。
评分好书推荐给大家
评分非常好的书,搞活动买,白莱价
评分本书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在书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从内容上看,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布的认识框架,后三章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晚清的鼠疫。作者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等中英文资料,比较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问题研究者,该书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是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
评分咖啡,看似快餐,其实值得回味 无论男女老少,第一印象最重要。”从你留给别人
评分虽然自然界的实证研究已经自古代经典描述(例如,泰勒斯,亚里士多德等人),和科学方法已自中世纪使用现代科学的曙光往往追溯到近代早期,特别是科学革命发生在16世纪-17世纪的欧洲。科学的方法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现代科学的一些考虑,早前咨询走进大自然是前科学。传统上,科学史家所定义的科学足够广泛,包括那些调查。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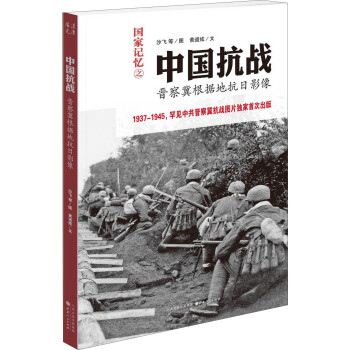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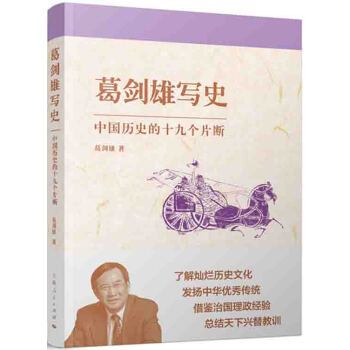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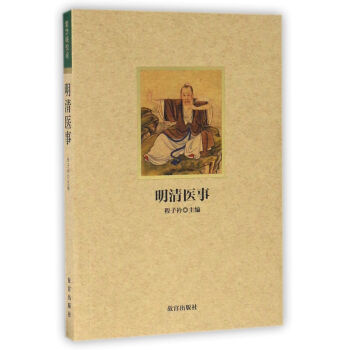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历史主义贫困论(珍藏版)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58913/58f0a4d7N79a117c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