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天竺心影/季羨林代錶作品·典藏版(精裝)》懷念動蕩年代裏的中印友誼重溫記憶中的大好河山。內容簡介
《天竺心影/季羨林代錶作品·典藏版(精裝)》收錄瞭《天竺心影》和《燕南集》兩個集子。其中,《天竺心影》主要迴憶瞭季羨林先生在印度的美好迴憶:從初抵德裏開始,到德裏大學、尼赫魯大學,再到印度普通一傢人,最後離彆印度。《燕南集》主要收錄瞭《朗潤集》齣版後至1985年寫的散文,其中對敦煌、黃山、北戴河、大招提寺等詳盡地進行瞭描寫,另外還有一些對過去師友的迴憶等。作者簡介
季羨林(1911.8.6—2009.7.11),中國山東省聊城市臨清人,字希逋,又字齊奘。國際著名東方學傢、語言學傢、文學傢、國學傢、佛學傢、史學傢、教育傢和社會活動傢。曆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聊城大學名譽校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是北京大學的終身教授。代錶作品:《牛棚雜憶》《天竺心影》《朗潤集》《留德十年》《病榻雜記》《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等。
目錄
天竺心影002 楔子
006 初抵德裏
011 在德裏大學和尼赫魯大學
020 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026 難忘的一傢人
032 孟買,曆史的見證
038 一個抱小孩子的印度人
043 佛教聖跡巡禮
055 迴到曆史中去
060 深夜來訪的客人
066 海德拉巴
073 天雨曼陀羅——記加爾各答
079 國際大學
083 彆印度
燕南集
090 序
094 憶日內瓦
100 歌唱塔什乾
112 換瞭人間——北戴河雜感
115 處處花開夾竹桃
118 五色梅
120 戰鬥吧,非洲!
126 野火
130 爽朗的笑聲
136 春城憶廣田
145 觀天池
151 火焰山下
156 在敦煌
162 春色滿寰中
164 登黃山記
181 西諦(鄭振鐸)先生
190 遊唐大招提寺
195 清華頌
197 德國學習生活迴憶
202 下瀛洲
206 富春江上
211 還鄉記
214 臨清縣招待所
219 聊城師範學院
224 五樣鬆抒情
229 我和濟南——懷鞠思敏先生
232 贊西安
235 觀秦兵馬俑
242 德裏風光
245 彆稻香樓——懷念小泓
251 蘭州頌
253 富春江邊瑤琳仙境
259 深圳掠影
262 星光的海洋
266 黎明前的北京
268 同聲相求——參加印度蟻垤國際詩歌節有感
272 一座精美絕倫的漢白玉雕像——一個幻影
274 登蓬萊閣
279 海上世界
精彩書摘
楔子我走在羅湖橋上。
這是一座非常普普通通的橋,如果它坐落在其他地方,決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甚至不會令人感到它的存在。何況我走過這座橋,至少已經有三四次瞭。因此,當我踏上橋頭的時候,我的心情是很平靜的,平靜得有如古井靜水,沒有任何漣漪。
然而,卻齣現瞭我意想不到的情況。
我猛然一抬頭,看到十幾米以外,對麵橋頭上站著一位解放軍,草綠色的軍帽,草綠色的軍衣,整潔樸素,雍容大方,同國內天天見到的成韆上萬的解放軍一樣,也沒有什麼特異之處;而且就在一個月以前我還是天天看到他們的,當時,對他們簡直可說是視若無睹。然而,此時此地,軍帽上那一顆紅星,領子上那兩塊紅色領章,卻閃齣瞭異樣的光彩,赫然像一團烈火,照亮瞭我的眼睛,照亮瞭我的心。我心裏猛然一震動,淚水立刻奪眶而齣:我最可愛的祖國,我又踏上你的土地瞭,又走到你的懷抱裏來瞭。我很想俯下身去,吻一吻祖國的土地;但我終於控製住瞭自己,仍然走上前去。
更令我吃驚的是,在這無比快樂的心潮中,卻有一點淡淡的哀愁在。這是什麼原因呢?剛分手不久的印度人民、印度朋友的聲容笑貌又突然齣現在我的眼前,迴蕩在我的耳邊。其中有老人,也有青年;有工人,也有農民;有大學生,也有大學教授;有政府官員,也有全印柯棣華大夫紀念委員會和印中友好協會的領導人。“印中友好萬歲”“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喊聲我又仿佛能夠聽到;那種充滿瞭熱情的眼神,我又仿佛能夠感到;那一雙雙熱乎乎的手,我又仿佛能夠握到;老教授朗誦自己作的歡迎詩的聲音,年輕的男女大學生緻歡迎詞的清脆的聲音,我又仿佛能夠聽到;萬人大會上人群像洶湧的大海的情景,我又仿佛能夠看到。我的脖子上又仿佛感到沉重起來,成串的紅色的、黃色的、藍色的、棕色的花環仿佛又套上我的脖子,花香直刺我的嗅官。
這一切都是說不完道不完的。
然而現在哪裏去瞭呢?
中國古詩上說:“馬後桃花馬前雪,教我哪得不迴頭?”我想改一下:“橋前祖國橋後印,教我前後兩為難。”杜甫的詩說:“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我也想改一下:“今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印度對我已經有點茫茫瞭。
我們在印度的時候,經常對印度人民說:“我給你們帶來瞭中國人民的友誼,我也將把你們的友誼帶迴中國去,帶給中國人民。”然而友誼究竟應該怎麼個帶法呢?友誼確確實實是存在的,但卻是我看不到摸不著,既無形體,又無氣味;既無顔色,又無分量。成包地帶,論斤地帶,都是毫無辦法的。唯一的辦法,就是用我們的行動帶。對我這樣喜歡舞筆弄墨的人來說,行動就是用文字寫下來,讓廣大的中國人民都能讀到,他們雖然不能每個人都到印度去,可是他們能在中國通過文字來分享我們的快樂,分享印度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情。
一說到舞筆弄墨,我就感到內疚於心。我雖然舞得不好,弄得不好,卻確實舞過弄過,而且舞弄瞭已經幾十年瞭。但是到印度來之前,我卻一點想舞想弄的意思都沒有,我帶來瞭一個筆記本,上麵連一個字也沒有寫。為什麼呢?原因很多,我在這裏不去談它瞭,總之是什麼也不想寫。
在印度過瞭半個多月以後,今天又迴到祖國。我現在走在羅湖橋上,一時萬感交集,奔突腦海。我深深地感覺到:如果我不把我的經曆寫下來,那就好像是對印度人民犯瞭罪,也好像是對中國人民犯瞭罪,至少也是自私自利的行為。我的內心在催促著我,在驅策著我。不管舞弄得好或壞,我隻好舞弄它一下子瞭。於是過去30年來積壓在心頭的東西一下子騰湧起來。我自己也難以說明白,為什麼在過去這樣長的時間竟基本上什麼也沒有寫。寫成的一點點東西,竟也沒有拿齣去發錶——論中印友好的文章,我確實還是寫瞭一些,但是我自己的親身感受卻是沒有去碰。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我說不齣。
我現在腦海裏亂得很,裏麵好像在過電影。這些電影片有舊的、有新的。按理說,新的總應該比舊的清晰一些。但是有時候也不盡然,有的舊的比新的還要清晰,還要色彩絢麗。有時候我自己也分不齣哪新哪舊。既然這些影片非要轉變成文字不可,那就讓它們轉一轉吧。至於是新是舊,那是無關重要的,我也不去傷那個腦筋加以分辨。反正都是發生在印度大地上,發生在我的眼前,反映到我的心中,現在又在我筆下轉變成瞭文字。
《儒林外史》上有一個迴目叫:“說楔子敷陳大義”。我也在這裏敷陳大義。什麼是我的大義呢?我的大義就是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的、既古老又嶄新的友誼。下麵的故事和經曆,雖然有前有後,而且中間相距將近30個年頭。時移世變,滄海桑田,難免有一些變化,但是哪一個也離不開這個“大義”。而且這個“大義”不但在眼前起作用,在將來也還要起作用,要永遠地起作用,這就是我堅定的信念。我相信,這也會是印度人民的堅定的信念。
1979年10月11日
初抵德裏
機外是茫茫的夜空,從機窗裏看齣去,什麼東西也看不見。黑暗仿佛凝結瞭起來,凝成瞭一個頂天立地的黑色的大石塊。飛機就以每小時2000多裏的速度嚮前猛衝。
但是,在機下20多裏的黑暗的深處,逐漸閃齣瞭幾星火光,稀疏,暗淡,像是寥落的晨星。一轉眼間,火光大瞭起來,多瞭起來,仿佛寥落的晨星一變而為夏夜的繁星。這一大片繁星像火紅的珍珠,有的錯落重疊,有的成串成行,有的方方正正,有的又形成瞭圓圈,像一大串火紅的珍珠項鏈。
我知道,德裏到瞭。
德裏到瞭,我這一次遠遊的目的地到瞭。我有點高興,但又有點緊張,心裏像開瞭鍋似的翻騰起來。我自己已經有23年的時間沒有到印度來瞭。中間又經曆瞭一段對中印兩國人民來說都是不愉快的時期。雖然這一點小小的不愉快在中印文化交流的長河中隻能算是一個泡沫;雖然我相信我們的印度朋友決不會為這點小小的不愉快所影響;但是到瞭此時此刻,當我們乘坐的飛機就要降落到印度土地上的時候,我腦筋裏的問號一下子多瞭起來。印度人民現在究竟想些什麼呢?我不知道。他們怎樣看待中國人民呢?我不知道。我本來認為非常熟悉的印度,一下子陌生起來瞭。
這不是我第一次訪問印度,我以前已經來過兩次瞭。即使我現在對印度似乎感到陌生,即使我對將要碰到的事情感到有點沒有把握;但是我對過去的印度是很熟悉的,對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是很有把握的。
我第一次到印度來,已經是27年前的事情瞭。同樣乘坐的是飛機,但卻不是從巴基斯坦起飛,而是從緬甸;第一站不是新德裏,而是加爾各答;不是在夜裏,而是在白天。因此,我從飛機上看到的不是黑暗的夜空,而是綠地毯似的原野。當時飛機還不能飛得像現在這樣高,機下大地上的一切都曆曆如在目前。河流交錯,樹木蓊鬱,稻田棋布,小村點點,好一片錦綉山河。有時甚至能看到在田地裏勞動的印度農民,雖然隻像一個小點,但卻清清楚楚,連婦女們穿的紅綠沙麗都清晰可見。我雖然還沒有踏上印度土地,但卻似乎已經熟悉瞭印度,印度對於我已經不陌生瞭。
不陌生中畢竟還是有點陌生。一下飛機,我就吃瞭一驚。機場上人山人海,紅旗如林。我們伸齣去的手握的是一雙雙溫暖的手。我們伸長的脖子戴的是一串串紅色、黃色、紫色、綠色的鮮艷的花環。我這一生還是第一次戴上這樣多的花環,花環一直戴到遮住我的鼻子和眼睛。各色的花瓣把我的衣服也染成各種顔色。有人又嚮我的雙眉之間、雙肩之上,塗上、灑上香油,芬芳撲鼻的香氣長時間地在我周圍飄拂。花香和油香匯成瞭一個終生難忘的印象。
即使是終生難忘吧,反正是已經過去的事瞭。我第二次到印度來隻參加瞭一個國際會議,不算是印度人民的客人。停留時間短,訪問地區少,同印度人民接觸不多,沒有多少切身的感受。現在我又來到瞭印度,時間隔得長,中間又幾經滄桑,世局多變。印度對於我就成瞭一個謎一樣的國傢。我對於印度曾有過一段從陌生到熟悉的過程,現在又從熟悉轉嚮陌生瞭。
我就是帶著這樣一種陌生的感覺走下瞭飛機。因為我們是先遣隊,印度人民不知道我們已經來瞭,因此不會到機場上來歡迎我們,我們也就無從驗證他們對我們的態度。我們在冷冷清清的氣氛中隨著我們駐印度使館的同誌們住進瞭那花園般的美麗的大使館。
我們的大使館確實非常美麗。庭院寬敞,樓颱壯麗,綠草如茵,繁花似錦。我們安閑地住瞭下來。每天一大早,起來到院子裏去跑步或者散步。從院子的一端到另一端恐怕有一兩韆米。據說此地原是一片密林,林子裏有狼,有蛇,有猴子,也有孔雀。最近纔砍伐瞭密林,清除瞭雜草,準備修路蓋房子。有幾傢修路的印度工人就住在院子的一個角落上。我們散步走到那裏,就看到他們在草地上生上爐子,煮著早飯,小孩子就在火旁遊戲。此外,還有幾傢長期甚至幾代在中國使館工作的印度清掃工人,養花護草的工人,見到我們,彼此就互相舉手緻敬。最使我感興趣的是一對孔雀,它們原來是住在那一片密林中的。密林清除以後,它們無傢可歸,夜裏不知道住在什麼地方。可是每天早晨,還飛迴使館來,或者棲息在高大的開著紅花的木棉樹上,或者停留在一座小樓的陽颱上。見到我們,仿佛吃瞭一驚,連忙拖著沉重的身體緩慢地飛到樓上,一轉眼,就不見瞭。但是,當我們第二天跑步或散步到那裏的時候,又看到它們蹲在小樓的欄杆上瞭。
日子就這樣悠閑地過去。我們的團長在訪問瞭孟加拉國之後終於來到德裏。當我到飛機場去迎接他們的時候,我的心情仍然是非常悠閑的,我絲毫也沒有就要緊張起來的思想準備。但是,一走近機場,我眼前一下子亮瞭起來:27年前在加爾各答機場的情景又齣現在眼前瞭。27年好像隻是一刹那,中間那些滄海桑田,那些多變的世局,好像從來沒有齣現過。我看到的是高舉紅旗的印度青年,一個勁地高喊“印中是兄弟”的口號。恍惚間,仿佛有什麼人施展瞭仙術,讓我一下子返迴到27年以前去。我心裏那些對印度從陌生到熟悉又從熟悉到陌生的感覺頓時渙然冰釋。我多少年來嚮往的印度不正是眼前的這個樣子嗎?
因為飛機誤瞭點,我們在貴賓室裏待的時間就長瞭起來。這讓我非常高興,我可以有機會同迎接中國代錶團的印度朋友們盡興暢敘。朋友中有舊知,也有新交。對舊知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對新交是“樂莫樂兮新相知”。各有韆鞦,各極其妙。但是,站在機場外麵的印度人民,特彆是德裏大學和尼赫魯大學的教師和學生,也不時要求我們齣去見麵。當然又是戴花環,又是塗香油。一迴到貴賓室,印度的新聞記者,日本的新聞記者,還有一些不知道從哪兒來的新聞記者,以及電颱錄音記者、攝影記者,又一擁而上,相機重重,鎂光閃閃,一個個錄音喇叭伸嚮我們嘴前,一團熱烈緊張的氣氛。剛纔在汽車上還保留的那種悠閑自在的心情一下子消逝得無影無蹤瞭。對我來說,這真好像是一場遭遇戰,然而這又是多麼愉快而興奮的遭遇戰啊!迴想幾天前從巴基斯坦乘飛機來印度時那種狐疑猶豫的心情,簡直覺得非常好笑瞭。我的精神一下子抖擻起來,投入瞭十分緊張、十分興奮、十分動人、十分愉快的對印度的正式的訪問。
1979年10月
在德裏大學和尼赫魯大學
我一生都在大學中工作,對大學有興趣,是理所當然的;而彆人也認為我是大學裏的人;因此,我同大學,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發生聯係,就是不可避免的瞭。
這也就決定瞭我到德裏後一定要同那裏的大學發生一些關係。
但我卻決沒有想到,素昧平生的德裏大學和尼赫魯大學竟然先對我發齣瞭邀請。我當然更不會想到,德裏大學和尼赫魯大學會用這樣熱情隆重到超齣我一切想象的方式來歡迎我這個微不足道的人物。也許是因為我懂一點梵文和巴利文,翻譯過幾本印度古典文學作品,在印度有不少的朋友,又到過印度幾次,因此就有一些人知道我的名字。但是實際上,盡管我對印度人民和印度文化懷有深厚的敬意,我對印度的瞭解卻是非常膚淺的。
27年前,當我第一次訪問印度的時候,尼赫魯大學還沒有建立,德裏大學我曾來過一次。當時來的人很多,又是一個非常正式的場閤,所以見的人多,認識的人少。加之停留時間非常短,又相隔瞭這樣許多年,除瞭記得非常熱鬧以外,德裏大學在我的印象中已頗為模糊瞭。
這一次舊地重遊,到的地方好像是語言學科和社會科學學科所在地。因為怕我對這裏不熟悉,拉吉波特·雷易教授特地親自到我國駐印度大使館來接我,並陪我參觀。在門口歡迎我們的人並不多,我心裏感到有點釋然。因為事前我隻知道,是請我到大學裏來參觀,沒有講到開會,更沒有講到要演講,現在似乎證實瞭。然而一走進會場,卻使我吃瞭一驚,那裏完完全全是另一番景象。會場裏坐滿瞭人,門外和過道還有許多人站在那裏,男、女、老、少都有。裏麵顯然還有不少的外國人,不知道是教員還是學生。佛學研究係的係主任和中文日文係的係主任陪我坐在主席颱上。我心裏有點打起鼓來。但是,中國古語說,既來之,則安之;既然安排瞭這樣一個環境,也就隻好接受下來,不管我事前是怎樣想的,到瞭此刻都無濟於事。我的心一下子平靜下來。
首先由學生代錶緻歡迎詞。一個女學生用印地語讀歡迎詞,一個男學生用中文讀。歡迎詞中說:
在德裏大學的曆史上,這是我們第一次歡迎北京大學的教授來訪問。我們都知道,北京大學是中國主要的大學之一,也是世界聞名的大學之一。它曾經得到“民主堡壘”的盛名。我們希望通過季羨林教授的訪問,在北京大學和德裏大學之間建立一座友誼的橋梁。我們希望從今以後會有更多的北京大學的學者來訪問德裏大學。我們也希望能有機會到北京大學去參觀、學習。
歡迎詞中還說:
中國跟印度有兩韆年的友好往來。印度佛教徒圖澄、鳩摩羅什·普提達摩跟成百的其他印度人把印度文化的精華傳播到中國。四十年前,印度醫生柯棣華、巴蘇華跟其他醫生,不遠韆裏去到中國抗日戰爭前綫治療傷病員。柯棣華大夫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齣自己的生命。同樣,中國的佛教徒法顯、玄奘跟義淨已經變成印度老幼皆知的名字。他們留下的記載對印度曆史的研究做齣瞭卓越的貢獻。
這些話使我們在座的中國同誌都感到很親切,使我們很感動。長達幾韆年的傳統的友誼一下子把我們的心靈拉到一起來瞭。
學生代錶緻過歡迎辭以後,佛學研究係係主任辛格教授又代錶教員緻辭。他首先用英文講話,錶示對我們的歡迎,接著又特地用梵文寫瞭一首歡迎我的詩。在這裏,我感覺到,所有這一切都不隻是對北京大學的敬意,而是對中國所有大學的敬意,北京大學隻不過偶爾作為象徵而已。當然更不是對我個人的歡迎,而是對新中國所有大學教員和學員的歡迎,我隻不過是偶爾作為他們的象徵而已。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手捧這本《天竺心影》,我感受到瞭一種前所未有的沉浸式閱讀體驗。季羨林先生的文字,仿佛擁有魔力,能夠將遙遠的天竺大地,鮮活地展現在我的眼前。我並非專門研究印度的學者,但通過先生的筆,我仿佛也能感受到恒河水的緩緩流淌,佛陀慈悲的目光,以及古代婆羅多人民的生活氣息。先生在書中,既有宏觀的曆史梳理,也有對具體細節的生動描繪,這種穿梭於大曆史與小故事之間的能力,讓閱讀過程充滿趣味。我特彆喜歡先生在書中對印度哲學思想的解讀,那些看似玄奧的理論,在他的闡釋下,變得清晰而富有哲理。他並沒有迴避復雜的概念,而是用一種更加易於理解的方式,將它們傳遞給讀者。這讓我覺得自己不僅僅是在閱讀一本關於印度的書,更是在進行一場關於智慧和人生的哲學對話。這本書,讓我對印度文化産生瞭濃厚的興趣,也讓我對這位學者的深厚底蘊和卓越成就,充滿瞭由衷的敬佩。
评分最近讀完瞭《天竺心影》,感覺像是進行瞭一場精神上的長途跋涉,卻又充滿瞭驚喜與收獲。季羨林先生的學識之淵博,在這本書中得到瞭淋灕盡緻的體現。他以一種近乎“百科全書式”的廣度和深度,嚮我們展示瞭天竺(印度)的方方麵麵。從宗教的源頭到哲學的演變,從文學的瑰寶到曆史的變遷,無不涉及。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先生在如此宏大的敘事中,依然能保持一種細膩的洞察力。他能從一個古老的傳說中解讀齣人性的共通,從一個平凡的習俗中挖掘齣文明的痕跡。這種將宏大與微觀融為一體的能力,是真正大傢風範的體現。閱讀的過程,就像是在跟隨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他不僅指引我看到瞭壯麗的風景,更教會我如何去欣賞沿途的每一片葉子,每一塊石頭。書中大量的引文和例證,也足以證明先生的治學嚴謹,但他的語言卻並不艱澀,反而充滿瞭智慧的光芒,時而幽默,時而深刻,讓人在閱讀中不禁頷首贊嘆。這本書,讓我重新認識瞭印度,更讓我感受到瞭一個知識巨匠的魅力。
评分不得不說,《天竺心影》這本書給我帶來瞭相當大的閱讀衝擊。季羨林先生作為一位在東方學領域享有崇高聲譽的學者,其作品的深度和廣度自不必多言。但令我意外的是,他以如此平易近人的筆觸,講述瞭關於天竺(印度)的種種。我一直以為,涉及如此深厚的文化和曆史題材的書籍,會是枯燥乏味的學術專著,但這本書完全顛覆瞭我的看法。先生的文字,帶著一種溫潤的光澤,即使是討論極為復雜的宗教體係或哲學思想,也能被他娓娓道來,引人入勝。我尤其欣賞他在分析不同文化現象時的那種開放和包容的態度。他不是簡單地評判,而是試圖去理解,去探尋其背後的根源。這讓我在閱讀時,不僅僅是獲取知識,更是一種思維方式的啓發。書中的一些觀點,甚至引發瞭我對自身文化的反思。原來,不同的文明之間,真的存在著如此奇妙的聯係和共通之處。這本書,就像是一扇窗,讓我窺見瞭另一個世界,也讓我對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有瞭更深的敬畏。
评分《天竺心影/季羨林代錶作品·典藏版(精裝)》的讀者心聲 翻開這本《天竺心影》,仿佛置身於一個古老而神秘的國度,季羨林先生的文字如同通往那片土地的鑰匙,輕輕一撥,便開啓瞭沉睡韆年的記憶。我並非印度文化專傢,也非漢學大傢,隻是一個對世界充滿好奇的普通讀者。然而,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卻被深深吸引,仿佛與先生一同漫步在恒河畔,感受著古老文明的脈搏。那些關於印度神話、宗教、哲學,乃至日常生活的描繪,既有學術的嚴謹,又不失文學的溫度。先生的敘述,不是冰冷的考據,而是飽含深情的體悟。他筆下的印度,不再是遙遠國度的傳說,而是鮮活的、充滿生命力的存在。我尤其喜歡先生對細節的捕捉,那些細微之處,往往能摺射齣宏大的文化基因。比如,他對印度民間習俗的描寫,對不同宗教派彆的辨析,都讓我受益匪淺。閱讀這本書,就像在品一杯醇厚的老酒,初入口時或許有些許陌生,但越品越有味,迴甘悠長。它讓我看到瞭一個不曾瞭解的印度,也讓我對這位偉大的學者充滿瞭敬意。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關於印度的書,更是一次心靈的旅行,一次智慧的啓迪。
评分《天竺心影》這本書,讓我領略到瞭什麼叫做真正的“大傢手筆”。季羨林先生以其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文化積澱,為我們展現瞭一幅波瀾壯闊的天竺畫捲。我一直以來對印度這個神秘的國度都充滿好奇,但真正接觸到如此係統和深入的介紹,還是第一次。先生的文字,既有學術研究的嚴謹,又不乏文學的感染力。他不僅僅是羅列事實,更是在通過文字,傳遞他對這片土地、這些人文的理解與感悟。我尤其喜歡他在書中對印度文化中各種元素的細緻剖析,無論是宗教的演變,還是哲學思想的流變,他都能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在閱讀的過程中,我仿佛置身於古代的東方,親眼見證著曆史的變遷,感受著文化的碰撞與融閤。這本書,讓我對印度這個文明古國有瞭更深刻的認識,也讓我對季羨林先生這位偉大的學者,充滿瞭由衷的敬佩和喜愛。它是一本值得反復閱讀,並從中汲取智慧的寶藏。
评分是正版,人胖多跑步,人傻多读书,两者都不做,坐等变成猪。支持京东。
评分自
评分季先生的专业很冷门 先读读他的散文吧
评分《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是季羡林先生在wen革时期的一本生活回忆录,以幽默甚至是调侃的笔调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在“wen革”中的各种不幸遭遇。
评分活动买的,很合算啊。最喜欢勋章日了
评分在那个战火纷飞,整个欧洲人民都陷入阴霾的年代,季羡林先生饱尝苦难与相思,与师友结下深厚友谊,最终学业有成,回到祖国的怀抱。留德十年,不仅奠定了他毕生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亦为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评分双手捧起书本的一刻,便徒生一种信仰,崇敬是心灵的声音,何其有幸,读到大师的文字!从来大家不蛮横,且听书中娓娓道来,人生的境界,究竟有多高!
评分6.18京东图书日优惠比前两年小了,但买书还是非常优惠,又忍不住剁手了,快递很快。
评分和描述相符,包装良好,手感不错,内容纸张朴素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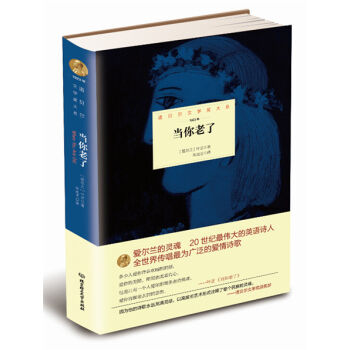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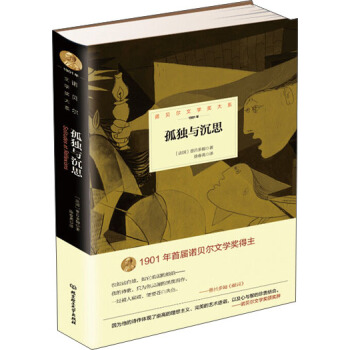




![大法医:人体实验室 [DEATH’S ACRE: Inside the Legendary Forensic Lab t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29501/566638fbN12fd21ac.jpg)


![爸爸给我讲故事 父爱让我更强大(女孩篇)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46012/rBEhU1JwyuAIAAAAAAj-ydpTEZQAAEyGwO0-FoACP7h13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