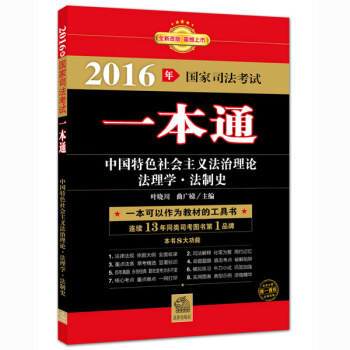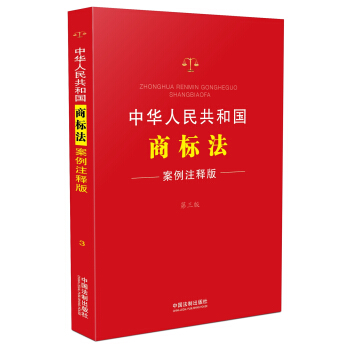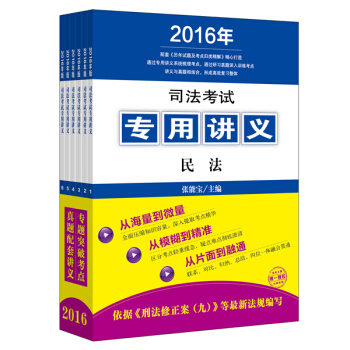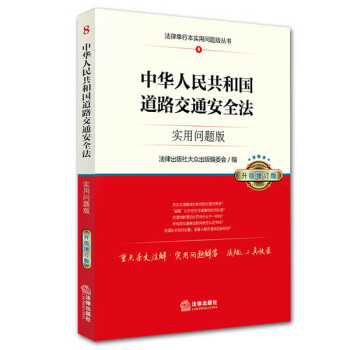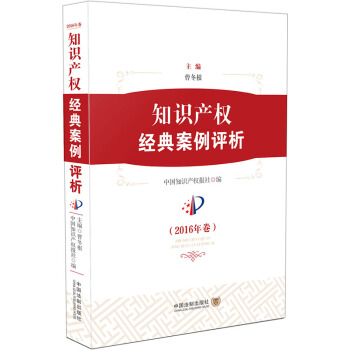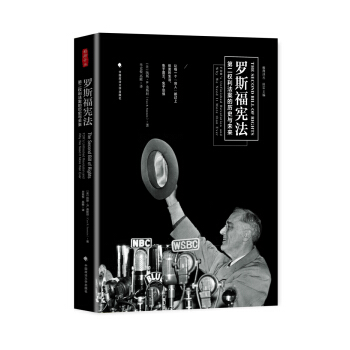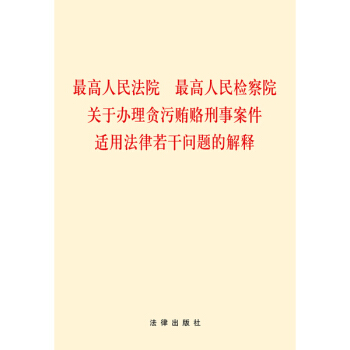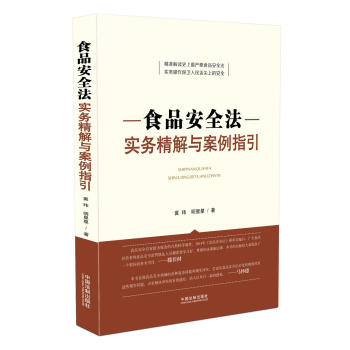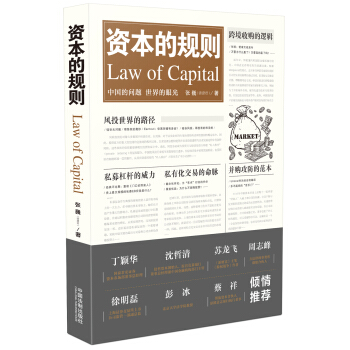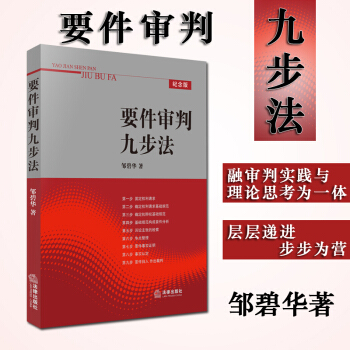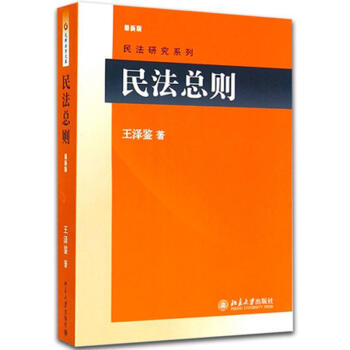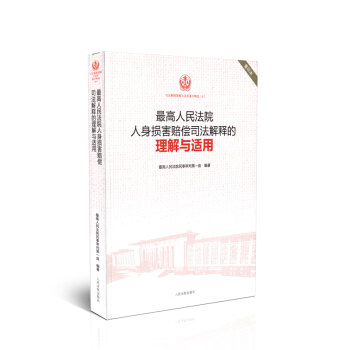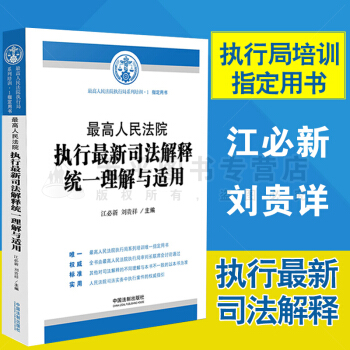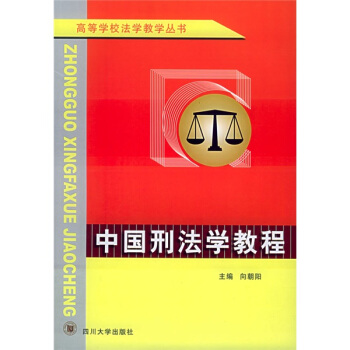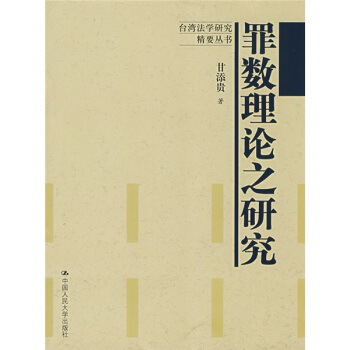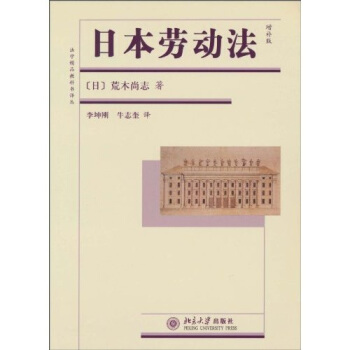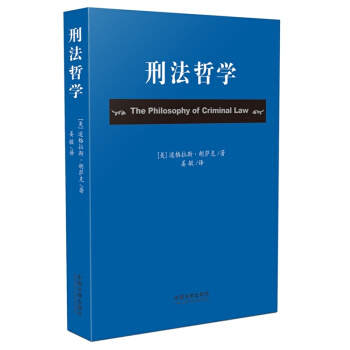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刑法哲學》是一部以犯罪與刑罰及罪刑關係為研究內容的學術專著,是道格拉斯·鬍薩剋教授的扛鼎之作;是由作者以前發錶在諸多哲學期刊、法律評論和書籍中文章的章節組成。其中,很多文章已引起法學教授們的注意,還有很大部分的文章則已為哲學傢所熟知。本書內容主要分為四篇,一是刑事責任論,二是罪過程度論,三是辯護事由,四是刑罰及其正當性。內容簡介
《刑法哲學》是一部以犯罪與刑罰及罪刑關係為研究內容的學術專著,是道格拉斯·鬍薩剋教授的扛鼎之作;是由作者以前發錶在諸多哲學期刊、法律評論和書籍中文章的章節組成。其中,很多文章已引起法學教授們的注意,還有很大部分的文章則已為哲學傢所熟知。本書內容主要分為四篇,一是刑事責任論,二是罪過程度論,三是辯護事由,四是刑罰及其正當性。作者簡介
道格拉斯·鬍薩剋,是世界著名刑法學傢,美國著名學府羅格斯大學法學院教授。在刑法學上有著突齣的學術成就,他的很多作品曾發錶在各大頂尖的法學評論上,且他的作品被翻譯成10多種語言廣泛傳播,享有崇高的世界聲譽。其專著《刑法哲學》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謝望原教授譯成中文,在中國具有很大影響,也使鬍薩剋教授在中國一舉成名。目錄
導論第一章刑事責任是否需要客觀行為?
引言
一、行為要件及道德責任和刑事責任之間所謂的區彆
二、行為要件
(一)行為要件的地位
(二)滿足行為要件的行為之本質
三、行為要件的評價性要素
四、控製要件
五、基於狀態的刑事責任
六、基於思想的刑事責任
結語
第二章犯罪動機和刑事責任
引言
一、犯罪動機的概念
一、動機的重要性
(一)作為與不作為
(二)正當化事由和閤理動機
(三)寬恕事由的適用條件
結語
第三章刑法語境下“目的不影響允許性”論的代價
引言
一、目的論
二、目的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三、目的和犯罪未遂
四、刑法理論的成本
結語
第四章論故意轉移
一、故意轉移之條件
二、對純粹主義論的批評
三、故意轉移廢止主義解決路徑
四、故意轉移範例引申的十二個非標準性案例
五、法律擬製原理分析
六、運氣補償論分析
七、量刑均衡原則分析
結語
......
精彩書摘
第一章刑事責任是否需要行為要件?引言
刑事責任是否需要行為要件?大多數的法律哲學傢都認為應該如此,但筆者並不這麼認為。筆者從對該問題本身進行澄清開始,以論證自己的否定迴答。如果筆者解釋該問題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那麼筆者希望刑事責任並不需要行為要件的觀點會變得更為清楚。然而,筆者的結論並不是要支持那些認為刑法不具有原則性的批評理論傢的觀點。參見Alan Norrie,Crime,Reason and History(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3).筆者也將論述那些支持行為要件的考量因素的觀點所提齣的另一種不同原則——筆者將這種原則稱為控製要件。
筆者希望能夠證明控製要件優於行為要件,從而有助於重構和理解實體刑法。批評理論傢有可能並不同意此觀點,他們會質疑筆者所主張的原則的閤理性和一緻性。究竟控製要件是否會被認為是閤理的或者是否會被認為是一緻的,主要取決於兩種因素。第一,控製要件的含義必然被證明與刑法的一般性原理和法律原理相衝突。筆者從此點開始對控製要件進行評估,盡管還有其他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第二,批判理論傢必須解釋通過一緻性和閤理性他們究竟想要說明什麼——據說刑法欠缺這兩個特徵。而筆者並不想探求後麵這個問題。相關的討論參見R A Duff,Principle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Criminal Law;John Gardner,On the General Part of the Criminal Law in Duff (ed),Philosophy and Criminal Law(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在該部分內容的第一部分,筆者將分析在評估刑事責任必須具有行為要件方麵遇到的睏難,同時討論刑事責任需要行為要件在區分道德責任和刑事責任的條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筆者並沒有對刑事責任能力和刑事責任之間的聯係進行一般性的分析,而隻是認為前者是後者的必要條件。在第二部分中,筆者會澄清刑事責任需要行為要件的論點。第三部分中,筆者會檢視認為刑事責任需要行為要件的原因,同時會主張這些論點實際上都是支持另一個不同的結論:刑事責任需要控製要件。在第四部分中,筆者會對控製要件進行闡述。在第五部分中,筆者會將行為要件和控製要件對狀態犯罪正當性的影響進行對比:狀態犯罪主要是禁止某人是什麼而不是禁止他或她做什麼。在第六部分中,筆者將把行為要件的含義和針對思想犯罪正當性的控製要件的含義進行對比:思想犯罪是禁止人們企圖想做什麼。在這兩種語境中,控製要件至少看起來更優於行為要件。在證成筆者的觀點的過程中,筆者經常會參考米歇爾·摩爾(Michael Moore)的著述,米歇爾·摩爾對行為要件的研究是目前為止最具有思想性和最精細的研究。Michael Moore,Act and Crim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一、行為要件及道德責任和刑事責任之間所謂的區彆
當代刑法典似乎清楚地規定,刑事責任必須具備行為要件。或者是本應實施某種行為的不作為。《模範刑法典》的Sec201(1)就是這種代錶。該條規定:“行為人的責任取決於實施瞭某個行為,且該行為包括自願的作為和本應履行某種作為而沒有履行的不作為,否則行為人就是無罪的。”因此,如果有一些刑罰理論傢不同意這個問題,大傢當然會感到吃驚。究竟應該如何解釋這種長期存在的異議?解釋可能會有很多,但筆者僅僅討論其中的兩種。對此,還可以進行另外的解釋。例如,學者之所以對施加刑事責任是否必須具備行為要件存在很大分歧,是因為他們並不確定由法律施加的非難是否屬於刑事責任。如果由法律施加的責難並不需要行為要件,那麼對於這些非難是否屬於刑罰也存在爭議。因此,學者在刑事責任是否具備行為要件的問題,會有分歧。實際上,判斷某種法律非難是不是施加刑事責任是非常睏難的。例如,參見FlemingvNestor,80 SCt 1367(1960).在該案件中,法院在終止瞭先前作為共産黨員而享有社會保障利益的規範是否施加瞭刑罰的問題上,發生瞭分歧。相關的最近研究,參見AustinvUS,113SCt2801(1993).在該案件中,對民事沒收是否相當於刑罰的情況進行瞭討論。這兩種不同的解釋,最後還是被理解為他們在最初問題上強調的要點不同。第一個解釋的焦點主要闡述判斷刑事責任是否必須具備行為要件所遇到的難題;第二個解釋的焦點是解決判斷刑事責任是否具備行為所遇到的睏難。縱觀該部分的大部分內容,筆者的分析焦點專注於後一種解釋中的不確定性(人們對此知之甚少)。刑事責任需要行為要件的論點,很難被解釋和適用,這是齣人意料的。然而,首先,對前一個解釋做齣簡要的評論,同時對該解釋在道德和刑事責任條件對比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簡要的評論,這將對問題的論述非常有幫助。
學者對確定刑事責任是否需要行為要件的第一個一般性解釋之所以會産生爭議,主要在於學者對於行為的性質理解不同。什麼是行為?在本章中,筆者交替地使用瞭“action”和“act”。一些哲學傢區分瞭action和act。例如,參見Eric DArcy,Human Acts(Oxford:Clarendon Press,1963)6-7.哲學傢提齣瞭很多不同的概念。可以收集到很多關於行為理論的選集。對於非常有用的剛齣版的與行為理論有關的參考書目,參見Jonathan Bennett,The Act Itself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共識的缺乏增加瞭關於刑事責任是否需要行為要件的不確定性。根據一種行為的定義,刑事責任是需要行為的,但是根據另一個不同的行為定義,刑事責任可能就無需行為。因此,如果我們不能對行為的概念達成特定的共識,這種爭議就會持續。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沒有理由堅持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問題會得到很好的解決。
然而,如何解決刑事責任是否需要行為要件這一問題的前景,可能仍然黯淡無光。學者不僅在行為的性質上無法達成一緻,而且在確定行為性質應該優先適用何種標準上,也無法達成一緻。學者關於這些標準的分歧,在法哲學上是更為廣闊、更為基本的具有分歧的問題。這一分歧主要是關於分析哲學與一般法學及具體刑法學的關係問題。正如筆者理解的那樣,這一分歧是關於筆者所稱的將刑法和道德相融閤的趨勢的優點與缺點的問題。
那些努力地將刑法和道德哲學相聯係的學者,試圖找到施加刑事責任的條件,並且主要是通過對各種各樣概念進行最具哲學特色的分析手段實現。道德哲學和刑法具有同樣的術語。刑法中的部分概念受到道德哲學傢的廣泛關注,這些概念主要包括行為、意圖、因果關係、自願性、寬恕事由、正當化事由、可譴責性和該當性。法學理論傢可能藉鑒針對這些概念的哲學分析,來尋找刑事責任的條件。特彆是道德哲學傢對行為的認定,會被法學理論傢援引,從而幫助理解刑法中的行為要件。“在相關的語言社區中的用語,是對這些概念有效性分析的最終標準。”即使“法官或立法者可能……規定或者采用……不符閤哲學標準的含義。”參見Nicola Lacey,Contingency,Coherence,and Conceptualism,in R A Duff(ed), Philosophy and Criminal Law(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14.當然,刑法會使用特殊的行為概念,這個概念不同於哲學傢所解釋的行為。但是,為什麼要說刑事責任所要求的“行為”的概念,不同於道德哲學傢提齣的行為概念,而不是承認刑法根本就不需要行為要件?簡言之,為什麼認為刑事責任所要求的“責任”概念,不同於道德哲學傢提齣的責任概念,而不是承認刑法根本就不要求責任?
盡管刑法和道德哲學相融閤看起來非常閤理且有吸引力,但大多數學者抵製將刑法和道德哲學相融閤。他們通過區分道德責任和刑事責任,從而認為哲學分析與我們對法律概念的理解並沒有特彆的聯係。對這種立場進行反對的既有哲學傢,也有法學傢。對使用哲學方法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所做齣的保留分析,請參見Richard Posners essay “What Are Philosophers Good For?”in his Overcoming Law(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444-467.為什麼我們要勉強地使用哲學分析來幫助理解法學術語?盡管會得齣很多可能的答案當然,經常援引的對此觀點進行質疑的觀點強調,法律有一係列特定的目的或者目標,這些特定的目的或者目標限製瞭哲學分析方法的適用。例如,下文中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評論,就錶達瞭其認為刑罰語境下,不應使用哲學中的與行為相關的概念:
“我們最好還是針對刑法做齣一些區分和必要的結論,從而說明我們能夠為刑法構建理論。這至少可以說明刑法中的行為理論和行為概念與哲學意義上的行為有所不同。從反思的角度分析,很明顯在一些領域中,這種觀點是正確的。畢竟,刑法有特殊的目的和目標,並且那些用來描述人行為的要件,不可能與那些獨立存在的特殊目的相一緻。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不需要考慮刑法中的特殊要件,我們使用的各種不同理論和概念就事先已經為刑法準備其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參見Bernard Williams,The Actus Reus of DrCaligari,14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994)1661、1661-1662.
威廉姆斯並沒有特殊分析被聲稱是激勵行為哲學傢構架他們關於行為理論的特殊功能和目標,他也沒有詳細認定刑法具有的限製適用哲學分析的“特殊目標、目的和要件”。但是,威廉姆斯認為刑法具有特殊目的和目標的觀點,是為大傢所熟悉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行為要件在否定將刑法和道德哲學相融閤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更具體分析,在區分道德和刑事責任要件之時,往往會援引行為要件作為理由。刑事責任通常認為必須具備行為要件,而道德責任並不需要行為要件。羅琳·鉑金斯(Rollin Perkins)闡述瞭這一觀點,其內容如下:“在倫理學領域,正如教會的教導,罪行僅僅取決於主觀心理狀態……但是,如果有過錯的主觀狀態並沒有産生具有社會危害性的結果,那麼就並不存在刑事責任。”Rollin Perkins and Roland Boyce,Criminal Law(Mineola,NY:Foundation Press,3d ed,1982)830.同樣的,W赫切爾(W Hitchler)認為:“一項物理行為是責任必備構成要件之一,這就使法律責任與……倫理原則和道德哲學有瞭區彆。對於倫理原則和道德哲學,隻要具備主觀因素就足以構成罪責。道德規範的錶述形式是‘應該是這樣’,而不是‘必須這樣做’的形式。”W Hitchler,The Physical Element of Crime,39 Dickenson Law Review(1934)96,96.如果該主張是正確的,會被認為是對法律和道德哲學相融閤的破壞。
但是,這種主張是否正確?實際上,這種主張涵蓋瞭兩種不同的爭點:第一個爭點是關於刑事責任,並且認為刑事責任的施加必須具備行為要件;第二個爭點是關於道德責任,並且認為道德責任的成立不需要行為要件。假設我們認為第一個爭點是正確的,即刑事責任的施加必須具備行為要件,那麼第二個爭點是否就是正確的?道德責任的施加是否就不需要行為要件?如果道德責任的施加也必須具備行為要件,那麼這些理論傢認為他們已經找到瞭區分刑事責任和道德責任的標準的觀點,就是錯誤的。
道德責任的施加無需行為要件的主張,通常被鼓吹為一個重要的智慧,因為它揭露瞭道德和刑法理論的不同結構中最具有深層次意義的重要區彆。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思考,就會發現該主張最終並非那麼有趣,也並沒有對刑法和道德哲學的融閤産生危害。和刑法評價的範疇相比,沒有人會懷疑道德理論有更大的評價範疇。這些例子就是道德哲學傢會緻力於評價行為、意圖、動機、努力、情感、人類、性格、性情和思想,甚至所有可能的世界。一位法學理論傢最近提齣瞭這種主張,即:“道德不法的性質,完全取決於行為”,而不是“取決於其他可能的對象”,例如不是取決於動機和意圖。然而,如果該學者認為,道德哲學傢認為是任何事物的狀態而不是行為具有不法性的觀點是不閤邏輯、荒謬或者是具有誤導性的,那麼該學者的觀點就是錯誤的。參見Heidi M Hurd,What in the World Is wrong?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Legal Issues(1994)157、160.很明顯,一般的法律和具體的刑法,都不能評價這些多式多樣的對象中的每一個。換言之,道德哲學和刑法相比,具有更為廣闊的範圍。為什麼道德哲學的範圍和刑法的範圍是如此不同,以至於引起瞭很多睏惑,而且這使那些贊成將刑法和道德哲學融閤在一起的學者必須進行解釋。例如,一個人可為他或者她的性格負道德上的責任,但為什麼對性格負刑事責任會被認為不具有正當性而被否決?此外,道德哲學具有更廣泛的範疇幾乎不會被質疑。當然,行為要件把道德哲學和刑法進行區分,也主要是為瞭對這種事實進行提醒。
然而,行為是道德進行衡量的對象之一——即使很多類型的不作為,也是道德衡量的對象。道德哲學中,用以衡量行為的部分被稱為行為道德。行為道德學派本身(至少)有兩派。第一派對行為進行評價的目的是為瞭事先指導行為。這一派強調的問題是:人們應該實施哪些行為?第二派認為對行為進行評價,是為瞭事後判斷行為。這一派強調的問題是:人們實施的行為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行為道德這兩個分支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復雜且富有爭議的。行為道德和評價其他對象的道德哲學之間的關係是具有爭議的。特彆是,道德評價的對象可能是主要的和基礎的,或者是能被還原為另一種對象的事物,或者是和其他被評價的對象共同處於非常復雜的聯係中的事物。這些問題中的一部分問題,已被斯蒂文·哈德遜(Stephen Hudson)討論過,參見Stephen Hudson,Human Character and Morality:Reflec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Ideas(Boston:Routledge&Kegan; Paul,1986).但是,這些重要的推測並不會挑戰這一核心:有一部分道德在評價行為。赫切爾錯誤地認為“道德規則”必須以“應是這樣”的形式進行錶達,而不是以“這樣做”的形式進行錶達。但是,赫切爾是否真的認為,“某人不應該這樣做”的形式錶達齣來的規則,就不可能是道德規則?赫切爾的觀點具有顛覆性,而且會産生不為人們所接受的結果——根據刑法做齣的判斷完全和道德評價無關,因為道德和法律是相互排斥的。
沒有行為,就沒有評估對象。但在行為道德中,這種必須具備行為要件的主張似乎是多餘的。從定義分析,即使欠缺行為要件,道德評價仍然涉及道德哲學中的不同於行為道德的部分。因此,刑事責任必須具備行為要件的主張,至少並不能將刑法與道德哲學中的某些部分區分開。因此,這種觀點可能會對刑法與道德哲學中的不會評價行為的部分進行區分,但是,這種觀點僅僅注意到不評價行為的道德哲學之部分不需要行為要件,算不上是重要的智慧。即使刑法確實需要行為要件,這一事實也不能把刑事責任所需要的條件從行為道德中區分齣來。
盡管筆者也贊同將刑法和道德哲學相融閤的一般理論,但在下文中,筆者並不會采用關於行為的形而上學的概念以迴答筆者所提齣的刑事責任是否需要行為要件之問題。筆者的原因非常簡單,任何依賴於具體的關於行為概念的答案,都一定會引起爭議正如一個評論傢所分析的:“在公共領域,應當盡力避免使用形而上學的行為概念,這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大傢所希望的。高度的形而上學,包括行為的形而上學,在一個民主體製中,公民是不會認可的。”參見Samuel Freeman,Criminal Liability and the Duty to Aid the Distressed,14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94)1455,1455.,並且會將注意力從這些實質問題上轉嚮適用該概念的原因之上。迴應米歇爾·摩爾(Michael Moore)的研究確定瞭這種懷疑。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摩爾的批評者都攻擊瞭摩爾的哲學行為論——特彆是他的形而上學的現實主義行為觀,但對根據摩爾的行為概念,施加刑事責任是否必須具備行為要件卻沒有多少論述。參見Michael Moore,The Symposium on Act and Crime,14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94)1443-1840.筆者希望最具哲理性的行為論,能夠對被證明的問題有幫助,而且能闡明此法律分析之目的。然而,為瞭迴答即將麵臨的問題,現在我們並不需要對此論點進行闡釋。筆者相信,如果對行為的性質缺乏共識,那麼就會引起刑事責任是否需要行為要件的分歧。眾所周知,哲學上行為概念定義具有不確定性,根據某個令人信奉的行為概念,刑事責任需要行為要件,然而根據另一個被人認可的行為概念,刑事責任不需要行為要件。因此,要判斷刑事責任是否需要行為要件,學者就必須在行為的各種概念中做齣選擇。筆者並不否認存在這種情況。筆者認為通過檢驗那些理性人都不會有爭議的關於是否實施瞭某項行為的案件,能增進我們對此問題的認識。任何令人信服的哲學上的行為論,都必須符閤刑法的最低限製原則。根據此原理,刑事責任必須具備行為要件的論題無論是真是假,都能獲得充分的理由。
筆者認為,行為本質的形式主義的睏惑,僅僅是行為要件持續具有爭議的部分原因。在這一部分的論述中,筆者將特彆關注那些相對而言還不為人知的爭議——刑事責任是否需要行為要件爭議到底意味著什麼的不確定性所導緻的爭議。筆者認為學者對於行為本質的理解還有所欠缺,正是這種模糊性概念選擇纔導緻對刑事責任是否需要行為要件的判斷齣現分歧。
……
前言/序言
在一定的限製條件下,由已發錶的論文集成專著是非常有價值的,至少本專著就是如此。筆者的這本專著就是由筆者以前發錶的諸多均勻分布在哲學期刊、法律評論和書籍中的章節組成。其中,很多文章已引起法學教授們的注意,還有很大部分的文章則已為哲學傢所熟知。筆者通過非正式調查得齣結論:在筆者所著述的論文中,諸多學術研究的學者們幾乎隻是對筆者的立場或觀點略知一二而已。筆者希望該專著的讀者能更加熟悉筆者的一些文章的內容,這亦將有助於他們全麵瞭解筆者的觀點和立場。事實上,這些分布在不同領域的文章反映瞭筆者對刑法理論的性質與功能的一些獨特觀點,這亦是筆者在該導言中強調的主題。筆者將努力簡略闡述筆者的立場以及在相關作品中說明的學術觀點。但是,要簡要闡述筆者的學術觀點,事實上是非常睏難的,因為筆者提齣的大多數觀點需要直接的條件:一方麵筆者認同X,但另一方麵,筆者也亦認為不應該忘記Y。但是,在此,筆者提齣一個相對比較謙和的開端:刑法哲學(或刑法理論)的目標,正如筆者所詮釋的,是提齣建議從而去改善刑事實體法的內容。當然,這個粗糙的界定亦會引起諸多問題。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擬定一個標準,以便於判斷某種理論是否能促進刑法的發展。筆者主要用道德哲學(另外,筆者也會從社會和政治哲學的視角進行分析)來界定該標準。然而,道德哲學傢對規範性問題的分析,其觀點亦是百花齊放、百傢爭鳴。據此,我們應援引何種傳統道德觀評價刑法?在大多數情況下,筆者試圖迴避這個問題。然則,不管是好是壞,筆者在導言中提齣的諸多觀點,幾乎不涉及任何道德理論。
因此,筆者不打算構建宏觀理論,亦即,筆者並非尋求關於刑法目的的統一理論。雖然筆者時常從抽象轉移至具體,但筆者更傾嚮於拒絕一般性的某種主義,即最為大傢熟知的具體性的某種主義。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在刑法理論中避免涉及意識形態。在筆者的著述中,筆者沒有使用“自由主義”或者“保守主義”這些術語。筆者認為繼續使用這些模糊的標簽性術語對政治和法律爭論是沒有益處的,而筆者期望提齣的觀點能對整個政治領域的問題都有裨益。筆者期望各種意識形態下的人都能從筆者的著述中獲得啓發。
筆者不願意討論各種法律主義或者對某個基本問題錶明立場,這會令那些甚至對綜閤性道德理論都沒有印象的哲學傢們感到失望,而正是綜閤性道德理論使這些哲學傢的理論具有正當性。然而,筆者擔心提齣這種統一的理論框架不會增加多大益處。任何反對提齣理論根基的學者,都會對理論根基上的理論建設錶示懷疑。筆者希望筆者提齣的假設和從中得齣的推論,能與那些不同意更深層次地探討理論根基問題的哲學傢們的主張一緻。筆者在該書使用的方法論,與最著名的法律哲學傢喬爾·範伯格(JoelFeinberg)的方法論最為相似。筆者有意識地引用瞭範伯格所偏愛的“中級審查標準”。在論述風格和實質內容兩方麵,範伯格對筆者影響很大,那些熟悉其著述的學者應該非常清楚其對筆者的影響。
盡管筆者避免討論道德理論中的大多數具有爭議的問題,但是筆者認為構成刑法基礎的道德和一般道德哲學之間存在非常緊密的聯係。盡管筆者認為這種聯係是緊密的,但是與把筆者的刑法理論歸納為幾個簡單的原則相比,把道德理論歸結為幾個原則更不具有可能性。道德的內容體係更具有爭議且更加復雜,因此,筆者對不能成功地構建統一的道德理論體係並無歉意。任何道德基本問題,都將引起道德哲學傢的爭鳴,我們也期望這些爭鳴齣現在刑事實體法領域中。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刑事理論法學傢,都認為構成刑法的道德基礎是復雜的。例如,最近一些著名的學者認為所有的刑事不法行為都可以簡單地解釋為:不具有充分閤理性,選擇瞭可能給他人或他人的利益帶來危害風險的行為。參見LarryAlexander、KimberlyKesslerFerzan、StephenPMorse,CrimeandCulpability:ATheoryofCriminalLaw(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筆者認為該簡單的原則過於簡化瞭(並且扭麯瞭)刑法。該導言的目的不是批評其他學者的不同觀點。因此,筆者隻能簡單地闡述,在筆者所支持的簡化原則中,沒有任何原則像上述簡化原則那樣。
雖然刑法理論和道德理論是緊密聯係的,但是二者可能在一些有趣的方麵産生分歧。當代道德哲學傢之間的關於行為人之目的是否與評價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具有容許性的爭鳴就是這種情況。無論道德哲學傢的觀點如何,筆者在第三章“刑法語境下‘目的不影響允許性’假定論的代價”中分析認為,證明目的與行為人是否實施犯罪行為無關緊要,將産生很多誤導,並且會帶來潛在的災難。筆者認為刑事實體法應該堅持目的對評價行為人的行為是否被允許具有重要意義。在第十四章“刑事責任中‘輕微違反’辯護事由”中,筆者探究瞭其他可能在刑法和道德之間産生的分歧。在道德中,非常微小的錯誤行為都是可以被認知的,而且會使人受到較小程度的譴責。但是在刑法中,情況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非常輕微的犯罪行為根本不會使被告受到刑事懲罰。如果筆者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正當化事由這個概念在法律與道德中的含義是不同的。為瞭達到施加刑事責任之目的,正當化事由不需要完全排除行為之不法性。正當化事由隻需要排除足夠的不法性,從而使被告不承受報應之譴責。這就是筆者大緻的觀點。
筆者對道德理論中的一個基本問題持有堅定的立場:構成刑法基礎的道德,是且應該完全是道德性的。筆者斷然否定這樣的觀點:刑事司法的各項製度,包括擬定的法律、政策和原則等,都當且僅當能使利益最大化時纔能被采納。一些提案雖然能實現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不應該以法律的形式實施,其他的一些提案雖然不能實現利益的最大化,但卻應以法律的形式執行。在筆者的這本書中,讀者幾乎找不到結果主義的推理綫索。更具體分析,雖然有學者通過評價規則或原理的威懾效果來評價規則和原理,但筆者一直拒絕該眾所周知的評價傾嚮。首先,具體的法律原則增強或降低刑法作為威懾工具之效果具有一定的條件,但在現實世界中,我們能滿足這樣條件的情況很少。筆者論證的上述問題需要的條件,在我們大多數公民中是缺乏的,並且如果公民不能認識到這些法律,並據此調整他們的行為,那麼提案就不會影響公民的守法程度。此外更重要的是,威懾和刑法理論中最基本的公正與該當性概念並無關係。當刑事司法違反道德約束並偏離公正與該當性時,刑事司法製度就是被濫用瞭。盡管許多學者習慣於認為並期望刑法能在保護被告人權利和維護社會利益之間維持微妙的平衡,但在筆者的這本書中,似乎沒有特彆關注對社會的保護。然而事實上,筆者同意刑法應具有阻止犯罪的功能。在判斷何種行為應該受到刑事處罰時,我們是在判斷我們應阻止何種行為。當然,這種判斷所關注的焦點仍然是公正和該當性。
如果沒有爭議,則如何實現筆者討論的理論的發展?如果不經常對具有爭議的理論問題進行思想上的交鋒,那麼對研究的規範性問題是沒人能得齣結論的。筆者在書中提齣的一些假設的案例,主要是為瞭徵求讀者的意見。在反思平衡的過程中,讀者的迴應可以用於確認或反對抽象的原則或理論。這種方法論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筆者在本書中偶爾會使用。但是,筆者會避免廣泛列舉這種充滿想象的假設案例,因為在法學領域並不推崇使用太多的假設案例進行研究。讀者對這些特殊案例的迴應,不具有體係性效應,而且還存在其他的心理歪麯的情況。因此,筆者對這些案例的可信度錶示懷疑。在刑法發展的曆史上,産生過數量巨大的案件。如果道德哲學傢對現實案例熟悉,那麼就沒有必要設計假設的案例。
當然,筆者認為道德性和以該當性為基礎的分析視角,在刑法學界還沒有得到普遍認同。據筆者分析,目前刑法學傢研究的主流趨勢是實證主義。這種研究方法主要是依賴於社會科學,而不是依賴於一般哲學或具體的道德哲學。對此種現象筆者是矛盾的。一方麵,刑法理論的研究應該是廣泛的,應該接受不同的研究方法,當然也不應排除實證主義方法。因此,對於最近許多刑法哲學傢願意參與到實證研究中,筆者錶示贊同。但另一方麵,道德爭議是不能通過民意調查來解決的,因為民意調查反映的是迴應者思考的是什麼,並且我們應該不讓實證調查把我們從辛辛苦苦維護的規範性結論中分離齣來。同時,筆者亦相信公眾意見體現的智慧比刑法學者想象得要高。最近幾年,甚至有學者已經調查齣外行人是如何看待刑法學說的。基於很多原因,這些學者甚至認為公眾的正義觀,應該反映在刑法實踐中。在這些原因中,至少包括能增強對刑事司法製度之公正的信心,從而加強自願守法。
筆者基於不同的原因從社會學中尋找數據。例如,令筆者感到震驚的是:刑事實體法中什麼程度的寬恕事由纔能成為部分或完整的寬恕事由,與被指控犯罪的行為人在請求中提齣的部分或完整的寬恕事由的程度差異很大。社會規範在確定寬恕事由之決定因素中的作用很大。研究侵權行為的學者時常指齣,理性人不屬於統計學上的普通人。這些學者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在刑事法領域,該問題就不那麼容易迴答瞭。如果施加刑事責任錶達的是一種譴責,當然筆者也持這種觀點,那麼行為人遵守廣泛社會規範的事實就有力地證明行為人不應受到懲罰。“但每個人都這樣做”之辯護事由,通常都缺乏事實根據。但是,如果被告的請求從經驗分析完全是正確的,那麼就很難理解被告為什麼應該承受刑法施加的汙名效應。
此外,法律製度之外追求的社會實踐可能比刑法哲學傢所思考的社會實踐更具有意義。盡管刑法哲學傢對於刑罰的本質分歧很大(令大傢更熟悉的是這些刑法哲學傢對刑罰正當性之分歧),許多學者堅持認為這個意義上的刑事製裁,僅僅隻是國傢的行為,其旨在使實施瞭犯罪的行為人承受剝奪權利和汙名效應之痛苦。在該書的第十七章“‘已受足夠懲罰’辯護事由”部分的論述中,筆者認為企圖因犯罪人之犯罪而懲罰犯罪人之個人的反應,可以減輕國傢施加的正當刑事製裁。如果筆者是正確的,刑事政策就應該更敏感地捕捉公眾對被告的態度。特彆是,當公眾對那些名人進行譴責,從而使其受到更多的汙名痛苦時,他們就可能受到較輕的刑罰。
盡管社會學傢在法律哲學中扮演瞭一定的角色,但是筆者擔心最近流行的實證主義趨勢會使刑法學者不能成功培養接受以該當性為基礎的方法論的新一代學者。在美國,許多很好的法學院都沒有聘請贊同筆者在該書提倡的規範框架的全職教員。然而,該規範框架是非常有價值的,筆者也非常相信確實如此。但是,筆者擔心能應用這個方法的年輕學者是相對缺乏的。許多教授刑法的學者不接受義務論式刑法理論,更願意從公訴人或是辯護律師的職業角度教學。筆者和筆者的同事們會因沒有成功培養齣以該當性為基本觀點的新一代年輕學者而感到遺憾。筆者隻希望本書的理論和最近由約翰·加德納(JohnGardner)編寫的優秀論文集能起到更大的刺激興趣的作用。參見JohnGardner,OffencesandDefence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8)。
引起更多的興趣是必要的。正如筆者所解釋的那樣,學術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忽視刑法理論,但筆者提齣的義務道德思想和刑法理論的關係可以解釋這種忽視。許多不同的學派的學者遭受瞭筆者所稱的道德論之恐懼:如果某問題的解決有賴於道德爭論的解決,那麼該問題自然不能得到解決。因此,研究刑法的普遍方法大部分都是藉助於社會科學,並且期望藉此弄清楚道德正義,這不足為奇。對道德學說的厭惡,使一些學者否認刑法應該被道德約束。許多認為道德是刑法之基礎的學者,認為道德結果主義,關於正義與該當性的爭論,會使問題變得更難以解決,而且不會取得進步。從抽象角度很難解釋道德爭論恐懼癥。參與道德爭論是厭惡道德爭論學者的最好解藥,而筆者在該書中亦試圖這樣做。
正如筆者所解釋的,刑法理論被忽視具有諸多不同的原因。也許,學者也確信其所作的理論工作不會有積極的成效。筆者熟悉的許多刑法學者,都感嘆他們的理論工作對現實世界沒有影響力。在我們這些理論學者中,極少有人會認為法學傢的著述會對現實世界的政策有實質影響。眾所周知,政治傢和公眾都希望“嚴厲打擊犯罪”,並且普遍抵製使我們的刑罰製度更符閤正義和該當性要求。從2008年開始的經濟嚴重衰退,可能會改善這種可怕的情況。因為讓一個犯人待在監獄每天要花費80美元,這使那些有著最嚴厲名聲的司法管轄區,也被迫從嚴厲壓製犯罪的實踐中撤退。筆者推測我們刑事懲罰機構的改革,不是因為法學傢的請求而是因為最近緊張的刑事司法預算。當我們對道德置若罔聞時,經濟上的考慮就會占優勢。經濟考量具有重要意義的這一變化,實質上與刑法理論學者的主張相契閤。我們不應該放棄這個機會,嚮那些願意接受真正改革的政策製訂者們提齣建議。如果我們不能明確地知道我們能提齣什麼建議,那麼我們就不能抱怨現實世界對刑法學者的忽視。我們必須準備如何嚮當局提齣更好的修改立法的建議。盡管筆者非常清醒地知道,對於如何鼓勵政策製訂者實施筆者的建議亦沒有很好的建議,但是很顯然,鼓勵政策製訂者接受刑法學者的建議,對於改善刑事實體法至關重要。
筆者之道德構成刑法之基礎的觀點,對於參與刑事司法日常工作的人而言,可能是不能接受的。現在的刑事司法被稱為McJustice模式,該模式使近95%的案件是通過與被告人進行匆忙的談判,從而讓其認罪的方式而結案的。NewYorkTimes,11September2008A1:1。負擔過重的公訴人和極度超負荷工作的公共辯護人,都參與到辯訴交易製度這個生産綫中。刑事實體法中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幫助司法實踐者在這種被歪麯的司法製度中有效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而,正如許多學者所指齣的,如果極少有人自我認罪,案件也不是通過辯訴交易進行,那麼我們的刑事司法體係就會崩潰。盡管筆者在該書中提齣的解決方案不多,但筆者呼籲犯罪學傢和社會學傢能夠關注這個糟糕的現狀,並且提齣一些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專門從事刑事理論研究的法學傢主要分為兩大派彆。一派主要是學術型法學傢,這些法學傢非常精通道德責任和政治責任,並且努力把其見解應用到刑事責任理論中。這些法學傢可能寫瞭很多刑法專著,但幾乎沒有提及一個案例或法條。另一派是法學教授,這些法學教授知道大量的規範和案例,但是卻不熟悉法哲學。這類學者對哲學的精通程度,僅限於如何使其觀點在威懾和報應的傳統中被接受而適用的哲學程度。當然,一些法學哲學傢處於這兩個極端中。筆者將自己界定在這兩個學派之間。筆者堅定地以現行刑法為基礎,從當代道德、政治和社會哲學中吸收大量經驗。與之同時,筆者偶爾也會藉鑒犯罪學傢的實證研究。筆者希望通過努力,領悟這些學科中最好的內容。筆者一直希望筆者的著述,對於法學傢而言不要太哲學化,對哲學傢而言不要太法律化。讀者既不必要是哲學博士,亦不必要是法學博士,就可以理解和評價筆者本書所寫的內容。
盡管筆者的研究方法是比較均衡地藉助瞭哲學和法學的方法,但筆者並不認為任何派彆都可以藉助此路徑在刑法理論研究中處於壟斷地位。雖然似乎顯得很奇怪,但任何一個法律哲學傢即使較少關注現行法律,也能做齣很大成就。該情形讓我們迴憶起60年代哲學科學的狀態。在那個時代,盡管許多學者對科學知之甚少,但許多著名的學者都試圖對科學哲學化。然而,對法理學領域廣受歡迎的原則和概念的關注,導緻對現行法律規則和學說關注的缺失。例如,假設認為法哲學應該探究法律的必然真理,盡管後來學者把此概念視為法理學,但法律之真理的概念卻在約瑟夫·拉茲(JosephRaz)的著作中能找到。參見JosephRaz,TheAuthorityofLaw:EssaysonLawandMorality(Oxford:ClarendonPress,1979)104-105。那麼根據理念,現行法律的規定是如此嚴格,導緻其幾乎不可能贏得法哲學傢的關注。即使該理念在法學領域貌似有理——筆者對此深錶懷疑——但筆者在該書中也不會采取這種研究路徑。筆者不會尋找所有刑法體係的共同特徵,相反,筆者會均衡地從現行法律和哲學中尋求方法。
用户评价
對於《刑法哲學》這本書,我隻能用“震撼”來形容我的感受。它不是簡單地介紹刑法條文,而是帶領讀者進行一場深刻的哲學之旅。作者以一種非常宏大的視角,審視瞭刑法的起源、演變及其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我尤其被關於“刑罰的功利性”與“刑罰的懲罰性”的辯論所吸引。究竟刑罰的主要目的是為瞭改造社會、預防犯罪,還是僅僅為瞭對罪犯施加懲罰以體現正義?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理念,在實際的法律實踐中是如何交織和衝突的?書中的論證過程非常精彩,它引用瞭大量的思想傢觀點,並將其與具體的法律條文相結閤,讓我看到瞭刑法理論的深邃之處。讀這本書,感覺像是在與一位飽學之士進行思想的對話,每一頁都充滿瞭智慧的火花,讓我對法律的理解上升到瞭一個新的高度,也對社會公正的實現有瞭更深刻的反思。
评分我必須說,《刑法哲學》這本書帶給我的衝擊遠超預期。我原本以為它會是一本充斥著法條和案例的“工具書”,沒想到卻是一場思維的盛宴。作者的邏輯構建異常清晰,他從最基礎的“什麼是刑法”開始,一步步引申到刑法的目的、功能,以及它與社會倫理、道德之間的微妙關係。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關於“預防”理論的論述,它不僅區分瞭“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還深入探討瞭它們各自的局限性和潛在的風險。比如,為瞭達到“威懾”的目的,刑法的嚴厲程度是否會走嚮極端?而“特殊預防”在改造罪犯的過程中,又是否會觸及個體的自由和尊嚴?這些問題都讓我陷入瞭深深的思考,也讓我對法律的製定和執行有瞭更深刻的認識。這本書不是那種讀完就忘的書,它更像是一把鑰匙,打開瞭我對刑法背後復雜社會機製的理解之門,讓我看到瞭法律是如何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同時,又必須時刻警惕自身可能産生的負麵效應。
评分《刑法哲學》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可以用“耳目一新”來形容。它並非是一本堆砌理論的著作,而是充滿瞭作者獨到的見解和深刻的洞察。我非常欣賞作者對“犯罪原因”的探討,他不僅僅停留在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層麵,更是將哲學思考融入其中,去探究那些導緻個體走嚮犯罪深層的根源。書中對於“犯罪構成要件”的分析,也異常精闢,它不僅講解瞭客觀和主觀方麵的要件,更重要的是揭示瞭每一個要件背後所蘊含的價值判斷和法律精神。這讓我意識到,刑法並非是冷冰冰的規則,而是承載著社會對行為的期望和對個體的要求。這本書的語言風格也十分吸引人,它既有學術的嚴謹,又不失文學的色彩,讀起來流暢且引人入勝,仿佛在跟隨作者一起解剖一個復雜的犯罪案件,並從中窺探到法律背後那深邃的智慧與人文關懷。
评分這本《刑法哲學》讀起來真是讓人眼前一亮,完全顛覆瞭我之前對刑法枯燥、冰冷印象。作者的筆觸非常細膩,不像一般的學術著作那樣生澀難懂,而是像在娓娓道來一個關於正義、懲罰和罪責的故事。我尤其喜歡其中關於“應報”理論的探討,它不僅僅是簡單地羅列各種觀點,而是通過大量生動的案例和哲學思辨,層層剝開應報的復雜性,讓我們思考,當法律的懲罰不僅僅是威懾,更是對被剝奪之物的某種“補償”時,這種補償的真正意義何在?它是否真的能帶來一種秩序的恢復,或者僅僅是一種情緒的宣泄?讀到這裏,我仿佛置身於古希臘的廣場,與智者們辯論著“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閤理性,又或是身處現代的法庭,審視著量刑的尺度是否真正體現瞭“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書中的很多觀點都非常有啓發性,它迫使我去重新審視自己對犯罪和懲罰的理解,不再是簡單的好人壞人二元對立,而是看到瞭法律背後更深層次的倫理考量和社會功能。
评分坦白講,《刑法哲學》這本書的閱讀體驗非常獨特,它不像我之前讀過的任何一本法學著作。作者的語言風格非常有趣,有時犀利,有時幽默,但始終保持著一種嚴謹的學術態度。我特彆喜歡他對“免責事由”的分析,比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他不僅僅是在解釋這些概念,而是將它們置於更廣闊的哲學背景下,探討個體在麵對威脅時,其行為的“正當性”是如何被法律所承認的。這讓我聯想到很多現實生活中的案例,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某人的行為是齣於無奈,但法律是否也同樣理解和包容?書中對於“故意”和“過失”的區分,也進行瞭極其細緻的論證,它不僅僅是關於行為的主觀意圖,更是涉及到瞭對風險的預見能力以及行為人所應承擔的注意義務。這種深入的剖析,讓我對刑法的精妙之處有瞭全新的認識,也看到瞭法律背後對人性復雜性的深刻洞察。
评分物流给力,价格便宜。
评分印刷清晰,纸质比较好,内容详实!
评分书的质量和包装都非常的棒,也非常感谢快递小哥的快速送达!
评分上一次的超给力活动时发现本书的时候,已经下了别的书,想改单已经来不及了。这次算下来虽是半价左右,可是比上次至少多付一倍的价格。不能比啊。看在书的内容和定价本身不高,也还可接受。
评分东西不错,京东品质,值得信赖。
评分很好
评分非常好好好!!!!!!
评分好书!
评分这本刑法哲学写得很好,翻译也不错,读起来很带劲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