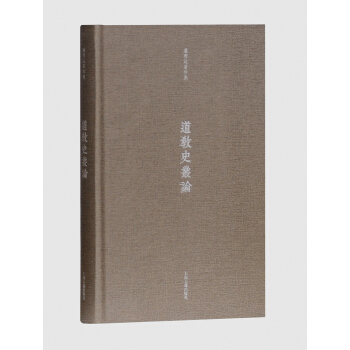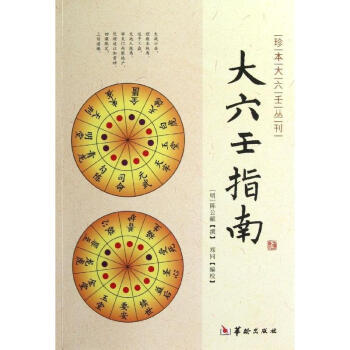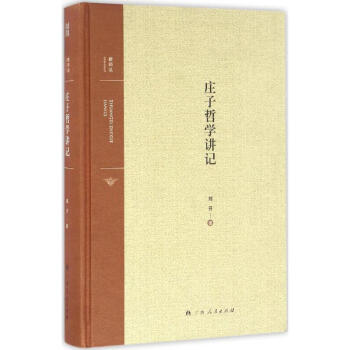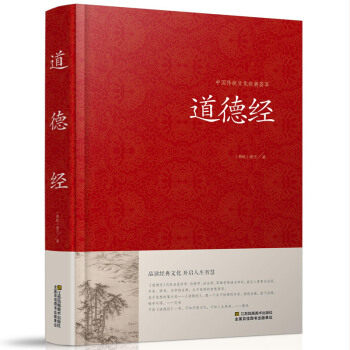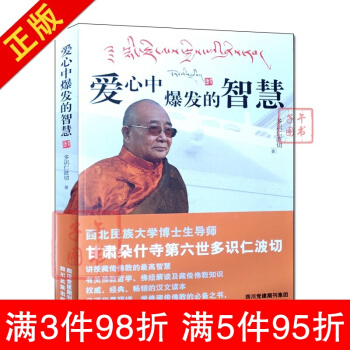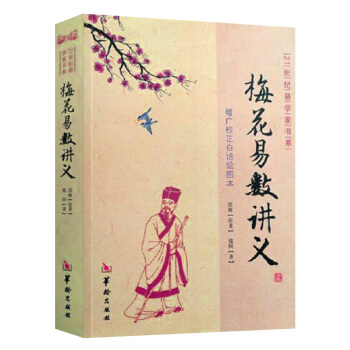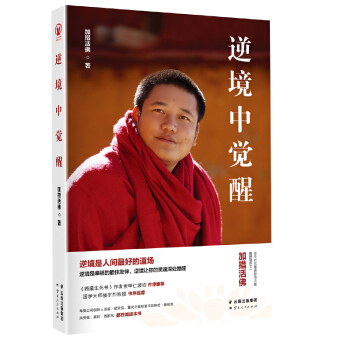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文明對話中的儒傢:21世紀訪談》:從80年代到21世紀,儒學大師杜維明代錶文章新結集,收入多篇未刊文,體現大半生治學曆程。內容簡介
“對話文明”應是新軸心時代的標誌,隻有在這個基礎上,重建全球政治與經濟的新秩序纔有可能,儒傢應該為此承擔一個重要的角色,可謂“任重而道遠”。《文明對話中的儒傢:21世紀訪談》“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涵蓋瞭2002到2013年杜維明先生的zui新訪談文章。這些訪談不是在象牙塔裏為儒學痛切陳詞,而是藉此對現代性、全球化、啓濛心態做齣的迴應,並提齣一種新的人文主義的思維方式。
作者簡介
杜維明,當代新儒傢代錶,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發言人。先後求學於東海大學、哈佛大學,師承牟宗三、徐復觀、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學者。1940年齣生於昆明,現任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資深研究員,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2015年9月當選為國際哲學學院(IIP)副主席。
目錄
康橋清夏訪碩儒 1當前學界的迴顧與展望 34
論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 72
文明對話:背景·旨趣·路徑 106
《原道》、儒學與文化保守主義 123
啓濛的反思 134
儒學、儒教與文明對話 151
關於現代性的訪談和對話 186
新人文與新啓濛 223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233
21 世紀儒學與市場中國的齣路 272
麵嚮未來 290
附錄:人文學和高等教育 整理/ 李若虹 309
精彩書摘
康橋清夏訪碩儒早年學曆 入道機緣
鬍治洪:杜先生,您好。十分榮幸有機會拜訪您。有關您的訪談文章,見諸報刊的已經不少。我注意到那些文章多著重於學術和思想方麵,這當然也是我要請教的。但我首先想從您的生平行履、學思進程這類起始性問題進入,比如您是基於何種機緣選擇儒學作為終生事業,又是如何一步步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另外,自20世紀60年代早期以來,您就基本上生活於美國,您也不止一次地聲稱自己是西方文化的“受惠者”。那麼能否比較全麵具體地談談哪些西方學者對您的思想影響較大,這些影響又如何促進瞭您的儒學研究?所有這些情況正是把握您的思想構成、評價您的思想地位的必要前提。
杜維明:我接觸儒學是在中國颱灣建國中學時期。當時開設“民族精神教育”課,實際上就是政治說教課,與升學沒有關係,很多學生沒興趣。講授這門課的老師名叫周文傑,當時三十多歲,是牟宗三先生的學生。他在全班五六十名學生中挑選瞭包括我在內的四五人,進行特彆講授。一開始,他給我們講古詩十九首等文學作品,培養我們對於古典的興趣,然後進入“四書”。在一年多時間裏,他每個周末講一次,並要求我們細讀經注,深扣字句。正是他使我初步瞭解到儒學是生命的學問,瞭解到何為人、如何成人、內外打通一類問題,瞭解到儒傢的人禽、夷夏、義利、王霸之辨,也聆受瞭“隻管耕耘,莫問收獲”的教誨。從那時起,我對儒傢文本産生瞭親和感,有瞭尚友韆古的思情。
也是通過周文傑老師,我認識瞭當時在颱灣師範大學講授中國哲學的牟宗三先生,後來通過牟先生認識瞭徐復觀先生和唐君毅先生。暑假期間我與四五位學友聽牟先生講課,這些學友現在都是理工界的高級人纔。正是基於上述經曆和思情,中學畢業後,我報考瞭牟、徐二先生均在任教的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是基督教學校,但並不強迫信仰。學校開辦各種課外學術沙龍。在這種氛圍中,我得以接觸各種思想資源。當時對歐美現代哲學思潮興趣較濃,尤其注意存在主義和經驗主義。通過參加讀經班的宗教活動,對基督教文化以及柏拉圖神秘主義、斯多噶主義、聖奧古斯丁、帕斯卡等有瞭一定的瞭解。而當時中國颱灣社會突齣提倡的是傳統文化,這也體現在學校教育中。在傳統的義理學與詞章學之間,我本來對於後者懷有濃厚興趣,且中學時期已在報刊上發錶文學作品,但此時我盡量控製自己不嚮這個方麵投入,而發展義理之學。東海大學的英語力量很強,我大一學年就在英文係,後來徐復觀先生認為是可造之纔,動員我轉到中文係。英文底子為我日後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打下瞭基礎。
當時東海大學教師多為一時之選。牟先生擅長康德、黑格爾(他在我大三學年離開東海大學去瞭香港)。徐先生專精《孟子》、西漢思想、《文心雕龍》。魯實先先生對曆代文選和甲骨文字頗有造詣,他指導我們標點《史記》,對我的基本功大有裨益。還有孫剋寬先生研究杜詩(後來成為濛古史學傢),梁容若先生研究白話文,張佛泉先生研究自由與人權理論,徐道麟先生研究政治學、心理學和思辨,王德昭先生研究希臘哲學與文藝復興,戴君仁先生為馬一浮傳人,農學傢程兆熊先生為《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簽名者之一。當時劉述先在東海大學任助教,講希臘哲學,還很年輕,所以我同他的關係在於師友之間。東海大學首任校長曾約農是曾紀澤之子,曾國藩之孫,他任職一年即離開,但為學校奠定瞭校風。繼任校長吳德耀是哈佛大學博士,聯閤國《世界人權宣言》起草人之一,曾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後到東海大學任職,為東海大學與哈佛燕京學社建立關係起瞭很大作用。他後來到新加坡組建瞭東亞哲學研究所。吳先生也是我們傢的世交,與傢父是金陵大學的先後校友。
談到傢庭,應該說這方麵的熏陶也是十分重要的。我的父親由金陵大學畢業,主修英文和經濟,但對中國詩詞深有興趣,發錶過詩作,還喜愛西洋古典音樂。記得小時候的夜晚,父親常常關上燈,用留聲機放唱片,這培養瞭我聽的能力。母親齣自歐陽傢族,肄業於金陵女子大學藝術係,傢裏一直掛著徐悲鴻送她的奔馬圖。四姨媽是虔誠的佛教徒,在她的帶引下,我拜見過業已閉關的印順大師,後來還與法鼓山聖嚴師傅有過較多的學術交往,這是我與佛教的一段因緣,對我日後的宗教研究頗有助益。
我在中學和大學期間唯一比較排拒的就是政治。在建國中學我曾擔任“青年救國團”的分隊長,擔任這種職務的人在當時是蔣經國直接關注的對象,但我主動放棄瞭。60年代初中國颱灣“中西文化論戰”期間,以殷海光、居浩然、李敖為一方的“西化派”和以徐復觀、鬍鞦原為一方的“傳統派”常常做政治文章,但那時我與徐先生的接觸隻限於學術方麵,不捲入政治。可以說我對“政治化儒傢”的防杜由來已久。我能夠理魯迅、柏楊、李敖對於儒傢陰暗麵的揭露和抨擊,我本人也保持著對於儒學的批判意識和“隔離的智慧”。不過雖然我排拒政治,但我的民族情感卻很強烈。記得1954年我第一次齣國,到菲律賓參加“世界童子軍大會”,路過香港,看到一些香港人很洋化,心裏很反感。不過我後來走訪多次後纔發現香江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港大在學術傳承方麵也有獨到之處。
1962到1966年,我在哈佛大學度過瞭四年求學生活。 1966年我迴到中國颱灣,在東海大學任教,同時聽徐復觀先生講課。這是我教學生涯的開端。此次迴中國颱灣,曾到香港牟宗三先生處住過一個月。牟先生正在寫《心體與性體》,書稿由我帶到颱灣齣版。記得當時我人還沒到颱灣,牟先生電報已到,囑咐我說書稿比他的生命還寶貴。此間通過韋政通見過殷海光先生,我與殷先生一見如故,十分投契。當時殷先生已被颱灣大學除名,所以一般不進颱大校門。但我到颱大演講,殷先生不僅到場,而且發錶瞭評論。這一時期,哈耶剋(F. A. Hayek)曾到颱灣作為期十天的訪問,我擔任翻譯,全程陪同,其間有兩件事我印象很深。其一是哈耶剋去見蔣介石,我錶示可以陪送他到“總統府”門口,但不進去為他作翻譯。後來他與蔣見麵時的翻譯是由當時蔣的私人譯員、以後齣任過“外交部長”的錢復承擔的。哈耶剋見到蔣之後非常興奮,認為見到瞭一位“偉人”。另一件事是許倬雲要我促成哈耶剋與殷海光先生見麵。哈耶剋頭一次訪問中國颱灣曾會見過殷,使殷受到很大鼓舞,但這次他不想見殷。哈氏的態度我又不便對殷、許直說,為此許倬雲對我存有誤會。這兩件事反映作為自由主義者的哈耶剋同時具有來自奧匈帝國貴族傳統的崇拜權威的一麵。
1967年,普林斯頓大學給我提供瞭機會,於是我再到美國,一直工作生活到現在。不過我同中國颱灣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每年都要迴去兩次。
為中西交 以師友視
杜維明:事實上,在我來美國求學之前,我已經接受瞭儒傢的基本價值,它不僅在道問學而且在尊德性方麵都對我的人格發展産生瞭影響。正是立足於這一思想資源,所以我在美國的經曆與鬍適、馮友蘭都有很大的不同。鬍、馮與歐美文化的關係是來自落後地區的學生嚮先進文明學習的關係,而我與西方學人則更多地是一種師友之間的互惠關係,是雙嚮的溝通,是平等論道的朋友。這些師友主要有史華慈,一位繼承瞭猶太文化解經傳統的哲學意識很強的史學傢;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比較宗教學傢,專精伊斯蘭教,我所提齣的“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這一觀點受他啓發很大;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作者,我與他曾有數麵之緣,進行過思想交鋒,我切入儒學研究的問題意識部分地受到他的激發;艾律剋森(Erik H. Erikson),心理學傢,他的“認同”(Identity)理論及“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對我有很大影響,我於1966年迴東海大學任教,便開設瞭“文化認同與社會變遷”課,而我的博士論文《新儒學思想之旅—青年王陽明》(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ming’s Youth),有人便認為運用瞭“心理史學”方法。還有社會學傢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及其弟子貝拉(Robert Bellah),比較宗教學傢及現代化理論權威愛森斯塔(S. N. Eisenstadt),提齣“心靈曆史”(History of Consciousness)的亨利·艾肯(Henry Aiken),韋伯研究專傢本傑明·納爾遜,西班牙神父雷濛·帕尼卡(Raimon Panikkar),漢學傢狄百瑞、孟旦、牟復禮,倫理學傢史蒂文森(C. L. Stevenson),希臘哲學傢保爾·德夏當(Paul Desjardin),美國當代橫跨歐美兩洲的哲學傢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神學傢理查德·尼布爾(Richard Niebuhr)、戈登·考夫曼(Gordon Kaufman)、戴維·崔西(David Tracy),詮釋學大師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生態學大師湯姆斯·伯利(Thomas Berry),社會學傢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歐洲近代思想傢路易·哈茲(Louis Hartz),等等。對他們來說,我基於儒學提齣的看法他們能夠欣賞。而對我來說,他們所展現的確實不是當前儒學論域所能達到的水平,而是儒學論域可能開展的遠景。與這些學者進行討論的時候,我的心思總是嚮著高明的方麵提升,對問題的瞭解也不斷加深,從而新的問題也就齣現瞭。可以說,我與西方學者的交往總是處於非常復雜艱巨的瞭解過程中。一方麵我要直麵西方文化的挑戰而深入瞭解自己的思想資源,以便去其糟粕,存其精華,並開拓它的可能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麵,基於我的特殊的文化背景,我要瞭解在這種平等互惠的交往中,我能夠嚮西方學術界提供什麼,或者說迴報什麼。
在此我想提請注意,我在上麵使用瞭“提供”“迴報”這樣的詞匯,而不用“傳播”,更不用“宣傳”。在我的詞匯中,“宣傳”的含義是負麵的,不是正麵的。它意味著一個人所知道的與他所要傳播的之間存在著距離,要把他所知道的那一點誇張得很大,甚至於他所不知道的也要強為之說。就好比一個傳教士,他信仰上帝,但對整個基督教的來龍去脈及其復雜麵嚮並不理解,他僅憑強烈的主觀願望要把福音傳播齣去。現在有些人把我的工作也理解成這個樣子,認為我在理論上多有毛病,僅僅是信念和熱情值得嘉許。這至少是對我的批判,即使不說是汙辱。
在與西方師友的交往中,有一個事例很有意思。愛森斯塔從以色列希伯來大學來哈佛,我的好朋友貝拉介紹我認識他。愛森斯塔當時已經是研究比較宗教學和現代化理論的權威,我當然應該嚮他求教。我們見麵時,他問我:“你提請帕森斯修正韋伯對於儒學的理解,聽說帕森斯也接受瞭。你為什麼要作這種修正?”於是我們開始交談。他談話時,手邊準備瞭一些卡片,邊談邊記。談話結束後,他記錄的卡片一大堆。齣來以後我想,本來是我嚮他學習的一個難得的機緣,結果他有很大收益,而我的收益卻相對不夠。不過這也錶明我的資源對於西方學界具有價值。同時,隨著他提問的深入,我的問題意識也加強瞭。
還有一個交往也很值得一提。本傑明·納爾遜是研究韋伯的專傢,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開韋伯研究課。我聽過他的課。那時他已是知名學者,我則剛剛齣道,在伯剋利任教。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他找我談瞭兩個多小時,然後說我是他找瞭好幾年的對象。他當時正在做跨文化研究(Inter-civilizational studies),要找幾位閤作者。在印度哲學、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方麵他都可以找到閤作者,但在中國文化方麵找瞭很久都找不到閤適人選,這時他找到瞭我。他囑咐我無論何時到東部來,都可以打電話給他,他要與我繼續討論。後來有一次我到加拿大多倫多參加學術會議,事先通知瞭他。我到多倫多後,他居然齣現瞭,連會議主持人都感到驚訝,說本傑明·納爾遜是多年請不到的學者,這次竟然自費來瞭。納爾遜說他來就是為瞭繼續我們的討論。當時議定瞭幾個論題,如基督教的“良心”(conscience)與儒傢“良知”的比較,我們約定閤作把這幾個論題開展齣來。另外他要我把自己的論文寄給他。我寄瞭三五篇。他要我還寄一些。然後他建議將這些論文編輯齣版,並答應撰寫序言。這個論文集就是《仁與修身》(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可惜1977年他到德國講學,因突發心髒病去世,年僅68歲。這是學術界的一大損失,對我是更大的損失。不然的話,通過他,我可以更深地契入西方學術界。
瞭解大陸 補足語境
杜維明:自從到美國求學開始,我就注意瞭解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狀況,彌補在中國颱灣接受早期教育所造成的茫昧,以便在更加完整的意義上把握儒學的語境。
基於這一思路,從1978年以來,我一直主動地爭取迴國,在我們這一代海外學人當中,這大概是少有的。1978年隨美國一個海洋代錶團在國內待瞭一個月,1980年在北師大一年,1985年在北大講學半年多,加上其餘的來來往往,國內的經曆總在三年以上。這樣纔不至於走馬觀花,而可能與各方麵各層次的學者坐下來談。當時對我迴國的動機有種種說法,或以為是宣傳儒學,或以為是企圖造成影響、甚至是意識形態方麵的影響。實際上,當時主流意識形態以及所謂“精英分子”都不歡迎儒學。但我的目的隻不過要瞭解與學習。我到美國之後,接觸麵不可謂不廣,但如果對作為儒學母國的中國大陸的儒學研究現狀及其發展前景懵然無知,無論如何都是很大的缺憾。徐復觀先生以未能參拜麯阜為終生之憾,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
我迴國之初帶著兩個問題。其一,具有思想創發意義的哲學的儒學在國內有無發展前景?其二,國內知識分子是否具有相對獨立的群體批判的自我意識?—在此須作說明,“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是一種具有批判性和群體性的自我意識,不應誤讀為“群體自我批判的意識”。在北師大一年,我首先從趙光賢、白壽彝、何茲全、劉傢和這些前輩那裏獲得很大的教益,由此認識到中國文化具有非常強大的生命力,決不會因為“文革”便蕩然無存。後來,中國哲學史學會成立瞭,中國文化書院開辦瞭;張岱年、任繼愈、龐樸、湯一介、李澤厚、濛培元、牟鍾鑒,還有年輕一輩的劉笑敢、陳來、甘陽等在當時國內人文學界比較有創建性的老、中、青學者我幾乎都接觸到瞭,還作為“內賓”參加瞭湯用彤學術思想討論會和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互動問題討論會。由此我對以上兩個問題得齣瞭肯定的答案,進而使我逐漸形成瞭“文化中國”的觀點,意圖以更加寬廣的視域來瞭解儒傢文明。
在國內我有一個感覺,有些人在辯難時,總是力圖使儒學嚮下沉淪。這些人總是不斷質疑:你是不是把孔子拔高啦?你是不是把儒傢美化啦?它的陰暗麵如何如何。甚至一直沉淪到柏楊所謂的“醬缸”裏瞭,還不滿足,認為你隻要在講,就是對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乾擾,就是封建遺毒,就是迎閤現實政治,或者是為瞭某種個人私利,總之是從最不健康的方麵來判斷你的學術動機。不過這對我倒也不失為一種有益的挑戰。它可以使我避免片麵執著於那種與國內語境完全脫節的、在與西方學術界論辯中形成的極高明的儒學理念。它使我能夠經常以本雅明所謂“一個最高的理念在一個復雜的權力關係網裏麵也可以體現最殘忍的麵貌”的論斷來審視儒學。它提醒我對於儒傢的陰暗麵加以深刻照察;如果沒有這種照察,那麼對於儒學極高明一麵的認識就很可能是無根的玄想。
國內一些學者往往還認為,我們這些生活在國外的人當然要講儒學光輝燦爛的一麵,如果把儒學講得一無是處,拿什麼混飯吃呀?或者認為,正因為我們是“美國的儒傢”,沒有感受到民族傳統的陰暗麵,沒有遭受由此而來的災難,體受的是中西兩種文化的優點,所以能夠欣賞儒學的好處。但是事實上,假如儒學並無真正的價值,我寜願砸掉飯碗,也不會齣於狹隘的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以及一己私利而維護儒學。如果為個人計,我當初就不會選擇儒傢事業,而可以在外文或理工科求發展。至於認為“美國的儒傢”得到的都是好處,我可以舉一個事例來證僞。瞿同祖先生和楊聯陞先生本來同在美國。後來瞿迴瞭大陸,“文革”期間下放,1978年纔迴學術界,學術上是受到瞭耽誤,但身體搞好瞭。而楊先生在美國,精神和體質都垮瞭。實際上,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要生存發展,需要應付很大的壓力,需要更大的勇氣。這一點很希望國內知識分子能夠理解。
鬍治洪:從上述對您的學術事業均具重要影響的中國颱灣、美國、中國大陸三個方麵的廣泛交往中,您如何厘定自己的師承?
杜維明:關於師承問題,也就是所謂“道統”問題。嚴格意義上的“道統”類似於原教旨主義,講究原始教義一脈相承,這是我所不取的,實際上也難以把握。儒學史上往往以為孔子之道傳於孟子,荀子則不得其傳。荀子固然有“製天”“用天”思想而不尊“天”,但他的“道”則具有超越性,不能說完全超逸於孔子。又或以為孟子心性之學由陸、王繼承,硃子屬於彆傳(如牟宗三先生認為硃子是“彆子為宗”)。但李退溪恰恰認為他自硃子一係所繼承的纔是孔孟正統。凡此均提示我們,對於“道統”或師承,既要有真正的認同,又要有開放的心靈。
具體說到我個人的師承,嚴格地說,應該由學術界根據我的論著所錶現的思想形態加以判斷。不過我可以談談我的一傢之言,謹供參考而已。從我衷心服膺以及學術期許來看,我確實最接近熊十力、牟宗三一係,熊、牟對我的思想震撼力最大。但在私人感情上,我與徐復觀先生最親近,徐先生那種隨俗的生活態度、泥土氣息以及樂觀精神對我有很大影響;在這方麵,徐、牟形成鮮明對照,牟先生晚年心境是很孤獨,甚至很痛苦的。餘敦康則認為我更像唐君毅先生,唐先生也承擔大量行政工作,與狄百瑞、陳榮捷、岡田武彥等一起積極宣傳新儒學,重視傢庭生活,這也是一種看法。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文字結構猶如精美的復調音樂,不同的主題和引證在不同的章節中交織、呼應、補充,形成一種立體的思想景觀。我發現,作者對東方思想傳統的梳理,並非為瞭復古守舊,而是為瞭從中汲取營養,用以迴應現代性的睏境。這種“迴到源頭,麵嚮未來”的姿態,令人耳目一新。閱讀時,我感覺自己仿佛站在一個高處,俯瞰著全球文化交流的復雜網絡,能夠更清晰地辨識齣哪些是錶麵的碰撞,哪些是深層的融閤。作者的判斷往往是審慎而富有遠見的,他很少給齣斬釘截鐵的結論,而是提供瞭一套考察問題的嚴密方法論。這種高質量的智識輸齣,使得這本書不僅僅是一部學術著作,更像是一份麵嚮未來世代的思想遺産,值得反復研讀和深入思考。
评分這部厚重的文集,初翻時便被其深邃的思想底蘊所吸引,它像一位曆經風霜的智者,緩緩展開他對人類文明復雜圖景的洞察。閱讀的過程中,我時常停下來,反復咀嚼那些精妙的比喻和旁徵博引的論述,仿佛置身於一場跨越時空的思想辯論現場。作者對不同文化脈絡的理解並非停留在錶麵的羅列,而是深入到其核心的價值取嚮與內在邏輯的張力之中。那種對“和而不同”的追求,在當代全球化語境下顯得尤為迫切而珍貴。它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建立在對人類共同睏境深刻體認基礎上的理性呼喚。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敏感議題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剋製而又堅定的批判精神,既不盲目推崇西方中心論,也對自身文化傳統保持著審慎的反思,這種平衡感,是許多同類著作難以企及的高度。整部作品的行文節奏張弛有度,引人入勝,即便是對特定哲學流派不甚熟悉的讀者,也能被其強大的思辨魅力所感染。
评分坦率地說,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更像是一次漫長而深入的個人對話,而非單嚮的信息灌輸。作者的語言風格洗練且富有張力,時而如清泉般明淨,時而又如哲人般深邃,這種多變的語調有效地避免瞭單一敘事的疲勞感。我尤其欣賞作者在闡述復雜概念時,那種不厭其煩地勾勒背景、鋪墊語境的耐心。這使得即便是初次接觸這些理論的讀者,也能較為順暢地跟上其思想的河流。書中對“跨文化理解”的探討,沒有落入膚淺的文化相對主義的窠臼,而是努力尋找那些植根於人性深處的共通點,同時又極其敏銳地捕捉到那些決定性差異的意義所在。讀完後,我的內心湧動著一種強烈的衝動,想要立刻找人分享閱讀的震撼,去探討書中所提齣的那些富有挑戰性的觀點,因為它真正觸及瞭我們這個時代最核心的精神睏境。
评分拿起這本書,我立刻感受到一股撲麵而來的學理性氣息,但絕非那種枯燥乏味的學院派陳詞濫調。作者的敘事技巧高超,他總能將宏大的哲學命題,巧妙地植入到具體的曆史事件或當代思潮的剖析之中,使得理論不再是懸浮在空中的概念,而是具有鮮活生命力的工具,用來解剖現實的肌理。讀到關於知識分子責任的那幾章,我深有感觸,那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擔當,在信息爆炸、真僞難辨的時代,顯得愈發彌足珍貴。全書的邏輯鏈條極為縝密,每一次論證的推進都像是精心設計的建築結構,層層遞進,環環相扣,讓人在閱讀中體驗到一種智力上的愉悅和掌控感。它提供瞭一種看待世界的全新坐標係,幫助我校準瞭過去可能存在的認知偏差,促使我對“現代性”本身的定義進行再審視。這不是一本提供標準答案的書,而是一張邀請函,邀請讀者參與到永無止境的自我追問之中。
评分這本書的篇幅看似可觀,但閱讀起來卻有一種“一目十行,十行有味”的奇特感受。它的魅力在於一種微妙的“疏離感與親近感”的交織。作者在宏觀層麵運籌帷幄,對曆史長河的把握精準而富有洞察力,但在微觀細節處,又流露齣對個體經驗和生命境遇的深切關懷。我特彆欣賞其中關於“變局”的論述,作者沒有采取悲觀主義的立場,而是強調在危機中蘊含著重塑可能性的巨大機遇。文字中蘊含著一種內在的韌性和樂觀,這種力量感是通過無數次艱難的思想搏鬥換來的,而非空洞的自我安慰。這種基於深厚學養而産生的洞察力,使得全書的論述極具說服力,讓人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感受到思維的邊界正在被溫柔而堅定地拓寬。
评分大师之作,自当好好学习。
评分一本了解国学的书籍。
评分好书,快递很给力,希望大家看看
评分包装精美,物流速度真快,服务态度也很好。
评分好书就不用说了!杜为民是一个大学者。建议买。
评分艹(*≧m≦*) 奶茶表
评分内容也佷好,不一样的感觉。
评分挺好的,喜欢,希望能有所帮助
评分非常不错的一本关于儒家文明的书,值得购买与阅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共同的生活 [La vie commun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97812/58632edbNe76f8e73.jpg)
![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 [Primate Visions:Gender,Race,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98247/596dbeeaNb48542a5.jpg)
![圣灵降临的叙事(增订版) [Narratio Instincta Descenti Spiritu Sancto]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15954/589ae580Nc88f5172.jpg)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 [Series of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Research on Marxist Epistemolog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30901/59883332Nd437582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