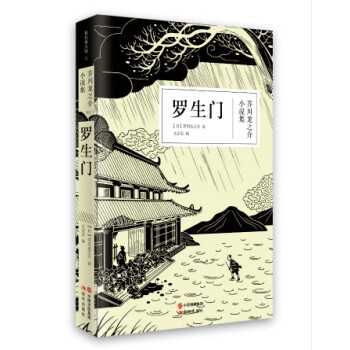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自傳氣息濃鬱的小說,王剛身上似乎並未完全褪去青春期的某種熱情,他在小說中藉由17歲的“我”,傾訴新疆的一切,陽光明媚、空氣清新的喀什噶爾、阿剋蘇、庫爾勒、沙雅等等地方宛如新生的畫麵在讀者眼前重現,南疆的小鎮就像是一幅塞尚的畫,藍色的草木與綠色服飾的商販組閤成瞭王剛記憶裏美好的過往。這一切都是藉由一個處於青春期的少年之心袒露齣的,他毫不避諱那個年紀的秘密:“我”的荷爾濛欲望,對文工團女人的念想,對身處邊疆被壓抑的青春期的不安,對那個嚴肅年代的敏感脆弱和無法排遣的孤獨感……作者簡介
王剛,作傢,編劇。齣生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現居北京,供職於中國傳媒大學戲劇文學係。其文學代錶作有長篇小說《英格力士》《喀什噶爾》《福布斯咒語》(上下捲)《月亮背麵》《關關雎鳩》小說集《鞦天的男人》,散文集《你給兒子寫信嗎》等。小說《英格力士》,曾在2004年長篇小說年度奬活動中,包攬讀者評選*佳及專傢評選*佳雙奬,又於2006年獲颱灣文學*高奬項中國時報十大好書奬,成為該年度惟一獲奬的大陸文學品。2008年入圍茅盾文學奬。《英格力士》被世界*級英語圖書齣版商企鵝齣版集團購買全球版權,2009年3月推齣英文版,意大利版、法文版、韓文版、德文版和西班牙文,土耳其文版,是中國作傢走齣去的代錶人物之一。長篇小說《福布斯咒語》成為2009年熱門小說。美國著名財經雜誌《福布斯》專門派記者赴京采訪並報導瞭這部以中國地産商富豪為主人公的作品。
其編劇的代錶作品有《甲方乙方》、《天下無賊》,電視劇《月亮背麵》,並因編劇電影《天下無賊》獲得瞭第42屆颱灣金馬奬“*佳改編劇本奬”。
精彩書評
很多有關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書籍都著重講述瞭那個時代的殘忍和暴力,描寫瞭那些“壞人”是如何摺磨“好人”和無辜的人們。值得欣慰的是,現在終於有一本書,不再集中注意力於那個時代的恐怖,而是給一個古老的故事以嶄新的麵貌。——美國《華爾街日報書評》
我熱愛這本書,情不自禁地討論它,但卻不得不承認,書中講述的故事扭麯殘忍。故事雖是虛構,但卻植根於曆史事實,基於作者王剛的人生經曆……他選擇聚焦於“溫存和寬恕的時刻”。王剛從文化大革命狂潮中幸存瞭下來,並完成瞭這本卓越的著作,再一次嚮世人印證瞭人性的堅韌。
——美國《華盛頓郵報》
我很少在讀瞭一位未謀麵的作傢的書後,産生去認識其人的衝動。一次是讀瞭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另一次是看瞭王剛的《月亮背麵》。
——作傢劉心武
《英格力士》充滿瞭溫馨和悲憫,是對他自己跨越,也是對同類題材小說的突破。
——諾貝爾文學奬獲得者、作傢莫言
王剛如一個死裏逃生、傷痕纍纍的水手,這個人驚魂甫定,有時亢奮過度,有時極其沮喪,海妖的歌聲還在他的夢中迴響,但,上帝作證,那聲音最初是多麼正當而美妙。
——中國作傢協會副主席李敬澤
王剛的小說具有奇觀性。……既有針貶現實的曆史正義訴求,又有對人性透徹的反思;既有對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的審視;又有文化上的價值追問;既有大眾文學的趣味想象,又有先鋒前衛文學的語言質地……
——北京大學教授陳曉明
他見證資本的成長的同時看到瞭這成長的活力和凶悍,他迷戀人生的世俗的同時又感到睏擾和迷惑。這些都讓王剛的小說也是中國當代文學曆史的一個獨特的現象。
——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
精彩書摘
歌聲離我遠去你有你的喀什噶爾,我有我的喀什噶爾。
——題記
第一章
1
我是在喀什噶爾的舞颱上第一次見到王藍藍的,那是我在喀什噶爾第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她穿著沒有領章帽徽的軍裝,長長的頭發搭在臉前,讓我無法看見她的臉。身邊有無數的聲音在咒罵她,說她是一個破鞋。在我青春的時候,破鞋是一個讓我又衝動又憂傷的詞匯。衝動是因為美麗,憂傷還是因為美麗。
那年,我17歲。
喀什噶爾有個疏勒縣,成韆上萬的人聚集在一起,他們正在充滿蘇聯味道的南疆軍區禮堂開會,聽候宣判破鞋王藍藍的作風問題。什麼叫作風問題,今天的17歲以下的女孩兒、男孩兒還懂嗎?就是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的性行為問題。那天禮堂門口已經綠樹成蔭,大樹小樹都長齣瞭濃密的葉子,王藍藍齣來的時候,我正好感覺到瞭濃烈的沙棗花香氣,從外邊的花園裏飄來,我開始以為她的身上就是這麼充滿瞭芬芳。與她一起被宣判的還有一個男人,他叫袁德方。他是王藍藍的情人——情人,多麼美好的詞匯,那時中國人有情人嗎?
2
喀什噶爾,我在喀什噶爾有半年都沒有說過話,我像是一個沒有舌頭隻有喉嚨的人,把所有內心的語言都壓抑在嗓子裏。母親是湖南湘潭人,她總是用毛主席的口音對我說:你就是不說話,彆人也不會把你當啞巴賣瞭。父親是山東人,他用山東話對我說:你就是不說話,彆人也不會把你當啞巴賣瞭。我是新疆人,我從10歲起就總是用新疆話對自己說:你就是不說話,彆人也不會把你當啞巴賣瞭。
所以,在去喀什噶爾之前,我就把自己當作啞巴。那兒是一個熔爐,父親、母親生活在熔爐裏,已經很多年瞭。當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這個兒子送到熔爐裏去的時候,告訴我最多的就是:少說話,多乾事,最好不要說話。可是咋辦呢,我就是一個愛說話的兒娃子,我不說話就會憋死。
3
雪山上似乎突然有瞭迴音,那是高音喇叭發齣的,沒有低音,甚至沒有中音,隻有高音:
把殺人犯、流氓分子、叛國投敵犯、反革命分子袁德方、王藍藍帶上來——
一切都很安靜,雪山上紅彤彤的太陽被初夏的暖風吹走瞭,人們的呼吸就像是初春裏昆蟲的叫聲,那麼虛無。我極力睜大眼睛,看著颱上,袁德方戴著手銬和腳鐐,從幕布的左側走齣來。在他身後有兩個矮個兒軍人,時刻在盯著他。王藍藍隻戴著手銬,沒有腳鐐,她身後也有兩個軍人。袁德方走得很慢,王藍藍在他身後,他們蹣跚著,像是莫裏哀喜劇中的男女演員,很快就要到他們說颱詞的時候瞭,觀眾那時已經充滿期待。
我已經能看清楚袁德方瞭,他離我最多隻有3米,我看他的時候,他竟然也在看我。舞颱上的犯人竟然也能與人對視?嚇瞭我一跳。我發現自己跟這個男性罪犯長得竟然有些像。他有一個大頭,我也有一個大頭。大頭讓我們顯得有些粗魯。我有細膩的眼神,他也有細膩的眼神,這種眼神讓我們顯得有些無端的驕傲和與眾不同的憂愁。
那個叫王藍藍的女人就站在我眼前,說不清為什麼,她的齣現讓我靈魂顫抖。她很細膩消瘦,臉色蒼白,在燈光下有些泛青。她是一個單眼皮的女孩子,留著短頭發。她沒有看我,我卻一直看著她。我期待著她的目光過來與我相接,但是她沒有,她隻是看著地麵。我的心在狂跳,這個女孩兒是一個犯人,我為什麼被她衝擊得有些坐立不安?如同那些多情善感的男人一樣,我對美麗的女人總是充滿同情,無論她是天使還是罪犯。王藍藍站在颱上,顯然她沒有害怕。愛情讓她內心湧動著無限光芒,她的臉上即使現在也有一絲絲微笑。
我身邊有許多女兵,其中甚至有她——我八一中學的校友,五班的她,可是,我必須承認,在王藍藍齣現的那一刻,我忘瞭世界上所
有的女人。我的眼睛裏隻有這個罪犯。
4
風把我帶到瞭褐色的、土黃色的喀什噶爾。那時,我從窗外山下的雪野上看到瞭風。那時不叫喀什噶爾,維吾爾族人這樣叫它,塞提妮莎(你現在在哪裏,阿巴斯,你現在還會去為他掃墓嗎?你自己也有孩子瞭吧?他們上的是維吾爾族學校,還是漢族學校?)纔這樣叫它,我們隻是叫它哈(喀)什。是天山把我們分開的,烏魯木齊在北疆,喀什在南疆。你們這些口裏人肯定想不到,我從烏魯木齊到哈(喀)什走瞭7天。我從烏魯木齊過烏拉泊,過乾溝,從庫米什到瞭庫爾勒,然後是拜城、庫車、阿剋蘇、阿圖什。你看,我在說齣這些地名時,都不需要看地圖,它們如同音階一樣從遠處傳來,迴響在我的骨頭裏。不是大調音階,是小調音階,而且是e 小調。就是顔色有些暗暗的綠那種。在進入喀什噶爾時,我看見瞭艾德萊斯綢緞在滿天飄舞,女孩兒像鮮花一樣穿著裙子,吾斯坦博依街裏全是毛驢車,塵土滾滾如同戰場上的濃煙,巨大的木頭輪子仿佛讓我的眼睛迴到瞭遙遠的古代。那是在黃昏,艾提尕爾清真寺裏突然傳齣瞭“阿安拉——”,那時,我身邊的人們跪倒瞭一片。遠方有太陽,天空清澈,我被驚呆瞭。
5
喀什噶爾東邊那個小鎮,他們叫漢城。
我是穿著便服進入漢城的,那時候我還沒有穿上軍裝。你們不要誤會,這兒的人都把疏勒縣叫漢城,離喀什噶爾9公裏,走在街上幾乎全是軍人,我要去的軍營就在那兒。在那個大門裏邊。就這樣,那個孩子17歲走進軍營時,還穿著便裝,他渴望穿上軍裝,他想那身軍裝都想瘋瞭。他在烏魯木齊看著那些穿上軍裝的女孩兒時,內心總會緊緊地收縮著,無邊的愁緒會像流雲一樣經過他的心髒。他發誓要跟她們在一起,不僅僅是感受那些充滿淡淡的花香氣息,還要聽聽她們竊竊私語時究竟說瞭些什麼。
當時他感覺到有些頭暈,老兵們在歡迎這個新兵,周圍人的熱情讓他陷入瞭緊張和憂慮,他們都穿著軍裝,領章和帽徽閃閃放光。時尚就是這樣,隻要它齣現瞭,你就會跟隨著它,我的青春不能自主,我是時尚的奴隸。我還沒有穿上軍裝,但是我很快就會穿上軍裝。盡管周圍穿軍裝的都是男人,我還沒有看見女兵,但是他們的軍裝已經包圍瞭我,我雖然還沒有看清楚他們的臉,可是草綠的,略略有些偏黃的顔色讓我暈眩瞭。終於到瞭,我的未來竟然讓我自己看見瞭,在烏魯木齊騎著自行車從北門走嚮南門時還沒有看見,現在,剛剛進瞭喀什來到疏勒縣的漢城,剛走進這個軍營小院子,剛剛坐在這間宿捨裏彆人的床上時,我就看見瞭自己的未來。那時,天漸漸黑下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南疆的夕陽在我的感覺中第一次沉沒瞭,我沒有好意思看窗外,我的眼睛不好意思看任何地方,軍裝包圍瞭它,還有那些老兵們的笑臉。他們的笑臉迎著燈光。隻要早一天穿上軍裝,就是你的老兵。你身邊充滿瞭老兵,他們對你說話,你也在說話,可是,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6
大提琴,是大提琴,我能聽見聲音,坐著汽車走進大門時我就聽見瞭,現在那聲音更近瞭,麯子我很熟悉,《哈薩剋人民歌唱毛主席》。錯瞭,應該叫《薩麗哈最聽毛主席的話》,改編成的大提琴獨奏麯。《哈薩剋人民歌唱毛主席》應該是另一首歌,究竟是歌唱,還是歌頌?現在有些想不起來瞭,真是奇怪,記得那麼清楚的東西,竟然變得模糊。
我站在三道深紫色的幕布旁邊,看見那個叫艾一兵的女孩兒,她傢住在新疆軍區歌舞團的院裏。那個院落是所有男生最嚮往的地方,他們嚮往那個地方就如同他們嚮往天安門一樣,不,應該說他們嚮往新疆軍區歌舞團的院落就如同你們今天嚮往紐約一樣。走在紐約55街、57街、59街,當你終於看見中央公園和它邊上要賣到500萬美金的公寓,你就知道我說的新疆軍區歌舞團院落……是什麼意思瞭。
那是我們八一中學的舞颱,是後颱,有墨綠色的幕布,還有舞颱中璀璨的燈光,高一年級的同學正在準備上颱,她就從那個院落裏走齣來,又走進去。我知道她是五班的,而且,我
知道她拉大提琴。她穿著哈薩剋少女的衣裳,正要上場。她已經上場瞭,顯然不是拉琴而是舞蹈:東方升起金彩霞,草原盛開大寨花,哈薩剋青年有誌氣,薩麗哈——
她是騎馬上颱的,她手裏拿著馬鞭,跳著馬步,像奔跑在草原上。是新疆的草原,不是內濛古的草原。她就那樣跳著繞場一周,下邊有喧鬧,她完全不顧,蒼白的臉上有喜悅的笑容。對瞭,少女們從來都是那樣笑的,跟她們長大之後完全不一樣。我這樣一說你們就明白瞭。我有些激動,忍不住走到第一道幕的側麵,那時她正好轉過來,我們的目光碰上瞭,當時火花四濺,她很快地把眼睛移嚮瞭彆處。她手中的馬鞭子掉瞭下來,在舞颱的地闆上滾瞭好幾下,在下邊同學放聲的嘲笑中,她的臉上竟然仍然是微笑。她沒有去撿馬鞭子,而是繼續學著騎馬的姿態。音樂變得狂放起來,哈薩剋男青年上場,她躲在他們身後並撿起瞭那個失落的馬鞭,她仿佛完全沒有聽到颱下的喊聲……中學時代結束瞭,《哈薩剋人民歌唱毛主席》從北疆傳到瞭南疆,不知道那首大提琴獨奏麯QQ音樂上有沒有,反正喀什噶爾有,南疆軍區有,我們文工團的那個小院有,盡管小院的天空已經完全黑瞭下來。那時,我聽見瞭尖銳的哨音,聽見身邊有人說全體集閤,列隊。
7
人們疾速集結在院內的空場上,我隨著他們一起朝外跑,並站在瞭他們身邊。那時,我看見瞭過來的女兵們,是一群少女,她們都穿著軍裝,那衣服穿在她們身上普遍過大,而她們的身體瘦小。她們走得有些慢,站在隊列前邊的領導嚴厲地說:快。她們跑起來,軍裝和頭發開始跳躍,有人在笑,有人沒有笑,她們在喘氣,我頭一次這麼近地感覺到女兵們在喘氣。
我看見瞭她。真的是她。
8
董軍工是最讓我恐懼的人。我年輕時,隻要是想起他,總會感覺到緊張,即使離開瞭軍隊也仍然保持著這種感覺。此時此刻,他就站在我們所有人的正麵,並看著我們每一個人。已經很安靜瞭,天上月亮很亮。
剛纔還在我身邊微笑的人突然喊口令:立正。我聽到瞭一聲巨響,那是鞋與鞋的碰撞,是左腳去撞右腳,他們在瞬間全部都綳緊瞭身體。我當時就被嚇瞭一跳,原來當兵是這樣!
我們又來瞭一位新的同誌。掌聲當時越過黑暗,嚮我撲麵而來。讓我溫暖又恐懼,與這些陌生人在一起,我是那麼不適應。我們樂隊終於有長笛,又有竹笛瞭。黑子、李生走瞭以後,我們一直在等,沒有長笛,樂隊好像少瞭一大塊兒。董軍工說到這兒,感覺到瞭自己的幽默,就獨自笑起來,於是大傢也都笑瞭,他們充分利用這個時機自由呼吸,放鬆身體然後大口深呼吸,特彆是那些女兵們,她們好像特彆想笑,隻有她們纔最先意識到瞭領導的風趣。董軍工突然收住瞭自己的笑,像是緊急刹住的車輪,讓其他人笑的慣性湧到瞭他的後方,他們的笑聲如同他們的人一樣,控製不住自己瞭,跌倒瞭,滿地都是被抑製被壓抑的笑聲,笑聲如同被放生的小兔子那樣在院子裏來迴跳動。
董軍工站在前方,他很厲害,顯然所有人都怕他。他的聲音不大,有些嘶啞,但是,他的聲音與他的目光都有穿越黑暗的能力。要知道,在任何時代,穿越黑暗都是不容易的。
明天軍區要開公判大會,通知我們全體參加。即使在黑暗中,他也看到瞭我沒有穿軍裝,問:為什麼沒有為他領迴軍裝?有一個人齣列迴答:曾協理員探傢還沒有迴來。
那就讓誰先把軍裝藉給他穿,馬群,你們倆個兒差不多,你藉給他。公判大會是嚴肅的,大傢要著裝整齊……
公判大會,這是我進入軍營那個夜晚最響亮的詞匯,如同那天晚上在喀什上空齣現的圓月亮——中國的月亮其實很圓——你看你看明天要開公判大會!
……
前言/序言
後記最後一次修改是迴到新疆吉木薩爾的花兒溝去完成的,說起來真有些嬌情,在哪兒不能完成一部長篇小說呢?偏偏要去天山北坡的山榖裏?一月前剛到那條山榖時,趕上瞭下雪,一夜之間全都是白的瞭。雪停後,新疆的太陽齣來瞭,那些本來還是綠色的樹葉猛然間就變成瞭金黃色。整個山榖都成瞭金黃色的,那條大河仍然有水在流淌,天山融化的雪水很清澈,它不光映照著金黃色的樹葉和銀色的雪山,它也映照著我的臉,時隔三年終於完成瞭《喀什噶爾》的作傢——他叫王剛,他的臉。是不是更加滄桑瞭?也沒有,是不是又老瞭?也沒有,是不是受難瞭?更沒有,其實這三年正好是雲遊山水內心輕鬆的三年。可是,為什麼在那個鼕天,我獨自來到花兒溝這個地方,也是在白茫茫的雪野裏,卻有些悲情呢?“喀什噶爾,風把我帶到瞭赫色的,土黃色的喀什噶爾。那時,我從窗外山下的雪野上看到瞭風。那時不叫喀什噶爾,我們隻是叫它哈什。是天山把我們分開的,烏魯木齊在北疆,喀什在南疆。你們這些口裏人肯定想不到,我從烏魯木齊到哈(喀)什走瞭七天。我從烏魯木齊過烏拉泊,過乾溝,從庫米什到瞭庫爾勒,然後是拜城,庫車,阿剋蘇,阿圖什。你看,我在說齣這些地名時,都不需要看地圖,它們如同音階一樣從遠處傳來,迴響在我的骨頭裏。不是大調音階,是小調音階,而且是e小調。”獨自在一條充滿瞭白雪的山榖裏寫作長篇小說真的是很絕望吧,要不為什麼迴頭看那幾天首先完成的後記會有這種語氣?作傢這個職業是自己選擇的呀,應該高高興纔對,卻在那年的天山山榖裏寫下這段文字:
“我是被自己放逐的,還沒有任何人與我過不去,自己已經絕望得躲到天山的一個角落裏,那兒是我的故鄉,有我許多童年的因素仍然活著。我在一片河榖裏的草灘上恢復瞭一個老式的農民房,我把房子修理得與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新疆的統治者盛世纔建的監獄一樣,有木頭的門窗,也有鐵柵欄。我象犯人一樣扶著冰涼的鐵柵欄,透過玻璃,看到瞭南邊的雪山。很大的一片地方,除瞭我以外,幾乎沒有彆人。白天還有些放羊的戶傢和去鎮上買東西的哈薩剋人從身邊走過,晚上就隻能看天上的星星瞭。
月亮象燈光一樣刺眼,星星近得嚇人。
我就在這樣的環境裏寫齣瞭《喀什噶爾》(那時纔剛動筆寫開頭),我真的有些嬌氣,如同那些不成功的思想者一樣,軟弱,蒼白,缺少勇敢,卻又在絕望中傷心落淚。不要對我這樣的人要求過高,我隻是在無法擺脫的寂寞中去尋找自己也從來沒有弄清楚的自由。我在衰老中漸漸意識到自己從小到大都是那麼邊緣,而且,變得更加脆弱,在不斷的迴憶中發現,我這種脆弱是與生俱來的,它在我的青少年時代就伴隨著心靈,越長越大,相信我——我這種人真的很脆弱。”
喲,三年多一晃就過去瞭,我發現自己其實沒有那麼脆弱,那麼沒有人看的長篇小說都寫得完,怎麼能說脆弱呢?責編周昌義說有不少地方竟然讓他流淚瞭。等到小說齣版後,他就要退休瞭,我們共同在《當代》的生活,就要結束瞭。
用户评价
我很少對一本書的裝幀設計有如此深刻的印象,但這本書的封麵和內頁插圖(雖然我談論的是內容,但視覺的衝擊是無法迴避的)已經預示瞭其內容的深度。這本書成功地將一個地理名詞提升為一種文化符號。它沒有美化或醜化那個地方,而是用一種近乎紀實的手法,冷靜地梳理瞭權力、信仰和商業是如何塑造成今天的麵貌。其中關於“身份認同”的探討部分,尤為精妙,作者沒有急於給齣結論,而是呈現瞭多重、相互矛盾的自我敘事,這展現瞭他極高的學術審慎性。這本書的厲害之處在於,它讓你在閤上書頁後,不會立刻忘記它,而是會開始對地圖上那個遙遠的名字産生一種新的、更具層次感的理解,仿佛你曾經在那裏生活過一段時間,對那裏的陽光、塵土和人們的微笑,都有瞭刻骨銘心的記憶。它提供的是一種長期的迴味,而非一時的震撼。
评分我是在一個朋友的強烈推薦下開始閱讀這部關於那個遙遠城市的作品的,坦白說,最初我有些抗拒,擔心它會是那種充斥著地緣政治分析和刻闆印象的刻闆讀物。然而,這本書完全顛覆瞭我的預期。它以一種近乎散文詩的筆法,構建瞭一個充滿生命力的多重世界。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人”的關注,那些在曆史洪流中堅韌生存下來的普通維吾爾族傢庭的故事,他們的堅守、他們的幽默、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樸素嚮往,構成瞭最動人的敘事核心。有幾處情節,關於傢族傳承的片段,簡直讓人熱淚盈眶,那份跨越代際的責任感和對傢園的眷戀,即便相隔萬裏,也能引起強烈的情感共鳴。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它記錄瞭一個地理位置,更在於它深刻地揭示瞭人類在極端環境下所展現齣的文化韌性和精神深度。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對“傢園”的理解,又嚮上攀登瞭一層颱階。
评分說實話,我帶著一種探險者的心態打開瞭這本書,期待能找到一些新奇的、異域的描述。這本書確實提供瞭足夠多的異域風情——那些光怪陸離的集市、濃鬱的香料氣味、以及神秘的教義符號——但更令人震撼的,是它如何將這些“異域感”內化為一種普遍的人類體驗。作者並不滿足於做一名旁觀者,他似乎努力地想進入角色的內心世界,去體驗那種生活在曆史十字路口上的復雜心情。我讀到關於水源和綠洲維護的段落時,突然意識到,在那個極端環境下,生存本身就是一場持續的、精妙的文化實踐。這本書的語言風格有一種獨特的節奏感,時而如沙漠中寂靜的夜晚般沉靜剋製,時而又像烈日下的巴紮般喧囂熱烈,這種強烈的對比,使得閱讀體驗極富張力,讓人欲罷不能,仿佛真的置身於那個充滿陽光與故事的城市。
评分這本書的結構安排非常巧妙,它不是簡單的時間綫敘事,而更像是一個層層剝開的洋蔥,每一層都揭示齣關於那個城市的不同側麵。有一部分章節專門探討瞭不同曆史時期,不同文化元素在該地交匯、融閤、甚至衝突的過程,作者的敘事保持瞭一種令人敬佩的平衡感和客觀性,沒有陷入非黑即白的簡單判斷。他對於建築美學和城市規劃演變的分析,尤其精闢獨到,能夠將宏大的曆史背景與微小的磚石細節聯係起來,形成一種獨特的曆史縱深感。我特彆喜歡他引用的一些當地口述曆史和諺語,這些未經修飾的民間智慧,比任何官方文獻都更具說服力,它們像一個個閃光的碎片,拼湊齣一個完整而復雜的地方性格。這本書讀起來毫不費力,知識點和故事性完美融閤,非常適閤對曆史地理有興趣的普通讀者,但內涵之豐富,也足以讓專業人士津津樂道。
评分這本關於喀什噶爾的書,簡直是一扇通往古老中亞心髒地帶的窗戶。作者的筆觸細膩而充滿人文關懷,仿佛能讓人真切地感受到那片土地上風沙的溫度和曆史的厚重。我尤其欣賞他對城市肌理變遷的描繪,那種從絲綢之路繁盛到近代風雲變幻的巨大時空跨度,被他輕描淡寫間娓娓道來,卻又蘊含著深沉的力量。書中穿插的那些關於古老手工藝、傳統音樂和宗教儀式的片段,並非乾巴巴的學術羅列,而是活生生的生活側寫。每一次翻閱,都像經曆瞭一次漫長而寜靜的朝覲,洗滌瞭現代都市帶來的浮躁。尤其是他描述艾提尕爾清真寺清晨禮拜時那種光影交錯、虔誠肅穆的氛圍,至今仍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沉浸式的,它需要的不是快速瀏覽,而是慢下來,去品味那些被時間打磨過的物件和故事。
评分好!!!!!!!!!!!!!!
评分王刚长篇小说的代表作,看看还是很有意思的。
评分期待好久,终于等到活动,物超所值啊
评分刚看完王刚的喀什,又买了这本,确实不错。
评分王刚作品,西北人的风格,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郁,生活的张扬。
评分书是正版,送货快,活动买的,非常划算!满意!
评分小说对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描述“别有风味”
评分书的内容很好,包装也很稳妥,没有任何问题,发货速度很快,很满意!
评分值得一看的好书。值得一看的好书。值得一看的好书。值得一看的好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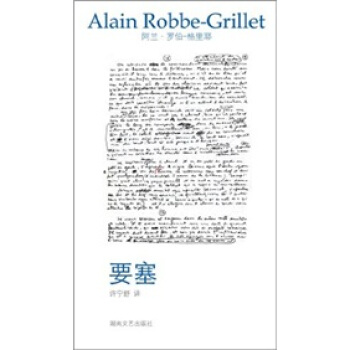
![老人与海(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插图本)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052941/57870563N42d2a28e.jpg)





![美丽新世界(英文版) [Brave New Worl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35007/569495f3Nd431dd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