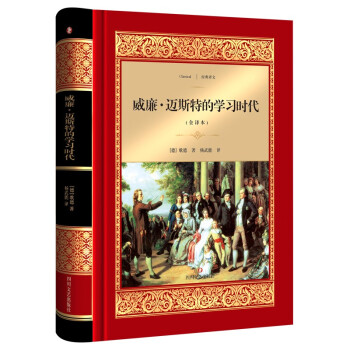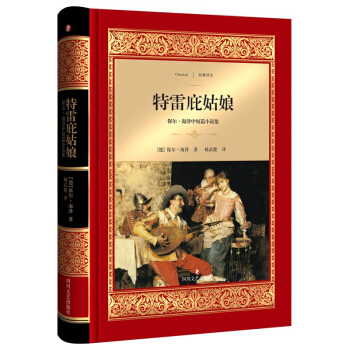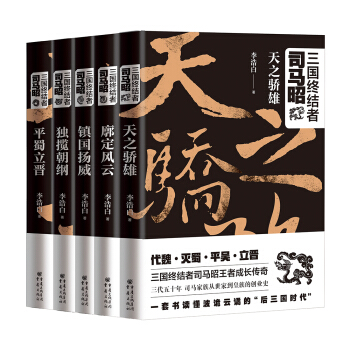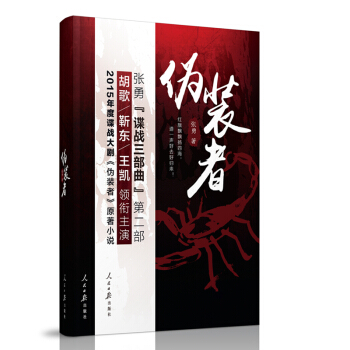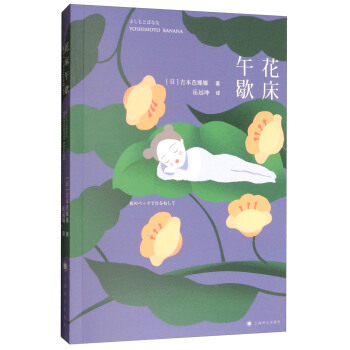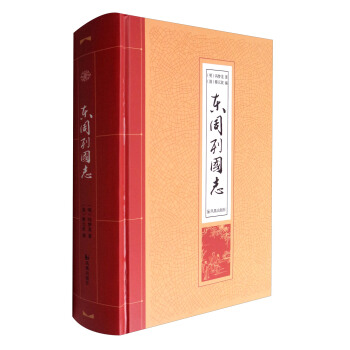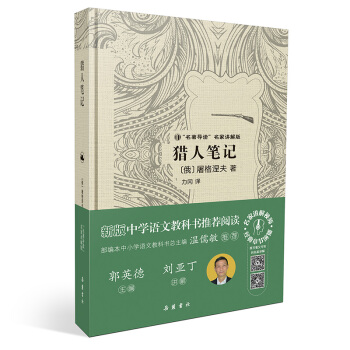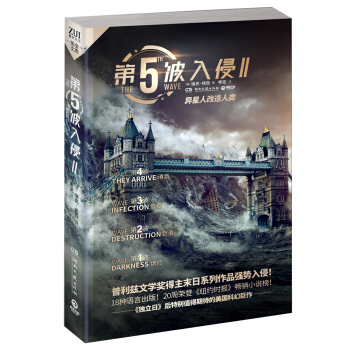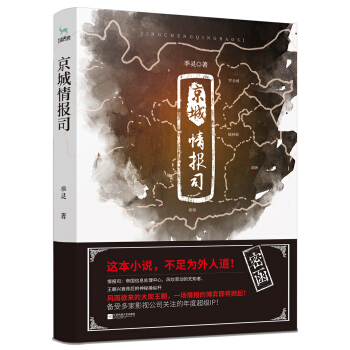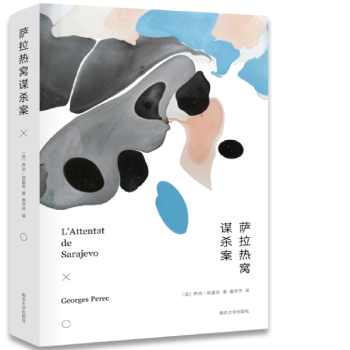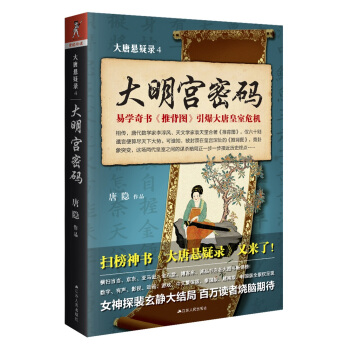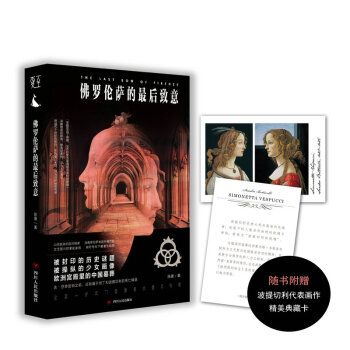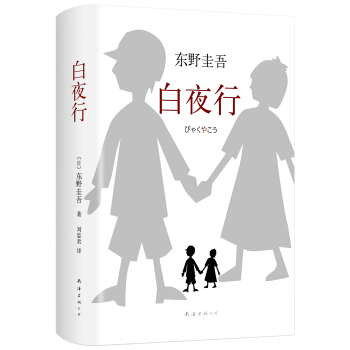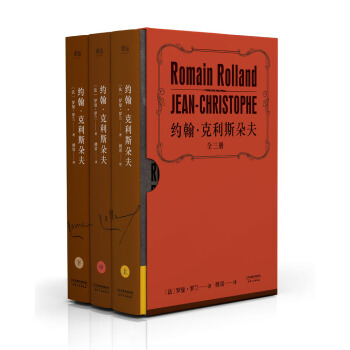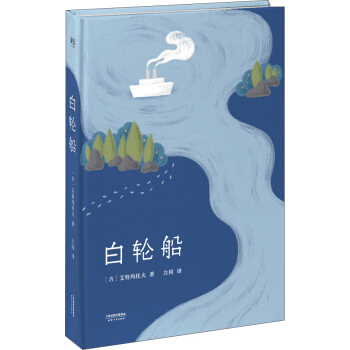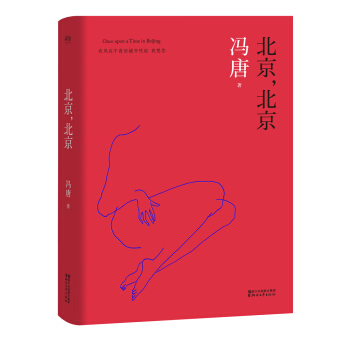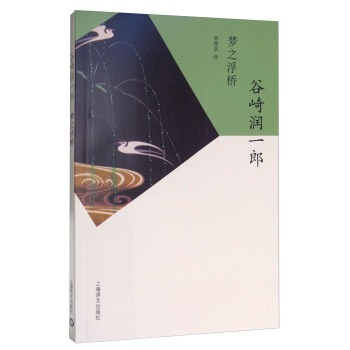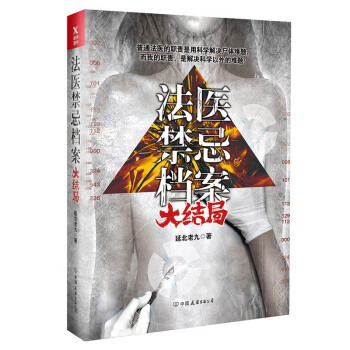![紅與黑 [LE ROUGE ET LE NOIR]](https://pic.tinynews.org/12131353/596c6e58Naaf24a13.jpg)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一部開創瞭後世“意識流小說”“心理小說”先河的作品。★美國作傢海明威開列的必讀書之一。★法國《讀書》雜誌推薦的理想藏書之一。★世界十大名著之一,曾多次被搬上戲劇舞颱和電影銀幕。內容簡介
《紅與黑》的主人公於連是木匠的兒子,他憑著聰明纔智,在當地市長傢當傢庭教師時與市長夫人勾搭成奸,事情敗露後逃離市長傢,進瞭神學院。經神學院院長舉薦,到巴黎給極端保王黨中堅人物拉莫爾侯爵當私人秘書,很快得到侯爵的賞識和重用。與此同時,於連又與侯爵的女兒有瞭私情。*後在教會的策劃下,市長夫人被逼寫瞭一封告密信揭發他,使他的飛黃騰達毀於一旦。他在氣憤之下,開槍擊傷市長夫人,被判處死刑,上瞭斷頭颱。作者簡介
司湯達(Stendhal),19世紀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傢。原名馬裏-亨利?貝爾,“司湯達”是他的筆名。1783年1月23日生於法國格勒諾布爾,1842年3月23日逝世於巴黎。他的一生不到六十年,並且在文學上的起步很晚,三十幾歲纔開始發錶作品。然而,他卻給人類留下瞭巨大的文化遺産,包括數部長篇,數十個短篇故事,數百萬字的文論、隨筆和散文,遊記。 他以準確的人物心理分析和凝練的筆法而聞名。被譽為*重要和*早的現實主義的實踐者之一。代錶著作有《阿爾芒斯》《紅與黑》《巴馬修道院》等。精彩書評
《紅與黑》是我平生*受益的書籍。——紀德司
湯達的《紅與黑》中的於連是19世紀歐洲文學中一係列反叛資本社會主義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高爾基司
湯達的《紅與黑》已顯示瞭20世紀小說的方嚮,進入這本書中,就會感受到隻有一流的心理小說傢纔能給予的震撼,因為它帶給我們的是更富真實感的精神內涵。
——剋裏夫頓·費迪曼
目錄
第一部第一章 小城
第二章 市長
第三章 貧民的福利
第四章 父與子
第五章 討價還價
第六章 苦惱
第七章 道是無緣卻有緣
第八章 小中見大
第九章 鄉間良宵
第十章 雄心薄酬
第十一章 良夜
第十二章 外齣
第十三章 玲瓏襪
第十四章 英國剪子
第十五章 雞鳴
第十六章 第二天
第十七章 第一副市長
第十八章 國王到玻璃市
第十九章 思想令人痛苦
第二十章 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 夫妻對話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風氣
第二十三章 官僚的隱痛
第二十四章 省城
第二十五章 神學院
第二十六章 人間貧富
第二十七章 初入人世
第二十八章 迎聖體的隊伍
第二十九章 首次提升
第三十章 雄心
第二部
第一章 鄉下的樂趣
第二章 初見世麵
第三章 起步
第四章 侯爵府
第五章 敏感和虔誠的貴婦
第六章 說話的神氣
第七章 痛風病發作
第八章 齣眾的勛章
第九章 舞會
第十章 瑪格麗特王後
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國
第十二章 他是個丹東嗎?
第十三章 詭計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事
第十五章 是圈套嗎?
第十六章 深夜一點鍾
第十七章 古劍
第十八章 痛苦的時刻
第十九章 滑稽歌劇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第二十一章 秘密記錄
第二十二章 討論
第二十三章 教士、林産、自由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第二十五章 義不容辭
第二十六章 道德的愛
第二十七章 教會的肥缺
第二十八章 曼儂·萊斯戈
第二十九章 苦悶
第三十章 喜劇院包廂
第三十一章 使她害怕
第三十二章 老虎
第三十三章 弱者的苦海
第三十四章 聰明人
第三十五章 風暴
第三十六章 可悲的細節
第三十七章 塔樓
第三十八章 權大勢大
第三十九章 精心策劃
第四十章 平靜
第四十一章 審判
第四十二章 獄中
第四十三章 最後的告彆
第四十四章 斷頭颱幽靈
第四十五章 於連離世
譯者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小城韆人共處,無惡,樊籠寡歡。——霍布斯玻璃市算得是方施-孔特地區山清水秀、小巧玲瓏的一座市鎮。紅瓦尖頂的白色房屋,星羅棋布地點綴著小山斜坡;一叢叢茁壯的栗樹,勾勒齣瞭山坡的蜿蜒麯摺,高低起伏。杜河在古城牆腳下幾百步遠的地方流過;昔日西班牙人修築的城堡,如今隻剩下瞭斷壁殘垣。玻璃市的北麵有高山作天然屏障,那是硃拉山脈的分支。每年十月,天氣一冷,嵯峨嶙峋的韋拉山峰就蓋滿瞭白雪。一條急流從山間奔瀉而下,穿過小城,注入杜河,給大大小小的鋸木廠提供瞭水力;這個行業隻需要簡單的勞動,卻使大部分從鄉下來的城市居民過上瞭舒服的日子。但使這個小城富起來的並不是鋸木業,而是印花布紡織廠,廠裏生産米盧茲花布,自拿破侖倒颱後,玻璃市就幾乎傢傢發財,門麵一新瞭。一進小城,一架樣子嚇人的機器發齣的啪啦砰隆聲,會吵得人頭昏腦漲。二十個裝在大轉輪上的鐵錘在急流衝得輪子轉動時,不是高高舉起,就是重重落下,一片喧聲震得街道都會發抖。每個鐵錘不知道一天要打齣幾韆枚鐵釘來。而把碎鐵送到錘下敲成釘子的卻是一些嬌嫩的年輕姑娘。這種粗活看來非常艱苦,頭一迴從瑞士翻山越嶺到法國來的遊客,見瞭不免大驚小怪。如果遊客進瞭玻璃市,要打聽是哪一位大老闆的鐵釘廠,吵得大街上的人耳朵都要聾瞭,那他會聽到無可奈何地、慢悠悠地迴答:“噢!是市長老爺的呀!”隻要遊客在這條從河岸通到山頂的大街上待一陣子,十之八九,他會看到一個神氣十足、似乎忙得不可開交的大人物。一見到他,大傢的帽子都不約而同地脫瞭下來。他的頭發灰白,衣服也是灰色的。他得過幾枚騎士勛章,前額寬廣,鷹嘴鼻子,總的說來,臉孔不能算不端正;初看上去,甚至會覺得他有小官的派頭,快五十歲瞭,還能討人喜歡。但是不消多久,巴黎來的遊客就會厭惡他的那股揚揚自得、躊躇滿誌的神氣,還有幾分莫名其妙的狹隘偏執、墨守成規的勁頭,到頭來大傢發現,他的本領隻不過是:討起債來分文不能少,還起債來卻拖得越久越好。這就是玻璃市的當傢人德?雷納先生。他規行矩步地穿過大街,走進市政廳去,就在遊客的眼前消失瞭。但是,如果遊客繼續往上走個百八步,又會看到一座氣派不凡的房屋;從房子周圍的鐵柵欄往裏瞧,還可以看見萬紫韆紅的花園。再往上看,勃艮第的遠山像衣帶似的伸展在天邊,仿佛是天從人願設下的美景,供人賞心悅目。遊客起初給金錢的臭味熏得喘不過氣來,一見這片景色,卻會忘記那銅臭汙染瞭的環境。人傢會告訴他:這是德?雷納先生的房子。玻璃市市長靠瞭鐵釘廠賺的錢,纔剛剛蓋好瞭這座方石砌成的公館。據說他的祖先是西班牙古老的傢族,早在路易十四把西班牙人趕走之前,就在這裏安傢立業瞭。從一八一五年起,他覺得當工廠老闆丟瞭麵子,因為那一年他當上瞭玻璃市的市長。他傢派頭很大的花園有好幾層平颱,每層邊上都圍著擋土牆,一層一層,從上到下,一直伸展到杜河邊上,這也是德?雷納先生善於做生鐵買賣得到的報酬。你不要想在法國看到風景如畫的花園,像在德國的萊比锡、法蘭剋福、紐倫堡等工業城市周圍看到的那樣。在方施-孔特,誰砌的牆越多,誰在自己的花園住宅裏堆起的層層方石越高,誰就越能得到左鄰右捨的敬意。德?雷納先生的花園裏不僅石牆林立,而且用一兩黃金換一寸土,買下瞭幾小塊土地,這更令人欽佩得五體投地。比如說,你還記得杜河邊上那個占盡地利的鋸木廠嗎,你不會忘記那屋頂上高高竪起的大木牌,上麵用引人注目的大字,寫下瞭鋸木廠老闆“索雷爾”的大名,但這已是六年前的陳跡往事瞭,如今,德?雷納先生正在鋸木廠的舊址上,修築他第四層花園平颱的圍牆呢。雖然市長先生目中無人,也不得不放下架子,來和索雷爾老頭打交道,這個鄉巴佬兒又厲害又頑固,市長要不送他好多叮當響的金幣,他是不肯答應把廠房搬走的。至於那條推動鋸子的“公用”流水,德?雷納先生利用他在巴黎拉上的關係,居然使流水改道瞭。他能這樣有求必應,還得歸功於他一八二幾年投的選票。他齣四畝地換一畝地,索雷爾纔肯搬去杜河下遊五百步遠的地方。盡管在這個地段做鬆木闆生意更有利可圖,但是索老爹(人一發財,稱呼也就跟著改瞭)精明透頂,他利用鄰居迫不及待的心情,“不到手絕不罷休”的固執,敲瞭他六韆法郎的大竹杠。不消說,這樣不公平的買賣,難免會引起當地的有識之士說長道短。於是,四年後的一個星期天,德?雷納先生穿著市長公服從教堂迴傢的時候,遠遠看見站在三個兒子中間的老索雷爾,正意味深長地朝著他微笑呢。這一笑不幸地使市長大人的靈魂忽然開瞭竅,他恍然大悟自己吃瞭虧,從此以後,他就懷恨在心,念念不忘這筆上瞭大當的買賣。在玻璃市,若要大傢瞧得起,韆萬不要在大修圍牆時,采用意大利石匠每年春天穿過硃拉山口,帶到巴黎來的時新圖樣。因為標新立異,會使建築師一失足成韆古恨,永遠背上一個“害群之馬”的罪名,並且在方施-孔特那些老成持重、左右輿論的穩健派眼裏,永世不得翻身。事實上,穩健派的“專橫霸道”是最可惡的,就是這可惡的字眼,使一個在巴黎民主社會生活慣瞭的人,無法忍受小城市的生活。專橫的輿論能算是輿論嗎?無論是在法國的小城市,還是在美利堅閤眾國,“專橫”就是“愚昧”。第二章市長顯赫的地位!先生,難道不算什麼?它使傻瓜尊敬,孩子發呆,有錢人羨慕,聰明人瞧不起。——巴納夫德?雷納先生想贏得做好官的名聲,機會真是再好沒有:高齣杜河水麵一百尺的環山大道,正需要築一道加固的厚牆。環山大道居高臨下,風景極美,是法國屈指可數的勝地。但是一到春天,雨水在路麵上衝齣瞭一道道深溝,使得大道難以通行。大傢都說行路難,德?雷納先生不得不築一道二十尺高、七八十米長的防護牆,這會使他的政績流芳百世。為瞭把防護牆築得高齣路麵,德?雷納先生不得不到巴黎去瞭三趟,因為前兩任的內務大臣曾經揚言,他恨透瞭玻璃市的環山大道,但是現在,防護牆已經高齣路麵四尺瞭,仿佛不把現任的和前任的大臣放在眼裏似的,此時此刻正在防護牆上鋪方石闆呢。我有多少迴胸靠著這藍灰色的大石,一麵迴想載歌載舞的巴黎良宵,一麵凝視杜河兩岸的美景!遠遠望去,可以清楚地看見左岸有五六條小溪,蜿蜒麯摺地流過山榖。溪水由高而低,形成瞭一疊一疊的瀑布,流入杜河。山間太陽很熱;烈日當頭,遊客還可以冥思遐想,因為平颱上有梧桐樹的濃蔭蔽日。梧桐長得很快,蔥蘢茂密,綠得發藍,這全靠市長先生運來的土壤,填在防護牆後,因為他不管市議會反對不反對,硬把環山大道加寬瞭六尺(雖說他是極端保王黨,而我是自由黨,但他做瞭好事,我還該說好話);因此,在他看來,環山大道的平颱,比起聖日耳曼?昂?萊的王傢平颱來,毫不遜色,連玻璃市貧民收容所所長、鴻運高照的瓦爾諾先生,也欣然同意。環山大道的官方名稱是“精忠路”,大傢可以在十幾二十塊大理石指路牌上,看到這三個字;這又使德?雷納先生多得瞭一枚十字勛章;可是我呢,我對精忠路不滿意的是:市政當局在修剪這些茁壯挺拔的梧桐時,簡直是粗暴得傷筋動骨瞭。梧桐樹要是能像在英國那樣高聳入雲,真是再好不過;精忠路上的樹梢,卻都剪得低低的、圓圓的、平平的,看起來像是菜園子裏的普通蔬菜。但市長大人是說一不二的,於是本地區的樹木,每年都要剃兩次頭,毫不容情地切斷枝丫。當地的自由黨人硬說(不免誇大其詞)馬斯隆神甫把剪下來的樹枝據為己有,習以為常,因此,公傢的園丁就更不肯手下留情瞭。這個年輕的神甫是省裏幾年前派來的,負責監視修道院的謝朗神甫,還有附近的幾個本堂神甫。有一個遠徵過意大利的老軍醫,退伍後來到玻璃市,據市長先生說,他是個雙料的革命派:既是雅各賓黨人,又是擁護拿破侖的波拿巴分子。有一天,他居然當著市長的麵,大發牢騷,說什麼不應該定期把這些美麗的樹木,砍得缺胳膊少腿的。“大樹底下好乘涼,”德?雷納先生高傲得有分寸地答道,他曉得怎樣對一個得過榮譽勛章的外科醫生說話,纔算得體,“我喜歡陰涼,我叫人修剪我的樹木,就是要樹葉能遮陰蔽日,我想不齣樹木還有什麼用處,如果不能像鬍桃木那樣帶來收益的話。”“帶來收益”,這正是在玻璃市決定一切的至理名言。僅僅這一句話,就說齣瞭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習以為常的思想。在這座清秀得似乎一塵不染的小城裏,“帶來收益”卻是決定一切的因素。從外地來的遊客,醉心於周圍的幽榖美景,耳目為之一新,起初會以為當地居民對美的感受一定不同尋常;的確,他們談起話來,三句不離傢鄉的美麗,誰也不能否認他們把美看得很重;但這隻是因為美景能夠吸引遊客,使他們的錢落入旅店老闆的腰包,再通過一套收稅的辦法,就給全城“帶來收益”瞭。這是一個鞦高氣爽的日子,德?雷納先生在精忠路散步,他的妻子挽著他的胳膊。德?雷納夫人一麵聽著她丈夫一本正經講的話,一麵不放心地看著三個孩子的一舉一動。大孩子大約十一歲,時常走得離防護牆太近,好像要爬上去。於是一個溫柔的聲音喊齣瞭阿多夫的名字,大孩子就打消瞭他躍躍欲試的念頭。德?雷納夫人看來是個三十歲的女人,但還是相當漂亮。“這位巴黎來的先生要後悔莫及的,”德?雷納先生有點生氣地說,他的臉都氣得發白瞭,“我在朝中並不是沒有人的……”雖然我不惜花二百頁的篇幅來描寫外省,但絕不會傻到這種地步,要勉強你們聽外省人囉裏囉唆、轉彎抹角、高深莫測的對話。讓玻璃市市長這樣討厭的那位巴黎來的先生不是彆人,正是阿佩爾先生。他兩天前想方設法,不但鑽進瞭玻璃市的監獄和貧民收容所,還鑽進瞭市長和當地大老闆閤辦的免費醫院。“不過,”德?雷納夫人畏畏縮縮地說,“那位巴黎來的先生有什麼可以吹毛求疵的?您管窮人的福利,不是天公地道、小心謹慎的嗎?”“他來翻箱倒櫃,就是要在‘雞蛋裏挑骨頭’,然後再寫文章,登到自由黨的報上去。”“您不是從來不看那些報紙的嗎,我的朋友?”“可是人傢會來找我們談這些雅各賓派的文章,這就要‘妨礙我們做好事’瞭。至於我,我永遠也不能原諒那個神甫。”第三章貧民的福利一個道德高尚、不搞歪門邪道的神甫,簡直是上帝下凡。——弗勒裏應該知道,玻璃市的神甫雖然是個八十歲的老人,但是山區空氣新鮮,所以他的身體健康,性格堅強,他有權隨時去看看監獄、醫院,甚至貧民收容所。大清早六點鍾,阿佩爾先生帶瞭巴黎的介紹信來找神甫。他怕這個愛打聽的小城走漏風聲,立刻就去神甫傢裏。謝朗神甫讀瞭德?拉莫爾侯爵給他的信,沉吟瞭一下,因為侯爵是法蘭西貴族院的議員,也是本省最有錢的大地主。“我老瞭,在這裏還受到愛戴,”他到底低聲地自言自語說,“諒他們也不敢!”於是他立刻轉過身來,對著這位巴黎來的先生,老眼裏閃射齣聖潔的光芒,說明他為瞭做好事,冒點危險也是樂意的。“跟我來吧,先生,但在監獄看守麵前,尤其是當著貧民收容所管理人的麵,不管我們看到什麼,都請不要發錶意見。”阿佩爾先生明白:和他打交道的是一個好心人;他就跟著這位可敬的神甫,參觀瞭監獄、醫院、收容所,提瞭許多問題,雖然迴答無奇不有,但他一點也沒有流露齣責備的意思。他們參觀瞭好幾個小時。神甫請阿佩爾先生共進午餐,他推托說有信要寫;其實,他是想盡量少連纍他的帶路人。下午三點鍾前,這兩位先生參觀完瞭貧民收容所,然後迴到監獄。他們在門口見到瞭看守,一個身高六尺、兩腿內拱的大漢子,他的臉孔本來就難看,由於怕受上級嗬責,變得更加叫人厭惡。“啊!先生,”他一看見神甫就問,“這一位和您同來的,是不是阿佩爾先生?”“是不是有什麼關係?”神甫反問道。“因為我們昨天得到省長大人派專人快馬、連夜送來的緊急命令,明確指示我們,不許阿佩爾先生進監獄。”“你聽我說,努瓦魯先生,”神甫說,“同我來參觀的,正是阿佩爾先生。難道你不知道:我有權隨時進監獄來,不管白天黑夜,願同誰來都行?”“是,神甫先生。”看守輕聲答道,他低下瞭頭,就像一條怕挨打的哈巴狗,“不過,神甫先生,我有老婆孩子,要是有人告發,就會撤我的職,打碎我的飯碗。”“也會打碎我的飯碗,我也會難過的。”好心的神甫說,聲音越來越帶感情。“那可不同!”看守趕快接著說,“您麼,神甫先生,誰不曉得:您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入,還有上好的不動産……”就是這樣一件事,經過添油加醋,傳來傳去,兩天以來,在玻璃市這座小城裏,引起瞭各種各樣的惡意議論。此時此刻,它也成瞭德?雷納先生和夫人之間的話題。那天早上,市長在貧民收容所所長瓦爾諾先生的陪同下,來到神甫傢裏,對他錶示強烈的不滿。謝朗先生沒有後颱撐腰;他感到瞭這番話的壓力。“那好,兩位先生!我八十歲瞭,讓本地的教民看到我做第三個被撤職的神甫,也不要緊。我來這裏已經五十六年,來的時候,這還是個小鎮,鎮上的居民差不多都是我行的洗禮。我天天為年輕人主持婚禮,以前為祖父,現在為孫子。玻璃市就是我的傢,我捨不得離開,但也不能昧著良心做事呀!我一見這個外地人,心裏就想:這個巴黎來的人可能真是一個自由派,不過現在自由派多的是;他們對我們的窮人和犯人,又會有什麼害處呢?”這時,德?雷納先生,尤其是貧民收容所所長瓦爾諾先生的指責,越來越厲害瞭。“那好,兩位先生!要他們撤我的職吧!”老神甫聲音顫抖,叫瞭起來,“不過,我還要住在這裏。大傢知道,四十八年前我就在這裏繼承瞭地産,一年有八百法郎的收入;這筆錢夠我過日子。我並沒有濫用職權謀取私利,兩位先生,所以我不怕人傢要撤我的職。”德?雷納先生和他的夫人日子過得非常和睦;但當她三番兩次、畏畏縮縮地問道:“這個巴黎來的先生對犯人有什麼害處呢?”他不知道如何迴答是好,正要發脾氣瞭,忽然聽見她叫瞭一聲。原來是她的第二個兒子剛剛爬到靠平颱的防護牆上,跑起來瞭,不怕牆頭離牆外的葡萄園有二十尺高呢。德?雷納夫人唯恐會把她的兒子嚇得掉到牆外去,一句話也不敢說。倒是自以為瞭不起的兒子,看見母親臉色慘白,就跳下牆朝她跑來,他好好挨瞭一頓罵。這件小事轉移瞭他們的話題。“我一定要把鋸木廠老闆的兒子索雷爾叫到傢裏來,”德?雷納先生說,“他可以替我們照管孩子,孩子們已經開始搗亂瞭。索雷爾差不多可以算是一個年輕的教士,拉丁文學得好,他會教得孩子們有長進的;因為聽神甫說,他的性格堅強。我打算給他三百法郎,還管夥食,我本來懷疑他的品性;因為他是那個得過榮譽勛章的老外科軍醫的得意門生,軍醫藉口是索雷爾的親戚,就在他們傢吃住。這個人實際上很可能是自由黨的奸細;他說我們山區的空氣新鮮,可以治他的哮喘病,但是沒有證據。他參加過波拿巴遠徵意大利的戰役,據說他當時還簽名反對過建立帝國。這個自由黨人教索雷爾的兒子學拉丁文,並且把他帶來的大批圖書都送給他瞭。因此,我本來不會想到叫木匠的兒子來教我們的孩子;但是恰巧就在我和神甫徹底鬧翻的前一天,神甫告訴我,小索雷爾已經學瞭三年神學,還打算進修道院;這樣說來,他就不是自由黨人,而是學拉丁文的學生瞭。“這樣安排還有一個好處,”德?雷納先生帶著一副會辦外交的神氣,瞧著他的夫人,接著往下說,“瓦爾諾傢剛為敞篷馬車買瞭兩匹諾曼底駿馬,得意揚揚。但是他的孩子總請不到傢庭教師吧。”“他會不會把我們這一個搶走?”“這樣說來,你贊成我這個主意咯?”德?雷納先生說時微微一笑,錶示感謝他妻子對他的支持,“行,那就一言為定瞭。”“啊!天啦!我親愛的朋友,你怎麼決定得這樣快!”“這是因為我的個性很強,神甫已經領教過瞭。不瞞你說,我們周圍都是自由派。所有的布商都妒忌我,我敢肯定;有兩三個已經發瞭財;那好,我要他們開開眼界,看看德?雷納先生傢的孩子,怎樣跟著傢庭教師散步的。這多神氣!我的祖父時常對我們講,他小時候也有傢庭教師。這可能要我多破費個百八金幣,不過,沒有這筆開銷,怎麼維持我們的身份呢?”這個突如其來的決定引起瞭德?雷納夫人的深思。她個子高,長得好,山區的人都說:她是本地的美人。她顯得很單純,動作還像少女;在一個巴黎人看來,這種天真活潑的自然風韻,甚至會使男人想入非非,引起情欲衝動。要是德?雷納夫人知道自己有這種魅力,她會羞得抬不起頭來。她的心裏從來沒有起過賣弄風情、舞姿弄騷的邪念。據說有錢的收容所所長瓦爾諾先生曾經追求過她,但是徒勞無功,這更使她的貞潔發齣瞭異樣的光輝;因為這個瓦爾諾先生是個高大的年輕人,身強力壯,滿臉紅光,頰髯又粗又黑,是那種粗魯、放肆、吵吵鬧鬧,外省所謂的美男子。德?雷納夫人非常靦腆,錶麵上看起來,性格不夠穩定,她特彆討厭瓦爾諾先生不停的動作,哇啦哇啦的聲音。她不像玻璃市一般人那樣尋歡作樂,人傢就說她太高傲,不屑和普通人來往。她卻滿不在乎,拜訪她的男人越來越少,她反倒心滿意足。不瞞你說,她在全城的女人眼裏,成瞭一個傻子,因為她不會對丈夫耍手腕,放過瞭好多機會,沒有從巴黎或貝藏鬆買些漂亮的帽子迴來。隻要讓她一個人在她美麗的花園裏散散步,她就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她的心地單純,從來不敢對丈夫妄加評論,也不敢承認他令人厭煩。她雖然口裏不說,心裏卻認為:夫妻關係本來就是淡如水的。她特彆喜歡德?雷納先生,是在他談到孩子們前途的時候:他要老大做武官,老二做文官,老三做神甫。總而言之,她覺得在她認識的男人當中,德?雷納先生還是最不討厭的一個。妻子對丈夫的評價不是沒有道理的。玻璃市市長附庸風雅的名聲和派頭,都得益於他叔叔的半打笑話。他叔叔德?雷納老上尉,革命前在奧爾良公爵的步兵團服過役,去巴黎時進過公爵的“沙龍”。他在那裏見過德?濛特鬆夫人,齣名的德?讓利夫人,改建王宮的迪剋雷先生。因此,這些人物一再齣現在德?雷納先生講來講去的逸聞趣事中。漸漸地,這些妙事的迴憶對他成瞭傢常便飯,後來,他隻在重大的場閤,纔肯重新講奧爾良傢族的趣聞。此外,隻要不談到錢財的事,他總是禮貌周到的,因此,他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玻璃市最有貴族派頭的人物。……
前言/序言
譯者前言《紅與黑》是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中第一部批判現實主義傑作。高爾基說過:《紅與黑》的主角於連是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中一係列反叛資本主義社會的英雄人物的“始祖”。《紅與黑》中譯本至少已有四種:第一種是1944年重慶作傢書屋齣版的趙瑞蕻譯本;第二種是1954年上海平明齣版社羅玉君的譯本;第三種是1988年北京人民文學齣版社聞傢駟的譯本;第四種是1989年上海譯文齣版社郝運的譯本。就我所知,江蘇譯林、浙江文藝、廣東花城還要齣版新譯,加上這本,共有八種,真是我國譯本最多的世界文學名著之一瞭。我在《世界文學》1990年1期第277頁上說過:“文學翻譯的最高目標是成為翻譯文學,也就是說,翻譯作品本身要是文學作品。”那麼,《紅與黑》的幾種譯本是不是文學作品呢?第一種譯本我沒有見到。現在將第二、三、四種譯本第一章第三段中的一句抄錄於後:②這種工作(把碎鐵打成釘),錶麵顯得粗笨,卻是使第一次來到法蘭西和瑞士交界的山裏的旅客最感到驚奇的一種工業呢。③這種操作看起來極其粗笨,卻是使初次來到法蘭西和瑞士毗連山區的旅客最感到驚奇的一種工業。④這種勞動看上去如此艱苦,卻是頭一次深入到把法國和瑞士分開的這一帶山區裏來的旅行者最感到驚奇的勞動之一。比較一下三種譯文,把碎鐵打成釘說成是“工作”,顯得正式;說成是“操作”,更加具體;說成是“勞動”,更加一般。哪種譯文好一些呢?那要看上下文。下文如用“粗笨”,和“工作”“操作”都不好搭配,仿佛是在責備工人粗手笨腳似的;如把“勞動”改成“粗活”,那就麵麵俱到瞭;但把“粗活”說成是“工業”,又未免小題大做,不如“手工業”名副其實。三種譯文隻有一個地方基本一緻,那就是:“旅客(旅行者)最感到驚奇的”幾個字。仔細分析一下,“旅客”指過路的客人,“旅行者”更強調旅遊,那就不如“遊客”更常用瞭。“驚奇”指奇怪得令人大吃一驚:把碎鐵打成釘恐怕不會奇怪到那種地步,所以不如說是“大驚小怪”,以免言過其實,不符閤原作的風格。以上說的是選詞問題。至於句法,法國作傢福樓拜說過:一句中連用三個“的”(de)字,就不是好句子。四種譯文都一連用瞭三個“的”字,第三種譯文雖然隻用兩個,但是讀起來也不像一個作傢寫齣來的句子。因此,無論是從詞法或是從句法觀點來看,三種譯文都不能說是達到瞭翻譯文學的水平,也就是說,譯文本身不能算是文學作品,所以需要重譯。試讀本書譯文:⑤這種粗活看來非常艱苦,頭一迴從瑞士翻山越嶺到法國來的遊客,見瞭不免大驚小怪。我在《世界文學》1990年1期第285頁上說過:“翻譯是兩種語言的競賽,文學翻譯更是兩種文化的競賽。譯作和原作都可以比作繪畫,所以譯作不能隻臨摹原作,還要臨摹原作所臨摹的模特。”比較一下以上四種譯文,可以說第二至四種都在“臨摹原作”,而第五種卻是“臨摹原作所臨摹的模特”;換句話說,前幾種是“譯詞”,後一種是“譯意”;前者更重“形似”,後者更重“意似”,甚至不妨說是“得意忘形”。例如第四種譯文用瞭“深入”二字,這和原文“形似”“意似”;第二、三種譯文用瞭“來到”,後麵還說是“旅客”,意思離原文就遠瞭,強調的是過路的客人,沒有“深入”的意思;第五種譯文也用瞭“到”“來”二字,不能算是“形似”;但把“旅客”改成“遊客”,強調的就不是“過路”,而是“旅遊”,“旅遊”當然比“過路”更“深入”,這就可以算是“捨形取義”“得意忘形”的一個例子。更突齣的例子是“翻山越嶺”四字,這四個字所臨摹的不是原文的關係從句,而是原文關係從句所描繪的“模特”(場景),所以譯文可以說是脫胎換骨,藉屍還魂,青齣於藍而勝於藍,發揮瞭譯文的優勢瞭。關係從句是原文的優勢,就是法文勝過中文的地方,因為法文有、中文沒有關係代詞;四字成語卻是譯文的優勢,也就是中文勝過法文的地方,因為中文有、法文卻沒有四字成語。法國作傢描繪法瑞交界的山區,用瞭關係從句,這是發揮瞭法文的優勢;中國譯者如果亦步亦趨,把法文後置的關係從句改為前置,再加幾個“的”字,那就沒有揚長避短,反而是東施效顰,在這場描繪山景的競賽中,遠遠落後於原文瞭。如果能夠發揮中文的優勢,運用中文最好的錶達方式(包括四字成語),以少許勝人多許,用四個字錶達原文十幾個詞的內容。那就好比在百米競賽中,隻用四秒鍾就跑完瞭對手用十幾秒鍾纔跑完的路程,可以算是遙遙領先瞭。競賽不隻是個速度問題,還有高度、深度、精確度,等等。如果說“驚奇”在這裏描寫瞭人心的深處,那麼,“大驚小怪”的精確度至少是“驚奇”的一倍。從這個譯例看來,可以說文學翻譯是兩種語言文化的競賽,是一種藝術;而競賽中取勝的方法是發揮譯文優勢,或者說再創作。什麼是再創作?我想摘引香港《翻譯論集》第66頁上鬍適的話:“譯者要嚮原作者負責。作者寫的是一篇好散文,譯齣來也必須是一篇好散文;作者寫的是一首好詩,譯齣來的也一定是首好詩。……所謂好,就是要讀者讀完之後要愉快。所謂‘信’,不一定是一字一字地照譯,因為那樣譯齣來的文章,不一定好。我們要想一想,如果羅素不是英國人,而是中國人,是今天的中國人,他要寫那句話,該怎樣寫呢?”我想,如果《紅與黑》的作者司湯達不是法國人,而是今天的中國人,他用中文的寫法就是“再創作”。例如第四十四章於連想到生死問題,譯文如下:④……因此死、生、永恒,對器官大到足以理解它們者是很簡單的……一隻蜉蝣在夏季長長的白晝裏,早晨九點鍾齣生,晚上五點鍾死亡,它怎麼能理解“黑夜”這個詞的意思呢?讓它多活上五個小時,它就能看見黑夜,並且理解是什麼意思瞭。對照一下原文,可以看齣譯文基本上是“一字一字地照譯”的。但假如司湯達是中國人,他會說齣“器官大到足以理解它們者”這樣的話來麼?如果不會,那就不是再創作瞭。因為法文可以用代詞來代替生、死、永恒等抽象名詞,中文如用“它們”來代,讀者就不容易理解;代詞是法文對中文的優勢,譯者不能亦步亦趨,而要發揮中文的優勢,進行創作。後兩段譯文問題不大,但兩段最後都是“意思”二字,讀來顯得重復,不是好的譯文,還可加工如下:⑤……就是這樣,死亡、生存、永恒,對人是非常簡單的事,但對感官太小的動物卻難以理解……一隻蜉蝣在夏天早上九點鍾纔齣生,下午五點就死瞭;它怎麼能知道黑夜是什麼呢?讓它多活五個小時,它就能看到,也能知道什麼是黑夜瞭。錢锺書在《林紓的翻譯》中說:“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齣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於‘化境’。”在我看來,再創作就應該入於“化境”。仔細分析一下,“化”又可以分為三種:深化、等化、淺化。第四種譯文“理解它們者”顯得“生硬牽強”;第五種譯文把“它們”刪瞭,用的是減詞法,也可以算是“淺化法”;把“者”字一分為二,分譯成“人”和“動物”,用的是加詞法或分譯法,也可以算是“深化法”;第一例的“粗活”一詞,是把原文分開的“粗”和“活”閤二為一,可算是閤譯法或“等化法”;第四種譯文說“器官大到足以理解它們者”,是從正麵說;第五種譯文說“感官太小的動物卻難以理解”,是從反麵來說,把“大”換成“小”,把“理解”改成“難以理解”,負負得正,大得足以理解,就是小得不足以理解,這是正詞反譯法,也可以算是“等化法”。總之,加詞、減詞,分譯、閤譯,正說、反說,深化、等化、淺化,都是譯者的再創作,都可以進入“化境”。但“化”是不是“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呢?我們來看《紅與黑》最後一章於連的遺言:④我很喜歡在俯視維裏埃爾的高山上的那個山洞裏安息——既然安息這個詞用來很恰當。我曾經跟你講過,我在黑夜裏躲進那個山洞,我的目光遠遠地投嚮法蘭西的那些最富饒的省份,野心燃燒著我的心;那時候這就是我的熱情……總之,那個山洞對我來說是寶貴的,沒有人能否認,它的位置連一個哲學傢的靈魂都會羨慕……這段譯文沒有“露齣生硬牽強的痕跡”,不能算是沒有“化”的譯文吧。但還要更上一層樓,我們不妨讀讀本書的譯文。⑤我喜歡長眠,既然人總是用“長眠”這個字眼,那就讓我在高山頂上那個小山洞裏長眠,好從高處遙望玻璃市吧。我對你講過,多少個夜晚我藏在這個山洞裏,我的眼睛遠望著法蘭西的錦綉河山,雄心壯誌在我胸中燃燒;那時,我的熱情奔放……總而言之,那個山洞是我鍾情的地方,它居高臨下,哪個哲學傢的靈魂不想在那裏高枕無憂地安息呢?……比較一下兩種譯文,不難看齣“安息”這個字眼,既可用於生者,又可用於死者,不如“長眠”用得恰當;而“靈魂”“安息”,卻隻能用於死者,又不能說“靈魂長眠”瞭。“俯視”二字是書麵語,不如“居高臨下”更口語化。“富饒的省份”像是地理教科書中的術語,不如“錦綉河山”更像文學的語言。“野心”含有貶義,這裏於連是在迴顧,而不是在作自我批評,所以不如說“雄心壯誌”。後麵的“熱情”也不明確,不如“熱情奔放”。“寶貴的”更重客觀;“鍾情的”更重主觀。“它的位置”又像地理術語,不如“居高臨下”移後為妙。“羨慕”自然譯得不錯;但“高枕無憂”說齣瞭羨慕的原因,似乎更深一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就是中西文化的競賽,用中國語文來描繪於連的心理,看看能否描寫得比法文更深刻,更精確。總之,這就是再創作。兩種譯文都不能說沒有“化”,但第五種譯文還發揮瞭中文的優勢。如果認為第五種譯文優於第四種,那就是說,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還有所不足,還要發揮譯文優勢。如果我的說法不錯,那我就要打破一條幾乎是公認的規律:能直譯就直譯,不能直譯時再意譯。我的經驗卻是:文學作品的翻譯,尤其是全譯,能意譯就意譯,不能意譯時再直譯。前幾種譯文遵照的可以說是前一條公認的規律,第五種卻是後一條未經公認的譯法,隻是我個人五十年翻譯經驗的小結。世界上的翻譯理論名目繁多,概括起來,不外乎直譯與意譯兩種。所謂直譯,就是既忠實於原文內容,又盡可能忠實於原文形式的譯文;所謂意譯,就是隻忠實於原文內容,而不拘泥於原文形式的譯文。自然,由於忠實的程度不同,所以又有程度不同的直譯,如第二例第四、五種譯文的後兩段;也有程度不同的意譯,如第三例第五種譯文意譯的程度,就高於第四種譯文。所以直譯、意譯之爭,其實是個度的問題。因為兩種語言、文化不同,不大可能有百分之百直譯的文學作品,也不大可能有百分之百意譯的文學作品,百分之百的意譯與其說是翻譯,不如說是創作;因此,文學翻譯的問題,主要是直譯或意譯到什麼程度,纔是最好的翻譯作品。比如說,第三例的譯文到底是直譯到第四種譯文,還是意譯到第五種譯文的程度更好呢?在我國翻譯史上,主張“寜信而不順”的魯迅是直譯的代錶;“重神似不重形似”的傅雷是意譯的代錶。茅盾也主張直譯,他在《直譯、順譯、歪譯》一文中說:“有些文學作品即使‘字對字’譯瞭齣來,然而未必就能恰好錶達瞭原作的精神。假使今有同一原文的兩種譯本在這裏:一種是‘字對字’,然而沒有原作的精神;另一種並非‘字對字’,可是原作的精神卻八九尚在。那麼,對於這兩種譯本,我們將怎樣批判呢?我以為是後者足可稱‘直譯’。這樣纔是‘直譯’的正解。”在我看來,茅盾說的“直譯”和魯迅的忠實程度不同,是另一種“直譯”,甚至可以說是“意譯”,至少是介乎二者之間的翻譯,這樣一說,直譯和意譯就分彆不大瞭。在國際譯壇上,奈達大概可以算個意譯派,因為他說過“為瞭保留信息內容,形式必須加以改變”(轉引自《中國翻譯》1992年6期第2頁)。紐馬剋則自稱“多少是個直譯派”,還說:“好的譯者隻有當直譯明顯失真或具有呼喚、信息功能的文章寫得太蹩腳的時候纔放棄直譯,而一個蹩腳的譯者纔常常竭盡全力避免直譯。”又說:“翻譯的再創作的成分常常被誇大,而直譯的成分卻被低估,這尤以文學作品為甚。”(同前3頁)這和我的看法是針鋒相對的。到底誰是誰非呢?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實踐,最好是論者本人的實踐,可惜這兩位英美學者都不懂中文,而中英互譯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翻譯,因為世界上有十多億人用中文,也有十多億人用英文,所以不能解決中英互譯問題的理論,實際上不能起什麼大作用。還有一個原因,中英文之間的差距遠遠大於英法等西方文字之間的差距。我曾做瞭一個獨一無二的試驗,就是把中國的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麯中的一韆多首古詩,譯成有韻的英文,再將其中的二百首唐宋詩詞譯成有韻的法文,結果發現一首中詩英譯的時間大約是英詩法譯時間的十倍,這就大緻說明瞭,中英或中法文之間的差距,大約是英法文差距的十倍,中英或中法互譯,比英法互譯大約要難十倍,因此,能夠解決英法互譯問題的理論,恐怕隻能解決中英或中法互譯問題的十分之一。由於世界上還沒有齣版過一本外國人把外文譯成中文的文學作品,因此,解決世界上最難的翻譯問題,就隻能落在中國譯者身上瞭。20世紀末,劉重德提齣瞭“信、達、切”的翻譯原則,他說信是“信於內容”,達是“達如其分”,切是“切閤風格”。從理論上說,“切”字沒有提齣來的必要,因為“切”已經包含在“信”和“達”之中。試問有沒有“信於內容”而又“達如其分”的譯文,卻不“切閤風格”的?從實踐上說,《紅與黑》的幾種譯文,哪種更符閤“信、達、切”的標準呢?恐怕前幾種都比第五種更“切”吧,但更“切”是不是更好呢?什麼是“好”,前麵鬍適講瞭:“好,就是要讀者讀完之後要愉快”,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要使讀者“知之”“好之”“樂之”。《紅與黑》的幾種譯文之中,到底是“切閤風格”的前幾種,還是“發揮優勢”的後一種譯文,更能使讀者理智上“好之”,感情上“樂之”呢?如果是後一種,我就要提齣“信、達、優”三個字,來作為文學翻譯的標準瞭。我在《翻譯的藝術》第4頁上說過:所謂“信”,就要做到“三確”:正確、精確、明確。正確如《紅與黑》第三例的“長眠”和“安息”,都算正確;精確如第一例的“大驚小怪”,要比“驚奇”精確度高;至於明確,第二例的“人”和“動物”就遠比“理解它們者”容易理解。我在同書第5頁上還說過:所謂“達”,要求做到“三用”:通用、連用、慣用。這就是說,譯文應該是全民族目前通用的語言,用詞能和上下文“連用”,閤乎漢語的“慣用”法。換句話說,“通用”是指譯文詞匯本身,“連用”是指詞的搭配關係,“慣用”既指詞匯本身,又指詞的搭配關係。如以《紅與黑》的三個譯例來說:第二例的“理解它們者”就不是“通用”的詞匯;第一例的“工作”和“粗笨”不好“連用”,“翻山越嶺”卻閤乎漢語的“慣用”法。最後,剛纔已經說瞭,所謂“優”,就是發揮譯語優勢,也可以說是“三勢”:發揚優勢,改變劣勢,爭取均勢。這是指譯散文而言,如果譯詩,還要盡可能傳達原詩的“三美”:意美、音美、形美。簡單說來,“信、達、優”就是“三確”“三用”“三勢”(或“三美”)。這種簡單的翻譯理論,可能有人認為不夠科學。我卻認為文學翻譯理論並不是科學,而是藝術,和創作理論、音樂原理一樣是藝術。我在北京大學《英漢與漢英翻譯教程》第1頁上說過:“科學研究的是‘真’,藝術研究的是‘美’。科學研究的是‘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的規律;藝術研究的卻包括‘有之不必然,無之不必不然’的理論。如果可以用數學公式來錶示的話,科學研究的是1+1=2,3-2=1;藝術研究的卻是1+1》2,3-2》1。因為文學翻譯不單是譯詞,還要譯意;不但要譯意,還要譯味。隻譯詞而沒有譯意,那隻是‘形似’:1+1《21=""1="2;如果不但是譯齣瞭言內之意,還譯齣瞭言外之味,那就是‘神似’:1+1"》2。”根據這個理論去檢查《紅與黑》的幾種譯文,就可以看齣哪句譯文是譯詞,哪句是譯意,哪句是譯味,對譯文的優劣高下,也就不難做齣判斷瞭。如果《紅與黑》的八種中譯本齣齊後,再做一次更全麵的比較研究,我看那可以算是一篇文學翻譯博士論文。如果把世界文學名著的優秀譯文編成一本詞典,那對提高文學翻譯水平所起的作用,可能比西文語言學傢的翻譯理論要大得多。總而言之,我認為文學翻譯是藝術,是兩種語言文化之間的競賽,這是我對文學翻譯的“認識論”。在競賽中要發揮優勢,改變劣勢,爭取均勢;發揮優勢可以用“深化法”,改變劣勢可以用“淺化法”,爭取均勢可以用“等化法”,這“三化”是我再創作的“方法論”。“淺化”的目的是使人“知之”,“等化”的目的是使人“好之”,“深化”的目的是使人“樂之”,這“三之”是我翻譯哲學中的“目的論”。一言以蔽之,我提齣的翻譯哲學就是“化之藝術”四個字。如果譯詩,還要加上意美、音美、形美中的“美”字,所以我的翻譯詩學是“美化之藝術”。我國著名的科學傢楊振寜說過:“中國的文化是嚮模糊、朦朧及總體的方嚮走,而西方的文化則是嚮準確而具體的方嚮走。”在我看來,中國傳統的翻譯理論也是走嚮總體,更重宏觀;西方的翻譯理論卻是走嚮具體,更重微觀。楊振寜又說:“中文的錶達方式不夠準確這一點,假如在寫法律是一個缺點的話,寫詩卻是一個優點。”(均見香港《楊振寜訪談錄》第83頁)我卻覺得,中文翻譯科學作品,如果說不如英法等西方文字準確的話,翻譯文學作品,提齣文學翻譯理論,卻是可以勝過西方文字的。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實踐,檢驗翻譯理論的標準是齣好的翻譯作品。希望《紅與黑》新譯本的齣版,新序言的發錶,能夠為中國翻譯走上二十一世紀的國際譯壇,添上一磚一瓦。試看明日之譯壇,竟是誰傢之天下!許淵衝1992年12月8日
北京大學暢春園舞山樓
用户评价
我特彆喜歡作者在處理情感綫索時的那種微妙和剋製。書中的愛情糾葛,絕非那種直來直去的浪漫敘事,它被牢牢地嵌入到社會背景和個人抱負的巨大壓力之下。情感的流露總是被現實的考量所扭麯、所異化。角色們似乎總是在衡量,愛一個人能帶來什麼,或者會失去什麼,這種“功利性”的考量貫穿始終,讓人既心痛又不得不理解。每一次情感的爆發點,都像是壓力鍋終於達到瞭臨界點,不是以狂喜告終,而是以更深的痛苦和更殘酷的現實收場。這種將激情與理智、欲望與道德捆綁在一起的寫法,使得整個故事充滿瞭宿命般的悲劇張力。讀完後,那種關於愛與生存的取捨,那種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搖擺的掙紮,長時間地盤桓在我的腦海中,讓人久久無法釋懷。
评分我花瞭很長時間纔從那股濃厚的時代氣息中抽離齣來。這部作品的敘事節奏處理得相當高明,它不是那種一味追求情節跌宕起伏的小說,更多的是一種細密入微的生活流描摹,但其中暗流湧動,張力十足。特彆是對於那些次要人物的塑造,絕非草草帶過,每個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內在的邏輯,即便是那些曇花一現的角色,也像被精心打磨過的寶石,摺射齣那個社會的不同側麵。我尤其欣賞作者那種近乎冷靜的客觀敘事風格,他似乎站在一個高處俯瞰著所有人的悲喜,不作直接的評判,而是將所有的道德睏境和人性掙紮原封不動地拋給讀者去消化。這使得整部小說在情感錶達上達到瞭剋製的美感,但正是這種剋製,反而將人物內心的波濤洶湧襯托得更加震撼。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像剛完成瞭一次漫長而艱苦的社會考察,對人性的復雜性有瞭更深一層的理解,那種細膩的筆觸和深刻的洞察力,是當下很多作品所欠缺的。
评分這本書簡直像一劑猛藥,初讀時,那種撲麵而來的壓抑感幾乎讓人喘不過氣。故事的背景設定在那個波譎雲詭的年代,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鴻溝,以及隨之而來的那種階級固化帶來的無力感,被作者描繪得淋灕盡緻。我特彆佩服作者對人物心理的刻畫,那種深藏於心底的不甘、對嚮上攀爬的渴望,以及在實現目標過程中不得不戴上的各種麵具,展現得極為立體。主人公的每一步選擇都像是走在刀尖上,每一步都充滿瞭算計和風險,讀者仿佛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內心的煎熬與掙紮。你看著他如何巧妙地周鏇於不同勢力之間,如何利用自己的聰明纔智去適應那個苛刻的環境,既替他捏一把汗,又不得不承認他的機敏。然而,這種基於現實的殘酷描寫,也讓人在閤上書本後,久久不能平復,它迫使我們去思考,在強大的社會結構麵前,個體的命運究竟能有多少自主權。那種宿命般的悲劇色彩,縈繞不散,讀完後,會留下漫長的迴味與反思。
评分說實話,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具有挑戰性的,它要求讀者有相當的耐心去跟進那些大量的社會細節和錯綜復雜的人際關係。對我而言,最大的樂趣在於解析那些隱藏在字裏行間的“潛颱詞”。角色們之間的話語交鋒,往往是錶麵一套,背後一套,每一次對話都像是一場精密的博弈。我常常需要停下來,反復揣摩某個眼神、某個手勢或者某句看似無心的話語背後到底蘊含著怎樣的深意和圖謀。這種閱讀過程,與其說是休閑,不如說是一種智力上的角力。作者構建的世界觀是如此真實可信,以至於我一度忘記瞭自己是在閱讀虛構的故事,仿佛真的置身於那個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之中,為角色的每一步試探感到緊張。這種強烈的沉浸感,來自於作者對細節的偏執般的關注,使得一切看起來都如此井然有序,又隨時可能因為一個微小的失誤而徹底崩塌。
评分這部作品的魅力,我認為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對“野心”這一主題的深刻剖析。它探討的不是那種高尚的、為瞭理想而奮鬥的抱負,而是那種根植於底層、渴望通過一切手段獲取地位和尊重的原始衝動。主人公身上那種強烈的矛盾性——既渴望被認可,又鄙視那些用世俗標準衡量成功的人——構成瞭全書最引人入勝的部分。每一次他試圖融入上流社會,都會被那套看不見的規則所嘲弄;而他試圖保持獨立,又會因為資源和齣身而被無情地打壓。這種拉扯,讓角色的形象瞬間豐滿起來,他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英雄或反派,而是一個被時代洪流裹挾的、有著嚴重自我認知衝突的個體。這種對人性弱點和強大驅動力的並置描寫,使得小說超越瞭單純的愛情故事或社會批判,上升到瞭對人類存在狀態的哲學探討。
评分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找了好久这个译本!
评分找了好久这个译本!
评分经典就是经典
评分经典就是经典
评分找了好久这个译本!
评分物美价廉,下次还会购买
评分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书很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