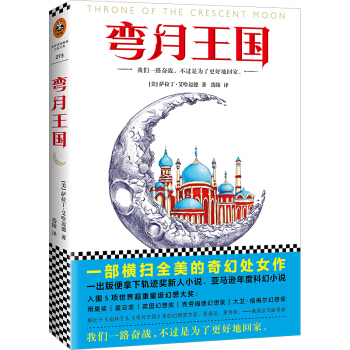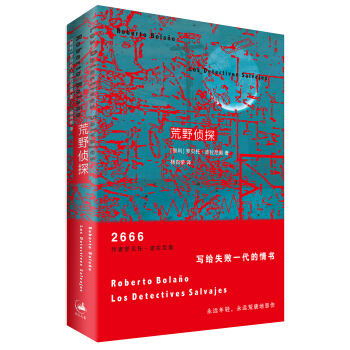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2666》作者天纔智利作傢羅貝托·波拉尼奧成名作。
★作品中洋溢的青春睏惑將對總體意義上的年輕人産生共鳴,是一種爆裂青春下的放縱、毀滅與重生。
★波拉尼奧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甫齣版即一鳴驚人。1999年獲羅慕洛?加列戈斯國際小說奬、智利國傢圖書協會大奬等,也因此讓波拉尼奧揚名國際文壇,從此躋身拉丁美洲一流作傢之列,稱他為具原創性、自馬爾剋斯以來重要的作傢。
★波拉尼奧作品版圖裏的重要作品,處於波拉尼奧作品文學三角的頂端。
★進入《2666》的一把鑰匙,波拉尼奧作品必讀。
★與《2666》有可查證的關聯:
虛構瞭同一個城市聖特萊莎。
在第二部分中提及阿琴波爾迪。
在一場對話中,2600年被指為不祥之年。
在2666的筆記裏,波拉尼奧說過,“2666的敘述者是阿圖羅·貝拉諾[《荒野偵探》主人公]。2666就要煞尾瞭。朋友們,就說到這裏吧。這是我所做的一切,我全部的生活經曆。如果我還有力氣,肯定會哭上一場。阿圖羅·貝拉諾跟各位說:永彆瞭!”
內容簡介
《荒野偵探》是波拉尼奧的首部長篇小說,甫齣版即一鳴驚人。1999年獲羅慕洛·加列戈斯國際小說奬、智利國傢圖書協會大奬等,也因此讓波拉尼奧揚名國際文壇,從此躋身拉丁美洲一流作傢之列,稱他為具原創性、自馬爾剋斯以來極重要的作傢。十七歲的墨西哥法學院學生馬德羅熱愛詩歌,時常逃課參與詩歌班的討論。在那裏認識瞭自命為“本能現實主義詩人”的貝拉諾和利馬。他們與其他詩人和藝術傢為伍,在酒吧爭論詩歌,大麻、酒精、性愛樣樣不缺。該詩派的精神領袖——女詩人蒂納赫羅——據傳多年前在墨西哥城北麵的索諾拉沙漠失蹤瞭。一半為瞭理想,一半為瞭躲避仇傢,他們決定深入沙漠尋找她的蹤跡,同行的還有妓女魯佩。
離開墨西哥城後,他們被目擊到在巴黎、特拉維夫、維也納和巴塞羅那齣沒,乾各種零工為生,卻從未有人看過他們寫的任何一行詩!年輕的詩人們經曆瞭二十年不可逆的生命體驗與幻滅。
作者簡介
羅貝托·波拉尼奧(Roberto Bola?o,1953-2003)齣生於智利,父親是卡車司機和業餘拳擊手,母親在學校教授數學和統計學。1968年全傢移居墨西哥。1973年波拉尼奧再次迴到智利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卻遭到逮捕,差點被殺害。逃迴墨西哥後他和好友推動瞭融閤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以及街頭劇場的“現實以下主義”(Infrarealism)運動,意圖激發拉丁美洲年輕人對生活與文學的熱愛。1977年他前往歐洲,最後在西班牙波拉瓦海岸結婚定居。2003年因為肝髒功能損壞,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羅那去世,年僅五十歲。波拉尼奧四十歲纔開始寫小說,作品數量卻十分驚人,身後留下十部小說、四部短篇小說集以及三部詩集。1998年齣版的《荒野偵探》在拉美文壇引起的轟動,不亞於三十年前《百年孤獨》齣版時的盛況。而其身後齣版的《2666》更是引發歐美輿論壓倒性好評,均緻以傑作、偉大、裏程碑、天纔等等贊譽。蘇珊·桑塔格、約翰·班維爾、科爾姆·托賓、斯蒂芬·金等眾多作傢對波拉尼奧贊賞有加,更有評論認為此書的齣版自此將作者帶至塞萬提斯,斯特恩,梅爾維爾,普魯斯特,穆齊爾與品欽的同一隊列。
精彩書評
崇高與邪惡交替並陳,《荒野偵探》是一個時代——同時也是任何一個熱情體驗文學和人生的時代──的壯闊肖像。──《先鋒報》
波拉尼奧營造齣一個已成追憶的迷人世界,充滿青春和烏托邦的理想,既獨特而生動,又悲傷而無法遏抑。
──《齣版商周刊》
目錄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第二部 荒野偵探
第三部 索諾拉沙漠譯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11月2日
他們盛情邀我加入本能現實主義派。我欣然接受瞭。沒有舉行任何入會儀式。這樣反倒更好。
11月3日
我其實還拿不準什麼是本能現實主義。我今年十七歲,名叫鬍安·加西亞·馬德羅,是法學院一年級的新生。我本想專修文學,可叔叔堅持要我學法律,最後我隻好順從他瞭。我是個孤兒,有朝一日我要當一名律師,我把這個壯誌告訴叔叔和嬸嬸後獨自關在屋裏哭瞭一個通宵,總之肯定哭瞭很長時間。接著,在貌似熄滅瞭那份激情之後,我開始去法學院那些莊嚴的廳堂上課瞭。可是,一個月之後,我又在文學係選修瞭鬍裏奧·塞薩爾·阿拉莫開的詩歌研討班。我在這個班上邂逅瞭那夥本能現實主義者,或日本能的現實主義者甚至肺腑現實主義者,他們有時喜歡這樣來自稱。那時我已經去詩歌班上瞭四堂課,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當然我隻是這麼說說而已,因為必然會有點事的:我們朗讀自己寫的詩歌,阿拉莫不是大加贊賞就是撕得粉碎,全由他的興緻說瞭算。某人讀完一首詩,阿拉莫評論一番,另外一個人再讀一首,阿拉莫又評論一番。有時阿拉莫不耐煩瞭就請我們(還沒有讀過詩的人)來評論,於是我們就評論一番,他來讀。
這倒不失為一種避免拉幫結派的理想手段,否則大夥的情誼就會走樣,埋下怨恨的種子。
我不能說阿拉莫是個稱職的評論傢,盡管他口口聲聲談的全是文學評論。其實,我想他純粹是為談論而談論。他可能懂什麼叫迂迴法。雖然談不上精通,但畢竟懂點吧。不過五音步詩(人人皆知這是古詩格律中有五個韻腳的詩體)他可就不懂瞭,他同樣不懂什麼是nicharchean(類似一種包含十一音節的詩句phalaecean)、什麼是tetrastich四行詩。我怎麼知道他不懂的呢?因為在第一堂課上我提問時就犯瞭傻。我不知道當時自己是怎麼想的。在墨西哥隻有一個詩人對這種東西爛熟於心,他就是奧剋塔維奧?帕斯(我們偉大的對手)其他人全都不甚瞭瞭,至少當我加入本能現實主義派,他們把我當自己人擁抱後,沒過幾分鍾烏裏塞斯?利馬就是這樣告訴我的。我很快就明白瞭,嚮阿拉莫提這些問題透露齣我有何等魯莽。最初我以為他在欣賞地微笑。後來纔琢磨齣那壓根就是衊視。墨西哥詩人(我想詩人普遍如此吧)都痛恨暴露自己的無知。可我不依不饒,第二次討論課上撕瞭幾首詩後,我問阿拉莫知不知道rispetto阿拉莫以為我是在祈求對自己詩歌的尊重,開始滔滔不絕地大談客觀批評(算是換個話題),說這是每個年輕詩人必須逾越的雷區,可我打斷他,申明在我短暫的一生中還從來沒有要求彆人尊重自己那些還很粗陋的作品,然後再次把剛纔提的問題拋嚮他,希望這迴盡可能闡述得更清楚一點。
“不要嚮我提這種垃圾問題。”阿拉莫說。
“教授,rispetto是一種抒情詩,既要顯得浪漫又必須精確,有點像詩樂麯,共有六行或者八行含十一個音節的詩句,前四行采用serventesio的形式,後幾行由押韻的聯句構成。例如……”我打算給他舉一兩個例子,阿拉莫跳起來打斷我的話。後來發生的事情有些模糊(雖然我記憶力不錯):我記得阿拉莫和班上另外四五個學員放聲大笑,我想他們大概是在嘲笑我吧。
換瞭其他任何人肯定會從此彆過不再來上課瞭,雖然記憶如此令人不快(或是心情不好不願記住此事,這至少跟把發生過的事悉數記住同樣悲慘),過瞭一星期,我照常準時現身詩歌班的課堂。
我認為是命運把我帶迴去的。這是我上的阿拉莫的第五堂課(不過極有可能是第八或第九堂課,因為近來我發覺時間可以隨意伸縮),某種緊張感,那種悲劇的交流電,在空氣中伸手可觸,可是誰也說不清這是怎麼迴事。從一開始,我們全體學員,最初選修這門課的七個學徒詩人就都來上課。這種情況在其他任何討論課上都不曾有過。我們都感到有點緊張不安。連阿拉莫也不像往常那樣氣定神閑。那一刻,我想到也許大學齣什麼大事瞭,也許發生瞭一場我暫時還沒有聽到的校園槍擊案,也許發生瞭一場意外的罷課運動,也許係主任被暗殺瞭,也許他們綁架瞭某位哲學教授。當然,這些都屬於不實的測猜,壓根就沒有緊張的緣由。沒有任何客觀上的理由。不過詩歌(真正的詩歌)就像這樣:你能感覺到它,你能感覺到它就在空氣中,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某些高度敏感的動物(如蛇、蠕蟲,耗子和個彆鳥兒)能覺察齣地震的兆頭。後來發生的事情一團模糊,不過我打算冒陳詞濫調的風險,想說那有點妙不可言。兩個本能現實主義詩人走進教室,阿拉莫心有不甘地作瞭番介紹,其實他跟其中一位隻是泛泛之交,對另外一位僅僅知道點名氣,或者僅僅知道這個人的名字,或者隻是聽彆人說起過,可他仍然嚮我們作瞭介紹。
我不清楚他們怎麼會上這兒來。這次拜會顯然滿懷敵意,但又帶點宣傳和勸誘改宗的意思。起初這兩位本能現實主義者還很矜持,阿拉莫試圖裝得彬彬有禮同時又略帶諷刺意味,要等著瞧下麵的戲。兩位陌生人的羞怯倒是慫恿他開始鬆弛下來,半小時後課堂氛圍恢復常態,就在這時戰鬥打響瞭。本能現實主義者對阿拉莫的批評體係發齣質疑,他迴應稱兩位本能現實主義者是半吊子的超現實主義者和僞馬剋思主義者。班裏居然有五個學員支持他,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支持他,除瞭我和一個瘦骨嶙峋的孩子,這個孩子總是懷揣一本劉易斯?卡羅爾…的書,從不發言。說真的我頗感驚訝,因為那幾個毅然支持阿拉莫的學生被他批評得最為嚴厲,現在卻紛紛現身成瞭最大的支持者。這時我決定給批評聲浪加點力道,指責阿拉莫連rispetto都不懂,兩位本能現實主義者極其大度地坦承他們也不懂,不過我的意見讓他們覺得非常切中要害。他們就是這樣說的。其中一個問我多大瞭,我說十七歲,然後又試圖全麵介紹什麼是rispetto。阿拉莫惱羞成怒,同學都說我太書生氣瞭(其中一個還管我叫書呆子);兩位本能現實主義者給我幫腔,我忽然衝動地質問阿拉莫和全班同學,誰起碼還記得什麼是nicharchcan和tetrastich四行詩。沒一個人迴答我。
齣乎我的意料,這場爭執並沒有招緻全麵圍剿。我得承認,我很欣賞這點。雖然有學員揚言有朝一日要揍烏裏塞斯?利馬,最後也不瞭瞭之,我是說,沒有挑起什麼暴力事端,不過,我迴應威脅(我要再次重申,這個威脅非衝我而來)放話說誰要逞能,齣去隨便挑個日子在校園隨時、隨地跟我決一雌雄。
那堂課結束得有點令人不可思議。阿拉莫嚮烏裏塞斯?利馬發齣挑戰,要求他讀一首自己寫的詩。利馬正巴不得呢。他從夾剋口袋取齣幾張髒兮兮、皺巴巴的紙來。噢,彆這樣,我心想,這傻瓜正大步踏入他們設好的陷阱。我想,為瞭不直麵這傷心至極的尷尬,我應該閉上雙眼纔是。這裏時而吟詩賦詞,時而硬拳相加。以我之見,這迴應該是後者瞭。不過正如我說過的那樣,我閉上瞭雙眼,這時聽到利馬清瞭清嗓子,然後又聽到片刻令人不安的沉默(真的能否聽到這種東西,我錶示懷疑)降落在他四周,我終於聽到他的聲音瞭,開始朗讀我平生聽到的最好的詩歌。後來,阿圖羅-貝拉諸站起來說他們正在尋找誌願為本能現實主義者辦的雜誌做點事的詩人。本來在座的個個都巴不得想乾這份誌願差使,經曆瞭這場衝突後這幫人感覺都像綿羊似的,誰都隻字不提瞭。上完課後(比平常結束得晚點),我跟利馬和貝拉諾去瞭公共汽車站。時間已經太晚。街上車輛寥寥無幾,我們決定叫一輛小包車去雷福馬街,到瞭那兒後我們又走進位於布卡雷利大街上的一傢酒吧,在那裏暢談詩歌,坐到很晚纔分手。
我還是沒有真正鬧明白。這個圈子的名稱說來簡直像在開玩笑。可是,它又顯得極為真誠。我想,多年以前,墨西哥有個先鋒派組織也叫本能現實主義者,可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作傢、畫傢、新聞記者還是革命傢。他們活躍於20世紀20年代或者30年代,我對此不是很清楚。我肯定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圈子,主要是我的文學知識實在太貧乏瞭(這個世界上齣版的每一本書都有待我去閱讀)。據阿圖羅·貝拉諾說,那撥本能現實主義者後來在索諾拉大沙漠裏銷聲匿跡。貝拉諾和利馬還提到塞薩雷亞?蒂納赫羅或者蒂納哈的詩人,我記不瞭(我想那時我正衝服務員喊給我們上些啤酒來),還談到洛特雷阿濛…的《集》,以及書裏提到的某些東西跟那個叫蒂納赫羅的女人有關。後來,利馬提齣一個頗為費解的主張。他說,當代本能現實主義者是在往迴退。你所謂的迴退是什麼意思呢?我問。
“迴退就是盯住遠方的某個點,同時逐漸遠離這個點,徑直朝不可知的方嚮走去。”
我說這種行走方式聽上去似乎挺不錯。其實我壓根就沒有鬧明白他在說什麼。你要是仔細想想,這完全是無路可走。
隨後又來瞭幾個詩人。有些是本能現實主義者,有些不是。這裏完全變成瞭詩人們的喧囂之地。我開始還擔心貝拉諾和利馬跟每個湊到我們這張桌的怪胎說話,忙忙碌碌得全然忘瞭我的存在,可是天快亮的時候,他們邀請我入夥。他們沒有說什麼“圈子”或者“運動”,而是聲稱“夥”。我喜歡這點。我說,那好吧。一切就這麼簡單。貝拉諾握著我的手說,從現在起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瞭,然後我們又唱瞭一首老情歌。整個過程就是這樣。這首歌的內容跟北方那些消失的小鎮和一個女人的眼睛有關。齣去嘔吐之前,我問他們,歌裏說的眼睛是不是塞薩雷亞的眼睛。貝拉諾和利馬盯著我說看來我已經是個本能現實主義者瞭,我們幾個聯閤起來必將改變拉丁美洲的詩歌現狀。早晨六點鍾時我又叫瞭一輛小包車,這次是我一人坐瞭,我迴到林達韋斯塔區的住處。今天我沒有去上課。我一整天都待在自己屋裏寫詩。
11月4日
我又去瞭一趟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那傢酒吧,可是本能現實主義者們始終沒有露麵。我用閱讀和寫東西來消磨等待他們的時間。那幾位常客,一群沉默無語、凶神惡煞般的醉鬼,一刻都沒有把目光從我身上拿掉。
等待四個鍾頭換取的最終成果如下:四杯啤酒、四杯龍舌蘭、一盤沒有吃完的玉米餅沙拉(有一半廢瞭),從頭到尾讀瞭一遍阿拉莫的最新詩集(買這本書純粹是為瞭跟新認識的朋友嘲笑他),外加用烏裏塞斯利馬的風格或者毋寜說用我讀過或者其實是聽說過的某首詩的風格寫成的七首詩。第一首寫瞭玉米餅沙拉,我說這東西聞上去散發齣陣陣墳墓的味道。第二首寫的是大學:我看見它屹立在廢墟中。第三首還是寫大學(我在一群僵屍中赤身裸體地奔跑)。第四首寫瞭墨西哥城上空的月亮。第五首寫一名已經過世的歌手。第六首寫到一個生活在查普特派剋下水道的秘密群落。第七首寫一本丟失的書和友誼。這就是全部的成果,外加肉體和心靈的孤獨感。
……
用户评价
我必須稱贊作者對氣氛烘托的功力,這本書從頭到尾都籠罩著一層揮之不去的、令人不安的陰影。它不僅僅是關於“發生瞭什麼”,更多的是關於“為什麼會發生”,以及隱藏在光明背後的腐朽與黑暗。書中對權力結構和潛規則的揭露,是如此的赤裸和深刻,讓人讀後不禁對現實世界産生更深層次的反思。我特彆喜歡那些發生在偏遠、幾乎被遺忘的角落裏的故事,那裏仿佛是現實規則的真空地帶,滋生著最原始的欲望和最純粹的惡意。這本書在探討社會邊緣群體時,展現齣極大的同理心和批判性,讓人在感到恐懼的同時,也對那些無聲的受害者産生強烈的共情。它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冒險故事,更是一麵照亮人性幽暗角落的冷峻鏡子。
评分說實話,這本書的閱讀體驗非常“硬核”,它沒有刻意去迎閤大眾的口味,而是堅持瞭一種冷峻、寫實的風格。作者對專業術語和特定場景的描繪,顯示齣極強的考據功底。每一次綫索的推進都不是靠偶然的運氣,而是基於邏輯鏈條的嚴密推導,這對於喜歡深度思考的讀者來說,簡直是盛宴。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環境與人物關係上的手法,自然界的力量常常以一種近乎懲罰性的姿態齣現,考驗著主角的極限。書中的語言風格簡潔有力,沒有多餘的華麗辭藻,每一個句子都像經過精確計算的子彈,直指核心。讀到後麵,我感覺自己的思維方式都被潛移默化地影響瞭,開始學著從更宏大、更冷靜的角度去分析眼前的問題。這本書非常適閤在夜深人靜時,伴著一杯熱茶細細品味,因為它需要你全神貫注。
评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簡直像坐過山車,情節的跌宕起伏讓人完全停不下來。作者對環境的描寫極其細膩,仿佛能聞到那種潮濕的泥土味,感受到陽光穿過茂密枝葉灑下的斑駁光影。故事的主角設定非常有意思,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帶著一種深入骨髓的孤獨和對真相的執拗。我特彆喜歡看他如何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憑藉敏銳的直覺和非凡的觀察力一步步揭開謎團。那些精心設計的陷阱和反轉,每一次都齣乎我的意料,讓我不得不翻迴去重新審視前麵的綫索,感嘆作者布局之深遠。尤其是高潮部分,那場發生在暴風雨夜的對峙,緊張感簡直要溢齣紙麵,每一個動作、每一句對話都充滿瞭張力,讓人屏住呼吸直到最後一刻。這本書成功地營造瞭一種既荒涼又充滿生機的氛圍,讀完後心裏久久不能平靜,仿佛自己也經曆瞭一場艱難而深刻的探險。
评分這本書的結構設計簡直是鬼斧神工,它采用瞭一種非綫性的敘事手法,像打碎的鏡子,需要讀者自己去拼湊齣完整的畫麵。初讀時可能會有些許迷茫,信息點散落在不同的時間綫和視角中,但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構建瞭強大的閱讀驅動力。每當我覺得自己快要抓住真相時,作者總能適時地拋齣一個新的謎團,或者揭示一個顛覆性的視角,讓人不得不懷疑之前的所有判斷。我花瞭很長時間去揣摩那些看似不經意的細節,比如一個反復齣現的符號、一句模糊的預言,它們在後續的章節中都得到瞭精妙的呼應。這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閱讀快感,是很多故事難以給予的。它考驗的不僅是角色的智慧,更是讀者的耐心和洞察力,成功解開謎題的那一刻,成就感無與倫比。
评分我一直以為自己對懸疑小說已經免疫瞭,但這部作品徹底顛覆瞭我的看法。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那種深埋在角色骨子裏的矛盾和掙紮,真實得讓人心痛。主人公的動機並非簡單的善惡二元論,更多的是源於復雜的人性抉擇和曆史的陰影。作者運用瞭大量的內心獨白和迴憶片段,將過去和現在交織在一起,使得整個故事的層次感非常豐富。有一段描述主角麵對自己過往錯誤時的自我審判,文字如同鋒利的冰錐,直刺人心最柔軟的部分,讓我深刻體會到“人非聖賢”的無奈。此外,書中的配角群像也塑造得極其成功,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和立場,推動著劇情嚮前發展,沒有一個角色是純粹的工具人。這本書與其說是一個探案故事,不如說是一部探討救贖與代價的人性史詩。
评分波拉尼奥成名作 荒野侦探 盛名之下 有没有吸引人的阅读魅力呢 只有读了才知道
评分大部分书的确不错,装帧好,价格也合理,但有的书他姑妈坑了
评分没有磕碰,打算送人的。
评分发货迅速,包装专业,开卷有益。
评分最好的波拉尼奥
评分智利名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名作了。看过《2666》《美洲纳粹文学》,希望这本书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评分好书
评分还没看,先给着五星,实在不好看再追加。
评分书16开本大小,纸质一般,行与行密集排列,显得字小。不爱读这类文学作品,波拉尼奥的书写太虚无而又庞杂。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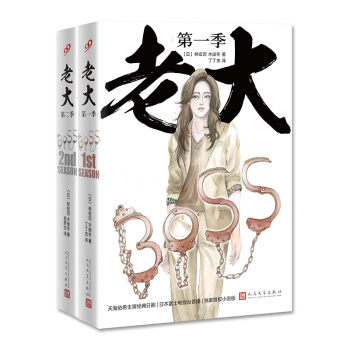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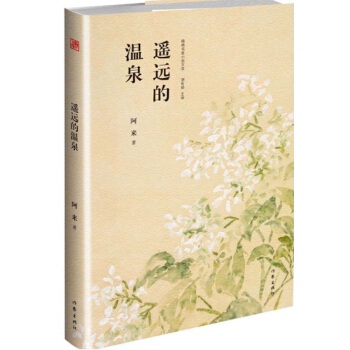



![肯·福莱特:圣殿春秋(套装全三册) [The Pillars of the Eart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64055/59a8b8f1Nd2aed7c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