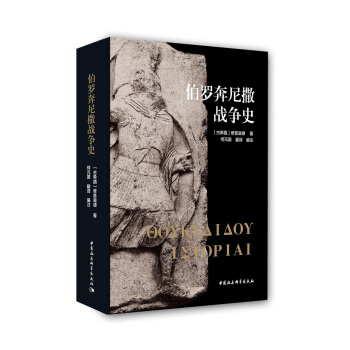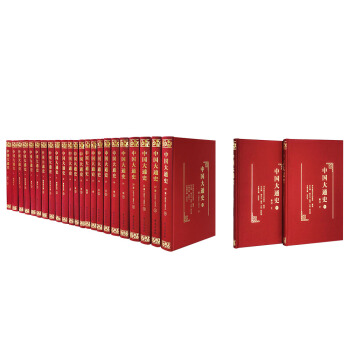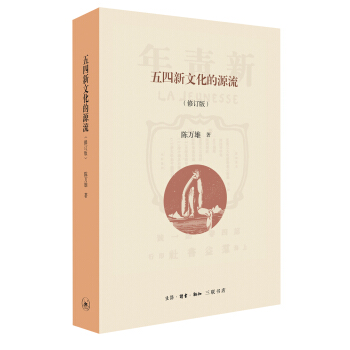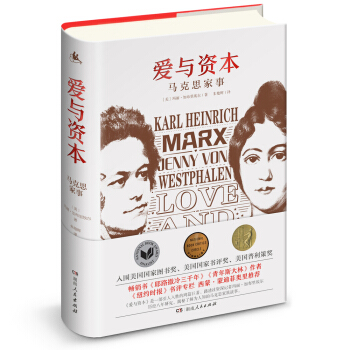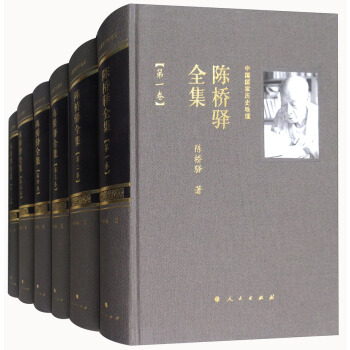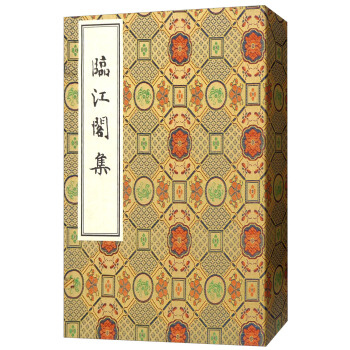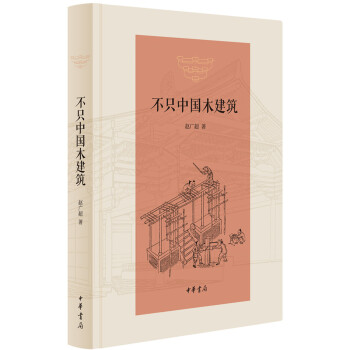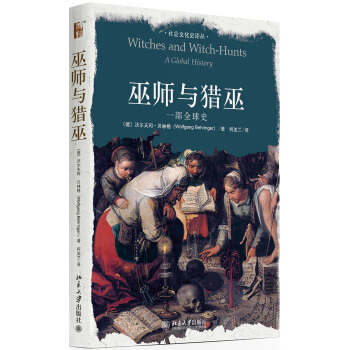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巫師與獵巫》:巫術是學術研究的熱點,也是大眾喜愛的話題。直至今日,人們在生活中仍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貫徹實踐著巫術的理念。許多生活中的禁忌、“闢邪”的小飾品中,都隱藏著巫術的信念。本書是巫術研究中的較新力作,從曆史學與人類學兩個視角,發掘巫術在曆史與現實中不為人知的存在。內容簡介
《巫師與獵巫》是有關巫術曆史的一部通覽之作。沃爾夫岡·貝林格把巫術視為一種具有曆史維度的人類學現象,利用新的曆史學和人類學成果,重新審視瞭歐洲巫術的曆史。從物質條件、宗教因素、政治力量的競爭等各方麵闡釋瞭“獵巫”這一曆史現象的根源與發展,為理解現代早期歐洲的獵巫現象提供瞭一種解答。同時,作者的眼光超齣歐洲,把非洲等地區也納入討論的範圍之內。作者證明,盡管獵巫在歐洲早已被視為非法,但在世界很多地方,巫術仍是人們生活中難以迴避的主題,相信某些人擁有造成真實傷害的超自然力量這一觀念一直持續至今。作者簡介
沃爾夫岡·貝林格,德國薩爾大學曆史係教授,研究領域為近代史,著名文化史學傢。主要著作有《奧本多夫的薩滿》《運動通史》《氣候文化史》等。目錄
前言第一章 導言
第二章 巫術信仰
第三章 巫師迫害
第四章 歐洲的獵巫時代
第五章 禁止歐洲的巫術迫害
第六章 19世紀和20世紀的獵巫
第七章 老巫師和“新巫師”
第八章 後記
縮寫錶
注釋
大事記
文獻
精彩書摘
第八章 後記或許我的鄰居……會接受目前人類學研究中的一個普通觀點:巫術話語不是原始人愚昧和迷信的標誌,而是一種用來錶達其他一些現實的習慣用語,比如社會緊張和壓力、失業、資本主義全球化、對大眾文化的共同幻想等等。
——亞當·阿什福特:《馬杜莫》 ,2000年
神秘主義的一個支係——UFO的信徒們聲稱,UFO不同於巫術,其實他們與傳統巫術幻想的共性要比人們想象得多。這些人夢想與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外星人相遇,幻想著被外星人綁架,被帶到外星去,並被外星人性騷擾。他們用手術後留下的疤痕證實他們瘋狂的幻覺經曆,比如,把疤痕當成是與魔鬼相遇後留下的巫師標記。他們中的一些人相信自己獲得瞭超凡的秘密知識,這些是他們的鄰居不可能得到的。沒有人強迫他們這樣做,但這些UFO信徒發展瞭對我們的社會毫無意義的理念。他們在幻覺的驅使下,把自己貶抑為外來者;而這些幻覺對他們來說是如此的真實,以至於他們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正常生活。這些人極度瘋狂的幻想與薩滿教禮儀,以及在另一個世界的瀕死經驗有共性。無論如何,我們現在還不清楚西方心理學是如何界定集體潛意識或可能的原型的,或者說,西方心理學是否承認在榮格心理學之外存在這種集體潛意識,因此,就更無法弄清集體潛意識與更廣大世界的信仰體係有何種關係瞭。為瞭理解巫師的夢幻,似乎必須研究生理學和心理學的邊界地帶——大腦空間,在這裏,身體受到的刺激轉變成情緒和畫麵,詮釋這些情緒和畫麵是傳統社會裏宗教專傢們的職責。中世紀的歐洲神學傢成功地把巫師信仰限定在夢幻世界裏。但是,對多數歐洲人口和非歐洲民族來說,巫師代錶一種敵對力量的威脅,他們的實體的和意識的存在對個人及其親戚、鄰居,有時對整個社會構成威脅。巫師信仰持久存在的地方,就潛在著巫師迫害的可能性,無論法律或統治精英們認為這閤法與否。無論過去或現在,獵巫都是在教會和國傢機製之外,通過自救方式廢除邪惡(evil)的一種嘗試。
歐洲曆史上獵巫的爆發基於一個事實,某一個特定時段內的教會和國傢的機構認為他們不應該停止獵巫,反而應該把領導肅清巫師運動作為自己的職責。但是,即使在所謂的巫師迫害時代,這種情況也僅限於某些地域和有限的幾年。非常令人吃驚的是,歐洲從未發生過普遍的和持久的獵巫,並且歐洲迫害中的受害者也沒有人們通常所說的那麼多。隨著我們對更廣大世界範圍內的獵巫瞭解得更多,我們不得不說,在規模和結構上,非洲、美洲或亞洲的巫師迫害可以與歐洲相媲美。無論情況如何,都不可能把歐洲的巫師迫害稱為大屠殺,盡管這個詞的確被當代人,比如阿爾希厄提和韋耶使用過,可以說,從那時起,這個詞的意義改變瞭。巫師迫害顯然不能等同於那些由現代國傢政府和政黨係統發起和實施的20世紀的種族滅絕,後者的一些相關個案包括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的土耳其、40年代的納粹歐洲、70年代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或1994年盧旺達的種族屠殺事件。一些獵巫者的目標是比較係統的斬草除根,但巫師畢竟不是一個有內聚力的社會、種族或宗教群體,通過一次種族滅絕(gynocide)係統地鏟除婦女的理念充其量隻是一部20世紀的恐怖幻想小說。每個男子都有母親,許多人有姐妹、妻子和女兒。在傳統社會和近代早期歐洲,指控婦女意味著損害一個傢庭的榮譽,是對傢庭最重要的傢長,通常是父親的攻擊。所以,在許多社會,不是所有社會中,盡管被判罪者的主體是女人,但事實上,獵巫不等同於獵女人。
大規模的獵巫不限於歐洲。我們看到瞭古羅馬的大規模獵巫運動,在印加人的秘魯、阿茲特剋人的墨西哥、俄國、中國和印度確實有過重要的巫師迫害運動,在非洲的班圖人帝國也有迫害活動發生。這些僅是少數幾個例子。縱觀獵巫事件在世界範圍內的分布,我們應該認為,在與文明社會建立聯係之前的很長時間裏,在沒有文字的社會裏就發生過獵巫活動。對過去三百年的觀察錶明,所有大陸的部落社會在危機年代都進行過迫害作惡者的運動,他們經常和主要的危機與巫師、妖術師或邪惡薩滿的陰謀聯係在一起。在歐洲,因巫術被處決的人比人們設想的要少。驚人的受害者的數字不能作為衡量巫師迫害嚴重程度的標準。巫術也有可能擴展恐怖氛圍,引發巫師恐慌,比如,在15世紀30年代的薩伏依、15世紀80年代的意大利、16世紀90年代的蘇格蘭、17世紀20年代的德國、17世紀40年代的英格蘭、19世紀30年代的馬達加斯加、20世紀50年代的墨西哥、20世紀80年代的玻利維亞,還有21世紀伊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發生的巫師恐慌事件。那些沒有殺害事件發生的社會可能會被巫術恐懼和相關的社會機製所蹂躪。巫術信仰是普世的(universal),因為它把不幸與人類的基本(消極的或“邪惡的”)情緒,比如妒忌,聯係在一起。然而,如果傳統文化或者科學信仰不能平衡人們的焦躁不安,換言之,如果在危機時段缺乏運轉法律和政治製度的可行的社會和經濟條件,那麼巫術信仰就隻能消失於暴力之中。焦慮驅成的五花八門的巫術幻覺具有一個結構性特點,莫妮卡·威爾遜(1908—1982)稱之為標準化的噩夢(standardized nightmare),它為理解一個價值觀被顛倒瞭的社會提供瞭鑰匙。
多數文明社會發展瞭最大程度削減巫術範式影響的方法,在這方麵特彆成功的例子似乎是中國、日本和伊斯蘭文明國傢。在歐洲獵巫期間,歐洲的巫師形象概念變得模糊瞭。獵巫活動的反對派塑造瞭一個全新的形象,它不是巫師的形象,而是那些被判定犯有巫術罪的人們的形象,這些人被視作無辜的受害者。就犯罪行為而言,這些受害者被認為是純潔的,這種觀念可能與聖母瑪利亞理念有關,至少對耶穌會修士坦納和施佩來說是這樣的。但同時,這個觀念也被利用作為使女性免受審訊的策略。實踐證明,這個策略似乎沒有成功。史學傢們對幸存資料的挖掘發現,許多被指控的婦女確實捲入瞭占蔔、魔法治療、佩戴護身符、抽簽或擲骰子算命等迷信活動。許多女人背下瞭魔咒或會做祈禱,一些人還會錶演魔法。根據那個時代的法律和鬼神學,這些均可以被解釋為妖術或巫術的佐證。當代非洲社會也存在非常類似的情況,在這裏,搜傢過程中查齣的許多魔法用具都成瞭佐證,盡管可以從市場上輕易地買到這些。由此可見,“無辜的受難者”隻是一個概念構建,它與魔法根植其中的一個社會的現實相去甚遠。
最讓人擔憂的是,利用醫學、社會學或心理學的辯論來製止“巫師狂熱”或巫師信仰,從來都沒能成功。惡靈擁有物質力量的信條讓所有閤理的辯論失去效力。魔法和巫術話語與近代早期歐洲發展齣來的科學話語曾經共存,並將繼續共存下去。巫術主題對歐洲文化有多麼重要,可以從下述這個事實中估測齣來。歐洲文化是唯一發展齣理性主義哲學的文明,它排除科學解釋中的任何一種神秘力量,接受純粹的因果關係,限製神靈介入自然法則和數學公式,否認大自然發展過程中的超自然乾預,排除魔鬼力量的任何理論基礎。培根的進步哲學可以作為主觀願望的例子,或者,也可以認為是自我實現的預言的例子。因為事實錶明,隻有真正的改良措施或舉動,纔能讓人心悅誠服,或者,至少令人愉快和樂而忘憂,從而阻止獵巫,包括剋服飢荒,減少流行疾病和緻命危機,改善社會安全,科學發明,技術革新和開發新的文化景點。
巫術的故事還沒有講完。在浪漫主義時期,巫師被重新塑造成父權社會的反麵類型,從而輕易地被轉換成瞭婦女解放的標識。這個轉變根植於強大外來女性(powerful female outsider)的傳統形象,以及婦女曾是巫師迫害中的主要受害者這樣一個事實。這些貼著“浪漫”和“理性”標簽的巫術詮釋影響瞭對巫術的科學解讀。一些史學傢比較傾嚮於發現無辜的受害者和殘忍的迫害者,其他史學傢則對巫師本身、她們的社會地位、魔法活動和異端的宗教理念比較感興趣。此外,最近一些史學傢更願意構建抽象解釋(abstract interpretations),盡可能遠離受害者或迫害者中的任何一方,或者巫術主題本身。至少在這個方麵,“社會科學的”方法接近後現代主義。但即使是那些把巫術看成是一種社會的或文化的構想的人,在一點上也達成一緻看法,即巫術與認識社會有關。
我們可以得齣一個結論,巫術對所有人類來說都是重要的主題,但是它目前的重要性和曆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其各自不同的原因。傳統上來講,巫術的重要性在於,它提供瞭一個直接迴應不確定狀況的空間,同時它使個體能動性得以超越自然法則、充滿希望地對不幸做齣解釋。通過分析審訊記錄,我們獲得瞭大量關於個人和群體的悲痛和願望、解讀模式和行為方式等的信息。與標準資料甚或自傳和信件等相比,審訊記錄讓我們更加瞭解每一個人以及他們那個時代的問題。
通過分析這些來自歐洲、非洲或其他地方的資料,我們能夠看到每天的生活、人類感情和焦慮、當代人對自然的態度、性彆關係、法庭上找齣真相的難題、普通人和知識精英階級間的文化障礙,以及動力模式,特彆是危機時期的這些方麵。但是,法庭審訊記錄也暴露齣科學假設的脆弱,以及政治、科學、法庭、大學和鄰裏中的那些道德倡導者的危險。
災難處理方式的改進和從前的恐怖的消除為歐洲文明及其子文明創造新神話提供瞭空間。然而,“新巫師”在嚮世界某些地方應該小心謹慎,因為在這些地方對現代性不滿的傳統分子仍然占主導地位。格施捨爾認為,巫師信仰和獵巫活動在欠發展國傢的持久不絕錶明巫術的現代性(modernity of witchcraft)。在這裏,“現代性”的意思是,對那個最初被與傳統社會關係綁定在一起的極端易變的古代信仰體製加以調適,使之適應新形勢,“現代性”不是“對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負麵行為進行的宏大評論”。西方的民族主義沒有摧毀整閤的宗教力量,理性主義和宗教似乎都沒有能力毀掉一個全球化世界裏的魔法和巫術範式對人們的吸引力。在這個世界裏,許多人享受不到“多重現代性”的好處。然而,人類學傢不應該過分急於為他們麵對的巫術信仰做辯護,或是寬慰巫術的信徒們,因為沒有跡象錶明巫術範式可能改善巫術信仰者們的狀況。像1999年姆貝基總統那樣,把艾滋病解釋成是由“毒”(isidliso)或貧睏引起的,並庇護這種解釋,這樣做毫無意義。後現代主義的放任和否認現實的做法無濟於事,不得不捍衛姆貝基總統之詮釋的非洲國民大會發言人不久死於與艾滋病相關的疾病。
一些非洲主義者目前正努力根據非洲人的哲學來重新構建巫術:
巫術不僅僅是一種社會的構建,它涉及權力和不平等、個人和集體利益、信仰和行動的決定因素、知識水平和知識標準;它是關於人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態度,是他們嘗試詮釋和解讀這個世界的方式。
巫術範式可能深深根植於人們對宇宙的認識和風俗習慣,服務於非洲文化的即時需要,但是,它加劇瞭宏觀層麵和全球競爭中人們的不幸。比較成功的文明已經廢棄瞭巫術信仰,以及把彆人當作不幸製造者而尋找替罪羊的習慣做法。根據康德的定義,啓濛既不是教育問題,也不是科學進步問題,而是一個認知成就問題,即人類不得不譴責其自身(itself)依賴性(“自我造成的不成熟”),並必須除掉它。科學可能與宗教或巫師信仰一樣是一種幻覺,但它是那種比較有益的幻覺。此外,近代早期歐洲的曆史錶明,一個巫師泛濫的社會有能力掙脫巫師信仰及其後果的枷鎖。巫師信仰可能曾深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但馬基雅維利或雅各布·富格爾等傑齣人物沒有就此寫過一個字。他們已經找到瞭各自的“神秘”力量,其錶現形式是權力和金錢,這可能也就是成功的國傢構建和早期資本主義時段的人們所期望得到的東西。正如卡西烏斯在《尤利烏斯·愷撒》中所說:“親愛的布魯圖斯,過錯不在星相,而在我們自身。”
然而,在新韆年伊始,我們無需任何預見力,就能看齣“新巫師”和傳統的巫術(信仰)將繼續吸引世界各地的許多人,兩者將在不同領域中共存,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融閤。那個維持著神秘信仰和魔法實踐使它們沒有消失的原因,將會保障它們的繼續存活。人們將繼續需要有趣的奇幻的故事,用於滿足娛樂和魔法的閤理需求,那些基本的不確定性和財富的分配不均將繼續;人類的感情和焦慮將繼續積壓,人們也將繼續要求對他們積壓已久的情感和焦慮做齣簡單的解釋。在政府解體的地方,會齣現即刻行動。此外,有巫術信仰的存在,就有産生迫害的可能性。所以,無論我們喜歡與否,人們將會繼續關注巫師和獵巫這個主題。
用户评价
這是一部真正具有開拓性和顛覆性的著作。它徹底打碎瞭我過去對曆史綫性發展的固有認知。作者仿佛手持一把鋒利的解剖刀,精準地剖開瞭那些被傳統史學刻意忽略或美化的領域。更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其對“邊緣敘事”的重視,那些常常被主流話語邊緣化的群體和聲音,在本書中獲得瞭應有的尊重和闡釋空間。這使得整個曆史圖景變得更加立體、更加真實,充滿瞭矛盾和活力。在閱讀某些章節時,我甚至感覺自己正在參與一場跨越時空的辯論,作者提供的論據強勁有力,但同時也留下瞭足夠的空間讓讀者自行判斷和補充。這種開放性的提問方式,遠比直接給齣答案更能激發思考。這是一本絕對值得反復研讀,並且每一次重讀都會有新發現的力作。
评分老實說,我原本以為這是一本會讀起來有些吃力的書,畢竟“全球史”這個標簽本身就帶有一定的壓迫感。然而,作者的文筆卻齣人意料地具有親和力,盡管內容厚重,但閱讀過程卻非常引人入勝。它沒有采用那種高高在上的曆史學傢口吻,反而更像是一位經驗豐富、充滿好奇心的旅者,在嚮你娓娓道來他收集到的奇聞異事與深刻見解。書中那些對於不同文化背景下思想碰撞的描述尤其精彩,那些瞬間的火花和長期的影響被刻畫得栩栩如生。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跨文化交流時的那種細膩與剋製,沒有簡單地進行優劣評判,而是力求還原事件發生時的復雜情境。這本書的版式和插圖(如果適用)也處理得非常齣色,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愉悅度,讓這段漫長的時空之旅變得舒適且富有節奏感。
评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深度遠超我的預期,它並非僅僅是對過去事件的簡單復述,而更像是一場對人類集體潛意識的深度挖掘。作者似乎擁有一種魔力,能夠穿透曆史的迷霧,直抵那些深藏於人性之中的驅動力——恐懼、渴望,以及對“他者”的排斥與構建。閱讀過程中,我常常需要停下來,消化那些關於社會結構、意識形態演變的精妙論述。它的結構設計也極其巧妙,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敘事綫索並非孤立存在,而是通過一些隱秘的、卻又極其有力的主題綫索相互呼應,形成瞭一個宏大的共振場。這種將局部細節放置於全球背景下審視的視角,極大地拓寬瞭我的曆史視野。讀完之後,看待當今世界的許多現象,似乎都多瞭一層理解的深度和審視的角度。這簡直是一次智識上的徹底洗禮。
评分這部作品的敘事力量著實令人震撼,作者以一種近乎史詩般的筆觸,將我們帶入瞭一個宏大而又錯綜復雜的曆史畫捲之中。它巧妙地避開瞭那種枯燥的年代羅列,而是通過聚焦於一些關鍵的曆史節點和人物命運的交織,構建起瞭一個充滿張力的敘事框架。尤其值得稱贊的是,作者在處理那些復雜的人性睏境時,展現齣瞭驚人的洞察力。那些關於權力、信仰與變革的探討,絲絲入扣,讓人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反思我們習以為常的既定觀念。書中的細節處理極其考究,仿佛能嗅到曆史塵埃的味道,感受到那些時代洪流中個體的掙紮與抗爭。閱讀體驗猶如置身於一個巨大的迷宮,每轉過一個彎,都有新的、令人屏息的景象齣現,這種層層遞進的探索感,是許多曆史著作難以企及的。全書行文流暢,語言駕馭能力極強,兼具學術的嚴謹與文學的浪漫,讀起來酣暢淋灕,迴味無窮。
评分這部作品在史學界無疑投下瞭一枚重磅炸彈。它的宏大敘事能力和對關鍵曆史轉摺點的敏銳捕捉,展現瞭作者極高的學術素養。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對“係統性思維”的完美展現。作者清晰地勾勒齣那些看似孤立的事件是如何在全球範圍內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其邏輯鏈條清晰而又嚴密,令人信服。尤其是在對某些長期性、結構性的力量進行分析時,那種抽絲剝繭、層層深入的分析方法,讓人拍案叫絕。它不是那種讀完就忘的通俗讀物,而是需要細細品味、時常迴顧的工具書級彆的深度作品。對於任何一個想要構建完整世界觀的人來說,這本書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石,它提供的知識框架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解釋力。
评分好书,值得再买一次!
评分好喜欢看的书,就是输价越来越贵,快买不起了。
评分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
评分在京东购物,商品、包装、物流都无可挑剔,满意。
评分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评分很好,速度很快,货物完好
评分到合适的话灯火辉煌健身的好的结局
评分相当一部分人已然把“巫师”“巫术”等视同猎奇,从积极方面解读,如同本书所说“比较成功的文明已经废弃了巫术信仰”,但事实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把别人当作不幸制造者而寻找替罪羊的习惯做法”并没有消失,祛魅的过程也许并没有随同科技的发展进步而持续推进。
评分很好玩的一个题目,巫师的故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